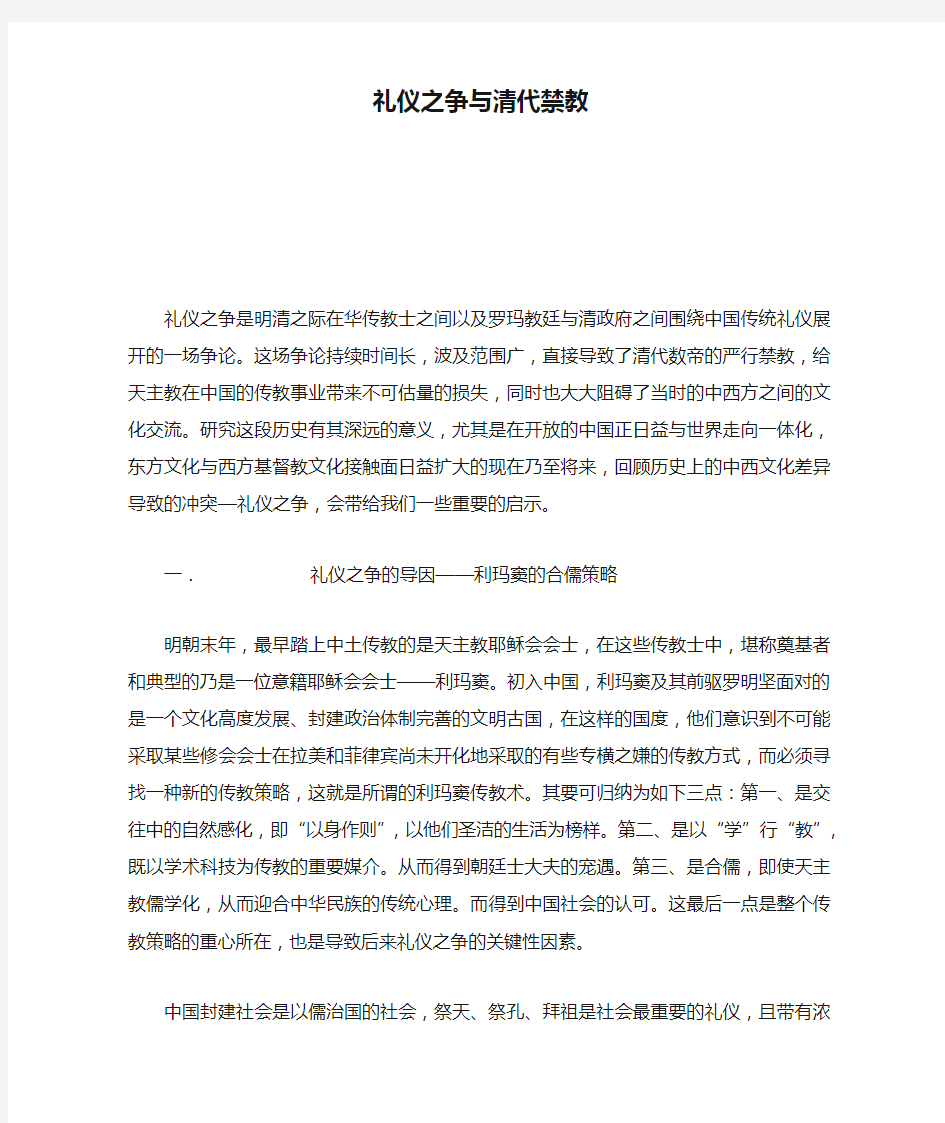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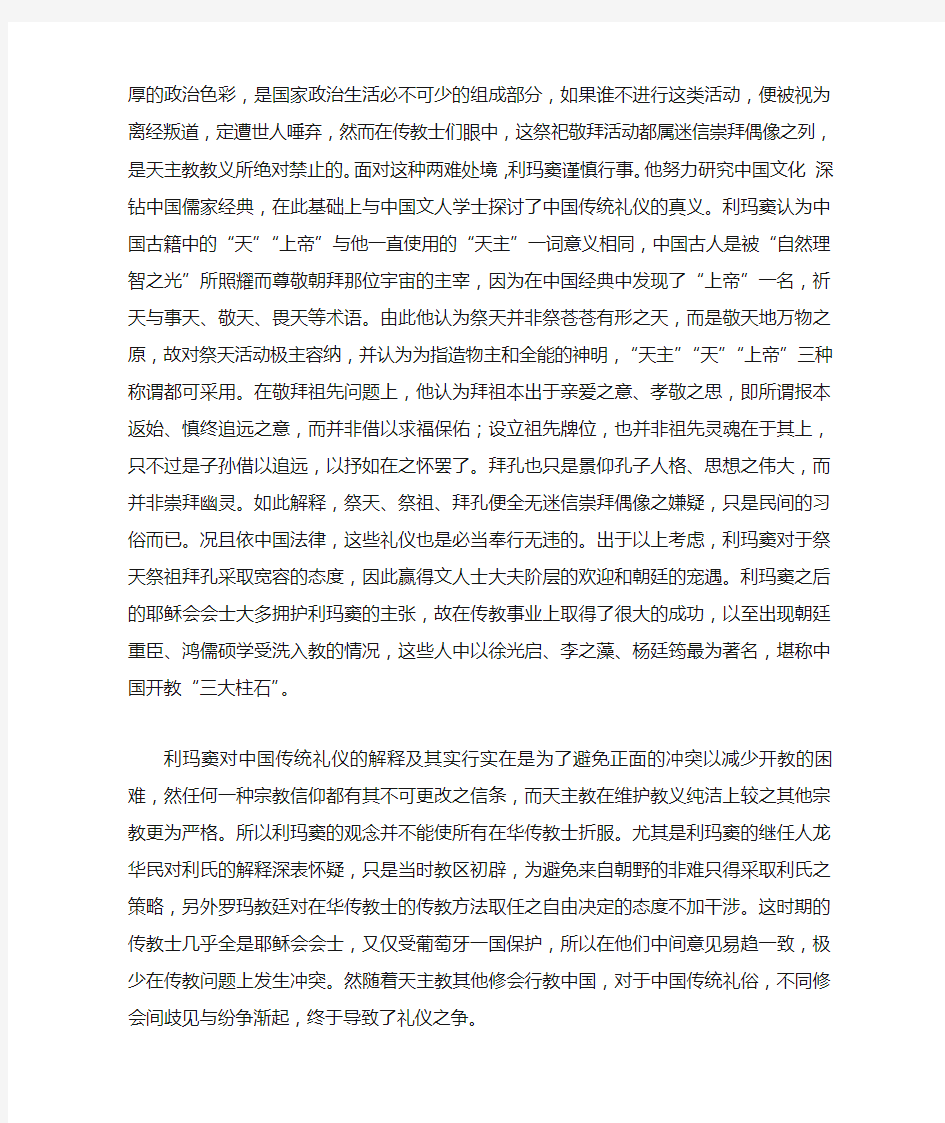
礼仪之争与清代禁教
礼仪之争是明清之际在华传教士之间以及罗玛教廷与清政府之间围绕中国传统礼仪展开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直接导致了清代数帝的严行禁教,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也大大阻碍了当时的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研究这段历史有其深远的意义,尤其是在开放的中国正日益与世界走向一体化,东方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接触面日益扩大的现在乃至将来,回顾历史上的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礼仪之争,会带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礼仪之争的导因——利玛窦的合儒策略
明朝末年,最早踏上中土传教的是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在这些传教士中,堪称奠基者和典型的乃是一位意籍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初入中国,利玛窦及其前驱罗明坚面对的是一个文化高度发展、封建政治体制完善的文明古国,在这样的国度,他们意识到不可能采取某些修会会士在拉美和菲律宾尚未开化地采取的有些专横之嫌的传教方式,而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传教策略,这就是所谓的利玛窦传教术。其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点:第一、是交往中的自然感化,即“以身作则”,以他们圣洁的生活为榜样。第二、是以“学”行“教”,既以学术科技为传教的重要媒介。从而得到朝廷士大夫的宠遇。第三、是合儒,即使天主教儒学化,从而迎合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而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这最后一点是整个传教策略的重心所在,也是导致后来礼仪之争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儒治国的社会,祭天、祭孔、拜祖是社会最重要的礼仪,且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国家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谁不进行这类活动,便被视为离经叛道,定遭世人唾弃,然而在传教士们眼中,这祭祀敬拜活动都属迷信崇拜偶像之列,是天主教教义所绝对禁止的。面对这种两难处境,利玛窦谨慎行事。他努力研究中国文化深钻中国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与中国文人学士探讨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真义。利玛窦认为中国古籍中的“天”“上帝”与他一直使用的“天主”一词意义相同,中国古人是被“自然理智之光”所照耀而尊敬朝拜那位宇宙的主宰,因为在中国经典中发现了“上帝”一名,祈天与事天、敬天、畏天等术语。由此他认为祭天并非祭苍苍有形之天,而是敬天地万物之原,故对祭天活动极主容纳,并认为为指造物主和全能的神明,“天主”“天”“上帝”三种称谓都可采用。在敬拜祖先问题上,他认为拜祖本出于亲爱之意、孝敬之思,即所谓报本返始、慎终追远之意,而并非借以求福保佑;设立祖先牌位,也并非祖先灵魂在于其上,只不过是子孙借以追远,以抒如在之怀罢了。拜孔也只是景仰孔子人格、思想之伟大,而并非崇拜幽灵。如此解释,祭天、祭祖、拜孔便全无迷信崇拜偶像之嫌疑,只是民间的习俗而已。况且依中国法律,这些礼仪也是必当奉行无违的。出于以上考虑,利玛窦对于祭天祭祖拜孔采取宽容的态度,因此赢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和朝廷的宠遇。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会士大多拥护利玛窦的主张,故在传教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出现朝廷重臣、鸿儒硕学受洗入教的情况,这些人中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最为著名,堪称中国开教“三大柱石”。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礼仪的解释及其实行实在是为了避免正面的冲突以减少开教的困难,然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有其不可更改之信条,而天主教在维护教义纯洁上较之其他宗教更为严格。所以利玛窦的观念并不能使所有在华传教士折服。尤其是利玛窦的继任人龙华民对利氏的解释深表怀疑,只是当时教区初辟,为避免来自朝野的非难只得采取利氏之策略,另外罗玛教廷对在华传教士的传教方法取任之自由决定的态度不加干涉。这时期的传教士几乎全是耶稣会会士,又仅受葡萄牙一国保护,所以在他们中间意见易趋一致,极少在传教问题上发生冲突。然随着天主教其他修会行教中国,对于中国传统礼俗,不同修会间歧见与纷争渐起,终于导致了礼仪之争。
二、教会内争
礼仪之争始于1631年西班牙道明会会士黎玉范入闽传教。黎玉范对耶稣会的宽容中国礼仪的作风甚感不满,遂于1643年返欧向罗玛询问有关中国信徒的一系列问题,其要如下中国信徒是否与其他天主教徒同例,每年必须举行认罪及圣餐礼一次?
教士对妇女行洗礼时,可否不用口津及盐,以及免除过量之涂油?
中国信徒如放债时,是否允其征收百分之三十之利息?如系以放债为生,在其皈信天主之后,是否允其继续经营?
应否允许中国信徒向社会祭神典礼捐献财物?
中国信徒可否参加政府所举行之必要祭典?
中国信徒可否参加祭孔典礼及丧葬祭拜之礼?
中国信徒可否参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礼,及其他祭祖之仪式?
在对中国人举行洗礼之先,应否告其天主教之教义,为绝对禁止祭拜偶像及举行其他祭典?
中国信徒尊敬孔子,可否用“圣”字?
中国信徒在其会堂中所悬匾额,对于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
对于中国非信徒,可否举行弥撒典礼?①
从以上黎玉范所举数点我们可知道中国礼俗实在难与天主教教义相调和。而耶稣会又极力调和之实为减少传教之困难达其开教之目的。然罗玛据黎玉范所述乃于1645年发出一道禁止敬拜孔子和祖先礼节的命令。在华耶稣会士对此禁令深感惊愕,乃迁卫匡国赴罗玛解释,于是1656年教宗又答复说,既然敬孔祭祖纯属社会礼俗,毫无宗教色彩,理应准予实行。以上两种看来互相矛盾,又有教士向罗玛询问是否后者已将前者否定,罗玛的答复摸棱两可;“两令均属有效,各应按照所陈意见遵守”。教会权威对此不置可否,终使此争论愈演愈烈。而法国外方传教会会士广州主教、福建代牧颜珰对耶稣会的攻击最为激烈。1693年颜珰下令所属教区严禁用“天”、“上帝”之称,禁止中国信徒行敬孔祭祖之礼,要求所有教士遵守且罢黜不遵禁令的耶稣会士两名。耶稣会士虽受此攻击,因有康熙帝之袒护亦不为之屈服,如此,在教士内部便产生公开的分裂以至不能合作的局面。
法国外方传教会颜珰反对耶稣会会士对中国礼俗,其针对的要点可概括为:(一)、对万世师表孔子的敬礼。(二)、对去世先人的祭礼。(三)、“天”、“上帝”称号的争论(有些传教士认为汉语里的“天”是物质性的天,即苍天的意思,决不能代表天主教的“天主”)。(四)、康熙在1675年曾送一“敬天”匾额给传教士,后来被悬于教堂内,令部分教士不满。反对者从维护教义纯正出发无可厚非,但却给中国传教事业带来灭顶之灾。
除因礼仪导致教会内部纷争外,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一、耶稣会与其他修会传教对象和方式不同。耶稣会士面对的是拥有古老和高度文化的中华民族,又因其学识渊博,精通汉语和儒家经典多与文人士子结交乃至在朝廷任职钦天监,充任皇帝的西学教师等原因,使其在传教策略上因袭了利玛窦的成法。而其他修会如道明会、方济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修会会士在来华以前多居西班牙殖民地之类文化落后的民族,他们所到一地便是推翻偶像,以欧洲基督教的风格习尚来代替异教的习尚。到中国以后,仍然袭用旧法,指责耶稣会士过分谨慎的作法,认为是世俗的明智,与传教人的身份不合。那些会士手持十字架,在市街中大喊:“凡拒绝相信福音,便如孔子一样堕落地狱”如此举动,在耶稣会士看来无疑是一种招致迫害的作风,事实确然,在他们的传教区很快地掀起了当地官府和民众的反教风潮。
二、教会传教系统的不完善,自15世纪始,葡萄牙国王便拥有教皇所授予的东亚保教权,凡是受教皇委托往远东治理传教事务的人员,都先得获葡王许可方可成行。当时在华的耶稣会士都是在葡王的保护之下。后来西班牙传教士行教中国,因两方传教事务隶属有别,又因其传教方式不同而彼此仇视、排斥而不能合作。其时在新大陆的传教情况也是如此,罗玛教廷鉴于此弊端于1622年创立“传信部”,由教廷总领全球传教事务。于是遂有负教廷监督之
权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的来华。葡人对此甚为不满,认为侵犯其固有之保护权。教廷执意收回传教权的作法,更激起传教权保护国、修会的怨恨。虽然最终增强了教廷对传教事业的统治权,却也因此而造成各会派之间的带政治倾向的权利之争。
三、教皇与康熙对礼仪之争的干预
颜珰出命禁行中国礼仪后不久,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徐日升、张诚等请求康熙正式声明敬孔祭祖和“上帝”、“天”的真正含义。康熙于1700年答复说“上帝”指的就是真神,敬孔祭祖并非宗教仪式。康熙与利玛窦等人看法相同,他说:“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譬如幼稚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物动于中,形于外也,…..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③”耶稣会士认为有此答复这次争论便告结束,遂将康熙的答复送至罗玛。但是罗玛认为耶稣会士直接向皇帝请求一个声明,也就是说寻求世俗统治者来裁决神学上的争端,这件事本身已否认了教廷的最高神学权威,还由于当时耶稣会在欧洲树敌颇多,教廷最终采纳了颜珰之说,1704年教宗格来孟十一世发出一道通谕禁行中国礼仪,其文要点如下:
……
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以及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此以后,总不许用“天”
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主”。如“敬天”之匾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悬挂。
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先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
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得进士、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庙行礼。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
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这是异端之事。再,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不过要报本的意思,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
……
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④
从此禁约可看出当时教士对中国传统思想风俗的看法,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实属肤浅,但罗玛认为欲保持信仰的纯正,这一切都是必须的,“远避迷信的一切色彩及一切嫌疑”
⑤。如此则中国的信徒就必须要改变他们认为无可非议的生活习惯且必须与本国所尊崇的传统断绝关系,这都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教廷也预料到此一纸禁令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便派遣多罗为教廷特使到中国予以公布,以就地解决传教士间的礼仪纷争,1705年多罗抵达北京受到康熙帝隆重接待。当康熙帝得知多罗来华目的后便改变了态度,而多罗又以不通汉文严禁中国礼仪的颜珰为顾问,愈使康熙发怒,说他“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⑥当康熙得知教廷禁约令后不久便逮捕了颜珰而后又令他及其随员出境。多罗也只得离开北京到达南京。康熙断然采取措施,让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领一种印票。声明要遵守利玛窦成规,拒绝领票者,一律被逐出境。1707年多罗在南京发表教廷禁令,并警告如有教友抗命,即处以绝罚。康熙耳闻即刻下令将多罗驱逐出境。这是对天朝皇帝莫大的侮辱。
康熙虽然采取限制教士传教的措施,但仍能保持冷静与容忍,派遣龙安国等赴罗玛谒见教宗,陈述对礼仪的意见书以寻求一折衷办法,希望1704年的禁令能够有所变更。然而,教廷于1715年又发出一道更为严厉的通谕“自登极之日”重申1704年禁令,要求所有在华
传教士宣誓服从。康熙得知大怒说:“若不随利玛窦规矩,在利氏之后二百年来之人,你们的教传不得,中国连西洋人也留不得。”⑦
康熙与教皇的抗争,促使本想取缔天主教的地方官吏都纷纷起来反对天主教,要求皇帝下令禁止西洋传教士传教。康熙遂重申前旨,禁止百姓自由入教。下令未领有印票的西洋教士都强迫返回澳门。如此大大限制了中国的传教事业。
教宗格来孟十一世为挽救时局,乃有二次谴使之意,即嘉乐的出使。嘉乐1720年到达中国。康熙得知其来华目的是劝导中国信徒遵守罗玛的决定,便传旨于他:
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及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若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⑧而后,康熙又令嘉乐所带之禁令译为汉文,康熙阅后朱批曰:
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于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⑨
此批语是如此坚决果断,再想有所变更已是不可。从此天主教便失去了在中国公开传教的自由。
嘉乐接到这个硃批,知事已成僵局,但为挽救起见,他自做八项妥协办法,然后来又遭教廷否决。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颁布“自上主圣意”通谕,废除嘉乐的八项准行条例,维持格来孟十一世的禁令,使有关名词和礼仪之争最后停止。
这场争论前后持续百年之久,教廷的禁令导致了康熙的禁教。从此,天主堂改为公所,教会财产被剥夺,教士传教受到极严格的限制,中国的信徒因不敢违抗朝廷旨意已不再象从前一样自由出入教堂,教徒不准敬孔祭祖不能参加科举也使教会与社会隔阂日深。更严重的后果是从此掀起了百年禁教排教的浪潮,几乎使天主教无立身之地。
纵观礼仪之争的全过程,尤其是后期教廷与康熙之间的对抗,实是教宗的普世教会首牧权与中国皇帝独揽包括宗教在内一切大权的对抗,是一场保持天主教教义纯正与维护儒家传统观念的斗争。而努力协调其间冲突主张教义儒学化的耶稣会士身处夹缝中或同反对派进行辩论或向教廷解释或寻求康熙的保证都未能改变这场争论的悲剧性结局。直到近代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以及社会的进步,在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当局重拾利玛窦旧策,提出天主教教义儒学化的口号,并于1939年由教宗庇护十二世最终取消对中国礼仪的禁令,使有关中国礼仪的争论画上最后的句号。本世纪60年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肯定了每个地方文化的价值,充分体现了使基督福音文化化、本地化的精神。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暗叹400年前利玛窦的明智之举,同时也不禁为利玛窦之后的教廷禁令而扼腕。
四、清代禁教
罗玛教廷下令禁止敬孔祭祖,这一涉及中国礼俗的行动又导致了康熙出谕禁传天主教。由此进入中国天主教史上的禁教期,它开始于康熙末年,经雍正、乾隆、嘉庆,直到道光二十一年(南京条约)解除教禁历一百三、四十年之久。各帝都执禁教之令,然因各帝对天主教态度不一,禁教之轻重缓急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康熙在位61年,他正式禁教是在康熙56年,因康熙并无消灭天主教之意,也无反教的决心,而使禁教政策施行的极不彻底。康熙素来重视西方科学,对传播西学的耶稣会士十分欣赏,同时他又坚决反对教士们干涉中国的法令。这便造成他对传教士们的十分矛盾的心理。如1719年他给传教士利国安的谕旨中说:
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以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外,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⑩
但第二年他在给苏霖等人的谕旨中又对耶稣会士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解除他们的疑虑
说:
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常无事,未犯中国法度。
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至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也无关涉⑾。
在教士被逐出境,不准内地行教的命令下达以后,在京教士苏霖。穆敬远等进朝启奏要求保护,康熙说:
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领票的西洋人,与有票的人无关。若地方官一概禁止,即将朕给之票观看,就是传教的凭证。你们放心去,若禁止有票的人,再来启奏。⑿
从以上康熙谕旨可以看出,终康熙之世,虽明布禁教之令,但北京的传教神父仍照常进行传教活动。而其他地方则各有不同,一般传教士的活动转入地下,且并未有大规模的教案发生。
雍正朝执行极严厉的禁教措施,这一方面是继承前帝之遗制,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康熙末年与雍正争储的第八皇子和第九皇子与天主教有牵连,前者受信教皇室贝勒苏奴和他儿子们的拥护,后者与传教士穆敬远神甫来往亲密,故雍正对天主教抱怀疑和憎恨态度。第二个重要原因是雍正怀疑教廷使者葡籍麦德乐来华的目的不纯,认为他是被欧洲国王所谴来谋取中国的先锋。此外反教的地方官吏纷纷上疏请求禁教,更加助长了雍正严厉禁教的决心。雍正二年,他对在京耶稣会士解释了他禁教的理由:
……在福建省的西洋人践踏我法律,扰乱我子民,当地大吏已向我报告(闽浙总督满保奏疏),事关国家,我应制止……你们到处社立教堂,你们的教也到处传
播……教徒唯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唯尔等之命是从,虽实在不必顾虑及此,
然,苟千万战船来我海岸,则祸患大亦……现在我准许你们在北京和广州居住,你们
若有怨言,则北京和广州也不能居住,我不愿在各省有你们的人……⒀
雍正五年又有上谕曰:
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奴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
乎?⒁
同年雍正又召见在京耶稣会士,据宋君荣神甫致盖雅尔神甫的信说:“赐茶之后,便当着我们的面把天主教大骂一通,并把他与邪恶教派相提并论。”还说:
朕不需要传教士,……朕岂能容忍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反对中国大道的教义?岂能象他人一样让此教义得以推广?……
你们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切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⒂
从以上雍正渝令可以看出,雍正也如前帝康熙一样重视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传统,不愿看到人心渐被天主教所煽惑而有损中国的圣统大道。另外也把天主教视为对国家构成某种威胁的秘密异端宗教来对待,虽然雍正为修治历法不得不在宫廷留用一些耶稣会,但总不因此而使教士们自由传教,他自始至终采取了极严厉的禁教措施。雍正二年初将各地教士陆续集中至广州,即使康熙朝领有印票的教士也不例外。此后一百多年间,天主教被官方定为异端邪教而严禁中国人入教,各地教堂均被改为公所,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仇教排教的浪潮,使天主教遭到在中国从未有过的全面的、长期的大迫害。
乾隆帝的禁教不似雍正严厉,实行的是“宽猛相济”的政策。他一方面执行前帝遗令继续禁教,另一方面又因其喜爱西方技艺和美术对传教士友善而对散布全国的秘密传教活动抱置若罔闻的态度。故而乾隆初年押解于广州的教士重又暗潜内地,传教活动重又暗中活跃起来。然由于地方官吏的反教仇教,乾隆朝还是兴起两次大的教案。不过终不能制止各地的传教,相反有的地方潜行传教之风越发厉害。终导致嘉庆朝1805和1811年的两次全国性大教案。
嘉庆帝对天主教所知极少,不象康熙喜爱西方科技,亦不象乾隆喜爱西方绘画,故留任宫中的传教士极少。在嘉庆朝前期因乾隆朝的严厉禁教而给传教活动以寂灭的假象,还由于传教活动的极为隐蔽而使嘉庆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这样遂使天主教呈现一片复兴状态。嘉庆十年,因意大利籍传教士德天赐所绘一张呈给罗玛的传教地图被搜获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大教案。一直到道光帝继位。
道光帝于1821年登极,他对天主教也是因袭禁教政策,但和前任态度有明显的不同:“道光皇帝天资敏捷,度量宏达,秉政以来,诸政务令和协,不忍加怒教长。⒃”他虽未明令改变以前的禁教令,但不像前任多次下令严酷迫害天主教,只是出现过几起由地方官吏遵遗制而兴起的地方性迫教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地下传教活动又逐渐活跃起来,至《南京条约》签定解除教禁前,全国信徒人数至30万人。已回复到康熙朝自由传教时期的数目。据记载有国籍神父80位,外籍神父64位在内地13省传教。
纵观这一百多年历史,天主教被官方定为异端邪教而时时受到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的仇视与迫害,然天主教总没有绝迹且不时有所发展,这事实不能不令我们深思。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是皇帝重西学。康、雍、乾三帝对传教士之态度,均重其所学但不重其教,而因其学为朝廷服务的教士则相反是利用其职其学以行教。故清初“教”系于“学”为其特点。其二是教士传教之矢志不渝。传教士们无不以“作耶稣的勇兵”为他持枪上阵征讨异教国家为己任,视艰苦开教、因教殉道为光荣。其三是教徒信教之诚笃、护教之热诚。其四是天主教自明末至清初一百多年之历史,教会基础稳固,建立于信仰之上的教会非若其他事业会轻易被武力之胁迫所能消灭。出于以上种种原因,天主教得以历经挫折而不灭于中国,并且在此稳固的基础上于道光帝解除教禁后很快地复兴起来。当然那时国际局势已趋复杂,且传教权被写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中,但绝不能看不到原有的天主教之稳固基础而简单地把天主教的复兴看作完全是在帝国主义舰炮保护下的文化侵略。这不是本文论述之重点,不便赘述。
清代禁教对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影响不言而喻,另外还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受到阻碍,几乎中断,在明末和清初禁教前,中国历史上因西学传入而出现了一些闪放异彩的科学家及科学著作,如《天工开物》和《农正全书》等百科全书式著作。另外还有大量由文人和教士合编的天文、历算、地理、火器、艺术等专门著作,在社会上流传颇广。然由于礼仪之争和清代禁教而使中西文化的交流处于低谷,而仅仅限于宫廷之修订历法。中国的社会重又回复至以前寂静不动的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说,禁教政策无疑起到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副作用。
(河北隆尧一中董宪敏)注释:①转引《中国教案史》P142
②⑤《中国天主教史》P88台湾光启出版社民国76年版
③《欧化东渐史》张星烺
④⑧⑨⑩⑾⑿⒀⒁⒂《文书》
⑥⑦《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P18台湾光启社民国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