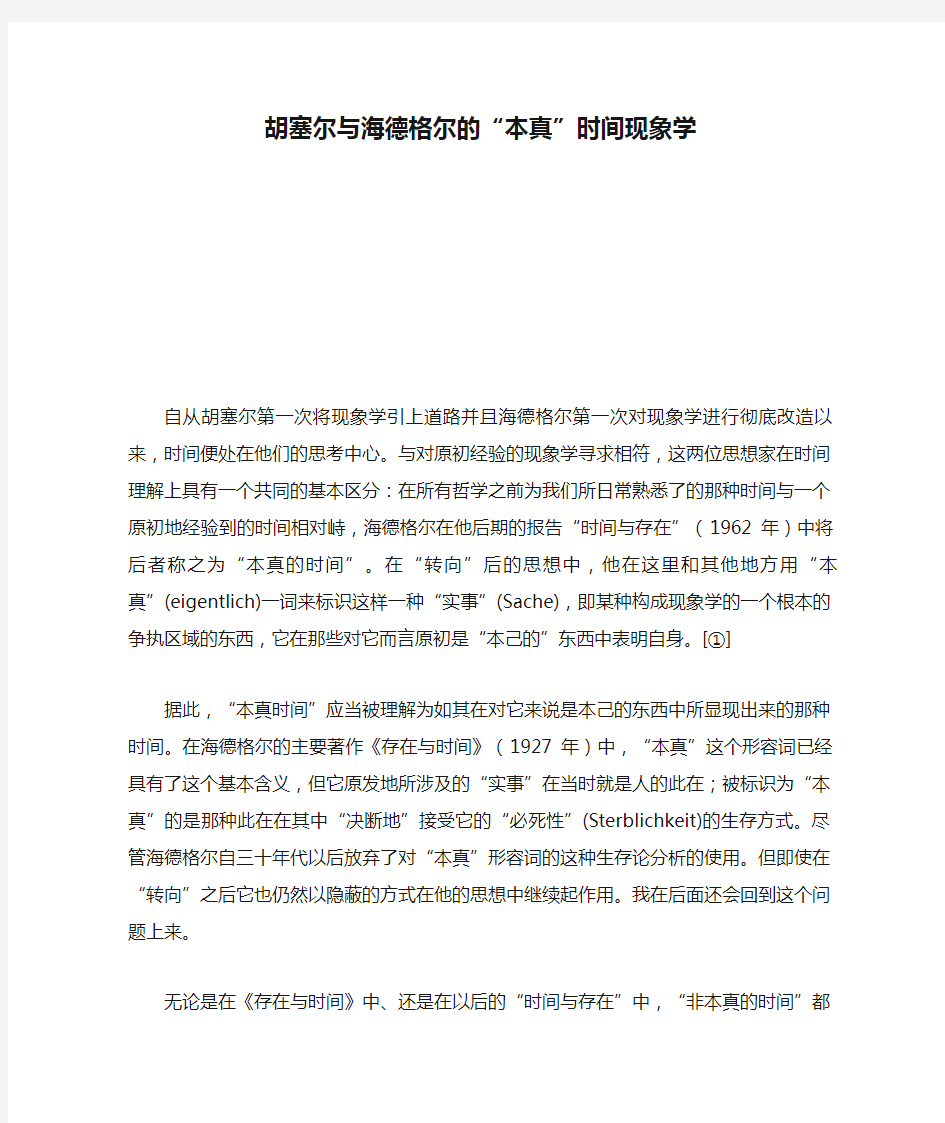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本真”时间现象学
自从胡塞尔第一次将现象学引上道路并且海德格尔第一次对现象学进行彻底改造以来,时间便处在他们的思考中心。与对原初经验的现象学寻求相符,这两位思想家在时间理解上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区分:在所有哲学之前为我们所日常熟悉了的那种时间与一个原初地经验到的时间相对峙,海德格尔在他后期的报告“时间与存在”(1962年)中将后者称之为“本真的时间”。在“转向”后的思想中,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用“本真”(eigentlic h)一词来标识这样一种“实事”(Sache),即某种构成现象学的一个根本的争执区域的东西,它在那些对它而言原初是“本己的”东西中表明自身。[①]
据此,“本真时间”应当被理解为如其在对它来说是本己的东西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时间。在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本真”这个形容词已经具有了这个基本含义,但它原发地所涉及的“实事”在当时就是人的此在;被标识为“本真”的是那种此在在其中“决断地”接受它的“必死性”(Sterblichkeit)的生存方式。尽管海德格尔自三十年代以后放弃了对“本真”形容词的这种生存论分析的使用。但即使在“转向”之后它也仍然以隐蔽的方式在他的思想中继续起作用。我在后面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无论是在《存在与时间》中、还是在以后的“时间与存在”中,“非本真的时间”都在于:时间对我们显现为各个当下、各个现在的次序(Folge)。这些“现在”可以在某些发生事情的时段(Phasen)上——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在“各个运动”上——被计数(anz?hlen),通过这种方式,对时间的自然科学理解也成为可能。自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以来,流行的——至少在西方文化中——便是这种把时间视为现在次序的观点,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这种时间观称作“庸俗的时间理解”。由于现在次序构成一个固定的形式,我们在其中遭遇到所有在时间中个体可定位的客体,因此这种时间在胡塞尔那里叫做“客观时间”。在由爱迪·施泰因所汇总的哥廷根时期的文字中,他把客观时间与“内意识”相对峙,在三十年代的后期手稿中,他把客观时间与“活的当下”相对峙。由于胡塞尔以此来标识时间原初在对它而言是本己的东西中被经验的方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他那里也有本真的和非本真的时间之间的区别,尽管他并没有使用这些概念。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实事(Sache)上一致的命题在于,从本真的时间来看,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把时间视为现在次序的时间观应当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派生的理解。据此,现象学具有一个双重的任务:它不可以局限于对本真时间特征的澄
清,而是也必须指明,非本真的时间是如何受此决定的,或如何因此而得以可
能的。在胡塞尔那里,这个指明在于:他试图表明,客观时间是如何在内时间
意识中“构造起”自身的。在这两个思想家之间尽管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他们
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作为现在次序的非本真时间之所以具有这种特征,是
因为那个被理解为现在的当下的缘故:现在次序的以前此刻是曾经存在的当下,现在次序的将来此刻是尚未到来的当下。由于这里的问题在于从本真的时
间经验出发澄清作为现在次序的时间,这两个哲学家必须特别注意:当下在本
真的时间经验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出于这个原因,胡塞尔将他的时间现象学植根于一种对我们各次当下的时间意
识的分析之中,在这里,在感性感知中进行的对一个对象的体现(Pr?sentation)构成一个范例。胡塞尔在此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发现[②]:具体地经验到的现在不是一个未延展的界限,而是现前域(Pr?senzfeld):当下意识以“前
摄”(Protention)和“滞留”(Retention)的形态自身展开到某个——依赖于各个注意力程度的——宽度之中,并且作为具有“原印象”的视域环境、作为体现之核心的视域环境而共同当下地(mitgegenw?rtig)具有正在到来的最近将来和正在消失的最近过去。
这样一种关于现前域的意识从本质上不同于作为现在次序的时间的意识,这个
区别在于,前者自身是一个发生——用隐喻的方式说是一条“河流”——,而被构造的客观时间作为现在次序却具有一个固定的、不动的形式的特征;在这
种形式中,原初的时间方式停滞下来。胡塞尔在所谓《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的文字中以及在最近(2001年)编辑出版的1917/18年贝尔瑙手稿中设想了不同的时间图式,他试图在这些图式中尽可能详细地展示现前域-发生,展
示在其原初性中被经验到的时间的“原流动”(Urstrom)。
据我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时间现象学中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在作为发生的时间
和作为不动的形式的时间的对立中,在哲学的时间理解中的第一个重大分歧又
回返了。尽管时间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作为对“运动”(Bewegung,kínesis)的“计数”(Anzahl,arithmós)而与运动相联结的(Physik 219 b 2),因为时间只能在运动上被读出,但对他而言,这样一种说法是荒谬的,即时间本
身是某种被运动的东西;时间作为数字毋宁说是不动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
现代自然科学的假设:借助于现在次序的各个位置的可数性,时间可以得到精
确的计量。与此相对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在《蒂迈欧》中所做的第一
个时间定义,在这个定义中,时间被规定为永恒的形象,这个形象被称作“活动的”(Timaios37 d 5)。
时间是由神圣造物主所创造的感性世界的基本秩序要素,按照《蒂迈欧》的极
端表述,关于这个感性世界的发生不能说:它存在(ist),而只能说:它生成(wird)(27 d 5/6)。据此,只能承认时间作为感性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生成的特征,亦即具有运动的特征。存在始终被保留给永恒。亚里士多德决定
背离他的老师而赋予时间以一个存在,因此他在《物理学》中将时间定义为某
种存在着的东西:它是“根据以前和以后的运动数量”。生成意味着对多个时段的穿越(Durchlaufen)。因此,柏拉图在他对由他引进哲学的“永
恒”(Ewigkeit,aión)的时间定义中说:永恒固存(beharrt)在“一”之中,即固存在一个排斥多的单数(Singular)之中。将时间理解为固定的形式、理解为一个与现在次序相关的数量的做法,乃是对亚里士多德时间定义的追随;而把时间视作现前域发生的看法则回溯到柏拉图的时间观上。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中含有“根据以前和以后”的规定,因为在一个运动的时段次序上可计数的现在次序之所以得到整理,是因为某个现在处在与所有其他的或前或后的曾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的关系之中。用一个语法概念来表达:这些现在在它们的这些相互接续中构成各个“时间阶段”。现代语法将时间阶段区别于时间“角度”。[③]角度是作为发生的时间所能提供的精神“外观”,即“时间流”如何向我们的经验表明自身的方式。这两种基本的、因为在所有其他可能的时间外观中都被预设了的外观就是“到来”和“离去”。胡塞尔在他对现前域-意识的描述中所分析的便是对作为一个发生的时间的这些角度的原初经验。
柏拉图在其《蒂迈欧》中第一个谈及时间的角度。源于拉丁文的“角
度”(Aspekt)一词无非是对希腊文的“埃多斯”(eíde)的翻译,柏拉图紧接上述时间定义后的一句话中使用了这个概念,他说:时间的“埃多斯”、时间的“外观”就是“它曾是”(es war,在希腊文中是ên)和“它将是”
(es wird sein,用希腊文是éstai——(37 e 3)。尽管柏拉图在同一句
中将这种时间外观区别于那些“时间部分(mére)”、即时间期(Zeitperioden),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标明在现在次序中的可计数的位置、即时间阶段,但人们在传统的柏拉图解释中仍然疏漏了这个区别,并且不加讨论地以为,柏拉图在这里所说的“它曾是”和“它将是”就标志着过去和将来的时间阶段。[④]“它曾是”和“它将是”虽然与这些时间阶段处在一种联系之中。但是它们并不标识这些时间阶段本身,而是将在其产生、在其生成中的它们表达出来:“它曾是”所指的是时间作为一个向过去之中的滑脱(Weggleiten)的时间的发生,而“它将是”所指的则是作为出自将来的到来的发生。在对这个哲学史联系并无所知的情况下,胡塞尔用他对“滞留”和“前摄”的划分所依据的便正是对这个角度的经验。
在这个联系中可以找到对时间这个“实事”的现象学澄清而言关键性的指明。这个指明在于,柏拉图在时间定义之后的几句话中明确地排除了这样的可能,即用“是”(ist)这个措辞所指称的东西属于时间的角度。与“它曾是”和“它将是”的外观不同,“是”标志着“当下”这个外观。在柏拉图看来,“它是”被保留给永恒,它无非在于“在一中固存”的当下。所以永恒也向我们提供一个外观、一个“埃多斯”,而这就是在“它是”中被表达出来的永恒的当下、理念的当下,除了“理念”(idéa)以外,柏拉图也可以使用在语言史上与之相近的“埃多斯”(e?dos)来称呼它。理念的这一个当下外观是与感性世界的生成相对立的,后者是在两个互补性的外观中表明自身的。
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通过柏拉图而获得的视角中来看一下胡塞尔对现前域的分析,那么就可以注意到,胡塞尔在其中有别于柏拉图,除了在前摄和滞留的形态中对时间角度的原初经验以外,他还允许有一个当下的核心,他也把这个核
心称之为原印象或原体现(Urpr?sentation)。关于这个核心,胡塞尔在一份贝尔瑙手稿中明确地说:意识在这里原初地经验到现实性(S. 14),而这就叫做:是。这意味着,胡塞尔把“它是”算作是时间的角度。这与柏拉图的明察是明显相悖的,这个明察是指:作为发生而被经验到的时间仅仅展示两个基本外观:来(Kommen)和去(Gehen)。对于胡塞尔来说,在这些为我们原初通过滞留和前摄所经验到的外观中表明出来的发生联系植根于一个作为其中心的现在核心中,恰恰是从这个中心出发,本真时间才显现为现前域、显现为各个“活的当下”。[⑤]
首先有两点有利于对一个当下核心、一个可以说在现前域中的原现在的设定:一方面,只有不断更新的现在核心的现身(Auftauchen)才适合于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作为客观现在次序的时间被解释为在现前域中的本真时间经验的衍生物,那么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为什么当意识借助于“滞留的彗星尾”而明确地回忆起某个过去的东西时,它能够通过在某个时间位置上的定位来认同这个过去的块片呢?对此的回答似乎只能是这样的一个设定:这对意识来说之所以是可能的,乃是因为,所有那些在它之中并且对它而言发生的东西的定位活动原初都是在不断更新的现在核心的现身中准备的。
另一方面,时间的前摄-滞留的原发生似乎不足以说明关于某物的意向意识。意识被指明:它撞到某些内容的规定性上——一个“素材”(Hyle)的各个因素上。这些素材的规定性原初地与意识相遇,先于所有明确的与对象的关联,因为意识觉知到,在感性领域中有某些区别或相似凸显出来。胡塞尔并没有追随经验主义传统的“材料”-点描主义,但只要他从这个传统中接受“印
象”(impression)的概念,他便仍然对这个传统承担义务。对于意识来说,素材的原初印象的当下便产生在现前域的现在核心中,胡塞尔就此而将它称作“原印象”(Urimpression)。
但是,这种认定一个在现前域内的原印象的现在核心的做法在现象学上是值得怀疑的,这一点从胡塞尔本人那里可以借助于这样的思考而得以表明,这个思考立足于从《危机》一书的周遭中形成的理念化(Idealisierung)概念:原印象的现在核心标志着现前域内的一个界限,它实际上并不是直观地被经验到的,而只展示着一个思想操作的产物,即作为临界构成(Limesbildung)的理念化产物:现前域的宽度在一个向一个愈来愈“窄细”的现在的前行着的思想过程中被狭隘化了,而这个直至无限的迈进被看作是贯穿的(durchlaufen)(参阅Krisis S. 359)。对一个现前域内的原印象界限的合法论证惟有通过这种思想操作才能完成,但却不能通过直观。
对一个原印象界限之设定的实际可疑性在于,以此方式在现前域中所经验到的那种时间的发生中引入了一个主宰的当下外观,即一个瞬间的素材的被给予之物的当下,滞留和前摄从它出发而被规定为〔它的〕环境:印象的现在作为在滞留和前摄之间的界限而构成现前域的中心,并且将时间的发生、到来和离去集拢在一起。在一些尤为给人以启发的贝尔瑙手稿中,胡塞尔试图一方面颠倒原印象的关系,另一方面试图颠倒滞留-前摄的关系。他不是从现在核-当下出发去解释前摄与滞留,而是从前摄和滞留的关系出发来规定当下核。因此在
现象学中首次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导向这样一个结局,即在作为“到来”的将来和作为“曾在”之间的“交互运
动”(Wechelbewegung)才“端出了”(erbringen)当下
(Zeit und Sein S. 14)。这样,当下便失去了主导地位,而如果哲学与科学追随了柏拉图的明察,那么当下是永远不应获得这个主宰地位的。
在对产生于前摄和滞留的共同作用中的现在意识进行说明时,胡塞尔依据了一个自《逻辑研究》以来的意向分析的基本概念:“充实”。这同时使他能够更深入到前摄之中,而在以往的文字中他为了滞留而几乎疏忽了前摄。正如在对“意向”(Intention)的类比中所构成的概念“前摄”(Protention)所已经表明的那样,前摄与意向有某些共同之处,即对充实的朝向。诚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意识在对充实的追求中“前指向”(protendiert)什么?这里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可能性。[⑥]但对于这里的思考之继续而言,这样一个前问题是决定性的:胡塞尔究竟有什么权利认为,在所有前摄中都有一个朝向充实的趋向?在这里,前摄与滞留的交互关系开始起作用。意识是从它的滞留地形成的过去出发在其前意指过程中受某些对意向生活之继续而言的前标识的引导。[⑦]
从这些前标识中产生的前摄是在完全宽泛词义上的直接“期待”;在它们之中可以预觉(antizipiert)将来可经验的对象,但也可以无对象化地预觉将来的素材内容。如此被理解的前摄始终包含在意识之中,即便它们已经充实了自身,因为在滞留中不仅保留了各个充实,也保留了它们(充实)在其中曾被预觉到的前摄。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可以说,前摄“作为前摄本身在其充实位置上并不丧失其本质特征”(第11页)。前摄始终作为前摄保存在滞留中,并且因此而可以引发新的前摄。在这个背景前面,每一个“当下的充实体验”都显现为“一个关于一个在过去前摄中被预觉之物的当下生成(Gegenw?rtig-Werden)的意识”。[⑧]
以此方式,意识在其整个时间延展中都为前摄所贯穿。与此相一致的是,它的标志是不断前行的滞留的变更过程的连续统。就像各个现前域一样,整个意识流也在两个互补的角度中显露自身:在每一个位置上,一方面有一个对充实的前摄趋向和这个趋向的一个现时的——至少是局部的——自身充实在主宰着,另一方面,各个自身已经充实(Sich-Erfüllthaben)的滞留保存在继续着。这两个方面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因为它们交互地使得对方得以可能:滞留的前摄(retinierte Protenieren)引发出新的前摄,而这些前摄由于其自身充实以滞留的方式作为一个自身已经充实而被保留下来,所以它们使滞留的蕴含链变得越来越长。
从这里出发,现前域的现在核现在可以得到更详细的标识。它始终还是界限,但这个界限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理念化的产物,而被理解为在现前域发生中的这样一个可被经验到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滞留变更与前摄变更的连续统相互交切”[⑨]。在这个位置上,各个现时地前摄的自身充实活动(Sich-
Erfüllen)转变为充实(Erfüllung)。但更确切地看,我们在这里还不能说“充实”,一旦说到“充实”,我们便会回到一个作为在前摄和滞留之间的中心中介点的原印象的现在核上去;相反,这种转变是直接在一个从一开始便滞留的
(retiniert)自身充实中进行的。
这样便获得了一个对现在核的规定,即使没有那种对一个原印象的当下外观的——据说时间的原初发生便是在其中具有其集拢的中心点——无法坚持的设定,这个规定也可以成立。但这个规定如前所述预设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在所有前摄中都有一个对无论何种类型的素材充实的趋向在起作用。这个设定看起来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无论我们在哪个位置上找到意识,它都始终已经具有一个提供着各个前标识的过去。由于所有为意识所遭遇的东西、所有原现前的内容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摄地“被期待的”,故而任何一个这样的内容都不是在完全严格的意义上“新”内容。
诚然,胡塞尔自己在贝尔瑙手稿中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异议说:还是可以想象在现前域中突然现出某种完全新的东西、一个十足令人惊异的事件。这样一个事件将不可能被任何与滞留组成相关的素材前标识来准备。先行于这个事件的前摄将会是一个无所约束的“空乏的”前摄。但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中也在这样一个极限情况中预设了一个朝向“充实”的前摄。即使在充实趋向完全失败的情况下,胡塞尔也认为,前摄的自身充实向滞留的自身已经充实的将来转变,以及从这里出发的滞留连续统的延长是被前指的(proteniert),[⑩]并且随着某种新东西的现出而得以表明,被预觉的充实在这种情况下无非就在于意向生活一般的继续前进。
可以注意到,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中回避了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明确回答:在现前域中的意识是否不可能遭遇全新的事件。他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解释说,一个全新的开端只能由“我们”做出,即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观察者,而不是由意识本身做出,我们始终发现这个意识已经处在“行进
中”(im Gange)。现前域-意识永远不会完全重新开始;每一个这样的意识的“起始点”都从一开始就扎根于前摄-滞留的意识流中,而这意味着:“新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只是作为对某些前标识的回答而被遭遇到。就此而论,在实事(Sache)上可以相信,胡塞尔实际上并不考虑绝对“新的”事件的可能性。但可以想象,这个可能性一再地使他不安,尽管它在方法上并没有受到考察;因为在这种不安中一再地有一个简单的、但被胡塞尔跳过的问题呈现出来:一个仅仅存在于意向生活一般中的充实是前摄地被预觉的吗?
胡塞尔可能会默默地认可这个回答,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未加思索地在他对前摄的分析中放弃了那种将人们在自然观点中所具有的对继续生活的原信任作为问题提出来的做法。胡塞尔把现象学理解为与自然观点的彻底决裂,这种自然观点是指那种在过渡到哲学之前始终未被注意的基本态度,在这种态度中有一些原则上未加考问的自明性。尽管有这样的现象学理解,胡塞尔在他对前摄的理解中仍然没有顾及到这个与自然的自明性的关键决裂,即对人类生存的动摇,在这些动摇中,通常的信心在本己生存的持续中丧失了它们的自明性。每当我们的必死性在一个相应混乱的情绪中现出自身,这个决裂便会进行。正如在开篇时所说,恰恰是这种由此而得以可能的生存方式被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称之为“本真的生存”。只要现象学顾及这种在“本真生存”中完成的时间经验,那么胡塞尔对那些由各种前摄所控管的充实趋向的基本设定就无法
长期得到坚持。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第329页)。这个发现如今也为胡塞尔所证实;因为看起来对作为现在次序的时间构造的理解而言关键之处在于前摄,即关于在其到来中的将来意识。但海德格尔也在“时间与存在”中谈及作为到来的将来,而更确切地看,即使在这篇后期报告中,如此被理解的将来也仍然具有它在《存在与时间》的时间性分析中所拥有的那种优先地位。——这使人能够揣度:对“本真时间”的规定也无法在不向本真性的生存状态理解进行回溯的情况下成立,尽管海德格尔显而易见地有意识避免向这样一种回溯并且不再想把“本真时间”理解为仅仅那个在其源始本己中被看到的时间。
即使在这篇后期文字中,在对“时间本性”(Eigene der Zeit)进行规定时(第13页),与本真生存的关联也表明自身是在实事上不可避免的,对此的第一标识是这样一个事实:海德格尔走了一条貌似的弯路,并且把人引入思考:人是被某个各次在场者的在场(Anwesen)“直接”“关涉着”,但也为不在场(Abwesen)“直接”“关涉着”(第13页)。我们人是在“曾在”和“将来”的双重内涵中经验到这种不在场,而将来被理解为一种“走向我们”(Auf-uns-Zukommen)、一种到达(Ankunft)。
如果“曾在”“直接”(un-mittelbar)关涉到人,那么以此而在现象学上具体所指的只能是——虽然海德格尔没有说出这一点——一种过去的方式,它不是作为一种唯独必须通过明确回忆的中介(Mittel)才能得以当下化的遥远而与我们相遭遇。我们在作为一个始终活在人的行动之中的遗传的习惯中经验到这样一种过去的方式;行动在这里之所以起作用,乃是因为只有在就人是行动的生物这一点而论时,“某物‘关涉到’人”这个说法才能有意义地被说出。与此相符——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也有一种“直接关涉到”我们的“到达”。在现象学的具体化中,这便是在行动中被经验到的“机会”(Gelegenheit)。是否有特定的机会提供给在各个境域中的行动,或者,是否相关的机会不提供给行动着的人,对此,无法消除的将来之混沌始终遮蔽不现,然而机会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处在“伸手可及”之处,亦即“直接”就在面前。
就当下对于本真时间之意义的问题而言,这样一个观察是根本性的:海德格尔在阐释这上述两种不在场的方式的“交互关系”时虽然也谈及当下,但却试图从这个交互关系出发来说明当下。这至少使人在结构上回忆起刚才提到的胡塞尔的贝尔瑙尝试:剥夺现前域中的现在核在作为“原印象”时还具有的那个优先地位,并且纯粹从前摄和滞留的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个现在核。至于“曾在”与“将来”的交互关系,我们首先考察作为到达的将来与曾在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于,到达“递达并端出”曾在。
“递达”(reichen)这个动词是指一种超出一段距离的给出(Geben)。这个距离是无法逾越的深渊,它把将来与当下分离开来。给出(Geben)关系到人在在场的发生中的角色:在场是一种赠礼(Gabe)。这个赠礼的“递达”虽然需要作为收悉者(Adressant)的人,但赠礼并不因为我们的参与就“达及”(er-reichen)我
们,相反,我们要依赖于这个给予来自自身的发生(第14页)。我们从这个给予中获得在场。但被到达所递达的当下,并不直接就是一个具有当下特征的在场,而是一个在“曾在”形态中的不在场。这从现象学上具体地说就是:由于我们在行动时总会有机会提供给我们,这表明,我们人可以说是一直随身背负着习惯。只是因为这样一种直接的到达发生,所以我们“具有”习惯,而在这个意义上,到达“端出”曾在。
正是这个动词“端出”(erbringen)(它听起来完全不同于“做出”),海德格尔在规定与此相反的关系时避免使用,这个相反的关系是指曾在与到达的关系:曾在“向将来……伸展(zureichen)”(第14页)。将此翻译为具体的话来说便是:为了能够作为习惯而活跃起来,习惯需要那个以机会的形态在人的行动中开启自身的将来。在这种曾在对到达的依赖性中无可争议地表明,即使他“时间与存在”中——用《存在与时间》的语言来说就是——,时间还是从将来出发而“被时间化的”。
到达和曾在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它们是不在场的方式并且彼此间有一段为递达所连接的距离。这种递达使它们相互“接近”,使它们进入到一个切近中,而这种“接近着的切近”实际上便是——动词地理解的——时间本质。(第16页)但这两种不在场的方式并不是对称的。在到达时的不在场方式就在于,接近的切近使这个来自将来的到达“保持敞开”,人在行动时在不确定性中具体经验到什么,在各个情景中是否有一个机会,这些问题都还有待回答。因而这里出现了不确定性:一个机会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始终是隐蔽着的,因为它尽管是直接切近的,却并不是当下的;而成为当下的东西则不再是机会了。所以海德格尔可以谈及“切近的接近”:它“在来中扣留当下,从而使处在将来的到达敞开”(第16页)。
与这种在“扣留”形态中的不在场完全不同的是这样一种不在场,即我们以“曾在”的方式所经验到的不在场。“接近的切近”“把曾在的到临(Ankunft)作为当下加以拒绝,从而使曾在敞开”(第16页)。对此可以做如此理解,即曾在始终被拒绝进入到临、到达(Ankommen)的发生之中;因为,到达——形象地说——开启了处在我们“面前”的东西,与到达不同,曾在始终不可消除地处在我们的“背后”。即便我们转过身来,我们也无法改变始终有某物在我们身后这一状况。这恰恰适用于曾在;我们可以说是被阻止“从前面”、即以到达的方式去遭遇习惯。在权衡一个机会时,我们的目光会朝向到达;与此相反,目光所朝向的一个习惯则因此而在原则上已经丧失了它的习惯特征。
故而当海德格尔说,曾在“被拒绝”以到临的方式发生时,他对曾在特征的现象学描述是合乎实事的。但随着这个规定,曾在便是从到达出发而得到特征描述的,而这重新表明,海德格尔也在这篇后期文字中坚持将来的优先地位。到达是一种发生,而从这种发生出发,“本真时间”的“本质”(Wesen)便得到规定。由此,这里的各个思考的出发点命题便得到证实,即:海德格尔——与胡塞尔连同其对现前域的分析一样——把“本真时间”理解为一个发生,并且因此原则上继承的是柏拉图而非亚里士多德。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也像胡塞尔一样,由于表明了当下的兴趣,因而对亚里士多德承担义务。因此,在结束时作为第二点提出的是一个问题:在他那里,到达和曾在的交互关系是如何“端出当下”的(第14页)。海德格尔所说的当下不可能是作为在现在次序中、即在非本真时间中的点或时段的现在;因为这样的话,他就离开了对他的报告的“实事”的描述,即对“本真时间”的描述。这里的问题毋宁在于作为维度的“当下”,它是保持敞开的,因为时间作为切近相互接近着“到达”与“曾在”的不在场,这恰恰是由于它通过扣留和拒绝而将这两者不可逾越地远隔开来。[11]这种接近是与对遥远(Ferne)维持和清除相一致的。
通过“递达”,即通过克服距离的接近,一个空间、一个维度被敞开:“时间空间”(Zeitraum),它在德文的日常语言中也出现,并且构成一个“场所”,在时间中出现的东西便在这里找到其“位子”。“空间”或“维度”意味着一种“相互分离”。也许海德格尔尽管没有这样说,却仍然想要伸展出去,即认为通过接近的疏远而递达的时间空间的相互分离便是“本真的当下”。但惟当我们不是在一种可测量的广延的意义上理解这种相互分离时,我们才可以认为,用“时间空间”和“维度”概念所指称的是一个在现在次序中的时间片段的长度,这个现在次序的范围可以通过对一批时段的给明而被给明。
海德格尔不知不觉地跟随了柏拉图的明察,即“实际上”〔“本真地”〕没有那种作为在时间中的现在的当下外观。从这个明察出发,哲学家早就必须受这样一个任务的引导,即从哲学地被经验到的时间出发,赋予当下以一个不同于现在时段的意义。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将时间经验认同为对非本真的现在的经验,哲学通向这个任务提出的道路被切断了。柏拉图回避了这个任务,因为他把出自时间的当下之外观移置到时间的永恒形象之中,移置到永恒之中。
随着对这个通过“现在”而向时间哲学提出的任务的“解决”,柏拉图便不再去理会这样一个情况:到达,即作为时间发生的到达,作为互补的外观乃是不可取消地属于滑脱(Weggleiten)的,因而当下无论如何都可以被看作是处在无限中的到达目标。通过对“诸理念”的设定以及对它们作为当下的存在方式、永恒外观的规定,柏拉图完成了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第一个基本的“理念化”,因为他把到达的无限发生看作是“穿越的”(durchlaufen)。自胡塞尔以来,现象学要回问到理念化之后的原初经验。也许可以说,随着在海德格尔后期的本真时间现象学中对当下作为维度的新规定,柏拉图首次提出的对当下的理念化,在两千多年来终于获得了一个回应。
[①]对于一个实事原初是“本己”的东西,也可以被称作这个实事“本身”之所是。古希腊语中的“自身”一词叫做"autós"。在这个意义上,“本真”这个形容词在其他语言中有别于德语,是通过像"authentic"、"autentico"等等来再现的。
[②]这个发现在奥古斯丁和威廉·詹姆斯那里已经早早地露出苗头。
[③]在有些语言中,那些能够表达一个发生的语词——在印欧语言中这便是动词——无法构成指示出像过去、当下或将来之时间阶段的表达式。但常常可以改变这样一些语词,以致于用它们可以言说不同的〔时间〕角度。
[④]这个解释的严重不精确性是德国哲学家格诺特·伯姆在1974年的研究“时间与数”中才发现的。
[⑤]在1966年以这个表达式为书名的书中,笔者本人还追随胡塞尔时间思考中的现在主宰地位。
[⑥]迪特·洛玛是贝尔瑙手稿的两位编者之一,他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前摄‘前摄’了什么?”——该文已被译成中文刊载于本辑中——编者注)中根据这些手稿在这方面做了仔细的研究。
[⑦]这些前标识(Vorzeichnungen)可以关系到对一个个别素材在其个体规定性中的被给予性的感知的继续,或者关系到这些被给予性的风格或类型的继续,或者关系到对它们的视域的维续。洛玛在“H-前展”的标题下严格区分了这些可能性。
[⑧]这是贝尔瑙手稿的另一个编者鲁道夫·贝耐特在该卷引论中的恰当表述(第XLII)。
[⑨]这还是贝耐特在同上书中的说法(第XLI页)。
[⑩]所以洛玛在这里有别于“H-前展”地使用“R-前展”一词。
[11]为了在语言上使“接近是作为疏远而发生的”这句话变得优雅,海德格尔在转向后其他的文字中使用了带连结号的“ent-fernen”这个德文词,并赋予它以去除遥远的意义——一个恰恰与在这个词在通常用语中的含义正相反对的意义。
主体主义的最终克服与现象学由胡塞尔通向海德格尔之路 人们经常说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可是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呢?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都不甚了了。仿佛海德格尔只是从弗莱堡的胡塞尔那里学到了?现象学的看?,然后用这种?看?去考虑他自己的问题。因为从表面上看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两人的旨趣和风格都是迥然相异,以至于翻译《观念1》的李幼蒸先生在译后记中呼吁将两人完全分开对待。不过我认为,除了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现象学方法?, 两人思想的内在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否则光凭现象学方法(何况他们二人的现象学方法具体来说是不同的)何以说海氏的思想是胡塞尔的发展,却从来没人说舍勒的思想是胡塞尔的发展呢?但是这种思想上的内在联系不是市面上某些一般性的论断——比如说胡塞尔考察的是认识问题,海氏是存在问题;或者说胡塞尔没有摆脱近代主体哲学的影响而海氏彻底摆脱了——可以澄清的,因为澄清这一联系恰恰要求的是给出这些论断的根据。这篇短文想从其中一个角度对这一联系加以探讨,看看胡塞尔的现象学如何为海氏的某些基本思想提供了线索。 抱歉给这篇文章起了一个这么长又这么零碎的题目,这是因为它其实是两篇文章。由于第二篇(本文的第二部分)的理解有待第一篇(第一部分),于是就把它们硬凑到一起了。两部分的连接十分滞涩,还请读者多担待。整篇文章描绘了一条上升的道路。其中第一部分讨论了胡塞尔现象学由?直观?向?构造?的推进,而第二部分则联系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思想,讨论了直观与解释之间的关系,梳理出了由胡塞尔的?事情本身?向海德格尔的?事情本身?的进路。 一,直观与构造 现象学的口号?Zu den Sachen selbst!?不仅要求?面向实事?,并且要求回到?实事本身?。也就是说,要在事物自身中把握事物。对于胡塞尔来说,作为思想的?零点?的
浅谈胡塞尔现象学之意向性行为 摘要: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以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和康德、笛卡尔哲学为主要思想渊源,试图通 过现象学方法建立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他的思想直接引起了一场现象学运动,形成一种以现象学 方法为主要特征的广泛的哲学思潮,对整个现当代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最 重要的成果之一。可以说,不了解现象学的哲学家,在欧陆哲学中几乎不可能站到思想的前沿。本 文借以对胡塞尔现象学理论基础意向性行为的着重梳理,为以后现象学的深层次的学习和理解打下 基础。 关键字:胡塞尔现象学现象学理论的基石意向性行为 现象学在20世纪的西方产生发展并十分流行,与其他一些思潮,比如生命哲学、克尔凯郭尔的 生存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等,一起极深刻地影响了欧陆哲学的发展。但是,在这 些思想中,广义的现象学最有方法论的新鲜含义和纯思维的穿透力。主要通过它,现代西方哲学中 的欧陆思潮与传统的西方哲学保持了内在的联系,现象学的词源可以追溯至18世界法国哲学家兰伯 尔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著作中,但其含义与后来有所不同。在新的视野和语境中理解老的 问题,现象学被赋予了特殊且意义深远的新时期含义,比如传统的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伦 理学、宗教哲学和美学问题。 而对现象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便是德国犹太裔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23岁时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并从事过短期的数学方面的工作。1884年至1886年, 他在维也纳听到了F. 布伦塔诺(Brentano, 1838-1911)的课,后者关于“意向性”的讲述使得他 的思路大开,从此决定献身于哲学事业。1891年他发表了《算术哲学》一书,对数学和逻辑的基础 从意识心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它的“心理主义”倾向受到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的批评。1900年至1901年,胡塞尔发表了两卷本的《逻辑研究》,对逻辑研究中的心理主义、包括他自己的 一些过去的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清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用“意向性”这个居于主体和(感觉 经验)对象之间的更本源的思路来理解“意义”的纯构成,并以此为基点,论述了现象学的一些基 本思想和方法。此书标志着二十世纪现象学运动的开始。1901年,胡塞尔到哥廷根大学任教。其后,他经历了某种思想危机,最后以1913年发表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一书作结,完成了从“描述现象学”到“先验现象学”的过渡。这之后,他对于意向性构成的思想又有更丰富 的论述。1916年,胡塞尔受聘于弗莱堡大学,接替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教席,并与海德格尔相识。1928年,发表了《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座》(海德格尔编辑)。1929年出版了《形式的和 先验的逻辑》。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更多地关注“主体间性”问题,而且提出了“生活世界”的学说,撰写了《笛卡尔的沉思》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由于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胡塞尔晚景凄凉,1938年去世时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只有一人参加他的葬礼。 胡塞尔认为哲学从一开始就想要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但不幸的是,一直到他那时为止,哲学还 根本不是这样一门严格的学问。虽然有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等人的努力,但哲学一 直未找到一个真正严格的起点。所以,“作为科学它还没有开始”。在胡塞尔看来,其原因在于哲 学家们还未能真正摆脱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的思想方式。采取这种思想态度的人将我们认识的 对象和认识的可能性都视为现成给予的和不成问题的。所以,这样的认识和思考从一开始就已经处 在某种前提规定的框架中,而缺少一种体验的和反思的彻底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思维和它所依 据的经验不是一个真正的起点,也不可能有一个内在严格的构成机制。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找 到一个“无(现成)前提的开端”就成为一切抱有严格科学“理念”的哲学探索的最重要的任务。 而这个“理念”或“观念”(Idee)只有在一门“纯粹的现象学”或“现象学的哲学”中才能实现。 现象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揭示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思考方法的可能,一个看待哲学问题更原处的视野。在他看来,以前所有的哲学都还不是一种具有自身规范性或完全自立的学问,总已包含了某种外在 的前提,以至各种任意的思想能够在哲学中泛滥。胡塞尔去获得这种最终的严格性的策略是:找到 一个无可怀疑、无所预设的绝对确定性,并且在此确定性中发现某种可以构成客观性的机制。他之
第35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1月 Vol.35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13 ──────────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支持计划资助项目(BYQK2012001) 收稿日期:2012-11-19 作者简介:郑丹青(1973-),男,湖南岳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35- 海德格尔语言之思的复调性 郑丹青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特征“此在在世界之中”,将世界问题和人的问题联系起来,又通过此在这一中介把世界现象最终同存在问题勾连起来。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是存在关系。海德格尔“言说观”:以词语创建存在。海德格尔的“言说”观是建立在对传统语言观批判的基础之上。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以“诗意的存在”重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有声的聚合与无声的聚合两个声部的奏鸣形成其语言之思的复调性。 关键词:海德格尔;存在;语言;复调性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3)01-0035-05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3.01.009 The Polyphony in Heidegger’s Thought on Language ZHENG Dan-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 of Heidegger’s ontology – “Dasein is in the world” – connects the idea of worldliness and that of man. Dasein also connects eventually the world of phenomena and Being. The intrinsic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 is the relation of being. Heidegger’s “speech of language” – Being is constructed with words – is founded on the critique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language. He posits the concept that “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 and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world with “poetic dwelling”. The audible whole and the silent whole reinforce each other to construct the polyphony in his thought on language. Key Words: Heidegger; Being; language; polyphony 一、复调性与存在 复调本是音乐术语,“不同的声音用不同的调子唱同一个题目”[1]。巴赫金在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文本分析时,将音乐中的“复调”概念引入小说理论中,经多方阐述成为其哲学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由隐喻演绎为概念,由术语提升为范畴,其涵义在多重变奏中不断绵延而日益丰厚。它们既是指文学体裁,也是指艺术思维;既是指哲学理念,也是指人文精神。“在美学理论中,‘复调’指的是艺术观照上的一种视界,因此而有‘复调型艺术思维’;在哲学理论‘复调’指的是拥有独立个性的不同主体之间既不相融合也不相分割而共同建构真理的一种状态,因此而有‘复调性关系’。”[2]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及《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等 书中,“对话”是巴赫金反复阐述的一个核心概念。对话性(对话关系)是其复调理论的基石。对话是复调得以形成的质的规定性。巴赫金的“复调性”的核心语义乃是“对话性”。经巴赫金的多方阐发“复调性”不仅指称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更是把它提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复调性”作为哲学理念,其精髓乃是不同主体间意识相互作用的对话性,其根源乃是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性。在巴赫金看来,凡是能够表达一定含义的事物,只要是以语言符号表现出来的,相互间就会有对话关系。任何存在只有经过对话,才能实现思想的、情感的、意义的交流,才能建立起人与物之间、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这样相互关系显现存在,对话是人的存在以及世界的本质。因此,对话思想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特征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将此在与世界联系起来,将世界问题和人的问题
海德格尔自由观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存在,是没有任何限制的终极本体。只有存在本身才使那种摆脱了任何限制的自由成为现实,而在他之前所有的哲学都只是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都是受限制的、处于“遮蔽”状态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意义上的、绝对的存在,无法实现绝对的自由。也就是说,在他之前所有的哲学都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而也就谈不上解决自由的问题。任何存在者都只是一种受限制的存在,只有“存在”本身才是没有限制的真正本体意义上(也就是他所谓的存在意义)的自由存在。他于是从“存在”的无限性推出了“自由”的绝对性。 但是,“存在”这一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本体的假设必然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的错误。也就是说,那种没有任何限制、自己决定自己的最终实体是不存在的。因为所谓没有任何外在限制的存在,也就是没有任何外在关系的存在,而关系就是属性,也就是本质的外在表现。那么,没有任何外在关系的限制,也就是没有任何属性和没有任何本质的存在,而没有本质及属性就是不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时空总是关系的时空,任何的存在总是一定关系中的时空存在,关系既时空,关系外的存在也必然是时空外的存在,而时空之外的存在也就是不存在。没有联系就没有本质,也就没有物的存在,更谈不上什么物的自由了。这显然是一种存在和自由的悖论。 何况,关系既差异,差异也就是关系。那种自我同一的绝对本体,因为与外部没有任何的关系,也就意味着它与外部没有任何的差异,那么,内在的本体就是外在的现象,没有任何差异的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就是自身绝对同一的、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片树叶。一方面,绝无限制的存在就是世界本身,另一方面,存在和世界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差异。这就是绝对本体的悖论。这或许是绝对本体论者所不愿看见的,然而,这却是一个逻辑事实。本体与外在世界的区别于是就变得毫无意义。 海德格尔否定了在他之前几千年哲学的本体(存在),但他忽略了这一点,既当他把在他之前的存在(本体)存在者化的时候,也就是把存在者存在(本体)化。从这个作为自己逻辑前提的悖论出发,海德格而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所苦苦追寻的“存在”究竟在那儿,他最后只能承认,自己所有的工作只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探索存在的路”。 因此,绝对自由赖以为基础的绝对本体“存在”,只是一个逻辑的虚构,以此虚无本体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诡辩——自由就是虚无,就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无。绝对的自由的大厦因此也就轰然倒塌。 而且,作为最抽象的思辨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这一个迂回曲折的关于存在意义上的自由思想,也似乎没有超过最感性的经验哲学家休谟多少。早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出版187年以前的1740年,休谟就在自己的《人性论》中认为,任何的存在者,无论如何自由自在地发展,无论如何自己决定自己,但由于受制于自己的存在(内在必然的本质),因而这种自由发展本质上都是不自由的。他说:“每一个物体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取决于一种绝对的必然性,而事物不仅无法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天使、灵魂或者是任何的超自然的存在,甚至不能丝毫偏离他自己正在运行于其中的、被精确设计的路线。”[①]他认为这种受制于必然性的物体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限制”,根本无自由可言,那么,他所谓
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简介 首先要了解他思想中的三个概念:描述法、自由想像法、地平线法。(一)描述法描述法是指,如果想分辨一样东西,先不要认定它是什么,而要先作一个客观的描写。然而,描写是相当困难的,并且每个人对同样一种东西的描写可能不太一样。因此,必须把所要描写的对象直接凸显出来,周边的东西先存而不论,一样一样地排除,此时就要配合自由想像法。(二)自由想像法 先举个例子:如果想要知道“人”到底是什么,那么可以问:“如果一个人车祸受伤.断了一只手,这样还算是人吗?”当然,这样叫做独臂人。接着继续问:“那么如果断了两只手.还算是人吗?”当然还算,因为这样叫做无臂人。相同的,断了一只脚叫做独脚人;就算两只手、两只脚都断了,也还是人。那么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不算是人呢?思考到最后,可能会认为如果没有头就不算是人了,因为我们从来不曾见过一个没有头的人。这就是自由想像法。使用自由想像法去认识一个人时.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要间:“如果少了这项特色,他还是他吗?”现象学的目的就在于让人知道一样东西的本质。假设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本质是什么,首先就要把我们能够掌握的、关于这个人的所有现象写下来,譬
如:身高、体重、家世背景、念什么科系、成绩如何、有什么嗜好、参加什么社团等。写下来之后,开始使用自由想像法,亦即问自己:“如果他少了这一样条件,他还是他吗?。(譬如:如果他身高没这么高,他还是他吗?)按照这种方式把每个细节一一问消楚,最后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些条件是绝对不能少的,一旦缺少了这些东西,他就不再是他了(如:他非常勇敢、非常诚实等)。涌常这些东西会g跟一个人内心的价值观有关,而不是与外在条件有关。由此可知,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不应该被外表所迷感,因为外表很多条件部是可以去掉的。把这些外在条件去掉之后,内在特质才会凸显出来。如果没有经过这种现象学的思考过程,就很难发现一个人的本质真相,以至干容易被外表迷感.举例来说.电现新闻的主播一个个都很上相,每天报新闻看起来好像很有见解,但是他们真的很明智吗?这就说明了,判断任何东西的时候,不能只看外表.而要问:“什么是它的本质?进而使用描述法与自由想像法去思考,如此才能发现真相。(三)地平线法.那么,地平线又是什么呢?英文是horizon ,有时候也翻成“视野”或是'视域”。人看任何东西都有视域,而这个视域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世界。例如.当你走在原野上,看到远处有一根尖尖的东西,很像犀牛角,也很像是教室的塔尖.但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就像我们有时候看电影,会着到一个人在原野上走了很久,看到远处有一个尖尖的
大三 帖子 125 精华 积分 282 威望 金钱 137 石头 阅读权限 30 一、导言任何一个了解《存在与时间》的人都知道,海德格尔在这一著作中试图摧毁关于知识对实践的优先性的笛卡尔传统.初看起来,海德格尔的确试图把这一传统简单地颠倒过来,即 论述纯粹的沉思是对日常经验内容的否定的修正.更为特别的是,他青起来是说这纯粹的 、赋予意义的知的主体仍然处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它必须被有所牵涉的、赋予意义的 行的主体所代替.但是一个人如果简单地颠倒传统,那他就要冒被误解和重新估价的风险 ,而且胡塞尔现象学的最佳注释者达格芬·弗勒斯达尔(Dagfonn Fllesdal)就不被误导至 低估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的独创性.在一篇论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关行动的作用的文章 中,弗勒斯达尔这样来解释海德格尔,即认为胡塞尔相传统过度强调了纯粹的沉思,他也 同意他所认为的海德格尔的观点,即实践活动是主体赋予客体以意义的基本方式. "一般认为,实践活动预设了对世界的理论的理解……海德格尔反对这一点.他把我们处 理世界的实践方式看作比理论更为基本.……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即……人的活动在我们 建构世界中发生作用的观点以及他对其发生方式的分析,在我看来是海德格尔对哲学的主 要贡献". 弗勒斯达尔指出:"胡塞尔在1916年来到弗莱堡之后,显然越来越意识到我们的实践活动 是我们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然后试图决定现象学中对实践活动的这一新兴趣 应当归功于谁.他写道:"胡塞尔有可能在这——'实践的'新方向上影响了海德格尔, "但他也承认,"也有可能是胡塞尔在与年轻的海德格尔讨论时受到了这一方面的影响. " 然而我要论证的是,一当人们看到海德格尔在这一问题上与胡塞尔的区别的深度,影响的 问题就显得无关重要了.有的问题比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重要得多.真正的问题关系到对意 向性的两种对立的说明.正如弗兰兹·布伦塔诺和后来的胡塞尔所采用的那样,"意向性 "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即感知、相信、欲求、惧怕、怀疑等精神状态总是关于某个事物的 ,也就是总对着加以描述的某个事物,无论这一超精神的客体存在与否.使这种指向得以 实现的精神特质被称为精神状态的表征的或意向的内容.弗勒斯达尔在集中讨论行动的意 向内容对思想的意向内容的相对重要性时,忽视了海德格尔的激进观点,即以精神内容对 意向性的说明预设了但却忽略了更为基本的意向性类型一—一种完全不包括意向内容的意 向性.海德格尔不想使实践活动处于首要地位;他想表明实践活动和沉思的认知都不能被 理解为自我满足的主体及其意向内容与独立的客体之间的关系. 弗勒斯达尔断定领海德格尔所反对的是关于实践的传统的表征理论.海德格尔试图打破这 一哲学传统,他集中于努力超越这些观点所预设的主体/客体之分.他在1929年的一次讲 演中说:"我的实质意图是首先提出(主/客关系)问题,然后这样来论证,即整个西方传
海德格尔哲学——张志伟 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 《存在与时间》《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林中路》《路标》 海德格尔的前期哲学将存在与时间联系起来,使形而上学-存在论呈现为完全不同的局面。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则探索了通往存在的不同道路。 结构: 一、存在问题 二、此在的世界 三、此在的沉沦 四、向死而在 五、海德格尔与老庄 一、存在问题 《存在与时间》(1927) 海德格尔前期思想的代表是《存在与时间》。《存在与时间》的出发点,也是海德格尔从现象学接受过来的思想,就是要破处传统西方哲学主客二元式的认识论框架,深入到主体客体分化之前更深层次的源始境域里去解决存在问题。 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了,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柏拉图 科学思维方式 通过抽象的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 (1)玫瑰花、牡丹花……“花”; (2)花、草、树、木……“植物”; (3)植物、动物……“生物”; (4)生物、非生物……存在物; (5)所有的存在物……“存在”。 作为主客二元式的认识论框架,科学思维方式看起来似乎越向上抽象越接近客观实在,而实际上归根结底封闭于主观性之中。而且存在是不可能通过无限的抽象获得的,不仅如此,存在与存在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的问题,并不是抽象到最高的层面才会抽象出存在,实际上最高层次的存在物与最低层次的存在物都“存在”。 在的遗忘 存在是什么=存在物是什么 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别 存在(Sein,Being) 存在:Being-to be Sein-zu sein 存在=去存在 =生成的境域 =生生不已的源泉 那么,我们怎样追问存在的意义?虽然存在者都是因存在而存在的,但是一问到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必须从存在者入手追问存在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找到一种存在者,这种存在者与存在有“存在论”的关系,即是说,这种存在者是由存在规定的,它能够追问存在并且因它的存在而使存在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向来所是的在者,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Dasein)。 一切在者都因存在而存在,但当它们存在时,存在却隐而不显了,唯独“此在”这种在者其本性独特,它始终处在“去存在”(zu sein,to be)的过程之中,因而它的存在就是存在的显现。我们不要把自己与自己的存在看作是两回事:我们始终存在着,存在在我们的行动中存在出来,显现了出来。因此,此在是存在的“澄明”或“林中空地”(Lichtung)。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正是由于作为“现象”的技术蔽而不显,使得通常关于技术的诸多议论远离技术的本质,对技术的本质视而不见。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就在于使技术这种“现象”澄明起来。技术作为“现象”的深藏不露,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密切相关。特别是在近代,这个通过科技的繁荣而使形而上学极度发达的时代,技术正是作为完成了的形而上学在起作用。 “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正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这个维度规定了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走向。 技术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质疑技术中立论 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超越存在者的层面,直追存在本身。如果他真的把运思的焦点对准了“技术”,那么,技术就不是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技术,技术就一定承担着让存在者的存在得以开显的决定性角色,也就是说,技术必定要作为真理发生的方式,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就是开显。 通常人们都说,技术是今天最显著的现象,因为我们在这儿那儿到处都碰到技术的东西,技术占据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空间。然而,这里说的“现象”绝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 在这个技术支配一切的时代,技术的本质作为一种“现象”反而可能是最不显著的。在时下关于技术的众多谈论甚至争论中,人们关于技术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海德格尔称为流俗的技术概念:它把技术看成是工具,看成是人的行为。由于共同的禀承这种工具论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观,海德格尔称那些表面上对立的双方——盲目的推动技术者和无助的反抗技术者——始终是一回事。说他们是一回事并不是说他们持有相同的观点,也不只是说他们有着某种共同“语言”,而是说,他们对于他们共同持有的技术观完全缺乏反思,特别是,在他们双方或多或少持有的技术中立的看法中,这种反思被完全消解和完全放弃了。 人们为何会持有技术中立观,以及为何会放弃对工具论和人类学的技术观的反思呢?因为它们是正确的。在我们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技术的东西中,哪一样都是人们为着某种用途和目的而制造的工具,无论这些工具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正确的东西又往往与真理相混同。然而,正确的东西并不等于真理。正确的东西总是活跃在某种开显之中,它是同处一个平面上的存在者之间的某种对位和错位,为着成为正确的东西恰恰并不需要使这种无蔽向我们显现出来。因此,在正确的东西那里,事情的本质尚未揭示出来,毋宁说,在正确的东西那里,真理恰恰被遮蔽起来。 因为工具论的技术观是正确的,人们就因此不再追问“工具”和“手段”是怎么一回事,把它们看成自明的东西,这就错失了“真理”──那使得正确性得以成为正确性的东西。因此,为了由正确性深入到真理,我们就得进一步追问“工具”和“手段”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从工具论(instrumental)的技术概念入手。通常的工具论总是带有“工具”与“目的”相分离的性质,以致人们常常把工具论也就看成是工具中立论。工具与目的相分离之后,工具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而且不受制于目的,相反,它仿佛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目的,
胡塞尔现象学的目标 胡塞爾現象學的目標 張典 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胡塞尔表达他非常怀念席勒—贝多芬的欢乐颂体现出来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胡塞尔将这样的人文主义视作古希腊罗马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古典理性精神在十八世纪的复现,与这种古典人文精神的健康相比,当下社会的精神显得颓败,二者形成了鲜明对照。[1]那么,欧洲已经遇到精神危机,胡塞尔的诊断:胡塞尔从欧洲科学精神的反思开始,欧洲科学的危机直接决定了欧洲哲学的千年王国的分解,普遍整体的哲学让位于经验性的实证哲学,普遍哲学瓦解,理性信仰崩溃,古典素朴的欧洲人性也崩溃了。欧洲科学的危机表现在科学丧失了周围生活世界(Lebensumwelt)。那么,胡塞尔为什么认为人性的危机来源于科学的危机?什么是周围生活世界? 胡塞尔的分析,古希腊罗马的科学是一种生活的技艺(τ?χνη),那时的周围生活世界就是指自然和人的精神和谐一体的世界,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人性没有分裂的,那时的数学和几何学来源于生活,是为了生活。胡塞尔分析,
欧洲科学的危机从伽利略开始,伽利略开始近代性,伽利略使自然精确数学化、纯几何学化、理念化,几何学实际上是数学的直观。伽利略作为纯几何学的继承人,这种直观的概念化,已经不是古希腊罗马的几何学了,伽利略的几何学已经抽空了活生生的生活体验,此后人们对几何学的精确体系的来源、动机不作应有的反思。自伽利略起,理念化的自然就开始不知不觉地取代了前科学直观的自然。[2]笛卡尔进一步开始二元论:自然世界和心灵世界二分,笛卡尔开辟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笛卡尔通向英国的经验论,到休谟那里达到高峰;另一条道追求先验超越论,到康德达到顶峰。康德第一次建立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方法,康德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说的,先验感性直观的建立是认识论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就是现象学革命。胡塞尔现象学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克服康德的现象学中的心理学残余,为哲学的前年王国建立牢固的根基。近代欧洲科学的开创者伽俐略、笛卡尔为起点的科学方法中本来就隐藏着本真的方法的丧失的原因,而致使欧洲科学精神被技术化的功利主义而抽空,陷入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中,这是欧洲科学精神危机的根本问题。[3] 胡塞尔思考的科学精神分裂为二,近代性的独立的数学-物理模式成为科学精神的主流形态,一种纯观念的科学,这种科学其实不是关注自然实际的科学,明天是刮风下雨,或风和
什么叫思想 海德格尔/著 编者按:此文原载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中译文原载孙周兴选编的《海德格尔选集》,这里刊出的是译者为中文版《演讲与论文集》新近校订的的修订译稿,感谢译者惠寄。 当我们亲自思想时,我们才通达那召唤思想的东西。而为了让这样一种尝试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准备学习思想。 一旦我们投身于这种学习,我们也就已经承认了:我们还不能够思想。 然而,人却被视为能思想的动物。人有理由被看作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人是理性的生物。而理性,即ratio,是在思想中展开自身的。作为理性的生物,只要人愿意,他是必定能思想的。可是,也许人意愿思想,其实却不能思想。说到底,在这种思想意愿中,人意求太多,因而所能太少。 就人具有思想的可能性而言,人是能思想的。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尚未保证我们真的能够思想。因为,能够做某事意味着:使某事按其本质进入我们自身之中,[2]迫切地守护这种进入。但我们往往只能够做我们喜欢的东西,[3]我们由于允许其进入而对之产生好感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只喜欢那个东西,它向来预先从自身而来喜欢我们,而且是在我们的本质上喜欢我们,因为它倾向于这种本质。通过这样一种倾向,我们的本质就被占有了。[4]倾向就是允诺(Zuspruch)。这种允诺向我们的本质发出诉求,把我们呼唤到本质之中,并且使我们守持在这种本质中。真正说来,守持意味着守护。[5]可是,只有当我们从自身而来亲身保持那个守持我们的东西时,使我们守持在本质中的东西才能守持我们。当我们不让它脱出记忆时,我们就保持它了。记忆乃是思想之聚集。向何处聚集呢?向那个使我们守持在本质中的东西,因为它同时已经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思虑。何以这个守持我们的东西必须已经得到了思虑呢?因为它本来就是有待思虑的东西(das zu-Bedenkende)。如果它被思虑,那它就获得了思念。我们为它迎面送去思念(An-denken),因为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本质的允诺来加以喜欢。 惟当我们喜欢那个本身有待思虑的东西时,我们才能够思想。 为了进入这种思想之中,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就必须学习思想。什么是学习呢?人学习,是使他的有为和无为与那个向来从本质上被允诺给他的东西适应起来。我们学习思想,我们的做法就是去关注有待思虑的东西。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 1962年9月11—13日, 海德格尔在黑森林托特瑙堡主持了关于他的?时间与存在?演讲的研讨课,在讨论记录中可以读到这样的看法:?胡塞尔本人在《逻辑研究》中——主要是在第六研究中——已经接近了本真的存在问题,但他在当时的哲学气氛中无法将它坚持到底?(注:参见:海德格尔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 1988, S. 47. 以下简称:SD。)。 1973年9月6日,在海德格尔主持的弗莱堡采林根研讨课上,首先讨论的出发点问题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胡塞尔那里没有存在问题??(注:参见:海德格尔,Vier Seminare, Frankfurt a. M.1977, S. 111. 以下简称:VS。) 我们试图接着这里的问题思考下去。 在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存在论的意义上,不仅胡塞尔,而且整个在他之前的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黑格尔),应当说都从没有真正地接触到存在问题。(注:严格地说,海德格尔认为,希腊哲学并非没有接触到存在问题,而是从存在出发,逐渐偏离开存在,因此西方哲学的历史是遗忘存在的历史。勒维纳斯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阐释说,西方哲学史试图从存在出发去达到一个完整地包容存在的存在者——上帝。(参见:E.Levinas,Le Temps et l'Autre, Montpellier 1979, p.24)据此而论,在胡塞尔那里没有存在问题(即没有海德格尔式的存在问题),这实际上是不成为问题的。(注:胡塞尔本人当然具有他自己意义上的?存在问题?(参见拙著:Das Problem des Seinsglaubens in derPha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Ein Versuch mit ihm,Dissertation, Darmstadt, 1990).概括地说, 他将纯粹意识领域视作真正的存在(参见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 1卷第46节中的论述;也可参见海德格尔在《时间概念历史导引》第11节中对胡塞尔这个意义上的存在的四重定义:意识作为?内在的存在?、?绝对的存在?、?被给予的存在?和?纯粹的存在?);并且,胡塞尔在此意义上划分出他自己的?形式存在论?和?质料存在论?(对此可以参见《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的第153节,以及该书的整个第2、3两卷的论述)。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问题。) 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又可以说,胡塞尔曾经在《逻辑研究》中接近过本真的存在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要取决于对另外一个前问题的回答:海德格尔本人在存在问题上究竟从《逻辑研究》中获益多少?因为,如果对后一个的问题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将这两人的存在问题放在一起讨论。 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逻辑研究》——它曾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存在问题上的一个交会点吗?撇开海德格尔对《逻辑研究》作用的多次一般性强调不论(注:例如参见:海德格尔,GA 20, S.30 (海德格尔全集本均用简称:GA,不再引书名),Sein und Zeit, Tübingen1979,S.38(以下简称:SuZ),Unterwegs zur Sprache, Pflingen1990, S. 90—91(以下简称:US),以及其他各处。海德格尔多次将《逻辑研究》称作现象学的?突破性著作?和现象学的?基本书?(Grundbuch)。),在早期(1925年)的马堡讲座中,他确定有必要坚持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六研究,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所区分的两个真理概念和两个存在概念,因为?我们以后会提出关于存在意义的原则问题?(注:海德格尔,GA20,S.73.重点号为原作者所加。); 在后期《我的现象学之路》(1963年)一文中,他再次明确指出了《逻辑研究》在存在问题
海德格尔存在论基础上的技术观 摘要:作为一位活在20世纪的现代人,海德格尔与现代技术世界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隔膜,他不断的对技术进行追问,并认为造成当今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源并不是现代技术手段本身的优劣,而是由现代技术的本质一一座架这种解蔽方式所决定的,他对技术的批判是建立在他对“存在”问题的沉思之上的,本文主要从海德格尔存在论视域下来把握其技术批判理论,同时又反过来从技术批判理论着眼去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 关键字:海德格尔;座架;现代技术;存在论 Heidegger's theory of Technology on the base of Ontology Abstract:As a modern people who are live in the 20th century, Heidegger and modern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seem to have a natural diaphragm, he will continue to ask, and the causing of the human's existence predicament of root is not modern technology’s pros and cons, but the essence of modern technology is determined by the enframing ,this disclosing of the decision, his criticism of technology is established on his thinking of ontology, this paper mainly from Heidegger's ontology theory to grasp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in turn from the critique of technology theory with an eye to understand Heidegger's ontological thought. Key words:Heidegger;Enframing;Modern technology ;Ontology 引言 在这个世界图象的时代中,人类的生活被日益强大的现代技术所支配着。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存样态愈来愈丰富,活动的空间愈来愈广阔。现代人沉醉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种物质利益中,为技术的每一个成就而欢心鼓舞。殊不知,我们已成为技术的傀儡。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对近现代技术的批判上,他认为现代技术统治着人类的各个方面,已成了现代人面临的最高危险,他洞察到:现代性的根源恰恰存在于近现代世界里最为普遍而根本的技术现象里,他对技术的批判并不是对技术先现象的一种批判,而是针对技术的“本质”进行批判,在对传统的技术观进行追问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发现现代技术的本质已经深深地遮蔽着,这种遮蔽源于人类对“存在”的遗忘。终生沉浸于对“存在”问题的沉思之中的的海德格尔,在一种对时代早己遗忘的东西的眷恋之情的激荡下开始了对技术本质的追问。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本真?时间现象学 黑尔德 自从胡塞尔第一次将现象学引上道路并且海德格尔第一次对现象学进行彻底改造以来,时间便处在他们的思考中心。与对原初经验的现象学寻求相符,这两位思想家在时间理解上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区分:在所有哲学之前为我们所日常熟悉了的那种时间与一个原初地经验到的时间相对峙,海德格尔在他后期的报告?时间与存在?(1962年)中将后者称之为?本真的时间?。在?转向?后的思想中,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用?本真?(eigentlich)一词来标识这样一种?实事?(Sache),即某种构成现象学的一个根本的争执区域的东西,它在那些对它而言原初是?本己的?东西中表明自身。[①] 据此,?本真时间?应当被理解为如其在对它来说是本己的东西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时间。在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本真?这个形容词已经具有了这个基本含义,但它原发地所涉及的?实事?在当时就是人的此在;被标识为?本真?的是那种此在在其中?决断地?接受它的?必死性?(Sterblichkeit)的生存方式。尽管海德格尔自三十年代以后放弃了对?本真?形容词的这种生存论分析的使用。但即使在?转向?之后它也仍然以隐蔽的方式在他的思想中继续起作用。我在后面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无论是在《存在与时间》中、还是在以后的?时间与存在?中,?非本真的时间?都在于:时间对我们显现为各个当下、各个现在的次序(Folge)。这些?现在?可以在某些发生事情的时段(Phasen)上——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在?各个运动?上——被计数(anz?hlen),通过这种方式,对时间的自然科学理解也成为可能。自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以来,流行的——至少在西方文化中——便是这种把时间视为现在次序的观点,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这种时间观称作?庸俗的时间理解?。由于现在次序构成一个固定的形式,我们在其中遭遇到所有在时间中个体可定位的客体,因此这种时间在胡塞尔那里叫做?客观时间?。在由爱迪?施泰因所汇总的哥廷根时期的文字中,他把客观时间与?内意识?相对峙,在三十年代的后期手稿中,他把客观时间与?活的当下?相对峙。由于胡塞尔以此来标识时间原初在对它而言是本己的东西中被经验的方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他那里也有本真的和非本真的时间
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 “存在在意识中的消融”是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思想的核心。胡塞尔认为,我们所能看到的事物只是“自在的对象”并不是“意向对象”,但是能被我们直观把握的对象或者说“明白清楚的感知”的对象是我们的意识中构造自身的,超越人的内在意识或者说在人的内在意识之外而存在的客体自身是不可能获得明见性的。因此,胡塞尔从思维的自明性出发,主张对一切事物的存在乃至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存在问题作“悬搁判断”或者放到括号中去,存而不论,来追求哲学的绝对自明的开端。通过现象学的还原,给所有的超越之物贴上无效的标志,使“存在”回复到“意识”中,对象在意识中构造自身,回到纯粹现象本身,即“回到事实本身”。 关键词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意义 一、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内容 如何认识这种既非物质又非感性经验的“自我意识”呢? 胡塞尔认为,这既不能采用传统哲学的方法,也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应采用他所特有的现象学的方法,即现象学还原法。所谓“现象学的还原”,就是要从自然科学的认识还原到思维的直观认识,从超越的认识还原到内在的认识,亦即还原到纯粹的主体性上去。用胡塞尔自己的话说,“现象学的还原就是说: 所有超越之物( 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东西) 都必须给以无效的标志,即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不能作为存在和有效性本身,至多只能作为有效性现象”。胡塞尔谈到过多种还原,但主要有两种: 先验还原和本质还原。他主张通过先验还原引导人们进入哲学的观点,通过本质还原引导人们进入本质的领域,从而使人们领会或把握先验的“纯粹意识”。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分先后。 (一)先验还原 先验还原又称悬置( epoche) 或括号法。“悬置”这个术语来源于古希腊怀疑论哲学家,意思指中止判断或将判断搁置起来,对一切给予的东西打上可疑的记号这一点同笛卡尔的“我在怀疑”有异曲同工之处。胡塞尔借用这个术语来表示现象学对经验的事实世界采取的一个根本立场。例如在计算一道数学题时,
初探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 论文导读: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籍西方思想家之一,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海德格尔一直深思科学技术并深切的关注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技术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劳动手段,是一种生产力。关键词:海德格尔,技术的本质,集置,现代技术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籍西方思想家之一,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海德格尔一直深思科学技术并深切的关注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众所周知,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技术作为一股强大的统治力量的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的历史,人们一方面从技术发展中受益,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批评,对于形成当代环境保护理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分析 1.1传统观念中的技术本质“技术术不同于技术的之本质,如果我们要寻求树的本质,我们一定会发觉,那个贯穿并且支配着每一棵树之为树的东西,本身并不是一棵树,一棵可以在平常的树木中间找到的树”[1]因此在追问技术本质中,技术的本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当我们仅仅追问及表象和技术的因素,那么我们将会被技术所束缚,什么也就看不出来了。按照最为原始、古老的看法,“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我们在追问技术,尽人皆知对我们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其一曰:技术是何目的的手段。论文参考网。其二曰:技术是人的行为。论文参考网。”[2],海德格尔把传统的观念称之为“流行观念”,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流行观念”不过是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从某种角度讲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没有准确的解释技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要在眼前讨论的东西中确定某个合适的东西,但是,这种确定要成为正确的,绝不需要揭示眼前讨论的东西的本质。”[3] 1.2技术不仅是一种手段了,而成为一种解蔽的方式单纯正确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会把我们带入一种自由的关系中,这样我们才会揭示技术的本质所涉及的东西,既然要从技术的工具性规定出发来寻求答案,那么工具性的东西本身是什么?我们必须通过对技术的工具性来寻找技术的本质,工具是人们为了获得某物对其发生所用的手段,这就涉及到因果性的问题了。几百年来,哲学一直教导我们说,有四种原因:一是质料因,二是形式因,三是动力因,四是效果因,海德格尔认为,因果性与起作用是毫无关系的,我们所说的因果性只不过是招致另一种方式的东西,四因乃是联系在一起的招致方式,招致具有进入到达的启动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招致就是引发。海德格尔借助柏拉图《会饮篇》中的一句话告诉了我们招致带了什么?“对于总是从来不在场者向在场者过渡和发生的东西来说,每一种引发都是产出”[4],产出又是如何发生地呢?产出是从遮蔽状态而来进入到无比状态中的,只是因为遮蔽者进入无蔽领域,产出才会发生。即产出就是基于解蔽。从追问技术的本质,到技术的工具性规定,然后到因果性,又牵涉到招致方式,最后到解蔽,那么这中间有什么关系呢?海德格尔认为“关系大矣”[5]首先招致的四种方式是因果性的四种原因,四原因中的质料因与目的因中含有工具性的东西,工具性的东西被看作是技术的最基本的特征,由招致到达产出,就来到解蔽,那么技术是工具,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