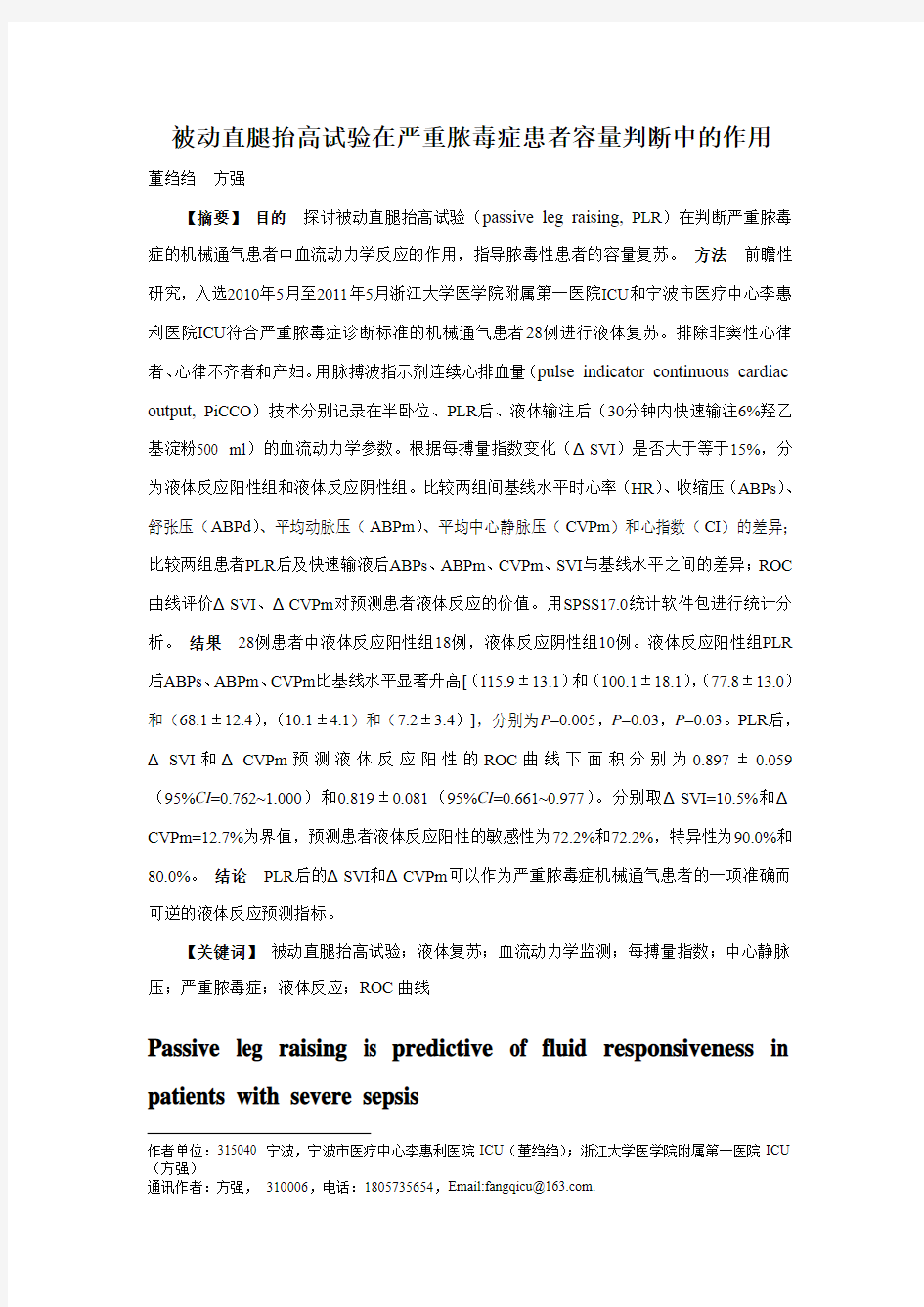

被动直腿抬高试验在严重脓毒症患者容量判断中的作用
董绉绉方强
【摘要】目的探讨被动直腿抬高试验(passive leg raising, PLR)在判断严重脓毒症的机械通气患者中血流动力学反应的作用,指导脓毒性患者的容量复苏。方法前瞻性研究,入选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ICU和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ICU符合严重脓毒症诊断标准的机械通气患者28例进行液体复苏。排除非窦性心律者、心律不齐者和产妇。用脉搏波指示剂连续心排血量(pulse indicator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 PiCCO)技术分别记录在半卧位、PLR后、液体输注后(30分钟内快速输注6%羟乙基淀粉500 ml)的血流动力学参数。根据每搏量指数变化(ΔSVI)是否大于等于15%,分为液体反应阳性组和液体反应阴性组。比较两组间基线水平时心率(HR)、收缩压(ABPs)、舒张压(ABPd)、平均动脉压(ABPm)、平均中心静脉压(CVPm)和心指数(CI)的差异;比较两组患者PLR后及快速输液后ABPs、ABPm、CVPm、SVI与基线水平之间的差异;ROC 曲线评价ΔSVI、ΔCVPm对预测患者液体反应的价值。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8例患者中液体反应阳性组18例,液体反应阴性组10例。液体反应阳性组PLR 后ABPs、ABPm、CVPm比基线水平显著升高[(115.9±13.1)和(100.1±18.1),(77.8±13.0)和(68.1±12.4),(10.1±4.1)和(7.2±3.4)],分别为P=0.005,P=0.03,P=0.03。PLR后,ΔSVI和ΔCVPm预测液体反应阳性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97±0.059(95%CI=0.762~1.000)和0.819±0.081(95%CI=0.661~0.977)。分别取ΔSVI=10.5%和ΔCVPm=12.7%为界值,预测患者液体反应阳性的敏感性为72.2%和72.2%,特异性为90.0%和80.0%。结论PLR后的ΔSVI和ΔCVPm可以作为严重脓毒症机械通气患者的一项准确而可逆的液体反应预测指标。
【关键词】被动直腿抬高试验;液体复苏;血流动力学监测;每搏量指数;中心静脉压;严重脓毒症;液体反应;ROC曲线
Passive leg raising is predictive of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作者单位:315040 宁波,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ICU(董绉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ICU (方强)
通讯作者:方强,310006,电话:1805735654,Email:fangqicu@https://www.doczj.com/doc/871101716.html,.
DONG Zhou-zhou, FANG Qiang*. *Intensive care unit,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Zhejiang,310006,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FANG qiang, 310006,Tel: 1805735654, Email:fangqicu@https://www.doczj.com/doc/871101716.html,.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value of passive leg raising as an indicator of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k to guide volume resuscitation.Method This was a prospective study. Twenty eight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admitted in ICU of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Ningbo Medical Treatment Center Lihuili Hospital from May 2010 to May 2011, were collected for volume resuscitation. Non-sinus rhythm or arrhythmia ones, parturients were excluded.Hemodynamic indices of the patients were obtained in a semi-recumbent position, then after passive leg raising, and after volume expansion (500 mL 6% hydroxyethyl starch infusion within 30 mins) by the technique of pulse indicator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 (PiCCO) system. The volume resuscitation were result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in stroke volume index (ΔSVI) over 15%. Heart rate (HR), systolic artery blood pressure (ABPs), diastolic artery blood pressure (ABPd), mean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ABPm), mean 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m) and cardiac index (CI)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The changes of ABPs, ABPm, CVPm, SVI after PLR and after fluid resuscitation were compared with the indices at the baseline. The ROC curve was drawn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ΔSVI and change of CVPm (ΔCVPm) in predicting volume responsiveness. SPSS l7.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 Results Among twenty eight patient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eighteen were responders and ten were non-responders. After PLR among the responders, some hemodynamic variables including (ABPs, ABPm and CVPm)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 (100.1±18.1) and (115.9±13.1), P=0.005; (68.1±12.4) and (77.8±13.0), P=0.03; (7.2±3.4) and (10.1±4.1), P=0.03]. After PLR, the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the ROC curve of ΔSVI and ΔCVPm to predict the responsiveness after fluid resuscitation were 0.897±0.059 (95%CI 0.762~1.000) and 0.819±0.081 (95%CI0.661~0.977) when the cut-off levels of ΔSVI and ΔCVPm were 10.5% and 12.7%, the sensitivities were 72.2% and 72.2%, the specificities were 90% and 80%. Conclusions Changes in ΔSVI and ΔCVPm induced by passive leg raising
are accurate indices for predicting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Key words] Passive leg raising; V olume resuscitation; Hemodynamic monitoring; Stroke volume index; Central venous pressure; Severe sepsis; Fluid responsiveness; ROC curve
容量评估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危重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严重脓毒症早期,包括液体复苏在内的集束化治疗策略可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1,2],但盲目的液体复苏会加重肺水肿,甚至引起呼吸衰竭、延长机械通气时间,增高腹内压,降低生存率[3]。判断危重患者是否需要液体负荷,主要通过评估患者的每搏量指数(stroke volume index, SVI)能否随着液体输入而增加。被动直腿抬高试验(passive leg raising, PLR)简便、安全,堪比可逆的自身容量负荷试验。我们以需要机械通气的严重脓毒症患者为对象进行前瞻性研究,采用脉搏波指示剂连续心排血量(pulse indicator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 PICCO)技术作为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先后对受试者进行PLR和液体负荷试验,分析相应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为评估PLR在容量判定中的临床价值提供理论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选取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ICU和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ICU进行机械通气的严重脓毒症患者共28例,其中男23例,女5例,年龄36~86岁,平均(59.7±14.4)岁。严重脓毒症的诊断符合2001年危重病医学会/欧洲危重病医学会/美国胸科医师协会(SCCM/ESICM/ACCP)对严重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的诊断标准[4],并同时具备以下组织灌注不足临床表现中的至少一条[5]:①收缩压<90 mmHg或既往有高血压病的患者血压下降>50 mmHg或需要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多巴胺>5 ug/kg/min或去甲肾上腺素);②尿量<0.5 ml/kg/hr至少持续2小时;③窦性心动过速,心率>100次/min;④皮肤出现花斑。排除非窦性心律者、心律不齐者和产妇。所有患者或家属知晓病情并签署针对临床诊治的知情同意书。
1.2 监测指标及方法:①经右颈内静脉穿刺置入双腔静脉导管(Arrow公司,美国)监测中心静脉压(CVP)。②经股动脉置入PiCCO导管(PV2014L13,Pulsion Medical Systems,德国),连接到带PiCCO模块的Philips IntelliVue MP50/70心电监护仪上。采用脉搏曲线分析及动脉热稀释法监测心输出量。③热稀释法操作步骤:自静脉导管快速(5 s)注入温度低于8℃的生理盐水10~15 ml,至少3次,取3次变异量<10%的数值取平均值。④实验过程中给
予患者充分镇静(Ramsay评分4分),呼吸机设置为容量控制通气(CMV)模式,潮气量10 ml /kg,吸入氧浓度0.50,吸呼比1:2,呼气末正压(PEEP)5 cmH2O(1 cmH2O=0.098 kPa)。在实验过程中以上参数保持不变。
1.3 试验步骤:①受试者禁食2小时,取45度半卧位(病床角度显示器显示),并保持2分钟,用热稀释法测定并记录各项血流动力学参数作为基线。②受试者平卧位,将双腿抬高45度(三角尺测量角度),保持该体位2分钟,热稀释法测定并记录参数。③取步骤1的体位,并保持2分钟。④保持步骤1体位,在30分钟内快速输注6%羟乙基淀粉(万汶,费森尤斯卡比公司)500 ml,热稀释法测定并记录以上参数,见图1。输液后ΔSVI≥15%定义为液体反应阳性[6]。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显著性检验水平为0.05。血流动力学参数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两变量之间相关性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各指标预测液体反应的准确性,以曲线下面积(AUC)和95%可信区间(95%CI)表示,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资料:28例严重脓毒症患者的感染来源:重症肺炎(21例,75.0%)、血行性感染(6例,21.4%)和腹腔感染(1例,
3.6%)。其中液体反应阳性组18例,液体反应阴性组10例,两组间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MI)、ICU住院天数、机械通气天数、APACHEII 评分、28天存活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2.2 液体反应阳性组基线水平的心率(HR)、收缩压(ABPs)、舒张压(ABPd)、平均动脉压(ABPm)、平均中心静脉压(CVPm)和心指数(CI)明显低于液体反应阴性组(P<0.05),见表1。
2.3 液体反应阳性组PLR后ABPs、ABPm、CVPm、SVI较基线水平显著升高(P<0.05或P<0.01);快速输液后ABPs、ABPd、ABPm、CVPm、SVI较基线水平显著升高(P<0.05或P<0.01)。液体反应阴性组PLR后及快速输液后各项血流动力学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取PLR后ΔSVI=10.5%为界值,预测患者液体反应阳性的敏感性为72.2%,特异性为90.0%。AUC(x±S x)=0.897±0.059,(95%CI 0.762,1.000),见图2。
2.5 取PLR后ΔCVPm=12.7%为界值,预测患者液体反应阳性的敏感性为72.2%,特异
性为80.0%。AUC(x±S x)=0.819±0.081,(95%CI 0.661,0.977),见图3。
3 讨论
严重脓毒症早期,由于血管床的扩张,导致有效循环血容量的不足。根据Frank-Starling 定律,前负荷在生理范围内与心室收缩作功成比例,所以容量复苏可以维持有效循环血容量(包括静脉容量和心脏腔内的容量),保证动脉血压,降低全身血管阻力,以改善组织灌注,对维持循环稳定,保持组织器官的灌注十分重要[7]。因为血容量关系到组织的氧输送,所以对有临床症状的血容量不足的患者快速输注晶体或者胶体已经成为常规的治疗措施[8]。然而,当增加的前负荷位于Starling曲线的平坦部位时,或合并心功能不全、心功能曲线左移时,心脏储备功能下降,过度补液非但不能有效增加心排血量,还会导致肺水肿及组织间质水肿,影响氧合及组织细胞的供氧,使病情进一步恶化。因此,扩容后左室SVI能否随之增加,是临床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容量复苏的标准,但是血容量状况却很难通过床旁的静态指标来判定[9]。
PLR可以让150~200 ml的血液快速地从下肢静脉回流至中心血管[10],由于心脏前负荷增加,SVI随之增加;当双腿放回水平位时,这一过程迅速逆转。PLR常在休克患者的初始干预中使用,Steven WT等认为,PLR前后SVI的测定可以预测患者液体负荷后的血流动力学反应[11]。PLR在ΔSVI上起的作用取决于心脏前负荷的储备情况[12],本研究液体反应阳性组在基线水平时的ABPs、ABPd、ABPm、CVPm均低于液体反应阴性组(P<0.05),提示液体反应阳性组PLR前的心脏前负荷储备明显低于液体反应阴性组。而液体反应阳性组PLR后ABPs、ABPm、CVPm、SVI均有显著升高(P<0.05),和输液后相符;液体反应阴性组PLR 后和输液后以上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证实PLR对患者是否需要液体负荷具有很好的预测价值。Lamia等指出[13,14],PLR可以很好地预测非机械通气患者对快速输液的反应,本研究证实PLR后ΔSVI和ΔCVPm也可以准确地预测机械通气的严重脓毒症患者对快速输液的反应。因此,PLR引起的容量可逆改变,堪比可逆的自身容量负荷试验,且适用范围广,可以用来评估血流动力学变化[12]。
有些学者认为中心静脉压(CVP)不能作为临床液体管理的依据[15],那可能是因为在机械通气、心室顺应性下降、胸内压力和腹腔压力变化等情况下,CVP、肺动脉嵌顿压(PAWP)等并不能准确地反应心脏前负荷的变化[16]。加之安全性方面的考虑,如今在北美的许多ICU 中,Swan-Ganz导管的使用已经越来越少[17]。但在本研究中,PLR后CVPm的动态变化却能较好地预测液体反应。这可能是因为在胸、腹内压及心室顺应性等外界条件几近恒定的情况
下进行PLR,所引起CVPm的动态变化比静态CVP指标能更好地反应患者的前负荷情况。所以,PLR后CVPm的动态变化为缺乏血流动力学监测条件的非ICU病房和基层医院的临床容量判断提供了新的方法。
Sebastien P等[8]认为用经食道超声测定SVI比较准确,并用该法对非气管插管的严重脓毒症患者进行了研究,认为取PLR后ΔSVI=10.0%为界值时,预测患者快速输液反应阳性的敏感性为86.0%,特异性为90.0%。而PiCCO因其操作简便、相对安全,如今被广泛应用于危重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监测,本实验用PiCCO对气管插管的严重脓毒症患者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与之相符的结果,证实PiCCO与经食道超声一样也可以准确地测定患者的SVI。由于经食道超声无法对气管插管的患者进行测定,所以本研究对需要进行机械通气的严重脓毒症患者的SVI测定以及液体反应预测提供了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PLR简便、有效、安全,联合PiCCO监测为临床医生在严重脓毒症患者的容量判断问题上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Micek ST, Roubinian N, Heuring T, et al. Before-after study of a standardized hospital order
set for the management of septic shock [J]. Crit Care Med, 2006, 34(11): 2707-2713.
[2]Rivers E, Nguyen B, Havstad S, et al. Early goal-directed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J]. N Engl J Med, 2001, 345(19): 1368-1377.
[3]Wiedemann HP, Wheeler AP, Bernard GR, et al. Comparison of two fluid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acute lung injury [J]. N Engl J Med, 2006, 354(24): 2564-2575.
[4]Levy MM, Fink MP, Marshall JC, et a1. 2001 SCCM / ESICM / ACCP/ATS/SIS
International Sepsis Definitions Conference [J]. Crit Care Med, 2003, 31(4): 1250-1256. [5]Monnet X, Rienzo M, Osman D, et al. Passive leg raising predicts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the
critically ill [J]. Crit Care Med, 2006, 34(5): 1402-1407.
[6]Soubrier S, Saulnier F, Hubert H, et al. Can dynamic indicators help the prediction of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spontaneously breathing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J]. Intensive Care Med,
2007, 33(7): 1117–1124.
[7]刘宁、顾勤. 全心舒张末期容积预测脓毒性休克腋体反应性的意义[J]. 中华急诊医学杂
志, 2008, 17(2): 137-140.
[8]Sebastien P, Fabienne S, Florent D,et al. Passive leg raising is predictive of fluid
responsiveness in spontaneously breathing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or acute pancreatitis [J].Crit Care Med, 2010, 38(3): 819-825.
[9]Antonelli M, Levy M, Andrews PJ, et al. Hemodynamic monitoring in shock and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Conference, Paris, France, 27-28 April 2006 [J]. Intensive Care Med, 2007, 33(4): 575-590.
[10]Jabot J, Teboul JL, Richard C, et al. Passive leg raising for predicting fluid responsiveness:
importance of the postural change [J]. Intensive Care Med, 2009,35(1): 85-90.
[11]Steven WT, Marin HK and Warren I. Non-invasive stroke volume measurement and passive
leg raising predict volume responsiveness in medical ICU patients: an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J]. Critical Care, 2009, 13(4): 111-119.
[12]De Hert SG, Robert D, Cromheecke S, et al. Evaluation of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anesthetized patients using femoral artery dP/dt (max) [J]. J Cardiothorac Vascanesth, 2006, 20(3): 325-330.
[13]Lamia B, Ochagavia A, Monnet X, et al. Echocardiographic prediction of volume
responsivenes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ly breathing activity [J]. Intensive Care Med, 2007, 33(7): 1125-1132.
[14]Maizel J, Airapetian N, Lorne E, et al. Diagnosis of central hypovolemia by using passive leg
raising [J].Intensive Care Med, 2007, 33(7): 1133-1138.
[15]Osman D, Ridel C, Ray P, et al. Cardiac filling pressures are not appropriate to predict
hemodynamic response to volume challenge [J]. Crit Care Med, 2007, 35(1): 64-68.
[16]龚仕金、陈进、李莉等. 连续右心容量监测指导感染性休克的液体复苏[J]. 中华急诊医
学杂志, 2009, 18(11): 1207-1210.
[17]Harvey S, Harrison DA, Singer M, et al. Assessment of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pulmonary artery catheters in management of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PAC-Man) [J].
Lancet, 2005, 366(9484): 472-477.
表1 液体反应阳性组和阴性组在步骤1时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Table 1 The changes of hemodynamic parameters at stage one in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液体反应阳性组液体反应阴性组P值
HR(次/分)88.7±26.4 111.8±17.9 0.02* ABPs(mmHg)100.1±18.1 118.6±23.7 0.03* ABPd(mmHg)53.0±11.8 64.8±10.7 0.014* ABPm(mmHg)68.1±12.4 81.9±14.4 0.02* CVPm(mmHg)7.2±3.4 11.9±4.0 0.003** SVI(ml/m2)33.9±8.3 35.3±13.3 0.72
CI(L/min/m2) 2.9±1.0 3.8±1.2 0.04* SVRI(DSm2/cm5) 1767.8±560.1 1611.8±598.1 0.5 EVLWI(ml/kg) 10.2±5.9 8.3±4.8 0.4 ITBVI(ml/m2) 913.1±196.4 841.8±153.9 0.33
**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
表2 液体反应阳性组和阴性组在实验过程中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
Table 2. The changes of hemodynamic parameter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study in
responders and nonresponders
步骤1 步骤2
P值
(2,1)步骤4
P值
(4,1)
P值
(4,2)
液体反应阳性组
HR(次/分)88.7±26.4 87.4±25.6 0.89 85.7±20.4 0.71 0.82 ABPs(mmHg)100.1±18.1 115.9±13.1 0.005** 125.8±7.8 0** 0.009** ABPd(mmHg)53.0±11.8 59.9±13.0 0.1 63.7±12.7 0.013* 0.39 ABPm(mmHg)68.1±12.4 77.8±13.0 0.03* 83.7±11.6 0** 0.16 CVPm(mmHg)7.2±3.4 10.1±4.1 0.03* 10.7±3.3 0.004** 0.62 SVI(ml/m2)33.9±8.3 39.6±9.6 0.049* 43.8±12.4 0.008** 0.3
CI(L/min/m2) 2.9±1.0 3.4±1.0 0.2 3.6±1.2 0.052 0.44
SVRI (DSm2/cm5) 1767.8±560.1 1699.8±480.5 0.7 1721.8±543.2 0.8 0.9 EVLWI(ml/kg) 10.2±5.9 9.9±6.1 0.89 11.0±5.7 0.69 0.6 ITBVI(ml/m2) 913.1±196.4 1031.7±209.1 0.09 1051.2±200.4 0.044* 0.78
液体反应阴性组
HR(次/分)111.8±17.9 114.9±16.3 0.69 110.6±17.0 0.88 0.57 ABPs(mmHg)118.6±23.7 124.7±25.8 0.59 124.7±24.2 0.58 1 ABPd(mmHg)64.8±10.7 70.3±14.7 0.35 68.8±14.6 0.49 0.82 ABPm(mmHg)81.9±14.4 87.6±16.6 0.42 86.7±15.4 0.48 0.9 CVPm(mmHg)11.9±4.0 13.3±5.1 0.5 14.2±3.7 0.2 0.65 SVI(ml/m2)35.3±13.3 36.1±12.7 0.89 37.7±13.3 0.69 0.79
CI(L/min/m2) 3.8±1.2 4.1±1.3 0.67 4.1±1.5 0.63 0.93
SVRI(DSm2/cm5) 1611.8±598.1 1606.7±600.0 0.99 1561.6±547.8 0.85 0.86 EVLWI(ml/kg) 8.3±4.8 7.8±3.6 0.76 8.2±3.7 0.93 0.8 ITBVI(ml/m2) 841.8±153.9 877.6±163.9 0.62 888.0±153.2 0.51 0.89
**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
P值(2,1)表示步骤2和步骤1两者的P值。
P值(4,1)表示步骤4和步骤1两者的P值。
P值(4,2)表示步骤4和步骤2两者的P值。
图1 试验流程图 Fig1 Test flow chart
图2 PLR 后ΔSVI 对液体反应预测的ROC 曲线
Fig2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for predicting response to volume
expansion in ΔSVI induced by passive leg raising.
步骤1 45度半卧位保持2分钟, 记录参数。 步骤2 平卧位,双腿抬高45度保持2分钟, 记录参数。
步骤3 复原步骤1体位,保持2分钟。
步骤4
保持步骤1体位,在30分钟内快速输液,记录参数。
图3 PLR后ΔCVPm对液体反应预测的ROC曲线
Fig3 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for predicting response to volume expansion in ΔCVPm induced by passive leg raising.
长期以来,由于临床医师对于烧(创)伤、外科手术等应激打击造成机体免疫功能失调的关键环节及其在脓毒症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临床上缺乏切实可行的免疫状态监测方法和免疫调理策略。新近的研究结果显示:机体免疫功能紊乱参与了脓毒症的病理生理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严重感染诱发的全身性炎症反应和多器官损害的结局。 1 外科脓毒症的免疫功能改变及其状态监测 严重烧(创)伤、外科大手术后随着炎症反应的加剧,机体自身存在着针对炎症刺激的有效负反馈调控机制,此时机体所表现出来的并非主要是炎症介质对机体的损害,宿主免疫调节失衡,特别是机体抗感染免疫防御能力严重受到抑制,成为病情进一步恶化的主要原因。在此过程中,不同免疫细胞及其功能亚群发挥着重要调控效应。 1.1 中性粒细胞 中性粒细胞是人体抵御外来微生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是天然免疫系统中重要的效应细胞。严重脓毒症状态下中性粒细胞迁移能力减弱及凋亡延迟,导致细菌清除率下降,感染部位的损伤程度得不到有效缓解,加剧了脓毒症病程的发展。中性粒细胞迁移能力障碍促进了腹腔渗出液及血液中细菌数量的增多,伴随组织损伤和系统性炎症反应。 这样通过测定表达调理素结合受体的中性粒细胞数量及中性粒细胞对吞入异物的杀灭能力有助于判断机体的免疫功能状况。新近的研究结果显示:中性粒细胞 可分泌大量细胞因子包括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IL-10,并在内毒素血症患者外周血中观察到成熟的CD16high hCD621ow 中性粒细胞可抑制T 淋巴细胞增殖,同时在部分严重创伤患者体内也发现这种免疫抑制性中性粒细胞。 因此,中性粒细胞作为重要的天然免疫反应细胞,其募集和迁移功能障碍严重影响外科脓毒症的发展与结局,密切监测其病理生理变化将有助于脓毒症的早期识别及干预治疗。 1.2 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作为机体免疫反应中的抗感染细胞及关键抗原提呈细胞,在脓毒症的免疫调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脓毒症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除存在T 淋巴细 胞的大量凋亡外,巨噬细胞亦出现明显凋亡。学术界已明确:巨噬细胞在启动、维持宿主免疫反应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大量的凋亡将导致脓毒症及多器官损害。
2020中国脓毒症早期预防与阻断急诊专家共识(完整版) 脓毒症是目前医学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与挑战,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各个领域对脓毒症的研究探索越来越深入,尽管多年来国际上对脓毒症采用积极的“拯救”措施,但是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根据目前国际指南对于脓毒症定义的更新,脓毒症被定义为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进而导致循环功能障碍及器官功能损害。感染是引发脓毒症的最初源头,而从感染发展到脓毒症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其中包括病原体的侵入、细胞因子的释放、毛细血管渗漏、微循环功能障碍等,最终导致器官代谢紊乱和功能衰竭。 在目前国际采用的脓毒症Sepsis 3.0 的指南推荐中,以感染+SOFA 评分≥2分为脓毒症诊断标准,而应对脓毒症则更多侧重在器官功能的“拯救”治疗上。经过近20年的努力,“拯救脓毒症运动”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急诊医学作为急重症的前沿学科,能够最早收治急性感染患者。如果能够在感染早期从人群特点、感染病原体和部位、病情严重程度等方面来预测脓毒症发生的可能性,通过细胞因子检测及时发现炎症风暴,利用有效的临床评分系统对患者进行评估,对脓毒症高危患者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治疗手段防止和阻断感染向脓毒症发展的进程,将有可能大大降低急性感染患者的脓毒症发病率和病死率。
基于此,中国急诊医学专家提出“预防与阻断”脓毒症的概念,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预防脓毒症行动(Preventing Sepsis Campaign in China,PSCC)”,提出在“脓毒症前期”以及“围脓毒症期”开展针对性的诊断、检查和处理,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降低脓毒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的“三早两降”,为急性重症感染患者的诊治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本共识由急诊医学领域的4个学(协)会和5个相关杂志社共同倡导、探讨、撰写,由来自急诊医学、重症医学、感染病学、药学及检验医学等专业学科的40余名专家多次讨论形成。共识内容包括急性感染患者的确定识别、抗感染治疗、脓毒症高危患者的排查筛查、炎症风暴的发现和应对、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和凝血功能的调控、液体支持方案及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等,不仅总结归纳了临床常用的西医诊断治疗措施,也将祖国医学在脓毒症防治中的优势融入共识,期望能为临床医生提供一个全面的诊疗参考,为降低感染患者发展为脓毒症提供可靠的诊疗依据。 [关键词] 脓毒症;预防;感染;细胞因子;器官功能 脓毒症(sepsis) 是感染引起宿主反应失调, 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损害的症候群, 是一个高病死率的临床综合征。脓毒症不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也给医疗卫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有学者对1979
脓毒症相关性脑病 脓毒症相关性脑病(Sepsis-associated encephalopathy, SAE)SAE 是指非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脓毒症所致的弥漫性脑功能障碍, 病原学特征以肠杆菌(如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非发酵菌(如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为主。 1. 与非 SAE 脓毒症患者相比,SAE 病情更为严重:APACHE II 评分和 SOFA 评分显著增加,住院时间和需机械通气时间更长; 2. 与非 SAE 脓毒症患者相比,SAE 死亡风险显著增加:根据一项回顾性研究,SAE 患者的 28 天死亡风险和 180 天死亡风险均显著增加; 3. 临床研究提示,SAE 预后易出现远期认知功能障碍:约 70% 患者出院时伴有神经认知障碍,约 45% 患者 1 年后症状仍未消失。 SAE 的发病机制与影响因素 脓毒症相关的脑部病理改变包括脑缺血、脑出血、脓肿和进行性多灶性坏死性白质脑病。导致 SAE 脑部病理改变的原因错综复杂,目前主流认同的发病机制主要分为两部分: 1. 脓毒症导致血脑屏障障碍,引发炎症反应氧化应激,进一步导致中枢神经递质传递异常,引起脑灌注与血液微循环障碍,这是导致 SAE 发生的核心机制; 2. 另一方面不适用的抗菌药物等间接因素导致的神经递质失衡同样影响 SAE 的发生。脓毒症患者常伴随发生多个器官系统,特别
是神经系统的器官障碍,间接加重 SAE 发生风险。一项回顾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脓毒症患者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概率高达 48.9%,仅次于心脏功能障碍。 影响 SAE 病程的因素主要包括: 1. 代谢障碍如急性肾损伤、肝功能不全、葡萄糖稳态受损等; 2. 药物因素,苯二氮卓类、5- 羟色胺类药物以及抗胆碱类等多种药物通过影响γ- 氨基丁酸(GABA)受体阻滞,影响 SAE 发生; 3. 当发生脑血流量不足、低血压、低氧血症等灌注异常时,可能导致脑组织缺氧和脑代谢异常。 当前 SAE 的治疗方案 全身性抗感染是 SAE 治疗的首要目标,同时结合辅助支持性治疗。由于 SAE 并非直接由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导致,治疗重点仍然是对系统性感染、脓毒症和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SIRS)恰当治疗。在治疗 SAE 时,首先要进行原发病的及时应对,早期足量的抗菌药物治疗,充足的液体复苏以及手术治疗是 SAE 的基础方案。药物治疗的主体是抗生素,在没有明确感染源或致病菌时,尽早开始采用广谱抗菌药物初始治疗,一旦完成标本采集确定致病微生物,根据药敏结果,选择窄谱抗菌药物进行降阶梯治疗,同时要结合当地抗菌药物耐药模式。 当前 SAE 的治疗方案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抗菌药物治疗后效果不理想,不同类型抗菌药物发生神经系统相关的副作用(AAE)风险具
第三章细菌感染 第十三节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 学习要求: 了解脓毒症常见病原体;熟悉脓毒症的诊断;掌握脓毒症的治疗;熟悉脓毒症休克的发病机制;熟悉脓毒症休克的诊断依据;掌握脓毒症休克的治疗。建立对临床出现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的患者进行相应的针对性检查项目并做出诊断。 脓毒症(sepsis)是指由任何病原体(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SIRS是指感染或非感染性损害因子引起的全身过度炎症反应及其临床表现(见表1)。 脓毒症临床表现为寒战、高热、呼吸急促、心动过速、皮疹、肝脾大及白细胞升高等。细菌栓子可随血流出现迁徙性炎症,形成多发脓肿。严重者出现脓毒性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弥散性血管内溶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C)、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及多脏器衰竭(multiple organ failure,MOF)。 脓毒性休克(septic shock),又称感染性休克。是由微生物及其毒素等产物直接 或间接引起急性微循环灌注不足,导致组织损害,无法维持正常代谢和功能,甚至造成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危重综合征。 链接:需要强调的是,有些传染病,如鼠疫、炭疽、伤寒等病程中的败血症期或型,不包括在脓毒症范围内。目前,临床文献越来越多地以SIRS取代毒血症,以脓毒症取代败血症等称谓。 表1 SIRS的诊断 诊断依据 1.体温>38℃或<36℃ 2.心率>90次/分 3.呼吸>20次/分或过度通气,或PaCO2<32mmHg 4.血白细胞计数>12×109/L或<4×109/L,或白细胞总数虽然正常,但中性杆状核粒细 胞>10% 。 除运动、贫血、失血等生理及病理因素影响外,上述指标≥2项,临床即可诊断。
脓毒症与感染性休克第三版国际共识定义(中文翻译版) 重要性:脓毒症与感染性休克的定义最后一次修订是在2001年。考虑到脓毒 症病理学(器官功能、形态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免疫学以及循环的变化)、管理以及流行病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因此需要对该定义进行复审。 目的:根据需要对脓毒症与感染性休克的定义进行更新和评估。 过程:危重病医学学会与欧洲重症监护医学学会召集19名脓毒症病理学、临床 试验以及流行病学方面的专家组成工作组。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的定义与临床诊断标准通过会议、Delphi程序、电子健康记录数据库分析、以及投票产生,然后送至国际专业协会,要求(在致谢中列出的31个协会)同行进行评审与认可。 来自综合证据分析的关键发现:以前的定义的局限性包括过度关注炎症反 应、认为脓毒症遵循一个从严重脓毒症发展至休克的连续性误导模式、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诊断标准的特异性与敏感性不足。目前已有多个术语用于脓毒症、感染性休克以及器官功能障碍的定义,导致在报告发生率与观察死亡率时出现差异。工作组得出结论:“严重脓毒症”这个术语是多余的。 建议:脓毒症应该定义为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所导致的致命性器官功能障 碍。为了便于临床操作,器官功能障碍可以用序贯[全身感染相关]器官功能衰竭评分(SOFA)的增加大于等于2分来表示,其相关的住院死亡率大于10%。感染性休克应该被定义为脓毒症的一个类型,与单独的脓毒症相比,特别是在严重循环、分子、代谢异常方面与高死亡风险密切相关。在临床上感染性休克患者可通过下列情况加以识别:在排除低血容量的情况下,需应用升压药以维持平均动脉≥65mmHg,以及血清乳酸>2mmol/L(>18mg/dL)。感染性休克的患者在临床上可以通过下情况被识别:需要应用血管加压素保持平均动脉大于等于65mmHg,以及在没有低血容量情况下血乳酸大于2mmol/L(>18mg/dL)。根据这一联合标准,感染性休克的住院死亡率>40%。这个联合标准诊断的感染性休克患者相关的住院死亡率大于40%。在院外、急诊科或医院普通病房可疑感染的成人患者若符合至少2项临床标准[这一标准构成一新的床旁指标即快速SOFA(qSOFA):呼吸频率≥22次/分、意识状态改变、收缩压≤100mmHg],即可快速识别那些可能出现典型脓毒症不良预后的可疑感染的非ICU患者。在院外、急诊科以及医院普通病房,怀疑存在感染的成年患者,如果下面的临床诊断标准存在至少2条(这些诊断标准构成一个新的临床评分称作quickSOFA[qSOFA]:呼吸频率大于等于22次/min,意识改变,收缩压小于等于100mmHg),则作为更可能存在预后不良的典型脓毒症患者而被快速识别。
·专家笔谈· 脓毒症是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在脓毒症发病机制中,除病原微生物及其毒素直接损害组织细胞外,免疫功能紊乱对其发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脓毒症免疫发病机制极其复杂,固有(innate)免疫和适应性(adaptive)免疫反应均参与发病,所导致的促炎反应/抗炎反应动态失衡是脓毒症进展为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不全的(MODS)的原因之一[1]。本文扼述脓毒症免疫功能紊乱及其可能的机制,旨在拓宽免疫调节治疗脓毒症的思路。 1脓毒症免疫功能紊乱机制 感染可通过免疫系统促发炎症反应。以往曾认为脓毒症可能存在SIRS和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CARS)两个免疫反应时相。早期主要为大量产生TNF-α、IL-1β等前炎症细胞因子,激发炎症反应(SIRS);其后随脓毒症促炎反应发展,机体启动代偿性抗炎反应机制,IL-10等抗炎细胞因子大量产生以拮抗过度产生的前炎症细胞因子,同时前炎症细胞因子因合成减少或消耗降解而降低,从而导致CARS[1]。近来在探讨脓毒症免疫抑制机制时,注意到成年脓毒症患者早期即可高表达IL-10等抗炎细胞因子,处于脓毒症免疫抑制状态(以CD14+单核细胞HLA-DR表达<30%为界定标准)患者同时存在超高水平的前炎症细胞因子和抗炎症细胞因子[2]。同样以CD14+单核细胞HLA-DR表达<30%或>30%为标准,观察不同免疫状态下婴幼儿脓毒症前炎症细胞因子/抗炎症细胞因 脓毒症免疫功能紊乱及免疫调节治疗 李成荣 深圳市儿童医院(广东深圳518026) 摘要:文章扼述脓毒症免疫功能紊乱机制。病原微生物(配体)通过Toll样受体(TLR)等模式识别受体(PRR)启动固有免疫反应,所产生的炎症细胞因子导致促炎反应并触发适应性免疫,诱导初始T细胞分为Th1、Th2细胞、CD4+CD25+Foxp3+调节性细胞(Treg)及Th17细胞,介导免疫抑制和炎症反应。脓毒症促炎/抗炎反应同时异常活化,导致免疫功能紊乱。免疫调节治疗脓毒症的思路是既能清除内、外源性配体抑制PRR持续活化,又不过度抑制抗感染免疫反应。[临床儿科杂志,2010,28(1):13-17]关键词:脓毒症;Toll样受体;固有免疫/适应性免疫;调节性T细胞;Th17细胞;免疫调节治疗 中图分类号:R7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3606(2010)01-0013-05 Pathogenesis of immune dysfunction in septic and immunoregulation therapy LI Cheng-rong(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Shenzhen518026,Guangdong,China) Abstract:The pathogenesis of immune dysfunction in septic has been summarized in this review.Innate immune response toward pathogens is initiated by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PRR)such as Toll-like receptor(TLR).Inflammatory cytokines derived from innate immune response not only cause inflammatory response,but also trigger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s through induc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naive T cell into Th1,Th2,CD4+CD25+Foxp3+regulatory T cells(Treg),and Th17cells.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might suppress or enhance inflammatory response.Abnormal activation of innate/adaptive immune responses may coexist in sepsis,resulting in immune dysfunction.Logical and adequate approach of immunoregulation therapy to sepsis may be to suppress PRR persistent activation by eliminating endogenous or exogenous ligands,as well as to avoid excessive inhibition of immune responses to infection.(J Clin Pediatr,2010,28(1):13-17)Key words:sepsis;Toll-like receptor;innate/adaptive immune responses;Treg;Th17;immuno-regulation therapy
重视脓毒症患者的体格检查 重症行者翻译组李文哲 关键点 1.体格检查是初始评估脓毒症患者的手段之一,具有可靠性强成本低且无创的优势特点。 2.通过体格检查来评估患者,临床医师应关注并理解如意识状态、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皮肤花斑评分、皮肤温度梯度等项目的机制和意义。 3.脓毒症相关性脑病与患者发病率和病死率升高相关,且很多幸存患者会经历长时期的认知功能障碍,更需注意的是临床工作中常常将其漏诊。 4.在预测识别脓毒症患者潜在器官功能障碍方面,体格检查,如:意识状态异常,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延长,皮肤花斑表现,皮肤温度梯度变化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有效性。 综述目的 监护重症患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无创手段来完成对患者意识状态和外周循环变化的监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体格检查可以替代性地评估临床治疗的短期疗效,所以应重视不同临床背景下(如脓毒症)对患者进行常规的体格监测。脓毒症相关性脑病的发生或意识状态的改变与患者不良预后具有相关性,评估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外周循环状态是预测其临床预后的一项实用易行且准确的监测方法。基于最新相关研究结果,本文目的在于强调对脓毒症患者进行常规的体格检查监测和评估。 最新发现
几项最新研究结果开阔了我们对脓毒症患者发生意识状态改变的病理生理机制和对外周循环状态进行临床评估的认知。脓毒症相关性脑病与重症患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升高相关。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CRT)延长和持续性的皮肤花斑表现对患者病死率有很大的预测意义,而皮肤温度梯度变化则提示血管收缩和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 总结 对于脓毒症患者常规进行体格检查来监测患者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临床重要的诊疗措施。反复地神经系统体检、评估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CRT)、进行皮肤花斑评分、测量皮肤温度梯度变化,这些都是重要的无创监测方法,这些方法在脓毒症患者接受复苏治疗过程中也显示出良好的协同一致性。 介绍 脓毒症的定义为感染引起宿主免疫反应失调进而导致器官功能障碍的综合征。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新定义(Sepsis )最近也已发布,新定义为:感染引起宿主免疫反应失调进而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脓毒性休克则定义为脓毒症伴有循环代谢紊乱,具有高病死率的特点。全球每年新发数百万脓毒症患者,约1/4的患者死亡。在脓毒症发生的最初几小时内及时识别并给予恰当干预治疗可以明显改善患者预后,而在整个脓毒症的诊疗过程中,体格检查展现出了其重要意义。本文中阐述经相关研究验证,体格检查与有创监测结果具有相关一致性,而且体格检查可以替代性地评估临床干预治疗的短期疗效。美国联邦政府医疗健康保险与医疗扶助服务中心(CMS)将体格检查作为脓毒症患者诊疗的“关键措施”之一,体格检查与6小时bundle治疗一样,在评估患者意识状态和组织灌注等方面得到了明确推荐。 脓毒症所致意识状态改变 脓毒症患者常有早期急性意识状态的变化,且与发病率和病死率相关。多数患者的表现符合谵妄,如:意识状态时好时坏、思维紊乱、注意力涣散等。谵妄是由多种相关危险因素所致的综合征,如:疾病严重程度、患者的急促情况(认知功能损害年龄)、环境因素(噪音,睡眠剥夺)、药物因素(苯二氮草类,阿片类)、
【述评】严重脓毒症免疫调节治疗:从免疫抑制走向免疫增强 脓毒症(sepsis)是危重病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在所有引起居民死亡的病因中脓毒症排在第10位[1]。早期对脓毒症发病机制的研究认为,失控的、持续放大的全身性炎症反应(SIRS)是引起脓毒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2]。但随着支持治疗手段的提高,绝大部分患者能够度过严重的全身炎症反应阶段即免疫亢进期,进入更加复杂的免疫抑制(麻痹)期。近年来对死亡的脓毒症患者进行尸检发现,脓毒症后期表现为严重的免疫麻痹,且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免疫麻痹导致后期出现继发性感染,大部分感染的病原体是多种耐药的细菌或真菌,无法控制的感染最终导致患者死亡。尽管早期液体复苏、感染灶的及时清除、抗生素的早期使用及器官功能支持的“集束化治疗” 是脓毒症治疗的基石,但脓毒症的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因此,不断探讨和研究新的治疗方法和理念迫在眉睫。近年来已经认识到免疫麻痹是严重脓毒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近期有多项研究证实免疫增强(刺激)治疗能够改善脓毒症患者的病情和提高生存率。本文将总结脓毒症免疫功能紊乱研究的最新认识,探讨脓毒症免疫增强治疗的可能性。 1脓毒症免疫功能紊乱的传统认识 当病原微生物突破皮肤、黏膜等入侵到人体后,机体快速启动非特异性(固有)免疫系统识别和清除致病微生物。固有免疫反应不仅是机体抵御外界微生物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其在诱导和激活获得性免疫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宿主细胞通过表达几类病原模式识别受体(PRRs)来识别病原体的保守结构即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MPs)。常见的PAMPs包括脂多糖、肽聚糖、鞭毛蛋白及微生物的核酸分子等。PRRs主要包括定位于炎症细胞膜和内体膜上的ToII样受体(TLRs)和C型凝集素受体(CLRs)、胞浆内的NOD样受体(NLRs)、视黄酸诱导基因I解旋酶(RIG-I)样受体(RLRs)和HIN200蛋白等。除识别PAMPs外,这些受体同时也可以识别由于组织损伤和细胞死亡而释放的内源性物质如热休克蛋白、DNA和RNA片段等内源性的危险信号。PAMPs被PRRs识别后启动下游的NF-KB信号通路,引起炎症介质的生成并介导炎症反应。适度的炎症反应有利于病原体的清除;但如果NF-KB信号通路持续激活,则引起炎症介质“瀑布样”的释放,过度的炎症反应对机体造成不利的影响,导致组织和器官功能的损伤。 过去的研究认为炎症介质的过量生成是脓毒症发病的主要病理过程[3]。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均证实炎症介质TNF-α和IL-1β等在脓毒症的发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有较多的动物实验也证实抗炎症治疗、拮抗内毒素的治疗能够改善脓毒症小鼠的预后。但随后以“免疫亢进” 为理论基础的,一系列(约25项)炎症介质(TNF-α和IL-1β等)单克隆抗体的临床实验,均发现“免疫抑制”
脓毒血症:针对感染的失调的宿主反应引起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 脓毒性休克:指脓毒症患者尽管充分的液体复苏仍存在持续的低血压,需要使用升压药物维持平均动脉压65mmHg以上,血乳酸2mmol/L以上。 A.早期复苏 1 对脓毒症诱导的低灌注,在开始的3h内,给与至少30ml/Kg的晶体液,在完成初始液体复苏后,需要反复进行评估血流动力学状态指导进一步的液体使用(CVP/血乳酸/平均动脉压/下腔静脉变异度等)。 2、对于脓毒性休克需要血管活性药物的患者,我们推荐初始目标平均动脉压为65mmHg。 3、对于乳酸水平升高,提示组织低灌注的患者,我们建议进行乳酸指导性复苏,并将乳酸恢复正常水平。 B.脓毒症筛查以及质量提高 C.诊断:常规在使用抗生素之前,进行微生物培养。 D.抗微生物治疗:在识别脓毒症或者脓毒性休克后1h内尽快启动静脉抗生素使用,经验性使用一种或者几种广谱抗生素进行治疗,以期覆盖所有可能的病原体(包括细菌以及潜在的真菌或者病毒,强推荐,中等证据质量),一旦可以确认微生物,同时药敏结果已经明确,和/或充分的临床症状体征改善,需要将经验性抗生素治疗转化为窄谱,针对性用药。抗生素治疗疗程为7-10天,对于大多数严重感染相关脓毒症以及脓毒性休克是足够的 E.感染源的控制 F.液体治疗 1.在血流动力学指标持续在改善的前提下,当持续进行液体输注时,使用补液试验。 2.在早期液体复苏以及随后的容量置换中,首选晶体液。也可以使用平衡液或者生理盐水进行液体复苏。当需要大量的晶体液时,可额外使用白蛋白;不建议使用羟乙基淀粉进行血容量的扩充。 G.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 1.去甲肾上腺素作为首先的血管活性药物,可以加用血管加压素(最大剂量0.03U/min)或者肾上腺素以达到目标MAP,或者加用血管加压素(最大剂量0.03U/min),以降低去甲肾上腺素的剂量。 2.在高选择性患者群体中,使用多巴胺作为去甲肾上腺素的替代血管活性药物(例如快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