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语拟人认知形式的比较分析及翻译
- 格式:pdf
- 大小:297.52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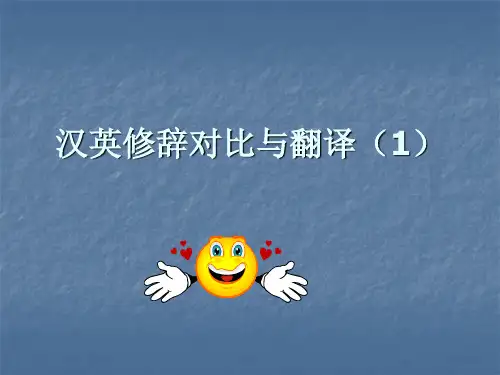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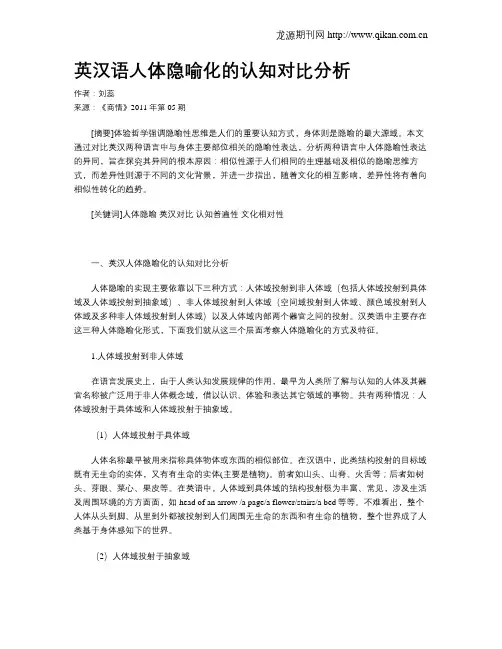
英汉语人体隐喻化的认知对比分析作者:刘蕊来源:《商情》2011年第05期[摘要]体验哲学强调隐喻性思维是人们的重要认知方式,身体则是隐喻的最大源域。
本文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与身体主要部位相关的隐喻性表达,分析两种语言中人体隐喻性表达的异同,旨在探究其异同的根本原因:相似性源于人们相同的生理基础及相似的隐喻思维方式,而差异性则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并进一步指出,随着文化的相互影响,差异性将有着向相似性转化的趋势。
[关键词]人体隐喻英汉对比认知普遍性文化相对性一、英汉人体隐喻化的认知对比分析人体隐喻的实现主要依靠以下三种方式:人体域投射到非人体域(包括人体域投射到具体域及人体域投射到抽象域)、非人体域投射到人体域(空间域投射到人体域、颜色域投射到人体域及多种非人体域投射到人体域)以及人体域内部两个器官之间的投射。
汉英语中主要存在这三种人体隐喻化形式,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层面考察人体隐喻化的方式及特征。
1.人体域投射到非人体域在语言发展史上,由于人类认知发展规律的作用,最早为人类所了解与认知的人体及其器官名称被广泛用于非人体概念域,借以认识、体验和表达其它领域的事物。
共有两种情况:人体域投射于具体域和人体域投射于抽象域。
(1)人体域投射于具体域人体名称最早被用来指称具体物体或东西的相似部位。
在汉语中,此类结构投射的目标域既有无生命的实体,又有有生命的实体(主要是植物)。
前者如山头、山脊、火舌等;后者如树头、芽眼、菜心、果皮等。
在英语中,人体域到具体域的结构投射极为丰富、常见,涉及生活及周围环境的方方面面,如head of an arrow /a page/a flower/stairs/a bed等等。
不难看出,整个人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被投射到人们周围无生命的东西和有生命的植物,整个世界成了人类基于身体感知下的世界。
(2)人体域投射于抽象域人体域向称呼域的映射属于一种特殊的隐喻化过程,即转喻。
与隐喻相同,转喻也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基于人们的基本经验,其本质是概念性的,是自发的认知过程,是丰富语言的重要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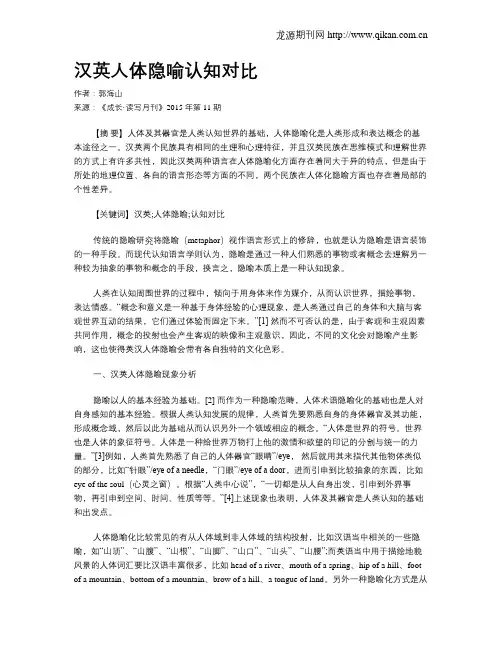
汉英人体隐喻认知对比作者:郭海山来源:《成长·读写月刊》2015年第11期【摘要】人体及其器官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人体隐喻化是人类形成和表达概念的基本途径之一。
汉英两个民族具有相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并且汉英民族在思维模式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上有许多共性,因此汉英两种语言在人体隐喻化方面存在着同大于异的特点,但是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各自的语言形态等方面的不同,两个民族在人体化隐喻方面也存在着局部的个性差异。
【关键词】汉英;人体隐喻;认知对比传统的隐喻研究将隐喻(metaphor)视作语言形式上的修辞,也就是认为隐喻是语言装饰的一种手段。
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则认为,隐喻是通过一种人们熟悉的事物或者概念去理解另一种较为抽象的事物和概念的手段,换言之,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
人类在认知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倾向于用身体来作为媒介,从而认识世界,描绘事物,表达情感。
“概念和意义是一种基于身体经验的心理现象,是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它们通过体验而固定下来。
”[1]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客观和主观因素共同作用,概念的投射也会产生客观的映像和主观意识,因此,不同的文化会对隐喻产生影响,这也使得英汉人体隐喻会带有各自独特的文化色彩。
一、汉英人体隐喻现象分析隐喻以人的基本经验为基础。
[2] 而作为一种隐喻范畴,人体术语隐喻化的基础也是人对自身感知的基本经验。
根据人类认知发展的规律,人类首先要熟悉自身的身体器官及其功能,形成概念域,然后以此为基础从而认识另外一个领域相应的概念。
“人体是世界的符号。
世界也是人体的象征符号。
人体是一种给世界万物打上他的激情和欲望的印记的分割与统一的力量。
”[3]例如,人类首先熟悉了自己的人体器官“眼睛”/eye,然后就用其来指代其他物体类似的部分,比如“针眼”/eye of a needle,“门眼”/eye of a door,进而引申到比较抽象的东西,比如eye of the soul(心灵之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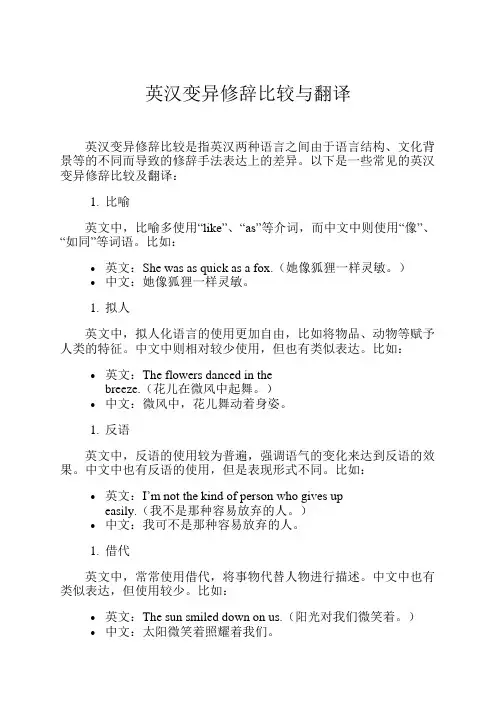
英汉变异修辞比较与翻译
英汉变异修辞比较是指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由于语言结构、文化背景等的不同而导致的修辞手法表达上的差异。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英汉变异修辞比较及翻译:
1.比喻
英文中,比喻多使用“like”、“as”等介词,而中文中则使用“像”、“如同”等词语。
比如:
•英文:She was as quick as a fox.(她像狐狸一样灵敏。
)
•中文:她像狐狸一样灵敏。
1.拟人
英文中,拟人化语言的使用更加自由,比如将物品、动物等赋予人类的特征。
中文中则相对较少使用,但也有类似表达。
比如:•英文:The flowers danced in the
breeze.(花儿在微风中起舞。
)
•中文:微风中,花儿舞动着身姿。
1.反语
英文中,反语的使用较为普遍,强调语气的变化来达到反语的效果。
中文中也有反语的使用,但是表现形式不同。
比如:•英文: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gives up
easily.(我不是那种容易放弃的人。
)
•中文:我可不是那种容易放弃的人。
1.借代
英文中,常常使用借代,将事物代替人物进行描述。
中文中也有类似表达,但使用较少。
比如:
•英文:The sun smiled down on us.(阳光对我们微笑着。
)
•中文:太阳微笑着照耀着我们。
总之,英汉之间存在很多的变异修辞,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结构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修辞表达。
翻译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和表达方式来进行恰当的转化和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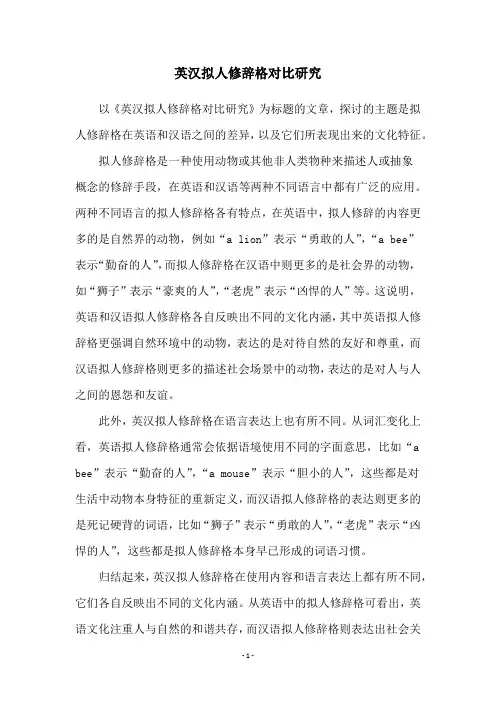
英汉拟人修辞格对比研究
以《英汉拟人修辞格对比研究》为标题的文章,探讨的主题是拟人修辞格在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
拟人修辞格是一种使用动物或其他非人类物种来描述人或抽象
概念的修辞手段,在英语和汉语等两种不同语言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两种不同语言的拟人修辞格各有特点,在英语中,拟人修辞的内容更多的是自然界的动物,例如“a lion”表示“勇敢的人”,“a bee”
表示“勤奋的人”,而拟人修辞格在汉语中则更多的是社会界的动物,如“狮子”表示“豪爽的人”,“老虎”表示“凶悍的人”等。
这说明,英语和汉语拟人修辞格各自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其中英语拟人修辞格更强调自然环境中的动物,表达的是对待自然的友好和尊重,而汉语拟人修辞格则更多的描述社会场景中的动物,表达的是对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和友谊。
此外,英汉拟人修辞格在语言表达上也有所不同。
从词汇变化上看,英语拟人修辞格通常会依据语境使用不同的字面意思,比如“a bee”表示“勤奋的人”,“a mouse”表示“胆小的人”,这些都是对
生活中动物本身特征的重新定义,而汉语拟人修辞格的表达则更多的是死记硬背的词语,比如“狮子”表示“勇敢的人”,“老虎”表示“凶悍的人”,这些都是拟人修辞格本身早已形成的词语习惯。
归结起来,英汉拟人修辞格在使用内容和语言表达上都有所不同,它们各自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内涵。
从英语中的拟人修辞格可看出,英语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汉语拟人修辞格则表达出社会关
系之间的恩怨和友谊。
因此,正确理解和使用拟人修辞格,能帮助我们不仅更好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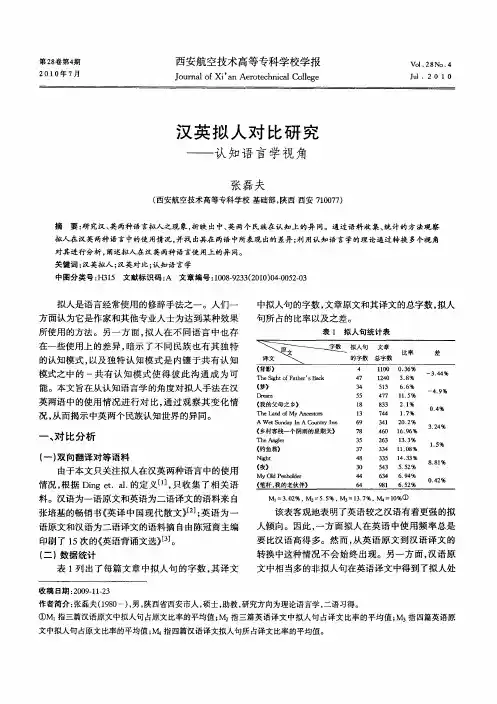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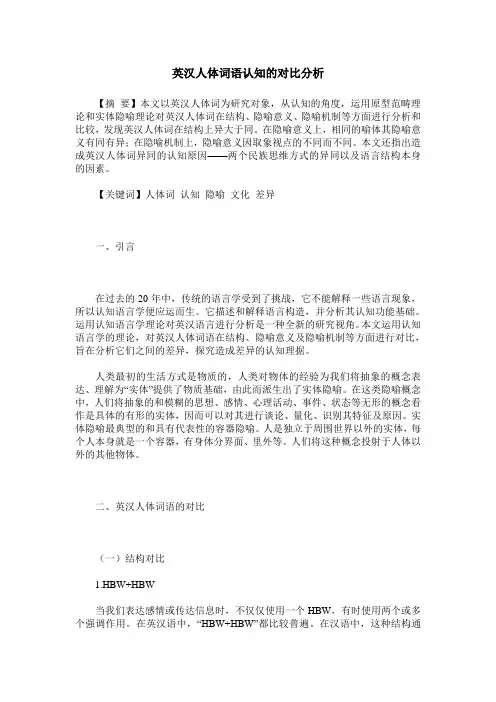
英汉人体词语认知的对比分析【摘要】本文以英汉人体词为研究对象,从认知的角度,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和实体隐喻理论对英汉人体词在结构、隐喻意义、隐喻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发现英汉人体词在结构上异大于同。
在隐喻意义上,相同的喻体其隐喻意义有同有异;在隐喻机制上,隐喻意义因取象视点的不同而不同。
本文还指出造成英汉人体词异同的认知原因——两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异同以及语言结构本身的因素。
【关键词】人体词认知隐喻文化差异一、引言在过去的20年中,传统的语言学受到了挑战,它不能解释一些语言现象,所以认知语言学便应运而生。
它描述和解释语言构造,并分析其认知功能基础。
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英汉语言进行分析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对英汉人体词语在结构、隐喻意义及隐喻机制等方面进行对比,旨在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探究造成差异的认知理据。
人类最初的生活方式是物质的,人类对物体的经验为我们将抽象的概念表达、理解为“实体”提供了物质基础,由此而派生出了实体隐喻。
在这类隐喻概念中,人们将抽象的和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无形的概念看作是具体的有形的实体,因而可以对其进行谈论、量化、识别其特征及原因。
实体隐喻最典型的和具有代表性的容器隐喻。
人是独立于周围世界以外的实体,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容器,有身体分界面、里外等。
人们将这种概念投射于人体以外的其他物体。
二、英汉人体词语的对比(一)结构对比1.HBW+HBW当我们表达感情或传达信息时,不仅仅使用一个HBW,有时使用两个或多个强调作用。
在英汉语中,“HBW+HBW”都比较普遍。
在汉语中,这种结构通常直接由两个人体词构成,形成并列结构,如:手足、嘴脸、唇舌、唇齿。
而在英语中,这种结构比较少,通常由两个人体词用“and“连接起来的情况比较多,如:“heart and hand”、“heart and soul”、“eyes and ears”,etc。
而其他由“N-N”(两个名词相同)的结构中,英汉语中看起来意义相同,如:心连心=heart linked to heart;面对面=face to face,et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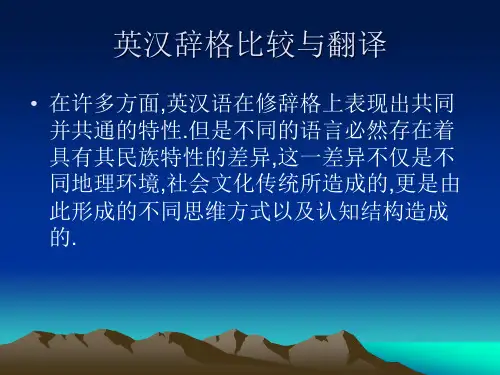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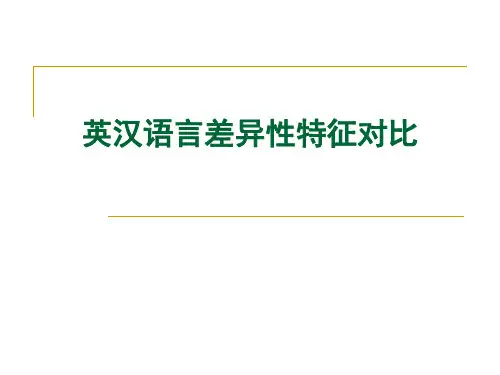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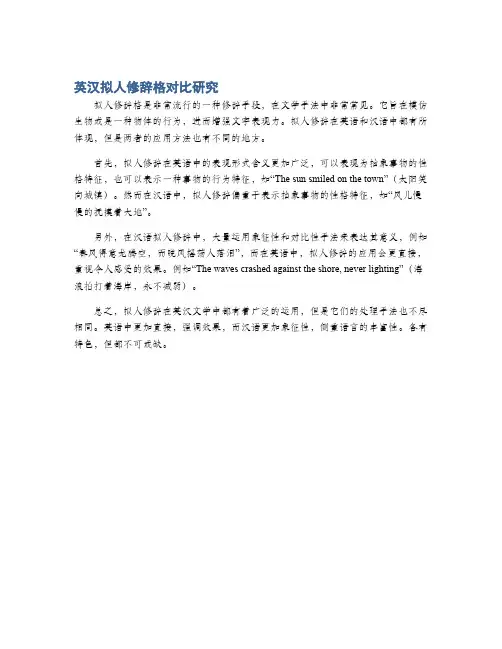
英汉拟人修辞格对比研究
拟人修辞格是非常流行的一种修辞手段,在文学手法中非常常见。
它旨在模仿生物或是一种物体的行为,进而增强文字表现力。
拟人修辞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有所体现,但是两者的应用方法也有不同的地方。
首先,拟人修辞在英语中的表现形式含义更加广泛,可以表现为抽象事物的性格特征,也可以表示一种事物的行为特征,如“The sun smiled on the town”(太阳笑向城镇)。
然而在汉语中,拟人修辞偏重于表示抽象事物的性格特征,如“风儿慢慢的抚摸着大地”。
另外,在汉语拟人修辞中,大量运用象征性和对比性手法来表达其意义,例如“春风得意龙腾空,而晚风摇荡人落泪”,而在英语中,拟人修辞的应用会更直接,重视令人感受的效果。
例如“The waves crashed against the shore, never lighting”(海浪拍打着海岸,永不减弱)。
总之,拟人修辞在英汉文学中都有着广泛的运用,但是它们的处理手法也不尽相同。
英语中更加直接,强调效果,而汉语更加象征性,侧重语言的丰富性。
各有特色,但都不可或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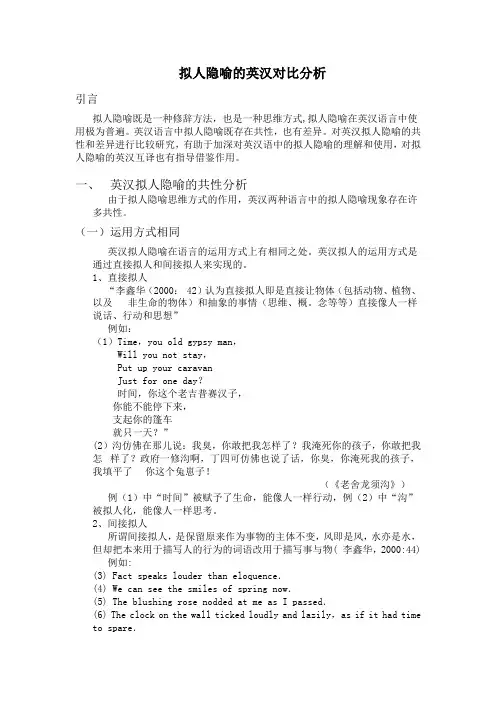
拟人隐喻的英汉对比分析引言拟人隐喻既是一种修辞方法,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拟人隐喻在英汉语言中使用极为普遍。
英汉语言中拟人隐喻既存在共性,也有差异。
对英汉拟人隐喻的共性和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英汉语中的拟人隐喻的理解和使用,对拟人隐喻的英汉互译也有指导借鉴作用。
一、英汉拟人隐喻的共性分析由于拟人隐喻思维方式的作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拟人隐喻现象存在许多共性。
(一)运用方式相同英汉拟人隐喻在语言的运用方式上有相同之处。
英汉拟人的运用方式是通过直接拟人和间接拟人来实现的。
1、直接拟人“李鑫华(2000: 42)认为直接拟人即是直接让物体(包括动物、植物、以及非生命的物体)和抽象的事情(思维、概。
念等等)直接像人一样说话、行动和思想”例如:(1)Time,you old gypsy man,Will you not stay,Put up your caravanJust for one day?时间,你这个老吉普赛汉子,你能不能停下来,支起你的篷车就只一天?”(2)沟仿佛在那儿说:我臭,你敢把我怎样了?我淹死你的孩子,你敢把我怎样了?政府一修沟啊,丁四可仿佛也说了话,你臭,你淹死我的孩子,我填平了你这个兔崽子!(《老舍龙须沟》)例(1)中“时间”被赋予了生命,能像人一样行动,例(2)中“沟”被拟人化,能像人一样思考。
2、间接拟人所谓间接拟人,是保留原来作为事物的主体不变,风即是风,水亦是水,但却把本来用于描写人的行为的词语改用于描写事与物( 李鑫华,2000:44) 例如:(3) Fact speaks louder than eloquence.(4) We can see the smiles of spring now.(5) The blushing rose nodded at me as I passed.(6) The clock on the wall ticked loudly and lazily,as if it had timeto spare.(7) 困难只能欺侮那些懒汉,它最害怕用功学习的人(8) 风是那样的温柔,小鸟是那样的欢乐在例(3) 到例(8)中,用于描述人的动词speak nod,欺侮害怕,名词smile,形容词blushing 温柔欢乐,副词loudly and lazily被用来描述无生命的事体,使之拟人化。
浅议英汉修辞对比与翻译
本文是关于英汉修辞对比与翻译的一篇文章,讨论这两种语言在修辞方面的差异,以及如何在翻译时在修辞方面做出妥善的处理。
英语和汉语都是两种著名的语言,也是两种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的语言。
在修辞方面,英汉又有着很大的差异。
比如,英语更注重语气的表达,而汉语则更注重语句的构成。
英语的修辞功能更多的体现在语气的运用上,比如得体的问候语,感叹词和一些强调句等;而汉语的修辞功能更多体现在句子构成上,比如引申句、复句、反问句、递进句、分句以及比喻句等。
英汉在修辞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如何在修辞方面做出处理。
首先,我们要仔细分解源语句子,弄清楚它所要表达什么意思,这样我们才能在翻译时用恰当的词语来表达出源语句子的本意。
其次,我们要根据母语的特点来处理译文中的修辞结构,比如在译文中补充一些引申句、复句、反问句、递进句、分句以及比喻句等,以使译文更加准确传神。
此外,我们还需要熟练掌握双语的语法知识和文化背景,以此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原文的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以及该信息所背后的文化背景,然后得出一种新的翻译结果,表达出作者原意的同时,还注重翻译译文的修辞结构,让译文更加丰富。
最后,我们要在翻译过程中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通顺性,以及对读者的交流效果。
综上所述,英汉在修辞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而在翻译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如何在修辞方面做出妥善的处理,以使译文更加准确传神。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通顺性,以及读者交流的效果。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信息准确地传递给读者。
汉英拟人修辞的认知对比研究拟人作为我国传统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之一,早在《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得到运用,我国学者对汉语拟人修辞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如对拟人修辞的研究重微观、轻宏观,没有充分运用国外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拟人修辞展开系统的、理论性的探究,没有把对拟人修辞的研究上升到论证性和解释性的高度,往往把对拟人修辞的探究与讨论集中于总结归纳和对此进行描写说明的层面上。
对拟人修辞往往开展的是“就辞格论辞格”的程式化、单一化研究,这种研究依托于修辞学的内部理论和方法,以占有丰富的拟人话语材料为基础,采用正向思维方式对拟人进行考察,较少考虑从多侧面、多角度运用其他与修辞学相关的诸如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的学科理论对拟人修辞进行考察研究。
因此,拟人修辞独有的内涵、规律与特征较难得到完整地体现。
本文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对汉英拟人修辞进行诠释与对比分析。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双域映射观,将拟人的本体和拟体分别视为“目标域”和“源域”,将汉英拟人重新定义为:拟人以体验性和相似性为基础,通过认知加工把两个不同概念之间的某一属性特征突显出来并作跨认知域的单向双层投射后产生的,这种投射实现了拟人源域向目标域的跨越并产生了两域之间恰当的叠合效应。
创造性的将拟人分为突显事体的拟人和突显行为的拟人两种类型。
同时,运用徐盛桓先生提出的“外延内涵传承说”等认知语言学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的“映射”,即拟人机制为什么能这样运作。
说明拟人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表现手法,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思维方式。
此外,本文从认知模式、汉英语言心理特征、图形背景分离理论等角度对汉英拟人修辞进行对比分析,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论证了英语较之汉语有着更强的拟人倾向,汉英拟人有差异也有相同。
英汉通感的认知比较与翻译英汉语言中都存在大量的通感用法,现阶段的研究表明,通感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认知思维方式。
本文对英汉两民族使用的通感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英汉通感的使用既有共性也存在个性,并探讨了通感的翻译。
标签:通感共性个性直译法异化法一、引言通感作为修辞手法在英汉民族中都其有很长的历史,以往对通感的研究都是把它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自从Lakoff 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创建后,人们对通感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认知视角。
这是通感研究的一大发展。
钱钟书先生把“Synaesthesia”翻译成为“通感”,并在《七缀集》中谈到“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眼、而、鼻、舌、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部分界限。
颜色似乎有温度,声音似乎有形象,冷暖似乎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
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中经常出现。
”也就是说,作用于某一感官产生的感受可以用其他感官的感受来表现,说明人类各种感官是相互连通的,对某感官产生的感觉可以引起其他相关感官的反映,于是就产生了通感的表达手法。
二、英汉通感的共性(一)英汉通感的认知本质认知科学的发展证明了通感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也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
它利用人类已有的某种感官经验去解释另一种感官经验,因此,人类能够利用更熟悉或更容易理解的经验去理解陌生的或难以理解的经验。
人在与客观世界的长期接触中,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五大感官的经验,这些经验储存在大脑中,当某一刺激物作用于某感官,由于感官的互通性,人类的其它感官也产生了某种体验,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维是语言的外壳,人类的多种体验相融合,就产生了通感的表达。
因此,可以说通感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之一,属于人类的认知思维。
中英两民族的人民有着共同的认知方式,反映在语言上,使得英汉这两个地理位置相距甚远,文化风俗迥然不同的民族,在通感的运用与发展中呈现出异曲同工的特点。
(二)英汉通感的生理-心理基础Ullmann对2009个通感用例的调查发现,感觉的移动方向呈现由较低级转向较高级感官。
汉英影视台词仿拟辞格的对比研究仿拟修辞格就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下,根据自己的表达需要,意识地使用偏离语言常规的表达方式,模仿已经存在的谚语、名言警句、诗句、歌词等语言材料及言语风格等,通过增减字词、变换词语顺序、正反模仿、改变语态等方式,融合自己的思想,临时创造出新奇、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以求达到幽默诙谐、引人思考的表达效果的一种修辞格。
多年来,对于仿拟修辞的研究一直都局限在修辞学、认知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对象也多为广告语、文学著作语言等,涉及到影视台词研究的并不多见。
然而,近年来,随着影视剧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影视剧台词中,仿拟修辞格的运用逐渐吸引了众学者的研究视线。
实质上,仿拟修辞格在影视台词中具有很大的使用空间,它可以呈现出各种形式。
因此本文试图以汉英影视台词为研究对象,从关联理论的视角下去探讨分析汉英仿拟修辞格的异同。
关联理论对台词中的仿拟修辞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仿拟修辞是否可以成功的运用的关键就在于找出仿拟的本体和仿体之间是否具有最佳关联性。
为了实现电影预期的交际效果,台词中的仿拟修辞应该以本体与仿体之间的最佳关联原则为指导,力求让观众经过积极地想象与合理地推断,付出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在关联理论的视角下,有效的仿拟实质上就是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仿拟中的本体与仿体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说话者模仿已存的词语或言语形式,创造出仿体,展示自己的交际意图(即明示过程);听话者依据特定的语境付出努力不断地进行猜测与推理,力图付出最小的努力寻找到本体与仿体在言语层面的最佳关联,捕捉到说话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即推理过程)。
仿拟效果的生成主要依据听话者付出额外的努力可以去识别本体与仿体之间的某种关联,即相似点、反差甚至冲突。
同时,关联理论指导下的台词仿拟辞格翻译研究也必然为翻译研究领域打开新的视角。
因此,本文试图首先运用关联理论去分析仿拟修辞格的构建机制,其次进一步研究对比仿拟修辞格在汉英影视剧台词中是如何运用的,并探索出仿拟修辞在汉英影视台词中运用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