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二三事
- 格式:doc
- 大小:29.0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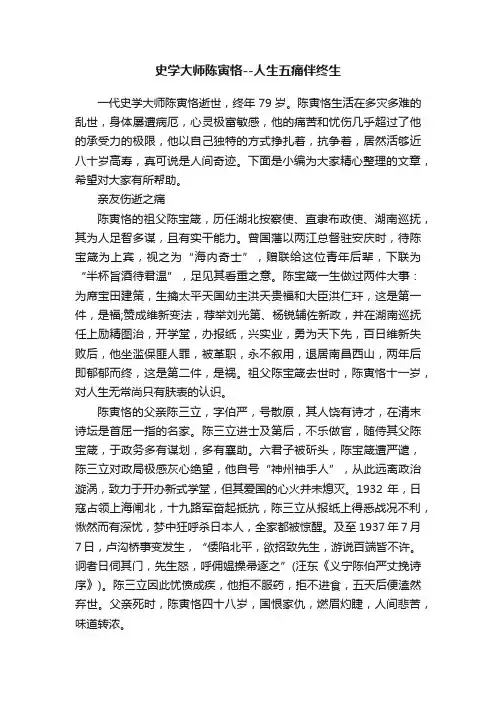
史学大师陈寅恪--人生五痛伴终生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逝世,终年79岁。
陈寅恪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乱世,身体屡遭病厄,心灵极富敏感,他的痛苦和忧伤几乎超过了他的承受力的极限,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挣扎着,抗争着,居然活够近八十岁高寿,真可说是人间奇迹。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亲友伤逝之痛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历任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其为人足智多谋,且有实干能力。
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赠联给这位青年后辈,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足见其看重之意。
陈宝箴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为席宝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玕,这是第一件,是福;赞成维新变法,荐举刘光第、杨锐辅佐新政,并在湖南巡抚任上励精图治,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勇为天下先,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坐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退居南昌西山,两年后即郁郁而终,这是第二件,是祸。
祖父陈宝箴去世时,陈寅恪十一岁,对人生无常尚只有肤表的认识。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其人饶有诗才,在清末诗坛是首屈一指的名家。
陈三立进士及第后,不乐做官,随侍其父陈宝箴,于政务多有谋划,多有襄助。
六君子被斫头,陈宝箴遭严谴,陈三立对政局极感灰心绝望,他自号“神州袖手人”,从此远离政治漩涡,致力于开办新式学堂,但其爱国的心火并未熄灭。
1932年,日寇占领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陈三立从报纸上得悉战况不利,愀然而有深忧,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都被惊醒。
及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倭陷北平,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
诇者日伺其门,先生怒,呼佣媪操帚逐之”(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序》)。
陈三立因此忧愤成疾,他拒不服药,拒不进食,五天后便溘然弃世。
父亲死时,陈寅恪四十八岁,国恨家仇,燃眉灼睫,人间悲苦,味道转浓。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字师曾,画坛一代大家,山民齐白石蛰居京师多年,寂寂无名,润格甚低,多赖陈衡恪逢人说项,为之广为延誉,且携齐白石多幅国画赴日本展销,引起轰动,卖出天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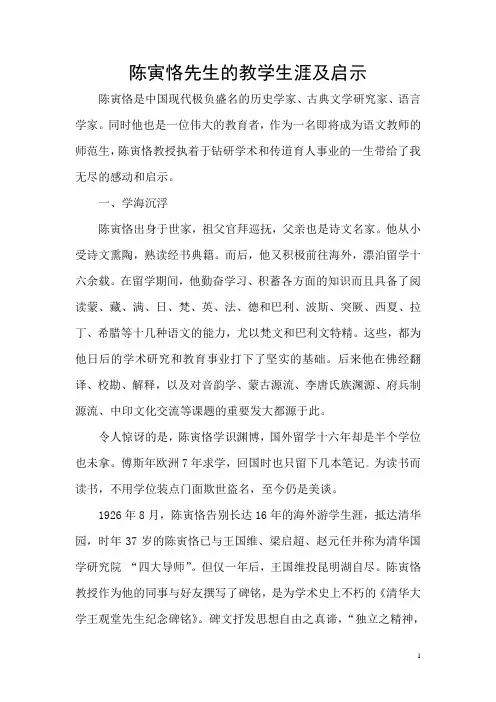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作为一名即将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陈寅恪教授执着于钻研学术和传道育人事业的一生带给了我无尽的感动和启示。
一、学海沉浮陈寅恪出身于世家,祖父官拜巡抚,父亲也是诗文名家。
他从小受诗文熏陶,熟读经书典籍。
而后,他又积极前往海外,漂泊留学十六余载。
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他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重要发大都源于此。
令人惊讶的是,陈寅恪学识渊博,国外留学十六年却是半个学位也未拿。
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也只留下几本笔记。
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至今仍是美谈。
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时年37岁的陈寅恪已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
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王国维自尽后,梁启超也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
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四大导师”纷纷离散,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院也随之解散,此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
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吴宓在其文集中写道:“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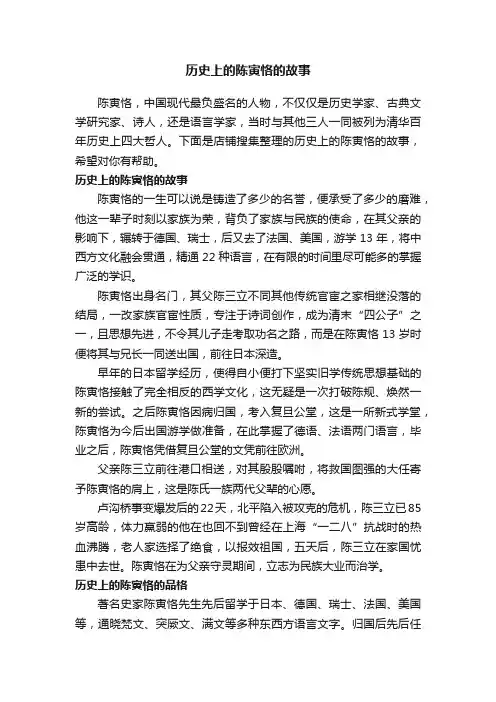
历史上的陈寅恪的故事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人物,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还是语言学家,当时与其他三人一同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历史上的陈寅恪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历史上的陈寅恪的故事陈寅恪的一生可以说是铸造了多少的名誉,便承受了多少的磨难,他这一辈子时刻以家族为荣,背负了家族与民族的使命,在其父亲的影响下,辗转于德国、瑞士,后又去了法国、美国,游学13年,将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精通22种语言,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掌握广泛的学识。
陈寅恪出身名门,其父陈三立不同其他传统官宦之家相继没落的结局,一改家族官宦性质,专注于诗词创作,成为清末“四公子”之一,且思想先进,不令其儿子走考取功名之路,而是在陈寅恪13岁时便将其与兄长一同送出国,前往日本深造。
早年的日本留学经历,使得自小便打下坚实旧学传统思想基础的陈寅恪接触了完全相反的西学文化,这无疑是一次打破陈规、焕然一新的尝试。
之后陈寅恪因病归国,考入复旦公堂,这是一所新式学堂,陈寅恪为今后出国游学做准备,在此掌握了德语、法语两门语言,毕业之后,陈寅恪凭借复旦公堂的文凭前往欧洲。
父亲陈三立前往港口相送,对其殷殷嘱咐,将救国图强的大任寄予陈寅恪的肩上,这是陈氏一族两代父辈的心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北平陷入被攻克的危机,陈三立已85岁高龄,体力羸弱的他在也回不到曾经在上海“一二八”抗战时的热血沸腾,老人家选择了绝食,以报效祖国,五天后,陈三立在家国忧患中去世。
陈寅恪在为父亲守灵期间,立志为民族大业而治学。
历史上的陈寅恪的品格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
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
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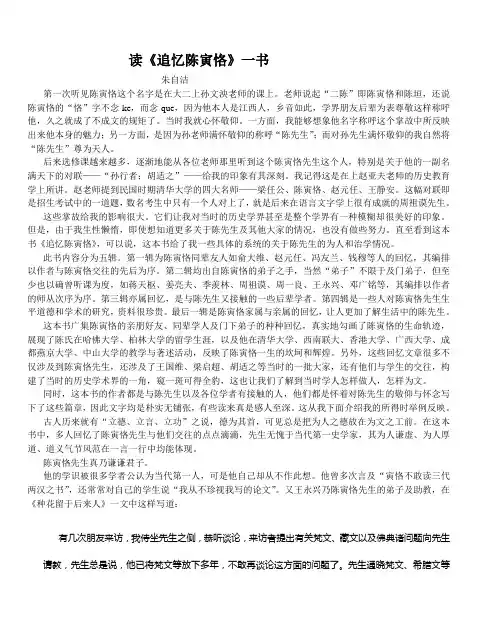
读《追忆陈寅恪》一书朱自洁第一次听见陈寅恪这个名字是在大二上孙文泱老师的课上。
老师说起“二陈”即陈寅恪和陈垣,还说陈寅恪的“恪”字不念ke,而念que,因为他本人是江西人,乡音如此,学界朋友后辈为表尊敬这样称呼他,久之就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了。
当时我就心怀敬仰。
一方面,我能够想象他名字称呼这个掌故中所反映出来他本身的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孙老师满怀敬仰的称呼“陈先生”;而对孙先生满怀敬仰的我自然将“陈先生”尊为天人。
后来选修课越来越多,逐渐地能从各位老师那里听到这个陈寅恪先生这个人,特别是关于他的一副名满天下的对联——“孙行者;胡适之”——给我的印象有其深刻。
我记得这是在上赵亚夫老师的历史教育学上所讲。
赵老师提到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四大名师——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王静安。
这幅对联即是招生考试中的一道题,数名考生中只有一个人对上了,就是后来在语言文字学上很有成就的周祖谟先生。
这些掌故给我的影响很大。
它们让我对当时的历史学界甚至是整个学界有一种模糊却很美好的印象。
但是,由于我生性懒惰,即使想知道更多关于陈先生及其他大家的情况,也没有做些努力。
直至看到这本书《追忆陈寅恪》,可以说,这本书给了我一些具体的系统的关于陈先生的为人和治学情况。
此书内容分为五辑。
第一辑为陈寅恪同辈友人如俞大维、赵元任、冯友兰、钱穆等人的回忆,其编排以作者与陈寅恪交往的先后为序。
第二辑均出自陈寅恪的弟子之手,当然“弟子”不限于及门弟子,但至少也以确曾听课为度,如蒋天枢、姜亮夫、季羡林、周祖谟、周一良、王永兴、邓广铭等,其编排以作者的师从次序为序。
第三辑亦属回忆,是与陈先生又接触的一些后辈学者。
第四辑是一些人对陈寅恪先生生平道德和学术的研究,资料很珍贵。
最后一辑是陈寅恪家属与亲属的回忆,让人更加了解生活中的陈先生。
这本书广集陈寅恪的亲朋好友、同辈学人及门下弟子的种种回忆,真实地勾画了陈寅恪的生命轨迹,展现了陈氏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的留学生涯,以及他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的教学与著述活动,反映了陈寅恪一生的坎坷和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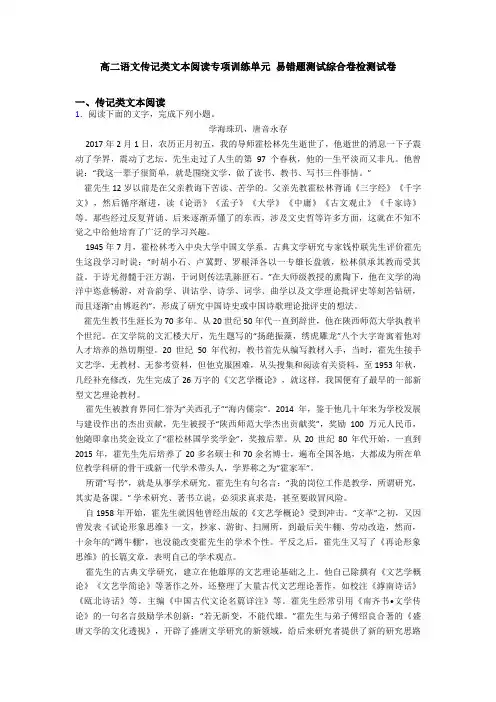
高二语文传记类文本阅读专项训练单元易错题测试综合卷检测试卷一、传记类文本阅读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学海珠玑,唐音永存2017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我的导师霍松林先生逝世了,他逝世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学界,震动了艺坛。
先生走过了人生的第97个春秋,他的一生平淡而又非凡。
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霍先生12岁以前是在父亲教诲下苦读、苦学的。
父亲先教霍松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古文观止》《千家诗》等。
那些经过反复背诵、后来逐渐弄懂了的东西,涉及文史哲等许多方面,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给他培育了广泛的学习兴趣。
1945年7月,霍松林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评价霍先生这段学习时说:“时胡小石、卢冀野、罗根泽各以一专雄长盘敦,松林俱承其教而受其益。
于诗尤得髓于汪方湖,于词则传法乳陈匪石。
”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他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畅游,对音韵学、训诂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而且逐渐“由博返约”,形成了研究中国诗史或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想法。
霍先生教书生涯长为70多年。
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辞世,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半个世纪。
在文学院的文汇楼大厅,先生题写的“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八个大字寄寓着他对人才培养的热切期望。
20世纪50年代初,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当时,霍先生接手文艺学,无教材、无参考资料,但他克服困难,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至1953年秋,几经补充修改,先生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被教育界同仁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
2014年,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发展与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先生被授予“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他随即拿出奖金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奖掖后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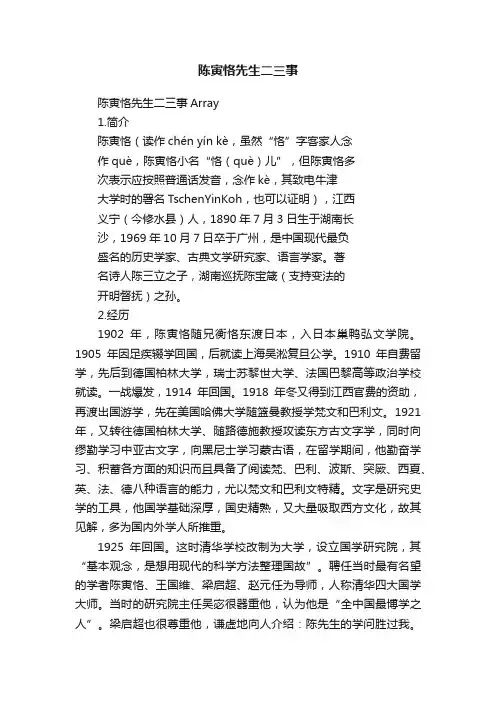
陈寅恪先生二三事陈寅恪先生二三事Array1.简介陈寅恪(读作chén yín kè,虽然“恪”字客家人念作què,陈寅恪小名“恪(què)儿”,但陈寅恪多次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其致电牛津大学时的署名TschenYinKoh,也可以证明),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
2.经历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一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回国。
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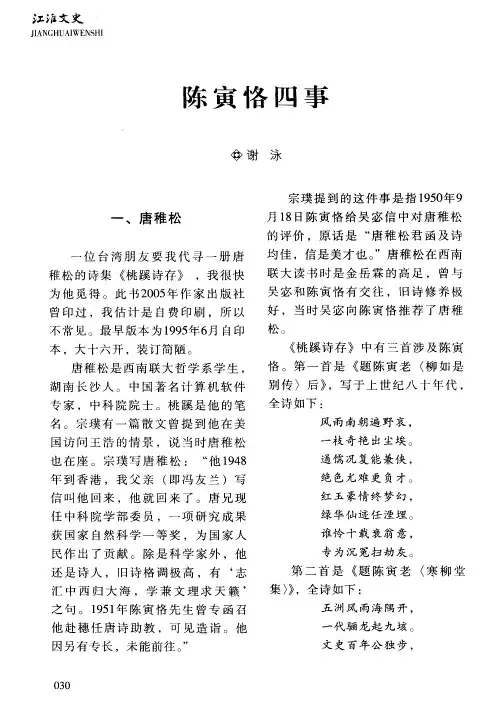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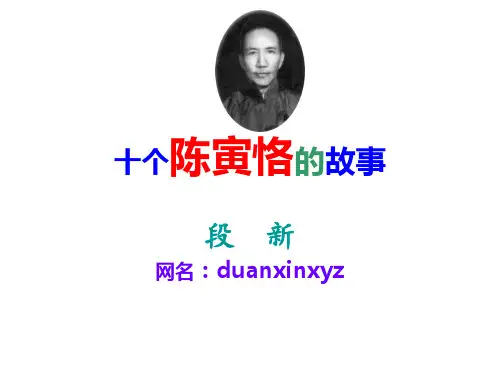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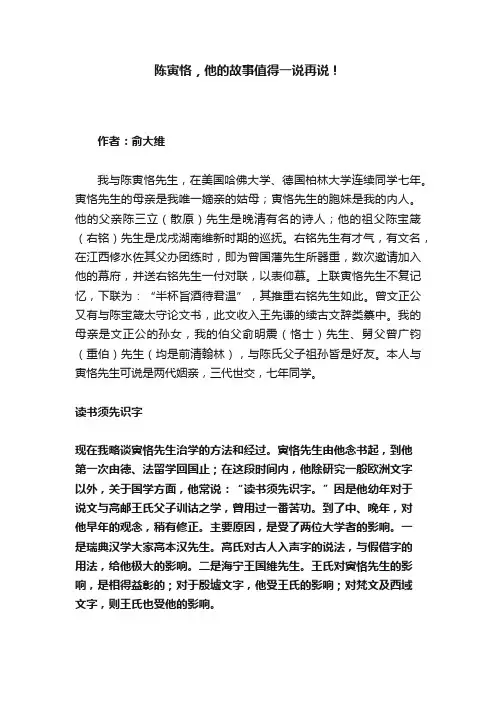
陈寅恪,他的故事值得一说再说!作者:俞大维我与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
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我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
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
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付对联,以表仰慕。
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
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
我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我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
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读书须先识字现在我略谈寅恪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经过。
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
”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
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
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
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
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
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
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在史中求史识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
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
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
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
”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
此外,对于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严谨而不偏狭我们对传统的典籍,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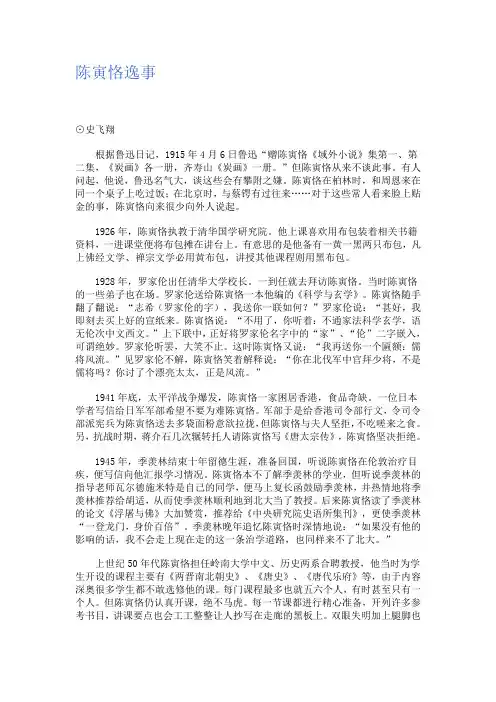
陈寅恪逸事⊙史飞翔根据鲁迅日记,1915年4月6日鲁迅“赠陈寅恪《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但陈寅恪从来不谈此事。
有人问起,他说,鲁迅名气大,谈这些会有攀附之嫌。
陈寅恪在柏林时,和周恩来在同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在北京时,与蔡锷有过往来……对于这些常人看来脸上贴金的事,陈寅恪向来很少向外人说起。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台上。
有意思的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包,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
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一到任就去拜访陈寅恪。
当时陈寅恪的一些弟子也在场。
罗家伦送给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
陈寅恪随手翻了翻说:“志希(罗家伦的字),我送你一联如何?”罗家伦说:“甚好,我即刻去买上好的宣纸来。
陈寅恪说:“不用了,你听着: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上下联中,正好将罗家伦名字中的“家”、“伦”二字嵌入,可谓绝妙。
罗家伦听罢,大笑不止。
这时陈寅恪又说:“我再送你一个匾额:儒将风流。
”见罗家伦不解,陈寅恪笑着解释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太太,正是风流。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食品奇缺。
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陈寅恪。
军部于是给香港司令部行文,令司令部派宪兵为陈寅恪送去多袋面粉意欲拉拢,但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
另,抗战时期,蒋介石几次辗转托人请陈寅恪写《唐太宗传》,陈寅恪坚决拒绝。
1945年,季羡林结束十年留德生涯,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
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羡林的学业,但听说季羡林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是自己的同学,便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地将季羡林推荐给胡适,从而使季羡林顺利地到北大当了教授。
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更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
陈寅恪归葬庐山一波三折纪实作者:李国强来源:《世纪》2019年第04期34年无着落,陈寅恪落墓何处?2019年是陈寅恪先生离世50周年、归葬庐山的第16个年头,人们对先生的思念无尽,先生墓前鲜花常年不断,清明时节尤其多。
先生1969年10月7日殒于“文革”凄风苦雨中,2003年6月16日,即先生113岁冥诞之日葬于庐山植物园。
一条归葬路走了整整34年,让人感叹不已。
我涉入这件事,是主持江西省社科院、江西省社联工作的时候。
1994年春,省社联正在筹备召开“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其间,我同省诗词学会秘书长胡迎建接待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陈氏后裔陈伯虞,了解到陈家想把庐山陈三立故居松门别墅改建成纪念馆,修复南昌西山陈宝箴坟墓,将陈寅恪骨灰安葬在陈宝箴墓侧,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在我看来,这三件事,合情合理,件件是好事,件件应该办。
我还获悉,先生生前遗愿是葬于杭州西湖杨梅岭先君陈三立墓侧。
“文革”结束后,先生家人先奔杭州,陈情有关部门,但因“风景区不能建墓”而被拒绝。
前后10余年,西湖断桥难渡,这才有欲葬南昌西山之议。
1994年春夏,江西兴起赣文化研究热潮。
8月17日,我向时任省长吴官正汇报赣文化研究事宜,在汇报结束时谈及陈伯虞教授的三点想法,吴官正略加思索,说:“你写个报告给我。
”第二天,省社联将《关于修复陈宝箴陵墓、陈三立庐山故居的报告》递呈省政府。
报告说: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一家三代,为著名爱国者,在中国近代史、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海内外均有重大影响。
省内一批学者曾联名于去年报告省文物局,建议在西山修复陈宝箴陵墓,在陈三立故居设陈列室,以增加江西旅游文化景点。
今年9月,我会将会同省诗词学会、省政协学习文史委等单位共同举办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
这有利于增强江西对境外赣胞的凝聚力,对促进江西对外开放,繁荣学术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大有好处。
此数项内容,得到陈氏后裔的大力支持,并希望能将陈寅恪骨灰从广州迁葬于西山。
宿迁市2021年高二上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I)卷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一、选择题 (共3题;共6分)1. (2分)下面语段中划线的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武侠小说《紫灵》有这样一个情节:“……他们这些无所不为而存活在世上的残暴强盗,一个个仰面摔倒在地上,嘴里惨叫了几声,蹬了蹬两腿,结束了他们罪不容诛的一生。
他们哪一个人的手上不是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而恶贯满盈?今天得到这样的结果,真是罪有应得,不过也算是他们死得其所。
A . 无所不为B . 罪不容诛C . 罪有应得D . 死得其所2. (2分) (2020高一下·哈尔滨月考)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A . 给学区房降温,关键在于教育公平起决定作用,要深入推进教育改革,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优化学校布局,缩小学校之间教育质量和理念的差距。
B . 近年来,《战狼》《流浪地球》等一批精良艺术品质和积极价值取向的文艺作品受到观众广泛认可,这充分证明过硬品质是新时代文艺引领文化的基本条件。
C . 当前,以芬太尼类物质为代表的新型毒品来势凶猛,已在一些国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将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入管制,是中国政府处理毒品问题的创新性举措。
D . 中国的哲学蕴含于人伦日用之中,中国建筑处处体现着人伦秩序与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五千年前的中华文明正是良渚大量建筑遗址的见证者。
3. (2分)下面四个句子中,语言表达不得体的一项是()A . 电视连续剧《东方朔》中,东方朔在参见了太后和皇上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这对夫妻,长期生活在乡下,有点拘束,请多多见谅他们。
”B . 作家张贤亮看到编辑给他的传真后,回复说:“我作品中疏忽之处绝对不止这些,有时偶然翻阅就有发现,谢谢!希望常指教!”C . 一公司主管给职员介绍一种推销经验:“这方法我用过,而且很有效,你也可以试试看。
”D . 夏泉在给老师汤开建编纂的文集的序言中说:“1998年暨南大学获得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翌年我忝列门墙,成为先生首届博士生。
回忆陈寅恪先生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清华大学算起。
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
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也是很富裕的。
除了选修课以外,学生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其他课程。
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
他的分析细致入微,如剥蕉心,愈剥愈细、愈剥愈深。
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最终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
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
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
前者就是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
我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寅恪师的接触并不太多。
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会见到寅恪师去上课。
他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
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
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光可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
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
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
到了那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
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
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二三事Array1.简介陈寅恪(读作chén yín kè,虽然“恪”字客家人念作què,陈寅恪小名“恪(què)儿”,但陈寅恪多次表示应按照普通话发音,念作kè,其致电牛津大学时的署名TschenYinKoh,也可以证明),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
2.经历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一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回国。
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
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
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3.学术成就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
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4.品性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
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解放后,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
”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出版。
5.治学理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
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尊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
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
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遂不能就任。
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6.评价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论语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
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
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石泉访谈录》: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产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
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死后评价: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
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
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学术老人留给世界的隐语。
文革后,陈寅恪与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上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钱钟书对陈寅恪的评价片段:钱先生对陈先生“酷评”:“不学之失”、“言考据而不解辞章者”、“fanciful literal-mindedness(很能空想但是又关注字面意思的心态)”、“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考《会真记》者”、“迂谬可笑”、“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柳传)适足令通人齿冷耳”、“目盲心苦,竭学之博,思之巧,以成就识之昧”……。
钱自己是这样说的:“我和陈先生从来未谈过话,二十七八年前,他忽然寄信给我夸奖《谈艺录》,并赠《元白诗笺》一本,我回信谢了。
我和他的交往仅限于此。
虽然他父亲和我父亲是有些交情的,但我一向不敢高攀名流,错过了想他请教的机会。
我很佩服他的博学,而对于他的思想始终抵触。
”(个人认为,钱钟书先生的评价仅限于文人之争,譬如“古诗是否可为史”之类的学问之争,对于钱钟书的评价,陈寅恪若有知,大概也只会一笑置之。
)7.陈寅恪语《编年事辑》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
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
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8.传记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9.陈寅恪与王国维1925年,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但是此时其身尚在德国,归国后又忙于家事,直到次年秋才到清华任教。
不久陈、王二位成为邻居,因为见识趣味相契,常常一起谈论古今,遂成为知交好友。
陈寅恪的挽词正文中说“回思寒夜话昌明,相对南冠泣数行”,正是对这段交情的回顾。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同仁们都怀念不已,两年后有学生为其立碑以寄托心意,请陈寅恪撰写碑铭,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
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碑文中陈寅恪三次提到学者对独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已经不仅是在悼念王国维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象出近代学者的一种新的人格理想,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是陈寅恪先生自己对学术界影响最为深刻的一种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