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2019年文档资料
- 格式:docx
- 大小:16.89 KB
- 文档页数: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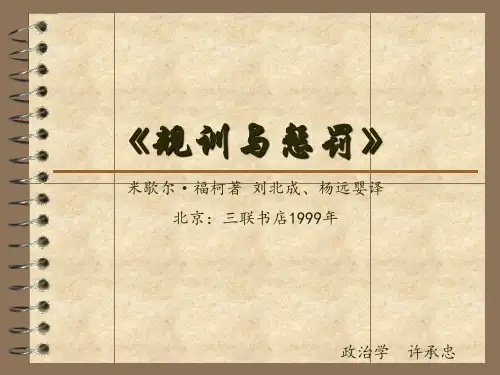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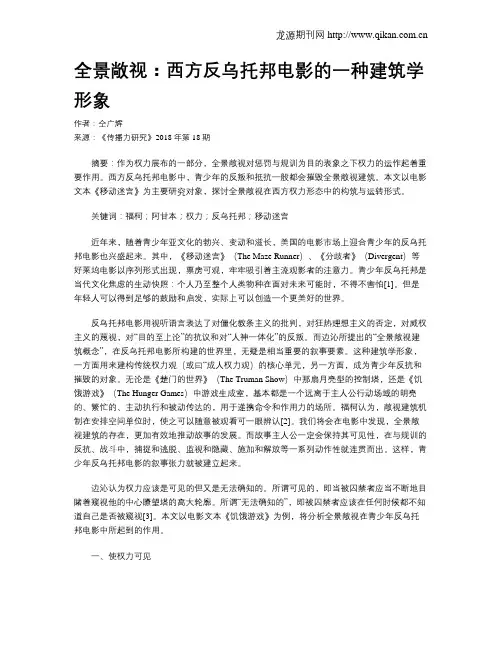
全景敞视:西方反乌托邦电影的一种建筑学形象作者:仝广辉来源:《传播力研究》2018年第18期摘要:作为权力展布的一部分,全景敞视对惩罚与规训为目的表象之下权力的运作起着重要作用。
西方反乌托邦电影中,青少年的反叛和抵抗一般都会摧毁全景敞视建筑。
本文以电影文本《移动迷宫》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全景敞视在西方权力形态中的构筑与运转形式。
关键词:福柯;阿甘本;权力;反乌托邦;移动迷宫近年来,随着青少年亚文化的勃兴、变动和滋长,美国的电影市场上迎合青少年的反乌托邦电影也兴盛起来。
其中,《移动迷宫》(The Maze Runner)、《分歧者》(Divergent)等好莱坞电影以序列形式出现,票房可观,牢牢吸引着主流观影者的注意力。
青少年反乌托邦是当代文化焦虑的生动快照: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物种在面对未来可能时,不得不害怕[1]。
但是年轻人可以得到足够的鼓励和启发,实际上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反乌托邦电影用视听语言表达了对僵化教条主义的批判,对狂热理想主义的否定,对威权主义的蔑视,对“目的至上论”的抗议和对“人神一体化”的反叛。
而边沁所提出的“全景敞视建筑概念”,在反乌托邦电影所构建的世界里,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叙事要素。
这种建筑学形象,一方面用来建构传统权力观(或曰“成人权力观)的核心单元,另一方面,成为青少年反抗和摧毁的对象。
无论是《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中那扇月亮型的控制塔,还是《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中游戏生成室,基本都是一个远离于主人公行动场域的明亮的、繁忙的、主动执行和被动传达的,用于递携命令和作用力的场所。
福柯认为,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随意被观看可一眼辨认[2]。
我们将会在电影中发现,全景敞视建筑的存在,更加有效地推动故事的发展。
而故事主人公一定会保持其可见性,在与规训的反抗、战斗中,捕捉和逃脱、监视和隐藏、施加和解放等一系列动作性就连贯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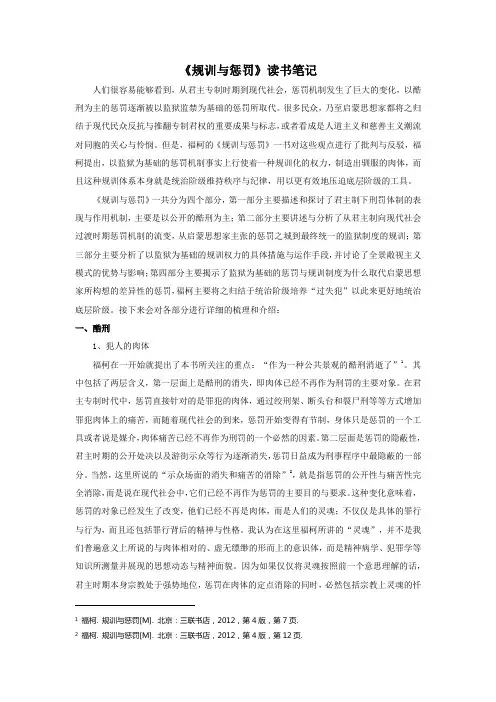
《规训与惩罚》读书笔记人们很容易能够看到,从君主专制时期到现代社会,惩罚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酷刑为主的惩罚逐渐被以监狱监禁为基础的惩罚所取代。
很多民众,乃至启蒙思想家都将之归结于现代民众反抗与推翻专制君权的重要成果与标志,或者看成是人道主义和慈善主义潮流对同胞的关心与怜悯。
但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判与反驳,福柯提出,以监狱为基础的惩罚机制事实上行使着一种规训化的权力,制造出驯服的肉体,而且这种规训体系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维持秩序与纪律,用以更有效地压迫底层阶级的工具。
《规训与惩罚》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述和探讨了君主制下刑罚体制的表现与作用机制,主要是以公开的酷刑为主;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与分析了从君主制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惩罚机制的流变,从启蒙思想家主张的惩罚之城到最终统一的监狱制度的规训;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以监狱为基础的规训权力的具体措施与运作手段,并讨论了全景敞视主义模式的优势与影响;第四部分主要揭示了监狱为基础的惩罚与规训制度为什么取代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差异性的惩罚,福柯主要将之归结于统治阶级培养“过失犯”以此来更好地统治底层阶级。
接下来会对各部分进行详细的梳理和介绍:一、酷刑1、犯人的肉体福柯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本书所关注的重点:“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逝了”1。
其中包括了两层含义,第一层面上是酷刑的消失,即肉体已经不再作为刑罚的主要对象。
在君主专制时代中,惩罚直接针对的是罪犯的肉体,通过绞刑架、断头台和裂尸刑等等方式增加罪犯肉体上的痛苦,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惩罚开始变得有节制,身体只是惩罚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是媒介,肉体痛苦已经不再作为刑罚的一个必然的因素。
第二层面是惩罚的隐蔽性,君主时期的公开处决以及游街示众等行为逐渐消失,惩罚日益成为刑事程序中最隐蔽的一部分。
当然,这里所说的“示众场面的消失和痛苦的消除”2,就是指惩罚的公开性与痛苦性完全消除,而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它们已经不再作为惩罚的主要目的与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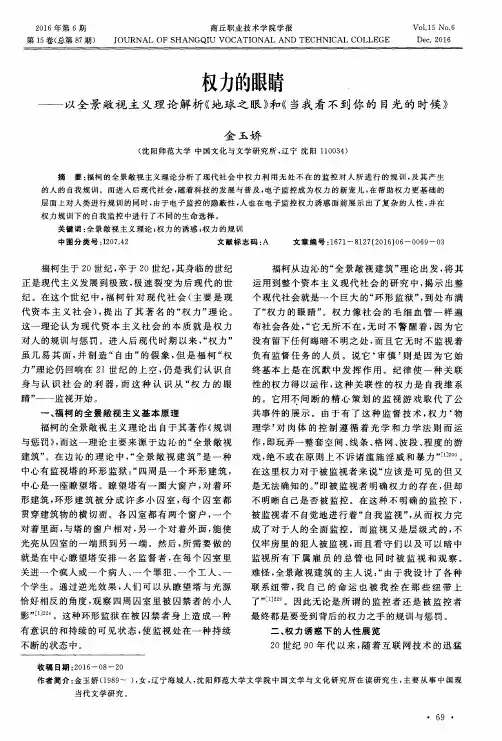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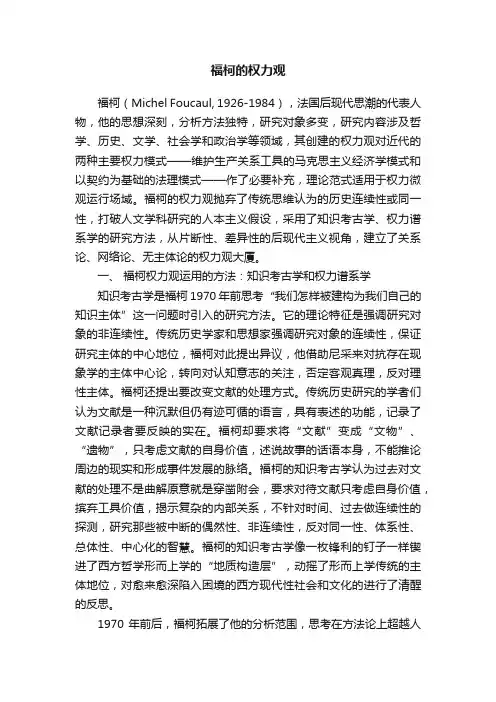
福柯的权力观福柯(Michel Foucaul, 1926-1984),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深刻,分析方法独特,研究对象多变,研究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其创建的权力观对近代的两种主要权力模式——维护生产关系工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模式和以契约为基础的法理模式——作了必要补充,理论范式适用于权力微观运行场域。
福柯的权力观抛弃了传统思维认为的历史连续性或同一性,打破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本主义假设,采用了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的研究方法,从片断性、差异性的后现代主义视角,建立了关系论、网络论、无主体论的权力观大厦。
一、福柯权力观运用的方法: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知识考古学是福柯1970年前思考“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我们自己的知识主体”这一问题时引入的研究方法。
它的理论特征是强调研究对象的非连续性。
传统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强调研究对象的连续性,保证研究主体的中心地位,福柯对此提出异议,他借助尼采来对抗存在现象学的主体中心论,转向对认知意志的关注,否定客观真理,反对理性主体。
福柯还提出要改变文献的处理方式。
传统历史研究的学者们认为文献是一种沉默但仍有迹可循的语言,具有表述的功能,记录了文献记录者要反映的实在。
福柯却要求将“文献”变成“文物”、“遗物”,只考虑文献的自身价值,述说故事的话语本身,不能推论周边的现实和形成事件发展的脉络。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过去对文献的处理不是曲解原意就是穿凿附会,要求对待文献只考虑自身价值,摈弃工具价值,揭示复杂的内部关系,不针对时间、过去做连续性的探测,研究那些被中断的偶然性、非连续性,反对同一性、体系性、总体性、中心化的智慧。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像一枚锋利的钉子一样锲进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地质构造层”,动摇了形而上学传统的主体地位,对愈来愈深陷入困境的西方现代性社会和文化的进行了清醒的反思。
1970年前后,福柯拓展了他的分析范围,思考在方法论上超越人文科学中主体与客体、经验与先验、我思与非思、起源的隐退与返回之间的二元对立,引入把握事物“差异”的权力谱系学,它标志着福柯从对理论和知识的考古学研究转向对社会制度和话语权力的系谱学研究,从知识轴线转到了权力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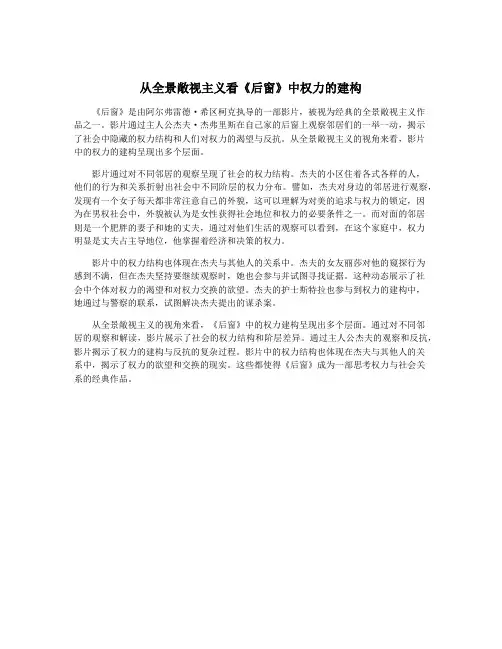
从全景敞视主义看《后窗》中权力的建构《后窗》是由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的一部影片,被视为经典的全景敞视主义作品之一。
影片通过主人公杰夫·杰弗里斯在自己家的后窗上观察邻居们的一举一动,揭示了社会中隐藏的权力结构和人们对权力的渴望与反抗。
从全景敞视主义的视角来看,影片中的权力的建构呈现出多个层面。
影片通过对不同邻居的观察呈现了社会的权力结构。
杰夫的小区住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的行为和关系折射出社会中不同阶层的权力分布。
譬如,杰夫对身边的邻居进行观察,发现有一个女子每天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貌,这可以理解为对美的追求与权力的锁定,因为在男权社会中,外貌被认为是女性获得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必要条件之一。
而对面的邻居则是一个肥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通过对他们生活的观察可以看到,在这个家庭中,权力明显是丈夫占主导地位,他掌握着经济和决策的权力。
影片中的权力结构也体现在杰夫与其他人的关系中。
杰夫的女友丽莎对他的窥探行为感到不满,但在杰夫坚持要继续观察时,她也会参与并试图寻找证据。
这种动态展示了社会中个体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交换的欲望。
杰夫的护士斯特拉也参与到权力的建构中,她通过与警察的联系,试图解决杰夫提出的谋杀案。
从全景敞视主义的视角来看,《后窗》中的权力建构呈现出多个层面。
通过对不同邻居的观察和解读,影片展示了社会的权力结构和阶层差异。
通过主人公杰夫的观察和反抗,影片揭示了权力的建构与反抗的复杂过程。
影片中的权力结构也体现在杰夫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揭示了权力的欲望和交换的现实。
这些都使得《后窗》成为一部思考权力与社会关系的经典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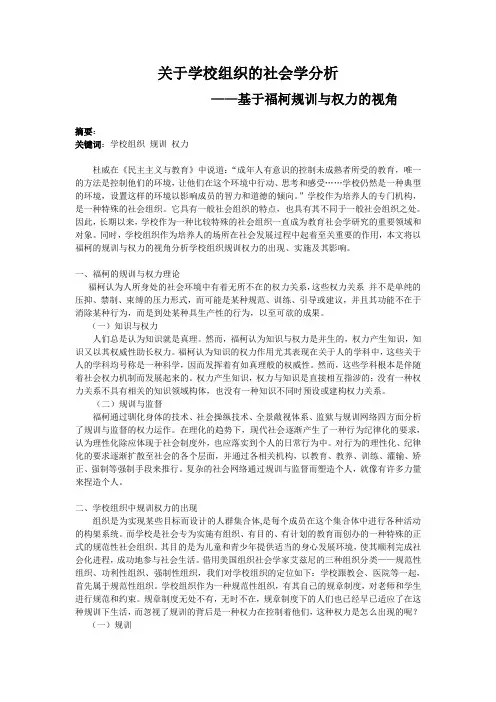
关于学校组织的社会学分析——基于福柯规训与权力的视角摘要:关键词:学校组织规训权力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说道:“成年人有意识的控制未成熟者所受的教育,唯一的方法是控制他们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环境中行动、思考和感受……学校仍然是一种典型的环境,设置这样的环境以影响成员的智力和道德的倾向。
”学校作为培养人的专门机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
它具有一般社会组织的特点,也具有其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之处。
因此,长期以来,学校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组织一直成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对象。
同时,学校组织作为培养人的场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福柯的规训与权力的视角分析学校组织规训权力的出现、实施及其影响。
一、福柯的规训与权力理论福柯认为人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中有着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压抑、禁制、束缚的压力形式,而可能是某种规范、训练、引导或建议,并且其功能不在于消除某种行为,而是到处某种具生产性的行为,以至可欲的成果。
(一)知识与权力人们总是认为知识就是真理。
然而,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是并生的,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又以其权威性助长权力。
福柯认为知识的权力作用尤其表现在关于人的学科中,这些关于人的学科均号称是一种科学,因而发挥着有如真理般的权威性。
然而,这些学科根本是伴随着社会权力机制而发展起来的。
权力产生知识,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没有一种权力关系不具有相关的知识领域构体,也没有一种知识不同时预设或建构权力关系。
(二)规训与监督福柯通过驯化身体的技术、社会操纵技术、全景敞视体系、监狱与规训网络四方面分析了规训与监督的权力运作。
在理化的趋势下,现代社会逐渐产生了一种行为纪律化的要求,认为理性化除应体现于社会制度外,也应落实到个人的日常行为中。
对行为的理性化、纪律化的要求逐渐扩散至社会的各个层面,并通过各相关机构,以教育、教养、训练、灌输、矫正、强制等强制手段来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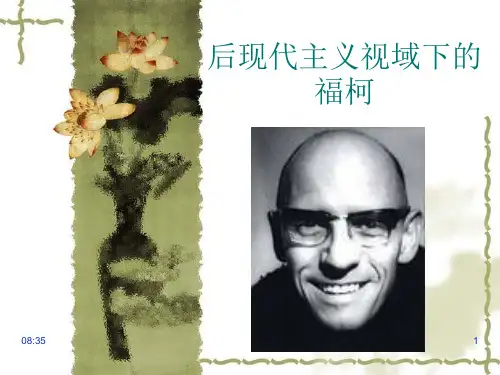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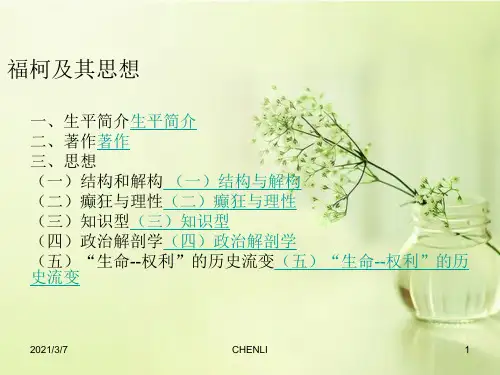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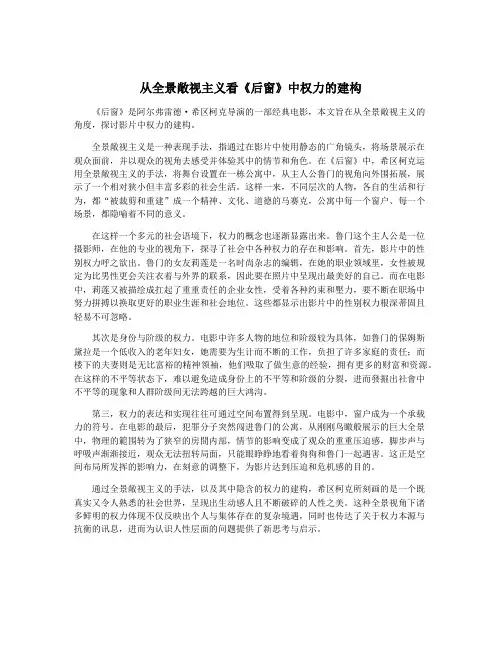
从全景敞视主义看《后窗》中权力的建构《后窗》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导演的一部经典电影,本文旨在从全景敞视主义的角度,探讨影片中权力的建构。
全景敞视主义是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在影片中使用静态的广角镜头,将场景展示在观众面前,并以观众的视角去感受并体验其中的情节和角色。
在《后窗》中,希区柯克运用全景敞视主义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一栋公寓中,从主人公鲁门的视角向外围拓展,展示了一个相对狭小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这样一来,不同层次的人物,各自的生活和行为,都“被裁剪和重建”成一个精神、文化、道德的马赛克,公寓中每一个窗户、每一个场景,都隐喻着不同的意义。
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语境下,权力的概念也逐渐显露出来。
鲁门这个主人公是一位摄影师,在他的专业的视角下,探寻了社会中各种权力的存在和影响。
首先,影片中的性别权力呼之欲出。
鲁门的女友莉莲是一名时尚杂志的编辑,在她的职业领域里,女性被规定为比男性更会关注衣着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要在照片中呈现出最美好的自己。
而在电影中,莉莲又被描绘成扛起了重重责任的企业女性,受着各种约束和壓力,要不断在职场中努力拼搏以换取更好的职业生涯和社会地位。
这些都显示出影片中的性别权力根深蒂固且轻易不可忽略。
其次是身份与阶级的权力。
电影中许多人物的地位和阶级较为具体,如鲁门的保姆斯黛拉是一个低收入的老年妇女,她需要为生计而不断的工作,负担了许多家庭的责任;而楼下的夫妻则是无比富裕的精神领袖,他们吸取了做生意的经验,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
在这样的不平等状态下,难以避免造成身份上的不平等和阶级的分裂,进而發掘出社會中不平等的现象和人群阶级间无法跨越的巨大鸿沟。
第三,权力的表达和实现往往可通过空间布置得到呈现。
电影中,窗户成为一个承载力的符号。
在电影的最后,犯罪分子突然闯进鲁门的公寓,从刚刚鸟瞰般展示的巨大全景中,物理的範围转为了狭窄的房間内部,情节的影响变成了观众的重重压迫感,脚步声与呼吸声渐渐接近,观众无法扭转局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狗狗和鲁门一起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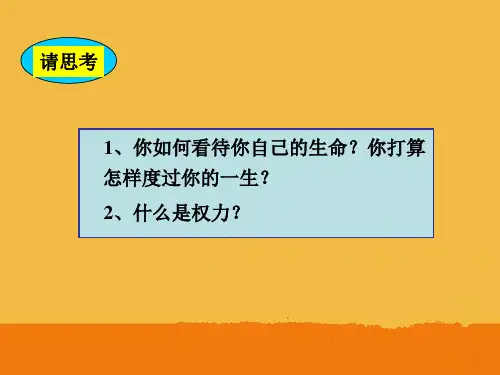
1 课堂报告 福柯 福柯是法国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在多所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和心理学教授,并于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教授,直至逝世。他对文学理论、哲学、艺术、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科学史(尤其是医学史)都有很大的影响。关于他有一个著名的评价,来自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福柯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一 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是对知识如何成为知识进行的一种历史分析。具体说来,这里的“知识”指的是特定的话语作为某个整体形成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的方式。一种知识要想成为可能,首先要有特定类型的问题,接着社会要承认这些问题的合法性,然后才能形成某些关于这个问题的知识。而“考古学”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研究领域,它考察并分析历史上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考古学关注的是各种客体,即那些从过去遗留下来的“沉默”的事物,以此来摆脱主体的统治。具体说来,考古学的对象不是隐藏在书籍或者语言中的内容,而是那些书籍或者语言是根据什么样的规则(往往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无意识的结构)写出来或者讲出来的。对于书籍或者语言的内容的关注,其实是一种对主体的关注,这是和现代性相联系的。福柯反对把主体做为一种本质的、内在起作用的中心,也不把它作为理解问题的最终的寻求。因此,他把作为客体或对象的话语事件和作为主体的投身于事件的人们分离开来。 福柯强调了知识考古学和观念史的不同,论述了四个区分二者的原则:一是观念史关注隐藏于话语中的思想、主题、意义等,而知识考古学关注话语本身,而不把话语当作某种中介。二是观念史制造了某种连续性,把各种话语整合进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去,而知识考古学注重差异和矛盾,关注断裂而不是连续。三是观念史关注作品的内容和作者,而知识考古学关注的是构建这种内容的条件和规则,即各种话语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四是观念史探寻观念的起源,而知识考古学只关注过程,对话语进行系统性描述。 在《事物的秩序》一书中,福柯的历史分析的重点是西方文化中认识论的两个重大的改变:一是17世纪中期开始的古典时代,二是19世纪初开始的近代。这两个转变并不代表着进步,而只是人们的观念模式(即知识型)发生了变化。在16世纪人们认为经验世界是由“一整套复杂的亲密关系、相似事物和亲和作用”所组成的。比如关于植物与动物,大地与海洋的描述,月亮和太阳像人的眼睛等等。此时的话语都直接表达或描述着外在事物,人们用笼统、未分化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而17世纪,人们根据事物不同的表现来把他们分门别类,注重事物的特征与差异,用分析的方法代替了之前的类比方法,构思出一个“秩序井然的表格”,“赋予事物名字,并用那个名字来命名他们的存在”。到了18、19世纪,人成为了思想的中心,此时的特点是崇尚历史分析,关注人性。比如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开始考虑生产者的因素。而人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的客体,这就导致的人的二元分裂。福柯认为,现在的人,作为一个概念,在18世纪以前并不存在,将来或许也会消失,即所谓的“人之死”。这里是指近代以来构筑的人的概念将要终结。因为作为现代“人”的概念是由时代和社会环境构建的,这种“人”的行为方式、思考方式、各种感觉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各种因素不断作用形成的,福柯认为应该走出现代意义上的这种“人”的概念。 2
观看的权力——福柯权力观中的监视理论党西民【摘要】福柯考察了古典社会中的视觉问题,认为视觉会产生权力,造成观看者和被看者之间权力的不平衡性。
他以古典社会的全景敞视监狱为隐喻,说明人们受到无所不在的视觉机器的监视。
视觉机器有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资本,并设置了权力的分布,保证了观看者目光的权威性、强制性,拥有着话语阐释权。
%Foucault analyzes the vision issue in the ancient time,and realizes that the vision can produce power,which as a result forms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watcher and the ing the classical prison panopticism as a metaphor,he advocates that people have been monitored under this ubiquitous vision machine.The vision machine has its support society and cultural capital and distributes its power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uthority,intimidation of sight of the watcher as well as the power to interpretation.【期刊名称】《宜宾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00)009【总页数】5页(P17-21)【关键词】观看者;目光;全景敞视;权力【作者】党西民【作者单位】深圳报业集团,深圳51803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565.59福柯非常关注权力的问题,即使在视觉方面也是如此。
他考察了古典时代视觉对人进行的规训,认为我们处在一个规训社会中,就连视觉也会对人产生如此的作用。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换而言之,监督建立在不断获取、更新被监督者的信息的基础上。
监督权力的细化、具体化都是为了更加容易地获取被监督者的信息,或者说所有的临时应急措施都是出于这种目的。
毋庸置疑,这种类似军事化的监管有助于政府对病情进行控制。
但是,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这些特殊时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断受到监视。
一旦情况对应于普遍的情况时, 我们发现监视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应对瘟疫这么简单了,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对我们进行监管?上一段提出的问题,福柯很早就给出了答案。
他认为,瘟疫发生时,社会容易陷入混乱,人群相互接触得越多疾病就容易传播。
监督作为一种把人群固定在寓所,把人群加以细分的手段, 正好是对抗这种混乱的方法。
引申开来,福柯认为,上述例子中的这种监督形式是“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形式。
”人类社会存在种种罪恶的行为,他们似乎乐于把社会拖入混乱之中, 规训机制是一种反向的拖动,它通过全方位的监视权力渗透来破除混乱。
接下来,福柯类比了麻风病人引起的驱逐和瘟疫引出的规训机制之间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的开头援引了中世纪麻风病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麻风病消失后仍然继续保持,这种影响就是对与主流相悖的异己的排斥和隔离。
麻风病不单单是一种可怕的瘟疫,还是一种强烈的象征,它通过可怕的麻风病病人形象引起人们的注意, 后来则延伸到价值 观等精神层面上。
排斥首先是一种二元区分, 人类整体被区分成 了两类人, 在各自的领域内却没有遭受进一步地细分, 在这种意 义上这种排斥的结果就是重新确立了一种混乱。
而瘟疫引发的规 训则不同, 它不是一种二元区分, 而是一种具体到每个人的多元 细分。
福柯列出的两者的不同,首先是“政治梦想”不同:驱逐 的那种二元区分树立了一种敌对, 但是在每个阵营内部却是“ 个纯洁的共同体”;而规训则相反。
再是在控制人员关系方面, 瘟疫所带来的规训社会中, 权力覆盖到了社会全体, 同时又不断 细化、具体化,是对瘟疫混乱状态的相反方向的假想。
两者存在种种不同, 但是却又是有联系的。
这两种不同的方 案后来逐渐混同起来。
首先,权力做出二元区分,并且标示出正 常/ 非正常、有害 / 无害等等。
接着,将规训机制的细化分割技术 应用带否定性的人群当中, 在原本是“纯洁的共同体”的内部进 行细分和隔离,并且对这些人群进行强制规定、安排。
这样原本 仅仅是驱逐的排斥机制加上了规训, 这种双重排斥机制的作用更 加强大,并且在现代社会也不例外。
以上福柯讨论了全景敞视主义的历史来源, 接下来他援引了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 通过具体、 物质的形式来说明了规训机制 中间高耸着一根类似 ?t 望塔的高大建筑, ?t 望 塔四周围着一圈环形建筑; 环形建筑被分割成很多小的囚室, 彼此之间并不能看到, 但是对着圆心方向的两扇窗户却敞开。
这种全景敞视建筑”的功能就是让囚犯暴露于隐藏的监视当中, 他 们知道自己受到监视, 但是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 同时犯人之 间的交流也被剥夺了。
犯人处于一座孤岛当中, 没有人可以交流、 没有人可以申诉, 但是在这座孤岛当中他并不是自由的, 监视者 像上帝那样拥有高空俯视视野,犯人的情况一览无遗,相反,犯 人却看不到如此“神迹”。
这种全景敞视建筑可以延伸开来, 仅仅适用于监狱建筑,也适用于工厂、学校、疯人院等等地。
这 是规训机制的绝对具体细分方法的尝试, 他把集体单位分割成了 无数细小的个体,让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交流。
此外,这种建筑的好处是为这些如此庞大的机构减少了人员 数量。
以监狱为例,犯人之间没有了交流,他们的人数优势就荡 然无存,他们跟狱警这个集体的力量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而且, 对犯人的监督和控制不再是肉体上的, 而是精神上的, 会让犯人 产生“监视者无所不在”的错觉。
显而易见, 从精神上加以控制 比肉体的惩罚更有成效。
同时,在现实中,一个监视者不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发挥作用的。
简要来说, 边沁设想了一种新型的监狱模型:24 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即使是用轮班制,也不可能保证一个人在工作时不开小差),监视权也有真空期,但是现在这一真空期的确存在,可是被监视者却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产生和结束,如此一来就在被监视者心里产生巨大的无形压力。
就这样,在一个监狱内、在一个学校内、在一个工厂内等等,虽然被监视者的数量大于监视者,但是通过这种简单的建筑学“奇迹”,就可以为这些机构解放大量人力并且减轻监视者的劳动量。
边沁抽离出具体的场景,概括了所有类似场合中权力普及 化、细化、绝对化的原则或条件:“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 法确知的。
”“可见”是树立权威,而“无法确知”是手段。
全景敞视建筑体现了由麻风病引发的排斥带来的那种二元对立状 态:“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 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
”到了这时候,权力不再体现在军队、富丽堂皇的典礼上,权 力被抽象成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一种权力结构。
这样的好处 是,不论什么人,只要在这套机制内,权力就可以自动发挥作用, 他对执行这套机制的人员并无苛刻的要求。
同时,不管出于什么 目的,光明正大的也好,邪恶卑鄙的也好,这套权力机制都会如 实地发挥作用。
处于其中的被监视者就像惊弓之鸟, 任何风吹草 动都会给他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福柯认为,全景敞视建筑除了监视作用, 还具有做社会实验 的功能。
在科学实验中,人们为了控制不同的变量,要对实验对 象(例如小白鼠)进行隔离、监控。
现在全景敞视建筑也具有这 种作用,它具有了验证假设的功能。
这样,权力就为知识的获取 提供了保障。
人们防范瘟疫而创立的种种临时机制与从此发展而来全景敞视建筑具有差异。
从瘟疫而制定的机制还比较原始, 仍旧处于想状态,它是现实中各种权利机制参照的象征。
边沁一开始把全 景敞视建筑运用于监狱,但是渐渐地它被利用到了各种场所,全景敞视建筑变成了一种主义、一种模式。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要 运用这种形式以保证权力的运行, 其条件是:“凡是与一群人打 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 可以使用全景敞视模式。
”全景敞视模式除了之前阐述的种种优点之外, 它还具有“从 不干预”、“自动施展”的好处。
其实也就是从对肉体的惩罚和 控制逐渐过渡到了对人们精神上的控制, 过渡之后的权力则更加 强力和有效。
仿佛权力机制自己有了生命力, 在效率和效能上都 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以往人们强调对肉体的控制和惩罚,但这仅 仅是一种从外界施压的手段, 往往会激起人?t 望 那种排斥麻风病的二元结构当中。
但是,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理们的反抗,效果因此也就不那么理想,同时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从瘟疫发展而来的运作权力的模式几乎都具有封闭的特性,因为封闭和隔离,权力才能渗透到极细微的地方,权力的效用才得以保证。
但是,全景敞视这种权力机制突破了这一点。
福柯认为,全景敞视机制的封闭性并非绝对的,或者说对于监视者来说是开放的。
福柯认为,这样的好处是这种全景敞视机制不会沦为暴政的机器,是保卫民主的强力武器。
与此同时,全景敞视权力机制的运用具有一种透明性,即是说监视者的身份不仅仅局限于原来那些人,它对社会上所有的人敞开了。
它使得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了解这种权力运行的方式和作用。
除此之外,被监视者的身份也就不再固定了,也敞开了。
这就使得所有人有可能既是监视者又是被监视者。
这种透明性的另一好处就是,在人们心中树立其权威和影响,它使得权力从人们的精神方面施加控制的力道又加强了。
全景敞视机制就这样普及到了全社会当中,它的威力加强了,但是它的手段却比之前的方式变得温和了。
福柯问,权力如何既加强自身的权威又可以不阻碍正常的社会运作呢?他的回答如下:“一方面,权力得以在社会的基础中以尽可能微妙的方式不听地运作,另一方面,权力是在那些与君权的行使相联系的突然、粗暴、不连贯的形式之外运作。
”在小范围地区(学校、军营、监狱等等)发展起来的种种规训机制,如何能在全社会领域内发挥作用?福柯区分了两种规训规训一封锁”和“规训一机制”。
前者原始,只能在某些小范围场景中适用,凝固,消极,封闭;而后者就是全景敞视机制,轻巧,灵便,高效。
从前者过渡到后者经历了一段时间,福柯认为西方社会在17、18 世纪的时候进入了后者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规训社会”。
福柯认为,至此,在规训社会中,规训的作用已经不是那种原始的作用了,而是变得更加积极。
规训或者纪律在学校中是为了防止学生开小差、迟到早退等等现象的发生,在工厂中是为了防止工人消极怠工,等等。
而现在,规训或纪律则是保证这些机构正常运行的必要保障了。
规训的防止消极影响的作用渐渐淡化,它的生产性功能得到了增强。
除了全景敞视主义向更多的非边缘地带的机构普及以外,其变。
为了达到规训的目的,各种新颖的手段也被不断发明。
也就是说,规训机构的功能不再单一了,它们所附带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一些机构所针对的人群往往是有限的和固定的,但是现在这些机构的规训或纪律也不断从这些中心人群向旁边辐射开来。
中的机制也并非总是条条框框和固定不变的,它们的形式变得多以警察部门为例,福柯认为,虽然权力机构是通过一个中枢从而调动整体进行运作,但是权力却遍及了所有极细微的地方。
福柯称之为“政治权力微分” [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40.] 。
这种警察机构拥有庞大的组织网络,其监视者或情报提供者已经不局限于警察,还包括“领赏钱的告密者”、“妓女”等等。
如同在当今警匪片中所看到的那样,福柯的观点至今仍旧适用。
在规训社会形成之前,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真空地带,这是一片无人看管的地区。
福柯认为,到了18 世纪的法国,这一区域的监控权被警察部门所掌握。
它把王权和地方权力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填补了空白。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原先一些不在法律职能范围内的不良事件”,现在也被纳入到监视体系中来了,发展到后来,人们的所有行为都受到了监控。
但是,福柯认为,规训或纪律的范围远远要大于警察部门的职能范围或任何一个别的什么机构。
正如前文所说的,规训是一种模式、一种结构,可以把它利用到任一机构上,这一机构就大大增强了它的监视特征,但是因此并不能说某一个就可以穷尽了规训,而仅仅只是其缩影罢了。
在古代社会,每个人都似乎隐藏在浓浓的迷雾后面,只有在某些场合(剧场、竞技场等等)少数人才变得夺人眼球。
至打规训社会,由于人群被绝对地分割了, 权力之网渗透进了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于是个人都浮出了水面, 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所遁形。
全景敞视建筑还被看成是一项技术发明,但是随着这种权力模式的向社会全面渗透,它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进程”了。
这使得我们不再需要竞技场、剧场了,个人的舞台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