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_梁启超
- 格式:doc
- 大小:40.00 KB
- 文档页数: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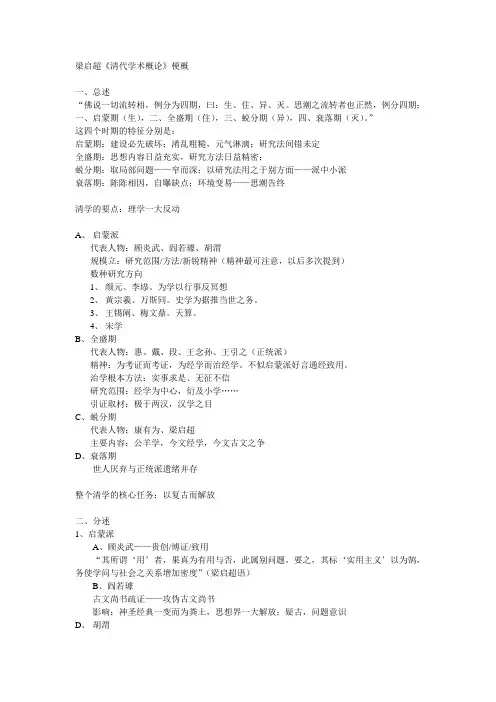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梗概一、总述“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为四期,曰:生、住、异、灭。
思潮之流转者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
”这四个时期的特征分别是:启蒙期:建设必先破坏;淆乱粗糙,元气淋漓;研究法间错未定全盛期:思想内容日益充实,研究方法日益精密;蜕分期:取局部问题——窄而深;以研究法用之于别方面——派中小派衰落期:陈陈相因,自曝缺点;环境变易——思潮告终清学的要点:理学一大反动A、启蒙派代表人物:顾炎武、阎若璩、胡渭规模立:研究范围/方法/新锐精神(精神最可注意,以后多次提到)数种研究方向1、颜元、李塨。
为学以行事反冥想2、黄宗羲、万斯同。
史学为据推当世之务。
3、王锡阐、梅文鼎。
天算。
4、宋学B、全盛期代表人物:惠、戴、段、王念孙、王引之(正统派)精神: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
不似启蒙派好言通经致用。
治学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研究范围: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引证取材:极于两汉,汉学之目C、蜕分期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主要内容:公羊学,今文经学,今文古文之争D、衰落期世人厌弃与正统派遗绪并存整个清学的核心任务:以复古而解放二、分述1、启蒙派A、顾炎武——贵创/博证/致用“其所谓‘用’者,果真为有用与否,此属别问题。
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梁启超语)B、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攻伪古文尚书影响:神圣经典一变而为粪土,思想界一大解放;疑古,问题意识D、胡渭易图明辨影响: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其途。
启蒙期之形成原因/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启蒙期多学派在全盛期中绝的原因2、全盛期A、惠栋治学特点: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纯汉学B、戴震梁启超对其方法论评价——科学之精神,也是清学之精神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戴氏哲学(非考证成就。
世人多有不知,故梁启超发“清代学派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之辞)清代考证学的价值和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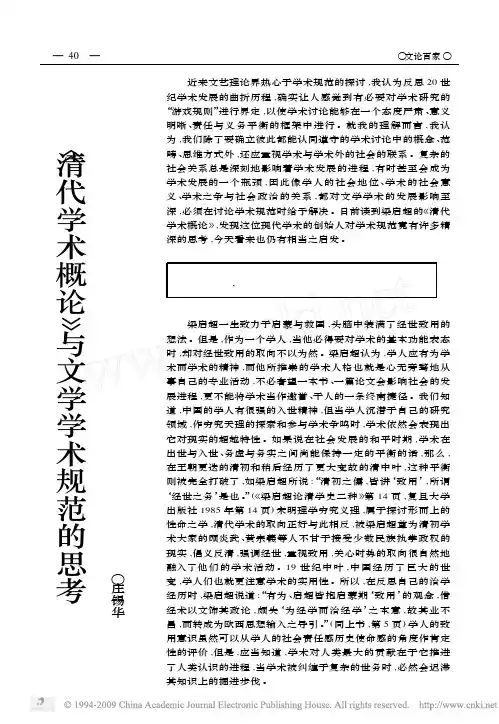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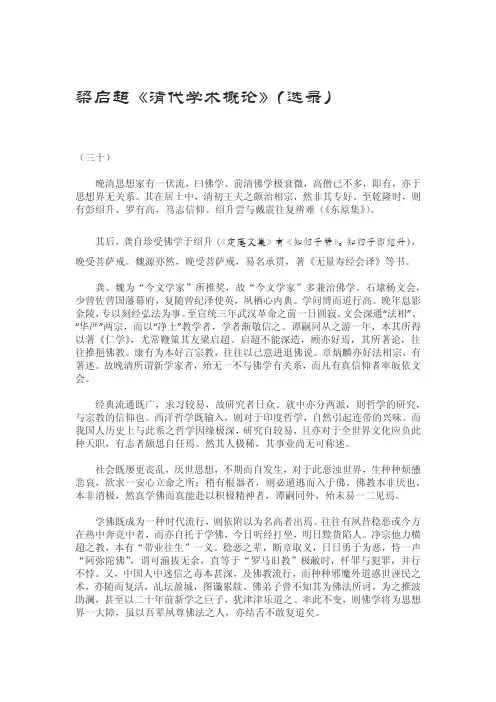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选录)(三十)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
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
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
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
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辨难(《东原集》)。
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
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
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
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
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
学问博而道行高。
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
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
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
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
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
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
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
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经典流通既广,求习较易,故研究者日众。
就中亦分两派,则哲学的研究,与宗教的信仰也。
西洋哲学既输入,则对于印度哲学,自然引起连带的兴味。
而我国人历史上与此系之哲学因缘极深,研究自较易,且亦对于全世界文化应负此种天职,有志者颇思自任焉。
然其人极稀,其事业尚无可称述。
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
佛教本非厌也,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学佛既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焉。
往往有夙昔稔恶或今方在热中奔竞中者,而亦自托于学佛,今日听经打坐,明日黩货陷人。
净宗他力横超之教,本有“带业往生”一义。
稔恶之辈,断章取义,日日勇于为恶,恃一声“阿弥陀佛”,谓可湔拔无余,直等于“罗马旧教”极敝时,忏罪与犯罪,并行不悖。
又,中国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种种邪魔外道惑世诬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乩坛盈城,图谶累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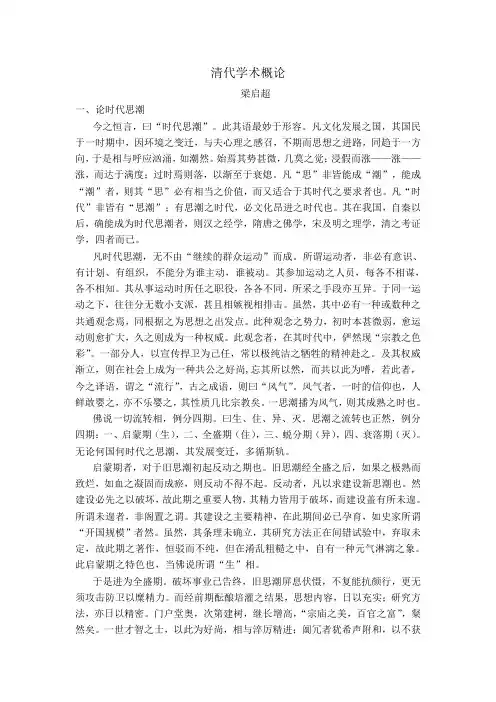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一、论时代思潮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
此其语最妙于形容。
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
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
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
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
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
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
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
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
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
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
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
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
曰生、住、异、灭。
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
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
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
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
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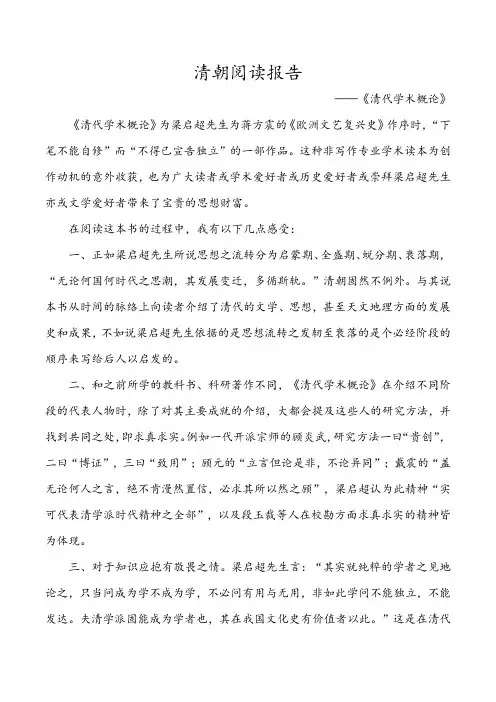
清朝阅读报告——《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学术概论》为梁启超先生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时,“下笔不能自修”而“不得已宣告独立”的一部作品。
这种非写作专业学术读本为创作动机的意外收获,也为广大读者或学术爱好者或历史爱好者或崇拜梁启超先生亦或文学爱好者带来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感受:一、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思想之流转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清朝固然不例外。
与其说本书从时间的脉络上向读者介绍了清代的文学、思想,甚至天文地理方面的发展史和成果,不如说梁启超先生依据的是思想流转之发轫至衰落的是个必经阶段的顺序来写给后人以启发的。
二、和之前所学的教科书、科研著作不同,《清代学术概论》在介绍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时,除了对其主要成就的介绍,大都会提及这些人的研究方法,并找到共同之处,即求真求实。
例如一代开派宗师的顾炎武,研究方法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顾元的“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戴震的“盖无论何人之言,绝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顾”,梁启超认为此精神“实可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以及段玉裁等人在校勘方面求真求实的精神皆为体现。
三、对于知识应抱有敬畏之情。
梁启超先生言:“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
夫清学派固能成为学者也,其在我国文化史有价值者以此。
”这是在清代启蒙运动、变法维新等倡导西学的运动热潮之下,仍然倡导“经世致用”的精神保障之一。
固然“学问非一派可尽”,但当术业有专攻,精益求精,不然学问不过流于肤浅,而不能成大器。
然而我整本书中喜欢的一句话却是朱维铮在导读中提到的梁启超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所倡导的不缠足运动的效应:“裹小脚的妇女抛弃裹脚布,固然是惊世骇俗的一种解放,而在倡导‘天足’的女权主义者看来,不再裹足的妇女依旧是‘小脚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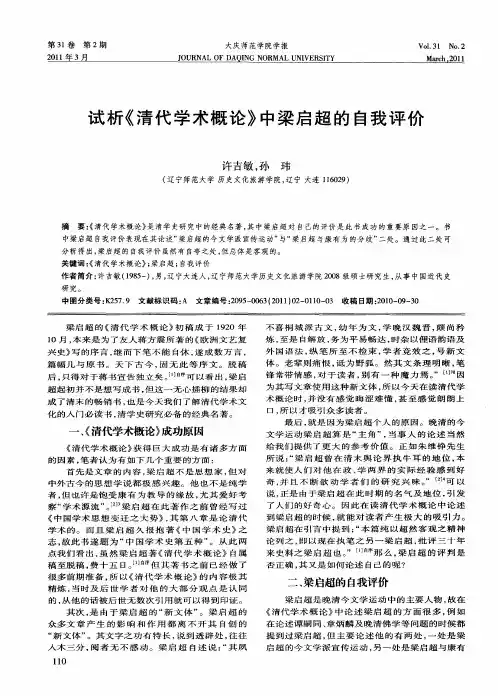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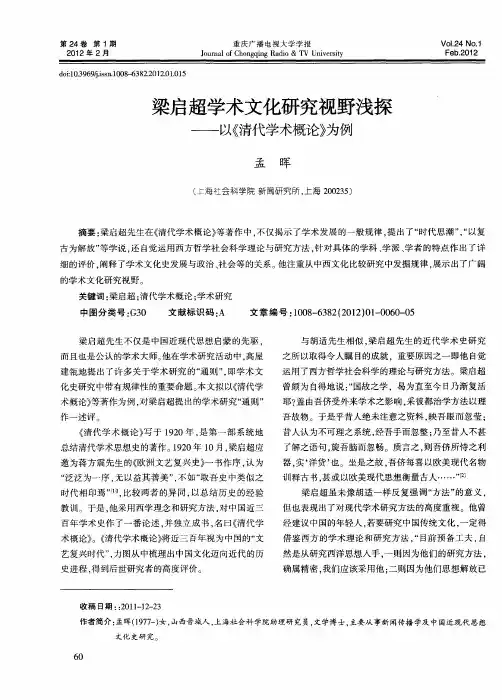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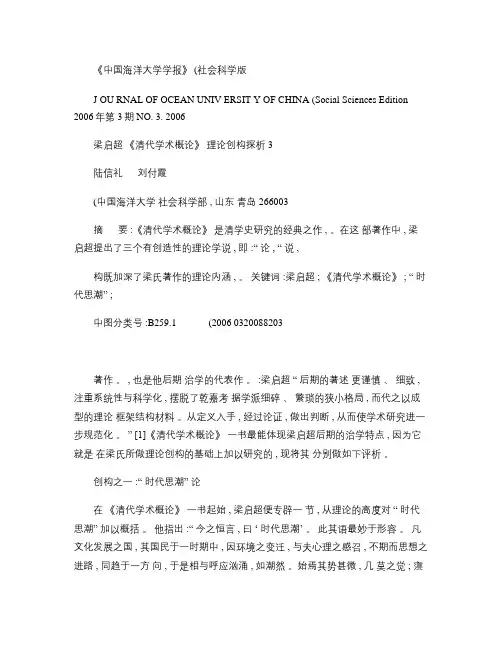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J OU RNAL OF OCEAN UNIV ERSIT 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6年第 3期 NO. 3. 200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理论创构探析 3陆信礼刘付霞(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 , 山东青岛 266003摘要 :《清代学术概论》是清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 。
在这部著作中 , 梁启超提出了三个有创造性的理论学说 , 即:“ 论, “ 说 ,构既加深了梁氏著作的理论内涵 , 。
关键词 :梁启超 ; 《清代学术概论》; “ 时代思潮” ;中图分类号 :B259.1 (2006 0320088203著作。
, 也是他后期治学的代表作。
:梁启超“ 后期的著述更谨慎、细致 , 注重系统性与科学化 , 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繁琐的狭小格局 , 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
从定义入手 , 经过论证 , 做出判断 , 从而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
” [1]《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最能体现梁启超后期的治学特点 , 因为它就是在梁氏所做理论创构的基础上加以研究的 , 现将其分别做如下评析。
创构之一:“ 时代思潮” 论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起始 , 梁启超便专辟一节 , 从理论的高度对“ 时代思潮” 加以概括。
他指出:“ 今之恒言 , 曰‘ 时代思潮’ 。
此其语最妙于形容。
凡文化发展之国 , 其国民于一时期中 , 因环境之变迁 , 与夫心理之感召 , 不期而思想之进路 , 同趋于一方向 , 于是相与呼应汹涌 , 如潮然。
始焉其势甚微 , 几莫之觉 ; 寖假而涨———涨——— , 而达于满度 ; 过时焉则落 , 以渐至于衰熄。
” 又说:“ 凡时代思潮 , 无不由‘ 继续的群众运动’ 而成。
所谓运动者 , 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 , 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
其参加运动之人员 , 每各不相谋 , 各不相知。
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 , 各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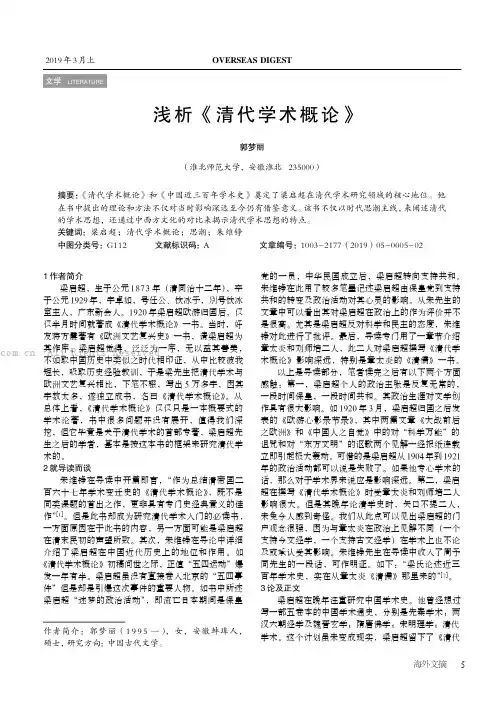
5海外文摘1 作者简介梁启超,生于公元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卒于公元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別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国后,仅仅半月时间就著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当时,好友蒋方震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其作序。
梁启超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于是梁先生把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下笔不辍,写出5万多字,因其字数太多,遂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从总体上看,《清代学术概论》仅仅只是一本概要式的学术论著,书中很多问题并没有展开,值得我们深挖,但它毕竟是关于清代学术的首部专著,梁启超先生之后的学者,基本是按这本书的框架来研究清代学术的。
2 就导读而谈朱维铮在导读中开篇即言,“作为总结清帝国二百六十七年学术变迁史的《清代学术概论》,既不是同类课题的首出之作,更非具有专门史经典意义的佳作”[1]。
但是此书却成为研究清代学术入门的必读书,一方面原因在于此书的内容,另一方面可能是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声望所致。
其次,朱维铮在导论中详细介绍了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如《清代学术概论》初稿问世之际,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一年有半。
梁启超虽没有直接卷入北京的“五四事件”但是却是引爆这次事件的重要人物。
如书中所述梁启超“迷梦的政治活动”,即流亡日本期间是保皇党的一员,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转向支持共和。
朱维铮在此用了较多笔墨记述梁启超由保皇党到支持共和的转变及政治活动对其心灵的影响。
从朱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其对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作为评价并不是很高。
尤其是梁启超反对科学和民主的态度,朱维铮对此进行了批评。
最后,导读专门用了一章节介绍章太炎和刘师培二人,此二人对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影响深远,特别是章太炎的《清儒》一书。
以上是导读部分,笔者读完之后有以下两个方面感触:第一,梁启超个人的政治主张是反复无常的,一段时间保皇,一段时间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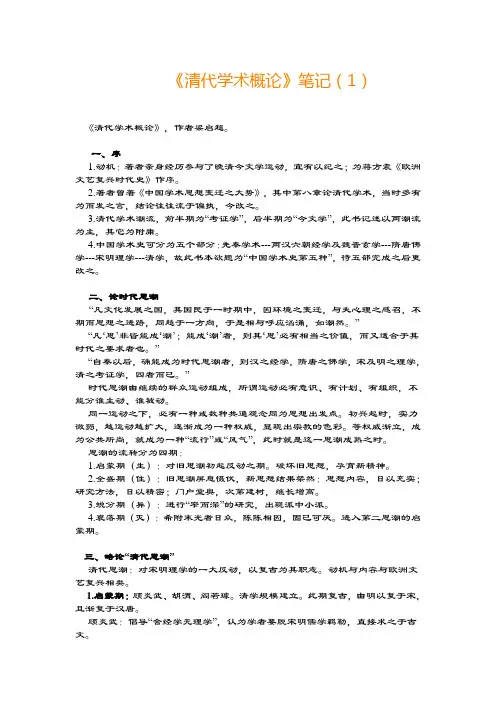
《清代学术概论》笔记(1)《清代学术概论》,作者梁启超。
一、序1.动机:著者亲身经历参与了晚清今文学运动,宜有以纪之;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
2.著者曾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第八章论清代学术,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结论往往流于偏执,今改之。
3.清代学术潮流,前半期为“考证学”,后半期为“今文学”,此书记述以两潮流为主,其它为附庸。
4.中国学术史可分为五个部分: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学,故此书本欲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待五部完成之后更改之。
二、论时代思潮“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时代思潮由继续的群众运动组成,所谓运动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谁主动、谁被动。
同一运动之下,必有一种或数种共通观念同为思想出发点。
初兴起时,实力微弱,越运动越扩大,逐渐成为一种权威,显现出宗教的色彩。
等权威渐立,成为公共所尚,就成为一种“流行”或“风气”,此时就是这一思潮成熟之时。
思潮的流转分为四期:1.启蒙期(生):对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
破坏旧思想,孕育新精神。
2.全盛期(住):旧思潮屏息慑伏,新思想结果粲然: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
3.蜕分期(异):进行“窄而深”的研究,出现派中小派。
4.衰落期(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
进入第二思潮的启蒙期。
三、略论“清代思潮”清代思潮: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以复古为其职志。
动机与内容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
1.启蒙期:顾炎武、胡渭、阎若璩。
清学规模建立。
此期复古,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现今治学的启示作者:李春燕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9期摘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轨迹清晰,脉络彰明,对清代学术史研究多有创获,而于学界影响深远。
虽然《清代学术概论》是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但通篇也贯穿着梁启超为学做研究坚持学术本位的基本态度,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保持思想独立而三者结合有所创获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这给我们当今治学提供了诸多启示,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学习。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治学;启示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9-0175-02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清帝国267年间学术的演进历程作了鸟瞰式的勾勒,轨迹清晰,脉络彰明,实在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一项伟大的创举。
此书是作者应邀为友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然正如作者自言“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1],历时仅15天,便成书付梓。
自1921年出版以来,大受欢迎,屡次再版而影响深远。
虽然《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作者率性之为,无心插柳之果,且篇幅短小,形式上亦不合后世之学术规范,然通篇著述轮廓清晰,思想独立,一气呵成,足见作者胸中宏阔之气象与厚积薄发之功力。
同时,他把清代学术史研究引向深入,为我们现今治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学习。
一、学术本位的治学态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把有清一代学术大致分为前半期考证学和后半期的今文学。
他极赞考证学派“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学术本位的治学态度,把其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归功于此。
认为“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而“学问即目的”,并无“有用无用之可言”。
即不图政治上的功利目的,不求思想上的新闻效应,“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2]。
恰若,晚期所谓“新学家”者,其治学之笼统、粗率、浅薄,根源便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
梁启超的学问意旨与学术人格黄永健摘要:梁启超一生以政治家始,以一个纯粹的学术人终,这固然未必是其本愿,但是从他一生都注重学术思想的巨大社会功能,从其唯心主义的思想立场及其文化淑世主义的人文理念等方面来考察,这其间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必然性。
梁启超做人做学问有其根本的且一以贯之的根本命意,这就是他的人格主义理想和宇宙情怀,在这个根本意旨之上,梁启超卓然自成一家,并形成了自别于他人,且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学术人格品性。
关键词:梁启超;人格主义;学问意旨;人格品性一、梁启超的学问意旨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精英,关于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和人格品性,历来有两种相反的判断,一者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和人生面目前后不一,正如他自己所说“保守性与进取性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
[1]”一者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和人格品性自有其内在的一贯性,如其文化思想中的爱国主义基调、文化调和主义倾向等[2],笔者在研读梁启超全集尤其是梁晚年[1]参见关健瑛:《试论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内在一贯性》,载《求是学刊》,1993年第3期,而16-20。
[2]参见关健瑛:《试论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内在一贯性》,载《求是学刊》,1993年第3期,而16-20。
[3]“人格主义”又称为“仁”的人生观,是一种自觉觉他,自渡渡人,自立立人,与人类全体和宇宙整体共同成就的人生观和实践观,梁启超谓“人格与宇宙无二无别”,“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人格主义的敢极目标在于“普遍人格之实现”,“要彼我交感成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
”达成这种大人格的途径在于知行合一,即第一,要认自然界和自己的生命为一体,第二,不靠冥著述,考察其一生行事的个性特征之后,认为梁启超的学问人格,文化立场和行为风范自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不管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梁启超还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的梁启超,抑或作为一个父师的梁启超及一个艺术家的梁启超,其人格立场和学问态度因有其内在的哲学根基作为支撑点而前后一贯,独立不移,梁启超晚年所撰之《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年12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及其所倡导的“人格主义”哲学立场[3],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平生学问立场和为人处世的总结和阐发,纵观其一生,从早年英才俊发意无反顾参与戊戌维新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到其中年鼓动舆论雷霆万钧天下为之风动,再至晚年潜心学问著述精博无涯,衡而论之,可以说梁启超作为思想转型时代的文化巨人,儒佛并施共济,中西—炉共冶,耽思竭虑知行合一,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自成格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一生都忙碌于政治斡旋和社会人际应酬的文化名流,能做到日写数千言,学术探索领域遍及思想史、政治、法律、地理学、哲学、宗教、艺术、训诂、目录学、学术史、方志学以至债券、数理等等,且创作诗歌、散文、小说不辍,在中国学术史上实所罕见。
西北大学研究生读书报告读梁启超先生《清代学术概论》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题专业:专门史学号:201120494姓名:姜明波院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任课教师:李江辉西北大学研究生院制读梁启超先生《清代学术概论》姜明波《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在其学术上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是一部阐述清代学术思潮源头及流变的经典著作,一经问世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欢迎并成为青年学子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之作。
早期开始接触历史学,只知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有很大的影响,而现在才知道先生在学术上也是有着极为深厚的造诣。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学于万木草堂。
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接受了今文经学的思路和学风,又于国学书籍外读了许多由传教士翻译的西学著述,这使他学问大长,眼界大开。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其在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欧游心影录》等。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于1920年旅欧回国后所完成的。
其在自序中说明著书目的时谈到,“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
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
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
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
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梁启超觉得,为好友泛泛的作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于是,他借题发挥,对比中西文化,对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作了一番议论。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一、论时代思潮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
此其语最妙于形容。
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
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
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
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
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
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
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
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
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
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
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
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
曰生、住、异、灭。
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
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
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
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
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
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
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
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
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
于是进为全盛期。
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慑,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
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
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
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
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
更进则入于蜕分期。
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
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
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
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
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
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
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
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
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
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
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
二、略论“清代思潮”“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
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
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
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
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
其一,颜元、李塨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瞑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
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
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
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
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迳路。
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
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
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
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皆有传于后。
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
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
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
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
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
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
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
开吴者惠,开皖者戴。
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
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
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春乔——等。
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
念孙以授其子引之。
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
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
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
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
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
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
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
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
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
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
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
当正统派全盛时,学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自珍最能传其学。
《公羊传》者,“今文学”也。
东汉时,本有今文古文之争,甚烈。
《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及《周官》,皆晚出,称古文,学者不信之。
至汉末而古文学乃盛。
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
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
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
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
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
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
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
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
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
千秋早卒。
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学。
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
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
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
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
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
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
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缺点益暴露。
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
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流于高邮王氏。
樾著书,惟二三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
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矣。
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业。
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
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
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
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
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
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九、由启蒙到全盛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
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
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
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
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
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
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
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余派则不盛,或全然中绝。
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其道大觳”,恐“天下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