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中国武侠电影的五次浪潮
- 格式:ppt
- 大小:16.63 MB
- 文档页数: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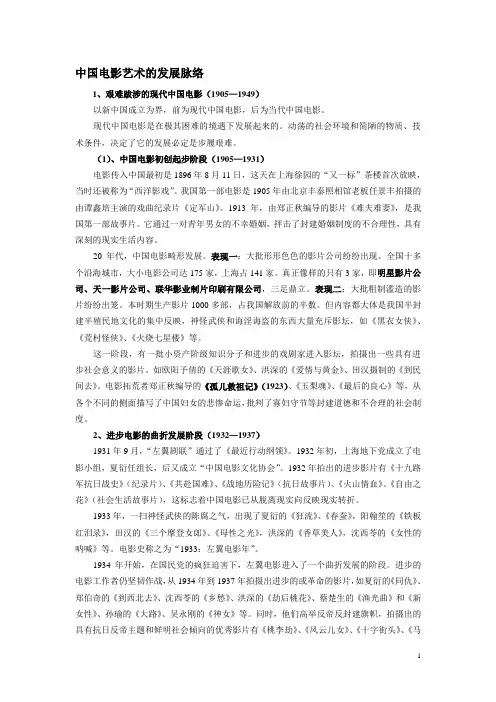
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脉络1、艰难跋涉的现代中国电影(1905—1949)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前为现代中国电影,后为当代中国电影。
现代中国电影是在极其困难的境遇下发展起来的。
动荡的社会环境和简陋的物质、技术条件,决定了它的发展必定是步履艰难。
(1)、中国电影初创起步阶段(1905—1931)电影传入中国最初是1896年8月11日,这天在上海徐园的“又一标”茶楼首次放映,当时还被称为“西洋影戏”。
我国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景丰拍摄的由谭鑫培主演的戏曲纪录片《定军山》。
1913年,由郑正秋编导的影片《难夫难妻》,是我国第一部故事片。
它通过一对青年男女的不幸婚姻,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具有深刻的现实生活内容。
20年代,中国电影畸形发展。
表现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影片公司纷纷出现。
全国十多个沿海城市,大小电影公司达175家,上海占141家。
真正像样的只有3家,即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三足鼎立。
表现二:大批粗制滥造的影片纷纷出笼。
本时期生产影片1000多部,占我国解放前的半数。
但内容都大体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集中反映,神怪武侠和诲淫诲盗的东西大量充斥影坛,如《黑衣女侠》、《荒村怪侠》、《火烧七星楼》等。
这一阶段,有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戏剧家进入影坛,拍摄出一些具有进步社会意义的影片。
如欧阳予倩的《天涯歌女》、洪深的《爱情与黄金》、田汉摄制的《到民间去》。
电影拓荒者郑正秋编导的《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最后的良心》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写了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批判了寡妇守节等封建道德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2、进步电影的曲折发展阶段(1932—1937)1931年9月,“左翼剧联”通过了《最近行动纲领》。
1932年初,上海地下党成立了电影小组,夏衍任组长,后又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
1932年拍出的进步影片有《十九路军抗日战史》(纪录片)、《共赴国难》、《战地历险记》(抗日故事片)、《火山情血》、《自由之花》(社会生活故事片),这标志着中国电影已从脱离现实向反映现实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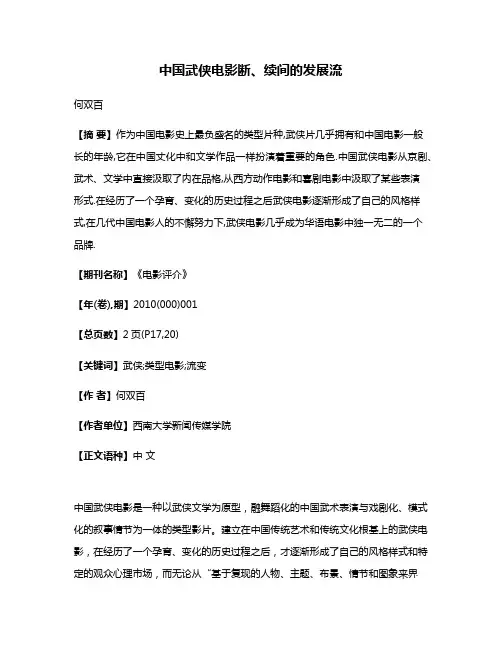
中国武侠电影断、续间的发展流何双百【摘要】作为中国电影史上最负盛名的类型片种,武侠片几乎拥有和中国电影一般长的年龄,它在中国丈化中和文学作品一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武侠电影从京剧、武术、文学中直接汲取了内在品格,从西方动作电影和喜剧电影中汲取了某些表演形式.在经历了一个孕育、变化的历史过程之后武侠电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样式,在几代中国电影人的不懈努力下,武侠电影几乎成为华语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一个品牌.【期刊名称】《电影评介》【年(卷),期】2010(000)001【总页数】2页(P17,20)【关键词】武侠;类型电影;流变【作者】何双百【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中国武术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
建立在中国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根基上的武侠电影,在经历了一个孕育、变化的历史过程之后,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样式和特定的观众心理市场,而无论从“基于复现的人物、主题、布景、情节和图象来界定”[1]或是从“三要素”[2]的定义来考查,都应该被视为初具类型表征的存在。
武侠片“类型程式”[3]的获取,主要采用的是从传统(民间和民俗化了的)历史传奇故事(戏文、评弹、评书、古典话本小说)中挪借化用的途径。
这些历史传奇历经承传所沉淀下来的核心程式。
[4]具有超常的稳定性,它“既作为美学约束,也作为含义的源泉而运作”[5]是重复生产炮制而无接受顾忌的基础性模本。
在此基础之上,武侠片创作又突出特别适合电影视觉表现的那些“微观细部”(诸如香艳逸事、趣味打闹、功、名、利、禄),由此达成了武侠片商业类型化的“装配”。
中国武侠电影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车中盗》为始,武侠电影在中国影史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所发展出的“武——舞”(武木套路化、表演化、循门派变化等)展示系统和一整套隐喻性的“对映\隔离”标志系统使武侠片表现的武林、门派、功夫、奇情……既完整地对映着社会、党派集团、行业营生、人世恋情……同时又可自主游离,甚至可以向志怪、志异(奇观化、神话化)的向度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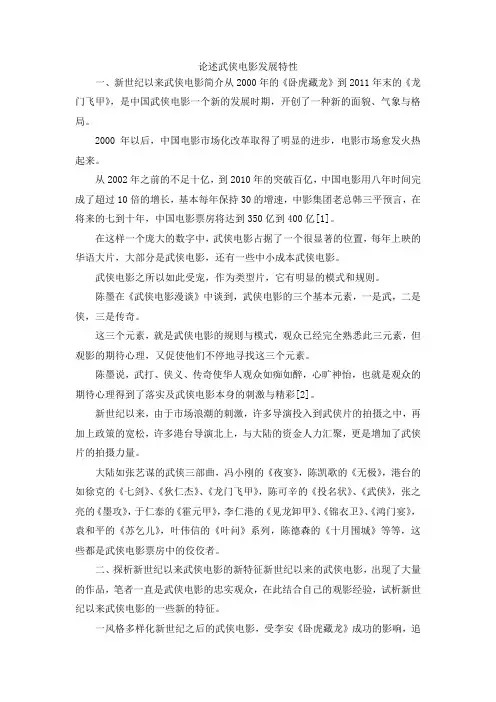
论述武侠电影发展特性一、新世纪以来武侠电影简介从2000年的《卧虎藏龙》到2011年末的《龙门飞甲》,是中国武侠电影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创了一种新的面貌、气象与格局。
2000年以后,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电影市场愈发火热起来。
从2002年之前的不足十亿,到2010年的突破百亿,中国电影用八年时间完成了超过10倍的增长,基本每年保持30的增速,中影集团老总韩三平预言,在将来的七到十年,中国电影票房将达到350亿到400亿[1]。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中,武侠电影占据了一个很显著的位置,每年上映的华语大片,大部分是武侠电影,还有一些中小成本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之所以如此受宠,作为类型片,它有明显的模式和规则。
陈墨在《武侠电影漫谈》中谈到,武侠电影的三个基本元素,一是武,二是侠,三是传奇。
这三个元素,就是武侠电影的规则与模式,观众已经完全熟悉此三元素,但观影的期待心理,又促使他们不停地寻找这三个元素。
陈墨说,武打、侠义、传奇使华人观众如痴如醉,心旷神怡,也就是观众的期待心理得到了落实及武侠电影本身的刺激与精彩[2]。
新世纪以来,由于市场浪潮的刺激,许多导演投入到武侠片的拍摄之中,再加上政策的宽松,许多港台导演北上,与大陆的资金人力汇聚,更是增加了武侠片的拍摄力量。
大陆如张艺谋的武侠三部曲,冯小刚的《夜宴》,陈凯歌的《无极》,港台的如徐克的《七剑》、《狄仁杰》、《龙门飞甲》,陈可辛的《投名状》、《武侠》,张之亮的《墨攻》,于仁泰的《霍元甲》,李仁港的《见龙卸甲》、《锦衣卫》、《鸿门宴》,袁和平的《苏乞儿》,叶伟信的《叶问》系列,陈德森的《十月围城》等等,这些都是武侠电影票房中的佼佼者。
二、探析新世纪以来武侠电影的新特征新世纪以来的武侠电影,出现了大量的作品,笔者一直是武侠电影的忠实观众,在此结合自己的观影经验,试析新世纪以来武侠电影的一些新的特征。
一风格多样化新世纪之后的武侠电影,受李安《卧虎藏龙》成功的影响,追求大制作、大场面、大明星,动辄投资数千万,甚至上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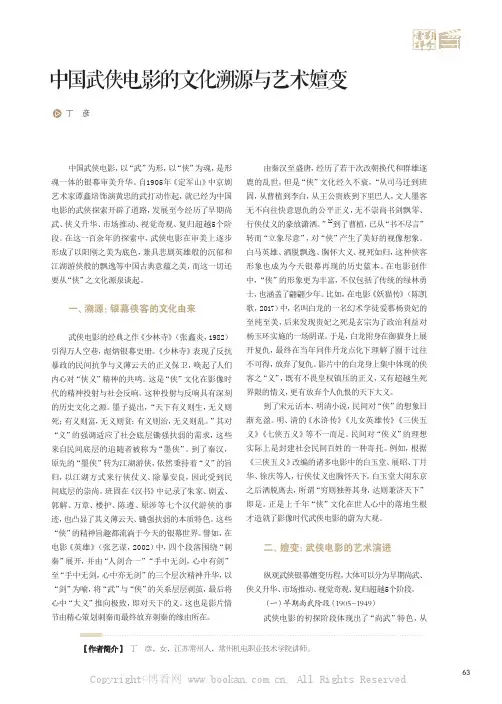
632020第19期中国武侠电影,以“武”为形,以“侠”为魂,是形魂一体的银幕审美升华。
自1905年《定军山》中京剧艺术家谭鑫培饰演黄忠的武打动作起,就已经为中国电影的武侠探索开辟了道路,发展至今经历了早期尚武、侠义升华、市场推动、视觉奇观、复归超越5个阶段。
在这一百余年的探索中,武侠电影在审美上逐步形成了以阳刚之美为底色,兼具悲剧英雄般的沉郁和江湖游侠般的飘逸等中国古典意蕴之美,而这一切还要从“侠”之文化源泉谈起。
一、溯源:银幕侠客的文化由来武侠电影的经典之作《少林寺》(张鑫炎,1982)引得万人空巷,彪炳银幕史册。
《少林寺》表现了反抗暴政的民间抗争与义薄云天的正义保卫,唤起了人们内心对“侠义”精神的共鸣。
这是“侠”文化在影像时代的精神投射与社会反响。
这种投射与反响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之源。
墨子提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
”其对“义”的强调适应了社会底层锄强扶弱的需求,这些来自民间底层的追随者被称为“墨侠”。
到了秦汉,原先的“墨侠”转为江湖游侠,依然秉持着“义”的旨归,以江湖方式来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因此受到民间底层的崇尚。
班固在《汉书》中记录了朱家、剧孟、郭解、万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七个汉代游侠的事迹,也凸显了其义薄云天、锄强扶弱的本质特色。
这些“侠”的精神旨趣都流淌于今天的银幕世界。
譬如,在电影《英雄》(张艺谋,2002)中,四个段落围绕“刺秦”展开,并由“人剑合一”“手中无剑,心中有剑”至“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的三个层次精神升华,以“剑”为喻,将“武”与“侠”的关系层层剥茧,最后将心中“大义”推向极致,即对天下的义。
这也是影片情节由精心策划刺秦而最终放弃刺秦的缘由所在。
由秦汉至盛唐,经历了若干次改朝换代和群雄逐鹿的乱世,但是“侠”文化经久不衰,“从司马迁到班固,从曹植到李白,从王公贵族到下里巴人,文人墨客无不向往快意恩仇的公平正义,无不崇尚书剑飘零、行侠仗义的豪放潇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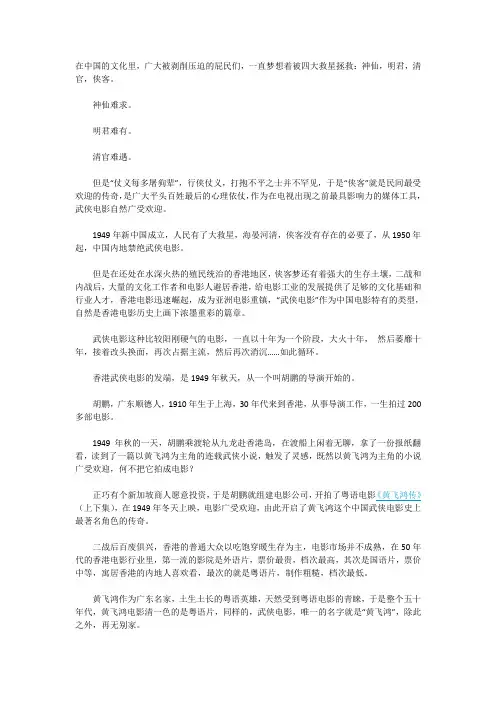
在中国的文化里,广大被剥削压迫的屁民们,一直梦想着被四大救星拯救:神仙,明君,清官,侠客。
神仙难求。
明君难有。
清官难遇。
但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之士并不罕见,于是“侠客”就是民间最受欢迎的传奇,是广大平头百姓最后的心理依仗,作为在电视出现之前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工具,武侠电影自然广受欢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有了大救星,海晏河清,侠客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从1950年起,中国内地禁绝武侠电影。
但是在还处在水深火热的殖民统治的香港地区,侠客梦还有着强大的生存土壤,二战和内战后,大量的文化工作者和电影人避居香港,给电影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文化基础和行业人才,香港电影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电影重镇,“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特有的类型,自然是香港电影历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武侠电影这种比较阳刚硬气的电影,一直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大火十年,然后萎靡十年,接着改头换面,再次占据主流,然后再次消沉……如此循环。
香港武侠电影的发端,是1949年秋天,从一个叫胡鹏的导演开始的。
胡鹏,广东顺德人,1910年生于上海,30年代来到香港,从事导演工作,一生拍过200多部电影。
1949年秋的一天,胡鹏乘渡轮从九龙赴香港岛,在渡船上闲着无聊,拿了一份报纸翻看,读到了一篇以黄飞鸿为主角的连载武侠小说,触发了灵感,既然以黄飞鸿为主角的小说广受欢迎,何不把它拍成电影?正巧有个新加坡商人愿意投资,于是胡鹏就组建电影公司,开拍了粤语电影《黄飞鸿传》(上下集),在1949年冬天上映,电影广受欢迎,由此开启了黄飞鸿这个中国武侠电影史上最著名角色的传奇。
二战后百废俱兴,香港的普通大众以吃饱穿暖生存为主,电影市场并不成熟,在50年代的香港电影行业里,第一流的影院是外语片,票价最贵,档次最高,其次是国语片,票价中等,寓居香港的内地人喜欢看,最次的就是粤语片,制作粗糙,档次最低。
黄飞鸿作为广东名家,土生土长的粤语英雄,天然受到粤语电影的青睐,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黄飞鸿电影清一色的是粤语片,同样的,武侠电影,唯一的名字就是“黄飞鸿”,除此之外,再无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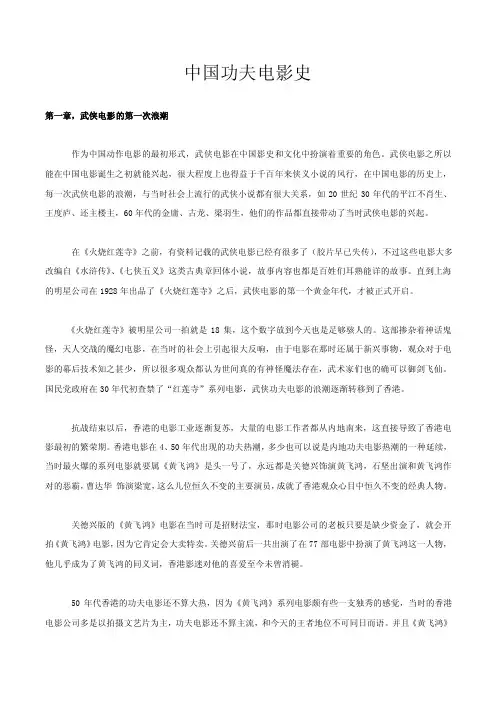
中国功夫电影史第一章,武侠电影的第一次浪潮作为中国动作电影的最初形式,武侠电影在中国影史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武侠电影之所以能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就能兴起,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千百年来侠义小说的风行,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每一次武侠电影的浪潮,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武侠小说都有很大关系,如20世纪30年代的平江不肖生、王度庐、还主楼主,60年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他们的作品都直接带动了当时武侠电影的兴起。
在《火烧红莲寺》之前,有资料记载的武侠电影已经有很多了(胶片早已失传),不过这些电影大多改编自《水浒传》、《七侠五义》这类古典章回体小说,故事内容也都是百姓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直到上海的明星公司在1928年出品了《火烧红莲寺》之后,武侠电影的第一个黄金年代,才被正式开启。
《火烧红莲寺》被明星公司一拍就是18集,这个数字放到今天也是足够骇人的。
这部掺杂着神话鬼怪,天人交战的魔幻电影,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由于电影在那时还属于新兴事物,观众对于电影的幕后技术知之甚少,所以很多观众都认为世间真的有神怪魔法存在,武术家们也的确可以御剑飞仙。
国民党政府在30年代初查禁了“红莲寺”系列电影,武侠功夫电影的浪潮逐渐转移到了香港。
抗战结束以后,香港的电影工业逐渐复苏,大量的电影工作者都从内地南来,这直接导致了香港电影最初的繁荣期。
香港电影在4、50年代出现的功夫热潮,多少也可以说是内地功夫电影热潮的一种延续,当时最火爆的系列电影就要属《黄飞鸿》是头一号了,永远都是关德兴饰演黄飞鸿,石坚出演和黄飞鸿作对的恶霸,曹达华饰演梁宽,这么几位恒久不变的主要演员,成就了香港观众心目中恒久不变的经典人物。
关德兴版的《黄飞鸿》电影在当时可是招财法宝,那时电影公司的老板只要是缺少资金了,就会开拍《黄飞鸿》电影,因为它肯定会大卖特卖。
关德兴前后一共出演了在77部电影中扮演了黄飞鸿这一人物,他几乎成为了黄飞鸿的同义词,香港影迷对他的喜爱至今未曾消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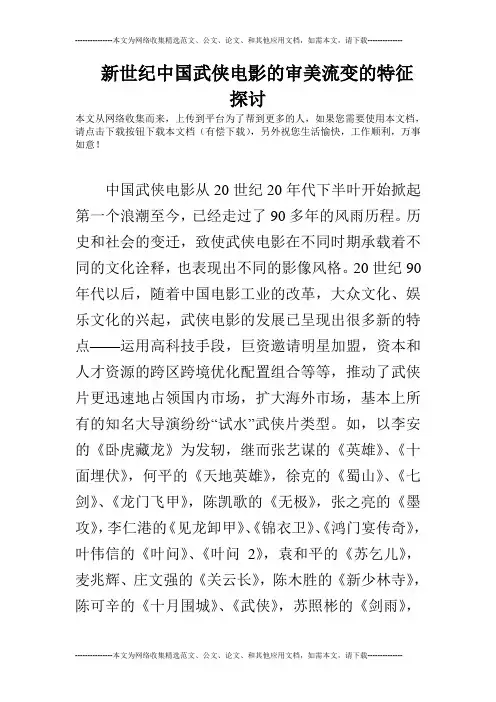
新世纪中国武侠电影的审美流变的特征探讨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中国武侠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开始掀起第一个浪潮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风雨历程。
历史和社会的变迁,致使武侠电影在不同时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诠释,也表现出不同的影像风格。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改革,大众文化、娱乐文化的兴起,武侠电影的发展已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运用高科技手段,巨资邀请明星加盟,资本和人才资源的跨区跨境优化配置组合等等,推动了武侠片更迅速地占领国内市场,扩大海外市场,基本上所有的知名大导演纷纷“试水”武侠片类型。
如,以李安的《卧虎藏龙》为发轫,继而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何平的《天地英雄》,徐克的《蜀山》、《七剑》、《龙门飞甲》,陈凯歌的《无极》,张之亮的《墨攻》,李仁港的《见龙卸甲》、《锦衣卫》、《鸿门宴传奇》,叶伟信的《叶问》、《叶问2》,袁和平的《苏乞儿》,麦兆辉、庄文强的《关云长》,陈木胜的《新少林寺》,陈可辛的《十月围城》、《武侠》,苏照彬的《剑雨》,陈勋奇的《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等有一定影响力的影片相继问世。
武侠电影在叙事策略、人物塑造和情节模式等方面与传统武侠电影比较,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笔者认为,在新时期,武侠电影呈现出的影像奇观化、游戏化和娱乐化的趋向,必然会促使武侠电影的审美体验宽泛化。
但同时,这种审美转向也带来了种种附着在“泛美学”化之中的消极因素和电影作者内心的焦虑性诉求。
“我们这里所谓的‘泛美学’化主要是指经典美学范畴内美学所倚重的‘意义’指向、人文精神的价值表述、文本中应产生的深层心理效应正逐渐淡化、模糊化或变得难以做出确切的界定,甚至表象与内涵、文本与意义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游离、断裂。
”①本文试图反思新世纪武侠电影的这种“泛美学”化趋向,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潜在的焦虑性,进而提出自己的理性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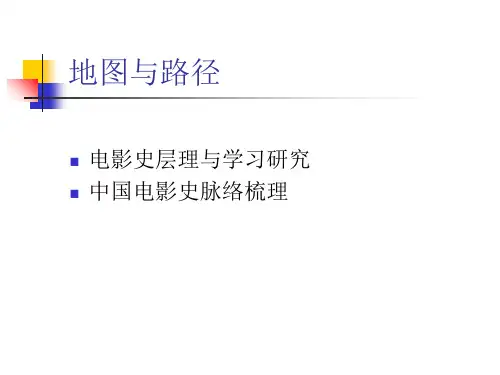
第八章中国功夫和侠义精神一、武和侠(一)武(1)技(武术或功夫):打斗的技术、招式(2)器:刀光剑影(3)道:止戈为武(以佛法化解恩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无名无相(破除“武功障”,直指人心)(二)侠1. “侠”的字义《说文解字》:“侠,俜也。
从人夹声。
”“甹,侠也,三辅谓轻财者为。
”《说文解字注》“今人谓轻生曰俜命,即此俜字。
”俜:拼命、搏命的意思。
“甲”(衣甲)——“夹”——“侠”:带甲之士,即武士。
从古文字学意义上说,侠,具备三种品格:搏命轻财(重义)善武2.侠的品格(1)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
如《雪山飞狐》中的胡一刀和苗人凤;(2)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他人于危难之中;(3)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如郭靖、乔峰。
3.侠的类型(1)乱世豪侠(2)江湖义士(3)绿林好汉(三)江湖江湖:地理名词-文化符号-象征世界。
作为总的世界图式的“江湖世界”基本上是虚拟的,作为具体生活背景的“江湖”却近乎写实。
典型场景: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寺庙道观。
这三者在相对于都市尘世,宫廷衙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都是王法鞭长莫及之处,是武侠小说所虚拟的法外世界。
(四)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以武行侠的小说流变:古代侠义公案小说清末民初旧派小说港台新派武侠小说宋话本“公案”、讲史侧重故事性;“侠义”、“武侠”侧重人物行为及其意义。
清末民初(二、三十年代)的武侠热:小说:南向(向恺然:《江湖奇侠传》)北赵(赵焕亭:《奇侠精忠传》、《大侠殷一官轶事》),电影:1928-1931年上海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摄四百部电影,其中武侠神怪片占二百五十部。
80年代中后期的港(金庸、梁羽生)台(卧龙生、古龙、司马翎、诸葛青云)武侠小说。
武侠盛行武侠在各文化层次的受众中广泛流传(武侠小说武侠电影武侠游戏武侠漫画)武侠盛行的原因(1)从主体而言:武侠的创作主体自身一直在力图融汇(或迎合)各种文化心理,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2)从接受者而言:中国具有江湖、庙堂的传统,受众具有强烈的武侠阅读期待视野。
2020智慧树,知到《中国武侠电影》章节测试完整答案2020智慧树,知到《中国武侠电影》章节测试完整答案智慧树知到《中国武侠电影》章节测试答案绪论1、《木兰从军》是在30年代上海孤岛时期试图借古讽今、隐喻抗战的电影。
答案: 对2、类型电影的悖论是既要重复自身又必须有所创新答案: 对3、中国电影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极有可能就是一部武侠电影,因为该片只拍摄了同名京剧里面的一个武打场面。
答案: 对4、开设中国武侠电影课程是希望能够在实际创作中有所运用,禁止对他人模拟或使用课程中所讲解的武术技巧。
答案: 对5、对于类型电影的说法错误的是?答案: 从电影叙事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来划分,如故事片,纪录片等第一章答案1、胡金铨作为武侠电影的导演,虽然他说自己不懂武功,但是他擅长将传统文化中的融入其武侠电影之中?答案: 京剧2、“武术指导”这一称谓是胡金铨在拍摄电影《大醉侠》时,由京剧演员韩英杰工作上的称呼而得来的。
答案: 对3、下列哪几部电影出现了以竹林为背景的戏?答案: 《侠女》,《十面埋伏》,《卧虎藏龙》4、1956年,长城公司拍摄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云海玉弓缘》,开启了武侠片的黄金时代A.对B.错答案: 对5、下列关于电影《侠女》说法正确的是A.根据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同名小说《侠女》改编B.电影中女主角从竹梢俯冲而下的镜头剪辑和特技设计影响了之后的《卧虎藏龙》《十面埋伏》C.集武侠题材,戏曲美学和东方思考的结合D.《侠女完成后》,将三小时的国际版送往戛纳影展,但遗憾的是并未获奖答案: 根据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同名小说《侠女》改编,电影中女主角从竹梢俯冲而下的镜头剪辑和特技设计影响了之后的《卧虎藏龙》《十面埋伏》,集武侠题材,戏曲美学和东方思考的结合第二章1、李小龙的过世、武侠片进入瓶颈期都发生于什么时间段?A.50年代后期B.60-70年代C.70年代后期D.80年代中期答案: 70年代后期2、李小龙的功夫电影主要以男性为主,女演员戏份很少,感情戏单薄。
见面课:入门知识补充:类型电影及武侠电影之间的关系1、功夫/武术的三个层次有A.军事格斗B.杀人越货C.竞技体育D.除暴安良E.强身健体/内外兼修正确答案:军事格斗;竞技体育;强身健体/内外兼修2、中国武侠精神的两个重点A.竞技体育能力B.武术技巧C.侠义精神/修为D.强身健体E.富国强兵正确答案:武术技巧;侠义精神/修为3、桩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并且作为习武之法养生的辅助之法A.对B.错正确答案:对4、关于类型电影的概念,正确的有A.视觉传统提供一个架构或环境,在这个架构或环境中,故事可以被叙述B.只在好莱坞体系内存在C.类型的外在形式包含视觉的要素,内在形式是布置视觉要素的方法D.由观众制定并形成固定的制作模式、叙事体系E.由制片厂制定并形成固定的制作模式、叙事体系正确答案:视觉传统提供一个架构或环境,在这个架构或环境中,故事可以被叙述;类型的外在形式包含视觉的要素,内在形式是布置视觉要素的方法5、西部片是典型的美国类型电影A.对B.错正确答案:对6、一部类型电影,都是由熟悉的、单一面向的演员在一个熟悉的场景里演出一个可以预期的故事模式。
A.对B.错正确答案:对7、类型的悖论包含A.制片厂与观众达成的模式B.观众的品味的提升C.制片厂体制的转变D.对创新的持续不断要求E.创新的难度正确答案:对创新的持续不断要求;创新的难度8、本课程对武侠电影的研究方法有A.武打场面设计B.叙事风格C.剪辑及蒙太奇技巧D.明星八卦逸闻E.主题正确答案:武打场面设计;叙事风格;剪辑及蒙太奇技巧;主题见面课:四、期末总结: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及未来1、《师父》中的师傅陈识自始至终都保持了一成不变的性格特征和情感A.对B.错正确答案:错2、《师父》的片尾中,男女主角均成功脱逃,意味着他们打破了江湖规矩,南拳成功北传A.对B.错正确答案:错3、六点半棍,由红木类木材(较重较实)或实木制成之长棍,棍法来源于马上枪,故执单头。
中国武侠电影的历史武侠电影贯穿与整个中国电影史,共分为形成期、发展期、兴盛期和衰弱与创新期。
从1905年至1931年都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形成期,《定军山》、《车中盗》《侠女李飞飞》等影片确定了武侠片若干基本元素。
但处于发展期的武侠电影带有明显的类型化特点,情节简单,人物性格形象固话。
并且这一时期虽是武侠电影的形成期,但因为武侠电影的叙事模式和中国观众传统的文化心理相契合,因此武侠电影一诞生,就显示出了如日中天的势头。
从1928到1931年,共上映了227部武侠神怪片,其中不免粗制滥造的作品。
当时因为民众相信怪力乱神,武侠片还被冠以“武侠神怪片”的恶名。
1931至1949年,大陆因为战乱禁止娱乐片的发行,武侠片首当其冲。
中国电影进入到“孤岛侠风”和“港岛剑影”的特殊时期。
上海从1937年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开始,至1941年日本军队进驻上海为止,这四年被称为孤岛时期。
为了与当时历史环境相契合,表现庄严肃穆之感,孤岛时期主要拍摄的是古装武侠片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题材片,代表作有《木兰从军》、《武则天》、《苏武牧羊》等。
这时期的香港武侠片已呈现中国传统武侠文化为核心电影主要是改编自民间故事或是稗官野史。
“1949至1979年间是武侠电影的兴盛期,因为大陆自1949至1979年全面禁止武侠文艺,所以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主要在台湾和香港发展。
1949至1969年是古装武侠片的兴盛期;1970至1980是功夫片兴盛期。
”1著名的有黄飞鸿系列电影,胡金铨的《龙门客栈》、《侠女》等。
胡金铨的电影被称为是文人武侠,因为他身上即具备儒生气质,又像是一位禅意大师。
他喜爱明朝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阐述人。
他将儒释道文化融入武侠电影中,展现了武侠电影的精神深度和文化内涵。
“通过善恶忠奸的二元对置与刀光剑影的电影叙事表达自己深藏于心而曲折幽深的家、国梦想。
”2胡金铨于是被西方称为个人化的导演,其作品也被称为“作者电影”。
他让人目睹了“热血刚肠的侠客鹰扬飞舞的身影后有着血汗熔铸的真情烈性”,武侠电影有了“文化艺术视野中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