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与炎症关系的研究进展
- 格式:doc
- 大小:106.50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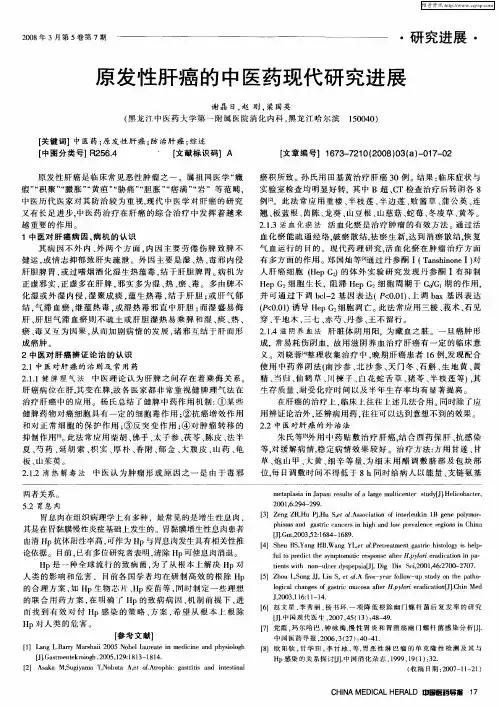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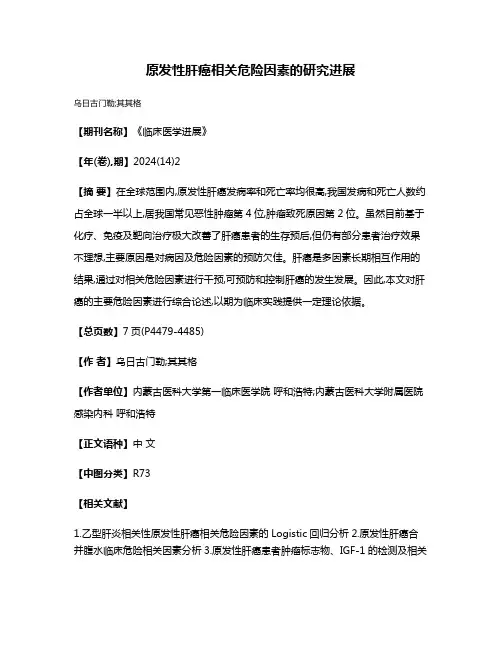
原发性肝癌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乌日古门勒;其其格
【期刊名称】《临床医学进展》
【年(卷),期】2024(14)2
【摘要】在全球范围内,原发性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很高,我国发病和死亡人数约占全球一半以上,居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第4位,肿瘤致死原因第2位。
虽然目前基于化疗、免疫及靶向治疗极大改善了肝癌患者的生存预后,但仍有部分患者治疗效果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对病因及危险因素的预防欠佳。
肝癌是多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可预防和控制肝癌的发生发展。
因此,本文对肝癌的主要危险因素进行综合论述,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总页数】7页(P4479-4485)
【作者】乌日古门勒;其其格
【作者单位】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呼和浩特;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感染内科呼和浩特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73
【相关文献】
1.乙型肝炎相关性原发性肝癌相关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2.原发性肝癌合并腹水临床危险相关因素分析
3.原发性肝癌患者肿瘤标志物、IGF-1的检测及相关
危险因素分析4.乙肝肝硬化并发原发性肝癌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5.乙型肝炎相关性原发性肝癌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早期复发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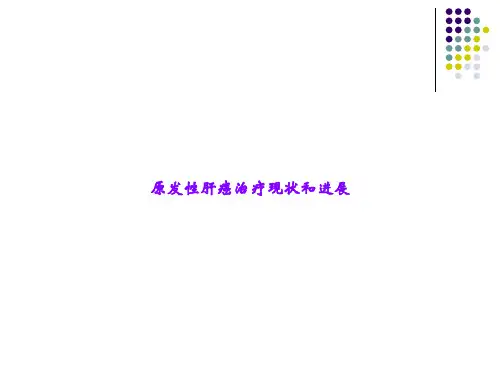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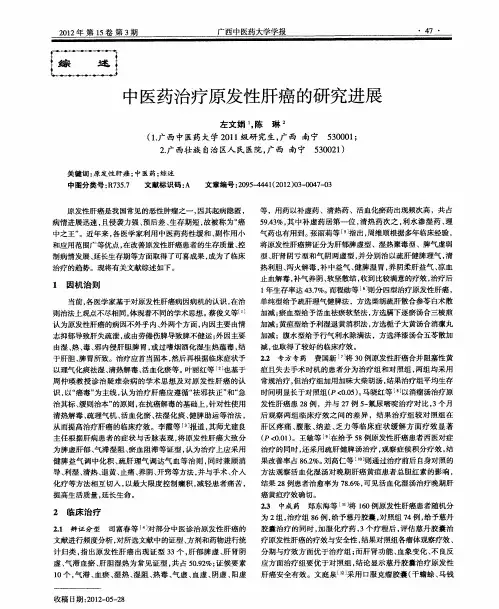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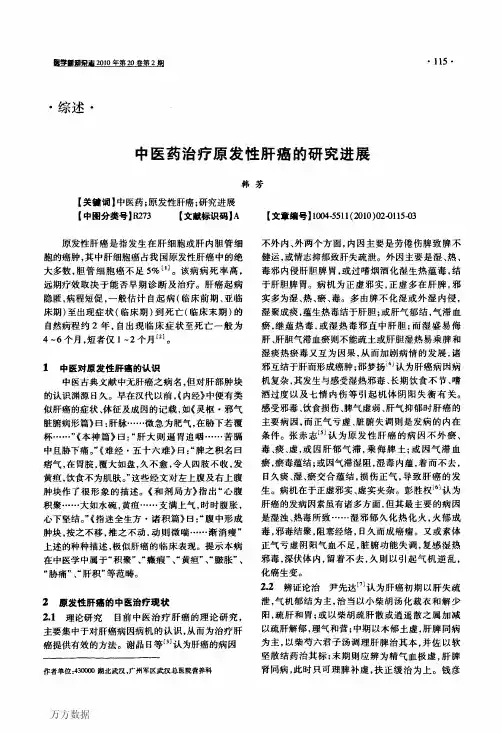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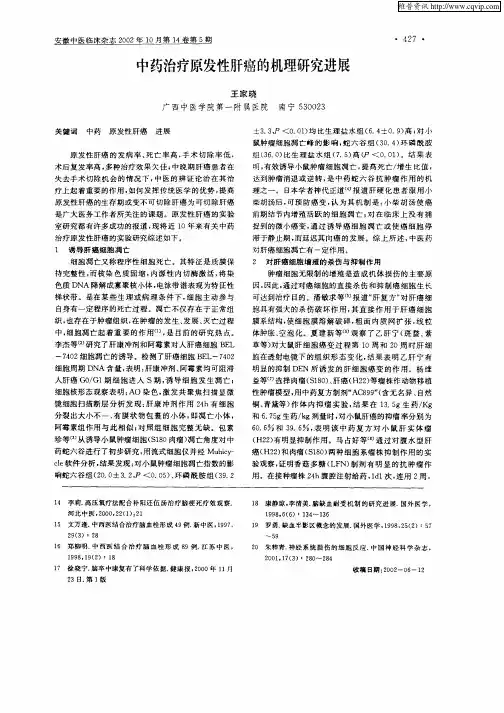
![[原发性,肝癌]原发性肝癌的研究及治疗进展](https://uimg.taocdn.com/308fd200360cba1aa911dad1.webp)
原发性肝癌的研究及治疗进展目的:中国医学会报道,全球病毒性肝炎感染人数是艾滋病的10倍,全国100万人死于肝癌,肝炎是我国甲乙类传染病中的第一位,我国有9300万乙肝的感染者,而90%的乙型肝炎,都遵循乙肝三部曲,肝炎,肝硬化,肝癌的转变,所以造成原发性肝癌是我国最常见恶性肿瘤,在我国肿瘤死亡率中占第三位。
以中青年发病率最高,我国乙肝与相关疾病,成为了政府的巨大的财政负担,直接损失达9000亿元,今年来我国肝炎报告病例逐年增加,所以控制与防止肝炎的蔓延,治疗慢性乙肝显得尤为突出,研制新的抗病毒药物,有效的控制乙肝病毒的发展是治疗关键。
其次还要寻找更好地手术方式来进行手术治疗。
【关键字】肝癌;研究进展;药物引言: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 Cancer,PLC,以下简称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其中90%为肝细胞肝癌(hepaeoeellular carcinoma,HCC),目前其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
我国是全球肝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据统计,目前我国肝癌发病人数占全球的55%,而死亡人数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45%,对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治疗肝炎的药物的发展,抗病毒药物的研发,肝癌由不治之症,变成了部分可治。
以手术切除为主的综合治疗大大提高了肝癌患者的生存率,目前手术切除是获得肝癌长期生存的最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其它治疗手段,如手术前后的分子靶向治疗,系统性化疗等,患者的生存质量明显提高,其作用机理和已经显示出来的治疗效果让人们对肝癌治疗的前景非常期待[1]。
1 手术治疗1.1以肝切除术为代表的外科治疗大大提高了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生存率,手术切除是获得肝癌长期生存的重要手段。
肝切除是治疗小肝癌的首选方法,无论是否合并肝硬化的小肝癌均仍以手术治疗为主要手段[2]。
术前评估:肝切除术术前肿瘤情况及肝储备功能的评估非常重要,我国一期手术前提条件是①患者一般情况较好,无明显重要脏器器质性病变②肝功能正常,或仅有轻度损害,按肝功能分级属A级,或肝功能分级属 B级,经短期护肝治疗后有明显改善,肝功能恢复到A级③肝储备功能正常范围2肝动脉插管栓塞化疗.(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研究表明:TACE后,80%以上的肝癌有不同程度的活细胞残留,这在本组的二步切除病人中也得到了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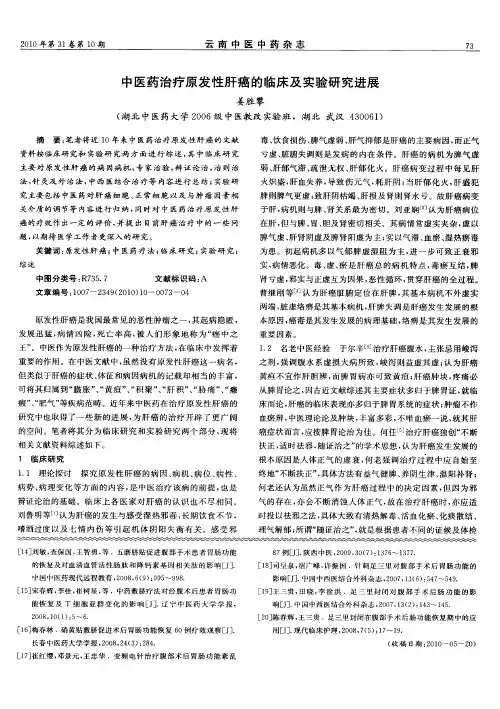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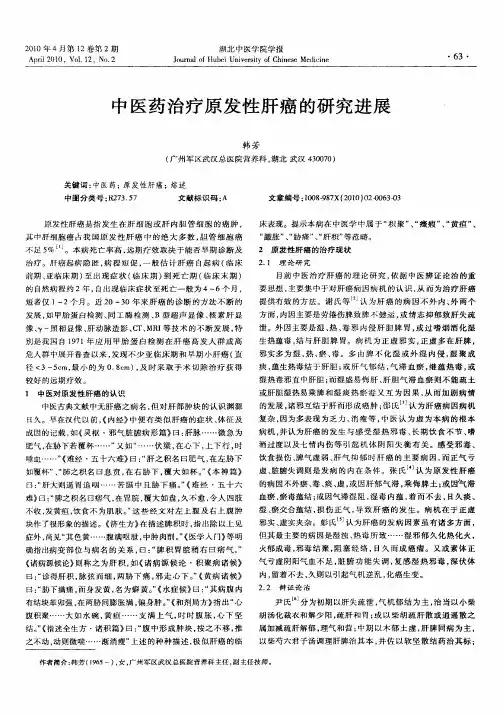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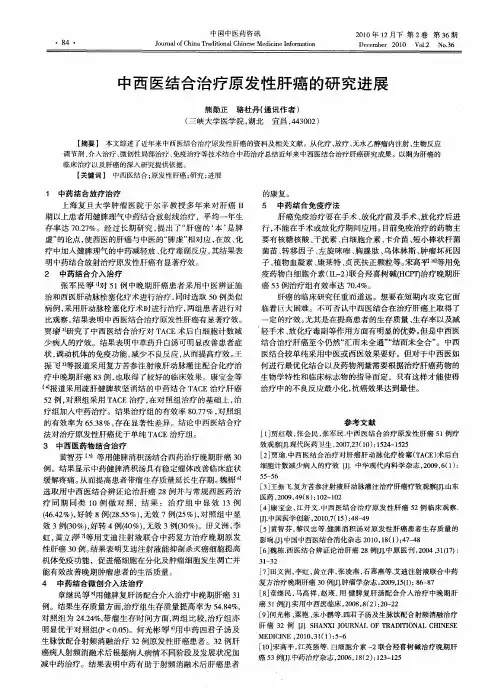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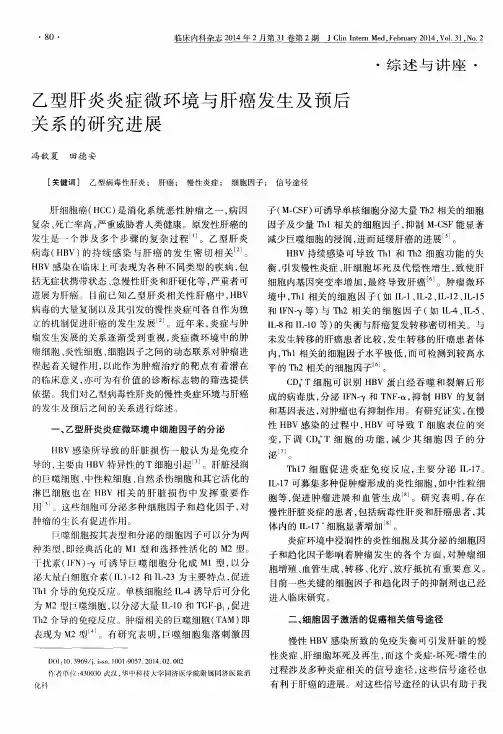
Advances in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进展, 2023, 13(7), 11529-11534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3 in Hans. https:///journal/acm https:///10.12677/acm.2023.1371612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及肝纤维化指标(GPR)在肝细胞癌中的研究进展韩 毅1,汪笑楠1,王宏宾2*1青海大学临床医学院,青海 西宁 2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普通外一科,青海 西宁收稿日期:2023年6月18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13日;发布日期:2023年7月21日摘 要肝细胞癌(HCC)是原发性肝癌(PHC)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是一种高度异质性、复杂性和侵袭性的恶性肿瘤。
目前根治性的肝切除术依旧是肝细胞癌的最主要的治疗方法,然而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以及肿瘤的高复发率依旧存在很大问题。
近些年来,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和γ-谷氨酰转肽酶/血小板比值(GPR)等已经成为HCC 研究的热点问题。
SII 作为一种全身炎症反应的评价指标,现已被证实与HCC 患者的预后相关。
γ-谷氨酰转肽酶、血小板也被证实是肝细胞癌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文将从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 和γ-谷氨酰转肽酶/血小板比值GPR 指标出发,与肝细胞癌相关联进行系统性综述,以便更好地了解相关指标在HCC 患者预后中的应用和作用。
关键词肝细胞癌,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γ-谷氨酰转肽酶与血小板比值(GPR),预后Research Progress on Systemic Immune Inflammation Index (SII) and Liver Fibrosis Index (GPR)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Yi Han 1, Xiaonan Wang 1, Hongbin Wang 2*1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2The First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Received: Jun. 18th , 2023; accepted: Jul. 13th , 2023; published: Jul. 21st , 2023 *通讯作者。
抗原发性肝癌粘附\侵袭与转移的研究进展原发性肝癌(hcc)是世界上最为常见一种恶性肿瘤疾病,彻底治愈的难度很大,患病死亡率高。
根据目前的研究报道,影响预后的最主要因素是复发转移。
研究统计结果显示hcc病患处切除5年后的复发率为55%~62%,切除肿瘤直径小于5cm的小肝癌复发率为44%,局部治疗的转移复发率则更高。
因此抗原发性肝癌侵袭转移,降低术后复发率是目前hcc治疗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1 在原发性肝癌转移过程中细胞粘附分子的作用在原发性肝癌的侵袭转移过程中,会有多种细胞粘附分子的异常表达现象存在,其中以钙黏素(cadherin)、连接素(catenin)和cd44最为重要。
e-钙黏素(e-cadherin)能够介导同种细胞间的粘附,同时也是细胞骨架的主要成分,如果想要促使肿瘤细胞脱离原发灶发生转移,就需要减弱e-钙黏素的表达。
而 -连接素常与e-钙黏素结合,共同作用形成细胞内的黏着复合体,该复合体布在膜下细胞与细胞连接处,具有维持细胞正常粘附和信号转导的功能,在细胞癌变过程中,复合分子在细胞内的表达和分布将发生异常。
e-钙黏素和-连接素的异常表达影响着原发性肝癌的组织分化、转移与预后。
其中肿瘤的早期复发受到e-钙黏素的下调表达的影响;而-连接素的表达和定位与原发性肝癌的肝内转移关系的研究也显示了对原发性肝癌的血管侵润程度密切相关:文献[1]中通过对97例手术切除的肝癌组织进行研究后,发现-连接素与血管浸润程度具有正比例关系,并在细胞膜中过度表达;宋丽娜等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验证了在胞核表达的-连接素与原发性肝癌的血管浸润程度的相关度很高。
cd44是分布极为广泛的细胞表面跨膜糖蛋白,通过与ecm中的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等基质分子相结合,来影响细胞与基质间的特异性粘附。
仅含由组成外显子的cd44转录子称为标准cd44(cd44s),主要存在于正常细胞和非转移性癌细胞中;而含有变异性拼接外显子的cd44转录子称为变异cd44(cd44v),cd44v常在转移性癌细胞中显著表达。
原发性肝癌与肠道微生物菌群的研究进展摘要:肠道菌群与肝癌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肠道菌群数量和种类的改变不仅能对肠道菌群平衡、肠道炎症和黏膜屏障功能起一定的调节作用,还能显著改善肝脏的硬化状况,对肝癌的发生进行预防。
本文综述了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菌群的研究现状,为原发性肝癌的早期临床诊疗提供依据。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肠道菌群;微生物环境一、原发性肝癌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HC)是起源于肝脏干细胞或者肝胆管粘膜的上皮细胞的肿瘤。
PHC患者的总病死率有可能超过或达约每小时9亿人次/每秒约为10多万人,其平均死亡总发病率和平均总肿瘤病死率在当前世界恶性肿瘤发病率统计中的排名为第六位和第四位[1]。
PHC也是我们国家常见到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在疾病发生早期临床症状大多还不明显,起源病期相对更为隐匿,多数患者进行体检时发现,可能都已转化发展为恶性疾病并进入中和晚期。
PHC恶性程度高、浸润和转移性强,病死率高,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PHC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目前认为是与多因素多途径相关。
现有的研究显示原发性肝炎、脂肪肝性疾病、肝纤维化等引起的慢性肝性疾病是PHC的主要危险因素。
根据临床PHC病变的临床不同及发展的阶段和临床诊断上可以进行各种个体化诊断治疗,早期确诊PHC患者常考虑采用个体化手术检查和治疗手术方法,包括全肝切除术治疗和全肝移植术,可达到部分治愈。
中及晚期传染性肝病PHC患者的抗病毒治疗使用的主要方法包括有包括肝动脉栓塞切除或手术结扎、化疗、放射消融治疗、生物活性靶向治疗、免疫调节药物化疗及现代中药靶向化疗综合应用治疗、中医西药结合个体化治疗新方案等。
以一线靶向药物为主的药物应用等以长期保守与支持结合治疗原则为主,靶线肿瘤的生物治疗中常见被采用治疗的一线多靶点药物类型通常也是多肽酶靶点、多种雄激酶活性释放抑制剂,有索拉菲尼单抗、仑伐替米尼、和瑞戈非尼二抗、和卡博替尼多抗、和雷莫芦单双抗等。
原发性肝癌与炎症关系的研究进展摘要原发性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与炎症密切相关。
在我国,肝癌患者中约大多数有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感染病史;在欧美及日本,肝癌与丙型病毒性肝炎有关。
本文总结原发性肝癌与炎症关系的最新研究进展,探讨多种炎症介质对肝癌发生、转移的促进机制,通过阻断相关炎症介质作用,探索出抑制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发展,减少复发、转移的新治疗途径。
原发性肝癌(primary hepatic carcinoma PHC)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十大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新发及死亡病例约占所有恶性肿瘤的5.4%。
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均有上升趋势。
原发性肝癌是一种与炎症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炎症在肝癌的发生和转移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1][2]。
本文就原发性肝癌与炎症关系的研究作一综述。
概述Rudolph Virchow[3]第一次提出炎症在恶性肿瘤进展中起一定的作用,认为慢性炎症可促进肿瘤的生长;随后Wiemann B[4]证明:通过给患者注射化脓性链球菌和粘质沙雷菌引起的急性炎症可使部分患者的恶性肿瘤退化。
目前炎症与肿瘤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
大量流行病学调查提示:炎症是导致肿瘤发生或促进肿瘤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约20%的恶性肿瘤由炎症诱发或促进[1] [2] [5]。
炎症与肿瘤发展的多个环节相关,包括肿瘤细胞形成、进展、逃逸、增生、浸润、血管生成、转移。
炎症引起恶性肿瘤的分子和细胞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有研究认为:炎症发生后,炎性细胞在迁入炎症部位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活性氧、活性氮物质,而且在慢性炎症过程中,内生抗氧化机制的抑制作用也可以产生超负荷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诱导DNA损伤,破坏增生细胞的基因稳定性,最终在炎症和活性物质的反复破坏下,细胞基因改变,包括点突变、基因缺失、基因重组[6]。
在我国,原发性肝癌患者中约1/3有明确的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欧美及日本,肝癌主要与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酒精性肝病有关。
肝癌与肝炎病毒、酒精性肝病的关系,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部分机制已经阐明。
研究证实:乙型肝炎病毒(HBV)是一种DNA病毒,它可以整合插入宿主基因组,改变宿主体细胞基因的表达,导致宿主细胞基因组的不稳定,易发生基因改变,从而转化为肝癌细胞[7];丙型肝炎病毒(HCV)为单链RNA病毒,可以和多种细胞蛋白作用,促进肝细胞向肝癌细胞转化[8];酒精性肝病诱导肝癌形成过程中,酒精产物乙醛可直接损伤肝细胞或乙醇代谢产生的反应性氧化剂和脂质过氧化物直接造成DNA损伤[9]。
原发性肝癌通常发生在慢性肝损伤的基础上,包括慢性肝炎、肝硬化,这些被认为是癌前病变。
慢性肝损伤引起的炎症反应促进肝硬化的发展,并且激活了肝细胞的再生能力[10]。
肝脏的修复机制若被短暂的激活,肝脏的结构和功能可迅速恢复,修复机制的持续激活可促进肝癌的形成和发展,肝炎病毒感染和长期饮酒可激活先天性免疫功能,维持持久的炎症反应,从而促进肝癌的形成和发展[11]。
目前研究已证明,在炎症与癌症的关系中,许多炎症介质具有重要作用。
炎症介质产生于炎症反应过程中,也可以由肿瘤细胞产生,其中起关键作用的炎症介质包括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核转录因子—kappaB(NF-kB)、肿瘤坏死因子(TNF-α)、补体系统。
.原发性肝癌与Cox-2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是花生四烯酸转变为前列腺素的限速酶,又称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合成酶,是一种完整的膜结合蛋白,至少有三种形式:Cox-1位于内质网,属于结构型基因,多种正常组织和细胞中表达,维持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Cox-2主要位于核膜,属于诱导型,静息时不表达,但可以在细胞因子、激素、致癌物质等多种诱导因子的刺激下快速表达, 参与多种病理生理过程;Cox-3由Cox-1转变而来,仅在少数组织中表达[12]。
近年来研究表明,Cox-2不仅与多种病理生理过程有关,而且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也有密切的联系。
Cox-2的表达与肝癌病理特点密切联系。
Melchiorre Cervello[13]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证实Cox-2在癌旁组织中的表达高于肿瘤组织,在高分化性肝癌中的表达高于低分化肝癌,并且肝癌细胞中Cox-2的表达水平随着肿瘤进展而降低,提示Cox-2在早期癌变过程中起作用。
多数学者和研究机构持有相同观点。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Terence C[14]教授则认为:原发性肝癌中Cox-2的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无显著差别,与肿瘤的TMN分期有显著差别。
Cox-2与肿瘤血管生成密切相关。
血管生成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Cox-2有生血管的特性,但近来的研究证明,Cox-2可能通过调高VEGF的表达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在肿瘤侵袭中占重要作用。
我们在实验中(结果尚未发表)观察到,原发性肝癌组织中Cox-2与血管内皮生成因子(VEGF)的表达均增高,且二者成正相关。
Cao Bin [15]在裸鼠体内证明:干扰素(IFN-α-2b)通过下调Cox-2及VEGF 表达水来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肝癌生长,并且认为Cox-2影响VEGF的表达水平。
肝部分切除是目前治疗原发性肝癌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术后复发转移一直困扰着医学界,Kondo M[16]认为Cox-2在肝癌切除术后复发中可能具有重要要作用。
目前局部介入治疗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肝癌患者,但远期疗效均不理想,复发、转移率高,预后差。
唐武兵等[17]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前后肝癌组织COX-2的表达变化,结果显示肝癌TACE后COX-2表达增强,提示肝癌患者经肝动脉化疗的同时选择特异性COX-2抑制剂,可能会提高肝癌介入治疗的远期疗效。
Cox-2信号通路在原发性肝癌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作用于肿瘤细胞浸润、增生、凋亡、血管生成等关键环节。
Cox-2基因的转录控制是细胞特异性的,多条信号通路共同调节Cox-2的表达。
Araki[18]报导:在原发性肝癌细胞中,Wnt通路和Ras通路的联合下调可导致Cox-2蛋白水平的mRNA的增高。
Cox-2的表达也会受到糖皮质激素、部分白介素、抗炎因子的抑制。
近期的研究显示,两种肝炎病毒均可增强Cox-2的表达,乙肝病毒DNA整合到宿主基因组后,病毒蛋白HBx通过相关转录子激活Cox-2启动子,进而调高Cox-2的表达[19];丙肝病毒可激活NF-kB,调节Cox-2的表达[20]。
Cox-2抑制剂已经在肿瘤的预防和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结直肠癌患者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比不服用该药可降低40%--50%的死亡率。
但对肝癌的作用暂无确切的数据。
Ji Yeon Baek[21]证实,选择性Cox-2抑制剂NS-398可抑制肝癌细胞HuH7、HepG2的生长,且与剂量和时间相关,该药物通过使细胞分裂停止在G1期而抑制细胞增生,但并未发现其可诱导细胞凋亡。
Michael Andre Kern[22]已在裸鼠活体中证实,选择性Cox-2抑制剂可抑制原发性肝癌生长。
大量研究成果已提示,阻断Cox-2介导的信号通路可能有效地预防和治疗肝癌,Cox-2可能成为肝癌治疗的新靶点。
原发性肝癌与TNF-αBharat B. Aggarwal教授1984年将肿瘤坏死因子(TNF-α)作为“抗癌细胞因子”第一次分离出来,却发现它能导致及促进癌症发展。
TNF-α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炎症调节因子,当受到致病因素刺激时,它可以诱导其它炎症调节因子和蛋白酶应对炎症反应。
研究已证实,TNF-α也可以由肿瘤产生,并且作为内生促进因子,与肿瘤发展过程的多个环节有联系,包括肿瘤细胞形成、逃逸、增生、浸润、血管生成、转移[23]。
许多肿瘤可以产生TNF-α,如B淋巴细胞瘤、急性白血病、结肠癌、乳腺癌、胰腺癌、鳞状细胞癌等。
体内大多数TNF-α作为自分泌生长因子促进肿瘤生长,在部分肿瘤中,它通过诱导其它生长因子表达调节肿瘤生长。
Lin W和Fukata M分别在动物体内和癌细胞中证明:包括TNF-α和白介素(IL-6)在内的许多炎症介质可以刺激肿瘤生长,促进肿瘤进展[24]。
在原发性肝癌的的研究中,多数专家认为TNF-α是通过核转录因子NF-kB通路在肿瘤的发生、进展中起作用的。
Pikarsky E[1]认为TNF-α激活肝细胞内细胞核因子-kappaB(NF-kB),不仅能加速细胞变异,导致癌细胞的“疯狂”生长,还能协助这种变异细胞逃离最初的肿瘤,转移到身体的其它部位。
白莉[25]通过动物实验证实:炎症细胞因子,尤其是TNF-α的表达与肝癌转移有显著的正相关,可能对肿瘤转移有一定的增强效果。
原发性肝癌与NF-kB真核细胞核转录因子-kappaB(NF-kB)广泛调控人类一系列基因的表达,尤其是免疫反应、炎症反应、病毒相关的基因及原癌基因。
正常细胞发生恶性转化的前提是受到正性生长信号的持续刺激或细胞凋亡受阻。
研究表明NF-kB信号转导途径与肿瘤发生密切相关,可能的途径有两条[26]:一是外界致瘤因素活化继而调节细胞周期D1(CyclinD1)的过表达,可以缩短G1期,促进细胞进入增殖期,从而促进细胞转化;二是抑制促凋亡因子,从而保护细胞免于凋亡。
研究证明,NF-kB在诱导细胞转化,促进细胞增生、血管生成、浸润、转移等方面起作用,参与多种肿瘤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27]。
.肿瘤与炎症关系的研究显示:多数炎症因子通过激活NF-kB发挥作用,多数抗炎因子则抑制NF-kB活性。
同样,大多数癌基因和肿瘤促进因子可激活NF-kB,而化学预防因子可抑制它[28]。
原发性肝癌与NF-kB的部分机制已阐明[29]。
Pikarsky[1]等在《Nature》发表文章证实:炎症诱发肝脏NF-kB 的表达,在小鼠出生后至7个月,阻断NF-kB,则无肝炎发生,在肝癌发生过程中,抑制NF-kB,肝癌则不发生,喂食小鼠非甾体类抗炎药10天,肝炎程度减弱,NF-kB表达明显减弱,同时认为NF-kB在肝脏发育过程中能保护胚胎肝细胞免受TNF-α介导的凋亡,已激活的NF-kB参与癌症的启动、发生及发展过程,在炎症与细胞癌变间起桥梁作用。
LiQ[30]则认为:肝炎病毒感染能刺激NF-kB表达并使其DNA结合能力增强,胞内NF-kB异常活化与原发性肝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我们实验证实(结果尚未发表):NF-kB在肝癌组织中细胞核中呈点灶状阳性表达,而在癌周组织细胞核中少量阳性表达,提示NF-kB可能在激活后进入胞核发挥其转录活性,从而参与肝癌的发生发展;而且发现人肝癌组织NF-kB的表达与VEGF的表达成正相关,证实了NF-kB参与肝癌的发展可能与血管生成相关,抑制NF-kB活性可能成为肿瘤基因治疗的新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