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
- 格式:doc
- 大小:34.5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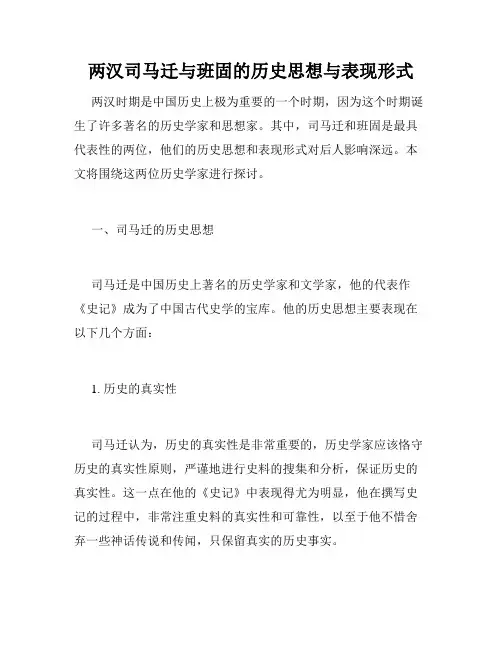
两汉司马迁与班固的历史思想与表现形式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其中,司马迁和班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历史思想和表现形式对后人影响深远。
本文将围绕这两位历史学家进行探讨。
一、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史记》成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宝库。
他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应该恪守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严谨地进行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这一点在他的《史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至于他不惜舍弃一些神话传说和传闻,只保留真实的历史事实。
2. 历史的意义司马迁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
他强调历史的价值,并通过历史对社会、人类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和研究。
他在史记中对于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提取出了历史意义,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思想。
3. 对于社会制度的观察司马迁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对于社会的制度和变革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在史记中,他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为后人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大的启示。
二、班固的历史思想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汉书》是对于西汉历史的全面记录和评述。
他在历史思想方面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历史的宏大班固在《汉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其中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政治斗争、军事战争等等,而且他的书写手法非常宏大,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庞大和辽阔。
2. 历史的延续性班固认为,历史是一种延续性的现象,过去的历史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在《汉书》中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并强调历史应该得到正确的诠释和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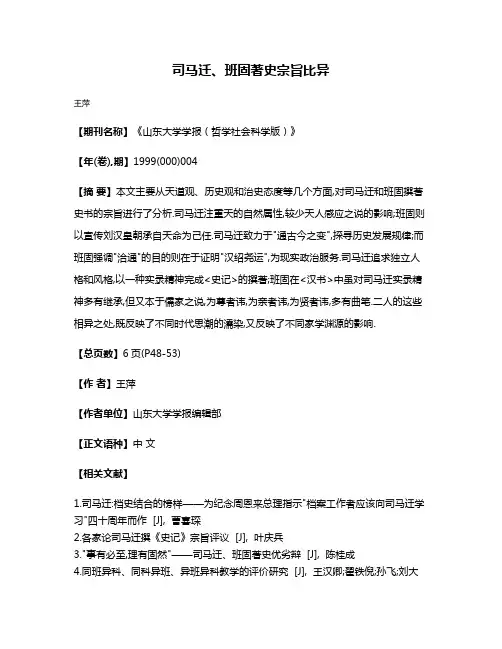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王萍
【期刊名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1999(000)004
【摘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总页数】6页(P48-53)
【作者】王萍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学报编辑部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司马迁:档史结合的榜样——为纪念周恩来总理指示"档案工作者应该向司马迁学习"四十周年而作 [J], 曹喜琛
2.各家论司马迁撰《史记》宗旨评议 [J], 叶庆兵
3."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司马迁、班固著史优劣辩 [J], 陈桂成
4.同班异科、同科异班、异班异科教学的评价研究 [J], 王汉卿;翟铁倪;孙飞;刘大
勇
5.论司马迁撰史宗旨 [J], 朱枝富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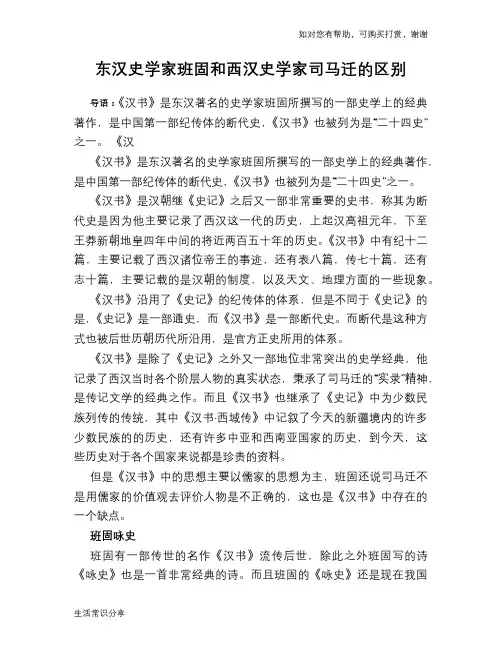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东汉史学家班固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区别
导语:《汉书》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一部史学上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也被列为是“二十四史”之一。
《汉
《汉书》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一部史学上的经典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也被列为是“二十四史”之一。
《汉书》是汉朝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非常重要的史书,称其为断代史是因为他主要记录了西汉这一代的历史,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中间的将近两百五十年的历史。
《汉书》中有纪十二篇,主要记载了西汉诸位帝王的事迹,还有表八篇,传七十篇,还有志十篇,主要记载的是汉朝的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方面的一些现象。
《汉书》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的体系,但是不同于《史记》的是,《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
而断代是这种方式也被后世历朝历代所沿用,是官方正史所用的体系。
《汉书》是除了《史记》之外又一部地位非常突出的史学经典,他记录了西汉当时各个阶层人物的真实状态,秉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是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
而且《汉书》也继承了《史记》中为少数民族列传的传统,其中《汉书·西域传》中记叙了今天的新疆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的历史,还有许多中亚和西南亚国家的历史,到今天,这些历史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是珍贵的资料。
但是《汉书》中的思想主要以儒家的思想为主,班固还说司马迁不是用儒家的价值观去评价人物是不正确的,这也是《汉书》中存在的一个缺点。
班固咏史
班固有一部传世的名作《汉书》流传后世,除此之外班固写的诗生活常识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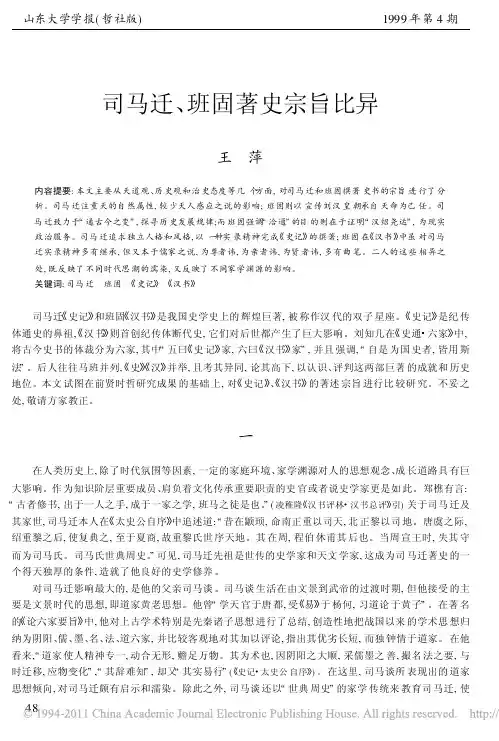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王 萍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
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
司马迁致力于 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 洽通 的目的则在于证明 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
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 史记 的撰著;班固在 汉书 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
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司马迁 史记 和班固 汉书 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
史记 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 汉书 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知几在 史通 六家 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 五曰 史记 家,六曰 汉书 家 ,并且强调,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
后人往往马班并列, 史 汉 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
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史记 、 汉书 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
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
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
郑樵有言: 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 汉书评林 汉书总评 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 太史公自序 中追述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司马迁和班固历史观差异比较[终稿]](https://uimg.taocdn.com/3a33705068eae009581b6bd97f1922791688be06.webp)
浅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差异内容摘要:《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史学家。
虽然同为纪传体史书,但是两部书中所体现出的两位史家的史学观确实不同的。
本文将就两部史书中所体现出的二人不同的史学观进行分析,同时对二人不同史学观的形成也有所探究。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史学观中国历史上司马迁和班固可谓是史学上的双子星座,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分别开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
固然,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两人有着很多相似点,但是二人在史学观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本文将就二人史学观的不同之处进行浅析。
首先就家学渊源的差异来说,对二人史学观的形成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于汉初,那个时期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而司马谈也是崇尚道教思想的。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出的更多是道家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而没有一味地崇尚儒家,他还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①这些都是和他受到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
班固的父亲班彪也是一位史学家,他对班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曾撰有《王命论》,更多的是强调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通篇贯穿着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的儒家经学思想”②。
再者,班固本人也是《白虎通》的撰写者,书中主要宣扬谶纬思想感应学说。
故而《汉书》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儒家正统思想,宣扬一些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而缺少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
为此,班固曾在《汉书》这样表达了他对司马迁的不满,“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③“是非谬于圣人”正说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能够无所畏惧,信笔直书,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爱憎掩功过,更加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
而班固作为一个正统史观的史家,并且还是奉旨修书,故而书中会有不同于司马迁犀利的批判的地方。
如对于吕后,司马迁为其立本纪,主要是出于历史事实考虑,惠帝在位,实权则由吕后掌握;而班固则给惠帝另立本纪,并置于《吕后纪》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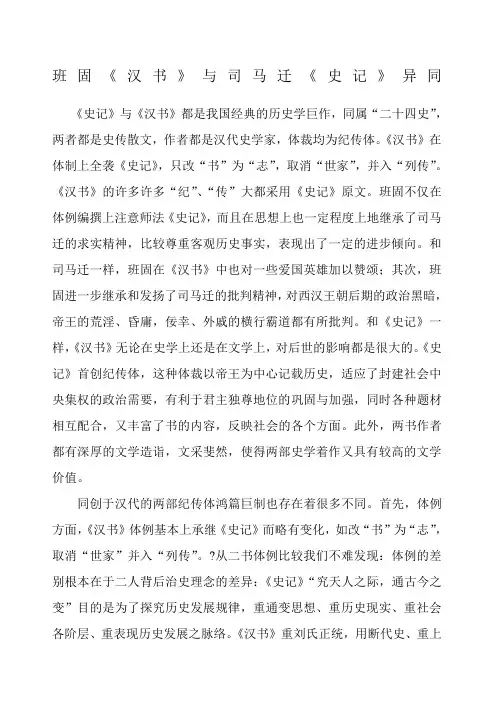
班固《汉书》与司马迁《史记》异同《史记》与《汉书》都是我国经典的历史学巨作,同属“二十四史”,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史记》首创纪传体,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种题材相互配合,又丰富了书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此外,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着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同创于汉代的两部纪传体鸿篇巨制也存在着很多不同。
首先,体例方面,《汉书》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
?从史学思想上的比较来看,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认为统治者应该顺应民众求利的自然之势来制定政策和组织经济活动。
《汉书》也重视民生经济,但它唯心思想教浓,且极力维护封建教条和封建伦理,与《史记》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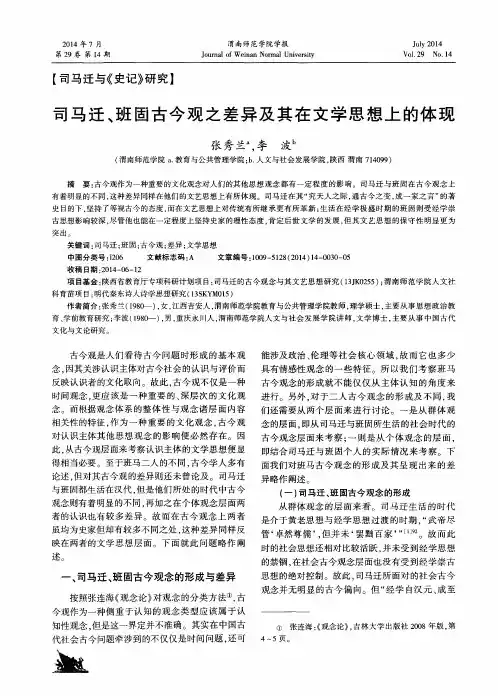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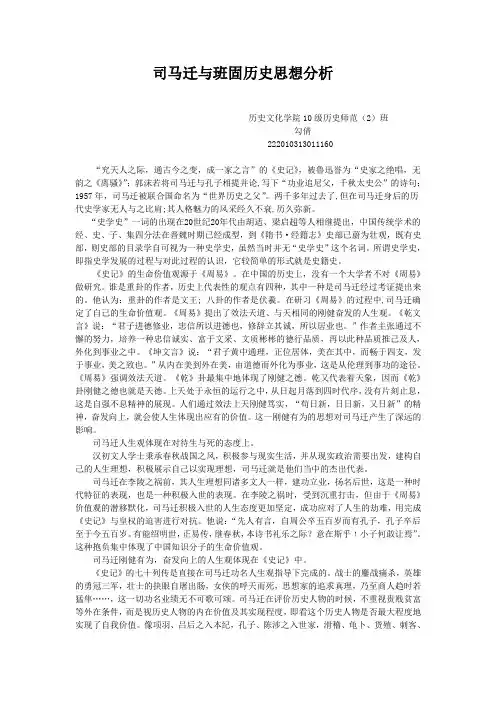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思想分析历史文化学院10级历史师范(2)班勾倩222010313011160“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史学史”一词的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梁启超等人相继提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在晋魏时期已经成型,到《隋书·经籍志》史部已蔚为壮观,既有史部,则史部的目录学自可视为一种史学史,虽然当时并无“史学史”这个名词。
所谓史学史,即指史学发展的过程与对此过程的认识,它较简单的形式就是史籍史。
《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
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
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
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
《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
《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
《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
”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
《周易》强调效法天道。
《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
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
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
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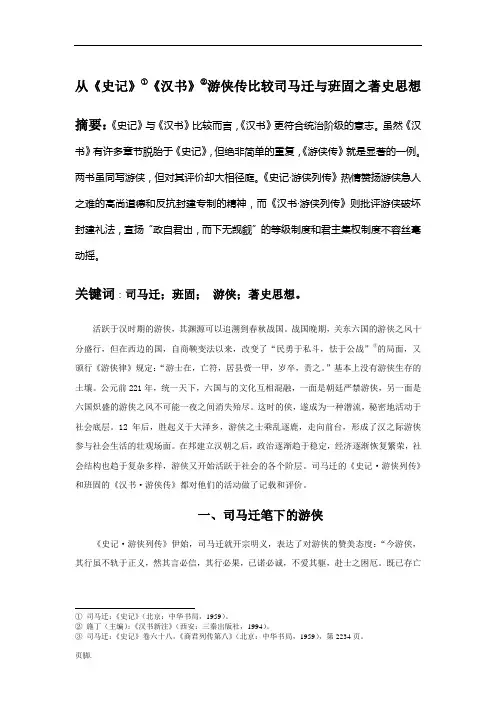
从《史记》①《汉书》②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摘要:《史记》与《汉书》比较而言,《汉书》更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虽然《汉书》有许多章节脱胎于《史记》,但绝非简单的重复,《游侠传》就是显著的一例。
两书虽同写游侠,但对其评价却大相径庭。
《史记·游侠列传》热情赞扬游侠急人之难的高尚道德和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而《汉书·游侠列传》则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宣扬“政自君出,而下无觊觎”的等级制度和君主集权制度不容丝毫动摇。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游侠;著史思想。
活跃于汉时期的游侠,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
战国晚期,关东六国的游侠之风十分盛行,但在西边的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改变了“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③的局面,又颁行《游侠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岁卒,责之。
”基本上没有游侠生存的土壤。
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六国与的文化互相混融,一面是朝廷严禁游侠,另一面是六国炽盛的游侠之风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时的侠,遂成为一种潜流,秘密地活动于社会底层。
12年后,胜起义于大泽乡,游侠之士乘乱逐鹿,走向前台,形成了汉之际游侠参与社会生活的壮观场面。
在邦建立汉朝之后,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经济逐渐恢复繁荣,社会结构也趋于复杂多样,游侠又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的《汉书·游侠传》都对他们的活动做了记载和评价。
一、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史记·游侠列传》伊始,司马迁就开宗明义,表达了对游侠的赞美态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既已存亡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施丁(主编):《汉书新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③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2234页。
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④”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这种意图阐发得尤为明确:“救人之厄,赈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⑤。

《史记》中的古文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的文化思想与艺术成就1. 引言1.1 概述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史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总结性历史著作,记录了从黄帝到西汉末年间共计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
其中,以司马迁和班固等人为代表的古文学家们不仅在记录和传承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在其作品中展示了卓越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分别对《史记》中的两位重要古文学家司马迁和班固进行深入剖析,并探讨他们独特的文化思想与艺术成就。
接着,在第四部分还将涉及其他一些在《史记》中有所记载的古文学家,以窥探其文化思想与艺术成就。
最后,在结论部分对整个文章所呈现出来的观点进行总结归纳。
1.3 目的通过对《史记》中这些重要的古文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进行深入研究,旨在展现他们的文化思想与艺术成就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并揭示他们作品中的智慧与艺术魅力。
同时,通过对其他古文学家也进行简要分析,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些古代文学巨匠在历史进程中卓越的地位和影响。
通过本篇长文的撰写,希望能够唤起读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关注和尊重。
2. 司马迁的文化思想与艺术成就:2.1 司马迁的背景介绍:司马迁(前145年-前86年),字子长,汉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世族世代务农的家庭中,受到良好的教育。
司马迁对于历史与文学有着极高的热情和天赋,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
2.2 司马迁的文化思想:司马迁的文化思想深受儒家经典《尚书》、《春秋》等影响。
他注重人类历史记录和研究,并将历史视为政治和社会变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他相信通过研究过去的事件可以指导未来,并倡导“守道安民”的观点,即君主应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而不是个人私欲。
司马迁非常重视道德伦理观念,在他看来,治理国家需要建立在仁爱和道义之上。
他认为大贤者能够通过仁政使社会获得和谐与稳定,同时也强调个人的修养和道德自律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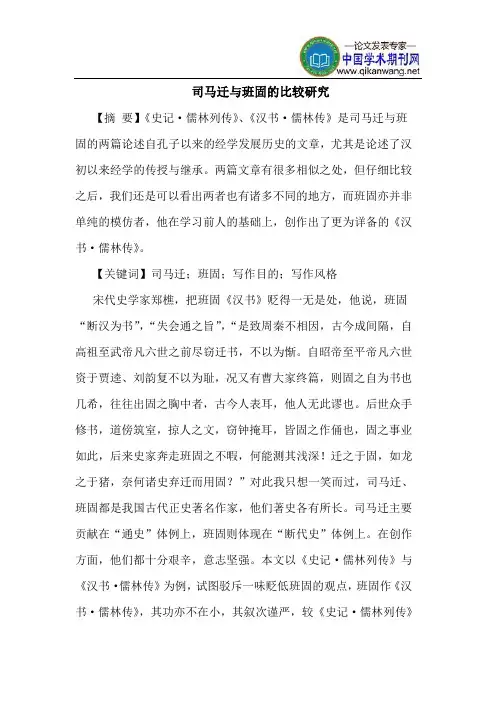
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研究【摘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是司马迁与班固的两篇论述自孔子以来的经学发展历史的文章,尤其是论述了汉初以来经学的传授与继承。
两篇文章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比较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两者也有诸多不同的地方,而班固亦并非单纯的模仿者,他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更为详备的《汉书·儒林传》。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写作目的;写作风格宋代史学家郑樵,把班固《汉书》贬得一无是处,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失会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
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韵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
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对此我只想一笑而过,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
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
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
本文以《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为例,试图驳斥一味贬低班固的观点,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其功亦不在小,其叙次谨严,较《史记·儒林列传》详备远甚。
一我们必须承认,《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以致与后者对前者有抄袭的嫌疑,如下面两段: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
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是时独魏文侯好学。
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
关于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比较的研究文献总结-经济思想史论文-经济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史记》、《汉书》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名着,自诞生以来,便受到后世学者的多方关注,指导着后世史书的编纂。
不同时期,史家对《史记》、《汉书》的评价各不相同,无论是扬班抑马,又或是扬马抑班,都有支撑其思想的理论与依据。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史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史学界开始对二者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
同时,由于史学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凸显,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史学,将史学与自身学科研究结合起来。
在各方学者专家的努力下,《史记》与《汉书》的比较从体例、编纂手法、指导思想等多方面入手,均取得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的中国,推动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成为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史学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史书中经济内容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经济史研究。
《史记》、《汉书》作为中国传统史书的代表着作,其经济内容的比较研究,也越发受到学者的关注。
本文将以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为主要内容,选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代表文章与着作,在综述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理论思考。
一、论文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推进,经济发展深入人心,20世纪80年代后期,陆续出现了对《史记》、《汉书》中经济内容比较的文章,并通过对相关篇章的比较,揭示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的异同。
1987年,归青的《司马迁、班固的经济观之歧异及其思考》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该文通过对经济相关篇章的比较,指出二人经济观上的歧异,包括对人性本质的不同、对商业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建立怎样经济秩序的不同看法,文章的后半部分对造成二者经济观不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是思想观念的差异和面对经济发展现实的复杂心态造成二者在经济观上的不同。
作者在文中指出:司马迁从性恶出发,认为人生而好利。
而班固则不然,他不仅删去了司马迁论述性恶和推崇货殖的句子,还竭力赞美上古的淳朴民风。
司马迁和班固的区别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司马迁和班固区别首先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两人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都非常的深远,也都被奉为是史学的经典。
但是二人也有一些差别,这些差别也都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上。
《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这是一个差别也就不再多做赘述了。
另外,《史记》可以说是一本私人的著作,是司马迁的外孙将《史记》呈给皇帝,《史记》才得以被广泛的阅读。
而《汉书》则不然,因为在成书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班固在写这本书,到后面《汉书》都已经有一些国史的味道了,与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有着很大的差别。
另外司马迁和班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思想差异,司马迁时期,儒家思想还没有被推倒那么高的位置,所以司马迁在评价很多历史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单单用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来做单一的评价,而是加入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和别人的看法。
而班固则不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班固则成为这个运动的产物。
班固已经把儒家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要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具有排他性,因此班固开始批评司马迁没有用儒家的思想来对人物进行评价。
任何时候,思想的单一都会造成闭塞和极端,所以这也是班固和《汉书》的一个缺点。
思想的多元化也能够使文章更加的生动、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显然在这一点上《汉书》和《史记》比起来尤为不足。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班固是《汉书》的作者,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汉书》和《史记》都是我国四史之一。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说班固对司马迁写史记的评价。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这句话,出现在班固的《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以及他的著作《史记》的评价。
原句是: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弊也,予按,此正是迁之微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很多关于是非判断方面是存在一些错误的。
比如说伦天仁大道是先讲的黄老之后说的六经。
中国史学史论文从《史记》《汉书》游侠传比较司马迁与班固之著史思想中国古代的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和传承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史记》和《汉书》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作,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思想。
而其中关于游侠传的内容,更是以司马迁和班固两位史学家的著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本文将从《史记》和《汉书》的游侠传入手,比较司马迁和班固在史学思想方面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被誉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人。
他的《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纪传体(记述历史实事)和表(编制历代君臣的年表)两部分组成。
他以王侯将相和大事为主线,通过纪传体的形式叙述了从五帝到西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的历史,并通过编纂历代君臣的年表,展示了千年历史的发展脉络。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的《汉书》在史学思想上有一些差异。
班固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他的《汉书》是一部以编年体为主要形式的纪传体通史。
不同于《史记》以王侯将相和大事为主要叙述对象,班固更多地关注汉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风貌,着重描写汉朝君臣的生平事迹。
在《汉书》中,班固强调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关系,并对历史人物的品德进行评价,试图通过历史的批判和启示来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
游侠传是《史记》和《汉书》中一个共同的篇章,它记录了古代中国游侠精神的发展以及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游侠传以陈胜吴广、刘邦和项羽等人为代表,反映了他们在战乱年代中的英雄事迹和传奇故事。
另一方面,在班固的《汉书》中,他以陈汤、陈平和翟方进等人为主要对象,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们的游侠行为和为国家辅助和维护的情念。
虽然司马迁和班固在史学思想上有一些差异,但他们都致力于通过历史的研究和记录来展示古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司马迁注重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力求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而班固则更加关注历史人物和道德修养的关系,试图通过历史的反思来提高人们的品德。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分类:大学学报•作者:赵连稳•字数:2827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
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编辑思想;比较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4—0151—05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字梦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司马迁除《史记》外,还著有《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等;班固的著作除《汉书》外,还有《白虎通义》和《东观汉记》等。
他们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
学术界对他们史学成就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对两人编辑思想、尤其是将他们的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很少见。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司马迁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思想;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编撰图书的指导思想。
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始终,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但在当时,儒家思想一时还未在思想领域取得独尊地位,诸子百家学说依然比较活跃,在汉初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家黄老思想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上其父司马谈的耳濡目染,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其头脑中既有道家思想,又新接受了儒家思想观念。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在批判现实,反抗“既成传统”方面有积极作用,司马谈生活在文景到汉武的过渡时期,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史记》和《汉书》的不同点:一、思想比较1、《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
2、《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3司马迁思想解放、观点新颖、批判性强;班固则谨守传统、奉行儒教、歌颂皇权。
、二、风格比较1、感情色彩:《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2、表达上:《史记》写人妙在传神,极富艺术感染力。
而《汉书》有意节制喜怒哀乐之情的表达。
3、取材上:司马迁钟情于才智杰出而落拓不遇之人,他不以成败论英雄,更看重历史人物所具有的精神价值;而班固则出于正统观念,对历史人物或赞或批,对于那些虽齐伟却无益于维护正统观念的人士如刺客、游侠、滑稽、日者等不予立传。
4、在行文上:《汉书》谋篇布局严密有法,记事祥备而删减精当,尚剪裁而词少芜蔓;看起来虽少生气更难有奇气,却也循规蹈矩,合于矩度。
而整齐则主要针对语言而言。
司马迁纵横开阖,以气驭文,故行文跌宕,文气郁勃;而班固为文张驰有度,谨言重法,具有骈化的倾向,如《公孙弘传赞》之“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司马迁传赞》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等皆是。
5、在具体叙述中:《史记》司马迁写得激情澎湃、栩栩如生,而《汉书》班固则是冷静客观,娓娓道来。
6、叙事方法方面:《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而《汉书》只是通过平时的叙述以完成清晰的记事,故其生动性、文学性不及《史记》。
,7、人物刻画方面:《史记》善于运用细节刻画人物性格,而且描绘出人物的内心活动。
《汉书》只是冷静而简略的写叙述。
《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
虽然,两书都长于刻画人物,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思想分析历史文化学院10级历史师范(2)班勾倩222010313011160“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史学史”一词的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由胡适、梁启超等人相继提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分法在晋魏时期已经成型,到《隋书·经籍志》史部已蔚为壮观,既有史部,则史部的目录学自可视为一种史学史,虽然当时并无“史学史”这个名词。
所谓史学史,即指史学发展的过程与对此过程的认识,它较简单的形式就是史籍史。
《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
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
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
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
《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
《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
《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
”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
《周易》强调效法天道。
《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
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
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
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司马迁和班固的编辑思想比较•分类:大学学报•作者:赵连稳•字数:2827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家庭影响有异、著书体例的差别等原因,其编辑思想也各有特色。
在编辑指导思想方面,司马迁注重儒道互补,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指针;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则为了“宣扬汉德”;在写书笔法方面,司马迁基本上秉笔直书,班固则突出地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编辑思想;比较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4—0151—05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班固(公元32—公元92年),字梦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司马迁除《史记》外,还著有《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等;班固的著作除《汉书》外,还有《白虎通义》和《东观汉记》等。
他们不仅是两汉最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很有成就的编辑学家。
学术界对他们史学成就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对两人编辑思想、尤其是将他们的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还很少见。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编辑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在编辑指导思想上,司马迁既有道家思想,又有儒家思想;班固则完全以儒家思想作为编撰图书的指导思想。
司马迁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和汉武帝在位时间相始终,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但在当时,儒家思想一时还未在思想领域取得独尊地位,诸子百家学说依然比较活跃,在汉初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家黄老思想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加上其父司马谈的耳濡目染,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其头脑中既有道家思想,又新接受了儒家思想观念。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否定天的人格和道德属性,在批判现实,反抗“既成传统”方面有积极作用,司马谈生活在文景到汉武的过渡时期,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有名的《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司马谈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我们今天常说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就是他率先提出来的。
司马谈认为六家各有长短,但他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司马谈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
司马迁不承认自然界能够主宰人类社会的活动,在《悲士不遇赋》中,他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在《史记》中,司马迁探讨古今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得出的结论是“物极必反”,这正是道家经典著作《老子》所主张的学说,而他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也与道家思想中反对传统的一面相吻合。
故班彪认为司马迁“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中,儒家思想就没有位置了,相反,由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被最高统治者采纳,儒家思想逐渐显赫起来,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司马迁不可能不受此影响,尤其是他曾经以董仲舒为师,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天人感应思想。
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沿用了董仲舒今文经学神学迷信的说法,什么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项“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明”。
在《高祖本纪》中说刘邦是其母和龙交配而生。
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西汉的建立“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但司马迁对儒家天人感应的思想并未盲从,在另外一些列传中,他认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没有内在必然联系,对儒家思想的天道提出疑义,如在《伯夷列传》中,他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若伯夷…余甚惑焉,偿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因此,在《项羽本纪》中,针对项羽把失败原因归于“天”,司马迁驳斥道:“岂不谬哉!”司马迁编辑指导思想以儒道为主,但并非只限于儒道两家,实际上,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六家要旨》的学术宗旨,对诸子百家兼容并包,认为它们各有所长,不能偏废,所以,《史记》中为老子、韩非、庄子、申不害、墨子、邹衍等各家代表人物立传,并且辑录了他们的典型思想材料。
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儒家思想经过西汉董仲舒及数代帝王的大力提倡,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班固的祖先在西汉时就是儒学世家,东汉时,班家又成为外戚,“家有赐书”,与皇室关系密切。
班固的父亲班彪在刘秀还没有统一全国时,就为刘氏政权寻找理论依据,“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
其中宣扬汉承尧运,天命有归,王者兴衰,非人力所致。
《王命论》的目的在于宣传君权神授思想。
汉章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撰成《白虎通》。
所有这些,使班固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从而把儒家思想作为编纂书籍的指导思想。
在《汉书·叙传》中,班固原文抄录《王命论》,并且开诚布公地宣称自己编纂《汉书》要“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辍道纲”,即要在书中贯穿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其中的原因正如他在《汉书·礼乐志》中所言:“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
”儒家思想“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
因此,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中批评《史记》不以圣人和六经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汉书》删除了《史记》中具有非儒思想的话语和资料,而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持赞赏态度,称之为“宪章六学,统一圣真”。
班固对儒家思想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汉书·艺文志》于各类典籍中,首先叙述儒家《六艺》,次叙诸子十家九流之书;十家之中,又首叙儒家,称赞其“于道最为高”,余下的九家,除去小说家外,“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即其他各家不过是儒家经典的附庸罢了。
班固评价各家学说优劣的标准也全以儒家思想为取舍,他说道家的最大缺陷在于抛弃了儒家的仁义学说,墨家的缺陷在于“非礼”和不知“别亲疏”,违背了儒家“贵贵贱贱”的原则。
在《汉书》中,班固还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如《汉书·古今人表》把上古以降至秦代的人物分为九等,在上上圣人中,班固共列举了14人,除孔子外,其余都是儒家推崇的古代帝王,只有孔子以儒家创始人的身份置身上上圣人之列。
孔门弟子有5人列上中仁人,20余人列上下智人,后学子思、孟子、荀子也居上中仁人。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列于上等。
列为中上等的有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子、兵家代表人物孙膑。
庄子则位居中下等。
诚如钱大昕在梁玉绳撰《古今人表考》序言中所说,孔子列“于上圣,颜、闵、思、孟于大贤,弟子居上位者三十余人,而老、墨、庄、刘诸家咸置中等”。
班固这样做的目的是抬高儒家思想的地位,以“用彰儒学”。
自从董仲舒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以来,这种唯心学说便成为两汉儒学的中心内容,所以,汉朝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形式,以阴阳灾异说与谶纬神学为内容的儒学。
班固在《白虎通》中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发挥到极致。
在《汉书》中,班固大肆宣扬天人感应,说儒家经典都是为了阐述天人感应而作的,《汉书-五行志》记载:“昔殷道驰,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
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又如在传记部分,班固不惜篇幅记载传主附会阴阳灾异的对策、谏言,并且为推崇阴阳灾异的大师立传,最突出的是把董仲舒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特立《董仲舒传》。
和《史记》记载的董仲舒事迹相比较,《汉书·董仲舒传》的内容主要是全文收录了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天人三策》等文献,把董仲舒的理论视为儒学正宗,说:“汉兴,乘秦灭学之后,景、孝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赞誉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
刘向事迹虽然附在《楚元王传》中,但是该传记实际上以刘向为主,传中主要记载了刘向四次上疏言阴阳灾异的内容,将刘向以灾异附会人事写得神乎其神,还称赞他的言论“有补于世”。
《汉书》中的表、志序言,纪、传赞语,多引经义,尤以引用《论语》为最多。
时人仲长统说《汉书》“宗经矩圣”,可谓一语中的。
班固把儒家思想作为编纂史书的指导思想,影响很大,在《汉书》出现后,中国古代书籍、特别是纪传体正史的撰写,大都沿袭了这一做法,并且逐渐形成一种传统。
二在著书宗旨方面,司马迁和班固差别比较明显。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班固著《汉书》则是为了“宣扬汉德”。
“究天人之际”就是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先秦思想界,对“天人关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命题。
司马迁祖先研究天文,是天文世家,他本人对天文学也很有造诣,这使他能够剔除自己思想中的迷信成份,把天视为一种客观存在,把天的运动看成自然界变化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人间吉凶的所谓先兆。
司马迁认为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通古今之变”,就是探求古往今来历史变化原因和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
《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共约3000年的历史,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即他的《史记》记述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大帝时期的历史。
这种通史体例,有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司马迁强调“通变”二字,说:“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略协古今之变”,“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在《史记》中,司马迁重视纵贯古今,企图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求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如《天官书》中说:“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平准书》说:“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十表”和“八书”,就是通变思想在编纂工作中的运用,在谈到作“八书”的目的时,他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如在《礼书》中,司马迁对礼的起源和古今变化做了详细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