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地狱变
- 格式:doc
- 大小:17.00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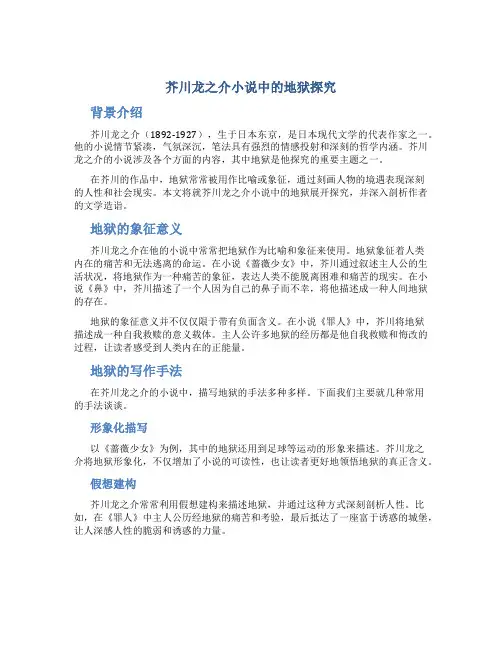
芥川龙之介小说中的地狱探究背景介绍芥川龙之介(1892-1927),生于日本东京,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他的小说情节紧凑,气氛深沉,笔法具有强烈的情感投射和深刻的哲学内涵。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涉及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地狱是他探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芥川的作品中,地狱常常被用作比喻或象征,通过刻画人物的境遇表现深刻的人性和社会现实。
本文将就芥川龙之介小说中的地狱展开探究,并深入剖析作者的文学造诣。
地狱的象征意义芥川龙之介在他的小说中常常把地狱作为比喻和象征来使用。
地狱象征着人类内在的痛苦和无法逃离的命运。
在小说《蔷薇少女》中,芥川通过叙述主人公的生活状况,将地狱作为一种痛苦的象征,表达人类不能脱离困难和痛苦的现实。
在小说《鼻》中,芥川描述了一个人因为自己的鼻子而不幸,将他描述成一种人间地狱的存在。
地狱的象征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带有负面含义。
在小说《罪人》中,芥川将地狱描述成一种自我救赎的意义载体。
主人公许多地狱的经历都是他自我救赎和悔改的过程,让读者感受到人类内在的正能量。
地狱的写作手法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中,描写地狱的手法多种多样。
下面我们主要就几种常用的手法谈谈。
形象化描写以《蔷薇少女》为例,其中的地狱还用到足球等运动的形象来描述。
芥川龙之介将地狱形象化,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也让读者更好地领悟地狱的真正含义。
假想建构芥川龙之介常常利用假想建构来描述地狱,并通过这种方式深刻剖析人性。
比如,在《罪人》中主人公历经地狱的痛苦和考验,最后抵达了一座富于诱惑的城堡,让人深感人性的脆弱和诱惑的力量。
氛围营造芥川龙之介在他的小说中巧妙地运用了氛围营造的手法来描写地狱。
在《杜拉拉昆达拉》中,他通过真实且恐怖的描写,让读者深深感受到地狱的无助和绝望。
宗教和哲学的融合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中,地狱既包含着宗教情感,同时也借鉴了哲学理论。
他在创作中常常在几种文化思想间进行融合,从而更好地表现出地狱的复杂内涵。
小说《地狱变》中,主人公地狱变形被描绘成一种经历了生与死交界的精神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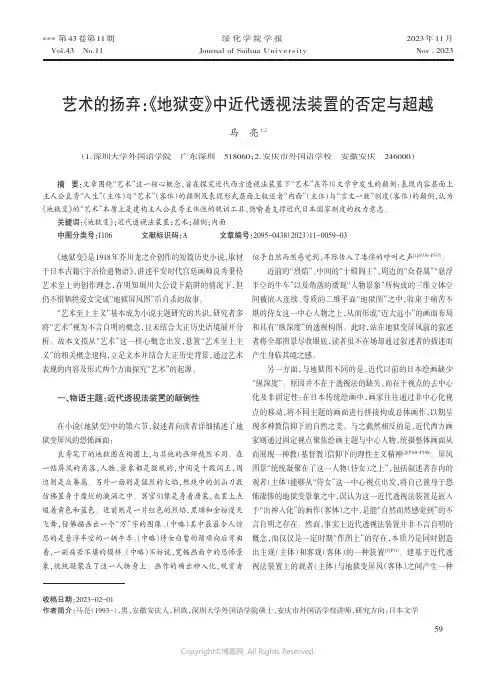
艺术的扬弃:《地狱变》中近代透视法装置的否定与超越摘要:文章围绕“艺术”这一核心概念,旨在探究近代西方透视法装置下“艺术”在芥川文学中发生的颠倒:表现内容层面上主人公良秀“人生”(主体)与“艺术”(客体)的颠倒及表现形式层面上叙述者“内面”(主体)与“言文一致”制度(客体)的颠倒,认为《地狱变》的“艺术”本质上是建构主人公良秀主体性的规训工具,隐喻着支撑近代日本国家制度的权力意志。
关键词:《地狱变》;近代透视法装置;艺术;颠倒;内面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23)11-0059-03(1.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2.安庆市外国语学校安徽安庆246000)《地狱变》是1918年芥川龙之介创作的短篇历史小说,取材于日本古籍《宇治拾遗物语》,讲述平安时代宫廷画师良秀秉持艺术至上的创作理念,在明知堀川大公设下陷阱的情况下,但仍不惜牺牲爱女完成“地狱屏风图”后自杀的故事。
“艺术至上主义”基本成为小说主题研究的共识,研究者多将“艺术”视为不言自明的概念,且未结合大正历史语境展开分析。
故本文拟从“艺术”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悬置“艺术至上主义”的相关概念建构,立足文本并结合大正历史背景,通过艺术表现的内容及形式两个方面探究“艺术”的起源。
一、物语主题:近代透视法装置的颠倒性在小说《地狱变》中的第六节,叙述者向读者详细描述了地狱变屏风的恐怖画面:良秀笔下的地狱图在构图上,与其他的画师截然不同。
在一帖屏风的角落,人物、景象都是微观的,中间是十殿阎王,周边则是众眷属。
另外一面则是猛烈的火焰,燃烧中的剑山刀数仿佛置身于糜烂的漩涡之中。
冥官们像是身着唐装,衣裳上点缀着黄色和蓝色。
近前则是一片红色的烈焰,黑烟和金粉漫天飞舞,仿佛描画出一个“万”字的图像。
(中略)其中最最令人惊恐的是悬浮半空的一辆牛车。
(中略)侍女白皙的颈项向后弯曲着,一副痛苦不堪的模样。
(中略)不妨说,宽幅画面中的恐怖景象,统统凝聚在了这一人物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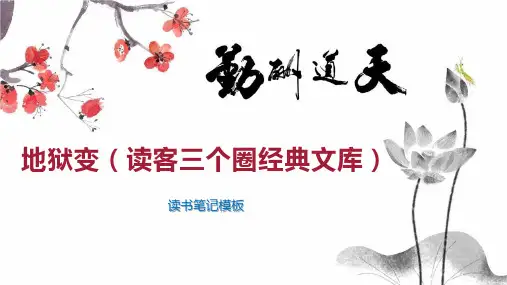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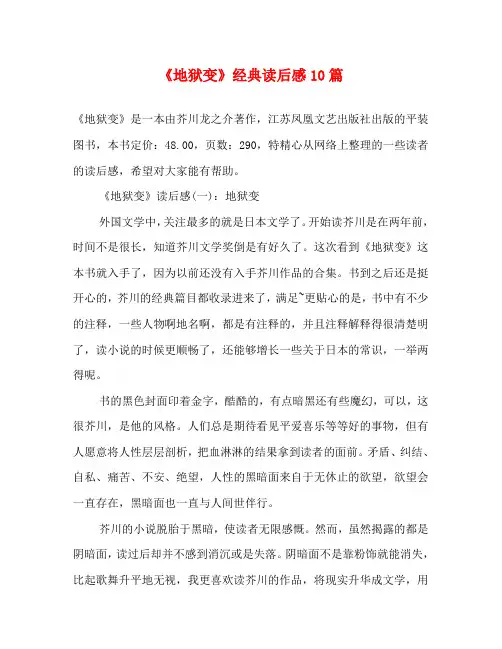
《地狱变》经典读后感10篇《地狱变》是一本由芥川龙之介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2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狱变》读后感(一):地狱变外国文学中,关注最多的就是日本文学了。
开始读芥川是在两年前,时间不是很长,知道芥川文学奖倒是有好久了。
这次看到《地狱变》这本书就入手了,因为以前还没有入手芥川作品的合集。
书到之后还是挺开心的,芥川的经典篇目都收录进来了,满足~更贴心的是,书中有不少的注释,一些人物啊地名啊,都是有注释的,并且注释解释得很清楚明了,读小说的时候更顺畅了,还能够增长一些关于日本的常识,一举两得呢。
书的黑色封面印着金字,酷酷的,有点暗黑还有些魔幻,可以,这很芥川,是他的风格。
人们总是期待看见平爱喜乐等等好的事物,但有人愿意将人性层层剖析,把血淋淋的结果拿到读者的面前。
矛盾、纠结、自私、痛苦、不安、绝望,人性的黑暗面来自于无休止的欲望,欲望会一直存在,黑暗面也一直与人间世伴行。
芥川的小说脱胎于黑暗,使读者无限感慨。
然而,虽然揭露的都是阴暗面,读过后却并不感到消沉或是失落。
阴暗面不是靠粉饰就能消失,比起歌舞升平地无视,我更喜欢读芥川的作品,将现实升华成文学,用精练的语言简明地讲出一个个直击人心的故事。
虽然篇幅不长,但每一篇都值得品味,值得深思。
《地狱变》读后感(二):人间到地狱,咫尺之遥美好的善良的情感和事物,似乎只能够引起人们对其的羡慕和向往。
只有丑的恶的,才能够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激发人们改变现实世界的决心,并为之做出相应的改变和实际的行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有那些深深揭露人性丑恶的作品,无论是艺术上的还是文学上的,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浓重地一笔,也促使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地狱变》就是这样。
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便将“修罗,恶鬼,地狱,畜生的世界,不总是在现世之外。
”的这样的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
尽管是爱伦坡和惊悚恐怖电影的爱好者,但书中所一一展现出来的,关于人性的自私,贪婪,癫狂,唯利是图……,每一张真实到极致的面孔无不让我感到脊背发凉,冷汗直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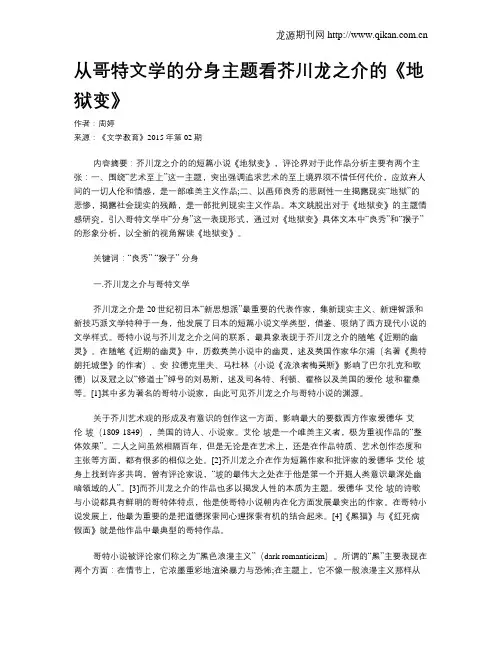
从哥特文学的分身主题看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作者:周婷来源:《文学教育》2015年第02期内容摘要:芥川龙之介的的短篇小说《地狱变》,评论界对于此作品分析主要有两个主张:一、围绕“艺术至上”这一主题,突出强调追求艺术的至上境界须不惜任何代价,应放弃人间的一切人伦和情感,是一部唯美主义作品;二、以画师良秀的悲剧性一生揭露现实“地狱”的悲惨,揭露社会现实的残酷,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本文跳脱出对于《地狱变》的主题情感研究,引入哥特文学中“分身”这一表现形式,通过对《地狱变》具体文本中“良秀”和“猴子”的形象分析,以全新的视角解读《地狱变》。
关键词:“良秀” “猴子” 分身一.芥川龙之介与哥特文学芥川龙之介是20世纪初日本“新思想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家,集新现实主义、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学特种于一身,他发展了日本的短篇小说文学类型,借鉴、吸纳了西方现代小说的文学样式。
哥特小说与芥川龙之介之间的联系,最具象表现于芥川龙之介的随笔《近期的幽灵》。
在随笔《近期的幽灵》中,历数英美小说中的幽灵,述及英国作家华尔浦(名著《奥特朗托城堡》的作者)、安·拉德克里夫、马杜林(小说《流浪者梅莫斯》影响了巴尔扎克和歌德)以及冠之以“修道士”绰号的刘易斯,述及司各特、利顿、霍格以及美国的爱伦·坡和霍桑等。
[1]其中多为著名的哥特小说家,由此可见芥川龙之介与哥特小说的渊源。
关于芥川艺术观的形成及有意识的创作这一方面,影响最大的要数西方作家爱德华·艾伦·坡(1809-1849),美国的诗人、小说家。
艾伦·坡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极为重视作品的“整体效果”。
二人之间虽然相隔百年,但是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作品特质、艺术创作态度和主张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2]芥川龙之介在作为短篇作家和批评家的爱德华·艾伦·坡身上找到许多共鸣,曾有评论家说,“坡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开掘人类意识最深处幽暗领域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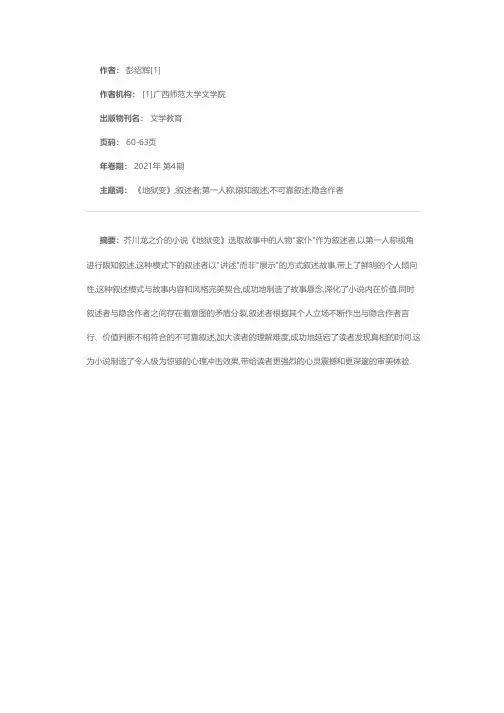
作者: 彭绍辉[1]
作者机构: [1]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文学教育
页码: 60-63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4期
主题词: 《地狱变》;叙述者;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不可靠叙述;隐含作者
摘要: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地狱变》选取故事中的人物"家仆"作为叙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限知叙述,这种模式下的叙述者以"讲述"而非"展示"的方式叙述故事,带上了鲜明的个人倾向性.这种叙述模式与故事内容和风格完美契合,成功地制造了故事悬念,深化了小说内在价值.同时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存在着意图的矛盾分裂,叙述者根据其个人立场不断作出与隐含作者言行、价值判断不相符合的不可靠叙述,加大读者的理解难度,成功地延宕了读者发现真相的时间.这为小说制造了令人极为惊骇的心理冲击效果,带给读者更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更深邃的审美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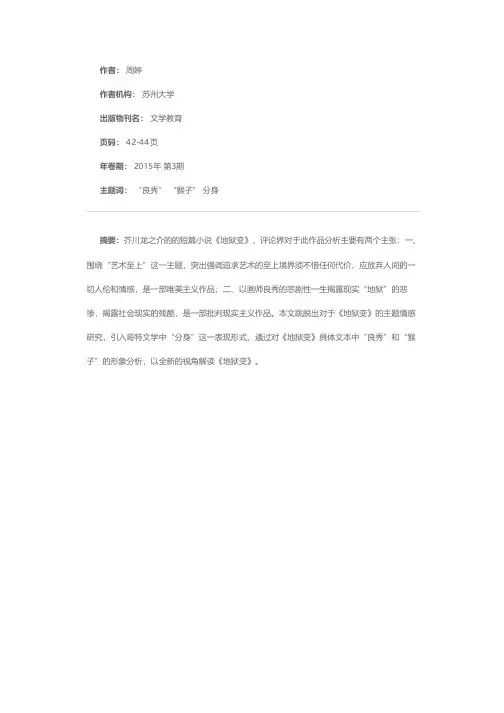
作者: 周婷
作者机构: 苏州大学
出版物刊名: 文学教育
页码: 42-44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3期
主题词: “良秀” “猴子” 分身
摘要:芥川龙之介的的短篇小说《地狱变》,评论界对于此作品分析主要有两个主张:一、围绕“艺术至上”这一主题,突出强调追求艺术的至上境界须不惜任何代价,应放弃人间的一切人伦和情感,是一部唯美主义作品;二、以画师良秀的悲剧性一生揭露现实“地狱”的悲惨,揭露社会现实的残酷,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本文跳脱出对于《地狱变》的主题情感研究,引入哥特文学中“分身”这一表现形式,通过对《地狱变》具体文本中“良秀”和“猴子”的形象分析,以全新的视角解读《地狱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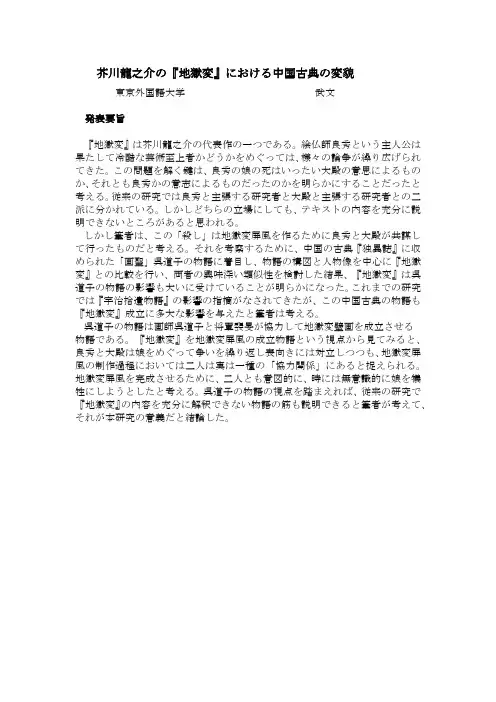
芥川龍之介の『地獄変』における中国古典の変貌東京外国語大学武文発表要旨『地獄変』は芥川龍之介の代表作の一つである。
絵仏師良秀という主人公は果たして冷酷な芸術至上者かどうかをめぐっては、様々の論争が繰り広げられてきた。
この問題を解く鍵は、良秀の娘の死はいったい大殿の意思によるものか、それとも良秀かの意志によるものだった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だったと考える。
従来の研究では良秀と主張する研究者と大殿と主張する研究者との二派に分かれている。
しかしどちらの立場にしても、テキストの内容を充分に説明できないところがあると思われる。
しかし筆者は、この「殺し」は地獄変屏風を作るために良秀と大殿が共謀して行ったものだと考える。
それを考察するために、中国の古典『独異誌』に収められた「画聖」呉道子の物語に着目し、物語の構図と人物像を中心に『地獄変』との比較を行い、両者の興味深い類似性を検討した結果、『地獄変』は呉道子の物語の影響も大いに受け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
これまでの研究では『宇治拾遺物語』の影響の指摘がなされてきたが、この中国古典の物語も『地獄変』成立に多大な影響を与えたと筆者は考える。
呉道子の物語は画師呉道子と将軍裴旻が協力して地獄変壁画を成立させる物語である。
『地獄変』を地獄変屏風の成立物語という視点から見てみると、良秀と大殿は娘をめぐって争いを繰り返し表向きには対立しつつも、地獄変屏風の制作過程においては二人は実は一種の「協力関係」にあると捉えられる。
地獄変屏風を完成させるために、二人とも意図的に、時には無意識的に娘を犠牲にしようとしたと考える。
呉道子の物語の視点を踏まえれば、従来の研究で『地獄変』の内容を充分に解釈できない物語の筋も説明できると筆者が考えて、それが本研究の意義だと結論した。
Comparing Hell Screen and the Story of Wu DaoziWu WenIntroductionResearchers have argued for a long time ov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Yoshihide is a stony-hearted artist or not. However, the key point in regard to this question is to establish whether the originator of the tragedy is Yoshihide or the archduke. The author himself suggests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ath of Yoshihide’s daughter does not simply lie on either one of them, but lies rather on the complicity of them both, whose their tacit objective being to create the matchless folding ‘hell screen’. Here, the author has cited the story of Wu Daozi, who was the most famous Buddhist artist in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n order to attest this viewpoint.Hell Screen,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Akutagawa Ryunosuke, uses the creation of a folding screen depicting hell as the main thread of the story. Telling the story of Yoshihide’s daughter, it depict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power, represented by the archduke Horigawa, and art, represented by the painter Yoshihide, and represents Akutagawa’s views on art and life. Hell Screen is an enigmatic work of fiction, and most previous research considers that the painter Yoshihide and the archduke are in opposing positions, and thu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factions, which, it is suggested, are led by Yoshihide and the archduke respectively. Researchers have different views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Yoshihide’s dream and the person who intended to rape Yoshihide’s daughter, and have not yet come to a consensus. If we consider Yoshihide to be a stony-hearted artist sacrificing his daughter on his own initiative, it would not conform to Akutagawa’s original idea, because Akutagawa mentioned the ‘instruction of brightness’ and the ‘instruction of dark’1when he reviewed this work, and told us clearly that the inflating of the archduke is indeed to show the outrageousness of his essential character. From the story, we may understand that the archduke is the prime criminal in the killing of the Yoshihide’s daughter. However, we cannot consider that the archduke planned the death of Yoshihide’s daughter as a retaliation, because the archduke did not know Yoshihide to be unable to ‘effectively paint anything he has not seen’ when he instructed Yoshihide to paint the folding screen, and for this reason, it could not be a plot.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in fact Yoshihide who offered to burn the cart and bring about his daughter’s death. Therefore, who actually caused the death of Yoshihide’s daughter, the archduke or Yoshihide?ContentAkutagawa was good at Sinology, and had great accomplishment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s. He often referred to things related to China, for instance, an shaman from China who took on the spirit of the famous doctor Huatuo and who opened up a patient’s legs to cut out the tumour (華陀の術を伝へた震旦の僧に、御腿の瘡を御切らせになつた事)2”, and hell officials in Tang-dynasty dress (唐めいた冥官). Considering that some of Akutagawa’s stories came from Chinese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hat there are even much more such expressions like these in Hell Screen than in other works, we should to establish whether Hell Screen is related to any Chinese story. Here, we shall consider the story of Wu Daozi, who liv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painted the first hell screen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story is recorded in Duyizhi3which is contained in a collection belonging to Akutagawa named Taipingguangji.This record is similar to Akutagawa’s Hell Screen in respect to the characters and the structure. Firstly, the two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Pei Qian as the General and Wu Daozi the artist, are similar to the archduke and Yoshihide respectively, and both sets exemplify the idea of ‘superman versus genius’. Secondly, the structure of the story – 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turn and conclusion (起承転結) – is similar. The mainframework of the works may be compared in detail:The introduction (起): in Hell Screen, the archduke orders Yoshihide to paint thefolding hell screen; similarly, in the story of Wu Daozi, General Pei asks Wu Daozi to paint the hell screen fresco.The development (承):Yoshihide agrees to paint; Wu Daozi also agrees.The turn (転): Yoshihide cannot imagine the lady in the burning cart, and asks thearchduke to carry this out; Wu Daozi says that he has not painted for a long time and wishes General Pei to perform a sword-dance in order to ‘get to hell’. Both wishes are approved. Yoshihide wished to see the actual image of the lady in the fire, while Wu Daozi wanted to feel the conditions of hell from the sword dance.The conclusion (結): the archduke burns Yoshihide’s daughter to death, after whichYoshihide devotes his life to finishing the masterpiece and then commits suicide himself; General Pei performs a sword-dance and Wu Daozi continues painting the masterpiece throughout his life.From the above, we can se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works is almost the same, not only in their structure, but also in their characters. Firstly, the characters Wu Daozi and Yoshihide are both the most famous painters of their time. Wu Daozi (685?-758) a sage of Chinese Painting, is famous for his Buddhist murals and landscape paintings. Furthermore, Yoshihid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talented painter in the world. Secondly, both of them are so eccentric that they do not believe in gods or demons. Wu Daozi painted his own face on the face of the Bodhisattva in the fresco, which indicated that he did not believe in any god. Meanwhile Yoshihide is depicted similarly in Hell Screen. ‘In his opinion, it is a lie that gods can transmit themselves to common peopl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he is a person who draws Lakshmi as ascoundrel and Acalanatha as a depraved buffoon, and who does things oddly on purpose’. From this comparison, we may discover that there are so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Yoshihide and Wu Daozi, including in the details of their depiction, that these similarities are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ones with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ere is a comparison:According to a previous study, Hell Screen comes from: a story from the Uji Shūi Monogatari, volume 3, “Ryōs hū, a Buddhist Artist who was Glad to see his Home been Burnt Down”; the story “A Buddhist Named Ryōs hū” in Chapter 6 of Jikkinshō; and the story of a painter called Hirotaka in chapter 11 of Kokon Chomonjū. According to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Nagano Shōichi4, the parts related with Uji Shūi Monogatari are mere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shihide and the fact that the painter realized his destiny. Because the complex story of Hell Screen could not be created using Yoshihide alone,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the figure of the archduke is related to Duyizhi. Actually, Akutagawa seems to emphasize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 story and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the archduke as Qin Shi Huang and Sui Yang Di (two famous emperors during the Tang and the Sui Dynasty). Also, Akutagawa provided Yoshihide the nickname of ‘chiraeiju’, which is a name for tengu coming from China. These facts hint that these two figures came from China. Of course, Duyizhi is only one of the origins of Hell Screen. The depiction of the archduke was greatly altered, and the figures of Yoshihide’s daughter, the little monkey, and the monk are Akutagawa’s own creation.Finally, we come back to the issue mentioned in the beginning: who caused the death of Yoshihide’s daughter, the archduke or Yoshihide? The reason why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considered as opposites, a good and an evil character, of which one of them brought about the tragedy. However, the relation between Wu Daozi and General Pei provides us with the inspiration that both sides make great efforts to create the hell screen, and thus have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If we consider Hell Screen as a story of the birth of a famous painting, in which both Yoshihide and the archduke are keen to give birth to the hell screen, and are even willing to sacrifice Yoshihide’s daughter, they are actually complici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may find an answer. The maxim ‘art for art’s sake’ means that is that art is everything for an artist, and 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not be sacrificed for art. In Akutagawa’s thought, this is the optimal spirit for an artist.Conclusion<Hell Screen> was writt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th Japanese and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s. <Duyizhi> influenced <Hell Screen> in two ways: one is on the plot of ‘genius versus superman’, it filled the figure of Yoshihid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Wu Daozi and made the character of Archduke out of General Pei Qian. The other is that it gives us a new point of view. If we consider Yoshihide and Archduke as accomplices, it would be very easy to explain the question in the beginning. Yoshihide and Archduke sacrificed Yoshihide’s daughter jus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the ‘Hell Screen’, a precious artwork.What the Akutagawa wanted to highlight is the pursuit of artistic creation,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it is, never give up. Yoshihide is just the real artist with such a great spirit.Reference1小島政二郎宛書簡(1918年6月)「芥川氏より――地獄変について」『三田文学』9-72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全集第一巻』岩波文庫1995年11月3李冗『独異志』巻中(『太平廣記』李昉1846年版)4長野甞一『芥川龍之介と古典』第九章「地獄変」勉誠出版2004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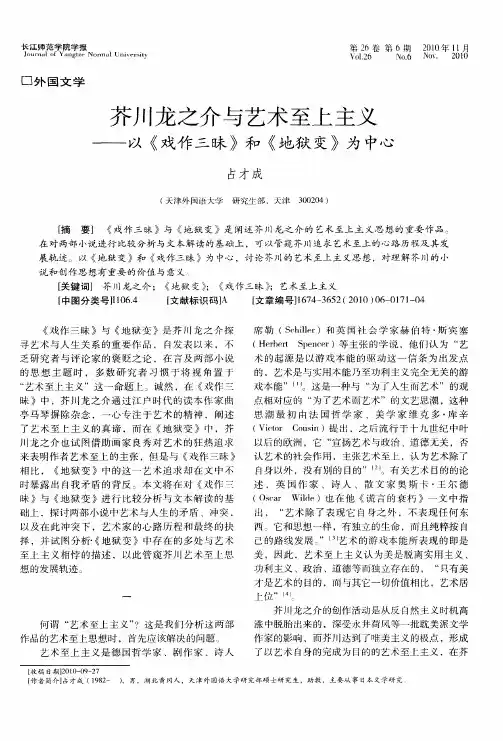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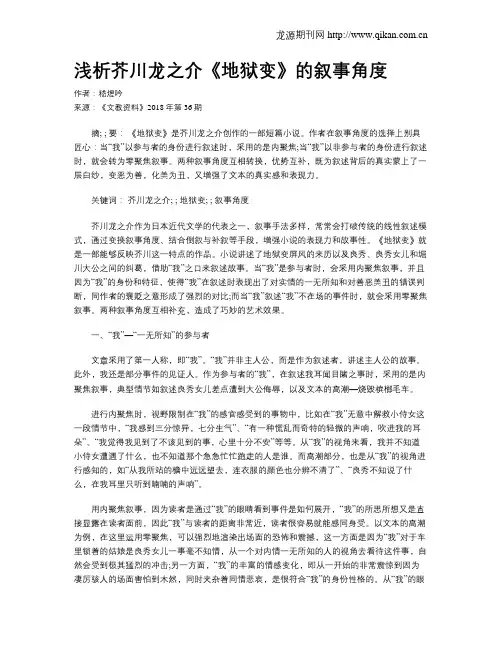
浅析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叙事角度作者:嵇煜吟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36期摘; ; 要:《地狱变》是芥川龙之介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
作者在叙事角度的选择上别具匠心:当“我”以参与者的身份进行叙述时,采用的是内聚焦;当“我”以非参与者的身份进行叙述时,就会转为零聚焦叙事。
两种叙事角度互相转换,优势互补,既为叙述背后的真实蒙上了一层白纱,变恶为善,化美为丑,又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感和表现力。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 地狱变; ; 叙事角度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代表之一,叙事手法多样,常常会打破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通过变换叙事角度、结合倒叙与补叙等手段,增强小说的表现力和故事性。
《地狱变》就是一部能够反映芥川这一特点的作品。
小说讲述了地狱变屏风的来历以及良秀、良秀女儿和堀川大公之间的纠葛,借助“我”之口来叙述故事。
当“我”是参与者时,会采用内聚焦叙事,并且因为“我”的身份和特征,使得“我”在叙述时表现出了对实情的一无所知和对善恶美丑的错误判断,同作者的褒贬之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当“我”叙述“我”不在场的事件时,就会采用零聚焦叙事。
两种叙事角度互相补充,造成了巧妙的艺术效果。
一、“我”—“一无所知”的参与者文章采用了第一人称,即“我”。
“我”并非主人公,而是作为叙述者,讲述主人公的故事。
此外,我还是部分事件的见证人。
作为参与者的“我”,在叙述我耳闻目睹之事时,采用的是内聚焦叙事,典型情节如叙述良秀女儿差点遭到大公侮辱,以及文本的高潮—烧毁槟榔毛车。
进行内聚焦时,视野限制在“我”的感官感受到的事物中,比如在“我”无意中解救小侍女这一段情节中,“我感到三分惊异,七分生气”、“有一种慌乱而奇特的轻微的声响,吹进我的耳朵”、“我觉得我见到了不该见到的事,心里十分不安”等等。
从“我”的视角来看,我并不知道小侍女遭遇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个急急忙忙跑走的人是谁。
而高潮部分,也是从“我”的视角进行感知的,如“从我所站的檐中远远望去,连衣服的颜色也分辨不清了”、“良秀不知说了什么,在我耳里只听到喃喃的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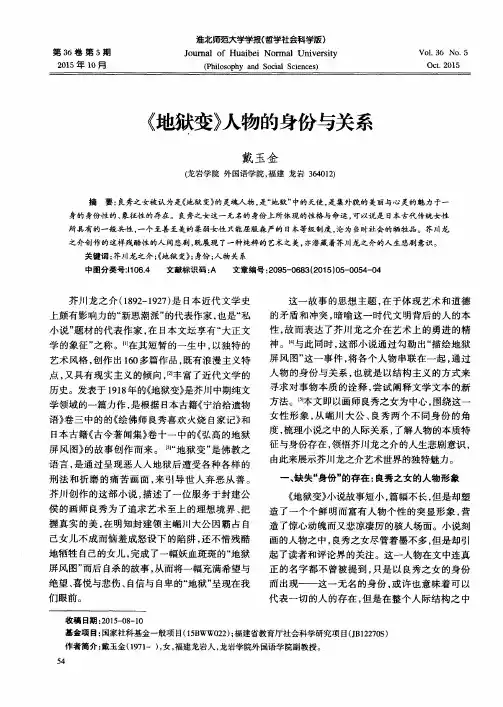
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主题探微作者:白英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02期摘要:本文从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名作《地狱变》的出场人物入手,结合对文章情节的分析,试图深入探讨其角色的设定和作品主题表现的关系。
笔者分析得出《地狱变》的主题不局限于“艺术至上”以及“作家芥川龙之介和艺术至上主义”等历来研究者所提出的观点。
而是更有深层的社会因素,即文章所体现出的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精神。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地狱变》;主题;封建社会[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0-02芥川龙之介( 1892- 1927)他是日本大正时代小说家。
他全力创作短篇小说,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了超过150篇短篇小说。
他的短篇小说篇幅很短,取材新颖,情节新奇甚至诡异。
作品关注社会丑恶现象,但很少直接评论,而仅用冷峻的文笔和简洁有力的语言来陈述,便让读者深深感觉到其丑恶性,因此彰显其高度的艺术感染力。
芥川于一九一三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学习,一九一五年发表短篇小说《罗生门》,之后连续发表过短篇小说《鼻子》、《芋粥》和《手绢》,逐步奠定了他的稳固的作家地位。
芥川龙之介作为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说既有浪漫主义的特点,也有现实主义倾向。
他早期的作品主要以历史小说为主,内容大多是借古讽今、针砭时弊。
《地狱变》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地狱变》是取材于日本典故的短篇小说。
该小说所取用的典故出自《宇治拾遗物语》的第三卷、《十训抄》的第六卷,以及《古今著文集》的第十一卷。
但其文章的构思以及主题思想完全独立于原典,属于作者的独立创作。
小说语言诡怪绚丽,所描写的场面惊心动魄,气氛神秘悲壮,具有震憾人心的气势和力量。
这其中主要的艺术成便是塑造了具有性格特征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其集中体现于画师良秀、良秀的女儿以及封建统治者堀川老爷形象等人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即作为文章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出场人物的堀川大公府中的仆役。
读《地狱变》后感何为地狱?地狱,被一些人认为是生前罪大恶极的人死亡后灵魂的归所。
与天堂相对,地狱尽显人性之恶,没有光明,没有喜乐,永受无尽的痛苦。
芥川龙之介说过这样的话:“人生,远比地狱还像地狱”,在《地狱变》中,他藉由主人公良秀的形象道明,希望读者能从故事中明白点什么,而良秀正是他表达这层寓意的口述者。
在小说中,画家良秀是一个长相丑陋、放荡不羁、傲慢自大的人,对别人都漠不关心,唯独关爱自己的女儿。
良秀是冷酷贵族堀川大公手下的一名画师,一手画技精妙绝伦,热爱艺术,甚至对女儿的疼爱都无法与其对艺术的热爱相媲美,几近癫狂。
良秀在绘画创作上有一个怪癖,只画亲眼所见之物,并且喜欢以显示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描绘妖魔鬼怪。
传说人们从他的《生死图》旁边经过时,可以听到神鬼的叹息,也会闻到死尸腐烂的恶臭。
一次,良秀受大公之命画一幅名为“地狱变”的屏风,来描绘地狱中的惨象,良秀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废寝忘食、没日没夜的创作了半年,屏风完成了一大半,但唯独画中缺少了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在牛车中被烈火焚烧的女人,因为他没有办法画自己没有见过的事物。
于是他请求大公帮他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火灾,把一个穿着华丽的女侍所在牛车中烧死。
大公玩味的笑了,答应了他的请求。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大公命人准备好的牛车、火把和一个穿着华美的女人,并把良秀叫到现场观看火灾,寻求灵感,但当大家看向笼子的那一刻,发现牛车里被捆住的美妇人不是别人,竟是良秀心爱的女儿,良秀惊慌失措的冲向马车,却晚了一步,牛车已经被点燃。
看着冲天的火光,大公露出了野兽一般的兴奋,然而更诡异的是,随着火势的增大,良秀在女儿痛苦的叫喊声中,竟渐渐冷静下来,甚至露出了愉悦兴奋的表情。
火灾之后,良秀顺利的完成了屏风最重要的部分,而他自己也在第二天悬梁自尽。
这篇短片小说写于1918年,当时日本经历里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巨额的战争赔款使日本经济的发展如虎添翼,经济的发展也迅速激发了日本社会上和思想上的矛盾。
新玉文艺6 一、绪论对于芥川龙之介作品的研究,以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较多,文本分析方面则大多是对芥川的艺术观或生死观展开研究。
涉及芥川的“疯癫”问题研究较少,而专门以福柯的疯癫理论来论述芥川“疯癫”问题的研究则更为少见。
芥川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精神状态使得他的很多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疯癫”问题。
因此本篇论文借用福柯的疯癫理论对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和《河童》这两部作品中涉及“疯癫”问题的地方进行探究。
二、福柯的“疯癫”理论福柯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前卫人物。
他认为精神病不是一种自然的或生理方面的疾病,而是一种对人群加以分类的社会功能。
关于“疯癫”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想认识疯癫就得先将其排除出去……甚至运用暴力使它们噤声。
人们使疯癫噤声,从而认识了疯癫。
”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疯癫的命运就是知识-权力这样一个制度把理性与非理性不断地分离的过程,是理性与疯癫之间的对话逐渐隔绝的过程,也是疯癫最终成为认识对象、一种疾病的过程。
在一开始理性与非理性是相通的,有桥梁进行沟通的,但是人们对癫狂进行了精神病的处理,把理性与非理性彻底分离开了。
实际上是人们人为地炮制了精神病这一现象。
在福柯看来疯癫一直被理性所言说、指控、谴责和统摄,从来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同样芥川龙之介也多次将这种疯癫运用到作品中,并折射出人性的丑恶与矛盾。
三、《地狱变》中的良秀式疯癫《地狱变》这部作品是芥川龙之介于1918年发表的小说,当时的日本经历了两次大战-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
这两场战争均以日本的胜利而结束。
战争的胜利和巨额的战争赔款给日本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机会。
但伴随而来的则是国内社会和思想上的矛盾日益趋向深刻和尖锐。
《地狱变》的主人公—画师良秀对于艺术近乎变态的痴迷与执着让人感受到震撼。
为了成就艺术,他放弃了亲情,背弃人伦人性。
他把徒弟捆绑起来任由猫头鹰的攻击以观察险象发生时的真实情形来作画,他在女儿被活活烧死的瞬间却只顾着埋头描绘一幅惨绝人寰的旷世绝作,自己也在画完地狱变相图的第二天夜里自缢身亡。
试论《地狱变》中猴子的角色作用作者:谢发朵来源:《牡丹》2016年第08期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地狱变》中一直陪伴良秀女儿的那只小猴子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的出现推动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同时也突出了小说主旨。
猴子的角色设定是《地狱变》中行文技巧方面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
《地狱变》是芥川龙之介的得意之作,文中比较形象地说明了作者对艺术的态度。
《地狱变》中人物并不是很多,主要是画师良秀及其女儿,以及他们的主人大公。
每个人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而文中还有一个不能被忽略的角色,就是出现在良秀女儿身边并最后陪着她死去的一只小猴子。
到目前为止,关于《地狱变》中的人物研究对象主要为良秀及其女儿两个人物,如寇淑婷和盖宇坤写的《“地狱”中的天使——试论〈地狱变〉中的“良秀之女”》、王晨的《日本近代小说〈地狱变〉中良秀的悲剧》等。
而小说中出现的猴子这一动物角色,虽有人提及但从未有系统的分析。
笔者认为,这只猴子虽是动物,但在小说中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芥川龙之介的苦心安排。
基于此,本文从情节发展和文章主题两方面来讨论猴子这一角色的重要作用。
一、推动情节发展良秀的女儿不仅美丽,且懂事、伶俐,因而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但她真正受到大公高度关注的是‘追猴子’事件。
大公得知这件事之后说:“‘看不出还是一个孝女哩,值得夸奖呀!’大公当场赏了她一方红帕,那猴儿见女儿捧着红帕谢恩,也依样对大公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逗得大公都乐了。
因此大公分外宠爱良秀的闺女。
”但是,从叙述者的多处表面为否认实为肯定的叙述看,大公对良秀女儿是别有用心的。
在这种情况下,小猴子的出现让她更受宠爱,实际上是为下文悲剧的发生埋下伏笔。
情节进一步发展,“就在这时候,有一天晚上,已经深夜了,我一个人独自走过廊下,那只名叫良秀的猴儿,忽然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使劲拉住我的衣边。
……”原来良秀的女儿被人欺负了,小猴子来求救。
危机暂且化解之后,“走了不到十来步,我的裤脚管又在后面被悄悄拉住,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你猜,拉我的是谁?原来还是那只猴子,它像人一样跪倒在我的脚边,脖子上金铃玎玲做声,正朝我连连叩头。
2018.7~8本版编辑/·高中◉执教:刘斐1观察:范飚2摘要:根据预习作业中显示的基本学情,制定了以“如何读懂”为目的的教学目标。
根据学情预判在实现教学目标过程中,学生的难点在于第一人称讲述者的话不完全可信和文本中极易忽略的对理解人物和情节至关重要的微小细节。
据此设计教学环节,一方面以问题和小结不断推进阅读策略的传授;同时,重视学生的学习经历,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运用策略,通过学习经历加深对阅读策略的理解。
关键词:阅读策略学情学习经历小结【教学设想】芥川的小说蕴含了非常丰富而深厚的日本文化。
想讲到什么高度都可以,怎么讲都不为过。
那么,教学内容要设定为高大上的日本美学或日本哲学吗?教学重点和教学目标究竟应该来自哪里?传统的小说教学往往以小说三要素为路径,侧重于挖掘作品的主题。
但我认为教学重点的确立应当取决于文本自身的特点。
正是基于《地狱变》自身最突出的特点———叙述视角,我抛弃了传统小说教学中以小说三要素为路径的教学方法。
更重要的是,不能脱离形式空谈主题。
形式即内容。
一部作品的形式不仅仅是为了吸引读者,更是为了表现主题。
很多时候,明白了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也就明白了作者要表现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讲故事的技巧和故事的主题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而教学目标的确立则完全应该来自学情。
不基于学生起点的教学,再怎么高深,对学生来说,都是虚妄,是无意义的。
我的教学目标的确立就是基于学生根本都不懂故事的学情。
教给他们读懂的方法和策略,才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
至于课堂上的调动引导。
重要的是要明确问题,引导学生根据问题来回答。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中的主导作用。
【课堂实录】一、导入师: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地狱变》。
芥川龙之介在日本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作家。
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芥川文学奖”是日本纯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
今天我们要学的这篇《地狱变》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地獄変」の主人公良秀の分析
——芸術至上主義
「地獄変」は、芥川龍之介の最高傑作のひとつとして、発表直後から高く評価されてきた。
それを詳細に分析してみると、良秀の芸術至上主義的姿勢を宣揚しようということが判明する。
小説の内容は「本朝第一の画師」である良秀は、大殿から<地獄変の屏風>を描くように命じられ、一人娘を見殺しにして絵を完成させる。
良秀自身は縊れ死んだが、絵は後世まで残った。
このように芸術家は最高の芸術を実現させた。
作者はあらゆる外界の対象に対し、敵意と不安を感じるの中で、『地獄変』の主人公良秀と呼ぶ画師の運命を思う。
それで良秀を設定する、良秀は、このような創作こそ、良秀の思想性の欠如、現実の中での孤立感、不安感があっだ。
このような良秀の存在とすれば、一体、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のか。
語り手によれば、良秀は「とにかく醜いものが好き」であり、彼も大殿の前で「かいなでの絵師には総じて醜いもの、美しさなどと申す事は、わからう筈がございませぬ」と嘯く。
まだ、良秀が「世間の習慣とか慣例とか申すやうなものまで、すべて莫迦に致さずには置かない」と語った。
良秀の<地獄変の屏風>の完成に至る苦悶の過程は、そのまま自己のイデォロギーを完全に裡に血肉化しようとする過程だ。
<地獄変の屏風>を完成させるために、不敵に「あでやかな上臈」を焼いた良秀は、大殿を筆頭とした世界からの悪意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のだろう。
このような良秀のアナーキーな態度から、語り手を代表とする秩序の奉仕者は危機を感じる。
良秀に対する不安から、彼の人柄、性格には嫌悪だ、それで、大殿を讃美する裏側で、良秀という芸術家の抹殺を暗に意図していることがある。
このような芸術家と現実の矛盾は恐らくいつの時代にでもは見られる、普遍的な関係だ。
体制の秩序維持の側に、決して解決する方法があるのだ。
表面は平静で、奇麗な日常世界、この虚飾の外から、奥に潜む醜悪な人間の本質を見通す。
そうした人間の生きる世界を<地獄>とみなす。
そして、そうした虚飾に充ちた外面の人間世界の中で、良秀は日常の階級や身分とは無縁だ。
日常の秩序は、すべて良秀の眼から脱落し、解体する。
このように、階級
関係に根ざした秩序の一切を転覆させることを良秀が夢想してあろう。
「地獄変」は芸術と現実との対決、そして芸術家の勝利を描くことが、作者自身の現実の中での存在意義を明確にすることが違いなかった。
現実の中での自己の存在意義を明確にせずには、一歩も進んではいけなかった。
それは芥川の本質に潜む不安定だろう。
だから、<主人公>良秀の「芸術の完成のためにはいかなる犠牲も厭わない」という姿勢が、芸術至上主義の徹底的追求という芥川自身の姿勢と同じである。
日语一班 20127932
戴茜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