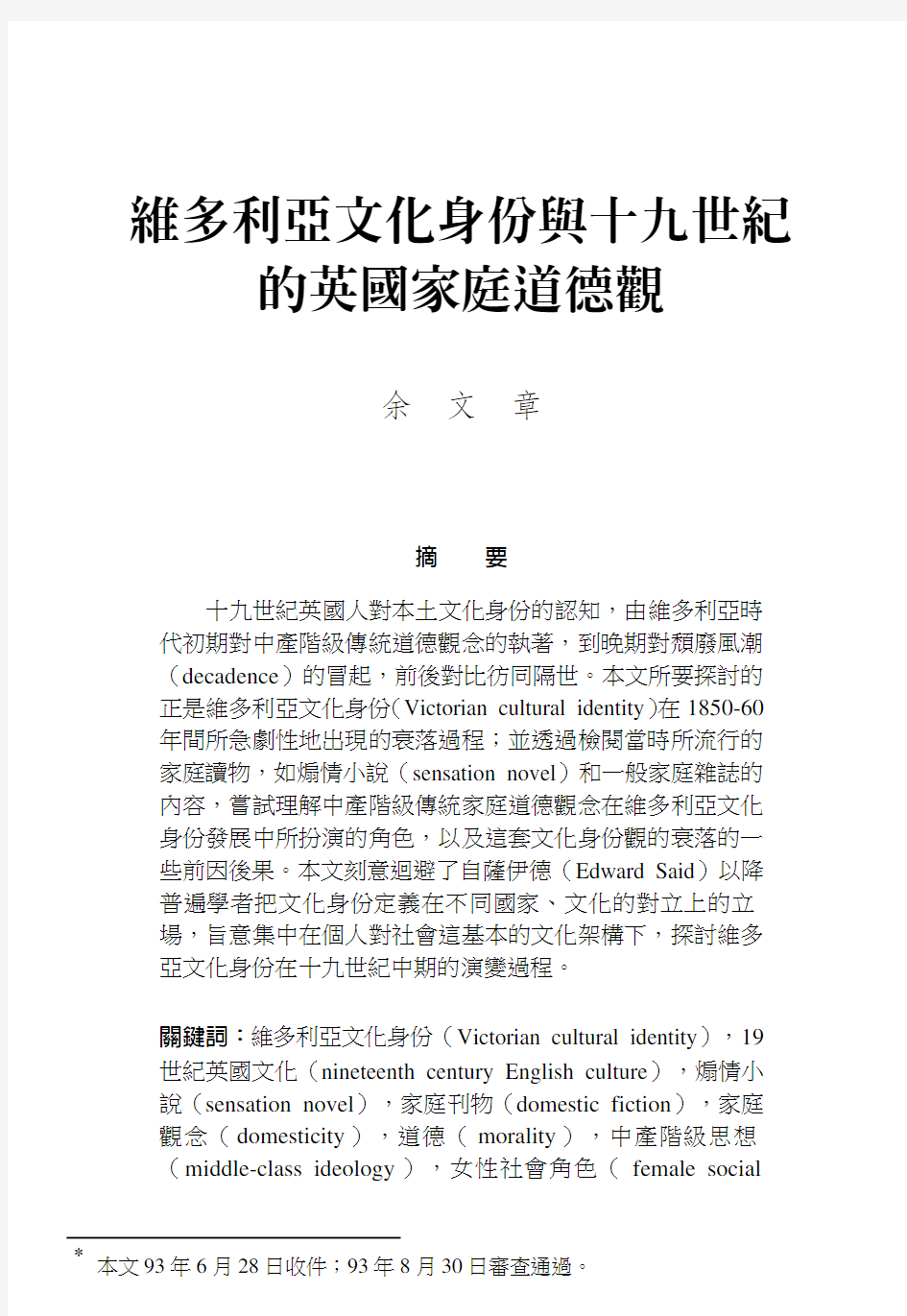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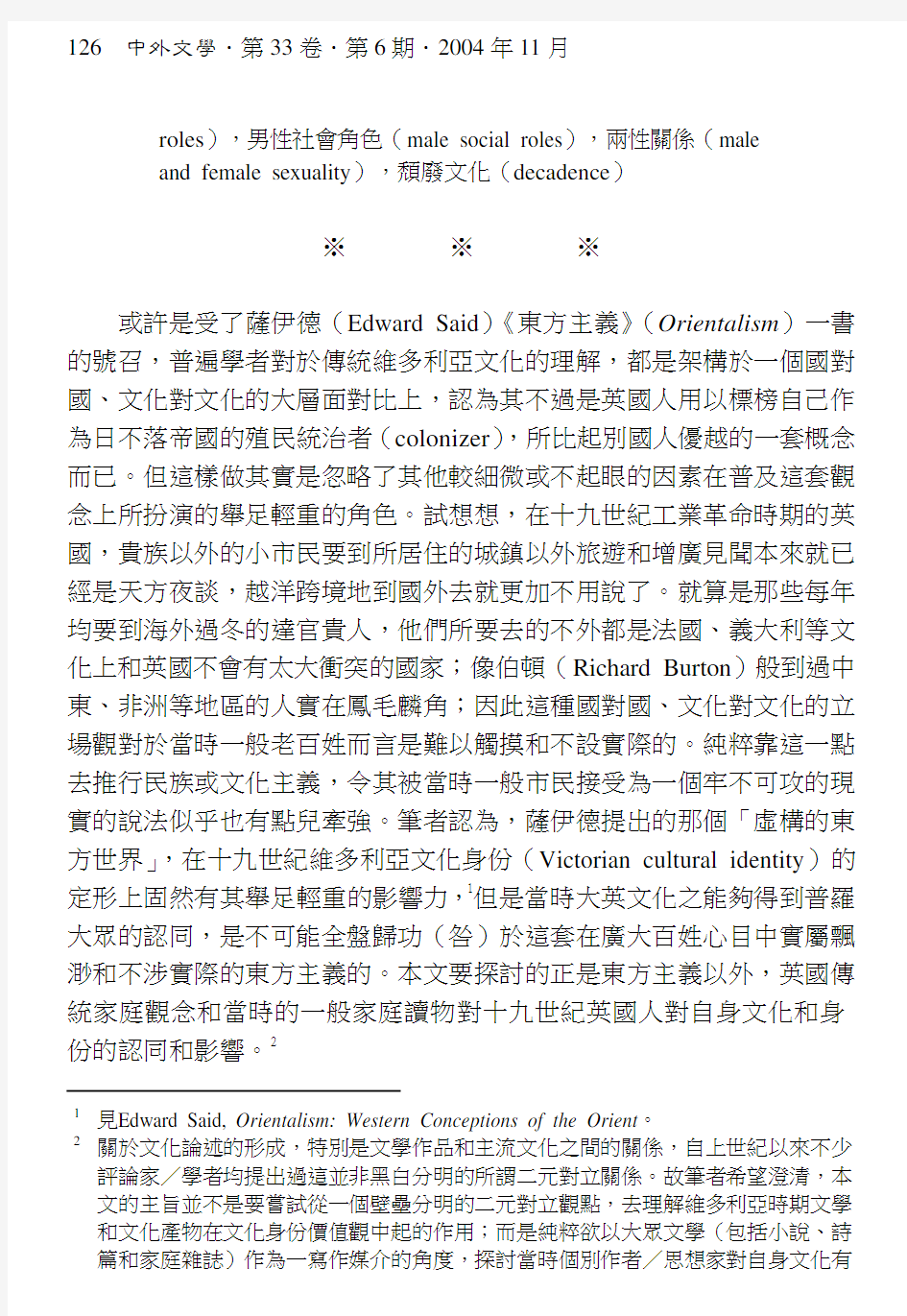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
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余 文 章
摘 要
十九世紀英國人對本土文化身份的認知,由維多利亞時代初期對中產階級傳統道德觀念的執著,到晚期對頹廢風潮
(decadence)的冒起,前後對比彷同隔世。本文所要探討的
正是維多利亞文化身份(Victorian cultural identity)在1850-60
年間所急劇性地出現的衰落過程;並透過檢閱當時所流行的
家庭讀物,如煽情小說(sensation novel)和一般家庭雜誌的
內容,嘗試理解中產階級傳統家庭道德觀念在維多利亞文化
身份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套文化身份觀的衰落的一
些前因後果。本文刻意迴避了自薩伊德(Edward Said)以降
普遍學者把文化身份定義在不同國家、文化的對立上的立
場,旨意集中在個人對社會這基本的文化架構下,探討維多
亞文化身份在十九世紀中期的演變過程。
關鍵詞:維多利亞文化身份(Victorian cultural identity),19
世紀英國文化(nineteenth century English culture),煽情小
說(sensation novel),家庭刊物(domestic fiction),家庭
觀念(domesticity),道德(morality),中產階級思想
(middle-class ideology),女性社會角色(female social
?
本文93年6月28日收件;93年8月30日審查通過。
126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roles),男性社會角色(male social roles),兩性關係(male
and female sexuality),頹廢文化(decadence)
※※※
或許是受了薩伊德(Edward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的號召,普遍學者對於傳統維多利亞文化的理解,都是架構於一個國對國、文化對文化的大層面對比上,認為其不過是英國人用以標榜自己作為日不落帝國的殖民統治者(colonizer),所比起別國人優越的一套概念而已。但這樣做其實是忽略了其他較細微或不起眼的因素在普及這套觀念上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試想想,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貴族以外的小市民要到所居住的城鎮以外旅遊和增廣見聞本來就已經是天方夜談,越洋跨境地到國外去就更加不用說了。就算是那些每年均要到海外過冬的達官貴人,他們所要去的不外都是法國、義大利等文化上和英國不會有太大衝突的國家;像伯頓(Richard Burton)般到過中東、非洲等地區的人實在鳳毛麟角;因此這種國對國、文化對文化的立場觀對於當時一般老百姓而言是難以觸摸和不設實際的。純粹靠這一點去推行民族或文化主義,令其被當時一般市民接受為一個牢不可攻的現實的說法似乎也有點兒牽強。筆者認為,薩伊德提出的那個「虛構的東方世界」,在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文化身份(Victorian cultural identity)的定形上固然有其舉足輕重的影響力,1但是當時大英文化之能夠得到普羅大眾的認同,是不可能全盤歸功(咎)於這套在廣大百姓心目中實屬飄渺和不涉實際的東方主義的。本文要探討的正是東方主義以外,英國傳統家庭觀念和當時的一般家庭讀物對十九世紀英國人對自身文化和身份的認同和影響。2
1見Edward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2關於文化論述的形成,特別是文學作品和主流文化之間的關係,自上世紀以來不少評論家/學者均提出過這並非黑白分明的所謂二元對立關係。故筆者希望澄清,本文的主旨並不是要嘗試從一個壁壘分明的二元對立觀點,去理解維多利亞時期文學和文化產物在文化身份價值觀中起的作用;而是純粹欲以大眾文學(包括小說、詩篇和家庭雜誌)作為一寫作媒介的角度,探討當時個別作者/思想家對自身文化有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127
論及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學和文化風氣,一般人自然會聯想到一系列對傳統道德的崇拜和保守的民風;而事實上直至十九世期中期為止,英國人民對於湯馬士?艾諾(Thomas Arnold)在世紀初期所提倡的那套中產階級道德思想觀,無疑是有著一份不容否定的濃厚依附感。艾諾自從於1828年被委任為拉格比公學(Rugby School)的校長後,對英國的公學制度旋即展開了一連串以中產階級道德思想為本的改革,導致這套保守的道德觀在維多利亞女皇執政始就已經根深蒂固地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人民腦海裡;所謂的「維多利亞文化」的定形無疑也自始而生。3米勒(J. S. Mill)曾經於1859出版的《自由論》(On Liberty)一書中提出:「在這個年代,從社會的貴族階級乃至於貧民階級,沒有一個人逃得出被審定(censorship)的命運」。這套控制人民思想的社會審定制度(social censorship),所指的就是由艾諾所提倡主宰著早期維多利亞社會文化風氣的中產階級道德觀;然而這套道德觀在成功地團結當時社會,為工業革命提供了一可以穩步發展的堅固基礎的同時,所帶來負面的影響便是對個人自由的無形壓抑。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小說《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裡道森(Dodson)一家人把個人身份定義於「忠於一切的傳統和可敬(respectable)的待人處世之道」的想法,其實就是艾略特對當時社會審定存在的一番直接反思;指出了這套道德觀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導致自我思想和自由主義流失的不可接受。事實上,自1850年起便續漸有越來越多的思想家對這種中產階級的道德思想審查感到不安,例如霍都(J. A. Froude)、克魯夫(Arthur Hugh Clough)和郭思(Edmund Gosse)等人,就曾經為掙扎於社會對他們的期望及他們內心對表現自我的渴望而感到痛苦不堪。
在世紀末期頹廢風潮(decadence)的影響力下刻意標榜鼓吹「離經
感而發的一些價值觀;從而藉著同類題材的文體的多寡,以及他們的普及程度,探索當中可能反映出來的當時社會對本身文化身份和立場的一些疑惑和迷茫。有關文化身份和文學之間的進一步分析和探討,請讀者參閱以下的相關著作: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 ociety, 1780-1950;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以及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3關於艾諾和英國公學制度的改革,請參見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128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叛道」的文學作品,便是當時文人對這份社會道德壓抑所作出的一種反叛。本文要探討的主要是維多利亞文學在初期受到中產階級道德主義支配下所產生的正義和純潔典範,到末期頹廢風潮的大肆流行,當中所經過對中產階級道德觀念的反思、幻滅(disillusionment)和離棄的發展過程。由於維多利亞文化身份所牽涉到的因素層面廣闊,內容博大精深,絕非一篇文章寥寥數萬字的篇幅所處理得來,因此本研究的重點將會放在1850-60年間所出現的家庭讀物,當中對傳統中產階級家庭道德觀念的定義與質疑,以及小說和雜誌等文化產物(cultural property)與當時實際文化環境(cultural atmosphere)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辯證(dialectic)關係。以傳統中產階級道德觀念為本的維多利亞文化,向來是重視「家」這個觀念,以及其所象徵的道德和人性中的善。這一點,只要看一些向來受中產階級重視的文學作品,如由莎士比亞的劇作或十九世紀初期珍?奧斯汀(Jane Austen)和司考特(Walter Scott)的小說,當中對家的正面描寫及其「安樂窩」(safe heaven)的形象,便可得知一二。在文化層面上,家庭在這套中產階級傳統當中所代表的凜然不可侵犯的聖潔形象,所反映的便是當時英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觀所抱有的認同。這點和東方主義中用以凸顯西方純潔和正義的那個充滿淫邪奸穢之氣的東方,是同出一轍的,因為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民的心目中,大英民族和文化的本身涵義就是正義和聖潔的。湯馬士?艾諾就曾言:「家者,家庭觀念之孕育地也」(Stanley 129)。艾諾所謂的家庭觀念,在當時就是指這份崇高的理念,也就是每個英國人在家庭教育中所不能缺少的東西。藝術評論家魯斯金(John Ruskin)亦曾指出:
〔家,就是〕一處和平之地,以及抗拒一切傷害、恐懼、迷惑和
分化的安全點。以上的因素缺一都不可。丈夫和妻子的責任,
就是確保外間的一切,如憎、隱、恨、惡等事物,不得進入家
門半步;對這些一旦失守則家不成家,剩下的就只有一個和外
邊世界沒有兩樣,不過是爐灶上蓋兩片瓦片而已。
(1902: 21-22)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129
魯斯金所言的「家」的概念,是十九世紀英國人普遍所認同的;而當中純潔正義的意象更代表了當時英國人對自己文化身份的最基本理解。這一點,現代評論家荻德拉?大衛(Deirdre David)就指出,只要看維多利亞女皇利用不同的宣傳手法,在人民心目中所刻意豎立起的「國母」形象,便可得知一二(6)。當時的英國社會架構,其實就形同一個以女皇為一家之首的「大家庭」,所要維繫的正是「家」這個觀念傳統以來在英國人心目中所象徵的至高無上的道德。這一點亦足以反映「家」在當時英國足以支持整個社會架構和文化觀念的重要地位。維多利亞時期對這一份視「家」為「道德」的觀念的宣傳活動,雖然歷史悠久,然而在1850年前後卻忽然地變得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活躍。這時候許多以家庭為主要銷售對象的雜誌和刊物,包括《倫敦日誌》(London Journal)、《庫克夫人日誌》(Eliza Cook’s Journal)、《家庭格言》(Household Words)和《家庭經濟雜誌》(Family Economist)等,4均不約而同地在數年之內先後崛起,而且都刻意標榜著「傳統家庭之重要性與道德觀念」這個宗旨(“Our First Words to Mothers” 2)。從單一方面看來,這無疑是當時英人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重視的力證;然而在另一層面上,這卻又隱含了一個相反的事實,那就是家庭道德觀念在十九世紀中期社會的日漸式微,以使這類刋物在這段時期能夠容易地吸引衛道之士的鼎力支持,冒起如雨後春筍。至於它們的銷量,從其平均只有十年左右的壽命看來,應該不會是太好的。這也證明了它們在這期間的迅速發展,背後如果沒有一個特定和明確的動機,是很難如實際情況般吸引到這麼龐大的投資。而它們的曇花一現亦說明了一則事實,那就是1860以後它們逐漸失去了讀者和財主的支持,這亦意味著中產階級傳統家庭道德觀的沒落的開端。
傳統道德觀念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沒落固然是不爭的事實,但在此之前這類家庭讀物在利用家庭觀念去宣揚中產階級主義思想,以及兩種
4按Catherine Waters對Waterloo Directory of Victorian Periodicals的研究,在這段時期出現的雜誌中,直接牽涉到「家庭」(family)的便有超過40種。詳見Catherine Waters, Dicken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Family, 16-17。
130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概念中間所不約而同地出現的共通點,對研究十九世紀英國文化觀念的轉變都是不容忽視的。首先,由1850到60年期間,這類讀物的主要銷售對象雖然是一些中、上階級家庭的婦人,5然而它們的影響力不僅不為此所限,反而因而得以擴散。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閱讀乃是十九世紀的主要消閒娛樂,婦人在購買刋物後通常都會在茶餘飯後拿出來和家人一起閱讀裡面的文章;而當中一些道德觀念較重的章節,甚至可以用來對僕人訓話之用。這些刋物的內容也因為這樣而得以向社會各階層傳播開去,其影響力基本上是不為銷量所限的。
至於文章當中的內容,涉及柴米油鹽醬醋茶等日常家庭瑣事的固然佔大部份;但是一些宗旨明顯是要宣揚家庭道德,甚至把傳統家庭觀念和帝國主義扯上關係的,為數亦不少。例如一本刋於1849年的雜誌,就詞正聲嚴地指出「家才是真正能夠主宰世界的地方,因為在那裡,大丈夫所學到的足以讓他們在社會上有一番作為」(“Home Power”129)。話雖短,但是十九世紀家庭觀念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卻是一針見血地道出來了。因為所謂「社會上有一番作為」,指的無非是傳統英國男性,也就是紳士(gentleman)在一般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而這個形象來自「家」的說法則指名道姓地道出了家庭和紳士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紳士的高尚和受人敬仰,乃是一脈相承自家的純潔無垢形象的。至於家之能夠「管轄」世界,原文所用的並非「統領」(rule)、「運營」(run)等比較常用的字眼,而是用了「管轄」(govern)這個帶有強烈殖民主義,令人容易聯想到殖民統治這一意象的詞;其對帝國主義的認同當時的讀者大概不會聯想不到。
十九世紀既為大英殖民主義的全盛時期,社會和經濟的穩定,跟殖民主義的發展都有莫大的關係。因此對一般讀者而言,任何有關殖民主義的言論,都很容易被理解成為對當時社會文化狀況的直接評論。這類刊物對殖民主義的宣揚,無形中也就是說男子漢大丈夫之能夠在因殖民主義而欣欣向榮的社會上有一番作為,全賴傳統中產階級家庭道德觀念
5見Margaret Beetham, A Magazine of Her Own?: Domesticity and Desire in the Woman's Magazine, 1800-1914。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131
教育的「正確」思想和理念。這點和前文所說有關這類讀物在十九世紀中期的迅速冒起,主要是針對當時社會地位正逐漸倒退的中產階級家庭道德觀念的說法,是一脈相承的。為了更深入地了解由1800至1900年維多利亞文化的成熟到衰落,對這時期的質疑中產階級傳統家庭道德觀念的看法,作進一步探討是有必要的。其實社會對這套沿自艾諾的中產階級觀念的懷疑,早在1840年左右的一些讀物中便可以看出當時人對這項「定論」或多或少的不認同。以40年代大行其道以孤兒為主題的小說(orphan novel)為例,如狄更斯的《孤雛淚》(Oliver Twist)、《老古董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勃朗特的《簡愛》(Jane Eyre)等,當中大都帶有很強烈而與傳統家庭觀念背道而馳的訊息。其中《老古董店》中小妮爾(Little Nell)的被迫四處流浪到最後客死異鄉、《簡愛》中女主人翁小時候在家中所受的苦、及其愛人的家園最終被大火毁於一旦等,更是充分地展現出這些作家對傳統完美家庭思想的一些不認同。現代學者彼得絲(Laura Peters)亦指出,孤兒小說的成功本身其實就是對傳統家庭觀念的一個挑戰,因為它們所象徵和意味的,乃是「家庭的各項傳統定義,包括正統性、民族性和國家性,正面臨崩塌」(1)。
1850年以後,隨著時代步伐加快,對「家」這個傳統完美觀念的質疑也相對提升了。一方面,家庭刋物在這期間的快速出現,在對抗這種反思想的同時無疑亦敗露了主流思想正在改變的這個不爭的社會現象;另外,在同期的小說作品中,亦可看得到一些大膽地偏離(甚至質疑)有關家的傳統完美思想的情節。就以狄更斯為例,雖然在當時讀者眼中,他的形象是較保守和能夠貫徹「家」的傳統中產階級形象的(一名十九世紀的學者就曾經毫不猶豫地形容狄更斯「擁有對家的一顆無窮無盡、慈悲溫暖的心」〔Ward 539〕),然而細讀狄氏的作品,不難發現這項說法的疑點其實是頗多的。不錯,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涉及家或家庭的情節十分之多,然而題材上與家有關並不就代表他是這個傳統的支持者,相反地,除了前述的《孤雛淚》可能跟他當時的家庭親善形象不大吻合外,其它作品很多對家的描寫也不完全是正面的。例如在《大期待》(Great Expectation)裡,雖然韋彌克(Wemmick)曾將家比喻為他夢寐以求的「城堡」,但實際上就如同評論家高韓(Monica F. Cohen)所言,
132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韋彌克經常掛在口邊的城堡歸根究底不過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幻空間,而這個空間更是男主角畢比(Pip)命中的一根刺,因為理想的家是他由始至終都無法獲得的(79)。再者,狄更斯在後期的小說中還往往大花筆墨地描述人們對傳統觀念的「家」之疏離。例如1853年的《荒涼之家》(Bleak House),小說的名字不僅己暴露了作者對家在中產階級傳統上扮演的道德角色提出質疑;情節上,小說中的喬(Jo)不但無法將「幸福」與「家」畫上等號,更可悲的是他對家之概念,不再是好壞之分,而是根本連聯想一下的空間也沒有;對他每天在城鎮中的流離、無家可歸的經歷,作者就有過以下的描寫:
他繼續地走,漫無目的地朝布萊克福利亞斯橋(Blackfriars
Bridge)走去。他在橋上的一角席地而坐,邊吃邊望著聖保羅
教堂上的十字架。十字架在層層微微泛紫的紅煙中閃閃發光。
男孩的神情彷彿訴說著,對他而言神聖的十字架象徵著城市的
謎題。城市美好的一面,猶如燦爛的十字架,高高在上,遙不
可及。他停留在橋上,望著日落、橋下急促的流水、身邊往往
返返的路人,一切的脈動都似乎正有目的地朝著同一個結果行
進著。他望著望著,直至有人搖了搖他,呼喚他離開。
(1951: 270-71)
由此可見,狄更斯在十九世紀讀者心目中捍衛「家」的傳統觀念的形象,不過是某些讀者一廂情願加諸其身上的而已。原因大概是欲借助狄氏的名氣來扭轉日趨微弱的家和中產階級道德觀念的聯繫。然而狄更斯筆下那冒著「層層微微泛紫的紅煙」的城市(暗示工業時代的降臨),卻無庸置疑地透露了他對「家」的理想的幻滅。喬徘徊在「偉大而混亂城市」中,孤身隻影,所缺乏的正是一個傳統且理所當然的家。這亦意味傳統思想中家溫暖及單純的形象已成為一個伊甸園般無法挽回的理想國,取而代之的乃是工業社會帶來的冷漠與孤寂。再比較一下1850年前後狄更斯對孤兒的描寫的改變,從1837年的《孤雛淚》中奧利華(Oliver Twist)雖然淪落為小偷,但仍能對家充滿憧憬,到1859年喬的絕望和悲慘結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133
局,所反映的正是當時社會逐漸對傳統的「家」失去信心的事實。
除了狄更斯的作品以外,在1850年以後的其他作家的小說中,對家的描寫往往也會透露出或多或少的疏離感。例如在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的《維萊特》(Villette)裡面,女主人翁露絲便由始到終都無法得到她想要擁有的家,最後只得低頭接受缺乏家庭溫暖的孤單人生。這點和《南與北》(North and South)中瑪格麗特(Margaret Hale)所無法確切地形容出心中理想的家的無奈,只能對人表示:「我無法形容我的家,家就是家」(Gaskell 14)是殊途同歸的,因為彼此都恰當地反映了當時某些人心目中理想的家的無法實現和不切實際。類似的例子還多不勝數。除了狄更斯、勃朗特和格斯歌夫人(Mrs. Gaskell)外,在特洛普(Anthony Trollope)、喬治?艾略特和瑪格麗特?歐麗梵(Margaret Oliphant)等人的同期作品中都不難找到這方面的佐證。這些作品的共通點是反映出了十九世紀中期英國人開始不再寄託一生的幸福於追逐一個理想的家的現象。然而有正便必有反,當時社會對傳統家庭道德觀念的日趨悲觀,除了引發先前提及到的那股家庭雜誌創辦潮外,有些小說家則採取了「以毒攻毒」的辦法,欲以自己的小說來積極地為理想的家作辯護,而且都語重心長地反反覆覆向讀者宣示傳統的家對英國社會和人民道德的重要。這方面的代表作,除了較為人熟識的楊葛(Charlotte Yonge)的《瑞里夫的繼承人》(The Heir of Redclyffe)外,還有凱利(H.
F. Chorley)的《洛加貝勒》(Roccabella)和克雷(Dinah Mulock Craik)的《高潔人生》(A Noble Life)。他們的共通點是以極其渲染的筆觸,去一面倒地宣揚家庭傳統道德的高尚。評論家史託洛(June Sturrock)對楊葛在這方面的評價,其實對這些同類型小說是一概通用的。她認為楊氏的作品,出發點都是從一而終地要讓讀者從小說中學習待人處事之道,並向他們灌輸家乃是道德行為的守護所的這個概念(98)。不過,這些嚴守著中產階級傳統家庭觀念的作者,是否真的能如其所願地傳達了她們的觀點給讀者,倒是令人質疑。例如,在當時以家庭為主題的雜誌《家庭格言》裡,就曾經出現過以下一段語帶嘲諷的文章,描寫著一位僅閱讀這類小說的少女:
134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有一位妙齡少女,以往經常光臨私人圖書館,可惜的是,幾年
前她不幸讀了一本以道德教訓為主題的小說。從此她只是反覆
地閱讀此書,不再閱讀其他刊物。(Stone 622)
跟據史頓(Harry Stone)的考證,這篇文章乃是出自韋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的手筆,經狄更斯批改後再行刋出的。此少女的事蹟是真是假,現已無從考究;但是它的重點並非這名少女是否真有其人,而是筆者諷刺和不屑的語氣(關於狄氏對50年代家庭道德觀念的看法,前文已有提及;至於柯林斯對中產階級文化思想的批判,則請參閱後文),因為這足以反映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普及文化中所出現對傳統中產階級家庭道德觀念的不認同。
如前所述,中產階級所信奉的傳統道德理念,自艾諾以來便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文化的基礎;因此它的不再受到尊重,無疑是亮起了這套文化傳統的紅燈。這種現象也可以從另一類大眾文學的興起看出端倪。煽情小說(sensation novels)興起於1850年代,大多以連載方式登刊於家庭性雜誌,並於短短的10年內成為廣受歡迎的文體。6煽情小說的目的與道德性家庭小說背道而馳,時時刻刻找機會對傳統家庭作出負面的描寫。在這類的小說裡,家庭不再象徵溫暖與安全,而是常與各式各樣的不道德扯上直接關係。談到煽情文學,已退休的英國文學教授艾廸克(Richard D. Altick)就認為:
煽情小說給1860年代的英國讀者帶來和鬼魅小說(Gothic
novel)相對的刺激和恐懼,題材不外乎是貝格芙廣場(Belgrave
Square)隱藏的駭人秘密或郊區別墅(country house)裡發生的
殺人事件。(77)
6關於煽情小說和當時家庭刋物之間的關係,可參閱Deborah Wynne, The Sensation Novel and the Victorian Family Magazine。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135
煽情小說如此大膽露骨地將貝格芙廣場7及郊區別墅做為故事的場景,把這些容易令對英國地理有所認識的讀者聯想到「家」的週遭描述為不道德事件發生的地方,其用心是十分明顯。在這種文體興起前,作家對於「家」的描述一般都是正面地代表著快樂的園地或是道德守護所。雖然在19世紀前期的《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或一些鬼魅小說中,基於劇情需要,恐怖的事情還是無可避免地在家庭的週遭發生了;但是有異於後期的煽情小說,這些早期的「家」都是千遍一律地位於遙遠的地方,例如蘇格蘭或義大利(雖然作者都是英國人);對於讀者而言這就不會像貝格芙廣場來的熟悉,讀者也較不會將這些地方與家聯想在一起。相較之下,煽情小說不僅抨擊理想的家的存在,甚至於質疑這個家在傳統中所象徵的道德,從而直接地由對家的抨擊否定了中產階級價值觀在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認同上所扮演的地位。舉例來說,在《歐德莉夫人的秘密》(Lady Audley’s Secret)中,作者布萊登(M. E. Braddon)便借題發揮地表示:
我們常聽說郊區某處發生了謀殺案——殘暴、背叛性的謀殺
案;殺手使親人慢慢死於劇毒,生不如死;以橡樹樹枝為凶器,
殘忍地突擊被害者(諷刺的是,橡樹的樹枝圍成的樹蔭象徵和
平)。曾經有人帶我到一片草原,這片看似寧靜的草原是一樁兇
案曾經發生的地方:在某個夏天的週日,一個農夫殺死了愛他、
信任他的姑娘。即使如此,至今這片草原仍保有安寧的面貌。
在這種甜美、鄉村、寧靜的地方,曾發生過像七面鐘地區(Seven
Dials)的殘酷命案,但是我們仍以悠悠的目光凝視這片鄉村草
原,嚮往它象徵式的安寧。(54)
7艾廸克所引述貝格芙廣場和煽情小說之間的關係,靈感大概是來自1871年吉伯特(W.
S. Gilbert)在音樂劇《煽情小說》(A Sensation Novel)中以貝格芙廣場作背景來諷刺該文體千篇一律的劇情;至於今天的貝格芙廣場外國使館林立,容易讓人聯想到家庭觀念、帝國主義和維多利亞文化身份的進一步關係,筆者認為這純屬巧合,因為在十九世紀中期該處並不存在任何外國使館。
136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從這段文章,不難看出作者刻意用諷刺的筆法批評當時的大眾,認為他們自欺欺人,不願面對邪惡存在的事實。這亦道出了當時一般英國人只願意承認事物(例如上述的草原)安寧的外表,刻意迴避其黑暗的一面(草原上發生過的謀殺案)的心態。白氏的小說到處充斥著這種對大眾自我蒙蔽心態的不滿。在《歐德莉夫人的秘密》的後段,她甚至拋棄了作者的身份,對這種行為作出直接指責:
邪惡可怕的事情往往會發生於最溫暖幸福的房子當中;不管景
致是多麼迷人,罪惡也可以隨時發生;而事後更不會留下任何
痕跡。我不相信什麼天網恢恢,漏而不漏之類的說法,我只相
信我們隨時隨地都可能身處罪案現場但仍懵然不知。甚至跟兇
徒面對面時,我們仍只懂麻木地欣賞該地方寧靜怡人的一面。
(140-41)
這般文字,對當時的讀者來說彷彿已經不再是小說裡的情節,而是直接的一番告誡。布萊登想說的,簡單而言就是要指出家庭的表面安寧並不代表殘暴的凶案就不能發生。這點和人性以及文化身份一樣,完美的外表(身份)極其量不過是一個虛殼,內在和真實的身份往往是不受外表所牽連的。更重要的是,因為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人的心目中,「家庭」與他們的社會文化身份密不可分,故白氏在質疑傳統家庭價值時,亦可看出她對當時大眾告誡的苦心,要他們不要過分沉醉於這份虛偽中,自欺欺人。
猶如布萊登的作品,煽情小說的一大特色就是將善惡視為一體,這點在當時可算是前無古人的。雖然狄更斯、格斯歌夫人及勃朗特等人均曾在煽情小說興起前在小說中探討善惡關係的問題,並大肆地將當代社會描寫為一個道德式微的地方;然而煽情小說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暗示邪惡來自每個人的內在,而非源自於人們的週遭環境,這點跟狄氏等人的作品是大為不同的。以當時大受歡迎的《白衣女子》(The Woman in White)、《東大宅》(East Lynne)、《弗洛伊小姐》(Aurora Floyd)、《艾瑪戴爾》(Armadale)及《月光寶玉》(The Moonstone)為例,它們的共通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137
點是故事主軸都圍繞著看似清廉的英國人其身份背後所掩飾的邪惡。評論家高邁夏(U. C. Knoepflmacher)也認為,煽情小說一般都含括「兩種背道而馳的社會秩序,前者是英國人傳統文化所認同的有秩序的社會,後者則是可以消除或破壞這套觀念的混亂社會」(362)。而這種現象所反映的無庸置疑就是當時小說家對人民固守刻板的維多利亞文化身份的不滿,再三要提醒著讀者英國人跟其他人一樣,都是可能擁有邪惡的一面的。
煽情小說的興起,引起了像魯斯金等保守人士的不滿。這些傳統道德的捍衛者極力反對煽情小說中以家庭環境作為兇案發生的地點,並針對小說散播的猥褻與不道德作出猛烈抨擊。例如凱利就曾經於1866年稱呼煽情小說為「病態的發明」(147)。而早在三年前亦有評論者攻擊這種文體,認為煽情小說中「既不完善又混亂的道德觀」容易使讀者不安,以至於:
是非黑白顛倒,對錯不分;彷彿一個人只要既奸狡又冷靜,便
能在作惡多端後逃之夭夭,不受任何身、心的制裁。(“Novels”
44)
在此有必要重申,諸如此類保守派的批評,一方面是說明了部分人對傳統道德的重視,不遺餘力地要打擊任何有損這種道德的文章或言論;然而另一方面,他們那近乎誇張的反應,卻同時亦透露了他們內心深處的某股不安,以及對於是否能守護這個傳統「身份」所感到的質疑。這些保守人士很難接受自己所屬的大英文化身份可能涵括謀殺、通姦及竊盜等等不道德的行為,因而極力地要捍衛它在世紀初期所代表的純樸和正義。雷伊(W. Fraser Rae)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他曾經攻擊布萊登的小說,嘲諷其目的在於:「說服大眾每個看似善良的鄰居都在自家的櫃子裡藏了骸骨;這些鄰居內心都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203)。另外,於一篇標題為〈小說:煽情派〉的文章中,不署姓名的作者亦抱怨道:
138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煽情小說〕教導讀者我們在自家中尋找不尋常的事件:我們的
搖籃裡隱藏個呼之欲出的秘密;我們的婚姻建立在駭人的騙局
上;不肖者與我們共桌;我們看似寧靜的花園裡曾經發生殘虐
殺人事件;我們的傭人接受年薪20英磅的酬勞,並對我們心懷
不軌。(“Our Novels” 422)
諸如此類的評論透露了當代保守人士對煽情小說的批評,因為煽情小說侮辱了他們堅守「家庭」所代表的道德理念,進而動搖了他們對自己文化身份的認知。然而值得探討的是,煽情小說是否真的為破壞傳統「道德家庭」的罪魁禍首?煽情小說家又是否為了嘩眾取寵而刻意將和平的「家庭」描述成混亂根源?不少近代煽情文學批評家已提出,許多1860及1870年代的煽情小說均是改編自當時報章曾報導過的凶殺案。其中沙澤蘭(John Sutherland)和甘珮(Sandra Kemp)就曾經為煽情小說的鼻祖韋基.柯林斯以當時凶案為靈感一說,分別提出過有效的力證;8而這些近乎怪誕的案件在當時可謂街知巷聞,不論是煽情小說的支持者或反對者,都是沒可能不知道的。而且這種取材於現實的手法在當時更可謂普遍非常。例如1861年轟動一時的耶菲頓案(Yelverton Case),短短一年間就被至少六位不同的作者先後改編為煽情小說。當時的保守人士為了堅持他們的社會是一個既道德又高尚的社會,在指責煽情小說的時候,對小說的靈感往往隻字不提;但這樣做卻無疑是忽視了現實社會與小說情結的關連。這些保守批評家自我蒙蔽的態度亦可由通姦及重婚這兩個社會議題看出端倪。在1860年代,通姦及重婚可謂相當普遍,以至於在短短的1860至1864間就有三本刊物呼籲民眾重視婚姻並要求法律條文多發揮束縛婚約的功能。9一位重視該問題的人士就曾經感慨地
8見John Sutherland為Armadale撰的註腳(696, 698),以及Sandra Kemp於The Moonstone 的前言。
9見John Fraser Macqueen,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Law of Marriage, Divorce, and Legitimacy, as Administered in the Divorce Court and the House of Lords;James Muirhead, Notes on the Marriage Law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with Suggestions for their Amendment and Assimilatio;以及Alfred Waddilove, The Laws of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139
表示:「確切束縛男女關係的條規近期可能不會出現,但總有一天我們必須慎重的探討這個議題」(“The Laws” 469)。然而抨擊煽情小說的保守人士並未注意到關於婚姻的社會問題,他們僅於煽情小說興起後在小說中察覺到這方面不妥當的行為,並將真實社會上的婚姻問題歸罪於這群小說家。難怪當小說家瑞德(Charles Reade)被保守人士指責,說他的小說題材既下流又沒品味時,瑞德在回覆《時代雜誌》主編的信中就無辜地表示自己所做的,不過取用了一些該雜誌曾經報導的新聞並將之戲劇化而已。如此又何罪之有呢?(qtd. in Brantlinger 10)。
小說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是少數能夠獨具慧眼地指出煽情小說中的「惡」是源自真實社會而非憑空想像的評論家。他相信煽情小說家「對日漸倍受關注、社會黑暗恐怖的一面有著深入的認識和見解」(745),煽情小說只不過是提醒社會「善良」與「邪惡」其實是共存的。對於詹姆士而言,閱讀煽情小說就猶如閱讀「當時的報紙所刊載的英國」(744)。只是保守人士卻無法效法詹姆士以同樣客觀的角度去分析煽情小說,唯懂得不斷抨擊這類小說如何蠶食他們所希望維護的傳統道德觀,而忽略了當時社會的一些實際情況。
煽情小說興起的時刻,剛好正是亨利?梅修(Henry Mayhew)撰文披露當時英國社會黑暗一面的高峰期,也是達爾文思想令人民開始對宗教產生質疑的年代。正因為社會的道德和守護信徒的宗教是當時英國中產階級文化認知的兩大支柱(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中也提出相同的論點),當時煽情小說對傳統大英文化身份觀所帶來的衝擊,亦因為時局的不安而變得更為實在;所涉及到的民族主義的爭議,步入1860年亦變得更為激烈。例如在1863年雜誌《讀者》(Reader)所刋登的一篇匿名文章,作者就深信煽情小說是「來自法國,而在流傳越洋的過程中遭惡性變化」(Reader 14-15)。而在1861年亦曾有投稿者認為煽情小說是由「直言無諱或不顧後果的粗俗美國人」(“Sensation Literature” 15)所發明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英國人往往將外來文學(特別是法國文
Marriage, and the Laws of Divorce, of England, as Established by Statute and Common Law, Arranged in the Form of a Code for Popular Use。
140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學)視為不道德且不適合英國高尚品味的文學。因此,當評論家將煽情文學視為外來文體,他們所傳達的訊息是:第一,當時的衛道之士既然無法接受自身文化不道德的一面,自然不願意讓煽情小說和自身文化扯上任何關係,把之往外推自然就順理成章;第二,當時英國社會直覺地將一切與不道德有關聯的事物歸罪於其他國家,從而凸顯自身文化的高尚和完美(見《東方主義》)。煽情小說既被視為不道德之物,把之歸咎於外來文化,一方面合乎維多利亞文化高高在上、一塵不染的觀念,其次亦可能貶低外國文化的地位,從而去凸顯出自己的清高,可謂一舉兩得。只是這樣做無疑是表示出了衛道之士對文化身份問題以偏蓋全的態度,以及社會主流思想的改變:個別衛道人士深感狂瀾之不可擋,唯有轉移民眾目標。
在歷史上,由於中產階級思想在世紀初期對教育制度的影響,較之其他時期,19世紀的英國人的確更為重視「家庭」,並往往將人性中的善及道德與之聯想在一起。已故英國文學評論家何頓(Walter E. Houghton)就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是以家庭為中心的」(341)。「家庭」這個觀念,不僅影響當時人民對事物的反應及展現的品味,更代表了道德觀和原則,並為之提供了直接的英國文化身份認知的基礎。
在此前提下,值得探討的一個議題便是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期許,以及社會希望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和文化身份的關係。女性主義學家維絲娜(Martha Vicinus)曾表示:
「家庭」是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社會的基石,而最完美的女性的任
務不外乎結婚和生子。社會對她的教育亦在於引出她天生「服
從」的性格和母愛。少女必須學會沒有己見才不會影響她在「婚
姻市場」的價值,因為男人不喜歡思想太獨立的女性。(10)
如同維氏所說,女性一生的任務就是管理家庭一切事務,包括養育子女及為家居營造溫暖和舒適的氣氛。這個「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充分地反映了當時人對女性活動範圍的限制。而正因為維多利亞時期的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141
女性與「家庭」的關係密不可分,當時的英國人在道德層面上對「家」的期許也延伸到對女性的期許。這種極度重視女性貞潔的態度使「女性崇拜」(woman-worship)風氣在十九世紀中期達到高峰。而他們崇拜的不僅是女性外在的美麗,還包括她們所象徵的純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柏德莫(Coventry Patmore)在1854年發表的詩集「家的守護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當中有句云:
她有虔誠的氣質,
天使般的神情;
最善良的人所知善良的事
都寫在她那親切的臉龐
失去信仰的人從她的神情
可看見天堂和希望。
(“The Angel in the House”, Bk. I, Canto IV,Preludes I: The Rose
of the World, ln. 11-16)
要暸解十九世紀中期英國人的文化認知,就必須先體會女性崇拜在當時社會的特別意義。就如前文所討論的「道德」與「家庭」的關係,由於受了中產階級道德觀念的影響,當時普遍英國人對婦女的理解是與「家庭」分不開的,因此女性在文化層面上所扮演的角色,與「道德」也扯上了直接的關係,並常常被用以鞏固傳統道德家庭的觀念(因為女性代表了家庭)。而女性在文化認知的層面所扮演的角色還不僅如此;從英國人文化認知傳統看來,女性守護著家的表現在維多利亞時期社會上一直被視為一種美德。因此,十九世紀中期女性崇拜的潮流亦顯現了當代人試圖將當時的文化認知追溯到傳統的文化認知,並在「一切合乎傳統」的號召力下試圖於道德動盪的年代穩固傳統的道德觀。提及中產階級所崇尚的文學中具美德的女性角色。何頓曾言:
莎士比亞、司考特、但丁(Dante)及荷馬(Homer)筆下的女
人總是「可靠、聰明又善解人意的」;男人因為她們的美德而不
142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再懦弱。在男女各守本分的前提下,男人擁有了女主人為他建
立並維護的神聖道德的家。(350)
如此,因為這套中產階級的美學觀,傳統女性的美德在十九世紀中期成為了保守人士用來支持維多利亞文化身份的面向。1870年代魯斯金就利用這套方式來詮釋傳統文學,將莎士比亞、司考特及奧斯汀的作品跟中產階級思想支配下的維多利亞文化道德觀劃上了等號。魯氏在演講中表示:「莎士比亞對實際生活中女性應扮演的角色是如此定義的──女人可靠、聰明、善解人意、公正無私、純潔,即使無法救濟他人時也不會忘記為他們淨化罪過」(1902: 8)。很明顯,其目的是要將莎士比亞筆下理想女性角色與他心目中的中產階級家庭觀念連聯想在一起,繼而證明女主內這一個歷久不衰的事實。事實上,除了魯斯金之外,19世紀中期尚有許多作者鼓勵婦女以創造和諧的家庭為己任並以成為道德象徵的目標邁進,例如艾莉絲(Sara Ellis)主編的《英國婦女:職責、影響力及社會責任》(The Wives of England: Their Relative Duties, Domestic Influence, and Social Obligations)、蘇瑤(Alexis Soyer)的《當代家庭主婦或管家》(Modern Housewife or Ménagère)及比頓夫人(Mrs Beeton)的《家庭管理手則》(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都是當時教育女性如何持家,同時鼓勵她們如何在「家」這個前提下安分守己的暢銷書。雖然這些刋物的編者多為女性,當中更不乏經濟上有能力完全擺脫中產階級性別觀念上的束縛,不靠男性或家庭而去獨當一面的「才女」;然而從她們的文章或言行舉止看來,她們非但不曾發表過任何跟中產階級傳統理念背道而馳的言論,對自身私生活上的要求,也是言行一致地相當保守和嚴格的。就以當中最有名的比頓夫人為例,替她立傳的史斌(Nancy Spain)就指出,比頓夫人和她的丈夫「對真理和德行都抱有同樣審慎和一絲不苟的態度」(253),並嚴謹地堅守著中產階級對家庭所持有的觀念,那就是「可靠的家庭生活就是一切道德之根源」的宗旨(12)。由此可見,這類書籍對當時女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照中產階級道德指標來進行的。例如一篇曾刊於《家庭經濟雜誌》(Magazine of Domestic Economy)的文章就指出:
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家庭道德觀 143
女人的天職在於管理家庭,而不是在外間的戰場上拚鬥;她的
智慧不是用來發明或創造的,而是用來佈置地方、張羅家務及
打點家中一切〔……〕大英帝國是一個以家為首的國度。國人
對於保護「家」的溫暖是認真和全力以付的〔……〕因為家仍
是一切之源。沒有了家,大英帝國也不可能榮華。(“Woman in
Domestic Life” 66)
如此可見,女人與家庭以及家庭與國家的關係密不可分。在中產階級思想引領下,一個家的「道德」,首先得視乎其女主人而定;其次,這份「道德」才可被推擴至社會,從而建立當時英國人心目中合乎維多利亞文化身份的道德觀念。在當時的社會,女主人必須成為一家的「守護天使」,亦唯有這樣才能給男人提供一個鞏固的道德基礎去服務社會國家。因此,對於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文化身份的理解,女性、家和道德三者有著密切得幾乎不可分割的關係;因為當時英國人對自己國民身份最直截了當的見解,就是對傳統道德的堅持,認為英國文化之所以強於其他文化(尤其是英屬殖民地的土著),就是因為英國人擁有高尚的道德觀。這份對於道德的堅定和執著,仍是源自對「家」的傳統概念;而維繫著「家」和「道德」這兩個關係的主要因素,則是當時的家庭婦女。在這個三角關係當中,任何的一方面受到動搖,都有可能影響整個道德觀念的架構,導致對維多利亞文化身份認同的瓦解。因此在十九世紀中期當該套以中產階級道德思想為主的大英文化傳統受到來自各方面的衝擊,保守人士除了要鞏固家的形象外,同時亦為了宣傳當時的婦女形象而下過一番功夫。其中讚揚傳統女性溫柔和能夠秉承道德傳統的文學名篇,除了上述柏德莫的詩集外,同期出現的還有推崇女性美德的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公主〉(“The Princess”)、以突出正邪對立的兩名女主角來眨惡揚善的《名利場》(Vanity Fair)、對女主角謙遜而不失尊嚴的處事手法大表認同的《雪蘭》(Shirley)、以及強調女性內在美德能戰勝所有外在虛榮的《瑪麗?保頓》(Mary Barton)等等。
由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女性地位,是與家庭和道德的關係一脈相承的;因此在十九世紀中期傳統家庭和道德觀念倍受質疑之際,傳統婦
144中外文學.第33卷.第6期.2004年11月
女所扮演的「家的守護天使」的角色自然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改革人士的攻擊目標。例如科學家赫胥黎(T. H. Huxley)就曾經嚴厲地撰文批評這種由「眾多保守人士及哲學家所推廣的新一代女性崇拜」(68-69)。狄更斯亦於1865年的小說《相互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裡塑造了貝菈(Bella)一角,強調她欲成為「比家中的天使更有用」(564)的人的抱負。相較於1850年之前狄氏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形象(如《馬丁?朱維特》〔Martin Chuzzlewit〕中的露芙?賓治〔Ruth Pinch〕),貝菈的理想充分顯示了十九世紀中後期英國社會對女性的態度的改觀,亦意味了中產階級思想將不再主宰維多利亞文化身份的定義的命運。
既然維多利亞時期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對道德文化身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以推翻維多利亞文化身份的單方面正面和不合乎實際情況的形象為己任的煽情小說家,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攻擊對象。在當時流行的煽情小說中,作者們常常將一個家庭的女主人描寫成擾亂家庭溫暖的罪魁禍首;並將英國人對傳統女性氣質的定義由正面的更改成負面的,以延續他們對於家庭負面呈現的一貫作風。評論家芘琪(Lyn Pykett)就曾經指出,「在每一部煽情小說中〔……〕都一定有一個甚至多個女角色守著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17)。而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暗示的則是一般婦人和顏悅色的背後所隱藏不為人知的一面,其作用亦和前文所述對家庭一概念提出的質疑一樣,打擊著當時人對女性美德(女性崇拜的根源)的信任。由於煽情小說往往以憐憫的筆法去描寫墮落的女主角,批評者常用這一點抨擊煽情小說不道德的一面。曾經有一位當代評論家就寫道,煽情小說對墮落女性的描寫往往是「將罪行描寫成女主角贖罪的過程,或將懺悔的犯人美化」(“Sensation Novels” 567)。就這點而言,評論家史密治(Cannon Schmitt)就曾言:
雖然煽情小說廣受大眾歡迎,但它們的指責者就感到反感,批
評煽情小說家是在攻擊當時英國社會對男女社會地位及責任的
定義,並藉以攻擊英國文化的民族性。因為在民族性的前提下,
煽情小說家對英國人愛戴的民族相關概念(特別是英國女性及
家庭)作出攻擊,無形中就等同在攻擊英國人的這個身份。(115)
Victorian fashion comprises the various fashions and trends in British culture that emerged and grew in province throughout the Victorian era and 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a period which would last from June 1837 to January 1901. Covering nearly two third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64 year reign would see numerous changes in fashion. 维多利亚风格指1837年至1901年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的服饰风格,该时代女性的服饰特点是,大量运用蕾丝、细纱、荷叶边、缎带、蝴蝶结、多层次的蛋糕裁剪、折皱、抽褶等元素,以及立领、高腰、公主袖、羊腿袖等宫廷款式。随着复古风潮的盛行,这股华丽而又含蓄的柔美风格,正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These changes would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changes in clothing, architecture, literature, and the decorative and visual arts. Victorian period design was based on imitation and reproduction, made easier by the induction of mass production. The Victorian period of fashion was about living more simply than the previous era. Clothing, makeup, and hairstyles become more natural and relaxed. The use of elaborate wigs made way for cleaner, gentler looks. False hair was limited to rats or switches. 服饰:Victorian Era, Clothing 1825-1850 这个时期两性服裝的潮流到达一种荒谬的定点。女性则持续使用裙撑架,利用褶皱及蕾丝等把自己过度装饰得像个会走路的婚礼蛋糕。由于缝纫机的发明,还有打版书和系统的散播,这个时期不论男人和女人的服裝都变的更为复杂。 By the later 1830s, fullness was moving from the upper to the lower sleeves. This morning dress of 1836–40 features shirring on the fitted upper sleeves;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Croquet players of 1864 loop their skirts up from floor-length over hooped petticoats. Small hats with ribbon streamers were very popular for young women in the mid-1860s. 到了1860年,hoop实在是太大了因而它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于是hoop的形状逐渐变成圓卵形加上在背后大量拖曳的裙摆。1866年,hoop的size逐渐縮小但仍维持圓卵形,直到1870年渐渐演变为所谓的Tornure或是Bustle。这样的演变使得女性的体型姿势向前倾斜,就像一艘船的船头一样。此时最特別的是,女性的裙撑架,出現「前扁后膨,强调臀部」款式造型的变化。1860年的crinoline如钢般坚挺,从1864年起,用三角形布拼缝起的裙子使得裙宽达到一种良好的状态。1870年,本时期初,女子穿着「臀垫」〈bustle〉以达到「强调臀部突出」的造型。在1875年之后,女性则转而流行「紧身与拖曳裙」款式的造型,并强调腰部以下背后华丽的装饰。 Bustles and elaborate drapery characterize evening dresses of the early 1870s. The gentleman wears evening dress. Detail of "Too Early" by Tissot, 1873
维多利亚风格服饰(Victorian Fashion) 维多利亚风格指1837年至1901年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的服饰风格风情,以唯美,高贵,雅致为主旋律 大体来说,维多利亚时代就是一个以烦琐体现优雅高贵的时代吧…… 我从各个年代的服饰变化角度切入 1825-1850 这个时期两性服裝的潮流到达一种荒谬的定点。男性服装清一色是未经装饰的黑色烟管状服裝;女性则持续使用裙撑架,利用褶皱及蕾丝等把自己过度装饰得像个会走路的婚礼蛋糕。由于缝纫机的发明,还有打版书和系统的散播,这个时期不论男人和女人的服裝都变的更为复杂。虽然男人的衣服外在看來简单却需要更复杂的剪裁来使服装线条更为贴近身体线条。 接下来重点介绍女性服饰的演变。 无论英国或西欧,再度流行起蓬松的袖摆如下图:
1840年才是有真正的维多利亚风格 此时女性的裙子又变得宽大(当然不如18世纪那麼宽)裙子并不需要刻意填充以使其膨胀,虽然也会显得丰满,但是大体上还是与自然体型相当。之后衬裙变得很沉重而且不灵活。
先从袖子谈起, 维多利亚女性的上衣其实已经具备现代女装的特色 长长的窄袖、披肩、封闭式的外衣 18世纪洛可可时代的女装,其实是开放式的外套,并且裸露裏头的低胸束腰。这点在道德观念严密的维多利亚,是非常要不得的。 ↑洛可可时代 因此你可以看到,维多利亚女人们的上衣都是 一体成形的罩衫 最明显的改变莫过於花纹
19世纪流行的风潮,其实把装饰都留给了花边 反而在布料染色跟绣花上的功夫,其实比较简约 1850年代,19世紀女性服裝的体态轮廓,在50年代为「半球型」 这时的洛可可的气息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受到家庭的道德观影响,女人们的衣著色调变得更深,更素雅 并且全身色系相当统一。 1850年代,女性采用Hoop Skirt(或称作Crinoline)取代以往又重又热又大又不卫生的衬裙,使得她们的双脚有更多活动的自由,而她们对于這服装上一点小小的改革感到滿足。这种Hoop Skirt可能会露出女性的双脚,因此她们必须采用The Bloomer Costume內搭的长裤,而且在初期这些裙撑架是以坚固的铁制成的,这种服饰使男性受到惊吓并企图阻止这样的流行继续下去,他们毫不留情的在报纸及公开场合等利用各种方式来嘲笑这种流行趋势。Hoop Skirt的好处使得大多数女性不顾父亲及丈夫的放对,Hoop Skirt 的材料也很快地从坚固的铁制成到有弹性的钢丝,这使得裙子可以越來越轻。到了1850年代中期,时髦的裙子需要圈环或者钢箍撑起来,膨胀得很厉害。在当时的幽默或者讽刺杂志上时常可以见到嘲讽的图画。这时期裙子的膨大化是靠穿数层衬裙来实现的,一般至少重叠四到六层衬裙。女装的下半部越来越沉重。但是圈环裙的流行并没有持续多久,许多女性并不喜欢。维多利亚女王也从没穿过这样的裙子。这一样式脱离实际,非常不便,而且显得不庄重(会有暴露内衣的危险)。 在1850-1865年间,女性服饰的轮廓变得更大和趋于水平线在过去所有的线条都是向下拉的。如图:
最新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都是近期写作 1 英文征婚广告和中文征婚广告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2 《野性的呼唤》中的自然主义 3 精神危机下的自我救赎--对索尔贝娄《赫索格》中社会异化与身份认同的解读 4 从功能对等和文化语境差异角度看商务英语翻译技巧 5 浅析中西价值观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及其解决方法 6 自然主义在《海狼》中的表现 7 论性别歧视 8 中美学校教育对比——学生个性发展方面 9 英汉基本颜色词的文化差异及其翻译策略 10 《抽彩》和《蝇王》的艺术魅力比较 11 从女性主义分析《红字》与《傲慢与偏见》 12 从妇女主义视角看《紫色》中西丽的成长 13 《麦克白》的独白 14 中英动物习语使用和翻译的差异研究 15 English to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s 16 Influence, Barriers and Soft Cultural Power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7 游戏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18 从文化角度谈美国俚语的汉译 19 Contradiction of Hawthorne Reflected in the Symbols and Images in Young Goodman Brown 20 福斯特《霍华德庄园》中的三个世界 21 论斯嘉丽的形象特征分析 22 《儿子与情人》恋母情结分析 23 A Study on the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in the Sino-American Joint-Venture Enterpris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angan & Ford Motor Company 24 探析《愤怒的葡萄》中人性的力量 25 《推销员之死》中男主人公悲剧命运分析 26 从《麦琪的礼物》和《爱的牺牲》分析欧?亨利的写作特色 27 中西服饰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28 英汉称赞语回应的对比研究 29 《太阳照常升起》中科恩屡遭排斥的根源分析 30 浅析“欧亨利式结尾”在其小说中的主题揭示 31 浅析英语新闻标题特点及其翻译技巧 32 语用移情及其在英语学习中的运用 33 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 34 论修辞格在英语广告中的运用 35 词汇教学法在中学英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36 目的论视角下《了不起的盖茨比》两个译本对比研究 37 旅游与文化 38 英汉礼貌用语及交际策略的对比分析 39 文化视野下的中美家庭教育方法的比较 40 An Analysis of The Woman Warr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of Discrete Identity in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Chapter 4 The Victorian Period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对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散文,小说在创作思想上的进步和创作技巧上的改革,以及对该时代主要作家的生平,观点,创作旨意,艺术品特点及其代表作的主题,结构,语言,人物刻画等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通过作品选读加深体会感受,增强对作品的理解和鉴赏能力。 二。考核要求 (一) 维多利亚时期概述 1. 识记:(1)维多利亚时期的界定 (2)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2. 领会:(1)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特点 (2)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3. 应用:宪章运动,功利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独自等名词的解释 (二) 该时期的重要作家 1. 一般识记:重要作家的生平与创作生涯 2. 识记:重要作品及主要内容 3. 领会:重要作家的创作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代表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社会意义等。
4. 应用:(1)狄更斯和萨克雷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想及各自的创作手法,艺术特色。 (2)小说《简.爱》,《呼啸山庄》的主题思想与人物塑造。 (3)“我逝去的公爵夫”;中的戏剧独白。 (4)乔泊.艾略特和哈代小说中环境,氛围描述与人物内世界的展示。 A. Introduction to the Victorian Period 1. 识记 (1) Definition: the Victorian Period Chronologically the Victorian period roughly coincides with 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who ruled over England from 1836 to 1901. The period has been general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glorious in the English history. (2) Political, Economical &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Victorian England was a tim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After the Reform Bill of 1832 passed the political power from the decaying aristocrats into the hands of the middle-class industrial capitalist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on geared up. Towards the mid-century,England had reached its highest point of development as a world power. And yet beneath the great prosperity & richness, there existed widespread poverty & wretchedness among the working class. The worsening living & working conditions, the mass unemployment & the new Poor Law of 1834 with its workhouse system finally gave rise to the Chartist Movement (1836-1848)。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发展史上迅猛上升的时期。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空前强大,势力范围迅速扩张。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英国,这似乎是现实世界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也许是许多维多利亚文学作品的背景。从《简·爱》(Jane Eyre,1847)中女主人公意外地继承叔叔在马地拉给她流下的两万磅的遗产,到《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1)中失意后的匹普去埃及经营茶叶,到《名利场》(Vanity Fair,1848)中的利蓓卡第一次施展身手就勾引从印度回国的财主乔瑟夫,人们不难看出,当时去殖民地捞钱是本国人民公认有效的“生财之道”。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是一个能让人梦想“远大前程”的自信的年代。有的评论家,如斯坦纳(Steiner),认为维多利亚的黄金时代像伊甸园,20世纪初的某些评论家则认为它像地狱。一般来说,为研究方便。维多利亚时期被文史家们分为三个阶段:维多利亚早期(1832~1848)、维多利亚中期(1848~1870)和维多利亚晚期(1970~1891)。 维多利亚早期也常被称为“多事之秋”(A Time of Troubles)。经济上的繁荣并不能阻止阶级矛盾的产生。就在新兴资产阶级奇迹般地暴富起来时,劳动者却不得不在残酷的压迫下过着穷困的生活。这一时期反抗压迫、争取民主选举权的运动蓬勃发展,在“宪章派”诗人的作品中得到忠实反映,最有代表性的有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19~1869)的《民主之歌》(The Songs of Democracy)。散文家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837)和《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843),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的《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1855)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钱拜物教和市侩主义对人类道德的腐蚀,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在他早期的小说中更是不遗余力地反映了英国私有制社会的阴暗面。 维多利亚中期正好处于相对稳定的五六十年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天文、地理和生物学等学科的新成果大大扩展了人类的眼界。这一时期被称为“经济繁荣和宗教分歧的时期(Economic Prosperity and Religious Controversy)”。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提出的进化论打破了上帝造物的唯心史观,给传统信仰以猛烈的冲击,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并再次定位;英国国教的势力衰减,新教派林立,福音派吸引了大批小生产者,知识界的所谓“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或“高教派”(High Church)也激烈展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天主教势力的抬头。尽管勤奋和富有责任感仍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价值取向,但全社会都在经历着一场信仰危机。许多文人学者对英国状况深感忧虑。狄更斯等一大批作家继续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弊端进行批判。最激烈的一位莫过于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他的《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1851~1853)预言了维多利亚工商业文明的毁灭,在《直到最后》(Unto the Last,1862)中对自由竟争的经济法则进行了无情攻击。较为客观的要数安索内·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的小说。教育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1822~1888)在他的著名论著《文化与无政府》(Culture and Anarchy,1869)中,反对对物质的迷信,提倡文化和精神价值。他对英国社会状况的反思代表了一代有识之士面对新现实的焦虑和危机感。尽管这个时期存在许多问题,但它仍然是一个繁荣时期。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各种文学样式,尤其是长篇小说发展的黄金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标准 此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维多利亚女性特点。 首先文章介绍了十九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从运动的起因,过程和特点阐述分析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特征。然后,文章描述了英国文学界的一次女性创作高峰,即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的兴起。在这个部分,文章对女性写作兴起的原因,女性作家写作特色进行了分析。最后,文章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女性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婚姻三个方面对她们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大体描述。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不得不说到女权主义(feminism)运动。西方的女权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和工业**同步,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 在19世纪以前,女性社会地位身份低下,尤其是已婚女子,被认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几乎失去了自由,存在感十分微弱。女性不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她们的活动范围基本被局限在家庭,社交场合,因而女性的创造力也受到了压制和忽视。女性在社会显然处于弱势,可是女性并没有因为弱小而收到保护,恰恰相反,在家庭或者公共场所,女性常常受到攻击和骚扰。由此看来,当时的女性面临着自我意识的觉醒问题,当女性渐渐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奋斗才可能获得成功,获得社会的认可时,女权主义运动也就顺着历史的潮流产生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下层劳动女性为了面包而工作,广大中产阶级女性为了权力而斗争。由于劳动女性斗争意识的增长和女权主义的呼吁,英国制定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采取了请愿的方式,广大女性纷纷组织社会团体,上街进行宣传讲演,在社会上扩大女权运动的影响,给议会施加压力,以迫使议会通过女性的要求。
女权运动在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之初,依然延续着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斗争方式,主要采取舆论宣传,组织请愿等方式。19世纪80年代,相续出现一批女权运动的团体。到1894年时,女性争取参政权的斗争有了一定效果,已婚妇女获得了在地方上的选举权。在女王去世的的头两年,一些激进的女权运动者认为通过和平请愿获得参政权力的方式已经过时,一些女权组织开始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抗议,运动更加激进化。但不论采取什么运动方式,直至维多利亚时代结束,女性的参政要求也没有被议会通过。分析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参政运动,不难发现,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是中、下层女性,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她们由于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学习中逐渐认识到她们作为中产阶级女性的权力的缺失,于是首先起来进行抗议。在她们的宣传影响下,更多的中、下层女性参与到运动中来,女权运动逐步发展壮大。 女权主义运动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请求,在维多利亚时代,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便是女性作家的兴起。 女性作家的兴起做主要的体现是女性写作在小说领域的兴起与发展。十九世纪以前,小说一度被当做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创作形式,当时的文学形式以诗歌创作为主,出现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浪漫主义诗人,如约翰济慈,雪莱,拜伦等等。而此时的诗歌领域,注定了只是男人们驰骋的疆场,因为浪漫主义诗人都是有机会大量接触拉丁文、腊文和古典文学成就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能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男人们。从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多产的女小说家简奥斯丁开始,随后出现了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和乔治艾略等等,形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女性创作文学的高峰。
六.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n Era 1837年—1901年)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杰出的小说家,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波兹特写》(Sketches by Boz),《匹克维克外传》(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雾都孤儿》(Oliver Twist),《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美国札记》(American Notes),《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荒凉山庄》(Bleak House),《艰难时世》(Hard Time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的小说家。代表作长篇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亨利·艾斯蒙德》(Henry Esmond),《纽可姆一家》(The Newcomers)。 勃朗特三姐妹(The Bronte Sisters): 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简爱》(Jane Eyre);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e)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安尼·勃朗特(Anne Bronte)的《安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著名的现实主义女作家。代表作《亚当·比德》(Adam Bede),《弗罗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织工马南》(Silas Marner),《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A Study of Provincial Life)。 盖斯凯尔夫人(Mrs. 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 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玛丽·巴顿》(Marry Barton),《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夏洛特·勃朗特传》(Life of Charlotte Bronte)。 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 小说家,代表作《理查德·法弗尔的苦难》(The Ordeal of Richard Feverel)。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伟大的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威赛克斯故事集》(Wessex Tales),《人生小讽刺》(Life’s Little Ironies),诗歌《列王》(The Dynasts)。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I.Multiple Choice(40 points in all, 1 for each) Select from the four choices of each item the one that best answers the question or completes the statement. Write the corresponding letter A, B, C or D on the answer sheet. chapter 18.The Victorian Age was largely an age of ____, eminently represented by Dickens and Thackeray. A.poetry B.drama C.prose D.epic prose (024) 18. A typical feature of the English Victorian literature is that writers became social and moral ______, exposing all kinds of social evils. A. revolutionaries B. idealists C. critics D. defenders(044) 16. The Victorian Age is most famous for its ________. A. plays B. novels C. poems D. essays (047) 14.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Victorian literature is NOT true?()4 A. Novels became the most widely read and the most vital and challenging expression of progressive thought. B. Victorian novelists were angry with the inhuman social institutions, the decaying social morality, the widespread misery, poverty and injustice. C. Influenced by a particularly strict set of moral standards, Victorian writers like Oscar Wilde, advocated the old moderate, respectable life-style. (057) D. Victorian prose writers joined forces with the critical realist novelists in exposing and criticizing the social reality. 18. Although writing from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with different techniques,writers in the Victorian Period shared one thing in common,that is,they were all concerned about ______. A. the fate of the upper class B. the re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C. the fate of the common people D. the future of their family clans(087) 1. The first mass movement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and the early sign of the awakening of the poor, oppressed people is_____. 3 A. The Enclosure Movement B.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C.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D. The Chartist Movement (097) 13. In the Victorian Period _____ became the most widely read and the most vital and challenging expression of progressive thought. 2 A. poetry B. novel C. prose D. drama(097) 14. All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Victorian period is true EXCEPT ______. 1 A. England was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B. The early years was a tim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erious social
维多利亚时代 亚利山德拉·维多利亚于1837年继承王位(当时她18岁),统治英国直到1901年逝世,是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她统治英国近一段时期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盛世。 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点时期,也是大英帝国经济文化的全盛时期。 维多利亚时期以崇尚道德修养和谦虚礼貌而著名,也是一个科学、文化和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的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还形成了男女平等和种族平等的进步观念,美国的废奴运动正是这一思想进步的体现。 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发明浪潮汹涌澎湃,维多利亚人信仰科学进步,对于工业革命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汽船的出现使得运输和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旺,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贯穿东西南北。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艺运动流派包括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派艺术,以及后印象派等。艺术界呈现出群星夺目的盛景。 维多利亚时代还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作家、诗人和他们的传世之作,如英国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简·爱》)以及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等。 当时还出现了许多代表各个时期风格的建筑。在这一时期,西方世界的建筑以简洁的形式重现了以往各个时代的古典风格,如:希腊风格、哥特式建筑风格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 那个时代的中上层阶级对于饮食非常讲究,他们从遥远的国度进口各种异国情调的香料调料,用于精心烹制的食品中。维多利亚时代有了历史上最早的烹调学校,名厨编写的烹调书籍风行英国,在这个时代人们最早将具体烹调方法如调料用量等详细写入书中。一些厨房小用具也流行起来,如开罐器等,维多利亚时代还形成了许多进餐礼仪。 这个时期,英国盛行下午茶,贵族们早餐丰富,午饭简单,晚饭很晚。据说,维多利亚女王的女侍从官——女公爵安娜每到下午就会觉得很饿,于是便让仆人拿些小茶点来吃,许多人纷纷效仿,下午茶渐渐成为一种例行仪式。事实上,围绕着这种下午茶习俗形成了多彩的茶文化,高雅的旅馆开始设起茶室,街上有了向公众开放的茶馆,茶话舞会更成为一种社会形式,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小姐们在那里与男友们会面。 这个令人神往的时代,并没有随着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而结束。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真正结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令我们中国人印象深刻的是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中国由此渐渐步入半殖民地深渊。而当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1839-1901)是不是英国海外扩张的鼎盛时期,我们留给历史学家去讨论。“星期六”读“文化广场”的人大概有兴趣知道蒸汽机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世界博览会(也叫万国博览会)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下午茶是这个时期产生的;“美人靠”之类的维多利亚式
英美文学选读翻译(英语专业自考) 第四章维多利亚时期 从时间上讲,维多利亚文学时期恰好与维多利亚女王1836年至1901年执政期相吻合,这一时 段是英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段。 维多利亚执行初期,英国面临着飞速的经济发展及严重的社会问题。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后,国家政权从腐朽没落的贵族手中移向新兴的中产阶级工业资本家,不久,大工业革命高潮迭起,各种科技发明与技术创新为国家经济带来新生力量,如火车、蒸汽船、纺织机器、印刷机器等。英国一度成为"世界工厂",通过向海外发展市场与剥削殖民地的各种资源积累了大量财富。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全世界的经济第一强国。但在这繁荣与财富下掩盖的是工人阶级的贫困与不幸,为了谋生连妇女和儿童都要受雇到艰险肮脏的工厂矿山去卖苦力。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终于引发了1836至1848年著名的英国宪章运动。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推出《人民宪章》,要求政府保障人权,改善生活与工作环境。运动席卷了几乎所有城市。这次运动尽管在1848年衰落下去,但却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标志着工人阶级的觉醒。 接下来的20年,英国相对繁荣稳定。中产阶级的生活显示出有前途、受尊敬、很富有的特点。人民整体也追求一种热情、自尊、谦逊、爱国的民族精神,而维多利亚女王也正是这些品格的榜样。这时道德与常理这些被浪漫主义时代遗弃多年的主题,又回到了文学主流中来。 但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大英帝国与维多利亚价值观都逐渐走向衰落。在海外英国虽然还是最大的殖民者,有着不可敌胜的经济、军事实力,但它的领袖地位已经开始面临正在崛起的德国的挑战,与美国的竞争也伤害了英国的经贸垄断地位。国内的爱尔兰民族问题悬而未决,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打破了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的政治制衡。维多利亚价值观在世纪末失去了光彩,原先谦和、体面的生活方式也被放纵与挥霍所取代。这种世纪末伤感在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与沃尔特·培特(1839-1894)的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这些唯美主义文学家都极力推崇"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在意识形态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与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打破了人们过去坚定的宗教信仰,宗教大厦开始坍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与《人类的进化》(1871)都是动摇了传统信仰的理论基。诗人丁尼生在长诗《悼念》中就明确表述了自己对宗教与上帝的怀疑。另一方面,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任何事物都要经过实用的检验方可定其价值,由于物质进一步战胜精神。《圣经》与《福音书》等宗教经典都被认为是过时的迷信,或干脆也要接受实用主义的检验。这些观念都使得资本家进一步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不再有精神道德上的顾虑。狄更斯、卡利尔、拉斯金及许许多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们都极力批驳实用拜金主义,尤其是它对文化道德的贬低及对人类情感的漠然。 维多利亚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自然带有宏大与多样性的特点。它是多侧面而且复杂的从各个角度,包括浪漫的与现实的反映了人民生活中的各种巨大变化,这个时代也诞生了一 大批顶天立地的文学巨人。 这个时期,小说广泛流行,繁荣发展。著名小说家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狄更斯、萨克雷、勃朗蒂姐妹、哥斯凯尔夫人(1810-1865〉与特罗洛普(1815-1882)等人。这些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一方面重新倡导18世纪的现实主义,一方面又肩负起批判社会,保卫人民利益的责任。尽管他们的创作角度与风格各不相同,但共同特点是关心广大百姓的生活与命运,他们为不人道的社会机构、堕落的社会道德、拜金主义的盛行及大面积的贫困与不公深感愤慨。他们作品中对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对社会制度的无情批判唤醒了公众对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的意识。在19世纪末还出现了一位勇敢的女性小说家乔治·埃略特与一个不仅揭露批判社会丑恶现象,还大胆向维多利亚传统道德观发起攻击的文学家哈代。
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是女性文学崛起的时期,被称为女性小说家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像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等一大批杰出的女作家,她们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影响,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更是充满了独特的时代魅力。维多利亚女王的漫长统治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盛世,之前还不受重视的女性文学陡然跃入巅峰。女性文学的发展不在于作品的多少,而在于其必须依随时代观念的革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文学无论从数量上抑或质量上皆蔚为大观,天才女作家层出不穷,女性作品俨然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朵奇葩,一个奇迹。她们为英国文学的画卷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更为丰富多彩、更富于深度和广度,而这一笔不仅为女性作家挣得了地位,也使英国文学远远走在了同时期世界文学的前面。其代表作家包括: 一、简?奥斯丁 1811年至1818年,奥斯丁先后发表了《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劝导》六部小说。这六部完整的作品,没有拜伦式慷慨激昂的抒发,也极少见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描写,她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喜剧,显示了“家庭”文学的可能性。她多次探索青年女主角从恋爱到结婚的自我发现过程。这种着力分析人物性格以及女主角和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做法,使她的小说摆脱了18世纪的传统风格而接近于现代的生活。正是这种现代性,加上她的机智和风趣,她的现实主义和同情心,她优雅的散文笔法和巧妙的故事结构,使其作品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称赞,部部堪称上乘之作。尤其是那部脍炙人口的《傲慢与偏见》,实属世界文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难怪毛姆将其列入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一。奥斯丁的作品是英国小说
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标准此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维多利亚女性特点。 首先文章介绍了十九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从运动的起因,过程和特点阐述分析维 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特征。然后,文章描述了英国文学界的一次女性创作高峰,即维多利亚时 代女性写作的兴起。在这个部分,文章对女性写作兴起的原因,女性作家写作特色进行了分析。最后,文章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女性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婚姻三个方面对她们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大体描述。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不得不说到女权主义(feminism)运动。西方的女权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发生在维多利亚时期,和工业**同步,也就是19世纪下 半叶。 在19世纪以前,女性社会地位身份低下,尤其是已婚女子,被认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几乎失去了自由,存在感十分微弱。女性不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她们的活动范围基本被局 限在家庭,社交场合,因而女性的创造力也受到了压制和忽视。女性在社会显然处于弱势,可是女性并没有因为弱小而收到保护,恰恰相反,在家庭或者公共场所,女性常常受到攻击 和骚扰。由此看来,当时的女性面临着自我意识的觉醒问题,当女性渐渐意识到只有依靠自 己的奋斗才可能获得成功,获得社会的认可时,女权主义运动也就顺着历史的潮流产生了。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下层劳动女性为了面包而工作,广大中产阶级女性为了权力而斗争。由于劳动女性斗争意识的增长和女权主义的呼吁,英国制定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这一阶段的斗争主要采取了请愿的方式,广大女性纷纷组织社会团体,上街进行宣传讲演,在社会上扩大女权运动的影响,给议会施加压力,以迫使议会通过女性的要求。 女权运动在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之初,依然延续着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斗争方式, 要采取舆论宣传,组织请愿等方式。19世纪8 0年代,相续出现一批女权运动的团体。到1894 年时,女性
· 维多利亚时期的大众化平面设计 维多利亚是整个19世纪的英国君主,她把18世纪和20世纪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和平、繁荣的、没有战争动乱的稳定局面,从而使英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和进步,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 上最强大的国家。 由于生活的安定,物质的日益丰裕,经济高速发展,因此人们对于艺术、审美的要求也日益增高。维多利亚时代是对美学价值的探索,研究和追求新形式、新艺术的时代。由于探索的方向各有不同,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设计风格一方面表现出复杂的矛盾和折衷倾向,同时也体现出由干物质丰裕而造成的繁琐 装饰化趋向。 维多利亚时期在设计风格上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干中世纪哥德风格的推崇和流行。在这种流行风格的后面,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干中世纪,特别是哥德时期的道德、宗教虔诚的崇拜和向往。推动这种风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英国建筑家普京,他的重要设计是英国国会大厦的室内和细部装饰设计,充分体现了当时流行的哥德复兴风格。普京对干哥德时期的道德和宗教虔诚是顶礼膜拜的。他虽然反复强调,他之所以设计哥德式的室内、家具和其他用品,不是为了“风格”,而只是为了复兴哥德时期的精神,但是,不可辩驳的是他的这些设计,确确实实地推动了哥德风格在英国的普及与流行。 追求中世纪浪漫主义风格和情调的主要设计家中,比较早的代表人物有欧文·琼斯(Owen Johns. 1809-1874)。为了掌握他认为真实的艺术和设计风格,琼斯曾经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在西班牙、近东地区、中东地区进行考察,对于伊斯兰艺术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他对于北非摩尔人的艺术和装饰最为钟爱,在西班牙,他对格拉纳达地区摩尔人修建的美轮美奂的阿尔汉布拉宫殿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这个研究使他对干北非伊斯兰教文化和艺术的特征有非常深刻的认识,1842-1845他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阿尔汉布拉宫的规划、布局、局部和细部》(Plans,Elevations, Sections, and Details of the Alhambra)·经过几年的深人探索,他干1856年出版了自己最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装饰的语法》(The Grammar of Ornament)。这本著作集中了大量他收集的中东和西班牙艺术及装饰的材料,有相当数目的彩色插图,为当时的设计师、建筑家提供了第一本可以信赖的有关非西方艺术和设计的资料手册,在维多利亚时期成为大量设计家、建筑家必备的工具书。伊斯兰教文化和艺术、装饰具有相当部分的繁琐特点,也通过琼斯的这本书引人西方,因此,维多利亚时期装饰上具有的繁琐特征,特别是建筑与家具的木构件上非常繁复的所谓“饼装饰”,(ginger bread woodwork),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种繁杂的装饰纹样不但出现在建筑、家具、家庭用品的装饰上,也同时出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书籍设计、印刷设计上,特别是版面的边缘装饰, 大量出现了繁琐的图案。 1850年前后,“维多利亚”这个词开始被用来形容这个时期的一种美学价值和风格,进而被用来形容这个时期的精神、问题特征。维多利亚时期是富裕的发展时期,设计上的矫揉造作、繁琐装饰、异国风气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建筑与室内设计上,还是从产品设计上,乃至平面设计上,都弥漫了这种风格,这种风格的流行,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长期和平繁荣发展的前途下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日后的不少设计运动,包括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和席卷欧美的“新美术”运动,其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与 这种繁琐装饰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