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的孤独-阿尔都塞
- 格式:doc
- 大小:71.50 KB
- 文档页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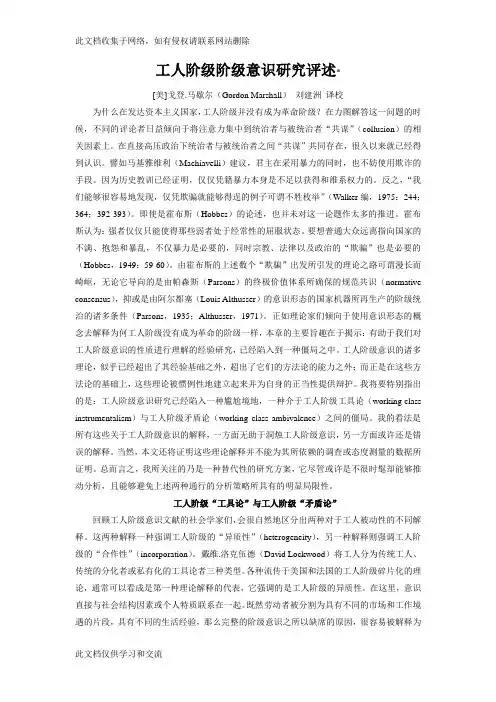
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研究评述*[美]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刘建洲译校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革命阶级?在力图解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不同的评论者日益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谋”(collusion)的相关因素上。
在直接高压政治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共谋”共同存在,很久以来就已经得到认识。
譬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建议,君主在采用暴力的同时,也不妨使用欺诈的手段。
因为历史教训已经证明,仅仅凭籍暴力本身是不足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
反之,“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仅凭欺骗就能够得逞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Walker编,1975:244;364;392-393)。
即使是霍布斯(Hobbes)的论述,也并未对这一论题作太多的推进。
霍布斯认为:强者仅仅只能使得那些弱者处于经常性的屈服状态。
要想普通大众远离指向国家的不满、抱怨和暴乱,不仅暴力是必要的,同时宗教、法律以及政治的“欺骗”也是必要的(Hobbes,1949:59-60)。
由霍布斯的上述数个“欺骗”出发所引发的理论之路可谓漫长而崎岖,无论它导向的是由帕森斯(Parsons)的终极价值体系所确保的规范共识(normative consensus),抑或是由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所再生产的阶级统治的诸多条件(Parsons,1935;Althusser,1971)。
正如理论家们倾向于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去解释为何工人阶级没有成为革命的阶级一样,本章的主要旨趣在于揭示:有助于我们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性质进行理解的经验研究,已经陷入到一种僵局之中。
工人阶级意识的诸多理论,似乎已经超出了其经验基础之外,超出了它们的方法论的能力之外;而正是在这些方法论的基础上,这些理论被惯例性地建立起来并为自身的正当性提供辩护。
我将要特别指出的是:工人阶级意识研究已经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一种介于工人阶级工具论(working class instrumentalism)与工人阶级矛盾论(working class ambivalence)之间的僵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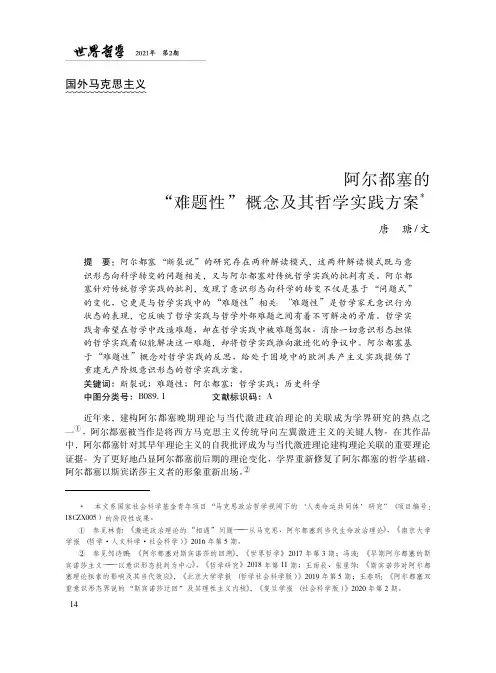
国外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难题性”概念及其哲学实践方案*唐瑭/文提要:阿尔都塞“断裂说”的研究存在两种解读模式,这两种解读模式既与意识形态向科学转变的问题相关,又与阿尔都塞对传统哲学实践的批判有关。
阿尔都塞针对传统哲学实践的批判,发现了意识形态向科学的转变不仅是基于“问题式”的变化,它更是与哲学实践中的“难题性”相关。
“难题性”是哲学家无意识行为状态的表现,它反映了哲学实践与哲学外部难题之间有着不可解决的矛盾。
哲学实践者希望在哲学中改造难题,却在哲学实践中被难题驾驭。
消除一切意识形态担保的哲学实践看似能解决这一难题,却将哲学实践推向激进化的争议中。
阿尔都塞基于“难题性”概念对哲学实践的反思,给处于困境中的欧洲共产主义实践提供了重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实践方案。
关键词:断裂说;难题性;阿尔都塞;哲学实践;历史科学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18CZX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参见林青:《激进政治理论的“相遇”问题———从马克思、阿尔都塞到当代生命政治理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②参见邹诗鹏:《阿尔都塞对斯宾诺莎的回溯》,《世界哲学》2017年第3期;冯波:《早期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中心》,《哲学研究》2018年第11期;王雨辰、张星萍:《斯宾诺莎对阿尔都塞理论探索的影响及其当代效应》,《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王春明:《阿尔都塞双重意识形态界说的“斯宾诺莎迂回”及其理性主义内核》,《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近年来,建构阿尔都塞晚期理论与当代激进政治理论的关联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①,阿尔都塞被当作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导向左翼激进主义的关键人物。
在其作品中,阿尔都塞针对其早年理论主义的自我批评成为与当代激进理论建构理论关联的重要理论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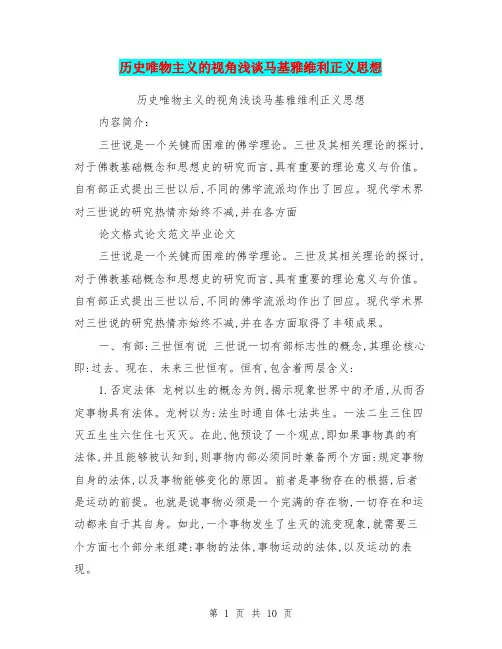
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浅谈马基雅维利正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浅谈马基雅维利正义思想内容简介:三世说是一个关键而困难的佛学理论。
三世及其相关理论的探讨,对于佛教基础概念和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价值。
自有部正式提出三世以后,不同的佛学流派均作出了回应。
现代学术界对三世说的研究热情亦始终不减,并在各方面论文格式论文范文毕业论文三世说是一个关键而困难的佛学理论。
三世及其相关理论的探讨,对于佛教基础概念和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价值。
自有部正式提出三世以后,不同的佛学流派均作出了回应。
现代学术界对三世说的研究热情亦始终不减,并在各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有部:三世恒有说三世说一切有部标志性的概念,其理论核心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恒有。
恒有,包含着两层含义:1.否定法体龙树以生的概念为例,揭示现象世界中的矛盾,从而否定事物具有法体。
龙树以为:法生时通自体七法共生。
一法二生三住四灭五生生六住住七灭灭。
在此,他预设了一个观点,即如果事物真的有法体,并且能够被认知到,则事物内部必须同时兼备两个方面:规定事物自身的法体,以及事物能够变化的原因。
前者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后者是运动的前提。
也就是说事物必须是一个完满的存在物,一切存在和运动都来自于其自身。
如此,一个事物发生了生灭的流变现象,就需要三个方面七个部分来组建:事物的法体,事物运动的法体,以及运动的表现。
否定作用龙树从因缘、因果的角度否定了有部的三世说中的引果作用之义。
总的看,仍然是以生为例进行批判的。
《中论》认为: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
龙树从不自生、不他生、不自他生三方面,指出因和缘不能必然导致结果。
按照一般的理解,一个事物要发生,需要自己作为内在原因,需要各种外在的原因,并且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这样才会有结果。
三、经部:缘无生心说《俱舍论》中记载的经部,以缘无生心论对三世说正面进行了批判。
有部以为六识与六根、六境结合后,可以形成某种关于事物的现象,由于存在着本体界的三世,并以此作用于现象世界,从而使得世界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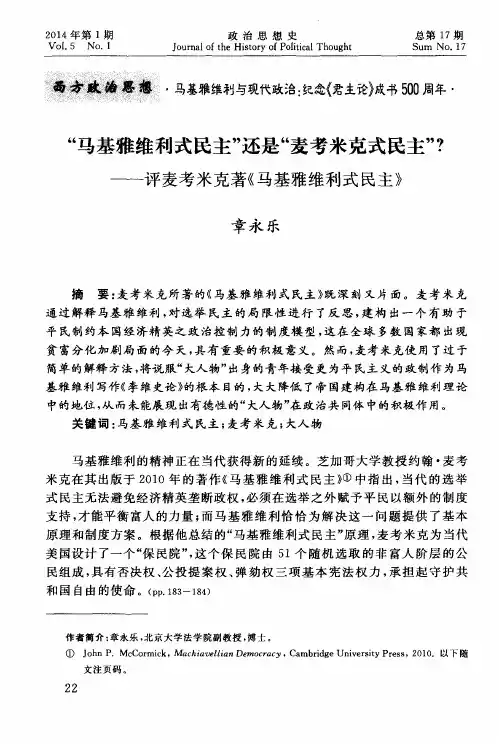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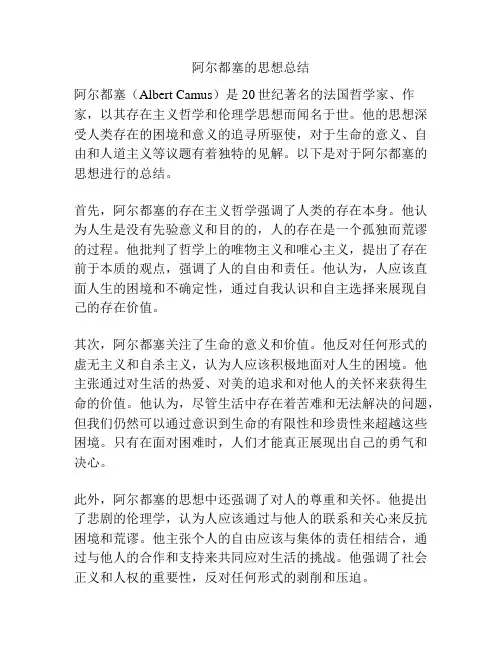
阿尔都塞的思想总结阿尔都塞(Albert Camus)是20世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作家,以其存在主义哲学和伦理学思想而闻名于世。
他的思想深受人类存在的困境和意义的追寻所驱使,对于生命的意义、自由和人道主义等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
以下是对于阿尔都塞的思想进行的总结。
首先,阿尔都塞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了人类的存在本身。
他认为人生是没有先验意义和目的的,人的存在是一个孤独而荒谬的过程。
他批判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提出了存在前于本质的观点,强调了人的自由和责任。
他认为,人应该直面人生的困境和不确定性,通过自我认识和自主选择来展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其次,阿尔都塞关注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和自杀主义,认为人应该积极地面对人生的困境。
他主张通过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和对他人的关怀来获得生命的价值。
他认为,尽管生活中存在着苦难和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和珍贵性来超越这些困境。
只有在面对困难时,人们才能真正展现出自己的勇气和决心。
此外,阿尔都塞的思想中还强调了对人的尊重和关怀。
他提出了悲剧的伦理学,认为人应该通过与他人的联系和关心来反抗困境和荒谬。
他主张个人的自由应该与集体的责任相结合,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和支持来共同应对生活的挑战。
他强调了社会正义和人权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最后,阿尔都塞对于政治和反抗也有独到的见解。
他批判了极权主义和压迫,主张个体的独立和反抗。
他提出了荒谬反抗的概念,即尽管人类存在的本质是荒谬的,但人们仍然应该通过反抗来展示他们的自由和尊严。
他还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认为艺术是人类反抗困境的一种方式,可以帮助人们表达情感和思想。
总之,阿尔都塞的思想强调了人的自由、责任和尊严。
他主张积极面对人生的困境和荒谬,通过自我认识和自主选择来展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他提倡关心他人和反抗困境,强调了社会正义和人权的重要性。
他的思想对于人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和追求个人自由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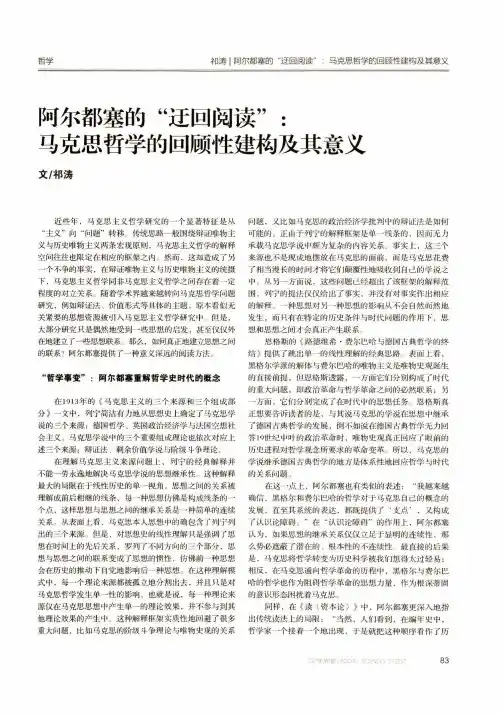
哲学祁涛I阿尔都塞的"迂回阅读":马克思哲学的回顾性建构及其意义阿尔都塞的“迂回阅读”:马克思哲学的回顾性建构及其意义文/祁涛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主义”向“问题”转移。
传统思路一般围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条宏观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空间往往也限定在相应的框架之内。
然而,这却造成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摄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关系。
随着学术界越来越转向马克思哲学问题研究,例如辩证法、价值形式等具体的主题,原本看似无关紧要的思想资源被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但是,大部分研究只是偶然地受到一些思想的启发,甚至仅仅外在地建立了一些思想联系。
那么,如何真正地建立思想之间的联系”阿尔都塞提供了一种意义深远的阅读方法。
“哲学事变”:阿尔都塞重解哲学史时代的概念在1913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简洁有力地从思想史上确定了马克思学说的三个来源: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学说中的三个重要组成理论也依次对应上述三个来源: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与阶级斗争理论。
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来源问题上,列宁的经典解释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马克思学说的思想继承性"这种解释最大的局限在于线性历史的单一视角.思想之间的关系被理解成前后相继的线条,每一种思想仿佛是构成线条的一个点,这样思想与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是一种简单的连续关系。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本人思想中的确包含了列宁列出的三个来源。
但是,对思想史的线性理解只是强调了思想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罗列了不同方向的三个部分,思想与思想之间的联系变成了思想的惯性,仿佛前一种思想会在历史的推动下自觉地影响后一种思想。
在这种理解模式中,每一个理论来源都被孤立地分割岀去,并且只是对马克思哲学发生单一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每一种理论来源仅在马克思思想中产生单一的理论效果.并不参与到其他理论效果的产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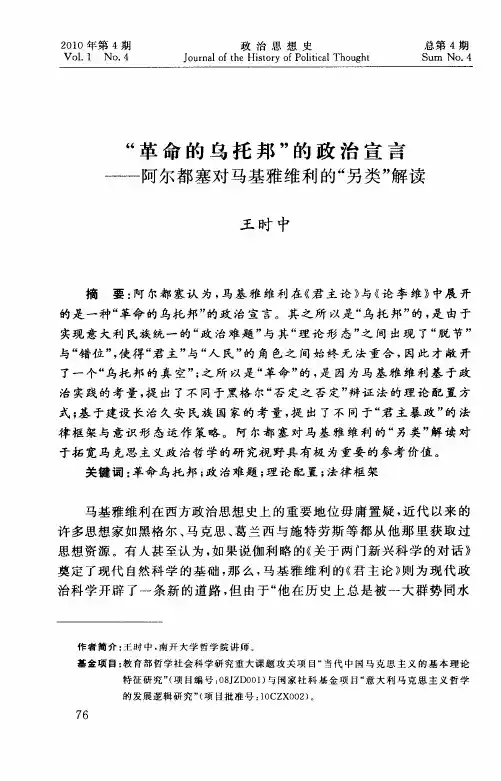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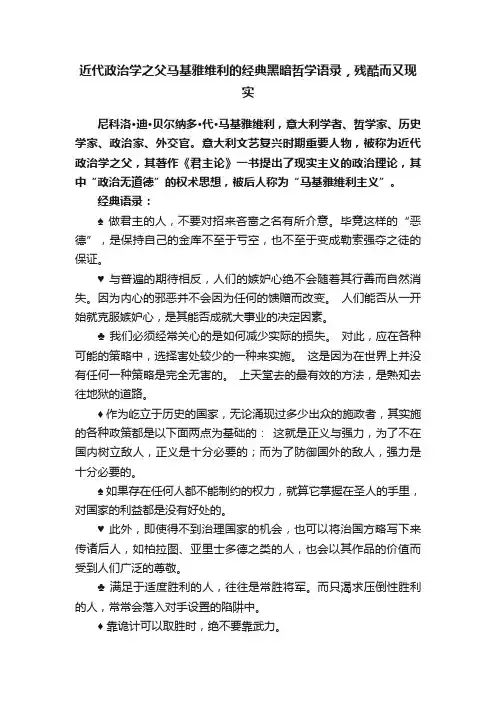
近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的经典黑暗哲学语录,残酷而又现实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维利,意大利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其著作《君主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经典语录:♠做君主的人,不要对招来吝啬之名有所介意。
毕竟这样的“恶德”,是保持自己的金库不至于亏空,也不至于变成勒索强夺之徒的保证。
♥与普遍的期待相反,人们的嫉妒心绝不会随着其行善而自然消失。
因为内心的邪恶并不会因为任何的馈赠而改变。
人们能否从一开始就克服嫉妒心,是其能否成就大事业的决定因素。
♣我们必须经常关心的是如何减少实际的损失。
对此,应在各种可能的策略中,选择害处较少的一种来实施。
这是因为在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种策略是完全无害的。
上天堂去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熟知去往地狱的道路。
♦作为屹立于历史的国家,无论涌现过多少出众的施政者,其实施的各种政策都是以下面两点为基础的:这就是正义与强力,为了不在国内树立敌人,正义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防御国外的敌人,强力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存在任何人都不能制约的权力,就算它掌握在圣人的手里,对国家的利益都是没有好处的。
♥此外,即使得不到治理国家的机会,也可以将治国方略写下来传诸后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类的人,也会以其作品的价值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
♣满足于适度胜利的人,往往是常胜将军。
而只渴求压倒性胜利的人,常常会落入对手设置的陷阱中。
♦靠诡计可以取胜时,绝不要靠武力。
♠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奉承,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
♥必要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
♣成就任何伟业都不可能没有风险。
♦命运支配我们行为的一半,而把另一半委托给我们自己。
♠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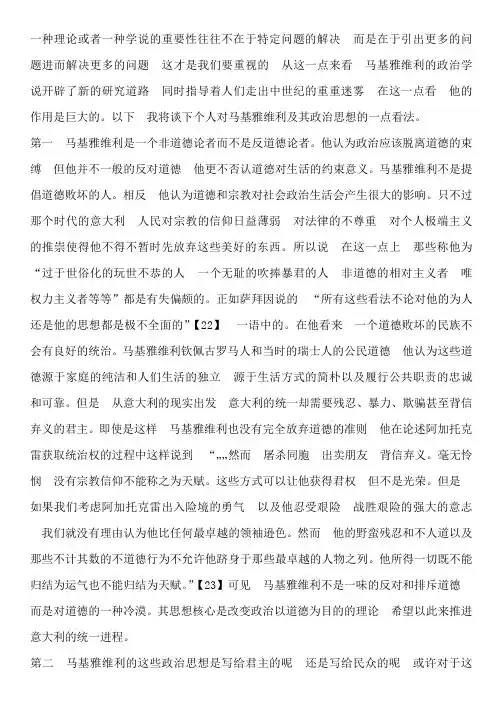
一种理论或者一种学说的重要性往往不在于特定问题的解决 而是在于引出更多的问题进而解决更多的问题 这才是我们要重视的 从这一点来看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开辟了新的研究道路 同时指导着人们走出中世纪的重重迷雾 在这一点看 他的作用是巨大的。
以下 我将谈下个人对马基雅维利及其政治思想的一点看法。
第一 马基雅维利是一个非道德论者而不是反道德论者。
他认为政治应该脱离道德的束缚 但他并不一般的反对道德 他更不否认道德对生活的约束意义。
马基雅维利不是提倡道德败坏的人。
相反 他认为道德和宗教对社会政治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意大利 人民对宗教的信仰日益薄弱 对法律的不尊重 对个人极端主义的推崇使得他不得不暂时先放弃这些美好的东西。
所以说 在这一点上 那些称他为“过于世俗化的玩世不恭的人 一个无耻的吹捧暴君的人 非道德的相对主义者 唯权力主义者等等”都是有失偏颇的。
正如萨拜因说的 “所有这些看法不论对他的为人还是他的思想都是极不全面的”【22】 一语中的。
在他看来 一个道德败坏的民族不会有良好的统治。
马基雅维利钦佩古罗马人和当时的瑞士人的公民道德 他认为这些道德源于家庭的纯洁和人们生活的独立 源于生活方式的简朴以及履行公共职责的忠诚和可靠。
但是 从意大利的现实出发 意大利的统一却需要残忍、暴力、欺骗甚至背信弃义的君主。
即使是这样 马基雅维利也没有完全放弃道德的准则 他在论述阿加托克雷获取统治权的过程中这样说到 “……然而 屠杀同胞 出卖朋友 背信弃义。
毫无怜悯 没有宗教信仰不能称之为天赋。
这些方式可以让他获得君权 但不是光荣。
但是 如果我们考虑阿加托克雷出入险境的勇气 以及他忍受艰险 战胜艰险的强大的意志 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最卓越的领袖逊色。
然而 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那些不计其数的不道德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那些最卓越的人物之列。
他所得一切既不能归结为运气也不能归结为天赋。
”【23】可见 马基雅维利不是一味的反对和排斥道德 而是对道德的一种冷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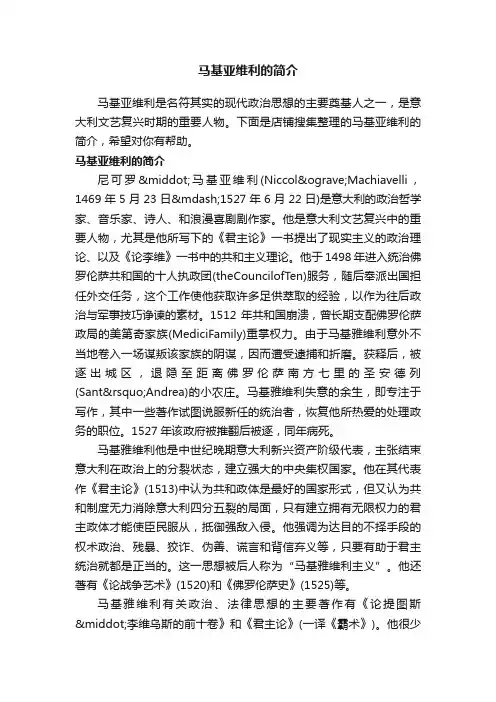
马基亚维利的简介马基亚维利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马基亚维利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马基亚维利的简介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1469年5月23日—1527年6月22日)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音乐家、诗人、和浪漫喜剧剧作家。
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尤其是他所写下的《君主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及《论李维》一书中的共和主义理论。
他于1498年进入统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十人执政团(theCouncilofTen)服务,随后奉派出国担任外交任务,这个工作使他获取许多足供萃取的经验,以作为往后政治与军事技巧诤谏的素材。
1512年共和国崩溃,曾长期支配佛罗伦萨政局的美第奇家族(MediciFamily)重掌权力。
由于马基雅维利意外不当地卷入一场谋叛该家族的阴谋,因而遭受逮捕和折磨。
获释后,被逐出城区,退隐至距离佛罗伦萨南方七里的圣安德列(Sant’Andrea)的小农庄。
马基雅维利失意的余生,即专注于写作,其中一些著作试图说服新任的统治者,恢复他所热爱的处理政务的职位。
1527年该政府被推翻后被逐,同年病死。
马基雅维利他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他在其代表作《君主论》(1513)中认为共和政体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但又认为共和制度无力消除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只有建立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政体才能使臣民服从,抵御强敌入侵。
他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政治、残暴、狡诈、伪善、谎言和背信弃义等,只要有助于君主统治就都是正当的。
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他还著有《论战争艺术》(1520)和《佛罗伦萨史》(1525)等。
马基雅维利有关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著作有《论提图斯·李维乌斯的前十卷》和《君主论》(一译《霸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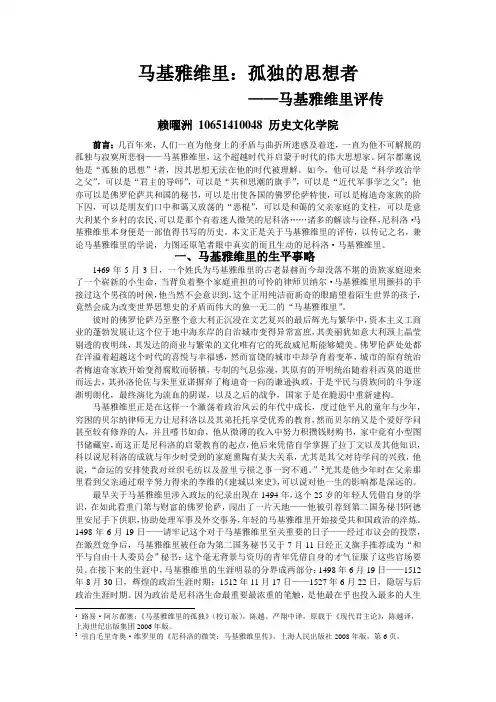
马基雅维里:孤独的思想者——马基雅维里评传赖曜洲10651410048 历史文化学院前言:几百年来,人们一直为他身上的矛盾与曲折所迷惑及着迷,一直为他不可解脱的孤独与寂寞所悲悯——马基雅维里,这个超越时代并启蒙于时代的伟大思想家。
阿尔都塞说他是“孤独的思想”1者,因其思想无法在他的时代被理解。
如今,他可以是“科学政治学之父”,可以是“君主的导师”,可以是“共和思潮的旗手”,可以是“近代军事学之父”;他亦可以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秘书,可以是出使各国的佛罗伦萨特使,可以是梅迪奇家族的阶下囚,可以是朋友们口中和蔼又放荡的“恶棍”,可以是和蔼的父亲家庭的支柱,可以是意大利某个乡村的农民,可以是那个有着迷人微笑的尼科洛……诸多的解读与诠释,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本身便是一部值得书写的历史。
本文正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评传,以传记之名,兼论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力图还原笔者眼中真实的而且生动的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一、马基雅维里的生平事略1469年5月3日,一个姓氏为马基雅维里的古老显赫而今却没落不堪的贵族家庭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小生命,当背负着整个家庭重担的可怜的律师贝纳尔·马基雅维里用颤抖的手接过这个男孩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意识到,这个正用纯洁而新奇的眼睛望着陌生世界的孩子,竟然会成为改变世界思想史的矛盾而伟大的独一无二的“马基雅维里”。
彼时的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正沉浸在文艺复兴的最后辉光与繁华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让这个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自治城市变得异常富庶,其美丽犹如意大利颈上晶莹剔透的夜明珠,其发达的商业与繁荣的文化唯有它的死敌威尼斯能够媲美。
佛罗伦萨处处都在洋溢着超越这个时代的喜悦与幸福感,然而富饶的城市中却孕育着变革,城市的原有统治者梅迪奇家族开始变得腐败而骄横,专制的气息弥漫,其原有的开明统治随着科西莫的逝世而远去,其孙洛伦佐与朱里亚诺摒弃了梅迪奇一向的谦逊执政,于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斗争逐渐明朗化,最终演化为流血的阴谋,以及之后的战争,国家于是在脆弱中重新建构。
之袁州冬雪创作马基雅维利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也是近代以来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摘录一些他的名言给您,但首先要说明一点,即他讲的很多内容可以都属于人们一般所谓的“权谋”、“阴谋”,为凡人所不耻,至少概况上不耻;但我认为,所谓害人之心不成有而防人之心不成无,您还是可以连系您的工作实际看是否有所鉴戒.别的,这些内容基根源自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是他专门写给君主看的,所以,您看过后,不管如何评价,最好不要告知旁人.下列内容为随机摆列.明智的君主应极力图于自身而不是求于他人.那些促使他人强大的人,将自取沦亡.君主在政治上应只思索有效与有害,不必思索正当与不正当,心中应怀揣治国目标,而不是仁义慈爱.君主应同时具有狐狸和狮子的本领:狮子有足够的实力震慑群兽,却不会躲避猎人的陷阱;狐狸懂得躲避猎人的陷阱,却没有实力震慑群兽.有权力,才有权利.所以,人们总是热衷于追求权力的.政治追求的是成功,因为成功了就可以定尺度.政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节制与被节制,实质是依附的关系.目标总可以为手段停止辩白,目标的达到总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他人对我们尊重,是对我们地位的尊重,而不是对我们人的尊重.消灭敌人要趁早.人的天性是欺软怕硬,得寸进尺.永远不要让人对你的期望,愚蠢的人才随意许愿.是非尺度永远出于成功者之手.君主应当拥有美德,但恶行不成不必.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人的欲望与教化无关,与环境无关.得到的不想放弃,得不到的永远最美.世界只属于强者.自立者强,自强者胜,而胜者必智.抱负和道德是号召和动员他人的旗帜,但作为实际运作的手段,毫无意义.让他人始终坚持他的尊严,同时忘掉他的缺点,并习惯他的缺点,这是成功者的伟大之处.永远不要炫耀自己的成功,炫耀成功等于树敌.真正的愚蠢者不在于干蠢事,而在于干了蠢事还不知道藏拙.与人交谈,要服膺,1不谈论自己的成功2不议论他人的不是3分歧错误交谈者当面否定要明白自己的弱点,然后隐藏好.如果受伤,要掩盖受伤之处.成功者乐于他人知晓的,是他的失败而不是成功.既要苦干,也要让你的苦干为他人所知.不要太亲近于人,也不要太让他人亲近,因为这会让弱者对你发生依赖心理,永远不要把弱者和蠢货抗在自己的肩上.对于自己懂得的真相,对他人未需要和盘托出.自己的见识,未必总要让每一个人懂得.恭敬他人就是庄严自己,因为恭敬使人与人之间坚持间隔,不容易窥测弱点.没有一个人不被诽谤,被诽谤往往意味着开端成功.在争论中取胜是最愚蠢的做法,真正的雄辩不是使人下不了台,而是说出自己该说的足矣.无妒忌心者,闻所未闻.懂得隐藏起自己的精明,才是真正的精明.君主在臣平易近眼前要坚持自己的神秘感,不克不及让旁人知道自己的底细.勇敢地承受一切既成事实.要学会对他人说不,他人有求于你,是试探你的底线.真正的成功是珍惜自己的资源和才能的,知道有些人该帮,有些人不该去管.旁人对你的期待过高毫不是好事.他人对你好,一定是有求于你.永远不要为自己的激情所左右,要始终岑寂回避自己的缺陷.允许自己犯小错误,但尽可以不让他人知道.始终让上司分享自己的成功;始终让上司发现自己存在有待提高之处.真正的智慧来自于痛苦的失败,真正的教化只有通过交往来取得.胜利者无需诠释,失败者莫言苦处.君主不克不及拘泥于完美正直,言而有信,在自己的好处可以因信守承诺而受损时,应当毫不犹豫地放弃诺言.君主应该紧紧掌控施恩分惠的事务,而把不得人心的事情假手他人.君主在概况上应该装作具有美德,有需要得到人们某种程度上的信赖.君主不该该受道德准则的束缚,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应该使用各种需要的手段.忽视交往对象的缺陷才干高兴生活.真正的智慧者,不关心他人的过错,而在意他人对自己可以的威胁.被人畏惧总比被人亲爱更平安,见利忘义者触目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圆滑,决没有圆满.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世界观.别的,其他一些可作参考的:曾国藩有言,“能忍者自安,能待者自胜”,“忍”不须多言,“待”指等候时机或拖延.永远让上司拥有对你的优越感.永远与同级坚持一定间隔,即若即若离.永远不要炫耀自己的胡想和计划.盘算在精不在多,手段在狠不在杂.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但操纵他人的欲望.成功的人在概况看上去大多是与世无争的样子.自己的见解与多数人向左时,不要公开提,虽然不料味着不提.一个想要成功的人,第一门功课是学会自保.让上级放松心态,让下级永不知足.适当自嘲能缩短与交谈者的间隔.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忘记既往的过失.对上司要展示分歧寻常的坚实,对下级要暗示关心其好处.这外面很多东西您一定是承受不了的.若不认同,大可一笑了之.我本也不是让您学习“尔虞我诈”,只是希望有些内容能让你宽宽解.。
马基雅维利的孤独(校订版)首先,让我感谢法国政治科学学会和让·夏洛(JeanCharlot)给我的殊荣,感谢他们邀请我来进行这场交流。
并且,我也应该马上向诸位表达我在接受这个邀请时产生的头一重顾虑。
贵学会原本的兴趣在于当代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我却提出了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缺乏现实性的话题:马基雅维利。
另外,我的再一重顾虑是,诸位平时听讲的对象,不是众所周知的政治人物,就是历史学家,或者是政治科学家。
但我只是个哲学家,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想和诸位一起探讨我所说的马基雅维利的孤独这个话题。
告知诸位我仅仅是一个哲学家,这等于说,我会发现很多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但是,至少在我努力说清楚我想要提出的那么几个观点之后,我希望诸位能够原谅我这一点。
我希望,尽管我们在学养、专业能力和兴趣方面彼此不同,但交流却是可能的,我个人对于这场交流寄予厚望。
我知道依照贵学会的惯例,客串讲演者应该回答一些事先就已经传达给他的问题。
想必是由于我的主题缺乏现实性,也不那么中规中矩,所以就限制了我的对话者。
因为我只收到了三个问题。
其中一个来自皮埃尔·法弗尔(Pierre Favre),关于那些认识论的观念,我在一些已经很早的文章里就概括过了。
请他允许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一次私下的交谈,因为它太个人化了,同时也会让我离题太远。
第二个问题来自科莱特·伊斯谟尔(Colette Ysmal),关于葛兰西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评价:是的,我的确和葛兰西一样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讨论民族国家的理论家,因而也是一个讨论作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过渡状态的绝对君主制的理论家,但我相信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些非常例外的条件,这正是我待会儿要讨论的内容。
第三个问题来自于盖·波特利(Hugues Portelli),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是的,我的确认为有这么一层关系,但它看起来更像是巧合和重复,而不是有什么直系的血统。
我可能也正在讨论这一点。
承蒙诸位允许,所以我很乐意从我对自己选定的主题——马基雅维利的孤独——的一些思考谈起。
似乎不得不抗议,我们面对这样一位作者谈论孤独实属悖论,因为他总是在缠扰着历史,从十六世纪至今,毫无间歇,他不断地像魔鬼、像最玩世不恭的恶人那样被谴责,或者得到最伟大的政治家们的身体力行,或者因为他的大胆、他的思想的深刻而备受赞誉(例如在启蒙运动和意大利复兴运动当中,例如受到葛兰西的赞誉,等等)。
当我们看到他在历史上总是被一大群势同水火的反对者、支持者以及殷勤周到的评论家包围着的时候,又怎么可能提出要来谈论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呢?然而,只要我们注意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给每一个试图面对它的人所强加的那种分裂,那么谈论他的孤独就是可能的。
事实上,他把自己的读者完全分裂开来,变成支持者和反对者,而且,不管历史环境怎样变化,他都一如既往地把他们分裂开来——这说明,要把他分派到某个阵营里去,对他进行归类,说出他到底是谁以及他思考的到底是什么,都是多么的困难!他的孤独首先在于这样的事实:他似乎是不可归类的,他不可能归属某个阵营,去跟其他思想家为伍,也不可能归属某个传统,像其他作者那样要么归属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要么归属自然法学派的传统。
无疑,也就是因为这种不可归类性,才有如此不同的党派和如此伟大的作者,到头来既没有成功地给他定罪,也没有成功地把他接受下来,无一遗漏;好像在马基雅维利身上永远有某些东西是不可消化吸收的。
如果我们不去管他的死党,如果从我们现在的优势地位出发,想一想上个世纪里那些一直在钻研他的作品的评论家,我们就会从他们的惊奇里再次对这一真相有所发现。
我刚才说的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
现在我要说的是那些伟大的现代评论家,他们实际上各自都——以折射的方式——把一个特征当作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接受了下来,而这个特征正好可以解释马基雅维利在历史上引起的那些急剧的分裂。
他的思想的的确确有着一个古典思想体系的所有外表,它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对象,例如君主、不同种类的君主国、征服和保持君主国的方式,统治它们的方式。
有着一个古典思想体系的所有外表,也就是有着一个可认知、可认同、可以给人安全感的思想体系的所有外表,有着一个可以毫不含糊地加以理解的思想体系的所有外表,即便这个体系还留下了尚未解决的难题。
但是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发现了跟那些尚未解决的难题有所不同的东西——一个谜——而且恐怕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克罗齐去世前就曾说过,这个马基雅维利问题可能永远无法解决。
这个谜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它可以采取那个众所周知的二难困境的形式: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还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它可以采取那些更微妙的形式:他的思想怎么可能既明确无误的又难以捉摸的呢?为什么就像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在他的论文里精彩地论证过的那样,它是通过一些中断、离题和悬而未决的矛盾来展开的呢?一个思想体系貌似受到那样严格的控制,而实际上恰恰是它的表达方式既明明白白又闪烁其辞、既完整又不完整——这又怎么可能呢?所有这些令人困窘的争论都证实了一个看法,即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就产生于他的思想的非凡特性。
不光评论家,就连普通的读者也能证明这一点。
甚至在今天,任何一个翻开已有350 年历史的《君主论》或《论李维》文本的人,恐怕都会被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陌生的熟悉,那种Unheimlichkeit[令人害怕的东西]所触动。
我们搞不懂这是为什么,但我们感到这些古老的文本在对我们说话,仿佛它们就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它们吸引着我们,仿佛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早就为我们写好了,并且要告诉我们一些与我们直接有关的事情,尽管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德·桑克第斯在19世纪记录下了这种奇怪的感觉,他说马基雅维利“他让我们震惊,他使我们冥想”。
为什么有这种被占有的感觉?为什么这样震惊?为什么冥想?因为他的思想无视我们本人而不断进入我们的内心。
为什么冥想?因为这种思想只有打破我们思考的事情,让我们震惊,才能不断进入我们的内心。
这种思想无限地接近我们,但我们至今都从未与它会合,它用惊人的力量折服我们,让我们措手不及。
可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我们搞得措手不及呢?让我们措手不及的,并不是那种通常的发现,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现代政治科学奠基人的那种发现:例如,这位奠基人就像霍克海默所说的那样,用后来伽利略的那种方式看待政治,试图证实各种要素的变化组成了一种恒定不变的关系,因而用“事情就是这样”和“这就是规律”之类的实证模式来看待政治,认为这套模式支配着各国政府的统治。
不,不是诸如此类的发现让我们措手不及,因为只要这种发现进入我们的文化,并且在整个科学传统中自我繁殖,它在我们眼里就是熟悉的,决不会让我们惊奇,“让我们震惊”。
然而,马基雅维利本人自称是一种新的知识形式的发明者——所有伟大的政治探索者,就像维柯和孟德斯鸠所做的那样,都使用过这种方式。
但这种形式的知识恰恰和伽利略的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始终无人继承,被孤立在那个目睹了它的诞生并给了它生命的时代和个人的身上。
我在这里已触及到了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和非凡特性方面的一个决定性的要点。
但是在继续讨论这个要点之前,为了能够继续讨论下去,我很乐意证明,我们首先必需驱除这个马基雅维利之谜的古典形式。
这种古典形态可以陈述如下:马基雅维利在骨子里,到底是像《君主论》似乎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呢?还是像《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似乎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呢?这就是人们提出难题的一般方式。
可一旦这样提出难题,也就等于不证自明地接受了一种先在的政府分类,一种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府类型学,用以思考不同的政体以及它们的正常和反常状态。
但是马基雅维利恰恰拒绝接受或实践那样的类型学,他并没有要求用他的思考来规定任何特定的政府类型的本质。
他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
正如德·桑克第斯和追随他的葛兰西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个目标完全不在于制订民族国家的一般理论——在他的生活的时代,这样的民族国家就以绝对君主制的形式存在于法国和西班牙——而在于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在一个没有统一的国家,在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意大利,什么才是奠定民族国家基业的前提。
马基雅维利用彻底的、政治的提法提出他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看到,这个建立意大利民族国家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由任何现有的国家来完成的,不管是君主们统治的国家,还是共和国,还是教皇国,因为它们统统是旧东西,或者用现代的说法,统统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而不能自拔——甚至包括那些自由城市。
马基雅维利用彻底的提法,提出“只有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因为一个新君主在一个旧的君主国里不会有任何成就——因为他只能沦为这个旧世界的囚徒。
我相信关键就在于准确地把握这种拒绝的政治意义,把握马基雅维利给读者留下的这种不确定性。
显然,马基雅维利寻找他希望中的君主,但他从一个君主找到另一个,终于明白自己是找不到的。
那个任务的迫切要求,意大利在政治上的不幸,意大利人民的品质,以及四面八方高涨的呼声,这一切都使他确信:这样一位君主将会受到人民一致的欢迎;因此他用动情的语调表达了这种迫切要求。
切萨雷·博尔贾的奇遇已经向他证明了这一要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个人几乎已经成功地奠定了一个新的国家,而这正是因为他在起步的时候一无所有,因为他是没有国家的君主,所以他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旧的政治形式的囚徒,而封建主义和教皇就用这些形式掩盖着一个备受侵略者蹂躏的意大利。
迫切的要求使马基雅维利对那个政治任务和在意大利大量存在着的手段确信不疑,他同样确信,这个呼之欲出的新君主必将摆脱一切封建的束缚,能够白手起家地承担起这项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一般地谈论“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一般地、抽象地谈论,没有说出任何人物、任何地点的名称。
他用这种匿名性谴责了一切现有的君主、一切现有的国家,同时呼唤一个未知的人物来创制一个新的国家,说到底,就像切萨雷·博尔贾那样,从他的父亲教皇陛下给他用来找乐子的一个连国家也不是的一小片外省的地方开始,塑造他自己的国家。
如果有一个未知的人物就这样从无起步,并且如果幸运眷顾了他的“virtù”[能力],他就有可能成功,但条件是他必须奠定一个新的国家,一个能够长存的国家,一个能够成长壮大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不管使用征服还是什么别的手段能够统一整个意大利的国家。
照这样看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关于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君主主义者还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的问题就整个儿被取代了,并且可以从这些前提出发得以阐明。
为了奠定一个新的国家,马基雅维利说,这个人必须是“独自一人”;他必须独自一人缔造出任何政治都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独自一人颁布最初的法律,独自一人奠定“基业”并维护它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