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四个观念
- 格式:docx
- 大小:17.86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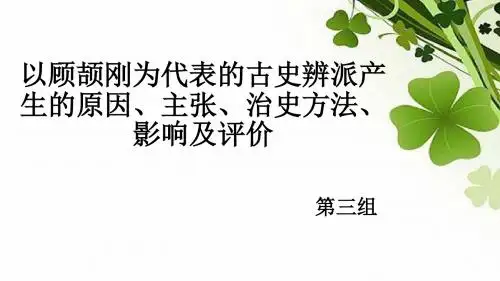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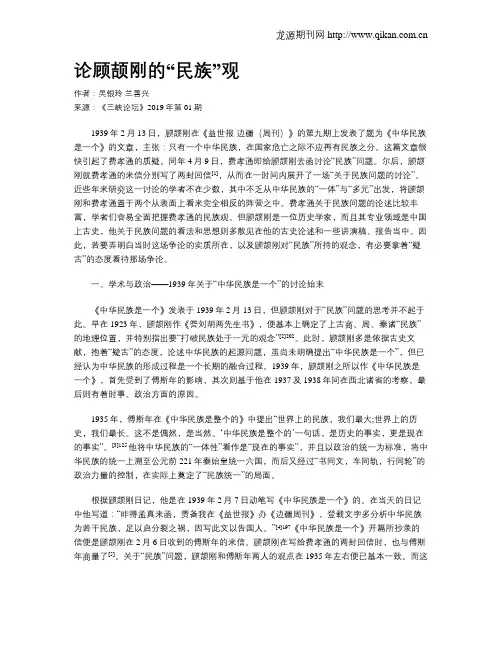
论顾颉刚的“民族”观作者:吴银玲兰善兴来源:《三峡论坛》2019年第01期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的第九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主张: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国家危亡之际不应再有民族之分。
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费孝通的质疑。
同年4月9日,费孝通即给顾颉刚去函讨论“民族”问题。
尔后,顾颉刚就费孝通的来信分别写了两封回信[1],从而在一时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
近些年来研究这一讨论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从中华民族的“一体”与“多元”出发,将顾颉刚和费孝通置于两个从表面上看来完全相反的阵营之中。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比较丰富,学者们容易全面把握费孝通的民族观。
但顾颉刚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其专业领域是中国上古史,他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和思想则多散见在他的古史论述和一些讲演稿、报告当中。
因此,若要弄明白当时这场争论的实质所在,以及顾颉刚对“民族”所持的观念,有必要拿着“疑古”的态度看待那场争论。
一、学术与政治——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始末《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1939年2月13日,但顾颉刚对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并不起于此。
早在1923年,顾颉刚作《答刘胡两先生书》,便基本上确定了上古商、周、秦诸“民族”的地理位置,并特别指出要“打破民族处于一元的观念”[2]202。
此时,顾颉刚多是依据古史文献,抱着“疑古”的态度,论述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虽尚未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但已经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融合过程。
1939年,顾颉刚之所以作《中华民族是一个》,首先受到了傅斯年的影响,其次则基于他在1937及1938年间在西北诸省的考察,最后则有着时事、政治方面的原因。
1935年,傅斯年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提出“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
这不是偶然,是当然。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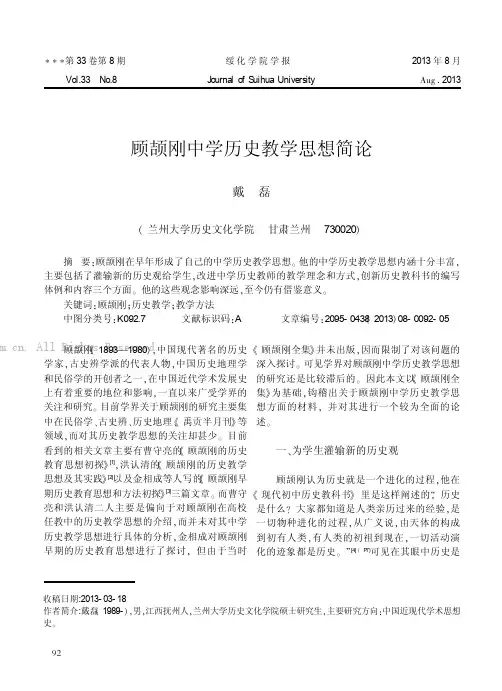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3-03-18作者简介:戴磊(1989-),男,江西抚州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
戴磊顾颉刚中学历史教学思想简论摘要:顾颉刚在早年形成了自己的中学历史教学思想。
他的中学历史教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了灌输新的历史观给学生,改进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创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内容三个方面。
他的这些观念影响深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顾颉刚;历史教学;教学方法中图分类号:K09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3)08-0092-05(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20)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一直以来广受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顾颉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俗学、古史辨、历史地理、《禹贡半月刊》等领域,而对其历史教学思想的关注却甚少。
目前看到的相关文章主要有曹守亮的《顾颉刚的历史教育思想初探》[1],洪认清的《顾颉刚的历史教学思想及其实践》[2]以及金相成等人写的《顾颉刚早期历史教育思想和方法初探》[3]三篇文章。
而曹守亮和洪认清二人主要是偏向于对顾颉刚在高校任教中的历史教学思想的介绍,而并未对其中学历史教学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金相成对顾颉刚早期的历史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当时《顾颉刚全集》并未出版,因而限制了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
可见学界对顾颉刚中学历史教学思想的研究还是比较滞后的。
因此本文以《顾颉刚全集》为基础,钩稽出关于顾颉刚中学历史教学思想方面的材料,并对其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为学生灌输新的历史观顾颉刚认为历史就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他在《现代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是这样阐述的,“历史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人类亲历过来的经验,是一切物种进化的过程,从广义说,由天体的构成到初有人类,有人类的初祖到现在,一切活动演化的迹象都是历史。

顾颉刚的民族观与民族自信摘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既不是一开始就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他在继承中国传统“华夷一统”观的基础上,立足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将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民族概念及其民族观进行了比较合理的阐释。
其民族观之所以对其后的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和走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所运用的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民族观所体现出来的那份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心。
关键词:顾颉刚;民族观;民族自信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不仅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而且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当时的史学界围绕中华民族概念及民族观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
在这场讨论中,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直到今天,有关中华民族形成方面的论著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个问题。
如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郝时远《关于构建中华民族的几点思考》,马戎、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等。
本文在分析顾颉刚民族观历史渊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民族观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做一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并揭示其民族观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力。
这对新的时期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顾颉刚民族观的历史渊源顾颉刚对其民族观的阐述并非侧重概念的分析和各种理论的列举、对比和解读,而是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将民族问题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
并力图从史实中寻求依据,尤其注意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追根究底,其民族观与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一统”观念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顾颉刚在论述种族概念时,先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指出“夏、商、周不是三个朝代而是三个种族”,因为春秋时期,黄河下游的人自称为“诸夏”,而瞧不起四围的人民,称他们为“蛮、夷、戎、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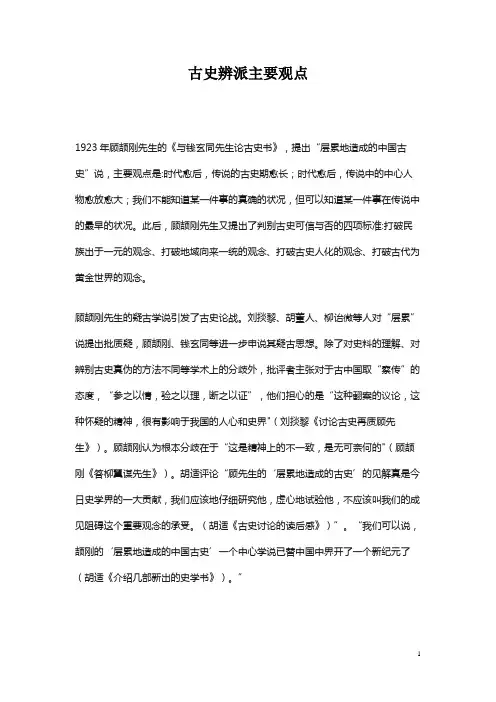
古史辨派主要观点1923年顾颉刚先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要观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此后,顾颉刚先生又提出了判别古史可信与否的四项标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引发了古史论战。
刘掞黎、胡董人、柳诒微等人对“层累”说提出批质疑,顾颉刚、钱玄同等进一步申说其疑古思想。
除了对史料的理解、对辨别古史真伪的方法不同等学术上的分歧外,批评者主张对于古中国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他们担心的是“这种翻案的议论,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刘掞黎《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
顾颉刚认为根本分歧在于“这是精神上的不一致,是无可奈何的"(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胡适评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中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1顾颉刚疑古学说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斩除思想的荆棘,指出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信,打破了长期以来被奉若经典而不可触动的圣贤之言,为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开辟了道路;促使中国史学走出旧学的案白,迈出了以史学独立、史学“求真”为宗旨的近代史学学科建设的实重在在的一步。
1926年6月,汇集了讨论古史的信件与文章的《古史辨》第一册由朴社出版。
一年重印了二十次,疑古学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至1941年,共出版七册,收入各类文章350余篇,300多万字。
在《古史辨》系列中支持、赞同并声援是古学说的学者被称为“古史辨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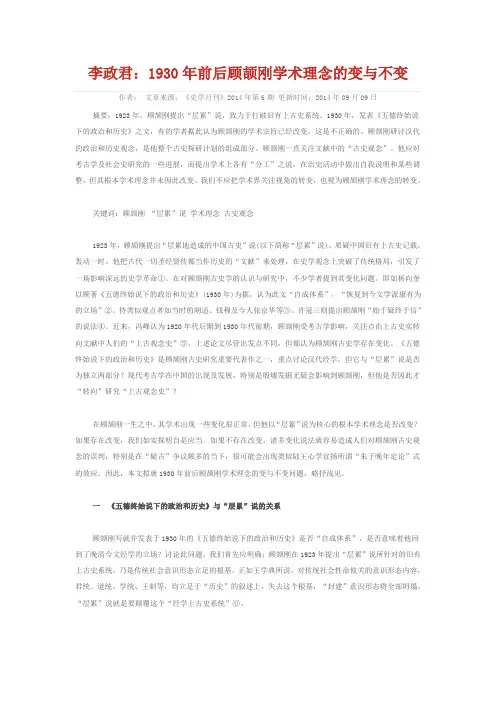
李政君: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作者: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更新时间:2014年09月09日摘要: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
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
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
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
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
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关键词:顾颉刚“层累”说学术理念古史观念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下简称“层累”说),质疑中国旧有上古史记载,轰动一时。
他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在史学观念上突破了传统格局,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①。
在对顾颉刚古史学的认识与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到其变化问题。
即如杨向奎以顾著《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为据,认为此文“自成体系”,“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②。
持类似观点者如当时的胡适、钱穆及今人张京华等③。
许冠三则提出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的说法④。
近来,冯峰认为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前期,顾颉刚受考古学影响,关注点由上古史实转向文献中人们的“上古观念史”⑤。
上述论文尽管出发点不同,但都认为顾颉刚古史学存在变化。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顾颉刚古史研究重要代表作之一,重点讨论汉代经学。
但它与“层累”说是否为独立两部分?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及发展,特别是殷墟发掘无疑会影响到顾颉刚,但他是否因此才“转向”研究“上古观念史”?在顾颉刚一生之中,其学术出现一些变化很正常,但他以“层累”说为核心的根本学术理念是否改变?如果存在改变,我们如实探明自是应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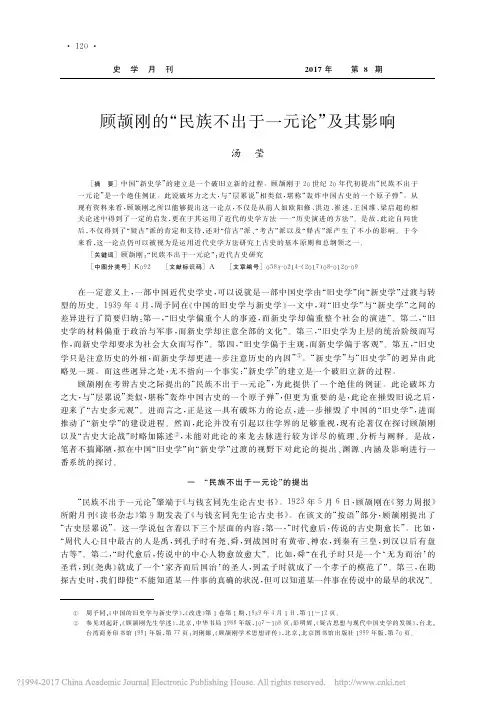
顾颉刚(1893—1980年),“古史辨”派的领袖,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
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读书世家,天资聪慧,素有悟性,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16岁时他正在读中学二年级,祖父又给他讲授《礼记》、《周易》、《尚书》等,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古史的知识基础。
在中学时代,顾颉刚就养成了喜欢买书的好习惯,常常把家里给的零钱节省下来到书市去买书,久而久之,对书籍的版本、目录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反复翻熟了《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的目录书,了解了中国历史典籍的有关知识。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来转读哲学门。
入学后由于毛子水同学的影响,参加章太炎主讲的“国学会”,聆听了太炎先生的国学系统讲演,深受启发,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所走的治学道路。
对顾颉刚批判传说古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
从《孔子改制考》中使顾颉刚知道了很多古史材料是靠不住的,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认为这时的传说史料不可靠。
受到这些启发,使大学时代的顾颉刚萌生了用个人的力量去“整理国学”的“野心”。
1920年毕业被留校做助教,从此踏上了潜心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道路。
由于他的学术志趣,对富于批判精神的郑樵和崔述的学术深感兴趣,于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也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志,先后撰著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清代著术考》,标点校定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标点补辑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
这些工作为顾颉刚后来的考辨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为他启发了思路、增加了智慧。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对中国的传说古史进行怀疑,认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
试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首发)黄海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史学家,贯通经史,著述等身,学术思想包罗宏富,在诸多学术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①顾颉刚史学思想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来的学术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古史辨派”主要代表的顾颉刚,其古史学观点与思想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下产生,继承传统,融会创新,从已是危机重重的传统学术研究中脱颖而出,开创了古史研究领域内的史学革命。
顾颉刚的古史学说在解放前有两个主要的课题:前期古史学说的重心是“古史层累说”;后期古史学说的重心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
“古史层累说”是顾颉刚古史学说中最先提出,是主要核心与灵魂,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体系。
就具体的古史研究而言,顾颉刚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提出了“古史层累说”,这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说这是在“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支配下的方法论体系。
在顾颉刚具体的古史研究中,无论他运用何种具体的史学方法,实际上都是从“古史层累说”演化出来的,或者说某一种具体的方法都是“古史层累说”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为其“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所服务的。
他所提出的“古史层累说”估定了传统经学的价值,开创了新的古史研究方法,成为二十世纪古史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范式之一,其余响至今仍在古史学界内回荡。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发展与成熟,地下出土材料的纷纷涌现,使过去被认为是伪书的古籍得以重新认识,过去模糊的古史认识也日益清晰,自宋代以来的疑古思想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长期致力于出土文献和传统文献的相互证明,以求对上古史再认识的一部分学者们纷纷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等口号。
②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搜集和考辨史料,这样的工作在任何时代的历史研究中都必不可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疑古时代”又是走不出去的。
③这样不可避免地在围绕如何看待“古史辨”与顾颉刚古史学说的学①顾颉刚作为一位博通的学者,不仅在历史学方面涉猎极广,横跨上古史、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等领域,同时他还对戏曲、歌谣和民俗学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在这些方面,他都有极为丰富的著述。
顾颉刚顾颉刚顾颉刚(1893~1980)中国历史学家。
原名诵坤,字铭坚。
笔名有无悔、天游、张久、诚吾、桂姜园、余毅、劳育、康尔典、周、武兴国等。
江苏苏州人。
1893年5月8日(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生于一个书香世家。
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1913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考入本科中国哲学门,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
1922年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伯祥)合编《新学制本国史教科书》,与叶圣陶合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1924年回北京大学,任研究所门助教,先后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1926年以后,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
他的“传”、“纪”不可信的思想来自崔述,“经”不可尽信的思想来自姚际恒,治学要融会贯通的思想来自郑樵。
他用历史进化论的寻求事物演变线索的治学方法学自,对今、古文家的看法则受之于钱玄同。
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他深刻的影响,王氏所考出的真古史被用以破坏伪古史。
1909年,他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
1915年始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计约二百册,四百余万字。
1916年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册,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有了全面了解。
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
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
以后,将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八册。
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上所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
《古史辨自序》读书报告顾颉刚先生(1893~1980)江苏省苏州人,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古史辨派的创始人。
这个学派以他编著的《古史辨》而闻名于世。
顾先生因考辨古史,对古代神话,民俗学,古典文学和歌谣也作了不少研究,并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现代神话学,民俗学,古典文学和民间文艺研究等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卓越奠基人之一。
而顾先生最重大的贡献乃是在考辨古史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二,揭示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层累地形成的。
三,打破民族出于一元与地域向来一统的传统说法。
四,考订古书著作时代为研究古史传说的演变打好基础。
而从这本《古史辨自序》中我们有幸一睹这些古史辨运动的珍贵遗产的光辉。
《古史辨自序》的前40页,作者用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坦诚了自己如何走上古史辨伪的心路历程。
用书中作者自己总结的辨伪思想的由来来说,是时势,个性与境遇使然。
那我们即从这三点入手来分析古史辨伪思想形成的过程。
先谈顾颉刚先生那桀骜不驯的个性。
正如他的儿子顾潮在《我的父亲顾颉刚》中所写,这位史学大师“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于他人的话”。
(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29页)正是源于骨子中的桀骜,顾颉刚绝不盲从于他人其中包括自己的老师。
虽然对于章太炎,康有为,胡适之等恩师们怀有极大的尊重,但他们的个人理论完全不能束缚顾颉刚这颗“自由的心”,更妄论将其同化,成为他们的忠实鼓手。
而当发现恩师的思想漏洞时,即使再敬佩,他也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真理,这便是一个治学者应具备的素质。
正是有了这种素质,顾颉刚才能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中起到先锋与旗手的作用。
再论时势。
无疑古史辨是时代的产物。
若无当时时代大潮的推动作用,古史辨便不会一出世便石破天惊,更不至一举颠覆中国社会史观体系。
可以说顾先生也是随了大潮的。
首先,古史辨运动的“疑古特性”,并非古史辨派的首创,而是当时的社会在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中所涌现对于传统的批判思潮的一个分支。
顾颉刚的“天圆地方”作者:史乐翔来源:《前线》2013年第03期顾颉刚,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学识渊博,在学术上颇有建树。
他曾将自己的治学经验归纳为四个字:“天圆地方”。
“天圆地方”,本是古代一种天体观。
古人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认为天似华盖,形圆;地如棋盘,形方。
故曰“天圆地方”。
顾大师巧借此语,将其赋予新的内涵,用以总结自己的治学之道,别具匠心,颇有见地。
他所说的“天”,系指人之朝天的脑袋;他所说的“地”,系指人之接地的臀部。
二者彼此制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记得另有名家也说过类似的话:比如,治学“脑袋要动,屁股要定”。
再比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这些名言,比之于顾颉刚的治学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顾颉刚在这里所说的“天圆”,就是求知识做学问,要脑袋“圆通”,勤于思索,学思合一。
正可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所谓“地方”,就是治学时,臀部要“方正”,坐得稳,坐得牢,像木板钉钉子一样,坚定不移。
治学者一旦做到臀稳坐、心平静、俯而学、仰而思,定会事半功倍,学有造诣。
应该说,“天圆”和“地方”不单是文人做学问的必须,也是党员干部干事业不可或缺的条件。
舍此,既不动脑思索,又不认真做事,党员干部只能一事无成。
对党员干部来说,所谓“天圆”,就是要开动脑筋,善于思考。
决不可思想惰怠,无所用心;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真假不辨,美丑不分。
就是要创新思维,更新观念。
切忌因循守旧,思想僵化,习惯于“穿旧鞋,走旧路”,抑或“穿新鞋,走老路”。
就是要深思熟虑,谋划方略。
制定政策、规定,当以审慎的态度,“三思而定”,力戒随意盲动,朝令夕改。
而所谓“地方”,就是要“坐得住”。
坐得住,才会静下心。
“心静则生慧,心静则觉悟”,正如诸葛亮《诫子书》中言:“非宁静无以致远。
”宁静乃一种境界。
一个人静了心,头脑才清醒,才会思考,才蓄势待发,才能站得高,看得远。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保持内心的宁静,最重要的一点:减少欲望。
顾颉刚四个观念:眼光向下的角度,反观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顾先生疑古的思想之下层累地构造中国古史的方法,是顾先生对民俗学兴趣的体现。
顾先生对家乡江苏当地的歌谣很感兴趣,在编歌谣的过程中,顾先生发现孟姜女的故事在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各地流传的孟姜女的故事并不相同,其间存在“空间差异”,这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之后发展出历史地理的兴趣,顾先生试图从历史学家时间的角度去解决空间的问题,这一点对赵世瑜的影响非常大,反之,如何从空间的问题去解释时间的变化,各地的孟姜女故事的形成看似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产生,译文不同体现出地域性差异,但实际上是各地在不同的时间点添加的故事情节内容。
顾先生找到孟姜女故事的最早起源在《左传》,一开始是齐王之妻,并不是孟姜女,把齐王妻的故事和长城联系起来是在汉代,正式改名为孟姜女是在唐代《孟姜女辩文》,孟姜女丈夫的名称在各个故事的版本中有很多,但都是齐王名字“范喜良”的进称,由此产生层累史观,把空间故事的差异找到时间点相连。
例如,以早期山西历史来说,山西是早期华夏民族的发展核心,但是该地在早期并不是农耕文明,当地有很多戎狄,可以确定这些人当时处于半农半牧的状态,并不是完全的农耕状态,山西南部的霍山,是历史上五镇中的中镇,是当时天下的统治中心,根据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戎狄少数民族是众数。
春秋战国之际三家分晋时,赵国在赵简子时代开始营建山西晋阳,到其子时代晋阳建立完全,到这时统治中心才开始向中心移动,这时西部的匈奴也在向东扩展,战国时齐桓公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打击混合在中原之中的少数民族族群,这是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逐渐扩展统治区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普遍发生的,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落后的,直至北方人群进入南方开发江南地区,这样的情况才在唐宋发生,例如赣南宋代时出现很多“贼”、“盗”、“寇”等词汇,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贼寇,只是有很多新的人来到此地开发,这些没有被官府编入户籍管理系统内的人都被称为“贼”、“盗”、“寇”,恰好在南宋偏安一隅的时代,洞庭湖一代处于新的大开发时代,湖南地方蛮的征剿的活动较多,在湖边开垦、打渔并不被政府允许,所以对岳飞?江西、湖南保留下来的族谱非常多,白光越喜欢收藏族谱,看族谱可以发现他们都在追溯宋元时代,同样在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出现族谱,在清初也有出现。
在各个地区出现的事件,可以建立一个时间的序列,这也就是顾先生对社会史的贡献。
所以在这样一种大的范围之下,有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关注,王国维、陶希圣(食货派创始人,关注经济史的重要人物)有汉代游侠研究等、吴晗开始在食货杂志发表文章,都是眼光向下的观察,关注下层的观念;与此相关这时还出现了明显的多学科的合作,例如顾先生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同时关注地理学,还做了许多社会调查,还有许多人类学家也借用了历史学的方法,这些都是眼光向下的史学观察,如费孝通先生与吴晗先生合作的《皇权与绅权》,潘光旦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苏松杭嘉湖是当时太湖地区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利用族谱等资料进行研究,还有林耀华(邓小南老师的公公——林宗成)的金翼,是关于一个镇子的故事,整个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他在燕大时作的硕士论文,就是30年代初,《义序的宗族》是很典型的中国学者所作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烈的历史感。
文学家郑振铎特别喜欢搜集真品的文献资料,也是一个眼光向下的学者,中国俗文学讲了很多民间俗史,其《汤祷篇》讲“起于桑林”中的“桑林”实际上是商人(汤)的“社”,成汤要用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东西代表生身献祭于神,实际上讲的是商人的一种信仰,所以说礼制传统是可以贯穿解释中国历史问题的线索。
与干将莫邪铸剑暗喻铸造业的人在关键时刻对铸造之神的献祭仪式,是要牺牲的祭身具有相同的寓意。
江绍泉的《发须爪》等都是这类的研究。
与多学科的合作并列还有一个特点,人们在社会学的角度下重新理解传统史学,比如制度史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点,考据学研究的新旧之别,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企图把胡三省隐藏在注释中的思想发掘出来,进而展示胡三省思想史,从制度史过渡到思想史、心态史;再比如陈寅恪先生,做的是不古不新的历史,希望史家应该具有一种神游冥想的特点,还原到与古人同样的情境之中,认为过去的历史都
是用经学的办法而不是史学的办法来解释历史,考实很重要考意更重要,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借助于文学形式来实现的,通过文学作品来参看过去的制度演变等,所以他们所作的东西都是以小见大,以全新的东西来反观制度史的东西,我们的重点是参考研究思路,所以说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所作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导,他们的共性是都在试图摆脱传统、旧的史学研究的框架之下研究,力图求变。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样的一种观念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入中国的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有冲突,经常受到排挤,费孝通提倡多元一体的发展观念;打破地域向外扩展的观念,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王明珂先生的研究英雄祖先和兄弟传说,在中国除了中原王朝核心地域之外,还有其他地域的发展;打破上古时代人化的观念,人化即把古史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变成历史上的真人,《尚书·尧典》是最早的人化的体现,宋明两朝乐于塑造上古圣王,言必称三代,夏商周确立的规范是一定要遵守的,出现这种观念的基础是认为过去的都是好的,顾颉刚先生的观念对于后世社会史的研究都是好的,从具体的批判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过去传统的方面的漏洞。
五岳、五镇、四海、四湖
四、政治史范式下的社会史研究:20世纪50-80年代
和民国早期的研究有区别,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在20世纪上半叶由社会史大论战还在延续
社会发展史
“五朵金花”与社会史研究: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古史分期问题(最热烈,实际上是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是当年的社会史大论战问题的延续)、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个大问题,总体来讲侧重于后面。
涉及到多种学科
奴变运动与清军入关以后江南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想研究》
社会史是什么?
概念诸说:冯尔康、乔志强的历史学分支说,认为社会史是史学中的专门学科;陈旭麓、张静如的通史说;张研等得综合史说,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变迁的综合,不同于第二种说法,这三个概念是社会学的概念,并不是史学中的概念,类似于国际中的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认为社会史是史学的分支学科,但不是同老一辈的简单的研究社会生活、社会下层人们的生活的学科;杨念群的中层理论说,《中层理论》,所谓中层理论并不是单纯的针对社会史阐发的,但是可以以此为视角来看社会史,是说过去在历史学界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常常提出一些宏大理论,但是这样的理论不利于社会学的指导,把所有的历史学实践纳入到历史学的框架中进行阐释无疑都是失败的,虽然有一种结论出来,但是并不能容纳历史的多样性,在过去历史的解释确实通常是这样一种做法,或者完全回避理论的问题,只重视考证完全不对历史进行解释,“研究平台”体现为一种不大不小的具体的理论概括模式,大家都可以在这样的理论平台上进行研究、交流,这样的理论属于一种中层的理论,例如研究现代化,不论是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亦或是经济学家都可以就此问题在现代化这个平台上进行讨论,实际上这样的一种理论也是舶来品,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其中学者默顿提出理论后经过人们的发挥“range”,但是并不是适用于四海,很多种理论的使用范围都是有限的、适度的,在赵世瑜看来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可操作性理论,要把社会史的概念放到一种中层理论上来理解,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社会史是关于穷人、关于下层人的历史;社会史
是关于社会生活、关于民族的历史;社会史是社会经济史。
为什么社会经济史在中国社会没有提出来呢?因为社会经济史是比较大的研究主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比较有成就的一块,因此不能将社会经济史从中剥离出来。
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的历史,马克思工作与闲暇。
社会史与整体史:无法狭义的社会史;政体研究的社会史;整体研究并不排斥微观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的政体的历史,所谓特定的社会就是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民族;社会史是关于生活体验的历史,法国回忆录
社会史与跨学科研究:
方法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