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
- 格式:doc
- 大小:47.50 KB
- 文档页数:6

“以形写神”与“以神写形”——简析中国传统绘画中形与神的关系摘要:关键词:“以形写神”与“以神写形”——简析中国传统绘画中形与神的关系方澄广州市马尊视觉艺术有限公司广东广州510250长久以来,形神兼备一直是中国传统绘画审美的理想追求。
历代画论都会把形神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加以阐释,但对于形神的阐释,各家又互有出入,互有对立。
它们孰先孰后,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看法。
一.何谓“形”?何谓“神”?平日里,我们常会听到“形神兼备”才能称之为一幅好画的说法,但是什么是形什么是神我们又是否知道呢?直接的从字面上理解:形即形状,神即精神。
它们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两大元素,一个是揭示事物的外延的,一个是揭示事物内涵的,一个外在一个内在,两者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形无神,则为木偶,陷于自然主义;有神无形,则为虚幻,容易脱离现实,形成唯心主义。
形是神的基础,神亦是形的统率。
形神兼备,才能成为一幅好画。
在我国古典画论中,“形”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韩非子论画》中:“客有为齐王画者?’曰:‘犬马难。
孰易者?’曰:‘鬼魅最易。
’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磬于前,不可类之,故难。
鬼魅,无形者,不磬与前,故易之也。
”犬马是有形的东西,我们早晚都能看见,不容易画像;鬼魅是无形的,比较容易画,因为没人见过就不用管像不像。
由此,我们可知,形是指画中客观事物的外在视觉现象,形是对象的外部形态特征。
神,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尽相同的内涵,但概括来说神有三方面涵义——画家自身的精神,所画对象的精神,画上表现出来的精神。
石鲁先生的《学画录·造型章》中曾这么阐释“神”的内涵:他认为“画贵全神,而神有我神他神,入他神者我化为物,入我神者物化为我,然合二为一则全矣。
”这里说的“我神”就是画家自身的精神,“他神”就是对象的精神,我神、他神的合二为一就是绘画表现出来的精神。
总的来说,形是相对事物外部而言的,是对象的外部形态特征;神则是相对事物内部而言,是指精神、气质、品德等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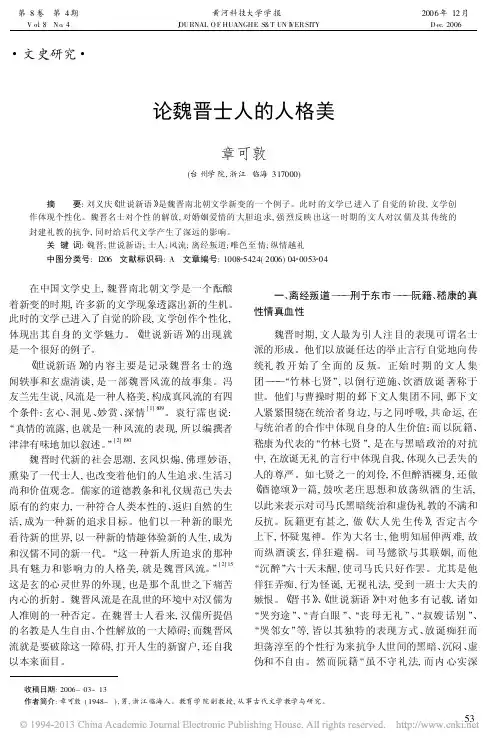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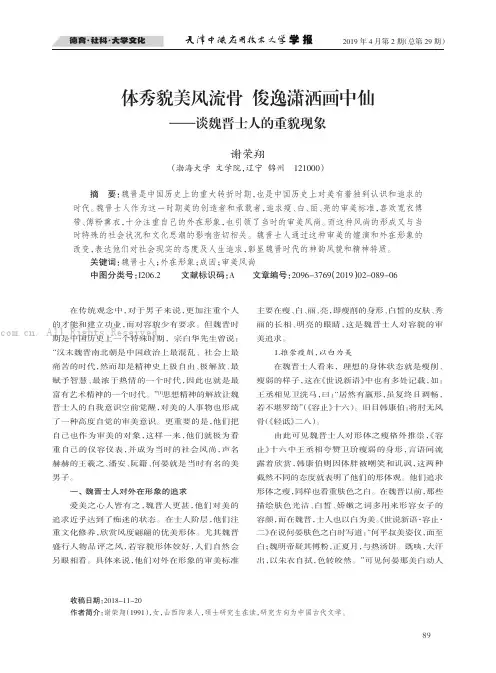
收稿日期:2018-11-20作者简介:谢荣翔(1991),女,山西阳泉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体秀貌美风流骨俊逸潇洒画中仙———谈魏晋士人的重貌现象谢荣翔(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00)摘要: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对美有着独到认识和追求的时代。
魏晋士人作为这一时期美的创造者和承载者,追求瘦、白、丽、亮的审美标准,喜欢宽衣博带、傅粉熏衣,十分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也引领了当时的审美风尚。
而这种风尚的形成又与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
魏晋士人通过这种审美的嬗演和外在形象的改变,表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及人生追求,彰显魏晋时代的神韵风貌和精神特质。
关键词:魏晋士人;外在形象;成因;审美风尚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19)02-089-06在传统观念中,对于男子来说,更加注重个人的才能和建立功业,而对容貌少有要求。
但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宗白华先生曾说:“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赋予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1]思想精神的解放让魏晋士人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对美的人事物也形成了一种高度自觉的审美意识。
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也作为审美的对象,这样一来,他们就极为看重自己的仪容仪表,并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声名赫赫的王羲之、潘安、阮籍、何晏就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
一、魏晋士人对外在形象的追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魏晋人更甚,他们对美的追求近乎达到了痴迷的状态。
在士人阶层,他们注重文化修养,欣赏风度翩翩的优美形体。
尤其魏晋盛行人物品评之风,若容貌形体姣好,人们自然会另眼相看。
具体来说,他们对外在形象的审美标准主要在瘦、白、丽、亮,即瘦削的身形、白皙的皮肤、秀丽的长相、明亮的眼睛,这是魏晋士人对容貌的审美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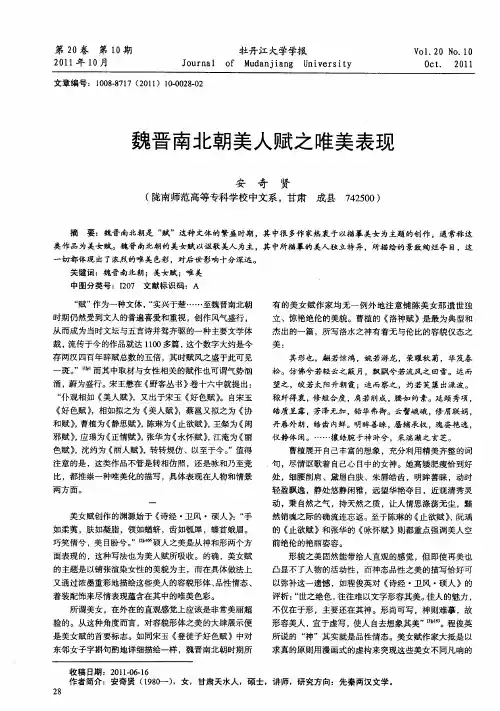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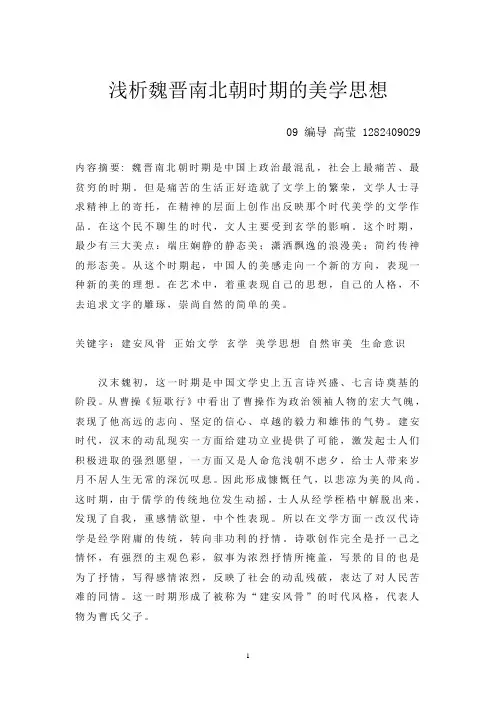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思想09 编导高莹 1282409029内容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上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最贫穷的时期。
但是痛苦的生活正好造就了文学上的繁荣,文学人士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在精神的层面上创作出反映那个时代美学的文学作品。
在这个民不聊生的时代,文人主要受到玄学的影响。
这个时期,最少有三大美点:端庄娴静的静态美;潇洒飘逸的浪漫美;简约传神的形态美。
从这个时期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表现一种新的美的理想。
在艺术中,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不去追求文字的雕琢,崇尚自然的简单的美。
关键字:建安风骨正始文学玄学美学思想自然审美生命意识汉末魏初,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奠基的阶段。
从曹操《短歌行》中看出了曹操作为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向、坚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
建安时代,汉末的动乱现实一方面给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激发起士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
因此形成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的风尚。
这时期,由于儒学的传统地位发生动摇,士人从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重感情欲望,中个性表现。
所以在文学方面一改汉代诗学是经学附庸的传统,转向非功利的抒情。
诗歌创作完全是抒一己之情怀,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叙事为浓烈抒情所掩盖,写景的目的也是为了抒情,写得感情浓烈,反映了社会的动乱残破,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这一时期形成了被称为“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代表人物为曹氏父子。
建安时期诗歌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正始之音。
此时玄风非常的畅行,诗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比建安有了重大的变化,诗歌创作的面貌也不大相同。
建安诗人在悲歌慷慨的抒情中得到满足,而正始士人则在玄思妙想中领悟人生。
玄学的基础是老庄思想,因而正始诗人在追求自然,心与道冥的同时,把老庄的人生理想自然而然地带入到诗中来,有的在诗中创造一个庄子逍遥游式的理想境界,诗人可以徜徉其中,作为解脱现实苦闷的精神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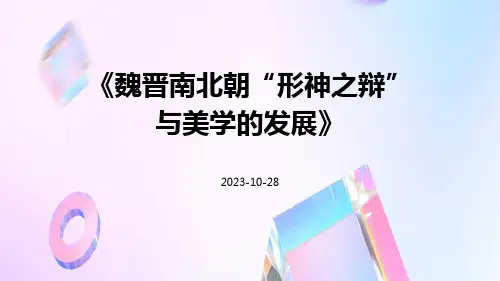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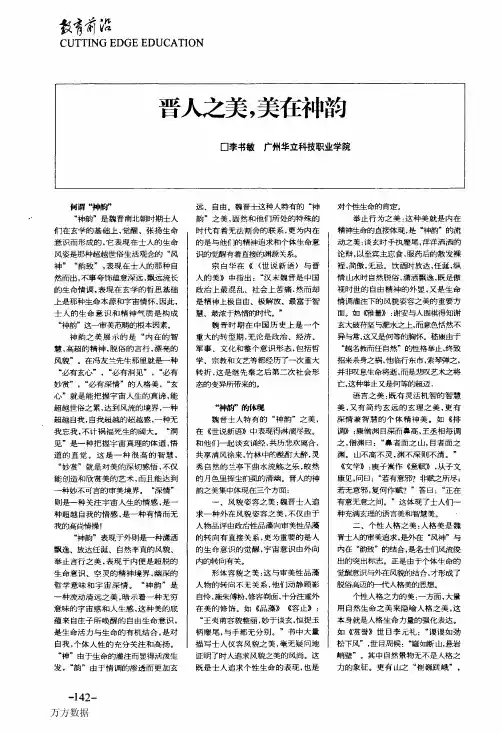
极奄前滗C U T T I N G ED GE E D U C A T I O N何渭‘喇}韵”远、自由。
魏晋士这种人特有的“神对个性生命的肯定。
“神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韵”之美,固然和他们所处的特殊的举止行为之美:这种美就是内在们在玄学的基础上,觉醒、张扬生命时代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更为内在精神生命的直接体现,是“神韵”的流意识而形成的,它表现在士人的生命的是与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个体生命意动之美:谈玄时手执麈尾,洋洋洒洒的风姿是那种超越世俗生活观念的“风识的觉醒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论辩,以至宾主忘食,服药后的散发裸神”“韵致”,表现在士人的那种自宗白华在((<世说新语>与晋裎,简傲,无忌。
饮酒时放达,任涎,纵然而出,不事夸饰蕴意深远,飘远流长人的美》中指出:“汉末魏晋是中国情山水时自然脱俗,潇洒飘逸,既是傲的生命情调,表现在玄学的哲思基础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苦痛,然而却视时世的自由精神的外显,又是生命上是那种生命本源和宇宙情怀,因此,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情调灌注下的风貌姿容之美的重要方士人的生命意识和精神气质是构成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
”面。
如(伢巨量》:谢安与入围棋得知谢“神韵”这一审美范畴的根本因素。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玄大破苻坚与淝水之匕,而意色恬然不神韵之美展示的是“内在的智重大的转型期,无论是政治、经济、异与常,这又是何等的胸怀。
嵇康由于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性格举止,终致风貌”。
在冯友兰先生那里就是一种学、宗教和文艺等都经历了一次重大招来杀身之祸,他临行东市,索琴弹之,“必有玄心”,“必有洞见”,“妊有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并非叹息生命将逝,而是悲叹艺术之将妙赏”,“必有深情”的人格美,“玄态的变异所带来的。
亡,这种举止又是何等的超迈.心”就是能把握宇宙人生的真谛,能语言之美:既有灵活机智的智慧超越世俗之累,达到风流的境界,一种‘‘神韵”的体现美,又有简约玄远的玄理之美,更有超越自我,自我超越的超越感,一种无魏晋士人特有的“神韵”之美,深情兼智慧的个体精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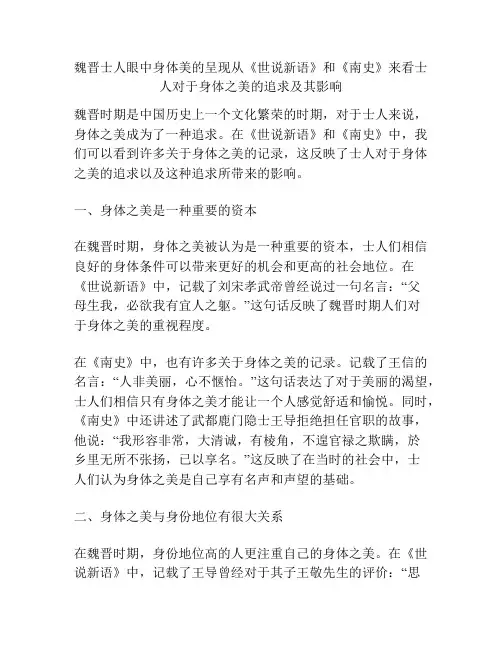
魏晋士人眼中身体美的呈现从《世说新语》和《南史》来看士人对于身体之美的追求及其影响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对于士人来说,身体之美成为了一种追求。
在《世说新语》和《南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身体之美的记录,这反映了士人对于身体之美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所带来的影响。
一、身体之美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在魏晋时期,身体之美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士人们相信良好的身体条件可以带来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刘宋孝武帝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父母生我,必欲我有宜人之躯。
”这句话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身体之美的重视程度。
在《南史》中,也有许多关于身体之美的记录。
记载了王信的名言:“人非美丽,心不惬怡。
”这句话表达了对于美丽的渴望,士人们相信只有身体之美才能让一个人感觉舒适和愉悦。
同时,《南史》中还讲述了武都鹿门隐士王导拒绝担任官职的故事,他说:“我形容非常,大清诚,有棱角,不遑官禄之欺瞒,於乡里无所不张扬,已以享名。
”这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中,士人们认为身体之美是自己享有名声和声望的基础。
二、身体之美与身份地位有很大关系在魏晋时期,身份地位高的人更注重自己的身体之美。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王导曾经对于其子王敬先生的评价:“思客自乡里之味高矣,王敬先生举止本卓,容貌加美,与上交好,意得唐人之贵。
”这个故事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中,身份高的人更注重自己的形象。
《南史》中也记录了司马昭的说法:“若为平民之子,那些好古不却要顾及下降。
然我辈点水晦迹,取之不得,不早为之,后期不足赛。
”这段话反映了身份地位高的人更注重自己的身体之美,并且他们难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所以需要靠自己的外貌和修养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三、身体之美与修养有很大关系在魏晋时期,身体之美也被认为是修养的一种体现,士人们认为通过仪态举止和言谈举止来体现出自己的身体之美。
《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事讲述了刘琨向殷仲堪学习仪态的经历,这个故事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中,良好的仪态举止被认为是身体之美的表现。
![第六讲 魏晋风度与优美的生命姿态 (2)[29页]](https://uimg.taocdn.com/ac1d77e3ee06eff9aff807aa.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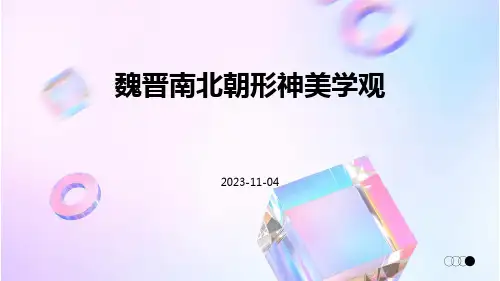
魏晋阮籍、嵇康及阮咸的人格美所谓人格美,则"意味着从地上、世俗的东西和一切束缚、烦累中,从变化不定的、有限的生的不安和动摇中脱却,生活于超现世的无限平安和静寂中的自我觉悟。
";[1] 也意味着人的道德人格的完善和人与天地宇宙同一的最高人格境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美主要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即儒家偏重社会人伦价值或道德政治的伦理之美,道家偏重个体自由理想或精神超越的自由之美,以及中国化佛教如禅宗偏重于高峰体验、万古长空的空灵之美。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哲学所追求的诸种人生境界,实际上是一种美的人格或人格美的境界,它说明在传统哲学中,美和人格是不可分割的,最高的人格美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格境界之美。
所以宗白华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美学是出于人物品藻之美学。
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
‘君子比德于玉’,中国人对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
";[2]李泽厚、刘纪纲也多次指出,"中国古代美学历来是从人的本质出发去认识美的本质的。
";[3]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学是根源于人格美的美学,而这种人格美则发轫于汉末清议和人物品鉴的魏晋玄学。
竹林七贤生活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魏晋时期,正是这种黑暗与光明尖锐的对立,让一代士人在反抗丑恶、堕落、异化的同时,重建人格理想、追求精神的超越。
其中饱含着异常激烈的痛苦和希望,所以竹林七贤们所理解、追求和实现的人格美的境界,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特品格。
"竹林七贤";堪称为魏晋人格美的代表,最具独特且又有人格美潜质的莫过于"精神逍遥型";的阮籍、嵇康及"至真至纯型";的阮咸。
一.精神逍遥型---离经叛道的阮籍、刑于东市的嵇康在魏晋时期,文人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可谓名士派的形成。
名家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精神风貌评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文学精神风
貌被许多名家所评析。
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情感内敛,意境深邃
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情感表达往往比较内敛,不直接展现
出来,而是通过意象的烘托和情感的暗示来表达,使得作品更加深刻、含蓄。
例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在表达自己的离愁别绪时,并没有
直接表述,而是通过景色、音乐等来暗示,让人在心理上感受到离别
的悲怆之情。
二、崇尚清新自然,追求修身养性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往往崇尚清新自然,在诗歌、散文中常常写到
山水、花鸟等自然景物,抒发对自然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他们也注
重修身养性,追求内心的平静和祥和,这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例如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旨在表达返璞归真的思想,崇尚自然、简朴、淡泊的生活态度。
三、推崇玄言玄理,探求人生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玄言、玄理的思想日益盛行,在
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形式中都有体现。
文学作品往往反映出人们
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和追求,希望通过哲思、思辨来解决人生的难题。
例如《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故事和典故,都蕴含着对人生意义的探求
和反思。
以上就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精神风貌的评析,这个时期的文学作
品风格独特,深受后人的推崇和喜爱。
魏晋人物画的美学原则【摘要】“传神写照”和“以形写神”是魏晋人物画美学原则的重要组成,也是顾恺之“形神论”的核心内容,它是“形神”这一对哲学范畴在艺术领域实践经验的一次总结,在我国艺术史和美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对魏晋人物画美学原则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对现当代中国画的创作起到一点微薄贡献。
【关键词】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美学原则;继承发展中国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史前就有迹可循,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绘画艺术也在不断的求新求变。
但在魏晋以前,从原始社会到秦汉时期绘画的目的还只是停留在“鉴戒”功能上,绘画只是由一些画工承担,没有士大夫从事绘画,到了汉末也只有少数文人士大夫从事绘画队伍;而在魏晋时期,在玄学的影响下,在士大夫的介入下,人的审美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讨论美的本质问题。
我国美术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物画就是在这一时期才逐步发育成熟并取得卓越成就的。
那么人物画为何会在魏晋时期得以蓬勃发展?在魏晋时期物画的最高境界又是什么?人物画创作遵循着什么样的美学原则?这些都是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加以探讨和廓清的。
一、从神坛走向自我——人物画的形成人类文明的演进是漫长而又繁杂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和繁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人物画亦是如此。
中国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对自然、人生和自我的认识局限,一切行为都寄托于神灵,当时的美术作品中大量出现“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怪诞形象,这种状况,直至魏晋时期才得以根本改变。
魏晋时期,由于政治混乱、杀戮不断,文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以崇尚老庄哲学思想为核心的一种儒家学派——玄学开始盛行。
“玄学是一种以‘自我超越’为主旨的人格本体论体系,也是一种蕴涵着新的自我人格美范式的价值论体系。
所谓的自我超越,就是个体实现从外部功利世界向自我情性本体的回归,不再是外在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道德节操名誉地位,而就是个体自我的天性、生命、心情、智慧、人格等成为至高无上的本体。
浅谈魏晋艺术精神之美浅谈魏晋艺术精神之美摘要:从审美的无利害性到“物我相忘”的境界体现出中国古代先贤人格的大美,人格个性的自由解放和多元化对于艺术精神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这个以“玄学”为思想基础的时代,晋人的美空绝前后,晋人的艺术精神更是后来者标榜的精神楷模,我们在“妙悟”前贤的经典中或许能得到心灵中的解放。
本文以古典传统美学思想出发探析晋人艺术精神之美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玄学;艺术精神;境界;体道一、魏晋玄学和晋人的美魏晋时期玄学的诞生和审美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政治混乱、人性、思想解放的时代,继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人的觉醒艺术自觉的时代,“这个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个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①这也正是汉代崇儒的思想禁锢后的大解放,首先是从人的意识形态去觉醒的,也就是晋人所显现出来的人格精神之美,这对后来的隋唐乃至以后时代的发展在艺术生命精神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回归到思想体位我们不得不提到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大致分为两派,以王弼为首的“贵无”;向秀、郭象为首的“崇有”。
简而言之“重无”和“贵有”的玄学思想,前者注重客观精神,并把精神看做为“道”,重传神,后者注重主观精神的超越,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
玄学的基本哲学立场是用道家思想去改造儒家,这种改造更多的是一种灵活的补充,儒家的思想统治地位虽是顺应统治者中央集权的主观意志,回归到社会思想本位,必然会存在其片面性,如魏晋时代的社会结构解体、政治混乱、门阀之间的征战层出不穷,儒教下的思想统治不再满足于士人,玄学讲求个人感情,注重思辨能力,崇尚自由,提倡天人合一的生命情怀,注重人格的发展,肯定自然人性。
玄学注重“体道”审美模式,强调自身的主观与客观的精神意志,这种审美模式了摆脱了以往政治和伦理的束缚成为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审美不再过多的受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的需要所影响,打破以往的伦理纲常的儒教审美模式,个人审美自觉的真正到来,这种“体道”式的审美表现出个人和自然之间“天人合一”的精神趣味,顾恺之笔下人物的“传神写照”,正是“体道”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达更是一种生命气质,表现一个宇宙生命,绝非对物象形体的写照。
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摘要:魏晋时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混乱的时代,三国纷争,八王之乱,晋室东迁…人们可以说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却是异常的发达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而这一时期的文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的大背景下所展现的风骨和风貌更是其他历史时期所没有的,魏晋时期的文人们的人格之美令人心折,而这种人格美又体现在了形美和神美两个方面。
在古代的十大美男中魏晋时期的就占了七个,美男并不会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魏晋时期的美男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他们风流倜傥,英俊伟岸的身姿,那种围绕在他们周身的自由狂放,潇洒不羁的气质才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而魏晋时期的审美标准背后有着怎样的背景原因?魏晋文人的形美与神美的纠缠和交织又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这都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关键词:魏晋文人、形貌、才思、神韵之美魏晋时期,这样一个黑暗又动荡的年代,战乱频繁,天无宁日。
“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写到了整个村庄的灭绝。
”①人们却将仪容和人体美作为了一种独立的审美内容。
很难想象,在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连温饱都需要烦恼的时候,还要分出精力来关注仪容仪表,这仅仅从表面上看是矛盾和难以理解的。
但当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深入的分析文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之后又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自古以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更加注重人们的内在美,即精神美。
而魏晋时期时对于人的形体之美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特色。
在儒家的审美中,着力强调美与善的联系,甚至直接将善转化成美。
美与善可以说是孔子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善是美之所以为美的先决条件,没有了善美也就不能称之为美。
徒有华丽的外表,而没有善作为内核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
孔子在论语中写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①。
“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②“里仁为美”③这种种言论都可看出孔子对美的阐释。
文质彬彬就是“美”与“善”的一种统一,而善甚至是要超过于美的。
可以说儒家是更注重内在美的。
而道家强调的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的自然之美,持一种无为自在的审美态度。
认为自然的天然的就是最美的。
庄子就主张万物各随其性,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道家在论述人格美的时候,也更推崇人的精神美,认为精神美远重要与外表形态之美,常常以形貌丑陋的人来反衬人物精神的伟岸高大。
由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不能成为魏晋独特审美理念的内在依据。
所以它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产物。
可以说正①是魏晋人赋予了人外貌形体之美的独立意义。
人的形貌之美是人形体之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汉朝四百年基业一夕瓦解之后,征战不断的魏晋时期,“重美不重德”蔚然成风。
有许多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反倒将物质文化的享受推向了极致。
甚至推崇“男风”。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就曾以“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一句对男色进行礼赞。
人们开始更加的重视人的形体和外表。
在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一篇中就收录了三十九篇对美男子们的风流俊美外表的记述。
先举一些其中的例子。
在世说新语容止中收录的三十九篇中,写潘安的就占了其中的三篇。
可见其古代第一美男的称号也并非浪得虚名。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容止》七)这也是“掷果盈车”这个典故的出处了。
在这一则中更是用一个对比,用潘安和左思对比来突出潘安的美貌。
而左思不过是男版的“东施效颦”贻笑大方罢了。
通过这段记录不难想象魏晋时期人们对于美貌的推崇,而从向潘安掷果的“妇人”们来看,其疯狂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下的追星族。
由此,魏晋时期的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是可见一斑的。
其中还有一个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看杀卫玠”了。
卫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
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
时人谓看杀卫。
(《容止》十九)这个故事似乎是有夸张的成分,可是因卫玠的美貌而引起人们的围观和轰动应该是真的,这也是不难想象的。
至于卫玠的死并不单纯是因被围观过度疲劳而死还可能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里边。
但不管是偶然也好是错误也罢。
卫玠的死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仍带给我们一种愕然和震撼,让我们不由自主的就去想象在魏晋那个时期的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和当时盛况空前的宏大的场面。
同时也不得不为一代美男的死而扼腕叹息。
以上两个小的故事都生动的再现了当时人们对于外在形貌的疯狂迷恋和追求。
那么当时的魏晋名士们的形貌又究竟是如何的呢?在《世说新语》中也有对其的一些描述。
多形容了两点:一个是肤白貌美、一个是眼睛有神。
写肤白的如其中的第二篇:“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
魏明帝疑其傅粉。
正夏月,与热汤。
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容止》)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
”(《容止》6)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容止》8)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容止》26)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
”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
”(《容止》37)以上几条都是写其肤色和眼睛。
可见,在魏晋时期,肤色洁白,眼睛有神是他们的一个审美要求。
而《诗经・卫风・硕人》中写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本是形容女性美的。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的审美是偏向女性的阴柔美的。
而魏晋的美男们不仅外表似玉般洁白无瑕,其思想,品行也是如玉般晶莹剔透。
常以玉喻人。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容止》3)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容止》9)骠骑王武子是卫之舅,俊爽有风姿。
见,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容止》14)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
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容止》12)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
”而玉正是晶莹发亮的物体。
《诗经・秦风・小戎》中有言“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君子如玉”的观念来自于此。
“玉”象征了珍贵、纯粹和纯洁,魏晋人常用玉树、珠玉来品评人物,甚至将人称为“玉人”。
而从装扮上看则是两个极端。
一种是喜爱修饰自己,甚至涂脂抹粉,偏似女性。
另一种则是放荡不羁,不修边幅。
既有美姿仪、妙神韵这类以卫玠为代表的瘦弱体,也有任性旷达粗头乱服皆好以嵇康为代表的糙男派。
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俊美的外表了。
当然那也并不只是一个靠脸就能走遍天下的时代,主要还得看气质。
任何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都有他背后自然而成的道理。
当我们身处历史的洪流中,无法跳脱出来俯瞰当世的种种,我们只是顺应着时代的潮流,顺水而下的“当局者迷”。
而当我们去回顾历史,去回望历史曾经走过的印记,懂得了知人论世,去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问题,就会收获不一样的境界。
那么魏晋时期的对人们的形貌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动荡的社会,生命的无常,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深受这种影响,这使人们加重了对自身的关注,对“人”本身的关注。
对于一些文人知识分子来说,时局动荡不安再加上社会的黑暗混乱,他们虽有一腔为国为民的衷心和雄心壮志的伟大抱负。
但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的,他们的仕途无望。
英雄已矣,小人当道。
这本是每一个时代都会存在的现象,但对于魏晋士人来说,这种愿望似乎更加迫切,这样的境况似乎更让他们感到一种绝望。
在一个方向前进的路上遇到了近乎绝境,便调转头来向相反的方向一路狂奔。
人们似乎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从对社会现实的关怀转向了对个体生命的重视。
因此人们更加的重视人的外貌了,在每个朝代美男都扎堆的情况下,魏晋时期的美男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名垂千古这与文学家用文字的记录是分不开的。
其次,是它的思想的背景。
经学式微,老庄盛行,玄学兴起,在这样的大分裂的时代,各种矛盾交织复杂,人们的思想也是不一而同,原有的依据一片混乱在这种混乱中索性也就打破了一切束缚,追求自我,个性解放。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对于美的追求。
老庄思想和佛教的流行,使人们摆脱了现实的纷争而使他们的心回归到了自然。
社会的礼教约束被抛弃,儒家学说被搁置一旁,其中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重美不重德”,在精神上追求极端的自由,在行为上享受放纵的快感,整个时代都弥漫着一种快意人生的放荡之风,及时享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在封建礼教束缚的时代中这或许是离经叛道又不可理喻的。
但当最基本的生命都没有了保障,现实的残酷的情景已经触及了人们最后的底线。
此时谁还会去管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教的规范。
就算明天就要流离失所,横尸街头,也要保持外表的整洁,快意的死去。
正是这些特殊的因素为魏晋的人们的审美理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再次重申的观点是,魏晋的文人们也并不仅仅靠脸就能走遍天下,受到众人的敬仰和拥戴的,主要还是要看气质的。
魏晋的人们不仅重视人外在的形体之美,也同样重视人的内在的神韵之美。
强调的是一种形和神的统一。
根据宗白华先生的观点:“这两方面的美——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
”将魏晋士人的审美理想分为了自然美和人格美两个方面,而其中的人格美又细分作形美与神美。
以上已对形体的美做了简单的描述和探究。
下面就探究一下魏晋士人们的神韵之美。
这种美并不是单单的一个方面,而是一种复杂神秘一言难尽的围绕在魏晋士人们周身的一种气质。
首先从他们的才情开始说起。
在东汉末年,汝南地区许劭、许靖兄弟所主持的月旦评闻名遐迩,盛极一时。
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选官制度以及稍后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月旦评虽为时不长,但却在史坛和文坛上留下了深深地烙痕。
“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则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月旦评影响深远,孔尚任《桃花扇•修礼》:“舌唇才动,也成月旦春秋。
”⑤可见一斑。
他们常在每月初一,发表对当时人物的品评,故称“月旦评”例如许劭评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凡得好评之人,无不名声大振。
一时引得四方名士慕名而来,竞领二许一字之评以为荣。
这就为魏晋的文人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言论提供了一个合适又广阔的平台。
而后“月旦评”渐渐消失隐去后,人们便开启了另一种模式“清谈”。
清谈是一种就玄学问题进行分析、推理、问难、辩论的文化现象,承袭于东汉清议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