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解读魏晋士人的人格悲剧(一)
- 格式:docx
- 大小:21.13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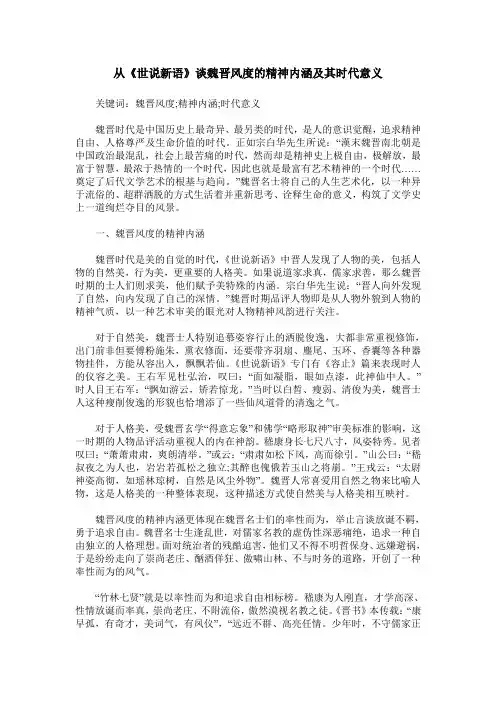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谈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及其时代意义关键词:魏晋风度;精神内涵;时代意义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奇异、最另类的时代,是人的意识觉醒,追求精神自由、人格尊严及生命价值的时代。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漢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魏晋名士将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一种异于流俗的、超群洒脱的方式生活着并重新思考、诠释生命的意义,构筑了文学史上一道绚烂夺目的风景。
一、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魏晋时代是美的自觉的时代,《世说新语》中晋人发现了人物的美,包括人物的自然美,行为美,更重要的人格美。
如果说道家求真,儒家求善,那么魏晋时期的士人们则求美,他们赋予美特殊的内涵。
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魏晋时期品评人物即是从人物外貌到人物的精神气质,以一种艺术审美的眼光对人物精神风韵进行关注。
对于自然美,魏晋士人特别追慕姿容行止的洒脱俊逸,大都非常重视修饰,出门前非但要傅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方能从容出入,飘飘若仙。
《世说新语》专门有《容止》篇来表现时人的仪容之美。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当时以白皙、瘦弱、清俊为美,魏晋士人这种瘦削俊逸的形貌也恰增添了一些仙风道骨的清逸之气。
对于人格美,受魏晋玄学“得意忘象”和佛学“略形取神”审美标准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人物品评活动重视人的内在神韵。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魏晋人常喜爱用自然之物来比喻人物,这是人格美的一种整体表现,这种描述方式使自然美与人格美相互映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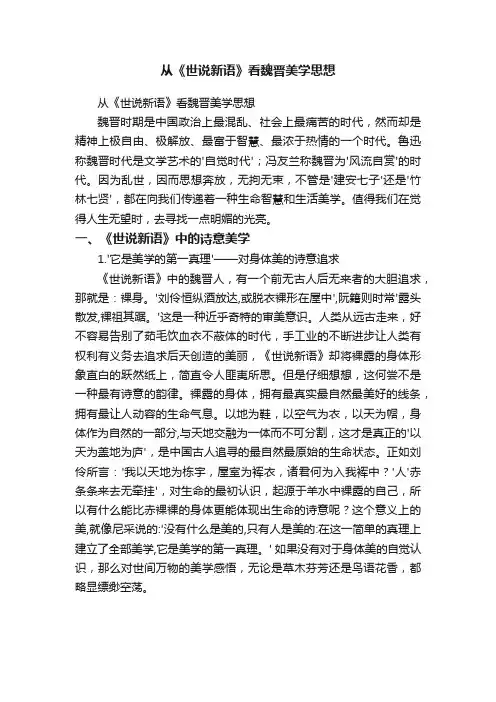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美学思想从《世说新语》看魏晋美学思想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鲁迅称魏晋时代是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冯友兰称魏晋为'风流自赏'的时代。
因为乱世,因而思想奔放,无拘无束,不管是'建安七子'还是'竹林七贤',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种生命智慧和生活美学。
值得我们在觉得人生无望时,去寻找一点明媚的光亮。
一、《世说新语》中的诗意美学1.'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对身体美的诗意追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有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胆追求,那就是:裸身。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阮籍则时常'露头散发,裸祖其踞。
'这是一种近乎奇特的审美意识。
人类从远古走来,好不容易告别了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时代,手工业的不断进步让人类有权利有义务去追求后天创造的美丽,《世说新语》却将裸露的身体形象直白的跃然纸上,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仔细想想,这何尝不是一种最有诗意的韵律。
裸露的身体,拥有最真实最自然最美好的线条,拥有最让人动容的生命气息。
以地为鞋,以空气为衣,以天为帽,身体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交融为一体而不可分割,这才是真正的'以天为盖地为庐',是中国古人追寻的最自然最原始的生命状态。
正如刘伶所言:'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生命的最初认识,起源于羊水中裸露的自己,所以有什么能比赤裸裸的身体更能体现出生命的诗意呢?这个意义上的美,就像尼采说的:'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
' 如果没有对于身体美的自觉认识,那么对世间万物的美学感悟,无论是草木芬芳还是鸟语花香,都略显缥缈空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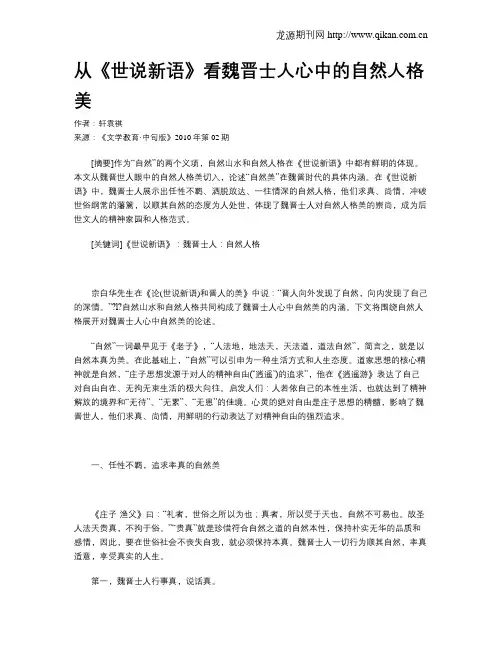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心中的自然人格美作者:轩袁祺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0年第02期[摘要]作为“自然”的两个义项,自然山水和自然人格在《世说新语》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本文从魏晋世人眼中的自然人格美切入,论述“自然美”在魏晋时代的具体内涵。
在《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展示出任性不羁、洒脱放达、一往情深的自然人格,他们求真、尚情,冲破世俗纲常的藩篱,以顺其自然的态度为人处世,体现了魏晋士人对自然人格美的崇尚,成为后世文人的精神家园和人格范式。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士人:自然人格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l?自然山水和自然人格共同构成了魏晋士人心中自然美的内涵。
下文将围绕自然人格展开对魏晋士人心中自然美的论述。
“自然”一词最早见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简言之,就是以自然本真为美。
在此基础上,“自然”可以引申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道家思想的核心精神就是自然,“庄子思想发源于对人的精神自由(‘逍遥’)的追求”,他在《逍遥游》表达了自己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的极大向往。
启发人们:人若依自己的本性生活,也就达到了精神解放的境界和“无待”、“无累”、“无患”的佳境。
心灵的绝对自由是庄子思想的精髓,影响了魏晋世人,他们求真、尚情,用鲜明的行动表达了对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
一、任性不羁,追求率真的自然美《庄子·渔父》曰:“礼者,世俗之所以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贵真”就是珍惜符合自然之道的自然本性,保持朴实无华的品质和感情,因此,要在世俗社会不丧失自我,就必须保持本真。
魏晋士人一切行为顺其自然,率真适意,享受真实的人生。
第一,魏晋士人行事真,说话真。
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
羊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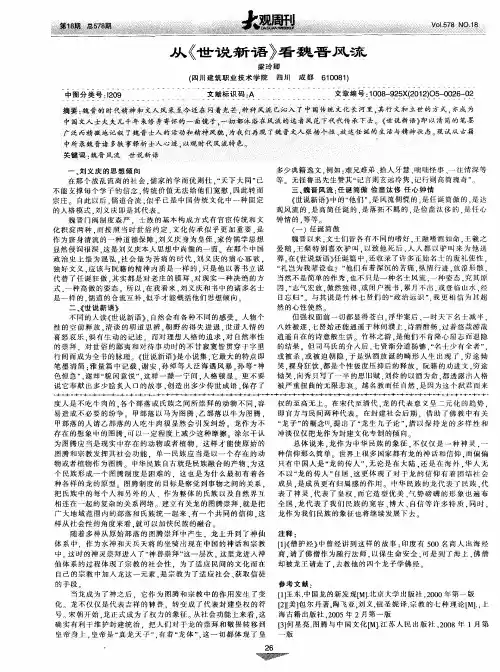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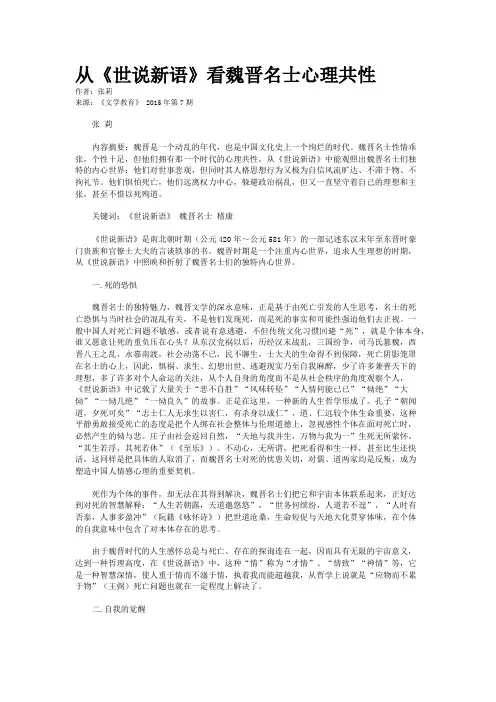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心理共性作者:张莉来源:《文学教育》 2015年第7期张莉内容摘要: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绚烂的时代。
魏晋名士性情乖张,个性十足,但他们拥有那一个时代的心理共性,从《世说新语》中能观照出魏晋名士们独特的内心世界:他们对世事悲观,但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旷达、不滞于物、不拘礼节。
他们惧怕死亡,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躲避政治祸乱,但又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主张,甚至不惜以死殉道。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士嵇康《世说新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的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的书。
魏晋时期是一个注重内心世界,追求人生理想的时期,从《世说新语》中照映和折射了魏晋名士们的独特内心世界。
一.死的恐惧魏晋名士的独特魅力,魏晋文学的深永意味,正是基于由死亡引发的人生思考,名士的死亡恐惧与当时社会的混乱有关,不是他们发现死,而是死的事实和可能性强迫他们去正视。
一般中国人对死亡问题不敏感,或者说有意逃避,不但传统文化习惯回避“死”,就是个体本身,谁又愿意让死的重负压在心头?从东汉党祸以后,历经汉末战乱,三国纷争,司马氏篡魏,西晋八王之乱,永嘉南渡,社会动荡不已,民不聊生,士大夫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死亡阴影笼罩在名士的心上,因此,惧祸、求生、幻想出世、逃避现实乃至自我麻醉,少了许多兼善天下的理想,多了许多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从个人自身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秩序的角度观察个人,《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悲不自胜”“风味转坠”“人情何能已已”“恸绝”“大恸”“一恸几绝”“一恸良久”的故事。
正是在这里,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形成了。
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道、仁远较个体生命重要,这种平静勇敢接受死亡的态度是把个人绑在社会整体与伦理道德上,忽视感性个体在面对死亡时,必然产生的恸与悲。
庄子由社会返回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生死无所萦怀,“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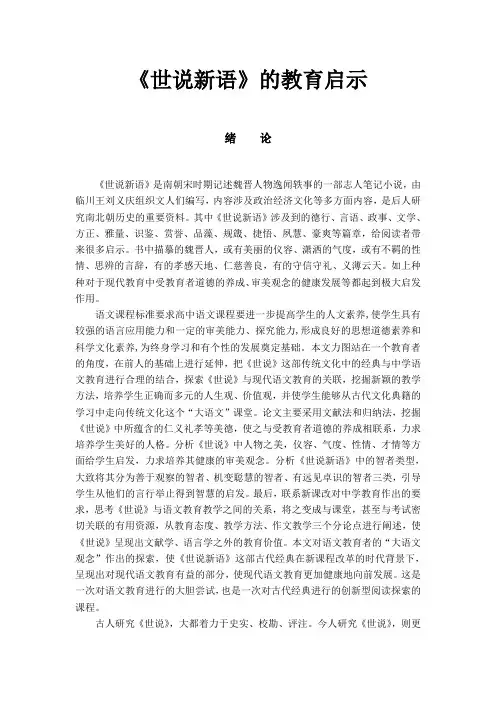
《世说新语》的教育启示绪论《世说新语》是南朝宋时期记述魏晋人物逸闻轶事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由临川王刘义庆组织文人们编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是后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其中《世说新语》涉及到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等篇章,给阅读者带来很多启示。
书中描摹的魏晋人,或有美丽的仪容、潇洒的气度,或有不羁的性情、思辨的言辞,有的孝感天地、仁慈善良,有的守信守礼、义薄云天。
如上种种对于现代教育中受教育者道德的养成、审美观念的健康发展等都起到极大启发作用。
语文课程标准要求高中语文课程要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本文力图站在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把《世说》这部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与中学语文教育进行合理的结合,探索《世说》与现代语文教育的关联,挖掘新颖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正确而多元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使学生能够从古代文化典籍的学习中走向传统文化这个“大语文”课堂。
论文主要采用文献法和归纳法,挖掘《世说》中所蕴含的仁义礼孝等美德,使之与受教育者道德的养成相联系,力求培养学生美好的人格。
分析《世说》中人物之美,仪容、气度、性情、才情等方面给学生启发,力求培养其健康的审美观念。
分析《世说新语》中的智者类型,大致将其分为善于观察的智者、机变聪慧的智者、有远见卓识的智者三类,引导学生从他们的言行举止得到智慧的启发。
最后,联系新课改对中学教育作出的要求,思考《世说》与语文教育教学之间的关系,将之变成与课堂,甚至与考试密切关联的有用资源,从教育态度、教学方法、作文教学三个分论点进行阐述,使《世说》呈现出文献学、语言学之外的教育价值。
本文对语文教育者的“大语文观念”作出的探索,使《世说新语》这部古代经典在新课程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对现代语文教育有益的部分,使现代语文教育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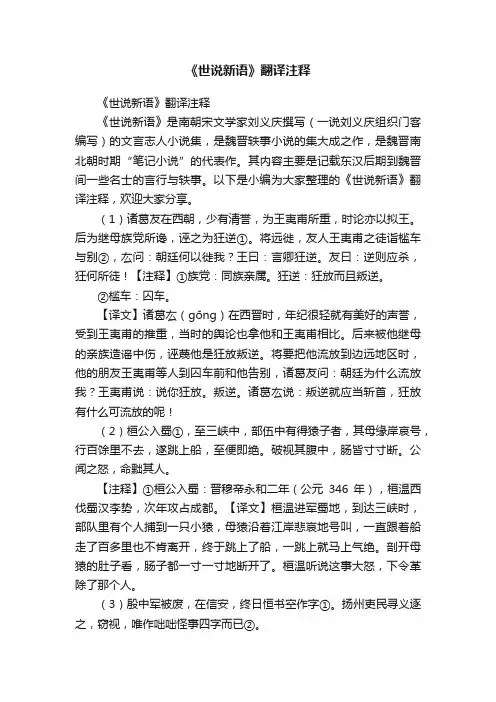
《世说新语》翻译注释《世说新语》翻译注释《世说新语》是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撰写(一说刘义庆组织门客编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
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说新语》翻译注释,欢迎大家分享。
(1)诸葛友在西朝,少有清誉,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
后为继母族党所谗,诬之为狂逆①。
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诣槛车与别②,厷问: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
友曰:逆则应杀,狂何所徒!【注释】①族党:同族亲属。
狂逆:狂放而且叛逆。
②槛车:囚车。
【译文】诸葛厷(gōng)在西晋时,年纪很轻就有美好的声誉,受到王夷甫的推重,当时的舆论也拿他和王夷甫相比。
后来被他继母的亲族造谣中伤,诬蔑他是狂放叛逆。
将要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时,他的朋友王夷甫等人到囚车前和他告别,诸葛友问:朝廷为什么流放我?王夷甫说:说你狂放。
叛逆。
诸葛厷说:叛逆就应当斩首,狂放有什么可流放的呢!(2)桓公入蜀①,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馀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
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
公闻之怒,命黜其人。
【注释】①桓公入蜀: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 年),桓温西伐蜀汉李势,次年攻占成都。
【译文】桓温进军蜀地,到达三峡时,部队里有个人捕到一只小猿,母猿沿着江岸悲哀地号叫,一直跟着船走了百多里也不肯离开,终于跳上了船,一跳上就马上气绝。
剖开母猿的肚子看,肠子都一寸一寸地断开了。
桓温听说这事大怒,下令革除了那个人。
(3)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①。
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②。
【注释】①殷中军句: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 年),殷浩以中军将军受命北伐,结果大败而回,被桓温奏请废为庶人,于是迁屠杨州东阳郡信安县。
②咄咄怪事:形容令人惊讶的怪事。
【译文】中军将军殷浩被免官以后,住在信安县,一天到晚总是在半空中虚写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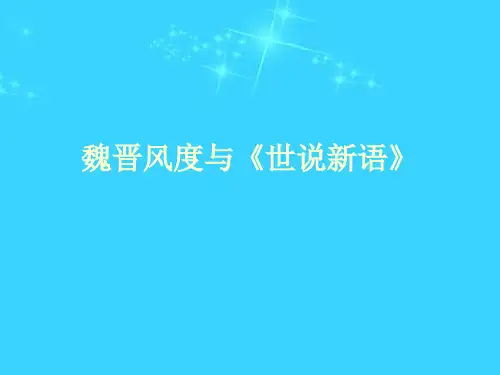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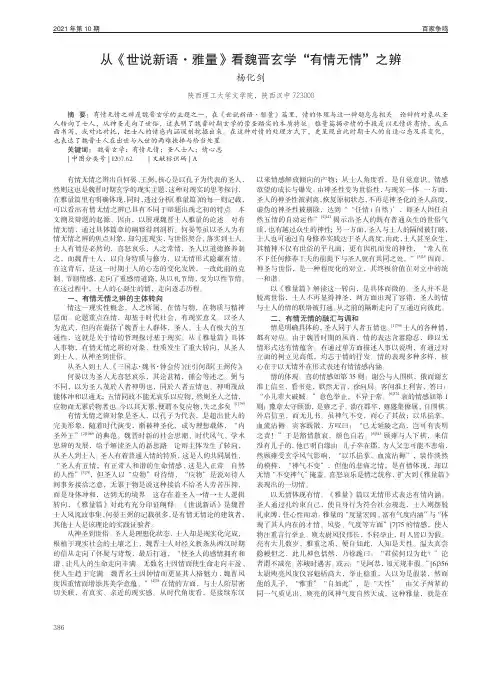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雅量》看魏晋玄学“有情无情”之辨杨化剑有情无情之辨出自何晏、王弼,核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然则这也是魏晋时期玄学的现实主题,这种对现实的思考探讨,在雅量篇里有明确体现,同时,透过分析《雅量篇》的每一则记载,可以看出有情无情之辨已具有不同于辩题出现之初的特点。
本文溯及辩题的起源、因由,以展现魏晋士人雅量的论述。
对有情无情,通过具体篇章的阐释得到剖析。
何晏等虽以圣人为有情无情之辨的焦点对象,却勾连现实,与世俗契合,落实到士人。
士人有情是必然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圣人以道德修养制之,而魏晋士人,以自身特质与修为,以无情形式隐藏有情。
在这背后,是这一时期士人的心态的变化发展,一改此前的克制、节制情感,走向了重感情道路,从以礼节情,变为以性节情。
在这过程中,士人的心诞生的情,走向逐志历程。
一、有情无情之辨的主体转向情这一现实性概念,人之所属,在情与物,在物质与精神层面。
论题重点在情,却基于时代社会,有现实意义。
以圣人为范式,但内在囊括了魏晋士人群体,圣人、士人有极大的互通性,这就是关于情的哲理探讨基于现实。
从《雅量篇》具体人事物,有情无情之辨的对象、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向,从圣人到士人、从神圣到世俗。
从圣人到士人。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何邵《王弼传》: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锺会等述之。
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
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於物者也。
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1]795有情无情之辨对象是圣人,以孔子为代表,是超出世人的完美形象,随着时代演变,渐被神圣化,成为理想载体,“内圣外王”[2]1069的典范。
魏晋时新的社会思潮、时代风气、学术思辨的发展,给予解读圣人的新思路。
论辩主体发生了转向,从圣人到士人。
圣人有着普通人情的特质,这是人的共同属性,“圣人有五情,有正常人和谐的生命情感, 这是人正常、自然的人性”[3]78,但圣人以“应物”对待情,“应物”是说对待人间事务接洽之意,无累于物是说这种接洽不给圣人劳苦压抑,而是身体冲和,达到无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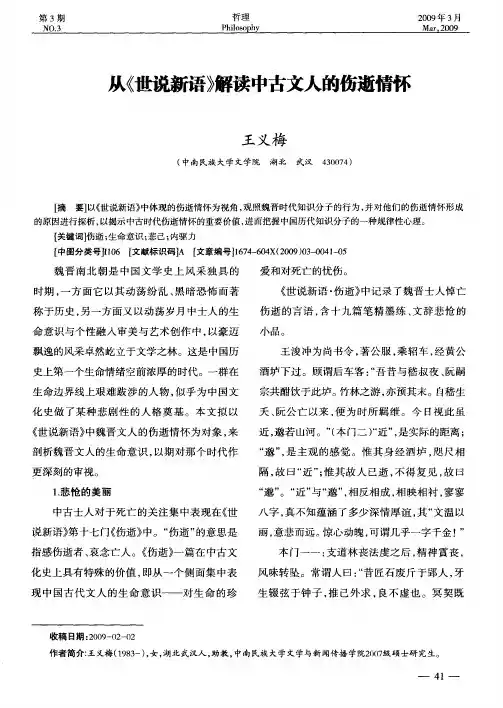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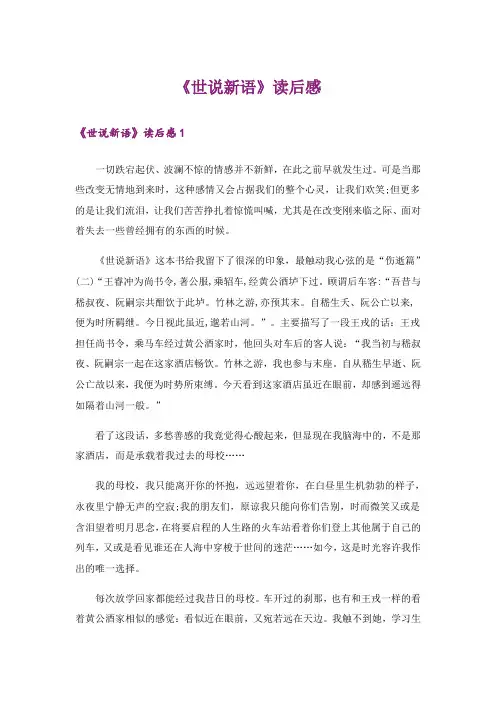
《世说新语》读后感《世说新语》读后感1一切跌宕起伏、波澜不惊的情感并不新鲜,在此之前早就发生过。
可是当那些改变无情地到来时,这种感情又会占据我们的整个心灵,让我们欢笑;但更多的是让我们流泪,让我们苦苦挣扎着惊慌叫喊,尤其是在改变刚来临之际、面对着失去一些曾经拥有的东西的时候。
《世说新语》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触动我心弦的是“伤逝篇”(二)“王睿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
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
竹林之游,亦预其末。
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
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
主要描写了一段王戎的话:王戎担任尚书令,乘马车经过黄公酒家时,他回头对车后的客人说:“我当初与嵇叔夜、阮嗣宗一起在这家酒店畅饮。
竹林之游,我也参与末座。
自从嵇生早逝、阮公亡故以来,我便为时势所束缚。
今天看到这家酒店虽近在眼前,却感到遥远得如隔着山河一般。
”看了这段话,多愁善感的我竟觉得心酸起来,但显现在我脑海中的,不是那家酒店,而是承载着我过去的母校……我的母校,我只能离开你的怀抱,远远望着你,在白昼里生机勃勃的样子,永夜里宁静无声的空寂;我的朋友们,原谅我只能向你们告别,时而微笑又或是含泪望着明月思念,在将要启程的人生路的火车站看着你们登上其他属于自己的列车,又或是看见谁还在人海中穿梭于世间的迷茫……如今,这是时光容许我作出的唯一选择。
每次放学回家都能经过我昔日的母校。
车开过的刹那,也有和王戎一样的看着黄公酒家相似的感觉:看似近在眼前,又宛若远在天边。
我触不到她,学习生活过于忙碌,以至于我几乎没有机会也没有理由再回到那里看一看。
唯一的理由是这份思念,但又有谁真正明白我这份复杂的感情,比起我的未来和学业,她在人们眼中实在太渺小,太不堪一击。
岁月改变了许多,从我的身心到这整个世界,一个都不放过。
就像那些校园里的风景,少了我和我的朋友,这些风景还是风景,但毕竟少了我们,毕竟还是变了。
魏晋时人的悲剧意识与喜剧精神魏晋时人的悲剧意识与喜剧精神代云魏晋时期长期以来在我们印象中似乎是一个完整无暇的历史性所在,一如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如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闭上双眼,袒胸绾扇的魏晋名士长袖飘飘,手执一秉塵尾(拂尘),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张口启齿间字字珠玑,“谈言微中”,举手投足中情纵气任,哲意尽显,那么的潇洒不群,超然自得,其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双眸闪闪若岩下电”,“濯濯如春月柳”,其文“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越名教而任自然”,有意无意中尽显“魏晋风流”——然而,当我们深入到时代的内核,多一点存在的呼应与“了解之同情”,我们就会发现魏晋名士们豪放的外在风骨下是怎样内敛的精魂。
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动乱使儒家前此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伦理规范逐渐变为教条,成了名副其实的“名教”。
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败和地方察举制度的腐化,“魏之初霸,术兼名法”,统治阶层试图通过“综核名实”一匡时弊;在这背景下,《人物志》应运而生,在对以往人物的考核品评中事与愿违的转入对概念本身的“辨名析理”;于是,“玄远之学”由此起步——魏晋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以门阀士族当政的地主阶级专政时期,门阀士族是极少数拥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的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们对农民实行农奴式的压迫和剥削,在地主阶级内部也排斥那些寒门庶族。
曹魏政权是在镇压汉末黄巾农民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农民阶级有着尖锐的矛盾。
同时曹魏政权内部,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的争权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
在门阀等级森严的社会中,高门士族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所谓“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广大的有着远大志向与襟怀的文人知识分子们通过正常途径根本无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出现了蔚为壮观的独特的“清谈”现象。
清谈的前身是东汉末年的清议。
当然,清谈和清议不同,这代表两个不同的时代,具体原因和内容也不尽相同。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摘要]《世说新语》所记人和事不仅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书中主要记载了魏晋清谈风尚,揭露了统治者豪奢淫佚和颓废堕落的面貌,赞颂了士人的嘉言懿行,并有对上层妇女精神风貌的描写,是了解魏晋士流、魏晋风度、魏晋玄学、魏晋妇女以及整个魏晋时期思想政治面貌的重要文献。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志人小说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并集大成的一种。
全书按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篇,以类相从。
主要记述自东汉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论、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
它是当时历史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士族名流的众生相,将他们的言行风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它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了解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文试就《世说新语》一书所描写的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做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世说新语》大量描写魏晋清谈风尚曹魏正始以后,曹氏与司马氏之间斗争激烈。
司马氏大诛异己,士族文人朝不保夕。
他们对现实不满,不敢也不屑谈论政事,于是“托怀玄胜,远咏老庄”,终日以清谈为事,清谈几乎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他们沉湎于此,有时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清谈常用互相辩论的方式以“辩名析理”(郭象:《庄子注·天下篇》)。
就《世说新语·文学》(以下引文凡出自《世说新语》者,仅举篇名)所记材料看,其争辩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分为主客两方,一方诘难,一方答辩。
双方辩论势如交战,分成回合,一来一往,称为“一番”,几个回合,称为“数番”。
如《文学》篇载:(羊)孚雅善理义,乃与(殷)仲堪道《齐物》,殷难之。
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
”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
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
”叹为新拔者久之。
一种是一人自作宾主,自己设问,自己答辩,即所谓“自为客主”。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文人心态“万花筒”作者:张凌蕾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20期摘要:《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宋,编者刘义庆(403-444),这部作品主在记载魏晋时期众多人物的言谈举止和遗闻逸事,有“名士教科书”的美誉,其内容涉及到魏晋时期社会、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当时社会风俗和心理状态等各个方面,涵盖极广,本文选取了《世说新語》中的一部分内容,旨在探讨《世说新语》中的所体现的文人心态的多样性。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文人;心态《世说新语》原名《世说》,诞生于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是我们国家典型的乱世。
众多文人都在这一时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或激流勇进,或避世全身。
不一样的选择折射出当时文人们不一样的心态。
结合《世说新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文人文人们的心态主要集中在如下四种:一、建功立业的进取关于这一种心态主见于如桓温、谢安这样的大家身上。
建功立业的典型代表第一个就是名将桓温。
《尤悔》第三十三则中记载: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尤悔》中的这一则通过寥寥几语,一个野心勃勃的的军事家形象跃然纸上,第二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是一代贤相谢安。
其在东山隐居的时候,表面上陶醉于山水之间,但事实上却是一直心系朝廷,为将来的出山做准备。
《识鉴》第二十一则中记载道:谢安隐居在东山时蓄养了很多歌女,简文帝知道了以后就说“安石必出”。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谢安应邀出山。
二、及时行乐的悲怆魏晋时期的及时行乐之风首先表现在奢侈腐败的生活上。
晋武帝司马炎灭吴后,以为四海一统,天下无事,便开始滋生安逸之心,慢慢地开始享受生活。
有皇帝带头,再加之国库宽裕,晋朝逐渐养成了奢侈之风。
《世说新语》中《汰侈》一篇,其主要内容就是描写晋朝贵族奢侈腐朽的生活。
其中就石崇和王恺比富,其中情状世所罕见。
其二表现在服“药”这一事上。
《世说新语》中《言语》第十四则记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世说新语读后感世说新语读后感(6篇)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何不写一篇读后感记录下呢?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说新语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世说新语读后感1《世说新语》是汉末人物品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它的不少故事是取材于魏晋时期作品《语林》、《郭子》、《名士传》等书的。
看了《世说新语》就能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逸事笔记的内容和形式了。
也可以说它是一部魏晋风流故事集,从而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
按冯友兰的一句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
当然这种人格美是以当时士族的标准来衡量的。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的史料。
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任诞,简傲,种种人格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
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如《德行》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
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
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赞扬管宁淡泊名利。
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出来的。
有德行的故事还有许多,如情绪这方面,德行较不好的人常会以它个人的情绪为中心,心情好时大家没事,心情不好时大家得遭殃,古时就有一位不管快乐或失意,都不会表现于自己的情绪上,那个人就是稽康,王戎说我和稽康在一起相处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高兴或者生气的表情。
人通常得到一个不好的东西,或遇到对自己有害的东西都会闪而避之,但是有的人得到这一个东西,或者遇到这个东西也不是闪而避之。
而倒霉反而还一点不会被那样东西所波及到。
瘐亮的坐骑中,有一匹叫的卢的凶马,有人劝告他派人牵去卖掉,瘐亮回答说:“卖它一定会有人买它,但这样又会害了别人;哪里可把对自己有害的东西转移到别人身上呢?从前孙叔敖杀了两头蛇,就是因为不让后人看见,从此他就成为古人乐于传颂的佳话,我效法他不也是合理的吗?”《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世说新语二则作品简介《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召集门下食客共同编撰。
接下来店铺为你整理了世说新语二则作品简介,一起来看看吧。
世说新语二则作品简介《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
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从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
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
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
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
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
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
《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世说新语二则艺术成就《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
从《世说新语》解读魏晋士人的人格悲剧(一)
【内容提要】
《世说新语》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较早而重要的笔记小说体,其内容
主要涉及汉末至东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逸闻趣事和玄虚清谈,故亦
可称之为是一部反映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而透过潇洒风流的名人士子
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不仅仅是魏晋士人们的狂狷、任诞等诸种荒唐
之举,我们发现这其中更浸渍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无奈、悲哀、苦
痛和血泪,他们是在悬崖边上痛苦挣扎着的灵魂,他们以其独特的言
行风貌向世人委曲地道出了心声。【关键词】《世说新语》知识分子困
境失落抗争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乱世,动荡不安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
律,整个社会时常笼罩在恐怖肃杀的气氛之下。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
社会各阶层、各集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作为社会文化界精
英和思想界领袖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的冲击尤为强烈。生活在这个
时期的世族文人,先是经历了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接着是曹魏
政权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利之争,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又爆发了“八王之
乱”,许多文人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血腥的政治斗争中而遭到杀戮。在
接连遭受了几次惨烈的打击之后,知识分子深刻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常
和世情的险恶,于是他们在自己的生存困境中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追求。
儒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悄然隐退,代之而起
的是一种对自我人生的强烈关照和个体生命的极度张扬,并由此形成
了为无数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但也正如古往今来众多学
者所指出的:魏晋风度不过是表面看起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着
巨大的痛苦、抑郁和悲哀。下文将撷取《世说新语》中世族名士的几
个生活片段来解读魏晋士人的悲剧人生,进而了解那个人的自觉的时
代。
一、从赏誉篇透视魏晋士人的内省式的精神世界
治国平天下本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天职,但时局的动乱、世情的险恶已
容不得他们随意插手政治,甚至他们为求得保身不得不对此退避三舍。
于是,这些在现实政治中战战兢兢、无法立足的文人士子们,暂时放
弃了他们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豪情壮志,而把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
对自我人生的追求和关照上。从赏誉篇中所记来看,率真质朴、闲适
清高、简约旷达、宁静淡泊等品性成为了时人品评关注的焦点,如: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这里,王戎
以未经雕饰的“璞玉浑金”来比喻山涛品地的率真、质朴,此间真意,尽
在其中。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这句话的意思是:“剥去他的皮,体内也全
是真诚的。”真可谓至真至诚!
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这里,
“省率”“胸中无宿物”即是对庾统品性直率和心无芥蒂的认同。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豫”即欢乐闲适的意思。
庾公目中朗:“神气融散,差如得上。”“神气融散”即“神情气质和达闲
适。”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楷清通。”意思是:武元夏品评裴楷、王戎
说:“戎崇尚简约,楷清明通达。”
谢动舆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简畅。”“清通简畅”即清明通达简约畅快之
意。
世目谢尚为“令达”。阮遥集云:“清畅似达。”意思是:世人品评谢尚是
“美好通达的人。”阮孚说:“谢尚清高畅快,象是旷达的人。”
世目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穆少”指的就是宁静淡泊之意。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举。从当时人们对魏晋士子
名流个体品性的关注来看,更多的士子文人已经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
开始向自我的人生回归:他们不再热衷于追逐尘世间的虚名浮利,他
们追求的是个体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超脱;他们流露出的是向人类自然
本性的迁移;他们试图放下负累,回到人生的原生态,释放个体生命
内心深处最朴实无华的性情。
二、从栖逸篇窥测部分士人的艰难生存状态
时局的动乱、政局的不稳和权力争夺的残酷性让更多士人看清了世道
的黑暗及他们的渺小和无助,于是,避官隐逸成为了众多士人的选择。
如苏门隐者,如道士孙登,他们都是隐居山林之士。栖逸篇中还记载
了一则“二隐分道”的小故事: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浔阳。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
务,周遂仕。翟秉志弥坚固。其后,周诣翟,翟不与语。
翟道渊、周子南二人本来有着共同的志趣,是一起避世隐居的志同道
合的朋友。但周经不住庾太尉的反复劝说,出山做官了。而翟的隐逸
心志却由此更加坚决。并且周再来探望他的时候,翟便不再同周说话,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说他故作清高也罢,说他自命不凡也罢,
但正是他的这份此志弥坚赢得了我们的敬佩之情!
比翟道渊更加坚决的便是嵇康了。《世说新语》中是这样记载的: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嵇康是竹林七贤之一。而作为曹魏皇室的姻亲(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
(曹林之女)为妻),不管是出于他的个人情感,还是从他作为传统士
人的忠君思想来看,他同司马氏在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都是格
格不入的。但由于他是当时世所称道的竹林名士集团的首领,在知识
分子士大夫中的影响很大,因此便成为了司马氏集团笼络的对象。特
别是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司马昭谋弑魏帝曹髦之后,为了掩盖其
弑君的恶名,急需舆论的支持。于是司马昭就请嵇康的好友山涛出面,
以山涛将转迁散骑侍郎而吏部郎出缺为由,推荐嵇康出任吏部郎,这
就把嵇康推向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当权者的威逼利诱,一方面是
朋友情谊和个体独立人格的矛盾斗争。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
么违背心志接受官职,那么其傲世独立的人格将受到压抑和束缚;要
么就拒绝引荐,等待命运的裁决,因为拒绝就意味着他公然打起了不
与司马氏集团合作的旗号。而在当时看来,司马氏篡位代祚早已成为
定局,但尽管如此,秉性刚直的嵇康由于深恶司马氏的残暴虚伪,不
仅没有接受山涛的举荐,反而拂了好友的脸面,愤然写下了《与山巨
源绝交书》。这种毅然决然的抗争态度虽然保住了他的自尊与名节,但
他也由此惹祸上身,并最终死在了司马昭的屠刀之下。
回味历史,每逢乱世,社会便不乏归隐之士。而他们之所以选择隐逸,
一方面是想远离社会纷争与杀戮,避祸保身,当然也有人是为了韬光
养晦;另一方面也是在看厌世道却无力改变社会现状、无法实现生命
价值的悲痛下做出的无奈选择。他们企求以这种不问世事、淡泊无为
的生存方式来求得一方净土,但残酷的社会现实甚至连这点机会都不
给,一步步把他们逼到了痛苦的深渊,他们终究逃不脱在位统治者的
掌控。而从他们的避世情怀和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我们也可以看出,
魏晋士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从主体角度、从自身个性去探求人的生存
发展的意义,而且他们不是单纯地探究人怎样适应社会,而是探究人
应该如何生活,这也反映出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对自我人格的
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