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世说新语_看魏晋士人心中的自然人格美
- 格式:pdf
- 大小:65.19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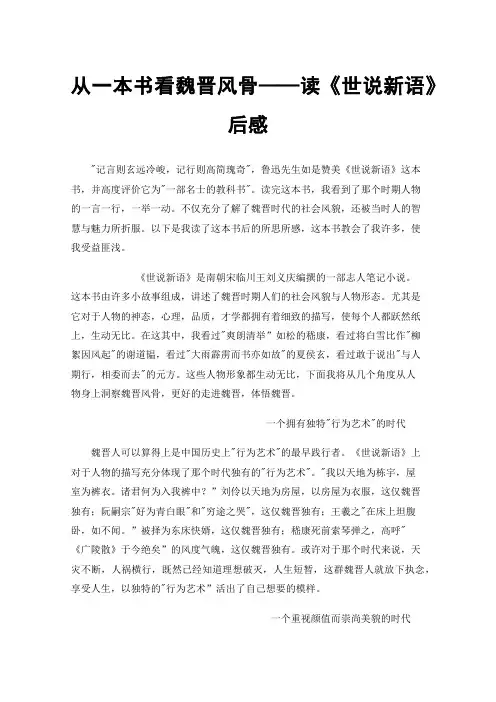
从一本书看魏晋风骨——读《世说新语》后感"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先生如是赞美《世说新语》这本书,并高度评价它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读完这本书,我看到了那个时期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不仅充分了解了魏晋时代的社会风貌,还被当时人的智慧与魅力所折服。
以下是我读了这本书后的所思所感,这本书教会了我许多,使我受益匪浅。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
这本书由许多小故事组成,讲述了魏晋时期人们的社会风貌与人物形态。
尤其是它对于人物的神态,心理,品质,才学都拥有着细致的描写,使每个人都跃然纸上,生动无比。
在这其中,我看过"爽朗清举”如松的嵇康,看过将白雪比作"柳絮因风起"的谢道韫,看过"大雨霹雳而书亦如故"的夏侯玄,看过敢于说出"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的元方。
这些人物形象都生动无比,下面我将从几个角度从人物身上洞察魏晋风骨,更好的走进魏晋,体悟魏晋。
一个拥有独特"行为艺术"的时代魏晋人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行为艺术"的最早践行者。
《世说新语》上对于人物的描写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行为艺术"。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
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刘伶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这仅魏晋独有;阮嗣宗"好为青白眼"和"穷途之哭",这仅魏晋独有;王羲之"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
”被择为东床快婿,这仅魏晋独有;嵇康死前索琴弹之,高呼"《广陵散》于今绝矣”的风度气魄,这仅魏晋独有。
或许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天灾不断,人祸横行,既然已经知道理想破灭,人生短暂,这群魏晋人就放下执念,享受人生,以独特的"行为艺术”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一个重视颜值而崇尚美貌的时代魏晋,是一个出了名的重视颜值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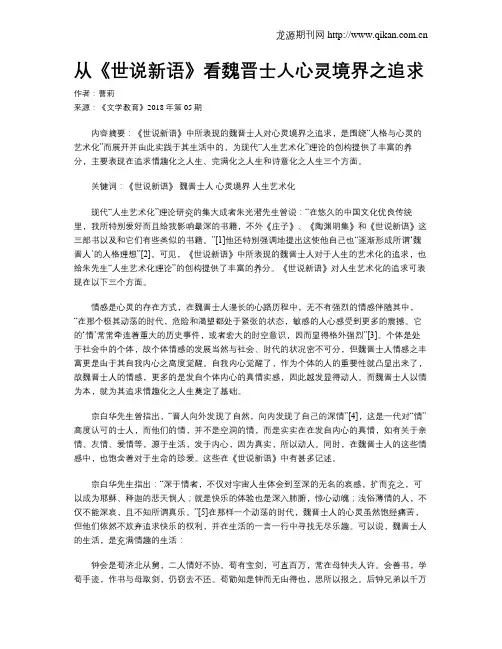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心灵境界之追求作者:曹莉来源:《文学教育》2018年第05期内容摘要:《世说新语》中所表现的魏晋士人对心灵境界之追求,是围绕“人格与心灵的艺术化”而展开并由此实践于其生活中的,为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的创构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主要表现在追求情趣化之人生、完满化之人生和诗意化之人生三个方面。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士人心灵境界人生艺术化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朱光潜先生曾说:“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里,我所特别爱好而且给我影响最深的书籍,不外《庄子》、《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这三部书以及和它们有些类似的书籍。
”[1]他还特别强调地提出这使他自己也“逐渐形成所谓‘魏晋人’的人格理想”[2]。
可见,《世说新语》中所表现的魏晋士人对于人生的艺术化的追求,也给朱先生“人生艺术化理论”的创构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世说新语》对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情感是心灵的存在方式,在魏晋士人漫长的心路历程中,无不有强烈的情感伴随其中,“在那个极其动荡的时代,危险和渴望都处于紧张的状态,敏感的人心感受到更多的震撼。
它的‘情’常常牵连着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宏大的时空意识,因而显得格外强烈”[3]。
个体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故个体情感的发展当然与社会、时代的状况密不可分,但魏晋士人情感之丰富更是由于其自我内心之高度觉醒。
自我内心觉醒了,作为个体的人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故魏晋士人的情感,更多的是发自个体内心的真情实感,因此越发显得动人。
而魏晋士人以情为本,就为其追求情趣化之人生奠定了基础。
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4],这是一代对“情”高度认可的士人,而他们的情,并不是空洞的情,而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的真情,如有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等,源于生活,发于内心,因为真实,所以动人。
同时,在魏晋士人的这些情感中,也饱含着对于生命的珍爱。
这些在《世说新语》中有甚多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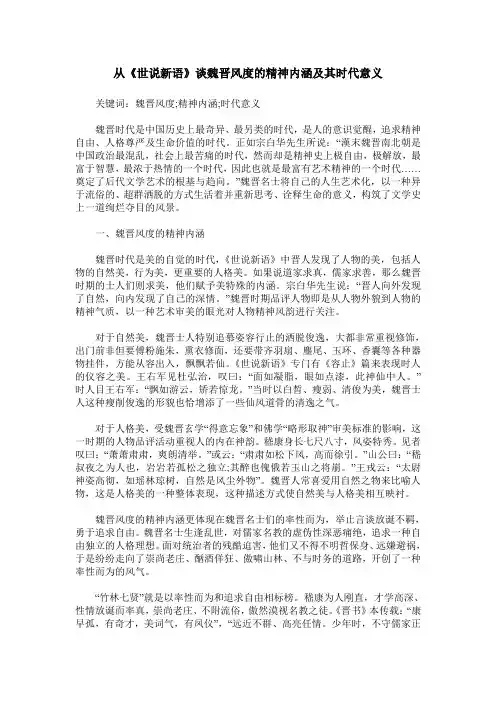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谈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及其时代意义关键词:魏晋风度;精神内涵;时代意义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奇异、最另类的时代,是人的意识觉醒,追求精神自由、人格尊严及生命价值的时代。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漢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魏晋名士将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一种异于流俗的、超群洒脱的方式生活着并重新思考、诠释生命的意义,构筑了文学史上一道绚烂夺目的风景。
一、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魏晋时代是美的自觉的时代,《世说新语》中晋人发现了人物的美,包括人物的自然美,行为美,更重要的人格美。
如果说道家求真,儒家求善,那么魏晋时期的士人们则求美,他们赋予美特殊的内涵。
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魏晋时期品评人物即是从人物外貌到人物的精神气质,以一种艺术审美的眼光对人物精神风韵进行关注。
对于自然美,魏晋士人特别追慕姿容行止的洒脱俊逸,大都非常重视修饰,出门前非但要傅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方能从容出入,飘飘若仙。
《世说新语》专门有《容止》篇来表现时人的仪容之美。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当时以白皙、瘦弱、清俊为美,魏晋士人这种瘦削俊逸的形貌也恰增添了一些仙风道骨的清逸之气。
对于人格美,受魏晋玄学“得意忘象”和佛学“略形取神”审美标准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人物品评活动重视人的内在神韵。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魏晋人常喜爱用自然之物来比喻人物,这是人格美的一种整体表现,这种描述方式使自然美与人格美相互映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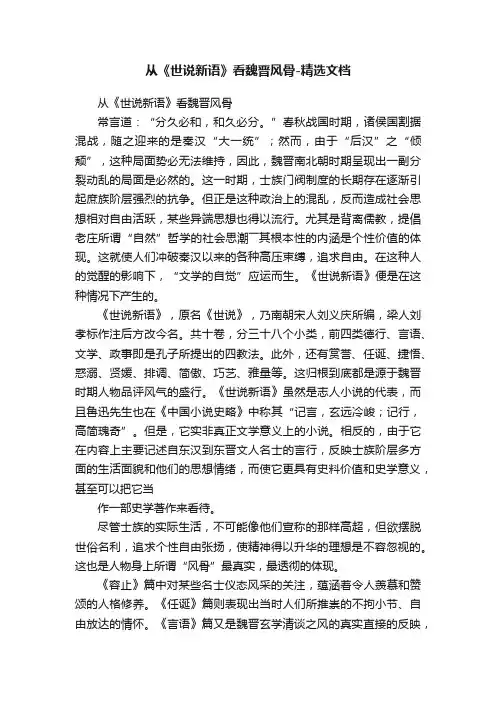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骨-精选文档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骨常言道:“分久必和,和久必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割据混战,随之迎来的是秦汉“大一统”;然而,由于“后汉”之“倾颓”,这种局面势必无法维持,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一副分裂动乱的局面是必然的。
这一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的长期存在逐渐引起庶族阶层强烈的抗争。
但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反而造成社会思想相对自由活跃,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
尤其是背离儒教,提倡老庄所谓“自然”哲学的社会思潮――其根本性的内涵是个性价值的体现。
这就使人们冲破秦汉以来的各种高压束缚,追求自由。
在这种人的觉醒的影响下,“文学的自觉”应运而生。
《世说新语》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乃南朝宋人刘义庆所编,梁人刘孝标作注后方改今名。
共十卷,分三十八个小类,前四类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即是孔子所提出的四教法。
此外,还有赏誉、任诞、捷悟、惑溺、贤媛、排调、简傲、巧艺、雅量等。
这归根到底都是源于魏晋时期人物品评风气的盛行。
《世说新语》虽然是志人小说的代表,而且鲁迅先生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记言,玄远冷峻;记行,高简瑰奇”。
但是,它实非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
相反的,由于它在内容上主要记述自东汉到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反映士族阶层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他们的思想情绪,而使它更具有史料价值和史学意义,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史学著作来看待。
尽管士族的实际生活,不可能像他们宣称的那样高超,但欲摆脱世俗名利,追求个性自由张扬,使精神得以升华的理想是不容忽视的。
这也是人物身上所谓“风骨”最真实,最透彻的体现。
《容止》篇中对某些名士仪态风采的关注,蕴涵着令人羡慕和赞颂的人格修养。
《任诞》篇则表现出当时人们所推崇的不拘小节、自由放达的情怀。
《言语》篇又是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的真实直接的反映,从其言谈中可看出名士们对人生的感悟。
《贤媛》篇更是一反妇女受压迫束缚的常态,使其个性情趣大胆地发挥……魏晋正始以后,人物品评之风大盛,以人物是否有个性、特色为标准,从个体角度,对人的个性、才情、感情加以评价――当时对于人物的个性之美、才情之美尤为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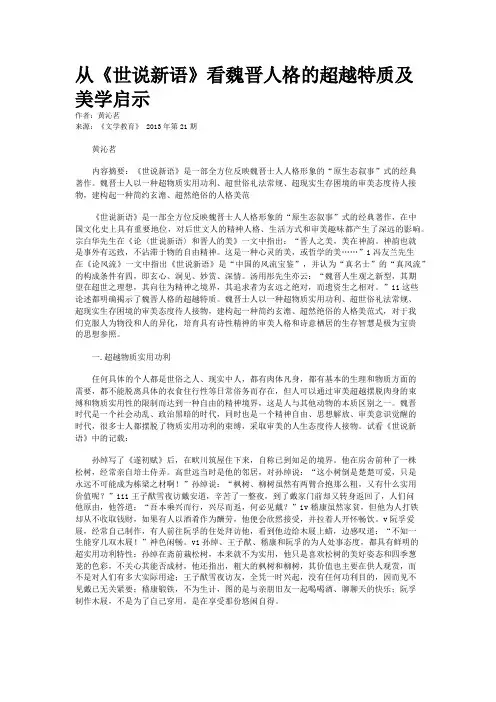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人格的超越特质及美学启示作者:黄沁茗来源:《文学教育》 2013年第21期黄沁茗内容摘要:《世说新语》是一部全方位反映魏晋士人人格形象的“原生态叙事”式的经典著作。
魏晋士人以一种超物质实用功利、超世俗礼法常规、超现实生存困境的审美态度待人接物,建构起一种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人格美范《世说新语》是一部全方位反映魏晋士人人格形象的“原生态叙事”式的经典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人的精神人格、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晋人之美,美在神韵。
神韵也就是事外有远致,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
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i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一文中指出《世说新语》是“中国的风流宝鉴”,并认为“真名士”的“真风流”的构成条件有四,即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汤用彤先生亦云:“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
”ii这些论述都明确揭示了魏晋人格的超越特质。
魏晋士人以一种超物质实用功利、超世俗礼法常规、超现实生存困境的审美态度待人接物,建构起一种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人格美范式,对于我们克服人为物役和人的异化,培育具有诗性精神的审美人格和诗意栖居的生存智慧是极为宝贵的思想参照。
一.超越物质实用功利任何具体的个人都是世俗之人、现实中人,都有肉体凡身,都有基本的生理和物质方面的需要,都不能脱离具体的衣食住行性等日常俗务而存在,但人可以通过审美超越摆脱肉身的束缚和物质实用性的限制而达到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
魏晋时代是一个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精神自由、思想解放、审美意识觉醒的时代,很多士人都摆脱了物质实用功利的束缚,采取审美的人生态度待人接物。
试看《世说新语》中的记载:孙绰写了《遂初赋》后,在畎川筑屋住下来,自称已到知足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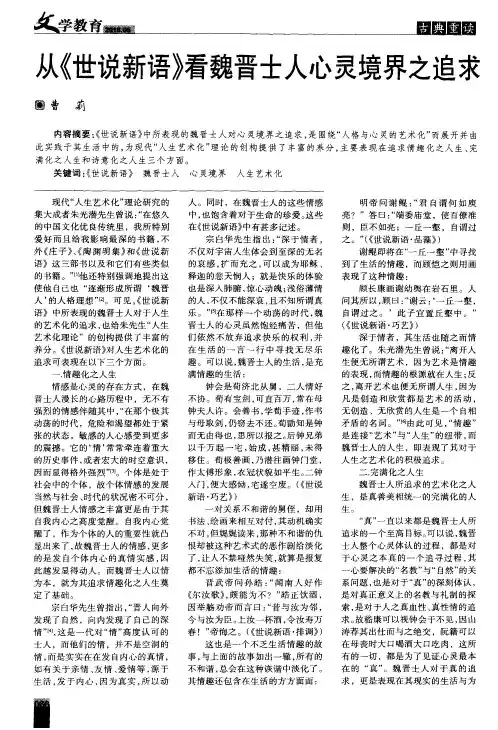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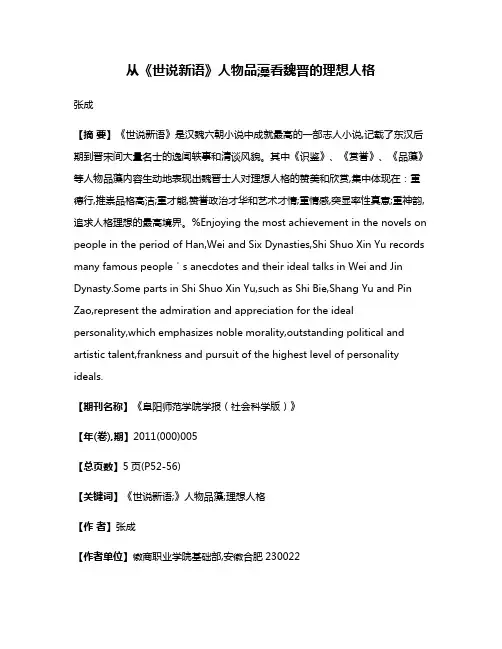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看魏晋的理想人格张成【摘要】《世说新语》是汉魏六朝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志人小说,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间大量名士的逸闻轶事和清谈风貌。
其中《识鉴》、《赏誉》、《品藻》等人物品藻内容生动地表现出魏晋士人对理想人格的赞美和欣赏,集中体现在:重德行,推崇品格高洁;重才能,赞誉政治才华和艺术才情;重情感,突显率性真意;重神韵,追求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
%Enjoying the most achievement in the novels on people in the period of Han,Wei and Six Dynasties,Shi Shuo Xin Yu records many famous people's anecdotes and their ideal talks in Wei and Jin Dynasty.Some parts in Shi Shuo Xin Yu,such as Shi Bie,Shang Yu and Pin Zao,represent the admiration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ideal personality,which emphasizes noble morality,outstanding political and artistic talent,frankness and pursuit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personality ideals.【期刊名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00)005【总页数】5页(P52-56)【关键词】《世说新语;》人物品藻;理想人格【作者】张成【作者单位】徽商职业学院基础部,安徽合肥23002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南朝刘宋宗室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汉魏六朝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志人小说,主要记载汉末、三国至两晋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貌和琐语轶事,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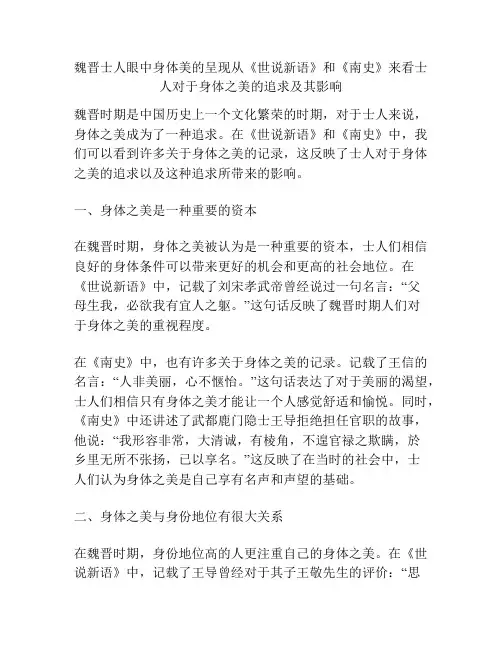
魏晋士人眼中身体美的呈现从《世说新语》和《南史》来看士人对于身体之美的追求及其影响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对于士人来说,身体之美成为了一种追求。
在《世说新语》和《南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身体之美的记录,这反映了士人对于身体之美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所带来的影响。
一、身体之美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在魏晋时期,身体之美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士人们相信良好的身体条件可以带来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刘宋孝武帝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父母生我,必欲我有宜人之躯。
”这句话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身体之美的重视程度。
在《南史》中,也有许多关于身体之美的记录。
记载了王信的名言:“人非美丽,心不惬怡。
”这句话表达了对于美丽的渴望,士人们相信只有身体之美才能让一个人感觉舒适和愉悦。
同时,《南史》中还讲述了武都鹿门隐士王导拒绝担任官职的故事,他说:“我形容非常,大清诚,有棱角,不遑官禄之欺瞒,於乡里无所不张扬,已以享名。
”这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中,士人们认为身体之美是自己享有名声和声望的基础。
二、身体之美与身份地位有很大关系在魏晋时期,身份地位高的人更注重自己的身体之美。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王导曾经对于其子王敬先生的评价:“思客自乡里之味高矣,王敬先生举止本卓,容貌加美,与上交好,意得唐人之贵。
”这个故事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中,身份高的人更注重自己的形象。
《南史》中也记录了司马昭的说法:“若为平民之子,那些好古不却要顾及下降。
然我辈点水晦迹,取之不得,不早为之,后期不足赛。
”这段话反映了身份地位高的人更注重自己的身体之美,并且他们难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所以需要靠自己的外貌和修养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三、身体之美与修养有很大关系在魏晋时期,身体之美也被认为是修养的一种体现,士人们认为通过仪态举止和言谈举止来体现出自己的身体之美。
《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事讲述了刘琨向殷仲堪学习仪态的经历,这个故事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中,良好的仪态举止被认为是身体之美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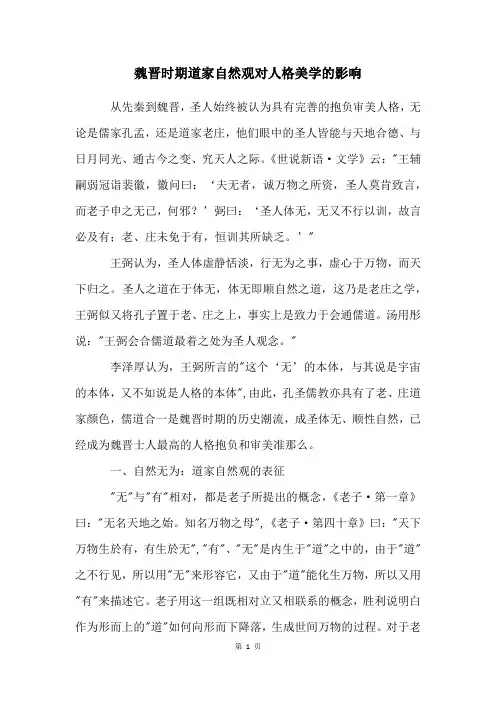
魏晋时期道家自然观对人格美学的影响从先秦到魏晋,圣人始终被认为具有完善的抱负审美人格,无论是儒家孔孟,还是道家老庄,他们眼中的圣人皆能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同光、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世说新语·文学》云:"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行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缺乏。
’"王弼认为,圣人体虚静恬淡,行无为之事,虚心于万物,而天下归之。
圣人之道在于体无,体无即顺自然之道,这乃是老庄之学,王弼似又将孔子置于老、庄之上,事实上是致力于会通儒道。
汤用彤说:"王弼会合儒道最着之处为圣人观念。
"李泽厚认为,王弼所言的"这个‘无’的本体,与其说是宇宙的本体,又不如说是人格的本体",由此,孔圣儒教亦具有了老、庄道家颜色,儒道合一是魏晋时期的历史潮流,成圣体无、顺性自然,已经成为魏晋士人最高的人格抱负和审美准那么。
一、自然无为:道家自然观的表征"无"与"有"相对,都是老子所提出的概念,《老子·第一章》曰:"无名天地之始。
知名万物之母",《老子·第四十章》曰:"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有"、"无"是内生于"道"之中的,由于"道"之不行见,所以用"无"来形容它,又由于"道"能化生万物,所以又用"有"来描述它。
老子用这一组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概念,胜利说明白作为形而上的"道"如何向形而下降落,生成世间万物的过程。
对于老子"无"的理解,陈鼓应说:"‘无’是用来指称‘道',由于’道‘是无形无色而不行见的,所以用’无‘来形容它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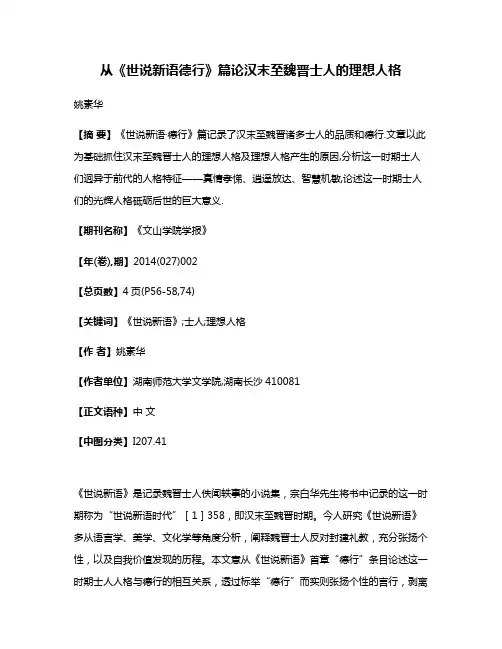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德行》篇论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姚素华【摘要】《世说新语·德行》篇记录了汉末至魏晋诸多士人的品质和德行.文章以此为基础抓住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及理想人格产生的原因,分析这一时期士人们迥异于前代的人格特征——真情孝悌、逍遥放达、智慧机敏,论述这一时期士人们的光辉人格砥砺后世的巨大意义.【期刊名称】《文山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27)002【总页数】4页(P56-58,74)【关键词】《世说新语》;士人;理想人格【作者】姚素华【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1《世说新语》是记录魏晋士人佚闻轶事的小说集,宗白华先生将书中记录的这一时期称为“世说新语时代”[1]358,即汉末至魏晋时期。
今人研究《世说新语》多从语言学、美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阐释魏晋士人反对封建礼教,充分张扬个性,以及自我价值发现的历程。
本文意从《世说新语》首章“德行”条目论述这一时期士人人格与德行的相互关系,透过标举“德行”而实则张扬个性的言行,剥离出时人迥异于其他时期的人格特征。
一、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思想呈现显著的变化趋势,即儒家衰微,玄学兴盛。
士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更是有别于前一时期。
他们的价值判断、为人处世的方式、思想修养和从中表现出的卓尔不群的气质都体现出这个特殊时期人们在人格追求上的不同。
(一)唯德是举《德行》篇第一条目:“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2]1陈蕃上任豫章太守伊始就去看望当时颇具名望的徐孺子,主薄劝他先去太守府,他还是拒绝了,称这是效法武王礼贤下士。
陈蕃作为汉末党人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行代表了这一时期士人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标准。
他身怀“澄清天下之志”,在汉末高举士为天下先的旗帜,以身作则。
周子居更将黄宪誉为如颜回一样的人,郭泰形容其为“汪汪如万顷之波……其气深广,难测量也”[2]4。
颜回是孔门弟子中德行最为高尚的一位,足见黄宪在时人心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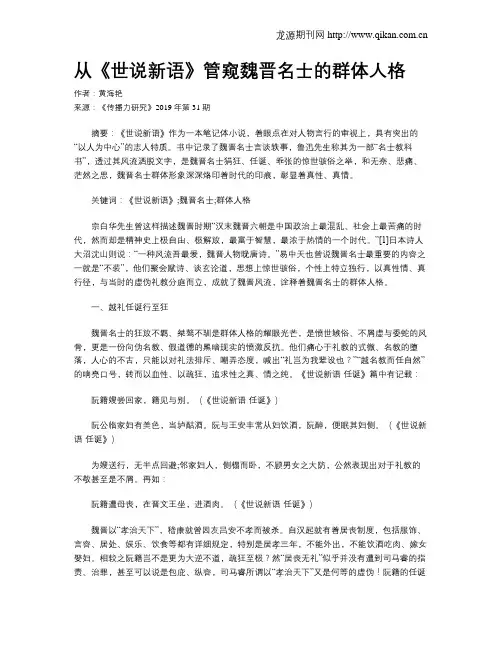
从《世说新语》管窥魏晋名士的群体人格作者:黄海艳来源:《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31期摘要:《世说新语》作为一本笔记体小说,着眼点在对人物言行的审视上,具有突出的“以人为中心”的志人特质。
书中记录了魏晋名士言谈轶事,鲁迅先生称其为一部“名士教科书”,透过其风流洒脱文字,是魏晋名士狷狂、任诞、乖张的惊世骇俗之举,和无奈、悲痛、茫然之思,魏晋名士群体形象深深烙印着时代的印痕,彰显着真性、真情。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士;群体人格宗白华先生曾这样描述魏晋时期“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1]日本诗人大沼沈山则说:“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
”易中天也曾说魏晋名士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不装”,他们聚会赋诗、谈玄论道,思想上惊世骇俗,个性上特立独行,以真性情、真行径,与当时的虚伪礼教分庭而立,成就了魏晋风流,诠释着魏晋名士的群体人格。
一、越礼任诞行至狂魏晋名士的狂放不羁、桀骜不驯是群体人格的耀眼光芒,是愤世嫉俗、不屑虚与委蛇的风骨,更是一份向伪名教、假道德的黑暗现实的愤激反抗。
他们痛心于礼教的式微、名教的堕落,人心的不古,只能以对礼法排斥、嘲弄态度,喊出“礼岂为我辈设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响亮口号,转而以血性、以疏狂,追求性之真、情之纯。
《世说新语·任诞》篇中有记载: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
(《世说新语·任诞》)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
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
(《世说新语·任诞》)为嫂送行,无半点回避;邻家妇人,侧榻而卧,不顾男女之大防,公然表现出对于礼教的不敬甚至是不屑。
再如: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
(《世说新语·任诞》)魏晋以“孝治天下”,嵇康就曾因友吕安不孝而被杀。
自汉起就有着居丧制度,包括服饰、言容、居处、娱乐、饮食等都有详细规定,特别是居孝三年,不能外出,不能饮酒吃肉、嫁女娶妇。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个性美和情感美作者:云月映来源:《新课程·教育学术》2009年第05期汉末以来,由于兵连祸结,岁无宁日,人们的人生观念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他们不再像以前的文人那样关注着这个多灾多难的社会,而是把眼光转向主体本身,产生并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于人的自觉意识,关于生命的自觉意识。
一、对人的个性的重视,并十分重视个性的张扬现在不少研究已经指出,先秦儒家在强调社会伦理的同时也提倡人的主体性,如孔夫子说的“吾欲仁,斯仁至矣,”孟夫子说的“吾善养浩然之气”便是很好的说明,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并对个体的行为作了种种严格的限制,所谓的君子形象却让人觉得是那样的做作,那样的僵硬,那样的冷冰冰,根本不像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与其说这是个人,还不如说是礼教塑造出来的一个呆板无比的雕像。
而魏晋时代是一个由战争、饥馑,死亡、阴谋、残忍、悲歌慷慨、背信弃义、寻欢作乐、潇洒风流等众多元素组合在一起的畸形儿,由于社会的动乱,政治的黑暗,这也使得士人们认识到了礼教的虚伪本质,因此士人们对这个社会现实,对束缚人的传统礼教彻底地失望了,而此时人的意识已觉醒的他们也不想因为进行徒劳的抗争而白白送命,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去逃避这个让人绝望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想给自己无助的精神寻找一个新的归宿,基于以上目的,他们信奉老庄,寄情山水。
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传统的礼教束缚已趋于松弛,先前那种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变得空前活跃起来。
由于魏晋士人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极端鄙视以往所谓的正人君子的那股酸腐迂顽之气。
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有一段精彩非常的虱子之论。
阮籍把愚守儒家礼法、行为循规蹈矩的君子视为“虱子处乎军中,逃乎深缝,匿夫坏絮,自以为吉宅也。
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者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
二、《世说新语》中的自然之美我们先来欣赏《世说新语》里面写的自然之美。
刚才我们说过《世说新语》其实是一部志人小说,它没有专门写自然之美的文字。
但是在写人物的时候常常也会写到自然之美,虽然不多,但是都写得非常精彩,有的是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来的。
我们看的第一条是“言语”篇第88 条: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这段文章可能同学们看到过,是写景的有名的名句。
这个顾长康是谁呢?顾长康就是当时著名的画家顾恺之,小名叫作虎头。
那么在画家的眼中这个会稽,我们现在绍兴这一带,山水是非常之美的,所以他有这样的评论。
第二条我们来看“赏誉”篇的第 15 条: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至疑隙。
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
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什么叫“行散”呢?这是魏晋时候名士们的一种日常的活动。
行就是走路,散就是当时的一种药物,叫作“五石散”,又称为“寒石散”。
它是由五种矿物质合在一起做成的一种药,叫“五石散”,大概是做成粉末状的,所以叫“散”。
当时的人相信这个“五石散”是对身体有益的,是可以养生的,所以就经常吃。
这个矿物质的药物是很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吃完以后就要走路,让它能够消化掉,这个就叫作“行散”。
所以当时的人经常行散,去走,走到后来要出汗。
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洗澡的条件,经常出了汗也不洗澡,所以当时很多人身上都会长虱子,即使是很有名的一些名士也会长虱子。
王恭有一次行散到了京口射堂这个地方。
大家看当时的自然景象是什么样的呢?《世说新语》就用了八个字来描写:“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早晨有露水,桐树刚刚长出新芽。
虽然只是简单的八个字,但是让我们可以想象到春天早晨这种美景。
所以王恭看到这样的美景,又看到他的老朋友王忱就说了一句:“王大故自濯濯。
”“濯濯”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同学们其实可以自己想象。
下面一条是“言语”篇的83 条: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两朝审美风尚的变迁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乱世,可思想却是高度的自由开放。
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
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
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
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
《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
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
”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
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
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
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
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
《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