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
- 格式:doc
- 大小:36.5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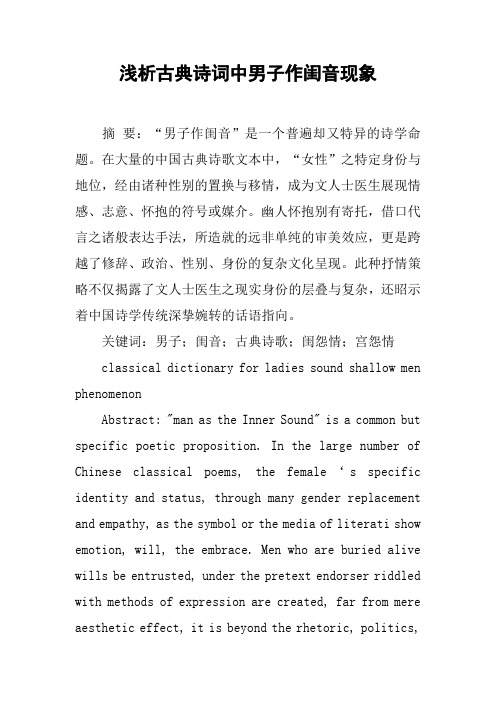
浅析古典诗词中男子作闺音现象摘要:“男子作闺音”是一个普遍却又特异的诗学命题。
在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文本中,“女性”之特定身份与地位,经由诸种性别的置换与移情,成为文人士医生展现情感、志意、怀抱的符号或媒介。
幽人怀抱别有寄托,借口代言之诸般表达手法,所造就的远非单纯的审美效应,更是跨越了修辞、政治、性别、身份的复杂文化呈现。
此种抒情策略不仅揭露了文人士医生之现实身份的层叠与复杂,还昭示着中国诗学传统深挚婉转的话语指向。
关键词:男子;闺音;古典诗歌;闺怨情;宫怨情classical dictionary for ladies sound shallow men phenomenonAbstract: "man as the Inner Sound" is a common but specific poetic proposition. In the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ms, the female‘s specific identity and status, through many gender replacement and empathy, as the symbol or the media of literati show emotion, will, the embrace. Men who are buried alive wills be entrusted, under the pretext endorser riddled with methods of expression are created, far from mere aesthetic effect, it is beyond the rhetoric, politics,gender, identity, the complexity of cultural presentation. Such lyrical strategy not only reveals the literati of the real identity of the layered and complex, yet clear to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in abundance mildly words point to.Keywords: Men Inner voice, classical poetry, the woe in the situation, palace a complaint第一章男子作闺音的内涵及特点一、内涵翻阅诗骚乐府,检诸唐诗宋词,就像旧时戏曲中的女性角色老是由男优扮演一样,“男子作闺音”作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也一样遍及文人写作的诸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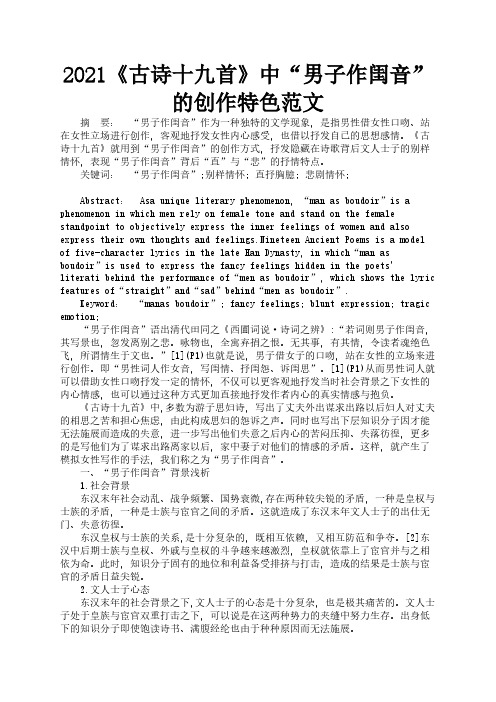
2021《古诗十九首》中“男子作闺音”的创作特色范文 摘要: “男子作闺音”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是指男性借女性口吻、站在女性立场进行创作, 客观地抒发女性内心感受, 也借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古诗十九首》就用到“男子作闺音”的创作方式, 抒发隐藏在诗歌背后文人士子的别样情怀, 表现“男子作闺音”背后“直”与“悲”的抒情特点。
关键词: “男子作闺音”;别样情怀; 直抒胸臆; 悲剧情怀; Abstract: Asa unique literary phenomenon, “man as boudoir”is a phenomenon in which men rely on female tone and stand on the female standpoint to objectively express the inner feelings of women and also express their own thoughts and feelings.Nineteen Ancient Poems is a model of five-character lyrics in the late Han Dynasty, in which“man as boudoir”is used to express the fancy feelings hidden in the poets'literati behind the performance of“men as boudoir”, which shows the lyric features of“straight”and“sad”behind“men as boudoir”. Keyword: “manas boudoir”; fancy feelings; blunt expression; tragic emotion; “男子作闺音”语出清代田同之《西圃词说·诗词之辨》:“若词则男子作闺音,其写景也, 忽发离别之悲。

怎样看待男子作闺音的现象一男子作闺音”首先应该出自对社会中自我的观照,以为女性代言来感慨男子自己的臣妾态。
所谓臣妾心态,就是一种附依于君主的心态。
这种心态,往往是男性作家自拟女性的行为、心理来加以表现。
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带来了以夫妻关系比附君臣关系的思维定势。
封建社会的男子实际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就其在男女、夫妇关系中说,他们是阳,而就其作为人子、人臣的地位而言,他们只能属阴。
士人们在朝中为人臣的感受与女子在家中的感受何其相似,如此便使他们产生了对女性角色的心理认同。
尤其是当他们怀才不遇,遭君主弃用时,更让他们视自己如同弃妇、怨妇。
久而久之,这些“政治失恋”的士大夫们假托弃妇贱妾之口寄托自己对夫主的或爱或恨或恋或怨的不同情怀,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二男子作闺音”也由于有很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人类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反思和认识。
如晏殊的《浣溪沙》感发:“一曲新词酒一怀,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
”词人较少眷恋功名事业,相反对其流露出厌倦之情。
连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也在词中说:“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耽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青楼约”。
像柳永等落魄文人表现得更强烈。
比如柳永在《夏云峰》说:“名缰利锁,虚费光阴”。
文人对生命的认识,更多体现为伤时、伤景,与女子青春易逝相仿,因此有共同的语言。
为女子伤春和为自己悲秋其实是一种心态。
三“男子作闺音”是词人们对爱情与婚姻和谐统一的执着及其不能实现的绝望。
“男子作闺音”的作品中,绝大多数是恋情词。
这应该是有词人对爱情的一种独有的深刻价值观。
对许多男人来说,爱情和事业是人生的两大追求,其实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均是自我确认的方式。
古代的婚姻多是出于家族的需要,很少出自感情的因素。
就像席慕蓉的《无题诗》所说:“爱/原来就为的是相聚/为的是不再分离”一样,我也可以看到那些作闺音的男词人的相同心态。

浅析花间词中的“男子作闺音”现象摘要:本文将从文学传统、词体特征、花间词中大胆的爱情意识表现及男子自我意识的衰退等方面对“男子作闺音”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男子闺音文学爱情“男子而作闺音”,出自清代学者田同之《西圃词说·诗词之辨》[1],用来概括男性文人代女性设辞,假托女性的身份、口吻,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
花间词出现在晚唐五代,花间词人都是男性,他们所著的词都是以女性的口吻来表现女性婚姻生活或对爱情的渴望或思念丈夫的心情等,男子演绎女声词境成为主流。
一、“男子作闺音”的文学传统什么是“男子作闺音”,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中的女巫装扮成男女诸神,在神秘的气氛中进行歌舞剧式的代言和表演[2]。
而中国文学早在《诗经》、楚辞时期就已有了性别意识,其中不少篇什咏赞了女性美,如诗经国风中的《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到了东汉,更出现了男性诗人以女子自述的口吻进行写作的现象,体现出一种不自觉的“性别越界”趋势。
从文论的角度来说,注意到这一现象是在六朝。
徐陵在宫体诗集《玉台新咏》的序文中[3],通过虚构一位姿容美丽、富于才情的佳人形象阐述了选诗标准。
“其中有佳人焉……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
……加以天时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
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
清文满箧,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葡萄之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辞。
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
……选录艳歌,凡为十卷。
”在他看来,宫体诗就是歌咏爱情与描写女性生活的诗作。
到了晚唐五代兴起的花间词承继了宫体诗“男子而作闺音”的审美趣味和写作方式。
二、“男子作闺音”是词体“应歌而制”的要求“应歌而制”的特定要求,也是造成男子作闺音的一个主要原因。
词的全称是“曲子词”,它是配合音乐(曲子)而歌唱的新体歌辞。
文人词最早是在贵族的酒筵歌席上创作演唱的,先由文人根据曲调作词,然后交付乐工歌妓伴奏演唱。

“男子作闺音”——论沈从文湘西小说女性形象创
作的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创作涉及多种题材,但以湘
西山村小说最为著名。
沈从文的小说中,女性形象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对象。
与传统的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塑造有所不同,沈从文的女性形象更
加真实、具体、生动,展现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人格特征。
其中,沈从文有时候会运用“闺音”等手法,让男性形象化身为女性,来描绘
女性形象,展现其细腻、柔情、柔弱之处。
因此,本文将从沈从文湘西
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对女性形象创作的影响,以期有
利于对沈从文小说中女性形象创作的理解和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现象,探讨其对
女性形象创作的影响,解析作家的写作技巧和创作思路,进一步深入认
识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塑造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1.研究内容:本文将通过对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特点及
其表现手法进行分析,进而从情感、性别、文化等角度探讨其对女性形
象创作的影响。
2.研究方法:本文将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实证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
对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男子作闺音的现象、女性形象的塑造和作家思想进
行深入探究,从而形成科学、系统的研究结论。
四、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
1.进一步丰富对沈从文小说的理解和认识,增进文学爱好者的审美和阅读体验;
2.深入探讨中国文化中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高社会公众对性别平等的认识;
3.为后续反思性别与文化的关系、提高女性地位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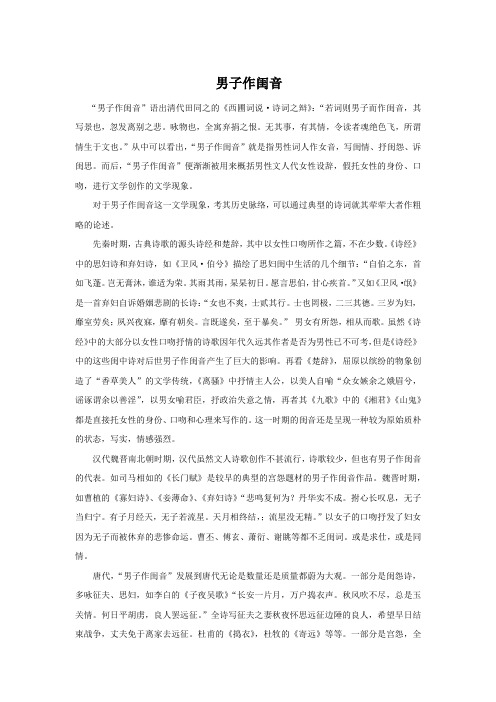
男子作闺音“男子作闺音”语出清代田同之的《西圃词说·诗词之辩》:“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
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
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
”从中可以看出,“男子作闺音”就是指男性词人作女音,写闺情、抒闺怨、诉闺思。
而后,“男子作闺音”便渐渐被用来概括男性文人代女性设辞,假托女性的身份、口吻,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现象。
对于男子作闺音这一文学现象,考其历史脉络,可以通过典型的诗词就其荦荦大者作粗略的论述。
先秦时期,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和楚辞,其中以女性口吻所作之篇,不在少数。
《诗经》中的思妇诗和弃妇诗,如《卫风·伯兮》描绘了思妇闺中生活的几个细节:“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岂无膏沐,谁适为荣。
其雨其雨,杲杲初日。
愿言思伯,甘心疾首。
”又如《卫风·氓》是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男女有所怨,相从而歌。
虽然《诗经》中的大部分以女性口吻抒情的诗歌因年代久远其作者是否为男性已不可考,但是《诗经》中的这些闺中诗对后世男子作闺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再看《楚辞》,屈原以缤纷的物象创造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离骚》中抒情主人公,以美人自喻“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以男女喻君臣,抒政治失意之情,再者其《九歌》中的《湘君》《山鬼》都是直接托女性的身份、口吻和心理来写作的。
这一时期的闺音还是呈现一种较为原始质朴的状态,写实,情感强烈。
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虽然文人诗歌创作不甚流行,诗歌较少,但也有男子作闺音的代表。
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是较早的典型的宫怨题材的男子作闺音作品。
魏晋时期,如曹植的《寡妇诗》、《妾薄命》、《弃妇诗》“悲鸣复何为?丹华实不成。
拊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
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
天月相终结,;流星没无精。
”以女子的口吻抒发了妇女因为无子而被休弃的悲惨命运。
写与被写:古代诗歌中“男子作闺音”的文化诗学透析张晓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摘要:古代诗歌作品中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作品绝大多数出自男性作家之手,这是中国文学特有的现象。
本文以男性创作的“怨妇诗”为例,分析阐述了“男子作闺音”两个方面的内容,并对这种独特现象进行了诗学的和文化的解读。
关键词:怨妇诗 ;男子作闺音 ;比兴寄托 ; 文化传统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诗歌作品,自三百篇以来屡见不鲜。
其中绝大部分是“怨妇诗”,描写的大都是:美人被弃,征夫思妇,倩女怀愁,妾身薄命的悲叹,色衰爱弛的抱憾……,哀怨感伤色调极为明显。
翻开诗经乐府,检索唐诗宋词,无论是描绘贫家女子,商人、征人妻子,还是抒写闺中名媛、青楼歌妓,传达的皆是女子对于爱情的执着与期待,乏人怜爱的寂寞苦闷和失望失宠的哀怨自怜。
按说作者应是闺中女子,才显得自然真切,但发人深省的是这些诗歌绝大部分却是出自男性之手。
几乎都是文人士子们代怨妇,借怨妇立言立心,而且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站在女子的立场上为她们书写内心的离愁别怨;一是“托志帷房”,“写怨妇思妇之怀,寄孽子孤臣之感”。
那么,为什么会有又如何解释“男子作闺音”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男性作者又是怎样处理自己与抒情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的呢?本文试图以“怨妇诗”为切入点,对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进行诗学的和文化的考察。
一、代替与摹拟:男子作闺音的无“我”之境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诗歌创作中的“男子作闺音”就是一个明证。
有学者将这种男子代替和摹拟女主人公的创作体式叫做“代言体”。
这种体式的特征是:多是用第一人称,完全站在女子的立场上,代她们发言、代她们喜怒哀乐,笔触细腻,含蓄委婉。
单就怨妇诗来看,诗歌中的女主人公,经历了由民间向朱门与青楼的转变。
早期闺怨诗大量涉及的是民间女子。
《诗经》里写弃妇的《邶风·谷风》、《卫风·氓》,写思妇的《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都是经典之作。
古典诗歌中的“男子作闺音”现象考察——以《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为中心成伟(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摘要:《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妇诗体现了独具特色的“男子作闺音”现象。
汉末文人以女性的口吻、身份和心境进行创作,对女性丰富敏锐的心灵和情感进行深入的剖析,传达出作者的人生感受和精神苦闷,为此后拟女性创作的发展与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男子作闺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底层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得不到实现,他们往往将内心的愁苦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代表作《古诗十九首》不仅呈现了汉末时期文人士子的生命意识,而且突出了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尤其是在写离别、失意的思妇诗中集中出现了独具特色的“男子作闺音”现象。
一、《古诗十九首》中“男子作闺音”现象产生的原因东汉中后期政治腐朽,宫廷争斗不断,党锢之祸更甚,外族入侵,战乱频繁,无辜生命被屠杀,加之自然灾害不断,致使社会动荡不安。
在桓灵时期尤为严重,外戚、宦官更是“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1](41),官僚集团垄断仕途,社会买官公行的黑暗现象,下层文人无法跻身庙堂,使得大多数士人政治出路日趋狭窄,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士人“兼济天下”的美梦也随之变为泡影。
这一时期的党锢之祸对文人的打击甚是沉重,就第二次“党锢之祸”而言,前次的众多党人都被折磨致死,“妻自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害,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2](p132)由此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到汉末党锢之祸对文人身心的伤害之深。
政治上外戚把持朝政,所实行的选举制度,实为豪强把持。
因而也就导致了中下层知识分子无缘被选举的现象。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如泥,富第良将怯如鸡”的童谣真实地表现了当时选举制度黑暗的程度。
政治、社会及自然重重因素使士人追求功名的理想在现实中被击碎,政治抱负无法伸展,加之残酷的党锢之争,使得文人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产生迷茫感。
“男子而作闺音”——对唐宋词中的一种文学现象的理解关键词:男子而作闺音、女性、审美、历史语境、闺怨摘要: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男子而作闺音现象数不胜数,在最为瑰丽的唐宋诗词部分,此现象更是值得关注。
本文将从对各学者作出的阐述进行理解、分析,并从作者人格结构、审美心态、创作行为入手,将文本、作者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考察,全方面理解男子而作闺音这一现象。
“男子作闺音”就是指男性此人作女音,写闺情、抒闺怨、诉闺思。
“男子作闺音”语出清代田同之的《西圃词说·诗词之辨》:“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
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
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
”但是只要翻翻文学史就会发现,“男子作闺音”现象在诗赋创作中非常普遍,跌见不鲜。
这就使其超出了单纯的文体风格的论域,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普遍而独特的命题。
大体上来说,“男子作闺音”这种古代文人代妇女或借妇女立言的书写实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创作主题模仿历史女性声音或代替女性抒发相思离愁,爱恨情仇,意向选择上带有明显的女性心理性格特征,内容上则多写女性的思慕与闺怨。
另一类则是“言此意彼”,就是所谓的“托志帏房”,似写怨夫思妇之情怀,实写孽子孤臣之感。
对于古典诗歌中大量存在的男子作闺音现象,对于文人士大夫为什么要在诗歌创作中以妾妇自居,又为什么采用这种“迂回”的言说策略,已有学者对此作出阐释,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寄托说”,这种观点认为,《诗经》以比兴抒情创其始,屈原的“香草美人”扬其波,到汉乐府诗歌,代抒闺怨的作品就渐渐发展为中国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题材,后来作为一种手法渐渐凝固转化为模式化的比兴思维,男性诗人可以很方便、很熟悉地借思妇的身世和口吻来表达他们自己的遭遇。
第二种观点称为“文体说”,这种观点主要是针对词的创作来说的。
论者认为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它的审美效应必须靠歌妓的演唱来实现,为了适应这种女音演唱的要求,文人学士便纷纷“男子而作闺音”——直接以女性的身份口吻说话,在词里写女性题材,妨女性腔调,抒女儿柔情,从而使得词的主题风格柔化、女性化,归于艳丽婉转一路,促使男子作闺音的繁荣。
在他们看来,唐宋词中存在着大量男性作家为女性代言的作品,与词最初诞生的酒宴歌席的环境及由女性歌手演唱的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此种现象的产生实际是“自律”要求所致。
第三种观点是“同情说”。
这种观点是杨义在探讨李白的代言体诗歌时提出的。
杨义认为,在古代中国,女性处于边缘地位,不过是男性的陪衬和附庸。
她们不仅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与创作的权利,而且彼时女性的爱情生活是很不幸:或远人长期不归,或郎君薄情背弃,凄楚哀怨、抑郁愁闷是其感情生活的主旋律。
命运不幸而又蕙质兰心的女性自然会赢得男性的怜爱与同情,进而产生为之代言的创作欲望,模仿其形态抒发柔情哀意。
这种创作欲望使他们主动关心女性,设想其处境,主动为之代言。
杨义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男扮女装”一方面自然出自对思妇、怨妇和弃妇的同情,而另一方面,又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发出了一个被冷落了群体的声音,宣泄了一种被压抑而积郁着的情感。
第四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双性情感说”。
认为人的内心世界是丰富而且多层面、多素质的,每个人身上都存着阳刚、阴柔两种对立的基因,都具有男性和女性双重气质,即“双性人格”。
当那些男性诗人文士们化身为女子的角色而写相思怨别的诗歌时,往往无意间流露他们自身隐含的怨妇心态。
最后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女权说”。
认为男子作闺音现象中包含着主流话语对“他者”的排斥和压制。
首先是女性在文本中的物化和虚拟性。
文本中的抒情主人公虽然是女性,却被迫女扮男装,诉说着男性诗人心中事;文本后的抒情主体分明是男性,却又男扮女装把自己的哀怨不平强加于女性,占据和取代了女性的表达和言说,使得“女性”落入双重假像的罗网。
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最为瑰丽的唐宋诗词中,男子而作闺音现象更是数不胜数,在极具影响力的诗人或是词人的诗中,也是屡见不鲜。
北宋史称其为人“刚简”的名相晏殊, 因为善于写宛转妩媚, 带有女性声腔的词作, 而被王安石批评为有失身份, 说: “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尽管晏殊的儿子晏几道为其父辩解: “先公平日, 小词虽多, 未尝作妇人语也。
”哪知偏有一位蒲传正听后不服气, 举出晏殊《玉楼春》词中两句: “绿杨芳草长亭路, 年少抛人容易去。
”反问小晏道: “岂非妇人语?”。
被人们尊为词坛豪放派的开山之祖的苏轼, 其《东坡乐府》现存的三百四十多首词中, 豪放词竟不足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 而较多的却是明丽、妩媚的婉约词, 且多上乘之作。
正如贺裳《皱水轩词笙》云: “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
然其《浣溪沙·春闺》曰:‘彩索身轻常趁燕, 红窗睡重不闻莺’。
如此风调, 令十七八女郎歌之, 岂在‘晓风残月’之下”。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也未能跳出男女恋情, 离愁别恨的格调, 吟唱: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之类的华艳闺情。
而刚毅执拗的政治家王安石也在《谒金门》(“红笺寄与添烦恼, 细写相思多少。
醉后几行书字小, 泪痕都了”) 中不知不觉地使用“柔丽之语”抒写离别相思之情。
那究竟这些文人士大夫是什么样的心理?前文所述的五种观点究竟经不经的起推敲呢?这些论述我们不难看到:研究者或者拘执于外部的视角,认为是古代中国特殊社会伦理特征决定了男子作闺音的抒情方式;或者仅仅是着眼于内部的视角,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文学自律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文本的产生不是作家和历史语境的“函数”,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定的环境就产生一定的行为,这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
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现象是文学传统自身发展的结果,不考虑外在的语境的作用,这种类似于形式主义的满足于文本和文学自足的方式显然也是狭隘的。
就男子作闺音的现象而言,只有从创作主题的人格结构、审美心态、创作行为入手,将文本、作者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考察才会更具考察与解剖的效力。
我们先看词产生的背景。
词起源于唐代中期的“曲子词”, 它是配合音乐而歌唱的一种新体歌辞。
供歌者在花间尊前演唱, 以达到赏心悦目的娱乐效应。
直到唐末出现被宋人尊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才奠定了婉约词的基本风格。
在《花间集》的序言中,五代后蜀词人欧阳炯是这样描绘作词的环境与动机的, “则有绮筵公子, 绣幌佳人, 递叶叶之花笺, 文抽丽锦; 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词, 用助娇娆之态。
”就是说,豪门贵族的公子、佳人们, 将词写在花笺上,举起纤细的玉指, 按着板拍来唱。
他们所写的都是清丽的文辞, 用以配合娇柔的舞姿。
可见词作的目的开始是为了应歌。
文人词既然诞生于这样“莺哼燕舌”的音乐环境中, 它自然会“屈从”于女性歌唱的需要, 使词的主题、风格、语言乃至声腔都服从并满足于她们的特殊需要。
正因如此, 才形成了词的风格偏向于轻软、阴柔、婉约。
宋代词坛承袭晚唐五代“花间派”词风。
宋王朝于公元960 年建立后, 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社会财富和生产水平逐渐超过了历史上的汉代和唐代, 出现了城乡区别,中国市民阶层兴起, 宋都城东京( 河南开封)出现市民的游艺娱乐场所——瓦市, 瓦市最重要的伎艺之一是演唱通俗歌词的“小唱”, 它以抒情方式表达了市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 深受民众的欢迎。
尤其是当女艺人语娇声颤、字真韵正地演唱起来能产生特殊的美感效果, 可起消遣与娱乐的作用, 使人们能在紧张的劳动之后或繁忙公务之余, 得到身心的休息。
在这种场合, 人们是不愿接受政治道德教化的, 由于接受群众基本上都是男性, 于是娇美的歌伎,艳科的内容, 通俗的演唱, 便最能满足男性的审美需要。
由此, 词体文学围绕着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爱情, 迅速繁荣起来。
但是, 以上只是从历史的背景方面来分析, 同时, 我们还应注意到, 在词人好作“闺音”的创作潮流深处, 毕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新观念、新信息。
否则, 它无法成为文学史上一种合理的存在, 也不能因此而创作出许多受人赞赏的优秀词篇。
首先, 词中涌现出“男子而作闺音”的作品, 有一部分只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也就是说, 正是某种共同的时代心理和审美趣味, 暗暗驱使这些词人, 使他们不约而同、习惯成自然地写下了这些为女性“代言”其心声的作品。
一方面, 是人们常说的“比兴”、“寄托”, 比如辛弃疾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 》, 词中, 他将自己“化”为一位失宠的后妃, 用女性伤春的哀怨口吻倾吐他对国势不振的忧急。
其实, 用“香花美人”喻托自己的政治情怀, 最早可追溯到屈原的《离骚》, 可谓由来久矣。
可见, 作者并非真有兴致描摹女性心态, 只是一种委婉的“比兴寄托”的创作传统。
另一方面, 与这传统截然不同的是作者饶有兴趣地刻画妇人心态, 不为寄托, 只是纯粹的一种趣味, 因而它的“女性”特征更加明显, 艺术境界也更臻丰满、细腻。
以李后主的《菩萨蛮》为例, 明明是他向小周后调情, 却写成小周后向他“乞怜”(“奴为出来难, 教君恣意怜”) 。
它的背后是一股低级趣味的向女性调情意识及把词作为抒发猎艳之情的工具来利用, 显然是不健康而消极的。
其次, 词中“男子而作闺音”的作品, 不管怎样, 多少也体现了社会对于妇女的注目和关心。
中国封建社会, 向来男尊女卑, 因此,妇女的命运、痛苦, 妇女的喜怒哀乐的内心世界, 在文学上, 除了民歌之外, 一直少人问津, 为男性作者所遗忘。
这种情况, 直到唐代才开始有所改观: 唐人传奇如《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以女性为主角的名篇, 不少“宫怨”、“闺怨”诗和元、明一些妇女诗篇,已开始触及妇女问题, 这无疑是文学表现领域的一种开拓。
而到了唐宋词中, 很多士大夫作者不惜彻底放下架子, “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地体味女性内心世界, 并不惮于丢失自己的“身份”, 为那些地位低微的歌妾立言,这本身就可视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比如长期混迹于下层社会的柳永, 他对女性就抱有了更多的同情和关心, 甚至还与她们结下深挚的友谊和恋情。
生前, 他和很多知心女友固然是两情缱绻, 而在死后, 也是由她们集资安葬, 这样的“生死之交”, 自然触发了柳永的深情。
他在《定风波》一词中, 倾吐了深深的祝愿: “镇相随, 莫抛躲, 针线慵拈伴伊坐。
和我, 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在歌妓而言,不啻是“爱情至上”的宣言, 而就柳永来说,也显露了他那种有别于一般文人对侍妾所持的“垂爱”态度, 多少带有“平等”意味的较新的“妇女观”和“恋爱观”。
这种新的思想意识影响着广泛的文人作者, 是社会日益进步、人性抬头所带来的思想观念方面变化而体现在词作上。
结合词产生的背景、作者的审美心态、创作行为来看,男子而作闺音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