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米勒的_文学终结论_
- 格式:pdf
- 大小:254.97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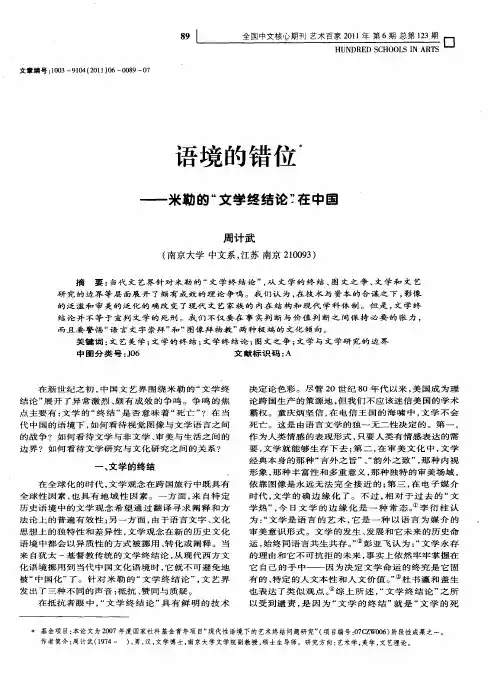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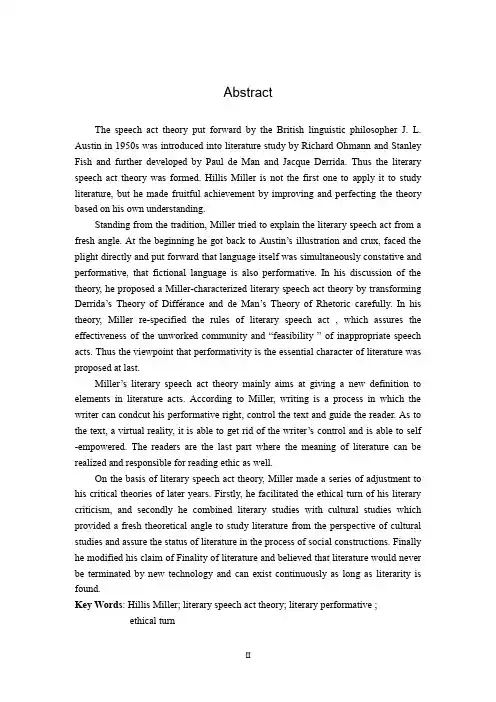
AbstractThe speech act theory put forward by the British linguistic philosopher J. L. Austin in 1950s was introduced into literature study by Richard Ohmann and Stanley Fish and further developed by Paul de Man and Jacque Derrida. Thus the literary speech act theory was formed. Hillis Miller is not the first one to apply it to study literature, but he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 by improving and perfecting the theory based on his own understanding.Standing from the tradition, Miller tried to explain the literary speech act from a fresh angle. At the beginning he got back to Austin’s illustration and crux, faced the plight directly and put forward that language itself was simultaneously constative and performative, that fictional language is also performative.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he proposed a Miller-characterized literary speech act theory by transforming Derrida’s Theory of Différance and de Man’s Theory of Rhetoric carefully. In his theory, Miller re-specified the rules of literary speech act , which assu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nworked community and “feasibility ” of inappropriate speech acts. Thus the viewpoint that performativity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was proposed at last.Miller’s literary speech act theory mainly aims at giving a new definition to elements in literature acts. According to Miller, writing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writer can condcut his performative right, control the text and guide the reader. As to the text, a virtual reality, it is able to get rid of the writer’s control and is able to self -empowered. The readers are the last part where the meaning of literature can be realized and responsible for reading ethic as well.On the basis of literary speech act theory, Miller made a series of adjustment to his critical theories of later years. Firstly, he facilitated the ethical turn of hi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secondly he combined literary studies with cultural studies which provided a fresh theoretical angle to study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assure the status of literatur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onstructions. Finally he modified his claim of Finality of literature and believed that literature would never be terminated by new technology and can exist continuously as long as literarity is found.Key Words: Hillis Miller; literary speech act theory; literary performative ;ethical turn目录摘要 (I)Abstract (II)绪论 (1)第1章米勒对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新阐释 (6)1.1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突破 (7)1.1.1直面奥斯汀的理论困境 (7)1.1.2突破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传统 (9)1.2文学言语行为的新规则 (11)1.2.1文学中无形共同体的有效性 (11)1.2.2文学中不恰切言语行为的有效性 (14)1.3述行性作为文学核心品质 (15)1.3.1文学用修辞表现述行 (16)1.3.2文学述行生产意义 (17)第2章基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文学要素新定位 (19)2.1行使述行权的作者 (19)2.1.1唤醒“幽灵”的皮革马利翁 (19)2.1.2诱使读者信任的“骗子” (21)2.2自我赋权的文本 (23)2.2.1文学作为虚拟现实 (24)2.2.2文本的自我证明 (25)2.3担当阅读伦理的读者 (27)2.3.1天真式阅读与去神秘式阅读 (28)2.3.2读者再次唤醒“幽灵” (29)第3章基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批评新转向 (32)3.1促成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 (32)3.1.1为解构主义辩护到批评的伦理转向 (32)3.1.2悖论结构与批评伦理的契合 (34)3.2联接文学与文化研究 (36)3.2.1文学话语再次参与社会建构 (36)3.2.2文化阐释成为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39)3.3修正文学终结论 (40)3.3.1新技术没有终结文学 (41)3.3.2基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文学未来 (43)结语 (45)注释 (47)参考文献 (53)致谢 (56)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58)绪论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1928—)[1],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美国意识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转向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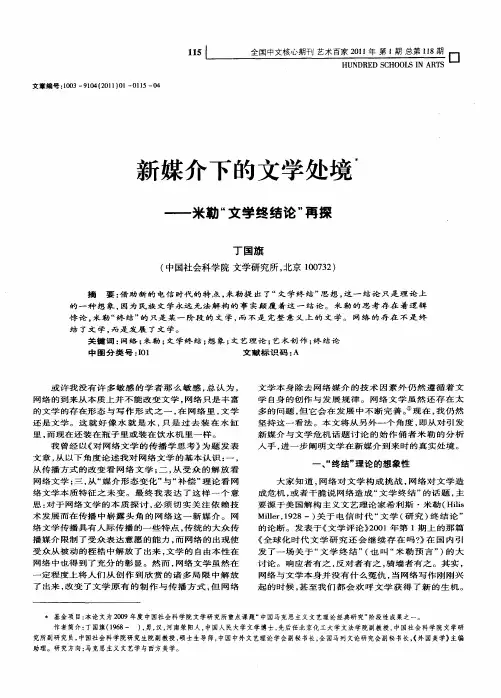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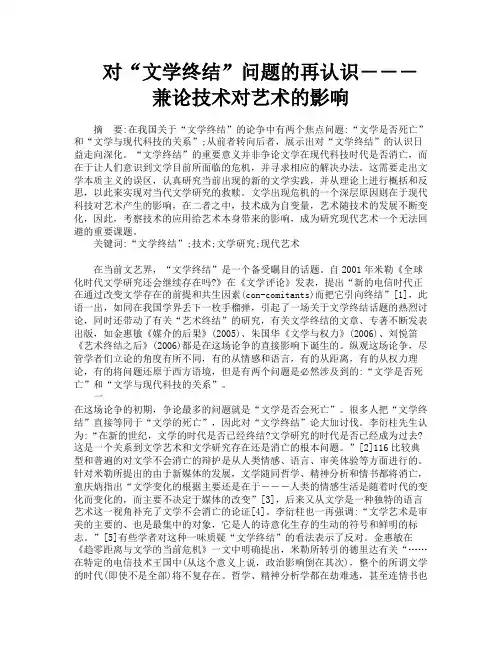
对“文学终结”问题的再认识―――兼论技术对艺术的影响摘要:在我国关于“文学终结”的论争中有两个焦点问题:“文学是否死亡”和“文学与现代科技的关系”;从前者转向后者,展示出对“文学终结”的认识日益走向深化。
“文学终结”的重要意义并非争论文学在现代科技时代是否消亡,而在于让人们意识到文学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并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
这需要走出文学本质主义的误区,认真研究当前出现的新的文学实践,并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反思,以此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救赎。
文学出现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则在于现代科技对艺术产生的影响,在二者之中,技术成为自变量,艺术随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因此,考察技术的应用给艺术本身带来的影响,成为研究现代艺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文学终结”;技术;文学研究;现代艺术在当前文艺界,“文学终结”是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
自2001年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文学评论》发表,提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1],此语一出,如同在我国学界丢下一枚手榴弹,引起了一场关于文学终结话题的热烈讨论,同时还带动了有关“艺术终结”的研究,有关文学终结的文章、专著不断发表出版,如金惠敏《媒介的后果》(2005)、朱国华《文学与权力》(2006)、刘悦笛《艺术终结之后》(2006)都是在这场论争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
纵观这场论争,尽管学者们立论的角度有所不同,有的从情感和语言,有的从距离,有的从权力理论,有的将问题还原于西方语境,但是有两个问题是必然涉及到的:“文学是否死亡”和“文学与现代科技的关系”。
一在这场论争的初期,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文学是否会死亡”。
很多人把“文学终结”直接等同于“文学的死亡”,因此对“文学终结”论大加讨伐。
李衍柱先生认为:“在新的世纪,文学的时代是否已经终结?文学研究的时代是否已经成为过去?这是一个关系到文学艺术和文学研究存在还是消亡的根本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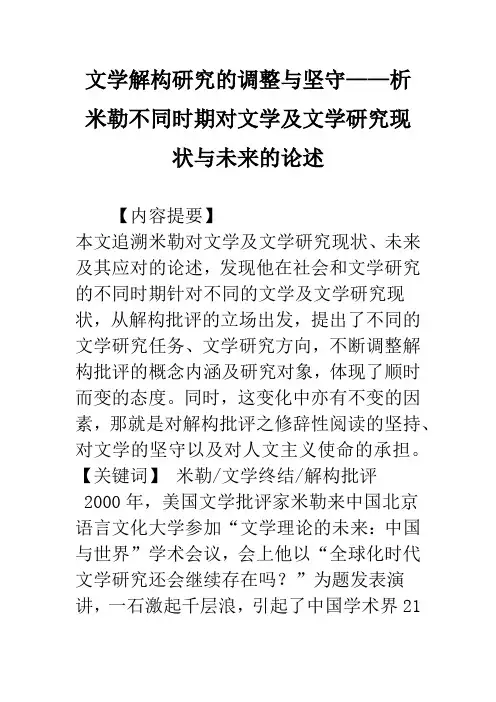
文学解构研究的调整与坚守——析米勒不同时期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与未来的论述【内容提要】本文追溯米勒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未来及其应对的论述,发现他在社会和文学研究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从解构批评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文学研究任务、文学研究方向,不断调整解构批评的概念内涵及研究对象,体现了顺时而变的态度。
同时,这变化中亦有不变的因素,那就是对解构批评之修辞性阅读的坚持、对文学的坚守以及对人文主义使命的承担。
【关键词】米勒/文学终结/解构批评2000年,美国文学批评家米勒来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参加“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学术会议,会上他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中国学术界21世纪初一场较为持久的关于文学及文学研究终结话题的讨论。
笔者以为,米勒提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问题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中生有,在米勒的思想中,有一个就此问题思考的发展轨迹。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米勒发表了多篇论述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及其应对策略的文章,笔者拟将这些文章放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看看米勒在不同时期是如何看待当时的文学及文学研究的,梳理一下米勒提出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希望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关于文学研究的启示。
笔者把米勒就文学及文学研究现状和应对的论述文章按三个时间点进行论述,每两个时间点的跨度大约为10年,把与该时间点年代接近的文章划归该时间点之内,集中论述。
这三个时间点分别是1979、1989、2000年。
一、文学及文学研究的边缘化与大力倡导解构批评1979年,经过不懈的写作和与艾布拉姆斯等人的论战,米勒代表的解构批评进入了美国主流批评之中。
当时虽有文学研究消亡的论调,但米勒对文学及文学解构研究充满了信心,并力图开拓新的疆土。
这体现在《在边缘:当代批评的交叉口》、《当前修辞研究的功能》两篇文章中。
《在边缘》一文中,米勒描述了当时文学研究的现状,并试图对文学研究的发展指明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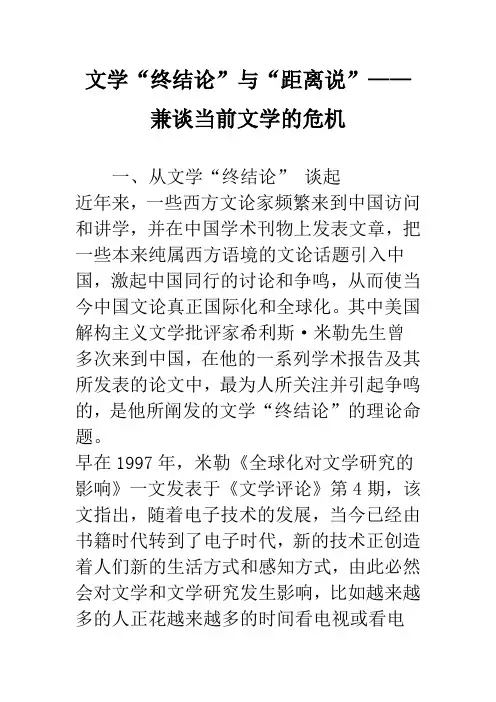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一、从文学“终结论” 谈起近年来,一些西方文论家频繁来到中国访问和讲学,并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把一些本来纯属西方语境的文论话题引入中国,激起中国同行的讨论和争鸣,从而使当今中国文论真正国际化和全球化。
其中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先生曾多次来到中国,在他的一系列学术报告及其所发表的论文中,最为人所关注并引起争鸣的,是他所阐发的文学“终结论”的理论命题。
早在1997年,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该文指出,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当今已经由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新的技术正创造着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由此必然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正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再转向电脑、网络等,很少关注书本的文学作品。
因此他认为,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
也许由于当时中国文论界关注的热点不在于此,因此对米勒提出的问题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时隔三年之后,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米勒再次就此命题作了发言,并在《文学评论》发表长篇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的观点。
从该文所述可知,这一论断其实来自解构主义理论大师、也是米勒的精神宗师雅克·德里达。
米勒在论文开篇,即引述了德里达《明信片》中那段耸人听闻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
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
[1] 米勒本人显然是认同和支持这一论断的,并按照他的理解对这一命题作了充分的阐述。
这一次也许是语境不同了,米勒阐发的文学“终结论”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讨论,一些学者着文与米勒商榷,对这一预言表示质疑和难予苟同,认为这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未免过于极端和武断;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以及对文学美的追求,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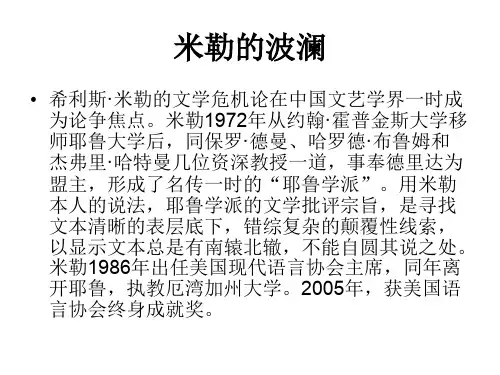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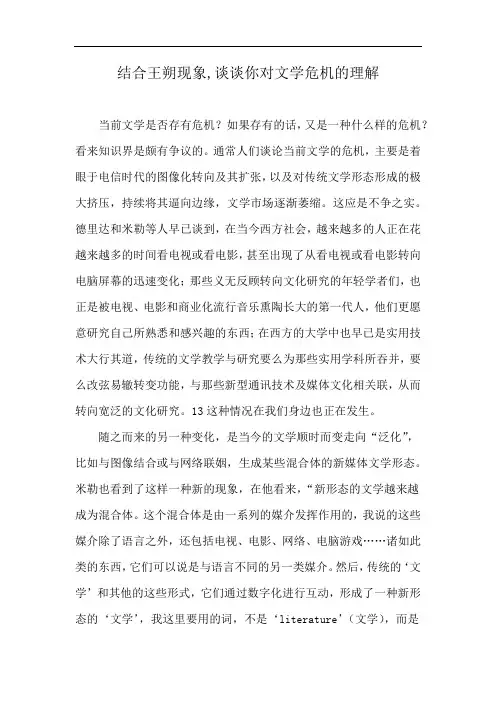
结合王朔现象,谈谈你对文学危机的理解当前文学是否存有危机?如果存有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看来知识界是颇有争议的。
通常人们谈论当前文学的危机,主要是着眼于电信时代的图像化转向及其扩张,以及对传统文学形态形成的极大挤压,持续将其逼向边缘,文学市场逐渐萎缩。
这应是不争之实。
德里达和米勒等人早已谈到,在当今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那些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也正是被电视、电影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更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在西方的大学中也早已是实用技术大行其道,传统的文学教学与研究要么为那些实用学科所吞并,要么改弦易辙转变功能,与那些新型通讯技术及媒体文化相关联,从而转向宽泛的文化研究。
13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也正在发生。
随之而来的另一种变化,是当今的文学顺时而变走向“泛化”,比如与图像结合或与网络联姻,生成某些混合体的新媒体文学形态。
米勒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在他看来,“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合体。
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
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我这里要用的词,不是‘literature’(文学),而是‘literarity’(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
”14米勒特别强调两个词汇的区别,其用意耐人寻味。
对于这种文学“泛化”现象,乐观者把它看成是文学新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极力为其欢呼叫好;悲观者则认为这仍然是一种文学的危机,因为传统的文学精神或“文学性”往往在消费主义和娱乐化中被转化或被消解了。
因此当前文学的危机,不仅仅表层的、文学形态意义上的危机,更根本的还是文学本质或文学精神意义上的危机,是一种深层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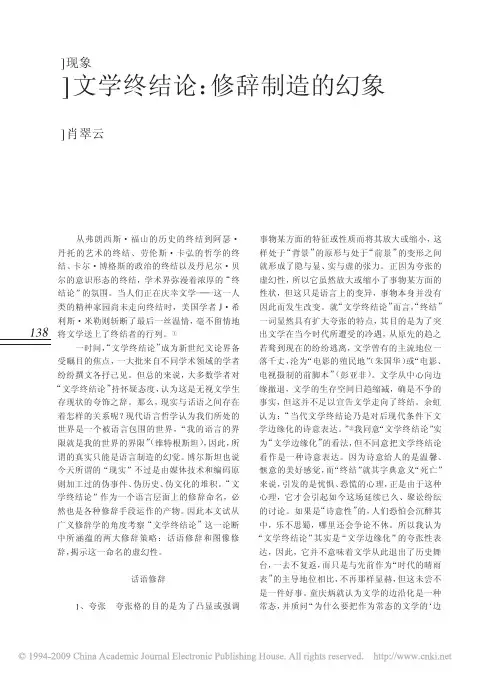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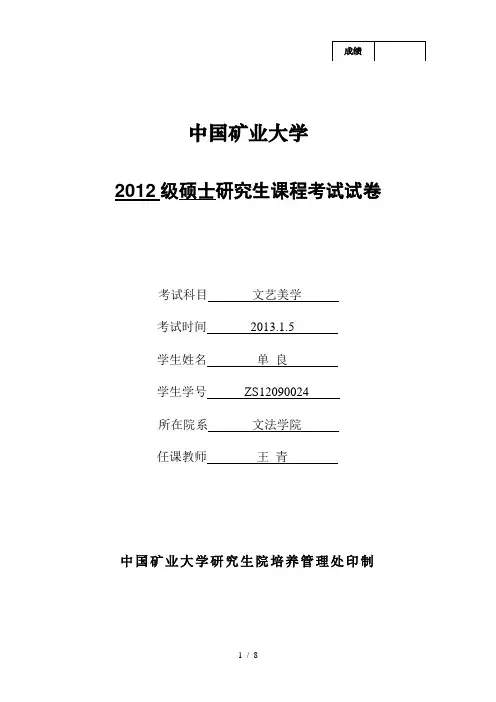
中国矿业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课程考试试卷考试科目文艺美学考试时间2013.1.5学生姓名单良学生学号ZS12090024所在院系文法学院任课教师王青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处印制文学终结论的思考摘要:米勒在本世纪初提出了文学终结的话题,并在中国文学评论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米勒认为文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么在这样的危机中,文学要该何去何从。
本文着重分析中西方文学终结论命题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学的出路问题。
关键词:米勒文学终结论边缘化失语化绪论2001年美国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这篇文章中,米勒发挥了德里达有关现代电信科技的论述,“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Glas)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比如欧美国家过去200年或者250年的历史文化) 得知……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
这样,米勒从创作、阅读与研究全方位地宣布了文学活动的消亡。
[1]米勒的“文学终结论”引发了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应,有支持,也有批判。
然而中西方学界对“终结”的含义理解又不尽相同:米勒、德里达等西方学者理解的终结是“完了、不存在”的意思,而中国学者如余虹、赖大仁、曹顺庆等先生所理解的是文学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和失语化。
西方“文学终结论”的讨论1、西方终结论的传统首先我们从西方来看,有关终结论的命题频频出现。
黑格尔最早提出了“艺术终结论”的命题,宣布了艺术作为人类最高旨趣和绝对真理的崇高地位的终结。
他认为艺术从象征型到古典型再到浪漫型的进化宣告结束,艺术的历史消融于哲学的历史。
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论”的科学语境
王轻鸿
【期刊名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00)002
【摘要】本文对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论"的语境进行了考察,认为他不是在后现代语境中而是在科学语境中来阐释这个命题的。
在米勒看来,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
术培育了主客二分的分析思维,划清了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为"文学"观念诞生提供
了契机;而信息科学技术转向了整体性、综合性思维,这种哲学思维的重大变革,使得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消失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则宣告了文学的"终结"。
米勒的论述
强化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理论中寻求依据。
【总页数】5页(P51-55)
【作者】王轻鸿
【作者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05
【相关文献】
1.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论"的本义考辨 [J], 肖锦龙
2.文化的意指与文学的意指——兼论希利斯·米勒文学认同方式悖论的一种解法 [J], 刘阳
3.美国文学家希利斯·米勒的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探邃 [J], 穆秀丽
4.误读米勒与米勒的误读——评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 [J], 张晓光
5.文学是“真死”还是“假死”?——在多媒体语境下重读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 [J], 刘文娟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浅谈“文学终结论”作者:牛维佳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16期摘要: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中提出“文学终结”的观点,他认为在铺天盖地的电子媒介浪潮席卷下,文学的末日即将降临。
现代阅读方式和视觉媒体等技术手段在将文学传统的范围扩大时,却消解了其文学性。
米勒的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论。
在此,笔者将就米勒的观点展开分析,探讨文学在当下的处境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词:文学;终结;希利斯·米勒作者简介:牛维佳,女,山西太原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6-0-01米勒对当今文化环境的认识是“技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1]”。
他对当代流行文化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提出阅读中出现的一种现象——“碎化”。
认为流行文化和电子阅读的泛滥导致了阅读方式的改变。
米勒的批判说到底是对以大众文化为典型的俗文化向雅文化渗透的排斥。
这一看法与法兰克福学也派有相似之处,该学派对大众的、商品性的视觉文化严厉抨击。
与西方普遍的“终结”思想不同,米勒的观点在中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文学理论界的一场激烈讨论。
赖大仁等接受这种观点,认为米勒看清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企图在全球化背景下把传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作比对,探讨两者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与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
但余虹将“终结”只看成一种“边缘化”的现象,童庆炳也相信文学不会终结,“由于电子图像时代的来临,文学自身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那种能够比较旧的写法被淘汰了,一种新的写法出现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2]”他认为不同的文学观念是批评家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的,不能迷信美国的文化霸权。
既然有关“文学终结”的论争如此激烈,那么不论米勒最后是否肯定这一现象,关于“文学终结论”的研究总还是有意义的。
文学“终结”的首先是视觉媒体是造成的,这是最直观的原因;其次是大众的欣赏喜好影响了大众媒介;此外,文学权威性和文化权力是解释“文学终结论”的文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范畴中的重要概念,从柏拉图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到康德对小说的严厉批判,都是对文学权威性的质疑与批判,文学作品很多时候是在以使读者愉悦的方式欺骗读者。
文学终结的论争与启示文学终结的论争与启示约瑟夫·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1928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195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哈佛、霍普金斯、耶鲁等校,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教授,并受聘于中国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
20世纪60年代,希利斯·米勒在欧美批评界崭露头角;70年代,以“耶鲁学派”重要代表之一在北美批评界产生影响;80年代,以“解构批评”而著称,并活跃于欧美理论批评界。
希利斯·米勒还兼任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会长,被学界称为耶鲁学派代表人物、解构主义批评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希利斯·米勒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当下文学状况以及理论前景的文章,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在1995-20XX年10年间,米勒在中国期刊亮相的文章接近20篇。
另外,由申丹翻译的米勒《解读叙事》也于20XX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米勒在上述文章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电信时代文学的处境以及文学的权威性等,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看起来又相互矛盾,却真实反映了米勒的学术心迹。
一、电信时代文学的处境作为一位从事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批评家,米勒先生对文学的洞察与体悟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锐。
他发现电信时代的文学受到了严峻的峻的挑战:“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轻,成为文化百家衣上的一个小小的补丁。
”①越来越少的人真正花大量的时间阅读被称为经典作家的作品,像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至少在欧洲和美国是这个样子……越来越少的人受到文学阅读的决定性的影响。
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现在的因特网,在塑造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ethos and values)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这些年来,正是这些虚拟的现实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lna—five efficacy),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世界。
文学经典的困境与突围作者:袁晓军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2期袁晓军(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摘要: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文学经典的处境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娱乐化倾向和离心倾向都为文学经典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何走出当下困境,如何让人们重新认识经典的重要性,如何回应文学经典消亡论,这些都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注经典、阅读经典已不是简单的个体问题,而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经典;困境;突围;经典改编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30-02文学经典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关注,近年来又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点话题,并非文学经典异常火热,而是距离人们越来越远。
文学经典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双重挤压下,处境渐趋尴尬,阅读群体也逐渐发生了较大变化。
随着文学经典搬上银幕,改编后的文学作品给受众带来文学盛宴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侵蚀着经典的固有形象。
文学经典如何从当下的消费主义语境中突围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文学经典的现状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电子媒介、图像时代都对经典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注经典、阅读经典的人群逐步萎缩,甚至有人感慨:“当我们现在大谈特谈经典的同时,经典就已经渐渐远离我们了。
”[1]这一论断可以从高校学生的经典阅读调查结果中得到印证。
《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是中外文学名著,也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它们应该是学生眼中的宠儿,但对北京10所高校的2000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读过《红楼梦》等我国四大古典名著的只有11.3%,读过《战争与和平》的只占42%”[2]。
这两部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何等重要,它们的命运尚且如此,其它文学经典的处境可想而知。
文学经典在传播中的另一遭遇是被改编或被改编后搬上银幕。
经典的改编由来已久,近年来中国对经典的改编进行得如火如荼。
名作欣赏 / 文苑经纬 >文学的终结与永恒⊙崔洪爱 [济南大学文学院, 济南 250022]摘 要: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文学似乎节节败退,面临着“终结”的命运。
“文学死了吗”在文学领域被广泛讨论。
J·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文中指出,传统的文学形式似乎面临死亡的局势,但真正的文学性是普遍的、永恒的。
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米勒说明了什么是文学、为什么阅读文学以及如何阅读文学等问题,有力地说明了文学并没有终结,文学是永恒的。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 文学 终结 永恒1817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发表了被称为“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了“艺术已经走向了终结”的著名论断,从此,对于艺术或者文学终结的论断层出不穷,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艺术大讨论。
1972年雅克·德里达曾在他的著作《明信片》中说道:“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 将不复存在。
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a而同样作为解构主义代表人物的希利斯·米勒在他的著作《文学死了吗》中也讨论着这个问题。
本文以米勒的书为基础,探究文学的永恒性。
一、文学面临的危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剧烈发展以及新媒体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而身处其中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
“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到来了”b,文学面临着危机,这再次引发一批人的恐慌。
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列举了种种文学面临的危机。
首先是作为文学载体的印刷产品等行业受到剧烈冲击。
进入新的网络时代,电子产品冲击着纸质文学,印刷行业的业绩不断下滑,众多报纸杂志停刊。
仅2018年就有近三十家报纸杂志停刊,其中包括《北京晨报》等老牌的报刊。
网络时代除了使印刷业受到重创外,希利斯·米勒还指出,新媒体的产生还带动了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但是被改编的影视作品不再是原来的文学,可以说它是一种再创造产生的新的艺术作品。
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人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 (1)“文学终结”近几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美国知名学者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以后,这种讨论就开始了。
米勒先生在这篇不长文章中说: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
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
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持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
因为许多这样的幽灵都是极端的暴力形象,它们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的屏幕上,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们可以跟它们面对面、看到、听到它们,而不仅是在书页上读到。
我想,这正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
[i]米勒相信:这是电信时代的电子传播媒介的“幽灵”,“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并认为“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成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的情书”,从而导致文学的终结。
文学终结了,“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样呢?文学研究时代已经过去了。
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政治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
那样做不合时宜。
”[ii]中国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学者对于米勒的关于文学的终结论深信不疑,以至于产生一种恐慌,有人相信文学在电子图像时代必然终结,而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也受到根本的威胁,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的学者就提出,文艺学的边界如果不越界不扩容,文艺学岂不要自取灭亡吗?趁现在的“文学性”还在那里“蔓延”,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蔓延,在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中蔓延,赶快抓住这些“文学性”的电信的海啸中的稻草,苟延残喘,实现所谓的“文化转向”,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吧!文学已经在电信王国的海啸中频临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