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柳宗元对苏轼贬谪生活之影响
- 格式:pdf
- 大小:131.21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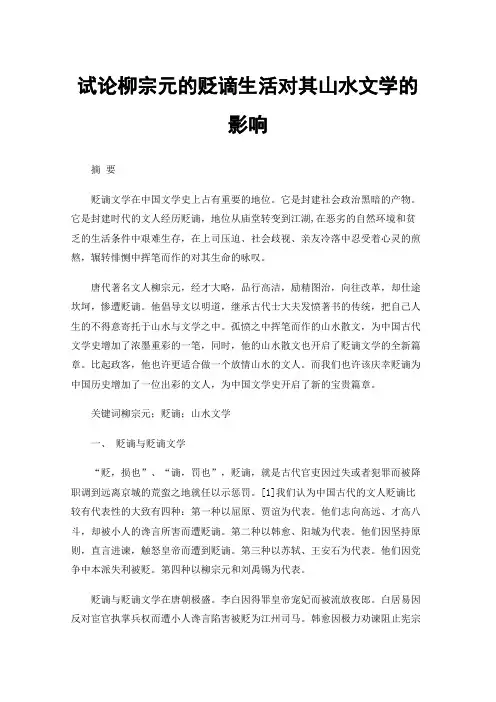
试论柳宗元的贬谪生活对其山水文学的影响摘要贬谪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是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的产物。
它是封建时代的文人经历贬谪,地位从庙堂转变到江湖,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贫乏的生活条件中艰难生存,在上司压迫、社会歧视、亲友冷落中忍受着心灵的煎熬,辗转悱恻中挥笔而作的对其生命的咏叹。
唐代著名文人柳宗元,经才大略,品行高洁,励精图治,向往改革,却仕途坎坷,惨遭贬谪。
他倡导文以明道,继承古代士大夫发愤著书的传统,把自己人生的不得意寄托于山水与文学之中。
孤愤之中挥笔而作的山水散文,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他的山水散文也开启了贬谪文学的全新篇章。
比起政客,他也许更适合做一个放情山水的文人。
而我们也许该庆幸贬谪为中国历史增加了一位出彩的文人,为中国文学史开启了新的宝贵篇章。
关键词柳宗元;贬谪;山水文学一、贬谪与贬谪文学“贬,损也”、“谪,罚也”,贬谪,就是古代官吏因过失或者犯罪而被降职调到远离京城的荒蛮之地就任以示惩罚。
[1]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文人贬谪比较有代表性的大致有四种:第一种以屈原、贾谊为代表。
他们志向高远、才高八斗,却被小人的谗言所害而遭贬谪。
第二种以韩愈、阳城为代表。
他们因坚持原则,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而遭到贬谪。
第三种以苏轼、王安石为代表。
他们因党争中本派失利被贬。
第四种以柳宗元和刘禹锡为代表。
贬谪与贬谪文学在唐朝极盛。
李白因得罪皇帝宠妃而被流放夜郎。
白居易因反对宦官执掌兵权而遭小人谗言陷害被贬为江州司马。
韩愈因极力劝谏阻止宪宗迎供佛骨触怒皇帝而差点被处以极刑,在崔群等同僚的求情下还是被贬到了潮州。
还有王昌龄、杜甫、刘禹锡等数不胜数的文人墨客。
他们都因贬谪而创造出了许多成就极高的贬谪作品。
而被贬最彻底在47岁盛年卒于贬谪地的柳宗元,在遭贬谪之后经历艰难的生活与精神的煎熬,心态发生变化,创作出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开启了贬谪文学的新篇章。
[2]柳宗元的悲剧游记文学是元和贬谪文学的典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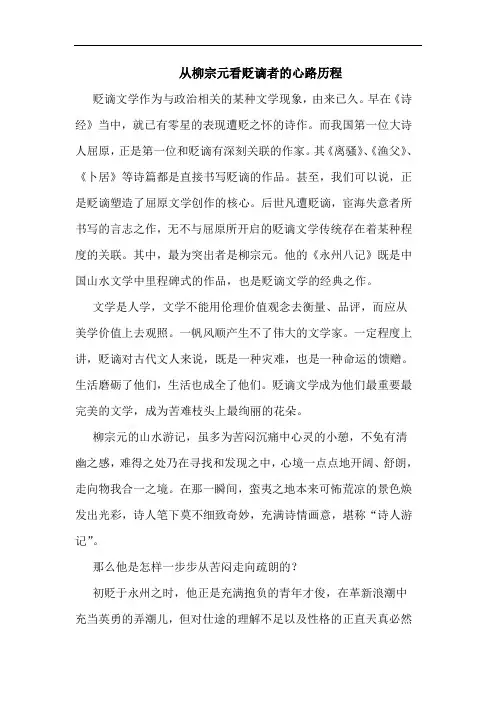
从柳宗元看贬谪者的心路历程贬谪文学作为与政治相关的某种文学现象,由来已久。
早在《诗经》当中,就已有零星的表现遭贬之怀的诗作。
而我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正是第一位和贬谪有深刻关联的作家。
其《离骚》、《渔父》、《卜居》等诗篇都是直接书写贬谪的作品。
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贬谪塑造了屈原文学创作的核心。
后世凡遭贬谪,宦海失意者所书写的言志之作,无不与屈原所开启的贬谪文学传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其中,最为突出者是柳宗元。
他的《永州八记》既是中国山水文学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贬谪文学的经典之作。
文学是人学,文学不能用伦理价值观念去衡量、品评,而应从美学价值上去观照。
一帆风顺产生不了伟大的文学家。
一定程度上讲,贬谪对古代文人来说,既是一种灾难,也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生活磨砺了他们,生活也成全了他们。
贬谪文学成为他们最重要最完美的文学,成为苦难枝头上最绚丽的花朵。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虽多为苦闷沉痛中心灵的小憩,不免有清幽之感,难得之处乃在寻找和发现之中,心境一点点地开阔、舒朗,走向物我合一之境。
在那一瞬间,蛮夷之地本来可怖荒凉的景色焕发出光彩,诗人笔下莫不细致奇妙,充满诗情画意,堪称“诗人游记”。
那么他是怎样一步步从苦闷走向疏朗的?初贬于永州之时,他正是充满抱负的青年才俊,在革新浪潮中充当英勇的弄潮儿,但对仕途的理解不足以及性格的正直天真必然使他落马失势,经历了十年在永州的磨砺,他在山水的怀抱中得到了抚慰。
那些幽静自然的美令他欣喜,却也令他怜惜——如此美景却被世人冷落,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耐不住感叹起来,可见山水之美让他暂时轻松,却无法令他真正释怀。
所以当长安的召唤传到谪地时,他空欢喜了一场——柳州,更加偏远和贫穷。
去了那里,便意味着今生回归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此时,他虽刚迈入中年,却身染百疾,甚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痺”(《与李翰林建书》)的地步,所以他知道,柳州将是他的终点。
这种状态下,心情反而放开了,不再做梦而是立足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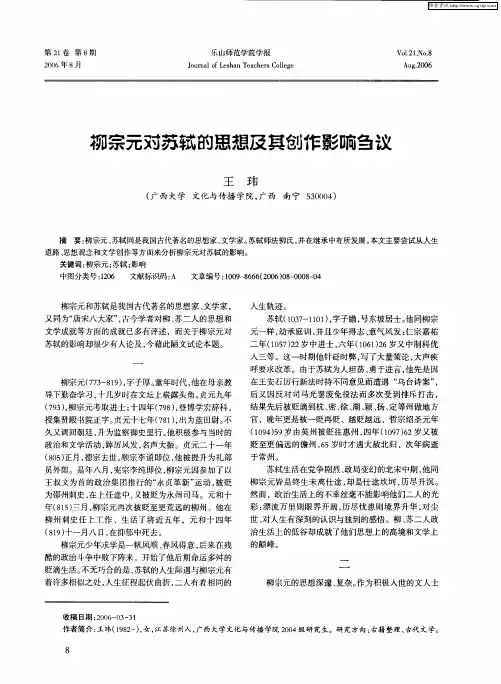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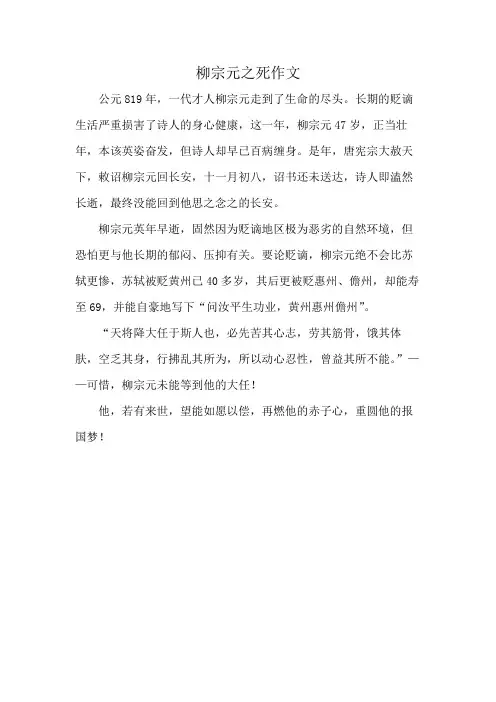
柳宗元之死作文
公元819年,一代才人柳宗元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长期的贬谪生活严重损害了诗人的身心健康,这一年,柳宗元47岁,正当壮年,本该英姿奋发,但诗人却早已百病缠身。
是年,唐宪宗大赦天下,敕诏柳宗元回长安,十一月初八,诏书还未送达,诗人即溘然长逝,最终没能回到他思之念之的长安。
柳宗元英年早逝,固然因为贬谪地区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但恐怕更与他长期的郁闷、压抑有关。
要论贬谪,柳宗元绝不会比苏轼更惨,苏轼被贬黄州已40多岁,其后更被贬惠州、儋州,却能寿至69,并能自豪地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可惜,柳宗元未能等到他的大任!
他,若有来世,望能如愿以偿,再燃他的赤子心,重圆他的报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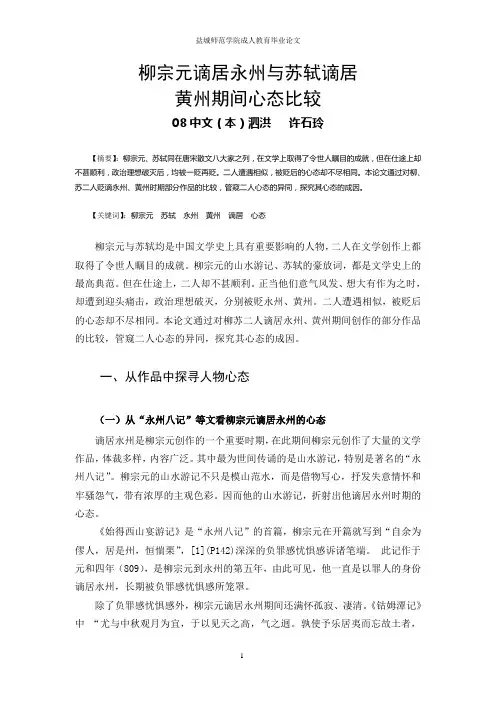
柳宗元谪居永州与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心态比较08中文(本)泗洪许石玲【摘要】:柳宗元、苏轼同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在文学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仕途上却不甚顺利,政治理想破灭后,均被一贬再贬。
二人遭遇相似,被贬后的心态却不尽相同。
本论文通过对柳、苏二人贬谪永州、黄州时期部分作品的比较,管窥二人心态的异同,探究其心态的成因。
【关键词】:柳宗元苏轼永州黄州谪居心态柳宗元与苏轼均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二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苏轼的豪放词,都是文学史上的最高典范。
但在仕途上,二人却不甚顺利。
正当他们意气风发、想大有作为之时,却遭到迎头痛击,政治理想破灭,分别被贬永州、黄州。
二人遭遇相似,被贬后的心态却不尽相同。
本论文通过对柳苏二人谪居永州、黄州期间创作的部分作品的比较,管窥二人心态的异同,探究其心态的成因。
一、从作品中探寻人物心态(一)从“永州八记”等文看柳宗元谪居永州的心态谪居永州是柳宗元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柳宗元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体裁多样,内容广泛。
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是山水游记,特别是著名的“永州八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只是模山范水,而是借物写心,抒发失意情怀和牢骚怨气,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因而他的山水游记,折射出他谪居永州时期的心态。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永州八记”的首篇,柳宗元在开篇就写到“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1](P142)深深的负罪感忧惧感诉诸笔端。
此记作于元和四年(809),是柳宗元到永州的第五年,由此可见,他一直是以罪人的身份谪居永州,长期被负罪感忧惧感所笼罩。
除了负罪感忧惧感外,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还满怀孤寂、凄清。
《钴姆潭记》中“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
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1](P147)设想中秋观月的情景,“乐”而忘乡。
貌似冲淡,实则激愤,以一个“乐”字透出遭贬“居夷”的悲怨凄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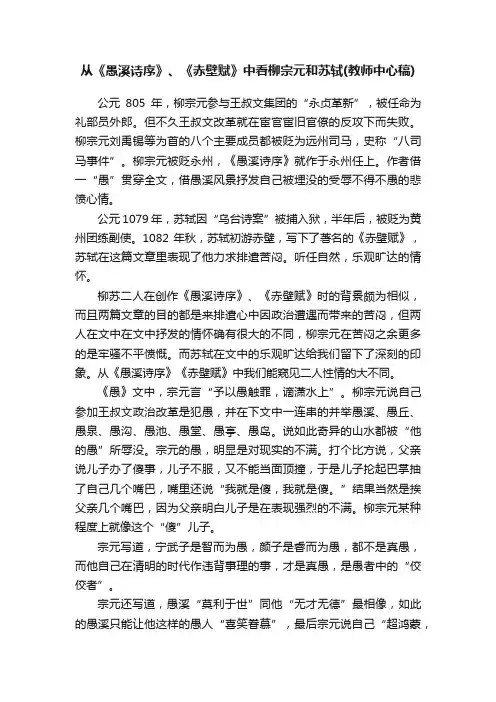
从《愚溪诗序》、《赤壁赋》中看柳宗元和苏轼(教师中心稿)公元805年,柳宗元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
但不久王叔文改革就在宦官宦旧官僚的反攻下而失败。
柳宗元刘禹锡等为首的八个主要成员都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被贬永州,《愚溪诗序》就作于永州任上。
作者借一“愚”贯穿全文,借愚溪风景抒发自己被埋没的受辱不得不愚的悲愤心情。
公元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半年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1082年秋,苏轼初游赤壁,写下了著名的《赤壁赋》,苏轼在这篇文章里表现了他力求排遣苦闷。
听任自然,乐观旷达的情怀。
柳苏二人在创作《愚溪诗序》、《赤壁赋》时的背景颇为相似,而且两篇文章的目的都是来排遣心中因政治遭遇而带来的苦闷,但两人在文中在文中抒发的情怀确有很大的不同,柳宗元在苦闷之余更多的是牢骚不平愤慨。
而苏轼在文中的乐观旷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愚溪诗序》《赤壁赋》中我们能窥见二人性情的大不同。
《愚》文中,宗元言“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
柳宗元说自己参加王叔文政治改革是犯愚,并在下文中一连串的并举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
说如此奇异的山水都被“他的愚”所辱没。
宗元的愚,明显是对现实的不满。
打个比方说,父亲说儿子办了傻事,儿子不服,又不能当面顶撞,于是儿子抡起巴掌抽了自己几个嘴巴,嘴里还说“我就是傻,我就是傻。
”结果当然是挨父亲几个嘴巴,因为父亲明白儿子是在表现强烈的不满。
柳宗元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个“傻”儿子。
宗元写道,宁武子是智而为愚,颜子是睿而为愚,都不是真愚,而他自己在清明的时代作违背事理的事,才是真愚,是愚者中的“佼佼者”。
宗元还写道,愚溪“莫利于世”同他“无才无德”最相像,如此的愚溪只能让他这样的愚人“喜笑眷慕”,最后宗元说自己“超鸿蒙,混希夷”达到了愚者最高的境界。
其中折射的悲愤不满不言而喻。
柳宗元以愚者自居故作旷达,实则表现的是对现实的不满,他的所谓旷达实际上是牢骚不平,宗元在挫折面前的如此表现反映了其性格的不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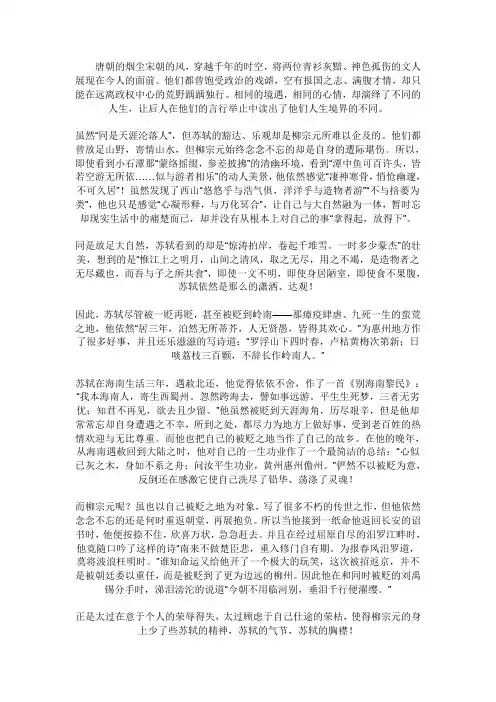
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穿越千年的时空,将两位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的文人展现在今人的面前。
他们都曾饱受政治的戏谑,空有报国之志、满腹才情,却只能在远离政权中心的荒野踽踽独行。
相同的境遇,相同的心情,却演绎了不同的人生,让后人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读出了他们人生境界的不同。
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但苏轼的豁达、乐观却是柳宗元所难以企及的。
他们都曾放足山野,寄情山水,但柳宗元始终念念不忘的却是自身的遭际堪伤。
所以,即使看到小石潭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清幽环境,看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似与游者相乐”的动人美景,他依然感觉“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不可久居”!虽然发现了西山“悠悠乎与浩气俱,洋洋乎与造物者游”“不与掊蒌为类”,他也只是感觉“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让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楚而已,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对自己的事“拿得起,放得下”。
同是放足大自然,苏轼看到的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一时多少豪杰”的壮美,想到的是“惟江上之明月,山间之清风,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即使一文不明,即使身居陋室,即使食不果腹,苏轼依然是那么的潇洒、达观!因此,苏轼尽管被一贬再贬,甚至被贬到岭南——那瘴疫肆虐、九死一生的蛮荒之地,他依然“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
”为惠州地方作了很多好事,并且还乐滋滋的写诗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还,他觉得依依不舍,作了一首《别海南黎民》:“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虽然被贬到天涯海角,历尽艰辛,但是他却常常忘却自身遭遇之不幸,所到之处,都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与无比尊重。
而他也把自己的被贬之地当作了自己的故乡。
在他的晚年,从海南遇赦回到大陆之时,他对自己的一生功业作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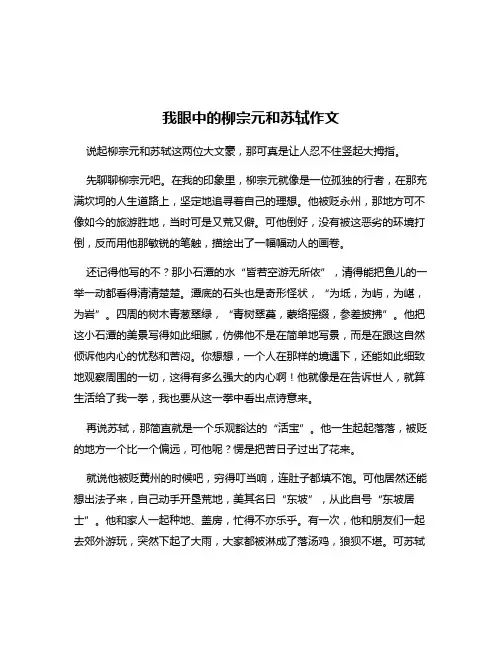
我眼中的柳宗元和苏轼作文说起柳宗元和苏轼这两位大文豪,那可真是让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先聊聊柳宗元吧。
在我的印象里,柳宗元就像是一位孤独的行者,在那充满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坚定地追寻着自己的理想。
他被贬永州,那地方可不像如今的旅游胜地,当时可是又荒又僻。
可他倒好,没有被这恶劣的环境打倒,反而用他那敏锐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
还记得他写的不?那小石潭的水“皆若空游无所依”,清得能把鱼儿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
潭底的石头也是奇形怪状,“为坻,为屿,为嵁,为岩”。
四周的树木青葱翠绿,“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他把这小石潭的美景写得如此细腻,仿佛他不是在简单地写景,而是在跟这自然倾诉他内心的忧愁和苦闷。
你想想,一个人在那样的境遇下,还能如此细致地观察周围的一切,这得有多么强大的内心啊!他就像是在告诉世人,就算生活给了我一拳,我也要从这一拳中看出点诗意来。
再说苏轼,那简直就是一个乐观豁达的“活宝”。
他一生起起落落,被贬的地方一个比一个偏远,可他呢?愣是把苦日子过出了花来。
就说他被贬黄州的时候吧,穷得叮当响,连肚子都填不饱。
可他居然还能想出法子来,自己动手开垦荒地,美其名曰“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他和家人一起种地、盖房,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去郊外游玩,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都被淋成了落汤鸡,狼狈不堪。
可苏轼却毫不在乎,反而在雨中吟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你瞧瞧,这是多么洒脱的心态!还有啊,苏轼特别爱吃。
大家都知道“东坡肉”吧?这可是他的拿手好菜。
据说当时猪肉在当地不怎么受欢迎,价格便宜得很。
苏轼就把猪肉切成大块,用慢火炖煮,加上调料,煮得那叫一个香。
他还专门写了一首来介绍做法:“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这哪里像是一个大文豪,简直就是一个资深的美食家!柳宗元和苏轼,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遭遇不同,但在我眼里,他们都有着一颗不屈服于命运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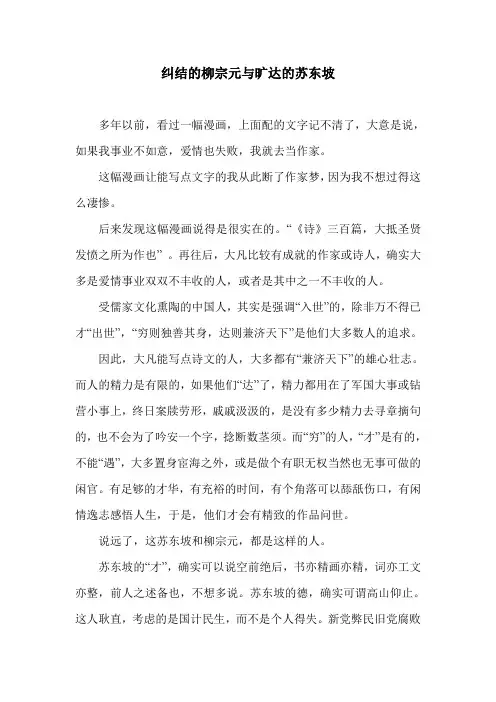
纠结的柳宗元与旷达的苏东坡多年以前,看过一幅漫画,上面配的文字记不清了,大意是说,如果我事业不如意,爱情也失败,我就去当作家。
这幅漫画让能写点文字的我从此断了作家梦,因为我不想过得这么凄惨。
后来发现这幅漫画说得是很实在的。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再往后,大凡比较有成就的作家或诗人,确实大多是爱情事业双双不丰收的人,或者是其中之一不丰收的人。
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其实是强调“入世”的,除非万不得已才“出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们大多数人的追求。
因此,大凡能写点诗文的人,大多都有“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
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他们“达”了,精力都用在了军国大事或钻营小事上,终日案牍劳形,戚戚汲汲的,是没有多少精力去寻章摘句的,也不会为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而“穷”的人,“才”是有的,不能“遇”,大多置身宦海之外,或是做个有职无权当然也无事可做的闲官。
有足够的才华,有充裕的时间,有个角落可以舔舐伤口,有闲情逸志感悟人生,于是,他们才会有精致的作品问世。
说远了,这苏东坡和柳宗元,都是这样的人。
苏东坡的“才”,确实可以说空前绝后,书亦精画亦精,词亦工文亦整,前人之述备也,不想多说。
苏东坡的德,确实可谓高山仰止。
这人耿直,考虑的是国计民生,而不是个人得失。
新党弊民旧党腐败他都同样抨击,所以新党执政把他当作旧党打击,旧党执政把他当作新党打击,终生抑郁不得志。
其实,他并没有陷入朋党之争,只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士人。
所以,他是“穷”人。
柳宗元也是如此,参与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
二人同为“迁客骚人”,情怀自然大同小异,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终日郁郁寡欢。
无法排遣,自然寄情山水,让大自然来医治他们受伤的心。
这寄情山水,与借酒浇愁效果也差不多,消得了一时,消不了一世。
明日酒醒,抑或山水之乐消失,还是悲伤接着悲伤。
他们的作品很多,一一评述无意义,仅以初中语文课本的一篇文章来分析,虽有断章取义之嫌、以管窥天之弊,但文字出自他们腹中,相差也不可能甚远。

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穿越千年的时空,将两位文人展现在面前。
他们都曾饱受政治的戏谑,空有报国之志、满腹才情,却只能在远离政权中心的荒野独行。
相同的境遇,相同的心情,却演绎了不同的人生,让后人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中读出了他们人生境界的不同。
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但苏轼的豁达、乐观却是柳宗元所难以企及的。
他们都曾放足山野,寄情山水,但柳宗元始终念念不忘的却是自身的遭际堪伤。
所以,即使看到小石潭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清幽环境,看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似与游者相乐”的动人美景,他依然感觉“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不可久居”!同是放足大自然,苏轼看到的却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一时多少豪杰”的壮美,想到的是“惟江上之明月,山间之清风,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即使一文不明,即使身居陋室,即使食不果腹,苏轼依然是那么的潇洒、达观!而柳宗元虽也以自己被贬之地为对象,写了很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但他依然念念不忘的还是何时重返朝堂,再展抱负。
所以当他接到一纸命他返回长安的诏书时,他便急急赶去。
谁知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这次被诏返京,竟是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正是太过在意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太过顾虑于自己仕途的荣枯,使得柳宗元的身上少了些苏轼的精神,苏轼的气节,苏轼的胸襟!柳宗元年少得志,二十岁中了进士,并且受到当时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重用,本来在仕途上大有作为,未想因宪宗即位,马上即遭贬谪,囚居荒蛮的永州十年之久,然而,柳宗元在那样的山水中,并没有平静下来。
苏东坡在被贬谪到黄州的时候,我想,那凄惨的情形大概跟柳宗元差不多吧,甚至更为艰难。
但读苏东坡黄州时期的几篇文章,会让人感觉到其中蕴涵着的一种巨大的主体精神力量,这也是苏东坡所最看重的生命独立的问题。
苏东坡一生都保持着从容坦然的心态,保持着积极奋进的行为。
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一种生命的纯真与自然。
他总是以自我与万物同一于自然,又保持着精神上的主动,这样就能用超然的眼光来看待万物,却又保持着生活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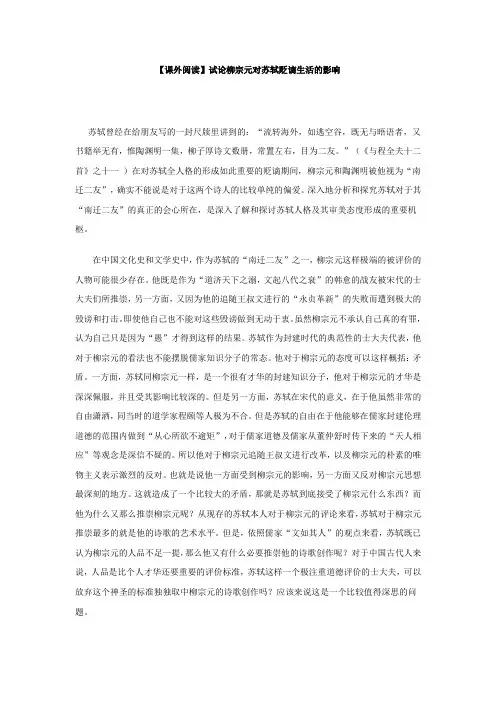
【课外阅读】试论柳宗元对苏轼贬谪生活的影响苏轼曾经在给朋友写的一封尺牍里讲到的:“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
”(《与程全夫十二首》之十一)在对苏轼全人格的形成如此重要的贬谪期间,柳宗元和陶渊明被他视为“南迁二友”,确实不能说是对于这两个诗人的比较单纯的偏爱。
深入地分析和探究苏轼对于其“南迁二友”的真正的会心所在,是深入了解和探讨苏轼人格及其审美态度形成的重要机枢。
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中,作为苏轼的“南迁二友”之一,柳宗元这样极端的被评价的人物可能很少存在。
他既是作为“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战友被宋代的士大夫们所推崇,另一方面,又因为他的追随王叔文进行的“永贞革新”的失败而遭到极大的毁谤和打击。
即使他自己也不能对这些毁谤做到无动于衷。
虽然柳宗元不承认自己真的有罪,认为自己只是因为“愚”才得到这样的结果。
苏轼作为封建时代的典范性的士大夫代表,他对于柳宗元的看法也不能摆脱儒家知识分子的常态。
他对于柳宗元的态度可以这样概括:矛盾。
一方面,苏轼同柳宗元一样,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封建知识分子,他对于柳宗元的才华是深深佩服,并且受其影响比较深的。
但是另一方面,苏轼在宋代的意义,在于他虽然非常的自由潇洒,同当时的道学家程颐等人极为不合。
但是苏轼的自由在于他能够在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范围内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于儒家道德及儒家从董仲舒时传下来的“天人相应”等观念是深信不疑的。
所以他对于柳宗元追随王叔文进行改革,以及柳宗元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表示激烈的反对。
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受到柳宗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对柳宗元思想最深刻的地方。
这就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矛盾,那就是苏轼到底接受了柳宗元什么东西?而他为什么又那么推崇柳宗元呢?从现存的苏轼本人对于柳宗元的评论来看,苏轼对于柳宗元推崇最多的就是他的诗歌的艺术水平。
但是,依照儒家“文如其人”的观点来看,苏轼既已认为柳宗元的人品不足一提,那么他又有什么必要推崇他的诗歌创作呢?对于中国古代人来说,人品是比个人才华还要重要的评价标准,苏轼这样一个极注重道德评价的士大夫,可以放弃这个神圣的标准独独取中柳宗元的诗歌创作吗?应该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简介]郭静,女,内蒙古医科大学教师。
从贬谪心态看柳宗元永州时期的寓言创作○郭静(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110)[摘 要] 柳宗元济世安民的美好初衷随着“永贞革新”的失败破灭了,随之而来的贬谪给他带来的是身心的双重折磨。
柳宗元通过文学创作,将满怀幽郁舒泄出来,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其寓言作品高度关注了朝廷政事、讽刺和鞭挞了政敌,赞美了革新派并表明了自己的斗志。
[关键词] 柳宗元; 贬谪心态; 寓言创作[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4)08-0031-02一、诗人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转折———永贞革新中国文人对政治的热衷是古已有之的传统。
他们不甘以文人自居,而欲于政治舞台上一展才华。
这在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以儒家济世安民思想为本的柳宗元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他的理想是“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
”(《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他在贞元九年(793)中进士,贞元十九年(803)为监察御史里行,受到王叔文赏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参加了王叔文,王伾领导的志在打击权奸,进用贤能,减免赋税,革除弊政的政治革新运动,史称“永贞革新”。
但这次革新仅进行了一百四十余天便夭折了:支持改革的唐顺宗被逼让位给李纯(唐宪宗);王叔文被杀、王伾被逼死;柳宗元等八人被贬远州司马,他先被贬邵州刺史,途中又改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贬柳州刺史。
他参加“永贞革新”,是欲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济世的美好初衷随着“永贞革新”的失败破灭了,随之而来的贬谪给他带来的是身心的双重折磨。
下面就简析贬谪给他造成的折磨及其对永州寓言创作的影响。
二、贬谪生活对诗人的影响贬谪给士人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折磨。
“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
…涉野有蝮虺大蜂…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且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与李翰林建书》),这里的自然环境相当恶劣。
“至则无以为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先太夫人县归袝志》),生活条件也很差。
浅析柳宗元贬谪永、柳期间的思想动态作者:饶玉群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7期摘要:柳宗元的游记散文和碑铭表志类文章在唐代及后世深受推崇。
尽管柳文熠熠生辉,却也淹没不了其诗歌在文坛上的成就。
柳宗元的诗歌留存一百六十多首,绝大多数为贬谪永州和柳州期间所作。
这些诗歌以字简意深的形式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作者面临政治革新失败后颠沛流离的半生。
而这些诗歌中有一类较为独特的是以记述种植的方式抒发作者贬谪南荒的复杂心态,这类诗歌从不同层面映射出诗人面临政治迫害后对自身的认识和外界的认知,从而在罹难中淡化苦痛、升华自我。
关键词:柳宗元;贬谪;种植诗;思想动态作者简介:饶玉群,性别:女,籍贯:广西来宾,1989 年6 月7日出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专业:文学硕士2012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7-0-02一、“远物世所重,旅人心独伤”一朝被贬,身系南荒。
这句话足以概括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所遭遇的处境。
政治革新之前,柳宗元的仕途较为平坦。
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六岁中博学鸿词科,随即成为集贤殿正字,后调任蓝田(今山西蓝田县西)县尉,不久又被中央调回朝廷任监察御史里行。
身为朝廷政员,希望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业的柳宗元需要跻身进入一个能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集团,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正是基于这种政治上的雄心壮志。
令柳宗元意想不到的是,他这么快就被同朝为官的群小施予政治挤兑,惨遭迫害被贬南荒。
韶州一贬成了柳宗元政治生涯由光明逐渐走向黑暗的转折点。
对此,作于贬谪永州期间的《行路难三首》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惨遭迫害的沉痛心情。
(其一)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坐使儿女相悲怜。
(其二)虞衡斤斧罗千山,……,爱材养育谁复论。
(其三)飞雪断道冰成梁,……,桃笙葵扇安可常。
韩醇《训诂柳集》评:“三诗皆意有所讽,上篇谓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如北方之短人,亦足以终天年,盖自谓也。
柳宗元苏轼哲人之文与骚人之文_苏轼与柳宗元贬地山水游记比较_杨有山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6期2012年11月·文学研究·JournalofXinyangNormalUniversity(Philos.&Soc.Sci.Edit.)Vol.32No.6Nov.2012哲人之文与骚人之文———苏轼与柳宗元贬地山水游记比较杨有山(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摘要:柳宗元与苏轼贬地山水游记具有不同的艺术风貌,苏文是哲人之文,而柳文则是骚人之文。
二者的不同表现在三个方面:寄托与超脱;刻意与随意;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透过柳、苏这类散文的不同艺术风貌,可以窥视唐宋山水游记的明显差异。
关键词:苏轼;柳宗元;山水游记;哲人之文;骚人之文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0964(2012)06-0083-04文章编号:1003-[2]1199《离骚》。
”:“唐人惟柳子厚深宋人严羽就认为[3]186”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
其贬后山水游记苏轼和柳宗元,都曾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顺利地踏上仕途,希望能大有作为,济世泽民,却都不幸地卷入党争,而致仕途连蹇,长期被贬荒远异乡。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1]3533,“纵逢恩赦,。
苏轼则因柳州不在量移之限”反对王安石等的变法被目为旧党,后又被看作“元可谓是典型的骚人之文。
苏轼服膺庄子及其文章,《庄子》:“吾昔有见于中,苏辙记述苏轼读时的感受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贬后山水游记吸取了庄子的齐物思想和超然物外、随遇而[4]1126,祐党人”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
为了排解忧愁,让谪居的生活相对自由和轻松,他们都寄情于山以此抚慰自己失意的心灵。
柳宗元为我们留下水,《永州八记》、《小石城山记》了等。
苏轼则留下了黄《记游定惠院》、《赤壁赋》、《记承天寺夜州作的前后》、《游沙湖》游等,离开黄州赴汝州途中作的《石钟,、《记游白水岩》惠州时作的《记游松风亭》山记》《在儋耳书》等,儋州时作的等美文。
解密柳宗元的大起大落从一个活跃在中唐政坛的青年才俊,陡然跌落为长居蛮荒之地的“囚徒”,他何以自处?又何以令自己的人生境界和才学升华到如此高的境界?十一二岁就很有名,31岁走入政权核心,却在最意气风发时跌落谷底古今有成就者,无不坎坷,但坎坷的形式各有不同:陶渊明不能忍受为五斗米折腰而躬耕归隐;苏东坡在入朝与远谪的起伏中,悟透人生的荒凉;还有人经历的是长夜漫漫的悲剧,历尽痛苦……将这样的苦难尝到极致的,也许就要算唐朝中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了。
从一个活跃在中唐政坛的青年才俊,陡然跌落为长居蛮荒之地的“囚徒”,他何以自处?又何以令自己的人生境界和才学升华到如此高的境界?这是柳宗元让我们永远不能停止探寻的问题。
祖辈曾是皇亲国戚柳宗元出身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柳氏。
唐朝人喜欢说自己先世出于高门,许多是不能相信的,但柳宗元的家族却是货真价实的门阀贵族。
北朝时期,黄河以东地区的柳氏,就与薛氏、裴氏一起,并称“河东三著姓”。
唐朝立国后,柳氏也被皇室倚重。
唐高宗李治一朝(公元649年—683年),柳家光在尚书省(相当于国务院)同时做官的就达20多人,权倾一时。
但也就是在高宗时期,柳家开始走向衰败。
当时,柳宗元的高伯祖(与柳宗元之高祖子夏为兄弟)柳奭(音同“是”)是高宗的宰相,高宗第一任皇后王皇后是柳奭的外甥女。
后宫斗争中,王皇后败于武则天,柳宰相也受到牵连,先是被贬,后来干脆被诛杀。
武则天上台主政后,打击旧姓,柳氏从皇亲国戚降为普通人,仅剩下良好的家风不绝如缕。
柳宗元的老朋友韩愈,说柳宗元正直、真诚,不计利害,为理想奋不顾身。
柳宗元的这种品性正遗传自他的父亲柳镇。
柳镇曾在晋州(今山西省境内)做官,他的上司是个粗暴而嗜杀的武夫,官府里的人都不敢得罪他。
看到无辜受刑的人快要被打死时,只有柳镇会去据理力争,甚至亲身为无辜者抵挡鞭笞棍棒,即使上司暴怒也毫不退避。
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也出身世家,通晓诗书,文采不凡。
柳宗元4岁时,父亲孤身在外,卢氏带着孩子们暂住长安西郊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