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 格式:doc
- 大小:3.33 MB
- 文档页数:9

刘再复:在哈佛大学李欧梵退休典礼仪式上的发言编按:今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哈佛大学在校园内为李欧梵教授举行有一百多人参加的隆重退休庆典仪式和告别性学术活动。
在开幕式上,韩南、葛浩文、王德威、杜维明、廖炳惠等八位知名学者对李欧梵的多方面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当中有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刘再复教授。
除了半天评价活动之外,其他时间均进行学术讨论,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的世界主义者”,在讨论中,学者们对就现代性与世界性、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
李欧梵在会上发表多次讲话,并告知大家,离开哈佛大学之後他将到香港“客座”一段时间。
本刊现把刘再复在开幕仪式上的发言刊登於此。
这一发言概述了李欧梵的精神特点和整体成就,在会上引起热烈反响。
最善於自嘲的人当大家在热烈评价欧梵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他多年前一篇谈论匈牙利当代作家康拉德(GeorgeKonrad)的小说《失败者》(TheLoser)的文章,这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传小说,但他不写自己的成就,偏写自己—生的失败。
对此,欧梵说,这正“合我个人的所好”,并且说了一句我一直难忘的话:“当别人认为我功成名就的时候,我反而感到失败。
”(《狐狸洞话语》)欧梵已经获得很高的成就,但是他总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永远的未完成,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过客,一个经历过失败但又超越成败的人文世界里的永远的流浪汉,因此总是一直往前走。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对鲁迅《野草》中的“过客”有很深的领悟,认为生活就是一个不断“走”的过程,“走”是在“无意义”威胁下的惟一有意义的行动。
也就是说,人生是悲剧性的令人绝望的存在,而“走”正是反抗绝望的惟一办法。
欧梵把握了这一点,所以他绝不停步、绝不自恋。
不像许多中国作家和学人那样,写了几部书,就自我膨胀,就自以为是“话语英雄”。
我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愈写愈自大;一类是愈写愈自由。
欧梵是属於愈写愈自由的人。
欧梵不仅不自恋,而且还常常自嘲与自省,他是我平生见到的一个最善於自嘲和自我反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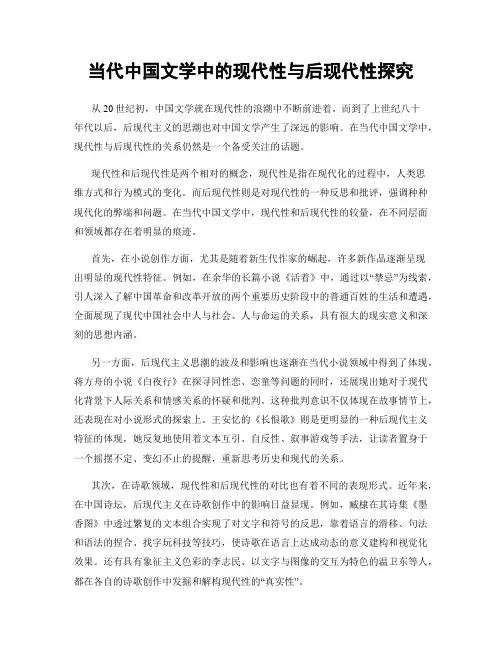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探究从20世纪初,中国文学就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不断前进着。
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现代性是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变化。
而后现代性则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和批评,强调种种现代化的弊端和问题。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较量,在不同层面和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痕迹。
首先,在小说创作方面,尤其是随着新生代作家的崛起,许多新作品逐渐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例如,在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中,通过以“禁忌”为线索,引人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中的普通百姓的生活和遭遇,全面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中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波及和影响也逐渐在当代小说领域中得到了体现。
蒋方舟的小说《白夜行》在探寻同性恋、恋童等问题的同时,还展现出她对于现代化背景下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的怀疑和批判。
这种批判意识不仅体现在故事情节上,还表现在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上。
王安忆的《长恨歌》则是更明显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特征的体现,她反复地使用着文本互引、自反性、叙事游戏等手法,让读者置身于一个摇摆不定、变幻不止的提醒,重新思考历史和现代的关系。
其次,在诗歌领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比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在中国诗坛,后现代主义在诗歌创作中的影响日益显现。
例如,臧棣在其诗集《墨香图》中透过繁复的文本组合实现了对文字和符号的反思,靠着语言的滑移、句法和语法的捏合、找字玩科技等技巧,使诗歌在语言上达成动态的意义建构和视觉化效果。
还有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李志民、以文字与图像的交互为特色的温卫东等人,都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发掘和解构现代性的“真实性”。
不过,在后现代思潮大规模涌入后,部分诗歌创作也出现了轻视纯粹美学的危险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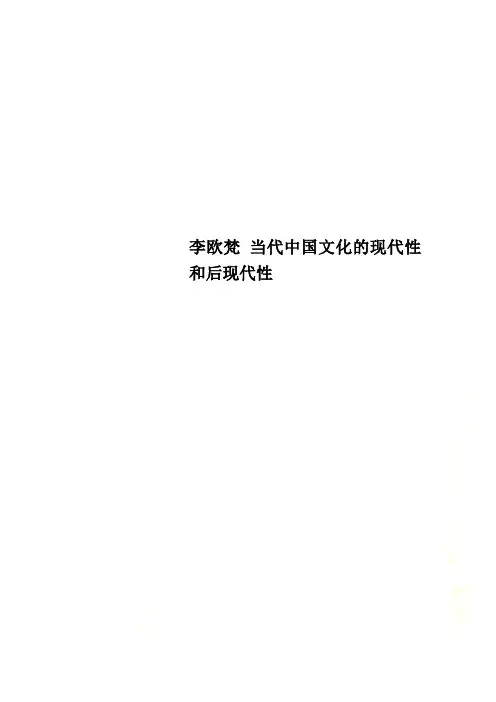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美国) 李欧梵内容提要:本文系作者1999年5月26日在北京大学为文科学生所作的演讲,主要介绍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及其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并借助其理论来观照分析当代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港地区)的一些文化现象,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杰姆逊所称的"后现代阶段"?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同时试图解释"后现代"问题何以在中国引起热烈争论的原因。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状况,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
1985年秋天,美国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在北大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再版了这本书,"后现代",或者说"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这个名词,据我所知就是杰姆逊教授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
在当时来说,此举相当大胆,因为他80年代初才开始从单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后现代理论,而他的那本"大书"《后现代主义后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访问北大后问世的。
换言之,他第一次向世人介绍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理论,是在北京大学。
我想这对于北大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誉。
最近我又重读这本书,仍然觉得受益良多。
来北大之前,我又买了一本杰姆逊教授最新出版的论文集TheCulturalTurn (Verso ,1998),译成中文名为《文化转向》,意即当代整个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的文化转向。
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83年到1998年的8篇论文,1983年那篇经典性的论文《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也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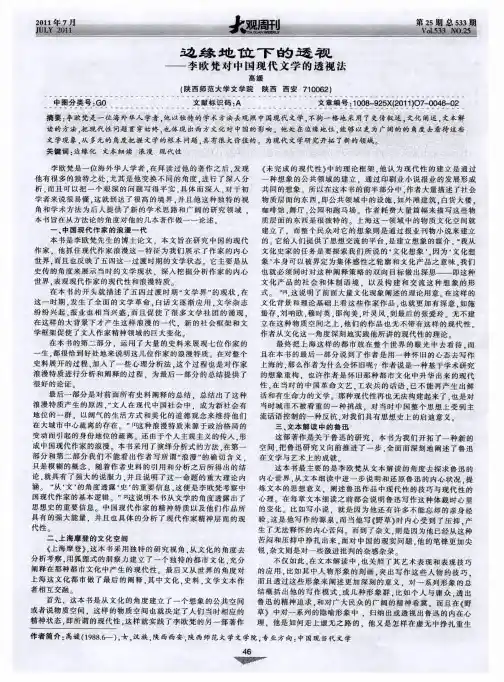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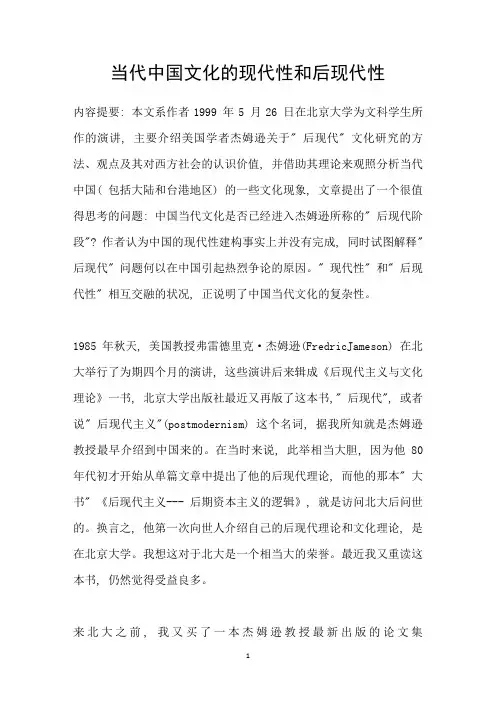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内容提要: 本文系作者1999 年5 月26 日在北京大学为文科学生所作的演讲, 主要介绍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 后现代" 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及其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 并借助其理论来观照分析当代中国( 包括大陆和台港地区) 的一些文化现象, 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杰姆逊所称的" 后现代阶段"? 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事实上并没有完成, 同时试图解释" 后现代" 问题何以在中国引起热烈争论的原因。
" 现代性" 和" 后现代性" 相互交融的状况, 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
1985 年秋天, 美国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 在北大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 这些演讲后来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再版了这本书," 后现代", 或者说"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这个名词, 据我所知就是杰姆逊教授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
在当时来说, 此举相当大胆, 因为他80 年代初才开始从单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后现代理论, 而他的那本" 大书" 《后现代主义--- 后期资本主义的逻辑》, 就是访问北大后问世的。
换言之, 他第一次向世人介绍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理论, 是在北京大学。
我想这对于北大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誉。
最近我又重读这本书, 仍然觉得受益良多。
来北大之前, 我又买了一本杰姆逊教授最新出版的论文集---TheCulturalTurn (Verso,1998), 译成中文名为《文化转向》, 意即当代整个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的文化转向。
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83 年到1998 年的8 篇论文,1983 年那篇经典性的论文《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也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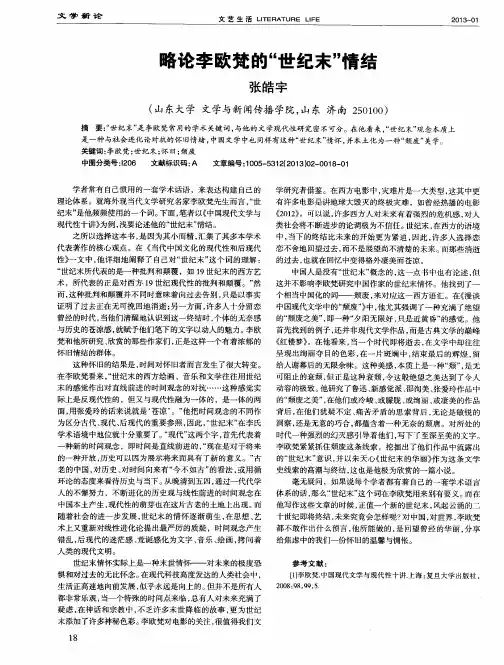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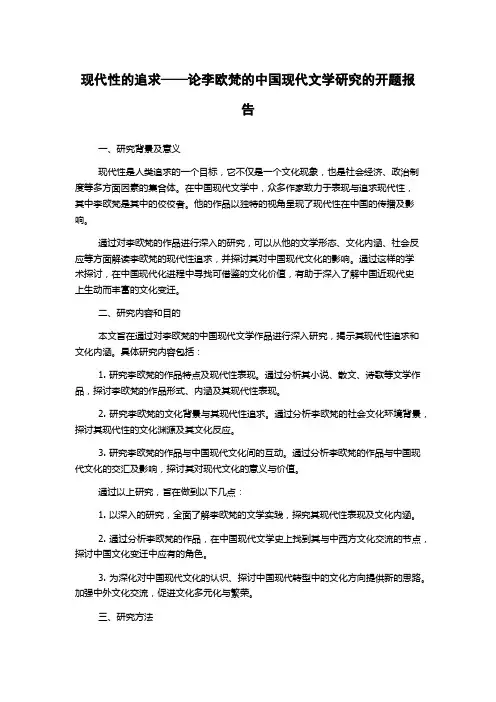
现代性的追求——论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及意义现代性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它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集合体。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众多作家致力于表现与追求现代性,其中李欧梵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了现代性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通过对李欧梵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从他的文学形态、文化内涵、社会反应等方面解读李欧梵的现代性追求,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
通过这样的学术探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寻找可借鉴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上生动而丰富的文化变迁。
二、研究内容和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其现代性追求和文化内涵。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 研究李欧梵的作品特点及现代性表现。
通过分析其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探讨李欧梵的作品形式、内涵及其现代性表现。
2. 研究李欧梵的文化背景与其现代性追求。
通过分析李欧梵的社会文化环境背景,探讨其现代性的文化渊源及其文化反应。
3. 研究李欧梵的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化间的互动。
通过分析李欧梵的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化的交汇及影响,探讨其对现代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通过以上研究,旨在做到以下几点:1. 以深入的研究,全面了解李欧梵的文学实践,探究其现代性表现及文化内涵。
2. 通过分析李欧梵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找到其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节点,探讨中国文化变迁中应有的角色。
3. 为深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认识、探讨中国现代转型中的文化方向提供新的思路。
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多元化与繁荣。
三、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
具体方法如下:1. 较为全面地了解李欧梵的生平和形成背景,从李欧梵的生平背景入手,了解其受到的文化影响和成长环境。
2. 系统地研究李欧梵的作品,既深入了解其文学形态与风格,又关注其思想内涵,探究其现代性重点。
3. 对比研究不同时期的作品创作,从历史性的角度考察李欧梵的文学实践与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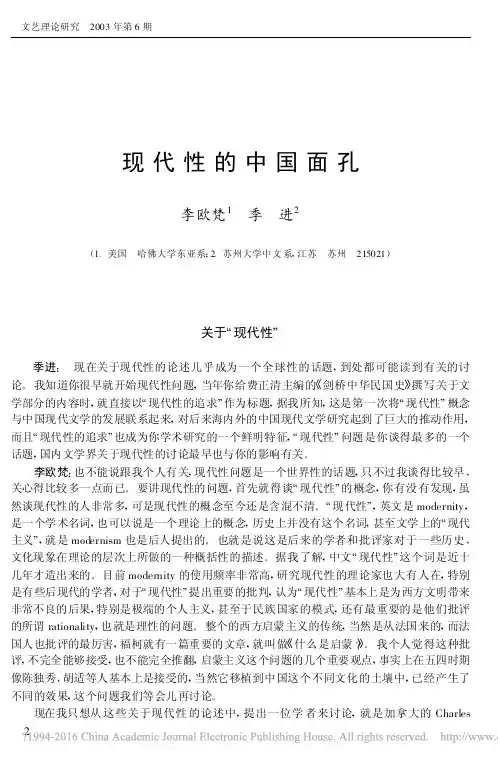
现代性的中国面孔李欧梵1 季 进2(1.美国 哈佛大学东亚系;2.苏州大学中文系,江苏 苏州 215021)关于“现代性” 季进: 现在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几乎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到处都可能读到有关的讨论。
我知道你很早就开始现代性问题,当年你给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撰写关于文学部分的内容时,就直接以“现代性的追求”作为标题,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将“现代性”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对后来海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现代性的追求”也成为你学术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现代性”问题是你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国内文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最早也与你的影响有关。
李欧梵:也不能说跟我个人有关,现代性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只不过我谈得比较早、关心得比较多一点而已。
要讲现代性的问题,首先就得谈“现代性”的概念,你有没有发现,虽然谈现代性的人非常多,可是现代性的概念至今还是含混不清。
“现代性”,英文是modernity,是一个学术名词,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名词,甚至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就是modernism也是后人提出的。
也就是说这是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
据我了解,中文“现代性”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
目前modernity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家也大有人在,特别是有些后现代的学者,对于“现代性”提出重要的批判,认为“现代性”基本上是为西方文明带来非常不良的后果,特别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于民族国家的模式,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批评的所谓rationality,也就是理性的问题。
整个的西方启蒙主义的传统,当然是从法国来的,而法国人也批评的最厉害,福柯就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就叫做《什么是启蒙?》。
我个人觉得这种批评,不完全能够接受,也不能完全推翻,启蒙主义这个问题的几个重要观点,事实上在五四时期像陈独秀、胡适等人基本上是接受的,当然它移植到中国这个不同文化的土壤中,已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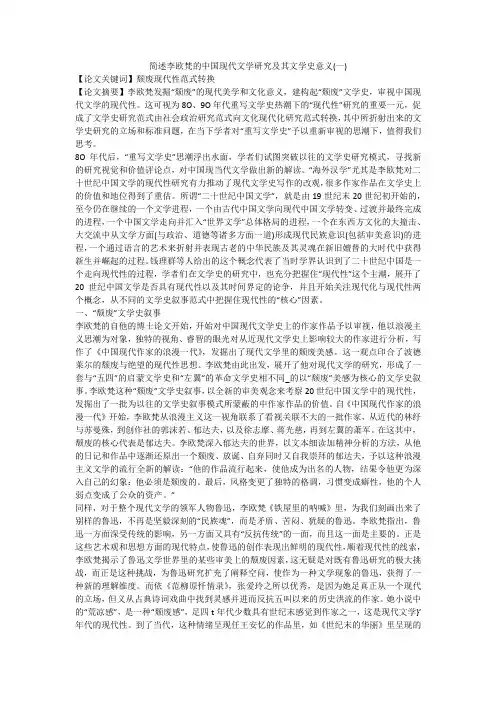
简述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意义(一)【论文关键词】颓废现代性范式转换【论文摘要】李欧梵发掘“颓废”的现代美学和文化意义,建构起“颓废”文学史,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这可视为8O、9O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下的“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一元,促成了文学史研究范式由社会政治研究范式向文化现代化研究范式转换,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和标准问题,在当下学者对“重写文学史”予以重新审视的思潮下,值得我们思考。
8O年代后,“重写文学史”思潮浮出水面,学者们试图突破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寻找新的研究视觉和价值评论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新的解读。
“海外汉学”尤其是李欧梵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有力推动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改观,很多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了重估。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过程。
钱理群等人给出的这个概念代表了当时学界认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走向现代性的过程,学者们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也充分把握住“现代性”这个主潮,展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以及其时间界定的论争,并且开始关注现代化与现代性两个概念,从不同的文学史叙事范式中把握住现代性的“核心”因素。
一、“颓废”文学史叙事李欧梵的自他的博士论文开始,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予以审视,他以浪漫主义思潮为对象,独特的视角、睿智的眼光对从近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进行分析,写作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发掘出了现代文学里的颓废美感。
这一观点印合了波德莱尔的颓废与绝望的现代性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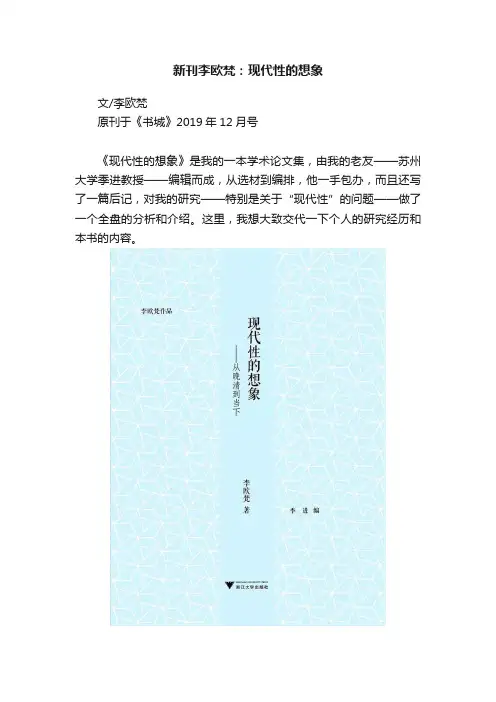
新刊李欧梵:现代性的想象文/李欧梵原刊于《书城》2019年12月号《现代性的想象》是我的一本学术论文集,由我的老友——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编辑而成,从选材到编排,他一手包办,而且还写了一篇后记,对我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做了一个全盘的分析和介绍。
这里,我想大致交代一下个人的研究经历和本书的内容。
《现代性的想象》李欧梵著季进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回顾这些文章所展示的学术研究历程,我发现自己的兴趣虽然很广,然而还是没有越过两个主要的研究领域:晚清和五四。
这两个领域,在理论上如何看待?我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
最近王德威为了纪念五四一百周年,写了一篇短文,提出一个吊诡的命题《没有五四,何来晚清》,显然是对他自己多年前写的另一篇文章《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回应。
这两篇文章彼此呼应,构成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双重悖论。
王德威有意“打破文学史单一和不可逆性的论述”,他借用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的理论,把这两个“历史节点”并置,做吊诡式的互相驳诘:“我们不再问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现代的开端,而要问何以某一个时间点、某一种论述将晚清或五四视为现代的开端。
”他又在句号后加上问号,要我们特别注意复杂多端的“问号语义学”。
这两个挑战性的命题,是从一个当今的“后见之明”的角度提出的,从“是否”问到“何来”和“何以”,已经超越实证性的研究而进入“后设”性的话语论述(discourse)。
我自认理论的训练不足,只能把这两个命题先做字面上的解释:前者指的是晚清的文学为五四的新文学奠定了一个基础,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应该从晚清开始;而后者则要我们把晚清和五四并置和对照,没有五四对晚清的期望和失望,我们也看不出晚清现代性的意义。
二者都可以视为现代的开端,端看用的是什么论述方法。
我如何发现五四和晚清,以及二者所揭示的“现代性”?只能说是一种“偶然”或“偶合”(serendipity)。
这名词源自科学实验,意大利名家艾柯(Umberto Eco)的解释是:往往一些假的或错误的想法和信仰会带领到真的发现,因而改变了世界。
评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术话题。
这个话题深刻地影响到文学史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的形成及其内在构造。
以下就是由为您提供的评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
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是一部相当重要的着作。
关注印刷文化对于现代性的意义,关注新感觉派小说以及城市文化的意义,考察颓废的美学风格,这一切无不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异于传统的坐标。
如果说,国民性、乡土中国、左翼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均是我们熟悉的范畴,那么,《现代性的追求》提到的诸多问题显示了新的视域。
尽管这些问题已经在现代性研究中得到程度不同的论述,但是,这些问题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仍然意义非凡。
当然,如同人们时常发现的那样,洞见与盲区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新的视域可能产生新的遮蔽。
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性的追求》也存在某些疑问,至少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这肯定将引起一系列后续的对话这篇书评不妨视为对话之一。
自夏志清1961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来,海外汉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仅蔚为风潮,而且能人辈出。
王德威曾指出:在中坚一辈的学者中,李欧梵教授的成就,堪称最受瞩目。
①李欧梵的现代文学研究,一方面和王德威一样,重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力图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推向晚清;另一方面,他从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出的美学现代性和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的对立这一基本问题出发,在反思现代性的问题视野中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代性追求的文化和美学特征,特别是城市-颓废文学、文化问题的提出,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以五四启蒙为分水岭、建立在线性进化论基础上的新/旧、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的常识框架,为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条新的理论线索。
《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李欧梵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
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真的恶声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印刷业和中国的现代性以及鲁迅思想的内在矛盾问题;第二辑浪漫的与颓废的共六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所谓五四浪漫个人主义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颓废第三辑则收入了两篇写作于70年代初的文章,这是他应《剑桥中国史》之邀而作的两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历程的长文。
32010年Vol.25No.2一、中西文化的衔接性有海外背景的学者大多是在大陆或港台完成学习,进而到海外深造的,因而也就是先受中国文化浸染,其后又受西方理论训练的,他们游走在中西方文化之间,有着较为完备而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完善的理论背景。
这种文化因素上的丰富多元使他们能够跳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语境,从他者角度反观中国现代文学,显示出独到的学术见解。
李欧梵曾为《剑桥中国近代史》写了“文学潮流:现代性探索,1895-1927”这样的题目。
这就包含着独特的视角:现代性所具有的张力必然要连通起中西方文学交汇与冲突,由此构成叙述的框架,体现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在认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上,李欧梵在西方对现代性认识的基础上勾勒了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条现代性潮流的线索。
他辩证地指出中国现代性概念中的独特之处:“当‘五四’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西方美学现代主义的艺术反抗情绪时,却并未放弃他们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等信念……个人和集体之间并无必然的分裂。
”[1]他重估“五四”浪漫一代作家的价值,形成了一套与“五四”和左翼对立的叙事。
李欧梵将中国现代性推向晚清,突破“五四起源”说,可以说是其在世界文学大框架中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整合和重构。
这种研究方式,既是横向的,又是纵向的,既通向中国文学发展独立性的传统,又建立起了西方文学在共时性的参照系。
同样具有海外背景的学者王德威《小说中国》中提出,“在研究上,下面几个方向有待努力:首先是大陆、港台、海外文学互动的问题;第二点是现代与古典文学的传承问题;第三是对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重新定位的问题,以及对文学作家或作品重新定位的问题。
”[1]王提出对中国现代文学重新建构的要求,与李欧梵的躬身实践探索不谋而合,正是要在中西方文化曾经的断裂之处找到衔接点,并以此作为基本判断依据。
二、文本阐释的个性化相比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国一直相对薄弱。
无论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都是在上世纪初和世纪末被大量引进的,国内学者也自然而然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了理论的演练场。
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现代性的起源与分类按照一般的说法,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8、19世纪之交初步形成,是一个摆脱迷信、愚昧和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过程。
[1]但其实,现代性的来源要复杂得多。
姚斯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认为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
历史学家汤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
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
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
现在一般意义上把现代性视为与资本主义同源的东西,但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的起源依旧是一个含糊的时间段而决非明晰的时间点。
现代性无疑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的概念,内涵比较庞杂。
因此,如果要进行详细的辨析最好先对其进行分类。
韦伯从宗教和形而上角度分离现代性,从而得到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方面。
加拿大学者Charles Taylor的文章《两种现代性》中,他综合了一般国外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提出了现代性的两种模式,其一就是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科技的传统”,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主义以后,理性的发展,工具的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是不可避免的。
韦伯当时创出了一个名词,叫“合理化”。
这个传统后常为一般的社会学家所用。
在科学现代性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
龙源期刊网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
作者:
来源:《大学生》2015年第02期
李欧梵在其《身处中国话语的边缘》(见《现代性的追求》,台北:麦田出版,1996)中讨论了张承志、扎西达娃、李陀等人的作品,他觉得他们在瓦解汉族/传统/主流的中心的意义,他认为内蒙古、西藏、商洛山、湘楚、黑龙江的区域地理与文化意义甚为重要。
但是,还应当注意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划分,远不如族群、知识、哲学、宗教的划分更重要。
正因为如此,海外华人、居住在汉族地区的异族、居住在少数族裔地区的汉人,才显示了其文化上的意味和创造,呈现一个多元的文化语境。
“真正的故乡在心里”,民族、国家、文化并不完全重叠,人们没有必要确认那个实在的客体(空间上的中心)并对其表示忠诚(也许是愚忠)。
李欧梵引用Edward Shils在Center and Periphery:Essays in Macro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中说的话:“本质上,中心价值系统的存在,基于一种人类的需求,这一需求混合着某种可以超越并改变人类具体生存的东西,人们往往有一种与秩序相联系的要求,这一秩序的意义在维度上比他们身体更伟大,比他们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更为中心地处于终极的现实结构中”(p.3),但是,这“中心”却并不是民族、国家、政权或某个人某个党派。
一旦这个中心扩张和渗透到所有日常生活,它会成为意识形态,并欺骗人们的常识,掩盖他们的真实位置和真正希望,从而引起疯狂的结果,比如纳粹。
(1998年1月8日)。
李欧梵:研究鲁迅和张爱玲方法正相反2011年10月27日 18:52:33 稿源: 新华网嘉宾: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李欧梵主持人:记者吴璟李欧梵,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
香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著有中英文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西文学的徊想》、《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上海摩登》,随笔集《狐狸洞话语》、《世纪末的沉思》等。
9月25日,由四川省鲁迅研究会、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跨世纪对话:鲁迅与现代中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近百名专家学者蓉城“论剑”,其中,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成为媒体的焦点。
从早年对“五四”浪漫传统及“现代性”、“后现代”思潮的研究,到近年来电影、音乐、建筑等领域无所不写,不仅有《上海摩登》引发持久不衰的上海文化热,也有研究鲁迅的专著《铁屋中的呐喊》影响着几代读者,李欧梵多方涉猎,自谦是那种薄而不深的“狐狸型学者”。
研讨会后,本报记者专访了李欧梵。
谈鲁迅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一个鲁迅记者:你到每个地方讲学都会讲鲁迅,但每次讲得都不一样。
这一次为什么选择《鲁迅与鬼魂》这个主题?李欧梵:这源于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
这本书里阐释鲁迅的思想文学中始终有各种“鬼”影在闪动,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隐喻,这个“鬼”象征的是,“国民性之鬼”和“民俗之鬼”纠结在一起形成的“黑暗世界”。
它是鲁迅思想文学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这种批判力量的源泉之一。
我就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用这种“幽灵”的意象来重新解释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关联。
现在,我们要“招”鲁迅的“鬼魂”和中国文化的“鬼魂”,就是用一种文学意象式取代严谨的时政式讲鲁迅。
我认为鲁迅是属于全世界的、大众的,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一个鲁迅。
上世纪60年代在欧洲、美国的学界出现左翼思潮,因此鲁迅的作品被介绍到美国和欧洲。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美国) 李欧梵内容提要:本文系作者1999年5月26日在北京大学为文科学生所作的演讲,主要介绍美国学者杰姆逊关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及其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价值,并借助其理论来观照分析当代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港地区)的一些文化现象,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是否已经进入杰姆逊所称的"后现代阶段"?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同时试图解释"后现代"问题何以在中国引起热烈争论的原因。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状况,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
1985年秋天,美国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在北大举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辑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又再版了这本书,"后现代",或者说"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这个名词,据我所知就是杰姆逊教授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
在当时来说,此举相当大胆,因为他80年代初才开始从单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后现代理论,而他的那本"大书"《后现代主义后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就是访问北大后问世的。
换言之,他第一次向世人介绍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理论,是在北京大学。
我想这对于北大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誉。
最近我又重读这本书,仍然觉得受益良多。
来北大之前,我又买了一本杰姆逊教授最新出版的论文集TheCulturalTurn (Verso ,1998),译成中文名为《文化转向》,意即当代整个文化批评和文化理论的文化转向。
书中收录了他写于1983年到1998年的8篇论文,1983年那篇经典性的论文《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也在其中。
这本书受到美国各个学界的重视,我从前的同事,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也是马克思主义者,PerryAnderson ,本来要为这本书作序,结果却越写越长,竟至成书,名为TheOriginsofPostmodernity (Verso ,1998),即《后现代性的来源》。
以介绍杰姆逊入手,Anderson把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都展现出来。
据Anderson 说,这个名词最早见于西班牙文坛,后来在1950年左右,中国革命刚刚成功时,有一位美国诗人CharlesOrson 提出了一个主张:20世纪的上半叶是现代,下半叶就是后现代;后现代的动力不是西方,而是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革命。
这样说来,中国与西方后现代的起源可能还有一层关系。
当然,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杰姆逊教授在其北大的演讲中提出的,他认为所谓文化上的现代和后现代,是和整个西方经济历史的发展相关的。
所谓现代主义是文学、艺术上的名词,而现代性是较为广义的文化历史上名词。
他把这个时期定在1880年左右到1930年左右;而他认为后现代阶段是从1960年前后开始的。
这是他的一种历史分期法。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现代性所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盛期的状况,他引用了列宁的名言: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就是帝国主义。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资本开始向世界发展,这种发展到了最极端之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而文学艺术表现的就是所谓"highmodernism",即高潮现代主义。
可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在文化方面有了非常大的变动。
杰姆逊受一位重要的比利时学者ErnestMandel 的影响,写了一本叫做LateCapitalism(《后期资本主义》)的书,认为后期资本主义和盛期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后期资本主义逐渐地跨国化、国际化乃至现在所说的全球化,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近几年来最大的发展就是全盘的金融化,所谓金融化就是把抽象的钱在世界的各地运转。
在他看来,这种抽象的金融化倾向给西方文化带来了非常大的转变,后现代的文化即所谓电动器械、电脑,以及资讯的高速流通,其中最重要的是媒体,特别是视觉媒体,已影响到所有人的生活,他认为,五六十年代电视的发明为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电视的普及使整个人类生活视觉化。
彩色电视机所表现出的形象完全是虚假的,是模拟式的。
当然他用的不是"假"这个词,而是援引了法国理论家波德里亚的一个词:simulacrum,意即"摹拟的假相"."假相"事实上在人们的生活中变成了真相,真实的生活反而被抽掉了,生活中展现的正是这种"假相",或称"模拟象".所以说电视的视觉影响对于整个人类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
另一个现象就是所谓高级文化和普通文化的融合。
当时现代主义所揭示的几个重要的立足点都已经被打破了。
比如,在思想上,现代性所标榜的是个体的建立,是一种理性,是对于前途的乐观。
杰姆逊教授认为这些在后现代时期都已经改了。
而最主要的是现代主义所谓"个体"问题在语言上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彻底消解。
现代主义所说的作家个人的视野,作家的天才,作家作品本身的震撼力,作家用自己的语言建立、并借以作用于读者的自己的世界等等一系列重要的论点,全部都被后现代主义理论推翻。
在这种情形下,他认为在后现代中没有所谓"独创性"这回事;假若说后现代具有独创性的话,那就是"复制",所有的东西都是按原本复制出来的。
电影就是一个最大的复制品,你并不知道原本是什么;电视中的形象也是一连串的复制品;甚至包括他自己的理论,他也认为是复制品。
这些复制品在全球各地不断地发展、衍生,其结果是一般人对于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从欣赏转为消费。
所以说现在我们处身的时代就是文化大规模的复制、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时代。
后现代理论中提到的已经不是一个个人阅读或创作的行为,而是一种集体的大众性消费行为。
他认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以上是我对杰姆逊教授的理论所作的简略介绍。
我是把杰姆逊的理论放在他个人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他所处的境遇以及西方文化思想史的境遇之中来看待的。
我认为杰姆逊教授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自己并不是非常热衷于后现代主义,可是他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看出了世界文化的转变之后,拒绝对这种现象作道德式的批判。
也就是说,他并不扮演上帝的角色,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作出评判,如果是这样,他未免把自已抬得太高了。
而另一方面,他认为历史还是向前走的,可是将来的世界会是何种景象?未来资本主义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后现代主义以后又将如何?他最近非常困扰的就是日本学者福山提出的所谓"历史终结"的问题。
福山认为,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全面征服世界,民主逐渐征服世界,以前的历史到此已是尽头,已经无路可走。
对于这种观点杰姆逊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意的,但是他又认为照此发展下去,对于整个人类并无益处。
而他又不愿扮演先知或领袖的角色,他始终困扰在自己所建立的这个理论系统之中,在其中对耳闻目睹的"假相"的文化作不停歇的探讨。
他探讨的面越来越广,甚至于从他原来的专业法国文学、理论一直探讨到文学作品、艺术、建筑(特别是洛杉矶的那家旅馆),最近又开始探讨美国好莱坞的电影。
他在这本书中提到,现在的意象世界已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看电影已经不注重情节,因为一切情节不过是为打斗和特技镜头作铺垫而已,人们只注目于所谓"镜头的精华",这是视觉文化发展到极致的表现。
于是他说:看样子,电影的预告片要比电影本身还重要,因为预告片是在短短两、三分钟里把电影中的精华镜头剪接起来。
他说这番话时,美国的《星球大战》续集即将上映,我这次来北大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人们争相观看这部电影的预告片。
许多人花费七、八美元去看一场名不见经传的电影,就是为了能一睹随片附映的《星球大战》的预告片。
当然,有一点是杰姆逊没有完全料到的,《星球大战》上映之后人们依然是排着长龙观看。
我们据此可以看出,杰姆逊教授的真知灼见是相当了不起的。
无论是高调的东西,还是低调的东西他都非常认真地加以研讨,并进行理论上的批判。
杰姆逊教授今天如果在场他一定会说,他的这个理论还是在西方的立场上提出的。
但是由于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性的,那么他将不得不承认,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将来必然会发展为后现代性的社会,这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你相信这种潮流,你就不能否认中国会进入这个世界性的潮流。
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的文化是否已经进入了杰姆逊所说的后现代阶段。
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随之产生。
如果我有机会与杰姆逊教授对话,我将重新提出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否具有直线般的关联,有了前者的产生,就必然有后者的出现?其中是否有错综复杂的可能性?就杰姆逊的理论来看,西方的发展非论。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公开的政策是要与世界挂钩,甚至要进入世界。
这个历程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梁启超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特别说他自已要作一个世界人,他在心目中所画的地图,就是将自已的足迹从广东画到中国,画到日本,画到夏威夷,画到美国,最后画到整个世界。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过程,而现在整个中国的国策是变成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进入所谓全球的系统。
这种情况之下,只有后现代适于描述中国所处的状态,因为后现代标榜的是一种世界"大杂烩"的状态,各种现象平平地摆放在这里,其整个空间的构想又是全球性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学者对于后现代在理论上争得非常厉害,但是并不"玩理论",这一点与@!#$学者正相反。
@!#$学者对于后现代理论早在二十年以前就已进行介绍,而且每个人都很善于引经据典地"玩理论",诸如女权理论、拉康理论、后殖民理论等,其争论仅局限于学界,并不认为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中国的学者则非常严肃,认为理论上的争论就代表了对中国文化的发言权,甚至有人说后现代理论也有所谓"文化霸权"这回事,要争得话语上的霸权、理论上的霸权,要比别人表述得更强有力,要在争论中把自己的一套理论表述得更有知识,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心态更证明了中国所谓现代性并没有完结。
从五四开始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五四"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从启蒙的立场来影响社会,当时的启蒙是理性的,是从西方的启蒙主义背景出发的;后现代的理论则倒过来,反对启蒙主义,但仍旧认为可以借助西方各方面的知识来影响中国社会。
换言之,它在思想内容上改变了很多,但在思想模式上仍不脱现代主义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