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逻辑发展
- 格式:pdf
- 大小:251.51 KB
- 文档页数: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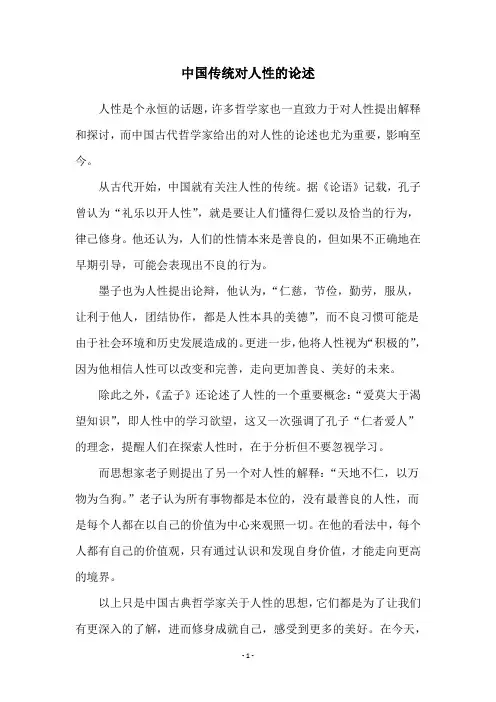
中国传统对人性的论述
人性是个永恒的话题,许多哲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对人性提出解释和探讨,而中国古代哲学家给出的对人性的论述也尤为重要,影响至今。
从古代开始,中国就有关注人性的传统。
据《论语》记载,孔子曾认为“礼乐以开人性”,就是要让人们懂得仁爱以及恰当的行为,律己修身。
他还认为,人们的性情本来是善良的,但如果不正确地在早期引导,可能会表现出不良的行为。
墨子也为人性提出论辩,他认为,“仁慈,节俭,勤劳,服从,让利于他人,团结协作,都是人性本具的美德”,而不良习惯可能是由于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造成的。
更进一步,他将人性视为“积极的”,因为他相信人性可以改变和完善,走向更加善良、美好的未来。
除此之外,《孟子》还论述了人性的一个重要概念:“爱莫大于渴望知识”,即人性中的学习欲望,这又一次强调了孔子“仁者爱人”的理念,提醒人们在探索人性时,在于分析但不要忽视学习。
而思想家老子则提出了另一个对人性的解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老子认为所有事物都是本位的,没有最善良的人性,而是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价值为中心来观照一切。
在他的看法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只有通过认识和发现自身价值,才能走向更高的境界。
以上只是中国古典哲学家关于人性的思想,它们都是为了让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修身成就自己,感受到更多的美好。
在今天,
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思想中吸取精华,为进一步探索和实践人性发展道路找到更多的灵感与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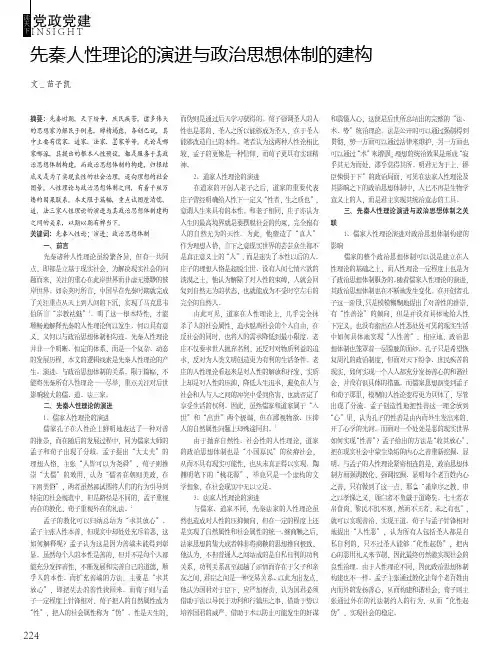
文_读天下党政党建224I N S I G H T摘要:先秦时期,天下纷争,庶民疾苦,诸多伟大的思想家为解民于倒悬,殚精竭虑,各创己说,其中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无论是哪家哪派,其提出的根本人性预设,都是服务于其政治思想体制构建,而政治思想体制的构建,归根结底又是为了实现良性的社会治理,迈向理想的社会图景。人性理论与政治思想体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本文限于篇幅,重点试图厘清儒、道、法三家人性理论的演进与其政治思想体制建构之间的关系,以期以期有裨当下。关键词:先秦人性论;演进;政治思想体制一、前言先秦诸种人性理论虽纷繁各异,但有一共同点,即都是立基于现实社会,为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来,关注的重心在此岸世界而非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如余英时所言,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完成了关注重点从天上到人间的下沉,实现了马克思韦伯所言“宗教祛魅”1。明了这一根本特性,才能顺畅地解释先秦的人性理论何以发生、何以具有意义,又何以与政治思想体制相勾连。先秦人性理论并非一个明晰、恒定的体系,而是一个复杂、动态的发展历程,本文的逻辑线索是先秦人性理论的产生、演进、与政治思想体制的关系。限于篇幅,不能将先秦所有人性理论一一尽举,重点关注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儒、道、法三家。二、先秦人性理论的演进1、儒家人性理论的演进儒家孔子在人性论上鲜明地表达了一种对善的推崇,而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同为儒家大师的孟子和荀子出现了分歧。孟子提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则推崇“大儒”的效用,认为“儒者在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两者虽然都试图将人们的行为引导到特定的社会规范中,但是路径是不同的,孟子重视内在的教化,荀子重视外在的礼法。2孟子的教化可以归纳总结为“求其放心”。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但现实中却处处充斥着恶,这如何解释呢?孟子认为这是因为善端未能得到彰显。虽然每个人的本性是善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善性,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道德,顺乎人的本性。而扩充善端的方法,主要是“求其放心”,即把失去的善性找回来。而荀子则与孟子一定程度上针锋相对,荀子把人的自然属性成为“性”,把人的社会属性称为“伪”。性是天生的,而伪则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荀子强调圣人的人性也是恶的,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在于圣人能够改造自己的本性。笔者认为这两种人性论相比较,孟子的更像是一种信仰,而荀子更具有实证精神。2、道家人性理论的演进在道家的开创人老子之后,道家的重要代表庄子曾经明确给人性下一定义“性者,生之质也”,意谓人生来具有的本性。和老子相同,庄子亦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摆脱社会的约束,完全抱有人的自然无为的天性。为此,他塑造了“真人”作为理想人格,言下之意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是迷失了本性以后的人。庄子的理想人格是超脱尘世、没有人间七情六欲的淡漠之士,他认为解除了对人性的束缚,人就会回复到自然无为的状态,也就能成为不受时空左右的完全的自然人。由此可见,道家在人性理论上,几乎完全抹杀了人的社会属性,追求脱离社会的个人自由,在反社会的同时,也将人的需求降低到最小限度。老庄不仅要求世人抛弃名利,还反对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反对为人类文明创造更为有利的生活条件。老庄的人性理论看起来是对人性的解放和抒发,实质上却是对人性的压抑,降低人生追求,避免在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受到伤害,也就否定了享受生活的权利。因此,虽然儒家和道家属于“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但在鄙视物欲、压抑人的自然属性问题上却殊途同归。3由于抛弃自然性、社会性的人性理论,道家的政治思想体制也是“小国寡民”的贫瘠社会,从而不具有现实可能性,也从未真正得以实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毕竟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学想象,在社会现实中无以立足。3、法家人性理论的演进与儒家、道家不同,先秦法家的人性理论虽然也造成对人性的压抑倾向,但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实现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继商鞅之后,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将商鞅的思想推向极致,他认为,不但普通人之间结成的是自私自利的功利关系,功利关系甚至超越了亲情而存在于父子和亲友之间,君臣之间是一种交易关系。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国君对于臣下,应严加督责,认为国君必须借助于法以导民于功利和行镇压之事,借助于势以培养国君的威严,借助于术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奸谋和震慑人心,这便是后世所总结出的完整的“法、术、势”统治理论。法是公开的可以通过强制得到贯彻,势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术”来增强,理想的统治效果是形成“寂乎其无为而处,谬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于下”的政治局面,可见在法家人性理论及其影响之下的政治思想体制中,人已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君主实现其统治意志的工具。三、先秦人性理论演进与政治思想体制之关联1、儒家人性理论演进对政治思想体制构建的影响儒家的整个政治思想体制可以说是建立在人性理论的基础之上,而人性理论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政治思想体制服务的。随着儒家人性理论的演进,其政治思想体制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开创者孔子这一阶段,只是模模糊糊地提出了对善性的推崇,有“性善论”的倾向,但是并没有具体地给人性下定义,也没有指出在人性恶处处可见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具体地实现“人性善”,相应地,政治思想体制也笼罩着一层朦胧的面纱。孔子只是希望恢复周礼的政治制度,但面对天下纷争、庶民疾苦的现实,如何实现一个人人都充分发扬善心的和谐社会,并没有很具体的措施。而儒家思想演变到孟子和荀子那里,模糊的人性论变得更为具体了,尽管出现了分流。孟子创造性地把性善这一理念放到“心”里,认为孔子的性善是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开了心学的先河。而面对一个处处是恶的现实世界如何实现“性善”?孟子给出的方法是“收其放心”,把在现实社会中蒙尘染垢的内心之善重新挖掘、显明。与孟子的人性理论紧密相连的是,政治思想体制方面强调教化,强调挖掘、显明每个老百姓内心之善,只有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就可以实现善治,实现王道。荀子与孟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人性恶”,认为所有人包括圣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不过圣人能够“化性起伪”,把内心的恶用礼义来节制,因此最终仍然能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由于人性理论不同,因此政治思想体制构建也不一样。孟子主张通过教化让每个老百姓由内而外的发扬善心,从而构建和谐社会;荀子则主张通过外在的礼法制约人的行为,从而“化性起伪”,实现社会的稳定。先秦人性理论的演进与政治思想体制的建构苗子凯读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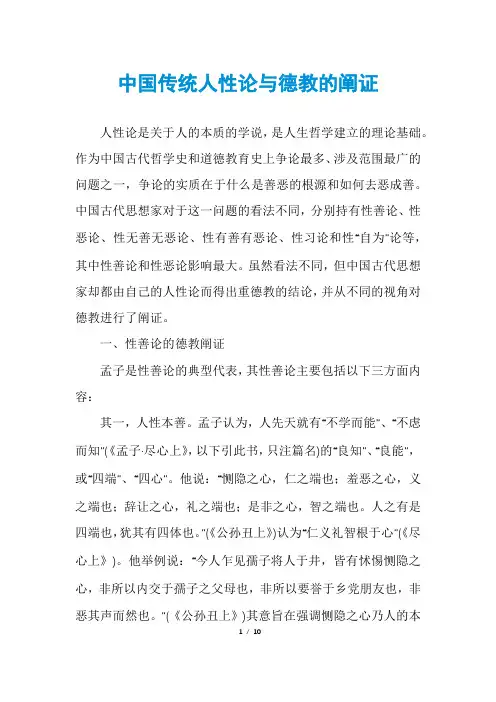
中国传统人性论与德教的阐证人性论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是人生哲学建立的理论基础。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和道德教育史上争论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问题之一,争论的实质在于什么是善恶的根源和如何去恶成善。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分别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习论和性“自为”论等,其中性善论和性恶论影响最大。
虽然看法不同,但中国古代思想家却都由自己的人性论而得出重德教的结论,并从不同的视角对德教进行了阐证。
一、性善论的德教阐证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其性善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其一,人性本善。
孟子认为,人先天就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孟子·尽心上》,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的“良知”、“良能”,或“四端”、“四心”。
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公孙丑上》)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
他举例说:“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公孙丑上》)其意旨在强调恻隐之心乃人的本1/ 10性。
其二,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
孟子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离娄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四心”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只有保存“四心”,才能成为“君子”;如果丢失“四心”,就会成为“庶人”。
丢失了“四心”而又不知找回,人就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了。
其三,人性可失又可求。
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为什么又有人为不善呢?对此,孟子解释道:“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告子上》)意即,有人为不善,并非由于这些人先天无“善端”,而是由于他们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丢弃了这些“善端”所致,用孟子的话来说就叫做“放其良心”:“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上》)这里所谓的“放其良心”,也就是“失其本心”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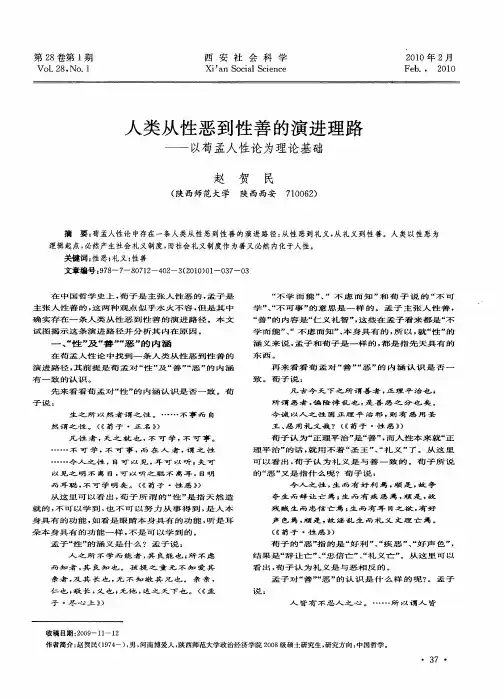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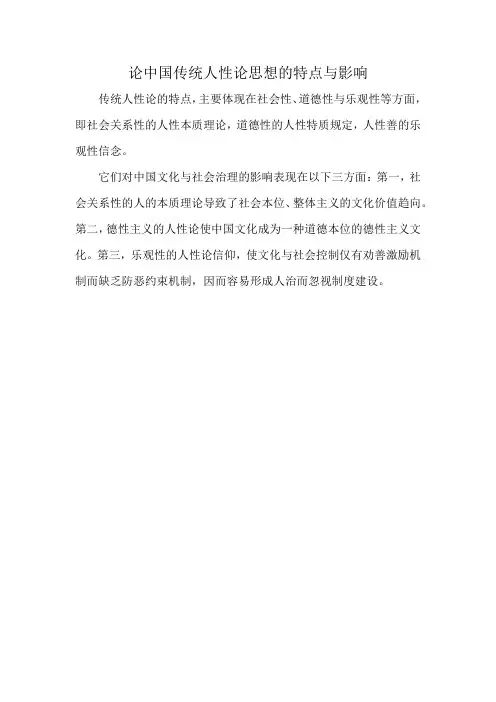
论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的特点与影响传统人性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社会性、道德性与乐观性等方面,即社会关系性的人性本质理论,道德性的人性特质规定,人性善的乐观性信念。
它们对中国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社会关系性的人的本质理论导致了社会本位、整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趋向。
第二,德性主义的人性论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道德本位的德性主义文化。
第三,乐观性的人性论信仰,使文化与社会控制仅有劝善激励机制而缺乏防恶约束机制,因而容易形成人治而忽视制度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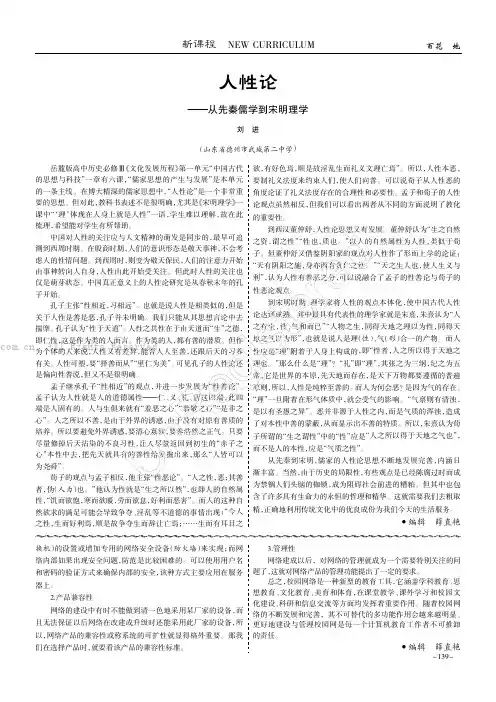
百花园地新课程NEW CURRICULUM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Ⅲ《文化发展历程》第一单元“中国古代的思想与科技”一章有六课,“儒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本单元的一条主线。
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中,“人性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但对此,教科书表述不是很明确,尤其是《宋明理学》一课中“‘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性”一语,学生难以理解,故在此梳理,希望能对学生有所帮助。
中国对人性的关注应与人文精神的萌发是同步的,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
在殷商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是敬天事神,不会考虑人的性情问题。
到西周时,则变为敬天保民,人们的注意力开始由事神转向人自身,人性由此开始受关注。
但此时人性的关注也仅是萌芽状态。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人性论研究是从春秋末年的孔子开始。
孔子主张“性相近,习相远”。
也就是说人性是相类似的,但是关于人性是善是恶,孔子并未明确。
我们只能从其思想言论中去揣摩。
孔子认为“性于天道”。
人性之共性在于由天道而“生”之德,即仁性,这是作为类的人而言。
作为类的人,都有善的潜质。
但作为个体的人来说,人性又有差异,能否人人至善,还跟后天的习养有关。
人性可塑,要“择善而从”“里仁为美”。
可见孔子的人性论还是偏向性善说,但又不是很明确。
孟子继承孔子“性相近”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为“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性就是人的道德属性———仁、义、礼、智这四端,此四端是人固有的。
人与生俱来就有“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
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外界的诱惑,由于没有对原有善质的培养。
所以要避免外界诱惑,要清心寡欲,要养浩然之正气。
只要尽量修掉后天沾染的不良习性,让人尽量返回到初生的“赤子之心”本性中去,把先天就具有的善性给发掘出来,那么“人皆可以为尧舜”。
荀子的观点与孟子相反,他主张“性恶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
”他认为性就是“生之所以然”,也即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
而人的这种自然欲求的满足可能会导致争夺、淫乱等不道德的事情出现:“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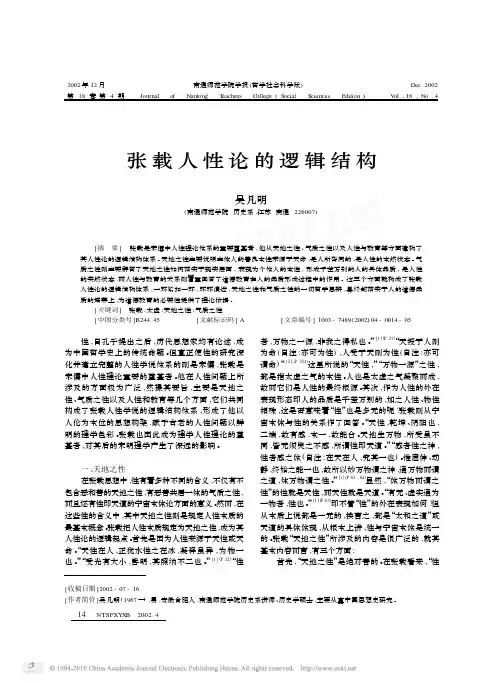
NTSFXY X B 2002.414吴凡明(南通师范学院历史系,江苏南通226007)张载人性论的逻辑结构性,自孔子提出之后,历代思想家均有论述,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传统命题。
但真正使性的研究深化并建立完整的人性学说体系的则是宋儒,张载是宋儒中人性理论重要的奠基者。
他在人性问题上所涉及的方面极为广泛,然撮其要旨,主要是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以及人性和教育等几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张载人性学说的逻辑结构体系,形成了他以人伦为本位的思想构架,赋予古老的人性问题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张载也因此成为理学人性理论的奠基者,对其后的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天地之性在张载思想中,性有着多种不同的含义,不仅有不包含恶和善的天地之性,有恶善共居一体的气质之性,而且还有性即天道的宇宙本体论方面的意义。
然而,在这些性的含义中,其中天地之性则是规定人性本质的最基本概念。
张载把人性本质规定为天地之性,成为其人性论的逻辑起点。
首先是因为人性来源于天性或天命。
“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
”“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纳不二也。
”[1](P.22)“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之得私也。
”[1](P.21)“天授于人则为命(自注:亦可为性),人受于天则为性(自注:亦可谓命)”[2](P.324)这里所说的“天性,”“万物一源”之性,都是指太虚之气的本性。
人也是太虚之气凝聚而成,故而它们是人性的最终根源。
其次,作为人性的外在表现形态即人的品质是千差万别的,加之人性、物性相殊,这是否意味着“性”也是多元的呢?张载则从宇宙本体与性的关系作了回答。
“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自注:在天在人,究其一也)。
惟屈伸、动静,终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万物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谓之性。
”[1](P.63-64)显然,“体万物而谓之性”的性就是天性,而天性就是天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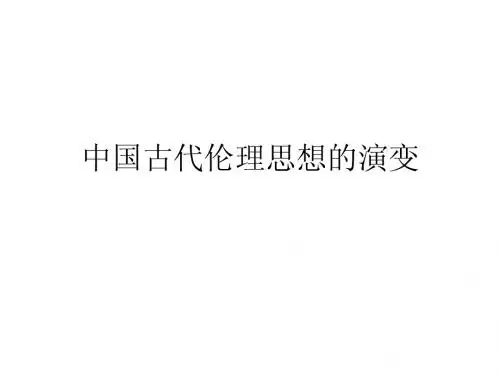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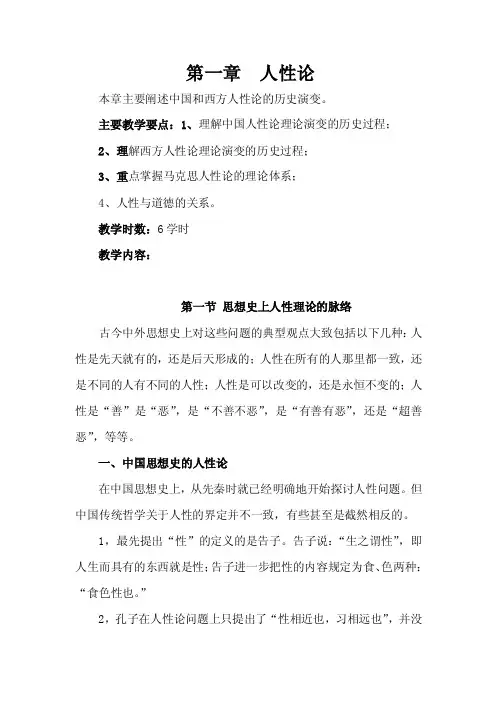
第一章人性论本章主要阐述中国和西方人性论的历史演变。
主要教学要点:1、理解中国人性论理论演变的历史过程;2、理解西方人性论理论演变的历史过程;3、重点掌握马克思人性论的理论体系;4、人性与道德的关系。
教学时数:6学时教学内容:第一节思想史上人性理论的脉络古今中外思想史上对这些问题的典型观点大致包括以下几种:人性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人性在所有的人那里都一致,还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性;人性是可以改变的,还是永恒不变的;人性是“善”是“恶”,是“不善不恶”,是“有善有恶”,还是“超善恶”,等等。
一、中国思想史的人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从先秦时就已经明确地开始探讨人性问题。
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性的界定并不一致,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1,最先提出“性”的定义的是告子。
告子说:“生之谓性”,即人生而具有的东西就是性;告子进一步把性的内容规定为食、色两种:“食色性也。
”2,孔子在人性论问题上只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并没有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
孔子把“仁”作为人的根本属性,他对人性充满乐观自信,对人的期望和要求都是很高的,把人的私利与公利对立起来,对人追求私利物欲,持贬抑或轻视态度。
孔子认为人性并非纯善纯美,也并非生而圣人君子,他认为人须经过自觉学习礼,加强自我修养才能成就人性之善。
孔子还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君子,而是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成为圣人君子。
由此他把人分为两极:圣人——凡人、君子——小人等。
孔子的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观定下了一个基调。
3,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性善论。
孟子认为告子的看法会混淆人、犬、牛等各种动物的区别,他从人与动物区别的角度来论述性。
孟子同样不同意告子把食色等感官满足作为性的内容,认为构成性的是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
4,荀子认为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尺度在于是否有“礼”,“礼”标志着“人之所以为人者。
”荀子认为人性是“所生而有”、“无待而然”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的生存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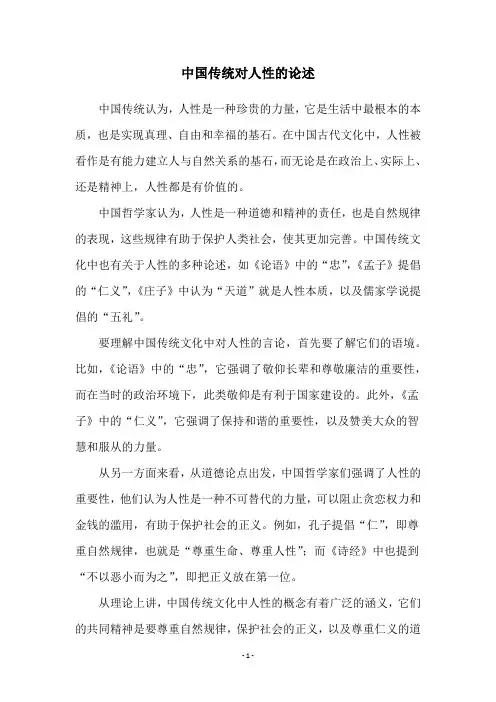
中国传统对人性的论述
中国传统认为,人性是一种珍贵的力量,它是生活中最根本的本质,也是实现真理、自由和幸福的基石。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人性被看作是有能力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石,而无论是在政治上、实际上、还是精神上,人性都是有价值的。
中国哲学家认为,人性是一种道德和精神的责任,也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这些规律有助于保护人类社会,使其更加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关于人性的多种论述,如《论语》中的“忠”,《孟子》提倡的“仁义”,《庄子》中认为“天道”就是人性本质,以及儒家学说提倡的“五礼”。
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言论,首先要了解它们的语境。
比如,《论语》中的“忠”,它强调了敬仰长辈和尊敬廉洁的重要性,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此类敬仰是有利于国家建设的。
此外,《孟子》中的“仁义”,它强调了保持和谐的重要性,以及赞美大众的智慧和服从的力量。
从另一方面来看,从道德论点出发,中国哲学家们强调了人性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性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可以阻止贪恋权力和金钱的滥用,有助于保护社会的正义。
例如,孔子提倡“仁”,即尊重自然规律,也就是“尊重生命、尊重人性”;而《诗经》中也提到“不以恶小而为之”,即把正义放在第一位。
从理论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的概念有着广泛的涵义,它们的共同精神是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社会的正义,以及尊重仁义的道
德规范。
在实践中,这种哲学思想也被贯彻到了日常生活中,以及家庭、学校等社会环境中。
当今,在现代社会,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一传承中学习到很多有价值的道理,从而提升我们的人格良知,为实现真理、自由和幸福而努力。
论先秦人性理论的演进与政治思想体制的建构一、前言先秦诸种人性理论虽纷繁各异,但有一共同点,即都是立基于现实社会,为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而来,关注的重心在此岸世界而非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
如余英时所言,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完成了关注重点从天上到人间的下沉,实现了马克思韦伯所言宗教祛魅。
明了这一根本特性,才能顺畅地解释先秦的人性理论何以发生、何以具有意义,又何以与政治思想体制相勾连。
先秦人性理论并非一个明晰、恒定的体系,而是一个复杂、动态的发展历程,本文的逻辑线索是先秦人性理论的产生、演进、与政治思想体制的关系。
限于篇幅,不能将先秦所有人性理论一一尽举,重点关注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儒、道、法三家。
二、先秦人性理论的演进1、儒家人性理论的演进儒家孔子在人性论上鲜明地表达了一种对善的推崇,而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同为儒家大师的孟子和荀子出现了分歧。
孟子提出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则推崇大儒的效用,认为儒者在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两者虽然都试图将人们的行为引导到特定的社会规范中,但是路径是不同的,孟子重视内在的教化,荀子重视外在的礼法。
2孟子的教化孟子的教化可以归纳总结为求其放心。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但现实中却处处充斥着恶,这如何解释呢?孟子认为这是因为善端未能得到彰显。
虽然每个人的本性是善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善性,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道德,顺乎人的本性。
而扩充善端的方法,主要是求其放心,即把失去的善性找回来。
而荀子则与孟子一定程度上针锋相对,荀子把人的自然属性成为性,把人的社会属性称为伪。
性是天生的,而伪则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
荀子强调圣人的人性也是恶的,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在于圣人能够改造自己的本性。
笔者认为这两种人性论相比较,孟子的更像是一种信仰,而荀子更具有实证精神。
三、先秦人性理论演进与政治思想体制之关联1、儒家人性理论演进对政治思想体制构建的影响儒家的整个政治思想体制可以说是建立在人性理论的基础之上,而人性理论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政治思想体制服务的。
1999年7月中州学刊Jul.1999第4期(总第112期)AcademicJournalofZhongzhouNo.4
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逻辑发展张怀承内容摘要 人性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它是对人自身本质的认识。孟子、荀子分别提出“性善论”和“性恶论”,奠定了传统人性论的基础。汉唐学者折中孟荀,建立了“性三品”、“性善情恶”等学说。宋代以后的学者总结了前人成就,完成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理论构建。如果说先秦孟荀的人性论是单一道德价值的人性一元论,汉唐的人性论则属于多重道德价值的人性多元论,只是把孟荀的观点简单的并列、综合,那么,宋明理学的人性论则是单一道德价值的人性二元论。孟荀把善与恶的斗争视为道德主体与客观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对立,汉唐学者则把这种对立转移到社会生活之中,用人的社会等级差别来寻找善恶的根据,导致了道德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宋明理学则将善与恶都植根于人性之中,强化了道德主体自身的紧张,强调了主体自我的理欲交战。这就在传统道德的范围之内最终确定了人的道德完善的内在超越之路。从不同学派的致思路径来看,儒家的人性论反映了人的德性觉悟,主要是追求道德精神的超越与不朽。道家以及道教的人性论反映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觉悟,追求生命的永恒与不朽。佛教的人性论(佛性论)则表现了主体的智性觉悟,它追求的不是任何生命的完善或现实的价值,而是对生命本
身的超越。关键词 中国传统 人性论 逻辑发展张怀承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 长沙 (410081)
人性论是中国传统伦理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道德是人的主体属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伦理学是关于人的完善的学说,是从道德的角度对人的存在、发展及其本质完善的认识。中国传统伦理学说从西周开始就对人在宇宙中的作用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形成了人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人成为传统伦理道德最为关心的核心内容,而对人的认识首先就必须回答人究竟是什么,他与自然界其他存在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从而论证道德的必需与可能。正是对人的认识的这一特殊视角,形成了中国传统伦理学说德性主义的人性论思想,为天人合德的道德学说提供了人性论的依据。从孔子到宋明理学,传统人性论的发展就反映了古代伦理学说对人的本质认识不断深入的逻辑进程。
一性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它是对客观对象世界(包括人自身)本质的认识。性范畴的产生,标志着古人对事物的认识已经由表层的现象深入到了里层的内在本质。目前已知的甲骨文中未见性字。最早的性字见于金文,而且其字形与“生”字几乎完全一致。《蔡姑簋》作“Β|”,《齐中子姜 》作“⊥Β”,其释义为“生命”、“性命”。故性之本义当为“生”,不过这个生非指生47长、滋生之生,而指生命之生。《左传・昭公十九年》中“民乐其性”这个性即用其本义。《说文系传通论》:“人因五方之风、山川之气以生。故曰:性者,生也。既生有禀,曰性。”生字本有生长、生命之义。《说文》:“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生之本义为草在土上生长。此种生长不同于无生的死物,且正是这种生长把有生之物与无生之物区别开来,故生为有生之物的特殊规定,生即由生长而转指生命的内涵规定,生而所有者称之为性,性便有了天生之本性、本质的涵义。推而广之,又引伸为宇宙万物的本质规定。当性从人身上抽象出来,成为一般的本质规定,并进而把它和本体相结合之后,就上升为天地万物共同的本质,性又具有了存在的本体和根据的义蕴。性在先秦诸子以前的典籍中已经出现,《尚书》二见,《诗经》三见,《左传》八见,《国语》四见,略备如下诸义:(1)生命。“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诗经・大雅・卷阿》)所谓“俾尔弥尔性”,意为使你生命长久。此性非指性质、本性,而指生命。(2)天地的本性。“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此处“天地之性”指天地的“六气”、“五行”的运化,故性为天地的本性。(3)人的本性。“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国语・晋语七》)这个性已经不单纯指生命,而已经包含有生命的本质内涵的义蕴,故“德”亦可以厚民之“性”。并且明确提出了“天性”和“人性”的概念。《尚书・西伯戡黎》有“不虞天性”,《国语・周语中》中有“夫人性陵上者也”。这种现象表明性已成为一个普遍概念,用以说明客体对象(包括人)的本质,但其内涵尚未展开。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最早的性的思想,是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论性仅见于此。这种观点包含着人们天生的本性不存在根本差异、人性的区别乃后天的产物的思想。众所周知,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也。人之所以能爱人或被人爱,就是因为每个人在本性上具有一致性。但孔子对此没有深究。真正最早建立较为系统的人性理论的学者是孟子。他认为,所谓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人区别于“犬之性”、“牛之性”的本质规定。在生之谓性的意义上,它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但从本质上说,人性的根本内容不在于此,而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他称之为“四端”,即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为人的本性之中先天具有仁义礼智的萌芽,它们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非由外铄我,我固有之也”。他与告子义内义外之争,就是为了明确“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把人性的本质内涵规定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以人性为人的德性。并且,他还表达了人性来源于天,与天的本性具有一致性的思想,故知性即可知天。由此,孟子肯定每个人都具有至善的道德本性,都可以通过自觉的努力成为道德完善的圣人。然而,他并没有否定人性中包含有自然属性的因素,并且承认“食色”亦为人的固有之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人的自然欲求属于天性,但它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却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并非形中所有就求之即得,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则为天之所命,尽管为君为臣等的社会地位非人所能够自定,但伦理道德的完善却完全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努力。这种思想显然是对人的道德主体性的高扬。荀子则把人性规定为人的自然本质,“凡性者,
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在他看来,人的自然本性是求得自己的生存与舒适,其发展的倾向与社会的伦理道德相冲突,故具有恶的道德价值,不能任其自然发展,而应施之以礼乐教化,引导其向善。因此,人性本恶,其善则是后天社会教化的结果。此即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伪,指人为,而非虚伪)也”(同上)的观点。在此,荀子通过人性论强调的主体的道德能动性并非个体的自觉,而是社会的觉悟。孟子和荀子的分歧在于:人性的本质内容是德性还是自然性,其道德价值是善还是恶,实现人的完善是依靠人的道德自觉还是依靠社会的礼乐教化。但是他们都肯定人性具有先验的道德价值,可以实现道德完善。他们的学说,奠定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发展的理论基础。《易传》论性,在先秦元典儒学中最富有思辨性,
它把性、命、理联系在一起,从本体的层面对性作了57
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逻辑发展深刻地论证。它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性不是简单的来源于天,而是天道本体运化在人身上的本质体现。人性之所以为善,仁义礼智只是其具体内涵,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性是对天道之善(即本体的绝对道德精神)的继承。由此,人性便与天道本体直接联系在一起,人的道德完善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更是宇宙运化的终极完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这些观点,对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道家庄子也以人性为人的自然本性:“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但他讲的人性主要指人的本真的精神自由,它超越儒家的善恶价值,是宇宙大道的本然规定。因此,庄子主张顺应自然,全真保性。人性的完善并非以道德修养、道德教育去培植、改变天生之质,而是返朴归真,实现精神的绝对超越。和儒家相同之处在于,道家也把人性的来源归之于天:“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庄子・知北游》)人性反映了天地的自然本质。儒家以天为伦理道德之天,故人性为善;道家以天为自然,故人性自然,并且应当顺应自然。法家韩非继承荀子以人性为人的自然本性的观点,“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韩非子・显学》),但否定人有自觉向善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人性的实质就是人的“利欲”之心,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逐自己的私利,利益的交换与算计,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法家看来,仁义道德不仅不是人的天性,而且与人的天性相冲突。由于伦理道德调控的软弱性,使得它根本无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要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只能借助于法律。商鞅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商君书・算地》)认为伦理道德与人性的矛盾导致了人们为利欲之恶的不可改变,而只能依靠法律对之加以严格地制裁,才能够避免其泛滥,危害他人和社会。由此,韩非得出一个结论:“吾是以明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儒家的德性主义主张是不现实的,只有法律才能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把主体的自觉由个体移向社会整体,否定现实个体具有道德自觉的可能性和内在根据,就有可能在社会的道德自觉中扼杀人类个体的道德自觉,最终走向残暴的统治。性恶论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展史上始终未曾占据过主导地位,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除了上述几家的观点之外,在人性的道德价值问题上,先秦时期还出现过世子的有善有恶论和告子的无善无恶论等理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关于性的理论格局基本形成,它确定了以德论性、主要关注于德性的理论方向,使得传统哲学对天性、物性的认识,都成为论证人性的理论环节。
二汉唐时期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人性论的发展,是对先秦学说的展开,而以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为基本线索。孟子的性善论肯定了人具有至善的道德本质,能够启迪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自觉,促进了道德主体积极进取精神的展开。然而,它无法说明为什么在至善的本性中会滋生出恶,后天的环境为何能够磨灭固有的善性。荀子的性恶论设立了恶的内在根源,强调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有利于道德规范体系和社会调控体系的建设。但是,它同样无法回答,
人性既然为恶,为什么具有向善的可能性,人类为什么要制定并且能够制定与自己的本性相对抗的道德礼义,并自觉接受它的规范。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汉唐的学者们提出了种种理论方案。汉儒董仲舒把性归本于天,人副天数,人性只是天性的表现。“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他并不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贪仁两种不同的性,而是认为天把贪与仁赋予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人性。一是纯善无恶的“圣人之性”,二是可善可恶的“中民之性”,三是有恶无善的“斗筲之性”。从理论上看,他对荀子继承的更多。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认为“性待教化而为善”(同上),又修正荀子,以人性为善的本原,“善出于性,而性不可谓善”(《春秋繁露・实性》)。于是,便由绝对至善的圣人制礼作乐,教化可善可恶的中民,以引导他们向善,而对有恶无善的斗筲之民则以刑赏制裁之。扬雄认为人性“善恶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