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华裔作家的姓名问题
- 格式:docx
- 大小:19.72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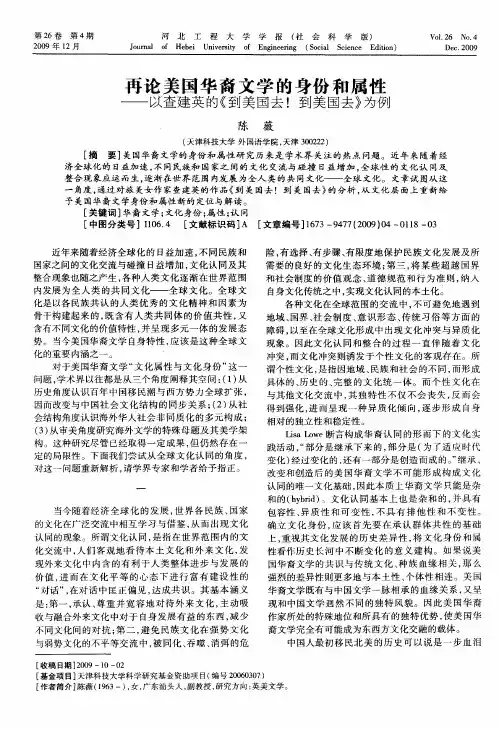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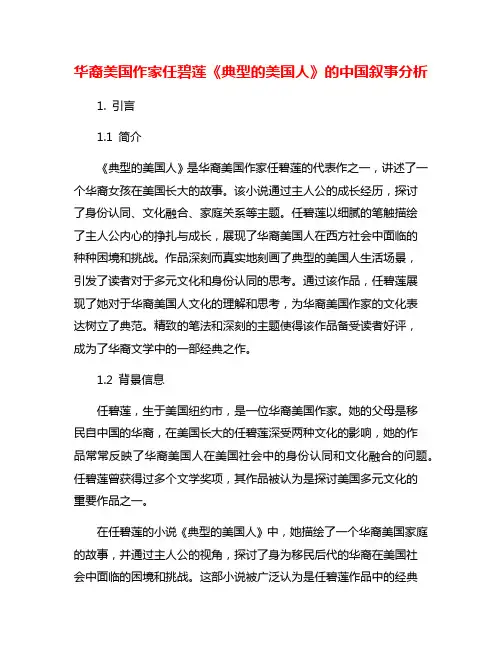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1. 引言1.1 简介《典型的美国人》是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长大的故事。
该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探讨了身份认同、文化融合、家庭关系等主题。
任碧莲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与成长,展现了华裔美国人在西方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
作品深刻而真实地刻画了典型的美国人生活场景,引发了读者对于多元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思考。
通过该作品,任碧莲展现了她对于华裔美国人文化的理解和思考,为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化表达树立了典范。
精致的笔法和深刻的主题使得该作品备受读者好评,成为了华裔文学中的一部经典之作。
1.2 背景信息任碧莲,生于美国纽约市,是一位华裔美国作家。
她的父母是移民自中国的华裔,在美国长大的任碧莲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她的作品常常反映了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融合的问题。
任碧莲曾获得过多个文学奖项,其作品被认为是探讨美国多元文化的重要作品之一。
在任碧莲的小说《典型的美国人》中,她描绘了一个华裔美国家庭的故事,并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探讨了身为移民后代的华裔在美国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这部小说被广泛认为是任碧莲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展现了她对于跨文化和身份认同议题的深刻思考与表达。
通过分析这部小说,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华裔美国作家在文学中所表达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融合问题。
2. 正文2.1 《典型的美国人》简介《典型的美国人》是任碧莲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华裔美国人的成长故事。
故事主要围绕着主人公杰瑞的生活展开,描绘了他在美国的种种遭遇和挑战。
在这部小说中,任碧莲通过杰瑞这个角色,深刻地探讨了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冲突。
杰瑞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生长在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接受着美国式的教育和价值观。
他的家庭却是一个充满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这让他在两种文化之间感到困惑和矛盾。
他努力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华裔身份,这让他感到徘徊和迷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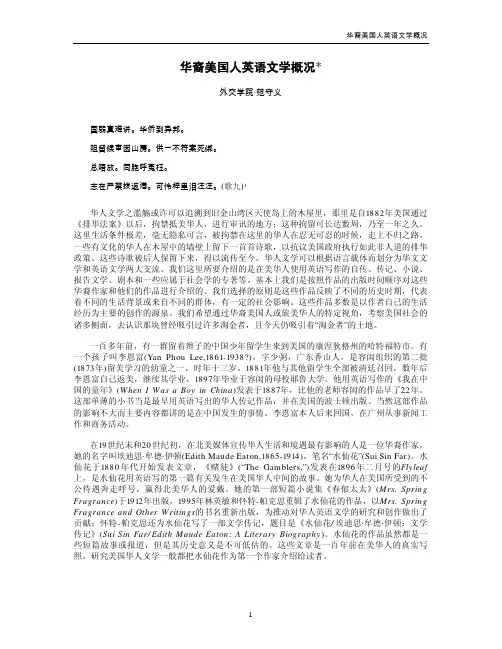
华裔美国人英语文学概况*外交学院·范守义国弱真难讲。
华侨到异邦。
阻留候审困山房。
供一不符案死绑。
总唔放。
同胞呼冤枉。
志在严禁拨返港。
可怜梓里泪汪汪。
(歌九)1华人文学之滥觞或许可以追溯到旧金山湾区天使岛上的木屋里,那里是自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以后,拘禁抵美华人,进行审讯的地方;这种拘留可长达数周,乃至一年之久。
这里生活条件极差,毫无隐私可言,被拘禁在这里的华人在忍无可忍的时候,走上不归之路。
一些有文化的华人在木屋中的墙壁上留下一首首诗歌,以抗议美国政府执行如此非人道的排华政策。
这些诗歌被后人保留下来,得以流传至今。
华人文学可以根据语言载体而划分为华文文学和英语文学两大支流。
我们这里所要介绍的是在美华人使用英语写作的自传、传记、小说、报告文学、剧本和一些应属于社会学的专著等。
基本上我们是按照作品的出版时间顺序对这些华裔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介绍的。
我们选择的原则是这些作品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着不同的生活背景或来自不同的群体,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这些作品多数是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要的创作的源泉。
我们希望通过华裔美国人或旅美华人的特定视角,考察美国社会的诸多侧面,去认识那块曾经吸引过许多淘金者,且今天仍吸引着“淘金者”的土地。
一百多年前,有一群留着辫子的中国少年留学生来到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市。
有一个孩子叫李恩富(Yan Phou Lee,1861-1938?),字少弼,广东香山人,是容闳组织的第二批(1873年)留美学习的幼童之一,时年十三岁。
1881年他与其他留学生全部被清廷召回,数年后李恩富自己返美,继续其学业,1897年毕业于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
他用英语写作的《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发表于1887年,比他的老师容闳的作品早了22年。
这部单薄的小书当是最早用英语写出的华人传记作品,并在美国的波士顿出版。
当然这部作品的影响不大而主要内容都讲的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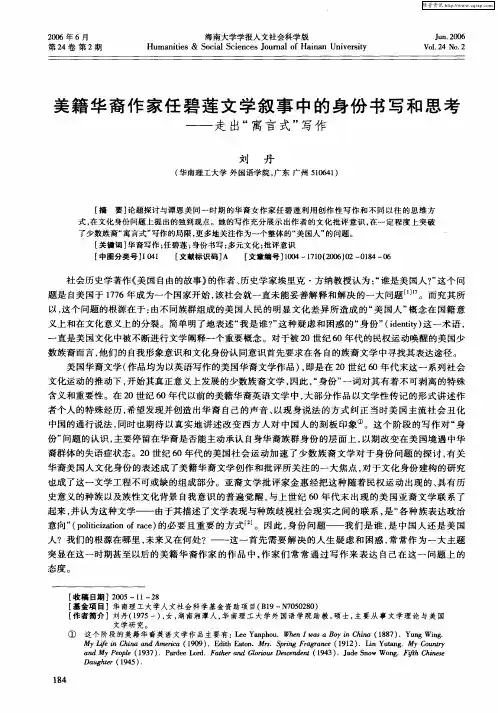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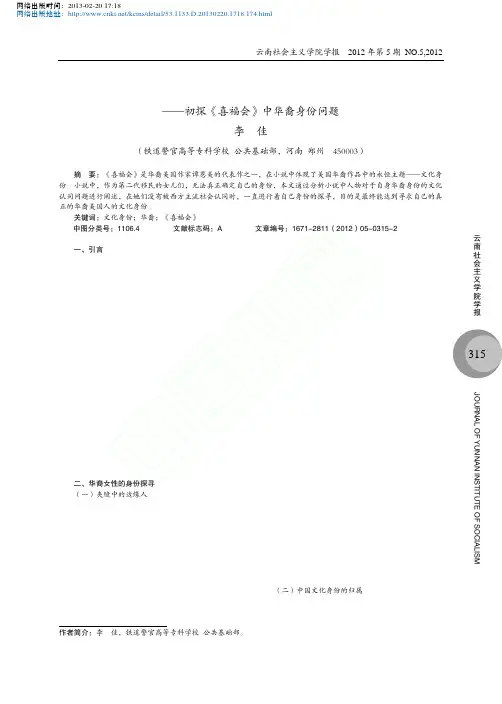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第5期 NO.5,2012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 O U R N A L O F Y U N N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O C I A L I S M 315异国文化下的身份探寻——初探《喜福会》中华裔身份问题李 佳(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基础部,河南 郑州 450003)摘 要:《喜福会》是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之一,在小说中体现了美国华裔作品中的永恒主题——文化身份。
小说中,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女儿们,无法真正确定自己的身份,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人物对于自身华裔身份的文化认同问题进行阐述,在她们没有被西方主流社会认同时,一直进行着自己身份的探寻,目的是最终能达到寻求自己的真正的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
作者简介:李 佳,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基础部。
网络出版时间:2013-02-20 17:18网络出版地址:/kcms/detail/53.1133.D.20130220.1718.174.html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第5期 NO.5,2012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 U R N A L O F Y U N N A N I N ST I T U T E O FS O C I AL I S M 316 广东省小学全科型教师培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析许 艳(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摘 要:师资尤其是农村小学师资已成为制约小学综合课程开展的瓶颈。
文章结合所在单位首次尝试的小学全科型教师培训项目以及以往的教师培训的实践,论述了广东省小学全科型教师培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期对小学师资培训工作提供若干理论与经验借鉴。
关键词:小学全科型教师;师资培训;广东;必要性;可行性中图分类号:G6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2)05-0316-2教育部自2001年推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小学阶段开设品德与生活(社会)、艺术、科学、体育与健康及综合实践活动等综合课程,强调淡化学科的界限,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和综合实践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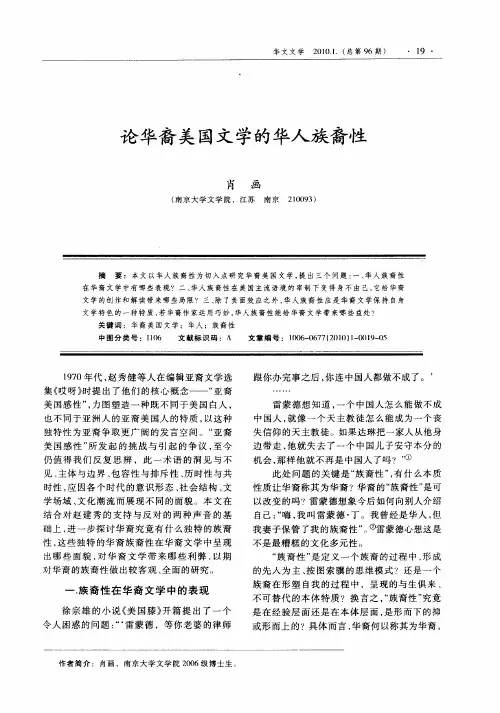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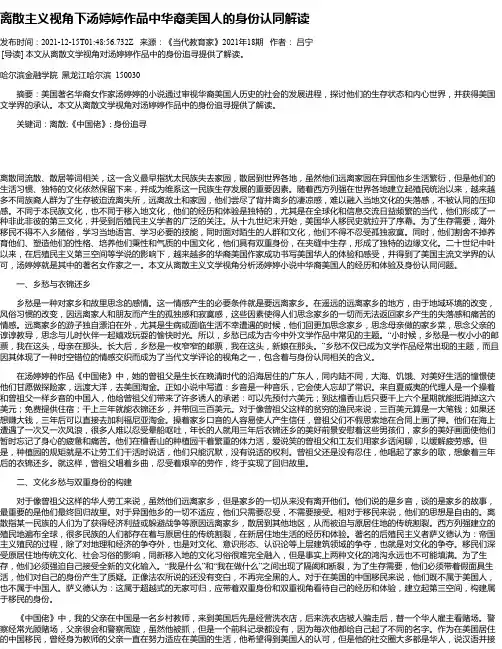
离散主义视角下汤婷婷作品中华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解读发布时间:2021-12-15T01:48:56.732Z 来源:《当代教育家》2021年18期作者:吕宁[导读] 本文从离散文学视角对汤婷婷作品中的身份追寻提供了解读。
哈尔滨金融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摘要: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的小说通过审视华裔美国人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进程,探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并获得美国文学界的承认。
本文从离散文学视角对汤婷婷作品中的身份追寻提供了解读。
关键词:离散;《中国佬》; 身份追寻离散同流散、散居等词相关,这一含义最早指犹太民族失去家园,散居到世界各地,虽然他们远离家园在异国他乡生活繁衍,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独特的文化依然保留下来,并成为维系这一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殖民统治以来,越来越多不同族裔人群为了生存被迫流离失所,远离故土和家园,他们尝尽了背井离乡的凄凉感,难以融入当地文化的失落感,不被认同的压抑感。
不同于本民族文化,也不同于移入地文化,他们的经历和体验是独特的,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他们形成了一种非此非彼的第三文化,并受到后殖民主义学者的广泛的关注。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美国华人移民史就拉开了序幕。
为了生存需要,海外移民不得不入乡随俗,学习当地语言、学习必要的技能,同时面对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他们不得不忍受孤独寂寞。
同时,他们割舍不掉养育他们、塑造他们的性格、培养他们秉性和气质的中国文化,他们具有双重身份,在夹缝中生存,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文化。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后殖民主义第三空间等学说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华裔美国作家成功书写美国华人的体验和感受,并得到了美国主流文学界的认可,汤婷婷就是其中的著名女作家之一。
本文从离散主义文学视角分析汤婷婷小说中华裔美国人的经历和体验及身份认同问题。
一、乡愁与衣锦还乡乡愁是一种对家乡和故里思念的感情。
这一情感产生的必要条件就是要远离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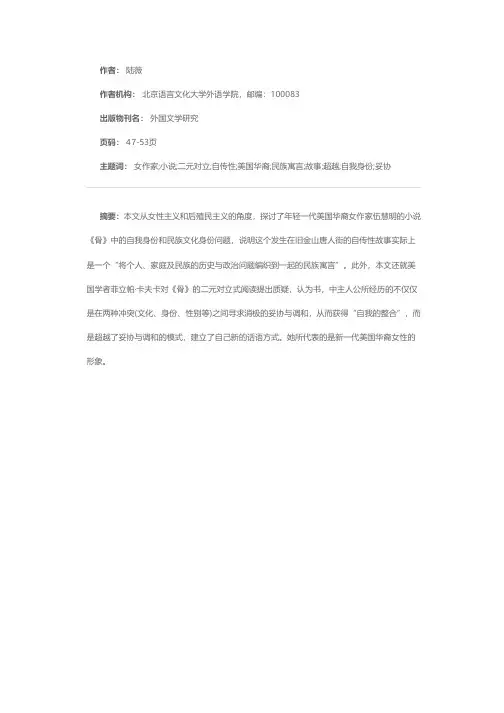
作者: 陆薇
作者机构: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语学院,邮编:100083
出版物刊名: 外国文学研究
页码: 47-53页
主题词: 女作家;小说;二元对立;自传性;美国华裔;民族寓言;故事;超越;自我身份;妥协
摘要:本文从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年轻一代美国华裔女作家伍慧明的小说《骨》中的自我身份和民族文化身份问题,说明这个发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自传性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将个人、家庭及民族的历史与政治问题编织到一起的民族寓言”。
此外,本文还就美国学者菲立帕·卡夫卡对《骨》的二元对立式阅读提出质疑,认为书,中主人公所经历的不仅仅是在两种冲突(文化、身份、性别等)之间寻求消极的妥协与调和,从而获得“自我的整合”,而是超越了妥协与调和的模式,建立了自己新的话语方式。
她所代表的是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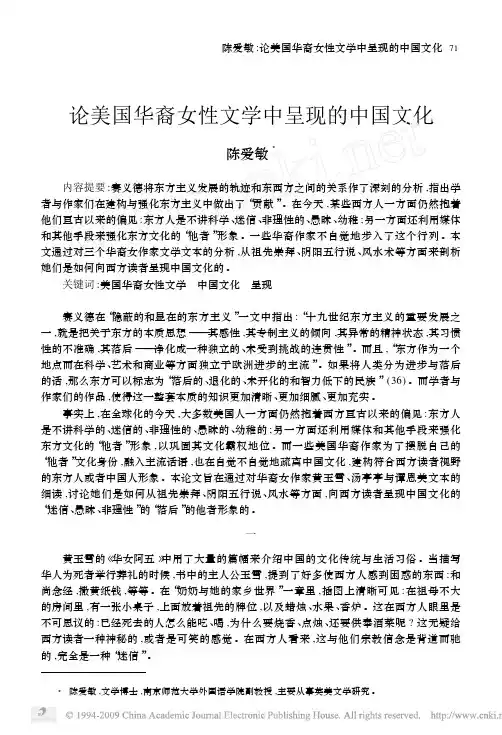
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呈现的中国文化陈爱敏3内容提要:赛义德将东方主义发展的轨迹和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学者与作家们在建构与强化东方主义中做出了“贡献”。
在今天,某些西方人一方面仍然抱着他们亘古以来的偏见:东方人是不讲科学、迷信、非理性的、愚昧、幼稚;另一方面还利用媒体和其他手段来强化东方文化的“他者”形象。
一些华裔作家不自觉地步入了这个行列。
本文通过对三个华裔女作家文学文本的分析,从祖先崇拜、阴阳五行说、风水术等方面来剖析她们是如何向西方读者呈现中国文化的。
关键词:美国华裔女性文学 中国文化 呈现赛义德在“隐蔽的和显在的东方主义”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东方主义的重要发展之一,就是把关于东方的本质思想———其感性,其专制主义的倾向,其异常的精神状态,其习惯性的不准确,其落后———净化成一种独立的、未受到挑战的连贯性”。
而且,“东方作为一个地点而在科学、艺术和商业等方面独立于欧洲进步的主流”。
如果将人类分为进步与落后的话,那么东方可以标志为“落后的、退化的、未开化的和智力低下的民族”(36)。
而学者与作家们的作品,使得这一整套本质的知识更加清晰、更加细腻、更加充实。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一方面仍然抱着西方亘古以来的偏见:东方人是不讲科学的、迷信的、非理性的、愚昧的、幼稚的;另一方面还利用媒体和其他手段来强化东方文化的“他者”形象,以巩固其文化霸权地位。
而一些美国华裔作家为了摆脱自己的“他者”文化身份,融入主流话语,也在自觉不自觉地疏离中国文化,建构符合西方读者视野的东方人或者中国人形象。
本论文旨在通过对华裔女作家黄玉雪、汤亭亭与谭恩美文本的细读,讨论她们是如何从祖先崇拜、阴阳五行说、风水等方面,向西方读者呈现中国文化的“迷信、愚昧、非理性”的“落后”的他者形象的。
一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
当描写华人为死者举行葬礼的时候,书中的主人公玉雪,提到了好多使西方人感到困惑的东西:和尚念经,撒黄纸钱,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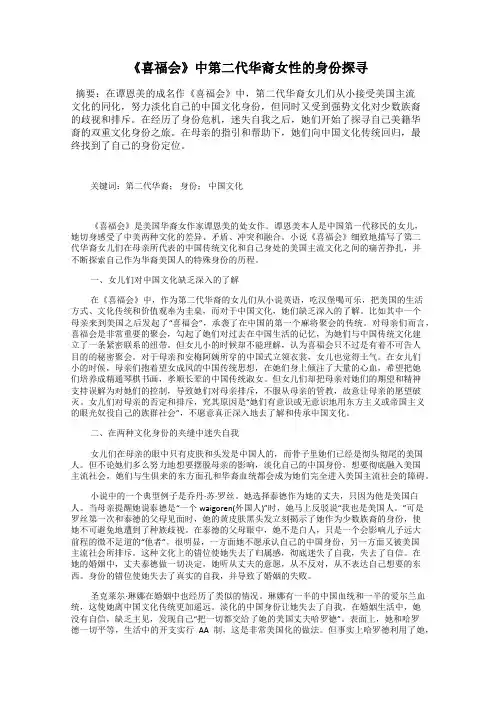
《喜福会》中第二代华裔女性的身份探寻摘要:在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第二代华裔女儿们从小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同化,努力淡化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但同时又受到强势文化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排斥。
在经历了身份危机,迷失自我之后,她们开始了探寻自己美籍华裔的双重文化身份之旅。
在母亲的指引和帮助下,她们向中国文化传统回归,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定位。
关键词:第二代华裔;身份;中国文化《喜福会》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
谭恩美本人是中国第一代移民的女儿,她切身感受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差异、矛盾、冲突和融合。
小说《喜福会》细致地描写了第二代华裔女儿们在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自己身处的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痛苦挣扎,并不断探索自己作为华裔美国人的特殊身份的历程。
一、女儿们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在《喜福会》中,作为第二代华裔的女儿们从小说英语,吃汉堡喝可乐,把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奉为圭臬,而对于中国文化,她们缺乏深入的了解。
比如其中一个母亲来到美国之后发起了“喜福会”,承袭了在中国的第一个麻将聚会的传统。
对母亲们而言,喜福会是非常重要的聚会,勾起了她们对过去在中国生活的记忆,为她们与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了一条紧密联系的纽带。
但女儿小的时候却不能理解,认为喜福会只不过是有着不可告人目的的秘密聚会。
对于母亲和安梅阿姨所穿的中国式立领衣裳,女儿也觉得土气。
在女儿们小的时候,母亲们抱着望女成凤的中国传统思想,在她们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希望把她们培养成精通琴棋书画,孝顺长辈的中国传统淑女。
但女儿们却把母亲对她们的期望和精神支持误解为对她们的控制,导致她们对母亲排斥,不服从母亲的管教,故意让母亲的愿望破灭。
女儿们对母亲的否定和排斥,究其原因是“她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东方主义或帝国主义的眼光奴役自己的族群社会”,不愿意真正深入地去了解和传承中国文化。
二、在两种文化身份的夹缝中迷失自我女儿们在母亲的眼中只有皮肤和头发是中国人的,而骨子里她们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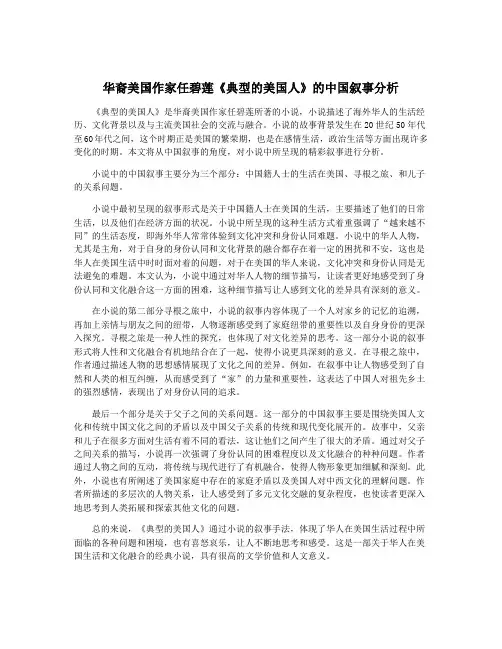
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典型的美国人》的中国叙事分析《典型的美国人》是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所著的小说,小说描述了海外华人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以及与主流美国社会的交流与融合。
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这个时期正是美国的繁荣期,也是在感情生活,政治生活等方面出现许多变化的时期。
本文将从中国叙事的角度,对小说中所呈现的精彩叙事进行分析。
小说中的中国叙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中国籍人士的生活在美国、寻根之旅、和儿子的关系问题。
小说中最初呈现的叙事形式是关于中国籍人士在美国的生活,主要描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经济方面的状况。
小说中所呈现的这种生活方式着重强调了“越来越不同”的生活态度,即海外华人常常体验到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难题。
小说中的华人人物,尤其是主角,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背景的融合都存在着一定的困扰和不安,这也是华人在美国生活中时时面对着的问题,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说,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是无法避免的难题。
本文认为,小说中通过对华人人物的细节描写,让读者更好地感受到了身份认同和文化融合这一方面的困难,这种细节描写让人感到文化的差异具有深刻的意义。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寻根之旅中,小说的叙事内容体现了一个人对家乡的记忆的追溯,再加上亲情与朋友之间的纽带,人物逐渐感受到了家庭纽带的重要性以及自身身份的更深入探究。
寻根之旅是一种人性的探究,也体现了对文化差异的思考。
这一部分小说的叙事形式将人性和文化融合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小说更具深刻的意义。
在寻根之旅中,作者通过描述人物的思想感情展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
例如,在叙事中让人物感受到了自然和人类的相互纠缠,从而感受到了“家”的力量和重要性,这表达了中国人对祖先乡土的强烈感情,表现出了对身份认同的追求。
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父子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部分的中国叙事主要是围绕美国人文化和传统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父子关系的传统和现代变化展开的。
性别、种族、文化——美国华裔女性写作探析性别、种族、文化——美国华裔女性写作探析近年来,美国华裔女性在文学和写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她们的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性别、种族和文化的交融,展现了她们作为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的独特经历和挑战。
本文将探析华裔女性在美国文学中扮演的角色,并分析她们如何通过写作表达自我,同时引起公众对性别、种族和文化议题的关注。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如玛兹·霍的《喜福会》,玛丽漂·林的豪华酒店世纪三部曲,梁美华的《女儿国》等作品,以不同的文体和题材描绘了华裔女性的生活和成长经历。
她们的作品围绕着性别、种族和文化这三个主题展开,表达了自己在这个多元化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和挣扎。
首先,性别是华裔女性作家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面临着传统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的压力。
她们会反思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探索自己的性别认同。
霍的《喜福会》中的女主人公李文夕就是一个例子。
她生活在一个传统家庭中,受到长辈和家庭的压迫,但她渴望自主和独立。
通过写作,华裔女性作家可以表达出她们对于性别平等和自由的渴望,同时也呼吁社会重视女性的权益。
其次,种族是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她们在作品中反思自己的种族认同和文化根源。
面对亚裔美国人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和歧视,华裔女性作家用故事和情感表达对于种族平等和尊重的追求。
比如,林的豪华酒店世纪三部曲通过家族历史来探讨种族和文化认同,以及移民在美国的经历。
通过写作,华裔女性作家不仅记录和传承文化,也揭示和抗争着种族不平等的存在。
最后,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融入了独特的文化元素,展示了她们作为华裔的身份和文化背景。
她们通过语言、食物、家庭传统等细节,传达出自己对于家乡的思念和温暖。
华裔女性作家借助写作,不仅向读者展示了华裔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也通过文学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不仅仅关注华人群体内部的议题,也超越种族和文化的限制,触及到更普遍的人类关系和情感。
流散者的困惑———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母亲形象解读陈爱敏(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摘要:美国华裔女作家作为海外流散华人的一部分,对祖先文化一方面表现出深深的眷恋,想通过创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但另一方面,为了融入主流话语,建构自己的身份,又不免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疏离。
在她们的作品中,中国文化/母亲被视为“他者”,而被扭曲。
本论文从分析一些华裔女作家的身份入手,指出她们如何将中国文化/母亲塑造为与她们对立的他者,而予以拒斥。
在此基础上,本文作者意在说明:为了融入主流文化,获得“美国作家”的身份,一些华裔女作家自觉与不自觉地成了美国新“东方主义”的同谋。
关键词:流散;华裔文学;“东方主义”!"#$%&’$:&’()(*+,-./(’),*/012/34’45/6/37,64*’4(’,12/34’4&84*/0(39,8439*/+4*’,,3+24,342(3.,’2,9(:443/3+4*4’+/3+24/*4+23/00;5+;*4,(3.(.4+4*8/3(+/,3+,/3+*,.;04/++,+249,*5.+2*,;729*/+/37;<;+,3+24,+24*,/3,*.4*+,<4845+4./3+,+248(/3’+*4(80;5+;*4,(3.+,74+(3/.43+/+=,-+24/*,93,+24=4>2/</+(3(5/43(+/,3-*,8+2412/34’40;5+;*4?@4304,12/34’40;5+;*4/A ,+24*/’’443(’“,+24*”,(3.+,’,84.47*44<4B 0,84’(+9/’+4./8(74/3+24/*9*/+/37?C 24)*4’43+)()4*’+(*+’-*,8+24(3(5=’/’,-+24*45(+/,3’2/)<4+9443+249*/+4*’’./5488(,-+24.;(5/.43+/+/4’(3.+240(;’4’,-+24/*(5/43(+/,3-*,8“A ,+24*”,+*=/37+,),/3+,;+2,9+24=.4)/0+12/34’40;5+;*4/8,+24*(’+246(7;4(3./8)4*/,;’“,+24*”?D (’4.,3+24(<,64(3(5=’4’,+249*/+4*,-+2/’)()4*0,305;.4’+2(+/3,*.4*+,<4(848<4*,-+248(/3’+*4(80;5+;*4(3.<40,84(*4(5&84*/0(39*/+4*,’,8412/34’49,8439*/+4*’2(64(0+;(55=-(5543;30,3’0/,;’5=/3+,+247*,;),-&84*/0(3E */43+(5/’+’?()*+,%-#:./(’),*/0;12/34’4&84*/0(35/+4*(+;*4;“,*/43+(5/’8”中图分类号:F #G 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H I G #J K (!##G )"!I ##J #I #J在美国定居的华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世纪中后期赴美并在那定居的大陆移民及其后代,另一部分是改革开放期间进入美国的新移民。
从《骨》中的三对父女关系看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纪莹
【期刊名称】《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00)003
【摘要】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是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作品中常见的主题。
伍慧明的《骨》是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作品中的代表作。
它主要从安娜与父亲、尼娜与父亲、莱拉与父亲这三对父女之间的关系来集中展现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三个女儿中,安娜是极端的反抗者,属于“失根”族群中的一员;尼娜是洒脱的西化者,她最终选择了抛弃中国文化身份;莱拉是温和的叛逆者,属于“落地生根”类型。
文章认为,莱拉所展现的这种“落地生根”类型的混杂新文化身份,对于当代华裔文化身份认同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总页数】3页(P136-138)
【作者】纪莹
【作者单位】湖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孝感 432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71
【相关文献】
1.从符号游戏性看恶搞中的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 [J], 王妍
2.“文化落差”中身份认同的吊诡——从《我爱比尔》看王安忆潜藏的身份意识[J], 姚冬梅
3.想象中的华裔美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解读汤亭亭小说中两则中西文化误读[J], 张鲁宁
4.冲突与和解——从《骨》中的父女关系看华裔代际问题 [J], 戚铭
5.冲突与和解——从《骨》中的父女关系看华裔代际问题 [J], 戚铭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现状摘要:美国族裔文学指由非白种少数族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以小说和诗歌为主的文学形式。
美国族裔文学是文化之间交融的产物,是美国整体文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丰富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而且激励了社会个体朝着构建更和谐的社会而努力。
其中,美国华裔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华裔文学是中美两种文化碰撞和杂交的产物,但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特色。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现状;双重文化身份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等院校与学术界围绕着族裔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心问题就是族裔文学到底应该在美国文学经典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这一讨论,不仅对美国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重写美国文学史,重编美国文学选集,重建美国文学教学大纲等,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美国之外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在美国文学的研究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也带来相当深刻的启发。
美国华裔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粗略的说,美国华裔文学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转折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可谓走向繁荣阶段。
根据目前的研究资料显示,美国华裔文学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初实为移民文学,形式多为口头文学,如歌谣、故事等。
但由于这一时期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太少,因此,第一本重要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应当是李延富于1887年出版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
今天的批评家大多认为,真正在美国华裔文学开创初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是一对中英混血儿姐妹艾迪丝•伊顿和温妮弗•莱德•伊顿的作品。
姐姐以“水仙花”为笔名,妹妹以日本名Onoto Watanna为笔名。
尤其是姐姐艾迪丝•伊顿常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先驱。
她于1912年发表的短篇故事集《春香太太》也常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
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最早被置于美国亚裔文学这一大脉络中。
美国华裔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V ol .39N o.10O ct .2018第39卷第10期2018年10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 our nalofChi f eng U ni ver s i t y (Soc.Sci )论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差异性黄丝,周文革(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摘要:紧随时代发展需要,华裔文学研究领域对文化身份的探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姿态。
差异性可视为促成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构建的基础元素之一,探究华裔文学中体现的文化身份差异性,既能有效加强读者对中美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又能通过中美文化间的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高大众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关键词:华裔文学;文化身份;差异性中图分类号:I 7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0-0094-04收稿日期:2018-08-16基金项目:2018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 SP18Y B C 365)随着美国华裔文学研究领域的日益深入,许多学者紧跟全球化趋势下多元文化迅速发展的步伐,从不同的视角对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进行解析。
因此,有关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研究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地涌现在读者的视野当中。
一些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的差异性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
管建明就对美国华裔文学文化身份的认同及其危机等进行过讨论,表现出华裔作家在错综复杂的跨文化交际的语境中谋求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共同追求[1]。
梁艳从后殖民主义、本民族文化及主流文化三个不同的层面对华裔文学与非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构建进行相对的比较,同时又通过强调两种文化之间相互兼容的重要性来突显文化身份地建立[2]。
徐颖果则从文化政治化的角度出发,对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族裔文化身份进行一定的思考与探索[3]。
在多元文化背景的诸多关照下,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身份的差异性研究,不仅能体现华裔作家在文化冲突的矛盾中对自身作品里隐含的文化身份有更理性的认识,还能将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基础加以巩固。
在当今我国翻译界,对于外国作家的姓名,一般是按照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语种姓名译名手册或两大卷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译出的。
这样做利于统一规范。
少数查不到的姓名,可按这些工具书的发音规则推断译出,但一些著名的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等,则不按这些工具书或其发音规则译出,而采用约定俗成的译法。
美国华裔作家总的说来自然也属于外国作家(王理行、郭英剑,2001:),但由于其家庭出身、成长环境、背景等不尽相同,更由于他们有中国血统,与中国有割不断的关系,他们的姓名,他们在中文里如何称呼,居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们当中,大致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作家自己若干年前从中国移民去美国。
他们在中国出生前后,父母已为他们取了中文姓名。
他们移民美国后,为了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便于交流,他们一般都新取并采用英文名字。
他们新取的英文名字中,有的基本与原中文名字相同,把中文名字转化成拼音,仅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把名置于姓前,如李恩富(Yan Phou Lee)、黎锦扬(Chin Yang Lee)等;许多人保留了自己原来的姓,原来的姓用拼音的方式置于英文姓名中放置姓的位置,即英文姓名的最后,因为姓是自己祖祖辈辈流传继承下来的,而名则完全采用西方的,如帕迪•刘(Pardee Lowe, 中文名叫刘裔昌),其中的名“帕迪”与原来的“裔昌”无关;有少数作家把中文名字的每个字翻译成英语,再按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的顺序排列,而原来的姓用拼音的方式置于英文姓名中放置姓的位置,如黄玉雪(Jade Snow Wong);也有的作家新取的英文名字与自己原来的姓名毫无关系,如路易•朱(Louis Chu,中文名叫雷庭招)。
第二种情况是,作家出生于中国以外的国家(大部分情况是美国或某一西方国家),父母自然按所在国的文化习惯给作家取西方人的名字,但由于对祖国的深情难以割舍,也希望儿女别忘了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同时都会给作家取一个中文名字,如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 中文名叫汤亭亭)。
到目前为止,第二种情况占美国华裔作家的姓名的大多数。
目前所见用中文发表的美国华裔文学方面的论文,提及作家时,绝大部分情况下都通行采用作家的中文名字,首次提到某一位华裔作家时一般会在其中文名字后的括号内注明其英文名字。
这种通行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或尴尬,而且与作家的实际生活状况相背。
由于汉语中的一音多字现象极为普遍,由汉语拼音转化过去的英文名字中的姓或名,在得不到作家本人、其父母或知情者的确认的情况下,很难准确地还原为作家原来中文名字中的姓或名。
如果取名者是按自己故乡的方言土音把自己中文的姓或名转化到英文名字中的,那对不掌握相关背景情况的研究者来说,再要把它们从英文名字中的姓或名准确地还原为作家原来中文名字中的姓或名,就完全是不可能的了。
至于作家的中文名字与英文名字完全无关的情形中,研究者除了逐个从作家本人、其父母或知情者那里查问以外,可以说是一筹莫展了。
尽管当今通讯联络手段极为丰富发达,作为个体或群体的研究者要想把美国华裔作家的中文名字全部搞清楚搞准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许多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从别的同行那里知道美国华裔作家的中文名字的,对于少数暂时无法知道的,就只好采取音译的办法了,但这样做就造成了同一篇文章中对同一个问题采用不同处理办法的尴尬情况。
因此,研究者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好不容易搞清楚某位美国华裔作家的中文名字后,都会如有重大发现般的高兴一阵子。
美国华裔文学方面的论文中通行采用作家的中文名字的做法,其好处是,中文名字让中文读者容易记住。
同时,这种做法无形中拉近了美国华裔作家与中文读者的距离,仿佛他们都是自己人,甚至有一种亲近感。
然而,这种做法却与作家的实际生活状况相背,与作家自身的文化身份定位有距离。
本人近年来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断,在美国社会中的华裔作家,在其日常生活中是极少有人、甚至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人用其中文名字来称呼的。
大部分美国华裔作家几乎、甚至完全不识中文,很可能根本就不认识、也不会写父母精心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对于绝大部分美国华裔作家来说,他们的中文名字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实际的意义,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则近乎毫无意义。
美国的文学研究界、新闻界、出版界和相关媒体都是用他们的英文名字称呼他们的。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知道美国华裔作家的中文名字,并无碍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一直主张并身体力行,像对待普通美国人(西方人)的姓名那样来处理华裔作家的姓名,即用其英文名字音译,当然,第一次提到时在音译名字后括号内加注英文名字,如果知道,就同时加注其中文名字。
在我涉足美国华裔文学之前和之后,也一直有部分研究者这样做,所不同的是,有的研究者是明确而清醒地这样做的,有的研究者则是习惯性地这样做,而有的研究者则是在其研究过程中时而用华裔作家的中文姓名,时而用华裔作家的英文姓名的音译。
2004年2月23日,著名美国华裔文学学者金-科克•张(King-Kok Cheung,中文名叫张敬钰,她本人就是十九岁时从香港去美国定居的华裔)在南京师范大学讲学时,本人曾经就我对美国华裔作家姓名问题的推断当面求教于她,得到了这位与美国华裔作家有广泛联系的学者的证实和充分肯定。
2006年11月31日,著名美国华裔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在南京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我趁机请她谈谈自己的名字。
汤亭亭说,Maxine Hong Kingston这个名字中,Kingston是她丈夫的姓,而她丈夫家也是从他国移居美国的少数族裔。
Kingston是美国一个小城的名字,他们家到美国后给自己取英文名字时,就拿这个小城的名字用作自己家的英文姓名中的姓。
中间名Hong是她父亲家的姓“汤”在广东方言中的发音。
Maxine是为她专门取的名字。
而汤亭亭这个名字则是她小时候上中文学校时取的。
她婚后的生活和文学生涯里一直使用Maxine Hong Kingston这个名字。
2005年她去复旦大学访问,她发现校园里欢迎她的横幅上她的名字全都用汤亭亭而不是Maxine Hong Kingston时,觉得怪怪的。
我把中国大陆用中文发表的美国华裔文学方面的论文里提及作家时绝大部分都采用作家的中文名字的情况及其遇到的尴尬告诉了她。
赵文书教授则告诉她,用汤亭亭这个中文名字能让中国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能拉近她与中国读者的距离,有利于她和她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这时,刘俊教授抢先把我的关键问题提了出来:作为美国华裔作家的一员,她喜欢自己在中文的文章里被称为汤亭亭还是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她想了想,最后说道:“Tang Tingting is ok(汤亭亭也是可以的)。
”对于她的这种回答,有必要仔细分析其真实的含义和她说这句话时的心态。
首先,“可以的”并非“最好”,并非她要提倡在中文的文章里称她为汤亭亭。
相反,其言外之意似乎更乐意称她为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但既然用中文发表的相关论文里绝大部分都称她为汤亭亭,而且考虑到这样做还能拉近她与中国读者的距离,有利于她和她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那她就不反对了,也是可以接受的了(这多少带有实用与功利的色彩)。
如果把她这句“想了想”后说出来的话理解为她更赞成使用汤亭亭而非马克辛•洪•金斯顿,那就与前面我还没提出关于美国华裔作家的名字的麻烦或尴尬时她流畅而自然地叙述的在复旦的那种“怪怪的”感觉相矛盾了。
美国华裔文学学者金-科克•张和美国华裔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都可谓这一领域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她们对美国华裔作家的姓名问题的回答,尤其是后者回答的真实含义及回答时的情景,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一贯对待美国华裔作家的姓名的方法,即用中文发表的美国华裔文学方面的论文中,提到华裔作家的名字时,为了避免找不到其中某几位的准确的中文名字的麻烦,可以干脆就统一采用下列办法:像对待普通美国人(西方人)的姓名那样来处理华裔作家的姓名,即用其英文名字音译,当然,第一次提到时在音译名字后括号内加注英文名字,如果知道,可同时加注其中文名字。
这样处理,说明其英文名字(在中文里是其音译)是首要的,而中文名字在括号里就是次要的了,既然是次要的,不知道时从缺也就没问题了。
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之间这样的关系,与美国华裔作家实际生活中的情况相符。
在国内美国华裔文学方面的论文普遍采用作家的中文名字的同时,有一个有趣的例外:对于1999年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得者,那位在山东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1985年赴美的长篇小说《等待》的作者,所有论文中都一致称他为哈•金(Ha Jin,他在美国使用的姓名,有的研究者喊习惯了竟忘了英文姓名音译为中文时姓名中间是要加中圆点的,直接称他为哈金),而没有人用其中文姓名金雪飞来称呼他。
这种惊人的一致完全是无意识的巧合吗?其背后的文化心态恐怕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如果说,对其他几十年前早已赴美、甚至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作家,需要放开胸怀拥抱他们并通过用其中文姓名称呼的方式来拉近他们与读者的距离,甚至希望读者认为他们都是中国人在远方的亲戚,他们的创作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那为什么对在中国生长并受教育、离开中国没多少年的那位很为华夏后裔争脸的作家,却一致不用他在中国一直使用、在华裔文学研究者中也广为人知的金雪飞这个名字来称呼他,而非要用他到美国后新起的名字哈•金或哈金来称呼他呢?难道对于他,就不需要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而需要通过使用其在美国使用的名字让读者误以为他是与中国无关的外国人来拉远他与中国读者的距离吗?说到底,目前对美国华裔作家中英文名字的选用,代表着选用者或明确、或模糊、或潜意识中对美国华裔作家的身份的不同理解。
必须明确的是,从客观上来说,美国华裔作家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也许许多中国读者从感情上更倾向于强调)他们有中国血统、与中华民族有着无法否认又难以割断的血脉联系这一特性。
作为中国(中文)读者,既然能够接受并记住普通美国人(西方人)的英文名字音译,那么接受并记住美国华裔作家的英文名字音译,也应该没有问题的。
而作为研究者,如何对待研究对象,不能片面强调自己的感受和方便,或凭自己想象中方便于读者,甚至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便不顾研究对象具体、客观而真实的情况了。
更何况,研究中采用美国华裔作家的中文名字,对研究者来说其实并不方便。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位研究者,对于自己已查清的那些美国华裔作家的中英文名字,都无法做到个个耳熟能详、运用自如,而常常看着一位华裔作家的英文名字却一时想不起其中文名字,非得去查一查才行,可查与不查对研究本身其实并无什么本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