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奈特_叙事话语
- 格式:ppt
- 大小:4.90 MB
- 文档页数: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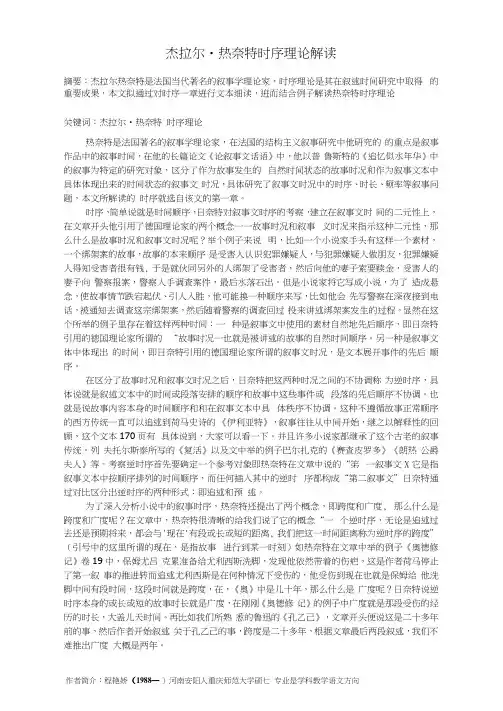
杰拉尔・热奈特时序理论解读摘要:杰拉尔热奈特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叙事学理论家,时序理论是其在叙述时间研究中取得的重要成果,本文拟通过对时序一章逬行文本细读,逬而结合例子解读热奈特时序理论关键词:杰拉尔•热奈特时序理论热奈特是法国著名的叙事学理论家,在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研究中他研究的的重点是叙事作品中的叙事时间,在他的长篇论文《论叙事文话语》中,他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事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区分了作为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的故事时况和作为叙事文本中具体体现出来的时间状态的叙事文时况,具体研究了叙事文时况中的时序、时长、频率等叙事问题,本文所解读的时序就选自该文的第一章。
时序,简单说就是时间顺序,日奈特对叙事文时序的考察,建立在叙事文时间的二元性上,在文章开头他引用了德国理论家的两个概念一一故事时况和叙事文时况来指示这种二元性,那么什么是故事时况和叙事文时况呢?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一个小说家手头有这样一个素材,一个绑架案的故事,故事的本来顺序是受害人认识犯罪嫌疑人,与犯罪嫌疑人做朋友,犯罪嫌疑人得知受害者很有钱, 于是就伙同另外的人绑架了受害者,然后向他的妻子索要赎金,受害人的妻子向警察报案,警察入手调查案件,最后水落石出。
但是小说家将它写成小说,为了造成悬念,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他可能换一种顺序来写,比如他会先写警察在深夜接到电话,被通知去调查这宗绑架案,然后随着警察的调查回过投来讲述绑架案发生的过程。
显然在这个所举的例子里存在着这样两种时间:一种是叙事文中使用的素材自然地先后顺序,即日奈特引用的徳国理论家所谓的“故事时况一也就是被讲述的故事的自然时间顺序。
另一种是叙事文体中体现出的时间,即日奈特引用的德国理论家所谓的叙事文时况,是文本展开事件的先后顺序。
在区分了故事时况和叙事文时况之后,日奈特把这两种时况之间的不协调称为逆时序,具体说就是叙述文本中的时间或段落安排的顺序和故事中这些事件或段落的先后顺序不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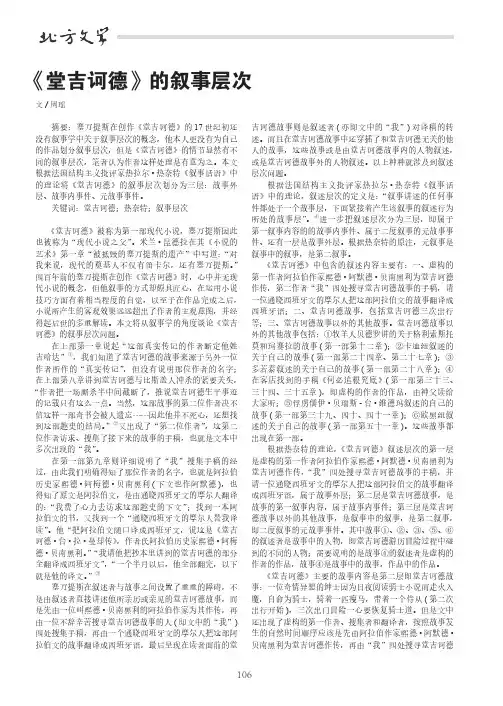
106《堂吉诃德》的叙事层次文/周瑶摘要:塞万提斯在创作《堂吉诃德》的17世纪初还没有叙事学中关于叙事层次的概念,他本人更没有为自己的作品划分叙事层次,但是《堂吉诃德》的情节显然有不同的叙事层次,笔者认为作者这样处理是有意为之。
本文根据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中的理论将《堂吉诃德》的叙事层次划分为三层:故事外层、故事内事件、元故事事件。
关键词:堂吉诃德;热奈特;叙事层次《堂吉诃德》被称为第一部现代小说,塞万提斯因此也被称为“现代小说之父”。
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的艺术》第一章“被抵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写道:“对我来说,现代的奠基人不仅有笛卡尔,还有塞万提斯。
”四百年前的塞万提斯在创作《堂吉诃德》时,心中并无现代小说的概念,但他叙事的方式却颇具匠心,在运用小说技巧方面有着相当程度的自觉,以至于在作品完成之后,小说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远远超出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并经得起后世的多重解读。
本文将从叙事学的角度谈论《堂吉诃德》的叙事层次问题。
在上部第一章说起“这部真实传记的作者断定他姓吉哈达”①,我们知道了堂吉诃德的故事来源于另外一位作者所作的“真实传记”,但没有说明那位作者的名字;在上部第八章讲到堂吉诃德与比斯盖人冲杀的紧要关头,“作者把一场厮杀半中间截断了,推说堂吉诃德生平事迹的记载只有这么一点。
当然,这部故事的第二位作者决不信这样一部奇书会被人遗忘……因此他并不死心,还想找到这部趣史的结局。
”②又出现了“第二位作者”,这第二位作者访求、搜集了接下来的故事的手稿,也就是文本中多次出现的“我”。
在第一部第九章则详细说明了“我”搜集手稿的经过,由此我们明确得知了那位作者的名字,也就是阿拉伯历史家熙德•阿梅德•贝南黑利(下文也作阿默德),也得知了原文是阿拉伯文,是由通晓西班牙文的摩尔人翻译的:“我费了心力去访求这部趣史的下文”;找到一本阿拉伯文的书,又找到一个“通晓西班牙文的摩尔人替我译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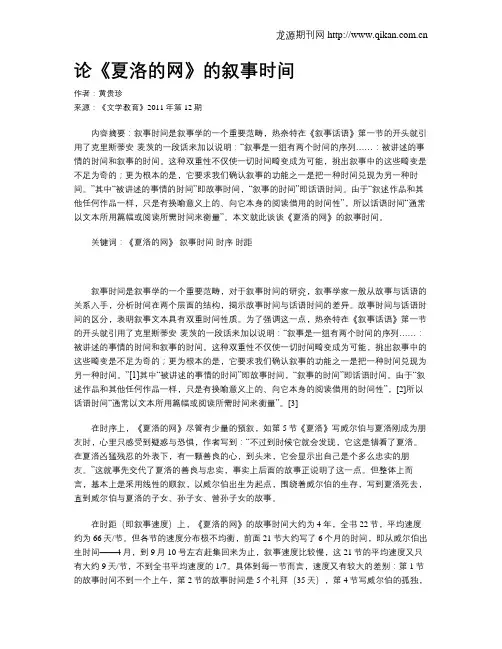
论《夏洛的网》的叙事时间作者:黄贵珍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12期内容摘要:叙事时间是叙事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热奈特在《叙事话语》第一节的开头就引用了克里斯蒂安·麦茨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
这种双重性不仅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挑出叙事中的这些畸变是不足为奇的;更为根本的是,它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种时间兑现为另一种时间。
”其中“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即故事时间,“叙事的时间”即话语时间。
由于“叙述作品和其他任何作品一样,只是有换喻意义上的、向它本身的阅读借用的时间性”,所以话语时间“通常以文本所用篇幅或阅读所需时间来衡量”。
本文就此谈谈《夏洛的网》的叙事时间。
关键词:《夏洛的网》叙事时间时序时距叙事时间是叙事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对于叙事时间的研究,叙事学家一般从故事与话语的关系入手,分析时间在两个层面的结构,揭示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的差异。
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的区分,表明叙事文本具有双重时间性质。
为了强调这一点,热奈特在《叙事话语》第一节的开头就引用了克里斯蒂安·麦茨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
这种双重性不仅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挑出叙事中的这些畸变是不足为奇的;更为根本的是,它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种时间兑现为另一种时间。
”[1]其中“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即故事时间,“叙事的时间”即话语时间。
由于“叙述作品和其他任何作品一样,只是有换喻意义上的、向它本身的阅读借用的时间性”,[2]所以话语时间“通常以文本所用篇幅或阅读所需时间来衡量”。
[3]在时序上,《夏洛的网》尽管有少量的预叙,如第5节《夏洛》写威尔伯与夏洛刚成为朋友时,心里只感受到疑惑与恐惧,作者写到:“不过到时候它就会发现,它这是错看了夏洛。
在夏洛凶猛残忍的外表下,有一颗善良的心,到头来,它会显示出自己是个多么忠实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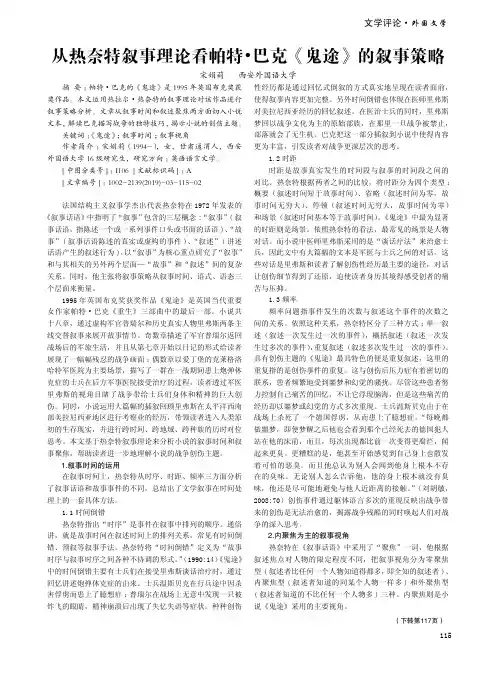
从热奈特叙事理论看帕特•巴克《鬼途》的叙事策略宋娟莉 西安外国语大学摘 要:帕特•巴克的《鬼途》是1995年英国布克奖获奖作品。
本文运用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理论对该作品进行叙事策略分析。
文章从叙事时间和叙述聚焦两方面切入小说文本,解读巴克描写战争的独特技巧,揭示小说的创伤主题。
关键词:《鬼途》;叙事时间;叙事视角作者简介:宋娟莉(1994-),女,甘肃通渭人,西安外国语大学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115-02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杰出代表热奈特在1972年发表的《叙事话语》中指明了“叙事”包含的三层概念:“叙事”(叙事话语,指陈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口头或书面的话语)、“故事”(叙事话语陈述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叙述”(讲述话语产生的叙述行为),以“叙事”为核心重点研究了“叙事”和与其相关的另外两个层面—“故事”和“叙述”间的复杂关系。
同时,他主张将叙事策略从叙事时间、语式、语态三个层面来衡量。
1995年英国布克奖获奖作品《鬼途》是英国当代重要女作家帕特•巴克《重生》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小说共十八章,通过虚构军官普瑞尔和历史真实人物里弗斯两条主线交替叙事来展开故事情节。
奇数章描述了军官普瑞尔返回战场后的军旅生活,并且从第七章开始以日记的形式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幅残忍的战争画面;偶数章以爱丁堡的克莱格洛哈特军医院为主要场景,描写了一群在一战期间患上炮弹休克症的士兵在后方军事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读者透过军医里弗斯的视角目睹了战争带给士兵们身体和精神的巨大创伤。
同时,小说运用大篇幅的插叙回顾里弗斯在太平洋西南部美拉尼西亚地区进行考察业的经历,带领读者进入人类原初的生存现实,并进行跨时间、跨地域、跨种族的历时对位思考。
本文基于热奈特叙事理论来分析小说的叙事时间和叙事聚焦,帮助读者进一步地理解小说的战争创伤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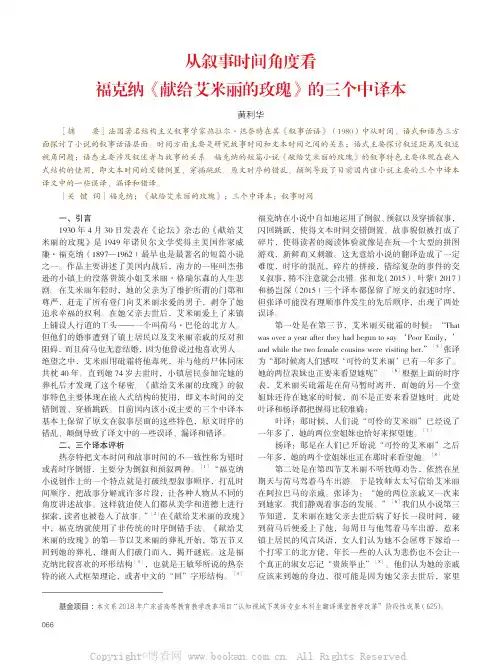
066一、引言1930年4月30日发表在《论坛》杂志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是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1897—1962)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
作品主要讲述了美国内战后,南方的一座叫杰弗逊的小镇上的没落贵族小姐艾米丽·格瑞尔森的人生悲剧。
在艾米丽年轻时,她的父亲为了维护所谓的门第和尊严,赶走了所有登门向艾米丽求爱的男子,剥夺了她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她父亲去世后,艾米丽爱上了来镇上铺设人行道的工头—一个叫荷马·巴伦的北方人。
但他们的婚事遭到了镇上居民以及艾米丽亲戚的反对和阻碍,而且荷马也无意结婚,因为他曾说过他喜欢男人。
绝望之中,艾米丽用砒霜将他毒死,并与他的尸体同床共枕40年。
直到她74岁去世时,小镇居民参加完她的葬礼后才发现了这个秘密。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叙事特色主要体现在嵌入式结构的使用,即文本时间的交错倒置、穿插跳跃。
目前国内该小说主要的三个中译本基本上保留了原文在叙事层面的这些特色,原文时序的错乱、颠倒导致了译文中的一些误译、漏译和错译。
二、三个译本评析热奈特把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的不一致性称为错时或者时序倒错,主要分为倒叙和预叙两种。
[1]“福克纳小说创作上的一个特点就是打破线型叙事顺序,打乱时间顺序,把故事分解成许多片段,让各种人物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
这样就迫使人们都从美学和道德上进行探索,读者也被卷入了故事。
”[2]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福克纳就使用了非传统的时序倒错手法。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第一节以艾米丽的葬礼开始,第五节又回到她的葬礼,继而人们破门而入,揭开谜底。
这是福克纳比较喜欢的环形结构[3],也就是王敏琴所说的热奈特的嵌入式框架理论,或者中文的“回”字形结构。
[4]福克纳在小说中自如地运用了倒叙、预叙以及穿插叙事,闪回跳跃,使得文本时间交错倒置。
故事貌似被打成了碎片,使得读者的阅读体验就像是在玩一个大型的拼图游戏,新鲜而又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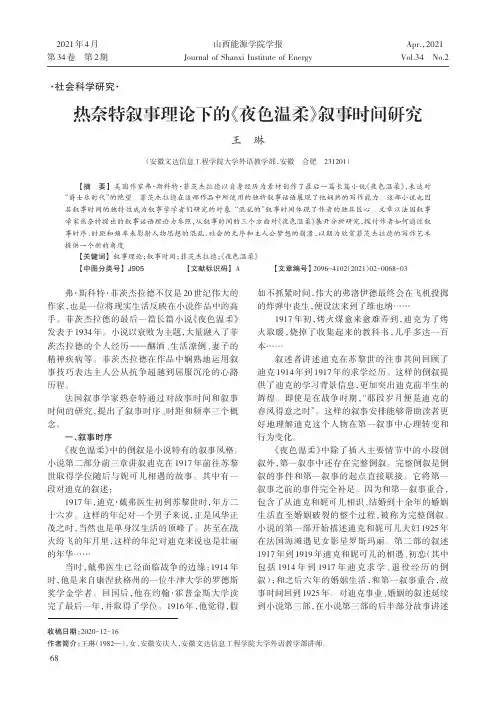
2021年4月第34卷第2期山西能源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xi Institute of EnergyApr.,2021Vol.34No.2·社会科学研究·热奈特叙事理论下的《夜色温柔》叙事时间研究(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安徽合肥231201)王琳【摘要】美国作家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最后一篇长篇小说《夜色温柔》,表达对“爵士乐时代”的绝望。
菲茨杰拉德在这部作品中所使用的独特叙事话语展现了他娴熟的写作能力。
这部小说也因其叙事时间的独特性成为叙事学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混乱的”叙事时间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
文章以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提出的叙事话语理论为参照,从叙事时间的三个方面对《夜色温柔》展开分析研究,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叙事时序、时距和频率来影射人物思想的混乱、社会的无序和主人公梦想的崩溃,以期为欣赏菲茨杰拉德的写作艺术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关键词】叙事理论;叙事时间;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102(2021)02-0068-03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不仅是20世纪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将现实生活反映在小说作品中的高手。
菲茨杰拉德的最后一篇长篇小说《夜色温柔》发表于1934年。
小说以衰败为主题,大量融入了菲茨杰拉德的个人经历——酗酒、生活潦倒、妻子的精神疾病等。
菲茨杰拉德在作品中娴熟地运用叙事技巧表达主人公从抗争超越到屈服沉沦的心路历程。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通过对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研究,提出了叙事时序、时距和频率三个概念。
一、叙事时序《夜色温柔》中的倒叙是小说特有的叙事风格。
小说第二部分前三章讲叙迪克在1917年前往苏黎世取得学位随后与妮可儿相遇的故事。
其中有一段对迪克的叙述:1917年,迪克·戴弗医生初到苏黎世时,年方二十六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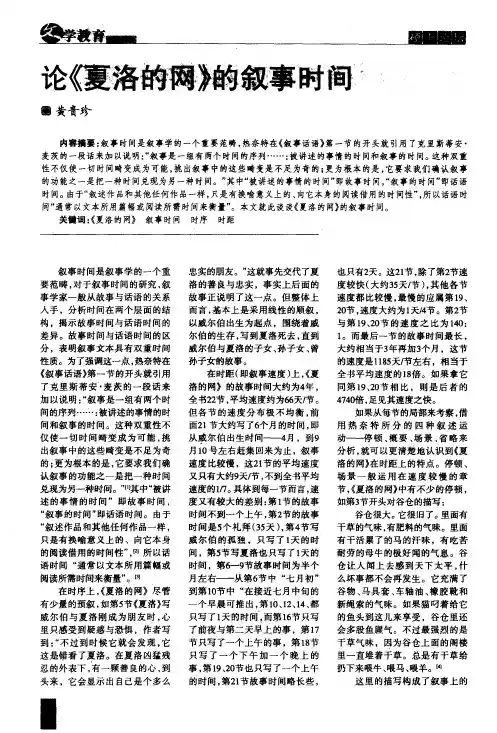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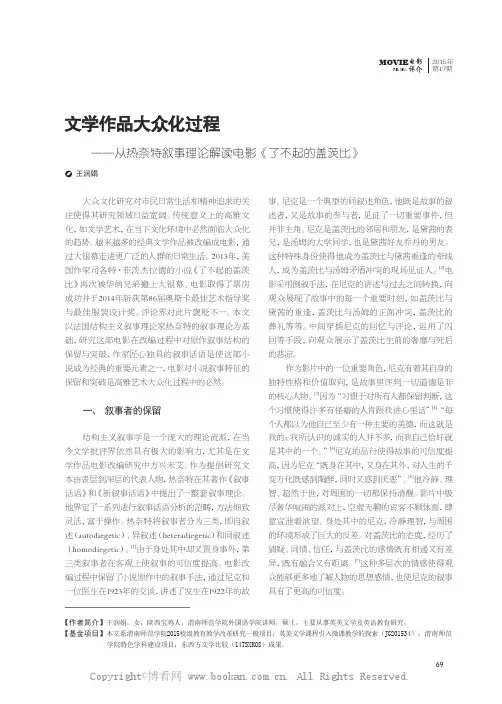
69MOVIE REVIEW 电影评介2015年第17期文学作品大众化过程——从热奈特叙事理论解读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王润娟大众文化研究对市民日常生活和精神追求的关注使得其研究领域日益宽阔。
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化,如文学艺术,在当下文化环境中必然面临大众化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通过大银幕走进更广泛的人群的日常生活。
2013年,美国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再次被华纳兄弟搬上大银幕。
电影取得了票房成功并于2014年斩获第86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与最佳服装设计奖。
评论界对此片褒贬不一。
本文以法国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家热奈特的叙事理论为基础,研究这部电影在改编过程中对原作叙事结构的保留与突破,作家匠心独具的叙事话语是使这部小说成为经典的重要元素之一,电影对小说叙事特征的保留和突破是高雅艺术大众化过程中的必然。
一、 叙事者的保留结构主义叙事学是一个庞大的理论流派,在当今文学批评界依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研究中方兴未艾。
作为提倡研究文本由表层到深层的代表人物,热奈特在其著作《叙事话语》和《新叙事话语》中提出了一整套叙事理论。
他界定了一系列进行叙事话语分析的范畴,方法细致灵活,富于操作。
热奈特将叙事者分为三类,即自叙述(autodiegetic )、异叙述(heteradiegetic )和同叙述(homodiegetic )。
[1]由于身处其中却又置身事外,第三类叙事者在客观上使叙事的可信度提高。
电影改编过程中保留了小说原作中的叙事手法,通过尼克和一位医生在1923年的交谈,讲述了发生在1922年的故事。
尼克是一个典型的同叙述角色,他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见证了一切重要事件,但并非主角。
尼克是盖茨比的邻居和朋友,是黛茜的表兄,是汤姆的大学同学,也是黛茜好友乔丹的男友。
这种特殊身份使得他成为盖茨比与黛茜重逢的牵线人,成为盖茨比与汤姆矛盾冲突的现场见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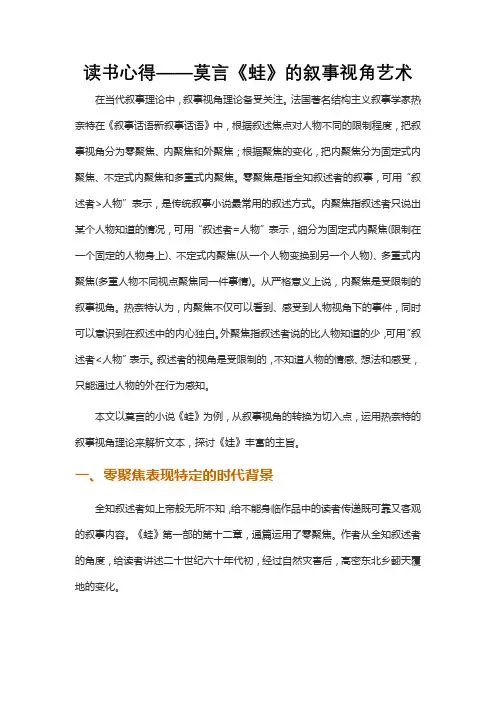
读书心得——莫言《蛙》的叙事视角艺术在当代叙事理论中,叙事视角理论备受关注。
法国著名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根据叙述焦点对人物不同的限制程度,把叙事视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根据聚焦的变化,把内聚焦分为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
零聚焦是指全知叙述者的叙事,可用“叙述者>人物”表示,是传统叙事小说最常用的叙述方式。
内聚焦指叙述者只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可用“叙述者=人物”表示,细分为固定式内聚焦(限制在一个固定的人物身上)、不定式内聚焦(从一个人物变换到另一个人物)、多重式内聚焦(多重人物不同视点聚焦同一件事情)。
从严格意义上说,内聚焦是受限制的叙事视角。
热奈特认为,内聚焦不仅可以看到、感受到人物视角下的事件,同时可以意识到在叙述中的内心独白。
外聚焦指叙述者说的比人物知道的少,可用“叙述者<人物”表示。
叙述者的视角是受限制的,不知道人物的情感、想法和感受,只能通过人物的外在行为感知。
本文以莫言的小说《蛙》为例,从叙事视角的转换为切入点,运用热奈特的叙事视角理论来解析文本,探讨《娃》丰富的主旨。
一、零聚焦表现特定的时代背景全知叙述者如上帝般无所不知,给不能身临作品中的读者传递既可靠又客观的叙事内容。
《蛙》第一部的第十二章,通篇运用了零聚焦。
作者从全知叙述者的角度,给读者讲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经过自然灾害后,高密东北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2年秋天,高密东北乡三万亩地瓜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
跟我们闹了三年别扭、几乎是颗粒无收的大地,又恢复了他宽厚仁慈、慷慨奉献的本性。
……县委书记杨林抱着这个大地瓜照了一张照片,刊登在《大众日报》的头版头条[2]52。
莫言以地瓜丰收,县委书记“抱着”地瓜的照片的全知叙述视角告诉读者高密人民告别自然灾害的痛苦经历,迎来丰收的喜悦心情。
同时,叙述视角还聚焦于县委书记杨林,为十五章文革时期批斗杨林埋下伏笔,暗示杨林坎坷的悲剧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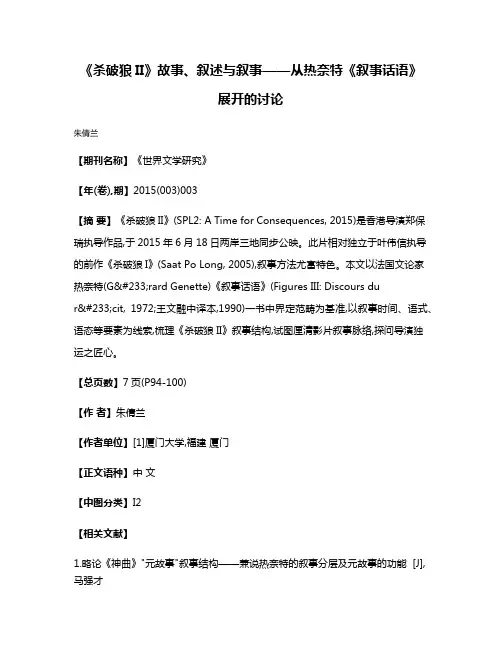
《杀破狼II》故事、叙述与叙事——从热奈特《叙事话语》
展开的讨论
朱倩兰
【期刊名称】《世界文学研究》
【年(卷),期】2015(003)003
【摘要】《杀破狼II》(SPL2: A Time for Consequences, 2015)是香港导演郑保瑞执导作品,于2015年6月18日两岸三地同步公映。
此片相对独立于叶伟信执导的前作《杀破狼I》(Saat Po Long, 2005),叙事方法尤富特色。
本文以法国文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叙事话语》(Figures III: Discours du
récit, 1972;王文融中译本,1990)一书中界定范畴为基准,以叙事时间、语式、语态等要素为线索,梳理《杀破狼II》叙事结构,试图厘清影片叙事脉络,探问导演独运之匠心。
【总页数】7页(P94-100)
【作者】朱倩兰
【作者单位】[1]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相关文献】
1.略论《神曲》"元故事"叙事结构——兼说热奈特的叙事分层及元故事的功能 [J], 马强才
2.热奈特叙述层理论与元故事叙事理论的文本应用--以《生死疲劳》为例 [J], 刘芹良;裴菱璐
3.热奈特的叙事理论分析及运用——以《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为主 [J], 李俊丽;
4.热奈特叙事话语理论下的综艺真人秀\r——以《明星大侦探》为例 [J], 李丹
5.用热奈特叙事学理论分析《苦恼》中的叙事话语 [J], 张燚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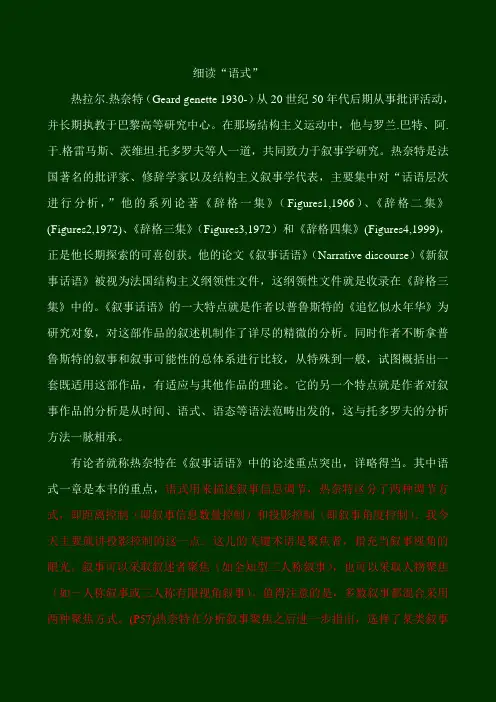
2050语式用来描述叙事信息调节,热奈特区分了两种调节方式,即距离控制(即叙事信息数量控制)和投影控制(即叙事角度控制)。
我今天主要就讲投影控制的这一点。
这儿的关键术语是聚焦者,指充当叙事视角的眼光。
叙事可以采取叙述者聚焦(如全知型三人称叙事),也可以采取人物聚焦(如一人称叙事或三人称有限视角叙事)。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叙事都混合采用两种聚焦方式。
(P57)热奈特在分析叙事聚焦之后进一步指出,选择了某类叙事聚焦,也就选择了信息数量和叙事角度,因为特定的聚焦只能感知到某些信息,如果叙事超越了这些信息,则被视为“视角越界”。
但他同时指出,很多情况下视角越界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判断,读者的认知策略可以帮助他们合理地排除这些越界可能带来的阅读困难。
(PP143-147)1.视角。
()卢伯克、克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沃伦等人的从内部分析来讲从外部观察事件叙事者作为人物在情节中出现(1)主人公讲述自己的故事(2)见证人讲述主人公的故事叙事者不是人物不在情节中出现(3)善于心理分析或全知的作者讲述的故事(4)作者从外部讲述故事接着,热奈特悉数以前的理论家们分类之不足,指出斯坦策尔(F.K. Stanzel))、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等》)热耐特就指出斯坦泽尔所区分的第二与第三种方式在叙事眼光上并无差异,因为两者采用的均为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他们之间妨用“聚焦人物”一词来指涉其眼光充当叙事视角的人物),而第三种类中的音与叙事眼光的区域。
诺尔曼·弗里德曼(Nor-man Friedman)的八分法显得更称”叙述(我=见证人或我=主人公)、两类“选择性全知”叙述(即有限视角,应该把分类的范围限定在纯语式里,范围不能太宽泛。
因此他极力推崇托多罗夫在对“视角”或“语体”的限定基础上提出的三分法:全知叙述者的叙事、“有限视野”的叙事和视角外叙事。
2. 聚焦。
经过细致地讨论后,热奈特发现,视角、视野或视点这些词属于专门的化的视觉范畴,因此,他主张用较为抽象的词语来替代它们,内聚焦叙事固定式。
明清小说中的倒叙文石慧内容提要明清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时期,中国古典小说长于预叙,但并不意味着缺少倒叙,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明清小说中的倒叙问题。
明清小说中的倒叙有特殊的标志词,常常通过人物对话自然呈现,多是对人物出身和经历的交代。
明清小说中的倒叙和西方传统小说中的倒叙有很大的不同,起着帮助读者理清人物关系,了解事件发展,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小说倒叙热拉尔?热奈特将倒叙定义为“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的追述”。
古人称之为“倒卷帘法”。
相较于预叙来说,西方文学中对倒叙的使用更频繁一些,故事从中间开始叙述,当要追溯来龙去脉的时候,倒叙就成为最合适的选择。
比如《荷马史诗》从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的争吵开始,《俄狄浦斯王》从忒拜城遭受瘟疫,俄狄浦斯调查原因开始。
清末学者周桂笙形容西方小说是“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
有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
”其实,中国古典文学也不乏倒叙,早在《左传》之《郑伯克段于鄢》中就有倒叙的使用。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生庄公及共叔段。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爱共叔段,欲立之。
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这个“初”就是倒叙的开始。
明清文学中也有这样的倒叙,一些公案小说就是从倒叙开始的。
《红楼梦》中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倒叙。
开篇对那块无才补天之石的离奇经历的倒叙,“原来女娲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随后,在“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冷子兴更是对贾府的家底及贾府的主要人物来了一个的全面的倒叙。
其实古人对倒叙的认识早在毛宗岗的《读三国志法》中就有详细的讨论:“《三国》一书,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秀之妙。
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
不但使前文不沓拖,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之妙品也。
如吕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夺徐州之前,却于困下邳时叙之;曹操望梅止渴本在击张绣之日,却于青梅煮酒时叙之;管宁割席分坐,本在华歆未仕之前,却于破壁取后时叙之;武侯求黄氏为配本在未出草庐之前,却于诸葛瞻死难时叙之。
故事外叙述≠在故事之外叙述张鹤2007年第2期外语学刊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1955年,斯坦泽尔依据讲述者在故事中所处的视点位置,在其《长篇小说的叙述情境》中提出三种叙述情境:作者“无所不知”叙述情境(第三人称全知叙述) 、叙述者作为书中人物的叙述情境(第一人称叙述)和根据一个人物的观察点用第三人称引导的叙述情境(人物叙述) 。
(华莱士1990:163)热奈特从结构分析角度,对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类型进行的划分既清晰又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许多叙事学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分类法(雷蒙·凯南1991: 111) 。
热奈特根据叙述者的叙述层次(故事外/故事内)和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异故事/同故事)确定叙述者在一切叙事中的地位,由此衍生出4类叙述者。
(1)故事外( extradiegetic) ———异故事叙述( heterodiegetic) :叙述者处于故事的第一层次,不参与故事的进程。
( 2 )故事外———同故事叙述( homodiegetic) : 叙述者处于故事的第一层次,参与故事的进程,不过叙述人不能与作者完全等同。
( 3 ) 故事内( intradiegetic ) ———异故事叙述:叙述者处于故事的第二层次,不参与故事的进程。
(4)故事内———同故事叙述:叙述者处于故事的第二层次,参与故事的进程。
(热奈特1990:175 - 176)依据热奈特的故事层次标准,相对于故事内(第二层故事,热奈特又称为元故事)而言,故事外叙述指的是文本中存在的第一层故事;有时没有故事内层的时候,就只有这一层故事。
那么,在故事外层中,叙述者可以是异故事叙述者,讲述与本人无关的故事,使用第三人称叙事;叙述者也可以是同故事叙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使用第一人称叙事。
其实,故事外叙述并不能说明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与由谁讲述故事、讲故事者是否与故事人物处于同一世界这些活动和现象无关,它只表明故事由几个层次构成。
类似叙事学理论的理论1.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1990.2.[美]詹姆斯·费伦.《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6.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8.申丹.《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张寅德编选.《叙事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1.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2.[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3.美]杰克·哈特.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4.金森修.巴什拉:科学与诗[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5.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6.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7.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8.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本.19.美]苏珊.S.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美]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3.龙迪勇《空间叙事学》24.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践》25.米克巴尔《叙事理论导论》26.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27.海阔《电影叙事的空间转向》。
从叙事学角度解读莫言《球状闪电》作者:王飞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09年第12期法国结构主义者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小说文本时间分为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
故事时间指小说中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发展的自然时间,其中体现出一种非人为可逆的客观性;而叙事时间,则是按照作者创作的主观意图进行叙述的时间,主要体现了作者创作时的能动性。
为体现叙事的艺术,小说家们往往已不再只按单纯的顺叙或单纯地加入倒叙来组织文本结构,他们希望通过对这两种时间的调整,不仅能显示艺术处理的痕迹,还能突出传统叙事模式无法达到的审美效果。
莫言的《球状闪电》就是其中一篇。
一.叙事迷宫的建构如果将《球状闪电》中发生在爆发球状闪电那天的故事,作为整个文本的时间主线,我们就可以将十个小节中在叙述按闪电出现前→闪电出现→闪电爆炸后的叙事时间作如下图示:第一节:ⅰ第二节:ⅱ′(注)第三节:ⅱⅱ′第四节:全节为回忆第五节:ⅲ第六节:(上同第四节)第七节:ⅴ第八节:ⅰ′ⅲ′第九节:ⅲ′第十节:ⅳⅴ′ⅵ(注:这个“′”是与其相同的数字所代表的故事时间相差不远的时刻,但作者在叙述时刻意将它们分离了)按此图示,每小节对球状闪电发生那天的时间(即前文所说的故事时间主线,下称“闪电故事时间”)的叙述皆按顺叙进行,比如第三节中ⅱ后才是ⅱ′,第八节ⅰ′后才是ⅲ′。
但为什么还是会带来文本阅读上的困难呢,原因有二:1、作者对闪电故事时间在每一小节中都进行了顺叙安排,但综观十个小节,却出现了叙事时间上的重新调整。
比如第四小节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接在ⅱ′这个故事时间之后,而是全节进行了回忆性叙述;而第八节也是抛开了前一节ⅴ这个故事时间,另起了ⅰ′这个时间重新叙述。
这样,单就闪电故事时间那天的叙述,作者就作了大调整,自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但更重要的,还是第二个方面。
2、热奈特用大写英文字母来表示叙事时间,而用阿拉伯数字代表故事时间。
莫言将每个小节内部的叙事时间进行重构,打乱了人们习惯的时间顺序,通过每小节中的倒叙、插叙等交替运用,以及人称与视角的转换,使文本构成了庞杂的叙事迷宫。
以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分析《琅琊榜》作者:麻玥来源:《今传媒》2016年第03期摘要:2015年一部《琅琊榜》,在同期的电视剧中,可谓一压群雄。
但有一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
该剧自上线以来,豆瓣上的评分呈下滑趋势。
笔者认为该剧在影像视听艺术上的突破,对中国电视剧来说确是一次大胆且较为成功的尝试,但在叙事上,仍存有漏洞。
虎头蛇尾的计谋阐释和过于拖沓的叙事节奏,无疑成为了该剧优于吸引观众却困于留住观众的关键。
本文将以法国结构主义叙述学代表:热奈特,所提出的叙事学理论,对该剧的叙事进行分析,力图从中找出该剧叙事力度不足的理论依据,供之后影视作品在叙事结构构建时,不单单关注镜语的发展,也着手于“叙事”的艺术琢磨,以期给以后的电视剧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琅琊榜》;叙事学;权谋剧;热拉尔·热奈特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087-02一、引言《琅琊榜》的热播使得“江左梅郎,麒麟之才,得之可得天下”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小谈。
这部良心之作,以国画墨色的浓淡相宜,儒家古训的低眉谦逊、琴曲合鸣的高山仰止、帝王家觥筹独奏的悲鸣、文人墨客推杯换盏的游移为影像气质,在画面色彩、叙事节奏、音乐渲染和镜头运用等视听语言方面,都唤起了观众的心理认同。
在个人主义、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导演所构造的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架空时代”,无疑唤起了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观众们深藏心底的“江湖情怀”。
这也是该剧上线后,迅速得到追捧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好评连连的背后,我们不能忽视其作为一部“权谋剧”在叙事上却显得单薄。
二、故事梗概与叙事线索和权谋剧的叙事模式《琅琊榜》整部剧以诡术多变、又重情重义的梅长苏作为主线,重在展现他以谋士的新身份重回朝堂后,通过自己的才智和权术,使谜案昭雪、新君登基,最终完成复仇的整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编剧重在展现朝堂之上夺嫡之战中的尔虞我诈、悬念迭起,朝野之下兄弟之间的有情有义,群臣之间的精忠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