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wang
- 格式:pptx
- 大小:400.26 KB
- 文档页数: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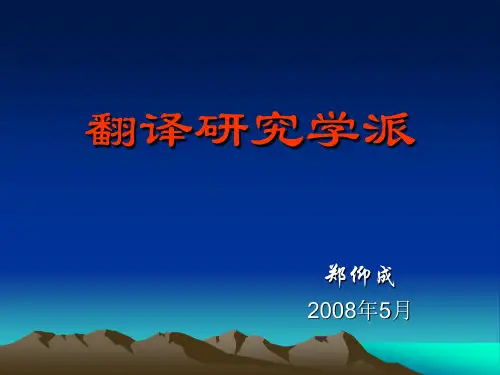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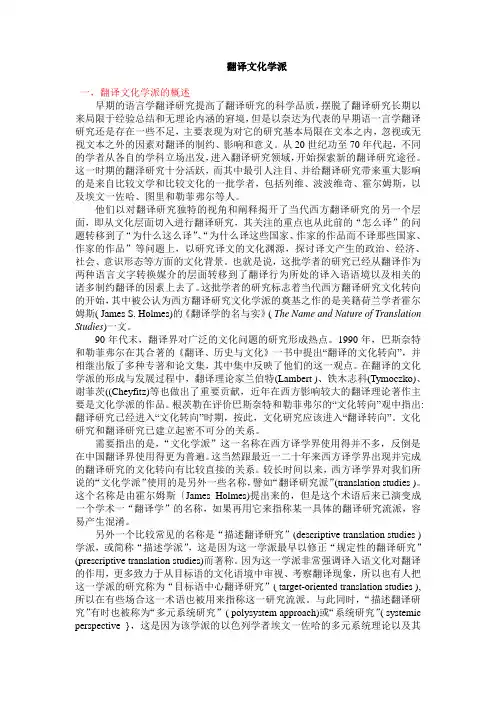
翻译文化学派一,翻译文化学派的概述早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提高了翻译研究的科学品质,摆脱了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经验总结和无理论内涵的窘境,但是以奈达为代表的早期语一言学翻译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它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文本之内,忽视或无视文本之外的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影响和意义。
从20世纪功至70年代起,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开始探索新的翻译研究途径。
这一时期的翻泽研究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给翻译研究带来重大影响的是来自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一批学者,包括列维、波波维奇、霍尔姆斯,以及埃文一佐哈、图里和勒菲弗尔等人。
他们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此前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探讨译文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背景。
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去了。
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 James S. 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
90年代末,翻译界对广泛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形成热点。
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并相继出版了多种专著和论文集,其中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观点。
在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翻译理论家兰伯特(Lambert )、铁木志科(Tymoczko)、谢菲茨((Cheyfitz)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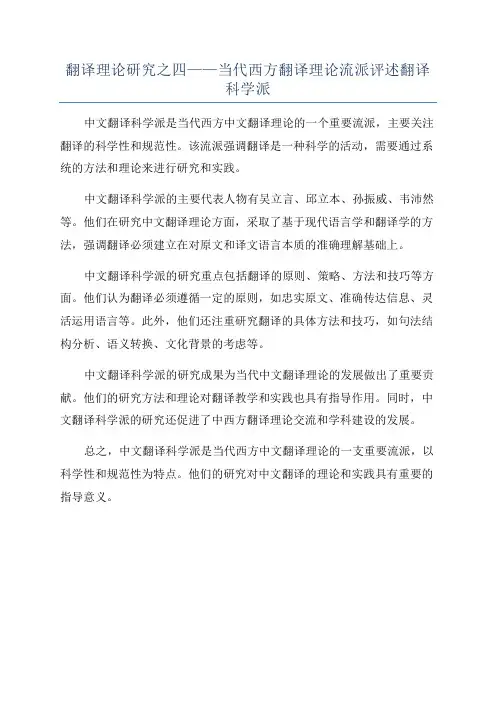
翻译理论研究之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翻译
科学派
中文翻译科学派是当代西方中文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主要关注翻译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该流派强调翻译是一种科学的活动,需要通过系统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研究和实践。
中文翻译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吴立言、邱立本、孙振威、韦沛然等。
他们在研究中文翻译理论方面,采取了基于现代语言学和翻译学的方法,强调翻译必须建立在对原文和译文语言本质的准确理解基础上。
中文翻译科学派的研究重点包括翻译的原则、策略、方法和技巧等方面。
他们认为翻译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如忠实原文、准确传达信息、灵活运用语言等。
此外,他们还注重研究翻译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如句法结构分析、语义转换、文化背景的考虑等。
中文翻译科学派的研究成果为当代中文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翻译教学和实践也具有指导作用。
同时,中文翻译科学派的研究还促进了中西方翻译理论交流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总之,中文翻译科学派是当代西方中文翻译理论的一支重要流派,以科学性和规范性为特点。
他们的研究对中文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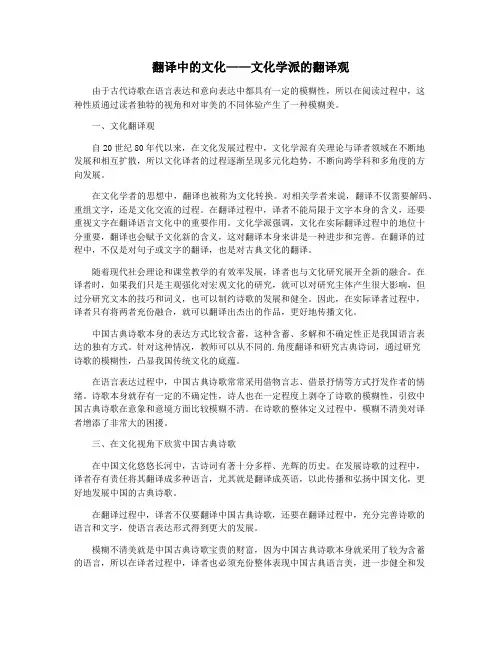
翻译中的文化——文化学派的翻译观由于古代诗歌在语言表达和意向表达中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在阅读过程中,这种性质通过读者独特的视角和对审美的不同体验产生了一种模糊美。
一、文化翻译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学派有关理论与译者领域在不断地发展和相互扩散,所以文化译者的过程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不断向跨学科和多角度的方向发展。
在文化学者的思想中,翻译也被称为文化转换。
对相关学者来说,翻译不仅需要解码、重组文字,还是文化交流的过程。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能局限于文字本身的含义,还要重视文字在翻译语言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学派强调,文化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翻译也会赋予文化新的含义,这对翻译本身来讲是一种进步和完善。
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是对句子或文字的翻译,也是对古典文化的翻译。
随着现代社会理论和课堂教学的有效率发展,译者也与文化研究展开全新的融合。
在译者时,如果我们只是主观强化对宏观文化的研究,就可以对研究主体产生很大影响,但过分研究文本的技巧和词义,也可以制约诗歌的发展和健全。
因此,在实际译者过程中,译者只有将两者充份融合,就可以翻译出杰出的作品,更好地传播文化。
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表达方式比较含蓄,这种含蓄、多解和不确定性正是我国语言表达的独有方式。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翻译和研究古典诗词,通过研究诗歌的模糊性,凸显我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中国古典诗歌常常采用借物言志、借景抒情等方式抒发作者的情绪。
诗歌本身就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诗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诗歌的模糊性,引致中国古典诗歌在意象和意境方面比较模糊不清。
在诗歌的整体定义过程中,模糊不清美对译者增添了非常大的困擾。
三、在文化视角下欣赏中国古典诗歌在中国文化悠悠长河中,古诗词有著十分多样、光辉的历史。
在发展诗歌的过程中,译者存有责任将其翻译成多种语言,尤其就是翻译成英语,以此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古典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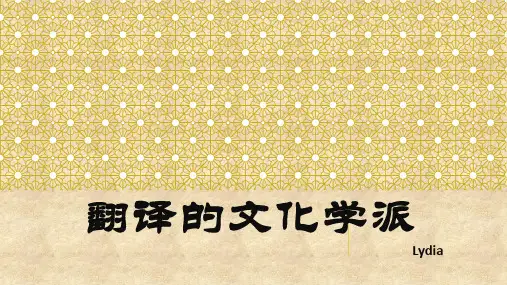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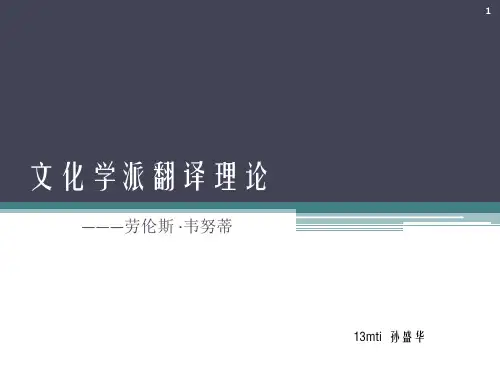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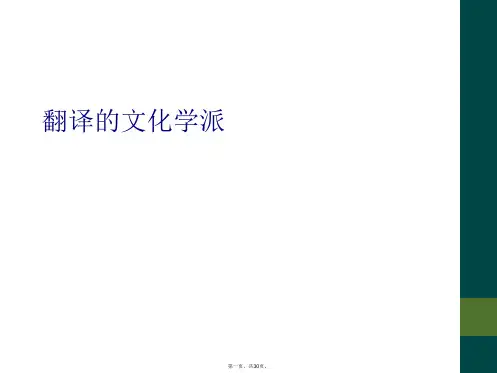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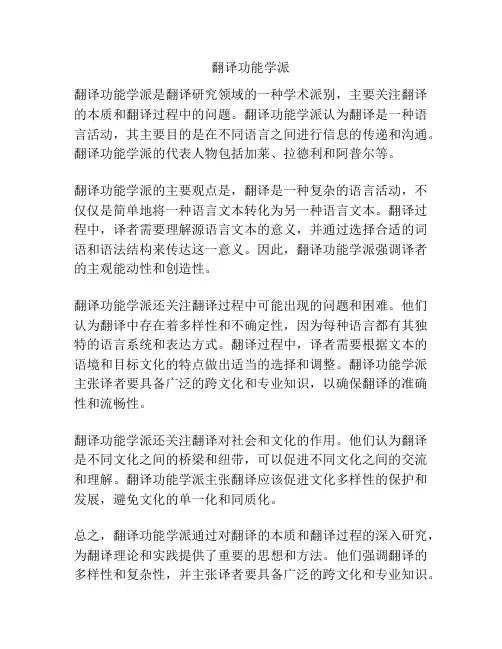
翻译功能学派
翻译功能学派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种学术派别,主要关注翻译的本质和翻译过程中的问题。
翻译功能学派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沟通。
翻译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加莱、拉德利和阿普尔等。
翻译功能学派的主要观点是,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不仅仅是简单地将一种语言文本转化为另一种语言文本。
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理解源语言文本的意义,并通过选择合适的词语和语法结构来传达这一意义。
因此,翻译功能学派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翻译功能学派还关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
他们认为翻译中存在着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言系统和表达方式。
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文本的语境和目标文化的特点做出适当的选择和调整。
翻译功能学派主张译者要具备广泛的跨文化和专业知识,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
翻译功能学派还关注翻译对社会和文化的作用。
他们认为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翻译功能学派主张翻译应该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避免文化的单一化和同质化。
总之,翻译功能学派通过对翻译的本质和翻译过程的深入研究,为翻译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方法。
他们强调翻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主张译者要具备广泛的跨文化和专业知识。
翻译功能学派的研究为翻译界的发展和翻译教育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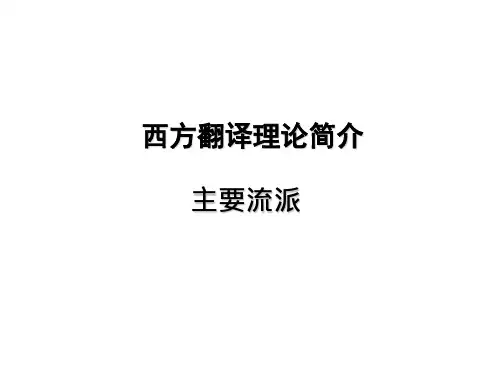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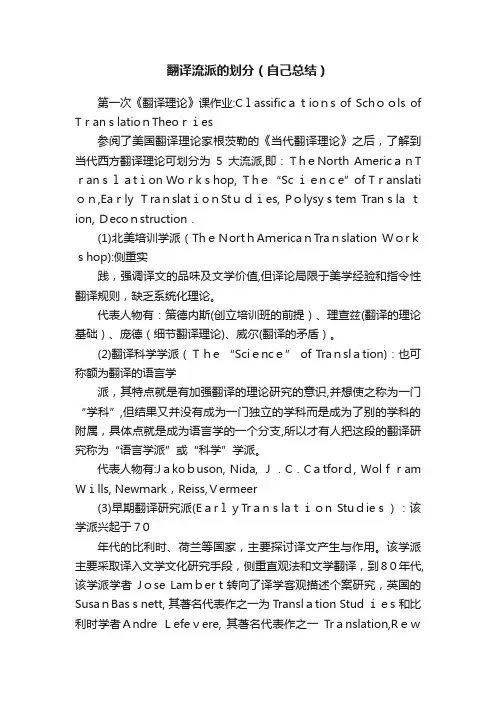
翻译流派的划分(自己总结)第一次《翻译理论》课作业:Classifications of Schools of TranslationTheories参阅了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之后,了解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可划分为5大流派,即:TheNorth AmericanT ranslation Workshop, The“Sc ience”of Translati on,Early TranslationStudies, Polysystem Transla tion, Deconstruction.(1)北美培训学派(TheNorthAmericanTranslation Workshop):侧重实践,强调译文的品味及文学价值,但译论局限于美学经验和指令性翻译规则,缺乏系统化理论。
代表人物有:策德内斯(创立培训班的前提)、理查兹(翻译的理论基础)、庞德(细节翻译理论)、威尔(翻译的矛盾)。
(2)翻译科学学派(The “Science” of T ranslation):也可称额为翻译的语言学派,其特点就是有加强翻译的理论研究的意识,并想使之称为一门“学科”,但结果又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成为了别的学科的附属,具体点就是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才有人把这段的翻译研究称为“语言学派”或“科学”学派。
代表人物有:Jakobuson, Nida, J.C.Catford, Wolfram Wills, Newmark,Reiss,Vermeer(3)早期翻译研究派(EarlyTranslation Studies):该学派兴起于70年代的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主要探讨译文产生与作用。
该学派主要采取译入文学文化研究手段,侧重直观法和文学翻译,到80年代,该学派学者Jose Lambert转向了译学客观描述个案研究,英国的SusanBassnett, 其著名代表作之一为Translation Stud ies 和比利时学者Andre Lefevere, 其著名代表作之一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则转向文化研究模式(4)多元体系学派(Polysystem Translation):其翻译理论反战与早期研究学派,是翻译研究学派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
文化翻译学派主要观点注重翻译与源语及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到与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翻译研究的目标不再止于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的对等问题,而需要同时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
它包含二重涵义:一指: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二指:从宽宏的文化层面来审视和阐释翻译。
主要体现在其文化功能对等论上,和“操纵”论、“文化构建”以及与“操纵”论和“文化构建”论一脉相承的后殖民翻译观上。
(第一,文化学派从文化这一宏观角度来研究翻译,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
第二,文化学派重视译者与目标语文化,否定了传统意义上将翻译工作视为低等活动的说法,提高了翻译与译者的地位。
第三,文化学派强调了文化才是翻译的单位,这就彻底否定了先前的认为字、词、句、篇是翻译单位的翻译理论----巴斯奈特。
)代表人物: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伊塔玛·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西奥.赫斯曼(Theo Hermans)詹姆斯·霍尔姆斯代表作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划时代意义)----霍尔姆斯着解决了重大的翻译理论问题,突出观点:翻译学的名与实A:首先是给学科命名,该文明确提出用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名称。
B:其次是下文确定其是指某一个研究领域还是指某一个学科。
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
在文中他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 )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 )。
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 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 Translation criticism)三大块研究领域,确立了“描述”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作者: 贾文山
出版物刊名: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69-72页
主题词: 翻译研究;文化学;中国传统文化;翻译观;理论支柱;翻译技巧;文化问题;翻译理论;不同文化;文化差异
摘要: <正> 到目前为止,古今中外的翻译研究大致形成了两个学派。
一是语文学派(PhilologicalSchool)。
该学派从经验出发,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翻译技巧,提出过一些翻译观点。
但它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柱,过于抽象、宽泛或肤浅,缺乏说服力。
二是语言学派(LinguisticalSchool)。
该学派是应西方语言理论日趋成熟而诞生的。
语言学的发展为翻译研究的理论化和科学化打下了基础。
本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以惊人的胆识将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中,从而使翻译研究第一次迈进理论和科学的宫殿。
由于有语言学作它的理论支柱,这一学派显然具备了语文学派所没有的优点,更具说服力。
但是,由于翻译的复杂性,无论语文学派还是语言学派都不能解决所有的翻译难题。
翻译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不仅与语言或文学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它还与以语言作为外壳或载体的文化密切相关。
以上两个学派因受其研究角度的局限,仅能解决某些特定问题,却不能解决翻译的实质性问题——翻译中的文化问题。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iturai StudiesIn 1990, André Lefevere and 阿I edited a collection of essays entitled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We co-wrote the introductory essay to the volume, intending it as a kind of manifesto of what we saw as a major change of empha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e were trying to argue that the study of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had moved on from its formalist phase and was beginning to consider broader issues of context, history and convention:Once upon a time, the questions that were always being asked were 'How can translation be taught?' and 'How can translation be studied?' Those who regarded themselves as translators were often contemptu- ous of any attempts to teach translation, whilst those who claimed to teach often did not translate, and so had to resort to the old evaluative method of setting one translation alongside another and examining both in a formalist vacuum. Now, the questions have changed. The object of study has been redefined; what is studied is the text embedded in its network of both source and target cultural signs and in this way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en able both to utilize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and to move out beyond it. (Bassnert & Lefevere, 1990)1990年,勒菲弗尔和我编了一本名为“翻译、历史和文化”的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