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余英时
- 格式:doc
- 大小:41.50 KB
- 文档页数: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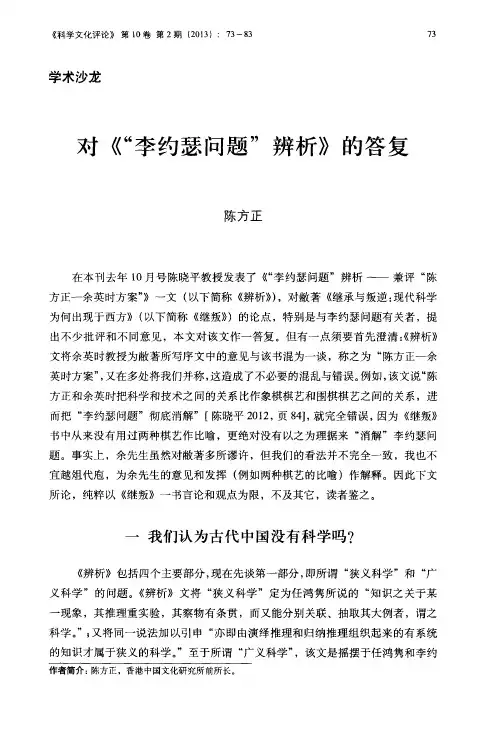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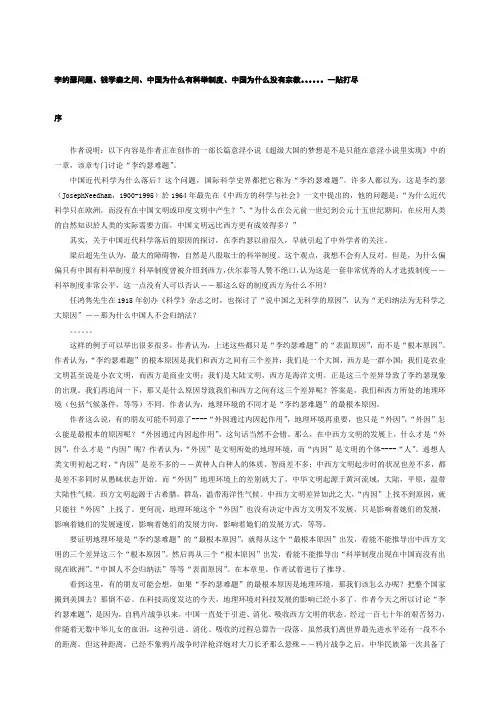
李约瑟问题、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有科举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
一贴打尽序作者说明:以下内容是作者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意淫小说《超级大国的梦想是不是只能在意淫小说里实现》中的一章,该章专门讨论“李约瑟难题”。
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
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於1964年最先在《中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其实,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梁启超先生认为,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这个观点,我想不会有人反对。
但是,为什么偏偏只有中国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曾被介绍到西方,伏尔泰等人赞不绝口,认为这是一套非常优秀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非常公平,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否认――那这么好的制度西方为什么不用?任鸿隽先生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也探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那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归纳法?。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作者认为,上述这些都只是“李约瑟难题”的“表面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和西方之间有三个差异:我们是一个大国,西方是一群小国;我们是农业文明甚至说是小农文明,而西方是商业文明;我们是大陆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
正是这三个差异导致了李约瑟现象的出现。
我们再追问一下,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和西方之间有这三个差异呢?答案是,我们和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条件,等等)不同。
作者认为,地理环境的不同才是“李约瑟难题”的最根本原因。
作者这么说,有的朋友可能不同意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地理环境再重要,也只是“外因”,“外因”怎么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句话当然不会错。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科技史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取得了众多重要科技发明,却没有实现工业革命以及相应的经济和科技发展。
这个问题得名于美籍华裔学者李约瑟,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
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李约瑟难题”。
要理解“李约瑟难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
中国古代发明了许多重要的科技,如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在某些方面甚至领先于其他国家。
这些发明为中国古代的军事、文化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中国在古代实现了一些重要的科技突破,但却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过工业革命,这成为了“李约瑟难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约瑟难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注重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这限制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与之相对,欧洲发达国家相对较早地形成了较为公平和透明的政治体制,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环境。
经济结构和传统价值观的差异也是“李约瑟难题”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农民地位低下,社会流动性有限。
相比之下,欧洲的经济更加多样化和商业化,经济上的自由度更强。
这使得欧洲更容易形成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并不完全缺乏对农业和工艺生产的关注。
在农业方面,中国古代引入了许多农具和耕作技术,对农业生产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工艺生产方面,中国古代的陶瓷、纺织和造船等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这些成就并没有转化为工业化的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以及政治制度等有关。
“李约瑟难题”涉及到多个因素,其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
通过对科技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科技发展不仅仅依赖于科技创新本身,还需要有适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来支持。
只有在这些方面的整合中,中国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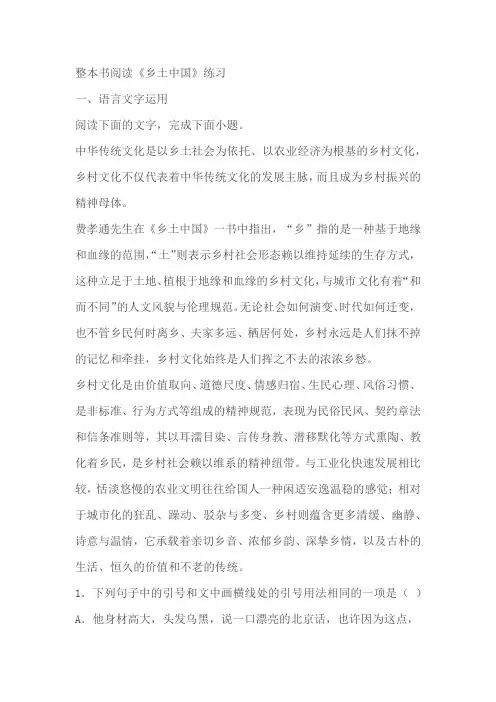
整本书阅读《乡土中国》练习一、语言文字运用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乡土社会为依托、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不仅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主脉,而且成为乡村振兴的精神母体。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乡”指的是一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范围,“土”则表示乡村社会形态赖以维持延续的生存方式,这种立足于土地、植根于地缘和血缘的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有着“和而不同”的人文风貌与伦理规范。
无论社会如何演变、时代如何迁变,也不管乡民何时离乡、夫家多远、栖居何处,乡村永远是人们抹不掉的记忆和牵挂,乡村文化始终是人们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
乡村文化是由价值取向、道德尺度、情感归宿、生民心理、风俗习惯、是非标准、行为方式等组成的精神规范,表现为民俗民风、契约章法和信条准则等,其以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等方式熏陶、教化着乡民,是乡村社会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
与工业化快速发展相比较,恬淡悠慢的农业文明往往给国人一种闲适安逸温稳的感觉;相对于城市化的狂乱、躁动、驳杂与多变、乡村则蕴含更多清缓、幽静、诗意与温情,它承载着亲切乡音、浓郁乡韵、深挚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不老的传统。
1.下列句子中的引号和文中画横线处的引号用法相同的一项是()A.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也许因为这点,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北京话”。
B.钟扬,这个15岁考入中科大无线电专业的少年,开始了他“不安分”的人生。
C.“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根线的长度,足够绕地球三匝,随卫星上天。
D.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了过去,叫做“发扬国光”。
2.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使用了对比的修辞手法,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其表达效果。
3.请以“乡村文化”为主语,用一个含递进关联词的复句概括第二、三段的主要内容。
不超过30个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从社会上说,取之于一乡的必须回之于一乡,这样,这个社会才能维持它的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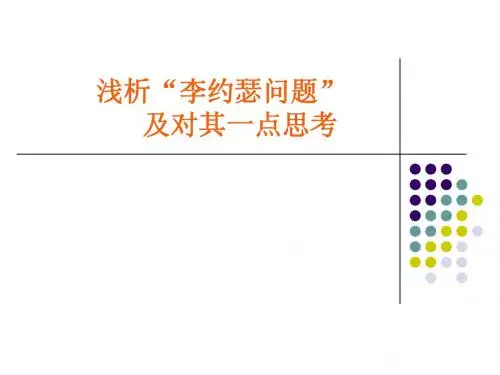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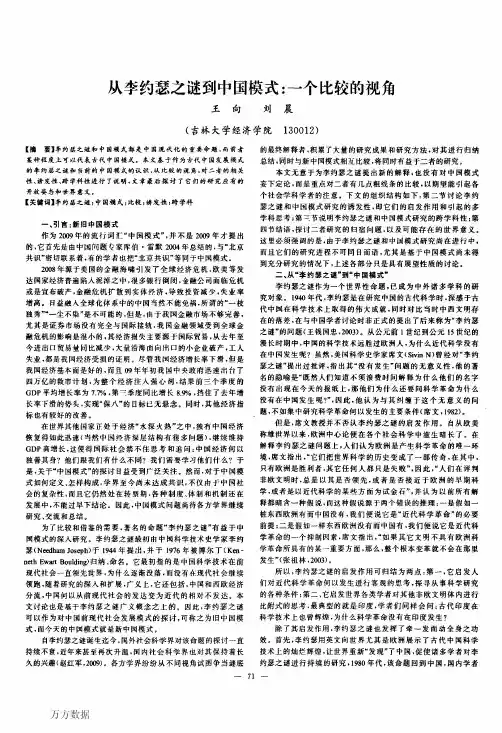
从李约瑟之谜到中国模式:一个比较的视角作者:王向, 刘晨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130012刊名:知识经济英文刊名:ZHISHI JINGJI年,卷(期):2010(12)1.席文(Sivin,1982)认为李约瑟之谜是一个无意义的伪问题,不如直接研究科学革命何以发生的基本条件,江晓原(2001)也认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不存在"领先"与否的问题,李约瑟之谜难以成立.但是,如果是基于广义的李约瑟之谜考虑,纳入早起强盛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进入现代社会,就不会有李约瑟之谜真伪之辩,著名的华人学者余英时(2009)也认为李约瑟之谜是假问题,所谓"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是两种棋类游戏,"道不同,不相为谋"2.首创"高水平陷阱"假说解释李约瑟之谜的Elvin(1973)就有以"过去中国的模式"为名的文章,虽然当前少有人拿李约瑟之谜代表古代中国发展模式,但是也有比如《求解中国经济的李约瑟之谜》这样的文章3.王钱国忠(2003)主编的《东西科学文化之桥--李约瑟研究》反映了国人对包括李约瑟之谜在内的李约瑟研究的广泛、持久的兴趣4."社会科学"在英文中是复数而非单数,丁学良(2005)认为任何良性社会发展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学科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学科可以唱独角戏5.这个问题首先由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提出,根据布罗代尔的话,"狄索托就把那种被哈耶克所称作的'人类合作的开展秩序'的市场经济被种种社会因素和机制所阻断和隔膜的社会安排称为'布罗代尔钟罩'"(韦森,2006)6.这是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的假说,在国内外由较大影响,他是以经济发展依赖于技术进步为前提、以近代前后不同的技术发明模式解释了中国古代技术何以发达、近代何以落后的问题7.在"北京共识"提出初期,"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甚至"北京模式"是并行或相互替代的(俞可平,2005),同时,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秦宣,2008;马龙闪,2008;刘国光,2009)8.邓正来(2008)认为研究中国过程中的"唯学科化"会肢解中国,反对"学科导向"研究9.2009年媒体对中国模式对非洲的影响有所关注,也有学者写有"中国模式的非洲效应的文章"(陶文昭,2008)10."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中国提倡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中国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极大的影响世界(胡伟,2009)1.魏嵬论古代中国经济和科技从领先到衰落的制度因素——关于"李约瑟之谜"的思考[期刊论文]-现代经济信息2010(1)2.江晓原.刘兵李约瑟在今天的意义与局限——从《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说起[期刊论文]-中国图书评论2009(8)3.魏志奇.张丽霞.Wei Zhiqi.Zhang Lixia从中西比较中看"李约瑟问题"[期刊论文]-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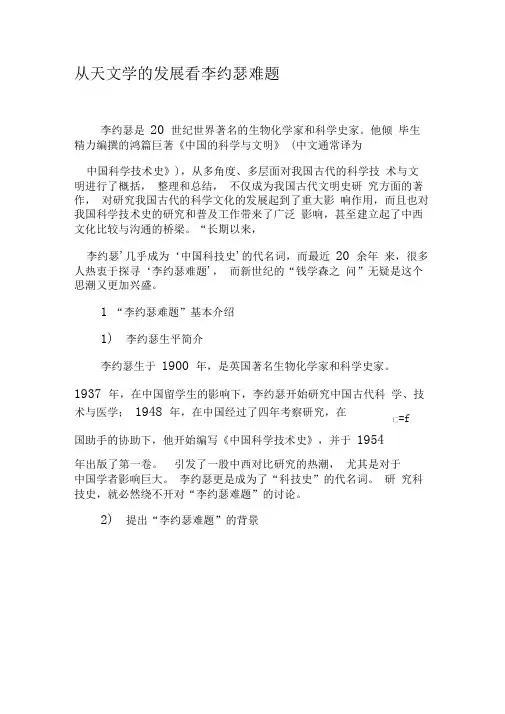
从天文学的发展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是 20 世纪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
他倾 毕生精力编撰的鸿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中文通常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我国古代的科学技 术与文明进行了概括, 整理和总结, 不仅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史研 究方面的著作, 对研究我国古代的科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 响作用,而且也对我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带来了广泛 影响,甚至建立起了中西文化比较与沟通的桥梁。
“长期以来,李约瑟'几乎成为‘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 20 余年 来,很多人热衷于探寻‘李约瑟难题', 而新世纪的“钱学森之 问”无疑是这个思潮又更加兴盛。
1 “李约瑟难题”基本介绍1) 李约瑟生平简介李约瑟生于 1900 年,是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
1937 年,在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李约瑟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 学、技术与医学; 1948 年,在中国经过了四年考察研究,在 国助手的协助下,他开始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于 1954中国学者影响巨大。
李约瑟更是成为了“科技史”的代名词。
研 究科技史,就必然绕不开对“李约瑟难题”的讨论。
2) 提出“李约瑟难题”的背景匚=f 年出版了第一卷。
引发了一股中西对比研究的热潮, 尤其是对于20世纪30 年代末期,李约瑟开始接触中国学者。
在不断地了解和研究的过程中,李约瑟发现:中国远在一千多年前就有着众多的科技成果与文化习俗,而且中国人大多数也都聪明勤劳,但是,近代的工业革命并没有从中国产生。
这引发了李约瑟的思考。
1939年,李约瑟被英国皇家科学院派为代表,带着援华使命开始到中国工作,工作中收集和查阅的众多有关中国科技史与文化史的资料,使他获得了实地考察中国及其历史文化的好时机。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研究,他提出著名的了“李约瑟难题”。
3)何谓“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由提出到精准的把握其内在含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李约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著作之中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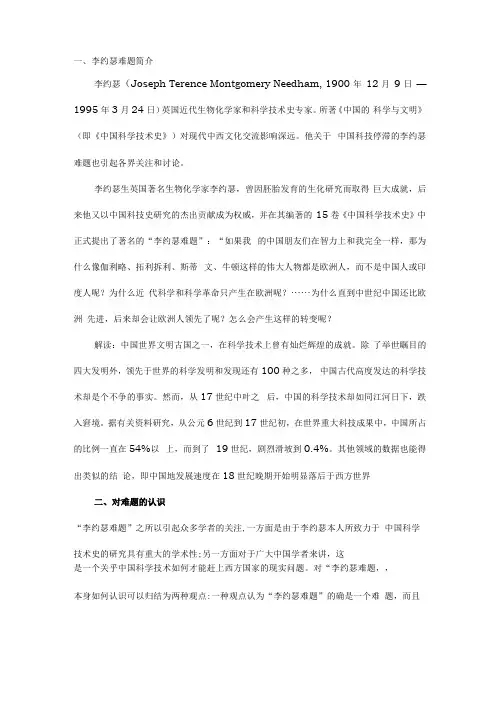
一、李约瑟难题简介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 年12 月9 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
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难题也引起各界关注和讨论。
李约瑟生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领先了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解读:中国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科学技术上曾有灿烂辉煌的成就。
除了举世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研究,从公元6 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烈滑坡到0.4%。
其他领域的数据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中国地发展速度在18世纪晚期开始明显落后于西方世界二、对难题的认识“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李约瑟本人所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性;另一方面对于广大中国学者来讲,这是一个关乎中国科学技术如何才能赶上西方国家的现实问题。
对“李约瑟难题,,本身如何认识可以归结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约瑟难题”的确是一个难题,而且有着多种多样的解答。
比如,黄生财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墨家、名家、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中国古代思想入手,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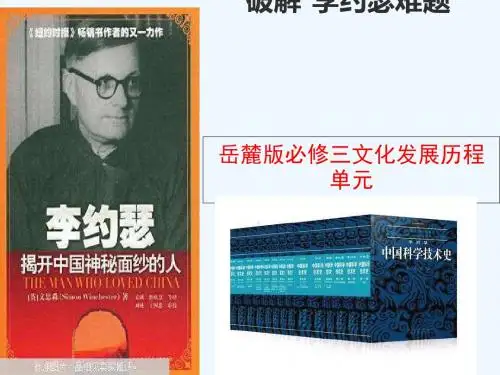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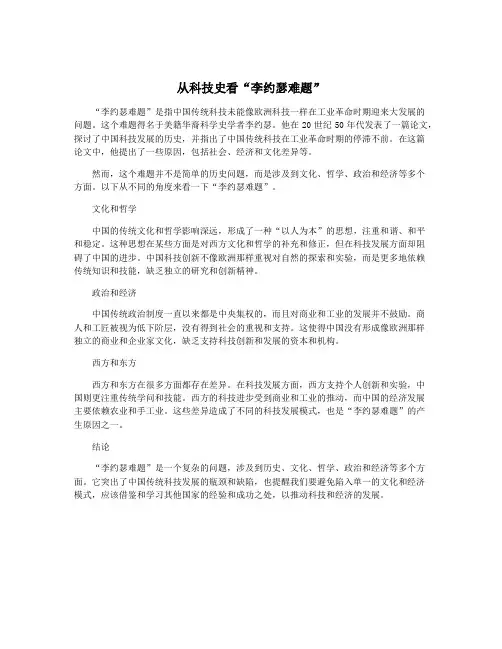
从科技史看“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传统科技未能像欧洲科技一样在工业革命时期迎来大发展的问题。
这个难题得名于美籍华裔科学史学者李约瑟。
他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并指出了中国传统科技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停滞不前。
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些原因,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异等。
然而,这个难题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哲学、政治和经济等多个方面。
以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李约瑟难题”。
文化和哲学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影响深远,形成了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注重和谐、和平和稳定。
这种思想在某些方面是对西方文化和哲学的补充和修正,但在科技发展方面却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中国科技创新不像欧洲那样重视对自然的探索和实验,而是更多地依赖传统知识和技能,缺乏独立的研究和创新精神。
政治和经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一直以来都是中央集权的,而且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并不鼓励。
商人和工匠被视为低下阶层,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和支持。
这使得中国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独立的商业和企业家文化,缺乏支持科技创新和发展的资本和机构。
西方和东方西方和东方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
在科技发展方面,西方支持个人创新和实验,中国则更注重传统学问和技能。
西方的科技进步受到商业和工业的推动,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农业和手工业。
这些差异造成了不同的科技发展模式,也是“李约瑟难题”的产生原因之一。
结论“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历史、文化、哲学、政治和经济等多个方面。
它突出了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瓶颈和缺陷,也提醒我们要避免陷入单一的文化和经济模式,应该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成功之处,以推动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论“李约瑟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作者:薛羿冰来源:《速读·中旬》2020年第02期上世纪,“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便有大量的中外学者试图寻找问题的答案。
对于“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这一谜题,尽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追本溯源,可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答案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因此,回答“李约瑟难题”便成了一个“浩大的工程”。
于是,当诸多学者开始思考“为什么”的时候,政治、经济、文化、个人、地理环境等各种因素使该问题变的更加难以捉摸。
对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无科学说”“伪问题说”“有毛病说”“无意义说”“逻辑矛盾说”众说纷纭。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对于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科技文化成就,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特别是对于反思中国人民为何缺乏创新意识,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成果为何缺乏原创性以及未来应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从文化多样性角度给“西方中心主义”毁灭性的一击在李约瑟眼中,所有的非西方文明不再被视为“落后”的。
当西方社会、西方科学史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普遍认为,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而非西方世界则没有对科学的诞生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的时候,李约瑟强烈反对这一看法,并且,李约瑟提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在很长的历史期间内还领先于西方,一点也不比西方逊色。
中国独立的书写技术、气势恢弘的水利工程、技艺精美的陶瓷工业、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以及有着明确记载的天文学、占星术、数学、气象学、绘图学、医学研究等,无不向世界展现着古代中国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
李约瑟穷尽后半生的精力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一方面公正的评价了中国文明对现代科学的贡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另一方面也纠正了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形成的偏见,打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
《“李约瑟问题”辨析》之澄清对陈方正教授答复之答复作者:陈晓平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14年第01期拙文《“李约瑟问题”辨析——兼评“陈方正-余英时方案”》(简称《辨析》)发表于本刊2012年第5期,陈方正教授的文章《对“李约瑟问题辨析”的答复》(简称《答复》)发表于本刊2013年第2期。
这两篇文章都主要涉及陈方正教授的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简称《继叛》)。
现就《答复》给以必要的回应。
一、关于“陈方正-余英时方案”的称谓《答复》说:“…辨析‟文将余英时教授为敝著所写序文中的意见与该书混为一谈,称之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又在多处将我们并称,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与错误。
例如,该文说…陈方正和余英时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比作象棋棋艺和围棋棋艺之间的关系,进而把李约瑟问题彻底消解‟,就完全错误,因为《继叛》书中从来没有用过两种棋艺作比喻,更绝对没有以之为理据来…消解‟李约瑟问题。
事实上,余先生虽然对敝著多所谬许,但我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陈方正2013,页73]为了让读者识别我的这种“完全错误”,在此转述《辨析》中引入“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这一称谓时所作的说明:“陈方正教授在其力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消解方案,余英时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加强了这一方案,我们不妨称之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
”[陈晓平2012,页79]显然,我没有说余英时方案和陈方正方案完全一样,而是说前者“加强”了后者。
不过,我认为余英时方案和陈方正方案的基本精神和思路是一致的,为了讨论方便,将二者并称为“陈方正一余英时方案”。
如果陈方正教授对我的这种“并称”不满,我觉得他应该在《继叛》出版之前就对余英时教授提出,即对他的棋艺比喻直接提出批评;《继叛》作者有必要就该书的核心观点与写序的人进行交流和讨论,特别是当写序者的观点与该书的核心观点相异的时候。
在我心目中,余英时教授是一位非常严肃和深刻的学者,在他为一本书写序的时候,一定是本着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的。
“李约瑟难题”思想研究作者:刘震来源:《农村农业农民·B版》2020年第04期摘要:在中西科学技术史上,“李约瑟难题”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因此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李约瑟从地理因素分析了中国没有发展近代科学的原因。
从历史唯物主义着手,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解析,社会存在会对社会意识产生影响,正是因为中国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的影响,社会存在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与此同时,社会意识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各项因素也对中国近代科学产生了束缚。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生产方式;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中国历史文化久远,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早在3~13世纪时期,我国在很多领域就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尤其是中国四大发明的问世,不仅促进了我国的发展,也对西方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早在古代社会,我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的科技发展中心。
然而,自从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后,科技发展速度飞快,这时中国的思想观念落后,科技没有任何突破,始终停滞不前,直至今日,这种情况才有所缓解,我国的经济与科技才开始逐渐复苏。
基于此,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撰写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曾一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一、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代表性观点“李约瑟难题”是在1948年提出的,自此之后,学术领域对此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许多专家学者均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李约瑟本人对问题的解答基于“李约瑟难题”考虑,学者李约瑟对此提出了很多见解与看法。
他在进行研究时,从地理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在他撰写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为:“欧洲就如同是一个群岛,四周被海域包围,包括波罗的海、爱尔兰海峡、北海、爱琴海、地中海以及黑海,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外,所面向的是大西洋,以上诸多因素均对船队活动与海上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约瑟问题”辨析兼评“陈方正-余英时方案”陈晓平【期刊名称】《科学文化评论》【年(卷),期】2012(009)005【摘要】'Needham Problem' is analyzed in different senses. As to 'Strong Needham Problem' , I endorse 'Chen Fongching-Yu Yingshih Solution' , which is to eliminate it; as to 'Weak Needham Problem' and 'Ren Hongjun Problem' , I think that they should be retained.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broad concept of science' and 'the narrow concept of science' , I put forward 'Ren Hongjun- Needham Problem' . Finally I discuss the problem of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scientificrevolution' .%将“李约瑟问题”从不同的意义上进行分析,对于“强李约瑟问题”本文赞同“陈方正-余英时方案”,将其消解掉。
对于“弱李约瑟问题”和“任鸿隽问题”则加以保留。
在区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任鸿隽-李约瑟问题”。
此外,明确了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数学化和实验性,据此对“第一次科学革命”之时段的问题进行讨论。
【总页数】15页(P75-89)【作者】陈晓平【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301【相关文献】1.中国总体基尼系数测定问题--兼评"陈宗胜-李实论战"并与陈宗胜教授商榷 [J], 周文兴2.中西语境下的民族问题辨析——兼评马戎的《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J], 聂孟强3.《“李约瑟问题”辨析》之澄清对陈方正教授答复之答复 [J], 陈晓平4.也谈社会主义与国家所有制的关系问题──兼评陈湘舸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J], 林锦森5.雇主责任制度若干问题辨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 [J], 魏树发;江钦辉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李约瑟问题”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
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
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
余英时我的老朋友陈方正兄费了多年功夫,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早在撰写期间方正便已约我为此书写序。
虽然我是一个十足的科学门外汉(“ignoramus”),当时却一诺无辞,大胆地接受了这任务。
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更因为本书的主旨涉及了我所关怀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
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作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
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力,却也颇有切磋之乐。
但不巧得很,现在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
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能陈述两点,以为本书读者之助。
第一,阐释本书的性质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于孟子“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则,对本书作者作简要的介绍。
首先,我必须郑重指出,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
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
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此。
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
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另一重大问题的答复:“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正如本书“导言”中所显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的一体之两面:“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很显然,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
在“导言”与“总结”两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及其他相关论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现在让我以简化的方式说一说本书作者与李约瑟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表示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问题当然要从李约瑟开始。
李约瑟至迟在1943年访华时便已坚信: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
因此他拒绝接受早期中国学人的看法,即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1975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
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
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
”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先后纠合了多位专家,终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
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不朽盛业。
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册的巨制将中国史上科技发明的辉煌纪录和盘托出,证实了他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
但是李约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基本事实,却亦未能对自己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他在全书最后一册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中曾试作种种解答,然而往往语焉不详,以致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甚信服其说,而评之为“见树不见林”。
这里让我顺便提一下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的看法。
他最近评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结”,即第七卷第二分册,曾对“李约瑟问题”表示过下列意见: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如果我的了解不错,那么本书作者的看法和席文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前面指出本书的最大贡献便在于交代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一根本问题,而且交代得原原本本,系统分明。
可见本书恰恰符合了席文的最高期待。
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李约瑟有分歧,与席文却不谋而合呢?我认为关键便在于彼此对“现代科学”的概念有不同理解。
早在1974年李约瑟便告诉我们:他把“现代科学”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
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
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the same path),今天已汇聚在“现代科学”之中。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席文的见解和他不同,判定中、西“科学”各自“分途”(separate paths)进行。
尽管如此,李约瑟还是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
可知他心中的“现代科学”是普世性的,与民族或文化的独特背景没有很大关系。
本书作者则不但同样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各自分途发展,而且还更进一步,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
西方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如作者所云,它恰恰是“西方文明大传统最核心的部分”。
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作者将西方科学传统的特征概括成以下两项: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是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
第二、它虽然可以清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吸收伊斯兰科学,到十六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发展出来的。
这两点概括都建立在坚强的史实之上,而作者识断之精也由此可见。
作者对本书内容的取舍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
他说:“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
”我必须郑重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放过。
本书胜义纷披,读者随处可自得之。
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就西方数理科学的问题稍稍引申作者的论点,然后回到“李约瑟问题”作一结束。
本书在“总结”第一段说,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实有画龙点睛之妙。
所谓“一个传统”即指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同一研究传统之内:“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飞跃所导致,但在性质上仍与古希腊科学同条共贯。
所谓“两次革命”,指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然界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便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两个部门。
通常我们用“科学革命”一词来指称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但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则在古代希腊,即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奥秘。
其中细节见本书第四章,这里毋须赘言。
我认为作者这一提示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正是西方科学传统的灵魂所在。
而且作者这一说法决不是向壁虚构,前人也早有见及者,不过没有像作者表达得这样一针见血罢了。
例如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便特别提出“自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the Pythagorian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并阐明其何以获得惊人的成功。
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所作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mathematicization”)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
甚至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经济学因为数学化比较成功,才被承认具有较高的“科学的身份”,而非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能企及。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
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已涉及此点。
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
本书作者解释这两句话说: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
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但数学原理则似少有问津者。
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其义全阙”的感叹。
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对此便可了无疑义。
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如作者所云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
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1809-1874)与李善兰(1810-1882)两人当可为其代表。
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
冯氏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
李氏则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其余部分(卷七至十五),于1858年以《续几何原本》的书名刊行;此外还有多种有关数理的译著问世,并已开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定名为《奈端数理》),可惜未能终卷。
由于他的造诣最高,为西方在华专家所特别推重,所以清廷设同文馆,聘他为数学总教席,在任共十三年(1869-1882)。
李善兰(字壬叔)是一位数学天才,他的朋友王韬(1823-1897)记他的话,说: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
这几句话证明他对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已有透辟的认识了。
但达到这种理解并非易事。
王韬虽自称在“西馆十年,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但仍不能接受李氏对“算学”的评价;囿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他竟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