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 格式:doc
- 大小:82.00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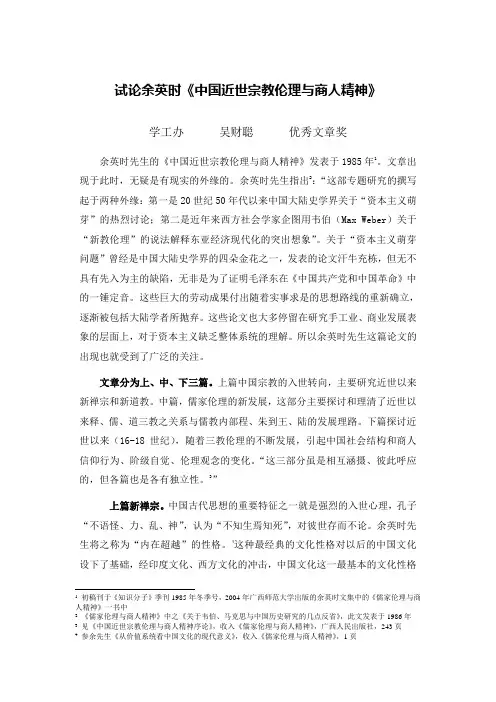
试论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学工办吴财聪优秀文章奖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发表于1985年1。
文章出现于此时,无疑是有现实的外缘的。
余英时先生指出2:“这部专题研究的撰写起于两种外缘:第一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热烈讨论;第二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学家企图用韦伯(Max Weber)关于“新教伦理”的说法解释东亚经济现代化的突出想象”。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曾经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四朵金花之一,发表的论文汗牛充栋,但无不具有先入为主的缺陷,无非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一锤定音。
这些巨大的劳动成果付出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逐渐被包括大陆学者所抛弃。
这些论文也大多停留在研究手工业、商业发展表象的层面上,对于资本主义缺乏整体系统的理解。
所以余英时先生这篇论文的出现也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文章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主要研究近世以来新禅宗和新道教。
中篇,儒家伦理的新发展,这部分主要探讨和理清了近世以来释、儒、道三教之关系与儒教内部程、朱到王、陆的发展理路。
下篇探讨近世以来(16-18世纪),随着三教伦理的不断发展,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和商人信仰行为、阶级自觉、伦理观念的变化。
“这三部分虽是相互涵摄、彼此呼应的,但各篇也是各有独立性。
3”上篇新禅宗。
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强烈的入世心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不知生焉知死”,对彼世存而不论。
余英时先生将之称为“内在超越”的性格。
4这种最经典的文化性格对以后的中国文化设下了基础,经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这一最基本的文化性格1初稿刊于《知识分子》季刊1985年冬季号,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余英时文集中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2《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之《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此文发表于1986年3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论》,收入《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人民出版社,243页4参余先生《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收入《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1页核心基本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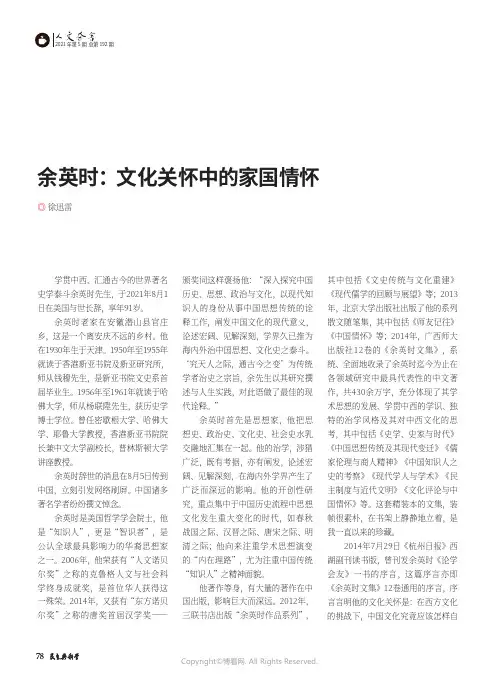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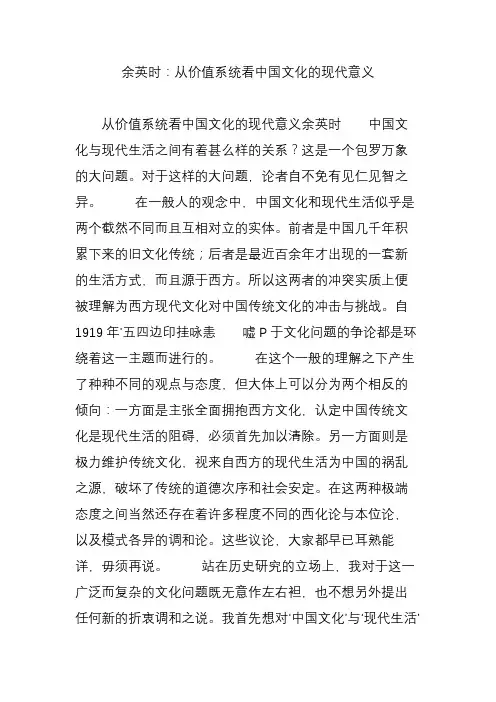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余英时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有着甚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问题。
对于这样的大问题,论者自不免有见仁见智之异。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中国文化和现代生活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而且互相对立的实体。
前者是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旧文化传统;后者是最近百余年才出现的一套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源于西方。
所以这两者的冲突实质上便被理解为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挑战。
自1919年‘五四边印挂咏恚嘘P于文化问题的争论都是环绕着这一主题而进行的。
在这个一般的理解之下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观点与态度,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相反的倾向:一方面是主张全面拥抱西方文化,认定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阻碍,必须首先加以清除。
另一方面则是极力维护传统文化,视来自西方的现代生活为中国的祸乱之源,破坏了传统的道德次序和社会安定。
在这两种极端态度之间当然还存在着许多程度不同的西化论与本位论,以及模式各异的调和论。
这些议论,大家都早已耳熟能详,毋须再说。
站在历史研究的立场上,我对于这一广泛而复杂的文化问题既无意作左右袒,也不想另外提出任何新的折衷调和之说。
我首先想对‘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两个概念进行一种客观的历史分析。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自然不能不根据某种概念性的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并非我个人主观愿望的投射,而是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
在综合判断方面,我当然也不能完全避免个人的主观,不过这种判断仍然是尽量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
必须说明,文化观察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出发,我所采取的自然不是唯一的角度,我所提出的看法更不足以称为最后定论。
我只能说这些看法是我个人经过郑重考虑而得到的,也许可以提供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参考。
文化一词有广义和狭义的种种用法。
以本文而言,则所谓中国文化是取其最广泛的涵义,所以政治、社会、经济、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无不涉及。
以近代学者关于‘文化’的讨论来说,头绪尤其纷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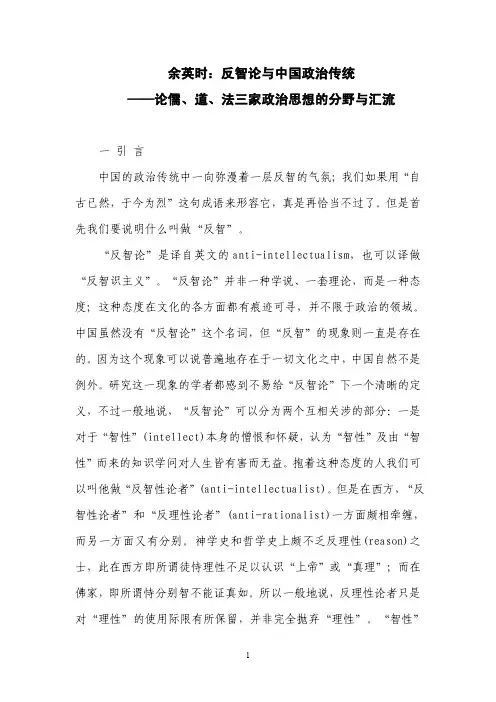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一引言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
“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
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
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
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
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
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
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
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
“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
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
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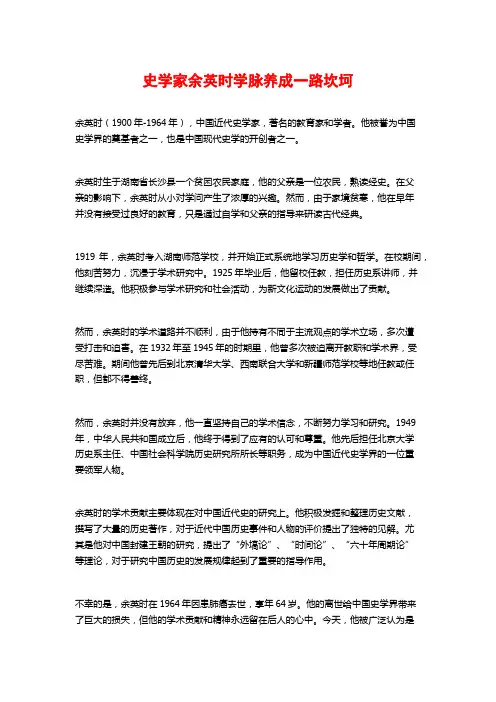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余英时(1900年-1964年),中国近代史学家,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他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余英时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民,熟读经史。
在父亲的影响下,余英时从小对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由于家境贫寒,他在早年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通过自学和父亲的指导来研读古代经典。
1919年,余英时考入湖南师范学校,并开始正式系统地学习历史学和哲学。
在校期间,他刻苦努力,沉浸于学术研究中。
192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担任历史系讲师,并继续深造。
他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余英时的学术道路并不顺利,由于他持有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学术立场,多次遭受打击和迫害。
在1932年至1945年的时期里,他曾多次被迫离开教职和学术界,受尽苦难。
期间他曾先后到北京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新疆师范学校等地任教或任职,但都不得善终。
然而,余英时并没有放弃,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不断努力学习和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位重要领军人物。
余英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
他积极发掘和整理历史文献,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尤其是他对中国封建王朝的研究,提出了“外塙论”、“时间论”、“六十年周期论”等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不幸的是,余英时在1964年因患肺癌去世,享年64岁。
他的离世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他的学术贡献和精神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
今天,他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位伟大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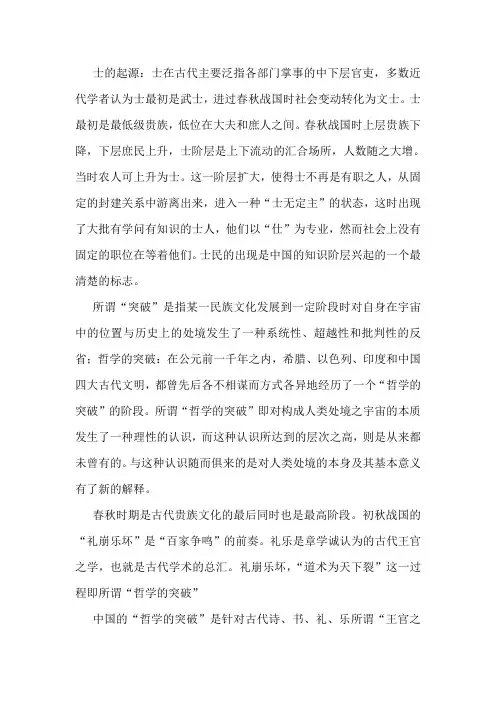
士的起源: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
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低位在大夫和庶人之间。
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
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哲学的突破: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
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
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
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
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学术的总汇。
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所谓“哲学的突破”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
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
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
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
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
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
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
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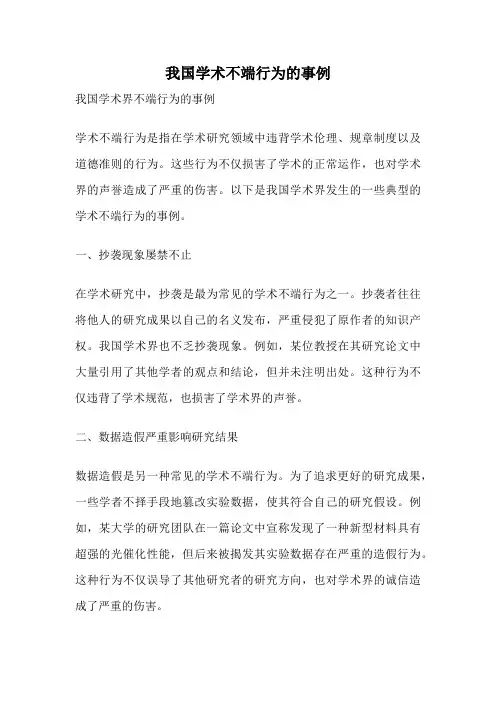
我国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例我国学术界不端行为的事例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违背学术伦理、规章制度以及道德准则的行为。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学术的正常运作,也对学术界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以下是我国学术界发生的一些典型的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例。
一、抄袭现象屡禁不止在学术研究中,抄袭是最为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之一。
抄袭者往往将他人的研究成果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严重侵犯了原作者的知识产权。
我国学术界也不乏抄袭现象。
例如,某位教授在其研究论文中大量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和结论,但并未注明出处。
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学术规范,也损害了学术界的声誉。
二、数据造假严重影响研究结果数据造假是另一种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
为了追求更好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不择手段地篡改实验数据,使其符合自己的研究假设。
例如,某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一篇论文中宣称发现了一种新型材料具有超强的光催化性能,但后来被揭发其实验数据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误导了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也对学术界的诚信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三、论文买卖现象频发论文买卖是学术不端行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一些学者为了追求学术声誉或者晋升职位,会购买他人的论文,以自己的名义发表。
例如,某位教授在个人的学术生涯中发表了大量的高水平论文,但后来被揭发这些论文实际上是通过购买他人的研究成果得到的。
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学术的公正性,也扭曲了学术评价体系。
四、学术评审中的不正当行为学术评审是学术界中的一项重要程序,用于评估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学术价值。
然而,一些学者在学术评审中存在不正当行为,例如,利用个人关系或金钱交易来干预评审结果。
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学术评审的公正性,也对学术界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以上只是我国学术界不端行为的一些典型事例,实际上还存在许多其他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
为了避免这些行为的发生,学术界需要加强对学术伦理的教育和管理,建立健全的学术规范和道德准则。
同时,还需要从制度上加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加大对不端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学术界的正常秩序和良好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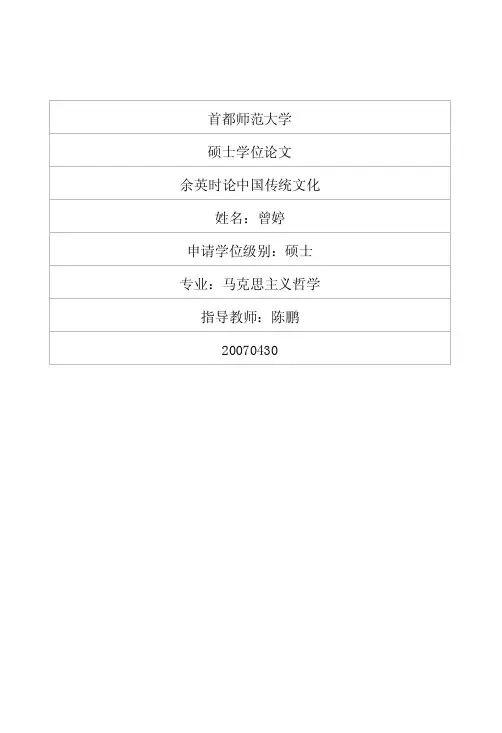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余英时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
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分析:1、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倾性特征;2、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价值;3、中国文化的重建。
余英时把儒家文化价值系统的根本特征概括为“内在而超越”。
在他看来,弄清价值的来源问题以及价值世界和实际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理解一个文化价值系统之特殊意义的关键。
而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倾性特征会在思想方式、制度形式上有相应的具体表现。
在余英时看来,正是这种内倾性的文化特征是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发展出民主、科学的重要原因。
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倾性特征有他特有的人文价值,具体来说,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价值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方面来看:一、强调人的价值、尊严;二、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没有阻碍:三、“依自不依他”的人生态度;四、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五、万物和谐;六、君子人格。
余英时认为与追求“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相比,追求“内在超越”的中国文化更容纳此世条件和此世努力基础上的希望和理想。
当然,能否做到超越,还要看个体价值自觉的努力方向。
儒家相信,通过个体的自身努力,从有限的存在之中即有可能获得意义的开显与境界的提升,最终达到“至善”的圆满境界。
根据以上的论点,余从其独特的角度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的重建论题,他既不同于牟宗三的“中国文化的主位性”、杜维明的“文化中国”,又不同于李泽厚为代表的“西体中用”。
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事实上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换的问题。
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实质是我们怎样能通过自觉的努力以使文化变迁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
余英时认为中国必须重建一套新的价值系统,而这一价值系统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人文基础之上并尽量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新成分。
传统儒家价值系统的现代转化仍然中国文化重建的核心内容。
余英时认为,在制度化儒家崩溃之后,儒家已不可能奢望再去“安排人类生活的一切秩序”,而是要从民间出发,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发展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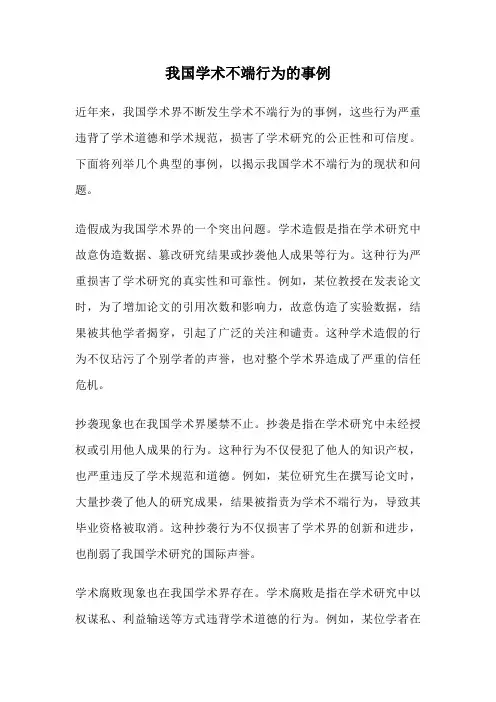
我国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例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不断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例,这些行为严重违背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损害了学术研究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下面将列举几个典型的事例,以揭示我国学术不端行为的现状和问题。
造假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突出问题。
学术造假是指在学术研究中故意伪造数据、篡改研究结果或抄袭他人成果等行为。
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例如,某位教授在发表论文时,为了增加论文的引用次数和影响力,故意伪造了实验数据,结果被其他学者揭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谴责。
这种学术造假的行为不仅玷污了个别学者的声誉,也对整个学术界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抄袭现象也在我国学术界屡禁不止。
抄袭是指在学术研究中未经授权或引用他人成果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也严重违反了学术规范和道德。
例如,某位研究生在撰写论文时,大量抄袭了他人的研究成果,结果被指责为学术不端行为,导致其毕业资格被取消。
这种抄袭行为不仅损害了学术界的创新和进步,也削弱了我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声誉。
学术腐败现象也在我国学术界存在。
学术腐败是指在学术研究中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方式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
例如,某位学者在评审学术论文时,利用职权向他人索取贿赂,以换取论文发表机会。
这种学术腐败行为严重破坏了学术研究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损害了学术界的声誉和形象。
学术不端行为还包括学术恶意竞争、论文代写、论文代表性不符等。
这些行为都严重违反了学术规范和道德,损害了学术研究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面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和规范学术行为。
首先,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增强学者的学术诚信意识和责任感。
其次,建立健全学术评价体系,减少对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的过度追求,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第三,加强学术监督和惩处机制,对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形成有力的震慑。
最后,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提高学者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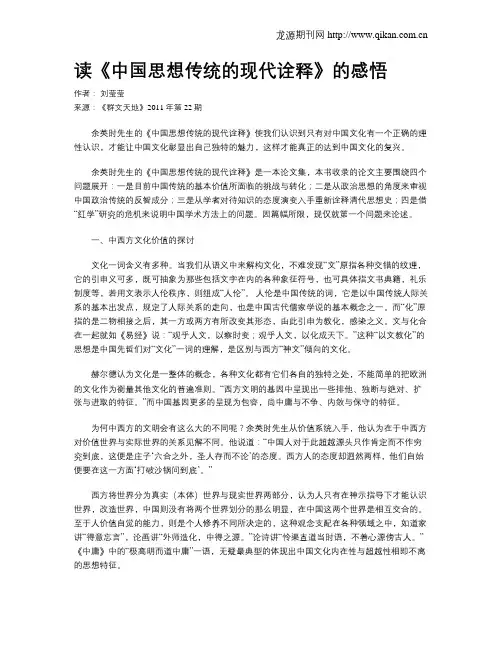
读《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的感悟作者:刘莹莹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22期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正确的理性认识,才能让中国文化彰显出自己独特的魅力,这样才能真正的达到中国文化的复兴。
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是一本论文集,本书收录的论文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是目前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所面临的挑战与转化;二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政治传统的反智成分;三是从学者对待知识的态度演变入手重新诠释清代思想史;四是借“红学”研究的危机来说明中国学术方法上的问题。
因篇幅所限,现仅就第一个问题来论述。
一、中西方文化价值的探讨文化一词含义有多种。
当我们从语义中来解构文化,不难发现“文”原指各种交错的纹理,它的引申义可多,既可抽象为那些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也可具体指文书典籍,礼乐制度等,若用文表示人伦秩序,则组成“人伦”。
人伦是中国传统的词,它是以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规定了人际关系的走向,也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基本概念之一。
而“化”原指的是二物相接之后,其一方或两方有所改变其形态,由此引申为教化,感染之义。
文与化合在一起就如《易经》说:“观乎人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种“以文教化”的思想是中国先哲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是区别与西方“神文”倾向的文化。
赫尔德认为文化是一整体的概念,各种文化都有它们各自的独特之处,不能简单的把欧洲的文化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准则。
“西方文明的基因中呈现出一些排他、独断与绝对、扩张与进取的特征。
”而中国基因更多的呈现为包容,尚中庸与不争、内敛与保守的特征。
为何中西方的文明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余英时先生从价值系统入手,他认为在于中西方对价值世界与实际世界的关系见解不同。
他说道:“中国人对于此超越源头只作肯定而不作穷究到底,这便是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态度。
西方人的态度却迥然两样,他们自始便要在这一方面‘打破沙锅问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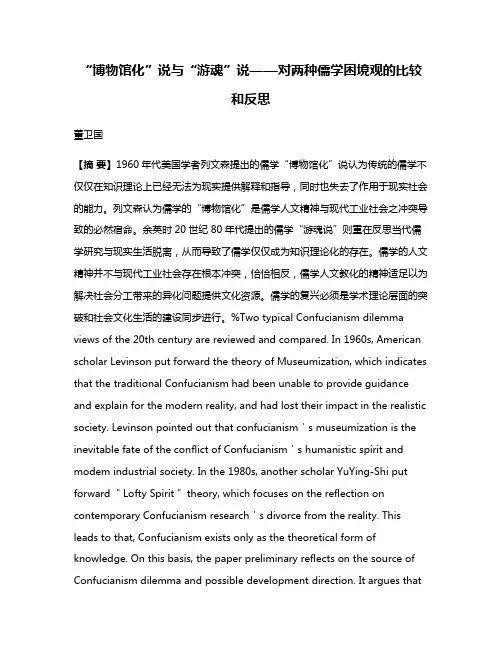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董卫国【摘要】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
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
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
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
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
%Two typical Confucianism dilemma views of the 20th century are reviewed and compared. In 1960s, American scholar Levinson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Museumiz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had been unable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explain for the modern reality, and had lost their impact in the realistic society. Levinson pointed out that confucianism's museum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fate of the conflict of Confucianism's humanistic spirit and modem 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1980s, another scholar YuYing-Shi put forward "Lofty Spirit" theory, which focuses on the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research's divorce from the reality. This leads to that, Confucianism exists only as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knowledg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eliminary reflects on the source of Confucianism dilemma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t argues that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Confucianism does not conflict with modem industrial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it is suitable to provide culture resources for solving the alienation problem brought by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Renaissance of Confucianism depends on both the academic research's breakthrough in Confucianism research as well as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construction.【期刊名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33)001【总页数】6页(P64-69)【关键词】儒学;现代困境;“博物馆化”说;“游魂”说;复兴【作者】董卫国【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碰撞以来,作为传统文化骨干的儒学逐渐陷入困境,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1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陆间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全书扫瞄一遍,其中很多地方不乏是跳动式的阅读,即使这样,自己从中也得到很多启发。
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索。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很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
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整个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扫瞄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当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好像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同学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同学是否应当得到爱护,由于他高校的专业好像与他的爱好并不相全都。
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索,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究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
这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应当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学问分子,根据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学问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全部的人都是学问分子,但并不是全部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学问分子的作用。
那本人也就忝列为学问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学问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推断应当是正确的。
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日所谓的“学问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学问分子的作用)。
依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学问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需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需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因此,有人指出,“学问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又为何,普及度又有多少)“学问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消失的时代也许不能早于十八世纪。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
史学家余英时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与学术道路的确曲折艰辛。
一开始,余英时的学术之路并不顺利。
他在研究生期间曾发表了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遭到了学校的指责。
由于政治原因,他的研究生学位也被取消,这给他的学术生
涯造成了困难。
然而,余英时并没有放弃他的学术梦想。
他积极参与人民解放战争后的教育改革,先
后担任了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多所学校的教师。
他的研究领域从中国近现代史
拓展到世界历史,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但余英时仍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在那个时期,他
被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标签,被迫离开了大学教职。
他在艰苦的环境下,靠
着自己的努力坚持研究,并在文革结束后迎来了学术复兴的机会。
余英时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被视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
他
不仅做出了学术贡献,还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尽管
他的学术之路充满坎坷,但他的坚持和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定位与诠释孙家洲高宏达《光明日报》(2011年03月31日11版)在梳理我国传统学术资源时,对若干沿用日久的学术概念,学人们有不同意见。
但学术概念的定位与诠释,对于学术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对其展开讨论,当然有其必要。
其中,关于“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不同评价,就值得我们关注。
刘梦溪、余英时两位先生有一篇对话,标题很醒目:《“经世致用”的负面影响》。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对话者对于传统学术在当下的命运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自有表述周备的风范,刘梦溪先生则对“经世致用”的负面作用,加以态度鲜明的批评:“这种传统过于看重学术的目的性,把学术只作为一种手段,不知道学术本身也是目的。
”他还指出,“经世致用思想也有负面影响,它也是造成中国学术不能独立的一个原因。
”(参见搜狐网《读书·明报·大家大讲堂》、《和讯网》《读书·明报月刊》文丛的同题文章)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同观点的讨论,理应继续展开。
“经世致用”的评价,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学术问题,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层面展开,这恐怕不是几篇讨论文章就可以达成共识的;但“经世致用”在传统学术史的地位,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应该首先展开讨论。
关于“经世致用”的基本诠释,学界往往以“学术思潮”或“学风”来做概括。
如《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这样的定义,如果从突出明清之际学林风尚的历史性转折而言,无疑是正确的。
在“明清易代”的现实冲击之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学者,力倡“经世致用”之学,使之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这批关注时政的大学者,在总结明朝灭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痛批明代儒林的学风空疏不实,对国家命运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如此强烈的反思意识,把学林风尚与国家兴亡直接对应的担当意识,确实是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特点与亮点。
但是,以“明清之际”与“学术思潮”两个关键词来界定“经世致用”,显然是不完备的定义。
余英时:我为何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口述/余英时记录/何俊6月20日,余英时教授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并就其治学经历发表演讲,凤凰网大学问摘编相关内容,与读者分享。
中国人重视传统,学术传承,往往以“守先待后”四字加以概括。
学问是公共的,不是一个人的私有物。
所以“守”不是自己老师一人之“先”,而是整个学术传统。
“道”非一人所得之私,若专以老师一人为主,那便流为“门户”之见了。
“待后”也不是专指自己的弟子或传人,而应是所有的后来者,否则又是立“门户”了。
另外,我们自己研究得来的东西也当包括在“先”之内。
“道问学”虽早就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只有在清代,对“士”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则是更进一步的现代转化;传统的“士”也因此而转变为现代“知识人”。
我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是“儒家”,是因为秦、汉以下,所谓“儒家”一直在随着时代而变动,而这些变动又是由于吸收了其他各学派的思想成分而来。
我一向以为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大运动,决不是“富国强兵”这一急功近利的目标所能尽。
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实用方面之外,学术思想则是现代化进程中更为根本的部分。
为什么我不认同所谓现代“新儒家”?其实理由很简单:首先,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自始便接受了多元价值的立场,无法信仰任何一家一派的理论系统,特别是宗教的或哲学的系统。
其次,现代“新儒家”是从哲学,尤其是日耳曼哲学,康德、黑格尔等的特殊观点来重新诠释儒学,而我则是从史学观点研究儒学在中国史各阶段的实际功能和变迁。
中国文化价值,整体地看,自成一独特系统,但从历史角度作观察则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不过虽变而不离其宗罢了。
这就是说,中国价值系统“常”中有“变”,“变”中也有“常”。
儒家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精神资源,关键在我们能不能做出创造性的运用。
我不敢妄测儒家的现代命运,不过从历史上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的新趋向大致是退出公领域而转移到私领域。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
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
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
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
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
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传统中国的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
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
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
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
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
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
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
这一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
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本文是作者与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李宗陶:在短短8页《我走过的路》中,看到安徽潜山官庄乡的自然风貌,您在那里度过了整整9年的少年时光。
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治思想史和文化史起到怎样的作用?余英时:1937—1946年我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生活,乡间既没有现代学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训练的国文师资,所以我在乡9年,无论是私塾或学校教育都是断断续续的。
私塾先后不过两年左右,此外在舒城县晓天镇我也读过不足一年的第七临时中学,后来因伤寒病而回乡了。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国学的基础。
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
惟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不过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
《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
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
唐诗、宋词我大概十二三岁便接触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
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言、七言绝句。
1945—1946年,我在邻县桐城县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
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是有才气的人,能诗、善书法。
他是清初张廷玉、张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但此时也相当衰落了。
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捡到一些诗文的知识。
我在一旁听到改诗经过,很受启发。
在桐城一年,我的国文比较以前进步了。
但9年的诗文背景也不过如此。
最大的收获是会写文言文和旧体诗,于新文学毫无所知,国文常识仍很欠缺。
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
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
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
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
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
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
“成见”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但并不根深蒂固,可以随时改变。
李宗陶:在《现代学人与学术》中,您对恩师钱穆、杨联,前辈陈寅恪以及胡适先生等都做了大块文章,对另一些学人,如顾颉刚、洪业、严耕望、张光直、费正清等,着墨虽不如前几位那么多,也同样精彩。
这里想请教先生对另几位——陈垣、吕思勉、董作宾、黄仁宇的看法。
此外,您对翦伯赞和郭沫若二位的学术如何评价?余英时:董先生是甲骨文学大师,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没有资格讨论他的专门绝业。
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写成的,他比我年长,后来是朋友关系,我不便写他。
但是我要指出,他中年才读大学,发愤治中国史,用功之勤极为少见;晚年写了不少通论性的书,表现出他的史识,成一家之言。
他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位“奇侠”式的学者。
著名学者余英时关于陈垣和吕思勉两位大家,我是读他们的著作长大的,受益之多,不在任何前辈(如陈寅恪)之下。
援庵(陈垣,字援庵)先生是我父亲(协中公)在燕京大学的导师,先父后来转治西洋史,编写了一部《西洋通史》,没有继续中国史的研究,但对援庵先生始终敬礼。
我受先父的启发,曾遍读援庵先生的专著与论文。
在我的专著中引用他的论点很多。
吕诚之先生是先师钱先生的中学老师,他的几部断代史和《燕石札记》也是我在研究和教学中经常翻阅的参考书。
不过我没有适当的机缘写到这两位“太老师”而已。
对翦伯赞、郭沫若两人的学术评价,我只能简单地说一两句话。
我知道翦先生在“文革”之前是中国史学界的正统代言人,他讲中国史的分期具有代表性,从《历史哲学教程》(早期)、《中国史》(秦汉篇)到论文集(晚期)都是如此。
其中心系统不是从中国史的内部整理出来的,而是借自西方的现成模式。
他在史学上的地位如何,恐怕要看后人是不是能从他的著作中继续得到启发。
我不敢轻下断语,只有让时间来考验。
郭沫若先生则不一样。
他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
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
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几部书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
他虽然也遵从“一家之言”。
却与套用公式有别。
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
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
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上述二陈(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
治学有成的学者可以参考他上述三书,但初学则不宜由此类作品入手。
李宗陶: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中,我们看到了您对郭沫若先生抄袭嫌疑的揭露,不知您对当今大陆的学术风气作何评价?您关心这方面的情况吗?您认为学术腐败,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余英时:我曾读过一些大陆学术腐败的报道,主要是大量抄袭他人(外国或本国学者)的著作,而且被揭发后仍然毫不在乎。
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说明中国学术界还未能建立起最起码的纪律,而一些号称教授、专家的人也无一点自尊心。
这种情形已远远超过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袭用《先秦诸子系年》的前例。
郭沫若只不过袭用他人的材料而不肯承认,他论文的中心观点还是自己构想出来的。
现在市场经济发达,抄袭的人大概出于赚钱或出名两种动机,也许大陆大学的升迁制度也在无意中鼓励了这一不良风气。
西方或日本如发生同样的情况,抄袭的人一定在学术界从此不能立足。
最主要的是这样绝无自尊心的人根本无意从事严肃的研究或教学工作,对于知识本无兴趣,因此对于贻害青年学生的事似毫不感觉愧悔。
我希望这是少数例外,如果成了普遍风气,那么中国便永无建立学术界的可能了。
学者自律与学术界自清运动是惟一解决之道。
李宗陶:您曾提到,最迟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逐渐取得一个共识:“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
现代知识人与“士”的核心分野在哪里?当代中国知识人是否还有可能对“士”的传统有所继承?余英时:传统的“士”和现代知识人的主要分别在于“士”是“四民之首”,而知识人在20世纪的社会结构中已退出了中心的地位,此中最大关键便是1905年科举的废止。
自先秦以下的中国结构理论,都假定“士”是最宜成为领导和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也就是不代表任何特殊的经济社会利益阶层而具有超越一己利害之上的“公”心。
因此自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以后,“士”通过考试而成为国家官吏的主要人选。
这个制度在1905年废止后,“士”便变成现代知识人了。
这一变动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环节,必须肯定是一种合理的社会、文化的演进。
我们只要比较一下1895年康有为所领导的举人“公车上书”和1919年北京学生所发动的“五四”运动,“士”与知识人的分野便无所遁形了。
正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知识人的身上才必然带有浓厚的“士”的精神。
事实上现代中国的种种“革命”最初都是由知识人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他们仍然继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意识。
制度是“硬体”,可以说废止即废止,文化传统是“软体”,不可能随着制度的死亡而完全消失。
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仍是改变或批评不合理现状的主要力量。
李宗陶:当今时代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大陆知识分子的地位?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今天在大陆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
以前是他们成了权力的奴仆,现在也有转为市场小贩的倾向。
所以知识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学术、文化、艺术种种专业的尊严。
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
李宗陶: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中国大陆商界精英多半是爱读书的人(以前没有读过的,现在正在补),也很愿意花许多钱去名校拿一个EMBA头衔,其中有一些人也热衷公益事业、注重德行,等等。
在您看来,这些表象下面,是否涌动着对15世纪以来至20世纪被截断的、涩泽荣一所说的“士魂商才”的渴慕?这些表象汇总起来,有没有恢复近代“士商”传统的可能?您如何看待专业人士与经济集团的结盟?余英时:我知道,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知识人“下海”经商的时期,这和十五十六世纪“弃儒就贾”的社会变化有相似之处。
我也知道,今天中国工商界有重视文化、知识的人,如果出于价值选择,这当然是好事。
“士魂商才”重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美国工商界的成功者绝大多数都重视文化教育的提倡,许多最好的私立大学都是靠成功校友的慷慨捐助而不断发展。
大型基金会更为重要,不少科学、技术、艺术、文化事业等是由基金会支持的。
西方大企业都已社会化,故可以长存,不像过去中国人致富主要靠一家、一族,而且发财后子孙往往败家,不过两三代便消失了。
这是我们应该向西方认真学习的东西。
如果仅仅“附庸风雅”则不可能恢复“儒商”的传统。
专业人士与经济集团的联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要看怎样互相配合与互相支援。
李宗陶:儒家的价值观和现代社会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联系是否还有可能?是否还有必要?余英时:儒家价值怎样在今天再发挥正面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简单地说,我认为在儒家价值与现代社会之间建立制度性的联系是行不通的。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上清楚的界线。
在“公领域”我们必须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来运作,任何一家/派的学说或理论都不能侵入。
这是全体人民通过选举、代议机构等等来决定的。
但在“私领域”中,每个家庭或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可以是选择的对象。
儒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只能靠家庭、私人个体来传播,国家权力不宜介入。
李宗陶:继台湾读经运动之后,大陆前段时间兴起一阵小朋友读经热,一些有条件的家长开始推崇由四书五经起步的家学,您觉得这些举措对恢复儒学传统是否有益?余英时:读经运动在20世纪曾一再有人提倡,如30年代地方长官如广东陈济棠、湖南何键等都曾做过努力,但并未见成效。
台湾读经运动并没有真正执行过,只有少数人写文章鼓吹而已。
大陆上近年来听说有些地方进行了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热潮”,成效如何,我完全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