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
- 格式:doc
- 大小:37.00 KB
- 文档页数: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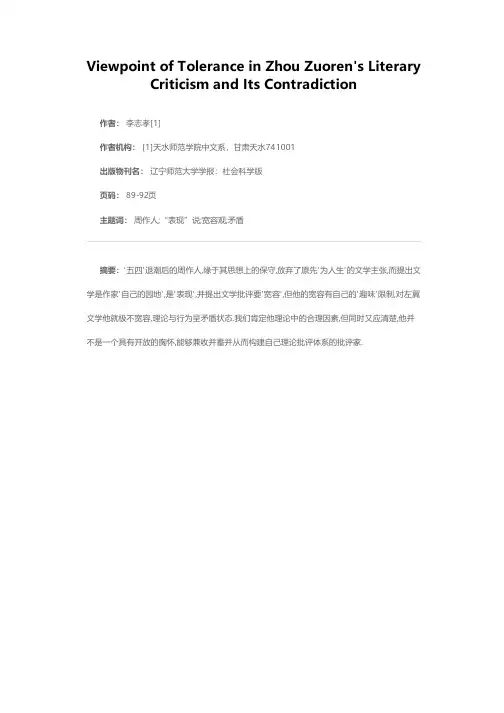
Viewpoint of Tolerance in Zhou Zuoren'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 作者: 李志孝[1]
作者机构: [1]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甘肃天水741001
出版物刊名: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89-92页
主题词: 周作人;“表现”说;宽容观;矛盾
摘要:'五四'退潮后的周作人,缘于其思想上的保守,放弃了原先'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而提出文学是作家'自己的园地',是'表现',并提出文学批评要'宽容',但他的宽容有自己的'趣味'限制,对左翼文学他就极不宽容,理论与行为呈矛盾状态.我们肯定他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但同时又应清楚,他并不是一个具有开放的胸怀,能够兼收并蓄并从而构建自己理论批评体系的批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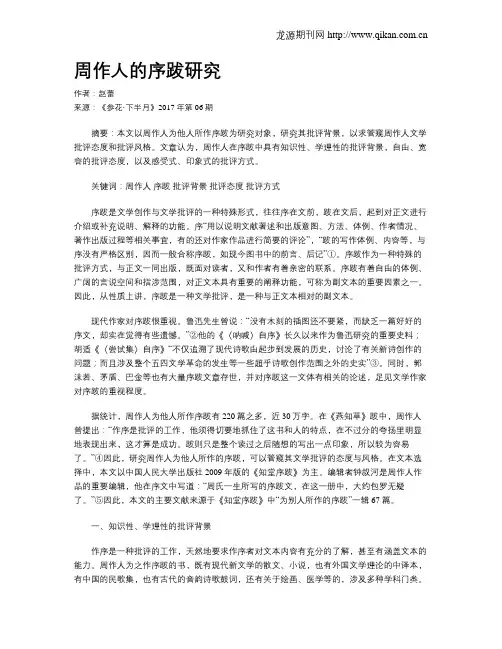
周作人的序跋研究作者:赵蕾来源:《参花·下半月》2017年第06期摘要:本文以周作人为他人所作序跋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批评背景,以求管窥周作人文学批评态度和批评风格。
文章认为,周作人在序跋中具有知识性、学理性的批评背景,自由、宽容的批评态度,以及感受式、印象式的批评方式。
关键词:周作人序跋批评背景批评态度批评方式序跋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往往序在文前,跋在文后,起到对正文进行介绍或补充说明、解释的功能。
序“用以说明文献著述和出版意图、方法、体例、作者情况、著作出版过程等相关事宜,有的还对作家作品进行简要的评论”,“跋的写作体例、内容等,与序没有严格区别,因而一般合称序跋,如现今图书中的前言、后记”①。
序跋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与正文一同出版,既面对读者,又和作者有着亲密的联系。
序跋有着自由的体例、广阔的言说空间和指涉范围,对正文本具有重要的阐释功能,可称为副文本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从性质上讲,序跋是一种文学批评,是一种与正文本相对的副文本。
现代作家对序跋很重视。
鲁迅先生曾说:“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遗憾。
”②他的《〈呐喊〉自序》长久以来作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史料;胡适《〈尝试集〉自序》“不仅追溯了现代诗歌由起步到发展的历史,讨论了有关新诗创作的问题;而且涉及整个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等一些超乎诗歌创作范围之外的史实”③。
同时,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也有大量序跋文章存世,并对序跋这一文体有相关的论述,足见文学作家对序跋的重视程度。
据统计,周作人为他人所作序跋有220篇之多,近30万字。
在《燕知草》跋中,周作人曾提出:“作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
跋则只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想的写出一点印象,所以较为容易了。
”④因此,研究周作人为他人所作的序跋,可以管窥其文学批评的态度与风格。
在文本选择中,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知堂序跋》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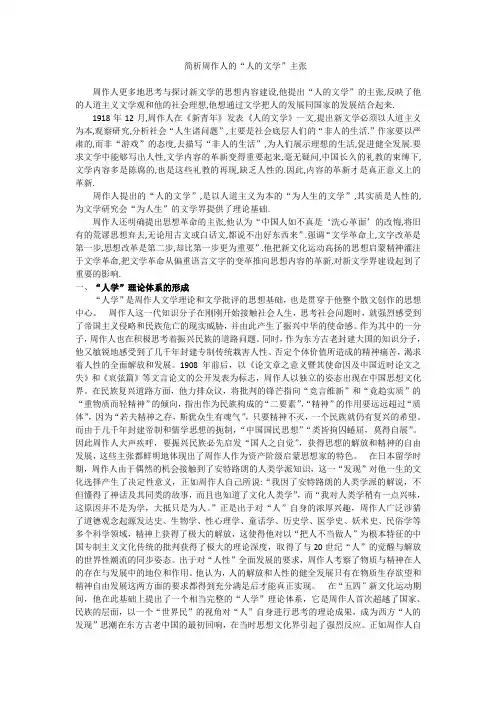
简析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周作人更多地思考与探讨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建设,他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和他的社会理想,他想通过文学把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要以严肃的,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为人们展示理想的生活,促进健全发展.要求文学中能够写出人性,文学内容的革新变得重要起来,毫无疑问,中国长久的礼教的束缚下,文学内容多是陈腐的,也是这些礼教的再现,缺乏人性的.因此,内容的革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其实质是人性的,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界提供了理论基础.周作人还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强调“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把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思想启蒙精神灌注于文学革命,把文学革命从偏重语言文字的变革推向思想内容的革新,对新文学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一、“人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人学”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
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刚刚开始接触社会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威胁,并由此产生了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周作人也在积极思考着振兴民族的道路问题。
同时,作为东方古老封建大国的知识分子,他又敏锐地感受到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栽害人性、否定个体价值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渴求着人性的全面解放和发展。
1908年前后,以《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等文言论文的公开发表为标志,周作人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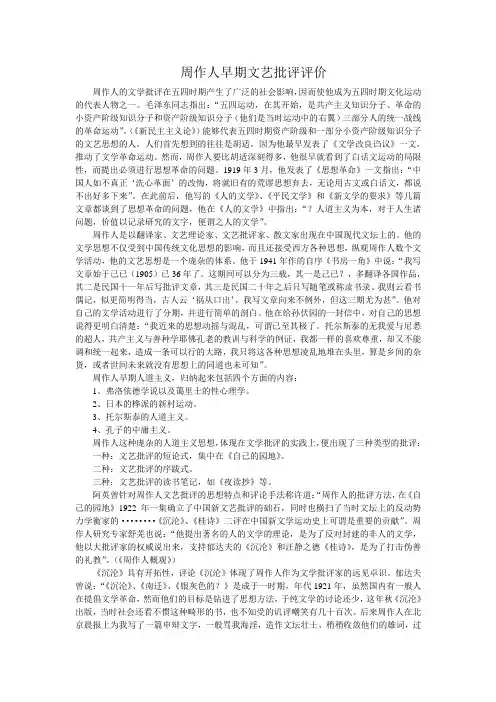
周作人早期文艺批评评价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新民主主义论》)能够代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因为他最早发表了《文学改良诌议》一文,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
然而,周作人要比胡适深刻得多,他很早就看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而提出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
1919年3月,他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指出:“中国人如不真正‘洗心革面’的改悔,将就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多下来”。
在此前后,他写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新文学的要求》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思想革命的问题,他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价值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周作人是以翻译家、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散文家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
他的文学思想不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接受西方各种思想,纵观周作人数个文学活动,他的文艺思想是一个庞杂的体系。
他于1941年作的自序《书房一角》中说:“我写文章始于己已(1905)已36年了。
这期间可以分为三载,其一是己已?,多翻译各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二十年之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
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得当,古人云‘祸从口出’,我写文章向来不例外,但这三期尤为甚”。
他对自己的文学活动进行了分期,并进行简单的剖白。
他在给孙伏园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思想说得更明白清楚:“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
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悉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算是乡间的杂货,或者世间未来就没有思想上的同道也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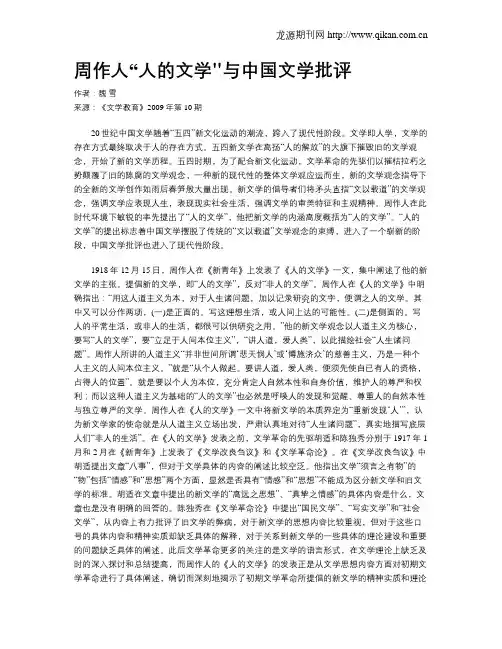
周作人“人的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作者:魏雪来源:《文学教育》2009年第10期20世纪中国文学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跨入了现代性阶段。
文学即人学,文学的存在方式最终取决于人的存在方式。
五四新文学在高扬“人的解放”的大旗下摧毁旧的文学观念,开始了新的文学历程。
五四时期,为了配合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旧的陈腐的文学观念,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整体文学观应运而生,新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全新的文学创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
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将矛头直指“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应表现人生,表现现实社会生活,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主观精神。
周作人在此时代环境下敏锐的率先提出了“人的文学”,他把新文学的内涵高度概括为“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文学摆脱了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束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文学批评也进入了现代性阶段。
1918年12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新文学的主张。
提倡新的文学,即“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明确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
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
(二)是侧面的。
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
”他的新文学观念以人道主义为核心,要写“人的文学”,要“立足于人间本位主义”,“讲人道,爱人类”,以此描绘社会“人生诸问题”。
周作人所讲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就是“从个人做起。
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已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就是要以个人为本位,充分肯定人自然本性和自身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而以这种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人的文学”也必然是呼唤人的发现和觉醒、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与独立尊严的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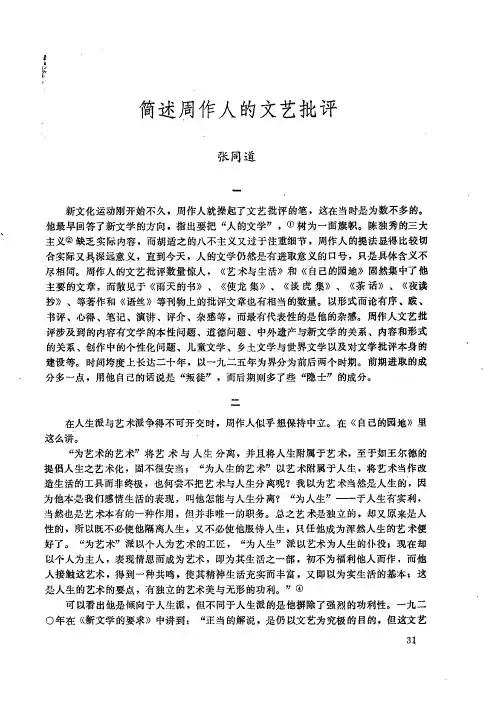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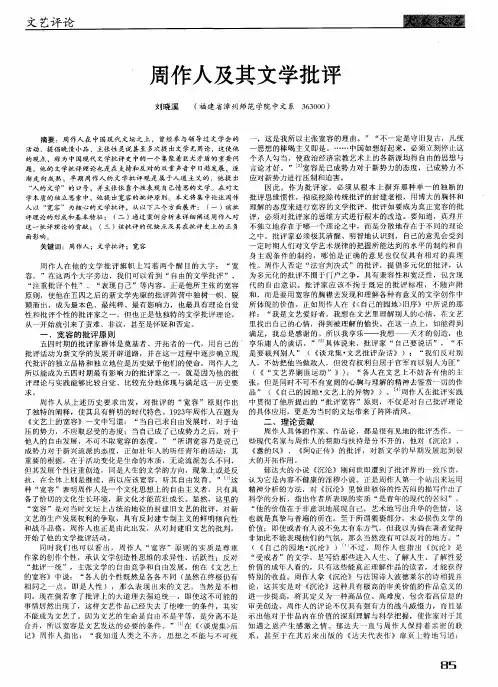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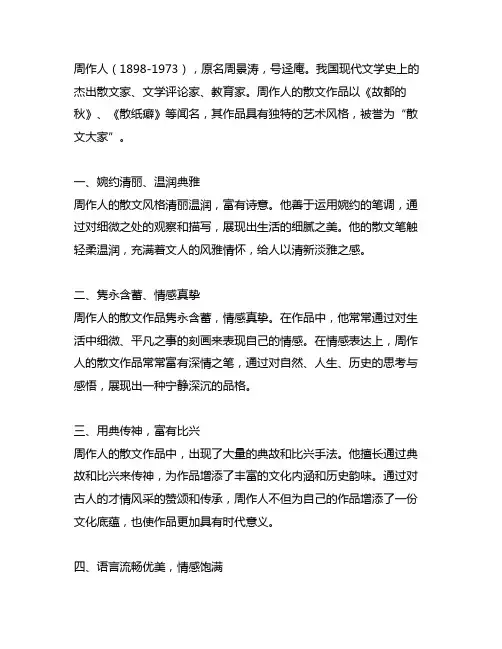
周作人(1898-1973),原名周景涛,号迳庵。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教育家。
周作人的散文作品以《故都的秋》、《散纸癖》等闻名,其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被誉为“散文大家”。
一、婉约清丽、温润典雅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清丽温润,富有诗意。
他善于运用婉约的笔调,通过对细微之处的观察和描写,展现出生活的细腻之美。
他的散文笔触轻柔温润,充满着文人的风雅情怀,给人以清新淡雅之感。
二、隽永含蓄、情感真挚周作人的散文作品隽永含蓄,情感真挚。
在作品中,他常常通过对生活中细微、平凡之事的刻画来表现自己的情感。
在情感表达上,周作人的散文作品常常富有深情之笔,通过对自然、人生、历史的思考与感悟,展现出一种宁静深沉的品格。
三、用典传神,富有比兴周作人的散文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典故和比兴手法。
他擅长通过典故和比兴来传神,为作品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韵味。
通过对古人的才情风采的赞颂和传承,周作人不但为自己的作品增添了一份文化底蕴,也使作品更加具有时代意义。
四、语言流畅优美,情感饱满周作人的散文语言流畅优美,情感饱满。
他擅长用简洁清新的句式,清丽澄澈的文字,流畅优美的篇章,展现出大家风范。
在情感表达上,周作人的作品往往富有真挚、深情的情感,读来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共鸣和触动。
五、独特的叙述手法,情感真挚周作人的散文作品中,他往往能够巧妙地运用独特的叙述手法。
他善于通过纯熟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叙述方式,使散文作品展现出深厚的内涵和丰富的情感。
通过对日常琐事的深度观察和细致描绘,周作人以其独特的叙述手法,塑造了许多富有生活气息和情感韵味的人物形象。
六、文学批评眼光独到除了自己的散文作品外,周作人还在文学批评方面有着独到的眼光。
他曾撰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对我国古代文学及近代文学有着深刻的研究,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作人的散文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情感内涵,成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瑰宝,对于我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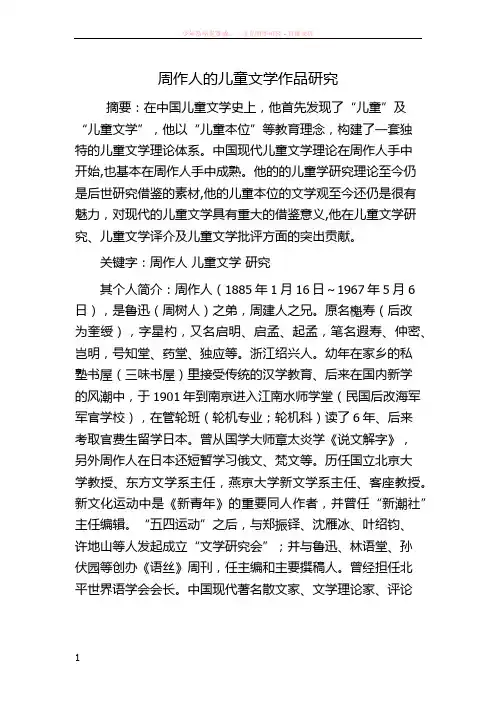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作品研究摘要: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他首先发现了“儿童”及“儿童文学”,他以“儿童本位”等教育理念,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在周作人手中开始,也基本在周作人手中成熟。
他的的儿童学研究理论至今仍是后世研究借鉴的素材,他的儿童本位的文学观至今还仍是很有魅力,对现代的儿童文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他在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及儿童文学批评方面的突出贡献。
关键字: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其个人简介: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
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
浙江绍兴人。
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后来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
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
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
“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儿童文学作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其创作背景。
1、“五四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学革命,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绚烂的春天。
许多作家在这里实践西方的创作理论,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创作经验;把边缘化的小说、散文等非主流文学体式推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辉煌。
在这场时代的洪流中,周作人以顶立浪尖的姿态创造着他的文学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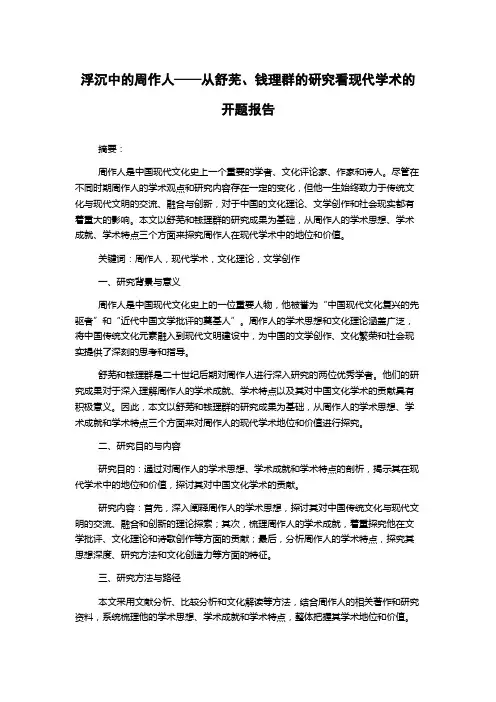
浮沉中的周作人——从舒芜、钱理群的研究看现代学术的开题报告摘要: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学者、文化评论家、作家和诗人。
尽管在不同时期周作人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内容存在一定的变化,但他一生始终致力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流、融合与创新,对于中国的文化理论、文学创作和社会现实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本文以舒芜和钱理群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特点三个方面来探究周作人在现代学术中的地位和价值。
关键词:周作人,现代学术,文化理论,文学创作一、研究背景与意义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化复兴的先驱者”和“近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奠基人”。
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涵盖广泛,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现代文明建设中,为中国的文学创作、文化繁荣和社会现实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指导。
舒芜和钱理群是二十世纪后期对周作人进行深入研究的两位优秀学者。
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入理解周作人的学术成就、学术特点以及其对中国文化学术的贡献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本文以舒芜和钱理群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三个方面来对周作人的现代学术地位和价值进行探究。
二、研究目的与内容研究目的:通过对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的剖析,揭示其在现代学术中的地位和价值,探讨其对中国文化学术的贡献。
研究内容:首先,深入阐释周作人的学术思想,探讨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流、融合和创新的理论探索;其次,梳理周作人的学术成就,着重探究他在文学批评、文化理论和诗歌创作等方面的贡献;最后,分析周作人的学术特点,探究其思想深度、研究方法和文化创造力等方面的特征。
三、研究方法与路径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和文化解读等方法,结合周作人的相关著作和研究资料,系统梳理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整体把握其学术地位和价值。
综上所述,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学者、文化评论家、作家和诗人。
周作人研究儿童文学根本动力是“国民性”批判周作人研究儿童文学根本动力是“国民性”批判刘绪源对儿童文学,周作人怎么说(上)1934年,虚岁50的周作人写过一篇短短的《自述》,其中强调:“如不懂茀洛伊特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
”他所指的,主要是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衍化出来的蔼理斯的儿童本位学说,周作人受其影响甚大,而在这里,他几乎将此看成自己一生事业的重心了。
在写于此前的《〈发须爪〉序》中,他说了自己对神话几近天然的爱好,又说:“我有时想读一篇牧歌,有时想知道蜘蛛的结婚,实在就只是在圈子里乱走……”看得出他的学术探讨中充满了童心的驱动。
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反复抄写的也是一部关于儿童生活的未刊诗稿:《儿童杂事诗》。
周作人对儿童学与儿童文学的研究发萌于1906年,当时他到日本留学,“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见《知堂回想录》)。
他在这方面的大量写作始于1912年,他的轰动“五四”新文坛的代表作《人的文学》,也突出了妇女问题与儿童问题。
1920年,应邀在孔德学校作题为《儿童的文学》的讲演时,他正式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命名。
周作人是中国最早引进安徒生作品的人,是最早在中国全面系统倡导儿童文学的人,也是最早投身于儿童文学研究及批评(包括儿童文学翻译的批评)的实践者。
“五四”以后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他的理论批评大有关系。
然而他又是个特殊的理论家,他没有理论专著(《儿童文学小论》也只是一本批评与论文的合集),他的所有创见都在散文随笔中(其论文严格说也还是“美文”),这一点与鲁迅十分相像。
所以要找出他的理论构架,必须在大量文章中寻觅,这不同于读那些框架谨严的论著,但因文章好,读来另有一番乐趣。
“国民性”批判周作人作儿童文学研究,其最初的根本动力还是“国民性”批判。
在写于1912年的《儿童问题之初解》中,他说到,成人对儿童的感情可有三个层次:“初主实际,次为审美,终于研究”。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及研究摘要: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他首先发现了“儿童”及“儿童文学”,他以“儿童本位”及“无意思之意思”等教育理念,构建了一套独特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周作人及其儿童文学理论体系,无论在理论或是译介方面,都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关键字: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考察“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理论批评,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它是与当时中国文学界的那些最辉煌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巨人和文坛精英人士的参与,写下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最富有时代光彩和文化底蕴的一页,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一大人文奇观。
本文就中国儿童文学先驱者之一——周作人,论述他在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及儿童文学批评方面的突出贡献。
周作人自从在日本留学时直到回国后的抗日战争前夕,从未间断过对儿童问题的关注和对儿童文学的研究。
早在1902年2月,周作人就与鲁迅合译了《域外小说集》,集子的首篇便是周作人译英国维尔特的(今译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也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
1911年秋,从日本归国不久的周作人,在1913-1914年间,陆续撰写和发表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文章,这些文章或转述人类学派有关神话、传说、童话的解释,或直接引用人类学派代表人物的言论,都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人类学派学术思想的巨大投影。
这是他在日本接受西方人类学派等理论后从事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的起步时期,也是以近代西方文化学术思潮为背景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开始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标志。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早期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热情地推捧儿童文学,发表过数十篇有关的理论文章。
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读安徒生童话<十九>》(1918.6.发表时题为《安德森的十之九》);《人的文学》:从重视人的问题出发,进而十分关注儿童文学;《儿童的文学》(1912.12)提出“中国向来对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作缩小的成人,拿‘圣贤经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孩子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文学评论
周作人的故乡是安徽省宣城市,这个地区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传统而著名。
因此,在周作人的作品中,野菜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元素。
周作人在《木兰花慢》这首诗中写道:“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里的“胭脂泪”指的就是野菜中的胭脂蕉花,它被用来表达人生的短暂和无常。
通过这样的描写,周作人将野菜与人生的哀感联系在一起。
此外,在《农村新闻》一文中,周作人也写到了故乡的野菜:“山家自有种种野菜,食物极多。
”在这里,周作人将故乡的野菜与农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呈现了一种朴素而充实的生活状态。
总的来说,周作人将故乡的野菜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融入到他的作品中,通过对野菜的描写,他表达了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生的思考。
同时,他也强调了故乡生活的朴实和充实。
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一、本文概述《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是一篇旨在深入探讨和分析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学术论文。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独特的文学观念和丰富的创作实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对周作人文学思想的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揭示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时代意义。
本文首先将对周作人的生平背景进行简要介绍,包括其成长经历、教育背景以及文学创作历程等,以便更好地理解其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重点分析周作人的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学创作实践,包括其对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性、文学与艺术等关系的独到见解,以及其在实际创作中的运用和体现。
通过对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同时也希望能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在此过程中,本文将采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做到论证充分、分析深入、观点明确。
二、周作人的文学观念周作人的文学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学的深刻理解之上。
他倡导一种“人的文学”,强调文学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
他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功利化,认为文学应独立于政治之外,以审美和人文关怀为核心。
在周作人看来,文学的价值在于其能够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和深度,能够触动人的情感,引起人的共鸣。
他提倡“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观,主张文学应独立于政治、道德等其他社会因素之外,以自身的审美价值为依归。
周作人也非常注重文学的形式和技巧。
他提倡简洁、质朴的文风,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涵。
他强调文学的创新和实验精神,鼓励作家在形式和技巧上进行探索和尝试。
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体现了他对文学的独特理解和追求。
他坚持文学的人道主义立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需求,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和人文关怀。
这些观念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新民主主义论》)代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因为他最早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
然而周作人要比胡适深刻的多,他很早就看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而提出了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
1919年3月,他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指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悔改,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
”在这前后,周作人写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思想革命的问题,他在《人的文学》中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纵观周作人早期文学批评理论,它的核心便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思潮和别的思潮一样,并不是与世俱来纵贯古今的东西,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人道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作家、思想家们用来反对封建主义束缚,要求思想解放的理论武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宗法观念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就成为当务之急。
周作人从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武库里搬来了人道主义,矛头直指封建主义。
虽然,当时欧洲已出现了反动的人道主义,但在中国,人道主义仍有它的进步性,成为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同盟军。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感慨:“生四千余年,现在去还讲人的意义,重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
”五四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态,投入了“辟人荒”的战斗,其中最突出的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开始将人的解放由个性解放的最低层次推进到阶级解放的最高层次。
而周作人却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去考究人、发现人。
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
”这种说法包括两种含义,其一,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着重点在动物,因为原来是动物,所以人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
从这里,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有“兽性的遗传”——肉体的欲望要求,即兽性的一面。
其二,人又是从动物进化的,着重点在进化,因此,“人的内面生活比动物更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的能量”。
从这里,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除了肉体的欲望以外,还有“灵魂”的愿望,精神的要求,即“神性的一面”。
既然“人是灵肉一致的人”,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那么,符合这种人性发展的理想的人的生活,势必既不同于禁欲主义的超于人间的“人性以外人力以上”的纯然灵的生活;也不同于纵欲主义的低于人间的纯乎肉的生活,而应该是以人间为本位的顺乎人性合乎人理的灵肉一致的生活。
实际上,周作顶礼膜拜的“人”恰恰是一个抽象的、超“人间性”的图腾,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推及于类”(《文学的讨论——玖月葵》),还可以用这样一个循环式来表述:利己——利他——利己,利己是起点,也是终点,这就是周作人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即人道主义。
很自然,人道主义便成为周作人文学批评的中心思想。
周作人的早期文学批评是很注重思想革命的。
他的思想革命与鲁迅一样,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的灵魂”,使中国人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从非人的生活中挣脱邮来,过上人的生活。
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新文学身上了。
周作人在讲到自己的文章时说:“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苦口甘口·序》)。
在《瓜豆集·自己的文章》里又说:“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也有一点好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
”在评价别人的文章时他也“带有一种偏见”,总多“留意其思想的分子,自己写时也是如此”(《过去的工作·过去的工作》)。
就拿他一生创作数量最丰的散文小品文来说,“生命仍然是在思想”(舒芜《周作人后期散文小品文的审美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辑),这里正好用的着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里的一个比喻,假如除去了思想的分子,他的小品散文就“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即使周作人当了汉奸后,他所鼓吹的仍是思想问题,那就是要中国人民树立“大东亚主义”的“中心思想”,替其日本主子做奴化宣传。
周作人运用蔼理斯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来反对封建禁欲主义,在文学上主张大胆描写爱与两性生活,并提倡正常的性教育。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提倡禁欲主义,中国的儒教也大谈“男女之大防”,宋元之后,道学家尤其在这上面大做文章。
这种道德观念是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所以受到周作人的批判。
周建人曾指出:封建礼教“向来看两性关系是非常卑下而且秽亵,以为男女之间,除了严防以外,更无别法,甚至于夫妻之间,也有‘男居外,女居内’。
深宫闺门固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周建人《性教育的理论与实际》)。
这样,在“万恶淫为首”的封建教条的严酷钳制下,人最起码的本能欲望也不能得到正常的满足。
另一方面,中国假道学的空气浓厚,官僚和老头子不必说了,就是青年也这样。
有些人看了心琴画会的画展,不去评价绘画艺术成就的大小,却绝口称赞“绝无一幅裸体画,更见其人品之高”;对此,周作人感慨万千:“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起来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首先的见地,提倡净观,反抗这假道学的教育,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
”(《两天的书·净观》)“要被火烤了为止”这句话,是从法国作家拉伯雷那里借过来的。
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讲这话者“未必有殉道的决心”(《两天的书·与故人论性道德书》)。
但是周作人这样说,还是有很大的反封建的勇气的。
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薄伽丘等人的作品,周作人推崇备至,“因为他们有一种非理法主义显现于艺术之中”,蔑视宗教用来禁锢人们的种种清规戒律。
他多次引用英国十九世纪中叶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主张,认为人应当有正常的性生活,因此,他提倡净观。
正是从这种净观的理论出发,他变为,性本能“在现代文明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必然“非意识的喷发出来”,在文艺创作中寻求变相的满足,“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庄的(即猥亵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
”(周作人《沉沦》)在谈到猥亵的歌谣时,他认为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般男女关系很不圆满”而造成的“两性的频闷”(《猥亵的歌谣》)。
他多次引用一行诗“嘴唱着歌,只在他不能亲吻的时候”来说明这个问题,意思是:只有当人不能亲吻(即性欲得不到满足)时,才需要用唱歌的方式来发泄被压抑的性欲。
所以他说:“猥亵的歌谣,赞美私情的种种的民歌,即是有此动机而不实行的人所采用的别求满足的方法”,并进而认为“其实一切情诗的起源起都是如此”(《猥亵的歌谣》)。
周作人这些高论深深地打上了弗洛伊德学说泛性论的印记。
周作人支持那描写爱情的文学,为一些被攻击为“猥亵”、“不道德”的作品辩护。
当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受到封建卫道士们指责诽谤的时候,周作人旗帜鲜明地说《蕙的风》能够“放情地唱”、“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倘若大惊小怪,以为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那有如见了小象还怪它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自己的园地·情诗》)。
对封建卫道士的有力回击还是对《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的充分肯定,“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它的价值在于写出了一个青年“生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批判和抗争”(《自己的园地·沉沦》)。
周作人在作了深刻的分析后写道:“我临末要郑重地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都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在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合适的。
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
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
”后来,郁达夫在回顾他的这本处女集出版后的情况时曾说:“在这一年(1921年)的秋后,《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
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淫秽,骂我造作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
”(《鸡肋集·题辞》)在以后出版的《达夫代表作》的扉页上,郁达夫还写下了这样一段题辞:“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
周作人在肯定爱情描写的同时,又划清了它与色情文学的界线。
周作人对“色情狂的淫书类”是持否定态度的。
他认为问题不在写作材料,而在作者的态度,比如,同是写“人间兽欲”,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一生》是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
“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
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觉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
”(《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1932年3月到4月,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首先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学新见解:文学无目的性的主张。
其次,他特别推崇晚明小品文,尤其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作品。
认为这是揭了反叛的旗帜,一扫复古的风气。
周作人非常赞赏他们的性灵讼,甚至把公安派和竟陵派看作是近代新文学的源头,认为五四文学革命“产生了胡适的所谓‘八不立义’,他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灵性,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
”所不同的只是“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对于周作人这种看法,林语堂极力称赞。
他在《新旧文学》一文中认为周作人“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派和竟陵派”,“所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地的话。
”周作人的散文小品创作步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独抒灵性”的后尘,而对同行们的批评,他所奉行的艺术标准便是闲适与趣味,一种冲淡朴纳的风格。
他在《竹林故事·序》中说:“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我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的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