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炜小说的苦难性
- 格式:doc
- 大小:23.50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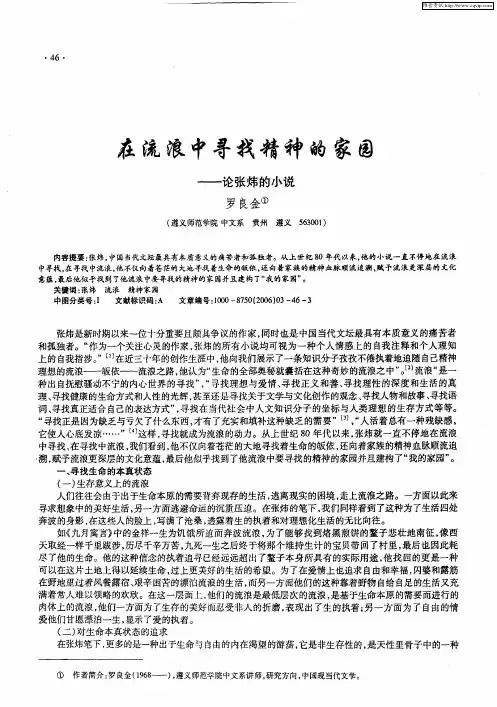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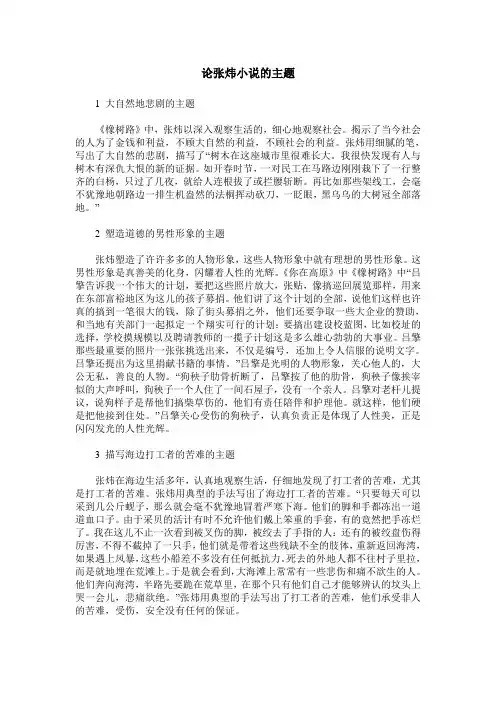
论张炜小说的主题1 大自然地悲剧的主题《橡树路》中,张炜以深入观察生活的,细心地观察社会。
揭示了当今社会的人为了金钱和利益,不顾大自然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利益。
张炜用细腻的笔,写出了大自然的悲剧,描写了“树木在这座城市里很难长大。
我很快发现有人与树木有深仇大恨的新的证据。
如开春时节,一对民工在马路边刚刚栽下了一行整齐的白杨,只过了几夜,就给人连根拔了或拦腰斩断。
再比如那些架线工,会毫不犹豫地朝路边一排生机盎然的法桐挥动砍刀,一眨眼,黑乌乌的大树冠全部落地。
”2 塑造道德的男性形象的主题张炜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中就有理想的男性形象。
这男性形象是真善美的化身,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你在高原》中《橡树路》中“吕擎告诉我一个伟大的计划,要把这些照片放大,张贴,像搞巡回展览那样,用来在东部富裕地区为这儿的孩子募捐。
他们讲了这个计划的全部,说他们这样也许真的搞到一笔很大的钱,除了街头募捐之外,他们还要争取一些大企业的赞助,和当地有关部门一起拟定一个翔实可行的计划;要搞出建设校蓝图,比如校址的选择,学校摸规模以及聘请教师的一揽子计划这是多么雄心勃勃的大事业。
吕擎那些最重要的照片一张张挑选出来,不仅是编号,还加上令人信服的说明文字。
吕擎还提出为这里捐献书籍的事情。
”吕擎是光明的人物形象,关心他人的,大公无私,善良的人物。
“狗秧子肋骨折断了,吕擎按了他的肋骨,狗秧子像挨宰似的大声呼叫,狗秧子一个人住了一间石屋子,没有一个亲人。
吕擎对老杆儿提议,说狗样子是帮他们搞柴草伤的,他们有责任陪伴和护理他。
就这样,他们硬是把他接到住处。
”吕擎关心受伤的狗秧子,认真负责正是体现了人性美,正是闪闪发光的人性光辉。
3 描写海边打工者的苦难的主题张炜在海边生活多年,认真地观察生活,仔细地发现了打工者的苦难,尤其是打工者的苦难。
张炜用典型的手法写出了海边打工者的苦难。
“只要每天可以采到几公斤蚬子,那么就会毫不犹豫地冒着严寒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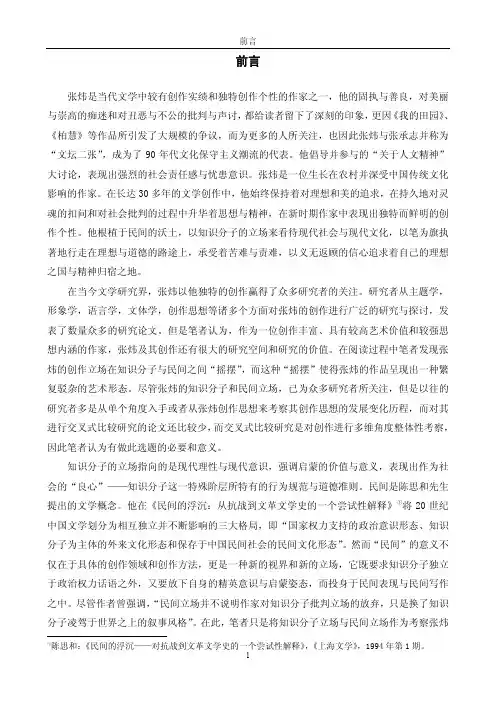
前言张炜是当代文学中较有创作实绩和独特创作个性的作家之一,他的固执与善良,对美丽与崇高的痴迷和对丑恶与不公的批判与声讨,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因《我的田园》、《柏慧》等作品所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议,而为更多的人所关注,也因此张炜与张承志并称为“文坛二张”,成为了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代表。
他倡导并参与的“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
张炜是一位生长在农村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
在长达30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他始终保持着对理想和美的追求,在持久地对灵魂的扣问和对社会批判的过程中升华着思想与精神,在新时期作家中表现出独特而鲜明的创作个性。
他根植于民间的沃土,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待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以笔为旗执著地行走在理想与道德的路途上,承受着苦难与责难,以义无返顾的信心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之国与精神归宿之地。
在当今文学研究界,张炜以他独特的创作赢得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研究者从主题学,形象学,语言学,文体学,创作思想等诸多个方面对张炜的创作进行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发表了数量众多的研究论文。
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位创作丰富、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较强思想内涵的作家,张炜及其创作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价值。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发现张炜的创作立场在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摇摆”,而这种“摇摆”使得张炜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繁复驳杂的艺术形态。
尽管张炜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已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单个角度入手或者从张炜创作思想来考察其创作思想的发展变化历程,而对其进行交叉式比较研究的论文还比较少,而交叉式比较研究是对创作进行多维角度整体性考察,因此笔者认为有做此选题的必要和意义。
知识分子的立场指向的是现代理性与现代意识,强调启蒙的价值与意义,表现出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这一特殊阶层所特有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
民间是陈思和先生提出的文学概念。
他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①将20世纪中国文学划分为相互独立并不断影响的三大格局,即“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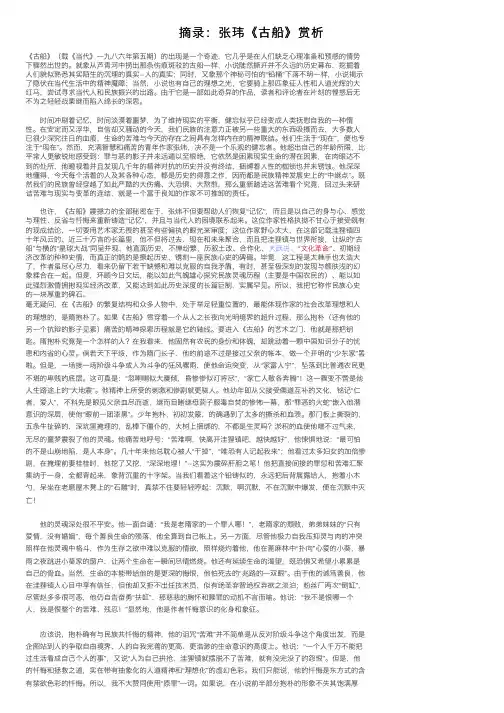
摘录:张玮《古船》赏析《古船》(载《当代》⼀九⼋六年第五期)的出现是⼀个奇迹,它⼏乎是在⼈们缺乏⼼理准备和预感的情势下骤然出世的。
就象从芦青河中捞出那条伤痕斑驳的古船⼀样,⼩说陡然撕开并不久远的历史幕布,挖掘着⼈们貌似熟悉其实陌⽣的沉埋的真实--⼈的真实;同时,⼜象那个神秘可怕的“铅桶”下落不明⼀样,⼩说揭⽰了隐伏在当代⽣活中的精神魔障;当然,⼩说也有⾃⼰的理想之光,它要骑上那匹象征⼈性和⼈道光辉的⼤红马,尝试寻求当代⼈和民族振兴的出路。
由于它是⼀部如此奇异的作品,读者和评论者在⽚刻的惶惑后⽆不为之轻轻战栗继⽽陷⼊绵长的深思。
时间冲刷着记忆,时间淡漠着噩梦,为了维持现实的平衡,健忘似乎已经变成⼈类抚慰⾃我的⼀种惰性。
在安定⽽⼜浮华,⾃信却⼜骚动的今天,我们民族的注意⼒正被另⼀些重⼤的东西吸摄⽽去,⼤多数⼈已很少深究往⽇的⾎痕,⽣命的苦难与今天的存在之间具有怎样内在的精神联结。
他们⽣活于“现在”,便也专注于“现在”。
然⽽,充满智慧和痛苦的青年作家张炜,决不是⼀个乐观的健忘者。
他超出⾃⼰的年龄所限,⽐平常⼈更敏锐地感受到:罪与恶的影⼦并未远遁以⾄根绝,它依然是困累现实⽣命的潜在因素,在⾁眼达不到的处所,他瞪视着并且发现⼏千年的精神对抗的历史并没有终结,捆缚着⼈性的枷锁也并未锈蚀。
他深深地懂得,今天每个活着的⼈及其各种⼼态,都是历史的得意之作,因⽽都是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的“中继点”。
既然我们的民族曾经穿越了如此严酷的⼤伤痛、⼤恐惧、⼤熬煎,那么重新踏进这苦难看个究竟,回过头来研诘苦难与现实与变⾰的连结,就是⼀个富于良知的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许,《古船》震撼⼒的全部秘密在于,张炜不但要帮助⼈们恢复“记忆”,⽽且是以⾃⼰的⾝与⼼、感觉与理性、反省与忏悔来重新铸造“记忆”,并且与当代⼈的困境联系起来。
这位作家性格执拗不⽢⼼于接受既有的现成结论,⼀切要⽤艺术家⽆畏的甚⾄有些偏执的眼光来审度;这位作家野⼼太⼤,在这部记载洼狸镇四⼗年风云的、近三⼗万⾔的长篇⾥,他不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聚合,⽽且把洼狸镇与世界衔接,让纵的“古船”与横的“星球⼤战”同呈并现;他直⾯历史,不惮纷繁,历叙⼟改、合作化、⼤跃进、“⽂化⾰命”、初期经济改⾰的种种史情,⽽真正的鹄的是撩起历史,镌刻⼀座民族⼼史的碑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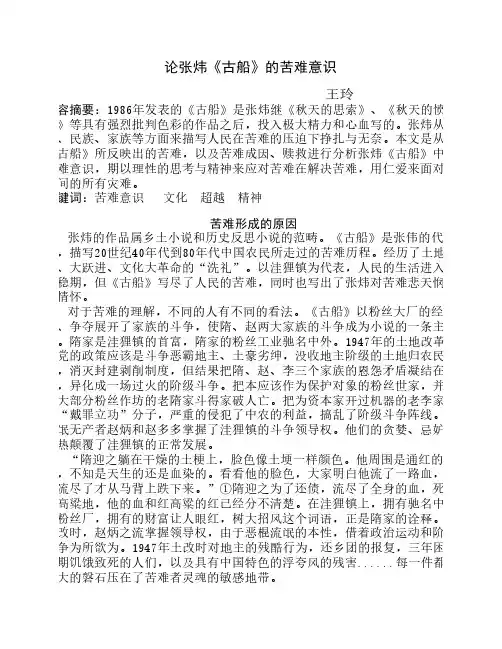
论张炜《古船》的苦难意识王玲内容摘要:1986年发表的《古船》是张炜继《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等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作品之后,投入极大精力和心血写的。
张炜从历史、民族、家族等方面来描写人民在苦难的压迫下挣扎与无奈。
本文是从《古船》所反映出的苦难,以及苦难成因、赎救进行分析张炜《古船》中的苦难意识,期以理性的思考与精神来应对苦难在解决苦难,用仁爱来面对人世间的所有灾难。
关键词:苦难意识 文化 超越 精神苦难形成的原因张炜的作品属乡土小说和历史反思小说的范畴。
《古船》是张伟的代表作,描写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农民所走过的苦难历程。
经历了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以洼狸镇为代表,人民的生活进入了平稳期,但《古船》写尽了人民的苦难,同时也写出了张炜对苦难悲天悯人的情怀。
对于苦难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古船》以粉丝大厂的经营、争夺展开了家族的斗争,使隋、赵两大家族的斗争成为小说的一条主线。
隋家是洼狸镇的首富,隋家的粉丝工业驰名中外。
1947年的土地改革,按党的政策应该是斗争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但结果把隋、赵、李三个家族的恩怨矛盾凝结在一起,异化成一场过火的阶级斗争。
把本应该作为保护对象的粉丝世家,并献出大部分粉丝作坊的老隋家斗得家破人亡。
把为资本家开过机器的老李家定为“戴罪立功”分子,严重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搞乱了阶级斗争阵线。
让流氓无产者赵炳和赵多多掌握了洼狸镇的斗争领导权。
他们的贪婪、忌妒、狂热颠覆了洼狸镇的正常发展。
“隋迎之躺在干燥的土梗上,脸色像土埂一样颜色。
他周围是通红的草叶,不知是天生的还是血染的。
看看他的脸色,大家明白他流了一路血,血快流尽了才从马背上跌下来。
”①隋迎之为了还债,流尽了全身的血,死在红高粱地,他的血和红高粱的红已经分不清楚。
在洼狸镇上,拥有驰名中外的粉丝厂,拥有的财富让人眼红,树大招风这个词语,正是隋家的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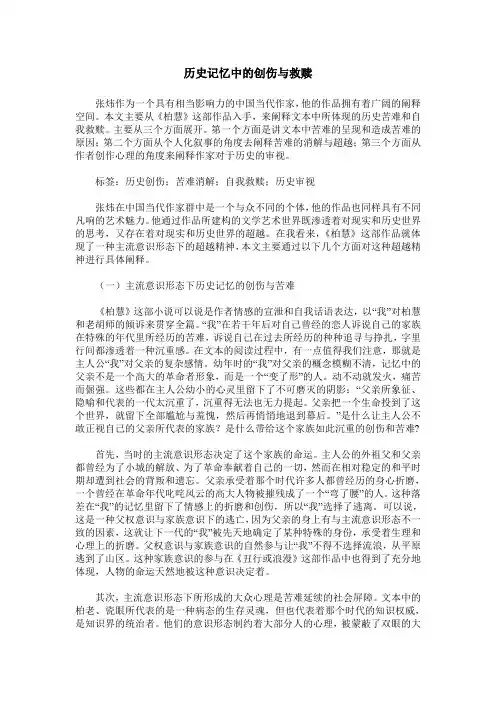
历史记忆中的创伤与救赎张炜作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他的作品拥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
本文主要从《柏慧》这部作品入手,来阐释文本中所体现的历史苦难和自我救赎。
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讲文本中苦难的呈现和造成苦难的原因;第二个方面从个人化叙事的角度去阐释苦难的消解与超越;第三个方面从作者创作心理的角度来阐释作家对于历史的审视。
标签:历史创伤;苦难消解;自我救赎;历史审视张炜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他的作品也同样具有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
他通过作品所建构的文学艺术世界既渗透着对现实和历史世界的思考,又存在着对现实和历史世界的超越。
在我看来,《柏慧》这部作品就体现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下的超越精神,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这种超越精神进行具体阐释。
(一)主流意识形态下历史记忆的创伤与苦难《柏慧》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作者情感的宣泄和自我话语表达,以“我”对柏慧和老胡师的倾诉来贯穿全篇。
“我”在若干年后对自己曾经的恋人诉说自己的家族在特殊的年代里所经历的苦难,诉说自己在过去所经历的种种追寻与挣扎,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沉重感。
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主人公“我”对父亲的复杂感情。
幼年时的“我”对父亲的概念模糊不清,记忆中的父亲不是一个高大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一个“变了形”的人。
动不动就发火,痛苦而倔强。
这些都在主人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父亲所象征、隐喻和代表的一代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也无力提起。
父亲把一个生命投到了这个世界,就留下全部尴尬与羞愧,然后再悄悄地退到幕后。
”是什么让主人公不敢正视自己的父亲所代表的家族?是什么带给这个家族如此沉重的创伤和苦难?首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个家族的命运。
主人公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曾经为了小城的解放、为了革命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然而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却遭到社会的背叛和遗忘。
父亲承受着那个时代许多人都曾经历的身心折磨,一个曾经在革命年代叱咤风云的高大人物被摧残成了一个“弯了腰”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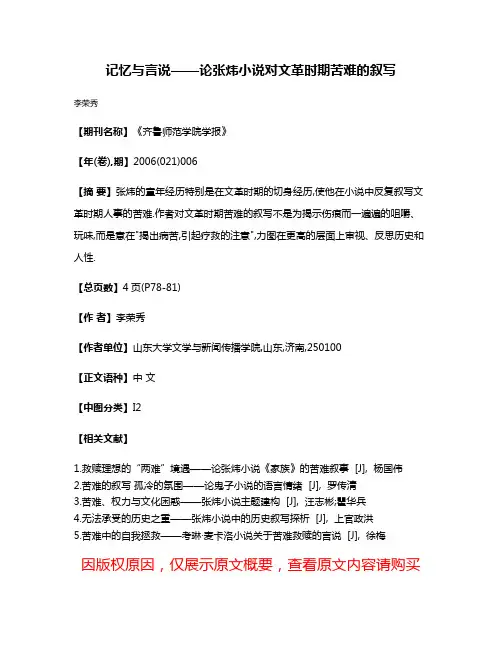
记忆与言说——论张炜小说对文革时期苦难的叙写
李荣秀
【期刊名称】《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6(021)006
【摘要】张炜的童年经历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的切身经历,使他在小说中反复叙写文革时期人事的苦难.作者对文革时期苦难的叙写不是为揭示伤痕而一遍遍的咀嚼、玩味,而是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力图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反思历史和人性.
【总页数】4页(P78-81)
【作者】李荣秀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相关文献】
1.救赎理想的“两难”境遇——论张炜小说《家族》的苦难叙事 [J], 杨国伟
2.苦难的叙写孤冷的氛围——论鬼子小说的语言情绪 [J], 罗传清
3.苦难、权力与文化困惑——张炜小说主题建构 [J], 汪志彬;瞿华兵
4.无法承受的历史之重——张炜小说中的历史叙写探析 [J], 上官政洪
5.苦难中的自我拯救——考琳·麦卡洛小说关于苦难救赎的言说 [J], 徐梅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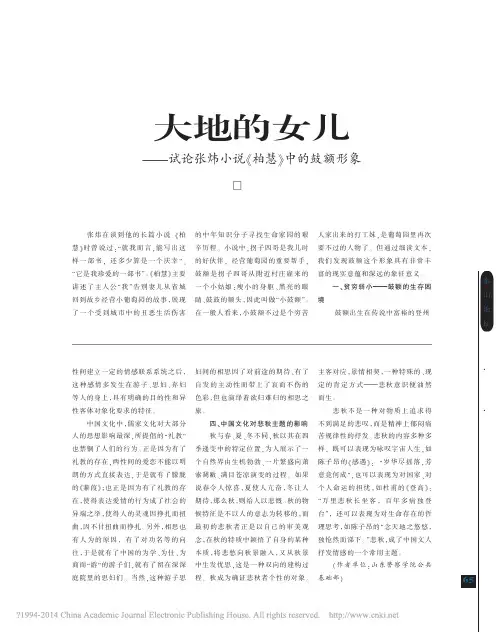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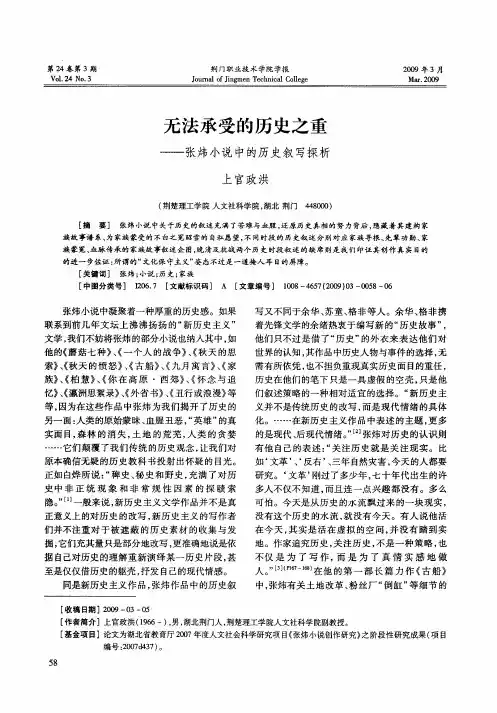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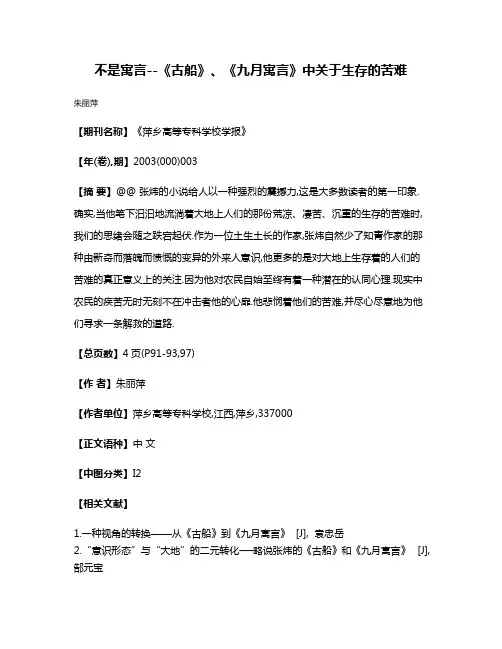
不是寓言--《古船》、《九月寓言》中关于生存的苦难
朱丽萍
【期刊名称】《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卷),期】2003(000)003
【摘要】@@ 张炜的小说给人以一种强烈的震撼力,这是大多数读者的第一印象.
确实,当他笔下汩汩地流淌着大地上人们的那份荒凉、凄苦、沉重的生存的苦难时,我们的思绪会随之跌宕起伏.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作家,张炜自然少了知青作家的那种由新奇而落魄而愤慨的变异的外来人意识,他更多的是对大地上生存着的人们的
苦难的真正意义上的关注.因为他对农民自始至终有着一种潜在的认同心理.现实中农民的疾苦无时无刻不在冲击者他的心扉.他悲悯着他们的苦难,并尽心尽意地为他们寻求一条解救的道路.
【总页数】4页(P91-93,97)
【作者】朱丽萍
【作者单位】萍乡高等专科学校,江西,萍乡,337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相关文献】
1.一种视角的转换——从《古船》到《九月寓言》 [J], 袁忠岳
2.“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略说张炜的《古船》和《九月寓言》 [J], 郜元宝
3.论张炜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嬗变——以《古船》、《九月寓言》、《丑行或浪漫》为例 [J], 何璐
4.苦难命运的诗性隐喻——读《九月寓言》兼论张炜小说的艺术转向 [J], 独木
5.悲悯与慨叹——重读《古船》与初读《九月寓言》 [J], 王彬彬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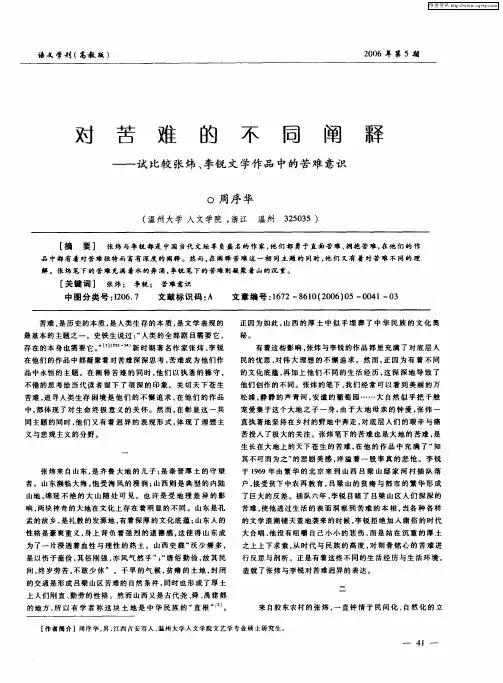
论张炜小说《柏慧》中的流浪意识张炜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柏慧》是其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
这部小说通过书信的方式讲述了“我”和“我的家族”身心流浪但最终回归葡萄园的全过程。
本文从流浪意识入手,研究张炜小说流浪书写的成因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
一、《柏慧》中的精神流浪(一)边缘化和疏离感在《柏慧》一书中,我们能看到以“我”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一直被边缘化。
“我”从地质社——零三所——杂志社——葡萄园一路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如人面兽心的柏老、蝇营狗苟的“瓷眼”、趋时奉势的柳萌;但也遇到了仗义可靠的果园四哥夫妇,善良纯洁的小鼓额……这也是“我”流浪到回归的过程。
当“我”在地质社读大学时,由于父亲的“秘密”被爱人柏慧告知了柏老,“我”被记了大过,艰难地度过剩下的日子,后被分配到了零三所,在这里“我”见识到了与柏老大同小异的“瓷眼”,他拉拢势力的手段以及无处不在的心腹让“我”见识到了人性的颓废与险恶。
当他们发现“我”是异类时,“我”又开始被排挤和边缘化,最终被迫离职。
来到杂志社,本以为终于能过上稳定的日子,但在经济大潮的不断冲击下,杂志社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组织,而是为了迎合市场和大众的口味使内容不断低俗化,不堪入目的小广告和大片娱乐八卦新闻让“我”再次想要逃离,“我”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回到了葡萄园。
随着机器轰鸣声的到来,大片的土地田野被“侵占”,大面积的污染使得渔民被迫迁移,这里也不再是印象中的家园。
在《柏慧》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不断被边缘化,在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人之后,终于发现人是可以区分为“善”与“恶”两种血缘的。
以“我”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即使经历了现实的强烈冲击,经历了一次次的焦虑与迷茫、彷徨与不安,但仍旧不言放弃,仍然追求真、善、美。
主人公“我”在给老胡师的信中明确表示坚定人文主义信念:“人为了追求高贵,可以贫困,可以死亡。
”事实他也是这么做的,在离开零三所后他再次给老胡师写信。
他认为真正的知识没有什么中心,只有心中存在才能永恒,只要拥有那样一颗心灵,走到哪里都不会失去“中心”。
论张炜《古船》中的流浪意识《古船》是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20 世纪80 年代末发表,至今仍受到广泛关注。
它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社会,以一条河流象征了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了灵魂的困境与挣扎。
小说内容跨越了近半个世纪,讲述了小村庄洼狸镇在四十年中各时期的重大事件以及隋、赵、李三大家族的沧桑变化。
作品以隋家为中心,主要讲述了隋家家道中落,隋迎之抱病身亡,隋不召出海远航,隋见素不甘命运为振兴家业做顽强斗争,隋抱朴从守磨人后来奋起抗争,赵多多将隋家家业据为己有等一系列事件,表现了书中人物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斗争与屈服。
本文将从流浪意识入手,研究《古船》中体现出来的流浪意识,并探索张炜流浪意识书写形成的原因。
一、流浪与流浪意识流浪的行为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形成,它是人类适应自然而做出的能动反应。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发展缓慢,最早的人们定居下来进行种植,从而促成了农业的出现,定居耕种收获粮食就能够让生活得到保障,因此人们不再四处流浪。
而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则恰恰相反,他们如果依靠定居是无法保证生活的,因此必须逐水草而迁徙放牧,这就是流浪的体现。
固守本土和流浪成了人类情感与理想追求的一对矛盾。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学作品也刻上了流浪的印记。
对流浪的书写是人们千百年来反复使用的文学母题,在中外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流浪的痕迹。
如《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再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西方的流浪者形象更多是一种文化英雄,他们乐观积极,勇敢地完成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和创造。
中国的流浪文学作品也有很多,但却没有形成系统,只可以零散地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见到,如《西游记》《水浒传》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在封建社会时期,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流浪没有在社会上形成风尚。
流浪和流浪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表里、共同生长的,流浪为流浪文学提供理论支撑,流浪文学又丰富了流浪的文学内涵,两者互相促进。
新时期文学的苦难意识-现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苦难作为重要的文学主题,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受到了作家们既深入又多面的思考与探究。
在对苦难的直面追问与对救赎的勇敢探寻中,新时期文学焕发出异样光彩:既有诸多严肃作家从民族文化、历史、人性等宏大角度对苦难意识进行反思与救赎,也有王朔这样的作家以戏谑式的解构之法来超越苦难,获得解脱。
新时期文学对苦难意识的多面思考,对救赎方式的多种尝试,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与启示作用。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苦难意识;救赎苦难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境遇,虽然其本身并非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但是在感受、承担和反思苦难这一客观事实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一种现实价值和理想价值。
换句话说,当苦难从一种客观事实上升为一种人类所独有的自觉意识——苦难意识——的时候,人们便会从浮华的现实苦难表象潜入深沉的人生底蕴,从而体验人类生命的独特价值。
因这种特殊价值,苦难意识与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具有相通性,成为众多文学家与艺术家常用的创作主题。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许多作家对苦难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的探索,并以多种方式来超越苦难,寻求救赎。
一、严肃式苦难救赎随着“寻根” 的出现,一种现代精神层面上的苦难意识开始被中国当代作家们重视。
自此之后,苦难成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
在对苦难的直面追问与对救赎的勇敢探寻中,一些作家从民族文化、历史、人性等宏大角度对苦难意识进行了严肃式的反思与救赎。
张承志因其在异国他乡的漂泊经历而产生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意识。
他在散文《无援的思想》中提醒国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在世界文明的战场上实际处于弱势,我们应该怀有民族危机意识,不能沦为新的地,即文化的地。
他期盼着民族文化的出现:“我一直想,文明的战争结束时,失败者的废墟上应当有拼死的”1。
于是张承志救赎民族文化苦难的方式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他高呼“今天需要抗战文学。
论张炜小说《独药师》中的流浪意识《独药师》是张炜在2011 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五年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作品以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革命为背景,讲述了基督教徒登陆山东半岛,传统教育与医疗被西式学校及西式医院所干扰,半岛的养生世家季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小说以长生秘籍为背景,将时代与革命相融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神秘色彩,将季府传人季昨非对长生、爱情、革命的倔强追寻描述得淋漓尽致,并一以贯之涉及张炜小说中通有的流浪意识。
本文将分析张炜长篇小说《独药师》中流浪意识的内涵、形成原因及体现。
一、流浪意识的内涵(一)对自由的倔强追寻《你在高原》《九月寓言》《我的田园》等作品都展现出主人公对自由的倔强追寻。
《你在高原》中的宁吉虽然年事已高,却执着于寻找醉虾,不远万里骑着大红马跨越南方,有着令人无法理解的痴狂。
《九月寓言》中的小村人不断奔跑、停留、再奔跑,漂泊、栖居、再漂泊,实际上也是对心中理想的倔强追寻。
小说《独药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倔强心灵”。
张炜的流浪意识并不是单指单纯的“倔强”,不是简单地与性格相关,而是指一份倔强追寻纯洁的流浪心灵,是指对真理的爱与自由追寻。
有着这种心灵的人不会搞机会主义,他们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会一直走下去,对真实和纯洁度有着至死不渝的追求。
《独药师》中季府老爷季昨非对长生、爱情、革命的追寻都与这种生命品质有关。
张炜怜惜有着这样心灵和品质的人,愿意把心血之作献给他们,他作品中通有的流浪意识,无不表现出其对自由的倔强追寻。
(二)对人类精神构建的思考精神是一种能够自由活动、有生命迹象的属于生物范畴内的存在形式,而构建人类精神一般指构建人类良好的品性。
张炜本身没有那么强烈的物质欲望,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竞争意识,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下,快节奏的生活逐渐成为潮流,一部分人变得急功近利,本应自由纯真的人性逐渐被改变,也不再对质朴美好的事物进行追寻。
张炜曾说过,人一旦陷入物质潮流中,再想葆有对大自然的敏感和敬畏之心,将是十分困难的。
论张炜小说的苦难性
摘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炜是重要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中,以其独特的创作,众多的作品,张炜小说深刻地描写了女性的苦难,社会的苦难,文革的苦难,张炜对苦难的描写真实而生动,具有典型的悲剧意义和深沉的悲剧力量,张炜从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人物的悲剧,发现他的作品深藏于其中的苦难。
关键词:张炜苦难女性社会文革
1 女性的苦难
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在社会中承受了了身体的苦难。
张炜的作品中,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凶残与丑陋,对女性的身体所承受的苦难做了淋漓尽致而生动详细的描写,尤其是女性身体遭受暴力的侵犯。
“后来那些狗娘养的还不是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
其实早就糟蹋了。
她忍着羞辱,因为要活着侍奉公爹。
”一个女性被生活所逼,成了裸体模特。
“再后来又有人提出给她画裸体素描,她扭扭捏捏,还是答应了。
就这样,关于她的裸体画不知怎么落到了其他人手里。
有关部门追查起来,就找到了她。
那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差点儿把这个姑娘从根上毁了。
当时她气愤地提出给自己做个体检,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姑娘。
可是这种检查不但没有给她带来更好的名声,反而使她的誉一落千丈。
在街道上,她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一走向街头,人们就尾随她,有的还对她做出各种淫荡的手势。
”
女性不仅承受了身体的苦难,还承受了精神和心灵的苦难。
张炜通过女性形象的描写,尤其是女性既没有财产权又失去尊严的生存状况,她们只能在社会中动荡浮沉,受尽非人的侮辱,却没有任何出路。
2 社会的苦难
张炜以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广阔地描写了当今社会,再现了当今社会的黑暗。
“其实人家倒极有可能是新贵,是传统农民蜕变而成的第三代,是孙子,这些孙子一旦进了城,做高官做大买卖,或者更有甚者,敢组织黑市社会贩毒走私,收藏吓人的艺术品。
”
张炜尤其描写了农场的工人的生活,农场的工人的工作环境的恶劣。
去年的这时候,一个人比你还年轻呢,只伤了一个小脚趾,后来先把两根脚趾截去,再后来又是截取脚掌。
这里条件太差。
张炜用第一人称“我”,更加直接地真实地揭露当今社会的苦难。
当父亲好不容易结束了牢狱之灾,欢天喜地与荒原上的一家人会合是,怎么会想到更漫长的苦役在等待他?不久就被押到南山的水利工地上了,编在了一些由释放的罪犯组成的二队。
民工春夏秋一律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冬天则搬到深入地面二分之一的地窖子,”以几个段落的描写了当今社会的苦难。
张炜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苦难,“于是他们重新找来一副脚铐,是刚刚让铁匠锻出来的,还没有凉透就硬套到你父亲脚上。
那时他脚踝上的皮立刻掉下来,满街
都听到父亲撕心裂肺的喊叫,这帮丧尽天良的人哪,对待自己人比对待敌人还凶残十倍。
母亲生前诉说着那个场面,泪水哗哗地流下来。
”张炜的这一小段就写出了社会的苦难,人性的狠毒,丑陋,无情。
2 文革的苦难
张炜用细腻而真实的手法表现了文革的苦难,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革的混乱环境中描写了文革的苦难,文革中的一位老教授就是其中之一的典型。
“文革中的一位老教授再也没出来,押的时候有两个解差,还带了锁链,解差穿着黑衣服,开着黑车,把他呜呜地拉走了。
上边的人要他写一份材料,他就是不写,上边的人问话,他偏要反着答。
后来上边的人气急了,就揍他,狠狠滴揍。
眼前的这个小屋紧靠着锅炉烟囱垒成,挤得只剩下一点点空间,又没有通风处,可以想见这里的夏天会怎样,那一定挤得像个大蒸笼。
老人指着土坯上的通洞说:“看见了吧?这些通洞还在,当年那些家伙就从这儿往里望。
最可恶的是,老教授死了,儿媳妇也给折磨死了,他们还向上汇报说,说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什么,那个闺女才羞死了”那年夏天老教授和他的儿媳就关在这间屋子里—他们故意让两人在一块儿,故意往锅炉里塞煤火,因为农场有个小作坊需要蒸气,住在这儿的人天天湿淋淋的,要想不给闷死热死,就得不停地喝水,冲洗。
”文革,这个早就成为过去的历史词汇,在张炜的文学作品中,它却是刺激人心灵的词汇,又一次展现了文革的苦难。
文革深刻的苦难。
3 结语
张炜的作品众多,深刻独特,细腻真实地描写了人类的苦难。
张炜小说深刻地描写了女性的苦难,社会的苦难.,文革的苦难,张炜对苦难的描写真实而生动,具有典型的悲剧意义和深沉的悲剧力量,张炜从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人物的悲剧,张炜以人道主义和悲悯的心创作,再现了张炜的道德精神。
参考文献:
[1]忆阿雅[M].作家出版社,2010,4,
[2]韩晓岚. 论张伟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