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小说中的死亡现象
- 格式:pdf
- 大小:168.59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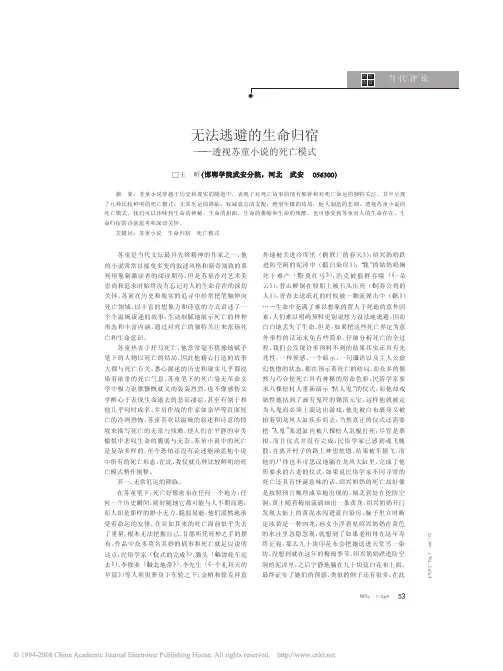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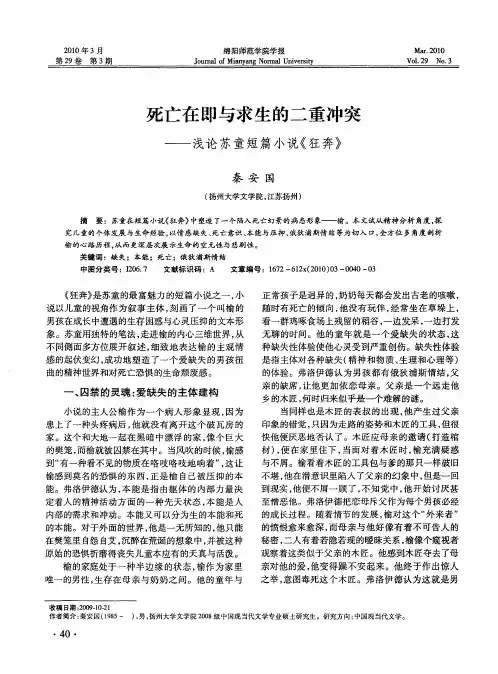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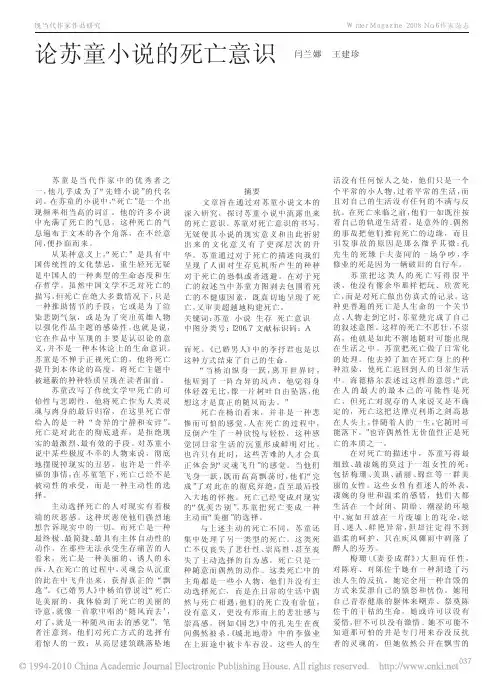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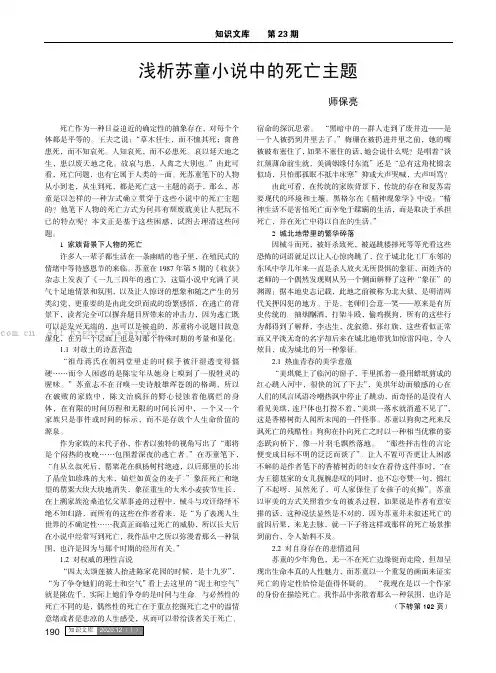
浅析苏童小说中的死亡主题师保亮死亡作为一种日益迫近的确定性的抽象存在,对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
王夫之说:“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
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
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
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
”由此可看,死亡问题,也有它属于人类的一面。
死苏童笔下的人物从小到老,从生到死,都是死亡这一主题的高手,那么,苏童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确立贯穿于这些小说中的死亡主题的?他笔下人物的死亡方式为何具有颓废耽美让人把玩不已的特点呢?本文正是基于这些困惑,试图去理清这些问题。
1 家族背景下人物的死亡许多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一条幽暗的巷子里,在殖民式的情绪中等待感恩节的来临。
苏童在1987年第5期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篇小说中充满了灵气十足地情景和氛围,以及让人惊讶的想象和随之产生的另类幻觉,更重要的是由此交织而成的纷繁感悟,在逃亡的背景下,读者完全可以摒弃题目所带来的冲击力,因为逃亡既可以是发兴无端的,也可以是被迫的,苏童将小说题目故意虚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对那个特殊时期的考量和显化。
1.1 对故土的诗意营造“祖母蒋氏在朝祠堂里走的时候手被汗湿透变得僵硬……而令人困惑的是陈宝年从她身上嗅到了一股牲灵的腥味。
”苏童志不在召唤一史诗般雄浑苍朗的格调,所以在破败的家族中,陈文治疯狂的野心侵蚀着他腐烂的身体,在有限的时间历程和无限的时间长河中,一个又一个家族只是事件或时间的标示,而不是存放个人生命价值的源泉。
作为家族的末代子孙,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写出了“那将是个闷热的夜晚……包围着深夜的逃亡者。
”在苏童笔下,“自从幺叔死后,罂粟花在枫杨树村绝迹,以后那里的长出了晶莹如珍珠的大米,灿烂如黄金的麦子。
”象征死亡和绝望的罂粟大块大块地消失,象征重生的大米小麦拔节生长,在上溯家族沧桑追忆父辈事迹的过程中,械斗与攻讦络绎不绝不知归路,而所有的这些在作者看来,是“为了表现人生世界的不确定性……我真正面临过死亡的威胁,所以长大后在小说中经常写到死亡,我作品中之所以弥漫着那么一种氛围,也许是因为与那个时期的经历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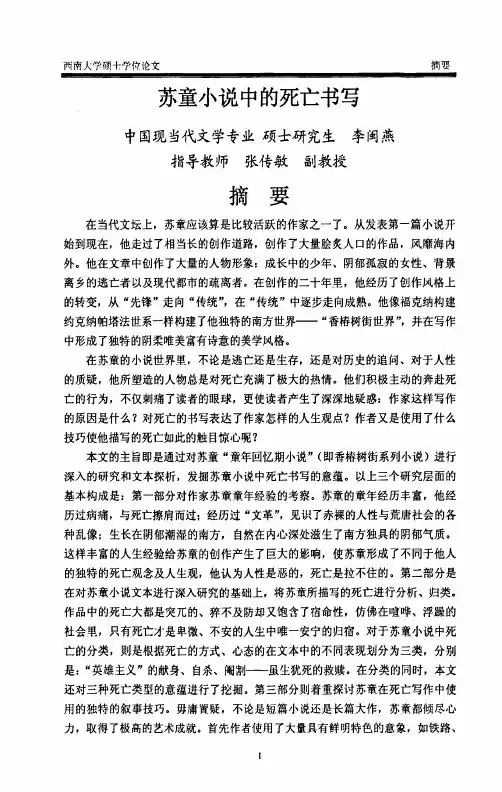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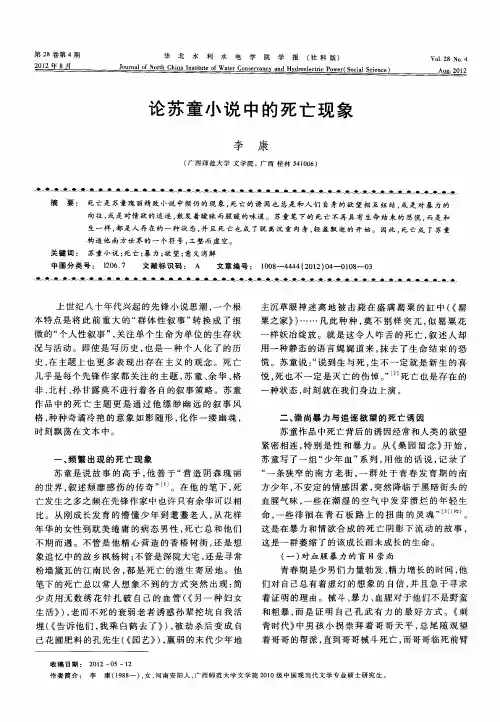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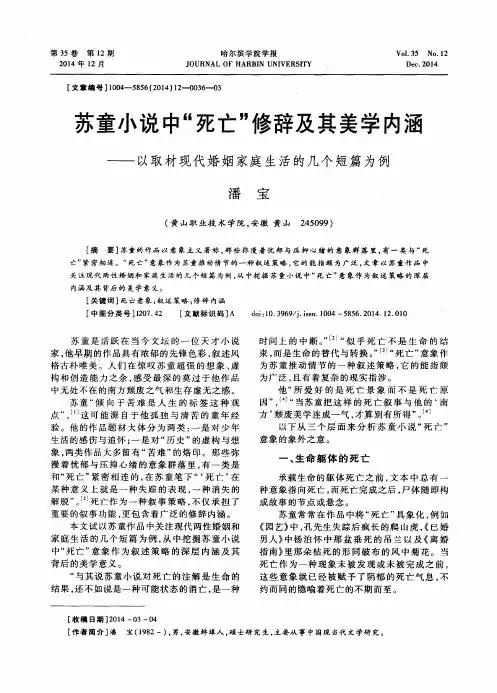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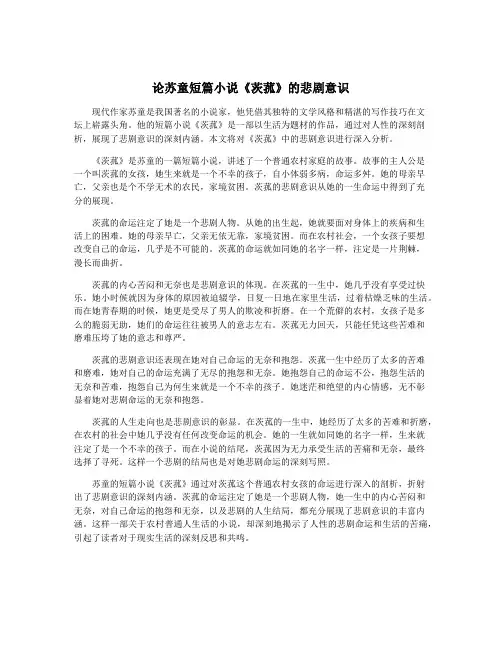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现代作家苏童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他凭借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精湛的写作技巧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他的短篇小说《茨菰》是一部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通过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展现了悲剧意识的深刻内涵。
本文将对《茨菰》中的悲剧意识进行深入分析。
《茨菰》是苏童的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茨菰的女孩,她生来就是一个不幸的孩子,自小体弱多病,命运多舛。
她的母亲早亡,父亲也是个不学无术的农民,家境贫困。
茨菰的悲剧意识从她的一生命运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茨菰的命运注定了她是一个悲剧人物。
从她的出生起,她就要面对身体上的疾病和生活上的困难。
她的母亲早亡,父亲无依无靠,家境贫困。
而在农村社会,一个女孩子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茨菰的命运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注定是一片荆棘,漫长而曲折。
茨菰的内心苦闷和无奈也是悲剧意识的体现。
在茨菰的一生中,她几乎没有享受过快乐。
她小时候就因为身体的原因被迫辍学,日复一日地在家里生活,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
而在她青春期的时候,她更是受尽了男人的欺凌和折磨。
在一个荒僻的农村,女孩子是多么的脆弱无助,她们的命运往往被男人的意志左右。
茨菰无力回天,只能任凭这些苦难和磨难压垮了她的意志和尊严。
茨菰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她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和抱怨。
茨菰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磨难,她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了无尽的抱怨和无奈。
她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公,抱怨生活的无奈和苦难,抱怨自己为何生来就是一个不幸的孩子。
她迷茫和绝望的内心情感,无不彰显着她对悲剧命运的无奈和抱怨。
茨菰的人生走向也是悲剧意识的彰显。
在茨菰的一生中,她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折磨,在农村的社会中她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命运的机会。
她的一生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生来就注定了是一个不幸的孩子。
而在小说的结尾,茨菰因为无力承受生活的苦痛和无奈,最终选择了寻死。
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局也是对她悲剧命运的深刻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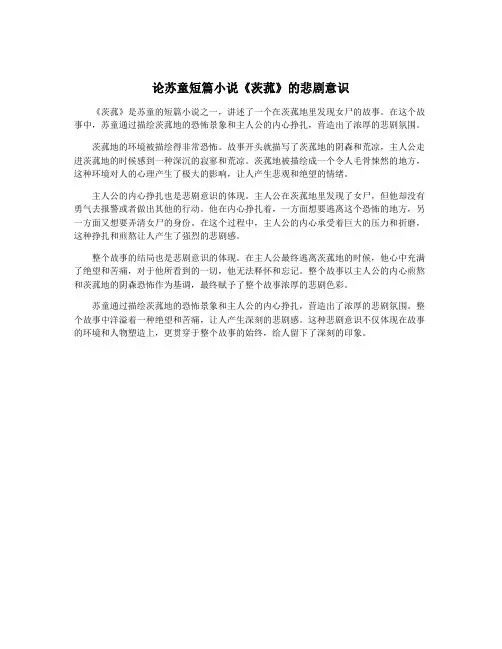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
《茨菰》是苏童的短篇小说之一,讲述了一个在茨菰地里发现女尸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苏童通过描绘茨菰地的恐怖景象和主人公的内心挣扎,营造出了浓厚的悲剧氛围。
茨菰地的环境被描绘得非常恐怖。
故事开头就描写了茨菰地的阴森和荒凉,主人公走进茨菰地的时候感到一种深沉的寂寥和荒凉。
茨菰地被描绘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这种环境对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人产生悲观和绝望的情绪。
主人公的内心挣扎也是悲剧意识的体现。
主人公在茨菰地里发现了女尸,但他却没有勇气去报警或者做出其他的行动。
他在内心挣扎着,一方面想要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想要弄清女尸的身份。
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折磨,这种挣扎和煎熬让人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感。
整个故事的结局也是悲剧意识的体现。
在主人公最终逃离茨菰地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绝望和苦痛,对于他所看到的一切,他无法释怀和忘记。
整个故事以主人公的内心煎熬和茨菰地的阴森恐怖作为基调,最终赋予了整个故事浓厚的悲剧色彩。
苏童通过描绘茨菰地的恐怖景象和主人公的内心挣扎,营造出了浓厚的悲剧氛围。
整个故事中洋溢着一种绝望和苦痛,让人产生深刻的悲剧感。
这种悲剧意识不仅体现在故事的环境和人物塑造上,更贯穿于整个故事的始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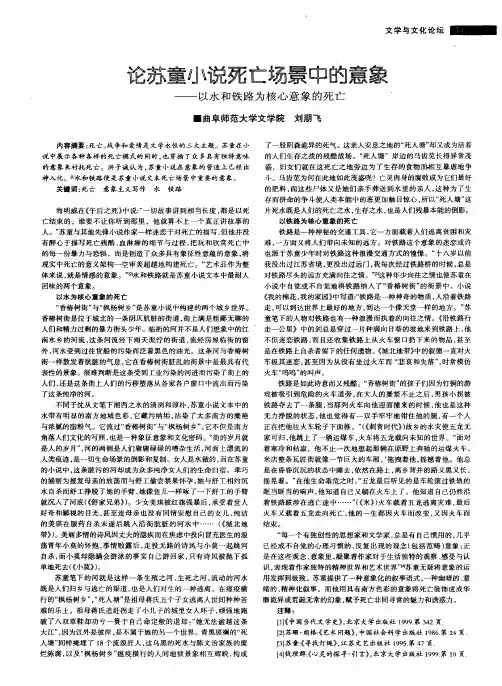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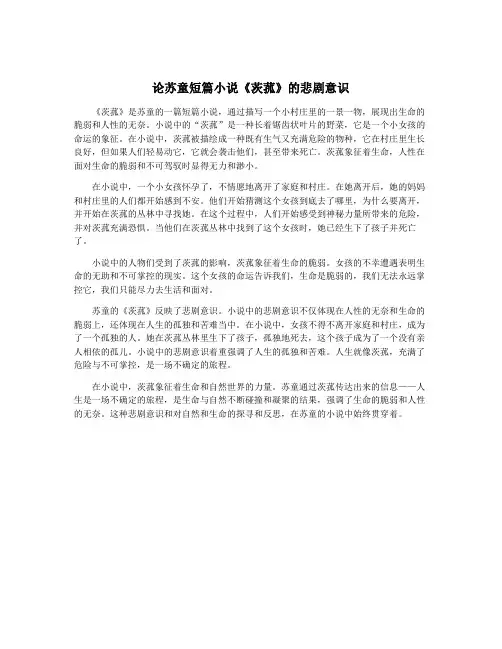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茨菰》是苏童的一篇短篇小说,通过描写一个小村庄里的一景一物,展现出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无奈。
小说中的“茨菰”是一种长着锯齿状叶片的野菜,它是一个小女孩的命运的象征。
在小说中,茨菰被描绘成一种既有生气又充满危险的物种,它在村庄里生长良好,但如果人们轻易动它,它就会袭击他们,甚至带来死亡。
茨菰象征着生命,人性在面对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驾驭时显得无力和渺小。
在小说中,一个小女孩怀孕了,不情愿地离开了家庭和村庄。
在她离开后,她的妈妈和村庄里的人们都开始感到不安。
他们开始猜测这个女孩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要离开,并开始在茨菰的丛林中寻找她。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感受到神秘力量所带来的危险,并对茨菰充满恐惧。
当他们在茨菰丛林中找到了这个女孩时,她已经生下了孩子并死亡了。
小说中的人物们受到了茨菰的影响,茨菰象征着生命的脆弱。
女孩的不幸遭遇表明生命的无助和不可掌控的现实。
这个女孩的命运告诉我们,生命是脆弱的,我们无法永远掌控它,我们只能尽力去生活和面对。
苏童的《茨菰》反映了悲剧意识。
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不仅体现在人性的无奈和生命的脆弱上,还体现在人生的孤独和苦难当中。
在小说中,女孩不得不离开家庭和村庄,成为了一个孤独的人。
她在茨菰丛林里生下了孩子,孤独地死去,这个孩子成为了一个没有亲人相依的孤儿。
小说中的悲剧意识着重强调了人生的孤独和苦难。
人生就像茨菰,充满了危险与不可掌控,是一场不确定的旅程。
在小说中,茨菰象征着生命和自然世界的力量。
苏童通过茨菰传达出来的信息——人生是一场不确定的旅程,是生命与自然不断碰撞和凝聚的结果,强调了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无奈。
这种悲剧意识和对自然和生命的探寻和反思,在苏童的小说中始终贯穿着。
《狂奔》中的死亡恐惧摘要:苏童的短篇《狂奔》可以看作是一首诗样的小说,是他对人生,对生命思索探询之后的产物。
在该小说中,苏童所力图表现的,是一种自儿童身上观照出的人类普遍宿命的深渊和人在命运漩涡中挣扎以期找到并“狂奔”出一条出路的本能努力。
而恰是由于儿童视点的选取,使作品的内涵意义更趋深刻和耐人寻味。
关键词:文学作品;恋母情结;死亡;恐惧《狂奔》是苏童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小说完全按照一个儿童的经验方式来叙事,以农村男孩榆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死亡恐惧和俄底浦斯情结这两种情感为主线(主线之中又以死亡恐惧为主),最终死亡恐惧导致主人公向着期待摆脱死亡的境地“狂奔”的结局。
小说两条线索中的死亡恐惧淹没一切的结局把读者引向了对人的生命及其价值的质疑与探询之中。
首先,男孩榆的恋母情结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在榆的眼中,他的母亲有着“很黑很亮的长发”;生活中父亲形象的缺失使得榆本能地抗拒有着父亲特质的一切男人,正是这种抗拒使得榆对母亲有着更深厚的依赖感和占有欲。
弗洛伊德认为,俄底浦斯情结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性本能,同时也是双亲的刺激加强了这种倾向。
在此情形之下,男孩早就对他的母亲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柔情,视母亲为自己的所有物,而把父亲看成是争得此所有物的敌人,并想取代父亲在父母关系中的地位。
小说中的王木匠不仅是因为走路姿势和随身携带着木匠工具的样子象榆的父亲,更是因为他走进了榆的家走进了榆的生活,夺去了母亲对榆的专注的爱。
榆在心中把木匠幻化成他的父亲这一角色,于是产生了针对王木匠的弒父的冲动。
小说中榆偷听自己母亲与木匠谈话、试图赶走王木匠的努力甚至毒杀王木匠的行动都是榆潜意识当中对于母亲的占有欲和对父亲的本能抗拒的具体体现。
而试图赶走王木匠进而下毒杀死他都是在王木匠进入榆的生活之后,其时,榆的母亲对王木匠一种莫名其妙的处处维护,对儿子反而表现出不耐烦,甚至漠不关心。
榆敏感地认为正是王木匠对于其生活的介入使得母亲对自己的爱发生了偏离和转移,这些因素都促使榆消除异己行为的发生。
现当代文学苏童小说中死亡书写的审美效果及独特意义探微——以《城北地带》、《舒家兄弟》为例冯燕茹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死亡是苏童小说中一道独特的景观,在苏童的小说中“死亡”这个意象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苏童对于死亡的书写有别于其他作家,他对死亡柔和温婉的描写使得这一意象被赋予了新的美学意蕴。
本文以《城北地带》、《舒家兄弟》为例来探讨苏童的死亡描写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和别样的审美效果,从而能更好的理解苏童独特的死亡叙述。
关键词:苏童;死亡叙述;审美效果苏童是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成绩斐然且创作风格独特,他以瑰丽的文笔和奇特的想象为我们构造了一个个哀婉凄迷的故事,以极大热情来建构故事的他被称为“说故事的高手”。
在他的故事中人物常常被赋予死亡的结局,死亡是苏童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
本文通过探讨其死亡叙述的审美效果及意义来阐释苏童对生死的别样理解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一、对死亡的审美刻画苏童凭借丰富多样的创作方法、出众的想象和诗意的语言总是能营造出一种颓废唯美的小说风格,这是他的创作追求和独具的文学魅力。
所以他的死亡叙述也有别于其他作家,他精致的描写和奇特的语言赋予死亡以别样的色彩,给读者一种审美的体验,从而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厌恶之感。
《舒家兄弟》中描写了涵丽死后依然美丽的姿态,她躺在地板上,浑身不停地滴着水,她身边的水和她的身体散发着蓝色的魅惑的光泽,她的眼睛张开着,比黑暗里的猫眼更具有吸引力。
这样的描写在给人以独特的美的感受外,更增加了读者对年轻生命逝去的哀婉和叹息。
《城北地带》里被红旗强暴后跳水自杀的美琪死后变成了幽灵,经常出现在香椿树街,但见过幽灵美琪的人一致认为死后的美琪更加美丽了。
幽灵美琪穿着一条绿裙子,湿漉漉的、乌黑的长发齐腰披散着,她的容貌笼罩在一圈绿色的神秘光晕里,楚楚动人,头发上还戴着一个用夜饭花串成的花饰,手里握着一沓鲜艳的蜡纸红心。
幽灵美琪的形象不像人们印象中的鬼魂那样凄厉恐怖,而是温婉美丽、楚楚可怜,她在香椿树街游荡着诉说着自己的冤屈和不幸。
苏童小说的死亡叙事作者:马炜关键词:苏童死亡叙事认知意义美学效果摘要:本文试图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观照下,对苏童笔下人物的死亡形态进行归类,从大量有别于传统的非理性的死亡叙事中探讨理性的认知价值和意义,从而阐释死亡叙事给小说文本带来的独特美学效果。
纵观苏童小说,可以发现他在小说中使用死亡笔墨的频率非常高。
他小说中人物的死亡,大多在一种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原因和意义。
而且,他写死亡也似乎并没有先行的目的设定。
这些都使他笔下的死亡叙事从小说文本中凸显出来,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死亡叙事的审美意蕴。
苏童是作为先锋派的一员而崛起于文坛上的。
上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后现代各种文学观念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西方哲学思潮也大量涌入中国,叔本华、柏格森、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等的哲学学说带给先锋作家看待社会、人生的一种全新的视角。
笔者认为,苏童小说中对人物死亡形态的展示,传达给读者的思考,以及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审美意蕴,其实都是与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暗合的。
他对死亡的异质性言说,呈现出别样的美学风格,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也给小说文本带来了更大的意义阐释空间。
一、死亡形态的展示如果按照死亡主体的意愿参与与否来加以划分的话,苏童笔下大量的死亡叙事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即自杀和莫名的祸事。
苏童小说中的人物选择自杀,有些是因为做了错事,迫于道德压力,以死亡来求解脱。
如《一无所获》中的李蛮因推开女浴室的门,被人唾弃,跳河自杀;《舒家兄弟》中的少年涵丽和舒工偷尝禁果,导致涵丽怀孕,两人跳河自杀;《妇女生活》中的邹杰欲对养女不轨被妻子发现,含愧卧轨自杀。
也有的是自己对生活绝望,把死亡当作是摆脱烦俗人生的最好归宿。
《白沙》中雪莱选择海葬结束生命;《我的棉花,我的家园》中的书来逃难,最后无处可逃,卧轨自杀;《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简少贞用无数绣花针扎破动脉血管而死;《平静如水》的雷鸟屡次被女孩骗而卧轨自杀……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冲动,这个冲动最初是向着自我而迸发的。
苏童《1934年的逃亡》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作者简介苏童,1963年1月生于江苏苏州,在苏州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期间开始学习写作,并在1983年发表小说处女作。
1984年到南京工作,1986年调入《钟山》杂志社当文学编辑至今。
著有长篇小说《米》、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红粉》、短篇小说集《伤心的舞蹈》、《祭奠红马》等作品。
内容概要1934年是个灾年。
我祖母蒋氏拖着怀孕的身子在财东陈文治家的水田里干活。
陈文治站立在东北坡地的黑砖楼上,从一架日本望远镜里窥视着蒋氏的一举一动,脸上漾满了痴迷的神色。
蒋氏是个丑女人,祖父陈宝年18岁娶了她。
陈宝年从前路遇圆脸肥臀的女人就眼泛红潮穷追不舍,兴尽方归。
陈宝年娶亲的第一夜,他骑在蒋氏身上俯视她的脸,不停地唉声叹气“你是灾星”。
以后的七个深夜陈宝年重复着他的预言。
1934年陈宝年一直在城里吃喝嫖赌、潜心发迹,没回过我的枫杨树老家。
在我已故亲人中,陈家老大狗崽以一个拾粪少年的形象站立在我们家史中。
蒋氏对狗崽说,你拾满一竹箕粪可以换两个铜板,攒够了钱娘给你买双胶鞋穿。
对一双胶鞋的幻想使狗崽的1934年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不过,他得到的铜板没有交给蒋氏而放进一只木匣子里。
那只木匣子在某个早晨失踪了。
蒋氏说,你非要那胶鞋,就把娘肚里的孩子打掉,省下钱给你买。
狗崽对着娘的腹部连打三拳。
那被击打的胎儿就是我父亲。
在收割季节里,蒋氏在干草垛上分娩了父亲。
陈文治借助望远镜窥见了分娩的整个过程后,瘫软在楼顶。
下人赶来时发现他那白锦缎裤子亮晶晶湿了一片。
陈文治和陈宝年祖上是亲戚。
陈宝年曾用他妹妹凤子跟陈文治换了十亩水田。
凤子给陈文治当了两年小妾,生下三个畸形男婴,被陈文治活埋了。
事后不久凤子就死了。
陈文治家有只白玉瓷罐,里面装着枫杨树人所关心的绝药。
一天,狗崽被陈文治骗到谷仓里,他萌芽时期的精液滴进了白玉瓷罐里。
事后陈文治给了他一双胶鞋。
在城里运竹子的人回来说,陈宝年发横财了。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苏童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短篇小说《茨菰》是一部富含悲剧意识的作品。
本文从小说的主题与结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等方面来分析苏童在《茨菰》中呈现的悲剧意识。
《茨菰》的主题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荒诞进行的深刻瞭望。
故事围绕着小女孩茨菰的死亡展开,通过揭示封建农村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以及贫困、疾病等现实问题,展现了人们在困境中的无力与痛苦。
茨菰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悲剧,是社会不给予弱势群体帮助的体现,以及生命的脆弱与无助。
作者通过表现这种悲剧意识,使人们反思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薄情。
小说的结构紧凑且富有张力。
作者通过星月的视角来引导读者进入故事,使得故事在视觉上具有鲜明的对比。
星月看到了茨菰的死亡,也色彩鲜明地展示了尘世的残酷与深沉的爱。
小说中的情节设置多层次,剧情紧凑,扣人心弦。
作者通过茨菰的死亡和星月的追忆,揭示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人们的面临的困境。
这种追溯的叙事形式,使读者对悲剧故事的经过和结果产生了更加深远的思考。
作者通过细腻且立体的人物塑造,体现了悲剧意识。
茨菰是一个纯真善良的小女孩,她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渴望,然而她却成了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茨菰的死亡不仅显示了社会对弱者的冷漠与无情,也暴露了茨菰自身的无助与软弱。
而星月则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她是茨菰的亲人,既是她的姐姐又是她的母亲。
星月对于茨菰的死亡带来了深深的悔恨和内疚,她一方面认识到了自己对茨菰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对社会的冷漠感到愤怒和无奈。
星月在茨菰死后的痛苦中不断反思自己和社会,体现了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小说中的情节设计也体现了悲剧意识。
茨菰的死亡是既无法预见又不可避免的悲剧。
尽管她父母尽力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封建社会中的陈规陋习和无情的观念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
当茨菰的父母找到当地的乡村医生时,医生对他们的无情和忽视很明显。
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和无知使得茨菰的死变得更加令人痛心。
茨菰的死让人们看到了生活中的无奈与悲剧,并且呈现了这个社会对待弱势群体的无情与冷漠。
论苏童短篇小说《茨菰》的悲剧意识《茨菰》是苏童的一篇短篇小说,通过对一个普通村庄中的一段悲惨命运的描写,呈现出了对人生的悲剧意识。
故事的主要人物是陈老二和茨菰。
从一开始,苏童就通过对这两个角色做了许多细致描写来刻画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命运。
陈老二是村庄里的穷人,因手脚不灵便而被人称为“瘸子”,一生都在挣扎着度过。
而茨菰,则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由于出生的时候有些“降头”,被村庄里的人嫉妒,父母因此对她疏远。
陈老二和茨菰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陈老二靠着卖茨菰的钱维持生计,而茨菰则找到了一个给她提供温暖的家庭。
他们之间的交往是这个村庄里唯一的温暖,两个生命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安慰。
然而,这种安慰并没有持续很久。
一场意外导致了茨菰去世,陈老二也因此失去了仅有的支撑。
这场意外更让人们认为茨菰是一位“降头姑娘”,这使得陈老二也因此受到村庄里的排斥,没有人再向他购买茨菰,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最终,他不得不贩卖茨菰时被一辆车撞死。
整个故事被悲剧的情绪所笼罩。
苏童透过主角的命运,露出了人们生活中的悲哀和无能为力。
他没有对陈老二和茨菰的人物性格做出太多强调,而是更注重描绘他们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他们的命运被安排在一个极其简陋而难以逃避的现实之中,这种现实是多么残酷和无情。
整个故事传递出的意义是:即使是最努力和热情的人,最终也不可能摆脱生命的全部挫折。
苏童通过陈老二和茨菰的命运所暴露出的深度悲哀,实现了一种对人生的深刻反思。
即便快乐,幸福的时光也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是艰辛与悲苦相伴。
命运从人的脆弱身上得到了证明,而这种证明并没有任何安慰。
在《茨菰》中,苏童让人们意识到生命无法掌控的无常,无论是个人一生中的巨大灾难,还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冲突,都在暗示着人生的狂欢与忧伤。
那些在生活中扮演微小角色的人们,他们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微弱无表,但正是这些全然不同的生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体系。
这种生命观不仅对当代社会的人们有着重要的启示,也给了这个充满着悲剧气质的故事一个坚实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