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童小说中的电影特质
- 格式:doc
- 大小:52.00 KB
- 文档页数: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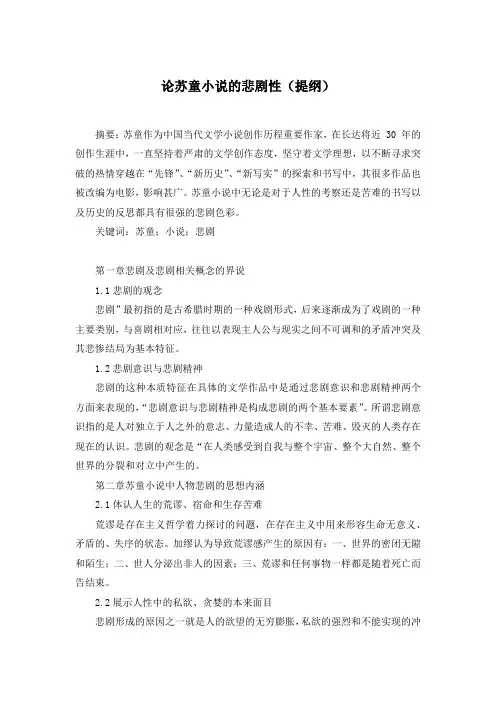
论苏童小说的悲剧性(提纲)摘要:苏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小说创作历程重要作家,在长达将近 30 年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坚持着严肃的文学创作态度,坚守着文学理想,以不断寻求突破的热情穿越在“先锋”、“新历史”、“新写实”的探索和书写中,其很多作品也被改编为电影,影响甚广。
苏童小说中无论是对于人性的考察还是苦难的书写以及历史的反思都具有很强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苏童;小说;悲剧第一章悲剧及悲剧相关概念的界说1.1悲剧的观念悲剧”最初指的是古希腊时期的一种戏剧形式,后来逐渐成为了戏剧的一种主要类别,与喜剧相对应,往往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征。
1.2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悲剧的这种本质特征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是通过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两个方面来表现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是构成悲剧的两个基本要素”。
所谓悲剧意识指的是人对独立于人之外的意志、力量造成人的不幸、苦难、毁灭的人类存在现在的认识。
悲剧的观念是“在人类感受到自我与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的分裂和对立中产生的。
第二章苏童小说中人物悲剧的思想内涵2.1体认人生的荒谬、宿命和生存苦难荒谬是存在主义哲学着力探讨的问题,在存在主义中用来形容生命无意义、矛盾的、失序的状态。
加缪认为导致荒谬感产生的原因有:一、世界的密闭无隙和陌生;二、世人分泌出非人的因素;三、荒谬和任何事物一样都是随着死亡而告结束。
2.2展示人性中的私欲、贪婪的本来面目悲剧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的欲望的无穷膨胀,私欲的强烈和不能实现的冲突造成了人生的多重悲剧。
所以,苏童作品中对悲剧的叙述也是为了展示人性的欲望,揭示人性的本来面目。
2.3颠覆传统文化意义中的生死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在生死问题的选择上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姿态,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走投无路,人物不会选择死亡,但这一传统文化命题在苏童笔下却不再如此呈现。
苏童用种种机会规避历史对人的权威话语,颠覆传统文化的坚不可摧,而“死亡”就是苏童使用频率比较高的颠覆和解构手段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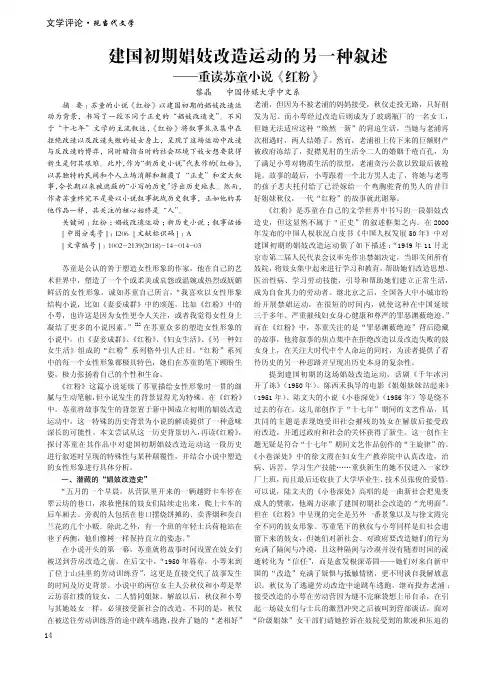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的另一种叙述——重读苏童小说《红粉》黎晶 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摘 要:苏童的小说《红粉》以建国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为背景,书写了一段不同于正史的“娼妓改造史”。
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主流叙述,《红粉》将叙事焦点集中在拒绝改造以及改造失败的妓女身上,呈现了这场运动中改造与反改造的博弈,同时暗指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妓女想要获得新生是何其艰难。
此外,作为“新历史小说”代表作的《红粉》,以其独特的民间和个人立场消解和颠覆了“正史”和宏大叙事,令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小写的历史”浮出历史地表。
然而,作者苏童终究不是要以小说叙事挑战历史叙事,正如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其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
关键词:红粉;娼妓改造运动;新历史小说;叙事话语[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14-03苏童是公认的善于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塑造了一个个或柔美或哀怨或温婉或热烈或妩媚鲜活的女性形象。
诚如苏童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比如《红粉》中的小萼,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或者我觉得女性身上凝结了更多的小说因素。
”[1]在苏童众多的塑造女性形象的小说中,由《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组成的“红粉”系列格外引人注目。
“红粉”系列中的每一个女性形象都极具特色,她们在苏童的笔下顾盼生姿,极力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和生命。
《红粉》这篇小说延续了苏童描绘女性形象时一贯的细腻与生动笔触,但小说发生的背景显得尤为特殊。
在《红粉》中,苏童将故事发生的背景置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娼妓改造运动中,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可能性。
本文尝试从这一历史背景切入,再读《红粉》,探讨苏童在其作品中对建国初期娼妓改造运动这一段历史进行叙述时呈现的特殊性与某种颠覆性,并结合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进行具体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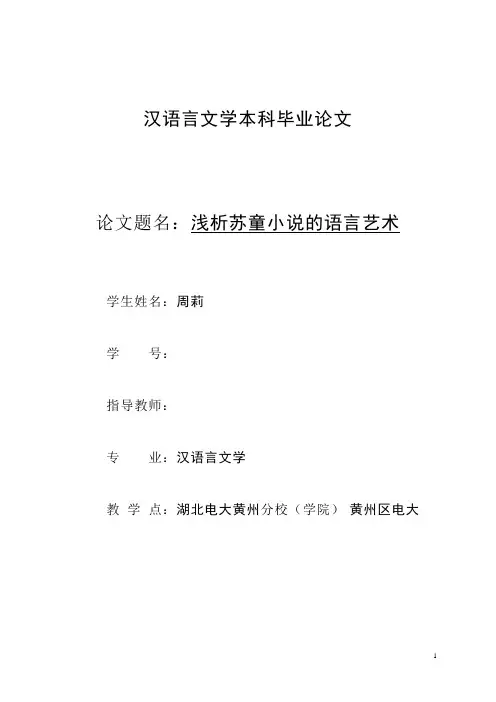
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论文题名:浅析苏童小说的语言艺术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专业:汉语言文学教学点:湖北电大黄州分校(学院)黄州区电大目录论文摘要 (3)关键词 (3)一、细节描述,细致如画 (3)二、表述隐藏于冷静背后的情感 (4)三、语言超常规的变异组合 (5)四、诗意化语言 (7)结束语 (7)参考文献 (8)浅析苏童小说的语言艺术[论文摘要]苏童是我国先锋派青年作家的代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在国内外享有很大的声誉,无可争议地成为青年一代作家的佼佼者。
他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无论是色彩语言的运用还是叙述语言的运用,都体现了这个新生代作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具有创造性的文学素养。
本文对苏童小说试从语言艺术方面细致分析了其中蕴含的奥秘,主要侧重于其小说语言艺术赋予读者的心理感受和审美体验。
[关键词] 苏童语言个性化苏童小说的语言,是极富魅力和创造力的。
他总能悠闲地玩弄着诡异绮丽的诗意般语言,利用娴熟的笔触,让一个个性格扭曲而倍受忽略的人物鲜活起来。
他的作品不断地在农村和城市,过去和现在之间转换,在时空与地域的交错中,在种种充满悲观、孤独、荒谬的情节中,苏童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令人叹服。
一、细节描述,细致如画苏童对“白纸上好画画”满怀信心,他的小说语言常常呈现出强烈的画面感。
在创作过程中,运用通感,比喻等各种复杂的修辞手法,经过变形与幻象,他仿佛打开自己所有的感官,敏锐地捕捉着对声色、光影、触觉和味道的感觉以及那些细碎琐屑的细节,并把它们细腻地表达出来。
1、细微的动作描写颂莲弯腰朝井中看,井水是蓝黑色的,水面上也浮着陈年的落叶,颂莲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沉闷而微弱、有一阵风吹过来,把颂莲的裙子吹得如同飞鸟,颂莲这时感到一种坚硬的凉意,像石头一样慢慢敲她的身体,颂莲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速度很快,回到南厢房的廊下,她吐出一口气,回头又看那个紫藤架,架上倏地落下两三串花,很突然的落下来,颂莲觉得这也很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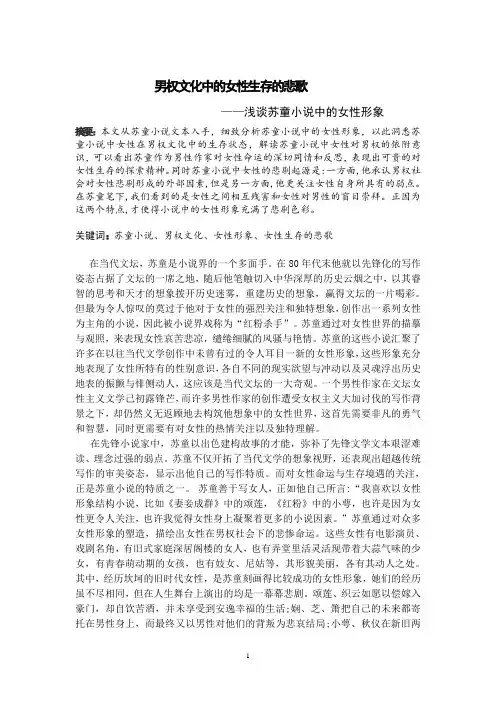
男权文化中的女性生存的悲歌——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摘要:本文从苏童小说文本入手,细致分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洞悉苏童小说中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解读苏童小说中女性对男权的依附意识,可以看出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对女性生存的探索精神。
同时苏童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起源是:一方面,他承认男权社会对女性悲剧形成的外部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女性自身所具有的弱点。
在苏童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之间相互残害和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
正因为这两个特点,才使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
关键词:苏童小说、男权文化、女性形象、女性生存的悲歌在当代文坛,苏童是小说界的一个多面手。
在80年代末他就以先锋化的写作姿态占据了文坛的一席之地,随后他笔触切入中华深厚的历史云烟之中,以其睿智的思考和天才的想象拨开历史迷雾,重建历史的想象,赢得文坛的一片喝彩。
但最为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他对于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想象,创作出一系列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因此被小说界戏称为“红粉杀手”。
苏童通过对女性世界的描摹与观照,来表现女性哀苦悲凉,缱绻细腻的风骚与艳情。
苏童的这些小说汇聚了许多在以往当代文学创作中未曾有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充分地表现了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各自不同的现实欲望与冲动以及灵魂浮出历史地表的振颤与悱侧动人,这应该是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
一个男性作家在文坛女性主义文学己初露锋芒,而许多男性作家的创作遭受女权主义大加讨伐的写作背景之下,却仍然义无返顾地去构筑他想象中的女性世界,这首先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同时更需要有对女性的热情关注以及独特理解。
在先锋小说家中,苏童以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弥补了先锋文学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
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显示出他自己的写作特质。
而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关注,正是苏童小说的特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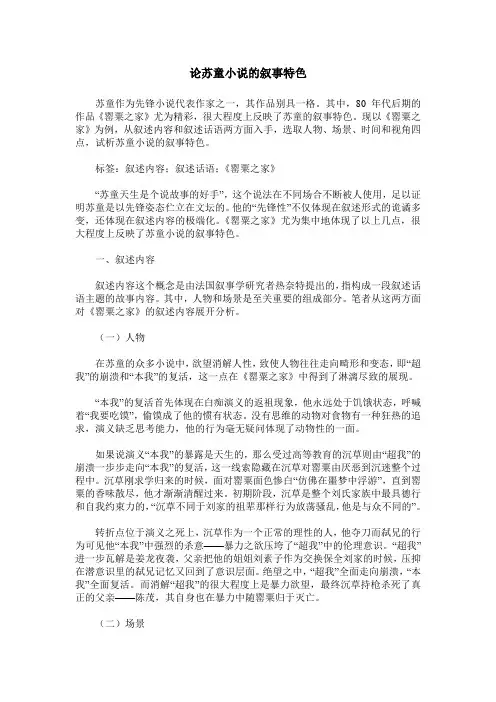
论苏童小说的叙事特色苏童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别具一格。
其中,80年代后期的作品《罂粟之家》尤为精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童的叙事特色。
现以《罂粟之家》为例,从叙述内容和叙述话语两方面入手,选取人物、场景、时间和视角四点,试析苏童小说的叙事特色。
标签:叙述内容;叙述话语;《罂粟之家》“苏童天生是个说故事的好手”,这个说法在不同场合不断被人使用,足以证明苏童是以先锋姿态伫立在文坛的。
他的“先锋性”不仅体现在叙述形式的诡谲多变,还体现在叙述内容的极端化。
《罂粟之家》尤为集中地体现了以上几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童小说的叙事特色。
一、叙述内容叙述内容这个概念是由法国叙事学研究者热奈特提出的,指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
其中,人物和场景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笔者从这两方面对《罂粟之家》的叙述内容展开分析。
(一)人物在苏童的众多小说中,欲望消解人性,致使人物往往走向畸形和变态,即“超我”的崩溃和“本我”的复活,这一点在《罂粟之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本我”的复活首先体现在白痴演义的返祖现象,他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呼喊着“我要吃馍”,偷馍成了他的惯有状态。
没有思维的动物对食物有一种狂热的追求,演义缺乏思考能力,他的行为毫无疑问体现了动物性的一面。
如果说演义“本我”的暴露是天生的,那么受过高等教育的沉草则由“超我”的崩溃一步步走向“本我”的复活,这一线索隐藏在沉草对罂粟由厌恶到沉迷整个过程中。
沉草刚求学归来的时候,面对罂粟面色惨白“仿佛在噩梦中浮游”,直到罂粟的香味散尽,他才渐渐清醒过来。
初期阶段,沉草是整个刘氏家族中最具德行和自我约束力的,“沉草不同于刘家的祖辈那样行为放荡骚乱,他是与众不同的”。
转折点位于演义之死上,沉草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他夺刀而弑兄的行为可见他“本我”中强烈的杀意——暴力之欲压垮了“超我”中的伦理意识。
“超我”进一步瓦解是姜龙夜袭,父亲把他的姐姐刘素子作为交换保全刘家的时候,压抑在潜意识里的弑兄记忆又回到了意识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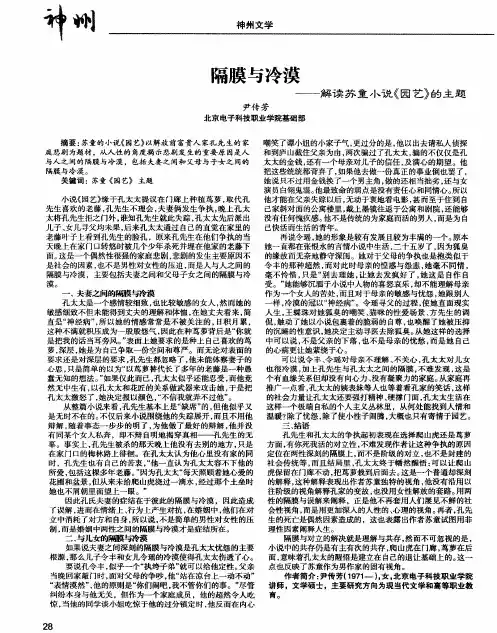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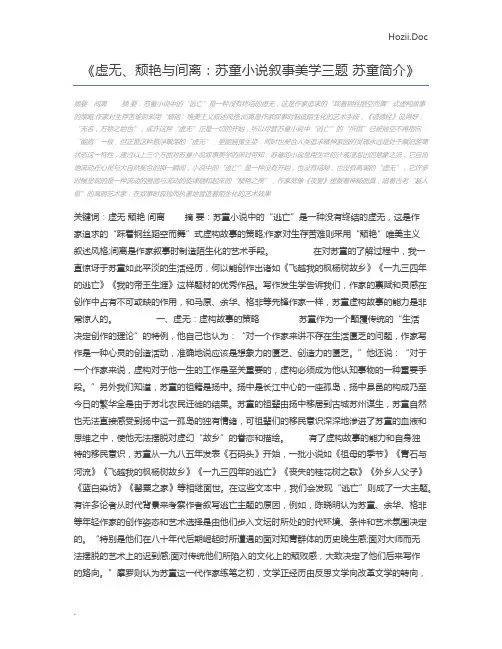
《虚无、颓艳与间离:苏童小说叙事美学三题苏童简介》摘要:间离摘要:苏童小说中的“逃亡”是一种没有终结的虚无,这是作家追求的“踩着钢丝蹈空而舞”式虚构故事的策略;作家对生存苦难则采用“颓艳”唯美主义叙述风格;间离是作家叙事时制造陌生化的艺术手段,《道德经》说得好,“无名,万物之始也”,或许这种“虚无”正是一切的开始,所以尽管苏童小说中“逃亡”的“所指”已被抽空不再指向“能指”一极,但正是这种悬浮飘荡的“虚无”,更能摇曳生姿,同时也契合人类追求精神家园的灵魂永远是处于飘泊游离状态这一特性,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对苏童小说叙事美学的探讨可知,苏童的小说是用生命的汁液浸泡出的意象之流,它自由地流动在心灵与大自然契合的那一瞬间,小说中的“逃亡”是一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也没有高潮的“虚无”,它许多时候呈现的是一种流动的画面与流动的旋律融和起来的“颓艳之美”,作家就像《夜宴》里戴着神秘面具,唱着古老“越人歌”的高明艺术家,在叙事时孤独而执著地营造着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关键词:虚无颓艳间离摘要:苏童小说中的“逃亡”是一种没有终结的虚无,这是作家追求的“踩着钢丝蹈空而舞”式虚构故事的策略;作家对生存苦难则采用“颓艳”唯美主义叙述风格;间离是作家叙事时制造陌生化的艺术手段。
在对苏童的了解过程中,我一直惊讶于苏童如此平淡的生活经历,何以能创作出诸如《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我的帝王生涯》这样题材的优秀作品。
写作发生学告诉我们,作家的禀赋和灵感在创作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和马原、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一样,苏童虚构故事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一、虚无:虚构故事的策略苏童作为一个颠覆传统的“生活决定创作的理论”的特例,他自己也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讲不存在生活匮乏的问题,作家写作是一种心灵的创造活动,准确地说应该是想象力的匮乏、创造力的匮乏。
”他还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虚构对于他一生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虚构必须成为他认知事物的一种重要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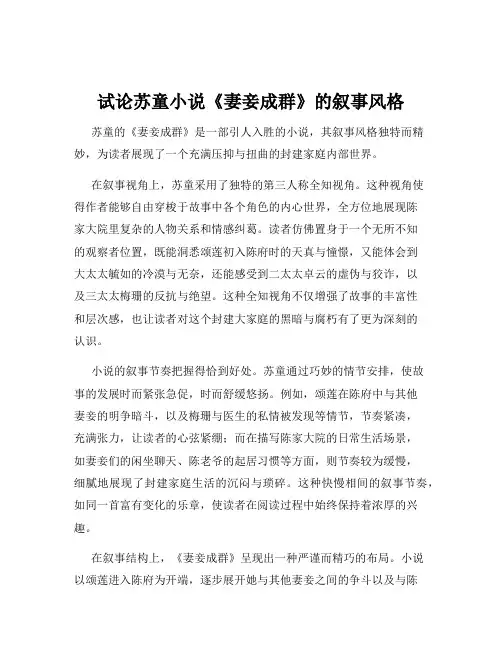
试论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叙事风格苏童的《妻妾成群》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其叙事风格独特而精妙,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压抑与扭曲的封建家庭内部世界。
在叙事视角上,苏童采用了独特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这种视角使得作者能够自由穿梭于故事中各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全方位地展现陈家大院里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
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无所不知的观察者位置,既能洞悉颂莲初入陈府时的天真与憧憬,又能体会到大太太毓如的冷漠与无奈,还能感受到二太太卓云的虚伪与狡诈,以及三太太梅珊的反抗与绝望。
这种全知视角不仅增强了故事的丰富性和层次感,也让读者对这个封建大家庭的黑暗与腐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小说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
苏童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使故事的发展时而紧张急促,时而舒缓悠扬。
例如,颂莲在陈府中与其他妻妾的明争暗斗,以及梅珊与医生的私情被发现等情节,节奏紧凑,充满张力,让读者的心弦紧绷;而在描写陈家大院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妻妾们的闲坐聊天、陈老爷的起居习惯等方面,则节奏较为缓慢,细腻地展现了封建家庭生活的沉闷与琐碎。
这种快慢相间的叙事节奏,如同一首富有变化的乐章,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在叙事结构上,《妻妾成群》呈现出一种严谨而精巧的布局。
小说以颂莲进入陈府为开端,逐步展开她与其他妻妾之间的争斗以及与陈老爷之间的复杂关系。
各个情节环环相扣,相互呼应。
比如颂莲与卓云之间的表面和睦与暗中较量,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梅珊的命运与颂莲的处境也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
这种紧密的结构使整个故事浑然一体,没有丝毫的松散之感。
苏童的语言运用也是其叙事风格的一大特色。
他的文字简洁明快,却又富有表现力。
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精准的刻画,将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例如,“颂莲梳着齐耳的短发,用一条天蓝色的缎带箍住,她的脸是椭圆的,不施脂粉,但显得有点苍白。
”短短几句话,就勾勒出了颂莲的外貌特征和气质。
同时,苏童还善于运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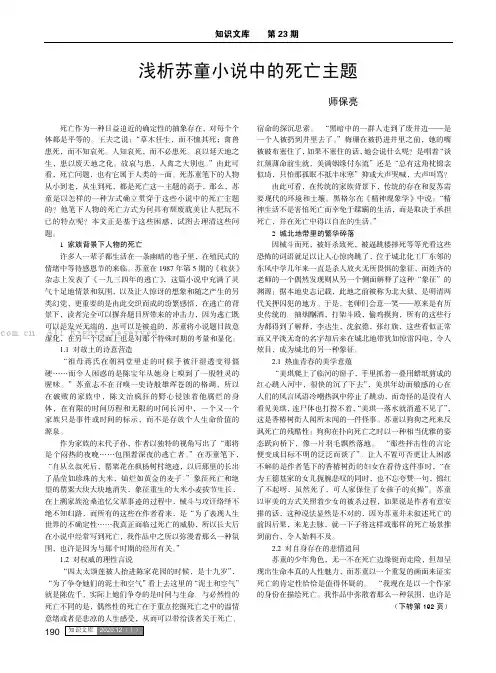
浅析苏童小说中的死亡主题师保亮死亡作为一种日益迫近的确定性的抽象存在,对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
王夫之说:“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兽患死,而不知哀死。
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
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废天地之化。
故哀与患,人禽之大别也。
”由此可看,死亡问题,也有它属于人类的一面。
死苏童笔下的人物从小到老,从生到死,都是死亡这一主题的高手,那么,苏童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确立贯穿于这些小说中的死亡主题的?他笔下人物的死亡方式为何具有颓废耽美让人把玩不已的特点呢?本文正是基于这些困惑,试图去理清这些问题。
1 家族背景下人物的死亡许多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一条幽暗的巷子里,在殖民式的情绪中等待感恩节的来临。
苏童在1987年第5期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篇小说中充满了灵气十足地情景和氛围,以及让人惊讶的想象和随之产生的另类幻觉,更重要的是由此交织而成的纷繁感悟,在逃亡的背景下,读者完全可以摒弃题目所带来的冲击力,因为逃亡既可以是发兴无端的,也可以是被迫的,苏童将小说题目故意虚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对那个特殊时期的考量和显化。
1.1 对故土的诗意营造“祖母蒋氏在朝祠堂里走的时候手被汗湿透变得僵硬……而令人困惑的是陈宝年从她身上嗅到了一股牲灵的腥味。
”苏童志不在召唤一史诗般雄浑苍朗的格调,所以在破败的家族中,陈文治疯狂的野心侵蚀着他腐烂的身体,在有限的时间历程和无限的时间长河中,一个又一个家族只是事件或时间的标示,而不是存放个人生命价值的源泉。
作为家族的末代子孙,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写出了“那将是个闷热的夜晚……包围着深夜的逃亡者。
”在苏童笔下,“自从幺叔死后,罂粟花在枫杨树村绝迹,以后那里的长出了晶莹如珍珠的大米,灿烂如黄金的麦子。
”象征死亡和绝望的罂粟大块大块地消失,象征重生的大米小麦拔节生长,在上溯家族沧桑追忆父辈事迹的过程中,械斗与攻讦络绎不绝不知归路,而所有的这些在作者看来,是“为了表现人生世界的不确定性……我真正面临过死亡的威胁,所以长大后在小说中经常写到死亡,我作品中之所以弥漫着那么一种氛围,也许是因为与那个时期的经历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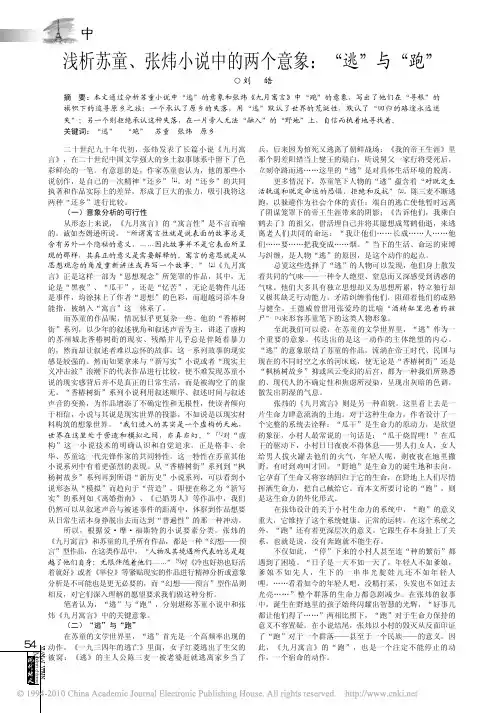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odern chineseM54XIANDAI YUWEN2008.0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张炜发表了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强大的乡土叙事脉系中留下了色彩鲜亮的一笔。
有意思的是,作家苏童也认为,他的那些小说创作,是自己的一次精神“还乡”[1]。
对“还乡”的共同执著和作品实际上的差异,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吸引我将这两种“还乡”进行比较。
(一)意象分析的可行性从形态上来说,《九月寓言》的“寓言性”是不言而喻的。
诚如杰姆逊所说,“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
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述或再写一个故事。
”[2]《九月寓言》正是这样一部为“思想观念”所笼罩的作品,其中,无论是“黑夜”、“瓜干”,还是“忆苦”,无论是物件儿还是事件,均涂抹上了作者“思想”的色彩,而超越词语本身能指,被纳入“寓言”这一体系了。
而苏童的作品呢,情况似乎更复杂一些。
他的“香椿树街”系列,以少年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为主,讲述了虚构的苏州城北香椿树街的现实、残酷并几乎总是伴随着暴力的,然而却让叙述者难以忘怀的故事,这一系列故事的现实感是较强的。
然而如果拿来与“新写实”小说或者“现实主义冲击波”浪潮下的代表作品进行比较,便不难发现苏童小说的现实感背后并不是真正的日常生活,而是被淘空了的虚无。
“香椿树街”系列小说利用叙述顺序、叙述时间与叙述声音的变换,为作品增添了不确定性和无根性,使读者倾向于相信,小说与其说是现实世界的投影,不如说是以现实材料构筑的想象世界。
“我们进入的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天地,世界在这里处于营造和模拟之间,亦真亦幻。
”[3]对“虚构”这一小说技术的明确认识和自觉追求,正是格非、余华、苏童这一代先锋作家的共同特性。
这一特性在苏童其他小说系列中有着更强烈的表现。
从“香椿树街”系列到“枫杨树故乡”系列再到所谓“新历史”小说系列,可以看到小说形态从“模拟”而趋向于“营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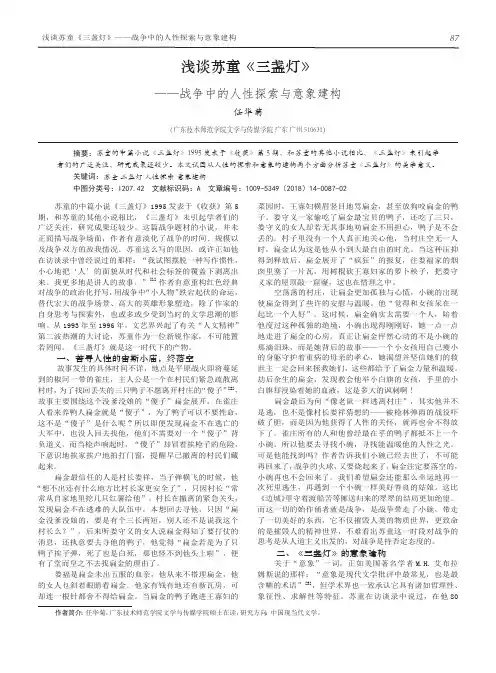
87浅谈苏童《三盏灯》——战争中的人性探索与意象建构作者简介:任华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浅谈苏童《三盏灯》——战争中的人性探索与意象建构任华菊(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摘要:苏童的中篇小说《三盏灯》1995发表于《收获》第5期,和苏童的其他小说相比,《三盏灯》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还较少。
本文试图从人性的探索和意象的建构两个方面分析苏童《三盏灯》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苏童 三盏灯 人性探索 意象建构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4-0087-02苏童的中篇小说《三盏灯》1995发表于《收获》第5期,和苏童的其他小说相比,《三盏灯》未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还较少。
这篇战争题材的小说,并未正面描写战争场面,作者有意淡化了战争的时间、规模以及战争双方的敌我情况。
苏童这么写的原因,或许正如他在访谈录中曾经说过的那样:“我试图摆脱一种写作惯性,小心地把‘人’的面貌从时代和社会标签的覆盖下剥离出来。
我更多地是讲人的故事。
”[1]作者有意重构红色经典对战争的政治化抒写,用战争中“小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替代宏大的战争场景、高大的英雄形象塑造,除了作家的自身思考与探索外,也或多或少受到当时的文学思潮的影响。
从1993年至1996年,文艺界兴起了有关“人文精神”第二波热潮的大讨论,苏童作为一位新锐作家,不可能置若罔闻。
《三盏灯》就是这一时代下的产物。
一、苦寻人性的宙斯小庙,终落空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地点是平原战火即将蔓延到的椒河一带的雀庄,主人公是一个在村民们紧急疏散离村时,为了找回丢失的三只鸭子不愿离开村庄的“傻子”[2],故事主要围绕这个没爹没娘的“傻子”扁金展开。
在雀庄人看来养鸭人扁金就是“傻子”,为了鸭子可以不要性命,这不是“傻子”是什么呢?所以即便发现扁金不在逃亡的大军中,也没人回去找他,他们不需要对一个“傻子”背负道义。
论文提纲浅析苏童创作的悲剧意识摘要在苏童的作品中,欲望、仇恨、暴力等人性丑陋的一面被揭露的淋漓尽致,这些人性的弱点将人们推向悲剧的深渊,从而使他的小说散发着淡淡的哀愁、笼罩着悲剧的氛围。
本文试着从苏童悲剧意识的来源着手,通过对苏童小说的悲剧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深层次的探析苏童作品的悲剧意识。
关键词:苏童悲剧意识人性一、苏童创作的悲剧意识概述苏童的作品无论的红粉系列、枫杨树系列还是香椿树街系列,抑或是宫廷系列,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悲剧的气息,其作品的重要价值在于重视、关注人在社会人生中存在的状态,以此揭示人命运的悲剧性。
二、苏童作品悲剧意识的根源(一)、童年生活对苏童以后创作的影响童年时期的悲剧性生命体验是形成他悲剧人格、悲剧意识的基础,童年的苏童体弱多病,生活孤独又单调,年幼的他深刻的体会到了生命的孤独与悲凉,这些对他之后的枫杨树乡村系列和香椿树街系列的小说有一定的影响。
(二)、苏童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化悲剧意识的继承中国传统典籍如《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以及三言二拍等都是苏童非常喜欢的作品,这些典籍对苏童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使他的小说也带着一层悲剧意识。
(三)、对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的推崇鲁迅和张爱玲都是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的作家,鲁迅在创作上塑造了无数的孤独形象的悲剧命运,而张爱玲创作上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刻画,这些对苏童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三、苏童创作的悲剧意识在其小说中的体现(一)人的悲剧1、悲剧的女性形象的塑造苏童的众多作品中,都塑造了无数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有着不同的身份,却有着同样悲惨的结局,通过《妻妾成群》中的颂连分析女性的悲剧。
2、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群体——男性形象刻画逃亡似乎成为苏童作品的一个意向,在他的作品中,许多的男性常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家乡漂泊在外,他们像一群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人,至死也无法回到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
如枫杨树系列。
(二)颓败的家族史描写一个家族由强盛到一点点衰败的过程,这种由盛而衰的家族颓败史,表现出了苍凉与悲悯的悲剧意识,如《罂粟之家》等(三)人性的丑恶欲望与仇恨等使人丢弃美好的人性走向不归途,从而演绎了他们悲剧的一生。
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苏童小说创作特色浅析
王昭;郭悦
【期刊名称】《科教文汇》
【年(卷),期】2010(000)019
【摘要】苏童被文学评论界誉为先锋派小说作家的领军人物,其作品有着非常独到的特点,擅长细腻唯美的人性描写,以华丽诡异的想象力和流畅的叙事风格著称.苏童以对现实冷静、本真的理性来审视、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孤独的逃亡巧妙揭示人物的宿命,以细微的动作描写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冷静的文字积极深入地去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
【总页数】2页(P62-63)
【作者】王昭;郭悦
【作者单位】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河北·唐山,063004;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河北·唐山,06300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
【相关文献】
1.悲情张爱玲——浅析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2.一场叙事的革命--试论先锋小说创作中的叙事特色
3.浅析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特色
4.从"先锋"到"现实"的蜕变r——浅析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
5.毛姆短篇小说创作特色浅析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浅析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特色陈连锦【摘要】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接纳与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绝对中心地位相对弱化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作家自身对文学创作创新的追求有关。
苏童的新历史小说创作带有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印迹。
注重个人化历史真实的阐释,偶然性叙事的彰显,民间价值的弘扬,颓废感伤美学的追求是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特色。
擅长抒情、擅长细腻描写的苏童使其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风格更为隐喻,更具魅力。
%The acceptance of Chinese new historicism novels from western new historicism trend of though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absolute center of the relative weakening of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in the 1980s, but also with the writer's own pursuit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innovation. Su Tong’s new historical novels are imprinted with western new historicism trend of thought. Paying attention to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truth, contingency narrative highlight, promoting civil values, and decadent sentimental aesthetic pursuit are characteristics of Su Tong’s new historicism novels. Su Tong makes his new historicism novels style more metaphorical and attractive because of his delicate depiction.【期刊名称】《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18)005【总页数】4页(P58-61)【关键词】苏童;新历史主义小说;历史观【作者】陈连锦【作者单位】黎明职业大学泉州 362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74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理论思潮。
35MOVIE REVIEW 电影评介2015年第18期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张艺谋导演总是以文化反思和人文关怀为宗旨,在创作电影中习惯于暗含一些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因此观众总能在其作品中感受到强烈的历史感和生命意识。
《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导演试图在申张个人的生命价值,强调对个人价值的理解和尊重,本文就将从《大红灯笼高高挂》影片中使用的艺术技巧逐一揭开这部经典作品中的主题思想意蕴。
一、《大红灯笼高高挂》故事梗概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著名导演张艺谋根据苏童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它成功地勾勒出“一夫多妻”的封建家庭制度下,妻妾之间相互勾心斗角的人生图景以及男权统治下形成的生存规则。
影片里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名叫颂莲的女人,她受过高等教育,可是为了能在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陈家生存下去,颂莲的性格在斗争过程中被异化、被扭曲。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故事开始在夏末秋初的季节,当时的颂莲才19岁,她是个年轻有为的女大学生,有着新的思想和执拗不屈服的个性。
然而她却也没能成功的逃离当时的封建传统对女人迫害的悲惨命运。
随着父亲去世,她被继母逼迫辍学最后嫁给了陈佐千做四太太,陈家有祖传下来的规矩:老爷在谁房中过夜,其院房内外就挂起高高的红灯笼。
为了一盏盏不熄的红灯笼能够高高挂起,颂莲与二太太卓云、三太太梅珊、甚至还有争宠的丫鬟雁儿之间展开了女人们可怕的斗争,直到次年夏,陈府迎来了第五位姨太太,这样没有尽头的斗争故事在封闭的深闺大院中循环上演。
影片叙述平淡,但其中包含了众多具有研究价值的要素,例如,在电影中多次巧妙的通过颜色的变化反映人物当时的心境,导演非常善于运用声音符号渲染气氛,借用音乐的变换到达一定的表意效果。
除了颜色和音乐,镜头的控制也是影片的一大特色,张艺谋导演运用一系列的技巧只是为了表现这个陈旧的大家庭里生活的最不像女人的女人们,借此给人们新的思考和反省。
二、 影片艺术特色解析(一)色彩的巧妙运用《大红灯笼高高挂》对色彩的运用是极为讲究的。
浅析苏童小说中的电影特质内容摘要:电影作为在20世纪最流行的艺术形式,它与现代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苏童的小说就存在着一种竭力与电影艺术沟通的文学精神,在苏童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他那娴熟的笔触,引领读者不断地在镜头之间跳转,随它进入人物的内心,从而使读者及时地观察到人物所处的环境,捕捉到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能让读者在其作品中读出一种电影特质。
本文将以苏童小说为重点研究对象,分析其作品中的电影特质,探究小说与电影作品之联系。
引言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鸿米店》、《红粉》到《茉莉花开》,再到张艺谋、侯咏等知名电影人引发的苏童小说改编热潮,苏童小说似乎始终都对电影界有着巨大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联系着文学作品与电影剧本,成为一座无形的桥梁,毕竟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文学作品通过语言叙述故事,电影通过画面的流动展现故事,这就造成两者虽然都有强烈的时间特性,但其表现形态却又完全不同。
“空间感”成为横亘在二者之间的最大障碍。
电影和文学作品之间的种种天然差异,使许多电影作品竭尽全力仍然难以完成观众心目中“再现”的意愿。
可以说,越是经典的、超越时代的文学作品,越难以用光影元素进行完美的还原。
苏童的小说被改编成为了电影后,电影中的台词多与小说中的对话接近,几乎没有做太大的改动,这说明电影导演都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中的精髓,并生动地用动态的表现形式将作品中静态的文字中蕴含的意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苏童的文学作品中可以读出苏童的塑造出的独特意境,可以理解苏童诠释的丰富的人物形象,想必电影导演改编苏童小说的目的也就在于能够在电影中塑造鲜明人物形象的同时又根据社会背景和人物命运描摹出鲜明的意境。
正是苏童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电影特质,才能成功地改变成电影作品。
笔者认为,所谓电影特质就是小说创作中所体现的电影剧本中特有的具有画面感、行动化语言等有电影表现形式的特质,是适合通过摄像机和演员表演诠释出来的东西。
本文就以苏童小说为重点研究对象,分析其作品中的电影特质,探究小说与电影作品之联系。
1 苏童小说中电影特质的具体表现苏童小说被张艺谋、李少红、侯咏等电影导演改编成了电影作品,因为这些导演看中其作品中的电影特质,那么在苏童的小说中具体有那些电影特质,本章将从语言和叙事两方面分析其电影特质。
1.1 小说语言上的电影特质之表现1.1.1 镜头式的语言描写小说中具有镜头描写的语言是体现其电影特质的主要因素,在塑造意象的同时能够深化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性格,体现小说的镜头感。
意象鲜明,苍劲有力的远景描写是苏童小说的特色。
小说中的这种远景描写能够制造场景,构成电影画面感。
如《妇女生活》一开篇就介绍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并用一种远景镜头的方式呈现:“汇隆照相馆座落在街角上,漆成桔红色的楼壁和两扇窄小的玻璃门充分显示了三十年代那些小照相馆的风格。
橱窗里陈列的是几个二流电影明星的照片和精心摆设的纸花。
那些女明星的美艳和欢乐对于外面凄清萧条的街道显得不合时宜莫名其妙。
从远一点的高处看汇隆照相馆,它就像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子,被周围密集的高大房屋挤压得近乎开裂。
有时候可以看见一只燕子从那里飞起来,照相馆的屋檐下曾有过燕巢。
”这样的场景可以不由地让人脑海里浮现出苍凉的景象,也预示着故事的悲剧意味,从一个远远的视角看作者眼里的旧上海,作者眼里娴的生活环境,也给读者营造出了一种苍凉的氛围。
《红粉》里对远景镜头的描写加入了秋仪和小萼的对话,镜头的来回转换也增加了小说的动态感,使得整体意境更加生动:“小萼追出饭店,看见秋仪身着黑袍站在街对面吵灯下。
小萼急步穿越马路时看见秋仪也跑了起来,秋仪的黑袍在风中飒飒有声。
小萼就站在路上叫起来,秋仪,你别跑,你听我说呀。
秋仪仍然头也不回,秋仪说,你回去结你的婚,什么也别说,小萼又追了几步就蹲下来了,小萼捂着脸呜呜哭起来,她说,秋仪,你怎么不骂我?原本应该是你跟老浦结婚的,你怎么不骂我呢?秋仪现在站在一家雨伞店前,她远远地看着哭泣的小萼,表情非常淡漠。
”这是小萼和秋仪姐妹关系的转折点,这种远景镜头体现了人物历史转折时期的悲壮心情,夹着瑟瑟的风,小萼因为伤害了秋仪而感到伤心和内疚,秋仪也因为自己的人生将陷入彻底的孤独而无可奈何,这种远景正能配合二人当时的心理状态,体现出了鲜明的电影特质。
苏童在运用远景时加入了包括鸟瞰角度、俯角、水平角度、仰角、倾斜角度等多种视角,这些电影特质为电影改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远景镜头以外,在苏童的小说中也出现了很多电影中的中景镜头,所谓中景是指画框下边卡在膝盖左右部位或场景局部的画面,这种镜头手法是喜剧片的主流,然而在苏童在小说中潜意识地用到多种多样的中景描写,目的也是为了体现其小说的叙事性。
《妇女生活》中就用到了这样的中景镜头:“外面刮着风,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穿着臃肿的行人和漫空飞舞的梧桐树叶,街角上的美丽牌香皂和花旗参的广告画被风吹得噼啪作响。
有一个人推开了玻璃门,摘下了头上的礼帽,他手中的银质夹克的光泽异常强烈。
正是这种光亮让娴猛地从画报上抬起头来,她看见那个男人站在柜台前约五尺远的地方,手执礼帽向她颔首微笑。
娴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总说她有一种晕眩的感觉,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后一生的命运。
”在写孟老板时,苏童运用了中景的描写手法,五尺远的距离正好可以看到他的上半身,对于体现一个男人的翩翩风度,上半身就够了,太远有种模糊感,太近又缺乏整体效果,因此选择五尺远恰如其分。
在他的《妻妾成群》里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中景描写:“两个人坐着很虚无地呷酒。
颂莲把酒盅在手指间转着玩,她看见飞浦现在就坐在对面,他低着头,年轻的头发茂密乌黑,脖子刚劲傲慢地挺直,而一些暗蓝的血管在她的目光里微妙地颤动着。
”这个中景描写的是飞浦坐着的样子,从头发到脖子到目光,两人的距离不是太近,还未到特写的程度,因此可以看做是中景的效果。
《妻妾成群》里的中景描写不多见,并且常常伴随着人物的对话,从而达到了人物对话与外部环境相融合的效果,以人为主,以景衬人。
苏童小说中描写动作镜头的语言也非常细致,这不仅有利于电影导演的拍摄,也有助于观众对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作品欣赏时能产生共鸣。
苏童用一言一语塑造着主人公的动作形态,字里行间将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慢慢浮现。
“颂莲弯腰朝井中看,井水是蓝黑色的,水面上也浮着陈年的落叶,颂莲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沉闷而微弱、有一阵风吹过来,把颂莲的裙子吹得如同飞鸟,颂莲这时感到一种坚硬的凉意,像石头一样慢慢敲她的身体,颂莲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速度很快,回到南厢房的廊下,她吐出一口气,回头又看那个紫藤架,架上倏地落下两三串花,很突然的落下来,颂莲觉得这也很奇怪。
”井中的世界对颂莲来说是个黑色的诱惑,她的一系列动作都表明她想将它看清楚以便使自己不再莫名地恐惧,所以她“看见自己的脸在水中闪烁不定,听见自己的喘息声被吸入井中放大了”可是她却永远也不敢靠近,“颂莲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速度很快,回到南厢房的廊下,她吐出一口气”这种恐惧既是对阴森的井和那个不祥的传说,更因为对自己不可掌控的,随时可能被幽黑深井般生活所吞噬的命运的恐惧,所以她永远摆脱不了那口井的阴影。
通过动作的细微描写,含蓄地表现出颂莲矛盾、恐惧、不安的内心。
这在电影表演的过程中演员也可以较为容易地通过肢体和眼神的表演诠释人物,使观众产生共鸣。
1.1.2 大量使用意象化和色彩化的语言可以说苏童创造了一种小说话语,这就是意象化的白描,或白描的意象化。
白描作为中国小说特有的技法,可以说在“五四”时期经鲁迅的改造出现了新的气象,但后来被简单化和庸俗化了,一度被人作为细节描写的同义词。
一些试验小说者因此而鄙视白描功夫,小说话语基本以引进国外的成品为主。
苏童大胆地把意象的审美机制引入白描之中,白描艺术便改变了原先较为单调的方式,出现了现代小说具有的弹性和张力。
《妻妾成群》中这样写道:“天已寒秋,女人们都纷纷换上了秋衣,树叶也纷纷在清晨和深夜飘落在地,枯黄的一片覆盖了花园。
几个女佣蹲在一起烧树叶,一股焦味弥漫开来,颂莲的窗口砰地打开,女佣们看见颂莲的脸因愤怒而涨得绯红。
她抓着一把木梳在窗台上敲着,谁让你们烧树叶的?好好的树叶烧得那么难闻。
女佣们便收起扫帚箩筐,一个大胆的女佣说,这么多的树叶,不烧怎么弄?颂莲就把木梳从窗里砸到她身上,颂莲喊,不准烧就是不准烧!然后她就砰地关上了窗子。
”这显然是在叙事,是在表现颂莲在秋日纷乱的心绪和越来越乖戾暴躁的性格,所用笔墨不加心理分析,也没有变形夸张之处,是纯粹的写实的白描,但整幅场景却给人意象性的阅读感受,具有一种强烈的画面感。
这一方面是由于落叶本身在诗歌中特有的意象内涵唤起人们的阅读经验,另一方面苏童将其场景与叙事进行定格处理,便形成了一种意象快面,这种方式延伸了意象的内涵,也为白描灌注了新鲜的汁液。
因而当《妻妾成群》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时,小说里的生活场景乃至色彩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入镜头。
色彩本位主义者认为张艺谋的电影艺术在于实现了故事的意象化,那苏童的小说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追求这种意象的视觉性效果,苏童在写人物对话时取消了引号和冒号,以充分发挥汉字方块特有的意象性功能。
加之苏童对色彩奇异的敏感以及他富有弹性的叙述语言,因而使小说具有一种造型功能。
但苏童的造型感不似雕塑那么棱角分明,也不像张艺谋的画面那么富有力度,苏童用来营构意象的是他那特有的类似苏州丝绸的语言,飘逸,柔软,色彩丰富,虽不厚重但绵延而有张力。
同样,色彩化语言也是构成苏童小说意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童在作品中习惯运用鲜艳的红色来抒情。
“去年冬天我和你们一起喝了白酒后打翻一瓶红墨水,在墙上画下了我的八位亲人。
我还写了一首诗想夹在少年时代留下的历史书里。
那是一首胡言乱语口齿不清的自白诗。
诗中幻想了我的家族从前的辉煌岁月,幻想了横亘于这条血脉的黑红灾难线。
有许多种开始和结尾交替出现。
最后我痛哭失声,我把红墨水拼命地往纸上抹,抹得那首诗无法再辨别字迹。
”无论是在《妻妾成群》、《城北地带》中,还是在《罂粟之家》中,红色成为了一种象征。
盛开的罂粟花、鬼火般的夜繁花和深夜里的红灯笼,在漆黑的夜晚,在荒僻之所,它们兀自鲜艳火红,但却如斯邪媚。
红色和沉重的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小说更具张力和撞击力,更渲染了一种颓废感伤的氛围。
从场景选择、舞台布景、摄像选景、演员表演等方面符合了电影拍摄的条件,从而使小说具有电影特质。
1.2 小说叙事上的电影特质之表现1.2.1 故事情节戏剧化,女性形象个性化“总结苏童的小说有四个特点:一是‘记录’人群和整个世界的强烈欲望;二是要使自己的文字成为超越‘历史’本事的叙述;三是试图摆脱所谓新闻对事物的‘真实’记载;四是使自己的叙述区别于同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