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童的文献综述
- 格式:doc
- 大小:35.5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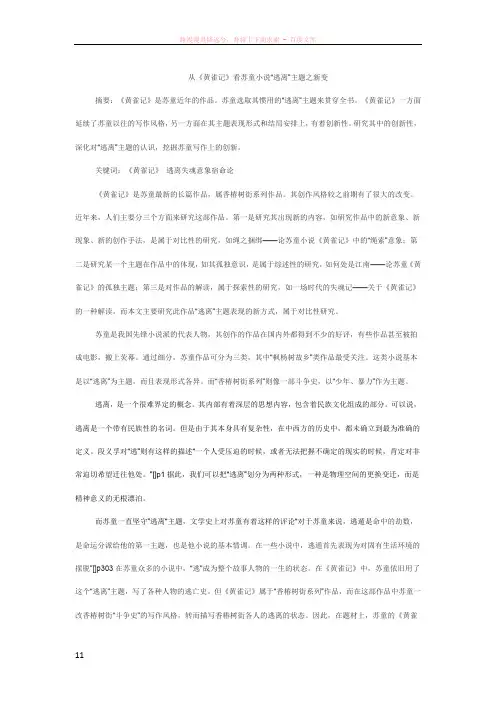
从《黄雀记》看苏童小说“逃离”主题之新变摘要:《黄雀记》是苏童近年的作品。
苏童选取其惯用的“逃离”主题来贯穿全书。
《黄雀记》一方面延续了苏童以往的写作风格,另一方面在其主题表现形式和结局安排上,有着创新性。
研究其中的创新性,深化对“逃离”主题的认识,挖掘苏童写作上的创新。
关键词:《黄雀记》逃离失魂意象宿命论《黄雀记》是苏童最新的长篇作品,属香椿树街系列作品。
其创作风格较之前期有了很大的改变。
近年来,人们主要分三个方面来研究这部作品。
第一是研究其出现新的内容,如研究作品中的新意象、新现象、新的创作手法,是属于对比性的研究,如绳之捆绑——论苏童小说《黄雀记》中的“绳索”意象;第二是研究某一个主题在作品中的体现,如其孤独意识,是属于综述性的研究,如何处是江南——论苏童《黄雀记》的孤独主题;第三是对作品的解读,属于探索性的研究,如一场时代的失魂记——关于《黄雀记》的一种解读。
而本文主要研究此作品“逃离”主题表现的新方式,属于对比性研究。
苏童是我国先锋小说派的代表人物,其创作的作品在国内外都得到不少的好评,有些作品甚至被拍成电影,搬上荧幕。
通过细分,苏童作品可分为三类,其中“枫杨树故乡”类作品最受关注。
这类小说基本是以“逃离”为主题,而且表现形式各异。
而“香椿树街系列”则像一部斗争史,以“少年、暴力”作为主题。
逃离,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
其内部有着深层的思想内容,包含着民族文化组成的部分。
可以说,逃离是一个带有民族性的名词。
但是由于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在中西方的历史中,都未确立到最为准确的定义。
段义孚对“逃”则有这样的描述“一个人受压迫的时候,或者无法把握不确定的现实的时候,肯定对非常迫切希望迁往他处。
”[]p1据此,我们可以把“逃离”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物理空间的更换变迁,而是精神意义的无根漂泊。
而苏童一直坚守”逃离“主题,文学史上对苏童有着这样的评论“对于苏童来说,逃遁是命中的劫数,是命运分派给他的第一主题,也是他小说的基本情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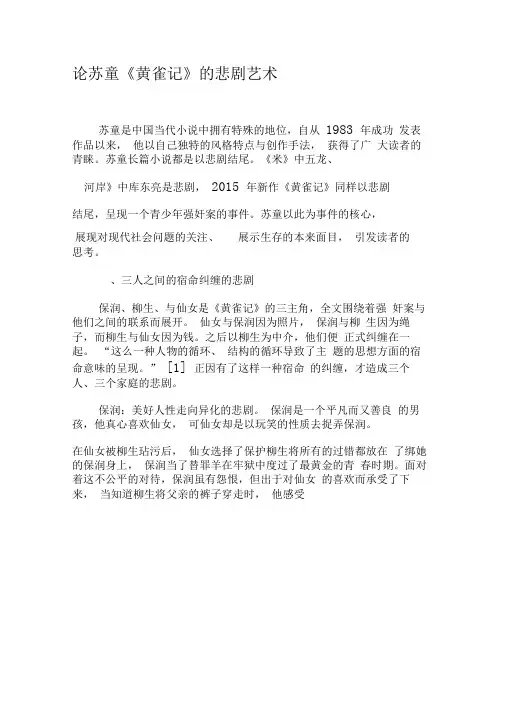
论苏童《黄雀记》的悲剧艺术苏童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拥有特殊的地位,自从1983 年成功发表作品以来,他以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与创作手法,获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
苏童长篇小说都是以悲剧结尾。
《米》中五龙、河岸》中库东亮是悲剧,2015 年新作《黄雀记》同样以悲剧结尾,呈现一个青少年强奸案的事件。
苏童以此为事件的核心,展现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关注、展示生存的本来面目,引发读者的思考。
、三人之间的宿命纠缠的悲剧保润、柳生、与仙女是《黄雀记》的三主角,全文围绕着强奸案与他们之间的联系而展开。
仙女与保润因为照片,保润与柳生因为绳子,而柳生与仙女因为钱。
之后以柳生为中介,他们便正式纠缠在一起。
“这么一种人物的循环、结构的循环导致了主题的思想方面的宿命意味的呈现。
” [1] 正因有了这样一种宿命的纠缠,才造成三个人、三个家庭的悲剧。
保润:美好人性走向异化的悲剧。
保润是一个平凡而又善良的男孩,他真心喜欢仙女,可仙女却是以玩笑的性质去捉弄保润。
在仙女被柳生玷污后,仙女选择了保护柳生将所有的过错都放在了绑她的保润身上,保润当了替罪羊在牢狱中度过了最黄金的青春时期。
面对着这不公平的对待,保润虽有怨恨,但出于对仙女的喜欢而承受了下来,当知道柳生将父亲的裤子穿走时,他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在柳生婚礼后的新房将其杀害,三人之间的纠缠彻底断了。
柳生:“逃避”责任到最终“死亡”的悲剧。
柳生在青春期犯下了强奸事件,但他没直面错误,选择了逃避,让保替他遭受牢狱之灾。
柳生虽获得了一时的人身自由,但付出了一生的心灵怕。
她一回来,他犯罪的青春也回来了,一个紊乱的记忆也回来了。
” [2] 那隐藏的不安,随时可以将柳生吞没。
当保润出来,当初的三人又一次聚集在了一起,柳生愧对于仙女,也愧对于保润。
柳生照顾保润的祖父、为仙女讨债、照顾怀了孕的仙女,只为承担自己曾经逃避过的过错。
当柳生放下曾经,迈向美好未来时,却又被保润所杀。
柳生只有死亡,才可以得到最后的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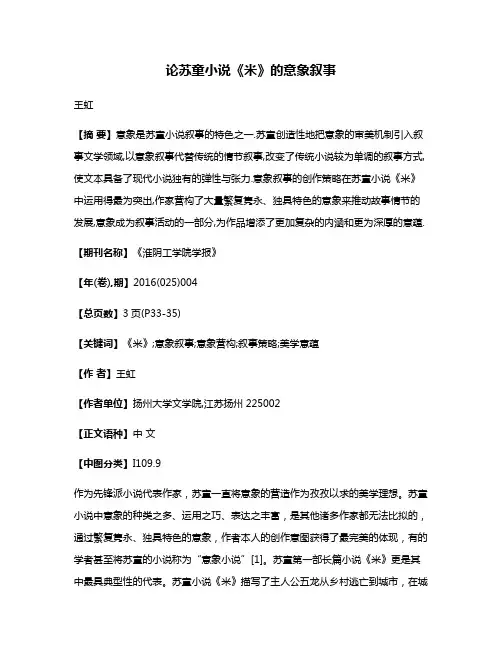
论苏童小说《米》的意象叙事王虹【摘要】意象是苏童小说叙事的特色之一.苏童创造性地把意象的审美机制引入叙事文学领域,以意象叙事代替传统的情节叙事,改变了传统小说较为单调的叙事方式,使文本具备了现代小说独有的弹性与张力.意象叙事的创作策略在苏童小说《米》中运用得最为突出,作家营构了大量繁复隽永、独具特色的意象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意象成为叙事活动的一部分,为作品增添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和更为深厚的意蕴.【期刊名称】《淮阴工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25)004【总页数】3页(P33-35)【关键词】《米》;意象叙事;意象营构;叙事策略;美学意蕴【作者】王虹【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9.9作为先锋派小说代表作家,苏童一直将意象的营造作为孜孜以求的美学理想。
苏童小说中意象的种类之多、运用之巧、表达之丰富,是其他诸多作家都无法比拟的,通过繁复隽永、独具特色的意象,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获得了最完美的体现,有的学者甚至将苏童的小说称为“意象小说”[1]。
苏童第一部长篇小说《米》更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
苏童小说《米》描写了主人公五龙从乡村逃亡到城市,在城市里发迹和幻灭,最终死于归乡途中的“具有轮回意义的一生”[2]。
作者巧妙地将伦理叙事和意象写作结合起来,在小说中精心营造大量独具特色的意象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叙事的明晰性和意象的含蓄性相得益彰,达到了对人性更为深入的揭示和对亲情伦理关系更为彻底的拆解。
可以说,《米》就是一个“意象集”。
“米”是小说的中心意象,是与食欲、情欲、权欲等欲望皆有所关联的意象。
作者构思精巧,实在近乎一米一世界的意境了。
回顾五龙的一生:逐米而来——拥米而生——为米而死。
米,已经不仅是五龙生命的保障,而且已经与他的一生发生了根本的关联,使五龙的一生有了宿命和轮回的意味。
“火车”也是小说《米》中的典型意象之一,具有象征逃亡、回归和死亡的涵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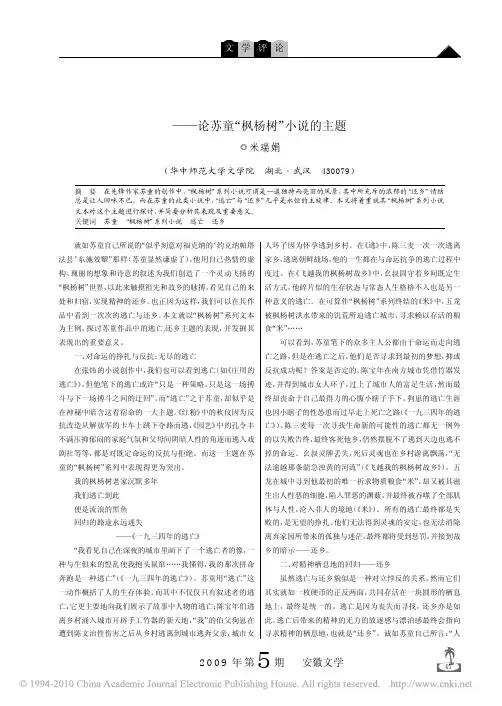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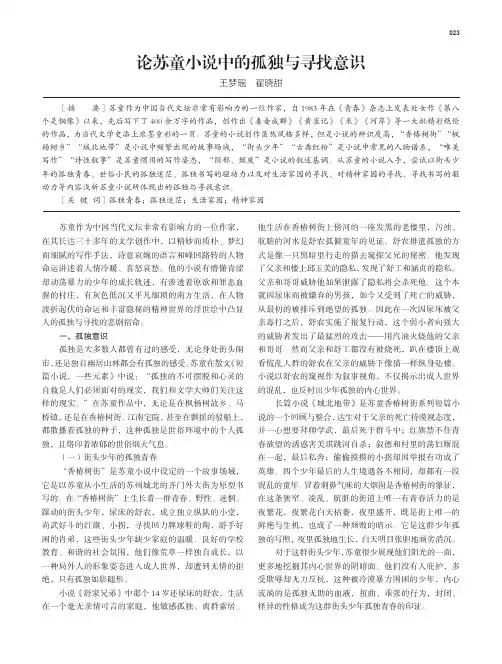
023王梦瑶 翟晓甜苏童作为中国当代文坛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作家,在其长达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以精妙而质朴、梦幻而细腻的写作手法,诗意哀婉的语言和峰回路转的人物命运讲述着人情冷暖、喜怒哀愁。
他的小说有懵懂青涩却动荡暴力的少年的成长轨迹,有渗透着原欲和罪恶血腥的村庄,有灰色低沉又平凡细琐的南方生活,在人物波折起伏的命运和丰富隐秘的精神世界的浮世绘中凸显人的孤独与寻找的悲剧宿命。
一、孤独意识孤独是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的感受,无论身处街头闹市,还是独自幽居山林都会有孤独的感受。
苏童在散文《短篇小说,一些元素》中说:“孤独的不可摆脱和心灵的自救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和文学大师们关注这样的现实。
”在苏童作品中,无论是在枫杨树故乡、马桥镇,还是在香椿树街、江南宅院,甚至在飘摇的驳船上,都散播着孤独的种子,这种孤独是世俗环境中的个人孤独,且烙印着浓郁的世俗烟火气息。
(一)街头少年的孤独青春“香椿树街”是苏童小说中设定的一个故事场域,它是以苏童从小生活的苏州城北的齐门外大街为原型书写的。
在“香椿树街”上生长着一群青春、野性、迷惘、躁动的街头少年,尿床的舒农,成立独立纵队的小堂,尚武好斗的红旗、小拐,寻找回力牌球鞋的陶,游手好闲的肖弟,这些街头少年缺少家庭的温暖、良好的学校教育、和谐的社会氛围,他们像荒草一样独自成长,以一种局外人的形象姿态进入成人世界,却遭到无情的拒绝,只有孤独如影随形。
小说《舒家兄弟》中那个14岁还尿床的舒农,生活在一个毫无亲情可言的家庭,他敏感孤独、离群索居。
他生活在香椿树街上傍河的一座发黑的老楼里,污浊、肮脏的河水是舒农孤僻童年的见证。
舒农排遣孤独的方式是像一只黑暗里行走的猫去窥探父兄的秘密。
他发现了父亲和楼上邱玉美的隐私,发现了舒工和涵贞的隐私。
父亲和哥哥威胁他如果泄露了隐私将会杀死他。
这个本就因尿床而被嫌弃的男孩,如今又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从最初的被排斥到绝望的孤独。
因此在一次因尿床被父亲毒打之后,舒农实施了报复行动,这个弱小者向强大的威胁者发出了最猛烈的攻击——用汽油火烧他的父亲和哥哥。
![[名人佳作]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https://uimg.taocdn.com/e7a53ca8cd22bcd126fff705cc17552707225e27.webp)
[名人佳作]苏童——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来源:作者:苏童发布时间:2012-11-09直到五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枫杨树一带还铺满了南方少见的罂粟花地。
春天的时候,河两岸的原野被猩红色大肆入侵,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波浪鼓荡着偏僻的乡村,鼓荡着我的乡亲们生生死死呼出的血腥气息。
我的幺叔还在乡下,都说他像一条野狗神出鬼没于老家的柴草垛、罂粟地、干粪堆和肥胖女人中间,不思归家。
我常在一千里地之外想起他,想起他坐在枫杨树老家的大红花朵丛里,一个矮小结实黝黑的乡下汉子,面朝西南城市的方向,小脸膛上是又想睡又想笑又想骂的怪异神气,唱着好多乱七八糟的歌谣,其中有一支是呼唤他心爱的狗的。
狗儿狗儿你钻过来带我到寒窑亲小娘祖父住在城里,老态龙钟了,记忆却很鲜亮。
每当黄昏降临,家里便尘土般地飘荡起祖父的一声声喟然长叹。
他迟迟不肯睡觉,“明天醒过来说不定就是瞎子了。
”于是他睁大了眼睛坐在渐渐黑暗的房间里,宁静、苍劲,像一尊古老的青铜鹰。
可以从祖父被回忆放大的瞳孔里看见我的幺叔。
祖父把小儿子和一群野狗搅成了一团。
从前的幺叔活脱是一个鬼伢子,爱戴顶城里人的遮阳帽,怪模怪样地在罂粟花地里游荡。
有一年夏天,他把遮阳帽扔在河里,迷上了一群野狗。
于是人们都看见财主家的小少爷终日和野狗厮混在一起,疯疯颠颠,非人非狗,在枫杨树乡村成为稀奇的丑闻。
“那畜生不谙世事,只通狗性。
”祖父诅咒幺叔。
他说,“别去管他,让他也变成一条狗吧。
”想起那鬼伢子我祖父不免黯然神伤。
多少个深夜幺叔精神勃发,跟着满地乱窜的野狗,在田埂上跌跌撞撞地跑,他的足迹紧撵着狗的卵石形蹄印,遍布枫杨树乡村的每个角落。
有时候幺叔气喘吁吁地闯到乡亲家里去讨水喝,狗便在附近的野地里一声一声地吠着。
沿河居住的枫杨树乡亲没有人不认识幺叔的,说起幺叔都觉得他是神鬼投胎,不知他带给枫杨树的是吉是凶。
逢到清明节,家族中人排成一字纵队,浩浩荡荡到祠堂祭祀祖宗时,谁也找不到幺叔的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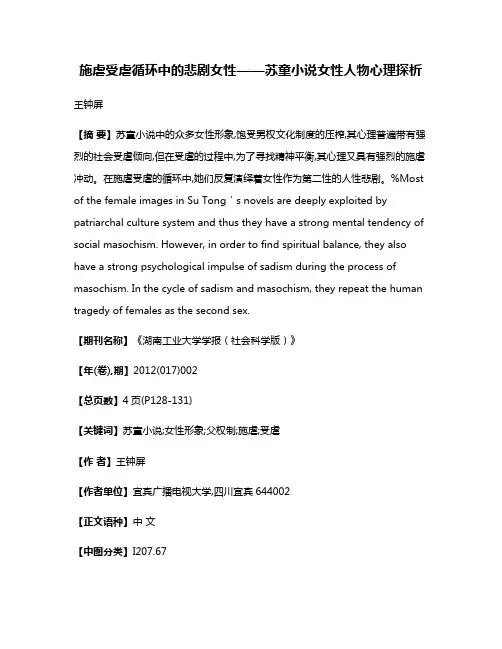
施虐受虐循环中的悲剧女性——苏童小说女性人物心理探析王钟屏【摘要】苏童小说中的众多女性形象,饱受男权文化制度的压榨,其心理普遍带有强烈的社会受虐倾向,但在受虐的过程中,为了寻找精神平衡,其心理又具有强烈的施虐冲动。
在施虐受虐的循环中,她们反复演绎着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人性悲剧。
%Most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Su Tong's novels are deeply exploited by patriarchal culture system and thus they have a strong mental tendency of social masochism. However, in order to find spiritual balance, they also have a strong psychological impulse of sadism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sochism. In the cycle of sadism and masochism, they repeat the human tragedy of females as the second sex.【期刊名称】《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17)002【总页数】4页(P128-131)【关键词】苏童小说;女性形象;父权制;施虐;受虐【作者】王钟屏【作者单位】宜宾广播电视大学,四川宜宾644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67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到“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
[1]有压迫的出现就有权力运作的空间。
“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使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附属地位,身上压抑的枷锁越来越沉重。
女性甚至成为男性赏玩的“物品”和“生产”的工具,被异化为非人,成为有价值的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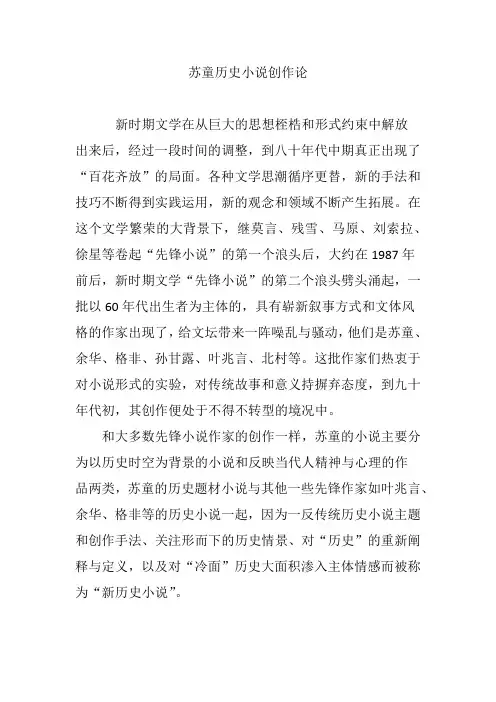
苏童历史小说创作论新时期文学在从巨大的思想桎梏和形式约束中解放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到八十年代中期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各种文学思潮循序更替,新的手法和技巧不断得到实践运用,新的观念和领域不断产生拓展。
在这个文学繁荣的大背景下,继莫言、残雪、马原、刘索拉、徐星等卷起“先锋小说”的第一个浪头后,大约在1987年前后,新时期文学“先锋小说”的第二个浪头劈头涌起,一批以60年代出生者为主体的,具有崭新叙事方式和文体风格的作家出现了,给文坛带来一阵噪乱与骚动,他们是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北村等。
这批作家们热衷于对小说形式的实验,对传统故事和意义持摒弃态度,到九十年代初,其创作便处于不得不转型的境况中。
和大多数先锋小说作家的创作一样,苏童的小说主要分为以历史时空为背景的小说和反映当代人精神与心理的作品两类,苏童的历史题材小说与其他一些先锋作家如叶兆言、余华、格非等的历史小说一起,因为一反传统历史小说主题和创作手法、关注形而下的历史情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与定义,以及对“冷面”历史大面积渗入主体情感而被称为“新历史小说”。
一九十年代初,先锋作家的形式实验由于自身创作与读者接受的双重限制,逐渐褪去了最初的炫目光环,呈现出脆弱的一面,不变已难以为继。
为摆脱写作困境,他们纷纷转型,不再一味地讲究技巧,开始将曾被自己摒弃的故事与意义纳入笔底视野。
但是决定与现实文化环境发生联系的先锋作家们,首先遭遇的是自身阅历的缺乏和对现时生活把握的无力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历史时空,想象与虚构成了他们拾掇历史碎片关注现实精神的重要手段。
这种出于自身变更创作需要而对历史关注的目的,使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呈现出逸出传统的特点。
苏童的创作向历史领域开拓正是发生在这种转型大气候之下。
作为在新历史小说领域创作颇丰、影响较大并取得了代表性成就的作家,他对历史进行了一番自我诠释,并在这种创作观的指导下创作了一大批历史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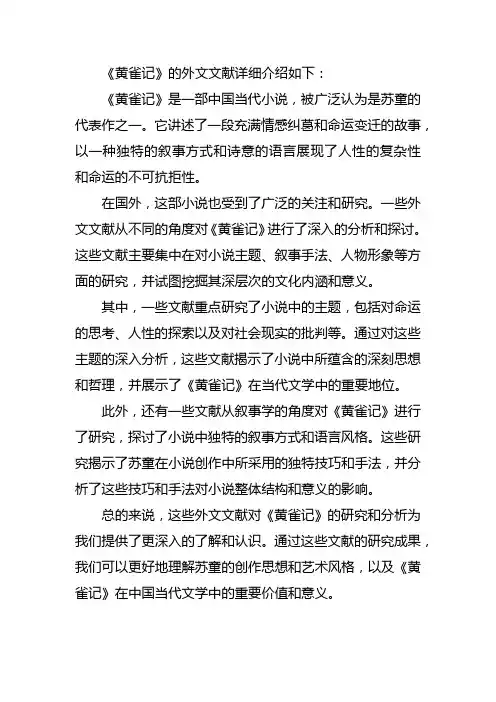
《黄雀记》的外文文献详细介绍如下:
《黄雀记》是一部中国当代小说,被广泛认为是苏童的代表作之一。
它讲述了一段充满情感纠葛和命运变迁的故事,以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诗意的语言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命运的不可抗拒性。
在国外,这部小说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一些外文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黄雀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这些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小说主题、叙事手法、人物形象等方面的研究,并试图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意义。
其中,一些文献重点研究了小说中的主题,包括对命运的思考、人性的探索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等。
通过对这些主题的深入分析,这些文献揭示了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哲理,并展示了《黄雀记》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从叙事学的角度对《黄雀记》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
这些研究揭示了苏童在小说创作中所采用的独特技巧和手法,并分析了这些技巧和手法对小说整体结构和意义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外文文献对《黄雀记》的研究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通过这些文献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苏童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以及《黄雀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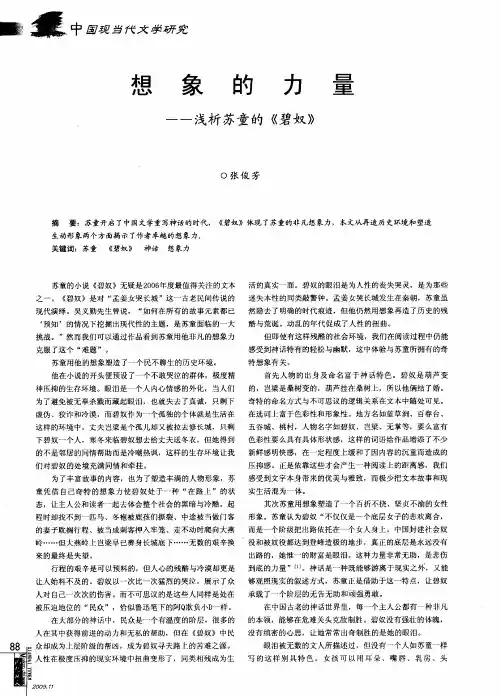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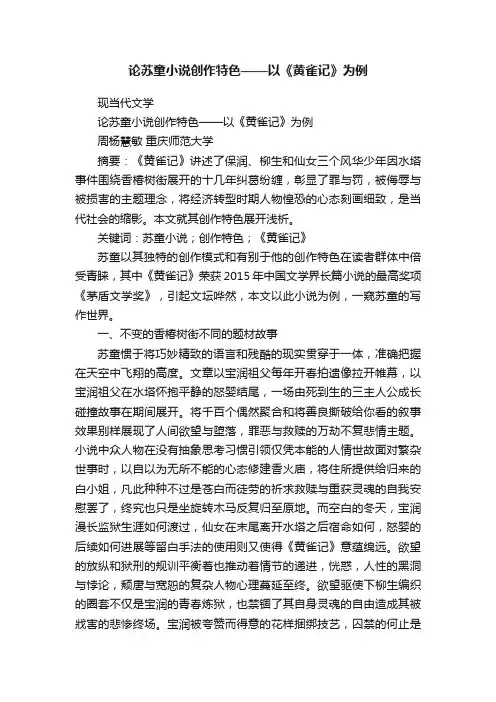
论苏童小说创作特色——以《黄雀记》为例现当代文学论苏童小说创作特色——以《黄雀记》为例周杨慧敏重庆师范大学摘要:《黄雀记》讲述了保润、柳生和仙女三个风华少年因水塔事件围绕香椿树街展开的十几年纠葛纷缠,彰显了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理念,将经济转型时期人物惶恐的心态刻画细致,是当代社会的缩影。
本文就其创作特色展开浅析。
关键词:苏童小说;创作特色;《黄雀记》苏童以其独特的创作模式和有别于他的创作特色在读者群体中倍受青睐,其中《黄雀记》荣获2015年中国文学界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引起文坛哗然,本文以此小说为例,一窥苏童的写作世界。
一、不变的香椿树街不同的题材故事苏童惯于将巧妙精致的语言和残酷的现实贯穿于一体,准确把握在天空中飞翔的高度。
文章以宝润祖父每年开春拍遗像拉开帷幕,以宝润祖父在水塔怀抱平静的怒婴结尾,一场由死到生的三主人公成长碰撞故事在期间展开。
将千百个偶然聚合和将善良撕破给你看的叙事效果别样展现了人间欲望与堕落,罪恶与救赎的万劫不复悲情主题。
小说中众人物在没有抽象思考习惯引领仅凭本能的人情世故面对繁杂世事时,以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心态修建香火庙,将住所提供给归来的白小姐,凡此种种不过是苍白而徒劳的祈求救赎与重获灵魂的自我安慰罢了,终究也只是坐旋转木马反复归至原地。
而空白的冬天,宝润漫长监狱生涯如何渡过,仙女在末尾离开水塔之后宿命如何,怒婴的后续如何进展等留白手法的使用则又使得《黄雀记》意蕴绵远。
欲望的放纵和狱刑的规训平衡着也推动着情节的递进,恍惑,人性的黑洞与悖论,颓唐与宽恕的复杂人物心理蔓延至终。
欲望驱使下柳生编织的圈套不仅是宝润的青春炼狱,也禁锢了其自身灵魂的自由造成其被戕害的悲惨终场。
宝润被夸赞而得意的花样捆绑技艺,囚禁的何止是仙女的身体,也铸建了其自身始终无法摆脱的精神牢笼。
膨胀而放逐的内心是剧中人物命运窘境的始,终而留下的仅是物是人非的井亭医院和满目疮痍的内心而已。
寄希望于用绳索捆绑别人拯救苍生的宝润,寄希望于讨好行善消释内心不安获得宽恕的柳生,寄希望于逢场作戏追逐虚荣不断逃离的白小姐,上演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从黑暗走向黑暗,也难免是戏剧化无望的挣扎,终究未抵达被救赎的彼岸。
014《名家名作》·评论[摘 要] 苏童的《米》以精巧细微的笔触书写了在现实的压抑下人性的扭曲。
织云是沉沦、纵欲的象征,却怀有同情之心,能在时代的残酷和冷漠下展现出些微人性的光辉。
绮云色厉内荏、清高封建,展现出人情的空缺、欲望的遏制以及人性的压抑。
《米》通过对织云和绮云等命运的聚焦和人性的书写,将历史的错愕、现实的荒诞与人性的纵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关 键 词] 苏童;《米》;人性;织云;绮云论苏童《米》的人性叙事——以织云和绮云为中心王 一一、引言在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敌人》、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等多部小说对人性、历史、欲望进行书写后,鲁枢元总结其为文学的“向内转”,即“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并以此构筑起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
小说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1]。
苏童的《米》深入人性结构的内部,对人性中潜在的层面进行描摹,不断在关于欲望的隐喻和“突破口”中呈现生命的真实状态。
小说《米》围绕织云、绮云等人物之间发生的有关欲望、财富、罪恶和死亡的沉痛故事,将人性的纵深彻底暴露给人看。
在苏童的书写中,人物总是陷于充满种种暗喻的巧合旋涡中,无法摆脱命运的沉重,在诸多突发性因素的合力下展现了人物命运与历史情状的复杂纠葛。
以往的研究以《米》的伦理情境阐释、细节败笔分析等方面为主,本文则以《米》中织云和绮云所展现的人性维度为切入口,揭示苏童是如何在小说中“以女性美艳的衰颓、个人生存境遇的沦落和凄楚、对外在世界的反抗”[2]构成叙事的情境,考察小说所表现的在“人情世情的冷暖、新欢与交恶的变奏”[3]下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不可兼容性,并探究苏童是如何描摹人“身陷深渊绝境之中而不自觉的意识状态和行为方式”[4]的。
二、织云:女性困境苏童笔下的女性往往是在性格上阴暗扭曲、在精神上承受着压抑、在命运上具有宿命般的悲剧性。
织云作为《米》中极富特色的女性形象,其性格中有着对贫苦人民的同情与怜悯、对个性自由的张扬与放纵,同时也体现出对权势和地位的迷恋与追求,以及扎根于其心灵深处的传统封建观念。
苏童《1934年的逃亡》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作者简介苏童,1963年1月生于江苏苏州,在苏州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大学期间开始学习写作,并在1983年发表小说处女作。
1984年到南京工作,1986年调入《钟山》杂志社当文学编辑至今。
著有长篇小说《米》、中篇小说集《妻妾成群》、《红粉》、短篇小说集《伤心的舞蹈》、《祭奠红马》等作品。
内容概要1934年是个灾年。
我祖母蒋氏拖着怀孕的身子在财东陈文治家的水田里干活。
陈文治站立在东北坡地的黑砖楼上,从一架日本望远镜里窥视着蒋氏的一举一动,脸上漾满了痴迷的神色。
蒋氏是个丑女人,祖父陈宝年18岁娶了她。
陈宝年从前路遇圆脸肥臀的女人就眼泛红潮穷追不舍,兴尽方归。
陈宝年娶亲的第一夜,他骑在蒋氏身上俯视她的脸,不停地唉声叹气“你是灾星”。
以后的七个深夜陈宝年重复着他的预言。
1934年陈宝年一直在城里吃喝嫖赌、潜心发迹,没回过我的枫杨树老家。
在我已故亲人中,陈家老大狗崽以一个拾粪少年的形象站立在我们家史中。
蒋氏对狗崽说,你拾满一竹箕粪可以换两个铜板,攒够了钱娘给你买双胶鞋穿。
对一双胶鞋的幻想使狗崽的1934年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不过,他得到的铜板没有交给蒋氏而放进一只木匣子里。
那只木匣子在某个早晨失踪了。
蒋氏说,你非要那胶鞋,就把娘肚里的孩子打掉,省下钱给你买。
狗崽对着娘的腹部连打三拳。
那被击打的胎儿就是我父亲。
在收割季节里,蒋氏在干草垛上分娩了父亲。
陈文治借助望远镜窥见了分娩的整个过程后,瘫软在楼顶。
下人赶来时发现他那白锦缎裤子亮晶晶湿了一片。
陈文治和陈宝年祖上是亲戚。
陈宝年曾用他妹妹凤子跟陈文治换了十亩水田。
凤子给陈文治当了两年小妾,生下三个畸形男婴,被陈文治活埋了。
事后不久凤子就死了。
陈文治家有只白玉瓷罐,里面装着枫杨树人所关心的绝药。
一天,狗崽被陈文治骗到谷仓里,他萌芽时期的精液滴进了白玉瓷罐里。
事后陈文治给了他一双胶鞋。
在城里运竹子的人回来说,陈宝年发横财了。
苏童小说论文:论苏童小说中的少年成长叙事【中文摘要】在惯常的文学划分中,少年往往是一个被遮蔽的阶段。
它或者被拉回到充满童趣的幼儿时代,或者被提前到太过严肃的成人阶段。
在宏大的叙事中,个体蜷缩在历史的羽翼之下,社会的发展往往取代了个体的成长。
而在苏童的创作中,时代的背景是模糊的,少年被从历史的长河中剥离出来,于是个体的生存状况来到了前台。
少年是苏童笔下一个绵延多年的叙述群体。
在他的创作中,少年的成长是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
他的少年成长小说关注的重点不是少年们外在形象的变化,而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心理上的波澜。
在苏童虚构的这个世界里,少年首先是成人世界之外的旁观者,完全被动地接受着来自那个神秘世界的信息,迷茫而又兴奋地看着那里所发生的一切。
在关注成人世界的同时,少年感受到的自我成长经历本身,即他们的生活也开始成为叙述的对象。
在逐渐走向成人世界的同时,少年也在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此时他需要来自外界,尤其是来自成人的认可,来不断确认自我的成长。
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力,少年表现出了叛逆与顺从,两种不同的成长状态。
成长是一个行走的过程,它的理想终点是成熟。
苏童笔下的少年以认同父亲的方式从街头回归家庭。
他们曾在两者间挣扎,但最终认同了后者。
伴随着苏童少年成长创作的不断丰富...【英文摘要】In the usual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often juvenile is a shade stage. It pulled back to childishchild age, or to forward to too serious adulthood. In the grand narrative, the individual curled up under the wings of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ten replaces the individual growth. But in the Su Tong’s creation, the times background is blurred, boy was spin-off from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the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individuals came to the fore.Junior described by Su Tong is a group stretc...【关键词】苏童小说少年成长叙事【英文关键词】Su Tong’s novel Narrative about Juveniles Growth【索购全文】联系Q1:138113721 Q2:139938848【目录】论苏童小说中的少年成长叙事中文摘要4-6英文摘要6-7引言9-14第一章蜕变之痛:少年成长叙事的主题指向14-31第一节神秘的他者:少年眼中的成人世界14-19第二节反叛他者:自我确认的代价19-22第三节回归他者:少年成长的终结22-27第四节由蛹到蝶:苏童少年成长叙事的意义27-31第二章讲述与回望:少年成长叙事的诗意生成31-39第一节旁观者的言说31-33第二节回忆的姿态33-35第三节少年叙事的美学意蕴:个体成长中的诗意35-39第三章苏童式少年成长叙事39-45第一节敬父与弑父:与莫言小说中儿童视角之比较39-41第二节粗粝的自省与温和的自我:与余华笔下少年之比较41-45结论45-47参考文献47-49后记49-50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50。
1
青春成长小说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对青春成长的书写一直是中外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春是一种“在路上”不断成
长的生命状态。而苏童以青少年为视角的成长小说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占据着很重要的比
重,他以截取少年成长道路上的一个片段为结构方式,重新解读了青春成长过程中少年
们遇到的痛苦、暴力和残酷,向读者呈现了一个个关于青春成长的残酷故事,并以此来
找出残酷青春背后所具有的美学价值。
“残酷书写”随着先锋文学的繁盛,渐渐在文坛蔚然成风。先锋文学一反中国当代
文学对于残酷和血腥描写的回避和节制,超越了道德尺度,通过打破常规的、超然的“零
度写作”,探寻着其丰富深刻的美学意义。其中,苏童通过他的成长系列小说的写作也
加入了“残酷书写”的行列。小说中苏童真实地呈现了少年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痛
苦与创伤,以一种颠覆式的视角阐释了残酷青春背后的美学价值,使文学从理论先导的
桎梏中释放出新鲜的个体生命体验,给当代文坛带来了新气息。
自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运动,带动了人们对“人”的本体价值的深入探讨,使许
多作家都在反对封建伦理的过程中触及到对青少年诸多问题的思考。如巴金在《家》中,
通过展现觉慧与鸣凤,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三对青年爱情上的不同遭遇,
以及他们所选择的不同生活道路,来揭露封建家庭的败落,和青年一代对光明和新的道
路的追求和探索。这时候的作家写青年人的成长历程更多的是为了控诉了封建家族制
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对年轻生命的摧残,以此来达到一种批判社会的作用。而自此
到改革开放,青春成长小说的发展之路可以说是处于低潮阶段。到了新时期文学,青春
题材又重新开始,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都是描写的另类的青春。不
过他们描写这些的初衷还是以此来控诉社会,带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一直到80年代
西方哲学、文学理论、文学作品的大量引介,中国当代作家的视域、感受、思考和表达
方式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于是在莫言、苏童、余华等作家笔下,青春成长小说从
原先的重内容和重社会批判性转向了重对形式和叙事技巧的开掘,有的又杂糅了非常态
的叙事视角、荒诞叙事等很多现代主义技巧,审美形态十分复杂。其中,苏童则把自己
仅仅定位为一个作家,而非社会的批判者。因此苏童对青春成长的书写进行了重新阐释,
他抛开社会、文化背景,转而关注人的存在属性,从人性的角度和人生发展的时间性上
去把握作品,从而使残酷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存在景观。因此同样是青春成长的题材
的作品,苏童却在主题上已经摆脱了旧有的批判社会、控诉社会的模式,并成功地实现
了反叛与消解,把写作的重心放在对人性的挖掘上,力图在作品中挖掘出隐藏在少年心
2
中的罪恶所造成的残酷和暴力。
王干说:“‘童年视角’被人们反复用来窥视历史、窥照人生,代代相沿,而寓意
永不陈旧,永远给人陌生而亲切的感觉,绝对不会产生审美的疲倦和重复。”[2]在苏童
的青春成长小说中,绝大多是通过少年的眼睛以及少年的窥视与发现来看社会的,所有
的历史都是孩子眼中的历史,所有的人物和自然都是童心所感受到的人和物。这样苏童
就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和时代背景消解,而突出了隐藏在少年心中的最原始、不经文明
矫饰的生命欲望所造成的必然的凶残和暴力。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真实同样也更为残酷
的青春。
李学武在《海峡两岸:成长的三个关键词》中说到:“目睹,或口语化的‘看’是
这一时期的核心动作之一。青春期是个无能为力的年代,独立的日子还在远处蛰伏。因
为稚弱也因为父母的无视,自以为是‘反叛’、‘主体觉醒’的行为,也常常被大人当做
是‘闹别扭’。所能做的,也只有或费尽心思或机缘巧合地‘看’了。而这‘目睹’让
人震惊,往日阻隔在少年成人之间的帷幕缓缓拉开,冰山一角带着无尽的寒意迎面扑
来。”[3]而苏童也正是通过这种“看”将成人世界的变幻莫测、美丑真伪一股脑地铺展开
来,从而使得少年们的美好童年一去不复返,使得少年对成人世界的美好幻想彻底幻灭。
在《乘滑轮车远去》中,便记录下了少年目睹了成人世界后所带给他的的无尽的困惑。
开学第一天,“我”遇见了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丧失、性、暴力、死亡,及种种尴尬
困惑。这一天之中的经历,几乎浓缩了童年之后人的一生。在这一天之中“我”始终为
羞耻感与罪恶感所困扰。
在面对成人世界的冲击后,少年们挣扎着向成人世界靠拢。而粗俗愚昧的父母们对
孩子的成长不闻不问,放任自由,学校也是形同虚设。成长中的少年也只能只身在现实
的迷雾中跌撞前行,对未来充满了恐慌。周莉在《苏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的少年
成长的三个关键词》中谈到:“在香椿树街,成长的终点——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已经
被提前抽空,社会的混乱无序,使这段旅途注定失去了终点,总有人终生未达到成熟。
香椿树街的少年们在经历了最初闯入成人世界的惶惑,痛苦艰难的挣扎与找寻后,感到
了宿命的力量,成长的轨迹画到这里就变成了模糊的虚线。我们看到少年们无助的身影
在香椿树街上徘徊游荡,却看不到任何成熟的希望。”[4]最后,在苏童的小说中我们感到
命运的强大,它深不可测,难以抗拒,而少年们是如此渺小,他们最终只能漠然地承受
命运的安排,在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祸事或死亡前面失去了重量,无法把握自己。最
终,少年们只能在绝望和死亡中完成了自己的残酷的成人仪式。
综上所述,关于青春成长题材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得到发展,并随着外国文学理论的
3
引进,该类小说由原先的重内容和重社会批判性转向了重对形式和叙事技巧的开掘。其
中苏童的青春成长小说更是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而学界关于苏童小说青春残酷的书写的
研究大多是从苏童童年视角的叙述方式入手,去探讨少年在成长过程目睹到的成人世
界,以及少年们在成长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尴尬、暴力和残酷。而本文则试图从一个比较
新颖的领域着手,即着力解读苏童小说中的残酷美学的价值。本文会通过分析苏童笔下
解构了的青春,挖掘出一个个迷茫、麻木的病态少年,分析出充斥在少年成长历程中的
暴力主题。而更重要的是找出隐藏在这种残酷青春书写背后的美学的价值,展现出苏童
式的另类的青春所特有的面对残酷时的冷漠之美、精致伤感的意象之美和难以抗拒的悲
剧宿命之美。
参考文献
[1] 汪政 何平.《苏童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7)
[2] 王干 费振钟.《苏童:在意象的河流里沉浮》.《上海文学》.1988,(1)
[3] 孔范今 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4] 周莉.苏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的少年成长的三个关键词. 2007,(07)
[5] 程明玉. 苏童小说青春主题探微.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6] 邹旗辉:《青春的祭奠——论苏童小说的成长主题》. 江西师范大学, 2007年
[7] 高承新. 旧城少年的成长之痛——苏童“顽童”系列小说成长主题浅论. 语文学刊.2008,
(05)
[8] 张文.论苏童小说中的少年成长叙事.河北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