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第四章)章学诚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 格式:ppt
- 大小:128.50 KB
- 文档页数: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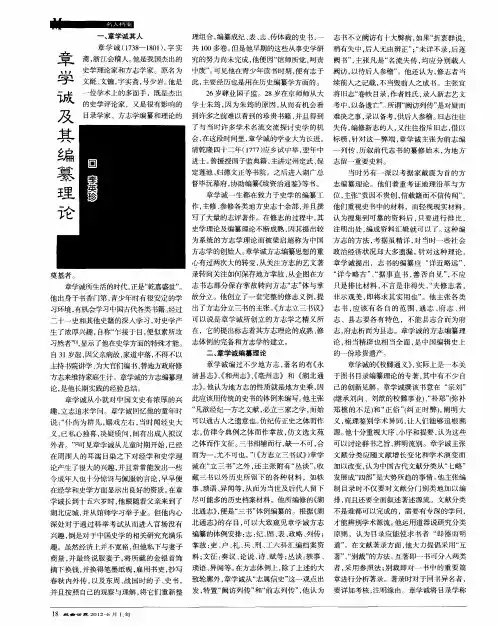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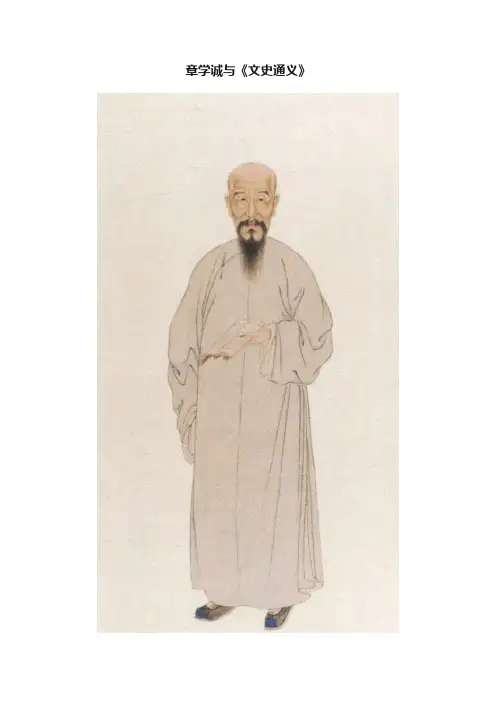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终年六十四岁。
由今而论,章学诚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但他却显于今而不著于时。
生前,他的学术不被理解,极为自负、有着别识独裁的《文史通义》一书也殊乏知音;身故后,没有像样的传记,生平事迹和著作足足埋没了一百二十余年。
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先生为之结撰《年谱》,其学术光辉终于日渐显耀。
到梁启超,更大力张扬,以章学诚之学术不盛行于清代,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辱。
他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也得到了极高的学术评价。
一、《文史通义》之撰著章学诚一再称自己所走的为学道路是一条寂寞之途,人弃我取,无人顾盼,举世所不为,但他的《文史通义》却应当不是在寂寞中完成的。
因为从《文史通义》初撰起,章学诚就屡屡将其中的篇章呈送给他自谓的“同志”、“通人”或一时大僚,致函商讨,请求校正,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
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对所撰《文史通义》的自负,另一方面,实际上也表现出他为推扬自己学术主张所作的努力。
《章氏遗书》所保留的信件中,相当一部分都与此有关。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史通义》撰写的宝贵资料,这些文字,也是章学诚的一种“自识”,即他对自己《文史通义》撰著目的的最直接认识。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大约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在篇章初成时,他就致信给汾阳曹学闵,并抄录“内篇”三首,托他转交国子监监正朱棻元和翰林院侍读学士钱大昕。
他致函朱棻元称:“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
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
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
”则这个“大指”当蕴含在写给钱大昕的《上晓征学士书》中。
其间,章学诚论述了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他初撰《文史通义》的旨趣亦在这封信中得到了明确展现。
信中写道: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术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
……而班史《艺文》独存。
《艺文》又非班固之旧,特其叙例犹可推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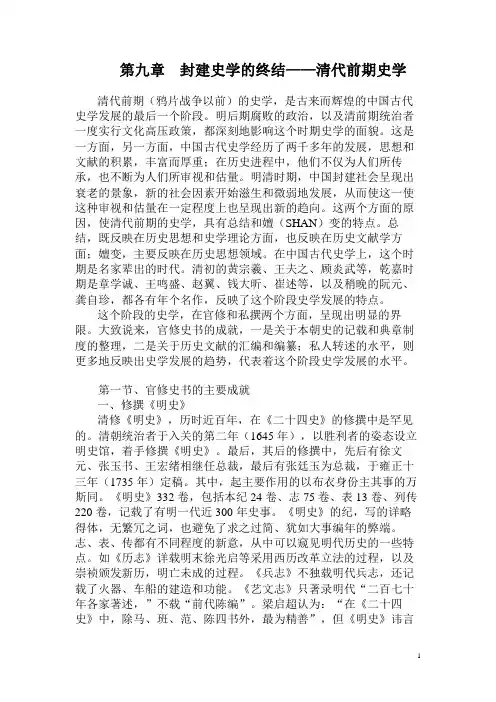
第九章封建史学的终结——清代前期史学清代前期(鸦片战争以前)的史学,是古来而辉煌的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
明后期腐败的政治,以及清前期统治者一度实行文化高压政策,都深刻地影响这个时期史学的面貌。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思想和文献的积累,丰富而厚重;在历史进程中,他们不仅为人们所传承,也不断为人们所审视和估量。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衰老的景象,新的社会因素开始滋生和微弱地发展,从而使这一使这种审视和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新的趋向。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清代前期的史学,具有总结和嬗(SHAN)变的特点。
总结,既反映在历史思想和史学理论方面,也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嬗变,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这个时期是名家辈出的时代。
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乾嘉时期是章学诚、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等,以及稍晚的阮元、龚自珍,都各有年个名作,反映了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特点。
这个阶段的史学,在官修和私撰两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界限。
大致说来,官修史书的成就,一是关于本朝史的记载和典章制度的整理,二是关于历史文献的汇编和编纂;私人转述的水平,则更多地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趋势,代表着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水平。
第一节、官修史书的主要成就一、修撰《明史》清修《明史》,历时近百年,在《二十四史》的修撰中是罕见的。
清朝统治者于入关的第二年(1645年),以胜利者的姿态设立明史馆,着手修撰《明史》。
最后,其后的修撰中,先后有徐文元、张玉书、王宏绪相继任总裁,最后有张廷玉为总裁,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
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以布衣身份主其事的万斯同。
《明史》332卷,包括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记载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史事。
《明史》的纪,写的详略得体,无繁冗之词,也避免了求之过简、犹如大事编年的弊端。
志、表、传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从中可以窥见明代历史的一些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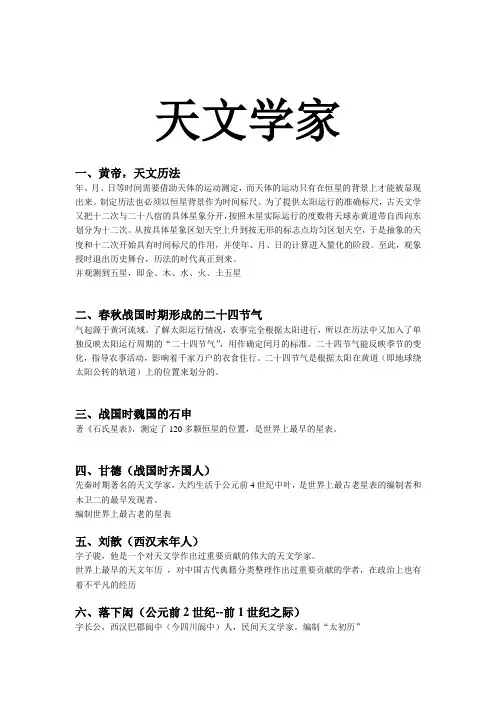
天文学家一、黄帝,天文历法年、月、日等时间需要借助天体的运动测定,而天体的运动只有在恒星的背景上才能被显现出来。
制定历法也必须以恒星背景作为时间标尺。
为了提供太阳运行的准确标尺,古天文学又把十二次与二十八宿的具体星象分开,按照木星实际运行的度数将天球赤黄道带自西向东划分为十二次。
从按具体星象区划天空上升到按无形的标志点均匀区划天空,于是抽象的天度和十二次开始具有时间标尺的作用,并使年、月、日的计算进入量化的阶段。
至此,观象授时退出历史舞台,历法的时代真正到来。
并观测到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五星二、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二十四节气气起源于黄河流域。
了解太阳运行情况,农事完全根据太阳进行,所以在历法中又加入了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二十四节气”,用作确定闰月的标准。
二十四节气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
三、战国时魏国的石申著《石氏星表》,测定了120多颗恒星的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四、甘德(战国时齐国人)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卫二的最早发现者。
编制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五、刘歆(西汉末年人)字子骏,他是一个对天文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伟大的天文学家。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对中国古代典籍分类整理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在政治上也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六、落下闳(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之际)字长公,西汉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民间天文学家。
编制“太初历”七、张衡,东汉(78~139)东汉科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召县石桥镇)人。
精通天文、历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候风地动仪。
在天文学理论方面,张衡是“浑天派”的主要代表。
关于天地之起源,他认为天地未分之前,乃是一片混沌,既分之后,轻者上升为天,重者凝聚为地,阴阳相荡,产生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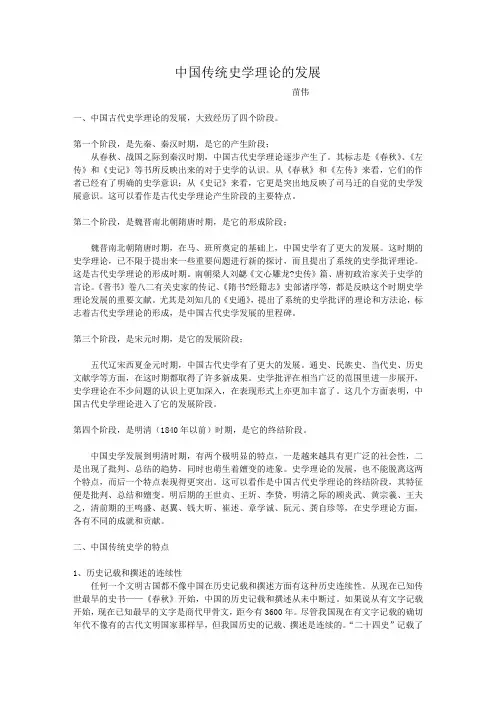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苗伟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是它的产生阶段;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逐步产生了。
其标志是《春秋》、《左传》和《史记》等书所反映出来的对于史学的认识。
从《春秋》和《左传》来看,它们的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从《史记》来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史学理论产生阶段的主要特点。
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它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马、班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这时期的史学理论,已不限于提出来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而且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
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
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
《晋书》卷八二有关史家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等,都是反映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
尤其是刘知几的《史通》,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时期,是它的发展阶段;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通史、民族史、当代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在这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亦更加丰富了。
这几个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它的终结阶段。
中国史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
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这两个特点,而后一个特点表现得更突出。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阶段,其特征便是批判、总结和嬗变。
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前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在史学理论方面,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

【章学诚《文史通义》】章学诚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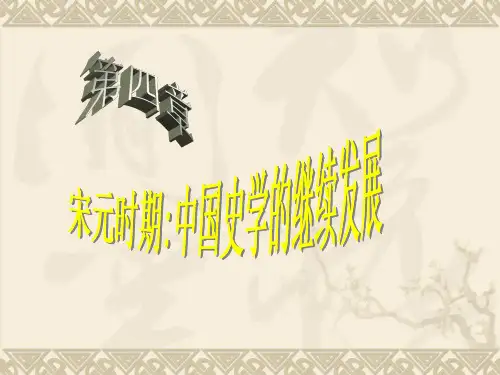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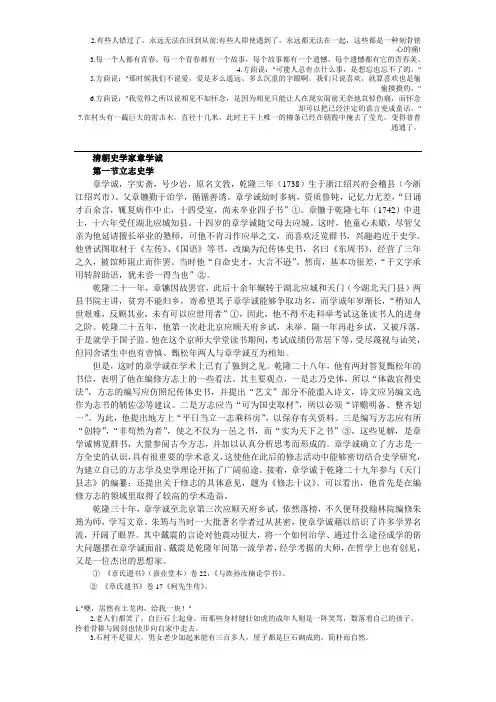
5.方茴说:"那时候我们不说爱,爱是多么遥远、多么沉重的字眼啊。
我们只说喜欢,就算喜欢也是偷偷摸摸的。
"6.方茴说:"我觉得之所以说相见不如怀念,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
"7.在村头有一截巨大的雷击木,直径十几米,此时主干上唯一的柳条已经在朝霞中掩去了莹光,变得普普通通了。
清朝史学家章学诚第一节立志史学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乾隆三年(1738)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
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
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①。
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十六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
十四岁的章学诚随父母去应城。
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
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
当时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逊”。
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学诚年岁渐长,“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
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未举。
隔一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他在这个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
乾隆二十八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②等建议。


清朝史学家章学诚第一节立志史学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乾隆三年(1738)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
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
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①。
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十六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
十四岁的章学诚随父母去应城。
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
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
当时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逊”。
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学诚年岁渐长,“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
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未举。
隔一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
他在这个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
乾隆二十八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②等建议。
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
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
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③。
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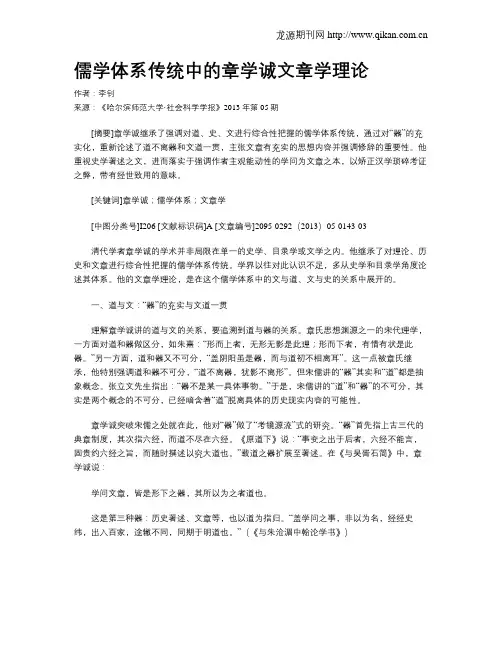
儒学体系传统中的章学诚文章学理论作者:李钊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05期[摘要]章学诚继承了强调对道、史、文进行综合性把握的儒学体系传统,通过对“器”的充实化,重新论述了道不离器和文道一贯,主张文章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并强调修辞的重要性。
他重视史学著述之文,进而落实于强调作者主观能动性的学问为文章之本,以矫正汉学琐碎考证之弊,带有经世致用的意味。
[关键词]章学诚;儒学体系;文章学[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143-03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学术并非局限在单一的史学、目录学或文学之内。
他继承了对理论、历史和文章进行综合性把握的儒学体系传统。
学界以往对此认识不足,多从史学和目录学角度论述其体系。
他的文章学理论,是在这个儒学体系中的文与道、文与史的关系中展开的。
一、道与文:“器”的充实与文道一贯理解章学诚讲的道与文的关系,要追溯到道与器的关系。
章氏思想渊源之一的宋代理学,一方面对道和器做区分,如朱熹:“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
”另一方面,道和器又不可分,“盖阴阳虽是器,而与道初不相离耳”。
这一点被章氏继承,他特别强调道和器不可分,“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但宋儒讲的“器”其实和“道”都是抽象概念。
张立文先生指出:“器不是某一具体事物。
”于是,宋儒讲的“道”和“器”的不可分,其实是两个概念的不可分,已经暗含着“道”脱离具体的历史现实内容的可能性。
章学诚突破宋儒之处就在此,他对“器”做了“考镜源流”式的研究。
“器”首先指上古三代的典章制度,其次指六经,而道不尽在六经。
《原道下》说:“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载道之器扩展至著述。
在《与吴胥石简》中,章学诚说: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为之者道也。
这是第三种器:历史著述、文章等,也以道为指归。
“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
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哪几位?中国十大历史学家及理由1、左丘明2、司马迁3、班固4、陈寿5、范晔6、刘知几7、杜佑8、司马光9、章学诚10、梁启超1、理由一,左丘明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奠基人、先秦史官文化时代第一位有名可考的史学家、相传他所著《左传》与早前的《尚书》相比,应是中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堪称中国史学形成的标志;理由二,《左传》与五经中的《春秋》有明显的互文性联系,其记人叙事不但更清晰完整,而且史料更丰富,范围远超出一国一地,对社会重大发展变革更加敏锐,典籍专家孔颖达特别指出“传实经虚”以示区别;理由三,《左传》作为纪传史学的最早范本,具有很高史学文学价值,尤擅战争描写,许多场面已成为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和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人物性格鲜明,夹叙夹议手法简洁,述评公允,对人事的预言精准。
2、理由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西汉史传文学泰斗,他的史学地位在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世界上也堪称一流大师;理由二,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的《史记》对汉族与周边多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一视同仁,首开记录社会经济的范例,不但有耿直犯颜的公义勇气、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拨乱反正的调查研究,而且,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叙事的整体构思、对史实因果关系的精辟分析、层次分明而五种类型相融的体例编制所具的原创性,都堪称千古典范;理由三,《史记》既是史家之绝唱,又是无韵之离骚,表现出发愤著书的顽强毅力,其人物之鲜明丰满、叙事之简洁老练、语言之丰富多彩都代表了中国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
3、理由一,班固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学家、中国断代史学第一人,传世名著《汉书》作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经班氏家族门生四人之手历数十年呕心沥血而成;理由二,班固治史意在追述西汉帝业,“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体例仿效《史记》而有所增删,内容因事命篇,述及五朝70余年大事,开创了以群雄夺权为始,以篡权贼臣被诛告终的断代记述新格局;理由三,班固叙事规模宏大,内容广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外征战与国际关系、物质生产与文化交流,以五行灾变说来取代司马迁的兴衰规律论,观念有蜕化而体例有改进,对后世官方正统史学影响深远。
史类《文史通义》清·章学诚著卷四内篇四文史通义清·章学诚著卷四内篇四说林道,公也;学,私也。
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
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
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
故曰道公而学私。
道同而术异者,韩非有《解老》、《喻老》之书,《列子》有《杨朱》之篇,墨者述晏婴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
述同而趣异者,子张难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说,张仪破苏秦之从。
宗旨不殊,而所主互异者也。
渥洼之驹,可以负百钧而致千里;合两渥洼之力,终不可致二千里。
言乎绝学孤诣,性灵独至,纵有偏阙,非人所得而助也。
两渥洼驹,不可致二千里;合两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负二百钧而各致千里。
言乎鸿裁绝业,各效所长,纵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据也。
文辞非古人所重,草刨讨论,修饰润色,固已合众力而为辞矣:朔于尽善,不期于矜私也。
丁敬礼使曹子建润色其文,以谓“后世谁知定吾文者”,是有意于欺世也。
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是使后世读一人之文,而获两善之益焉,所补岂不大乎?司马迁袭《尚书》、《左》、《国》之文。
非好同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
司马迁点窜《尚书》、《左》、《国》之文,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非好异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
有事于此,询人端末,岂必责其亲闻见哉?张甲述所闻于李乙,岂盗袭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
张甲述李乙之言,而声容笑貌,不能尽为李乙,岂矫异哉?孔子学周公,周公监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
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
”盖尝观于山下出泉,沙石隐显,流注曲直,因微渐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观于孩提呕哑,有声无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整齐故事,与专门家学之义不明,详《释通》、《答客问》。
而一代之史,鲜有知之者矣;州县方志,与列国史记之义不明,详《方志》篇。
而一国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谱牒不受史官成法,详《家史》篇。
而一家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诸子体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鲜有知之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