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
- 格式:doc
- 大小:31.00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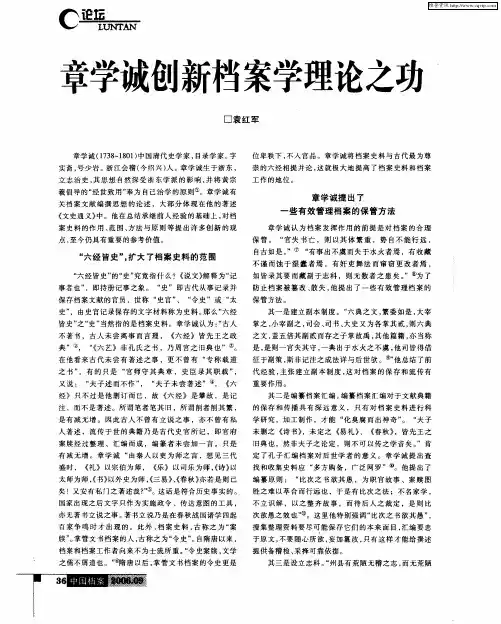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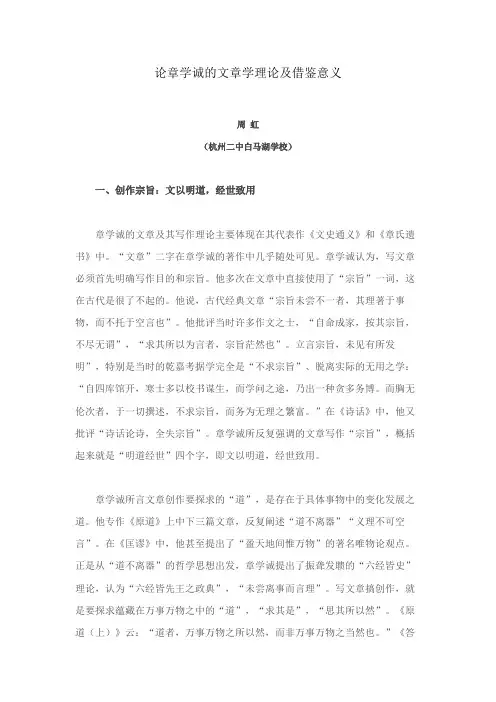
论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及借鉴意义周虹(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一、创作宗旨:文以明道,经世致用章学诚的文章及其写作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
“文章”二字在章学诚的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
章学诚认为,写文章必须首先明确写作目的和宗旨。
他多次在文章中直接使用了“宗旨”一词,这在古代是很了不起的。
他说,古代经典文章“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
他批评当时许多作文之士,“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
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特别是当时的乾嘉考据学完全是“不求宗旨”、脱离实际的无用之学:“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
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
”在《诗话》中,他又批评“诗话论诗,全失宗旨”。
章学诚所反复强调的文章写作“宗旨”,概括起来就是“明道经世”四个字,即文以明道,经世致用。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变化发展之道。
他专作《原道》上中下三篇文章,反复阐述“道不离器”“义理不可空言”。
在《匡谬》中,他甚至提出了“盈天地间惟万物”的著名唯物论观点。
正是从“道不离器”的哲学思想出发,章学诚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理论,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未尝离事而言理”。
写文章搞创作,就是要探求蕴藏在万事万物之中的“道”,“求其是”,“思其所以然”。
《原道(上)》云:“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答沈枫墀论学》又云:“文求是而学思其所以然。
”《与史余村简》也说:“文求其是耳。
”《朱陆》则反复强调:“学求其是”“实,学求是”。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更是指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有补于世”、可以“救世扶偏”的具体方略。
《与史余村》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俗嫌》又说:“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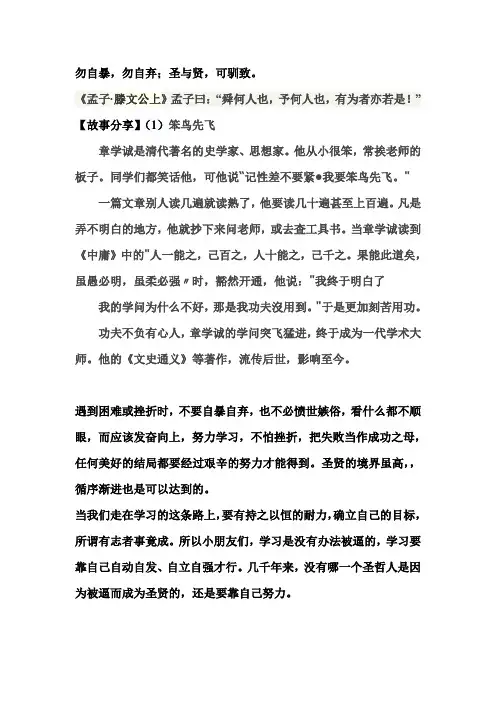
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故事分享】(1)笨鸟先飞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
他从小很笨,常挨老师的板子。
同学们都笑话他,可他说“记性差不要紧•我要笨鸟先飞。
"
一篇文章别人读几遍就读熟了,他要读几十遍甚至上百遍。
凡是弄不明白的地方,他就抄下来问老师,或去査工具书。
当章学诚读到《中庸》中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时,豁然开通,他说:"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学问为什么不好,那是我功夫沒用到。
"于是更加刻苦用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章学诚的学问突飞猛进,终于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他的《文史通义》等著作,流传后世,影响至今。
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不要自暴自弃,也不必愤世嫉俗,看什么都不顺眼,而应该发奋向上,努力学习,不怕挫折,把失败当作成功之母,任何美好的结局都要经过艰辛的努力才能得到。
圣贤的境界虽高,,循序渐进也是可以达到的。
当我们走在学习的这条路上,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力,确立自己的目标,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所以小朋友们,学习是没有办法被逼的,学习要靠自己自动自发、自立自强才行。
几千年来,没有哪一个圣哲人是因为被逼而成为圣贤的,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一、章学诚其人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人。
他是我国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
原名为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
他是一位学术上的多面手,既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又是很有影响的目录学家、方志学编纂和理论的奠基者。
章学诚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盛世”。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有很安定的学习环境,有机会学习中国古代各类书籍。
经过二十一史和其他史籍的深入学习,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自称“乍接于目,便似素所攻习然者”[1],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特殊才能。
自31岁起,因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不得不以主持书院讲学、为大官们编书、替地方政府修方志来维持家庭生计。
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是他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
章学诚从小就对中国文史有浓厚的兴趣,立志追求学问。
章学诚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
”[2]可见章学诚从儿童时期开始,已经在周围人的耳濡目染之下对经学和史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且常常能发出一些令成年人也十分惊讶与佩服的言论,早早便在经学和史学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在章学诚长到十五六岁时,他跟随着父亲来到了湖北应城,并从馆师学习举子业。
但他内心深处对于通过科举考试从而进入官场没有兴趣,倒是对于中国史学的相关研究充满乐趣。
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他私下与妻子商量,并最终说服妻子,将所戴的金银首饰摘下换钱,并换得笔墨纸砚,雇用书吏,抄写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并且按照自己的观察与理解,将它们重新整理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一共100多卷。
但是他早期的这些从事史学研究的努力尚未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
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便有志于此,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26岁肄业国子监。
28岁在京师师从大学士朱筠,因为朱筠的原因,从而有机会看到许多之前难以看到的珍贵书籍,并且得到了与当时许多学术名流交流探讨史学的机会,在这段时间里,章学诚的学业大为长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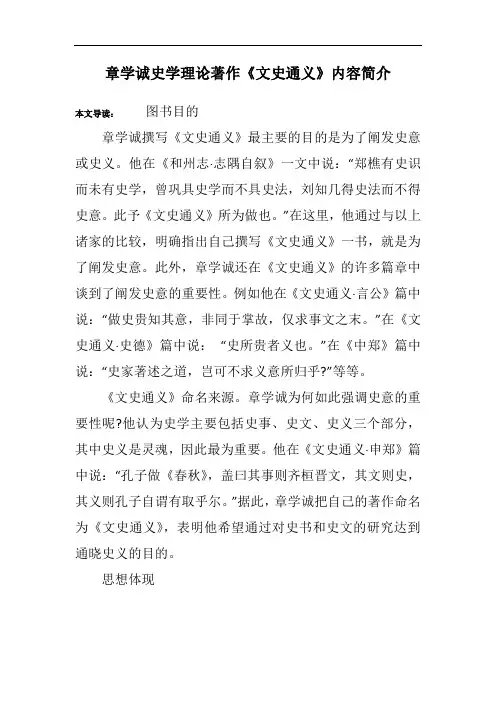
章学诚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内容简介本文导读:图书目的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义。
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
”在这里,他通过与以上诸家的比较,明确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史意。
此外,章学诚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
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
”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史所贵者义也。
”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
《文史通义》命名来源。
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
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
”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
思想体现首先,扶持世教,匡正人心。
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学诚读书着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
”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所在,不过我们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
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在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的,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进步意义。
其次,扭转僵化的考据学风。
这点前文已有论述。
再次,对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进行揭露和抨击。
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鄙着《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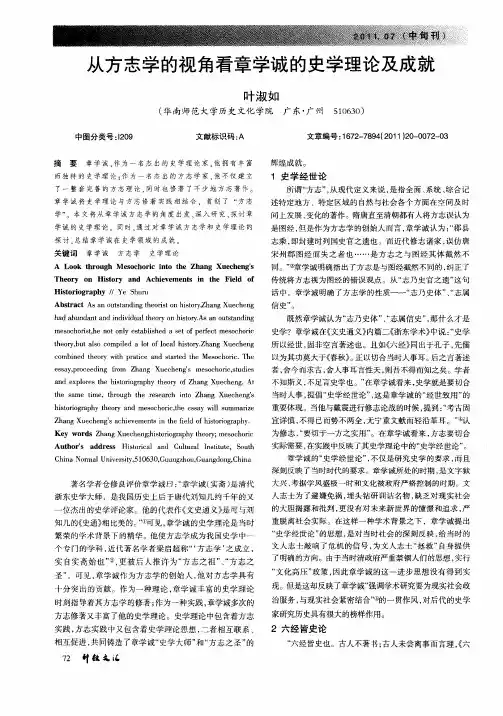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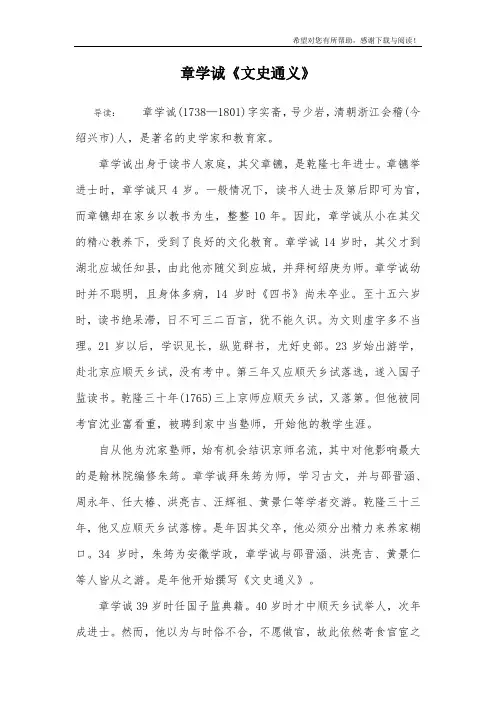
章学诚《文史通义》导读: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
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
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
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
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
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
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
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
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
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
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
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
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
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
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
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
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
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
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
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
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
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
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
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
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
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
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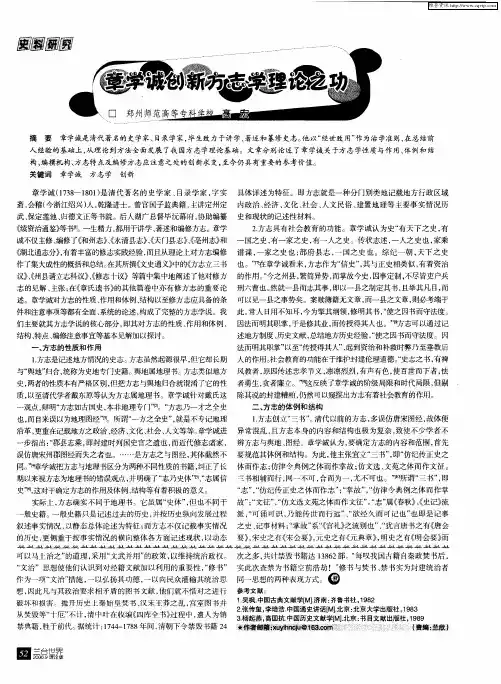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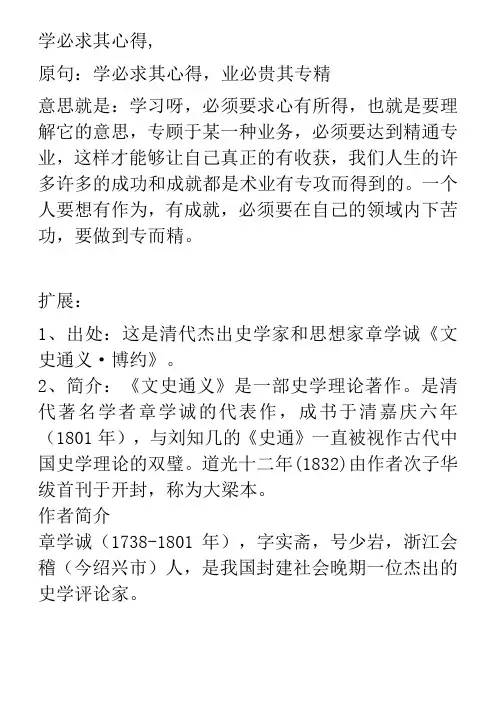
学必求其心得,
原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其专精
意思就是:学习呀,必须要求心有所得,也就是要理解它的意思,专顾于某一种业务,必须要达到精通专业,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有收获,我们人生的许多许多的成功和成就都是术业有专攻而得到的。
一个人要想有作为,有成就,必须要在自己的领域内下苦功,要做到专而精。
扩展:
1、出处:这是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
2、简介:《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成书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
道光十二年(1832)由作者次子华绂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
作者简介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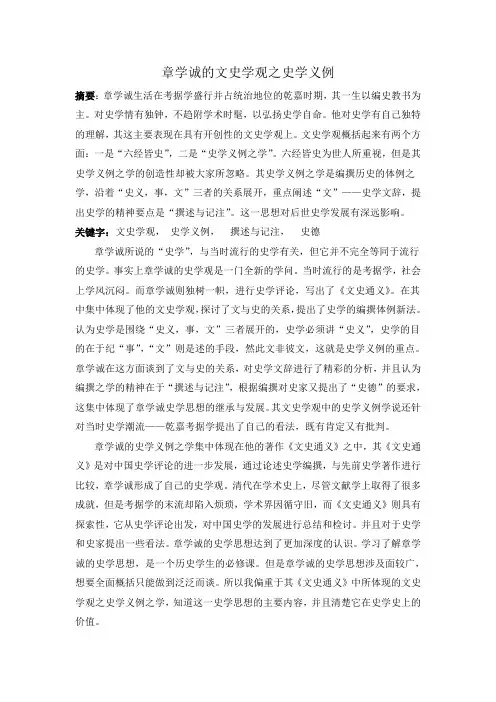
章学诚的文史学观之史学义例摘要:章学诚生活在考据学盛行并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时期,其一生以编史教书为主。
对史学情有独钟,不趋附学术时髦,以弘扬史学自命。
他对史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其这主要表现在具有开创性的文史学观上。
文史学观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六经皆史”,二是“史学义例之学”。
六经皆史为世人所重视,但是其史学义例之学的创造性却被大家所忽略。
其史学义例之学是编撰历史的体例之学,沿着“史义,事,文”三者的关系展开,重点阐述“文”——史学文辞,提出史学的精神要点是“撰述与记注”。
这一思想对后世史学发展有深远影响。
关键字:文史学观,史学义例,撰述与记注,史德章学诚所说的“史学”,与当时流行的史学有关,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流行的史学。
事实上章学诚的史学观是一门全新的学问。
当时流行的是考据学,社会上学风沉闷。
而章学诚则独树一帜,进行史学评论,写出了《文史通义》。
在其中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史学观,探讨了文与史的关系,提出了史学的编撰体例新法。
认为史学是围绕“史义,事,文”三者展开的,史学必须讲“史义”,史学的目的在于纪“事”,“文”则是述的手段,然此文非彼文,这就是史学义例的重点。
章学诚在这方面谈到了文与史的关系,对史学文辞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并且认为编撰之学的精神在于“撰述与记注”,根据编撰对史家又提出了“史德”的要求,这集中体现了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文史学观中的史学义例学说还针对当时史学潮流——乾嘉考据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有肯定又有批判。
章学诚的史学义例之学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文史通义》之中,其《文史通义》是对中国史学评论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论述史学编撰,与先前史学著作进行比较,章学诚形成了自己的史学观。
清代在学术史上,尽管文献学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考据学的末流却陷入烦琐,学术界因循守旧,而《文史通义》则具有探索性,它从史学评论出发,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总结和检讨。
并且对于史学和史家提出一些看法。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达到了更加深度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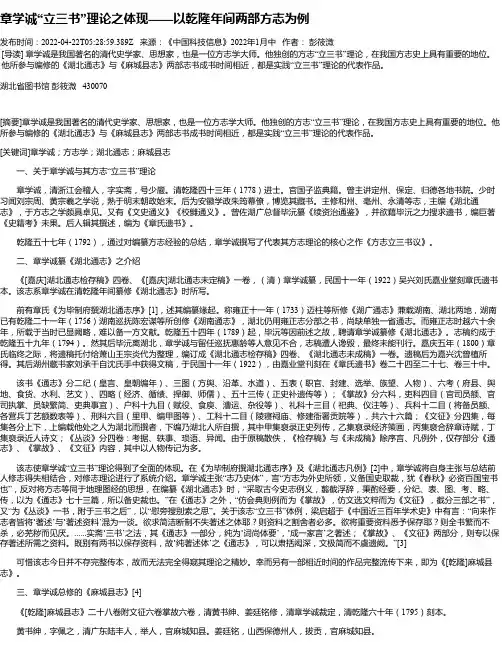
章学诚“立三书”理论之体现——以乾隆年间两部方志为例发布时间:2022-04-22T05:28:59.389Z 来源:《中国科技信息》2022年1月中作者:彭筱溦[导读] 章学诚是我国著名的清代史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方志学大师。
他独创的方志“立三书”理论,在我国方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他所参与编修的《湖北通志》与《麻城县志》两部志书成书时间相近,都是实践“立三书”理论的代表作品。
湖北省图书馆彭筱溦 430070[摘要]章学诚是我国著名的清代史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方志学大师。
他独创的方志“立三书”理论,在我国方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他所参与编修的《湖北通志》与《麻城县志》两部志书成书时间相近,都是实践“立三书”理论的代表作品。
[关键词]章学诚;方志学;湖北通志;麻城县志一、关于章学诚与其方志“立三书”理论章学诚,清浙江会稽人,字实斋,号少巖。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
官国子监典籍。
曾主讲定州、保定、归德各地书院。
少时习闻刘宗周、黄宗羲之学说,熟于明末朝政始末。
后为安徽学政朱筠幕僚,博览其藏书。
主修和州、亳州、永清等志,主编《湖北通志》,于方志之学颇具卓见。
又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
曾佐湖广总督毕沅纂《续资治通鉴》,并欲藉毕沅之力搜求遗书,编巨著《史籍考》未果。
后人辑其撰述,编为《章氏遗书》。
乾隆五十七年(1792),通过对编纂方志经验的总结,章学诚撰写了代表其方志理论的核心之作《方志立三书议》。
二、章学诚纂《湖北通志》之介绍《[嘉庆]湖北通志检存稿》四卷、《[嘉庆]湖北通志未定稿》一卷,(清)章学诚纂,民国十一年(1922)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章氏遗书本。
该志系章学诚在清乾隆年间纂修《湖北通志》时所写。
前有章氏《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1],述其编纂缘起。
称雍正十一年(1733)迈柱等所修《湖广通志》兼载湖南、湖北两地,湖南已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湖南巡抚陈宏谋等所创修《湖南通志》,湖北仍用雍正志分部之书,尚缺单独一省通志。
F e b .2024V o l .44N o .1语文学刊J o u r n a l o f L a n g u a ge a n d L i t e r a t u r e S t u d i e s 2024年2月第44卷第1期[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 文体视阈下的古代写作教育思想研究 (2017B -01);甘肃省 十四五 教育规划课题 两个结合 视域下高校创建特色文化品牌路径研究 (G S [2023]G H B 1503)阶段性研究成果㊂[作者简介]张祖玲,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教育考试院高级教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崔正升,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博士研究生,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㊂章学诚文章写作教育观论略ʻ张祖玲1 崔正升2(1.甘肃白银市白银区教育考试院,甘肃 白银 730900;2.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30)[摘 要] 章学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写作教育经验㊂他以史学家的宽广视野考察作文教学,提出了一些独到观点,主要有:文史并重㊁迎机善导的初学入门观;倡论文德㊁积养学问的主体建构观;言之有物㊁有补于世的文章美学观;注重整体㊁先后有序的文体训练观㊂虽说章学诚主要是针对八股文写作教学而言,但放在今天看,其贯通文史㊁博综诸学的写作教育主张仍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㊁指导性㊂[关键词] 章学诚; 写作教育; 初学入门; 主体建构; 文体训练[中图分类号]H 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24)01-0103-06d o i :10.3969/j.i s s n .1672-8610.2024.01.016 被誉为浙东史学殿军 的章学诚,因不满乾嘉时代脱离实际的学术风气,抱着 救世纠偏 的文化使命另辟蹊径,在史学㊁目录学㊁文章学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㊂目前人们对章学诚学术思想各方面的研究已很深入,而对其文章写作教育思想研究还远远不够㊂章学诚一生以著书讲学为主,曾先后主讲定武书院㊁清漳书院㊁敬胜书院㊁莲池书院㊁文正书院,还担任过梁国治等人的家庭教师㊂长期的教学实践,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㊁史学思想,还积累了宝贵的写作教育经验,值得我们深入开掘和探赜㊂一㊁文史并重㊁迎机善导的初学入门观中国古代十分重视青少年的学文之道,有关初学者 入门 的论述颇多㊂作为一代文史大家,章学诚也十分重视写作的入门问题,强调写作入门务必要谨慎而行㊂但他没有停留在过去 先放后收 或 先收后放 的单线论争上,而是以史学家的宽广视野考察作文教学,提出了更加切合儿童身心特点和教学规律的独到见解㊂在教学内容和教材选用上,章学诚认为写作的根本在于有充实的学问,因而主张将传统的经学㊁史学作为初学入门的重要内容㊂明清两代的写作教育中,各种文选泛滥成灾㊂学堂中大多急功近利,以讲习八股时文为主,但也有人竭力反对诵读时文,提倡研习古文㊂对此章学诚都不以为然,他认为不论是古文还是八股时文,判断其优劣的关键在于 有为而言与无为而言 [1]87,这里所谓的 有为 主要指学问的充实㊂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他在自己编写的教材‘文学“(该书不传)中如此阐明编选宗旨: 取先民撰述,于典籍有所发挥,道器有所疏证,华有其文,而实不离学者,删约百篇,劝诱蒙俗㊂ [1]337看得出,他心目中 文 的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一般的诗歌散文,也囊括了经史㊁典章等实用之文,体现出文史并重的选文取向㊂还有,传统私塾教学主要以诵读儒家经典为主,这样极易造成学生食古不化㊂对此,章学诚指出: 童子之学,端以先入为主,初学为文,使串经史而知体要,庶不误于所趋㊂ [1]682在他看来,诵读经典固然重要,但不能架空经典㊁割断源头,必须要充分了解经典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主张在历史语境中去复活经典㊁理解经典㊂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写作教育也极具启发意义:一方面,写作教育要开展以经典文化为内容的 根性 教育,惟有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才能叶茂;另一方面,要改变那种囫囵吞枣式的死记硬背,尽可能让学生在复活经典的历史语境中咀嚼经典㊁消化经典㊂在教学方法方面,章学诚主张要切合初学者的身心实际,尽可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㊂汉代以来的写作教学大多要求学生阐发经典义理,但是这种 揠苗助长 的做法明显脱离了实际,学生其实很难写出真情实感㊂对此,章学诚指出: 为童幼之初,天质未泯,遽强以所本无,而穿凿以人事,揠苗助长,槁固可立而待也㊂夫凤雏出,不必遽能飞也;急以振翼为能事,则藩篱雀,何足喻其多哉! [1]688意思是要根据儿童的天性和心理特点,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如果拔苗助长㊁急于求成,那么无异于摧残幼苗㊂在他看来, 善教学者,必知文之节候㊁学之性情,故能使人勤而不苦,得而愈奋,终身愤乐而不能自已也 [1]688㊂意思是写作教学要遵循学生心理,调动学习兴趣㊂为此,他主张写作教学要 迎其机而善导 [1]682,意思是要尊重㊁顺应学生的言语天性,做到因势利导,这样才能才尽其用㊂至于具体方法,他主张 初学先为论事,继则论人 [1]683,意思是初学为文要由易到难,先从‘左传“‘史记“学习论事,而后从‘诗经“学习论人,这样更能诱发学生的写作欲望,滋养学生的写作才情㊂另外,章学诚对初学写作的法度问题也极为重视㊂他认为适当地摹仿有助于提高写作水平,但他反对机械呆板的 死法 ,认为 孺子学文,但拘一例,则蹊径无多,易于习成括调㊂体格时变,使之得趣无穷,则天机鼓舞,而文字之长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1]684㊂意思是初学写作如果墨守成规㊁拘泥定法,就会越走越窄㊁思维僵化;只有不断地突破既有的写作范式,才能富有活力㊁日久弥新㊂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批评 世俗训课童子必从时文入手 的习气,指出 时文体卑而法密,古文道备而法宽㊂童幼知识初开,不从宽者入手而使之略近于道,乃责以密者而使之从事于卑 [1]682㊂章氏所谓的 时文 也即八股文,有固定的程式套路㊂他认为初学者一开始就摹仿八股文,不但会束缚学生思维,还会产生畏惧心理㊂他认为这种急功近利㊁看重形式的训练对提高写作水平并无太多益处,而那些 道备而法宽 ㊁弥久不衰的经典文章才是初学者研习的典范㊂二㊁倡论文德㊁积养学问的主体建构观写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作者的心理结构㊁个性素养对创作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㊂在中国文学 内重外轻 的思维方式和 以心为贵 的文化观念中,文学创作主体的才情素养历来受到人们关注,如曹丕提出的 文以气为主 命题,刘知己的 才㊁学㊁识 论,清初叶燮提出的 才㊁胆㊁识㊁力 说等㊂相较而言,章学诚的 文德 论可谓独树一帜,它不仅极大丰富了传统写作主体论的内涵,还从修德㊁修身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㊂身处乾嘉时代的章学诚深恶当时文人迎合流俗㊁言不由衷的不良文风,认为文章写作必须要树立良好的道德风范㊂他一方面强调 才㊁学㊁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 [2]255;另一方面又指出 道德不修,学问无以自立,根本蹶而枝叶萎 [2]436,认为作者除了要具备才气㊁学问㊁识见㊁阅历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文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还要具备良好的写作职业道德㊂章氏所论之 德 具体分为 史德 与 文德 ㊂所谓 史德 ,指作者的学术品德;所谓 文德 ,主要指对待文章应取的态度,又分 临文主敬 与 论古必恕 ㊂其中 临文主敬 要求作者加强心性锻炼,在写作时能以理性制约情感,使之尽量符合事理; 论古必恕 要求评论者要对古人的经历㊁处境要有所认识,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㊂我们也可以把二者看作是章学诚构建写作人格的理想范式,其实质是要求作者对待文章要端正心术㊁严谨求实,切不可矫情虚饰㊁迎合流俗㊂章学诚还以自己的著述经历为例,指出 凡意见与古人不约而同者,必著前人之说,示不相袭 [2]86,强调文章写作要尊重他人成果,绝不能蹈袭别人的观点㊂章学诚的 文德 论不仅有力批判了当时的不良文风,对我们今天建构健康㊁真诚㊁丰满的主体人格也具有指导意义㊂注重作者学养是章氏主体论的又一特色㊂他强调 故待学问充足,而自以有得于中者,发而为文,文乃不入于恍惚也 [1]606,意思只有学识充足深厚,才可为立言行道打下坚实的根基㊂具体到如何打下深厚的学养根基,章学诚一方面认为应该从古典原著入手,广泛涉猎㊁汲取精华;另一方面又强调 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 博而不杂,约而不漏 [2]192,认为只有把 博学 与 守约 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治学之道㊂他还反复强调建立在学问之上的 志识 对文章写作的决定性作用,认为 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 ,意思是决定文章价值的关键在于有无独到深刻的思想见地㊂至于积养学问的具体方法,他一方面推崇诵读,认为熟读背诵时如果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就能把佳词好句㊁精彩语段深刻地留在记忆中;另一方面还十分看重札记在积累素材方面的作用,指出 一切专门名家,苦心孤诣,自非造次可达,即案头有翻涉之书,每日必有所记,而札记于册,以待日后之会通,岂有所难者,亦消遣所藉以不寂寞也,宁不图之 [1]641㊂看得出,札录是知识积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功力,凡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都有过作札记的艰苦经历㊂为了储存积累素材,章学诚还提出了 别类分求之法 ,也即 标立宏纲细目,摘比排纂,以意贯之 学问既得恢扩,而文章亦增色彩 [1]663,主张既要眼看口诵,更要勤于动手,做到分门别类,按款摘记,这样不仅充实了学问,文章也会增色不少㊂这些易于操作㊁切实可行的方法经验放在今天看,不论对于治学还是写作,都是颇有裨益,毫不过时的㊂三㊁言之有物㊁有补于世的文章美学观对文章美学特质和理想范式的探求与建构,历来是文章学家孜孜不懈的追求㊂作为一位 经世致用 的文史学家,章学诚不仅十分重视文章写作的美学规则,强调诗文对社会的功用,还把 言之有物 中有所见 放在首位,将传统实用主义文学观推向一个新高度㊂清代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是桐城派古文,他们虽然也标榜 言有物 修辞立其诚 ,但在创作实践上却过分追求 法度 ,强调文章的形式美㊂章学诚对这种浮华空疏的文弊极为不满,主张 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 [1]643,认为文章写作固然离不开文辞形式,但必须要教育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写出有用之文㊂怎样才能做到 有补于世 ?对此,章学诚指出: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㊂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有所见,初非好为炳炳娘娘,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㊂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㊂ [2]347在他看来,诗文创作最要紧的是内容充实,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文辞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了表达思想,而并非是为了炫耀文采㊂但是章学诚也没有轻视㊁否定文章艺术形式的意思,而是强调 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 [2]423,意思是文章的艺术形式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艺术上的美与丑不能简单根据作品思想内容的真确㊁充实与否而下结论㊂章学诚所阐述的这些观点,不仅有力矫正了当时的不良文风,对于今天写作教育中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㊂章学诚曾提出著名的 文律观 ,并将其概括为 清真 二字,实质上是文章写作的美学规则㊂何谓 清 ?章学诚说: 清之为言,不杂也 [1]365㊂意思是文章的外在形式必须做到体制风格纯正一致,文辞文气清而不杂㊂他继承了中国古代 立言得体 的传统,认为 ‘诗“语不可以入‘书“,‘易“言不可以附‘礼“,虽以圣人之言,措非其所,即不洁矣,辞不洁则气不清矣 [1]613㊂意思是说,即便是圣贤之文,如果用语不符合文体特征,那么写出来的文章也不会纯正清洁㊂他还从 清而不杂 的角度提出了 精练雅洁 的语言风格要求,强调文章语言 要简㊁要严㊁要核㊁要雅 [2]136的 四要 原则㊂那么什么又是 真 呢?章学诚说, 真则理无支也 [1]81; 真之为言,实有所得而著于言也 [1]377㊂可见这里的 真 是从思想内容和写作宗旨而言的,要求文章写作要有真情实感,要有独到见识㊂基于对 真 的认识,章学诚又提出了 至文 的美学标准: 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㊂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㊂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㊂ [2]259在他看来, 至文 必须具备气昌与情挚两重特质,只有抒发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做到气平情正,才能成为真正的 至文 ㊂章学诚的 清真 说,不仅要求艺术形式上的纯洁不杂和思想内容上的真情实感,更在于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㊂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章学诚文章美学观的精髓所在: 文贵发明,亦期用世,斯可与进于道矣㊂ [3]280就是文章既要有独到的见识,又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才是为文的最高境界㊂四㊁注重整体㊁先后有序的文体训练观在科举泛滥的时代,一般人总是把学问和举业视为二途,以为做学问㊁学古文会影响举业,不如专习时文来得快捷,这遭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竭力反对㊂章学诚虽然深知八股文的流弊,但他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抱着 救世纠偏 的初衷理性审视㊁积极改造,提出了 学问与文章并进,古文与时文参营 的折中原则㊂他意识到,在举业至上的情势下,写作教学终究还是以八股文为主㊂只有探索出许多具体可行的训练方法,才能通过 高品位 的八股文写作来实现写作水平的整体跃升㊂章学诚文体训练观的要义首先在于他对八股文的客观认识以及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文体分类训练法㊂在许多人眼中,八股文僵化刻板㊁流弊丛生,而章学诚却不这样认为㊂在他看来,科举考试的初衷是通过撰写高品位的八股文来考察人们的品性才学,而那些 世之徒务举业者 却因为醉心功名㊁贪恋富贵而写出了空洞的 无质八股文 ㊂章学诚还注意到八股文具有综合性极强的体式特征,其‘论课蒙学文法“如是说: 时文之体,虽曰卑下,然其文境无所不包,说理㊁论事㊁辞命㊁记叙㊁纪传㊁考订,各有得其近似,要皆相题为之,斯为美也㊂ [1]686-687意思是说,八股文在长期的发展中吸收借鉴了其他文体的写作方法,它本身并没有错误,反而因其 集古代文体之大成,表现出文备众体的独有特征 [4],在培养综合写作能力方面具有优势㊂章学诚如此强调八股文的综合性特征,这与他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文体分类训练观不无关系㊂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是章学诚作为史学家的独到治学思想,大意是将各类著作按照科学㊁系统㊁辨证的原则进行分类,将其来龙去脉考证得像镜子一样明净透彻㊂他特别强调辨明古文源流的重要性,认为 古文体制源流,初学入门,当首辨也 [2]674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章学诚认为文章的体裁种类虽然繁多,但大体上包含在 论事㊁论人㊁传赞㊁叙列㊁考订㊁叙事㊁说理 这七种文体之内,即所谓 是知文体虽繁,要不越此六七类例 [1]686㊂在他看来,学生只要强化训练㊁切实掌握这7种常用文体,就可以做到举一反三㊁无所不能㊂其实‘文心雕龙“对此早有论述: 文场笔苑,有术有门㊂务先大体,鉴必穷源㊂乘一总万,举要治繁㊂ [5]只不过刘勰谈论的是一般的文学创作,而章学诚则把这种 鉴必穷源,举要治繁 的思想创造性运用到写作教学,强调学生如能掌握最基本的文体和最常用的方法,就能以少总多㊁以不变应万变,可谓抓住了提高写作训练实效的 牛鼻子 ㊂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文教学就将文体分为记叙㊁说明和议论3大类,认为学生掌握了这3种最常用文体或5种表达方式,自然就会触类旁通地写出其他文体来㊂可以说,这一文体分类训练观的提出,虽说源头在刘勰,但真正将其运用到写作教学的还要首推章学诚㊂注重训练的整体性和渐进性,是章学诚文体写作训练的又一特色㊂自宋代以来,八股文在长期的教学中逐渐形成了分解式程序教学法㊂对此,蔡元培这样描述到: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㊂破题作得及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㊂承题作的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㊂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㊂ [6]但是章学诚并不认同这种分解式的训练方式,他主张学习八股文必须着眼于全篇,不能肢解开来逐段拼凑㊂其‘论课蒙学文法“云: 属句为文,无论文有短长,必成其章,不可支离破碎,如散沙一盘㊂ 由小而大,引短而长,使知语全气足,三五言不为少,而累千百言不为多也㊂ [1]683这里一方面继续阐述了写文章要胸怀整体㊁观照全篇,另一方面也指出写作训练要由易到难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㊂他还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论述写作训练的次序性和渐进性: 夫文之有前后,犹气之有呼吸,啼笑之有收纵,语言之有起乞㊂未闻欲运气者,学呼多年,而后学吸;为啼笑者,学纵久之,而后学收;习言语者,学乞语几时,而后学起语㊂此则理背势逆,不待知者决矣㊂ [1]682意思是文章写作要先后有序,层次清晰,如果 理背势逆 ,写作训练就会陷入无效㊂具体到训练文体,章学诚注意到7种常用文体难易程度并不相同,所以他又给出了一个训练顺序:先学论事再学论人,然后再学辞令㊁叙列㊁考订和叙事[1]683㊂除此之外,章学诚还主张采用多样化的训练方式,以此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内驱动力㊂如他所谓的 体格时变,使之得趣无穷 [1]684,意思是只有不断变换训练方式和内容,才能保持源源不断的写作兴趣㊂应该说,这种注重整体㊁先后有序的训练法以及调动写作兴趣的做法不仅切合学生心理,放在今天看也极具实践价值㊂总体上看,章学诚的写作教育观是建立在其对写作教育传统㊁现实的透彻理解及自身教学实践合理把握上的批判与革新㊂尽管章学诚主要针对的是八股文写作教学,但其写作教育观具有一种开阔的历史视野和自觉的历史理性㊂其贯通文史㊁博综诸学的写作教育主张不仅较好地处理了学问与举业㊁古文与时文㊁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扭转当时的学术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㊂在古代写作教育史上,能够像章学诚这样既能深刻揭示写作教育规律,又对写作教学法提出独到见解,并能形成独树一帜写作教学理论体系的实属罕见㊂ʌ参考文献ɔ[1]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章学诚.文史通义[M].严杰,武秀成,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3]章学诚.文史通义[M].李春伶,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张富林.文备众体:论八股文之 杂 兼伦八股文文体特征[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5]周振甫.文心雕龙注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390.[6]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M]//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612.Z h a n g X u e c h e n g s E s s a y W r i t i n g E d u c a t i o n V i e w p o i n tZ h a n g Z u l i n g1 C u i Z h e n g s h e n g2(1.B a i y i n D i s t r i c t E d u c a t i o n E x a m i n a t i o n I n s t i t u t e,B a i y i n,G a n s u,730900;2.N o r t h w e s t M i n z u U n i v e r s i t y,L a n z h o u,G a n s u,730030)A b s t r a c t:Z h a n g X u e c h e n g h a s a c c u m u l a t e d v a l u a b l e w r i t i n g e d u c a t i o n e x p e r i e n c e i n l o n g-t e r m t e a c h i n g p r a c t i c e.H e p u t f o r w a r d a s e r i e s o f u n i q u e v i e w p o i n t s f r o m h i s t o r i a n s b r o a d p e r s p e c t i v e s,m a i n-l y i n c l u d i n g a t t a c h i n g e q u a l e m p h a s i s o n l i t e r a t u r e a n d h i s t o r y a s w e l l a s g o o d g u i d a n c e f o r b e g i n n e r s;t h e v i e w o f s u b j e c t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o f a d v o c a t i n g t h e v i r t u e o f t r e a t i s e s a n d c u l t i v a t i n g k n o w l e d g e;t h e v i e w o f a r-t i c l e a e s t h e t i c t h a t w o r d s h a v e s u b s t a n c e a n d c o m p l e m e n t t h e w o r l d a n d t h e s t y l i s t i c t r a i n i n g v i e w o f f o c u-s i n g o n t h e w h o l e a n d o r d e r.A l t h o u g h Z h a n g X u e c h e n g i s m a i n l y b a s e d o n t h e t e a c h i n g o f s t e r e o t y p e d w r i t i n g,h i s c l a i m s o f w r i t i n g e d u c a t i o n t h r o u g h l i t e r a t u r e a n d h i s t o r y s t i l l h a v e p r o f o u n d u n i v e r s a l s i g n i f i-c a n c e a n d s t r o n g r e a l i s t i c p e r t i n e n c e a n d g u i d a n c e.K e y w o r d s:Z h a n g X u e c h e n g; w r i t i n g e d u c a t i o n;b e g i n n e r;s u b j e c t c o n s t r u c t i o n;s t y l i s t i c t r a i n i n g。
文言文阅读训练:章学诚《文史通义》(附答案解析与译文)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10-14题。
原道章学诚学于圣人,斯为贤人。
学于贤人,斯为君子。
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非众可学也,求道必於一阴一阳之迹也。
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
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
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
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
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于三时也。
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
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谓天纵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拟议,而为一定之名也,于是援天与神,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
斯其所见,何以异于党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尽。
孔子虽大,不过天地,独不可以一言尽乎?或问何以一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
周公之外,别无所学乎?曰: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
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
“祖述尧、舜”,周公之志也。
“宪章..文、武”,周公之业也。
一则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
再则曰:“甚矣吾衰,不复梦见周公。
”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
”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哀公问政,则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或问“仲尼焉学?”子贡以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
“好古敏求”,周公之遗籍也。
党人生同时而不知,乃谓无所成名,亦非全无所见矣。
后人观载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学,是不如党人所见矣。
而犹嗤党人为不知,奚翅【注】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
章学诚章学诚(1738年-1801年),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方志学家。
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乾隆43年(1778)进士。
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
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
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遍览群籍。
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
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习。
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
晚年目盲,著述不辍身处嘉乾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
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的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
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
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
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
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
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
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
后人辑为《章士遗书刊行》。
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
一生精力都用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
所著《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
曾编纂《史籍考》,拟尽收古今史部书叙目凡例,总目达三百二十五卷,但书未完成,稿亦散失。
所修方志,传世有和州、亳州、永清三志。
曾主修《湖北通志》,现存遗稿数十篇。
哲学上提出“道(理)寓于器(事物)”命题,认为“道”是客观事物之规律,“求道”应根据对事物的实际考察。
所提出“六经皆史”之说,主张治经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将治经引向治史,反映其解脱旧经学传统束缚学术趋向。
论文注重内容,反对拟古和形式主义倾向,批判了当时桐城派的流弊。
其学说至清末始为人重视。
1922年有《章氏遗书》刊行。
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
所著《文史通义》共 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
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
他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
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
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
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
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
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
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
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
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
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
《文史通义》有近人叶长青注本。
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均收入吴兴嘉业堂刊本《章氏遗书》。
文史通义《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
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
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
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
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
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
章氏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
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
"(《志隅·自序》)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
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
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
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又增《补遗》8篇。
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篇。
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
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
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
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
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
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
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
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
"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
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
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
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
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
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
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
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
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通史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
“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
“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
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
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
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
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
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
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
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
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
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
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
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
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