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画的界限——读《拉奥孔》有感
- 格式:docx
- 大小:16.97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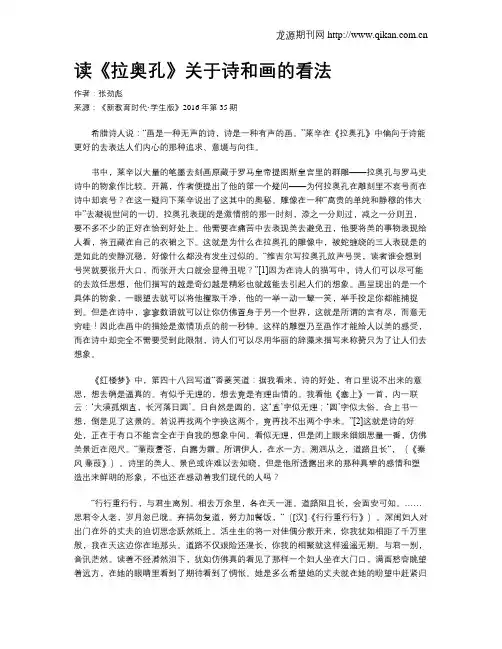
读《拉奥孔》关于诗和画的看法作者:张劲彪来源:《新教育时代·学生版》2016年第35期希腊诗人说:“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诗是一种有声的画。
”莱辛在《拉奥孔》中偏向于诗能更好的去表达人们内心的那种追求、意境与向往。
书中,莱辛以大量的笔墨去刻画原藏于罗马皇帝提图斯皇宫里的群雕——拉奥孔与罗马史诗中的物象作比较。
开篇,作者便提出了他的第一个疑问——为何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中却哀号?在这一疑问下莱辛说出了这其中的奥秘。
雕像在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中”去凝视世间的一切。
拉奥孔表现的是激情前的那一时刻,添之一分则过,减之一分则丑,要不多不少的正好在恰到好处上。
他需要在痛苦中去表现美去避免丑,他要将美的事物表现给人看,将丑藏在自己的衣裙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在拉奥孔的雕像中,被蛇缠绕的三人表现是的是如此的安静沉稳,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维吉尔写拉奥孔放声号哭,读者谁会想到号哭就要张开大口,而张开大口就会显得丑呢?”[1]因为在诗人的描写中,诗人们可以尽可能的去放任思想,他们描写的越是奇幻越是精彩也就越能去引起人们的想象。
画呈现出的是一个具体的物象,一眼望去就可以将他攫取干净,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你都能捕捉到。
但是在诗中,寥寥数语就可以让你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哇!因此在画中的描绘是激情顶点的前一秒钟。
这样的雕塑乃至画作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而在诗中却完全不需要受到此限制,诗人们可以尽用华丽的辞藻来描写来称赞只为了让人们去想象。
《红楼梦》中,第四十八回写道“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确是逼真的。
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由情的。
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
合上书一想,倒是见了这景的。
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
”[2]这就是诗的好处,正在于有口不能言全在于自我的想象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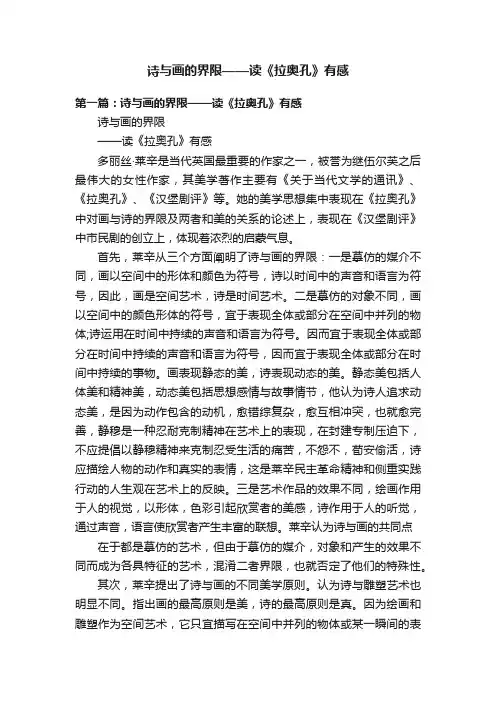
诗与画的界限——读《拉奥孔》有感第一篇:诗与画的界限——读《拉奥孔》有感诗与画的界限——读《拉奥孔》有感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继伍尔芙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其美学著作主要有《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拉奥孔》、《汉堡剧评》等。
她的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拉奥孔》中对画与诗的界限及两者和美的关系的论述上,表现在《汉堡剧评》中市民剧的创立上,体现着浓烈的启蒙气息。
首先,莱辛从三个方面阐明了诗与画的界限:一是摹仿的媒介不同,画以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为符号,诗以时间中的声音和语言为符号,因此,画是空间艺术,诗是时间艺术。
二是摹仿的对象不同,画以空间中的颜色形体的符号,宜于表现全体或部分在空间中并列的物体;诗运用在时间中持续的声音和语言为符号。
因而宜于表现全体或部分在时间中持续的声音和语言为符号,因而宜于表现全体或部分在时间中持续的事物。
画表现静态的美,诗表现动态的美。
静态美包括人体美和精神美,动态美包括思想感情与故事情节,他认为诗人追求动态美,是因为动作包含的动机,愈错综复杂,愈互相冲突,也就愈完善,静穆是一种忍耐克制精神在艺术上的表现,在封建专制压迫下,不应提倡以静穆精神来克制忍受生活的痛苦,不怨不,荀安偷活,诗应描绘人物的动作和真实的表情,这是莱辛民主革命精神和侧重实践行动的人生观在艺术上的反映。
三是艺术作品的效果不同,绘画作用于人的视觉,以形体,色彩引起欣赏者的美感,诗作用于人的听觉,通过声音,语言使欣赏者产生丰富的联想。
莱辛认为诗与画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摹仿的艺术,但由于摹仿的媒介,对象和产生的效果不同而成为各具特征的艺术,混淆二者界限,也就否定了他们的特殊性。
其次,莱辛提出了诗与画的不同美学原则。
认为诗与雕塑艺术也明显不同。
指出画的最高原则是美,诗的最高原则是真。
因为绘画和雕塑作为空间艺术,它只宜描写在空间中并列的物体或某一瞬间的表情,擅长表现静态事物,这就决定了它应着力描写的是事物的形态美或美的表情,因此美便成了绘画,雕塑创作的最高美学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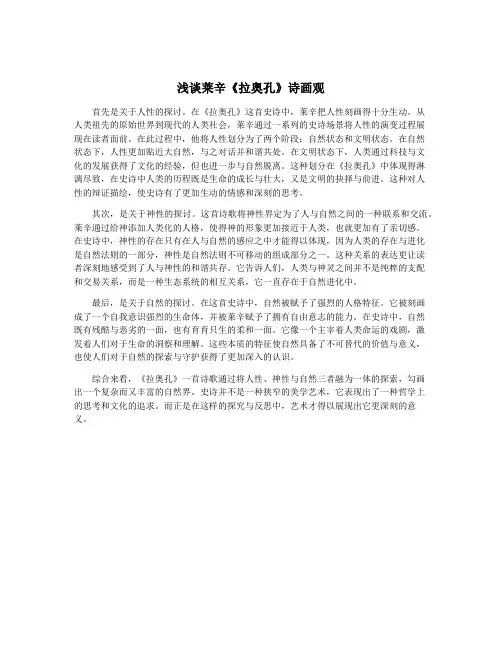
浅谈莱辛《拉奥孔》诗画观首先是关于人性的探讨。
在《拉奥孔》这首史诗中,莱辛把人性刻画得十分生动。
从人类祖先的原始世界到现代的人类社会,莱辛通过一系列的史诗场景将人性的演变过程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此过程中,他将人性划分为了两个阶段: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
在自然状态下,人性更加贴近大自然,与之对话并和谐共处。
在文明状态下,人类通过科技与文化的发展获得了文化的经验,但也进一步与自然脱离。
这种划分在《拉奥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史诗中人类的历程既是生命的成长与壮大,又是文明的抉择与前进。
这种对人性的辩证描绘,使史诗有了更加生动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
其次,是关于神性的探讨。
这首诗歌将神性界定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联系和交流。
莱辛通过给神添加人类化的人格,使得神的形象更加接近于人类,也就更加有了亲切感。
在史诗中,神性的存在只有在人与自然的感应之中才能得以体现,因为人类的存在与进化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神性是自然法则不可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这种关系的表达更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了人与神性的和谐共存。
它告诉人们,人类与神灵之间并不是纯粹的支配和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它一直存在于自然进化中。
最后,是关于自然的探讨。
在这首史诗中,自然被赋予了强烈的人格特征。
它被刻画成了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生命体,并被莱辛赋予了拥有自由意志的能力。
在史诗中,自然既有残酷与恶劣的一面,也有育育只生的柔和一面。
它像一个主宰着人类命运的戏剧,激发着人们对于生命的洞察和理解。
这些本质的特征使自然具备了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也使人们对于自然的探索与守护获得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综合来看,《拉奥孔》一首诗歌通过将人性、神性与自然三者融为一体的探索,勾画出一个复杂而又丰富的自然界。
史诗并不是一种狭窄的美学艺术,它表现出了一种哲学上的思考和文化的追求。
而正是在这样的探究与反思中,艺术才得以展现出它更深刻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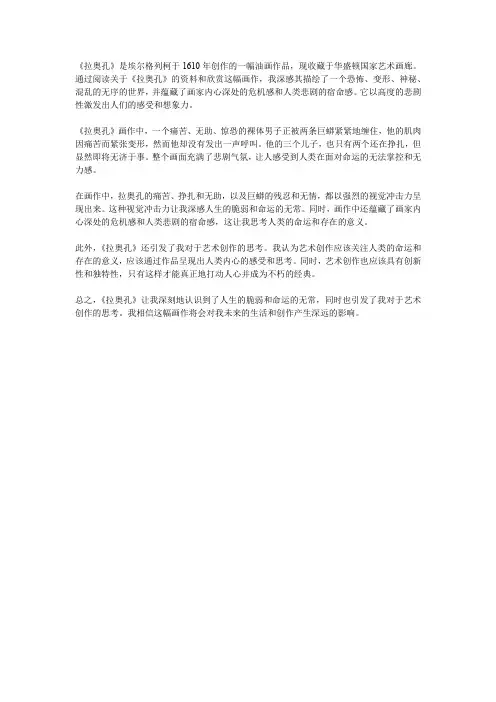
《拉奥孔》是埃尔格列柯于1610年创作的一幅油画作品,现收藏于华盛顿国家艺术画廊。
通过阅读关于《拉奥孔》的资料和欣赏这幅画作,我深感其描绘了一个恐怖、变形、神秘、混乱的无序的世界,并蕴藏了画家内心深处的危机感和人类悲剧的宿命感。
它以高度的悲剧性激发出人们的感受和想象力。
《拉奥孔》画作中,一个痛苦、无助、惊恐的裸体男子正被两条巨蟒紧紧地缠住,他的肌肉因痛苦而紧张变形,然而他却没有发出一声呼叫。
他的三个儿子,也只有两个还在挣扎,但显然即将无济于事。
整个画面充满了悲剧气氛,让人感受到人类在面对命运的无法掌控和无力感。
在画作中,拉奥孔的痛苦、挣扎和无助,以及巨蟒的残忍和无情,都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呈现出来。
这种视觉冲击力让我深感人生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
同时,画作中还蕴藏了画家内心深处的危机感和人类悲剧的宿命感,这让我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存在的意义。
此外,《拉奥孔》还引发了我对于艺术创作的思考。
我认为艺术创作应该关注人类的命运和存在的意义,应该通过作品呈现出人类内心的感受和思考。
同时,艺术创作也应该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打动人心并成为不朽的经典。
总之,《拉奥孔》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生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同时也引发了我对于艺术创作的思考。
我相信这幅画作将会对我未来的生活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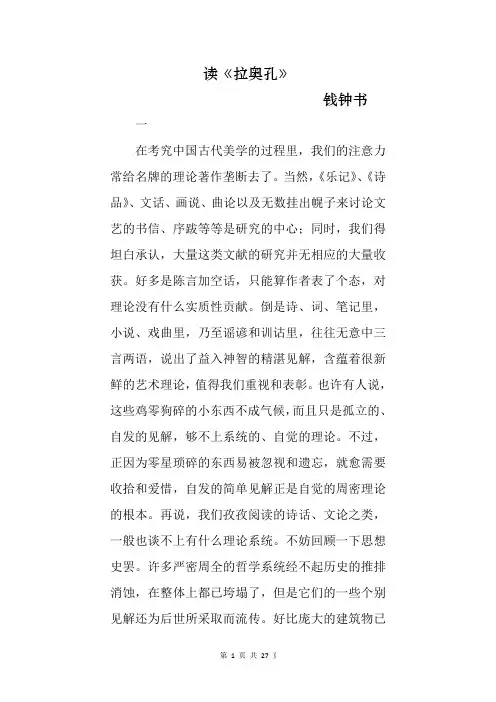
读《拉奥孔》钱钟书一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
当然,《乐记》、《诗品》、文话、画说、曲论以及无数挂出幌子来讨论文艺的书信、序跋等等是研究的中心;同时,我们得坦白承认,大量这类文献的研究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
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表了个态,对理论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
倒是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入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
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而且只是孤立的、自发的见解,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
不过,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
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一般也谈不上有什么理论系统。
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
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
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利用的材料。
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
脱离了系统的片段思想和未及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彼此同样是零碎的。
所以,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那是一种粗浅甚至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疏忽的借口。
试举一例。
前些时[1],我们的文艺理论家对狄德罗的《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发生兴趣,写文章讨论。
这个“诡论”的要旨是:演员必须自己内心冷静,才能维妙维肖地体现所扮角色的热烈情感,他先得学会不“动于中”,才能把角色的喜怒哀乐生动地“形于外”(c’est le manque absolu de sensibilite qui prepare les acteurs sublimes);譬如逼真表演剧中人的狂怒时(jouer bien la fureur),演员自己绝不认真冒火发疯(etre furieux)[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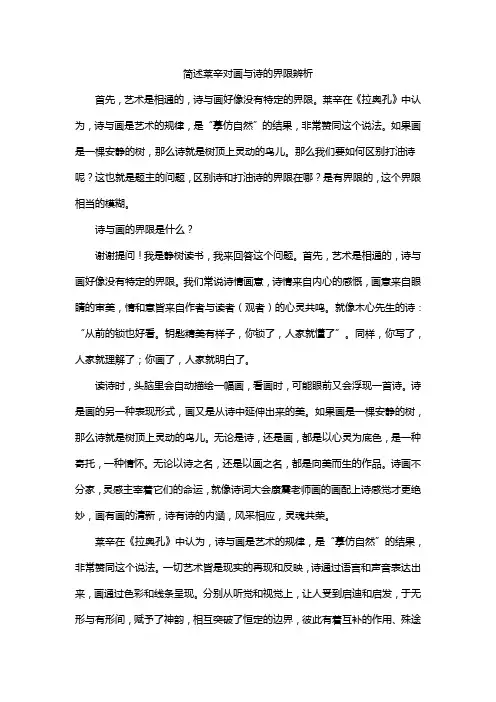
简述莱辛对画与诗的界限辨析首先,艺术是相通的,诗与画好像没有特定的界限。
莱辛在《拉奥孔》中认为,诗与画是艺术的规律,是“摹仿自然”的结果,非常赞同这个说法。
如果画是一棵安静的树,那么诗就是树顶上灵动的鸟儿。
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别打油诗呢?这也就是题主的问题,区别诗和打油诗的界限在哪?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相当的模糊。
诗与画的界限是什么?谢谢提问!我是静树读书,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艺术是相通的,诗与画好像没有特定的界限。
我们常说诗情画意,诗情来自内心的感慨,画意来自眼睛的审美,情和意皆来自作者与读者(观者)的心灵共鸣。
就像木心先生的诗:“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同样,你写了,人家就理解了;你画了,人家就明白了。
读诗时,头脑里会自动描绘一幅画,看画时,可能眼前又会浮现一首诗。
诗是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画又是从诗中延伸出来的美。
如果画是一棵安静的树,那么诗就是树顶上灵动的鸟儿。
无论是诗,还是画,都是以心灵为底色,是一种寄托,一种情怀。
无论以诗之名,还是以画之名,都是向美而生的作品。
诗画不分家,灵感主宰着它们的命运,就像诗词大会康震老师画的画配上诗感觉才更绝妙,画有画的清新,诗有诗的内涵,风采相应,灵魂共荣。
莱辛在《拉奥孔》中认为,诗与画是艺术的规律,是“摹仿自然”的结果,非常赞同这个说法。
一切艺术皆是现实的再现和反映,诗通过语言和声音表达出来,画通过色彩和线条呈现。
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上,让人受到启迪和启发,于无形与有形间,赋予了神韵,相互突破了恒定的边界,彼此有着互补的作用、殊途同归的效果。
诗书画,意境相融相通,各有其美。
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在哪里?谢邀。
打油诗和诗的界限在哪里?比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他就是诗,可是你如果改成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婆娘。
它就成了打油诗。
那么诗和打油诗的界限在哪里?首先我们确定一点,打油诗也是诗。
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别打油诗呢?这也就是题主的问题,区别诗和打油诗的界限在哪?是有界限的,但是这个界限相当的模糊。

浅谈莱辛《拉奥孔》诗画观
莱辛是17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和画家,他的诗和画作具有相互照应、互为补充的特点,而他的诗画观则是由他的生命境遇、审美经验、艺术理念等多方面因素共
同塑造而成的。
《拉奥孔》是莱辛的一部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农民瑞斯特朗的故事。
这个故事中
展现了生命的苦难、人类的平等和宇宙的神秘,同时诗中也闪现出了莱辛的某些审美情趣
和表现手法。
通过对《拉奥孔》的诗画观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莱辛的文艺创作思路和风
格特点。
首先,莱辛在《拉奥孔》中强调了艺术与现实的联系。
他通过对瑞斯特朗的描写,反
映出贫苦农民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从而更加生动地展现出人性的善良、坚强和爱,这
些都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反映,同时也凸显了艺术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其次,莱辛的诗画观中还强调了情感与形式的统一。
他追求温婉、柔和、清新的情感
表达方式,自然而不做作,使读者产生亲近感和安心感,这种情感表达与他诗画创作中清
新明亮的风格一致,体现了他追求形式和内容的平衡与统一。
最后,莱辛的诗画观还体现出他对自然的赞美与抒发。
他通过对自然界的描绘和赞美,表达了对宇宙的敬畏和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同时也通过对自然的感悟和领悟,展现了自然
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这种对自然的深刻感受和抒发,可以在莱辛的创作中得到体现,
让人产生共鸣和思考。
总的来说,莱辛的诗画观是一种将艺术与现实、情感与形式、自然与人文联系起来的
审美视角,体现了诗人与画家对生命、自然和人类的理解与感悟。
这种独特的诗画观使得
他的作品具有自己的风格和价值,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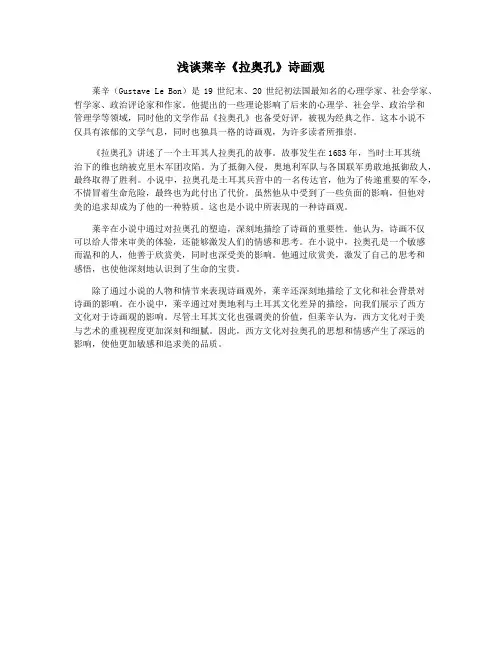
浅谈莱辛《拉奥孔》诗画观莱辛(Gustave Le Bon)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最知名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评论家和作家。
他提出的一些理论影响了后来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同时他的文学作品《拉奥孔》也备受好评,被视为经典之作。
这本小说不仅具有浓郁的文学气息,同时也独具一格的诗画观,为许多读者所推崇。
《拉奥孔》讲述了一个土耳其人拉奥孔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683年,当时土耳其统治下的维也纳被克里木军团攻陷。
为了抵御入侵,奥地利军队与各国联军勇敢地抵御敌人,最终取得了胜利。
小说中,拉奥孔是土耳其兵营中的一名传达官,他为了传递重要的军令,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最终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虽然他从中受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他对美的追求却成为了他的一种特质。
这也是小说中所表现的一种诗画观。
莱辛在小说中通过对拉奥孔的塑造,深刻地描绘了诗画的重要性。
他认为,诗画不仅可以给人带来审美的体验,还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和思考。
在小说中,拉奥孔是一个敏感而温和的人,他善于欣赏美,同时也深受美的影响。
他通过欣赏美,激发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生命的宝贵。
除了通过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来表现诗画观外,莱辛还深刻地描绘了文化和社会背景对诗画的影响。
在小说中,莱辛通过对奥地利与土耳其文化差异的描绘,向我们展示了西方文化对于诗画观的影响。
尽管土耳其文化也强调美的价值,但莱辛认为,西方文化对于美与艺术的重视程度更加深刻和细腻。
因此,西方文化对拉奥孔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更加敏感和追求美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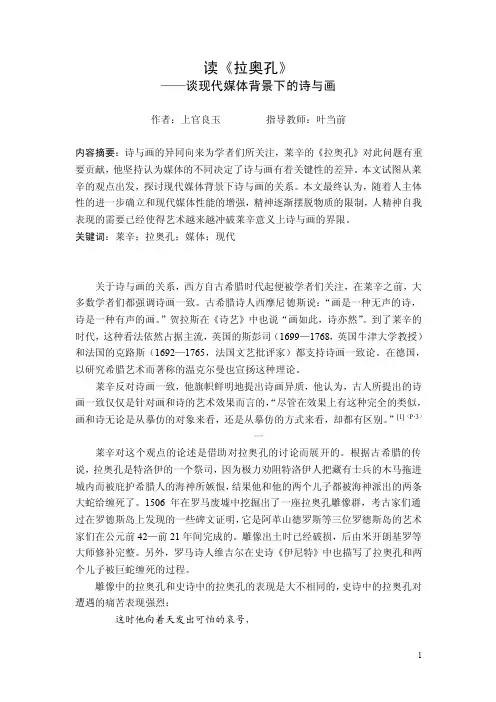
读《拉奥孔》——谈现代媒体背景下的诗与画作者:上官良玉指导教师:叶当前内容摘要:诗与画的异同向来为学者们所关注,莱辛的《拉奥孔》对此问题有重要贡献,他坚持认为媒体的不同决定了诗与画有着关键性的差异。
本文试图从莱辛的观点出发,探讨现代媒体背景下诗与画的关系。
本文最终认为,随着人主体性的进一步确立和现代媒体性能的增强,精神逐渐摆脱物质的限制,人精神自我表现的需要已经使得艺术越来越冲破莱辛意义上诗与画的界限。
关键词:莱辛;拉奥孔;媒体;现代关于诗与画的关系,西方自古希腊时代起便被学者们关注,在莱辛之前,大多数学者们都强调诗画一致。
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说:“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诗是一种有声的画。
”贺拉斯在《诗艺》中也说“画如此,诗亦然”。
到了莱辛的时代,这种看法依然占据主流,英国的斯彭司(1699—1768,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和法国的克路斯(1692—1765,法国文艺批评家)都支持诗画一致论。
在德国,以研究希腊艺术而著称的温克尔曼也宣扬这种理论。
莱辛反对诗画一致,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诗画异质,他认为,古人所提出的诗画一致仅仅是针对画和诗的艺术效果而言的,“尽管在效果上有这种完全的类似,画和诗无论是从摹仿的对象来看,还是从摹仿的方式来看,却都有区别。
”[1](P.3)一莱辛对这个观点的论述是借助对拉奥孔的讨论而展开的。
根据古希腊的传说,拉奥孔是特洛伊的一个祭司,因为极力劝阻特洛伊人把藏有士兵的木马拖进城内而被庇护希腊人的海神所嫉恨,结果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都被海神派出的两条大蛇给缠死了。
1506年在罗马废墟中挖掘出了一座拉奥孔雕像群,考古家们通过在罗德斯岛上发现的一些碑文证明,它是阿革山德罗斯等三位罗德斯岛的艺术家们在公元前42—前21年间完成的。
雕像出土时已经破损,后由米开朗基罗等大师修补完整。
另外,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史诗《伊尼特》中也描写了拉奥孔和两个儿子被巨蛇缠死的过程。
雕像中的拉奥孔和史诗中的拉奥孔的表现是大不相同的,史诗中的拉奥孔对遭遇的痛苦表现强烈:这时他向着天发出可怕的哀号,正像一头公牛受了伤,要逃开祭坛,挣脱颈上的利斧,放声狂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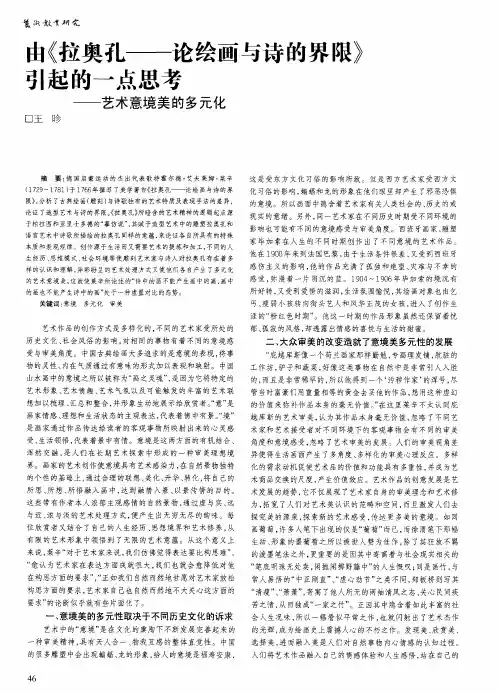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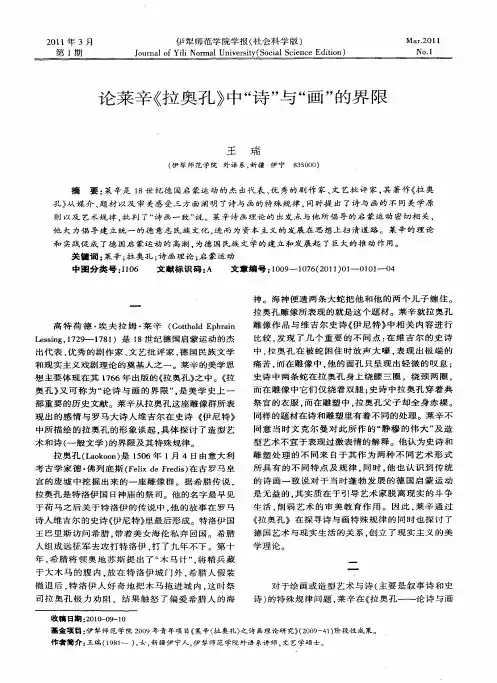
浅谈莱辛《拉奥孔》诗画观《拉奥孔》是法国诗人莱辛的一首长诗,以描绘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拉奥孔的故事为主线,同时融入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思考。
这首诗以其独特的诗画观呈现了莱辛的艺术风格和思想主张。
莱辛在《拉奥孔》中运用了丰富的描写手法,用色彩鲜明的词句描述了诗中的场景和人物形象。
他以诗画结合的方式,通过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于艺术的思考和追求。
他的描写不仅仅是静态的画面,更是通过文字的运用,将画面呈现给读者,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能够看到画面中的动态。
莱辛对于画面的描写非常细腻和生动,他运用了形象化和夸张的手法,使得画面更加鲜活。
在描写拉奥孔一战赢得凯旋的场景时,他用词生动地描绘了冒烟的战场,奋力杀敌的英勇士兵,以及欢呼的人群。
通过这种方式,莱辛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英雄的威猛和壮丽的景象。
莱辛还通过对画面中细节的描写,塑造了各个人物形象的个性和特点。
在描写拉奥孔的妻子伊菲洛剃去自己的头发以换取丈夫的胜利时,他描述了她的委婉和无私,以及她眼中的坚定和忧愁。
这种描写使得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伊菲洛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除了对画面的描写,莱辛还通过对色彩的运用来表达诗中的情感和思想。
在描写洛利库斯的延寿船上,他描绘了海水的颜色和阳光的光芒,使得读者能够感受到宁静和温暖的氛围。
而在描写战争和杀戮的场景时,他使用了黑暗和血红色来表现出战争的残酷和悲剧。
这种运用色彩的手法使得诗中的画面更加丰富和层次感更强。
莱辛的《拉奥孔》以其独特的诗画观表达了他对于艺术的追求和对于现实的思考。
他通过对画面的描写和色彩的运用,使诗中的场景和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和鲜活,同时抒发了他对于战争和人性的思考和担忧。
这首诗既是一幅艺术的画卷,又是对现实的审视和思考,展现了莱辛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心灵的深度。
诗画之辨—莱辛《拉奥孔》诗画观研究一、本文概述《诗画之辨—莱辛《拉奥孔》诗画观研究》一文,旨在深入剖析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在其名著《拉奥孔》中提出的诗画观,探讨其对于诗歌与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的独特理解和区分。
莱辛的这部作品在文艺理论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我们理解诗歌与绘画的本质和特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为后世的文艺创作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本文首先将对莱辛的生平及其文艺理论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接着,文章将重点解读《拉奥孔》中莱辛关于诗画关系的论述,包括他对诗歌和绘画各自特性的分析,以及两者在表现同一主题时的不同手法和效果。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莱辛诗画观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意义,分析其对后世文艺理论及创作实践的影响。
通过对莱辛《拉奥孔》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诗歌与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在表现力和审美体验上的独特魅力,以及它们在人类文化和艺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也希望通过对莱辛诗画观的解读,为当代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提供新的启示和思考。
二、莱辛的诗画观概述莱辛,作为18世纪德国的重要文艺理论家,他的《拉奥孔》一书在文艺理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这部著作中,莱辛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诗与画两种艺术形式的独特见解,尤其是他对于诗画界限的划分以及对两者各自特性的强调,成为了后世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莱辛认为,诗与画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其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他指出,诗歌是一种时间艺术,通过语言的流动和节奏的变换,在读者的想象中构建出丰富的画面和情节。
而绘画则是一种空间艺术,通过色彩、线条和构图等视觉元素,在平面上呈现出静态的、凝固的美。
这种差异决定了诗与画在表现同一主题时,必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效果。
莱辛进一步指出,诗歌在表现情感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认为,诗歌可以通过语言的韵律和节奏,以及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直接触动读者的情感,引发强烈的共鸣。
浅谈莱辛《拉奥孔》诗画观作为17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约翰·克里斯托夫·莱辛(Johann Christoph Leibniz)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塑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形象。
他的《拉奥孔》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被誉为他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一部作品。
这部诗歌作品以其富有想象力和独特的意象使人耳目一新。
在这篇文章中,将浅谈莱辛《拉奥孔》的诗画观,探索其作品中所展现的艺术魅力和意蕴。
《拉奥孔》以宏大的叙事气魄和精湛的诗学技巧刻画了一个独特的幻想世界。
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和对情感的深刻描绘,莱辛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梦幻和奇幻的雅典古国。
在这个幻想世界里,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情感更加丰富,同时也更加超凡脱俗。
莱辛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和对情感的表达,将其作品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使读者能够在其中体味到诗歌的美感和情感的力量。
在这个幻想世界里,莱辛将情感和想象力融为一体,展现了诗歌的独特魅力和艺术的无穷魅力。
在《拉奥孔》中,莱辛运用了丰富多彩的诗歌语言和独特的意象,展现了他对诗画的深刻理解和敏锐观察。
他通过对细节的精湛描绘和对意象的巧妙运用,使得他的诗歌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和美感。
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山川的雄浑,河流的奔腾,星空的璀璨,仿佛一幅幅华丽的画面在我们眼前展开。
他将诗歌比作一幅画,将自己比作一位画家,通过对诗歌语言和意象的运用,展现了诗歌的绚丽和艺术的魅力。
在他的诗歌中,诗与画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使得他的作品更加有深度和内涵。
莱辛在《拉奥孔》中运用了丰富的宇宙观念和丰富的哲学思想,展现了他对诗歌和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感悟。
他通过对宇宙和自然的描绘,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展现了诗歌的广阔和意蕴。
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宇宙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和感悟。
他将诗歌比作一种超越时空的意象,将自己比作一位超然的哲人,在诗歌中探寻人生的真谛和宇宙的奥秘。
浅谈莱辛《拉奥孔》诗画观莱辛(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是18世纪德国文学史上备受尊敬的作家之一,他的著作《拉奥孔》(Anmerkungen übers Theater)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
这部作品不仅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拉奥孔》以其独特的诗画观念成为文学史上的亮点,对于探讨艺术和文学的关系、诗歌与绘画的互动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了诗画的互动关系。
在这部作品中,莱辛不仅探讨了诗歌和绘画的相互关系,还探讨了诗歌和音乐、诗歌和戏剧等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
他通过分析诗歌和绘画在描绘对象、表现手法、审美功能等方面的共通之处,指出两者在表现形式和审美价值上存在的相似性,以及它们在艺术发展中互相促进、互相借鉴的关系。
莱辛认为诗歌和绘画都是艺术创作的形式,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魅力,但在表现世界、抒发情感和传达思想等方面又有着共通的艺术追求。
这种互动关系不仅在《拉奥孔》中得到了深刻的阐述,同时也对于后世对于诗歌和绘画的审美观念和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了诗画的发展趋势。
在这部作品中,莱辛不仅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诗画的发展脉络,还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诗画的未来发展趋势。
他认为,诗画作为艺术形式在不断的发展中必将呈现出新的面貌,其表现形式、审美功能和社会价值将获得深刻的提升。
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的诗画的发展趋势,并不仅仅是对于当时艺术形式的一种预测和展望,更是为后世有关诗画创作和审美实践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为促进诗画的创新和发展指明了重要的方向。
在《拉奥孔》中,莱辛以其独特的诗画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思维和艺术理解的范式。
他通过对于诗画的互动关系、审美功能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探讨,开辟了诗画研究的新领域,为后世对于诗画的创作和鉴赏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拉奥孔》的诗画观念不仅对于德国文学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于世界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精神和审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诗与画的异同——《拉奥孔》评析作者:朱颖怡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7年第02期摘要:本文总结并分析莱辛在《拉奥孔》一书中的观点,如诗与画的界限,艺术家选取的情节性安排以及艺术的规律总结等。
关键词:莱辛;拉奥孔;诗画界限;顷刻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05-0177-01莱辛在温克尔曼的影响下写成的《拉奥孔》,主旨是为了反对把温克尔曼的艺术理想应用到诗或文学的领域。
他从前言开始提出诗(文学)和艺术(造型艺术与绘画)都能令人产生一种快感。
两种艺术都可以把不在目前出现的表现为就像在目前的,把外形表现为显示;他们都产生逼真的幻觉。
诗与画无论是从摹仿的对象来着,还是从摹仿的方式来说,却都有区别。
在此莱辛从拉奥孔雕像群出发,提出了诗与画在美的规律,诗画的界限,是诗摹仿画,还是画摹仿诗的问题。
莱辛从拉奥孔雕像群的表情入手,提出了处理哀号表情的手法应用在诗与画里面的分别,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在古希腊人看来,美是造形艺术的最高法律,凡是为造形艺术所追求的其他东西,如果和美不相容,就必须让路给美;如果和美相容,也至少须服从美。
莱辛提出了绘画当中应选取具有运动情节的顷刻,来表现绘画中的瞬间;他把这种瞬间表达为“最富孕育性的顷刻”,指画家描写动作时应选用的发展顶点前的一顷刻,这一顷刻包含过去,也暗示未来,所以让想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莱辛根据“最富孕育性的顷刻”进一步说明诗与画的界限:诗人运用观念性,意象可以最大量地想象,并且是诗具有时间的承续性;而绘画的意象是直接代表具体的实物,在时间的承续性上,绘画只能截取其中一点“最富孕育性的顷刻”,而不能像诗那样表达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承续性。
通过莱辛对诗画界限之间的分析,说明了诗是时间艺术,而画是属于空间艺术。
这些论据包括了在选材,艺术语言,表达方式以及想象方面的差异去表达。
绘画处于空间艺术表达的范畴,也表达了具体事物的直观反映,采取描绘美的事物的特征。
《拉奥孔》读后感_拉奥孔《拉奥孔》里有什么《拉奥孔》是几年前买的一本书了,依稀记得当时在参加本科自学考试,选修过一门关于美学的课程。
对于美学很不懂,又很好奇,挨着考试的东风看见了朱光潜翻译的美学著作《拉奥孔》,于是德国的莱辛便来到了书架。
这上架了的书一呆便是几年光阴,直到孙绍振教授在《月迷津渡》的引用文献里提到诗画关系里用到了《拉奥孔》,这才下决心把尘封已久的莱辛请出来听他都说些什么。
不好意思啦,莱辛!拉奥孔是什么,是一座著名的雕像群,原藏在罗马皇帝提图斯的皇宫里,这座雕像群长久埋没在罗马废墟里,一直到1506年才由一位意大利人佛列底斯在挖葡萄园时把它发掘出来,献给教皇朱理乌斯二世,现在藏在梵蒂冈宫。
这就是那著名的雕像:罗马宫廷诗人维吉尔在史诗《伊尼特》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任海神司祭的拉奥孔正在宰杀公牛的时候,两条蟒蛇从海上而来,先一条一个缠住他的儿子撕咬,拉奥孔赶来搭救时再气势汹汹地缠住他撕咬。
雕像群把蟒蛇撕咬儿子们先发生的顷刻和拉奥孔搭救被缠后发生的顷刻合二为一。
由这个著名的雕像群出发,莱辛展开了他的美学理念大阐发。
《拉奥孔》不同于一般的美学著作,没有一般德国美学著作在概念里兜圈子的习气,它是一个就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范例。
他的主题是划定诗和画的界限,找出一切艺术的共同规律以及各门艺术的特殊规律。
依他看,诗和画主要有这些差异:第一,题材来说,描绘在空间并列的物体,诗则叙述在时间上先后承续的动作。
画的题材只局限于可以眼见的事物,诗没有这种局限,诗的范围更广泛。
画只宜美的事物,诗则可以写丑,写喜剧性的,写悲剧性的,可嫌厌的和崇高的事物。
画只适宜表现没有个性的抽象的一般性的典型,诗才能做到典型和个性结合。
第二,媒介来说,画用颜色线条之类的自然符号,诗用语言的人为符号。
第三,就接受艺术的感官和心理功能来说,画所写的物体是通过视觉来接受的,物体是平铺并列的,一眼能看出整体,借用想象少。
诗语言叙述动作情节,主要诉诸听觉。
诗与画的界限
——读《拉奥孔》有感多丽丝·莱辛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继伍尔芙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其美学著作主要有《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拉奥孔》、《汉堡剧评》等。
她的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拉奥孔》中对画与诗的界限及两者和美的关系的论述上,表现在《汉堡剧评》中市民剧的创立上,体现着浓烈的启蒙气息。
首先,莱辛从三个方面阐明了诗与画的界限:一是摹仿的媒介不同,画以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为符号,诗以时间中的声音和语言为符号,因此,画是空间艺术,诗是时间艺术。
二是摹仿的对象不同,画以空间中的颜色形体的符号,宜于表现全体或部分在空间中并列的物体;诗运用在时间中持续的声音和语言为符号。
因而宜于表现全体或部分在时间中持续的声音和语言为符号,因而宜于表现全体或部分在时间中持续的事物。
画表现静态的美,诗表现动态的美。
静态美包括人体美和精神美,动态美包括思想感情与故事情节,他认为诗人追求动态美,是因为动作包含的动机,愈错综复杂,愈互相冲突,也就愈完善,静穆是一种忍耐克制精神在艺术上的表现,在封建专制压迫下,不应提倡以静穆精神来克制忍受生活的痛苦,不怨不,荀安偷活,诗应描绘人物的动作和真实的表情,这是莱辛民主革命精神和侧重实践行动的人生观在艺术上的反映。
三是艺术作品的效果不同,绘画作用于人的视觉,以形体,色彩引起欣赏者的美感,诗作用于人的听觉,通过声音,语言使欣赏者产生丰富的联想。
莱辛认为诗与画的共同点
在于都是摹仿的艺术,但由于摹仿的媒介,对象和产生的效果不同而成为各具特征的艺术,混淆二者界限,也就否定了他们的特殊性。
其次,莱辛提出了诗与画的不同美学原则。
认为诗与雕塑艺术也明显不同。
指出画的最高原则是美,诗的最高原则是真。
因为绘画和雕塑作为空间艺术,它只宜描写在空间中并列的物体或某一瞬间的表情,擅长表现静态事物,这就决定了它应着力描写的是事物的形态美或美的表情,因此美便成了绘画,雕塑创作的最高美学原则。
而诗作为时间艺术,运用的是语言符号,所以在直接描写事物的形态美方面不如绘画,雕塑,但它却有比造型艺术更自由的空间,它善于描写动态的事物,描写事物运动发展过程,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人类心灵世界,所以诗的目的在于真实地描写自然和社会现实,所以真实是诗创作的最高美学原则。
莱辛运用“美”和“真”原则对雕像拉奥孔与诗拉奥孔的差异作了分析比较和解释:“雕刻家要在既定的身体苦痛的情况之下表现出最高度的美。
身体苦痛的情况下的激烈的形体扭曲和最高度的美是不相容的。
所以他不得不把身体苦痛冲淡,把哀号化为轻微的叹息。
这并非因为哀号就显出心灵不高贵,而是因为哀号会使面孔扭曲,令人恶心。
”而诗要真实表现痛苦,所以尽情地真实地描写拉奥孔被蛇绞住时的哀号,以突出内心的苦痛。
同样的道理,维吉尔的诗描写拉奥孔被蛇缠腰三道,绕颈两道,而雕像只表现蛇缠住腿部;维吉尔诗中的拉奥孔穿的是祭司的衣帽,而雕像中的人物均是裸体。
这些解释是符合情理的。
再次,莱辛提出了艺术的时空辩证观。
并运用于艺术创作,提出了关于选取“包孕性顷刻”的规律:“绘画在它的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使得前之后之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解。
同理,诗在它的持续性的摹仿里,也要运用能够引起该物体的最生动的感性形象的那个属性。
艺术家选择的这一顷刻最富于包孕性,最发人深思和想象。
就拿《拉奥孔》这篇文章来说吧,它通过分析古典雕刻与诗歌的表现手法的差异,论证造型艺术与诗的界限,即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界限,得出画更适合于表现美的结论。
从莱辛的《拉奥孔》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与画的界限其实就是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的界限。
其中,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为了遵循这一原则,可以牺牲艺术的真实;而诗人有时却可以运用形体的丑,从而体现诗歌的真。
莱辛在《拉奥孔》中关于诗与画的交互影响中认为,那段用效果的手法反映海伦之美的诗歌,如果搬上画布,就会失去效果了,因为,那些元老的表情无宜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而让人无法透过他们的表情去感受到海伦的美。
其实,这种看法,在钱钟书看来,也是类似的。
他说,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无宜将梅的影和香很生动地描绘出来了,但是,如果把这种感觉搬上画面时,就会觉得失去了诗中的味道了。
那么诗与画的界线该如何认定呢?我认为,诗中有画,而不全是画;画中有诗,而不全是诗。
诗画各有表现的可能性范围。
中国古
代抒情诗里有不少是纯粹的写景,描绘一个客观境界,不写出主体的行动,甚至于不直接说出主观的情感,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无我之境”,但却充满了诗的气氛和情调。
而诗里所咏的光的先后活跃,不能在画面上同时表现出来,画家只能捉住意义最丰满的一刹那,暗示那活动的前因后果,在画面的空间里引进时间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