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的心性论阐释
- 格式:pdf
- 大小:496.93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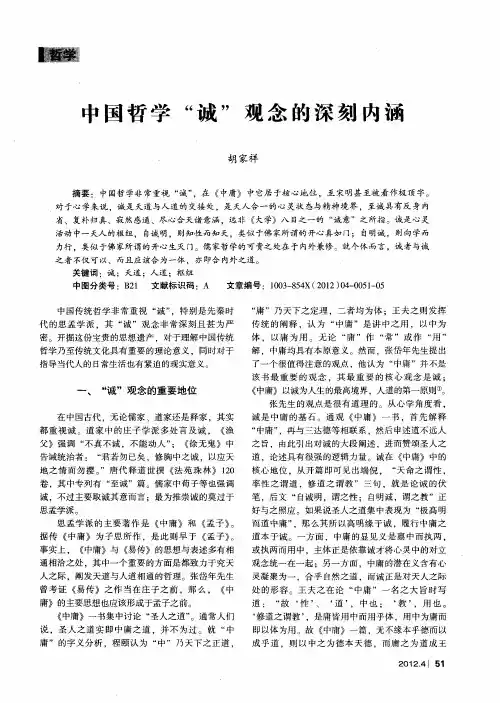

宋初儒学“心性论”转向的一个重要环节——论智圆、晁迥《中庸》新释的意义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关键在于民族哲学精神的重建。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重建中华民族哲学精神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传统文化在汲取世界优秀文化基础上的再生性创新”。
宋学诞生于外来宗教——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儒学论争的时代,是儒学通过汲取佛教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发生变革、实现“再生性创新”的产物。
正所谓“寻水者必穷其源,则水之所自来者无遁隐”,对宋学起源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与理解宋学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从而为当前民族哲学精神的重建提供一定的思路与方法。
但当前学界对宋学起源问题的认知尚有“未发之覆”,具体表现在片面地强调儒家在促进宋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而有意地忽视了佛教一方。
本文拟通过对智圆、晁迥《中庸》新释成果的考察,说明两人在推动宋学“心性论”系统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期能对目前学界关于宋学起源问题的研究作以补充。
一、智圆、晁迥的思想与宋学的关系毫无疑问,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便陷入了如何处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困境,中国传统哲学也由此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
这一发展概况亦构成19世纪中叶以来学界研究中国文化之视域:研究者一方面要对中国文化传统何去何从这一时代问题作出回应,另一方面也要对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传统文化精神作以归纳总结。
值此时代环境下,陈寅恪率先提出“中国文化之重建与更新,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并认为宋学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和文化复兴的基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
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
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继承陈氏衣钵的钱穆也十分推崇宋学,他说:“以中国史比之西洋史,唐末五代,俨如罗马帝国之崩溃,而自宋以下,学术重兴,文化再起,迄于今千年以来,中国之为中国,依然如故,时惟宋儒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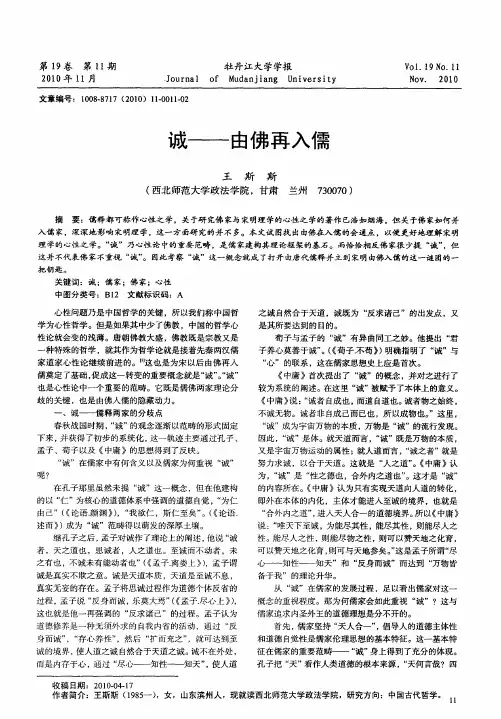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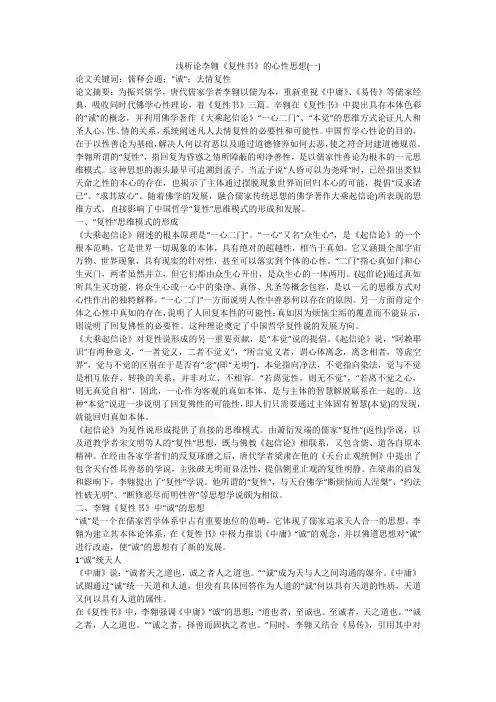
浅析论李翱《复性书》的心性思想(一)论文关键词:儒释会通;“诚”;去情复性论文摘要:为振兴儒学,唐代儒家学者李翱以儒为本,重新重视《中庸》、《易传》等儒家经典,吸收同时代佛学心性理论,着《复性书》三篇。
辛翱在《复性书》中提出具有本体色彩的“诚”的概念,并利用佛学著作《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本觉”的思维方式论证凡人和圣人心、性、情的关系,系统阐述凡人去情复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国哲学心性论的目的,在于以性善论为基础,解决人何以有恶以及通过道德修养如何去恶,使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
李翱所谓的“复性”,指回复为昏惑之情所障蔽的明净善性,是以儒家性善论为根本的一元思维模式。
这种思想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孟子。
当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时,已经指出类似天命之性的本心的存在,也揭示了主体通过摆脱现象世界而回归本心的可能,提倡“反求诸已”、“求其放心”。
随着佛学的发展,融合儒家传统思想的佛学著作大乘起信论)所表现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哲学“复性”思维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一、“复性”思维模式的形成《大乘起信论》阐述的根本原理是“一心二门”。
“一心”又名“众生心”,是《起信论》的一个根本范畴,它是世界一切现象的本体,具有绝对的超越性,相当于真如。
它又涵摄全部宇宙万物、世界现象,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甚至可以落实到个体的心性。
“二门”指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两者虽然并立,但它们都由众生心开出,是众生心的一体两用。
{起倌论}通过真如所具生灭功能,将众生心或一心中的染净、真俗、凡圣等概念包容,是以一元的思维方式对心性作出的独特解释。
“一心二门”一方面说明人性中善恶何以存在的原因。
另一方面肯定个体之心性中真如的存在,说明了人回复本性的可能性;真如因为烦恼尘垢的覆盖而不能显示,则说明了回复佛性的必要性。
这种理论奠定了中国哲学复性说的发展方向。
《大乘起信论》对复性说形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本觉”说的提倡。
《起信论》说,“阿赖耶识”有两种意义,“一者觉义,二者不觉义”,“所言觉义者,谓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觉与不觉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念”(即“无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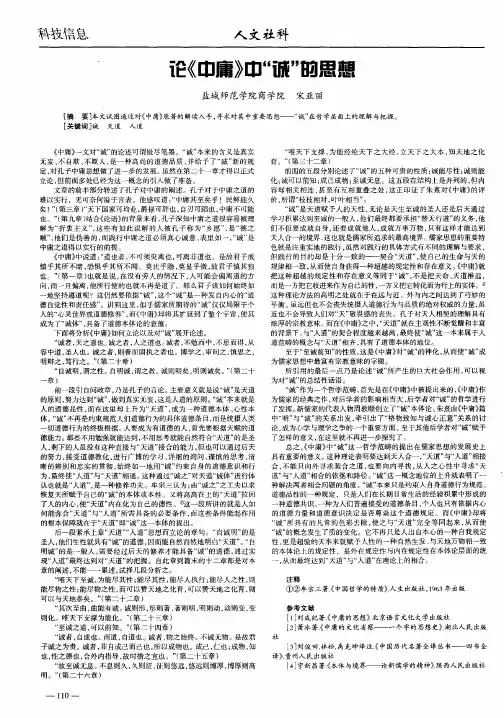

《中庸》“诚”说解读《中庸》作为儒家的重要典籍,历来受到当政者的极大重视,注释者不绝,官方推荐的作为科举考试法定的注释本,或者众多的民间注释本,对其中的各种观念作出各式各样的解释。
本文仅就其中提到的“诚”,考察几个重要的解释者的不同解读。
一、《中庸》之“诚”说“诚”是《中庸》篇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作者将之作为全文之枢纽,进行了反复的论述。
历来对它的诠释莫衷一是。
在此,笔者拟对之加以梳理蠡测,以图发覆其内在之意蕴。
《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也”[P36],“诚”是天道之本然属性。
它与天俱来,“自成” [P39]无依,超越万有,具有绝对的合理性与至上性,天地万有莫不以之为本。
天地万物在产生之时,便具有了这种天然的本性。
它作为万物生化的终极依据流行于万物之中,生生不息,从不间断,与万物相伴终身,“不可须臾离也”[P20]。
进而言之,天地之间不存在不具有此性的物体,“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P39]说的正是此义。
既然“诚”涵泳万物,贯穿万有之始终,那就是说,万有不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具有同样的质性,都是天道的一种体现。
但问题是,万有本性既然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为什么又会有圣人、常人这样的区分呢?《中庸》认为,虽然万物之中都具有完全同一的“诚”存在,但并非都能做到对本性“诚”的完全体认,对“诚”能做到完全体认的就是圣人,能体认部分“诚”的就是常人。
也就是说,万物的分别并非因其内在属性存有差异,而是源于个体对自身内在属性的体认程度不同所致。
在《中庸》看来,天地万有之中,能自觉做到对天道之“诚”完全体认的,除了其自身之外,就只有圣人了。
圣人对“诚”的体认至简至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P36]。
同时,《中庸》还认为,天道之自然本质的“诚”,并非是死寂的,它具有自觉的功能,也就是说,万有一旦达成对其自身内在“诚”的完全体认,这种内在的本性就会自觉地显发出来,所谓“自诚明,谓之性”[P37]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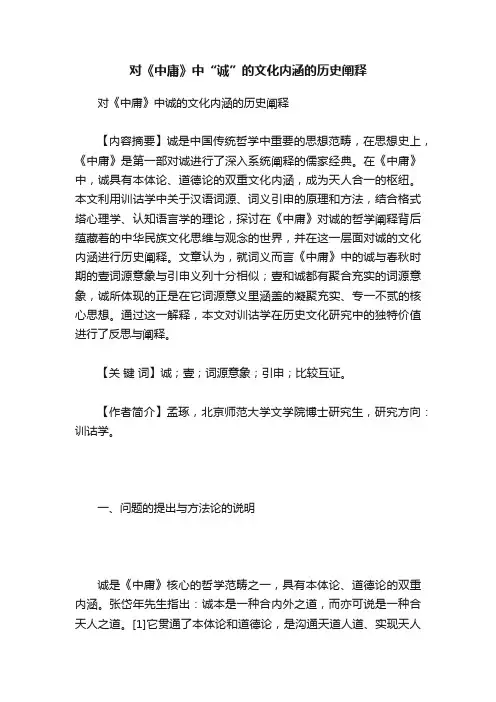
对《中庸》中“诚”的文化内涵的历史阐释对《中庸》中诚的文化内涵的历史阐释【内容摘要】诚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思想范畴,在思想史上,《中庸》是第一部对诚进行了深入系统阐释的儒家经典。
在《中庸》中,诚具有本体论、道德论的双重文化内涵,成为天人合一的枢纽。
本文利用训诂学中关于汉语词源、词义引申的原理和方法,结合格式塔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探讨在《中庸》对诚的哲学阐释背后蕴藏着的中华民族文化思维与观念的世界,并在这一层面对诚的文化内涵进行历史阐释。
文章认为,就词义而言《中庸》中的诚与春秋时期的壹词源意象与引申义列十分相似;壹和诚都有聚合充实的词源意象,诚所体现的正是在它词源意义里涵盖的凝聚充实、专一不贰的核心思想。
通过这一解释,本文对训诂学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独特价值进行了反思与阐释。
【关键词】诚;壹;词源意象;引申;比较互证。
【作者简介】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训诂学。
一、问题的提出与方法论的说明诚是《中庸》核心的哲学范畴之一,具有本体论、道德论的双重内涵。
张岱年先生指出:诚本是一种合内外之道,而亦可说是一种合天人之道。
[1]它贯通了本体论和道德论,是沟通天道人道、实现天人合一的枢纽。
在《中庸》之前的文献中,能见到的诚字很少。
经史著作中仅见四例:《左传文公十八年》:齐圣广渊,明允笃诚。
《国语晋语三》:贞为不听,信为不诚。
《大雅崧高》:申伯还南,谢于诚归。
《论语颜渊》: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论语》中的诚是情态副词,其余三例均为诚信、诚实之义,皆无《中庸》中诚所具有的本体论内涵。
因此,学者一般认为《中庸》对诚进行本体论阐释是一种哲学上的创新。
我们要追问的是:(1)诚有没有可以追溯的思想史渊源?(2)同样表示诚信,为何诚具备本体论的内涵,信不具备?本文认为,诚源自春秋时期壹的观念,其本体论内涵由先秦特定的文化思维模式所决定。
为了证明此点,我们借助传统训诂学中关于词义引申、汉语词源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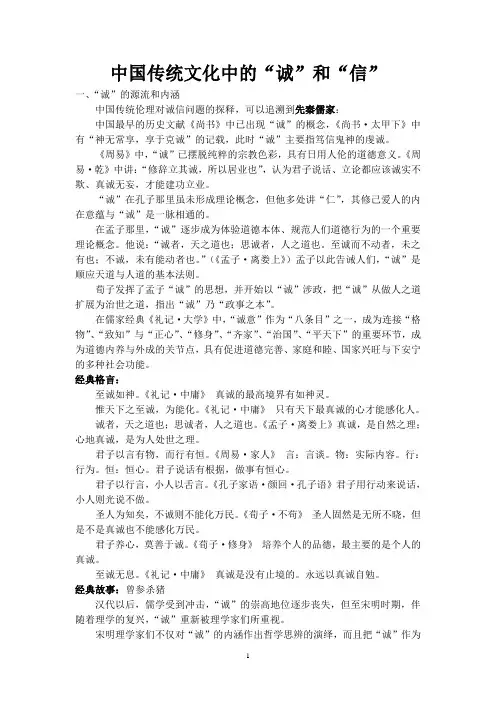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和“信”一、“诚”的源流和内涵中国传统伦理对诚信问题的探释,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尚书·太甲下》中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此时“诚”主要指笃信鬼神的虔诚。
《周易》中,“诚”已摆脱纯粹的宗教色彩,具有日用人伦的道德意义。
《周易·乾》中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功立业。
“诚”在孔子那里虽未形成理论概念,但他多处讲“仁”,其修己爱人的内在意蕴与“诚”是一脉相通的。
在孟子那里,“诚”逐步成为体验道德本体、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
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此告诫人们,“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
荀子发挥了孟子“诚”的思想,并开始以“诚”涉政,把“诚”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指出“诚”乃“政事之本”。
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成为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成为道德内养与外成的关节点,具有促进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国家兴旺与下安宁的多种社会功能。
经典格言:至诚如神。
《礼记·中庸》真诚的最高境界有如神灵。
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化。
《礼记·中庸》只有天下最真诚的心才能感化人。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真诚,是自然之理;心地真诚,是为人处世之理。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周易·家人》言:言谈。
物:实际内容。
行:行为。
恒:恒心。
君子说话有根据,做事有恒心。
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孔子家语·颜回·孔子语》君子用行动来说话,小人则光说不做。
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
《荀子·不苟》圣人固然是无所不晓,但是不是真诚也不能感化万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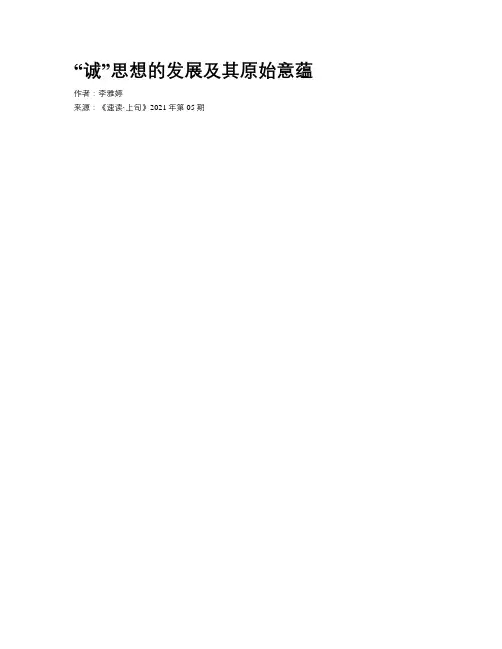
“诚”思想的发展及其原始意蕴作者:***来源:《速读·上旬》2021年第05期◆摘要:“诚”作为道德概念和儒学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敬神”到具有道德与哲学涵义的儒家思想概念的历史变迁。
直至朱熹将“诚”解释为“真实无妄”,“诚”思想趋于成熟,不仅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也成为了儒家“诚”思想的主流解读。
◆关键词:“诚”;发展;儒学;字源儒家思想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思想生活,“诚”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也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支撑着正常的社会秩序。
对于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和道德中的“诚”,我们理应了解其变化发展的过程。
一、“诚”字的原始意蕴文字是思想观念的体现,因此在探究“诚”思想发展之前,我们首先要通过分析“诚”的字源,了解其原始意蕴。
“诚”字据说最早出现于商朝,“真德秀曰:唐虞时未有诚字,《舜典》允塞即诚之义。
至伊尹告太甲始见诚字。
”,但此字没有已知的甲骨文和金文,始见于战国文字。
《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诚,信也。
”从推测的甲骨文“诚”之义,我们可以看出“诚”的原始意蕴中包含的古人诚心实意的态度以及对神灵的崇拜。
二、“诚”思想的发展任何一个观念的形成都有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刘乾阳(2016)指出一般认为“诚”观念诞生于原始祭祀之中,体现了对神灵和祖先的虔诚崇拜和信服。
早在《周易·蒙卦》中即有“初筮告。
再三渎,渎则不告”的记载,意味着向神灵请教时,要诚心诚意;《礼记·祭统》中也有“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即祭祀时需要表达自己的诚信,有了诚信才算尽心,才算是虔敬,才能够侍奉神明。
从《周易》和《礼记》中我们能看出“诚”与祭祀时和神灵沟通的思想态度是分不开的,而且从《礼记》中的记载我们也能感受到,“诚”不再仅仅是面对神灵的恭敬之心,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道德内涵。
之后“诚”在一代代学者的研究中逐渐丰满,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是借助儒家思想之手一步步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并辐射至整个东亚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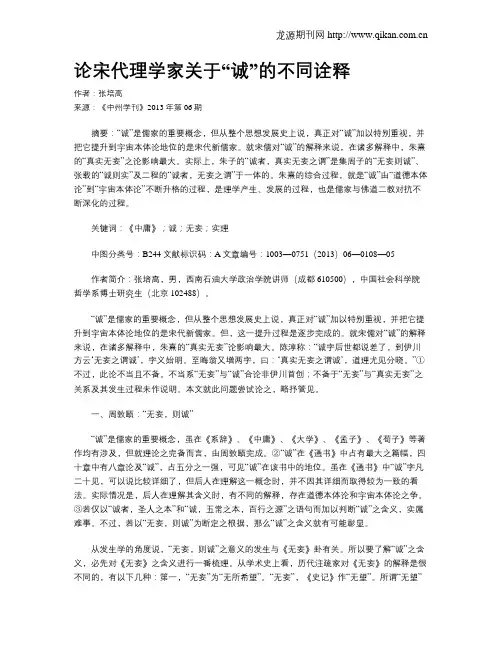
论宋代理学家关于“诚”的不同诠释作者:张培高来源:《中州学刊》2013年第06期摘要:“诚”是儒家的重要概念,但从整个思想发展史上说,真正对“诚”加以特别重视,并把它提升到宇宙本体论地位的是宋代新儒家。
就宋儒对“诚”的解释来说,在诸多解释中,朱熹的“真实无妄”之论影响最大。
实际上,朱子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是集周子的“无妄则诚”、张载的“诚则实”及二程的“诚者,无妄之谓”于一体的。
朱熹的综合过程,就是“诚”由“道德本体论”到“宇宙本体论”不断升格的过程,是理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是儒家与佛道二教对抗不断深化的过程。
关键词:《中庸》;诚;无妄;实理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108—05作者简介:张培高,男,西南石油大学政治学院讲师(成都610500),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
“诚”是儒家的重要概念,但从整个思想发展史上说,真正对“诚”加以特别重视,并把它提升到宇宙本体论地位的是宋代新儒家。
但,这一提升过程是逐步完成的。
就宋儒对“诚”的解释来说,在诸多解释中,朱熹的“真实无妄”论影响最大。
陈淳称:“诚字后世都说差了,到伊川方云‘无妄之谓诚’,字义始明。
至晦翁又增两字,曰:‘真实无妄之谓诚’,道理尤见分晓。
”①不过,此论不当且不备。
不当系“无妄”与“诚”合论非伊川首创;不备于“无妄”与“真实无妄”之关系及其发生过程未作说明。
本文就此问题尝试论之,略抒管见。
一、周敦颐:“无妄,则诚”“诚”是儒家的重要概念,虽在《系辞》、《中庸》、《大学》、《孟子》、《荀子》等著作均有涉及,但就理论之完备而言,由周敦颐完成。
②“诚”在《通书》中占有最大之篇幅,四十章中有八章论及“诚”,占五分之一强,可见“诚”在该书中的地位。
虽在《通书》中“诚”字凡二十见,可以说比较详细了,但后人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并不因其详细而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
实际情况是,后人在理解其含义时,有不同的解释,存在道德本体论和宇宙本体论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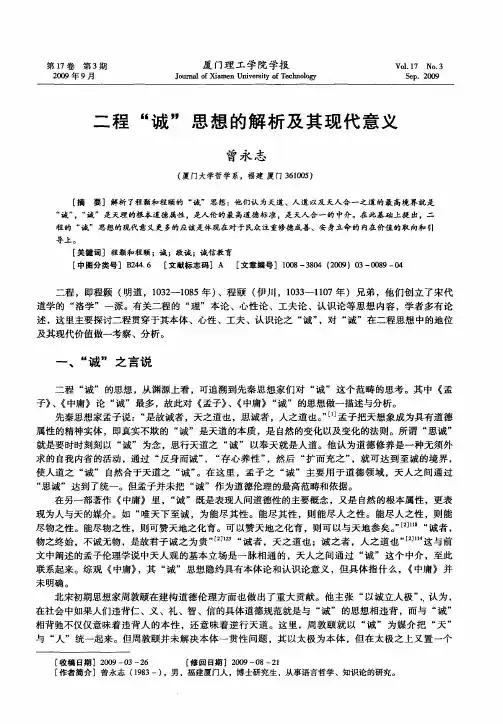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大学》《中庸》本为《礼记》中二篇,是战国时期懦家的重要作品。
有人言《大学》作者为曾子,《中庸》作者为子思。
而通行之说法,子思乃曾子之弟子,而子思之学则再传于孟子,由此形成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至关重要之“思孟学派”。
无论以上说法准确与否,我们今天考察《大学》《中庸》与《孟子》,其内在思想倾向确为一脉相承,其最大特点即开创了儒家学说中的“心性”之学及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为学路径。
在《大学》《中庸》尤其是《中庸》中,这种心性哲学理论以及修齐治平的整个道德政治哲学体系,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概念展开的,这个概念就是“诚”。
理解这一概念对于完整把握由其出发建设的整个哲学体系,对于理解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的核心精神,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一、“诚意”乃修齐治平之本《大学》一篇,核心为所谓“三纲领”“八条目”。
“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而如何达至此三纲领?《大学》又有“八条目”具体落实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后四条为儒家由己及人之政治哲学,前四条却是修身之道德哲学。
儒家向来认为政治即一推己及人之过程,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成为八条目中最为关键之环节,它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条则是修身之具体路径。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这里暂且不讲。
那么儒家所讲之“修身”到底如何修?这恐怕是儒家学说中最为关键、根本之学,亦为一切学问之基础。
因此我们这里将目光投向《大学》“八条目”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条。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讲的正是修身之道。
然而,相比修齐治平之说之简明易懂因而名气也更大,此四条自古即较难理解,以致众说纷纭。
儒家论“诚”儒家论“诚”“诚”与“仁”、“乐”一起,构成了儒家哲学中特有的关于真、善、美的学说,“诚”就是在“真”的意义上说的。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由“诚”组成的词组非常多,如真诚、诚实、诚恳、诚心、诚信、诚意等等。
由这些词组的现存意义上看,我们也多少能看到儒学所谓“真”的确切内涵。
这些词组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用来描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或对待生活本身的态度,就是一种真情实感。
这是儒家学者特别强调的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意义上的“诚”。
落实在哲学的本体论意义上说,此“诚”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就是说,有此“诚”,方不失为人。
“诚”作为人的真实存在,有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天道的根源。
天道流行变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有常”,说明自然确实是一个有目的的存在。
此一“确实”,就是自然对人所作出的承诺,朝来暮往、四时代兴、万物生长,这是自然的存在的言说。
自然目的落在实处,就是人的存在被赋予的使命感,此为人道之“诚”。
人对他人、对自然、天地万物本来是有义务的,这就要求人对自然作出承诺,此承诺是人的存在的言说。
人作出承诺、履行义务,是向存在的家园的回归。
此回归,是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之“诚”的最终实现。
这需要一定的修养工夫,而“思诚”、“诚明”、“诚意”等等所讲述的作为工夫论意义上的“诚”,再度表现了儒家哲学本体与工夫合一的特征。
(一)、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诚”现代社会日益步入商品社会,我们也在搞市场经济,在这样的形势下,“诚”作为一种人生态度、作为一种美德,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装饰品或点缀物。
如此,再大谈特谈“诚”,似乎不合时宜。
如果真的这样,那是我们时代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
儒学创始人孔子很少谈到“诚”,《论语》中“诚”字的出现仅有两处,一为“诚不以富”,一为“诚哉”,用以加重语气,不具有后来所说的作为美德的“诚”含义。
但《论语》中对孔子言行的记载,却往往是在强调“诚”之美德,强调一种有真情实感的人生态度。
孔子的语言中教育学生如此,行动中更体现为如此。
59《中庸》“明诚关系”的价值生成论阐释刘 进( 西安思源学院思政部,陕西 西安 710038 )【摘 要】宋明理学家对《中庸》的明诚关系基本上是沿着形上学的价值预成论予以阐发,即全善的天命规定了人性,藉着人的道德实践而显示出来,人只需做到率性而动的诚,即可达到道德认知的效用,即“自诚明谓之性”。
反之,“自明诚谓之教”是凭借道德学习认知开始道德实践以生成价值的过程。
然而,纵观《中庸》修德功夫论对道德主体的实践在价值生成中的彰显,不难发现,天道的形上依据与人道的后天实践是价值本源论上的互文同构,《中庸》在当今的意义并非基于天命的道德形上学,而是人在道德文化中笃行实践以成德的价值生成论。
【关键词】明诚关系;价值实践;道德文化;价值生成《中庸》因形上学意蕴浓厚,唐宋以降受到注经者的关注。
《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经典论述也因涉及到道德认知与实践的关系而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哲学公案。
朱熹的注释是从圣人与贤人的修德路线差异出发的,他认为“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
”[1](P32)圣人天性不失天道全善,他只需率性而为,真诚地照天性去行动,不违背天性的要求,他就可以做到道德认知上的明察,因为从善的天命规定的天性发出的行为也是善的。
这是藉着天性的作用由明而诚。
这是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形上逻辑。
然而,朱熹认为贤人的修德路线不同于此。
“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
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2](P32)贤人是先认知到道理,然后依着道理去实践,才恢复本性的诚。
这条路线强调教育的重要角色。
朱熹的诠释蕴含了张力:价值的预成论和生成论的张力。
前者主张道德价值由天道先天预成了,人的行动只是显明这已预成的价值。
后者主张,道德认知是源,教育是主要方法,道德实践是道德价值生成的根本。
“自诚明”的论述显然含有“天命”全善的理论预设。
这实际上是把后天生成的道德价值归于一个“天命”概念。
“诚”与“思辨”:德性的载体,天人相通的途径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江苏徐州 221116 “中庸”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中庸》中讲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而谈到所说的“致中和”,我们首先要探讨“诚”及其与“中庸”的关系。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 [1]这句话中提到了一个“诚”与“中庸”连接的桥梁——“天性”。
万物都有天赋的本性,本性与天性是相关联的,实现了本性即实现了天性,同时,实现本性的过程也便是在实现天性。
而“人与人的关系正是这一总体关系中的一个特殊例子,并体现为‘诚’。
一个‘诚’者实现了其内在善性,并因此体现了天道。
” [2]又如“‘致中和’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恢复人固有的善的本性。
要恢复人的善的本性,首先要努力做到‘诚’,因为‘诚’是‘物之终始’,是沟通人道和天道的桥梁,因此‘诚’是中庸的关键所在。
”这样来看,在“天”与“人”的同一中,天性与人性的沟通中,“诚”是至关重要的。
“诚”者“言”“成”也。
无疑,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起很大作用,在通过对自我善性实现中、实现后来实现天性,以达统一。
这提示我们,这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是品格、修养、“德性”的内化,成为身体或自我的一部分的过程,它由内向外彰显,具有稳定性、影响力。
那么“诚”内化与外显的过程是否便是在实现“中庸”呢?“致中和”是“达道也”,是本性与天性、人道与天道的统一,自我内部的协调,自我与他人、个体与世界的“和”。
“中庸的‘诚’有三个难度:一、连接天与人(‘天命之谓性’);二、‘诚’是贯通天、地、人的一种普遍规范,使天和人、地和人、人和人、人和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理性状态;三、‘诚’强调个体和群体的关系。
‘诚’既是道德本性,也是道德实践,是个人自身的修养、人际关系充分协调的原则、国家间交往的原则。
收稿日期:2005-04-15基金项目:2004年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道德的心灵根基:儒家“诚”论研究》(课题编号:04Z C053)。
作者简介:鲁 芳(1973-),女,湖南桃源人,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第20卷第2期2005年6月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 L OF CH ANG SH A UNIVERSITY OF SCIE NCE &TECH NO LOGY (SOCIA L SCIE NCE )V ol .20N o .2Jun .2005“诚”的心性论阐释鲁 芳(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76)[摘要]宋明理学曾对“诚”给出了“真实无妄”、“诚实不欺”的道德规定,但是由于他们又把“诚”与“心”紧密相连,从而又给“诚”赋予了心性论内涵:(1)“诚”是主体至高的心灵境界,(2)“诚”是主体道德意识与客观道德法则的高度合一,(3)“诚”是主体“择善固执”的道德意志。
[关键词]诚;心;性[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 (2005)02-0024-03An I nterpretation of “Sincerit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H eart and SpiritLU Fang(School o f Law ,Changsha Univer sity o 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76,China )Abstract :The neo -C on fucians in the S ong and M ing Dynasty defined sincerity as being m orally truth ful and honest.As sincerity is closely ass ociatedwith the heart ,s o it had been given the connotative meanings derived from the Heart and S pirit Theory :First ,sincerity is the supreme spiritual state ;Second ,sincerity is the greatest harm ony between m oral consciousness and m oral rules ;Third ,sincerity is the m oral will that stimulates individuals to stick to what is g ood.K ey w ords :sincerity ;heart ;spirit “诚”者,“真实无妄”,“诚实不欺”之谓也。
宋明时期儒家所形成的对“诚”的这一解释,主要是对天道、人性的道德内涵的一种规定,是从“天”的自然属性中所抽象出来的一种伦理属性。
当我们从天之道、人之性的角度理解“诚”时,还只是体会到了它的客观内容,而当我们把“诚”放在儒家心性论中来重新审视时,即从“心理合一”的角度来理解“诚”时,“诚”的主观方面,也就是“诚”自身所蕴涵的超越性、主体性、自觉性等特征就都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只有同时从心性论的角度把握“诚”,才算真正了解儒家“诚”论的伦理精髓;也只有从心性论角度来进一步把握“诚”,才能体会到“诚”对于人的意义。
一、“诚”是主体至高的心灵境界“诚”作为“天之道”,是一种天地境界,它与人的心灵无关;但当孟子、《中庸》将“诚”视为“人之性”,并认为人必须“思诚”、“诚之”时,“诚”作为人的心灵境界的地位就已得到了确定。
宋明时期,当理学家把“诚”与“心”相联系进一步说到“诚”是“心之体”,是心的本体存在、本然状态时,“诚”作为人的心灵境界的意义才更加凸显和明朗起来。
“诚”为“天之道”、“人之性”,但是,作为禀“天之道”而来的“人之性”落脚于人的何处?对此,宋明理学家给予了回答。
他们认为,“诚”具于“心”中,以“心”为存在的“寓所”。
张载就曾以“天之实”和“心之实”的合一来解释“诚”,其后,朱熹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发挥,他说:“盖诚之为言,实而已矣。
……有以理之实而言者,……有以心之实而言者。
”①“天之实”、“理之实”都是在天之诚,而“心之实”则是在人之诚,可见,在人之诚不能离“心”而存在。
陈献章则说得极为直截明了:“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
”②但是“诚”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心”中?理本派和心本派的基本观点是:“诚”是“心”之体。
他们认为,具于“心”中之“诚”决不是像物件摆放在容器中那样,与“心”只是空间上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存储关系,而是以“心之体”的形式与心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诚就是心的本然状态。
例如,朱熹说“理无心,则无着处”,故心与理“本来贯通”。
理在心则言之为性,“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故性也具于心中,“心将性做馅子模42样”。
朱熹说“心将性做馅子模样”,并不是将心、性视为截然分割的两个事物,而只是藉此表明心与性的存属关系,因为他同时还说“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③,所谓“心之理”就是心之体。
由此可以逻辑地推出,性理为心之体,性理以心之体的方式存在。
程、朱又以至善之性为心之体,而至善之性即为诚,故心之体亦为诚。
心本派则将“诚”与心本体等同,使二者直接具有本体论上的统一性。
陆九渊认为人的本心就是诚,“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此吾之本心也”④。
“本心为诚”也就是“心之体为诚”。
王守仁更是从心体立论,直言“诚是心之本体”⑤。
当儒家说“诚”是“心”之本体时,实际上就意味着“诚”是人心与天道、天理合一的本然状态,是心灵的至高境界。
作为心灵的至高境界,“诚”具有这样的道德规定性:人心能够随时随处、自然而然地实现与“天道”、“天理”的合一,而不需要勉强为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境界。
这不仅是“天”所具有的伦理属性,而且是人心所应具有的道德属性。
之所以说“诚”所标志的这种心灵境界是至高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其内涵上说,“诚”与“天道”合一,它本身是天地境界在人的表现,而天地境界正是人们道德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至高、至善的。
其次,从对它的道德实践上说,“诚”这种心灵境界是圣人境界,一般人哪怕终其一生付出艰苦的努力,将之作为追求的目标,孜孜以求,都只能不断接近,而难以彻底达到这一境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才以“思诚”、“诚之”为“人之道”,而不说“诚”为“人之道”。
对此,朱熹说得更为清楚明白:“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
”⑥再次,从“诚”在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地位来看,“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原”,⑦“诚”的境界的实现是其它道德规范被履行的根本保证。
由此可知,儒家的“诚”是一种终极存在,是对人的最高的道德要求,也是为人所设置的最终的追求目标。
二、“诚”是主体道德意识与客观道德法则的高度合一“心”不仅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功能性的意义,即具有认识的作用。
当我们说“诚”存在于人的心中,是对人心的道德规定时,“诚”还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它只有被人所认识,成为主体的道德意识,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存在,而这离不开心的认知功能的发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诚”体现了主体道德意识与客观道德法则的高度合一。
宋明理学家在强调心为“实”、心有道德内容的同时,也都认为心是认识器官,具有认识和思维的功能。
也就是说,心不仅是义理之心,而且是认知之心;不仅是本体之心,而且是功能之心。
既然心具有知觉思虑的功能(能知),那么,心的认识对象(所知)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宋明理学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但在分歧中又体现出共同之处,即以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为内容的性理(义理)始终是“心”的认识对象。
于是,以性理形式存在于人心中的“诚”也有待于认知之心将它发掘出来。
心本派将“诚”与“心”、“性”、“理”甚至“良知”等同,认为人首要的就是存心,“夫此心存则一,一则诚;不存则惑,惑则伪”⑧,而要存诚,首先就要明诚,就要致良知,也就是以主体之心去认识本体之心,从而使自心之诚得以彰显。
理本派也认为人首要的工夫就是明诚,但是他们所说的“明诚”不仅仅是向内认识自心之本体,而且包括格物致知,向外求物理,因为朱熹认为,穷得物理,则可豁然贯通,从而明得心中之理。
由此可见,虽然同样是以诚为心之体,但识诚的方式和途径却不尽相同。
如果说,理本派和心本派还十分强调“诚”的本体性,那么,气本派的代表王夫之则强调了“诚”作为意识的特质。
他认为:“诚,心也,无定体而行其性者也。
心统性,故诚贯四德,而四德分一,不足以尽诚。
”⑨由于王夫之所理解的“心”主要为知觉之心,所以,“诚”虽然具于“心”中,但“心”与“诚”却非本体的同一关系,而主要是认知与被认知的关系,故王夫之说:“实有是物则实有处是物之事,实有此事则实有成此事之理,实有此理则实有明此理行此理之心。
……诚以实心行实理之谓。
” λυ以“心”“明此理”,表达的显然是一种认知关系。
他所理解的“诚”就是通过心的认识功能将心中之理变为人的自觉认识,并将之付诸于行动,或者说,“诚”就是“心”的一种诚实无伪的状态。
这样,“诚”就丧失了本体论的含义,而成为对人的主观意识的一种描述。
“心”通过对“诚”的认知和把握而将“诚”置于意识的控制之下,使之成为主体意识中的存在,渗透到主体的认识、情感、意志、信念之中。
“诚”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它以封建伦理纲常为其客观内容,因此也就内在地体现着主客观的统一。
只是它并不是主客体的一般层次上的统一,而是主体道德意识与客观道德内容的高度融合统一,表现为:主体对道德法则有高度的认同,对之持有挚热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并以自身最终实现“诚”为最高的理想和追求。
在这种意义上说,“诚”所表现的又是人的一种至善至美的精神状态。
它与“诚”的心灵境界说并不矛盾,而毋宁说它就是对“诚”的境界的心理诠释。
三、“诚”是主体“择善固执”的道德意志宋明理学认为,心不仅具有知觉思虑的功能,而且具有主宰功能。
心的主宰功能不仅表现为心“为一身之主宰” λϖ,更重要的是,心是“万事之主”,使人在应事接物上能够始终一以贯之,因此,心为主宰就在于心不“走东走西”,能够“一而不二”,能够“命物而不命于物”。
借助于“心”的主宰功能的发挥,“诚”又转化为了人们择善固执的道德意志。
朱熹认为:“‘心统性情。
’统,犹兼也。
” λω“性,其理;情,其用。
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
” λξ心将性和情包含于其中,并不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而是将其视为“客”,将自身视为“主”,并以理对性和情进行管摄和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