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诗歌创作与其诗歌理论的关系
- 格式:pdf
- 大小:3.69 MB
- 文档页数: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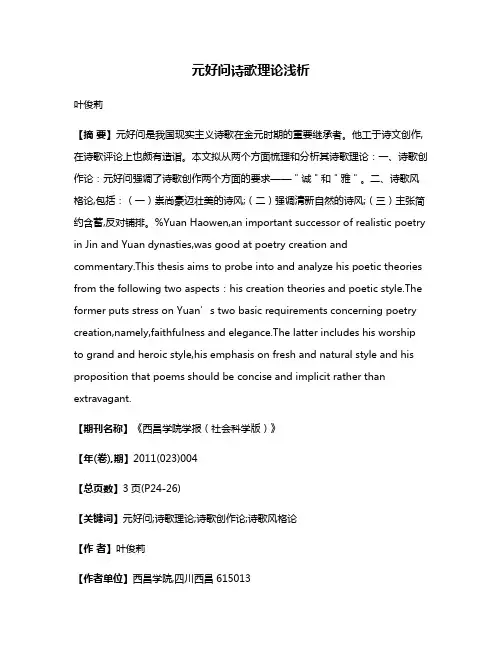
元好问诗歌理论浅析叶俊莉【摘要】元好问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在金元时期的重要继承者。
他工于诗文创作,在诗歌评论上也颇有造诣。
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梳理和分析其诗歌理论:一、诗歌创作论:元好问强调了诗歌创作两个方面的要求——"诚"和"雅"。
二、诗歌风格论,包括:(一)崇尚豪迈壮美的诗风;(二)强调清新自然的诗风;(三)主张简约含蓄,反对铺排。
%Yuan Haowen,an important successor of realistic poetry in Jin and Yuan dynasties,was good at poetry creation and commentary.This thesis aims to probe into and analyze his poetic theories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his creation theories and poetic style.The former puts stress on Yuan’s two basic requirements concerning poetry creation,namely,faithfulness and elegance.The latter includes his worship to grand and heroic style,his emphasis on fresh and natural style and his proposition that poems should be concise and implicit rather than extravagant.【期刊名称】《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23)004【总页数】3页(P24-26)【关键词】元好问;诗歌理论;诗歌创作论;诗歌风格论【作者】叶俊莉【作者单位】西昌学院,四川西昌61501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金代文学家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在金元时期的重要继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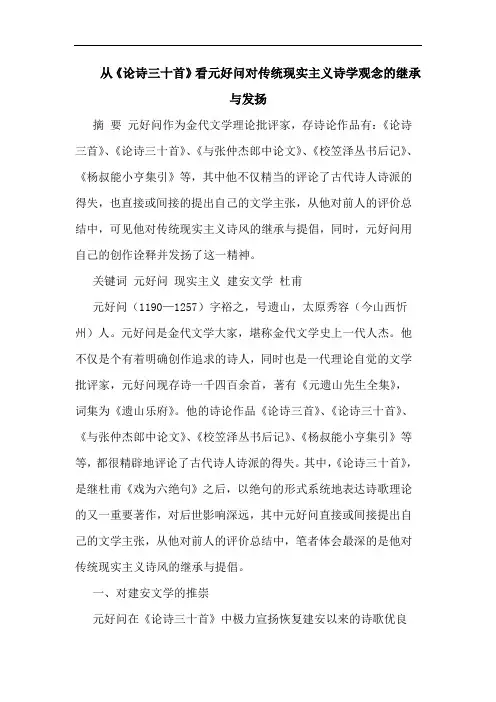
从《论诗三十首》看元好问对传统现实主义诗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扬摘要元好问作为金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存诗论作品有:《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杨叔能小亨集引》等,其中他不仅精当的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也直接或间接的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从他对前人的评价总结中,可见他对传统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提倡,同时,元好问用自己的创作诠释并发扬了这一精神。
关键词元好问现实主义建安文学杜甫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
元好问是金代文学大家,堪称金代文学史上一代人杰。
他不仅是个有着明确创作追求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代理论自觉的文学批评家,元好问现存诗一千四百余首,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
他的诗论作品《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杨叔能小亨集引》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
其中,《论诗三十首》,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以绝句的形式系统地表达诗歌理论的又一重要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元好问直接或间接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从他对前人的评价总结中,笔者体会最深的是他对传统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提倡。
一、对建安文学的推崇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极力宣扬恢复建安以来的诗歌优良传统,笔者认为他所推崇的建安传统,主要是建安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
他在第二首中论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觉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元好问论诗从建安才子说起,钟嵘在《诗品》中说,“曹刘殆文章之圣”,元好问也以曹植、刘桢为代表说起,从“曹刘坐啸虎生风”中,可见他推重建安诗人的是他们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气概和力量,元好问欣赏他们的慷慨激昂、悲壮动人。
曹植《前录自序》里自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
”他又在《赠徐干》中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
”曹植的诗歌明显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抒发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抱负,寄托诗人欲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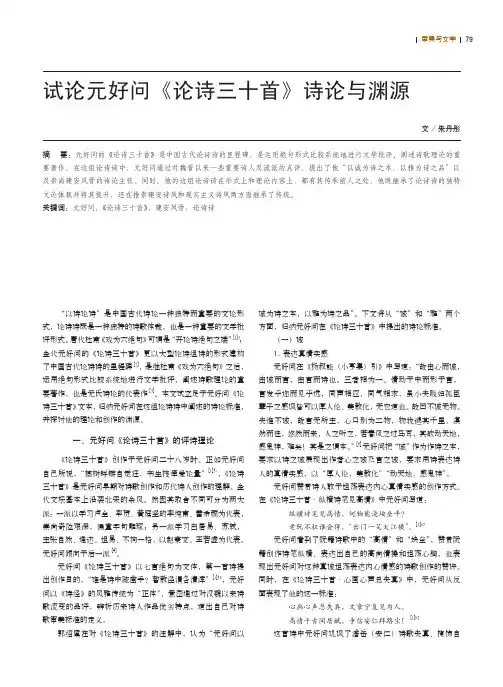
79审美与文学“以诗论诗”是中国古代诗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文论形式,论诗诗既是一种独特的诗歌体裁,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
唐代杜甫《戏为六绝句》可谓是“开论诗绝句之端”[1]3;金代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更以大型论诗组诗的形式建构了中国古代论诗诗的里程碑[2],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运用绝句形式比较系统地进行文学批评,阐述诗歌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元氏诗论的代表作[3]。
本文试立足于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文本,归纳元好问在这组论诗诗中阐述的诗论标准,并探讨他的理论和创作的渊源。
一、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评诗理论《论诗三十首》创作于元好问二十八岁时。
正如元好问自己所说,“撼树蜉蝣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1]57,《论诗三十首》是元好问早期对诗歌创作和历代诗人创作的理解。
金代文坛基本上沿袭北宋的余风。
然因其取舍不同可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学习卢全、李贺、黄庭坚的李纯甫、雷希颜为代表,崇尚奇险艰深,偏重字句雕琢;另一派学习白居易、苏轼,主张自然、通达、坦易、不拘一格,以赵秉文、王若虚为代表。
元好问倾向于后一派[4]。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以七言绝句为文体,第一首诗提出创作目的,“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1]58,元好问以《诗经》的风雅传统为“正体”,意图通过对汉魏以来诗歌流变的品评,辨析历来诗人作品优劣特点,道出自己对诗歌审美标准的定义。
郭绍虞在对《论诗三十首》的注解中,认为“元好问以诚为诗之本,以雅为诗之品”。
下文将从“诚”和“雅”两个方面,归纳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提出的诗论标准。
(一)诚1.表达真情实感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写道:“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
三者相为一。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它道也。
故曰不诚无物。
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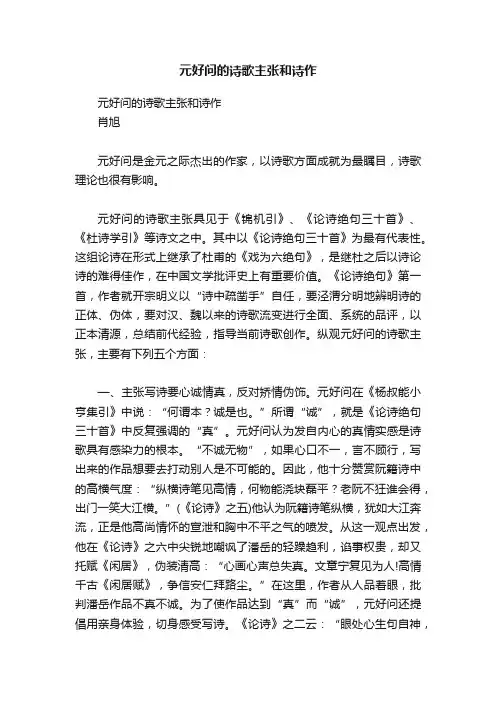
元好问的诗歌主张和诗作元好问的诗歌主张和诗作肖旭元好问是金元之际杰出的作家,以诗歌方面成就为最瞩目,诗歌理论也很有影响。
元好问的诗歌主张具见于《锦机引》、《论诗绝句三十首》、《杜诗学引》等诗文之中。
其中以《论诗绝句三十首》为最有代表性。
这组论诗在形式上继承了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继杜之后以诗论诗的难得佳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价值。
《论诗绝句》第一首,作者就开宗明义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要泾渭分明地辨明诗的正体、伪体,要对汉、魏以来的诗歌流变进行全面、系统的品评,以正本清源,总结前代经验,指导当前诗歌创作。
纵观元好问的诗歌主张,主要有下列五个方面:—、主张写诗要心诚情真,反对矫情伪饰。
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说:“何谓本?诚是也。
”所谓“诚”,就是《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反复强调的“真”。
元好问认为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是诗歌具有感染力的根本。
“不诚无物”,如果心口不一,言不顾行,写出来的作品想要去打动别人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十分赞赏阮籍诗中的高横气度:“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论诗》之五)他认为阮籍诗笔纵横,犹如大江奔流,正是他高尚情怀的宣泄和胸中不平之气的喷发。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在《论诗》之六中尖锐地嘲讽了潘岳的轻躁趋利,谄事权贵,却又托赋《闲居》,伪装清高:“心画心声总失真。
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在这里,作者从人品着眼,批判潘岳作品不真不诚。
为了使作品达到“真”而“诚”,元好问还提倡用亲身体验,切身感受写诗。
《论诗》之二云:“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他认为从眼所接触的实境,激发诗情,自能写出入神之句。
“见得真,方道得出”,如果没有现实生活感受,只是凭空虚拟,便不会有真情实境。
所以他鄙夷江西诗派,认为他们那种拙劣的形式模拟,既得不到杜甫的“古雅”,又失却了李商隐的“精纯”。
他告诫人们不要步江西诗派的后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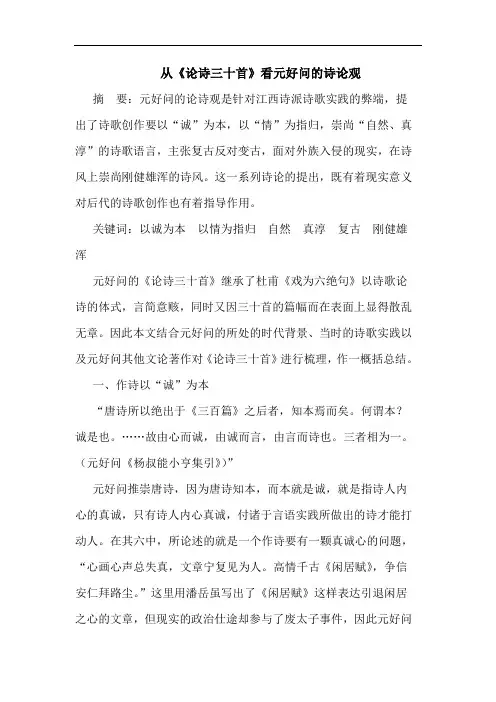
从《论诗三十首》看元好问的诗论观摘要:元好问的论诗观是针对江西诗派诗歌实践的弊端,提出了诗歌创作要以“诚”为本,以“情”为指归,崇尚“自然、真淳”的诗歌语言,主张复古反对变古,面对外族入侵的现实,在诗风上崇尚刚健雄浑的诗风。
这一系列诗论的提出,既有着现实意义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也有着指导作用。
关键词:以诚为本以情为指归自然真淳复古刚健雄浑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继承了杜甫《戏为六绝句》以诗歌论诗的体式,言简意赅,同时又因三十首的篇幅而在表面上显得散乱无章。
因此本文结合元好问的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诗歌实践以及元好问其他文论著作对《论诗三十首》进行梳理,作一概括总结。
一、作诗以“诚”为本“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而矣。
何谓本?诚是也。
……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
三者相为一。
(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元好问推崇唐诗,因为唐诗知本,而本就是诚,就是指诗人内心的真诚,只有诗人内心真诚,付诸于言语实践所做出的诗才能打动人。
在其六中,所论述的就是一个作诗要有一颗真诚心的问题,“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这里用潘岳虽写出了《闲居赋》这样表达引退闲居之心的文章,但现实的政治仕途却参与了废太子事件,因此元好问感叹文章并不与人的道德品质相符,但是“文章宁复见为人”是有前提条件的,就如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所说:“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之所以出现“心画心声总失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人心“不诚”所导致的。
可见,元好问所提倡的诗歌是那些作者以真诚心来写作的,如若不如此,则诗歌就会“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
”二、作诗以“情”为指归“虽然,方外之学(指佛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
……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
《陶然集诗序》”。
这里,元好问点出“诗家圣处”在于“不离文字”而又“不在文字”,这是因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不离文字”是要通过文字来写出诗人之情,“不在文字”说明作诗不在于表面的语言,是以“情”作为指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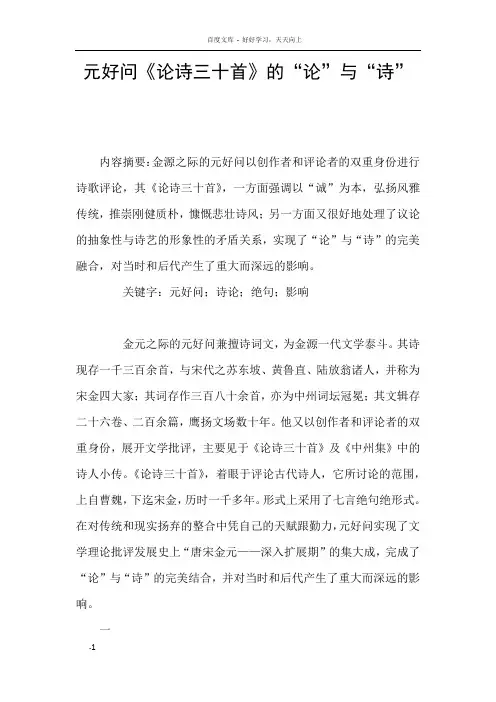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论”与“诗”内容摘要:金源之际的元好问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进行诗歌评论,其《论诗三十首》,一方面强调以“诚”为本,弘扬风雅传统,推崇刚健质朴,慷慨悲壮诗风;另一方面又很好地处理了议论的抽象性与诗艺的形象性的矛盾关系,实现了“论”与“诗”的完美融合,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元好问;诗论;绝句;影响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兼擅诗词文,为金源一代文学泰斗。
其诗现存一千三百余首,与宋代之苏东坡、黄鲁直、陆放翁诸人,并称为宋金四大家;其词存作三百八十余首,亦为中州词坛冠冕;其文辑存二十六卷、二百余篇,鹰扬文场数十年。
他又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展开文学批评,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及《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
《论诗三十首》,着眼于评论古代诗人,它所讨论的范围,上自曹魏,下迄宋金,历时一千多年。
形式上采用了七言绝句绝形式。
在对传统和现实扬弃的整合中凭自己的天赋跟勤力,元好问实现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的集大成,完成了“论”与“诗”的完美结合,并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主张“诚”为诗的本原,坚持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弘扬诗歌的“风雅”传统,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形成了自己的诗歌批评体系。
“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
何谓本?诚是也。
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
三者相为一。
情动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厚人伦,美风化,无他也。
故曰:不诚无物。
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邀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所听之,若春风之过焉耳。
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
其是之谓本”(《杨叔能〈小亨集〉引》)。
由此可见元好问认为诗的本原在一个“诚”字,也即诗人的真性情,只有“以诚为本”,才能有真正感人的诗作。
《论诗三十首》反复强调“诚”是创作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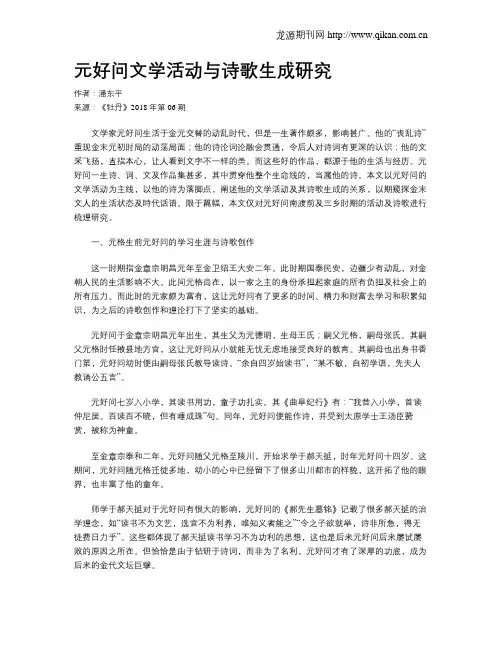
元好问文学活动与诗歌生成研究作者:潘东平来源:《牡丹》2018年第06期文学家元好问生活于金元交替的动乱时代,但是一生著作颇多,影响甚广。
他的“丧乱诗”重现金末元初时局的动荡局面;他的诗论词论融会贯通,令后人对诗词有更深的认识;他的文采飞扬,直指本心,让人看到文字不一样的美。
而这些好的作品,都源于他的生活与经历。
元好问一生诗、词、文及作品集甚多,其中贯穿他整个生命线的,当属他的诗。
本文以元好问的文学活动为主线,以他的诗为落脚点,阐述他的文学活动及其诗歌生成的关系,以期窥探金末文人的生活状态及時代话语。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元好问南渡前及三乡时期的活动及诗歌进行梳理研究。
一、元格生前元好问的学习生涯与诗歌创作这一时期指金章宗明昌元年至金卫绍王大安二年。
此时期国泰民安,边疆少有动乱,对金朝人民的生活影响不大。
此间元格尚在,以一家之主的身份承担起家庭的所有负担及社会上的所有压力。
而此时的元家颇为富有,这让元好问有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去学习和积累知识,为之后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好问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出生,其生父为元德明,生母王氏;嗣父元格,嗣母张氏。
其嗣父元格时任掖县地方官,这让元好问从小就能无忧无虑地接受良好的教育。
其嗣母也出身书香门第,元好问幼时便由嗣母张氏教导读诗。
“余自四岁始读书”,“某不敏,自初学语,先夫人教诵公五言”。
元好问七岁入小学,其读书用功,童子功扎实。
其《曲阜纪行》有:“我昔入小学,首读仲尼居。
百读百不晓,但有唾成珠”句。
同年,元好问便能作诗,并受到太原学士王汤臣赞赏,被称为神童。
至金章宗泰和二年,元好问随父元格至陵川,开始求学于郝天挺,时年元好问十四岁。
这期间,元好问随元格迁徙多地,幼小的心中已经留下了很多山川都市的样貌,这开拓了他的眼界,也丰富了他的童年。
师学于郝天挺对于元好问有很大的影响,元好问的《郝先生墓铭》记载了很多郝天挺的治学理念,如“读书不为文艺,选官不为利养,唯知义者能之”“令之子欲就举,诗非所急,得无徒费日力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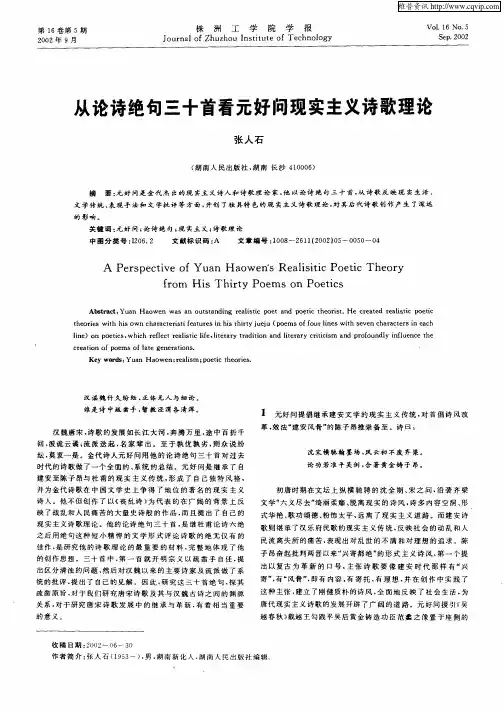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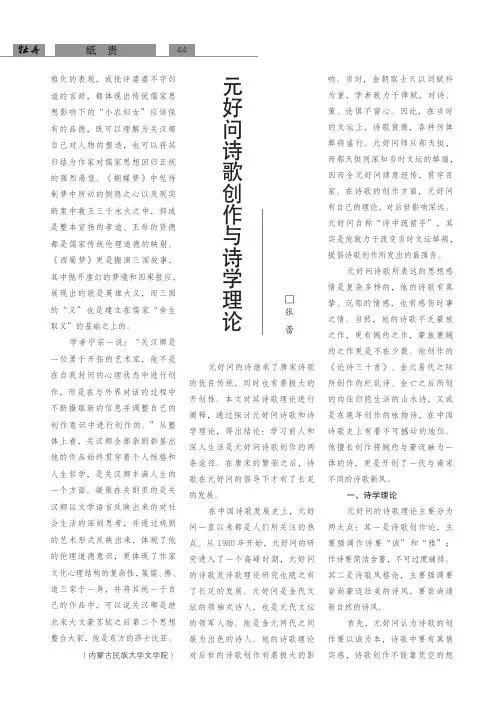
雅化的表现,或批评婆婆不守妇道的言辞,都体现出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小农妇女”应该保有的品德,既可以理解为关汉卿自己对人物的塑造,也可以将其归结为作家对儒家思想回归正统的强烈渴望。
《蝴蝶梦》中包待制梦中所动的恻隐之心以及现实断案中救王三于水火之中,抑或是整本宣扬的孝道、王母的贤德都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映射。
《西蜀梦》更是搬演三国故事,其中抛开虚幻的梦境和因果报应,展现出的就是英雄大义,而三国的“义”也是建立在儒家“舍生取义”的基础之上的。
学者宁宗一说:“关汉卿是一位勇于开拓的艺术家,他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中进行创作,而是在与外界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创作意识中进行创作的。
”从整体上看,关汉卿全部杂剧彰显出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个人性格和人生哲学,是关汉卿丰满人生的一个方面。
凝聚在关剧里的是关汉卿以文学语言反映出来的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思考,并通过戏剧的艺术形式反映出来,体现了他的伦理道德意识,更体现了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复杂性,集儒、佛、道三家于一身,并将其统一于自己的作品中,可以说关汉卿是继北宋大文豪苏轼之后第二个思想整合大家,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元好问的诗继承了唐宋诗歌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有着极大的开创性。
本文对其诗歌理论进行阐释,通过探讨元好问诗歌和诗学理论,得出结论:学习前人和深入生活是元好问诗歌创作的两条途径。
在唐宋的繁荣之后,诗歌在元好问的倡导下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元好问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热点。
从1980年开始,元好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元好问的诗歌及诗歌理论研究也随之有了长足的发展。
元好问是金代文坛的领袖式诗人,也是元代文坛的领军人物。
他是金元两代之间最为出色的诗人。
他的诗歌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张蕾元好问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响。
当时,金朝取士只以词赋科为重,学者致力于律赋,对诗、策、论俱不留心。
因此,在当时的文坛上,诗歌衰微,各种伪体弊病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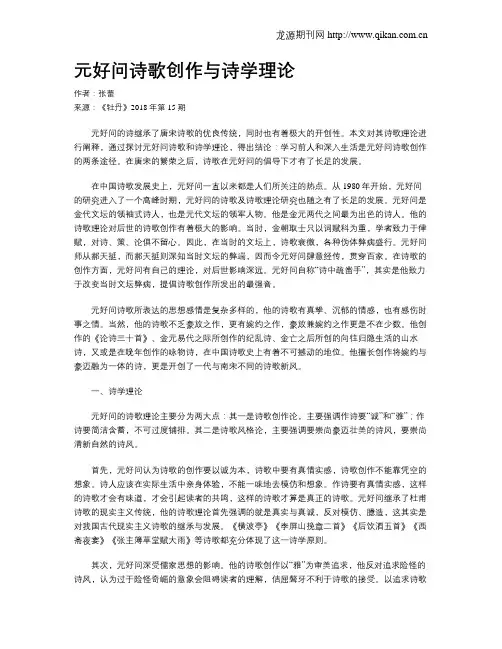
元好问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作者:张蕾来源:《牡丹》2018年第15期元好问的诗继承了唐宋诗歌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有着极大的开创性。
本文对其诗歌理论进行阐释,通过探讨元好问诗歌和诗学理论,得出结论:学习前人和深入生活是元好问诗歌创作的两条途径。
在唐宋的繁荣之后,诗歌在元好问的倡导下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元好问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热点。
从1980年开始,元好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元好问的诗歌及诗歌理论研究也随之有了长足的发展。
元好问是金代文坛的领袖式诗人,也是元代文坛的领军人物。
他是金元两代之间最为出色的诗人。
他的诗歌理论对后世的诗歌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
当时,金朝取士只以词赋科为重,学者致力于律赋,对诗、策、论俱不留心。
因此,在当时的文坛上,诗歌衰微,各种伪体弊病盛行。
元好问师从郝天挺,而郝天挺则深知当时文坛的弊端,因而令元好问肆意经传,贯穿百家。
在诗歌的创作方面,元好问有自己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好问自称“诗中疏凿手”,其实是他致力于改变当时文坛弊病,提倡诗歌创作所发出的最强音。
元好问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复杂多样的,他的诗歌有真挚、沉郁的情感,也有感伤时事之情。
当然,他的诗歌不乏豪放之作,更有婉约之作,豪放兼婉约之作更是不在少数。
他创作的《论诗三十首》、金元易代之际所创作的纪乱诗、金亡之后所创的向往归隐生活的山水诗,又或是在晚年创作的咏物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他擅长创作将婉约与豪迈融为一体的诗,更是开创了一代与南宋不同的诗歌新风。
一、诗学理论元好问的诗歌理论主要分为两大点:其一是诗歌创作论,主要强调作诗要“诚”和“雅”;作诗要简洁含蓄,不可过度铺排。
其二是诗歌风格论,主要强调要崇尚豪迈壮美的诗风,要崇尚清新自然的诗风。
首先,元好问认为诗歌的创作要以诚为本,诗歌中要有真情实感,诗歌创作不能靠凭空的想象。
诗人应该在实际生活中亲身体验,不能一味地去模仿和想象。

元好问(约公元648—公元713),字元亮,号好问,唐代文学家,与孟郊、王勃、刘长卿、柳宗元齐名为唐代五大家,是唐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
他著有《元氏随园集》《元氏雅言》《好问杂言》等著作。
其中,《好问杂言》是元好问的文论代表作,被誉为“盛唐史诗评价的最高表现”。
而《论诗三十首》则是《好问杂言》的一部分,是元好问论诗的代表作之一。
第一、《论诗三十首》的价值《论诗三十首》是元好问的诗学著作,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语言优美,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著作之一,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我国诗歌批评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对诗歌的创作技巧、审美标准、音乐韵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学审美观念和诗学理论。
这些观念和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理论和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二、《论诗三十首》对诗歌的审美标准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提出了“真”、“情”、“趣”、“致”四大审美标准,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真实感人”、“情致动人”、“姿态趣人”、“文采致人”。
这些标准对于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和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后世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论诗三十首》对诗歌的创作技巧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对诗歌的创作技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主张诗歌要“狷狭护雅”、“志致尚清”、“文辞贞肃”、“韵律清新”,并且提出了“志约风行”、“韵捷风流”、“辞贵风雅”、“句清风发”等创作原则。
这些创作技巧和原则对于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第四、《论诗三十首》对音乐韵律的探讨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还对诗歌的音乐韵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音同”“韵异”“声长”“辞近”等音韵原则,并且展示了对古代诗歌音乐韵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这对于我国古代诗歌的音乐性和韵律美的表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五、结语通过对《论诗三十首》的分析,可以看出元好问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独特见解和深刻思考,他的诗论观念和诗学理论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后世的诗歌批评理论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解析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蕴含的诗歌理念解析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蕴含的诗歌理念解非第一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赏析:元好问认为汉乐府民歌与建安诗歌是对《诗经》的风雅传统“正体”继承与发扬,是值得借鉴与学习的,而宋金诗坛上“伪体”盛行,汉魏诗歌传统得不到弘扬,迫切需要有“诗中疏凿手”出世来正本清源,引领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
这“诗中疏凿手”就是我们今天的“诗评家”。
且由诗评家来分开泾水、渭水这样一清一浊的诗歌之流。
这组诗:论诗的动机、目的和标准。
第二首: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赏析:元好问用形象的比喻来推崇曹植和刘桢为建安诗人的“两雄”,诗歌风格“啸虎生风”,具有骨气奇高,真骨凌霜之美。
这也是肯定了风骨刚健、风神飘逸的建安文学的风骨论。
而西晋诗人刘琨的“雅壮而多风”和“清拔之气”(《诗品》)可比建安风骨。
这组诗:论诗歌的艺术风格。
第三首: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若何。
赏析:元好问认为建安文风西晋时期的诗人继承的很多,建安风骨的影响比较大,真的就是:“壮怀犹见缺壶歌”。
但是,诗歌绮靡文风也已经潜滋暗长了,他以张华为例子,指出张华的诗歌:“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钟嵘评张华诗语)以至于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更是儿女情长,风格婉约。
而这样的绮靡婉艳,文字妍冶的诗歌是不利于诗歌的发展的,虽然诗人的名气高,也不过一时罢了,缺乏豪壮慷慨之气的诗歌无建安的风骨,而风骨才是元好问所肯定的诗品,所以“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问对绮靡文风的强烈不满之情绪。
这组诗:论诗人的品格。
第四首: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赏析:这首诗是元好问评价陶渊明的,元好问崇尚陶渊明诗歌自然天成,无人工雕琢粉饰的痕迹,清新真淳而无矫揉造作诗风。
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诗句是那么的自然质朴,剥尽铅华,独见真率,具有真淳隽永、万古常新的诗艺魅力。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一)按前半两句谓:自汉魏迄今,诗体繁多,究竟谁是正体,谁是伪体,始终无人细加评论.后半二句谓:不知谁为凿通山川之巨手,能暂时判分诗坛之清浊.这是全诗之总起,以下所论,正为疏凿之内容.由诗意看来,元好问不但以「诗中疏凿手」自任,而且表明全诗之目的在彰显诗之正体,别裁诗之伪体.诗之正体,渊源甚远,就中国之诗歌源流言,《诗经》当为一切正体之源头.而元好问所论,则自汉、魏起.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二)按《诗品》序尝谓:「曹刘殆文章之圣.」这是元好问论诗由曹植、刘桢起的原因.《诗品》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论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故本诗前半两句谓曹植、刘桢坐啸诗坛,虎虎生风,四海之内众多俊才,竟无人能与相敌.后半两句谓:西晋永嘉时期,担任并州刺史的刘琨(越石),犹有汉魏风骨,可惜生之太晚,未能并列建安诗坛,和曹刘一起横槊赋诗.刘琨诗「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不但同为北人,其诗风且与元好问十分接近,因此得到元好问之推崇,可知他论诗以气骨为宗旨,赏识雄伟刚健之诗风.三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之三)本诗元好问〈自注〉曰:「锺嵘评张华诗,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可知是借《诗品》之论见出发.在元好问观念中,晋初之诗格高出齐、梁.故前半两句认为:建安诗坛之流风余韵,在晋朝仍留存甚多,以王敦为例即可概见晋人之壮怀.据《晋书王敦传》所载,王敦酒后好以如意敲击唾壶为节,吟咏曹操之乐府,往往击缺壶口.后半两句谓:张华之诗,往往巧用文字,托兴不高,似乎缺乏风云之气.然而,持其诗与晚唐时温庭筠、李商隐言情之作相比,又将为之奈何虽然本诗为张华开脱,其实仍旧主张作诗不宜「风云气少,儿女情多.」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之四)本诗元好问〈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在〈继愚轩和党承旨诗〉末章云:「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可知元氏激赏陶渊明.萧统〈陶集序〉谓渊明:「语事理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锺嵘《诗品》谓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苏轼谓:「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故元好问指出陶诗谓诗语自然却万古常新,繁华落尽而显现真淳.陶渊明之胸怀朗若白日,俨然羲皇上人.渊明的诗风如此真淳自然,虽生于晋朝,无伤其为淑世之人.本诗意在表彰陶诗之自然真淳,显示元好问以「气骨」为正体之外,亦以「天然」为正体.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之五)按《诗品》谓阮籍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宋严羽《沧浪诗话》:「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气骨.」本诗前半则指出诗人之所以用俶诡之诗笔,寄寓渊放之情怀.实因为已无其他东西能够浇平胸中之块垒.后半两句谓:以晋人之诗才来说,被世人视为狂诞的阮籍,实际并不狂.只是这种真况谁能领会阮籍之作风,一如黄庭坚(山谷)诗句所示:「面对横在面前之大江,纵声大笑.」只不过以傲视万物的姿态发为旷放的吟咏而已.这是论「旷放」的诗风,和「气骨」,「天然」同为元好问最欣赏的正体.阮籍处身乱世,为保全性命,故作狂诞,逾越礼教,他的诗俶诡不羁,兴寄无端,其实是寄托无限的沉痛和难言的志节在其中.因此,阮籍的「旷放」,与曹刘的「气骨」,有其内在的共通性,皆为真情之流露.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之六)按扬雄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遗憾的是心声心画常常失真,因此,仅看表现于外的文章,岂能论断作者真实的人格后半两句指出晋人潘岳(安仁)当年写的《闲居赋》,显现高逸的情操,足以名垂千古;谁能相信他为了求官,见到贾谧出门,竟望着路尘而屈膝下拜呢此诗主要在讥讽潘岳文行不一,并指出文章本于性情,性情之真假,直接影响到文章品致之高低.此与《文心雕龙情采篇》云:「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所言,相互印证.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之七)按前半两句谓:汉魏歌谣中那种慷慨任气之风格,到了六朝已经断绝不传,只有北齐斛律金所唱之《敕勒歌》犹有此风.后半两句谓:大概是中原地区万古以来之英雄气慨,也传到阴山的敕勒川.本诗提及之《敕勒歌》原文如下:「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敕勒族旧有之歌谣,极为豪莽.本诗举一实例,用以说明北朝文学的特质.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论》曾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显然元好问赞赏北方文学之主于气质住豪壮,意在对照南方文学之流宕绮靡.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之八)按《新唐书》卷壹○七〈陈子昂传〉云:「唐初,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此为全诗之所本.元好问于唐初诗人,仅推崇陈子昂.此因沈佺期、宋之问纵横驰骋于诗坛,犹不能湔除齐、梁绮靡之风.必待陈子昂承接六代风会,绍继传统,独开新途,始振起一代诗风.故后半两句谓:若论唐诗恢复正体之功劳,应依句践平吴为范蠡铸像之往例,也为陈子昂铸一座黄金塑像,以表彰他追复汉魏风骨之功.本诗指出六朝绮靡之诗风,至唐初仍然存在,始变绮靡,恢复汉魏风骨,当推陈子昂.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之九)按前半两句谓:缀辞行文,斗靡夸多,徒增阅览之劳.以潘岳、陆机相较,陆机之文章,犹有较潘岳冗芜之遗憾.后半两句谓:诗文为心灵之声音,但能完整传述心意,目的已达.倘如布谷鸟之澜翻啼叫,岂有何难《世说新语文学》云:「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此当为本诗之所本.然全诗之主眼并不在比较潘、陆之诗文,而是就潘、陆以针砭晋、宋诸家诗文之斗靡夸多.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之十)按唐元稹于〈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之中,对杜甫诗之铺陈,排比、词气、风调、属对,深致赞叹之意.元好问则谓:铺陈终始,排比声律,但为诗歌创作之一途而已,推许杜甫,若局限于此,则其藩篱未免太窄.后半两句指出:杜甫自有旷世无匹之连城璧,怎奈元稹识见短浅,只识其中之碔砆杜诗之奥妙,元好问在《杜诗学引》已有说明,此诗重申杜诗为诗中之集大成,要妙难言,即如元稹,亦不能识.继前诗针砭晋、宋诸家之「斗靡夸多」,本诗又间接指斥「排比铺张」.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之十一)前半两句谓:眼目所及,必生心象,就此心象以文句表达,自能传神.若未亲临其境,只是暗中摸索,总是无法写真.清人查初白所谓:「见得真,方道得出.」正是此意.后半两句谓:杜甫在长安,秦川景物尽入题咏,真切入神,恰似张张摩写出来的《秦川图》,只是,像杜甫这样亲到长安,身历其境,刻划写真的诗人,古来能有几人.本诗指出诗歌写作,贵在身临其境,亲自体验,方能传神写真.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十二)按前半两句谓:望帝的春心,托附在杜鹃鸟的悲鸣中;佳人的锦瑟,激起对逝去年华的怅惘.后半两句谓:晚唐诗人李商隐诗旨的难以明了,大体与此相类.而诗家总是喜爱西昆之美好,唯独遗憾的是无人像郑玄笺注《毛诗》般,一一阐述他的义旨.按所谓「西昆」,众说纷云.宋刘攽《中山诗话》云:「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宋释惠洪《冷斋夜话》云:「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辟晦,时号西昆体.」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本诗似乎沿袭释惠洪《冷斋夜话》之观点,视李商隐诗为「西昆体」,然其所论之重心,在李商隐诗「用事深僻」,以致「诗意晦涩」也.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庐.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之十三)玉川庐指中唐诗人卢仝.其诗以鬼怪趋险见称于后世.就元好问〈小亨集序〉来看,元氏对于鬼怪一派,必然深恶痛绝.因此前半两句指出:自古以来,诗文创作皆有正当途径,谁像卢仝那样,恣意运笔,险怪作诗呢后半两句谓:正规的诗像楷书,往往不能让今人看入眼;别寻险径的怪诗,好比小孩涂鸦,有时反而受到世人之激赏.本诗旨在斥责卢仝诗,别寻险径、刻意鬼怪,实非诗之正途,不足为训.出处殊途听所安,山林何得贱衣冠.华歆一掷金随重,大是渠侬被眼谩.(之十四)按前半谓:人的出处进退,有种种不同,大抵听凭个性所安.幽居山林的人,那能贱视廊庙里的衣冠士呢后半两句谓:华歆见到片金,掷去不取,随即受到时人的尊重,其实不过伪装清高,以便求官觅侯.而那些崇敬华歆清高的人,结果都被自己的双眼所瞒骗.诗文之伪饰,正与此相类.这是对刻意作伪之指责.前论潘岳之「言行不符」,此则更进一步论「刻意作伪」之失,拈出华歆之故事,目的不在批判华歆之人品,而是借此说明诗歌创作不能作伪.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世间东抹西涂手,枉著书生待鲁连.(之十五)按前半两句谓:李白诗笔洒落,境格旷远,正如其诗所示:「好比银河洒落九天.」何尝作过「饭颗山前」讥诮杜甫之劣诗后半两句谓:世间还有一些东抹西涂的论者,批评李白在中原扰扰之际,欲借永王璘之力量以建奇功.这又一种书生功利之见,诬枉像鲁仲连这一流的高士.本诗评论李白诗境格旷远.世俗失察,竟以不实之作相诬,书生功利之见相枉.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之十六)按前半两句谓:自古抒哀伤之情,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写苦境之作,亦若灯前山鬼之落泪.实因哀苦易于撼动人心,比较讨好.此盖针对晚唐李贺所作之评论.后半两句谓:像太湖春景的朗丽,就鲜少有人能写得好,只有李白:「岸夹桃花锦浪生」,堪称古今独步.此又进一步引李白诗为例,暗示李贺「幽冷哀激」之诗格,不及李白之「高华俊伟」也.切响浮声发巧深,研磨虽苦果何心;浪翁《水乐》无宫征,自是云山《韶》,《濩》音.(之十七)按前半两句谓:沈约「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之说,的确深入发掘诗歌声律的奥秘,其研究创发之工夫,固然应予肯定,但是,这种人为声律果真值得用心吗后半两句谓:试看唐元结《水乐说》:本无宫征之音响,却也自成云山间自然的雅乐.这是元好问反对人为声律之主张,因为他论诗主天然,诗歌中本有天然的声调,比起人为刻意之声律,更为可贵.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之十八)按前半两句谓:孟郊喜欢以穷困愁苦作为诗歌题材,至死如此.处身在高天厚地之间,却自囿于苦吟,不啻诗中囚徒.后半两句谓:试看韩愈自潮州还朝后之文章,与江山同其不朽.韩孟相比,韩愈应居陈元龙高卧的百尺楼上,高下岂可同日而语本诗指出韩、孟虽齐名,孟郊之穷愁实不堪与韩愈雄奇相提并论.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何如.万古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何如.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之十九)按本诗前半谓:万古以来,不知多少高士幽居涧阿,未能显扬于世.其一生的孤愤,如何抒解唐代诗人陆龟蒙〈自遣诗〉云:「无多药圃在南荣,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随春草斗输赢.」曾以名品药草和一般青草作喻,谓稚子不知珍惜,恐将明品药草持与一般春草共斗输赢.后半二句惋惜无人告知陆龟蒙:诗之品秩何独不然高低之比较,能有几多差别亦惟务实略名而已.本诗指出诗名之高下,无关乎诗之实质.如陶诗不为六朝人所贵,却大重于后代,即为实真名虚之例证.是以高人才士,励品为诗,应以实质为重,无须措意于声名品秩之高低.谢客风容动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之二十)元好问自注:「柳子厚,宋之谢灵运.」前半两句谓:谢诗之风神,映照古今.渊源于谢灵运之诗人很多,然而谁能比柳宗元所得更为深切呢以柳诗接谢诗,清人查初白誉为「千古特识.」又谢灵运〈斋中读书诗〉前四句云:「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最能突显谢客之心境.而柳宗元自王叔文党失势,贬邰州、永州、柳州,窜逐荒疠,自放山泽,悲恻抑郁,一寓于山水诗文.其寂寞不遇,实与谢灵运相同.故后半两句谓:柳诗正如拂动朱弦的瑟,一唱三叹的遗音彷佛犹在.这种冷寂的诗境,正象征谢灵运当年的心境.窘步相仍死不前,唱无复见前贤.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之二十一)按前半两句谓:作诗若窘束步履,一仍旧贯,至死不敢超越,就如后世的唱之作,见识不到前贤作诗的真性情.后半两句谓:作诗应秉持凌云之笔自创新格,若只能俯仰步趋,那也未免太可怜了.本诗指出诗人应自创新格,不当窘步因袭.都穆《南濠诗话》云:「东坡云: 诗须有为而作. 山谷云: 诗文惟不造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 予谓今人之诗惟务应酬,无怪其语之不工.」古人和诗,初不拘体制,后有「用其韵」,「次其韵」,雕镂过甚,扭曲性情,毫无情趣可言.由此可知,本诗旨在讥议宋人唱之风.皮述民先生另有一说,认为是论宋初西昆馆阁诸公。
94美学2021/02生于金元易代之际的元好问,是北方文坛的代表人物。
其诗作《论诗三十首》以“以诗论诗”的形式,比较全面地表达了其诗学主张。
“以诗论诗”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形式,诗人借助诗歌这一载体来评点其他诗人及诗作,从而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
本文以《论诗三十首》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元好问的诗学主张。
一、推《诗经》之风雅,崇建安之风骨元好问写作这组论诗诗的缘由、标准以及目的,可以在《论诗三十首》中的前两首里找到答案。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针对宋金诗歌的某些弊病以及“伪体”盛行的现象,诗人从《论诗三十首》看元好问的诗学主张文/王欢欢摘 要:《论诗三十首》是中国古代论诗诗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通过“以诗论诗”的形式,比较全面地表明了其诗学主张。
即推崇风雅精神和建安风骨,欣赏诗歌自然天成、不假修饰,提倡写诗要表达真情实感等。
在诗歌的语言、内容、手法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探讨《论诗三十首》对研究元好问其人及其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诗学主张的观念以及王自称为“天子”这一做法虽出自周代,但据此断其为“宋诗”亦是武断。
从后人改诗的传统来看,改诗的一大原因是为了方便读诗。
《商颂》文辞优美,但无后世“德”“孝”之观念掺杂其中,可见其有一层“抵制”改诗传统的屏障,若真创于殷商,这层屏障又何以存在?故而,若以当下之所存断其为“商诗”,至少存在以上三个疑问。
参考文献:[1]刘波.《诗经·商颂》创作年代考述[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2]朱志荣.商代审美意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王振复,陈立群,张艳艳.中国美学范畴史(第一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4]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212.[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562.[6]晁福林.说商代的“天”和“帝”[J].史学集刊,2016(3):130-146.[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9.[9]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06.[10]程颐,撰.孙劲松,范云飞,何瑞麟,译注.周易程氏译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824.作者简介:柯利强,广西师范大学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元好问诗学简论
一、诗学的本质
诗学是研究诗歌艺术的学科,它的本质是研究诗歌的美学内涵和文学形式。
简言之,诗学是研究诗歌的美学和审美学。
二、诗学的价值
诗歌是一种更接近自然的形式,它可以抒发人类生活中的情感,引发人类思想的激荡,丰富人们的审美观,同时也可以使人收获更多的精神财富。
它可以唤起人们许多对生活的思考和审视。
诗学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让人们从诗歌当中挖掘出精神上的意义和价值。
三、诗学的研究
诗学主要围绕诗歌的形式、内容、角度和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断探索诗歌的传统和创新。
它从生活的角度探究诗歌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美学内涵,开发出新的创作路径和审美观念。
从《论诗三十首》看元好问诗歌创作主张从《论诗三十首》看元好问诗歌创作主张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是金元时代重要的论诗诗。
元好问(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
金兴定五年进士,曾为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官。
金亡不仕。
编金人诗为《中州集》(十卷),有《遗山集》(四十卷),《金史》卷一二六《文艺》有传。
是金、元二代最杰出的诗人。
以绝句诗的形式论述诗歌创作和理论问题,即所谓的“论诗诗”,滥觞於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这以后各种形式的“论诗诗”风行起来,韩愈的《调张籍》、戴复古的《论诗十绝》,直至清代的钱谦益、王士祯、袁枚、赵执信、赵翼、近代丘逢甲、柳亚子、陈衍等等,作者很多,数量极大。
从内容方面说,有阐述诗歌理论的,有偏重于作家作品品评的。
唐以后,“论诗诗”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于:作为金代的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对我国诗歌创作在唐以后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本清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诗三十首》之作,很明显地继承了杜甫《戏为六绝句》的精神。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最后一首的结尾,曾经提出过“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著名主张。
“伪体”即以《诗经》《风》《雅》为代表的正体之反。
杜甫提出这一主张,是针对当时诗坛的齐梁遗风而言。
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元好问,在宋诗的流弊影响着金代诗坛的情况下,以当年杜甫所进行的“别裁伪体”为己任,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诗中疏凿手”。
这正如《论诗三十首》(以下简称《论诗》)开宗明文所说的:“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诗是问的语气,实则以“疏凿手”自居。
“汉谣魏什”,泛指汉魏风骨的诗,“久纷纭”,即久纷乱,在后代逐渐失去了它的优良传统。
《论诗》中的每一首虽然所论各异,或正面的提倡,或反面的批评,都体现着一个鲜明的纲领,即力图恢复汉魏以后以至杜甫所代表的“正体”的优良文学传统,不赞成和批评以后诗歌发展中所出现的“伪体”。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美学理想探析清代学者章学诚论及北宋以后南宋与金对峙局面时曾说:“当日程学盛行于南,苏学盛于北。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第九条)程学指理学,由杨时、尹敦传入南宋,朱熹后来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后来影响巨大的程朱学派。
苏学指诗、文,它经由金朝著名的文学家如蔡松年,赵秉文等继承和传播,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
正是在金朝这样的文化传统的熏染下,有着鲜卑豪放血统的元好问,又受北方雄健民风的影响,其“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
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语。
”(徐世隆《遗山新生集序》)“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
”(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同时,元好问又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理论。
在二十八岁时,他作《论诗三十首》。
受东方审美意识特有的古朴性、神秘性和感悟性影响,这些诗论体现着中国古代文论所具的民族特色:一是着眼于文学作品对读者产生的直接效果。
再者,受人物评品的影响,它们不是出于理智的分析批判而是出于直观想象;不是借助于抽象的概括而是诉诸具体的形象。
就以诗论诗的形式而言,元好问效法杜甫。
杜甫曾作《戏为六绝句》,为其滥觞。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的规模较杜扩展了五倍,其范围上至汉魏,下迄唐宋,著名的诗人多有涉猎,且三十绝句有机排列,自称机杼,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语言雅畅。
就其诗论所体现的美学理想而言,其诗美的纲领在“真”、在“天然”。
这种美学理想源于元好问的庄佛思想。
道家推崇“道”,认为道先天地而生,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天地间万物荣枯,众生生息,无不以道为转移。
道,只任万物依照自己天然的本性而生而灭,此即为“无为”。
人若为着某种执着而干扰客观物体,必然破坏客体天然的个性,同时也相应的使自己受累而破坏主体天然的个性,此即“有为”。
庄子的齐物论主张齐一自由,追求天然美或“真”,认为,道之所在即美之所在,得道之人便是最自由的人,便是美。
“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
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