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丹溪治痰
- 格式:doc
- 大小:29.5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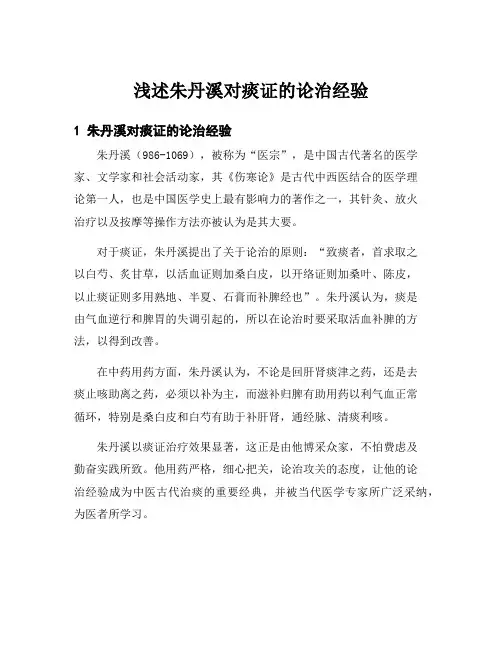
浅述朱丹溪对痰证的论治经验
1 朱丹溪对痰证的论治经验
朱丹溪(986-1069),被称为“医宗”,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伤寒论》是古代中西医结合的医学理
论第一人,也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其针灸、放火
治疗以及按摩等操作方法亦被认为是其大要。
对于痰证,朱丹溪提出了关于论治的原则:“致痰者,首求取之
以白芍、炙甘草,以活血证则加桑白皮,以开络证则加桑叶、陈皮,
以止痰证则多用熟地、半夏、石膏而补脾经也”。
朱丹溪认为,痰是
由气血逆行和脾胃的失调引起的,所以在论治时要采取活血补脾的方法,以得到改善。
在中药用药方面,朱丹溪认为,不论是回肝肾痰津之药,还是去
痰止咳助离之药,必须以补为主,而滋补归脾有助用药以利气血正常
循环,特别是桑白皮和白芍有助于补肝肾,通经脉、清痰利咳。
朱丹溪以痰证治疗效果显著,这正是由他博采众家,不怕费虑及
勤奋实践所致。
他用药严格,细心把关,论治攻关的态度,让他的论
治经验成为中医古代治痰的重要经典,并被当代医学专家所广泛采纳,为医者所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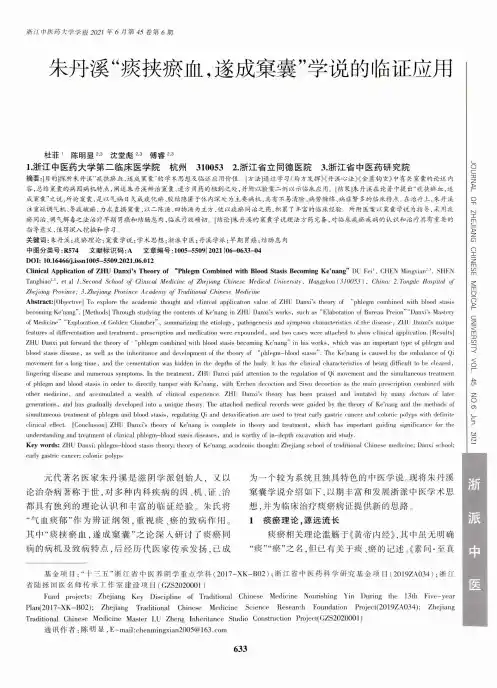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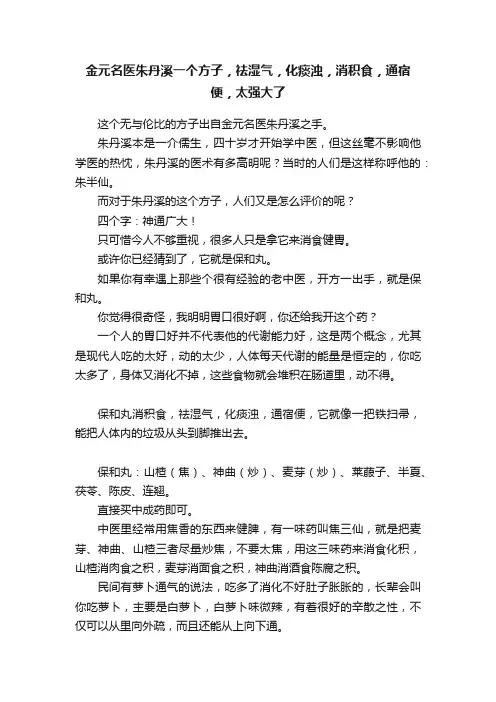
金元名医朱丹溪一个方子,祛湿气,化痰浊,消积食,通宿便,太强大了这个无与伦比的方子出自金元名医朱丹溪之手。
朱丹溪本是一介儒生,四十岁才开始学中医,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学医的热忱,朱丹溪的医术有多高明呢?当时的人们是这样称呼他的:朱半仙。
而对于朱丹溪的这个方子,人们又是怎么评价的呢?四个字:神通广大!只可惜今人不够重视,很多人只是拿它来消食健胃。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它就是保和丸。
如果你有幸遇上那些个很有经验的老中医,开方一出手,就是保和丸。
你觉得很奇怪,我明明胃口很好啊,你还给我开这个药?一个人的胃口好并不代表他的代谢能力好,这是两个概念,尤其是现代人吃的太好,动的太少,人体每天代谢的能量是恒定的,你吃太多了,身体又消化不掉,这些食物就会堆积在肠道里,动不得。
保和丸消积食,祛湿气,化痰浊,通宿便,它就像一把铁扫帚,能把人体内的垃圾从头到脚推出去。
保和丸:山楂(焦)、神曲(炒)、麦芽(炒)、莱菔子、半夏、茯苓、陈皮、连翘。
直接买中成药即可。
中医里经常用焦香的东西来健脾,有一味药叫焦三仙,就是把麦芽、神曲、山楂三者尽量炒焦,不要太焦,用这三味药来消食化积,山楂消肉食之积,麦芽消面食之积,神曲消酒食陈腐之积。
民间有萝卜通气的说法,吃多了消化不好肚子胀胀的,长辈会叫你吃萝卜,主要是白萝卜,白萝卜味微辣,有着很好的辛散之性,不仅可以从里向外疏,而且还能从上向下通。
而白萝卜的种子,也叫莱菔子,与萝卜有相同的物性,但因其精小,所以药性更强。
萝卜子下气,焦三仙消食,加在一起能把身体里各种各样的积滞都化掉。
朱丹溪用药有理有法,又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这个方子可不是到了消食导滞这一步就结束了。
朱丹溪呢,想的更周到更全面,他想到了食积会阻气、生痰,所以加了半夏、陈皮和茯苓。
陈皮,气味特别清香,它就是靠着这股香气去流通的,陈皮行气除胀是一把好手,有些人胃口总是胀气,想打嗝也打不出来,这时候陈皮就很适用。
陈皮行气,就像平静的水面上徐徐吹来的微风,可以使池水流动起来,它是温和又百搭的药物,如果少了陈皮这一味,很多中医大夫都不好开方子了,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协助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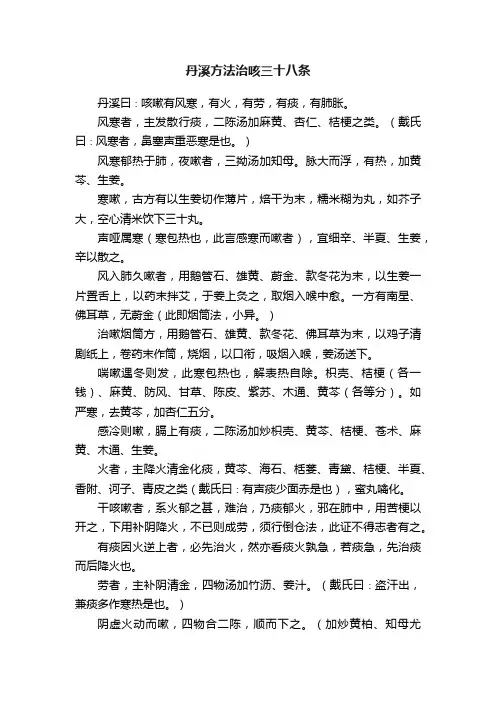
丹溪方法治咳三十八条丹溪曰∶咳嗽有风寒,有火,有劳,有痰,有肺胀。
风寒者,主发散行痰,二陈汤加麻黄、杏仁、桔梗之类。
(戴氏曰∶风寒者,鼻塞声重恶寒是也。
)风寒郁热于肺,夜嗽者,三拗汤加知母。
脉大而浮,有热,加黄芩、生姜。
寒嗽,古方有以生姜切作薄片,焙干为末,糯米糊为丸,如芥子大,空心清米饮下三十丸。
声哑属寒(寒包热也,此言感寒而嗽者),宜细辛、半夏、生姜,辛以散之。
风入肺久嗽者,用鹅管石、雄黄、蔚金、款冬花为末,以生姜一片置舌上,以药末拌艾,于姜上灸之,取烟入喉中愈。
一方有南星、佛耳草,无蔚金(此即烟筒法,小异。
)治嗽烟筒方,用鹅管石、雄黄、款冬花、佛耳草为末,以鸡子清剧纸上,卷药末作筒,烧烟,以口衔,吸烟入喉,姜汤送下。
喘嗽遇冬则发,此寒包热也,解表热自除。
枳壳、桔梗(各一钱)、麻黄、防风、甘草、陈皮、紫苏、木通、黄芩(各等分)。
如严寒,去黄芩,加杏仁五分。
感冷则嗽,膈上有痰,二陈汤加炒枳壳、黄芩、桔梗、苍术、麻黄、木通、生姜。
火者,主降火清金化痰,黄芩、海石、栝蒌、青黛、桔梗、半夏、香附、诃子、青皮之类(戴氏曰∶有声痰少面赤是也),蜜丸噙化。
干咳嗽者,系火郁之甚,难治,乃痰郁火,邪在肺中,用苦梗以开之,下用补阴降火,不已则成劳,须行倒仓法,此证不得志者有之。
有痰因火逆上者,必先治火,然亦看痰火孰急,若痰急,先治痰而后降火也。
劳者,主补阴清金,四物汤加竹沥、姜汁。
(戴氏曰∶盗汗出,兼痰多作寒热是也。
)阴虚火动而嗽,四物合二陈,顺而下之。
(加炒黄柏、知母尤佳。
)阴虚喘嗽或吐红者,四物汤加知母、黄柏、五味子、人参、麦门冬、桑白皮、地骨皮。
好色之人,元气虚弱,咳嗽不愈,琼玉膏最捷。
肺虚甚者,人参膏以生姜、陈皮佐之,有痰加痰药,此好色肾虚者有之。
久嗽、劳嗽,用贝母、知母各一两,以巴豆同炒黄色,去巴豆,再用白矾、白芨各一两为末,以生姜一片蘸药,睡时噙化,药尽嚼姜咽之。
麦门冬、陈皮、阿胶珠各等分,蜜丸噙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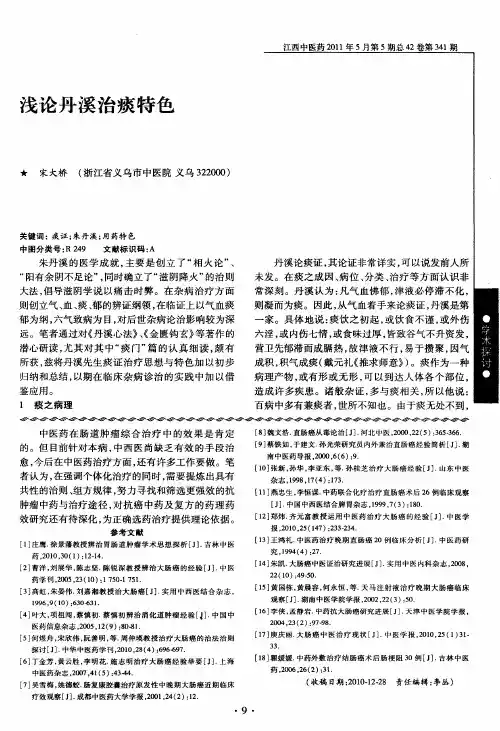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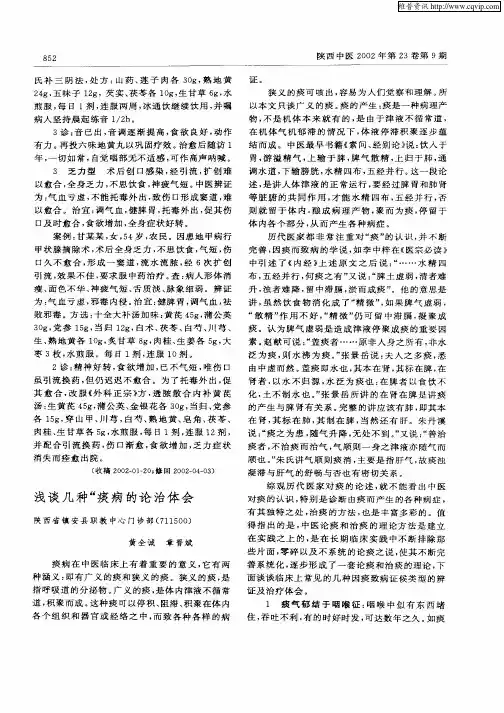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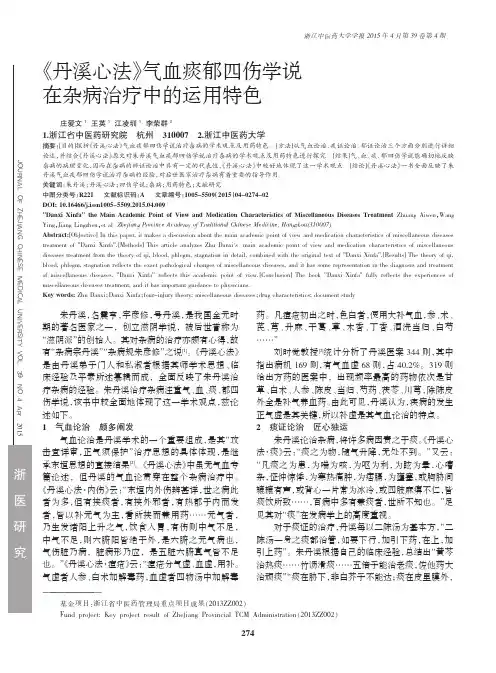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年4月第39卷第4期朱丹溪,名震亨,字彦修,号丹溪,是我国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之一,创立滋阴学说,被后世誉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
其对杂病的治疗亦颇有心得,故有“杂病宗丹溪”“杂病规朱彦修”之说[1]。
《丹溪心法》是由丹溪弟子门人和私淑者根据其师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及平素所述纂辑而成,全面反映了朱丹溪治疗杂病的经验。
朱丹溪治疗杂病注重气、血、痰、郁四伤学说,该书中较全面地体现了这一学术观点,兹论述如下。
1气血论治颇多阐发气血论治是丹溪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是其“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治疗思想的具体体现,是继承东垣思想的直接结果[2]。
《丹溪心法》中虽无气血专篇论述,但丹溪的气血论贯穿在整个杂病治疗中。
《丹溪心法·内伤》云:“东垣内外伤辨甚详,世之病此者为多,但有挟痰者,有挟外邪者,有热郁于内而发者,皆以补元气为主,看所挟而兼用药……元气者,乃生发诸阳上升之气,饮食入胃,有伤则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则六腑阳皆绝于外,是六腑之元气病也,气伤脏乃病,脏病形乃应,是五脏六腑真气皆不足也。
”《丹溪心法·痘疮》云:“痘疮分气虚、血虚,用补。
气虚者人参、白术加解毒药,血虚者四物汤中加解毒药。
凡痘疮初出之时,色白者,便用大补气血,参、术、芪、芎、升麻、干葛、草、木香、丁香、酒洗当归、白芍……”刘时觉教授[2]统计分析了丹溪医案344则,其中指出病机169则,有气血虚68则,占40.2%。
319则给出方药的医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药物依次是甘草、白术、人参、陈皮、当归、芍药、茯苓、川芎,除陈皮外全是补气养血药。
由此可见,丹溪认为,疾病的发生正气虚是其关键,所以补虚是其气血论治的特点。
2痰证论治匠心独运朱丹溪论治杂病,将许多病因责之于痰。
《丹溪心法·痰》云:“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
”又云:“凡痰之为患,为喘为咳,为呕为利,为眩为晕,心嘈杂,怔忡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皆痰饮所致……,百病中多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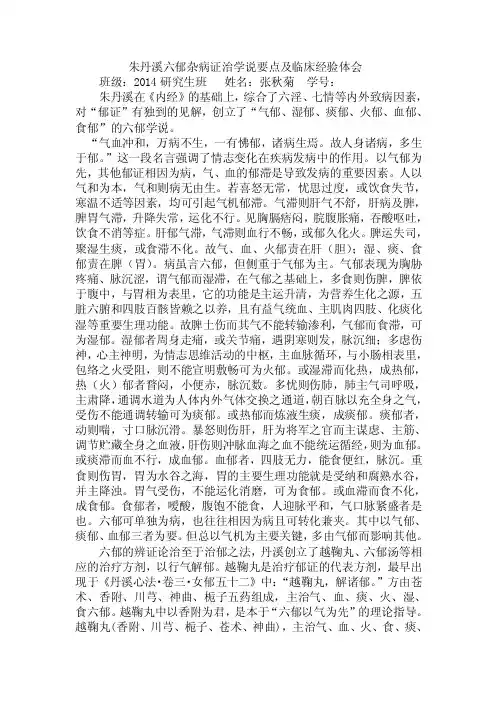
朱丹溪六郁杂病证治学说要点及临床经验体会班级:2014研究生班姓名:张秋菊学号:朱丹溪在《内经》的基础上,综合了六淫、七情等内外致病因素,对“郁证”有独到的见解,创立了“气郁、湿郁、痰郁、火郁、血郁、食郁”的六郁学说。
“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
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
”这一段名言强调了情志变化在疾病发病中的作用。
以气郁为先,其他郁证相因为病,气、血的郁滞是导致发病的重要因素。
人以气和为本,气和则病无由生。
若喜怒无常,忧思过度,或饮食失节,寒温不适等因素,均可引起气机郁滞。
气滞则肝气不舒,肝病及脾,脾胃气滞,升降失常,运化不行。
见胸膈痞闷,脘腹胀痛,吞酸呕吐,饮食不消等症。
肝郁气滞,气滞则血行不畅,或郁久化火。
脾运失司,聚湿生痰,或食滞不化。
故气、血、火郁责在肝(胆);湿、痰、食郁责在脾(胃)。
病虽言六郁,但侧重于气郁为主。
气郁表现为胸胁疼痛、脉沉涩,谓气郁而湿滞,在气郁之基础上,多食则伤脾,脾依于腹中,与胃相为表里,它的功能是主运升清,为营养生化之源,五脏六腑和四肢百骸皆赖之以养,且有益气统血、主肌肉四肢、化痰化湿等重要生理功能。
故脾土伤而其气不能转输渗利,气郁而食滞,可为湿郁。
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多虑伤神,心主神明,为情志思维活动的中枢,主血脉循环,与小肠相表里,包络之火受阻,则不能宣明敷畅可为火郁。
或湿滞而化热,成热郁,热(火)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数。
多忧则伤肺,肺主气司呼吸,主肃降,通调水道为人体内外气体交换之通道,朝百脉以充全身之气,受伤不能通调转输可为痰郁。
或热郁而炼液生痰,成痰郁。
痰郁者,动则喘,寸口脉沉滑。
暴怒则伤肝,肝为将军之官而主谋虑、主筋、调节贮藏全身之血液,肝伤则冲脉血海之血不能统运循经,则为血郁。
或痰滞而血不行,成血郁。
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
重食则伤胃,胃为水谷之海,胃的主要生理功能就是受纳和腐熟水谷,并主降浊。
胃气受伤,不能运化消磨,可为食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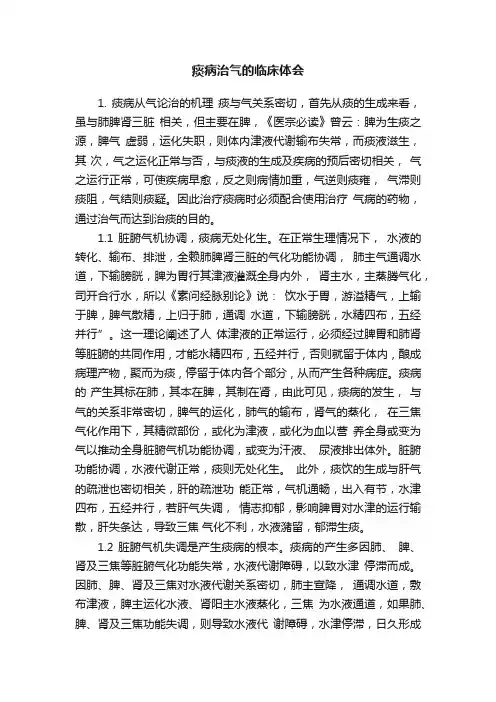
痰病治气的临床体会1. 痰病从气论治的机理痰与气关系密切,首先从痰的生成来看,虽与肺脾肾三脏相关,但主要在脾,《医宗必读》曾云:脾为生痰之源,脾气虚弱,运化失职,则体内津液代谢输布失常,而痰液滋生,其次,气之运化正常与否,与痰液的生成及疾病的预后密切相关,气之运行正常,可使疾病早愈,反之则病情加重,气逆则痰雍,气滞则痰阻,气结则痰疑。
因此治疗痰病时必须配合使用治疗气病的药物,通过治气而达到治痰的目的。
1.1 脏腑气机协调,痰病无处化生。
在正常生理情况下,水液的转化、输布、排泄,全赖肺脾肾三脏的气化功能协调,肺主气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脾为胃行其津液灌溉全身内外,肾主水,主蒸腾气化,司开合行水,所以《素问经脉别论》说:饮水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这一理论阐述了人体津液的正常运行,必须经过脾胃和肺肾等脏腑的共同作用 , 才能水精四布 , 五经并行 , 否则就留于体内 , 酿成病理产物 , 聚而为痰 , 停留于体内各个部分 , 从而产生各种病症。
痰病的产生其标在肺,其本在脾,其制在肾,由此可见,痰病的发生,与气的关系非常密切,脾气的运化,肺气的输布,肾气的蒸化,在三焦气化作用下,其精微部份,或化为津液,或化为血以营养全身或变为气以推动全身脏腑气机功能协调,或变为汗液、尿液排出体外。
脏腑功能协调,水液代谢正常,痰则无处化生。
此外,痰饮的生成与肝气的疏泄也密切相关,肝的疏泄功能正常,气机通畅,出入有节,水津四布,五经并行,若肝气失调,情志抑郁,影响脾胃对水津的运行输散,肝失条达,导致三焦气化不利,水液潴留,郁滞生痰。
1.2 脏腑气机失调是产生痰病的根本。
痰病的产生多因肺、脾、肾及三焦等脏腑气化功能失常,水液代谢障碍,以致水津停滞而成。
因肺、脾、肾及三焦对水液代谢关系密切,肺主宣降,通调水道,敷布津液,脾主运化水液、肾阳主水液蒸化,三焦为水液通道,如果肺、脾、肾及三焦功能失调,则导致水液代谢障碍,水津停滞,日久形成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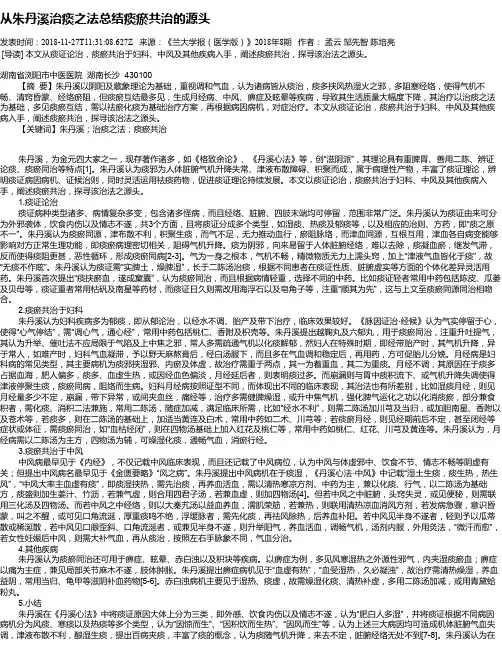
从朱丹溪治痰之法总结痰瘀共治的源头发表时间:2018-11-27T11:31:08.627Z 来源:《兰大学报(医学版)》2018年8期作者:孟云邹先智陈培亮[导读] 本文从痰证论治,痰瘀共治于妇科、中风及其他疾病入手,阐述痰瘀共治,探寻该治法之源头。
湖南省浏阳市中医医院湖南长沙 430100【摘要】朱丹溪以阴阳及藏象理论为基础,重视调和气血,认为诸病皆从痰治,痰多挟风热湿火之邪,多阻塞经络,使得气机不畅、清窍昏蒙、经络瘀阻,但痰瘀互结最多见,生成月经病、中风、痹症及眩晕等疾病,导致其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其治疗以治痰之法为基础,多见痰瘀互结,需以祛瘀化痰为基础治疗方案,再根据病因病机,对症治疗。
本文从痰证论治,痰瘀共治于妇科、中风及其他疾病入手,阐述痰瘀共治,探寻该治法之源头。
【关键词】朱丹溪;治痰之法;痰瘀共治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现存著作诸多,如《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创“滋阴派”,其理论具有重脾胃、善用二陈、辨证论痰、痰瘀同治等特点[1]。
朱丹溪认为痰邪为人体脏腑气机升降失常、津液布散障碍、积聚而成,属于病理性产物,丰富了痰证理论,辨明痰证病因病机、证候治则,同时灵活运用祛痰药物,促进痰证理论持续发展。
本文以痰证论治,痰瘀共治于妇科、中风及其他疾病入手,阐述痰瘀共治,探寻该治法之源头。
1.痰证论治痰证病种类型诸多、病情复杂多变,包含诸多怪病,而且经络、脏腑、四肢末端均可停留,范围非常广泛。
朱丹溪认为痰证由来可分为外邪袭体,饮食内伤以及情志不遂,共3个方面,且将痰证分成多个类型,如湿痰、热痰及郁痰等,以及相应的治则、方药,即“痰之原不一”。
朱丹溪认为痰瘀同源,津布散不利,积聚生痰,而气不足,无力推动血行,瘀阻脉络,而津血同源,互根互用,津血各自病变能够影响对方正常生理功能,即痰瘀病理密切相关,阻碍气机升降。
痰为阴邪,向来易留于人体脏腑经络,难以去除,痰凝血瘀,继发气滞,反而使得痰阻更甚,恶性循环,形成痰瘀同病[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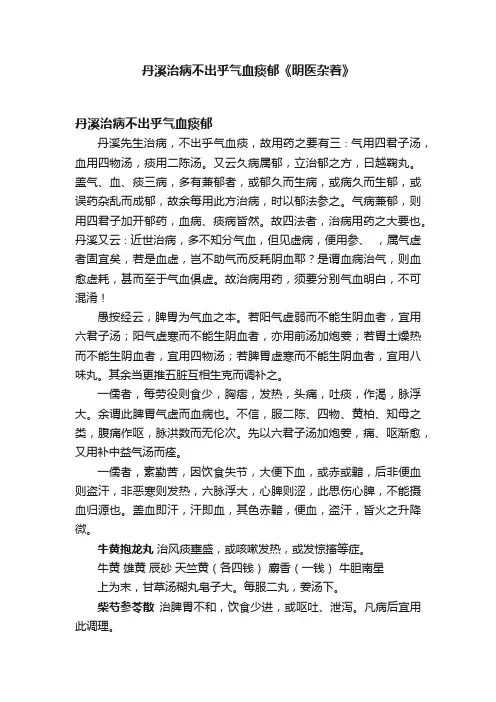
丹溪治病不出乎气血痰郁《明医杂着》丹溪治病不出乎气血痰郁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
又云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
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余每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参之。
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加开郁药,血病、痰病皆然。
故四法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
丹溪又云∶近世治病,多不知分气血,但见虚病,便用参、,属气虚者固宜矣,若是血虚,岂不助气而反耗阴血耶?是谓血病治气,则血愈虚耗,甚而至于气血俱虚。
故治病用药,须要分别气血明白,不可混淆!愚按经云,脾胃为气血之本。
若阳气虚弱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六君子汤;阳气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亦用前汤加炮姜;若胃土燥热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四物汤;若脾胃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八味丸。
其余当更推五脏互相生克而调补之。
一儒者,每劳役则食少,胸痞,发热,头痛,吐痰,作渴,脉浮大。
余谓此脾胃气虚而血病也。
不信,服二陈、四物、黄柏、知母之类,腹痛作呕,脉洪数而无伦次。
先以六君子汤加炮姜,痛、呕渐愈,又用补中益气汤而痊。
一儒者,素勤苦,因饮食失节,大便下血,或赤或黯,后非便血则盗汗,非恶寒则发热,六脉浮大,心脾则涩,此思伤心脾,不能摄血归源也。
盖血即汗,汗即血,其色赤黯,便血,盗汗,皆火之升降微。
牛黄抱龙丸治风痰壅盛,或咳嗽发热,或发惊搐等症。
牛黄雄黄辰砂天竺黄(各四钱)麝香(一钱)牛胆南星上为末,甘草汤糊丸皂子大。
每服二丸,姜汤下。
柴芍参苓散治脾胃不和,饮食少进,或呕吐、泄泻。
凡病后宜用此调理。
柴胡芍药人参白术茯苓陈皮当归(各五分)甘草丹皮山栀(炒,各三分)上为末,每服一钱,白汤下。
或作丸服。
五味子汤治咳嗽,皮肤干燥,唾中有血,胸膈疼痛等症。
五味子(炒)桔梗(炒)紫菀甘草(炒)续断(各五分)竹茹(一钱)赤小豆(一撮)生地黄(二钱)桑白皮(炒,二钱)上水煎服。
人参平肺散治心火克肺,咳嗽喘呕,痰涎壅盛,胸膈痞满。
丹溪学派诊治痰证的理论研究丹溪学派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医学流派之一,其学说对中医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
痰证是丹溪学派所的重点之一,本文旨在探讨丹溪学派诊治痰证的理论研究,为临床医生和研究者提供参考。
丹溪学派诊治痰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其代表人物朱丹溪创立了“痰致病”的理论。
他认为,痰是人体内水湿运化失常的产物,可引起多种疾病。
在朱丹溪的理论体系中,痰证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丹溪学派的痰证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丰富。
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丹溪学派诊治痰证的理论进行研究。
对丹溪学派诊治痰证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总结了其优点和不足。
从丹溪学派的学术思想、痰证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阐述了其中的逻辑和科学性。
同时,本研究也指出了丹溪学派诊治痰证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丹溪学派诊治痰证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痰致病”的理论和脏腑虚损、气化失常的病机。
其中,“痰致病”的理论认为,痰是人体内水湿运化失常的产物,可引起多种疾病,如咳嗽、哮喘、眩晕、癫痫等。
脏腑虚损、气化失常的病机则认为,痰证的病因主要包括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累过度等因素,这些因素可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化失常,进而产生痰。
在临床实践中,丹溪学派诊治痰证的方法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丹溪学派强调辨证论治,即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舌脉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其症候类型,然后根据不同的症候类型给予相应的治疗。
丹溪学派提出了系列行之有效的方剂,如治疗咳嗽的贝母瓜蒌散、治疗眩晕的二陈汤等。
丹溪学派还注重预防,强调通过调节饮食、加强锻炼等方式来预防痰证的发生。
然而,在实践中,丹溪学派诊治痰证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
由于痰证的病因复杂,病情多变,因此辨证论治的难度较大,需要医生具备较高的医学素养和临床经验。
丹溪学派的方剂多以草药为主,制备较为繁琐,给临床应用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虽然丹溪学派注重预防,但由于人们对医学知识的了解程度不同,往往难以有效地采取预防措施。
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导读:痰由多种原因而致,但总责之脏腑功能失调,气机升降失常。
所以治痰以治气为先,从补气、化气、理气、降气四着手,常可获较好的疗效,临证中诸多验案都说明了此理。
《丹溪心法》云:“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
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
”这里指出了理气化痰的重要意义。
我们在临证中遇到很多病证与痰有关,所以“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也就是说,治气是治疗痰证的关键一环。
痰与气关系密切痰是人体内的一种病理性产物,亦是一种致病物质,诸多疑难杂症每责之于痰,故有“怪病责之于痰”,“百病皆由痰作祟”之说。
《类证治裁》云:“饮唯停蓄肠胃,痰则随气升降,遍身皆到,在肺则咳,在胃则呕,在心则悸,在头则眩,……变幻百端,昔人所谓怪病多属痰,暴病多属火也。
”此处较详细地指出了痰饮随气升降引起的诸多病症。
其中治气一法,笔者以为能保持或恢复机体正常的气化功能,令全身之津液输布正常,是治痰的重要原则。
痰由多种原因而致,但随气病而生者较多。
在人体中,气属功能活动,痰乃水津所化。
在正常情况下,“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津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矣”。
若脏腑功能失调,水津不布,必致津液停蓄而生痰。
如肺气失宣,水不布散,则气壅为痰;肝气郁结,疏泄失职,则气滞成痰;脾失运化,水不转输,则水湿停聚,凝而成痰;肾气虚衰,蒸化失职,则水泛为痰;三焦壅滞,气化失司,则气结生痰。
《杂病广要》云:“人之一身,无非血气周流,痰亦随之。
夫痰者,津液之异也,流行于上,则为痰饮。
散周于下者,则为津液,其所以使之流行上下者,亦气使之然耳。
大抵气滞则痰壅,气行则痰行。
”又云“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一失其宜则气道壅塞,停饮聚于膈上,结而成痰。
”可见痰的产生无不与气有关。
气病可生痰,痰亦可阻气,两者互为因果。
如肺炎喘嗽患者,由于外邪袭肺,肺气失宣,津液不能敷布,停积为痰,而见咳喘,喉中痰鸣。
朱丹溪治痰知要李爽姿;王勤明【摘要】重点阐述金元四大家朱丹溪对痰证诊疗的独特见解.论痰治痰是朱丹溪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临床实践,他从整体上认识到在气、血、痰、郁四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由是论“痰”证时反复阐发、举例论证、立法稳妥.论“痰”之精要要在宏观的整体视角,认为临证治痰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审其所犯何邪,坚持从实际病情出发,先视标本缓急而后辨证施治;其治痰之要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至今在临床上仍有深刻影响.【期刊名称】《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年(卷),期】2015(021)006【总页数】2页(P646-647)【关键词】朱丹溪;痰病;论治【作者】李爽姿;王勤明【作者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222.15朱丹溪是治痰大家,论痰治痰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元以前,治痰不外吐、下、温等法。
朱丹溪却言:“大凡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下虚,则痰易生而多。
”批评了治病不求其本,专事汗、吐、下、温之弊并提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还提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之而顺矣。
”这些学术见解至今影响深远。
朱丹溪论“痰”有其精要之处。
“痰”为病理产物,其生成与气、血、津液有密切关系。
血与津液的正常运行全赖气的推动,气、血、津液一有阻塞即积痰成郁致病,所谓“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结则痰生,气畅则痰消”。
病因学说从《内经》始至宋·陈无择《三因方》止,似已成定论,将痰饮外归六淫、内归七情引起的阴阳气血失调,主要作为病而未作为因。
朱丹溪则将痰饮作为致病因素加以讨论,如“无痰则不能作眩”、“癫狂病……大概多因痰结心胸间”等,这种把痰饮作为体内致病因素的观点,冲破了宋元以前病因学说的框框。
尤其是针对中风病的论说,朱丹溪认为:“西北气寒,为风所中,或有之矣。
浅谈丹溪治痰
【关键词】朱丹溪
朱丹溪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其学说渊源于《内经》,并继承了刘完素、张从正、李杲诸家学术思想,因而,丹溪治医能发挥经旨,参合哲理,融合诸家,并能结合临床实践而创立新说。
丹溪学术虽以养阴为特色,但在临床上擅长于治疗气、血、痰、郁等杂病,临证每以气、血、痰、郁立论,尤其治痰更具特色,浅析如下,请同道指正。
临证识“痰”,独具慧眼
痰饮一证,前人论述其多,引戴思恭《推求师意·痰饮》中说:“至仲景分饮为四,一曰痰饮、二曰悬饮、三曰溢饮、四曰支饮。
而痰之义始见河间,分五运六气之病于火淫条下则云,中风、风癫等病……”
痰是一种病理产物,由津液不行,自积成痰。
凡情志忧郁、饮食厚味、外感无汗、滥用补剂,都可使气血失常,“清化为浊”,结为老痰宿饮。
其关键在于脾虚、湿滞、气郁、火炽。
丹溪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
认为其痰来去无定,聚散无常,五脏六腑莫不为患,或贮于肺,或贮于胃,或凝滞于心膈,或聚于肠间,或客于经络四肢等等,故丹溪临床诊疾,无不尽其从痰论证之能事。
如论热
痰,则多烦热,惊悸,结于咽喉为喉痹肿痛;结于胃中为呕吐,为嗳气,为嘈杂;若七情郁而生痰动火,随气上厥为眩晕,痰郁其火,于咳难治。
气痰随气机攻注走窜不定,阻于咽喉,如絮如膜,甚至如梅核,咽咯不去;滞于膈间,为气膈;积于胸腹为癥瘕积聚,为心腹块痛。
风痰多见奇证,上攻头目,为头痛,为眩晕,为目眶痛,流注经络,为肢节臂痛,为偏瘫。
湿痰倦怠软弱,体肥之人多有之,积于心下为痞,攻于头部为重痛;在腹为腹痛,为泄泻;注于下焦为白浊,为带下,为癫疝;流于经络为结核,或在顶、在颈、在臂、在身,其症不红不痛,不作脓;若妇人体胖饮食过度,经水不调者,乃是湿痰;惊痰多见疟痢口臭,痞块满闷;脾虚生痰,食不美,反胃呕吐等,皆痰之所为。
因此,痰病复杂,诸证多端,正如丹溪所说“百病之中多有兼痰”确是经验所得。
审因论治,贵在求本
痰病论治,历代医家多尊仲景“以温药和之”的原则,认为痰饮为阴邪,每多挟寒,非温不化。
丹溪认为“大凡治病用利药过多,致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
盖脾为后天之本,脾运不健,则津液不化,聚而成痰,正所谓脾为生痰之源,若脾健恒常,气顺津畅,湿不能聚,岂有成痰之理。
因而,丹溪提出“顺气为先,分导次之”的创见,所谓“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
认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也”。
所以主张以二陈汤
为准绳,成方活用,统治一身之痰证。
如清痰属寒,则宜温阳化痰,以二陈汤加温药;湿痰致痿者,加苍术健脾燥湿,芩、柏燥湿清郁热,竹沥入络行痰,颈项痰核,加柴胡、桔梗升提气机,加炒大黄、连翘清热通下。
湿痰下注,带下甚者,先以吐法提气,继以二陈加苍、白术健脾化痰;肥人湿痰闭塞胞宫,致经闭不行者,加南星、枳实破痰行郁,若郁而生热,再加川芎、黄连;内伤挟痰,则宜扶正化痰,如半身不遂,气虚痰阻者,二陈合四君子加竹沥;皮里膜外见痞块,气虚痰滞者,先予补气,香附开之,继用二陈加芪、参类调治;脾虚伤食,痰食相阻者,二陈加苍术、白术、山楂、川芎,以消积行气,开郁化痰;疟病久延,脾气伤者,二陈加苍术、川芎、柴胡、葛根;甚至妇女月色淡迟至,血虚痰郁者,亦用二陈加芎、归等出入化裁,曲尽其妙。
这种非见痰治痰,以治气为先的原则,正是反映了丹溪治痰重脾胃的良苦用心。
遣方用药,自成格局
丹溪用药治痰,品种不繁,但能药随证转,机动灵活。
他根据痰的不同属性,各拟主方,自成格局。
如湿痰用二陈汤;气热者用清礞石丸;气滞湿热郁甚者用参萸丸、苍妙丸;湿痰气热用中和丸,或抑痰丸、黄连化痰丸;热痰用润下丸;上焦积热用三补丸;中焦热痰,用清痰丸;膈间热痰,用清膈化痰丸;风痰用千缗汤;食积痰用黄瓜蒌丸。
食积痰兼阴虚者,取川芎、黄连、瓜蒌仁、白术、神曲、麦芽、青黛、
人中白研末姜汁蒸饼为丸服;兼火郁者,选贝母、知母、巴豆制丸等等。
丹溪治痰,除按湿、热、食积、风痰辨证选方外,也总结了不少有特殊功效的药物,如湿痰用苍术、白术;热痰用青黛、黄芩、黄连;食积痰用神曲、麦芽、山楂;风痰用南星、白附子、天麻、僵蚕、猪牙皂角之类;老痰用海石、半夏、瓜蒌、香附、五倍子;滑痰用竹沥;酒痰用青黛;郁痰用僵蚕、杏仁、瓜蒌、诃子、贝母治之。
他还指出: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达;痰在皮里膜外,非姜汁、竹沥不可导达;痰在四肢非竹沥不开,非姜汁不能行经络;痰结核在咽喉中,燥不能出入,用化痰药加咸药软坚之味。
凡此种种,足见丹溪辨治痰证、遣方用药的娴熟功力。
痰瘀并施,去菀陈莝
《内经》对“痰瘀相关”的理论早有记载,但未明确提出“痰瘀同治”。
丹溪对痰瘀关系较前人更为注重,首先提出“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挟瘀血,遂成窠囊”的论点,主张痰瘀同治。
如论中风,丹溪云:“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治痰为先,次养血治血。
”“若不先顺气化痰,遂用乌、附,又不活血,徒用防风、天麻、羌活辈,吾未见能治也。
”尤其对中风出现半身不遂,他主张“以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竹沥、姜汁”治之,这一认识对后世医家治疗中风影响很大。
论臌胀,丹溪认为系脾土受伤,转运失职而气浊、血瘀、热留、湿阻,故治疗上主张用禹余粮丸合小温中丸化裁,以补气行湿,活血化瘀,脾虚用大剂人参、白术,佐以陈皮、茯苓、苍术之类,蓄血而胀者,则宜抵当丸下死血。
论噎膈,认为主要是污血在胃脘之口,气因郁而为痰或“怒甚血菀于上,积在膈内,碍气升降,久则血枯津耗,胃肠传运失习所致,宜养血祛瘀、润燥和胃,投韭汁牛乳饮治之。
”再如论治痰瘀肺胀,丹溪又用四物汤加桃仁、诃子、青皮、竹沥、姜汁之类。
治痰瘀、身痛、胁痛,用控涎丹加桃仁泥丸,并认为人体内外所生包块,皆是痰浊死血积聚而成,治疗积聚成块,择其痰瘀多寡而治,开创了痰瘀致病之说。
可见丹溪痰瘀同治的经验颇为丰富,很能启迪后人。
综上所述,丹溪治痰,巧思妙悟,匠心独具。
临床运用痰药,灵活不呆,颇具特色,以其创窠囊之说,痰瘀并施,确是自树一格,为后世取法者殊多,诚不愧为临床治痰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