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致肝损伤研究进展
- 格式:pdf
- 大小:1.51 MB
- 文档页数: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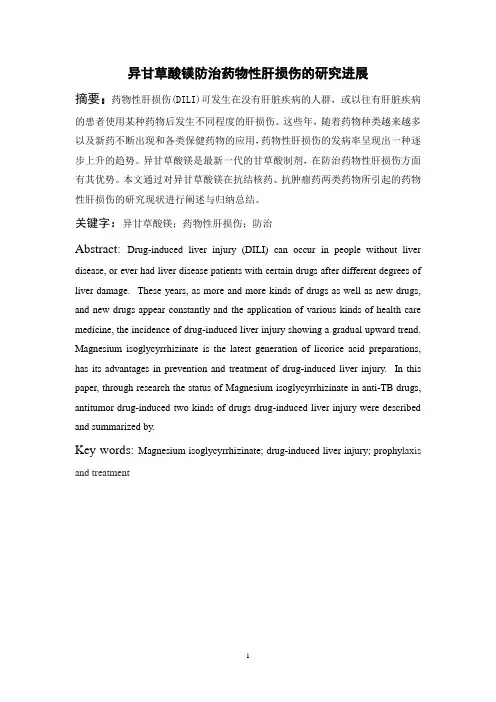
异甘草酸镁防治药物性肝损伤的研究进展摘要:药物性肝损伤(DILI)可发生在没有肝脏疾病的人群,或以往有肝脏疾病的患者使用某种药物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这些年,随着药物种类越来越多以及新药不断出现和各类保健药物的应用,药物性肝损伤的发病率呈现出一种逐步上升的趋势。
异甘草酸镁是最新一代的甘草酸制剂,在防治药物性肝损伤方面有其优势。
本文通过对异甘草酸镁在抗结核药、抗肿瘤药两类药物所引起的药物性肝损伤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与归纳总结。
关键字:异甘草酸镁;药物性肝损伤;防治Abstract: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 can occur in people without liver disease, or ever had liver disease patients with certain drugs after different degrees of liver damage. These years, as more and more kinds of drugs as well as new drugs, and new drugs appear constantl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kinds of health care medicine, the incidence of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showing a gradual upward trend. Magnesium isoglycyrrhizinate is the latest generation of licorice acid preparations, has its advantages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In this paper, through research the status of Magnesium isoglycyrrhizinate in anti-TB drugs, antitumor drug-induced two kinds of drugs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were described and summarized by.Key words: Magnesium isoglycyrrhizinate;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prophy laxis and treatment目录摘要............................................... 错误!未定义书签。

大陆中草药肝损害调查2014-08-28 11:11 来源:凤凰周刊作者:曾鼎愈来愈多的医药学研究发现,一大类传统中草药正在损害国人的肝脏。
长期、大剂量的服用——包括中成药和草药,均可能造成致命损害。
安徽医科大学的许建明教授 2005 年曾开展一项覆盖全国 16 家大型医院的药肝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1200 多例药物性肝损伤病例中,中草药的致病因素占 20.6%。
”2013 年,来自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从 1994 年到 2011 年的24112 例药物性肝损伤病人中,“中草药是导致中国药物性肝损伤的第二大原因”,占18.6%。
排在药肝比例首位的是西药中的抗结核药,占将近 1/3。
该论文的课题负责人、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副主任医师郭红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该研究没有采取一手病例调查,而是回顾了国内以往医学文献报告的病例。
由于缺乏原始数据,该论文存在一定局限,主要目的是在于呼吁国内外的医师重视药物性肝损害,特别是中草药引起的肝损害。
一些单个医院的数据开始在业界得到披露和讨论。
2014 年 5 月 23 日,在由《药物不良反应》学术杂志举办的第 6 届药源性疾病与安全用药论坛上,诸多专家均在报告中强调中草药的肝病风险,并给出了几个单个医院的数值。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杜晓曦介绍:北京一家肝病专科医院院长此前曾告诉她,该院大约 60% 的药肝病例跟中药相关;另一西医医院院长则在此次论坛的私下场合估计,该医院中药相关的药肝病例可能占到一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魏来披露该院中草药肝病比例的数据。
“中药和化学药(即西药)在药物性肝病中所占比例,一个是 51%,一个是 49%。
致肝病的化学药比较集中,而哪些中药导致药肝?我们还没有搞清楚。
”在临床上,药物性肝病是一种排除性诊断,它主要由肝病医生依靠药物不良反应数据库,根据既往的知识积累来辅助诊断。
现有超过 900 种化学药被明确可以导致药物性肝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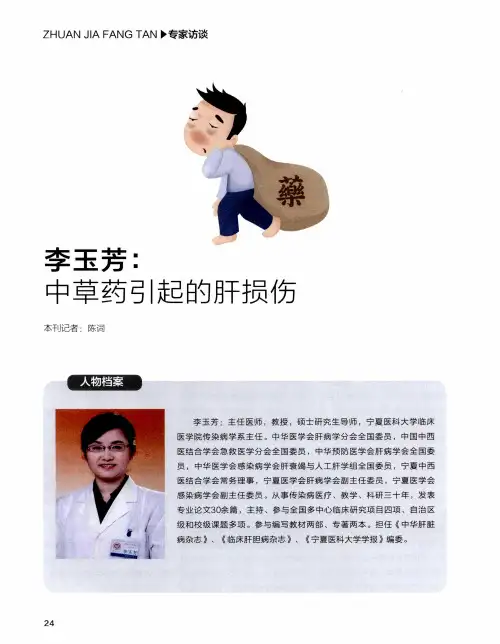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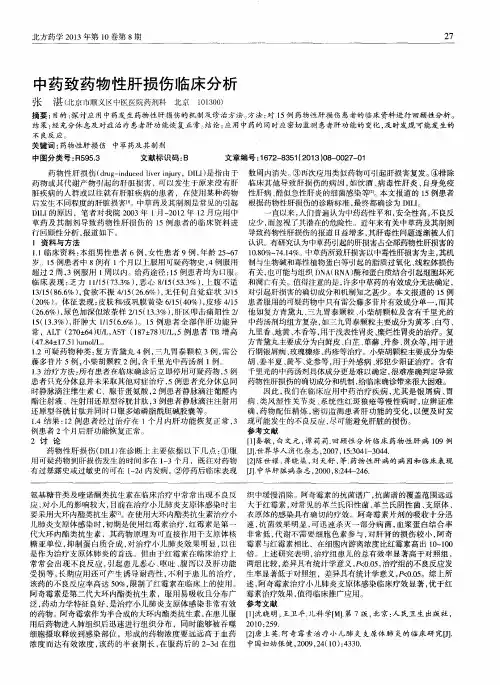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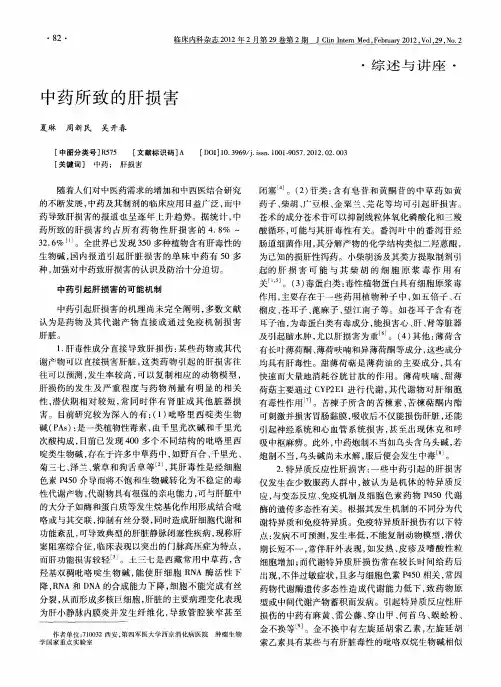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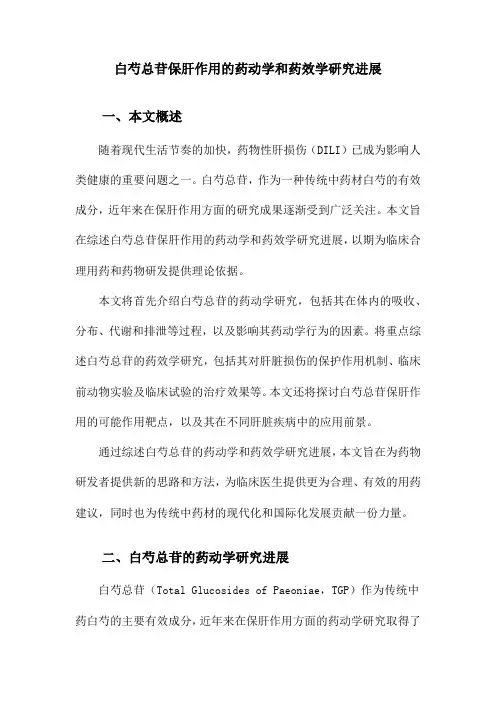
白芍总苷保肝作用的药动学和药效学研究进展一、本文概述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药物性肝损伤(DILI)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问题之一。
白芍总苷,作为一种传统中药材白芍的有效成分,近年来在保肝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综述白芍总苷保肝作用的药动学和药效学研究进展,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和药物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将首先介绍白芍总苷的药动学研究,包括其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等过程,以及影响其药动学行为的因素。
将重点综述白芍总苷的药效学研究,包括其对肝脏损伤的保护作用机制、临床前动物实验及临床试验的治疗效果等。
本文还将探讨白芍总苷保肝作用的可能作用靶点,以及其在不同肝脏疾病中的应用前景。
通过综述白芍总苷的药动学和药效学研究进展,本文旨在为药物研发者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临床医生提供更为合理、有效的用药建议,同时也为传统中药材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白芍总苷的药动学研究进展白芍总苷(Total Glucosides of Paeoniae,TGP)作为传统中药白芍的主要有效成分,近年来在保肝作用方面的药动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药动学,即药物动力学,主要研究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对于理解药物作用机制、优化给药方案以及评估药物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在白芍总苷的药动学研究中,研究者们通过运用先进的分析技术和动物实验模型,对其在体内的吸收和分布进行了深入研究。
结果显示,白芍总苷在口服后能够迅速被机体吸收,并广泛分布于各组织器官中,尤其是在肝脏中的浓度较高,这为其发挥保肝作用提供了物质基础。
代谢方面,白芍总苷在体内的代谢过程相对复杂,涉及多种酶类的参与。
研究者们通过体外酶解实验和体内代谢研究,揭示了其主要的代谢途径和代谢产物,为进一步研究其药效学和药物相互作用提供了依据。
在排泄方面,白芍总苷主要通过肾脏和胆道系统进行排泄。
研究发现,其在尿液和胆汁中的排泄量较高,这表明肾脏和胆道系统在白芍总苷的排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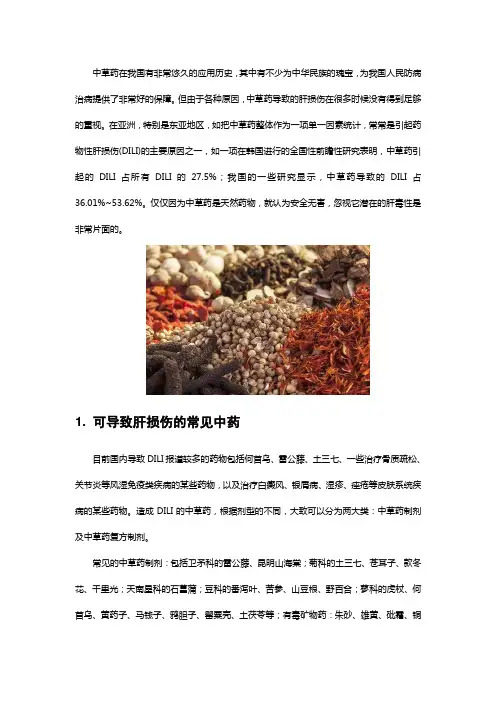
中草药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应用历史,其中有不少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为我国人民防病治病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
但由于各种原因,中草药导致的肝损伤在很多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如把中草药整体作为一项单一因素统计,常常是引起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一项在韩国进行的全国性前瞻性研究表明,中草药引起的DILI占所有DILI的27.5%;我国的一些研究显示,中草药导致的DILI占36.01%~53.62%。
仅仅因为中草药是天然药物,就认为安全无害,忽视它潜在的肝毒性是非常片面的。
1. 可导致肝损伤的常见中药目前国内导致DILI报道较多的药物包括何首乌、雷公藤、土三七、一些治疗骨质疏松、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类疾病的某些药物,以及治疗白癜风、银屑病、湿疹、痤疮等皮肤系统疾病的某些药物。
造成DILI的中草药,根据剂型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中草药制剂及中草药复方制剂。
常见的中草药制剂:包括卫矛科的雷公藤、昆明山海棠;菊科的土三七、苍耳子、款冬花、千里光;天南星科的石菖蒲;豆科的番泻叶、苦参、山豆根、野百合;蓼科的虎杖、何首乌、黄药子、马钱子、鸦胆子、罂粟壳、土茯苓等;有毒矿物药:朱砂、雄黄、砒霜、铜绿等。
常见中草药复方制剂:包括牛黄解毒丸、六神丸、壮骨关节丸、天麻丸、鱼腥草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穿琥宁注射液、复方丹参素注射液、养血生发胶囊、补肾乌发胶囊、湿毒清、地奥心血康等。
上述中药及复方制剂,请不要在缺少专业医师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服用。
2. 中草药致DILI的临床病理类型中草药引起DILI的临床病理表现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已知的肝脏病理变化。
虽然某些药物可引起一定的病理特征,但通常并不能依据组织学的变化来确定起因的药物。
肝活组织检查往往用于临床生化异常的肝病患者在诊断和鉴别诊断,特别是除外DILI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DILI组织学一般特征为:(1)局灶性(小叶中央)边界较为明显的坏死和脂肪变性,坏死灶严重程度比临床不成比例;(2)肝脏炎症较轻,小胆管胆汁淤积较明显;(3)门管区炎症程度较轻(可能有胆管破坏性病变);(4)多数为嗜中性细胞或嗜酸性细胞浸润;(5)类上皮肉芽肿形成;(6)微泡性脂肪变(线粒体损伤)和脂肪性肝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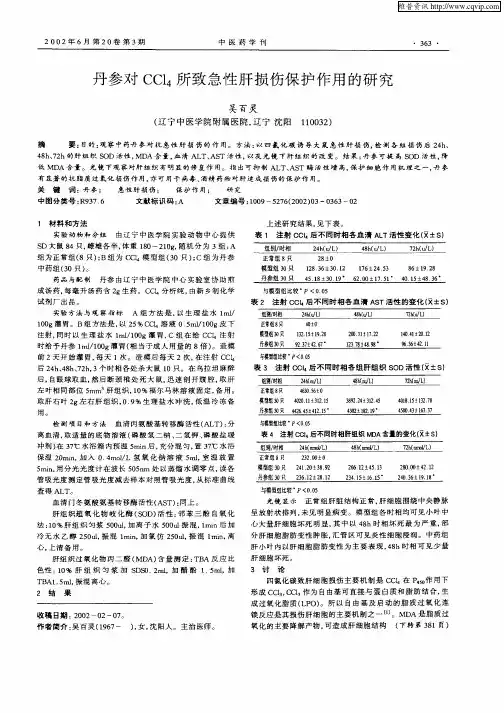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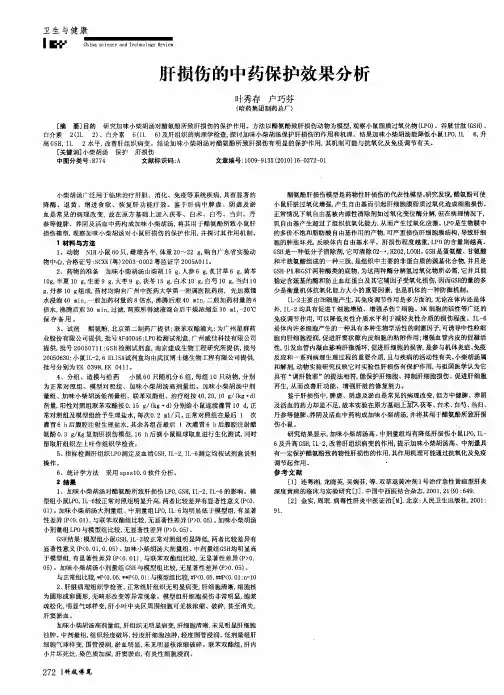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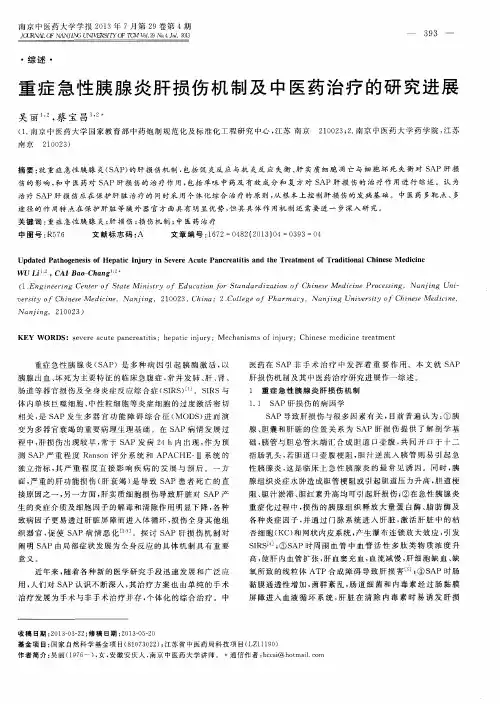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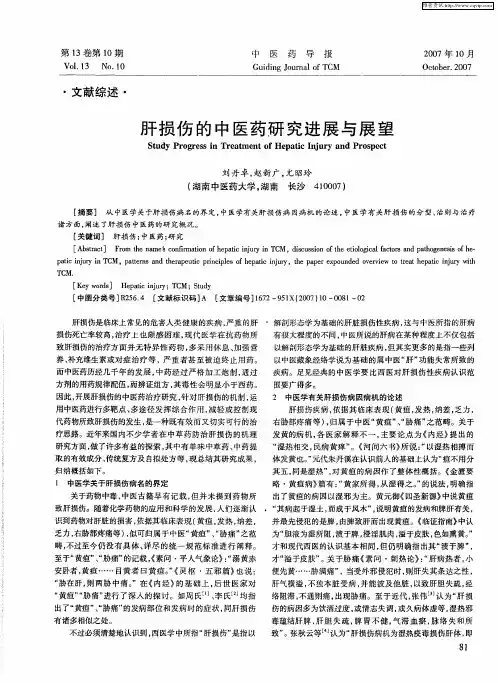
浅谈常用中药的肝损害【摘要】本文就常见致肝损伤的中药及其成分与致肝损害机制及临床特点及加强预防措施等作简要述。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辨证施治、合理用药,才是防止中药引起肝损伤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中药;肝损害近年来中药及其制成品所引起不良反应的报道有增多之势,而中药所引起的肝损害占药物性肝损害的比例20.04%一74.14%不等[1],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重视中药的肝损害。
1 中药引起肝损害的原因1.1 中药因素①中药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非常复杂,表现出药效和药害的双重性。
即既可治疗肝病,同时也能引起肝损害,如大黄、柴胡;②对一些中药的毒性认识不足,传统认为“无毒”的中药品种,现代临床却发现其具有肝毒性,如黄药子、天花粉、番泻叶、何首乌等。
③中药中同名异物或异名同物的情况不少,可因误认误用而致中毒。
如防己有广防己、粉防己,广防己临床己报道有肝、肾毒性。
④中药因产地、种植、采收季节、加工炮制、运输贮存等条件不同,也可影响其药效和不良反应,⑤中药引起的肝毒性损害也与剂型、剂量、用药时间过长、配伍和使用方法等有关,如服用大剂量未经炮制的生首乌会导致肝脏的损害。
⑥不按照中医药辨证论治的基本特征使用中药,违反禁忌原则。
1.2 患者因素①患者缺乏对某些中药制剂具有肝毒性的认识,因而服用中药剂量过大,用药时间过长而引起肝损害。
②患者因年龄或健康状况和个体差异,在常规剂量也可发生毒性反应;③某些人存在遗传性肝脏代谢缺陷的疾病,容易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
中药中能引起肝损害的药物分为三类,有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1.2.1 常见植物药物及其肝损害的临床症状见下表[2]—[8]1.2.2 单味动物药如蜈蚣、蟾蜍、斑蝥、青娘虫、穿山甲等[9]1.2.3 单味矿物药如朱砂、雄黄、铅粉、硝石、砒石、代赭石、胆矾、硫黄等[9]。
2 中药引起肝损害按照其所含的主要成分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类2.1 毒性成分为生物碱类吡咯里西啶生物碱是一类植物性毒素。
栀子苷保肝利胆和肝毒性双重作用的研究进展王荣慧1,2,3,吴 虹1,2,3,王梦蝶1,2,3,邓 然1,2,3,王 言1,2,3,戴学静1,2,3,占 翔1,2,3,孙明慧1,2,3,卜妍红1,2,3,张 衡1,2,3(1.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安徽合肥 230012;2.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安徽合肥 230012;3.中药复方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安徽合肥 230012)[摘要]栀子苷是中药栀子的主要药用活性成分,对肝脏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然而,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报道栀子苷具有一定的肝毒性。
研究表明,栀子苷对肝脏的保护作用是多方面的,其能够调节肝微粒体酶的活性;诱导信号通路的激活进而调控相关肝细胞的凋亡和炎症因子的释放;此外,栀子苷对氧化应激反应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能够清除肝组织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的生成;促进脂肪代谢,对代谢障碍引起的肝脏损伤具有治疗作用。
栀子苷产生肝毒性作用是由患者个体的差异性、给药途径不同、给药剂量不同、肠道内pH差异造成的。
栀子苷造成肝毒性的机制与其半缩醛结构相关。
[关键词]栀子苷;保肝利胆;肝脏毒性[中图分类号]R285.5 [DOI]10.3969/j.issn.2095 7246.2020.03.022 中药栀子是茜草科植物栀子犌犪狉犱犲狀犻犪犼犪狊犿犻 狀狅犻犱犲狊犈犾犾犻狊的干燥成熟果实,具有广泛的药理学作用[1]。
栀子含有栀子苷、绿原酸、藏红花素等活性成分[2],具有保肝利胆、抗炎、抗抑郁、抗氧化、神经保护等多种药理活性,对糖尿病肝脏损伤、抑郁症、自身免疫性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3 4]。
其中,栀子苷作为中药栀子的主要活性成分在治疗肝脏疾病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近年来研究表明,栀子苷具有肝脏毒性,这使得栀子苷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阻碍了临床处方中栀子的广泛使用。
现就栀子苷对肝脏的保护与致毒作用机制作一综述,为栀子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栀子苷对肝脏保护作用研究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器官,也是新陈代谢最主要的器官,具有一定的解毒作用。
吴茱萸致肝毒性研究臧宝珊;孙向明;李文兰【摘要】通过对近年来有关吴茱萸肝毒性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及总结。
对吴茱萸提取物的肝毒性研究及其肝毒性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便为吴茱萸临床安全用药和科学研究提供更多参考。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of Evodia rutaecarpa related to the hepatotoxicity in recent years were collected, collated and summarized.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of hepatotoxicity caused by Evodia rutaecarpa extract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mechanism of hepatotoxicity providing more reference and methods for clinical safe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期刊名称】《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6【总页数】4页(P641-644)【关键词】吴茱萸;肝毒性;作用机制【作者】臧宝珊;孙向明;李文兰【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76; 国家教育部抗肿瘤天然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76;哈尔滨商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76; 国家教育部抗肿瘤天然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76;哈尔滨商业大学生命科学与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76; 国家教育部抗肿瘤天然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7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285传统观点认为,中药取材于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少,且对一些西药无效的疾病具有一定的疗效,往往忽略了其潜在的毒副作用.李文兰、薛佳等[1-2]等研究发现,穿心莲提取物和穿心莲内酯对雄性小鼠具有生殖毒性作用,并呈现一定的“时-毒”、“量-毒”关系.随着中药在东西方国家中日益广泛的应用,有关中药诱发药源性肝损伤(DILI)的报道也逐渐增多[3-5].药源性肝损伤是指药物在治疗过程中,肝脏由于药物的毒性损伤或对药物过敏反应所致的疾病.在全球死亡原因中,根据WHO统计的数据显示,药源性损伤导致的肝毒性因素位于第五位[6].在我国,中药所致的急性肝损伤仅次于抗结核药物位列第二[7-8],近年来已引起临床高度重视.吴茱萸为芸香科植物吴茱萸(Evodia rutaecarpa(Juss.)Benth.)、石虎(Evodia rutaecarpa(Juss)Benth Var.officinalis(Dode)Huang.)或疏毛吴茱萸(Evodia rutaecarpa(Juss)Benth Var.bodinier(Dode)Huang.)的干燥近成熟果实.辛、苦、热,有小毒.归肝、脾、胃、肾经.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功效[9].吴茱萸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属传统的中药温理药.在历代中医药书籍中记载其有小毒,《别录》言其“大热,有小毒”;《药性论》记载:“吴茱萸,味苦、辛,大热,有毒”;李时珍认为吴茱萸“有小毒,动脾火,病目者忌之”等.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吴茱萸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深入研究,已为揭示吴茱萸药效物质基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0-14].近年来,吴茱萸的临床应用日趋广泛,临床上因服用吴茱萸不当而产生中毒的报道也时有发生[15-18],亦有部分文献指出其可以引起肝毒性[19],吴茱萸的用药安全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因此,笔者对近年来吴茱萸所致的肝毒性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综述,以便为吴茱萸临床安全用药和科学研究提供依据及方法.1 吴茱萸不同部位致肝毒性作用目前已经从吴茱萸植物中分离得到了100多个化合物,研究发现吴茱萸植物所含的化学成分种类较多,包括生物碱、黄酮类、萜类、香豆素、甾体、精油、木脂素、核苷酸及其他成分,其中生物碱、苦味素为主要成分[20-22].1.1 吴茱萸水提物致肝毒性通过收集近些年关于吴茱萸水提物致肝毒性的研究发现,吴茱萸水提物引起的肝毒性多呈现一定的急性毒性.研究发现[18],多次灌胃吴茱萸水提物可导致明显的肝损伤,且存在一定的肝毒性的“量-时-毒”关系.吴茱萸水提物的剂量的不同会对肝脏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伴随着肝脏指数的变化、血清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的明显升高,且呈现剂量依赖相关性.周璐等[23]报道,吴茱萸水提取物影响大、小鼠部分肝药酶亚型的活性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根据大、小鼠实验结果显示,吴茱萸水提取物可以诱导大、小鼠CYP1A、CYP2C和CYP2E1的活性,且对CYP1A活性的诱导更为显著.吴茱萸水提取物可以诱导小鼠CYP3A活性,抑制大鼠CYP2D的活性,而对小鼠CYP2D、大鼠CYP3A的活性无显著影响.1.2 吴茱萸醇提物致肝毒性李波等[24]等研究发现,吴茱萸乙醇提物灌胃给予大鼠后,对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毒性.实验将80只SD雌雄各半的大鼠随机分成4组,分别给予吴茱萸乙醇提物15、30、60 g(原生药)/kg及等量蒸馏水灌胃14 d,于第3、14 d测定血液生化学、血液细胞学指标,观察肝脏组织病理变化,计算脏器系数.给药3 d后,吴茱萸乙醇提物30、60 g(原生药)/kg组尿素氮(BUN)、血清总胆红素(TBIL)和碱性磷酸酶(ALP)较对照组升高,白蛋白(ALB)和血清总蛋白(TP)明显降低,肝脏系数显著增大.给药14 d后,与对照组相比,吴茱萸乙醇提物30、60 g(原生药)/kg组血清谷草转氨酶(AST)升高,吴茱萸乙醇提物60 g(原生药)/kg组脏器系数较正常组明显增大.根据对各组大鼠肝脏病理组织学的观察,如图1、2所示,主要表现为肝脏中央静脉及小叶下静脉周围肝细胞变形、灶性坏死,毒性无性别差异,并呈现一定的“时-毒”、“量-毒”关系.图1 吴茱萸乙醇提取物一次灌胃急性毒性试验肝脏病例变化(给药3 d后)图2 吴茱萸乙醇提取物一次灌胃急性毒性试验肝脏病例变化(给药14 d后)由此可知吴茱萸乙醇提物具有一定毒性,肝脏是其主要毒性靶器官之一,推测吴茱萸醇提物的肝毒性是通过其吸收代谢的产物影响肝药酶活性来损害肝脏.1.3 吴茱萸挥发油致肝毒性吴茱萸挥发油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肝损伤.孙蓉等[25]用小鼠研究吴茱萸挥发油肝毒性“量-时-毒”关系,发现单次灌胃小鼠6 h后血清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达到峰值,8~72 h内造成明显肝损伤,且呈一定剂量依赖相关性.黄伟等[26]研究发现,多次灌胃小鼠吴茱萸挥发油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肝损伤,与时间、剂量呈现一定相关性.根据实验结果显示,给药7 d之内小鼠血清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碱性磷酸酶(AKP)及总胆红素(TBI)升高,白蛋白(ALB)降低,脏器系数增大,以及不同程度的肝细胞水肿、脂肪变性和间质充血.2 吴茱萸致肝毒性机制的研究吴茱萸致肝毒性的机制复杂,其毒理学基础尚不完全明确,目前研究认为,吴茱萸致肝毒性机制可能与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有关.2.1 与其引起机体氧化应激有关正常情况下,机体内的氧化系统和抗氧化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谷胱甘肽(GSH)、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丙二醛(MDA)等都是抗氧化系统的重要成员.GSH-Px可以催化GSH变为GSSG,使有毒的过氧化物还原成无毒的羟基化合物,同时促进H2O2的分解,从而达到保护细胞膜的结构及功能不受过氧化物的干扰及损害的目的.GSH是机体内主要的低分子清除剂,保护许多蛋白质和酶等分子中的巯基,它是GSH-Px和GST两种酶的底物GSH,GSH 含量的降低会产生毒性作用,因此GSH的含量是影响机体抗氧化作用的重要因素. 根据研究报道[27],吴茱萸水提物可引起血和肝中MDA含量的显著升高,GSH-Px、SOD活性的降低,NO含量的升高,NOS活性的增大, GHS含量的下降,且呈现出一定的剂量依赖相关性.血和肝中MDA含量升高,阻碍线粒体氧化磷酸化,损害线粒体功能,导致自由基增多,损害肝细胞;GSH-Px、SOD活性的降低,机体内自由基含量的升高,破坏了氧化系统和抗氧化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引起细胞凋亡;NO含量的升高和NOS活性的增大导致自由基增多,产生肝毒性;GSH含量的减少,降低了抗氧化作用.由此推测,引起机体氧化应激后诱导脂质过氧化可能是吴茱萸致肝毒性机制之一.2.2 与其引起机体炎症反应有关IL-1β、IL-6及TNF-α等均是与炎症反应十分相关的炎症介质.IL-1β是致炎性的细胞因子,它可以促进细胞增殖,释放炎性介质,参与炎症后期纤维化的形成.IL-1β会促进病理性成纤维细胞分泌更多的IL-6和IL-8.IL-6是活化的T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产生的淋巴因子,能使B细胞前体成为产生抗体的细胞;和集落刺激因子协同,能促进原始骨髓源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裂解功能.TNF-α是一种由激活的巨噬细胞产生的能抑制成骨细胞和刺激破骨细胞的细胞因子,其被证实在肝纤维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TNF-α的过度分泌会引起肝损伤.周璐等[28]在研究吴茱萸水煎液致小鼠肝毒性机制中发现,连续21 d给予高、中、低3个剂量的吴茱萸水煎液后,如表1所示,与正常组相比,给药组的小鼠肝脏中IL-1β、IL-6及TNF-α的含量明显增高.提示大量炎症介质释放与产生,是吴茱萸致肝损伤的原因之一,见表1.表1 吴茱萸水煎液对小鼠肝组织炎症介质的影响组别生药剂量/(g·kg-1·d-1)IL-1β/(ng·L-1)IL-6/(pg·L-1)TNF-α/(ng·L-1)正常- 15.33±0.74 24.99±1.96104.89±8.86吴茱萸1018.71±1.03∗27.14±1.71∗125.04±8.722020.95±0.86∗29.89±1.81∗131.13±9.963027.64±1.43∗41.57±3.59∗155.84±8.9∗与正常组比较*P<0.013 结语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的精华,中药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对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些年临床上因服用了未炮制透的中药或直接服用了生品中药或因超剂量服用或因配伍不当而引起肝脏毒性的报道日益增多.如何避免中药可能存在的肝脏毒性,提高中药临床用药安全,是中药走向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关键所在.吴茱萸为临床常用中药,其水煎剂为常用剂型,历代本草中一般记载其有小毒,从日益增多的吴茱萸临床不良反应报道中得知肝损害占大部分,吴茱萸的用药安全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目前,认为吴茱萸致肝毒性的作用机制为:一是与引起机体氧化应激后诱导脂质过氧化有关;二是与引起机体炎症反应有关.吴茱萸引起肝毒性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明确,是解决吴茱萸致肝毒性问题的有效途径.参考文献:[1] 李文兰, 丁振铎, 王铁山, 等. 穿心莲生殖毒性的量效关系研究[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29(3): 257-261.[2] 薛佳, 李文兰, 王学志, 等. 穿心莲生殖毒性的时效关系研究[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27(5): 645-666.[3] 高尚, 孙向明, 许颖, 等. 中药致肝毒性相关机制研究[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30(3): 257-270.[4] WANG J, JI L, LIU H, et al. Study of the hepatotoxicity induced by Dioscorea bulifera L. rhizome in mice [J]. Bioscience Trends, 2010, 4(2): 79-85.[5] CHAU T N.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an update [J]. The Hong Kong Medical Diary, 2008, 13(3): 23-26.[6] LARREY D. Epidemiology and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to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ffecting the liver [J]. Seminars in Liver Disease, 2002, 22(2): 145-155.[7] TESCHKE R, WOLFF A, FRENZEL C, et al. Herbal hepatotoxicity: a tabular compilation of reported cases [J]. Liver International, 2012, 32(10): 1543-1556.[8] MEIER Y, CAVALLARO M, ROOS M, et al. Incidence of 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in medical inpatients [J].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2005, 61(2): 135-143.[9]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 160.[10] YAN R, WANG Y, SHEN W J, et al. Relative determination of dehydroevodiamine in rat plasma by LC-MS and study on its pharmacokinetics [J].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ic Science, 2012, 50(7): 582-585.[11] XIAO B Y, MAO S J, LI X D. Variations in the composition of Fructus Evodiae after processing with Radix Glycyrrhizae extract [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2012, 18(10): 782-787.[12] HUANG X, LI W, YANG X W. New cytotoxic quinolone alkaloids fromfruits of Evodia rutaecarpa [J]. Fitoterapia, 2012, 83(4): 709-714.[13] CHEN F, LI S, LI D, et al. Transdermal behaviors comparisons among Evodia rutaecarpa extracts with different purity of evodiamine and rutaecarpine and the effect of topical formulation in vivo [J]. Fitoterapia, 2012, 83(5): 954-960.[14] NOH K, SEO Y M, LEE S K, et al. Effects of rutaecarpine on the metabolism and urinary excretion of caffeine in rats [J]. Archives of Pharmacal Research, 2011, 34(1): 119-125.[15] 朱兰兰, 黄伟, 黄幼异, 等. 基于功效和物质基础的吴茱萸毒性研究思考[J]. 中国药物警戒, 2011, 8(6): 366-369.[16] 蔡雪映, 孟楠, 杨冰. 服用吴茱萸过量致中毒1例分析[J]. 北京中医药, 2006, 25(3): 171-172.[17] LI L, ZHAO J N, YI J H, et al. Research on toxicity characteristics in Evodia Fructus of different orgins and producing areas [J].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2012, 37(15): 2219-2222.[18] HUANG W, LI X J Y, SUN R. “Dose-time-toxicity” relationship study on hepatotoxicity caused by multiple dose water extraction components of Evodiae Fructus to mice [J].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2012, 37(15): 2223-2227.[19] 周绮, 张茜, 金若敏. 茱萸致小鼠肝毒性时效、量效关系研究[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1, 17(9): 232.[20] 张起辉, 高慧媛, 吴立军, 等. 吴茱英的化学成分[J].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2005, 22(1): 12-14.[21] 孟娜, 陈凤凰, 惠斌. 吴茱萸化学成分研究[J]. 贵州大学学报, 2006, 23(2):188-190.[22] 张璐, 冯育林, 王跃生. 吴茱萸现代研究概况[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0,22(2): 78-82.[23] 周璐, 徐婷婷, 金若敏, 等. 吴茱萸水煎液对大、小鼠肝药酶亚型影响的比较研究[J]. 中国药理学通报, 2014, 30(2): 279-282.[24] 李波, 李莉, 赵军宁, 等. 吴茱萸乙醇提取物对大鼠急性毒性及肝毒性的影响[J]. 中药药理与临床, 2013, 29(2): 120-124.[25] 孙蓉, 黄伟, 吕丽莉. 吴茱萸挥发油单次给药对小鼠肝毒性“量-时-毒”关系研究[J]. 中国药理与临床, 2012, 28(3): 55-58.[26] 黄伟, 孙蓉, 李晓宇. 吴茱萸挥发油多次给药致小鼠肝毒性“量-时-毒”关系研究[C]//中国药学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药师周论文集, 2013.[27] 黄伟, 孙蓉. 吴茱萸水提组分多次给药致小鼠肝毒性氧化损伤机制研究[J]. 中国药理与临床, 2012, 28(5): 114-116.[28] 周璐, 姚广涛, 曹智丽, 等. 吴茱萸水煎液致小鼠肝毒性机制研究[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3, 19(22): 269-272.。
药物性肝损伤的研究进展作者:于春萍李若飞兰丁璇来源:《中国保健营养》2019年第09期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指药物本身或者药物的代谢产物通过多种机制导致的肝脏损伤,以乏力、消化道症状、尿黄、发热、皮疹为主要表现[1],并伴随谷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肝酶谱的升高。
常见的导致肝损伤的药物有以对乙酰氨基酚为代表的解热镇痛药、以氯丙嗪为主的抗精神病药、以异烟肼为主的抗结核药、以伏立康唑为主的抗生素类药物、以何首乌为主的传统中药及以阿糖胞苷为主的抗肿瘤药。
这些药物导致肝损伤的发病机制复杂,可通过代谢激活、线粒体损伤、免疫损伤、遗传损伤、溶酶体损伤、胆道损伤等多种途径造成肝脏损伤。
本文综述了常见的导致肝损伤的药物及其致病机制,以为药物性肝损伤的预防及治疗提供参考。
1.药物性肝损伤的主要致病机制1.1代谢激活肝脏是药物代谢的主要场所,进入肝脏的药物代谢需经过两个过程:I相反应(以CYP450酶为主的氧化、还原、水解过程);II相反应(结合反应)。
在I相反应会形成大量的亲电子基和自由基等肝毒性物质,II相反应则通过谷胱甘肽等物质对I相反应中形成的肝毒性物质进行清除。
当机体的清除能力小于肝毒性物质的产生能力时,二者的平衡被打破,导致肝毒性物质在体内的大量蓄积。
亲电性物质可以与大分子物质结合损伤肝脏;自由基可通过脂质、蛋白质、氨基酸、核酸过氧化,造成肝脏损伤。
1.2线粒体损伤线粒体是三羧酸循环和能量产生的主要场所,在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生命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肝脏内线粒体损伤则会严重影响肝脏的生理功能。
造成线粒体损伤的主要原因是①氧化应激:药物在代谢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造成脂质过氧化,损伤线粒体。
②呼吸链被抑制:呼吸链被抑制主要表现为电子传递受阻,导致氧的沉积与ATP产生不足,难以供应身体的需求,损伤肝脏。
③线粒体渗透性转变模孔开放,可诱导肝脏细胞凋亡。
④钙紊乱。
⑤自由基造成线粒体DNA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