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礼法之争”的评价与启示
- 格式:pdf
- 大小:254.84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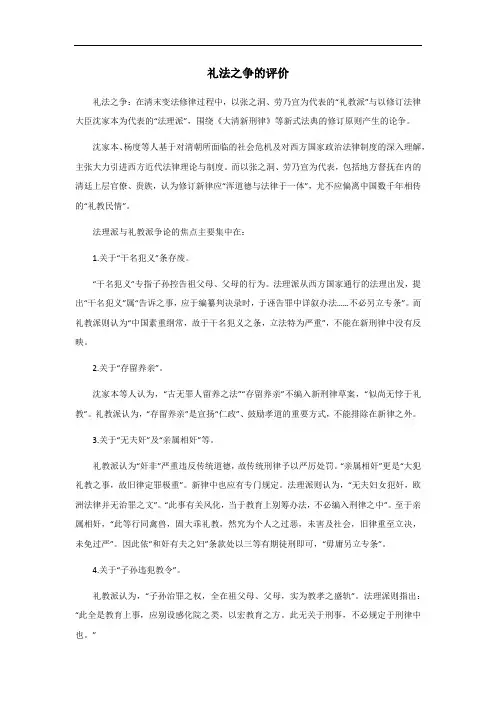
礼法之争的评价礼法之争: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原则产生的论争。
沈家本、杨度等人基于对清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对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深入理解,主张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制度。
而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包括地方督抚在内的清廷上层官僚、贵族,认为修订新律应“浑道德与法律于一体”,尤不应偏离中国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
法理派与礼教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关于“干名犯义”条存废。
“干名犯义”专指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的行为。
法理派从西方国家通行的法理出发,提出“干名犯义”属“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
而礼教派则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不能在新刑律中没有反映。
2.关于“存留养亲”。
沈家本等人认为,“古无罪人留养之法”“存留养亲”不编入新刑律草案,“似尚无悖于礼教”。
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排除在新律之外。
3.关于“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等。
礼教派认为“奸非”严重违反传统道德,故传统刑律予以严厉处罚。
“亲属相奸”更是“大犯礼教之事,故旧律定罪极重”。
新律中也应有专门规定。
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
“此事有关风化,当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
至于亲属相奸,“此等行同禽兽,固大乖礼教,然究为个人之过恶,未害及社会,旧律重至立决,未免过严”。
因此依“和奸有夫之妇”条款处以三等有期徒刑即可,“毋庸另立专条”。
4.关于“子孙违犯教令”。
礼教派认为,“子孙治罪之权,全在祖父母、父母,实为教孝之盛轨”。
法理派则指出:“此全是教育上事,应别设感化院之类,以宏教育之方。
此无关于刑事,不必规定于刑律中也。
”5.关于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
礼教派认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惩治,最多像舜帝那样“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绝无“正当防卫”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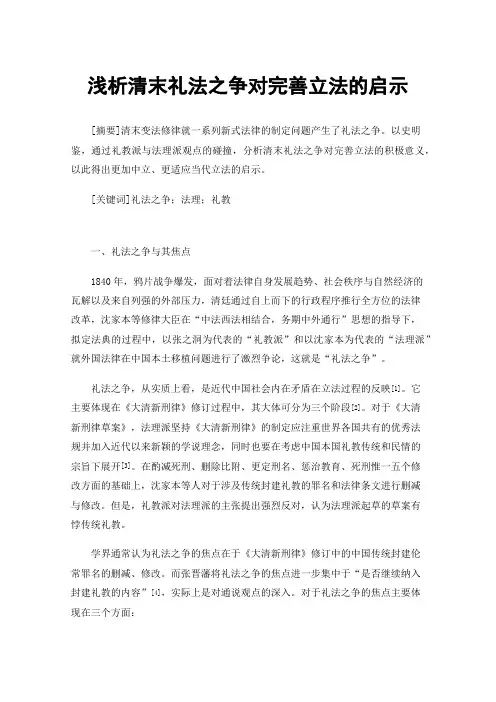
浅析清末礼法之争对完善立法的启示[摘要]清末变法修律就一系列新式法律的制定问题产生了礼法之争。
以史明鉴,通过礼教派与法理派观点的碰撞,分析清末礼法之争对完善立法的积极意义,以此得出更加中立、更适应当代立法的启示。
[关键词]礼法之争;法理;礼教一、礼法之争与其焦点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面对着法律自身发展趋势、社会秩序与自然经济的瓦解以及来自列强的外部压力,清廷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推行全方位的法律改革,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在“中法西法相结合,务期中外通行”思想的指导下,拟定法典的过程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就外国法律在中国本土移植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这就是“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从实质上看,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矛盾在立法过程的反映[1]。
它主要体现在《大清新刑律》修订过程中,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
对于《大清新刑律草案》,法理派坚持《大清新刑律》的制定应注重世界各国共有的优秀法规并加入近代以来新颖的学说理念,同时也要在考虑中国本国礼教传统和民情的宗旨下展开[3]。
在酌减死刑、删除比附、更定刑名、惩治教育、死刑惟一五个修改方面的基础上,沈家本等人对于涉及传统封建礼教的罪名和法律条文进行删减与修改。
但是,礼教派对法理派的主张提出强烈反对,认为法理派起草的草案有悖传统礼教。
学界通常认为礼法之争的焦点在于《大清新刑律》修订中的中国传统封建伦常罪名的删减、修改。
而张晋藩将礼法之争的焦点进一步集中于“是否继续纳入封建礼教的内容”[4],实际上是对通说观点的深入。
对于礼法之争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修律指导思想:西方法律原则或传统礼教沈家本主张如果想要学习西方法律的宗旨,那么就必须要认真研究西方人的学说和书籍[5]。
沈家本等人通过研习西方先进的法律原理原则,对旧律进行改革,提出删除比附、罪刑法定。
他们认为比附存在以下弊端:在司法中,审判官根据自我的意志,当法律无明确规定时,比照类似的条文使得他人受到惩罚,这时司法者取代了立法者的作用;法律应具有可预测性,若保留比附,使得司法官可以根据自身的意见进行律外适用,就会导致人民无法预测其行为是否合法;比附使得司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有更高的地位,由于每个司法官主观判断不同,易造成同罪异罚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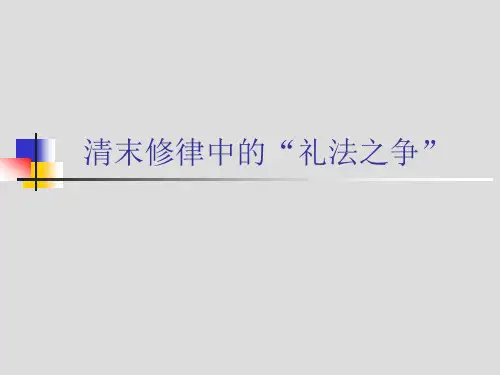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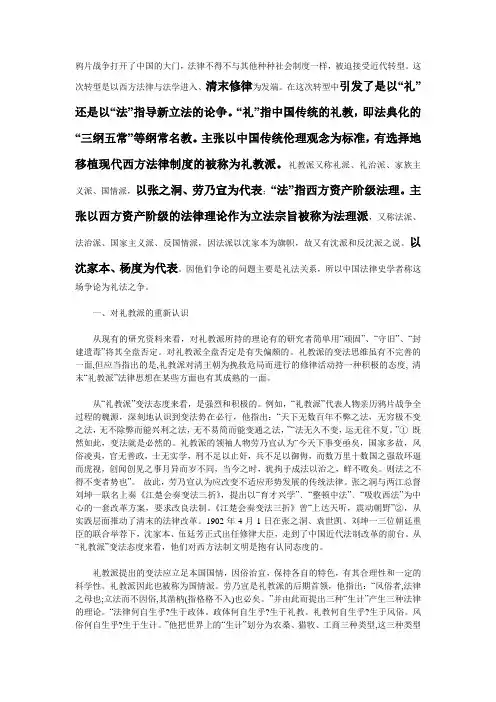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法律不得不与其他种种社会制度一样,被迫接受近代转型。
这次转型是以西方法律与法学进入、清末修律为发端。
在这次转型中引发了是以“礼”还是以“法”指导新立法的论争。
“礼”指中国传统的礼教,即法典化的“三纲五常”等纲常名教。
主张以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为标准,有选择地移植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被称为礼教派。
礼教派又称礼派、礼治派、家族主义派、国情派,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法”指西方资产阶级法理。
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理论作为立法宗旨被称为法理派,又称法派、法治派、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因法派以沈家本为旗帜,故又有沈派和反沈派之说。
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
因他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礼法关系,所以中国法律史学者称这场争论为礼法之争。
一、对礼教派的重新认识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对礼教派所持的理论有的研究者简单用“顽固”、“守旧”、“封建遗毒”将其全盘否定。
对礼教派全盘否定是有失偏颇的。
礼教派的变法思维虽有不完善的一面,但应当指出的是,礼教派对清王朝为挽救危局而进行的修律活动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清末“礼教派”法律思想在某些方面也有其成熟的一面。
从“礼教派”变法态度来看,是强烈和积极的。
例如,“礼教派”代表人物亲历鸦片战争全过程的魏源,深刻地认识到变法势在必行,他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
”①既然如此,变法就是必然的。
礼教派的领袖人物劳乃宣认为“今天下事变亟矣,国家多故,风俗凌夷,官无善政,士无实学,刑不足以止奸,兵不足以御侮,而数万里十数国之强敌环逼而虎视,创闻创见之事月异而岁不同,当今之时,犹拘于成法以治之,鲜不败矣。
则法之不得不变者势也”。
故此,劳乃宣认为应改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传统法律。
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的一套改革方案,要求改良法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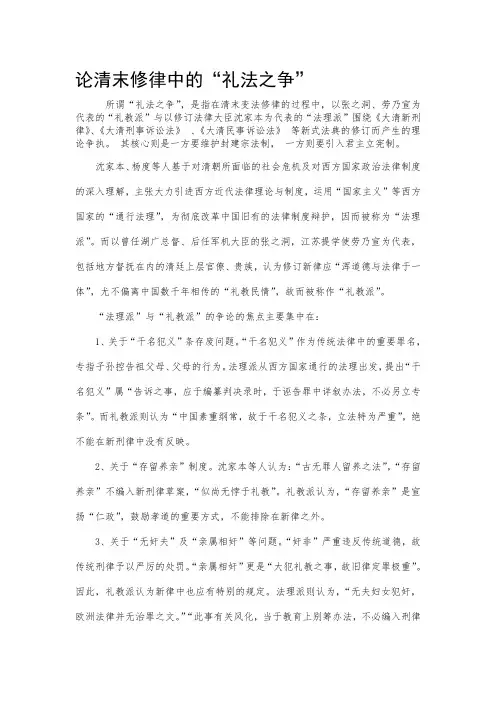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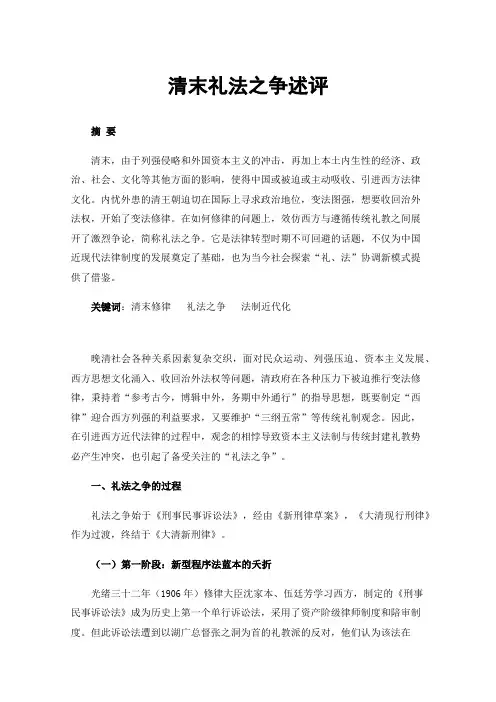
清末礼法之争述评摘要清末,由于列强侵略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再加上本土内生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影响,使得中国或被迫或主动吸收、引进西方法律文化。
内忧外患的清王朝迫切在国际上寻求政治地位,变法图强,想要收回治外法权,开始了变法修律。
在如何修律的问题上,效仿西方与遵循传统礼教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简称礼法之争。
它是法律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话题,不仅为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今社会探索“礼、法”协调新模式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法之争法制近代化晚清社会各种关系因素复杂交织,面对民众运动、列强压迫、资本主义发展、西方思想文化涌入、收回治外法权等问题,清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推行变法修律,秉持着“参考古今,博辑中外,务期中外通行”的指导思想,既要制定“西律”迎合西方列强的利益要求,又要维护“三纲五常”等传统礼制观念。
因此,在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的过程中,观念的相悖导致资本主义法制与传统封建礼教势必产生冲突,也引起了备受关注的“礼法之争”。
一、礼法之争的过程礼法之争始于《刑事民事诉讼法》,经由《新刑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作为过渡,终结于《大清新刑律》。
(一)第一阶段:新型程序法蓝本的夭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学习西方,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单行诉讼法,采用了资产阶级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
但此诉讼法遭到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反对,他们认为该法在“诉讼权利男女尊卑长幼应该平等,私有财产应该得到政府承认、法律保护”这两个问题上坏明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有违纲常伦纪,并认为仅以改良中国司法不可能使列强放弃领事裁判权。
《刑事民事诉讼法》在立法程序、收回治外法权、法律范畴等方面经不住推敲,效仿西方鼓励个体发展、保护私有财产,企图一步到位,反而操之过急,成为礼教派攻击的致命缺陷,最终只能束之高阁。
(二)第二阶段:对《新刑律草案》的攻击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和十二月,沈家本奏进《刑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并附《刑事总则清单案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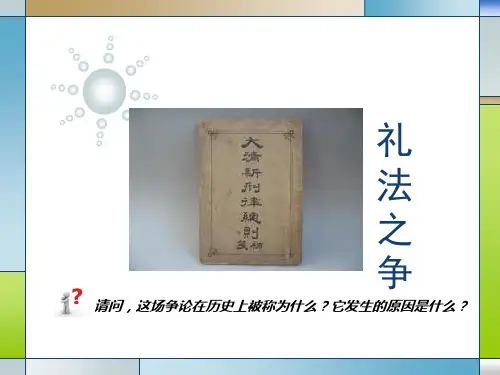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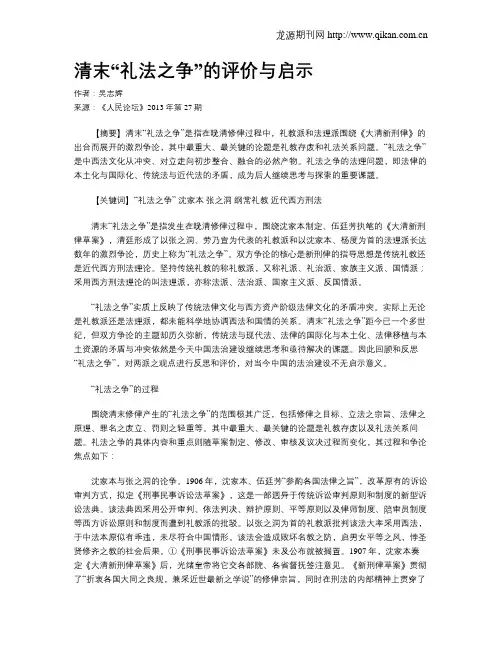
清末“礼法之争”的评价与启示作者:吴志辉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27期【摘要】清末“礼法之争”是指在晚清修律过程中,礼教派和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的出台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其中最重大、最关键的论题是礼教存废和礼法关系问题。
“礼法之争”是中西法文化从冲突、对立走向初步整合、融合的必然产物。
礼法之争的法理问题,即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法与近代法的矛盾,成为后人继续思考与探索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礼法之争” 沈家本张之洞纲常礼教近代西方刑法清末“礼法之争”是指发生在晚清修律过程中,围绕沈家本制定、伍廷芳执笔的《大清新刑律草案》,清廷形成了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杨度为首的法理派长达数年的激烈争论,历史上称为“礼法之争”。
双方争论的核心是新刑律的指导思想是传统礼教还是近代西方刑法理论。
坚持传统礼教的称礼教派,又称礼派、礼治派、家族主义派、国情派;采用西方刑法理论的叫法理派,亦称法派、法治派、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
“礼法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的矛盾冲突。
实际上无论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都未能科学地协调西法和国情的关系。
清末“礼法之争”距今已一个多世纪,但双方争论的主题却历久弥新,传统法与现代法、法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今天中国法治建设继续思考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因此回顾和反思“礼法之争”,对两派之观点进行反思和评价,对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无启示意义。
“礼法之争”的过程围绕清末修律产生的“礼法之争”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修律之目标、立法之宗旨、法律之原理、罪名之废立、罚则之轻重等。
其中最重大、最关键的论题是礼教存废以及礼法关系问题。
礼法之争的具体内容和重点则随草案制定、修改、审核及议决过程而变化,其过程和争论焦点如下:沈家本与张之洞的论争。
1906年,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律之旨”,改革原有的诉讼审判方式,拟定《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这是一部迥异于传统诉讼审判原则和制度的新型诉讼法典。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的内容及意义清末礼法之争啊,这可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呢。
咱得先知道这礼法之争是咋回事儿。
简单来说,就是在清末修律的时候,新派和礼教派之间有了很大的分歧。
新派呢,想引进西方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让咱的法律变得更现代。
礼教派呢,就觉得咱老祖宗传下来的礼教可不能丢,这法律得和礼教相结合。
比如说在关于“干名犯义”这个事儿上就有大分歧。
新派觉得这种封建时期的罪名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应该废除。
礼教派就不干了,他们觉得这可是维护家族伦理关系的重要东西啊,要是没了,那不就乱套了吗?就好比一个家庭本来有一套很传统的规矩,突然有人说这规矩都得扔了,按照外面新的方式来,家里的老人肯定觉得不行啊,这就像礼教派的想法一样。
还有关于子孙违反教令这一规定,新派觉得这不该在刑法里规定,这更多的是家庭内部教育的事儿。
礼教派就觉得这是天经地义要管的,子孙要是不听长辈的话,就得用法律来约束,不然礼教何在呢?这就像一群人在讨论一个孩子不听话该咋办。
新派说这是家里自己教育的事儿,别用法律插手。
礼教派就说,这要是不管,就像放羊一样,孩子不就没了约束,到处乱跑了吗?再说说这礼法之争的意义吧。
这可太重要了。
它就像是一场新旧观念的大碰撞。
新派的想法呢,其实是想让咱中国的法律走向世界,和国际接轨。
这就像一个封闭的小村子,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想把这些好东西引进来,让村子变得更好。
礼教派的存在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守护的礼教也是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要是全扔了,就像把自己的根给砍了,这多可怕呀。
通过这场礼法之争,咱中国的法律开始慢慢转型了。
新的法律思想开始一点点地渗透进来。
就好比给一个老旧的房子慢慢地换上新的部件,虽然过程很艰难,但是在一点点地变好。
这让咱们后来的法律发展有了新的方向,不再只是拘泥于传统的礼教约束。
而且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到底该怎么平衡传统和现代呢?从社会层面来说,这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以前大家都觉得礼教就是天,不可违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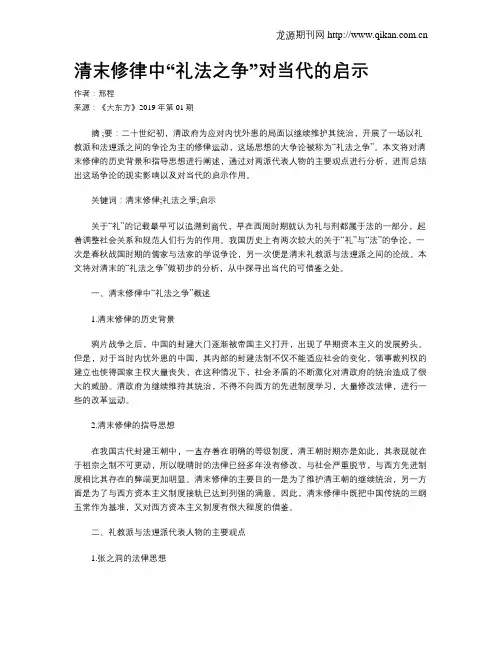
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对当代的启示作者:邢程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01期摘 ;要: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以继续维护其统治,开展了一场以礼教派和法理派之间的争论为主的修律运动,这场思想的大争论被称为“礼法之争”。
本文将对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进行阐述,通过对两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出这场争论的现实影响以及对当代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清末修律;礼法之爭;启示关于“礼”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早在西周时期就认为礼与刑都属于法的一部分,起着调整社会关系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有两次较大的关于“礼”与“法”的争论,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的学说争论,另一次便是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之间的论战。
本文将对清末的“礼法之争”做初步的分析,从中探寻出当代的可借鉴之处。
一、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概述1.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封建大门逐渐被帝国主义打开,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
但是,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其内部的封建法制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领事裁判权的建立也使得国家主权大量丧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清政府为继续维持其统治,不得不向西方的先进制度学习,大量修改法律,进行一些的改革运动。
2.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一直存着在明确的等级制度,清王朝时期亦是如此,其表现就在于祖宗之制不可更动,所以晚晴时的法律已经多年没有修改,与社会严重脱节,与西方先进制度相比其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
清末修律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继续统治,另一方面是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已达到列强的满意。
因此,清末修律中既把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作为基准,又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大程度的借鉴。
二、礼教派与法理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1.张之洞的法律思想张之洞生长于封建官僚家庭,深受传统礼教的影响,在其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之后更是深知礼教对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对礼教大力推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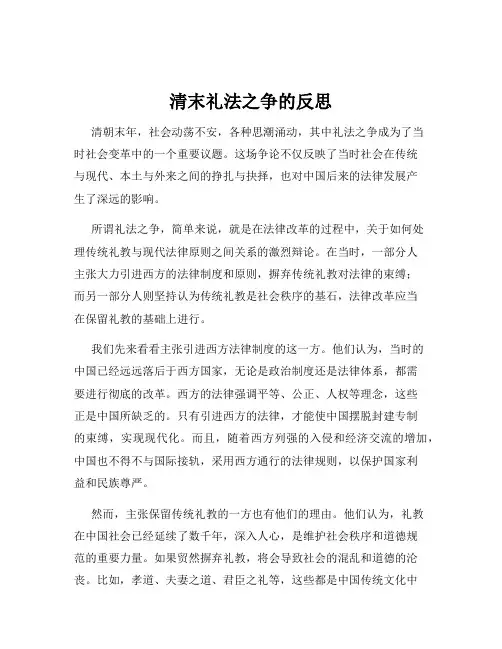
清末礼法之争的反思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潮涌动,其中礼法之争成为了当时社会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场争论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挣扎与抉择,也对中国后来的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礼法之争,简单来说,就是在法律改革的过程中,关于如何处理传统礼教与现代法律原则之间关系的激烈辩论。
在当时,一部分人主张大力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摒弃传统礼教对法律的束缚;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认为传统礼教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法律改革应当在保留礼教的基础上进行。
我们先来看看主张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的这一方。
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法律体系,都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西方的法律强调平等、公正、人权等理念,这些正是中国所缺乏的。
只有引进西方的法律,才能使中国摆脱封建专制的束缚,实现现代化。
而且,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经济交流的增加,中国也不得不与国际接轨,采用西方通行的法律规则,以保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然而,主张保留传统礼教的一方也有他们的理由。
他们认为,礼教在中国社会已经延续了数千年,深入人心,是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重要力量。
如果贸然摒弃礼教,将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道德的沦丧。
比如,孝道、夫妻之道、君臣之礼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轻易抛弃。
而且,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而应该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实际进行改革。
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主张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的一方,看到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弊端和落后之处,希望通过改革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过于激进地追求西化,可能导致法律与社会的脱节。
而主张保留传统礼教的一方,虽然强调了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传统礼教中存在的封建糟粕和不合理之处,容易阻碍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从更深层次来看,清末礼法之争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简述清末“礼法之争”一、背景清末变法的礼法之争,是指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曾任湖广总督、后任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及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
二、双方1、法理派。
该派以沈家本为代表,主张运用“国家主义”等政法理论来改革中国旧法律制度,因在修订《大清新刑律》、《大青民事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常用西方国家的“通行法理”来对抗保守派的攻击,因而被称为“法理派”。
2、礼教派。
该派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主张修订新法律应当“浑道德与法律与一体”,不应偏离中国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因而被称为“礼教派”。
三、焦点1、“干名犯义”的废存“干名犯义”是指子孙控告父母、祖父母的行为。
“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得相首匿”,亲属相互告言“亏教伤情,莫此为大”,因此在明清律中“干名犯义”属“十恶”之条。
鉴于此,礼教派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因此“干名犯义”之条大于礼教之事,是传统伦理的根本所在,因而应当在新刑律有所反应。
而法理派根据西方通行法理,指出“干名犯义”属“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
2、“存留养亲”的废存“存留养亲”指“亲老丁单”时即凶犯属系独子、父母年老有病、家中无其他男丁,考虑到其父母无人奉养,又无其它男丁继承宗嗣,经皇帝特许,可免其死罪,施以其它处罚,令其回家“奉养其亲”的制度。
礼教派认为“存留养亲”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从新律中排除。
沈家本则认为“古无罪人留养之法”,且指出嘉庆六年上谕中曾表示:“是承祀、留养、非以施仁,实以长奸,转以诱人犯法”。
3、“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的定罪量刑礼教派认为内,无夫奸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而亲属相奸属于“大犯礼教之事”,因此应当在新律中对上述情况有特别规定。
法理派则认为,“无夫妇女犯奸,欧洲法律并无治罪之文”,因此“此事有伤风化,当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之中”。
文 史 漫 笔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内忧外患不绝,内外交困地度过了五十来年后,感到若不对现行法制作些变改,便不利于继续统治。
于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被迫于1901年下诏变法,准备立宪,实行新政,任命刑部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公使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要求:“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订考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沈家本立即组织修订法律馆,开始工作,并于1907年担任修订法律大臣兼资政院副总裁。
在他的主持下,修订法律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制定法律、修改旧律、译介外国法律、创办法律学堂、制定法院编制法。
清末修律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近代法学思想相互融合和冲突的过程。
贯穿修律活动始终的,是以张之洞、劳乃宣等人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之间的礼、法之争。
其形式是围绕着《大清刑事诉讼法》、《大清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展开争论,其核心则是一方要维护封建宗法制,一方则要引入君主立宪制。
这场礼法之争,具体表现在以沈家本和杨度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共有三次。
1906年,沈家本主持制定了《刑事诉讼法》,采用律师制度及陪审团制度及其他一些西方法律,当即遭到张之洞等人的反对。
张之洞认为使父子异财、兄弟析产、夫妇分资,是“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道。
”理由是“中国立教首重亲亲,定律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有罚……”并以《奸非罪章》中无和奸无夫妇治罪条例,指为败坏礼教,得到很大响应。
同时,张之洞认为,律师制度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陪审制度使“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词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
”应该看到,张之洞对律师、陪审制度的反对,是很有些道理的。
引进任何一种制度,不仅要看这种制度的长短优劣,同时还要看引进后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它的存在和发展。
评述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清末时期,发生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争论,叫做“礼法之争”。
这可不是一般的争论,它关系到当时的法律怎么制定。
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以前,大家都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和礼仪来生活。
比如说,见到长辈要行礼,要尊重长辈的意见。
这些礼仪,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人们的生活都串起来了。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外国的交流越来越多。
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法律,和的老规矩不太一样。
这时候,清朝的一些人就觉得,也得改改法律,要学习外国的一些好东西。
于是,就开始了修律。
这修律,就像给一件旧衣服缝缝补补,让它变得更合适。
但是,问题就来了。
有一些人觉得,老祖宗的礼仪和规矩可不能丢,法律得按照这些来制定。
比如说,按照传统的礼仪,儿子要孝顺父母,要是儿子不孝顺,那就是大错特错,法律就得惩罚他。
就像有个小故事,有个小男孩,总是对自己的父母大喊大叫,不尊重他们。
按照老规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小男孩做得不对,应该受到批评教育。
所以,支持传统礼仪的人就觉得,法律得把这些都考虑进去。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觉得,现在时代变了,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法律理念。
外国的法律更注重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有自己的权利。
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不能随便被别人打断或者惩罚。
这就像在学校里,每个小朋友都有发言的机会,老师不能因为某个小朋友说得不好就不让他说话。
所以,这部分人就希望法律能多考虑这些方面,不要总是按照老规矩来。
这两拨人,就开始争论起来。
支持传统礼仪的人觉得,要是不把礼仪放在法律里,那社会就会乱套,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相处了。
而支持学习外国法律的人则说,要是不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国就会落后,会被其他国家欺负。
这场争论,就像两个小朋友在争论到底是吃巧克力好还是吃糖果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不过,这场“礼法之争”最后也没有一个完全确定的结果。
但是,它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法律到底应该怎么制定,才能让大家都过得更好。
第四章清末法制变革评价与启示第一节清末法制变革结果及评价一、法制变革的先进性清末法制变革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是清政府为了挽救行将就木的专制统治而被迫做出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
虽然在变革开始后不久,清王朝就灭亡了,法制变革对清王朝而言,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它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始,被誉为世纪法律变革之里程碑。
从这个角度看,清末法制变革颇具进步意义。
(一)法制变革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律“诸法合体”的状况,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与法律制度。
中国的历代法典发展到清朝,虽然“体例复杂,体系详备”但是一直遵守“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原则,不存在独立的法律体系,公法和私法、实体法与诉讼法相互交织在一起,缺乏一个科学的结构。
这次变革在所修订法典的外在形式上移植了西方法律体系和制度,不仅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还引进了西方法律编纂的某些原则和制度。
1、西方的法典编纂体例。
彻底废除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体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大陆法系的编订体例,如《大清新刑律》正式以总则、分则分篇,《大清民律草案》仿德国民法,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5篇,这些都体现了近代法律体例。
此外,还把实体法、程序法分开,民法、商法等从刑律中剥离出来,各自单独成篇,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基本符合近代法制规范的法律体系。
从此中国有了实体法和程序法、刑法和民法、商法、行政法的明确分工。
尽管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是,在客观上全面突破了原有的“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
这样的法律体系就为中国建立完全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石,并且,它也影响到了在此之后的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通过这次法制变革,中国基本上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
2、西方的宪政制度。
清末礼法之争的反思作者:谈知诚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25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沈家本将修订法律馆制定的新刑律草案呈递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这部草案对于旧律有着彻底的根本性地修改,主要体现在:(1)在体例上,彻底抛弃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分为总则、分则两编,只规定专属刑法范畴的内容;(2)在刑种上确立了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附加刑为褫夺公权、没收财产的新刑罚体系;(3)在技术上大量引进西方法律术语和刑法制度,有些术语甚至直接借用了日本刑法术语,比如犹豫行刑(即缓刑)、假出狱(即假释)等。
正是由于新刑律从刑法思想到刑法制度都彻底抛弃了旧律,激起了一些以维护封建礼教为己任的官员的强烈不满,他们与沈家本为代表的修订法律馆围绕着干名犯义、存留养亲、无夫奸、亲属相奸、子孙违犯教令、卑亲属对尊亲属适用正当防卫等条款的存废展开了一场大争论,史称“礼法之争”。
一、礼法之争的实质礼法之争从实质上说是中西法律文化之争、家庭伦理和个人权利自由之争、新法和旧法之争。
在礼法之争的过程中,法理派运用的理论武器是他们已经接受的西方法律文化,而礼教派用来回击的是他们长期认可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以从实质上是中西法律文化之争。
虽然礼教派在礼法之争中又争取回了一些被法理派废除的封建礼教,但从中华民族整体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看,这些礼教纲常终究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法理派所提倡的近现代刑法被延续了下来。
中西法律文化的不同在于前者以家族为本位,强调集体的规范,后者则以权利为本位,强调个人的自由。
因为要以家族为本位、要强调集体规范,所以要建立一套维护家族利益、集体利益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臣不能犯君、子不能犯父、妻不能犯夫,尊卑长幼良贱有序;而要以权利为本位、要强调个人自由,就要承认人人平等、承认义务不过是保障权利的手段。
法理派正是希望通过新刑律能将中国从家族本位引向权利本位,对于这一点,杨度早有言明:“与国家主义日近,而与家族主义日远,此即新律精神及主义所在,即与旧律之区别所在。
清末礼教派的法理念一、目前学界对清末“礼法之争”的研究与定性鸦片战争以来,与世界已有相当隔膜的中国社会揭开了旨在“自强”的近代变革的序幕,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入侵的打击,清廷终于从本能的反应转到主动自觉的回应,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启动了。
1902年至1911年,清政府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在厉行“新政”和“仿行宪政”的招牌下,进行了一次在此次政治变革中居重要地位的修律活动。
在修律的过程中,爆发了一场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和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法理派,就《刑事民事诉讼法》,特别是《大清新刑律》的立法指导思想,实质上也是清末整个修律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大争论,这次大争论在近代法律史上被称为“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中双方争论的核心在于:鉴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应以资产阶级法律的原理原则为主要指导思想,还是应以封建礼教为主要指导思想制定新法。
正如当时的《法政浅说报》所说的那样?quot;新刑律为采取世界最新之学理,与我国旧律统系及所持主义不同,故为我国“礼教派”所反对。
“礼法之争,随新律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以下的一个发展过程:(一)审议《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
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模范列强”,制订了中国法律史上的第一个单行诉讼法规-《刑事民事诉讼法》,废弃封建的苛法滥刑,礼教与法律相分离,采用资产阶级的律师制度和陪审制度。
这个诉讼法遭到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反对。
张之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大肆攻击,全盘否定这个法典。
清廷循张之洞之议,宣告废除尚未公布的《刑事民事诉讼法》。
(二)签注《大清新刑律草案》。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和十二月,沈家本先后奏上《大清新刑律草案》和该草案的案语,清政府交由各部院及督抚签注意见。
《大清新刑律草案》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法律与礼教相分离的精神,如量刑定罪不依“服制”,废除旧律中“犯罪存留养亲”的规定,故杀子孙无减轻,妻妾殴夫无加重,“无夫奸”不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