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朝鲜王朝华夷思想
- 格式:doc
- 大小:53.00 KB
- 文档页数:5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朝鲜王国眼中的清政府:冒充中华天朝的“蛮族”导语:近日,思想史家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面世。
明代灭亡后的清代,李朝朝鲜使者记载的燕行文献显示,“中国”已经近日,思想史家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面世。
明代灭亡后的清代,李朝朝鲜使者记载的燕行文献显示,“中国”已经“华夷变态”,是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
他们记录下他们感到不寻常的种种现象,又在想象异域悲情的情感驱使下,李代桃僵地为大明王朝招魂,处处搜寻大清帝国的种种怪现状。
这似乎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东亚以及中国,重看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史,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等问题。
“小中华”性质凌驾于“蛮夷”性质之上如果我们站在朝鲜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不是从1840年、1860年或1900年开始的,而是从1644年开始的。
朝鲜夹在中央王朝(天朝)、日本和满蒙各部落之间,处境最为微妙,对认同政治最为敏感。
明清“华夷变态”对李朝“中国观”的刺激之深,充分体现在“朝天录”和“燕行录”的“正名”意识上。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一个京师,两种表述。
天是京师的升级,燕是京师的贬抑。
朝鲜对前明的忠诚通过两种途径抬高了自身的地位,划定了“他者”的边界。
首先,朝鲜的“小中华”性质凌驾于大清的“蛮夷”性质之上。
其次,朝鲜士大夫的孤忠耿耿羞辱了二三其德的江南士大夫。
东海君子国的优美形象就此树立,不同于而且高于任何其他邻邦。
这种边界意识仍然是儒家式的,以礼乐文教为标准,不能视为近代以来的国族建构,但无疑已经具备了某些共同体的性质。
共同体意识萌发的特征之一就是内外有别。
在这方面,李朝与清朝的关系表现得特别生活常识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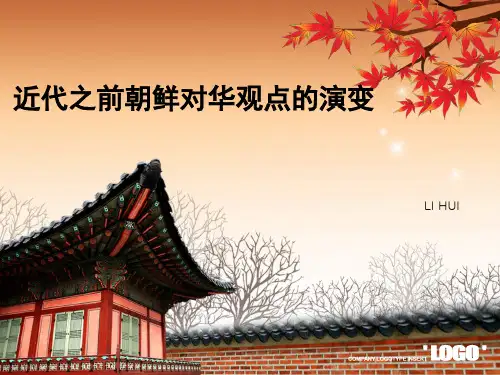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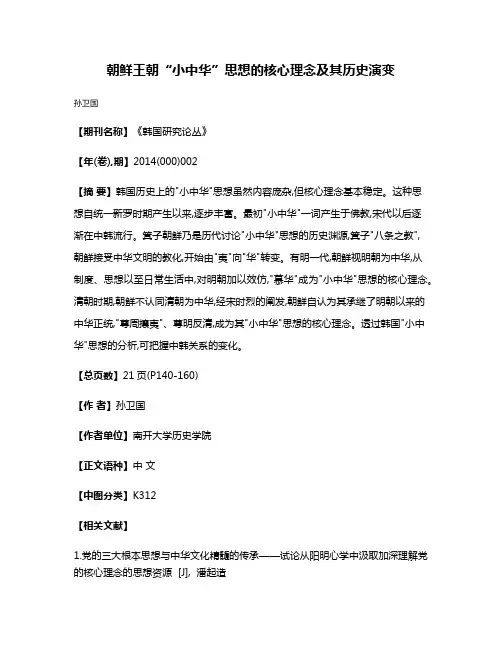
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历史演变孙卫国【期刊名称】《韩国研究论丛》【年(卷),期】2014(000)002【摘要】韩国历史上的"小中华"思想虽然内容庞杂,但核心理念基本稳定。
这种思想自统一新罗时期产生以来,逐步丰富。
最初"小中华"一词产生于佛教,宋代以后逐渐在中韩流行。
箕子朝鲜乃是历代讨论"小中华"思想的历史渊源,箕子"八条之教",朝鲜接受中华文明的教化,开始由"夷"向"华"转变。
有明一代,朝鲜视明朝为中华,从制度、思想以至日常生活中,对明朝加以效仿,"慕华"成为"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
清朝时期,朝鲜不认同清朝为中华,经宋时烈的阐发,朝鲜自认为其承继了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尊周攘夷"、尊明反清,成为其"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
透过韩国"小中华"思想的分析,可把握中韩关系的变化。
【总页数】21页(P140-160)【作者】孙卫国【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312【相关文献】1.党的三大根本思想与中华文化精髓的传承——试论从阳明心学中汲取加深理解党的核心理念的思想资源 [J], 潘起造2.文化视域下的朝鲜"小中华"思想研究:以《小华外史》为中心 [J], 刘喜涛3.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历史演变 [J], 孙卫国4.中华仁爱思想的历史演变、当代价值及时代发展 [J], 安丽梅5.中华仁爱思想的历史演变、当代价值及时代发展 [J], 安丽梅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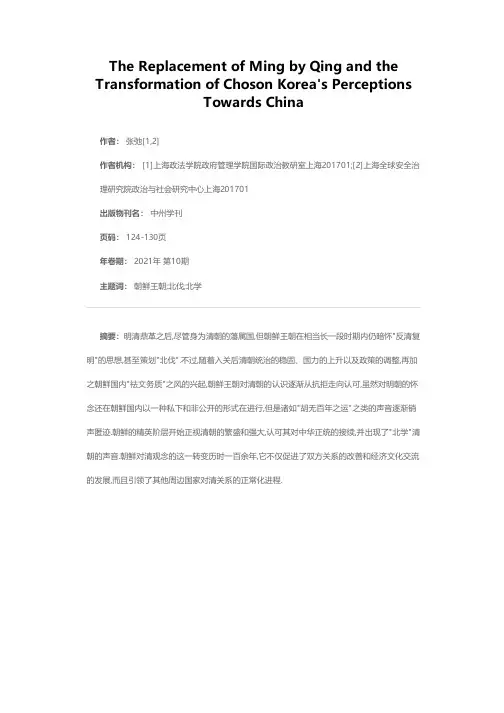
The Replacement of Ming by Q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oson Korea's Perceptions
Towards China
作者: 张弛[1,2]
作者机构: [1]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教研室上海201701;[2]上海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院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上海201701
出版物刊名: 中州学刊
页码: 124-130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10期
主题词: 朝鲜王朝;北伐;北学
摘要:明清鼎革之后,尽管身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朝鲜王朝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暗怀"反清复明"的思想,甚至策划"北伐".不过,随着入关后清朝统治的稳固、国力的上升以及政策的调整,再加之朝鲜国内"祛文务质"之风的兴起,朝鲜王朝对清朝的认识逐渐从抗拒走向认可,虽然对明朝的怀念还在朝鲜国内以一种私下和非公开的形式在进行,但是诸如"胡无百年之运"之类的声音逐渐销声匿迹.朝鲜的精英阶层开始正视清朝的繁盛和强大,认可其对中华正统的接续,并出现了"北学"清朝的声音.朝鲜对清观念的这一转变历时一百余年,它不仅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改善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而且引领了其他周边国家对清关系的正常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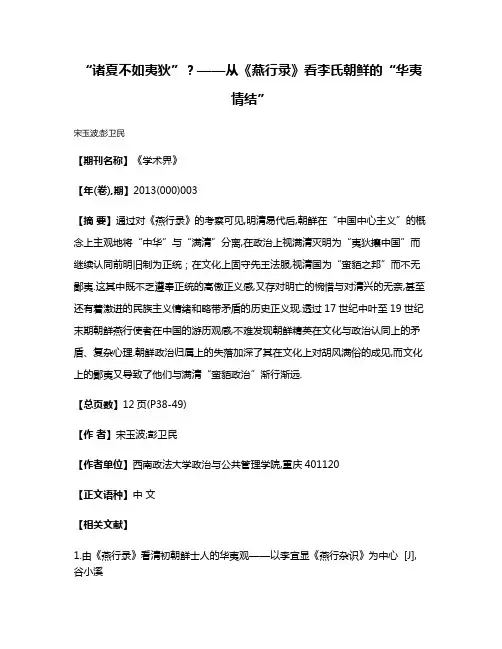
“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
情结”
宋玉波;彭卫民
【期刊名称】《学术界》
【年(卷),期】2013(000)003
【摘要】通过对《燕行录》的考察可见,明清易代后,朝鲜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上主观地将“中华”与“满清”分离,在政治上视满清灭明为“夷狄攘中国”而继续认同前明旧制为正统;在文化上固守先王法服,视清国为“蛮貊之邦”而不无鄙夷.这其中既不乏遵奉正统的高傲正义感,又存对明亡的惋惜与对清兴的无奈,甚至还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略带矛盾的历史正义现.透过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期朝鲜燕行使者在中国的游历观感,不难发现朝鲜精英在文化与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复杂心理.朝鲜政治归属上的失落加深了其在文化上对胡风满俗的成见,而文化上的鄙夷又导致了他们与满清“蛮貊政治”渐行渐远.
【总页数】12页(P38-49)
【作者】宋玉波;彭卫民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1120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J], 谷小溪
2.《日知录》“素夷狄行乎夷狄”条校读记 [J], 张京华
3.明代朝鲜使节对永平府夷齐庙的认知——以《燕行录全集》为中心 [J], 张循; 李玥
4.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汉族士人形象——以朝鲜北学派人士的《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J], 徐东日
5.“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考证 [J], 朱咏梅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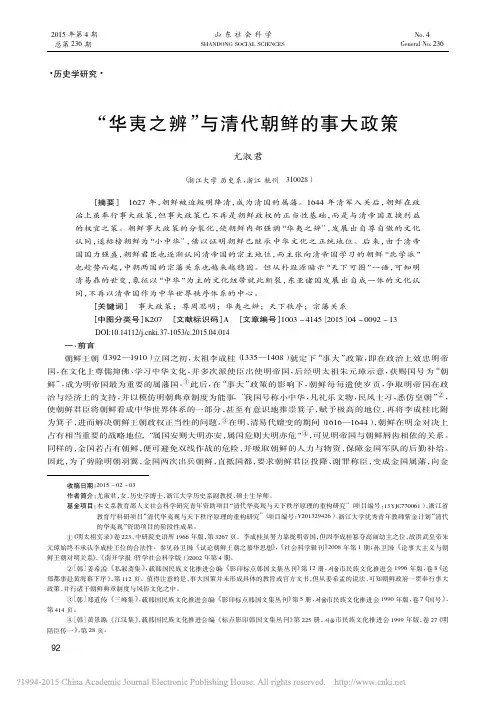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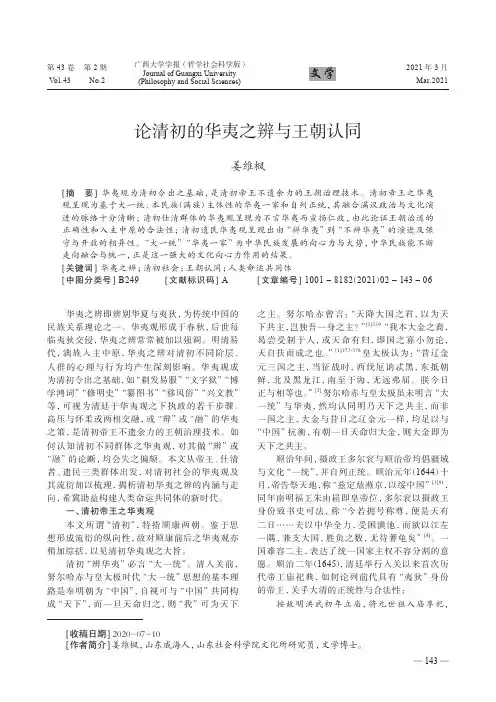
— 143 —论清初的华夷之辨与王朝认同[摘 要] 华夷观为清初令出之基础,是清初帝王不遗余力的王朝治理技术。
清初帝王之华夷观呈现为基于大一统、本民族(满族)主体性的华夷一家和自列正统,其融合满汉政治与文化演进的脉络十分清晰;清初仕清群体的华夷观呈现为不言华夷而宣扬仁政,由此论证王朝治道的正确性和入主中原的合法性;清初遗民华夷观呈现出由“辨华夷”到“不辨华夷”的演进及保守与开放的相异性。
“大一统”“华夷一家”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向心力与大势,中华民族能不断走向融合与统一,正是这一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华夷之辨;清初社会;王朝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图分类号] B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182(2021)02 – 143 – 06 华夷之辨即辨别华夏与夷狄,为传统中国的民族关系理论之一。
华夷观形成于春秋,后世每临夷狄交侵,华夷之辨常常被加以强调。
明清易代,满族入主中原,华夷之辨对清初不同阶层、人群的心理与行为均产生深刻影响。
华夷观成为清初令出之基础,如“剃发易服”“文字狱”“博学鸿词”“修明史”“纂图书”“移风俗”“兴文教”等,可视为清廷于华夷观之下执政的若干步骤。
高压与怀柔或两相交融,或“辨”或“融”的华夷之策,是清初帝王不遗余力的王朝治理技术。
如何认知清初不同群体之华夷观,对其做“辨”或“融”的论断,均会失之偏颇。
本文从帝王、仕清者、遗民三类群体出发,对清初社会的华夷观及其流衍加以梳理,揭析清初华夷之辨的内涵与走向,希冀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一、清初帝王之华夷观本文所谓“清初”,特指顺康两朝。
鉴于思想形成流衍的纵向性,故对顺康前后之华夷观亦稍加综括,以见清初华夷观之大旨。
清初“辨华夷”必言“大一统”。
清入关前,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基本理路是奉明朝为“中国”,自视可与“中国”共同构成“天下”,而一旦天命归之,则“我”可为天下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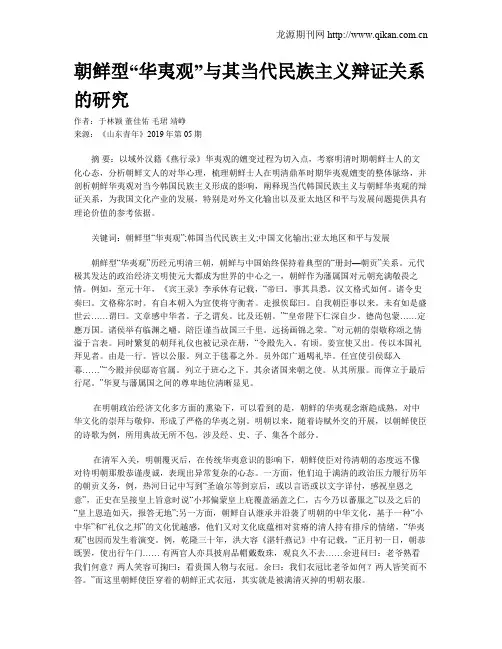
朝鲜型“华夷观”与其当代民族主义辩证关系的研究作者:于林颖董佳佑毛珺靖峥来源:《山东青年》2019年第05期摘要:以域外汉籍《燕行录》华夷观的嬗变过程为切入点,考察明清时期朝鲜士人的文化心态,分析朝鲜文人的对华心理,梳理朝鲜士人在明清鼎革时期华夷观嬗变的整体脉络,并剖析朝鲜华夷观对当今韩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阐释现当代韩国民族主义与朝鲜华夷观的辩证关系,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外文化输出以及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问题提供具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朝鲜型“华夷观”;韩国当代民族主义;中国文化输出;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朝鲜型“华夷观”历经元明清三朝,朝鲜与中国始终保持着典型的“册封—朝贡”关系。
元代极其发达的政治经济文明使元大都成为世界的中心之一,朝鲜作为藩属国对元朝充满敬畏之情。
例如,至元十年,《宾王录》李承休有记载,“帝曰。
事其具悉。
汉文格式如何。
诸令史奏曰。
文格称尔时。
有自本朝入为宣使将守衡者。
走报俟邸曰。
自我朝臣事以来。
未有如是盛世云……谓曰。
文章感中华者。
子之谓矣。
比及还朝。
”“皇帝陛下仁深自少。
德尚包蒙……定應万国。
诸侯举有临渊之嚼。
陪臣谨当故国三千里。
远扬画锦之荣。
”对元朝的崇敬称颂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繁复的朝拜礼仪也被记录在册,“令殿先入。
有顷。
姜宣使又出。
传以本国礼拜见者。
由是一行。
皆以公服。
列立于毯幕之外。
员外郎广通喝礼毕。
任宣使引侯邸入幕……”“今殿并侯邸寄官属。
列立于班心之下。
其余诸国来朝之使。
从其所服。
而俾立于最后行尾。
”华夏与藩属国之间的尊卑地位清晰显见。
在明朝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熏染下,可以看到的是,朝鲜的华夷观念渐趋成熟,对中华文化的崇拜与敬仰,形成了严格的华夷之别。
明朝以来,随着诗赋外交的开展,以朝鲜使臣的诗歌为例,所用典故无所不包,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部分。
在清军入关,明朝覆灭后,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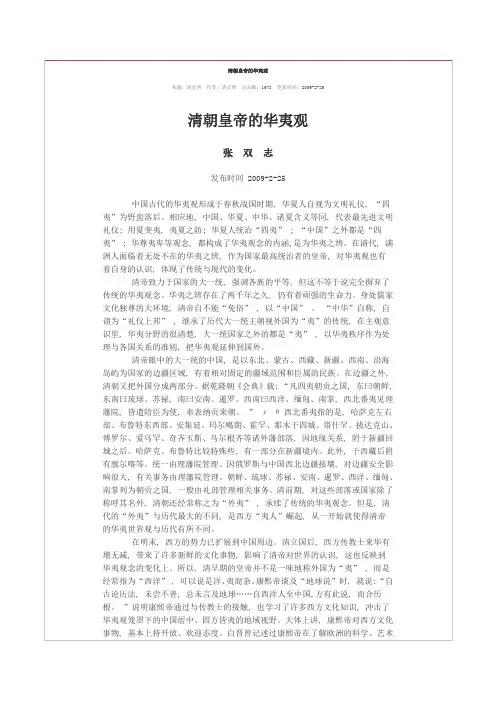
清朝皇帝的华夷观来源:清史所作者:清史所点击数:1673 更新时间:2009-2-25清朝皇帝的华夷观张双志发布时间 2009-2-25中国古代的华夷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人自视为文明礼仪, “四夷”为野蛮落后。
相应地, 中国、华夏、中华、诸夏含义等同, 代表最先进文明礼仪; 用夏变夷, 夷夏之防; 华夏人统治“四夷” ; “中国”之外都是“四夷” ; 华尊夷卑等观念, 都构成了华夷观念的内涵,是为华夷之辨。
在清代, 满洲人面临着无处不在的华夷之辨,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 对华夷观也有着自身的认识, 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变化。
清帝致力于国家的大一统, 强调各族的平等, 但这不等于说完全摒弃了传统的华夷观念。
华夷之辨存在了两千年之久, 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身处儒家文化独尊的大环境, 清帝自不能“免俗” , 以“中国” 、“中华”自称, 自诩为“礼仪上邦” , 继承了历代大一统王朝视外国为“夷”的传统, 在主观意识里, 华夷分野的很清楚, 大一统国家之外的都是“夷” , 以华夷秩序作为处理与各国关系的准则, 把华夷观延伸到国外。
清帝眼中的大一统的中国, 是以东北、蒙古、西藏、新疆、西南、沿海岛屿为国家的边疆区域, 有着相对固定的疆域范围和臣属的民族。
在边疆之外, 清朝又把外国分成两部分。
据乾隆朝《会典》载: “凡四夷朝贡之国, 东曰朝鲜, 东南曰琉球、苏禄, 南曰安南、暹罗。
西南曰西洋、缅甸、南掌, 西北番夷见理藩院, 皆遣陪臣为使, 奉表纳贡来朝。
” εθ西北番夷指的是,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等诸外藩部落, 因地缘关系, 附于新疆回城之后。
哈萨克、布鲁特比较特殊些, 有一部分在新疆境内。
此外, 于西藏后附有廓尔喀等。
统一由理藩院管理。
因俄罗斯与中国西北边疆接壤, 对边疆安全影响很大, 有关事务由理藩院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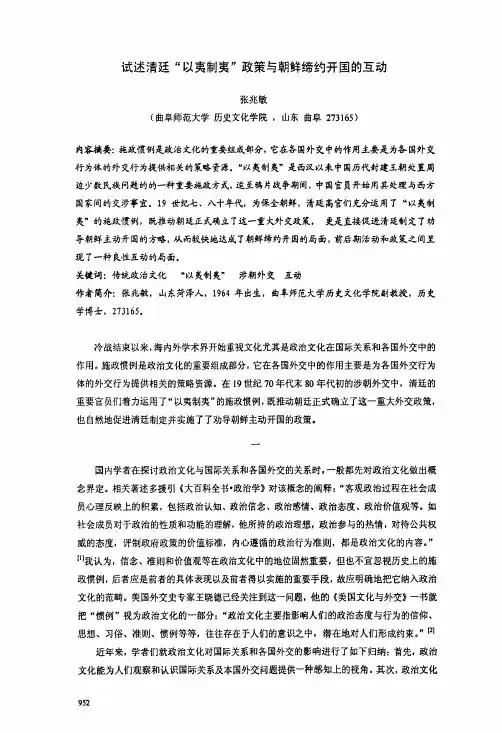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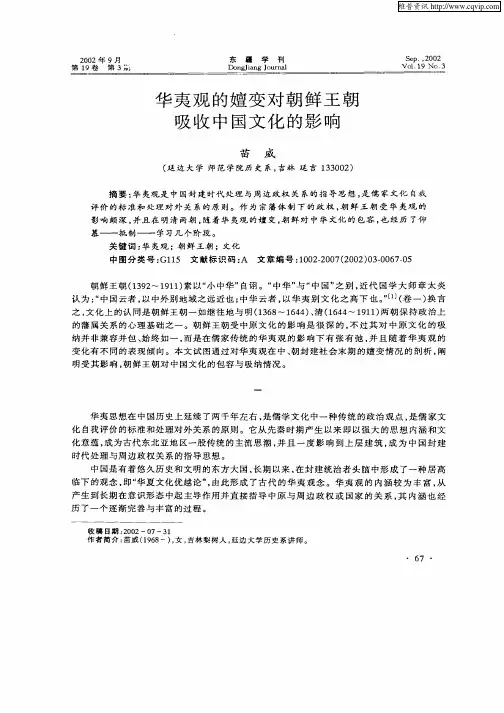
明清之际朝鲜王朝的华夷心态李竞恒1780年六月,一支朝鲜王国的使团北上到达了鸭绿江边。
使团中的成员朴趾源在日记的开头处这样写道:“曷不称崇祯?将渡江,故讳之也。
曷讳之?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称崇祯也。
曷私称崇祯?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
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四十余年。
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
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热河日记》,朴趾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页1)。
末尾的纪年是“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
在这里,作者不无无奈地表示自已在进入清朝领土后必需小心隐匿对“大明”,“中华”怀念炽热感情的原因。
明代最后一位皇帝之死在朝鲜王国的集体记忆中被赋予了一种无比崇高悲壮的伤感与伟大象征意义。
作者表示,并非不梦想“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但是,弱小的朝鲜王国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只能守护着韩半岛梦想着“明室”这一华夷秩序的神圣象征仍存在于韩半岛的三千里江山。
这是明代灭亡一百三十六年后的事,距南明永历帝之死也已有一百一十九年了。
实际上,在整个清朝,自诩为明朝孤臣的朝鲜士人出使北京到达义州渡鸭水之前,往往都会出现一些非常复杂的心态。
不仅仅是朴趾源在渡过鸭水的前夜写出了“江以外清人也”的感慨,此种以鸭水作为明朝与清朝、华夏与夷狄、文明与野蛮的边界心态,在朝鲜使臣中非常普遍。
1711年,闵镇远渡过鸭水的前夜,就将对岸描述为“胡天”、“胡山”,并表示“无处不伤心”。
1778年出使的的蔡济恭,将鸭水称为“胡地才分江一带”。
将要进入野蛮胡人统治的世界,他们的内心普遍感到不安、凄凉,甚至畏惧。
(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第64—77页)作为对明清易代背后的文化,伦理价值判断的华夷想象一直贯穿了整个清代朝鲜入贡使团的记忆。
进入曾经是高度文明的“华夏”而今却“终为羯胡之窟”的中国领土,尤其容易唤起朝鲜使者与文人强烈的情感记忆与伤感体验。
朝鲜汉籍里的中国:满清是“夷狄”不配称天朝张伯伟从高丽末期到朝鲜末期,朝鲜半岛每年都会派使臣来中国。
到了清代,他们认为满清是“夷狄”,不配称天朝,所以几乎不用“朝天录”,而改成“燕行录”或“燕行记”。
这类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至少有500多种。
近代朝鲜资料图张伯伟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近著有《东亚汉籍研究论集》、《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等等。
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形象,如果从比较文学意义上看,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就被称作“形象学”,这和我们今天要谈的很相契合。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自觉的意识之中。
这个形象是对两种类型的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或者非文学的一种表述。
我们不妨举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15世纪后半以下的朝鲜,除了在外交文书上面称日本,通常都是用倭国、倭人,把日本看成是在文化上比较低劣、野蛮的区域,从而形成了一个“日本小国观”。
1526到1534年之间所绘的《混一历代国都疆理图》现存韩国高丽大学仁村纪念馆,这幅地图把日本画得非常小。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地图并不总是客观的反映,在这里它是一种意志的反映,在绘图者的意志当中,日本就是一个远远小于朝鲜半岛的“小日本”。
在这样一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来讨论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形象。
为便于说明,我将之分为四个阶段:(一)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到高丽时代,大概是14世纪末(1392年)之前。
(二)朝鲜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差不多15到17世纪的中叶,相当于中国的明代。
(三)大概有100年,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
(四)18世纪中叶以下。
核心观点从高丽末期到朝鲜末期,朝鲜半岛每年都会派使臣来中国。
在长达500多年无间断的历史中,这些使团的成员几乎都会留下他们的使行记录。
域外中华:李氏朝鲜主体意识的萌生作者:管习化来源:《青年时代》2019年第15期摘要:“华夷之辨”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朝鲜王朝受朱子学影响颇深,囿于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民族文化,对于这一命题的接受有着缓慢而又复杂的过程。
本文试图以韩儒“子欲居九夷”章注疏为文本,从地理位置、道之有无、夷狄之有君等角度,考察明清易代之际李氏王朝对于“华夷之辨”的接受史。
关键词:接受史;华夷之辨;子欲居九夷;韩国儒者华夷观在东亚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对于华夷观的解释,自古以来大致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是重视华夷之辨,强调“尊中华,攘夷狄”二是重视华夷一家,强调春秋大一统。
华夷观的这两种思想倾向在秦汉以后,随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秩序的建立、发展,不仅影响到中国,同样也影响到东亚各国的国家观念和国际秩序认识。
但是到了近代,在西势东渐的冲击下,中华秩序也受到西方万国公法秩序的挑战,最后因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导致了中华秩序的崩溃。
在这一过程中,韩国等周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检讨、清算传统的事大关系。
在日常语言中,人们习惯将“中国”与“中华”等同,但在中国哲学的视域下,二者有本质区别,“中國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此处既言明“中国”与“中华”的区别,又提及“华夷之辨”。
朝鲜王朝与中国在政治上是宗藩关系,文化上也深受儒学熏染,但对于“华夷之辨”并非主动接受,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演变。
近年来,“华夷之辨”成为朝鲜--韩国学的一个热点。
中、日、韩等国学者从不同视角解析华夷观念的产生背景、内容、流变过程和意义,进一步探讨了“天朝礼治体系”、“华夷秩序”、“华夷情结”、“华夷变态”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围绕着“华夷之辨”展开探讨。
总体上看,韩国方面主要是对“小中华”的论述,以满足本国的政治、文化需求;中国方面的研究则以儒家典籍为中心,多维度阐释其正统地位;而日本方面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细读,将朝鲜的燕行使与通信使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From "the Boundary Beween Liao and Yan" to "the Boundary Beween Hua and Yi" : Shanhaiguan as Described by Korean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作者: 黄普基
作者机构: 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210093
出版物刊名: 清史研究
页码: 28-36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4期
主题词: 山海关;华夷思想;朝鲜使者
摘要:明朝时期,朝鲜人并无以山海关为界、关内外华夷不同的“分界”概念。
但明清易代,政治局面的巨变促使朝鲜人大大地强化了华夷分界的意识,以致最终认定山海关为明晰
的“界线”。
具体而言,清时期朝鲜人对关内的种种自然、人文景观往往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宽
容和肯定;相反,对关外却持着过于苛刻的否定态度。
然而,有趣的是,清时期朝鲜人对关内
外分界意识逐渐强化之时,两地的文化差距实际上却在日益缩小。
而且,关内永平府与关外辽
西之间,其相似性甚至大于差异性。
此外,对于中华秩序占主导地位的东亚来说,华夷之辨除表示了文化、地域和种族上的分别外,其实也表示了政治秩序上中心与周边的分别。
在现实的中华秩序之下,存于藩属地位的政权要想成为中华正统是不可能的。
当时朝鲜在事实上对清事大,奉清正朔,在中华秩序中既然处于藩属的地位,即使不被视为夷狄,也很难超越“小中华”的地位。
所以洪大容说,“我东之慕效中国,忘其为夷也久矣。
虽然,比之中国而方之,其分自在也。
”李种徽认识到,中国人之所以始终以朝鲜为东夷,是因为朝鲜一直处于外服的缘故。
虽然《春秋》主张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是如果不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楚、吴那样,参与中国区域之内的会盟、征伐,则很难被彻底视为中华。
要改变这种状况,李种徽提出的办法是设法将朝鲜文化介绍到中国,使中国人知道海外尚有邹鲁之乡。
朝鲜在中国周边国家中确实是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是如果根据朝鲜士大夫的文化自尊意识而认为朝鲜是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则是将历史虚像当成了事实。
当时对于朝鲜士大夫来说,相对于中国值得自豪的一是保持了明朝的衣冠制度,一是崇奉朱子学,以为朝鲜继承了性理学的正统,所谓“道统在东”。
就衣冠制度而言,朝鲜后期的实学者曾对其意义有所批评。
李溟(1681~1763)即指出,“今天下悉已髡发,而惟一片东韩尚保旧制,非力有以自全,此殆天意在也。
”朴齐家(1750~1805)也说,清允许朝鲜保持原来的衣冠制度,“自我论之,幸则幸矣,而由彼之计,不过利我之不通中国也”。
所以他们认为朝鲜得以保衣冠之旧也不是什么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所以,洪大容指出,中国人虽然剃发胡服,与满洲族无别,但仍为中华故家后裔,朝鲜人虽以阔袖大冠,沾沾自喜,乃不过“海上之夷人”,贵贱不可相等,他反对朝鲜士大夫趁中国人遭受变乱之际,落井下石,隐然以中华正统自居。
朴趾源在比较了朝鲜和中国之后也说,“以我较彼,固无寸长,而独以一撮之结,自贤天下曰: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也,其山川则罪之以腥膻,其人民则辱之以犬羊,其言语则诬之以侏离,并与其中国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则亦将何所仿而行之耶?”而且,由于朝鲜过分注重衣冠制度等象征中华的礼乐文物,试图恢复中华古制,反而限制了朝鲜文化的发展。
朝鲜时期北学派的华夷天下观陈毅立【内容提要】17世纪,朝鲜国内受“西学东渐”与明清更迭的影响,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华夷天下观发生了动摇,形成了为匡复“中华文明”而欲讨伐清朝的北伐派和提倡只要“其法优秀,亦可拜其为师”的北学派。
洪大容和朴趾源是北学派的代表,他们在吸收西方的天文、地理知识后,否定了象征华夷秩序的“天圆地方”说。
在此基础上,前者提出了“华夷一也”的主张,而后者虽提倡“北学”,但内心充满了“尊明排清”的情绪,将“中华文化”与清朝统治区别对待,形成了独特的华夷天下观。
近代以后,部分学者将北学派的华夷观置于实学范畴予以再诠释,并从中透析出“近代”“民族”元素,但是“北学”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性问题却遭到等闲视之。
【关键词】北学派朴趾源洪大容华夷天下观实学【作者简介】陈毅立,博士,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有倭国使者呈献国书,其中出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等词句,隋炀帝看后不悦,怒曰:“蛮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从倭国立场出发,此国书似有公然挑战当时东亚国际秩序、谋求对等外交之意,但在隋朝皇帝眼中,日本与其他慕名来朝的小藩无异。
尽管内心气恼,隋炀帝依然命令鸿胪卿接待倭国使者,同时为宣扬上国威仪,决定派使者回访倭王。
同年,百济因不胜高丽侵扰,遣使入隋,奉表-169-请师。
隋炀帝依据“失礼入刑”原则,最终决意征伐。
究其原因,亦与“往岁为高丽不供职供,无人臣礼”有关。
毋庸置疑,当时东亚世界已经形成了建立在中华意识基础上的华夷天下秩序,伴随这种秩序的具体制度被称为朝贡与册封。
高增杰指出,由于各自构成自给自足系统,国家关系中缺少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因,文明中心又存在文明与化外的观念,因此国家间交往的主要表征是:周边国家“朝贡”,表示臣服;文明王朝赐予物产,表示“怀柔”和认可。
这一时期,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征伐和战乱,但这个体系基本上保证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明末清初朝鲜王朝的华夷想象作者:李竞恒1780年六月,一支朝鲜王国的使团北上到达了鸭绿江边。
使团中的成员朴趾源在日记的开头处这样写道:“曷不称崇祯?将渡江,故讳之也。
曷讳之?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称崇祯也。
曷私称崇祯?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
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四十余年。
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
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热河日记》,朴趾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页1)。
末尾的纪年是“崇祯百五十六年癸卯”。
在这里,作者不无无奈地表示自已在进入清朝领土后必需小心隐匿对“大明”,“中华”怀念炽热感情的原因。
明代最后一位皇帝之死在朝鲜王国的集体记忆中被赋予了一种无比崇高悲壮的伤感与伟大象征意义。
作者表示,并非不梦想“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但是,弱小的朝鲜王国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只能守护着韩半岛梦想着“明室”这一华夷秩序的神圣象征仍存在于韩半岛的三千里江山。
这是明代灭亡一百三十六年后的事,距南明永历帝之死也已有一百一十九年了。
作为对明清易代背后的文化,伦理价值判断的华夷想象一直贯穿了整个清代朝鲜入贡使团的记忆。
进入曾经是高度文明的“华夏”而今却“终为羯胡之窟”的中国领土,尤其容易唤起朝鲜使者与文人强烈的情感记忆与伤感体验。
早在1683年,即台湾最后一支汉族抵抗满洲贵族的武装力量被消灭的这一年,朝鲜一位叫金锡胄的使者途经山海关丰润县附近的榛子店,见到墙上有一首旧日的题诗:“椎髻空怜昔人妆,红裙换着越罗裳。
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
”题诗者是一位名叫季文兰的江南女子丈夫被满洲人杀害后,还被掳到沈阳。
金锡胄看到诗后便写了两首和诗。
此后,“榛子店”就成为一个象征,朝鲜使者凡从此经过,都会在此留下诗文,通过对这一个孤弱苦难的江南汉族女子的同情而缅怀其象征背后的“大明”与华夏认同。
直到1862年,朝鲜使者崔秉翰仍在此处留下了题诗。
而此时,距明清易代已两百多年,距朝鲜被日本吞并也仅半个世纪了(葛兆光《想象异域悲情》,载《读书》2005年7期)。
对贯穿整个清代的朝鲜文化心态来说,明代的覆亡被赋予了太沉重的痛楚含义,因之也不难理解以反对“北伐派”(朝鲜国内激进的反满清势力)而著称的朴趾源为何会在日记的首页留下这样激昂的文字了。
明代本身是在“驱逐靼虏”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朱元璋《讨元檄文》:“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在华夷秩序的天道伦理之应然性中,“华夏”即意味着对高尚的文化与族群正义性,对中华的彻骨认同即是对文化与族群尊严的彻骨认同。
因此,朝鲜也向来乐于自已“小中华”的美称。
“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朝鲜实录,成宗》)”。
“山川险隘,人民多贫。
只以稍遵礼俗,自古中国亦许之小中华(《湛轩书外集,杭传尺椟》卷二)”。
这种对“小中华”深切认同的价值正是基于世界伦理法则的最终体认之上。
因此,对“中华”的伤害与侮辱,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宇宙法则的挑战。
而朝鲜王国对作为“中华”的明帝国则是“朝鲜忠顺天朝,从来已远”(《宣祖实录》三十二年)。
“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孝宗实录》十四年十二月丙戌)。
“本朝之于大明,君臣而父子也”(《孝宗实录》十六年七月丙戌)。
“中朝于我国至尊也``````我国贡献至薄,而中朝赐赉极厚”(《仁祖实录》十四年庚申)。
“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劈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
所谓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也。
而君臣之中,受恩罔极,又未有若本朝之于皇明也”(《孝宗实录》八年十月丙戌)。
朝鲜对明朝的深刻感情除了“三百年受恩”的文化,经济等重要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壬辰战争中,明帝国为了保护朝鲜王国而出兵救援,与丰臣秀吉的精锐日军血战,付出巨大代价,先后开支军费达2400万两的白银,死亡士兵数万人(《中韩交流三千年》,陈尚胜,中华书局,1997年,页41)。
此种“中华”字小的恩义对朝鲜举国上下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因此“天朝再造之恩不为不厚,朝鲜图报之义不敢不诚”(《宣祖实录》三十二年二月已巳)。
明代灭亡一百多年后,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写道:“呜呼!皇明,吾上国也。
上国之于属邦其锡赉之物虽微如丝毫,若陨自天,荣动一域,庆流万世;而其奉温谕,虽数行之扎,高若云汉,惊若雷霆,感若时雨”(《热河日记》,页187)。
一丝一毫的恩义,在这个自古“知礼”的“小邦”那里都可以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恩情结,而付出巨大牺牲去拯救这个国家将使朝鲜会以怎样一种巨大的感恩与景仰交织的心理去认同大明就不难想象了。
在《燕行录全集》中,记载着“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朝鲜使臣在北京看到崇祯皇帝旧笔迹“会同馆”三个字后的感慨与联想:“窃惟我国家事大明近三百年。
况在壬辰之乱,我宣庙大王特盟神宗皇帝恤小救难之恩,则我国之有今日,秋毫皆帝力也。
今来故都,去亡年才四十七岁。
左右肆不惟不改,至如会同馆字旧构宛然`````”(《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刘顺利,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46)伤感之情无以言表。
早在明代灭亡之前的1627年,满洲贵族即大规模入侵过韩半岛一次,要求朝鲜放弃明朝年号,并“约为兄弟之国”,韩人称为“丁卯虏乱”。
1636年,满洲贵族又再次入侵朝鲜,击溃了朝鲜所有的官方和民间抵抗力量,捕获王室宗亲七十六人,朝鲜被迫投降。
此一事件韩人称为“丙子虏乱”。
这两次大入侵与破坏与明朝对朝鲜的恩义形成了巨大而鲜明的对比,更加深了朝鲜对“靼虏”的仇恨。
正是丙子虏乱使朝鲜在形式上成为了满清的属国,并从此在对清文书上不再使用明朝年号。
古代东亚建立在宇宙论政治神学文化背景下的年号“正朔”所代表的天命权力之神圣性正是合法性的思想依据。
“普天之下都要依照王朝历法所制定的时间节奏进行生产生活,并依靠文治武功将王朝历法推行远方。
奉正朔成为王朝治权实现的重要标志。
这使天文历法在王朝政治的层面上表现为一种政治神学的知识形态”(韦兵《头顶的星空和身边的日子》,载《读书》2007年3期)。
在华夷想象的宇宙论天命正统政治神学之时空秩序中,华夏年号的“正朔”所代表的真理与正义性即是天所生发的依据“理”,而在蛮族军事暴力的压迫下使用蛮族非“正朔”年号则是“势”。
丙子虏乱后的两年,朝鲜对年号的处理态度为“是时内外文书多用清国年号,而祭享祝辞,仍用大明年号”(《仁祖实录》十六年正月朔乙丑)。
朝鲜迫于满洲贵族的野蛮暴力而在形式上屈从,私下则仍称清皇为“犬羊禽兽” ,“胡皇”,称清使为“虏使”。
而国王则对陪臣们表示“绝不书崇德年号”(《仁祖实录》二十三年)。
“丁丑以来,宗庙祝辞,朝臣告身,只书岁月,不用年号,此乃大行大王所定之制也”(《孝宗实录》八年已亥)。
总之,在年号问题上,对外用满清年号是因为“势”,对内用大明年号则是基于“义”。
或者宁使用中性的干支记年月也不使用满清年号。
正如朴趾源所说,朝鲜举国上下“皆能尊崇祯以存中国也”。
在满洲贵族的军队入侵朝鲜的过程中,朝鲜对明朝一直怀着等待拯救的信念,甚至打算国家灭亡也不对满洲人投降。
丙子虏乱中,国王的态度是“唯望父母邦之来救矣”(《仁祖实录》十四年九月朔壬寅)。
“壬辰之役,微天朝则不能复国,至今君臣上下,相保而不为鱼者,其谁之力也?今虽不幸而大祸迫至,犹当有陨而无二也。
不然,将何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乎?”(《仁祖实录》十四年十月丁丑)。
宁愿灭亡也不愿背离华夏,重要的理由还有无法面对“天下后世”。
这一切的动机背后是巨大的伦理决择与价值判断。
朝鲜“宁获过于大国(指满清),不忍负皇明”(《仁祖实录》十五年正月辛亥)。
而在战败被迫投降之后,即使是“身在满营心在汉”,朝鲜国王仍在自身心理的道德自律感上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感。
“正月朔乙丑,上于宫庭设位西向中原哭拜,为皇明也。
”(《仁祖实录》十六年正月朔乙丑)。
而在其子孝宗国王的记载中,这位仁祖大王每当“语及皇明,至于呜咽不能言”(《孝宗实录》元年五月甲寅)。
由于此种内在的道德压力与深切自责,朝鲜国甚至在发生了虚造的传言据说“(日本)关白执政辈,以朝鲜与鞑靼合,莫不骇愤,将欲兴师而来”(《仁祖实录》二十五年二月丙子)。
惊恐之中,正是集体意识中对道德要求的执着与自责意识。
对于丙子虏乱,其后一百多年后朝鲜人朴趾源的记载中,仍对当时明朝的态度心怀感激:“崇祯丙子清兵之来也,烈皇帝闻我东被兵,急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
洪范奏官兵出海,而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
帝以继祖不能协图匡救,下诏切责之。
当是时,天子内不能救福,楚,襄,唐之急,而外切属国之忧,其救焚拯溺之意,有加于骨肉之邦”(《热河日记》,页61)。
崇祯十七年,明皇帝“殉社稷”,满洲军队侵入中国。
这对朝鲜王国来说同样是天崩地坼一样的巨变。
举其一百余年后韩人吴熙常在他《小华外史序》中对满洲入侵中华的态度为例:“今夫夷狄主入中华,举先王疆土人民,尽化为旙裘湩酪之俗。
自古猾夏之祸,未有若是之烈,乃阴道之极盛也。
”(《半岛唐风:朝韩作家与中国文化》,页76)。
而朝鲜则在此背景下秘密拟定了北伐满清,恢复明朝的政治计划。
早在仁祖国王时,朝鲜就曾计划过请日本出兵讨伐满清,“宜假道朝鲜,出送援兵````邻国之道,岂以假道为惮?”(《仁祖实录》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
为了反抗满清,甚至不再计较壬辰战争中的仇敌日本。
而孝宗大王则更是坚定的反清派。
他将反清的“明国九义士”收罗在左右,日夜与之谋划反清。
“王尝叹曰,寡人北征之志何日忘之!其于兵少力弱,愿闻公等之计。
福吉流涕对曰,大王英武之资,秉《春秋》之义,兴仁义之师,沛然北伐,孰能御之?天下忠义之士,孰不鼓动而景从乎?王动容嘉纳。
”(牟元珪《明清时期中国移民朝鲜半岛考》,自《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342)。
其子显宗大王时记录也有:“先王尝以若得十万精兵,可以伸大义于天下”(《显宗实录》元年十一月戍午)。
为了与南明小朝庭进行联系,朝鲜计划通过忠于“大义名分”的文官出任济洲太守从水路交通南明“则我朝君臣上下数十年痛迫冤欎之诚意,或可一朝而达于天朝矣”(《孝宗实录》八年冬十月乙亥)。
对于起兵抗清可能因失败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孝宗认为“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
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
”通过这一行为本身去实践其价值意义的追求,即使灭亡,意义也实现了。
这种对观念的执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清代朝鲜华夷观念的集体想象。
通过武力直接发动反清复明这一主张长期存在于朝鲜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