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刘禹锡天人观
- 格式:ppt
- 大小:234.50 KB
- 文档页数: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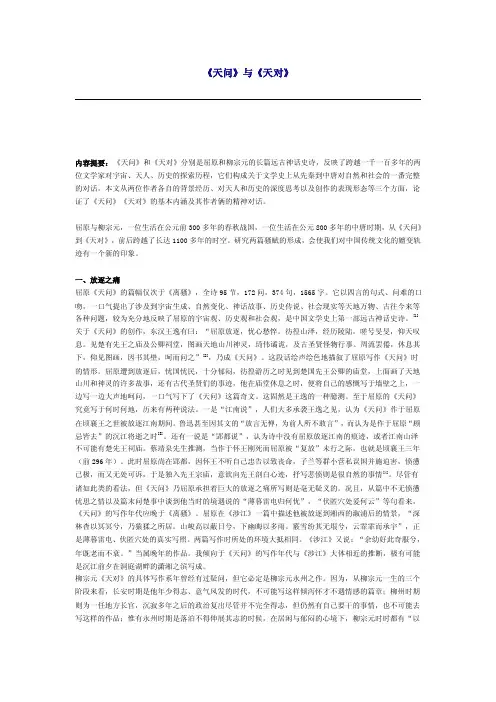
《天问》与《天对》内容提要:《天问》和《天对》分别是屈原和柳宗元的长篇远古神话史诗,反映了跨越一千一百多年的两位文学家对宇宙、天人、历史的探索历程,它们构成关于文学史上从先秦到中唐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番完整的对话。
本文从两位作者各自的背景经历、对天人和历史的深度思考以及创作的表现形态等三个方面,论证了《天问》《天对》的基本内涵及其作者俩的精神对话。
屈原与柳宗元,一位生活在公元前300多年的春秋战国,一位生活在公元800多年的中唐时期,从《天问》到《天对》,前后跨越了长达1100多年的时空。
研究两篇骚赋的形成,会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轨迹有一个新的印象。
一、放逐之痛屈原《天问》的篇幅仅次于《离骚》,全诗95节,172问,374句,1565字。
它以四言的句式、问难的口吻,一口气提出了涉及到宇宙生成、自然变化、神话故事、历史传说、社会现实等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等各种问题,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屈原的宇宙观、历史观和社会观,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远古神话史诗。
[1]关于《天问》的创作,东汉王逸有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
彷徨山泽,经历陵陆。
嗟号旻旻,仰天叹息。
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伟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
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2],乃成《天问》。
这段话绘声绘色地描叙了屈原写作《天问》时的情形。
屈原遭到放逐后,忧国忧民,十分郁闷,彷徨游历之时见到楚国先王公卿的庙堂,上面画了天地山川和神灵的许多故事,还有古代圣贤们的事迹,他在庙堂休息之时,便将自己的感慨写于墙壁之上,一边写一边大声地呵问,一口气写下了《天问》这篇奇文。
这固然是王逸的一种臆测。
至于屈原的《天问》究竟写于何时何地,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是“江南说”,人们大多承袭王逸之见,认为《天问》作于屈原在顷襄王之世被放逐江南期间。
鲁迅甚至因其文的“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而认为是作于屈原“顾忌皆去”的沉江将逝之时[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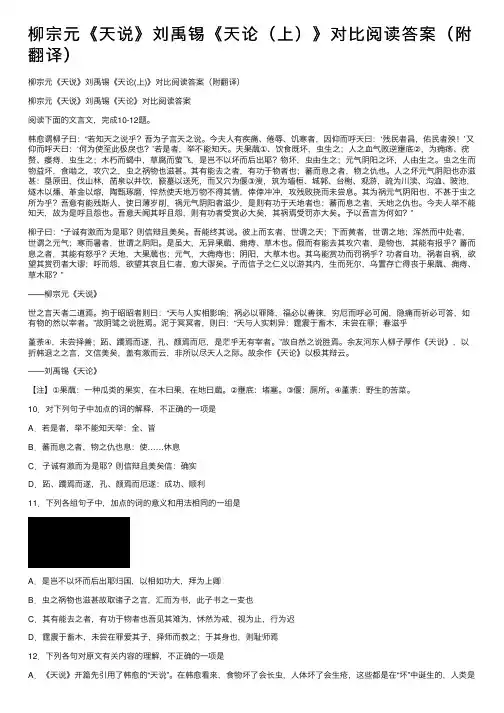
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上)》对⽐阅读答案(附翻译)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上)》对⽐阅读答案(附翻译)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对⽐阅读答案阅读下⾯的⽂⾔⽂,完成10-12题。
韩愈谓柳⼦⽈:“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天之说。
今夫⼈有疾痛、倦辱、饥寒者,因仰⽽呼天⽈:‘残民者昌,佑民者殃!’⼜仰⽽呼天⽈:‘何为使⾄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
夫果蓏①、饮⾷既坏,⾍⽣之;⼈之⾎⽓败逆壅底②,为痈疡、疣赘、瘘痔,⾍⽣之;⽊朽⽽蝎中,草腐⽽萤飞,是岂不以坏⽽后出耶?物坏,⾍由⽣之;元⽓阴阳之坏,⼈由⽣之。
⾍之⽣⽽物益坏,⾷啮之,攻⽳之,⾍之祸物也滋甚。
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蕃⽽息之者,物之仇也。
⼈之坏元⽓阴阳也亦滋甚:垦原⽥,伐⼭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为偃③溲,筑为墙桓、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以燔,⾰⾦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倖倖冲冲,攻残败挠⽽未尝息。
其为祸元⽓阴阳也,不甚于⾍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使⽇薄岁削,祸元⽓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蕃⽽息之者,天地之仇也。
今夫⼈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
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矣,其祸焉受罚亦⼤矣。
予以吾⾔为何如?”柳⼦⽈:“⼦诚有激⽽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
吾能终其说。
彼上⽽⽞者,世谓之天;下⽽黄者,世谓之地;浑然⽽中处者,世谓之元⽓;寒⽽暑者,世谓之阴阳。
是虽⼤,⽆异果蓏、痈痔、草⽊也。
假⽽有能去其攻⽳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果蓏也;元⽓,⼤痈痔也;阴阳,⼤草⽊也。
其乌能赏功⽽罚祸乎?功者⾃功,祸者⾃祸,欲望其赏罚者⼤谬;呼⽽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谬矣。
⼦⽽信⼦之仁义以游其内,⽣⽽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耶?”——柳宗元《天说》世之⾔天者⼆道焉。
拘于昭昭者则⽈:“天与⼈实相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徕,穷厄⽽呼必可闻,隐痛⽽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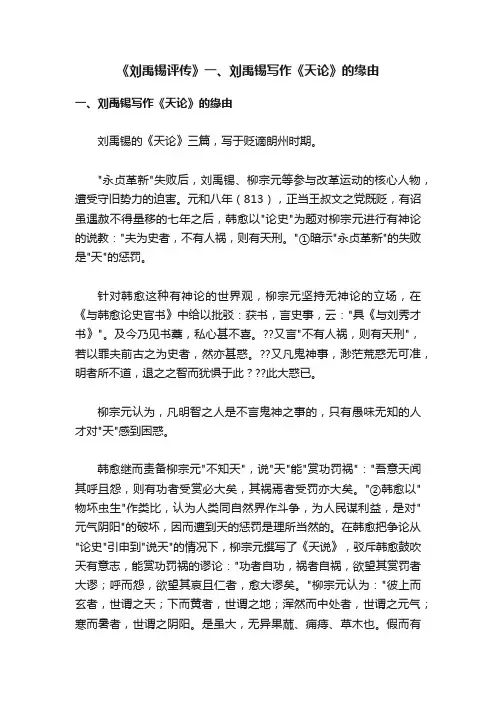
《刘禹锡评传》一、刘禹锡写作《天论》的缘由一、刘禹锡写作《天论》的缘由刘禹锡的《天论》三篇,写于贬谪朗州时期。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参与改革运动的核心人物,遭受守旧势力的迫害。
元和八年(813),正当王叔文之党既贬,有诏虽遇赦不得量移的七年之后,韩愈以"论史"为题对柳宗元进行有神论的说教:"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①暗示"永贞革新"的失败是"天"的惩罚。
针对韩愈这种有神论的世界观,柳宗元坚持无神论的立场,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给以批驳: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
及今乃见书藁,私心甚不喜。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此大惑已。
柳宗元认为,凡明智之人是不言鬼神之事的,只有愚味无知的人才对"天"感到困惑。
韩愈继而责备柳宗元"不知天",说"天"能"赏功罚祸":"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
"②韩愈以"物坏虫生"作类比,认为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为人民谋利益,是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因而遭到天的惩罚是理所当然的。
在韩愈把争论从"论史"引申到"说天"的情况下,柳宗元撰写了《天说》,驳斥韩愈鼓吹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的谬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柳宗元认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
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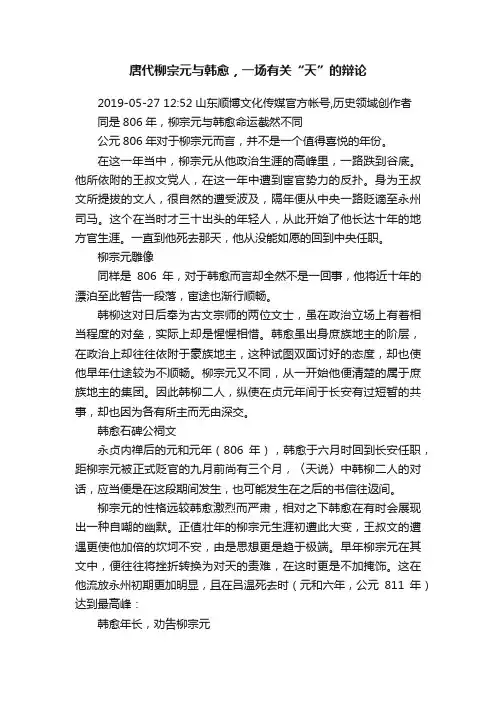
唐代柳宗元与韩愈,一场有关“天”的辩论2019-05-27 12:52山东顺博文化传媒官方帐号,历史领域创作者同是806年,柳宗元与韩愈命运截然不同公元806年对于柳宗元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喜悦的年份。
在这一年当中,柳宗元从他政治生涯的高峰里,一路跌到谷底。
他所依附的王叔文党人,在这一年中遭到宦官势力的反扑。
身为王叔文所提拔的文人,很自然的遭受波及,隔年便从中央一路贬谪至永州司马。
这个在当时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地方官生涯。
一直到他死去那天,他从没能如愿的回到中央任职。
柳宗元雕像同样是806年,对于韩愈而言却全然不是一回事,他将近十年的漂泊至此暂告一段落,宦途也渐行顺畅。
韩柳这对日后奉为古文宗师的两位文士,虽在政治立场上有着相当程度的对垒,实际上却是惺惺相惜。
韩愈虽出身庶族地主的阶层,在政治上却往往依附于豪族地主,这种试图双面讨好的态度,却也使他早年仕途较为不顺畅。
柳宗元又不同,从一开始他便清楚的属于庶族地主的集团。
因此韩柳二人,纵使在贞元年间于长安有过短暂的共事,却也因为各有所主而无由深交。
韩愈石碑公祠文永贞内禅后的元和元年(806年),韩愈于六月时回到长安任职,距柳宗元被正式贬官的九月前尚有三个月,〈天说〉中韩柳二人的对话,应当便是在这段期间发生,也可能发生在之后的书信往返间。
柳宗元的性格远较韩愈激烈而严肃,相对之下韩愈在有时会展现出一种自嘲的幽默。
正值壮年的柳宗元生涯初遭此大变,王叔文的遭遇更使他加倍的坎坷不安,由是思想更是趋于极端。
早年柳宗元在其文中,便往往将挫折转换为对天的责难,在这时更是不加掩饰。
这在他流放永州初期更加明显,且在吕温死去时(元和六年,公元811年)达到最高峰:韩愈年长,劝告柳宗元身为虚长柳宗元几岁的老大哥韩愈,看见这位他一向欣赏的朋友这般的怨天尤人,也只能够这样委婉的劝告他:韩愈口中的“仰而呼天”者,正符合了当时柳宗元不稳定的心理状态,指的当然是柳宗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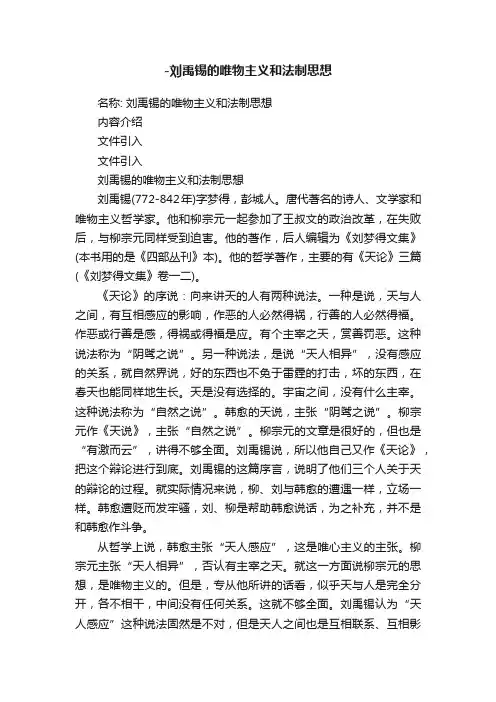
-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和法制思想名称: 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和法制思想内容介绍文件引入文件引入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和法制思想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彭城人。
唐代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
他和柳宗元一起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改革,在失败后,与柳宗元同样受到迫害。
他的著作,后人编辑为《刘梦得文集》(本书用的是《四部丛刊》本)。
他的哲学著作,主要的有《天论》三篇(《刘梦得文集》卷一二)。
《天论》的序说:向来讲天的人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天与人之间,有互相感应的影响,作恶的人必然得祸,行善的人必然得福。
作恶或行善是感,得祸或得福是应。
有个主宰之天,赏善罚恶。
这种说法称为“阴骘之说”。
另一种说法,是说“天人相异”,没有感应的关系,就自然界说,好的东西也不免于雷霆的打击,坏的东西,在春天也能同样地生长。
天是没有选择的。
宇宙之间,没有什么主宰。
这种说法称为“自然之说”。
韩愈的天说,主张“阴骘之说”。
柳宗元作《天说》,主张“自然之说”。
柳宗元的文章是很好的,但也是“有激而云”,讲得不够全面。
刘禹锡说,所以他自己又作《天论》,把这个辩论进行到底。
刘禹锡的这篇序言,说明了他们三个人关于天的辩论的过程。
就实际情况来说,柳、刘与韩愈的遭遇一样,立场一样。
韩愈遭贬而发牢骚,刘、柳是帮助韩愈说话,为之补充,并不是和韩愈作斗争。
从哲学上说,韩愈主张“天人感应”,这是唯心主义的主张。
柳宗元主张“天人相异”,否认有主宰之天。
就这一方面说柳宗元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
但是,专从他所讲的话看,似乎天与人是完全分开,各不相干,中间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不够全面。
刘禹锡认为“天人感应”这种说法固然是不对,但是天人之间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这种情况,刘禹锡称之为“天人交相胜”。
他们三个人所讨论的问题,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关系的问题,即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天人之际”的问题。
宗教迷信对于自然界作了歪曲,认为有一个主宰,能够干预人事,赏善罚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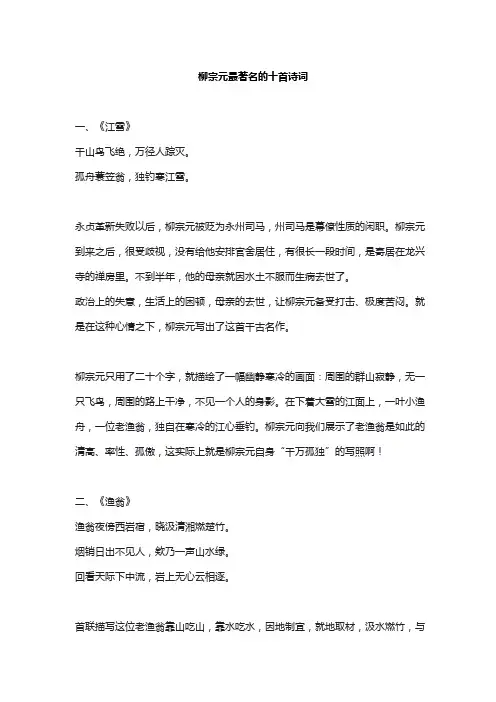
柳宗元最著名的十首诗词一、《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州司马是幕僚性质的闲职。
柳宗元到来之后,很受歧视,没有给他安排官舍居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寄居在龙兴寺的禅房里。
不到半年,他的母亲就因水土不服而生病去世了。
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困顿,母亲的去世,让柳宗元备受打击、极度苦闷。
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柳宗元写出了这首千古名作。
柳宗元只用了二十个字,就描绘了一幅幽静寒冷的画面:周围的群山寂静,无一只飞鸟,周围的路上干净,不见一个人的身影。
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渔舟,一位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
柳宗元向我们展示了老渔翁是如此的清高、率性、孤傲,这实际上就是柳宗元自身“千万孤独”的写照啊!二、《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首联描写这位老渔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汲水燃竹,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实际上是柳宗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写照。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这是该诗的千古名句,“欸乃”两字用得极为传神,有声有色,使整个画面动了起来,极富美感。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出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里:“云无心而出岫”一句,表现了柳宗元淡泊闲逸的心境和清静恬适的生活情趣。
柳宗元通过描写在山青水绿间独往独来的“渔翁”,表明自己领悟了人生的真意,宁可孤芳自赏,也决不同流合污。
三、《零陵早春》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
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
永州地处江南,春天来的比长安早。
热闹忙碌的早春,引起了柳宗元的思乡之情。
可惜,他被贬在永州,是被软禁和监管的,因此,他借春风来寄付自己的思乡情,恳切希望春风把自己带回故乡。
“殷勤入故园”的“殷勤”一词,写出了柳宗元思乡之浓烈、期盼之殷切,是全诗的点睛之笔。
爱与思、盼与望交织在一起,这大概是他到永州后最强烈的情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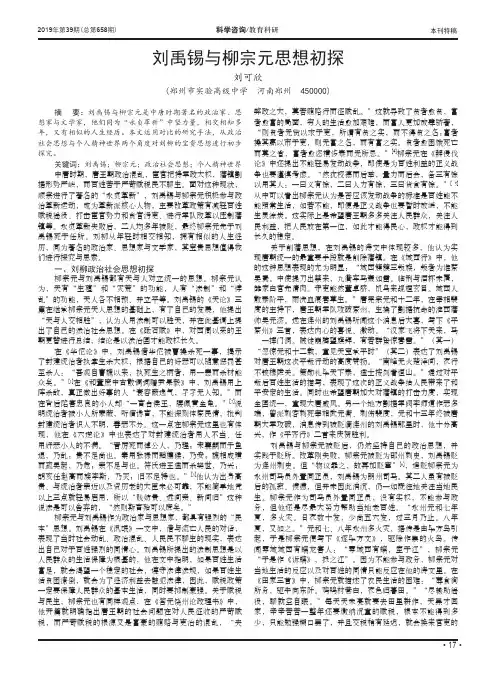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审查大纲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大纲一、概述
㈠矿区位置、隶属关系和企业性质。
如为改扩建矿山, 应说明矿山现状、
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㈡编制依据
(1简述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及与有关方面对项目的意向性协议情况。
(2 列出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所依据的主要基础性资料的名称。
如经储量管理部门认定的矿区地质勘探报告、选矿试验报告、加工利用试验报告、工程地质初评资料、矿区水文资料和供水资料等。
对改、扩建矿山应有生产实际资料, 如矿山总平面现状图、矿床开拓系统图、采场现状图和主要采选设备清单等。
二、矿产品需求现状和预测
㈠该矿产在国内需求情况和市场供应情况
1、矿产品现状及加工利用趋向。
2、国内近、远期的需求量及主要销向预测。
㈡产品价格分析
1、国内矿产品价格现状。
2、矿产品价格稳定性及变化趋势。
三、矿产资源概况
㈠矿区总体概况
1、矿区总体规划情况。
2、矿区矿产资源概况。
3、该设计与矿区总体开发的关系。
㈡该设计项目的资源概况
1、矿床地质及构造特征。
2、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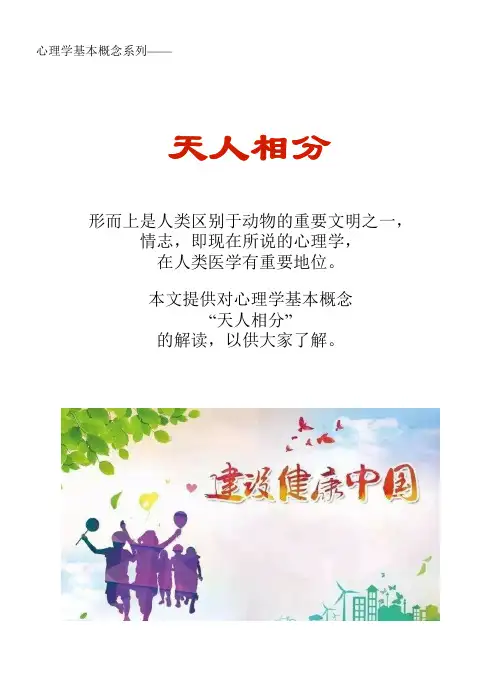
心理学基本概念系列——
天人相分
形而上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文明之一,
情志,即现在所说的心理学,
在人类医学有重要地位。
本文提供对心理学基本概念
“天人相分”
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天人相分
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一种观点。
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区别和相对立。
荀子首先明确提出。
《荀子·天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故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
认为自然界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人类社会的贫富灾祸也与大自然界没有必然联系,完全由人自己造成,否定天有意志、可以主宰人的命运的观点。
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肯定人能认识和利用自然界。
唐柳宗元继承并发挥荀子“天人之分”的观点,进一步提出天人“不相预”的天人观。
即认为天道与人事各有自己的规律,二者区别严格,互不干预。
并强调谋事完全在人,而不必祈求于天:“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
(《天说》)刘禹锡则在同意柳宗元天人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
即认为天与人互相争胜而又互相利用,乃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
并认为“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
(《天论上》)正因为天与人处于如此的关系之中,大自然才能加以利用和改造,人类社会也才得以发展和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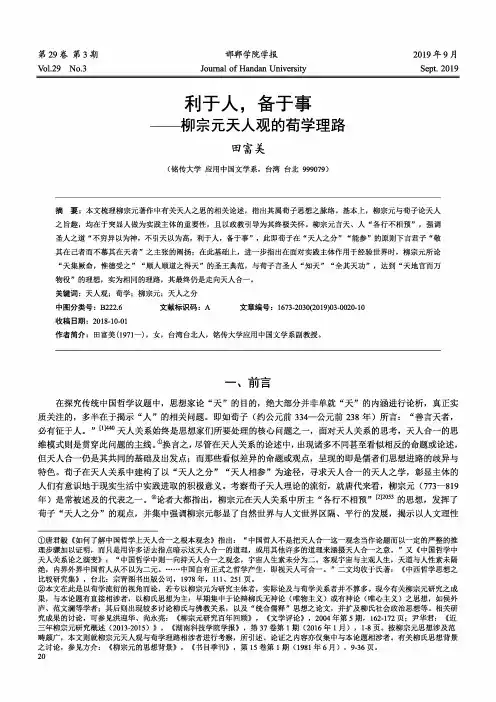
2019年9月Sept. 2019第29卷第3期Vol.29 No.3邯郸学院学报Journal of Handan University 利于人,备于事—柳宗元天人观的荀学理路田富美(铭传大学应用中国文学系,台湾台北999079)摘要:本文梳理柳宗元著作中有关天人之思的相关论述,指出其属荀子思想之脉络。
基本上,柳宗元与荀子论天人 之旨趣,均在于突显人做为实践主体的重要性,且以政教引导为其终极关怀。
柳宗元言天、人“各行不相预”,强调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此即荀子在"天人之分”"能参”的原则下言君子“敬 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之主张的阐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面对实践主体作用于经验世界时,柳宗元所论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 “顺人顺道之得天”的圣王典范,与荀子言圣人“知天” “全其天功”,达到"天地官而万 物役”的理想,实为相同的理路,其最终仍是走向天人合一。
关键词:天人观;荀学;柳宗元;天人之分中图分类号:B22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19)03-0020-10收稿日期:2018-10-01作者简介:田富美(1971-),女,台湾台北人,铭传大学应用中国文学系副教授。
—'前言在探究传统中国哲学议题中,思想家论“天”的目的,绝大部分并非单就“天”的内涵进行论析,真正实 质关注的,多半在于揭示“人”的相关问题。
即如荀子(约公元前334—公元前238年)所言:“善言天者, 必有征于人。
”皿44。
天人关系始终是思想家们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面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天人合一的思 维模式则是贯穿此问题的主线。
©换言之,尽管在天人关系的论述中,出现诸多不同甚至看似相反的命题或论述, 但天人合一仍是其共同的基础及出发点;而那些看似差异的命题或观点,呈现的即是儒者们思想进路的歧异与 特色。
荀子在天人关系中建构了以“天人之分” “天人相参”为途径,寻求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学,彰显主体的 人们有意识地于现实生活中实践进取的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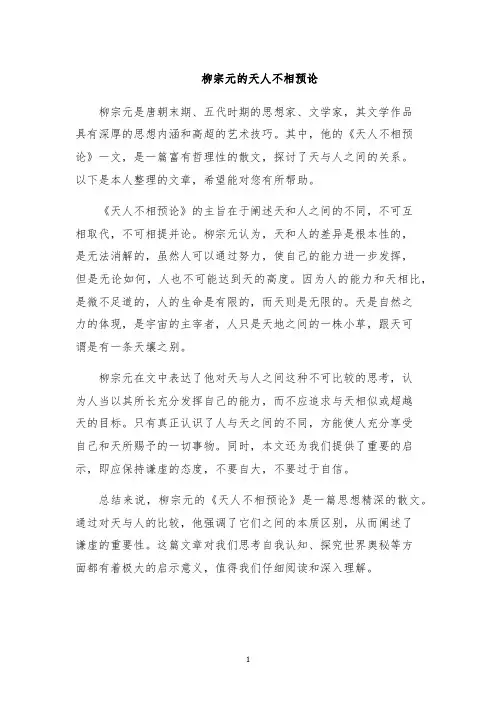
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论
柳宗元是唐朝末期、五代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其文学作品
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技巧。
其中,他的《天人不相预论》一文,是一篇富有哲理性的散文,探讨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下是本人整理的文章,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天人不相预论》的主旨在于阐述天和人之间的不同,不可互
相取代,不可相提并论。
柳宗元认为,天和人的差异是根本性的,
是无法消解的,虽然人可以通过努力,使自己的能力进一步发挥,
但是无论如何,人也不可能达到天的高度。
因为人的能力和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天则是无限的。
天是自然之
力的体现,是宇宙的主宰者,人只是天地之间的一株小草,跟天可
谓是有一条天壤之别。
柳宗元在文中表达了他对天与人之间这种不可比较的思考,认
为人当以其所长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不应追求与天相似或超越
天的目标。
只有真正认识了人与天之间的不同,方能使人充分享受
自己和天所赐予的一切事物。
同时,本文还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即应保持谦虚的态度,不要自大,不要过于自信。
总结来说,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论》是一篇思想精深的散文。
通过对天与人的比较,他强调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阐述了
谦虚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对我们思考自我认知、探究世界奥秘等方
面都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仔细阅读和深入理解。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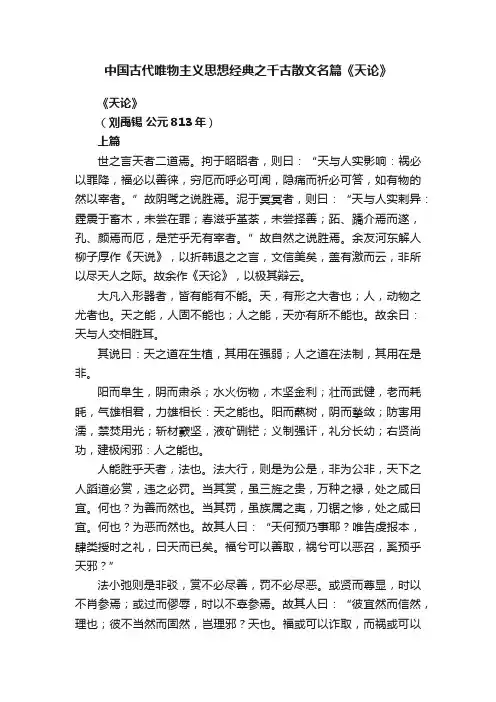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经典之千古散文名篇《天论》《天论》(刘禹锡公元813年)上篇世之言天者二道焉。
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徕,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
”故阴骘之说胜焉。
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剌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蹻介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
”故自然之说胜焉。
余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
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
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
阳而爇树,阴而揫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
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种之禄,处之咸曰宜。
何也?为善而然也。
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
何也?为恶而然也。
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事耶?唯告虔报本,肆类授时之礼,曰天而已矣。
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
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
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
福或可以诈取,而祸或可以苟免。
”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
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
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