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贝克特荒诞剧《终局》的隐含意思
- 格式:doc
- 大小:29.50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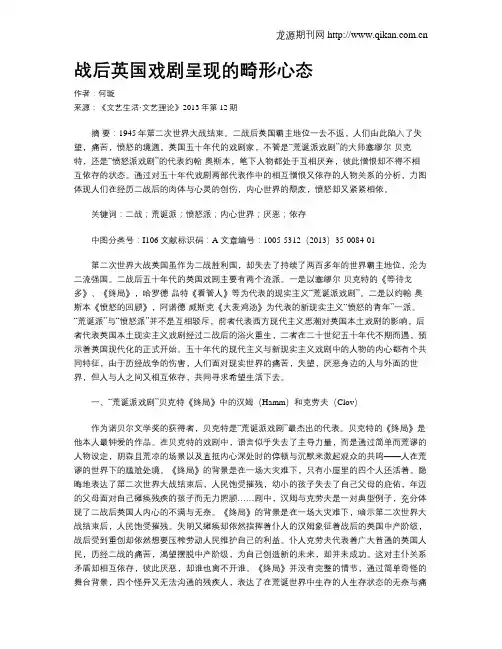
战后英国戏剧呈现的畸形心态作者:何璇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3年第12期摘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二战后英国霸主地位一去不返,人们由此陷入了失望,痛苦,愤怒的境遇。
英国五十年代的戏剧家,不管是“荒诞派戏剧”的大师塞缪尔·贝克特,还是“愤怒派戏剧”的代表约翰·奥斯本,笔下人物都处于互相厌弃,彼此憎恨却不得不相互依存的状态。
通过对五十年代戏剧两部代表作中的相互憎恨又依存的人物关系的分析,力图体现人们在经历二战后的肉体与心灵的创伤,内心世界的颓废,愤怒却又紧紧相依。
关键词:二战;荒诞派;愤怒派;内心世界;厌恶;依存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5-0084-01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虽作为二战胜利国,却失去了持续了两百多年的世界霸主地位,沦为二流强国。
二战后五十年代的英国戏剧主要有两个流派。
一是以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终局》,哈罗德·品特《看管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
二是以约翰·奥斯本《愤怒的回顾》,阿诺德·威斯克《大麦鸡汤》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愤怒的青年”一派。
“荒诞派”与“愤怒派”并不是互相驳斥,前者代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英国本土戏剧的影响,后者代表英国本土现实主义戏剧经过二战后的浴火重生,二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期而遇,预示着英国现代化的正式开始。
五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戏剧中的人物的内心都有个共同特征,由于历经战争的伤害,人们面对现实世界的痛苦,失望,厌恶身边的人与外面的世界,但人与人之间又相互依存,共同寻求希望生活下去。
一、“荒诞派戏剧”贝克特《终局》中的汉姆(Hamm)和克劳夫(Clov)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贝克特是“荒诞派戏剧”最杰出的代表。
贝克特的《终局》是他本人最钟爱的作品。
在贝克特的戏剧中,语言似乎失去了主导力量,而是通过简单而荒谬的人物设定,阴森且荒凉的场景以及直抵内心深处时的停顿与沉默来激起观众的共鸣——人在荒谬的世界下的尴尬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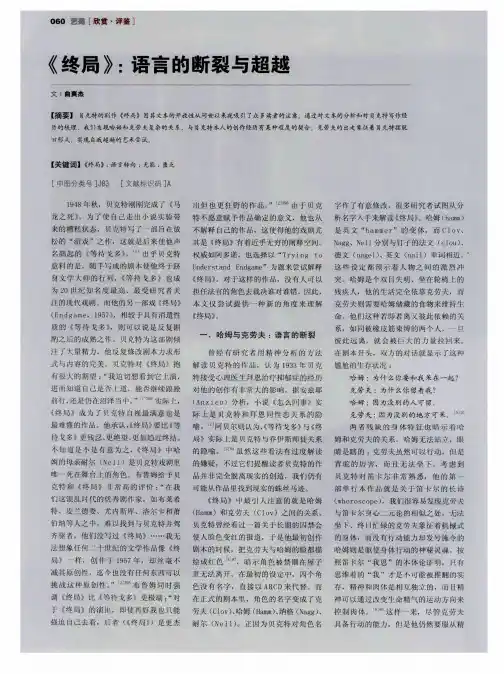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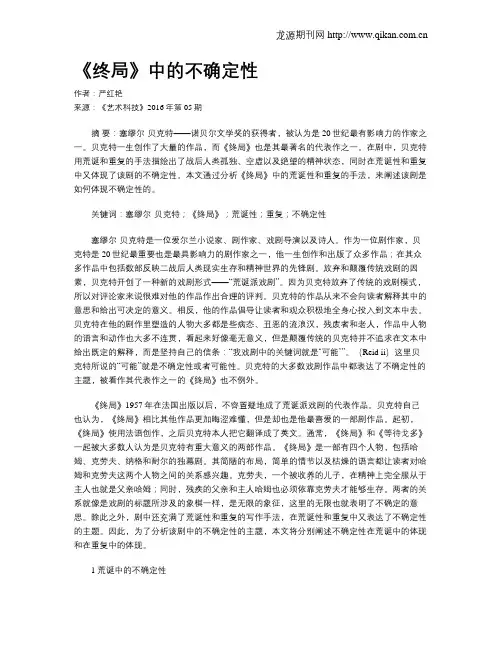
《终局》中的不确定性作者:严红艳来源:《艺术科技》2016年第05期摘要:塞缪尔·贝克特——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贝克特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而《终局》也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在剧中,贝克特用荒诞和重复的手法描绘出了战后人类孤独、空虚以及绝望的精神状态,同时在荒诞性和重复中又体现了该剧的不确定性。
本文通过分析《终局》中的荒诞性和重复的手法,来阐述该剧是如何体现不确定性的。
关键词:塞缪尔·贝克特;《终局》;荒诞性;重复;不确定性塞缪尔·贝克特是一位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戏剧导演以及诗人。
作为一位剧作家,贝克特是20世纪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和出版了众多作品;在其众多作品中包括数部反映二战后人类现实生存和精神世界的先锋剧。
放弃和颠覆传统戏剧的因素,贝克特开创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荒诞派戏剧”。
因为贝克特放弃了传统的戏剧模式,所以对评论家来说很难对他的作品作出合理的评判。
贝克特的作品从来不会向读者解释其中的意思和给出可决定的意义。
相反,他的作品倡导让读者和观众积极地全身心投入到文本中去。
贝克特在他的剧作里塑造的人物大多都是些病态、丑恶的流浪汉,残废者和老人,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和动作也大多不连贯,看起来好像毫无意义,但是颠覆传统的贝克特并不追求在文本中给出既定的解释,而是坚持自己的信条:“我戏剧中的关键词就是…可能‟”。
(Reid ii)这里贝克特所说的“可能”就是不确定性或者可能性。
贝克特的大多数戏剧作品中都表达了不确定性的主题,被看作其代表作之一的《终局》也不例外。
《终局》1957年在法国出版以后,不容置疑地成了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品。
贝克特自己也认为,《终局》相比其他作品更加晦涩难懂,但是却也是他最喜爱的一部剧作品。
起初,《终局》使用法语创作,之后贝克特本人把它翻译成了英文。
通常,《终局》和《等待戈多》一起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贝克特有重大意义的两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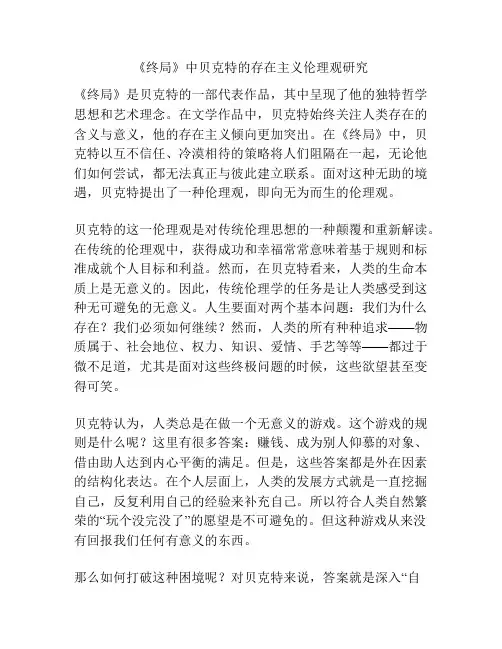
《终局》中贝克特的存在主义伦理观研究《终局》是贝克特的一部代表作品,其中呈现了他的独特哲学思想和艺术理念。
在文学作品中,贝克特始终关注人类存在的含义与意义,他的存在主义倾向更加突出。
在《终局》中,贝克特以互不信任、冷漠相待的策略将人们阻隔在一起,无论他们如何尝试,都无法真正与彼此建立联系。
面对这种无助的境遇,贝克特提出了一种伦理观,即向无为而生的伦理观。
贝克特的这一伦理观是对传统伦理思想的一种颠覆和重新解读。
在传统的伦理观中,获得成功和幸福常常意味着基于规则和标准成就个人目标和利益。
然而,在贝克特看来,人类的生命本质上是无意义的。
因此,传统伦理学的任务是让人类感受到这种无可避免的无意义。
人生要面对两个基本问题: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必须如何继续?然而,人类的所有种种追求——物质属于、社会地位、权力、知识、爱情、手艺等等——都过于微不足道,尤其是面对这些终极问题的时候,这些欲望甚至变得可笑。
贝克特认为,人类总是在做一个无意义的游戏。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这里有很多答案:赚钱、成为别人仰慕的对象、借由助人达到内心平衡的满足。
但是,这些答案都是外在因素的结构化表达。
在个人层面上,人类的发展方式就是一直挖掘自己,反复利用自己的经验来补充自己。
所以符合人类自然繁荣的“玩个没完没了”的愿望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种游戏从来没有回报我们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困境呢?对贝克特来说,答案就是深入“自我”,避免寻找外在的意义。
可是,个人如何才能超越自身,如何才能打破自身的限制呢?这就是贝克特的伦理观里所谓的“无为而生”之意。
我们必须静下来,了解自己。
这是唯一通向新生的方式。
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个人才能真正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才能超越外界的束缚。
在《终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无为而生的伦理观被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
甚至可以说,《终局》的故事本质上就是一种“无为而生”的表现形式。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囚犯们过着荒诞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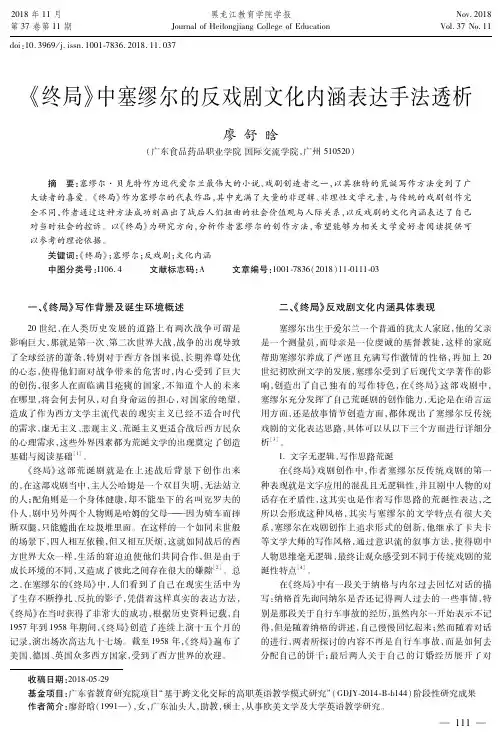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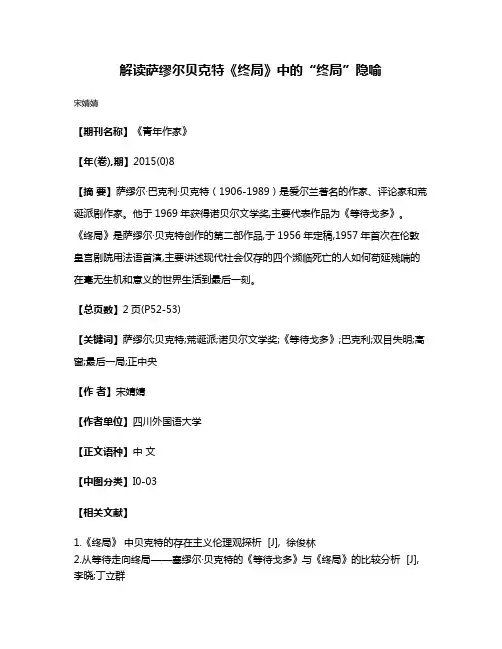
解读萨缪尔贝克特《终局》中的“终局”隐喻
宋婧婧
【期刊名称】《青年作家》
【年(卷),期】2015(0)8
【摘要】萨缪尔·巴克利·贝克特(1906-1989)是爱尔兰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和荒诞派剧作家。
他于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代表作品为《等待戈多》。
《终局》是萨缪尔·贝克特创作的第二部作品,于1956年定稿,1957年首次在伦敦皇宫剧院用法语首演,主要讲述现代社会仅存的四个濒临死亡的人如何苟延残喘的在毫无生机和意义的世界生活到最后一刻。
【总页数】2页(P52-53)
【关键词】萨缪尔;贝克特;荒诞派;诺贝尔文学奖;《等待戈多》;巴克利;双目失明;高窗;最后一局;正中央
【作者】宋婧婧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03
【相关文献】
1.《终局》中贝克特的存在主义伦理观探析 [J], 徐俊林
2.从等待走向终局——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与《终局》的比较分析 [J], 李晓;丁立群
3.浅析贝克特戏剧《终局》中的荒诞主义思想 [J], 纪聪
4.“一裁终局”将遏制一些用人单位“滥诉”——解读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一裁终局”制度 [J], 张智君
5.浅析贝克特戏剧作品中的荒诞感——以《终局》为例 [J], 银盈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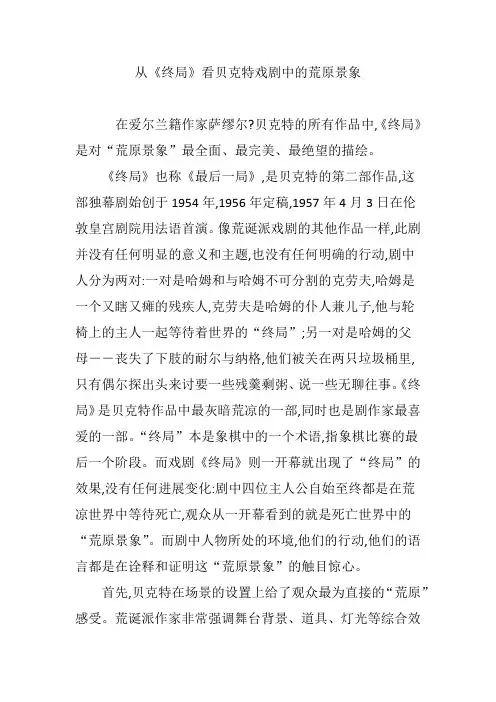
从《终局》看贝克特戏剧中的荒原景象在爱尔兰籍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所有作品中,《终局》是对“荒原景象”最全面、最完美、最绝望的描绘。
《终局》也称《最后一局》,是贝克特的第二部作品,这部独幕剧始创于1954年,1956年定稿,1957年4月3日在伦敦皇宫剧院用法语首演。
像荒诞派戏剧的其他作品一样,此剧并没有任何明显的意义和主题,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剧中人分为两对:一对是哈姆和与哈姆不可分割的克劳夫,哈姆是一个又瞎又瘫的残疾人,克劳夫是哈姆的仆人兼儿子,他与轮椅上的主人一起等待着世界的“终局”;另一对是哈姆的父母――丧失了下肢的耐尔与纳格,他们被关在两只垃圾桶里,只有偶尔探出头来讨要一些残羹剩粥、说一些无聊往事。
《终局》是贝克特作品中最灰暗荒凉的一部,同时也是剧作家最喜爱的一部。
“终局”本是象棋中的一个术语,指象棋比赛的最后一个阶段。
而戏剧《终局》则一开幕就出现了“终局”的效果,没有任何进展变化:剧中四位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是在荒凉世界中等待死亡,观众从一开幕看到的就是死亡世界中的“荒原景象”。
而剧中人物所处的环境,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语言都是在诠释和证明这“荒原景象”的触目惊心。
首先,贝克特在场景的设置上给了观众最为直接的“荒原”感受。
荒诞派作家非常强调舞台背景、道具、灯光等综合效果,贝克特把这种舞台语言称之为“直喻”,尤奈斯库称为“语言的延伸”,他们认为直观的舞台效果较之于语言更能引起观众的注意,激起观众的同情,所以荒诞派戏剧往往都会在剧本开头出现大段的场景提示。
但需要说明的是,在舞台场景的具体设置上,尤奈斯库和贝克特这两位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却是截然不同的,尤奈斯库喜欢让他的剧中人在热闹的场合出现,比如吵闹的街区,布置繁琐的房间等,而贝克特似乎更习惯于让他笔下的人物在荒芜的场景中出场。
观众最熟悉的也许是《等待戈多》中那条只有一棵秃树的乡村道路了,两位老流浪汉爱斯特拉冈(戈戈)和弗拉季米尔(狄狄)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中相遇并等待。

贝克特的名词解释贝克特(Samuel Beckett)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爱尔兰作家和戏剧家,他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对人生存在的深刻探索而闻名于世。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类存在的无奈、虚无和孤独的思考,在艺术领域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几个与贝克特的作品和思想相关的名词进行解释,以更好地理解他的创作和思想。
1. 虚无(Nihilism):虚无是贝克特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
它表达了对人类存在的缺乏意义和价值的看法。
贝克特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孤独、绝望和无望的情境,这些情境反映了虚无主义的核心思想。
他在剧本《等待戈多》中写道:“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我为自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
”贝克特通过其作品传达了一个深刻的信息:人的存在本质是毫无意义的,生活的目的和价值是虚构的。
2. 孤独(Solitude):贝克特的作品中,孤独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
他通过描述人物与自己和世界的脱离来表达这种孤独感。
孤独不仅是一种生理状态,更是一种内心的孤独和空虚。
贝克特的作品中的人物往往被置于一个荒凉、无人的环境中,与其他人隔绝并处于无尽的等待之中。
在剧本《等待戈多》中,主人公们不断地等待戈多的到来,而这个等待只是一种无尽的徒劳。
孤独成为了他们存在的代表,反映了人类存在的本质。
3. 演员(Actor):贝克特在剧本中对演员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他通过演员的行为和言语来传递他的思想。
在贝克特的作品中,演员经常出现在一个空无一物、无意义的情境中。
演员不仅是一种表演者,更是一个承载作者思想的媒介。
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的角色表达了演员的困境和无助,强调了演员在表演艺术中的困扰和挣扎。
4. 自由(Freedom):自由是贝克特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他对自由的理解与传统定义有所不同。
在贝克特的世界里,自由不是指人的意志和行为完全自主的状态,而是指摆脱机械反应和固定模式的束缚。
他的作品中的人物经常沉浸在习惯和惯例中,缺乏真正的自由。
贝克特认为人们应该超越常规和惯例的框架,寻求真正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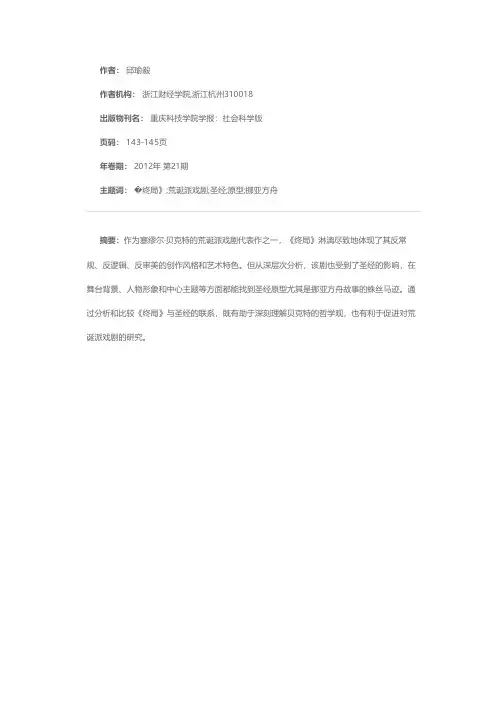
作者: 邱瑜毅
作者机构: 浙江财经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出版物刊名: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143-145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21期
主题词:�终局》;荒诞派戏剧;圣经;原型;挪亚方舟
摘要:作为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代表作之一,《终局》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其反常规、反逻辑、反审美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
但从深层次分析,该剧也受到了圣经的影响,在舞台背景、人物形象和中心主题等方面都能找到圣经原型尤其是挪亚方舟故事的蛛丝马迹。
通过分析和比较《终局》与圣经的联系,既有助于深刻理解贝克特的哲学观,也有利于促进对荒诞派戏剧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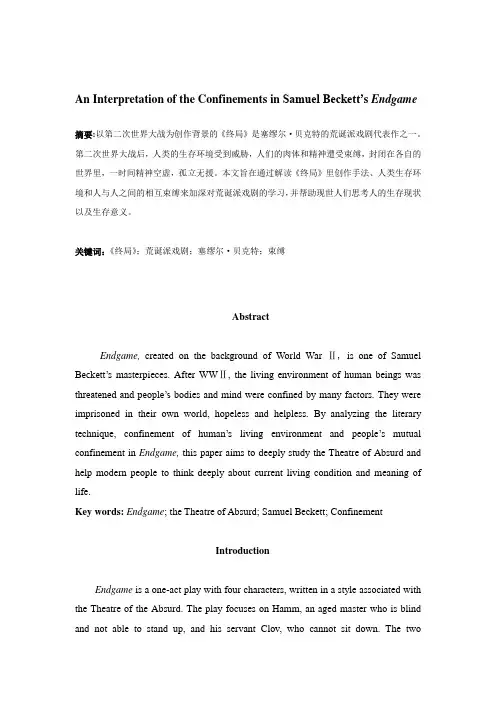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inements in Samuel Beckett’s Endgame摘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创作背景的《终局》是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代表作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人们的肉体和精神遭受束缚,封闭在各自的世界里,一时间精神空虚,孤立无援。
本文旨在通过解读《终局》里创作手法、人类生存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束缚来加深对荒诞派戏剧的学习,并帮助现世人们思考人的生存现状以及生存意义。
关键词:《终局》;荒诞派戏剧;塞缪尔·贝克特;束缚AbstractEndgame, created on the background of World WarⅡ,is one of Samuel Beckett’s masterpieces. After WWⅡ,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human beings was threatened and people’s bodies and mind were confined by many factors. They were imprisoned in their own world, hopeless and helpless. By analyzing the literary technique, confinement of human’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mutual confinement in Endgame, 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study the Theatre of Absurd and help modern people to think deeply about current living condition and meaning of life.Key words: Endgame; the Theatre of Absurd; Samuel Beckett; ConfinementIntroductionEndgame is a one-act play with four characters, written in a style associated with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The play focuses on Hamm, an aged master who is blind and not able to stand up, and his servant Clov, who cannot sit down. The twocharacters, mutually dependent, have been fighting for years and continue to do so as the play progresses. Clov always wants to leave but never seems to take actions. The other two characters present are Hamm's legless parents Nagg and Nell, who live in rubbish bins and always request food or argue inanely. They are all confined to a bare shelter located by the sea. In order to get rid of such boredom and emptiness, Hamm makes Clov move him around the room, fetch objects, and look out the window for signs of life; what’s more, they argue with each other and talk nonsense resistively all the time. Not only are they all confined in a limited space, they also exert restrictions on each other by absurd talks and actions.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se confinements from three aspect, namely, literary technique, confinement of human’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mutual confinement.Not being able to express people’s feelings any more,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way is confined by newly emerged changes. That’s why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took its course and stepped on the stage as time goes by. The most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 of Endgame is the use of absurd approach. Beckett wrote it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at a time when Western culture was terrified by the possibility of nuclear annihilation.Plays within Theatre of the Absurd are absurd in that they focus not on logical acts, realistic occurrences, or traditional character development; they, instead, focus on human beings trapped in an incomprehensible world subject to any occurrence, no matter how illogical. Before WWⅡ, people cannot release their emotions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literary way, which pays much attention to logical acts,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plot development. However, after that,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as heavily destroyed, people lost faith for god and found life was meaningless. Human existence has no purpose and therefore all communication breaks down. And the conventional way has limitations and words failed to express the essence of human experience, not being able to penetrate beyond its surface. Thus the conventionally 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argument gives way to irrational and illogical speech.Abandoning the conventional creating techniques, dramatic plots and complicated, absurdist works make use of the plainest fragmented words, the most common happenings and the simplest plots to demonstrate the most mundane life and reveal the philosophy of life. For example,Left and right back, high up, two small windows, curtains drawn.Front right, a door. Hanging near door, its face to wall, a picture.Front left, touching each other, covered with an old sheet, two ashbins.Center, in an armchair on castors, covered with an old sheet, Hamm.(Beckett 1)By ridiculing conventional and stereotyped speech patterns,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tries to make people aware of the possibility of going beyond everyday speech conventions and communicating more authentically. Conventional speech acts as a barrier between us and what the world is really about: in order to come into direct contact with natural re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discredit and discard the confinement of conventional approach.Apart from the confinement in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confinement of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is also worth notice. The setting for Endgame is a small bare, partially underground room; high up the wall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 there are two small windows. Outside all seems dead and nothing happens; inside, the four characters are confined to this limited dark space. As the protagonist Hamm indicates, “HAMM: Out side of here it's death.”(3) “HAMM: You stink already. The whole place stinks of corpses.”“CLOV: The whole universe.” (13)All these descriptions present readers a dark picture of the hell on earth, which suffocates them even though they take refuge in this confined shelter. Although they can see the outside world, through the high-up windows, nothing can enter into their sight, no wind, no waves, no light, and no life. “HAMM: Nothing stirs. All is.”(8) And the whole nature, the whole universe is a lifeless prison to imprison the four characters. Nature is like an invisible and powerful force controlling the humankind, and no matter how hard people struggle with it, they can never shake of the shatters ofit. So the nature is a great confinement for them. Save the external factors to confine them, the four characters are confined in their own ways. Hamm is disabled and paralyzed, confined to his wheelchair; his eyes lose sight and can see nothing. And the servant Clov has some trouble with his legs, which makes him have to stand and lie all the time.While Hamm’s parents get their legs damaged when they crashed on their tandem and lost their shanks, so they are confined to two dirty trash cans. All these factors lay a barrier between their real life and ideal life. This is the same situation as we are in. One may want to achieve a lot of accomplishments, and lead a colorful and beautiful life, but the path of life is always winding forward, and the environment is not to one’s advantage, which makes the journey tough, in some worse case, makes people despaired. So the confinement in life is same no matter in past time or present. Considering this, we may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bout life.In addition to the two kinds of confinements mentioned above, the confinements of the four characters, especially the one between Hamm and Clov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study. Hamm and Clov, their relationship is father and an adopted son or servant; they depend on each other and meanwhile control or confine each other. Nagg and Nell, they lose their legs and are confined to the dustbins. The parents are not only confined physically, but also psychologically, for they can not move and the only thing they can do is to recall the old bygones, to live in the old times. What’s more, their desire to love Hamm and to be loved by Hamm is restricted. To love Hamm is impossible, because they are aged and disabled people and can no longer take care of Hamm; to be loved is also out of problem, for Hamm treat them badly. W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is the confinement between Hamm and Clov. In Endgame, Hamm acts as the master and Clov the servant. Hamm is in the absolute dominant position. He gives orders at his will. He makes Clov fetch things for him, move the wheelchair around and makes Clov be his eyes to know how is the without and what is going on outside to help him get rid of loneliness and absence. While Clov have to obey him for only Ham can give him the food to survive. Clovrepetitively proclaims that he will leave, but he fails himself time and again; because if he leaves, he can not survive either, for there is no sign of life outside. Even when he finds out a little boy out of door, which may stand for life, and determines to leave, he hesitates. When the play ends, he still struggles to make a decision to stay or leave. Whether Clov can break through and step out of Hamm’s confinement is a question stirred up in readers’ mind. This situation is a mutual confinement between them to some degree.ConclusionThe ending of Endgame goes the same surroundings as the beginning, and their situation is the same when the play begins. The whole process is like a circle. The four characters’ actions and speeches seem to be confined to this circle, which makes readers consider that these activities may take place the following day. It seems like that life if full of confinements and restrictions, whether we should stay on the spot or move out of it, it is really worthy of thinking. By analyzing the three types of confinements in Endgame, we can know well about the confusion and fears when seeking for the meaning of life.Works CitedBeckett, Samuel. Endgame. N.d.. Microsoft Word file.Draper, James P.. e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 ol.83.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4.Hugh, Kenner, ed.. A Reader’s Guide to Samuel Beckett. London: Thames and Hundson, 1996.Pilling, Joh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eckett.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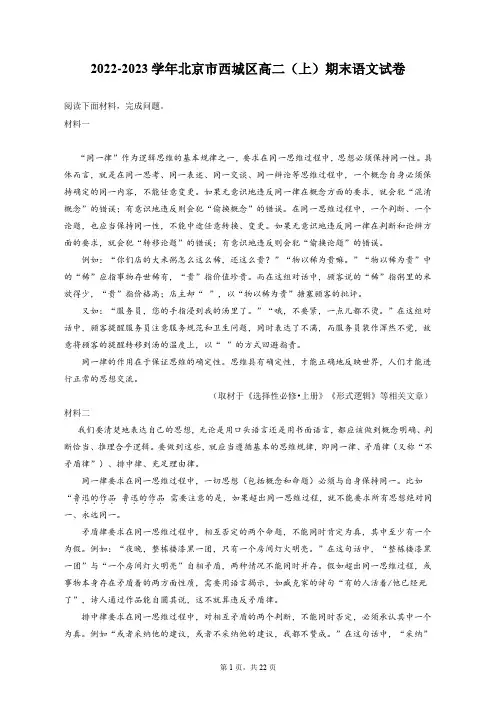
2022-2023学年北京市西城区高二(上)期末语文试卷阅读下面材料,完成问题。
材料一ㅤㅤ“同一律”作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之一,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思想必须保持同一性。
具体而言,就是在同一思考、同一表述、同一交谈、同一辩论等思维过程中,一个概念自身必须保持确定的同一内容,不能任意变更。
如果无意识地违反同一律在概念方面的要求,就会犯“混淆概念”的错误;有意识地违反则会犯“偷换概念”的错误。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判断、一个论题,也应当保持同一性,不能中途任意转换、变更。
如果无意识地违反同一律在判断和论辩方面的要求,就会犯“转移论题”的错误;有意识地违反则会犯“偷换论题”的错误。
ㅤㅤ例如:“你们店的大米粥怎么这么稀,还这么贵?”“物以稀为贵嘛。
”“物以稀为贵”中的“稀”应指事物存世稀有,“贵”指价值珍贵。
而在这组对话中,顾客说的“稀”指粥里的米放得少,“贵”指价格高;店主却“”,以“物以稀为贵”搪塞顾客的批评。
ㅤㅤ又如:“服务员,您的手指浸到我的汤里了。
”“哦,不要紧,一点儿都不烫。
”在这组对话中,顾客提醒服务员注意服务规范和卫生问题,同时表达了不满,而服务员装作浑然不觉,故意将顾客的提醒转移到汤的温度上,以“”的方式回避指责。
ㅤㅤ同一律的作用在于保证思维的确定性。
思维具有确定性,才能正确地反映世界,人们才能进行正常的思想交流。
(取材于《选择性必修•上册》《形式逻辑》等相关文章)材料二ㅤㅤ我们要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无论是用口头语言还是用书面语言,都应该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
要做到这些,就应当遵循基本的思维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又称“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
ㅤㅤ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切思想(包括概念和命题)必须与自身保持同一。
比如“鲁迅的作品.....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超出同一思维过程,就不能要求所有思想绝对同.....鲁迅的作品一、永远同一。
ㅤㅤ矛盾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相互否定的两个命题,不能同时肯定为真,其中至少有一个为假。
存在与时间:等待之中的生命荒诞意识法国作家、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一部充满荒诞意识的剧作,简单枯燥的反戏剧情节蕴涵着丰富而深邃的哲学内涵,在形象与抽象的和解断章中展示了人类生存境况的图景。
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名为《存在与时间》,阐释存在与时间二者的相关命题,受其启发,围绕“存在”与“时间”的关系,来解读《等待戈多》中关照人类生存和体现于时间叙述之中的生命荒诞意识。
标签:《等待戈多》;存在;时间;等待;生命荒诞意识一、“等待”中时间的无意义循环与生存的荒诞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通过对剧中人物所感受的时间、历史和两个流浪汉所代表的人类作为等待主体的存在关系的叙述,通过叙述时间的无意义循环,消磨剧中人物的“等待”,渲染了人类生存处于荒诞状态的效果。
生活在贝克特笔下那个荒凉而又凄惨的世界上,作为人类象征的两个流浪汉——弗拉吉米尔和艾斯特拉贡(狄狄和戈戈),生活在荒诞、痛苦、非理性的世界中,他们对一切茫然无知,只是一味地等待戈多,在流浪的路上循环于痛苦无望、无始无终的等待之中——等待着始终未露面的戈多。
他们等待着戈多,却不知道戈多是谁,戈多一次次让他们失望,但他们还是得等待下去——就像西西弗斯的命运一样,明知石头会滚下山去,还得日复一日重复着推石上山的生活——明知戈多不会来,他们可以选择的只有继续等待。
正如艾斯林所认为的,剧中的“等待”就是“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本质的等待”;而这种“存在”也正如萨特所说的“是荒诞的,无法辩解的”[1]336。
《等待戈多》剧中人物对话重复,仿佛患上失忆症,对自我的存在、他人、历史和环境的存在产生遗忘,形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的间离效果,尤其是对“昨天”和“过去”的遗忘最为突出,历史对他们而言只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剧中时间是周而复始的,仿佛象征着两个流浪汉存在于无始无终的循环等待之中,没有尽头。
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具体时间,好像在一起已经等待了五十年,但是当往事被埋葬之后,他们所面对的还只是徒劳的等待,等待着永恒的“明天”——戈多到来的时间。
《终局》:语言的断裂与超越作者:曲爽杰来源:《艺苑》2014年第03期【摘要】贝克特的剧作《终局》因其文本的开放性从问世以来就吸引了众多读者的注意。
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对贝克特写作经历的梳理,我们发现哈姆和克劳夫复杂的关系,与贝克特本人的创作经历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克劳夫的出走象征着贝克特摆脱旧形式、实现自我超越的艺术尝试。
【关键词】《终局》;语言转向;无能;匮乏[中图分类号]J83 [文献标识码]A1948年秋,贝克特刚刚完成了《马龙之死》。
为了使自己走出小说实验带来的糟糕状态,贝克特写了一部旨在放松的“游戏”之作,这就是后来使他声名鹊起的《等待戈多》。
(1)出乎贝克特意料的是,随手写成的剧本使他终于跻身文学大师的行列,《等待戈多》也成为20世纪知名度最高、最受研究者关注的现代戏剧。
而他的另一部戏《终局》(Endgame,1957),相较于具有消遣性质的《等待戈多》,则可以说是反复斟酌之后的成熟之作。
贝克特为这部剧倾注了大量精力,他反复修改剧本力求形式与内容的完美。
贝克特对《终局》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迫切想看到它上演,进而知道自己是否上道,能否继续踉跄前行,还是仍在沼泽当中。
”[1]296实际上,《终局》成为了贝克特自视最满意也是最难懂的作品。
他承认,《终局》要比《等待戈多》更残忍、更绝望、更加趋近终结。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终局》中哈姆的母亲耐尔(Nell)是贝克特戏剧里唯一死在舞台上的角色。
布鲁姆给予贝克特和《终局》非常高的评价:“在我们这混乱时代的优秀剧作家,如布莱希特、皮兰德娄、尤内斯库、洛尔卡和萧伯纳等人之中,难以找到与贝克特并驾齐驱者,他们没写过《终局》……我无法想象任何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像《终局》一样,创作于1957年,却丝毫不减其原创性,迄今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挑战这种原创性。
”[2]398布鲁姆同时强调《终局》比《等待戈多》更极端:“对于《终局》的演出,即使再好我也只能强迫自己去看,后者(《终局》)是更杰出但也更狂野的作品。
荒诞艺术的概念荒诞艺术是一种探索现实和虚幻之间边界的艺术形式。
它采用非传统的方式表现世界,突破常规的逻辑和理性,产生出荒诞、离奇甚至矛盾的效果。
荒诞艺术具有挑战传统观念的特点,在表达中常常使用夸张、反讽和黑色幽默等手法,用以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谬性和存在的无常。
荒诞艺术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欧洲,特别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运动为其奠定了基础。
荒诞艺术家试图通过颠覆传统的艺术规范和语法结构来破除对现实的局限,从而展现出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例如,马塞尔·杜尚的“泉”作品,他将一个普通的小便池放在展厅中,挑战了人们对艺术的传统定义和审美标准,使观者重新思考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荒诞艺术主张艺术家不受传统认知和道德准则的约束,他们试图逃离日常生活的压力和限制,进而获得自由和创造力的释放。
这种理念在荒谬剧、荒诞小说和电影等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是一部经典的荒诞剧作,通过描述两个无聊的人物在无尽的等待中漫无目的地度过时间,以荒诞的手法揭示人生的虚无和无意义。
荒诞艺术在风格和手法上呈现出多样性。
有的作品追求离奇的画面效果,通过对形式和表象的扭曲来达到荒诞的效果。
例如,萨尔瓦多·达利的作品《记忆的永恒》中,他将各种物象进行组合和重塑,让观者感到异想天开的荒唐和梦幻。
还有的作品则专注于逻辑的颠倒和反讽,以达到对现实世界规则和道德观念的挑战。
例如,中国作家田清波的小说《疯人院》中,他以荒诞的故事情节和怪异的人物形象,揭示了社会现实中的荒谬和愚昧。
荒诞艺术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对现实的固有认识和逻辑,激发了观者的思考和想象力。
它通过艺术形式的扭曲和变异,呈现了一个相对真实世界之外的存在。
荒诞艺术家试图通过对常识的颠覆和语义的扭曲,探寻人类存在的真相和本质。
荒诞艺术强调的是对社会生活奇异和失序的揭示,通过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和对日常生活的颠覆,创造出一种尖锐的嘲讽和威胁。
中泰朝贡的终局
黄璧蕴[泰国]
【期刊名称】《《民族史研究》》
【年(卷),期】2014(000)001
【摘要】本文大多根据泰国方面的史料,围绕中泰两国之间朝贡贸易关系,探讨到近代中泰关系中断,以及泰国禁止向中国朝贡的因素。
吞武里王朝时期,1767年泰国华裔王郑信登位以后,派遣陈美到广东向清朝请求封他为泰国国王,进一步采取了亲近中国的政策。
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郑信遣使人贡,可是使节还未返回泰国,郑王已被杀死。
(有关郑王被杀的原因,参阅第二章吞武里王朝时代)
【总页数】17页(P261-277)
【作者】黄璧蕴[泰国]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75
【相关文献】
1.司法终审抑或行政终局——行政终局裁决行为可诉性之理论思考 [J], 邓辉林;魏巍
2.从等待走向终局——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与《终局》的比较分析 [J], 李晓;丁立群
3.朝贡的名实与朝贡之外的东亚——分类框架、案例举隅与研究建议 [J], 万晓;
4.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J], 郭嘉辉
5.解读萨缪尔·贝克特《终局》中的“终局”隐喻 [J], 宋婧婧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塞缪尔·贝克特荒诞剧《终局》的隐含意思
摘要:本文旨在结合荒诞剧的特点来解读贝克特的戏剧《终局》,归纳其显著特点和挖掘其隐含意思。
关键词:赛缪尔.贝克特,荒诞剧,荒诞,终局
一、荒诞派戏剧
荒诞派戏剧最初是英国剧作家马丁·埃斯林在他的《荒诞派戏剧》一书中提出的。
他将这一流派产生的时间界定为1952 至1962 年,因为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是这一年在巴黎上演并大获成功,旋即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而实际上,尤奈斯库早在1948 年就已经创作出了被后人大为推崇的、被誉为荒诞派经典作之一的《秃头歌女》。
所不幸的是,该剧1950 年在巴黎上演的时候遭到了惨败,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寥寥无几,有时因为到场的观众太少,剧场不得不将票款退还给观众并关门停演。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对荒诞剧的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的作品受到了人们越来越热烈的欢迎。
马丁·埃斯林虽然在他的《荒诞派戏剧》一书中将贝克特、尤奈斯库、亚当和日奈划归为荒诞派。
但实际上,这些剧作家一直都将自己视作孤独的、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作家,他们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各自的世界里,与外界隔绝。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主题、创作题材以及创作背景,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共同遵循的创作纲领或艺术原则。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关注人的本体,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意义,作品中都渗透出强烈的悲剧精神和忧患意识;在创作上,他们一反传统的戏剧创作模式,将情节、悬念、人物刻画等必不可少的戏剧因素统统抛弃,用最直白的语言、最平凡的事件、最不具戏剧性的情节,表现最真实的生活,揭示出最深刻的人生哲理。
正是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剧作,在西方社会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因为这些剧作就像一面镜子,它使人们透过舞台,看到了自己,也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现实世界。
之所以称之为―荒诞派‖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试图传达这样一种思想:人的存在是没有目的的,没有意义的,人在世界上经常感觉到不知所措,不平静和受到威胁。
‖ (王左良,472)
二.显著特点
贝克特创作的另一个就是故事场景的荒凉和人物命运的凄惨。
孤独、寂寞就像一块怎么也挥之不去的乌云,笼罩着贝克特的全部作品。
这种凄惨孤独的场景在贝克特的另一部剧作《终局》中得到了更好的表现。
在一间空荡荡的、只在高
墙上开了两个小窗户的房间里,双目失明的哈姆瘫痪在轮椅上,他的双亲早年在骑双人自行车时出了车祸,摔断了双腿,现在只能呆在墙边的两只垃圾桶里,屋里唯一能行走的仆人克洛夫却不能坐下来。
房子外面发生的灾难使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灵都已经灭绝,而他们是仅有的幸存者。
剧中,哈姆是主人,他自私自利、专横武断、贪图享受;克洛夫是他的仆人,对哈姆充满仇恨,一直想要离开这儿。
但如果他决然离去,哈姆就必死无疑,因为克洛夫是唯一能够伺候他的人。
但是克洛夫却始终没有离开,因为外面的世界已经没有生命了,如果他离开,等待他的也是死亡,而这儿还存有吃的东西,虽然已经不多了。
《终局》中的这四个濒临死亡的人就这样苟延残喘,为过去的事情争吵着,发泄着彼此间的怨恨。
最后,克洛夫透过他架在窗户上的望远镜,似乎看见了远处有一个小男孩。
这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否真的看清了这象征着生命延续的景象。
克洛夫终于下决心要离开这生不如死的坟墓,他穿戴整齐,打开关闭已久的房门,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听着哈姆的长篇大论。
直到大幕落下,他还在那儿,进行着最后的抉择。
当世界已然死亡,新生活显露曙光,这些浑陷绝境中的畸零人,能否冲破茧缚,走出终局,剧作给观众留下回味与遐想。
在此,人物、事件和情节都不是荒诞剧作家所要注重表现的,它们不过是用来表现世界、表现人性的某个层面或特点的手段而已,只有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较完整地体现剧作家的某个思想。
因此,荒诞剧也就不注重具体事件的开头和结尾,而是将笔触停留在不断重复的、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各种状态上。
这种等待、希望、失望的循环交错的过程,这种交织在人物性格中的爱与恨的情感,不正是人类社会浓缩并被衍变为具象的永恒不变的主题吗?
三.成对关系
是贝克特戏剧中人物安排的重要特征。
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常常成对出场,如汉姆与克洛夫,威利与维尼,迪迪与戈戈,在《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中,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也是成对出现。
这种成对关系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其确立主要是出于形象塑造和主题表达的需要。
贝克特笔下的人物都缺乏形而上的精神寄托,必须依赖成对关系这一最小的人际关系单位来填补精神的空虚。
他们并不是意气相投的至交,而是无法独立面对痛苦的人生;他们只有确知对方的存在,并通过与对方的相互关系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才能在荒诞的世界中得以生存。
毕竟,―存在就是被感知‖。
但贝克特并未把成对关系当作笔下人物最后的避风港,而是将异化主题深入渗透到了这一最小的人际关系单位,使荒诞,孤独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绝对存在。
在《快乐的日子》里,作为夫妇的威利和维尼竟然同陌生人一样,缺乏互相间的心灵沟通。
甚至同一人的两个自我也已疏离,如同互不相知的他者:在《克拉帕的最后一盘磁带》中,人物现在的自我竟咒骂过去的自我是―愚蠢的私生子‖,这明显表露出两个自我之间的隔阂与陌生。
从人与外界的分离到人际间的心理隔
阂,再到个人内心两个自我间的矛盾冲突,这些无不是异化的恶果。
在作者笔下,异化是绝对而彻底的。
四.《终局》的深刻含义
―终局‖是国际象棋中的一个术语,是指象棋比赛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时候棋盘上的大多数棋子都已经被挪走了(Fidel Fajardo- Acosta) 。
和在下象棋一样,两人轮流下棋,在《终局》中,―哈姆总是在故事发展前宣布―我下了‖(Me to play), 虽然不同是―他要结束的比赛是他自己的生命‖ (A. Alvarez 90)。
贝克特用这个词,是比喻人们在这段时期中的两难境地。
贝克特试图描述的就是―人类灭绝之前的时刻‖ (Homan 1269).二战造成了人们的恐慌,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长久的阴影,人类一时间迷失了方向,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怀疑。
他们怀疑社会是否真的在进步,怀疑世界上有没有可信的领导或权威。
他们始终找不到答案回答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灾难和不公? 人们究竟为什么而活? 于是西方世界霎时间丢掉了信仰,一切的文明和发展都成了谎言。
因此,人们在混乱的战后生活中手足无措,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们的生活(布赖恩·阿普里亚得)。
正如象棋游戏中的终局阶段,此时已经是一种僵局状态,身处其中的人们陷入了绝境。
因为结局早已经注定,不论是放弃还是继续游戏,结果都将是一样的。
即使选择继续游戏,唯一的区别就是时间的延迟,延迟了那个无可避免的结局。
所以,这部戏剧的题目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无助和窘迫。
然而,事实上人们所面临的是关于生存的问题。
经过了无数次梦魇般的战争和动乱,人们要做的抉择却始终未变———死亡或生存。
如果选择死亡,那么所有的痛苦和不安都还将持续,况且死亡不是人类另一种更巨大的痛苦吗? 人们都惧怕遭受痛苦,所以人们总是不愿意选择死亡;但如果选择生存,那么如何继续生存,是维持这种残破现状还是终止它,重新开启一个新局面? 因此《终局》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复杂问题。
其实,这部戏剧到最后也未能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答案,甚至剧中的四个人物也无一个做出他的最终选择。
例如,剧中人克劳夫(Clov) 虽然多次声称他将要离开,可他却始终未能迈出门去,在戏剧的结尾他仍然守在门旁,谁也无法确信他是否真的要离开。
《终局》的开始和结尾似乎没有多少变化,唯一的区别只是戏剧最终将这个生存的问题带给了观众。
正如爱斯林所说:―我们当今的西方社会缺乏人们普遍认可的伦理或哲学标准,因此当代戏剧只是提出问题,却不提供解决方案。
‖所以,人们不得不思索他们自己的生活态度,关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终局》中的结局是指死亡,那么其中的人物便是在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们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们对死亡感到迷惑和恐惧。
《终局》所表现的是人在寻求生存意义所感到的迷惑和烦恼。
这种状态―源于人在宇宙中所处的模糊位置,源于人对死的恐惧以及人渴望获得绝对真理的本能‖。
随着西方世界信仰的丧失,统一体制的崩塌,人们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答案。
最后,让我引用Richard Server的话来总结贝克特的戏剧的意思:―贝克特的戏剧有什么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意义就在于缺乏意义‖ (Alvarez 85)。
贝克特的戏剧让我们笑得很尴尬,我们嘲笑剧中人物的荒诞,然而在反思时我们会感到胸口隐隐作痛。
参考文献
[1]Alvarez, A.Beckett . Glasgow: Fontana/Collins, 1973.
[2]布赖恩·阿普里亚得.生存的边缘[N ].伦敦泰晤士报,1982 - 11 – 09。
[3]Homan, Sidney. ―The Ending of Endgame‖, ed. By Lawrence Graver, and Raymond Federman. Samuel Beckett: The Critical Heritage. Detroit: Wayne State UP, 1973.
[4]王左良.欧洲文化入门[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