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
- 格式:doc
- 大小:57.50 KB
- 文档页数: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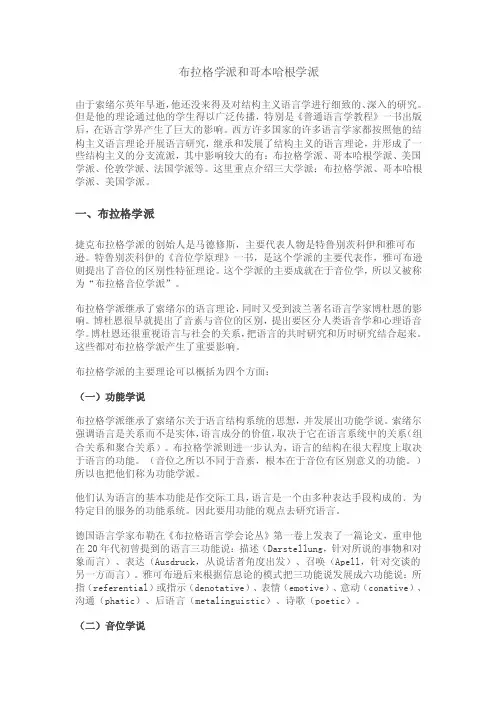
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由于索绪尔英年早逝,他还没来得及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细致的、深入的研究。
但是他的理论通过他的学生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出版后,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许多国家的许多语言学家都按照他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开展语言研究,继承和发展了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并形成了一些结构主义的分支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学派、伦敦学派、法国学派等。
这里重点介绍三大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学派。
一、布拉格学派捷克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是马德修斯,主要代表人物是特鲁别茨科伊和雅可布逊。
特鲁别茨科伊的《音位学原理》一书,是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作,雅可布逊则提出了音位的区别性特征理论。
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就在于音位学,所以又被称为“布拉格音位学派”。
布拉格学派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同时又受到波兰著名语言学家博杜恩的影响。
博杜恩很早就提出了音素与音位的区别,提出要区分人类语音学和心理语音学。
博杜恩还很重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把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
这些都对布拉格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布拉格学派的主要理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功能学说布拉格学派继承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结构系统的思想,并发展出功能学说。
索绪尔强调语言是关系而不是实体,语言成分的价值,取决于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布拉格学派则进一步认为,语言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功能。
(音位之所以不同于音素,根本在于音位有区别意义的功能。
)所以也把他们称为功能学派。
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作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
因此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
德国语言学家布勒在《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第一卷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重申他在20年代初曾提到的语言三功能说:描述(Darstellung,针对所说的事物和对象而言)、表达(Ausdruck,从说话者角度出发)、召唤(Apell,针对交谈的另一方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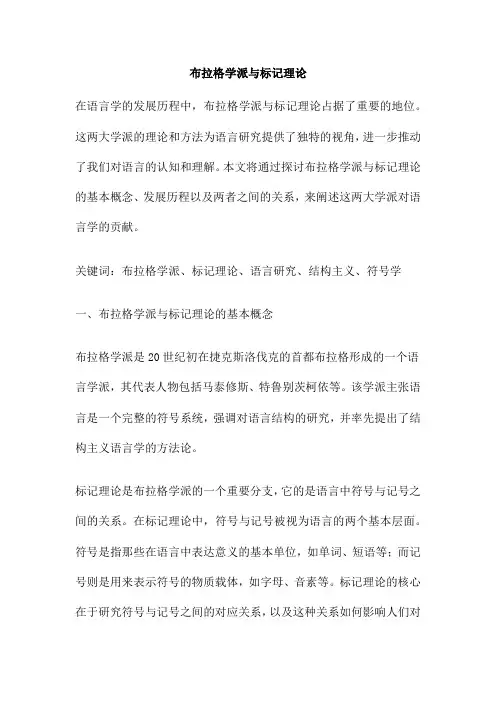
布拉格学派与标记理论在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中,布拉格学派与标记理论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这两大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为语言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进一步推动了我们对语言的认知和理解。
本文将通过探讨布拉格学派与标记理论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来阐述这两大学派对语言学的贡献。
关键词:布拉格学派、标记理论、语言研究、结构主义、符号学一、布拉格学派与标记理论的基本概念布拉格学派是20世纪初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形成的一个语言学派,其代表人物包括马泰修斯、特鲁别茨柯依等。
该学派主张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强调对语言结构的研究,并率先提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论。
标记理论是布拉格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是语言中符号与记号之间的关系。
在标记理论中,符号与记号被视为语言的两个基本层面。
符号是指那些在语言中表达意义的基本单位,如单词、短语等;而记号则是用来表示符号的物质载体,如字母、音素等。
标记理论的核心在于研究符号与记号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
二、布拉格学派的发展历程布拉格学派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语言学界普遍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
然而,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们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存在局限性,于是提出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论。
他们主张将语言视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认为语言研究应该语言的结构,而不是历史演变。
在发展过程中,布拉格学派经历了多个阶段。
初期的布拉格学派主要语言的音位和形态结构,后来逐渐扩展到研究语言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
这一学派对于20世纪中叶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
三、标记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前景标记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广泛。
首先,标记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语言的符号与记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究语言的本质和特征。
其次,标记理论为语言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语言教学中,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符号与记号之间的对应关系,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和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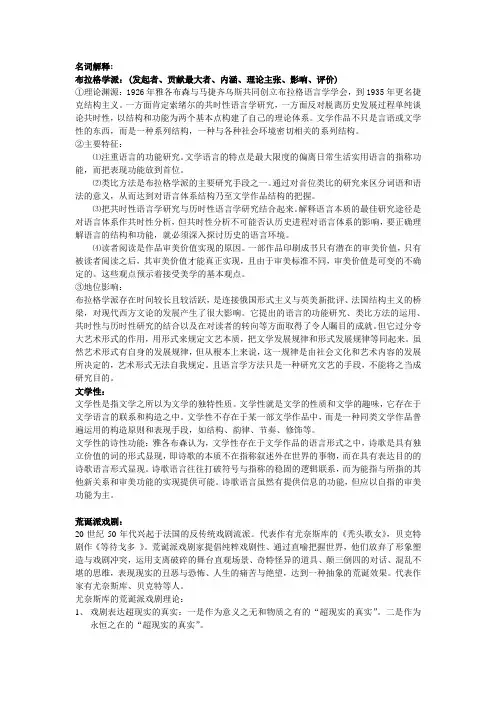
名词解释:布拉格学派:(发起者、贡献最大者、内涵、理论主张、影响、评价)①理论渊源:1926年雅各布森与马捷齐乌斯共同创立布拉格语言学学会,到1935年更名捷克结构主义。
一方面肯定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研究,一方面反对脱离历史发展过程单纯谈论共时性,以结构和功能为两个基本点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文学作品不只是言语或文学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系列结构,一种与各种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系列结构。
②主要特征:⑴注重语言的功能研究。
文学语言的特点是最大限度的偏离日常生活实用语言的指称功能,而把表现功能放到首位。
⑵类比方法是布拉格学派的主要研究手段之一。
通过对音位类比的研究来区分词语和语法的意义,从而达到对语言体系结构乃至文学作品结构的把握。
⑶把共时性语言学研究与历时性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
解释语言本质的最佳研究途径是对语言体系作共时性分析,但共时性分析不可能否认历史进程对语言体系的影响,要正确理解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就必须深入探讨历史的语言环境。
⑷读者阅读是作品审美价值实现的原因。
一部作品印刷成书只有潜在的审美价值,只有被读者阅读之后,其审美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且由于审美标准不同,审美价值是可变的不确定的。
这些观点预示着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
③地位影响:布拉格学派存在时间较长且较活跃,是连接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桥梁,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它提出的语言的功能研究、类比方法的运用、共时性与历时性研究的结合以及在对读者的转向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它过分夸大艺术形式的作用,用形式来规定文艺本质,把文学发展规律和形式发展规律等同起来。
虽然艺术形式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规律是由社会文化和艺术内容的发展所决定的,艺术形式无法自我规定。
且语言学方法只是一种研究文艺的手段,不能将之当成研究目的。
文学性:文学性是指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独特性质。
文学性就是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趣味,它存在于文学语言的联系和构造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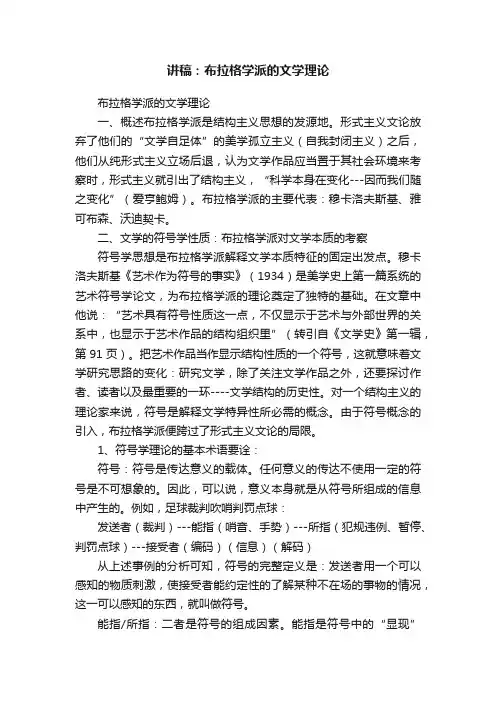
讲稿: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一、概述布拉格学派是结构主义思想的发源地。
形式主义文论放弃了他们的“文学自足体”的美学孤立主义(自我封闭主义)之后,他们从纯形式主义立场后退,认为文学作品应当置于其社会环境来考察时,形式主义就引出了结构主义,“科学本身在变化---因而我们随之变化”(爱亨鲍姆)。
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穆卡洛夫斯基、雅可布森、沃迪契卡。
二、文学的符号学性质:布拉格学派对文学本质的考察符号学思想是布拉格学派解释文学本质特征的固定出发点。
穆卡洛夫斯基《艺术作为符号的事实》(1934)是美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艺术符号学论文,为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奠定了独特的基础。
在文章中他说:“艺术具有符号性质这一点,不仅显示于艺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也显示于艺术作品的结构组织里”(转引自《文学史》第一辑,第91页)。
把艺术作品当作显示结构性质的一个符号,这就意味着文学研究思路的变化:研究文学,除了关注文学作品之外,还要探讨作者、读者以及最重要的一环----文学结构的历史性。
对一个结构主义的理论家来说,符号是解释文学特异性所必需的概念。
由于符号概念的引入,布拉格学派便跨过了形式主义文论的局限。
1、符号学理论的基本术语要诠:符号:符号是传达意义的载体。
任何意义的传达不使用一定的符号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可以说,意义本身就是从符号所组成的信息中产生的。
例如,足球裁判吹哨判罚点球:发送者(裁判)---能指(哨音、手势)---所指(犯规违例、暂停、判罚点球)---接受者(编码)(信息)(解码)从上述事例的分析可知,符号的完整定义是:发送者用一个可以感知的物质刺激,使接受者能约定性的了解某种不在场的事物的情况,这一可以感知的东西,就叫做符号。
能指/所指:二者是符号的组成因素。
能指是符号中的“显现”(即可以感知)的部分;所指是符号的意指对象部分。
在语言符号中,能指就是语言的“音-形”部分,所指是语言的“意”,即它所指代的事物或意义、思想、情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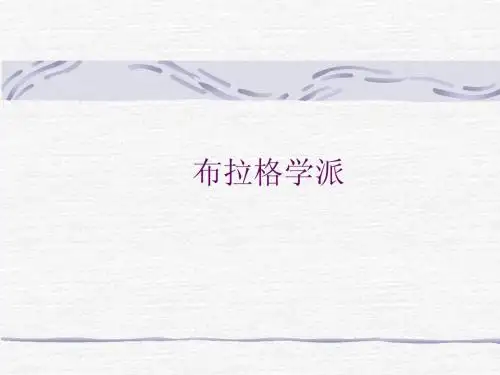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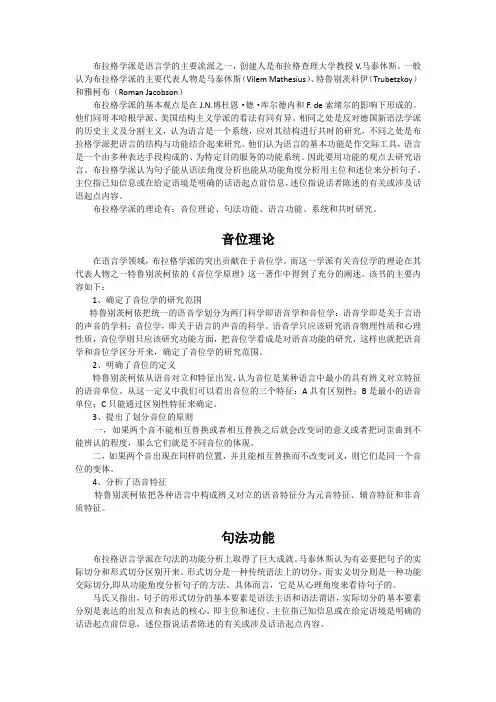
布拉格学派是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创建人是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V.马泰休斯。
一般认为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Vilem Mathesius)、特鲁别茨科伊(Trubetzkoy)和雅柯布(Roman Jacobson)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F. de索绪尔的影响下形成的。
他们同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看法有同有异。
相同之处是反对德国新语法学派的历史主义及分割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应对其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不同之处是布拉格学派把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研究。
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作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
因此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
布拉格学派认为句子能从语法角度分析也能从功能角度分析用主位和述位来分析句子。
主位指已知信息或在给定语境是明确的话语起点前信息,述位指说话者陈述的有关或涉及话语起点内容。
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有:音位理论、句法功能、语言功能、系统和共时研究。
音位理论在语言学领域,布拉格学派的突出贡献在于音位学。
而这一学派有关音位学的理论在其代表人物之一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这一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该书的主要内容如下:1、确定了音位学的研究范围特鲁别茨柯依把统一的语音学划分为两门科学即语音学和音位学:语音学即是关于言语的声音的学科;音位学,即关于语言的声音的科学。
语音学只应该研究语音物理性质和心理性质,音位学则只应该研究功能方面,把音位学看成是对语音功能的研究,这样也就把语音学和音位学区分开来,确定了音位学的研究范围。
2、明确了音位的定义特鲁别茨柯依从语音对立和特征出发,认为音位是某种语言中最小的具有辨义对立特征的语音单位。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音位的三个特征:A具有区别性;B是最小的语音单位;C只能通过区别性特征来确定。
3、提出了划分音位的原则一,如果两个音不能相互替换或者相互替换之后就会改变词的意义或者把词歪曲到不能辨认的程度,那么它们就是不同音位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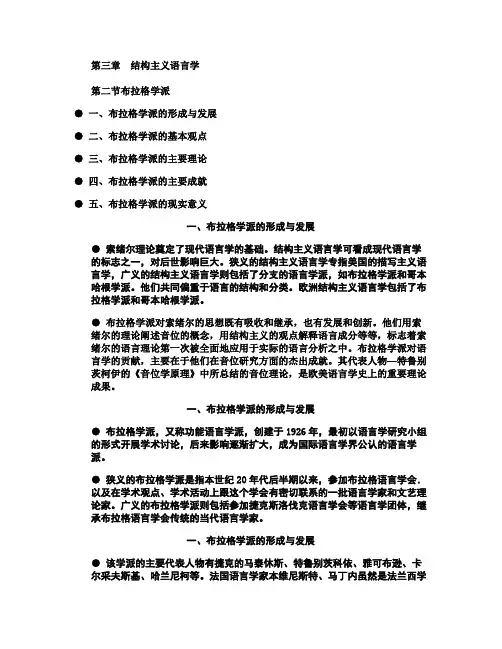
第三章 结构主义语言学第二节布拉格学派● 一、布拉格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二、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 三、布拉格学派的主要理论● 四、布拉格学派的主要成就● 五、布拉格学派的现实意义一、布拉格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索绪尔理论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
结构主义语言学可看成现代语言学的标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巨大。
狭义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专指美国的描写主义语言学,广义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则包括了分支的语言学派,如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
他们共同偏重于语言的结构和分类。
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包括了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
● 布拉格学派对索绪尔的思想既有吸收和继承,也有发展和创新。
他们用索绪尔的理论阐述音位的概念,用结构主义的观点解释语言成分等等,标志着索绪尔的语言理论第一次被全面地应用于实际的语言分析之中。
布拉格学派对语言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音位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
其代表人物—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中所总结的音位理论,是欧美语言学史上的重要理论成果。
一、布拉格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布拉格学派,又称功能语言学派,创建于1926年,最初以语言学研究小组的形式开展学术讨论,后来影响逐渐扩大,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的语言学派。
● 狭义的布拉格学派是指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跟这个学会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广义的布拉格学派则包括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等语言学团体,继承布拉格语言学会传统的当代语言学家。
一、布拉格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捷克的马泰休斯、特鲁别茨科依、雅可布逊、卡尔采夫斯基、哈兰尼柯等。
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马丁内虽然是法兰西学派的后期重要人物,但他们的观点与布拉格学派基本一致,也曾积极参加布拉格学派的学术活动,因此,也被看做布拉格学派的重要人物。
● 1926年秋,布拉格语言学会在布拉格成立。
● 1928年,布拉格学会在参加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海牙时把音位学的观点第一次公诸于世.引起很大的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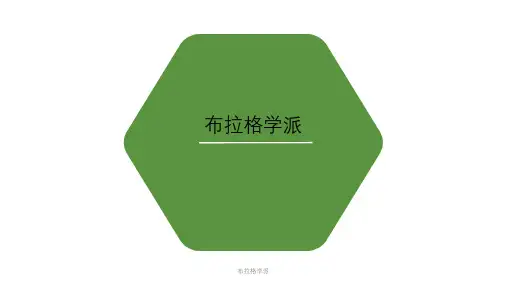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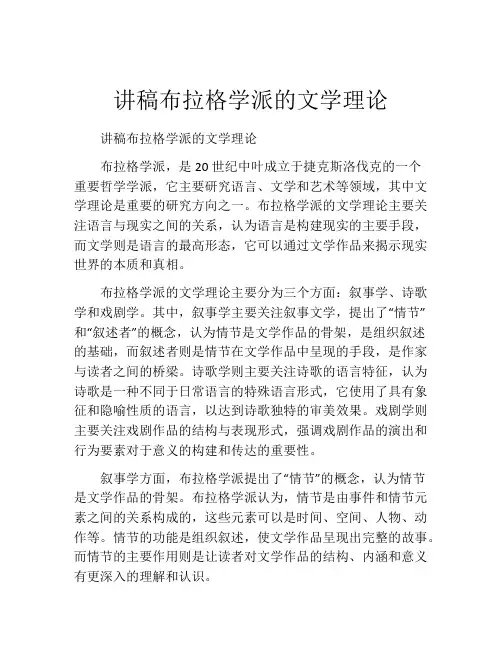
讲稿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讲稿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布拉格学派,是20世纪中叶成立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重要哲学学派,它主要研究语言、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其中文学理论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主要关注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是构建现实的主要手段,而文学则是语言的最高形态,它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来揭示现实世界的本质和真相。
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叙事学、诗歌学和戏剧学。
其中,叙事学主要关注叙事文学,提出了“情节”和“叙述者”的概念,认为情节是文学作品的骨架,是组织叙述的基础,而叙述者则是情节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手段,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诗歌学则主要关注诗歌的语言特征,认为诗歌是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特殊语言形式,它使用了具有象征和隐喻性质的语言,以达到诗歌独特的审美效果。
戏剧学则主要关注戏剧作品的结构与表现形式,强调戏剧作品的演出和行为要素对于意义的构建和传达的重要性。
叙事学方面,布拉格学派提出了“情节”的概念,认为情节是文学作品的骨架。
布拉格学派认为,情节是由事件和情节元素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这些元素可以是时间、空间、人物、动作等。
情节的功能是组织叙述,使文学作品呈现出完整的故事。
而情节的主要作用则是让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结构、内涵和意义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叙述者则是情节在文学作品中呈现的手段,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布拉格学派认为,叙述者的存在和表现方式对于叙事格局和意义的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不仅仅是一个叙事者,更是一个主题的阐释者、价值观的传达者,是将事件和情节联系起来的纽带。
在诗歌学方面,布拉格学派主要关注诗歌的语言特征。
他们认为,诗歌是一种具有象征和隐喻性质的语言形式,与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同。
诗歌的语言是经过精心的构思和运用的,它可以通过语言的美感和音乐性来触发读者的情感反应,使读者对于诗歌作品的意义和内涵产生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布拉格学派主张,诗歌的语言需要具有一种独特的充实感,该语言可以进行意义扩张、形式伸展,并产生意义的差异和关联。
布拉格学派对索绪尔的思想既有吸收和继承,也有发展和创新。
他们用索绪尔的理论阐述音位的概念,用结构主义的观点解释语言成分等等,标志着索绪尔的语言理论第一次被全面地应用于实际的语言分析之中。
布拉格学派对语言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音位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
其代表人物—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原理>>中所总结的音位理论,是欧美语言学史上的重要理论成果。
正如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特鲁别茨柯伊的音位学,就不可能有今日美国的音位学,犹如没有欧几里德几何,就不会有今日的现代几何一样。
”布拉格学派(亦称功能结构主义)是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三大流派之一,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西方语言学流派。
正如美国语言学者鲍林杰所说:“欧洲任何其他语言学团体都没有像布拉格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下面我们从产生背景、代表人物及著作、理论研究、主要成就等四个方面对布拉格学派作简要的评述。
一、产生背景1、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衰微整体上讲,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历史的方法比非历史的方法影响更加广泛。
裴德森在其名著《19世纪的语言学》中甚至没有论及洪堡特。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方法的局限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首先,历史方法过多注意语言个别语音和个别词形的原始形式,对这些个别语音和个别词形与其他语音和词形的相互关系考察不够。
由于这种方法的关注点在于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语言的整体结构性和系统性往往被忽略了。
其次,语言的历史材料离我们越是久远越是残缺不全,而根据一些残缺不全的材料虚构原始语言形式往往会使问题简单化,并带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
在语言学史上,一种方法的提出和发展往往是基于对已有的方法的批判性的继承的。
1911年,马泰修斯在布拉格发表了《论语言现象的潜势》的著名演讲,索绪尔在日内瓦讲授共时语言学,博阿斯撰写序言的《美洲印第安手册》在美国出版。
这表明共时研究的思想已经在同一个阶段在不同的地区产生的。
12.0 绪论12.1 布拉格学派12.2 伦敦学派12.3 美国结构主义12.4 转换生成语法12.5 修正还是反叛?问题与练习答案12.1 布拉格学派12.1.1 绪论12.1.2 音位学和音位对立12.1.3 句子功能前景(FSP)12.1.1 绪论布拉格学派(布拉格语言学会)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26年,V.马泰休斯(1882-1946)领导召开了该学会的第一次会议。
布拉格学派实践了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即共时语言学研究。
它对语言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语言。
布拉格学派一度成为影响语言学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源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洲任何其他语言学团体都没有像布拉格语言学会那样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布拉格学派曾影响到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要发展"(Bolinger, 1968)。
在布拉格学派形成的诸多观点中,有三点至为重要。
第一,对语言的共时研究由于可以得到全面的、可控制的语言材料以供参考而被充分强调,同时,也没有严格的理论藩篱被树立起来将之同历时语言研究相分离。
第二,布拉格学派强调语言的系统性这一本质属性。
指出语言系统中的任何成分如果以孤立的观点去加以研究,都不会得到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要作出正确的评价,就必须明确该成分与同一语言中相共存的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语言成分之所以存在,就在于他们彼此功能上的对比或对立。
第三,布拉格学派在某种意义上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功能",是一种由某一语言社团使用的,用来完成一系列基本职责和任务的工具。
12.1.2 音位学和音位对立布拉格学派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其音位学说以及对语音学和音位学的区分。
在这一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就是特鲁别茨柯依。
他最完整和权威的论述都集中表述于1939年出版的《音位学原理》一书中。
特鲁别茨柯依沿用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的理论,提出语音学属于"言语",而音位学则属于"语言"。
布拉格学派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是由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发展出来的,主要包括三个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
下面我们先介绍布拉格学派。
一布拉格学派的形成1926年,特鲁别茨柯依(H.C.Tpy euko ,1890—1938)、马德修斯(V.Mathesius,1832—1945)、雅可布逊(R.Jakobson,1896—1982,20至30年代侨居布拉格,后移居美国,在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在布拉格成立布拉格语言学会(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1928年,第一次语言学家国际会议在海牙召开,他们在会议上十分活跃,提出了好几篇音位学论文,被称为“布拉格音位学派”。
1929年的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他们提出了布拉格学派的论纲,1929—1939年,他们出版了《布拉格语言学会会刊》(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de Prague)。
1935—1953年,出版季刊《词与文》(SaS),刊物的副标题是:布拉格语言学会机关刊物。
1953年布拉格语言学会在组织上解体后,《词与文》变成了捷克科学院的刊物,至今仍在出版。
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理论,既受到索绪尔很大的影响,也受到波兰著名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J.Baudoin de Courtenay,1845—1929)的影响。
博杜恩早在1870年就明确地提出语言和言语区分的问题。
1876年己提出应区分语言的静态和动态的思想,这些,都与索绪尔的理论有共同之处。
博杜恩的最大贡献在音位学方面。
在1881年,他就指出,必须明确地区分音素和音位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单位。
音素是一种纯语音现象,而音位则是词的某一部分语音性质的总和。
他提出必须区分两门不同的语音学学科:人类语音学和心理语音学。
人类语音学从生理—声学观点研究人类语言所有的语音,即音素。
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一、概述布拉格学派是结构主义思想的发源地。
形式主义文论放弃了他们的“文学自足体”的美学孤立主义(自我封闭主义)之后,他们从纯形式主义立场后退,认为文学作品应当置于其社会环境来考察时,形式主义就引出了结构主义,“科学本身在变化---因而我们随之变化”(爱亨鲍姆)。
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穆卡洛夫斯基、雅可布森、沃迪契卡。
二、文学的符号学性质:布拉格学派对文学本质的考察符号学思想是布拉格学派解释文学本质特征的固定出发点。
穆卡洛夫斯基《艺术作为符号的事实》(1934)是美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艺术符号学论文,为布拉格学派的理论奠定了独特的基础。
在文章中他说:“艺术具有符号性质这一点,不仅显示于艺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也显示于艺术作品的结构组织里”(转引自《文学史》第一辑,第91页)。
把艺术作品当作显示结构性质的一个符号,这就意味着文学研究思路的变化:研究文学,除了关注文学作品之外,还要探讨作者、读者以及最重要的一环----文学结构的历史性。
对一个结构主义的理论家来说,符号是解释文学特异性所必需的概念。
由于符号概念的引入,布拉格学派便跨过了形式主义文论的局限。
1、符号学理论的基本术语要诠:符号:符号是传达意义的载体。
任何意义的传达不使用一定的符号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可以说,意义本身就是从符号所组成的信息中产生的。
例如,足球裁判吹哨判罚点球:发送者(裁判)---能指(哨音、手势)---所指(犯规违例、暂停、判罚点球)---接受者(编码)(信息)(解码)从上述事例的分析可知,符号的完整定义是:发送者用一个可以感知的物质刺激,使接受者能约定性的了解某种不在场的事物的情况,这一可以感知的东西,就叫做符号。
能指/所指:二者是符号的组成因素。
能指是符号中的“显现”(即可以感知)的部分;所指是符号的意指对象部分。
在语言符号中,能指就是语言的“音-形”部分,所指是语言的“意”,即它所指代的事物或意义、思想、情感等。
能指/ 所指的关系是武断规定的,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的关联方式是规约性的。
由谁来规定?由相对固定的社会契约所规定,例如给朋友送鲜花,得要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决定是送玫瑰、康耐馨还是送白色的菊花。
而这些规定又往往由于文化背景和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
因此,这又带来下面的问题:能指 /所指具有不对应性。
为什么?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符号体系的人,对能指/ 所指的分割标准不同,例如,中国人说“红茶”,英国人认为是黑的;中国人说白开水、白纸、白酒,外国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水、纸、酒的“白”色。
由能指/ 所指的不对应性,说明:所指并不是明确地预先存在,等待着“能指”来“指”代它们。
言语/ 语言:言语/ 语言的区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对语言学作出的划时代的贡献。
在此之前,语言学是一种个体语言学,或称描述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把研究对象界定为语言,而不是言语。
为什么?在一个系统中,显在的、具体的行为总是受制于一个深层的、隐在的系统,结构主义者就把前者叫做表层结构,后者叫做深层结构。
在语言符号中,言语是个别的、零乱的,语言则是系统的、有序的。
索绪尔提出言语和语言的二元对立,是受到19世纪末社会学创建时期的一场争论的启发。
争论中,杜克海姆坚持社会的集体意识观,而塔尔德则坚持独立的个人表现。
索绪尔敏锐的意识到二人的差异实际上是一个语言/ 言语的二元对立关系。
符号中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差不多的人文科学中,都可以找出一个或者几个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则);意识/ 潜意识(精神分析学);无数的讲述实践 /“知识体系”(富柯的“知识考古学”)。
在文学中,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的表现就更为复杂:文学作品 /意识形态(伊格尔顿);作品/ 生活(洛特曼);批评/ 诗学(惹奈特);叙述情节 /叙述语法(托多罗夫);述本/ 底本(巴尔特);作品的语言表现/ 构成元素的基本逻辑(格雷马斯)。
信息/符码:言语 /语言的二元对立,在符号学中首先表现为符号信息/ 符码的二元对立。
符码是预先以某种方式规定好的把能指转换成所指的规则。
没有符码,发送者进行的符号活动只是一堆能刺激感官而毫无规则的乱七八糟的游戏,而且完全不可解;而接受者不掌握符码,就无法理解符号活动所传达的意义,例如很多人不能欣赏交响乐、芭蕾舞和京剧,首先是因为没有掌握它们的艺术符码。
如同一个不懂得围棋规则的人,观赏围棋怎么可能入迷呢?信息是符号的能指部分。
一个符号活动是信息的发送者用符码把他要传达的意义转换成信息,而符号信息的接受者则用同一套符码把这信息转换成他所能理解的意义。
例如,火车开车前,信号员用信号灯发出信息(灯的颜色,摇晃的方向、幅度等),司机根据既定符码将信息转换成意义。
在上述活动中,发送者进行的工作称为“编码”,接受者所做的工作称为“解码”。
2、雅可布森对符指过程的分析和他对文学特性的解释:符指过程:一个符号表意的全过程。
雅可布森提出了符指过程六因素分析法:发送者(发电报的人)、接受者(用符码解读能指认出所指的人)、信息(能指,即电报)、接触(符号传送的中介渠道,即无线电)、符码(电码本)、语境(所指)。
与符指过程六因素相对应,有六种不同的功能:情绪性(发送者)、意动性(接受者)、交际性(接触)、元语言倾向(符码)、指称性(语境,即所指)、诗性(信息,即能指)。
(说明:所谓元语言,是指符号的代码集合。
元语言的原意是对语言诠释作出规定的语言。
所谓“元语言倾向”,是指对编码、解码等元语言操作的关心。
)雅可布森对符指过程六因素及其与之相应的六种不同功能,曾经提出下列经典图式:语境(所指)指称性(所指)信息(能指)诗性(能指)发送者-------------------接受者情绪性(发送者)------------------意动性(接受者)接触(符号传送中介)交际性(接触)符码(编码本)元语言倾向(符码)雅可布森不仅区分了符指过程的六因素,而且指出各种不同的符指过程并非平衡的,而是在这六个因素中各有侧重。
当某一具体的符指过程强调六种因素中的一种时,某种特殊的功能就占据支配地位,成为系统中的“主导”,正是“主导”决定着符指过程的性质。
在六种功能中,如果一个符指过程突出诗性功能,即符号指向本身时,这个符号就成为艺术文本。
在“诗性”即符号的自指性较为明显的符指过程中,符号表达的意思受到美感功能的干扰,所以读者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语义联想,因此接受活动中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审美和语义上的阐释。
雅可布森指出,诗性不仅出现在艺术中,日常语言中也常出现(“可怕的哈里”例:“一个女孩总是说‘可怕的哈里’这类话,人家问她:‘为什么要用可怕的这个词?’她说:‘因为我恨他。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说他是坏透的、可恨的、讨厌的等词儿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可怕的这词对他更合适。
’”雅可布森分析说,“可怕的”一词的音节读法中有一种品质不可代替,这个女孩喜欢这个词本身,而不仅仅是它的“所指”。
此后,学术界就把雅可布森所说的这种“诗性”称为符号的自指性。
)。
雅可布森指出的“文学的特异性在于符号指向本身”,对于文学本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雅可布森认为,“诗性功能并不是语言艺术的唯一功能,但却是它的主导性的、决定性的功能”,文学文本并非没有其他功能,只是在文学作品中,诗性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诗性“加深了符号同客体间的根本分裂”,也就是说,符号的自指性越强,越无法传达信息,无法达到所指,“诗性”与“认知性”成反比。
例如,中国传统京剧符号的自指性很强(表现在服装、表演程式、脸谱、唱腔等方面),而认知性很弱;革命样板戏弱化了传统京剧的符号自指性(表现在淡化传统京剧的表现手段,加进现实主义手法,即“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从而使认知性得到强化;前者娱乐性很强,后者强调艺术功能的宣传教化层面。
3、横组合/纵聚合的双轴关系与文学类型的划分西方文论史上文学类型划分的传统依据是亚里斯多得的“模仿”说,即根据模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来划分文学类型。
例如,从模仿对象来划分,“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如果从模仿的方式来说,“既可以象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模仿者用动作来模仿”。
(《诗学》第二章、第三章)雅可布森从符号学角度重新审视文学类型,他对文学类型进行分类的根据是符号学中另一组二元对立:横组合 /纵聚合(转喻/ 隐喻)。
(1)横组合/ 纵聚合横组合关系,是符号或符号链(符号链是有句法的符号集合,例如,“按姓氏笔画排列”就是一种句法)内各成分之间的有顺序的排列,因此,横组合也就是一个系统内各因素在“水平方向”的展开,这样展开所形成的任何一个组合部分,称为“横组合段”。
纵聚合关系,是横组合段上的每一个成分后面所隐藏的、未得以显露的、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替代它的一切成分,它们构成了一连串的“纵聚合系”(又称“词汇套”)。
因为它们是“垂直”展开的,故称“纵聚合”。
任何系统构成中必然出现这两个方面:横组合是系统本身要求的排列,纵聚合是系统内成分的选定。
例如写诗,诗行按特殊要求形成横组合,“炼字”则是纵聚合上的运作(“春风又绿江南岸”,诗行是七言律诗排列的要求,“绿”字是纵聚合上的选择;又如“僧敲月下门”句中的“推、敲”,只是对横组合段上某一成分进行纵聚合轴上的选择。
由此可见,横组合轴上的每个成分有若干可供选择的替代物(但每个成分具有的“可供选择的替代物”的多少各不相同)。
(2)横组合/ 纵聚合的双轴关系与比喻中的转喻/ 隐喻雅可布森把“横组合关系”称为“结合轴”,“纵聚合关系”称为“选择轴”。
横组合段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邻接性”的,纵聚合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相似性”的。
邻接只有一种可能,而相似可以在不同的方面相似,因此,每一成分可以有一系列的纵聚合系。
雅可布森又指出,上述特征正是比喻中两个主要类型的特征:依靠相似性的比喻就是隐喻,就是因某一方面相似而替代(例如以鲜花代美女);依靠邻接性的比喻就是转喻,就是因一定的邻接关系而替代(例如以辫子或裙子代美女)。
在正常的语言交流中,必须依靠这两者才能正常运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就会得“失语症”。
失语症是一种由大脑受损伤而造成的疾病,主要病症是语言障碍。
这种障碍可以分成两类:一是连接词、介词、副词等语言连接性因素的丢失,不能进行正常的句法组合,表现为词序混乱。
这类病人丢失的是横组合功能(表现为语无伦次),但由于保持了纵聚合能力,找不到适当的词时会从纵聚合系中拖出很奇怪的词来作比喻(例如用“小望远镜”来代替显微镜,表现出“出语惊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