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自由与社会化
- 格式:doc
- 大小:19.00 KB
- 文档页数: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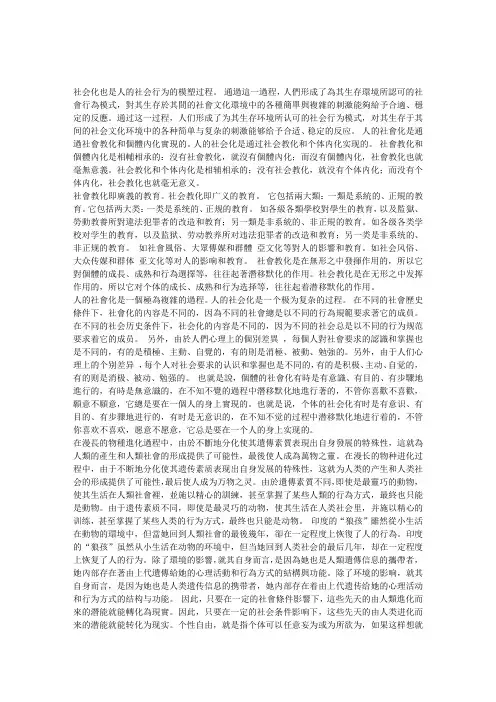
社会化也是人的社会行为的模塑过程。
通過這一過程,人們形成了為其生存環境所認可的社會行為模式,對其生存於其間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的各種簡單與複雜的刺激能夠給予合適、穩定的反應。
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形成了为其生存环境所认可的社会行为模式,对其生存于其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各种简单与复杂的刺激能够给予合适、稳定的反应。
人的社會化是通過社會教化和個體內化實現的。
人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实现的。
社會教化和個體內化是相輔相承的:沒有社會教化,就沒有個體內化;而沒有個體內化,社會教化也就毫無意義。
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是相辅相承的:没有社会教化,就没有个体内化;而没有个体内化,社会教化也就毫无意义。
社會教化即廣義的教育。
社会教化即广义的教育。
它包括兩大類:一類是系統的、正規的教育。
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系统的、正规的教育。
如各級各類學校對學生的教育,以及監獄、勞動教養所對違法犯罪者的改造和教育;另一類是非系統的、非正規的教育。
如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以及监狱、劳动教养所对违法犯罪者的改造和教育;另一类是非系统的、非正规的教育。
如社會風俗、大眾傳媒和群體亞文化等對人的影響和教育。
如社会风俗、大众传媒和群体亚文化等对人的影响和教育。
社會教化是在無形之中發揮作用的,所以它對個體的成長、成熟和行為選擇等,往往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社会教化是在无形之中发挥作用的,所以它对个体的成长、成熟和行为选择等,往往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人的社會化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
人的社会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社會化的內容是不同的,因為不同的社會總是以不同的行為規範要求著它的成員。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化的内容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社会总是以不同的行为规范要求着它的成员。
另外,由於人們心理上的個別差異,每個人對社會要求的認識和掌握也是不同的,有的是積極、主動、自覺的,有的則是消極、被動、勉強的。
另外,由于人们心理上的个别差异,每个人对社会要求的认识和掌握也是不同的,有的是积极、主动、自觉的,有的则是消极、被动、勉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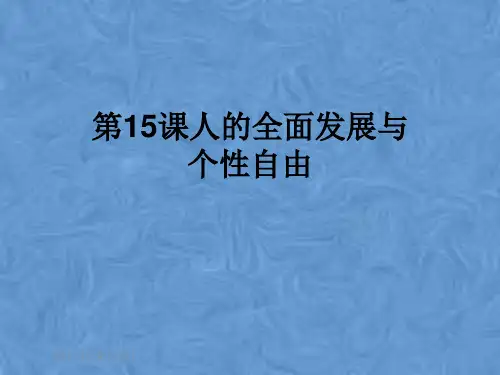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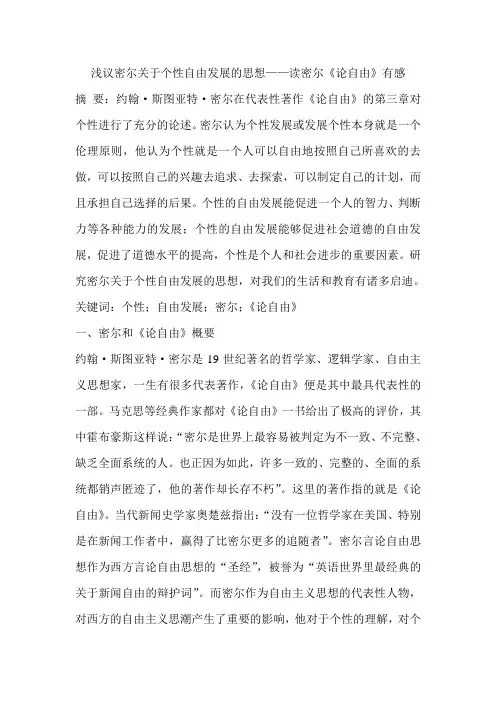
浅议密尔关于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读密尔《论自由》有感摘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代表性著作《论自由》的第三章对个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密尔认为个性发展或发展个性本身就是一个伦理原则,他认为个性就是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追求、去探索,可以制定自己的计划,而且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个性的自由发展能促进一个人的智力、判断力等各种能力的发展;个性的自由发展能够促进社会道德的自由发展,促进了道德水平的提高,个性是个人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研究密尔关于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对我们的生活和教育有诸多启迪。
关键词:个性;自由发展;密尔;《论自由》一、密尔和《论自由》概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一生有很多代表著作,《论自由》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都对《论自由》一书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其中霍布豪斯这样说:“密尔是世界上最容易被判定为不一致、不完整、缺乏全面系统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一致的、完整的、全面的系统都销声匿迹了,他的著作却长存不朽”。
这里的著作指的就是《论自由》。
当代新闻史学家奥楚兹指出:“没有一位哲学家在美国、特别是在新闻工作者中,赢得了比密尔更多的追随者”。
密尔言论自由思想作为西方言论自由思想的“圣经”,被誉为“英语世界里最经典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辩护词”。
而密尔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对于个性的理解,对个性发展的重视更是引起了人们更深的思考。
本文将就密尔《论自由》第三章关于个性的论述发表一点浅薄的看法。
《论自由》共5章,以公民自由为中心,对自由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
第一章为引论,指出全书要阐述的是公民自由,也称作社会自由,探讨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的关系。
第二章论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认为人类应当自由形成意见、自由发表意见,否则便是人类理性与德性的毁灭,阐述了思想自由的伦理依据和伦理正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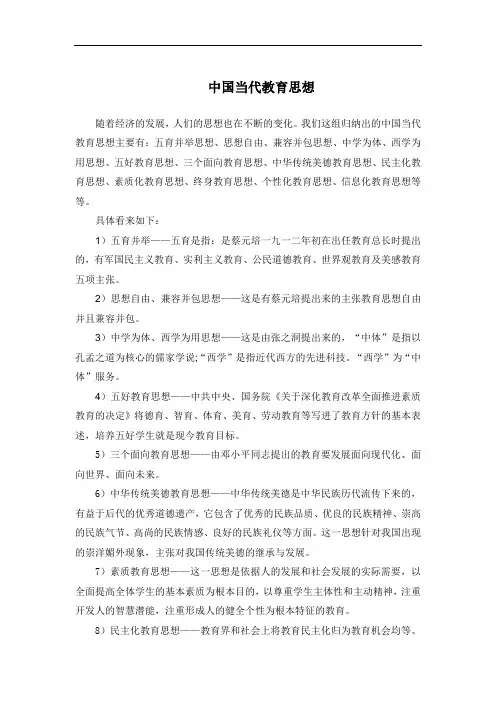
中国当代教育思想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的变化。
我们这组归纳出的中国当代教育思想主要有:五育并举思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五好教育思想、三个面向教育思想、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思想、民主化教育思想、素质化教育思想、终身教育思想、个性化教育思想、信息化教育思想等等。
具体看来如下:1)五育并举——五育是指:是蔡元培一九一二年初在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的,有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主张。
2)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这是有蔡元培提出来的主张教育思想自由并且兼容并包。
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这是由张之洞提出来的,“中体”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
“西学”为“中体”服务。
4)五好教育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写进了教育方针的基本表述,培养五好学生就是现今教育目标。
5)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6)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思想——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历代流传下来的,有益于后代的优秀道德遗产,它包含了优秀的民族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等方面。
这一思想针对我国出现的崇洋媚外现象,主张对我国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展。
7)素质教育思想——这一思想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
8)民主化教育思想——教育界和社会上将教育民主化归为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自由、学制民主化、课堂生活民主化、学习机会民主化等几点。
主张教育的民主化。
9)终身教育思想——提倡建立以终生学习体系为主轴的新教育体系,指社会每个成员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个体发展的需要,贯穿于人的一生的,持续的学习过程,以生活、终身、教育三个为基本大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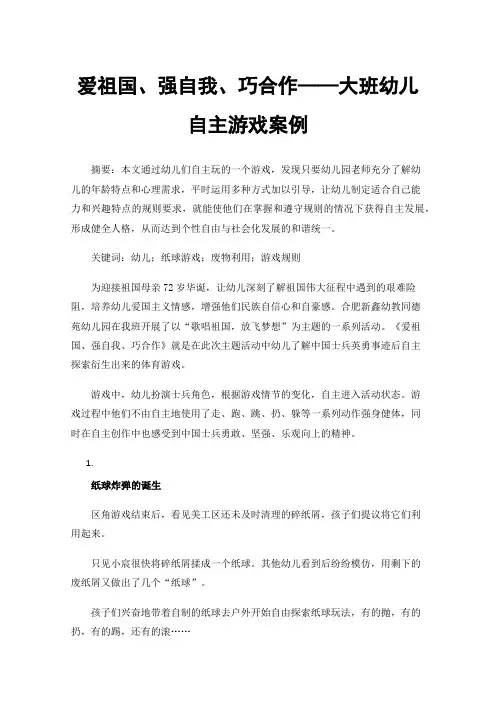
爱祖国、强自我、巧合作——大班幼儿自主游戏案例摘要:本文通过幼儿们自主玩的一个游戏,发现只要幼儿园老师充分了解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心理需求,平时运用多种方式加以引导,让幼儿制定适合自己能力和兴趣特点的规则要求,就能使他们在掌握和遵守规则的情况下获得自主发展,形成健全人格,从而达到个性自由与社会化发展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幼儿;纸球游戏;废物利用;游戏规则为迎接祖国母亲72岁华诞,让幼儿深刻了解祖国伟大征程中遇到的艰难险阻,培养幼儿爱国主义情感,增强他们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合肥新鑫幼教同德苑幼儿园在我班开展了以“歌唱祖国,放飞梦想”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
《爱祖国、强自我、巧合作》就是在此次主题活动中幼儿了解中国士兵英勇事迹后自主探索衍生出来的体育游戏。
游戏中,幼儿扮演士兵角色,根据游戏情节的变化,自主进入活动状态。
游戏过程中他们不由自主地使用了走、跑、跳、扔、躲等一系列动作强身健体,同时在自主创作中也感受到中国士兵勇敢、坚强、乐观向上的精神。
1.纸球炸弹的诞生区角游戏结束后,看见美工区还未及时清理的碎纸屑,孩子们提议将它们利用起来。
只见小宸很快将碎纸屑揉成一个纸球。
其他幼儿看到后纷纷模仿,用剩下的废纸屑又做出了几个“纸球”。
孩子们兴奋地带着自制的纸球去户外开始自由探索纸球玩法,有的抛,有的扔,有的踢,还有的滚……突然,小宸被杨杨的纸球砸中,杨杨高兴的欢呼到:“你被炸弹砸中了,你输了。
”“好吧,这次我没躲开炸弹,是我输了,我们再来一局”旁边几个小男生看见后,纷纷要求加入。
通过商议,他们自由组合分成两队,分别是小宸带领的红队和以杨杨为首的蓝队。
两队士兵在队长的带领下面对面站好后,不知谁喊了一声“开火”,双方开始向对方投掷“炸弹”,一时间场面十分热闹,只见幼儿在扔“炸弹”的同时,也试图通过跑、跳、躲等方式进行躲避,其他幼儿看见后纷纷为他们的好朋友加油助威。
教师的思考这次美工活动即将结束时,孩子们创造性的对纸进行了“废物利用”,做成纸球后变成体育游戏的道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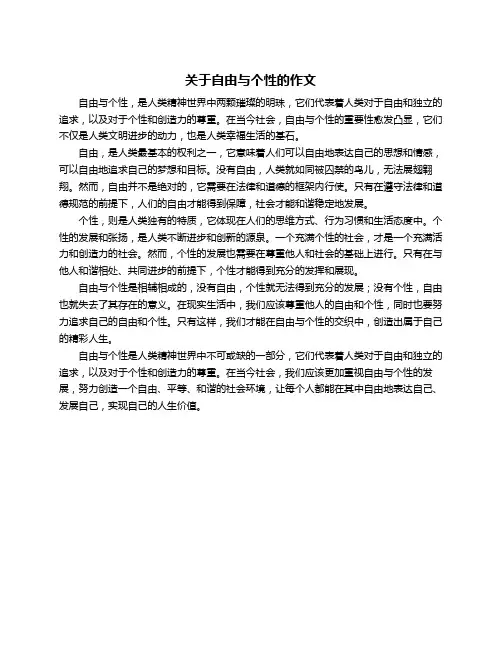
关于自由与个性的作文
自由与个性,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两颗璀璨的明珠,它们代表着人类对于自由和独立的追求,以及对于个性和创造力的尊重。
在当今社会,自由与个性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它们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也是人类幸福生活的基石。
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它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没有自由,人类就如同被囚禁的鸟儿,无法展翅翱翔。
然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它需要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行使。
只有在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人们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地发展。
个性,则是人类独有的特质,它体现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生活态度中。
个性的发展和张扬,是人类不断进步和创新的源泉。
一个充满个性的社会,才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
然而,个性的发展也需要在尊重他人和社会的基础上进行。
只有在与他人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
自由与个性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自由,个性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个性,自由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自由和个性,同时也要努力追求自己的自由和个性。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由与个性的交织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自由与个性是人类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代表着人类对于自由和独立的追求,以及对于个性和创造力的尊重。
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由与个性的发展,努力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自由地表达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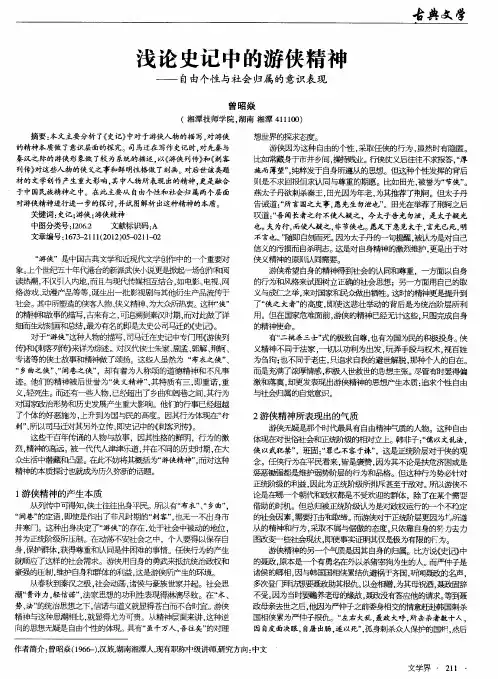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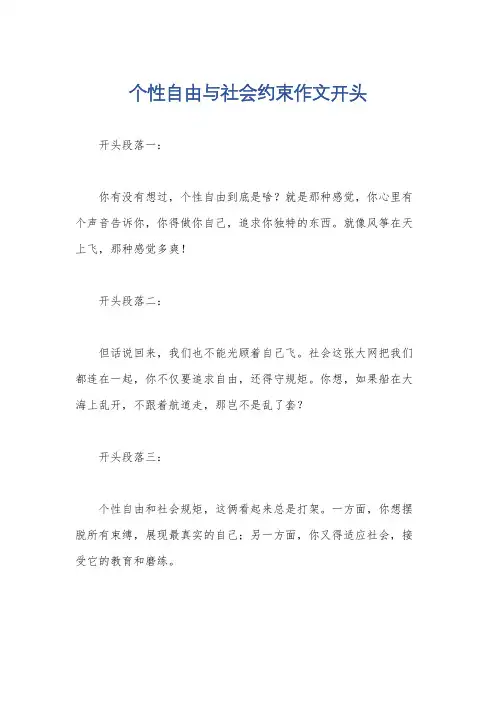
个性自由与社会约束作文开头开头段落一:
你有没有想过,个性自由到底是啥?就是那种感觉,你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你,你得做你自己,追求你独特的东西。
就像风筝在天上飞,那种感觉多爽!
开头段落二:
但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能光顾着自己飞。
社会这张大网把我们都连在一起,你不仅要追求自由,还得守规矩。
你想,如果船在大海上乱开,不跟着航道走,那岂不是乱了套?
开头段落三:
个性自由和社会规矩,这俩看起来总是打架。
一方面,你想摆脱所有束缚,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另一方面,你又得适应社会,接受它的教育和磨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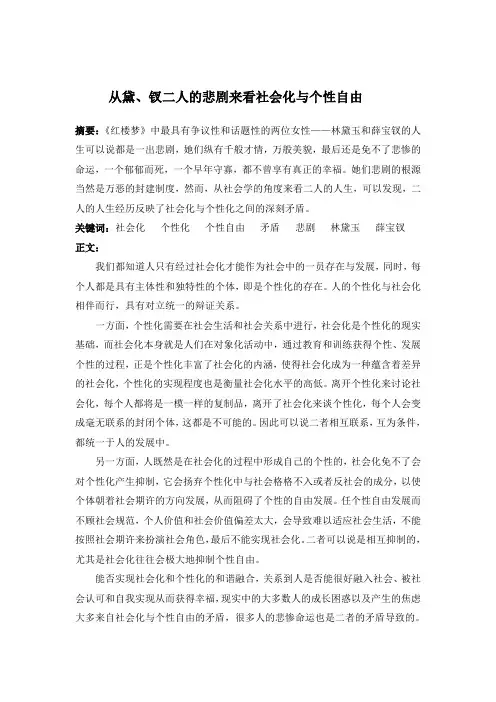
从黛、钗二人的悲剧来看社会化与个性自由摘要:《红楼梦》中最具有争议性和话题性的两位女性——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人生可以说都是一出悲剧,她们纵有千般才情,万般美貌,最后还是免不了悲惨的命运,一个郁郁而死,一个早年守寡,都不曾享有真正的幸福。
她们悲剧的根源当然是万恶的封建制度,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二人的人生,可以发现,二人的人生经历反映了社会化与个性化之间的深刻矛盾。
关键词:社会化个性化个性自由矛盾悲剧林黛玉薛宝钗正文:我们都知道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存在与发展,同时,每个人都是具有主体性和独特性的个体,即是个性化的存在。
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相伴而行,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个性化需要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进行,社会化是个性化的现实基础,而社会化本身就是人们在对象化活动中,通过教育和训练获得个性、发展个性的过程,正是个性化丰富了社会化的内涵,使得社会化成为一种蕴含着差异的社会化,个性化的实现程度也是衡量社会化水平的高低。
离开个性化来讨论社会化,每个人都将是一模一样的复制品,离开了社会化来谈个性化,每个人会变成毫无联系的封闭个体,这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可以说二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都统一于人的发展中。
另一方面,人既然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个性的,社会化免不了会对个性化产生抑制,它会扬弃个性化中与社会格格不入或者反社会的成分,以使个体朝着社会期许的方向发展,从而阻碍了个性的自由发展。
任个性自由发展而不顾社会规范,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偏差太大,会导致难以适应社会生活,不能按照社会期许来扮演社会角色,最后不能实现社会化。
二者可以说是相互抑制的,尤其是社会化往往会极大地抑制个性自由。
能否实现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和谐融合,关系到人是否能很好融入社会、被社会认可和自我实现从而获得幸福,现实中的大多数人的成长困惑以及产生的焦虑大多来自社会化与个性自由的矛盾,很多人的悲惨命运也是二者的矛盾导致的。
例如下面的林黛玉和薛宝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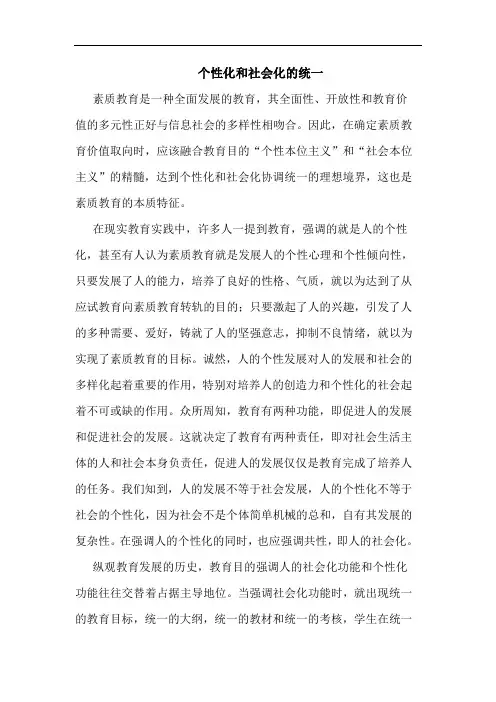
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种全面发展的教育,其全面性、开放性和教育价值的多元性正好与信息社会的多样性相吻合。
因此,在确定素质教育价值取向时,应该融合教育目的“个性本位主义”和“社会本位主义”的精髓,达到个性化和社会化协调统一的理想境界,这也是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
在现实教育实践中,许多人一提到教育,强调的就是人的个性化,甚至有人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发展人的个性心理和个性倾向性,只要发展了人的能力,培养了良好的性格、气质,就以为达到了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目的;只要激起了人的兴趣,引发了人的多种需要、爱好,铸就了人的坚强意志,抑制不良情绪,就以为实现了素质教育的目标。
诚然,人的个性发展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多样化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对培养人的创造力和个性化的社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众所周知,教育有两种功能,即促进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发展。
这就决定了教育有两种责任,即对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和社会本身负责任,促进人的发展仅仅是教育完成了培养人的任务。
我们知到,人的发展不等于社会发展,人的个性化不等于社会的个性化,因为社会不是个体简单机械的总和,自有其发展的复杂性。
在强调人的个性化的同时,也应强调共性,即人的社会化。
纵观教育发展的历史,教育目的强调人的社会化功能和个性化功能往往交替着占据主导地位。
当强调社会化功能时,就出现统一的教育目标,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考核,学生在统一的模式中铸就,压抑了个性和创造性,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也就失去了独立性,最终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
当强调个性化功能时,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学生的个性,教育目标、教学大纲、教材,甚至教师都成了发展学生个性的条件和工具,教育缺乏必要的控制,学生呈自由发展趋势,多元化、个性化不能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结果致使伦理道德滑坡,社会责任意识减弱,人际关系冷淡,缺乏合作、理解、认同的精神,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同样不适合信息社会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第一章: 教育与教育学第一节: 教育的概念定义: 教育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促使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体化的实践活动。
性质:1.实践性。
2.交往性: 个性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性化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基础、密不可分。
动力性: 教育活动在上述进程中起到促进和加速作用。
社会性:教育活动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也是塑造不同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学校教育的定义: 学校教育实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促使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体化的实践活动。
基本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作用于学生的全部信息, 既包括了信息的内容, 也包括了信息传递和反馈的形式, 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要素的关系: 相互独立、相互规定、构成完整的系统。
学校教育的过程就是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二节: 教育的起源与发展起源:1.神话起源说宗教(错误的、非科学的)2.生物起源说代表人: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勒图尔诺、英国教育学家沛西·能3.教育不只存在于人类社会, 甚至存在于动物界, 完全来自动物的本能, 是种族发展的本能需要。
4.没有把握教育的目的性和社会性, 仅从外在行为的角度论述。
5.心理起源说代表人: 美国教育史家孟禄6.劳动起源说代表: 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和我国,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产生发展: P16各阶段教育的特征:古代社会与古代教育1.原始社会教育:2.教育水平低3.教育没有阶级性4.教育与原始宗教或仪式有着密切的联系1.奴隶社会的教育:2.古代学校的出现教育阶级性的出现: 奴隶主对精神生活和生产资料的绝对占有, 同样占领了学校, 使学校培养奴隶主阶级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人才。
教育对象主要是奴隶主贵族子弟, 内容以军事教育与道德教育为主。
古代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 有非正规的教育方式。
1.封建社会教育:2.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适合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官吏、牧师或骑士, 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治国方略, 培养能够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官吏。
社会化和性格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社会化一直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小到大,我们的性格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遗传、环境和社会化等方面。
社会化对于我们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化和性格的关系。
社会化的概念社会化,是指人类在社会中成长和发展的过程。
我们通过接受和参与社会的各种规范、价值观、文化和行为方式等,来适应社会和学习如何生存和发展。
社会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对外界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是外界对个体的影响。
社会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行为、个性、价值观等方面。
社会化和性格的关系社会化对于我们的性格塑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性情、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从而塑造了我们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社会化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许多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
例如,我们接受到了通情达理的观念,就会在与他人交流时更加理性和友善;而如果我们接受了权力至上的观念,则可能会变得喜欢施加自己的意志力。
另一方面,社会化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
我们在成长中接受了许多社会规范和行为方式的约束,这些规范和行为方式会影响我们的日常行为。
例如,我们接受了劳动的价值观,就会习惯于勤奋工作;而如果我们接受了消费至上的观念,则可能会形成浪费的行为习惯。
此外,社会化还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个性特质。
我们在接受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接受到许多与价值观相关的观念;而人的个性特质则是由遗传和环境两方面决定的,其中环境因素主要是指社会化的影响。
因此,社会化会与我们的遗传背景一起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个性特质。
例如,我们接受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就会形成义利观相平衡的个性特质;而如果我们接受了牟利至上的观念,则可能会形成利益优先的个性特质。
如何进行良好的社会化良好的社会化,可以让我们形成良好的性格和品德,帮助我们适应社会并获得成功。
从黛、钗二人的悲剧来看社会化与个性自由
摘要:《红楼梦》中最具有争议性和话题性的两位女性——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人生可以说都是一出悲剧,她们纵有千般才情,万般美貌,最后还是免不了悲惨的命运,一个郁郁而死,一个早年守寡,都不曾享有真正的幸福。
她们悲剧的根源当然是万恶的封建制度,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二人的人生,可以发现,二人的人生经历反映了社会化与个性化之间的深刻矛盾。
关键词:社会化个性化个性自由矛盾悲剧林黛玉薛宝钗
正文:
我们都知道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存在与发展,同时,每个人都是具有主体性和独特性的个体,即是个性化的存在。
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相伴而行,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个性化需要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进行,社会化是个性化的现实基础,而社会化本身就是人们在对象化活动中,通过教育和训练获得个性、发展个性的过程,正是个性化丰富了社会化的内涵,使得社会化成为一种蕴含着差异的社会化,个性化的实现程度也是衡量社会化水平的高低。
离开个性化来讨论社会化,每个人都将是一模一样的复制品,离开了社会化来谈个性化,每个人会变成毫无联系的封闭个体,这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可以说二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都统一于人的发展中。
另一方面,人既然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个性的,社会化免不了会对个性化产生抑制,它会扬弃个性化中与社会格格不入或者反社会的成分,以使个体朝着社会期许的方向发展,从而阻碍了个性的自由发展。
任个性自由发展而不顾社会规范,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偏差太大,会导致难以适应社会生活,不能按照社会期许来扮演社会角色,最后不能实现社会化。
二者可以说是相互抑制的,尤其是社会化往往会极大地抑制个性自由。
能否实现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和谐融合,关系到人是否能很好融入社会、被社会认可和自我实现从而获得幸福,现实中的大多数人的成长困惑以及产生的焦虑大多来自社会化与个性自由的矛盾,很多人的悲惨命运也是二者的矛盾导致的。
例如下面的林黛玉和薛宝钗。
一、林黛玉
林黛玉应该算是文学作品中社会化不成功的人物形象中的典型了。
她幼年丧母,后又丧父,一直在外婆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的人生和与生俱来的敏感忧伤气质使得她在贾府中显得孤僻、难以让人亲近和喜爱。
她自幼沉醉在诗书营造的美的世界里,一味专注于对天地人生的感悟,也使得她不谙世故人情,与贾府的世俗社会距离太远。
如此敏感孤僻、的性格加上常被他人认为小气多心、不能得罪、不好迁必然显得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不符合以贾母、王夫人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人物对女子的审美标准,尽管她才情相貌出众,有个性有思想,但是与当时社会对女子要求的德、言、容、功存在分歧差异,导致无法像薛宝钗一样得到贾府上下的认可和赞美。
贾府的人对她的态度转变从里面最能代表社会权威的贾母对她感情的渐渐疏远可以明显看出来,从“被贾母搂在怀里心肝儿肉儿的大哭、万般怜爱”,到“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法,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的嫌弃,到“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是断断有不得的。
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
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的冷漠,连最亲的外祖母也是黛玉最大的依靠的贾母都尚且如此,贾府中其余上上下下的人无疑更没有真正接纳她,除了与宝玉的精神契合,纯真爱情,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她,认可她。
这样看黛玉无疑是世俗社会的失败者。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很好实现自我的社会化,融入贾府的世俗环境,而是一味的沉浸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虽然保持个性的最大自由,却失去了社会的接纳。
由此导致的孤僻、不被理解也侵蚀着她的命运,吞食着她的健康,最后使我们看到“黛玉焚稿断痴情,宝钗出闺成大礼”的结局。
从林黛玉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完全的个性化,任由个性自由发展,不顾社会规制,不按照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环境对角色的期许来完成自我发展完善,会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自己也会因为这种心灵巨大的孤独感而痛苦,产生“心病”,最终难以完成自我实现和获得幸福。
当然林黛玉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压制人性的社会,过分强调社会规制,很少注重个性自由,这更加注定了林黛玉的悲剧。
二、薛宝钗
如果说林黛玉的悲剧是由于她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很好地实现自我的社会化,那么宝钗几乎得到贾府上下所有人的赞许认可,上至贾府权威的化身贾母,下至丫鬟小厮,无不对她满口称赞,心服口服,认为她稳重和平,通情达理,宽容识体,应该说是完美的实现了社会化,把自身打造成封建社会里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的模范,那么为什么说她的人生也很悲剧呢?因为成功的社会化并不等同于自我实现与个人幸福的实现,真正的幸福时建立在个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
从书中可以看出,薛宝钗处处以社会对大家闺秀的要求来为人处世,十四五六岁的年龄,正是个性自由发展的时期,在她身上却看不到自由个性的显露,相比黛玉的爱使性子,湘云的洒脱开朗,甚至宝玉身边的丫鬟都显露出少女的可爱张扬,宝钗行事却一如既往地端庄正经,从她园中捉蝶的活泼可以看出她并非没有,但是她将自己的个性隐藏在心里某个甚至她自己也不知道的角落,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未来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只有获得掌握自己命运大权的长辈们的认可和赞许,她才能更好地生存,实现自己的愿望。
这么评价宝钗有点完全忽略她的个性色彩,把她形容得太虚伪功利,她当然不仅仅是如此,只是父亲早逝、哥哥胡闹,与母亲的相依为命滋生了她的家庭责任感,对母亲的体恤和对自己未来的理性设计已经装满了这个少女的心,使得她自觉不自觉的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合乎规范,长此以往,她原本自然的自由个性受到抑制,成为习惯,到后来很难从她身上看到我们现在赞许的自由鲜明的个性。
早期,当她发现林黛玉在看《牡丹亭》、《西厢记》等当时的闺房女儿不宜看的闲书时,便对黛玉说“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药”,可见她幼时也曾接触过这些书,只是知道不该看后便不再碰,并以此来劝导黛玉,这个时候的她展现给读者的是循规守礼的一面,不至于说个性泯灭;后来当薛姨妈应了宝玉的亲事,征求宝钗的意见时,宝钗竟正色对母亲道:“妈妈这话说错了。
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
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虽然知道自己的意见对婚事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加上本身中意宝玉,但是如此严格地遵从“父母之言,媒妁之约”的封建婚姻模式的话语,把自己变成制度的奴隶一般,实在让人反感,难怪那么多红迷不喜欢她,因为在她身上我们看到自由个性的逐
渐磨灭,社会权威对个性的统治。
如此的宝钗自然得不到生性乖张,比黛玉更加不认可世俗礼法的宝玉的喜欢,二人在精神上难以交流,没有默契,曹公才会说出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株寂寞林”的感叹,而宝钗即使在深知宝黛二人爱情的前提下还是顺从母命嫁给了宝玉,宝玉后来出家,宝钗最终落得了守寡一生的结局。
纵观宝钗一生,即使从始至终都得到了社会的赞许,但是由于自由个性的光辉日趋暗淡,成为了制度的奴隶,自然也就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牺牲品,没有获得个人的幸福。
三、小结:
从林黛玉和薛宝钗身上我们看到人生的两种不同追求,林黛玉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薛宝钗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而爱情是实现个性之路,婚姻更多的是承担社会责任,所以林黛玉拥有纯真的爱情,薛宝钗拥有社会认可的婚姻。
这个选择也是我们每个人成长都需面对的,但它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两种追求间寻找适合自己的那个点。
黛钗所处的社会,是一个腐朽制度压制自由个性的社会,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存在尖锐的矛盾,无论选择哪一个都难以得到真正的幸福,这也使我们看到脱离时代背景来谈论社会化与个性化是不恰当的,只有在合理的、人性化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和谐统一,个人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和幸福。
而无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只追求社会的承认或只在乎个性的自由都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不能成为制度的奴隶,被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绑架,也不要只追求自由,脱离我们生活的社会,而要辩证的看待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寻找自己心中的“度”,还有不要忘了社会化或者个性化都不是人存在的目的,自我实现和幸福的获得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参考文献:
《红楼梦》
《社会学》
《心灵、自我与社会》
《论社会化与人的自由——<红楼梦>的社会学解读》(商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