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里的名教与自然-从《是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13
- 格式:pdf
- 大小:172.52 KB
- 文档页数:2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辩
李明磊
【期刊名称】《林区教学》
【年(卷),期】2016(000)004
【摘要】魏晋时期,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性、非功利性的名教已经变得虚伪化、矫饰化和功利化.一批具有儒学知识背景的魏晋名士援道入儒,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进行辨析.王弼主张"化名教为自然",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向秀、郭
象则坚持"名教即自然".如果说阮籍、嵇康偏向于自然,裴頠偏向名教一端,那么,王弼、向秀、郭象则处于自然与名教之间.与先秦儒家化自然为名教相对,魏晋名士化名教
为自然,并希望最终能够弥合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紧张,实现二者的同一.
【总页数】3页(P61-63)
【作者】李明磊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临沂276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41
【相关文献】
1.略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J], 马忠杰
2.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问题研究 [J], 李雪姣
3.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 [J], 孟凯
4.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J], 王孝春
5.略论魏晋玄学之名教自然 [J], 卫鹏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李晓筝(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
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
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言谈举止,这就是后人所向往的魏晋名士的时代精神。
《世说新语》(下文简称《世说》),是我国小说发轫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志人”体小说的代表作。
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语),是一部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古典名著。
它以生动传神的笔触,优美精炼的语言,分门别类记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轶闻轶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特别是士族阶层,深刻反映了魏晋时代两百多年间的政治、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成为“魏晋风流”的主要载体,起到了名士的“教科书”的作用。
《世说》刻画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魏晋人物,如“竹林七贤”及陆机、陆云、张华、左思等文人才子;何晏、王弼、孙绰、殷浩、王衍等清谈名家;王导、谢安、桓温、陶侃、顾荣等名臣名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顾恺之等书画大家……真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名士的人物画卷。
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就是通过《世说》中这些人物活脱脱地表现出来的。
概而言之,魏晋风流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的不同流俗,这些方面都可以从《世说》找到佐证。
一、生活:真率自然、不拘礼法“魏晋风流”的主要特性在于心超脱于万物的畛别之上,率性而行,自事其心,不求取悦于人。
所以,其风流精神首先在于一种率性的生活。
对于生活,魏晋士人讲究的是真率自然、不拘礼法,主要通过脱俗的举止表现出来。
《世说》中有一则关于刘伶的故事:“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诸君何为入我禈中!’”[1](《任诞篇》)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不拘礼法,在家里一丝不挂,诚然是以此为乐,但他还从中感受到自在于天地宇宙之中的轻松与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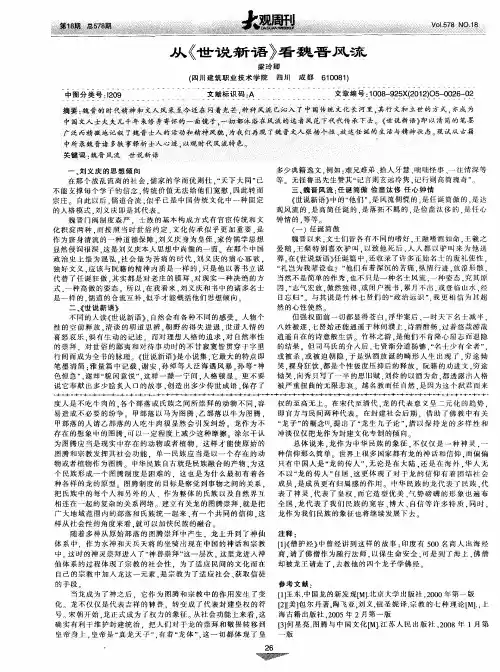

玄学里的名教与自然——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讲座报告讲座内容概述:一、说“风流”:无言之美风流是指一种人格的美。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可谓我国古代的一部风流宝鉴。
《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主要表现便是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但世上也有不少假名士,如《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孝伯说的便是个假名士,假风流。
“真风流”的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玄心”指一种领悟了天人分际、意象关联、情理融合的神秘幽远的超越之心,是超乎得失成败、祸福生死的心灵的宁静状态。
“洞见”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就能获得对于真理的认识。
只须几句话或几个字,此即所谓名言隽语,是风流名士常用言语。
“妙赏”,就是对美的深切感觉。
《世说新语》的名士,有些行为乍一看似乎匪夷所思,但从妙赏的角度看,又不难理解。
“深情”是指有妙赏的人,对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同情,而在这种同情中照见的是他自己的怀抱。
二、说“玄学”:“说不可说”玄学实际就是超越“有名”“有形”“万物”之上的玄妙学说,历经《周易》、《老子》、《庄子》、汉代宇宙论,而渐与名教碰撞遇合,并形成所谓玄学。
“玄学”自先秦以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1.老子的“玄道”。
玄学就是从老子关于“可道”与“不可道”、“可名”与“不可名”、“有名”与“无名”、“无欲”与“有欲”而延异出的某种形而上的学说。
当然,在老子看来,这种“形而上”的“道”是可以在“形而下”的“器”中体现出来的。
2.庄子的“道论”。
庄子关于道的非时间性、非空间性的本体论言说并不是主要的,而其重心更落在“无名”的“道”和“有名”的“万物”之间的转化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玄学在庄子这里进一步获得了其当下性和实践性的形态。
3.汉代从“宇宙发生”论“道”。
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
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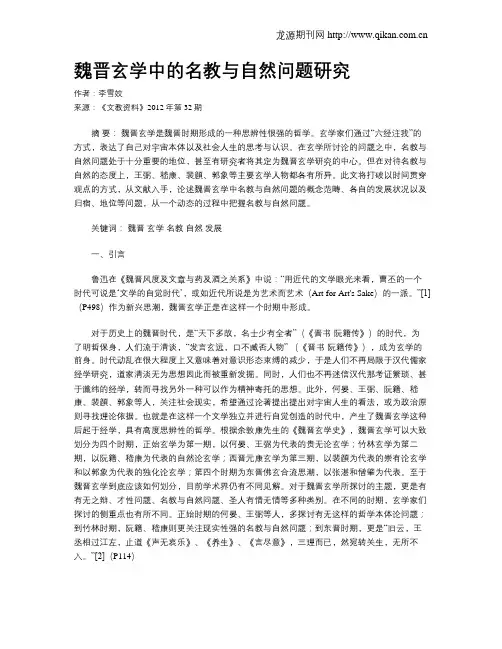
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问题研究作者:李雪姣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2期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
玄学家们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宇宙本体以及社会人生的思考与认识。
在玄学所讨论的问题之中,名教与自然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有研究者将其定为魏晋玄学研究的中心。
但在对待名教与自然的态度上,王弼、嵇康、裴頠、郭象等主要玄学人物都各有所异。
此文将打破以时间贯穿观点的方式,从文献入手,论述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问题的概念范畴、各自的发展状况以及归宿、地位等问题,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把握名教与自然问题。
关键词:魏晋玄学名教自然发展一、引言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
”[1](P498)作为新兴思潮,魏晋玄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形成。
对于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时代,为了明哲保身,人们流于清谈,“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晋书·阮籍传》),成为玄学的前身。
时代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又意味着对意识形态束缚的减少,于是人们不再局限于汉代儒家经学研究,道家清淡无为思想因此而被重新发掘。
同时,人们也不再迷信汉代那考证繁琐、甚于谶纬的经学,转而寻找另外一种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思想。
此外,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裴頠、郭象等人,关注社会现实,希望通过论著提出提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或为政治原则寻找理论依据。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独立并进行自觉创造的时代中,产生了魏晋玄学这种后起于经学,具有高度思辨性的哲学。
根据余敦康先生的《魏晋玄学史》,魏晋玄学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正始玄学为第一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玄学;竹林玄学为第二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自然论玄学;西晋元康玄学为第三期,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玄学和以郭象为代表的独化论玄学;第四个时期为东晋佛玄合流思潮,以张湛和僧肇为代表。

从魏晋玄学看魏晋书学思想中的自然观摘要: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矛盾激烈,并受佛道思想的冲击,儒家思想产生了危机,士人们逐渐加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把魏晋思想引向了玄学。
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主张个性张扬,追求“简约自然”的审美风尚。
这种审美思潮充分反映在当时的书法理论与创作之中。
魏晋书学思想中对书法创作主体虚静之心的重视、书法形态、书法品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自然观念等对后世书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书学;自然;道家一、魏晋书学自然观理论溯源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荒乱之世,政权林立,相互征伐,加之灾荒,因此社会急剧变化,阐发圣人微言大义的儒学思想产生了危机。
其中“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当时普遍的思想倾向。
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在思想领域宣扬老庄思想。
王弼主张朴素、清净的政治,将名教与自然相统一,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主张。
因此魏晋时期士大夫如嵇康、郭象等人大都崇尚道家自然观思想,并将其作为躲避灾祸、调适心态的工具。
在此思想影响下,士人们重新思考自我,向往一种率性而动、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思想精神获得了空前解放,开始肯定自我的人生价值。
因此,魏晋时代被称为人的意识觉醒的时期。
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魏晋时期形成了书法艺术自觉的艺术思潮。
近人马宗霍认为:“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
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
”当时出现了成批的书法家,如蔡邕、张、钟、“二之”(王羲之、王献之)等。
人们对书法的探讨如痴入迷,并且出现了众多的书法理沧著作,如崔瑗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笔论》、《九势》等。
其中最能体现魏晋时期书法艺术自然思想观念的是魏晋书学理论。
这些书学理论在对书法创作中书家的要求、书法形态的描述、书法品评、书法美学规范的论述中,都以自然思想为宗,对后世的书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然”一词在道家代表作《老子》中共出现五次。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玄学里的名教与自然——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讲座报告风流是一种人格的美。
这种美是一种自然流露,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魅力,是无法模仿作秀出来的。
从现今利益横流、物欲熏心的情状,我们有必要回顾古时真名士的生活的自在随性,以深刻理解人的需要是什么,所追求的幸福是什么。
《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主要表现便是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但世上也有不少假名士,如《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孝伯说的便是个假名士,假风流。
那么真名士真风流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真风流”具有四个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玄心”合而释之,就可以指一种领悟了天人分际、意象关联、情理融合的神秘幽远的超越之心,是超乎得失成败、祸福生死的心灵的宁静状态。
可以看出,这种思想与道家哲学观很相似,追求一种逍遥自在,毫不为人为的任何规条秩序所束缚。
即使有时候它会显得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却并不违背人最原初的道德,给人无可厚非的感觉,便是有点风流的意味了。
洞见。
不借推理,专凭直觉,就能获得对于真理的认识。
只须几句话或几个字,此即所谓名言隽语,是风流名士常用言语。
“词约旨达”;“谈言微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这是一种高语境文化状态下才有的情况。
其实具体说来,中国文化就是含蓄内敛的特色,从琴棋书画各个角度来看都是如此。
崇尚留白艺术,给予人想象空间。
因此,中国式矛盾总是美丽的误会。
但是对于风流名士而言,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更是显得温暖默契,意味深长。
妙赏,就是对美的深切感觉。
《世说新语》的名士,有些行为乍一看似乎匪夷所思,但从妙赏的角度看,又不难理解。
比如《世说新语·任诞》的故事,王子猷与桓子野各为对方的艺术所倾倒,但他们妙赏的是艺术之美,并不在于人,所以两人以艺术相会却不交一言,人不以为怪。
创造美是一种能力,欣赏美也是一种能力,而不将艺术美与人事交情混杂更是难处了。


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内容提要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思潮的主题。
关于此,汤用彤、陈寅恪、唐长孺、牟宗三、余英时和庞朴等方家均有专题研究。
这里,笔者试图把名教与自然之辨拆解为名实、情礼、古今、天人四个理论层面,逐一解读。
本文除了不可避免地要涉诸儒道关系外,立论的主旨则在于揭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基本论域、内在理路及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语境。
颠倒的社会塑造了颠倒的人格。
生当魏晋乱世的玄学名士,他们对名教的矛盾心态和人格行为的不统一,有着真切的历史内涵。
我们不应无视而是应该充分揭示这种真实的矛盾——矛盾的真实,并由此来完整地把握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思想意味。
从何晏、王弼到嵇康、阮籍,再到向秀、郭象,这是玄学思想发展的“三部曲”,名教与自然之辨在这三段中也展现为一种逻辑递进关系。
然而,这种逻辑演进并不明显,而玄学家们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又多有重叠之处。
而且,由于名教与自然范畴的歧义性以及名教与自然之辨在玄学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乃涉诸语言、人性、社会和宇宙等诸多方面。
由是,本文选择了共时性的结构性的话语分析,同时尽可能兼顾历史性的说明。
玄学家的名教与自然之辨以及由此衍生的一些议题,多是当代哲学关注的理论问题,玄学家以其对这些问题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丰富了人类思想的宝库,给后人以宝贵的启迪。
(一)引言魏晋之际,经学式微,玄风振起。
玄学名士们清谈雅论,旷达风流,煽起了一股颇具异端色彩的思想潮流。
作为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玄学当然不是无主题变奏,或无主题的变相说法所谓多主题。
那么,玄学的思想主题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名教与自然之辨。
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对魏晋社会的时代课题的理论解答,是玄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终点,规定与凸显了玄学思潮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品位。
当然,名教与自然概念其来有自,在先秦时代即已形成。
但是,把二者的关系自觉而明确地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议题的,当是魏晋玄学。
与中国传统思想上其他概念术语一样,名教与自然这对范畴也具有模糊性与歧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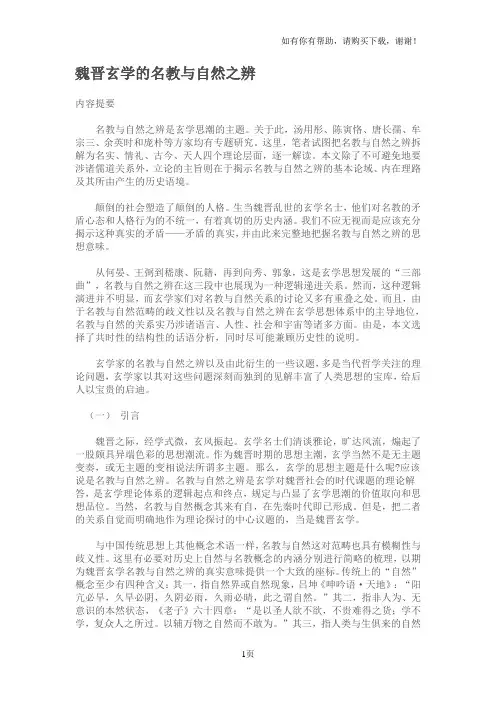
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内容提要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思潮的主题。
关于此,汤用彤、陈寅恪、唐长孺、牟宗三、余英时和庞朴等方家均有专题研究。
这里,笔者试图把名教与自然之辨拆解为名实、情礼、古今、天人四个理论层面,逐一解读。
本文除了不可避免地要涉诸儒道关系外,立论的主旨则在于揭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基本论域、内在理路及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语境。
颠倒的社会塑造了颠倒的人格。
生当魏晋乱世的玄学名士,他们对名教的矛盾心态和人格行为的不统一,有着真切的历史内涵。
我们不应无视而是应该充分揭示这种真实的矛盾——矛盾的真实,并由此来完整地把握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思想意味。
从何晏、王弼到嵇康、阮籍,再到向秀、郭象,这是玄学思想发展的“三部曲”,名教与自然之辨在这三段中也展现为一种逻辑递进关系。
然而,这种逻辑演进并不明显,而玄学家们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又多有重叠之处。
而且,由于名教与自然范畴的歧义性以及名教与自然之辨在玄学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乃涉诸语言、人性、社会和宇宙等诸多方面。
由是,本文选择了共时性的结构性的话语分析,同时尽可能兼顾历史性的说明。
玄学家的名教与自然之辨以及由此衍生的一些议题,多是当代哲学关注的理论问题,玄学家以其对这些问题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丰富了人类思想的宝库,给后人以宝贵的启迪。
(一)引言魏晋之际,经学式微,玄风振起。
玄学名士们清谈雅论,旷达风流,煽起了一股颇具异端色彩的思想潮流。
作为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玄学当然不是无主题变奏,或无主题的变相说法所谓多主题。
那么,玄学的思想主题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名教与自然之辨。
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对魏晋社会的时代课题的理论解答,是玄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终点,规定与凸显了玄学思潮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品位。
当然,名教与自然概念其来有自,在先秦时代即已形成。
但是,把二者的关系自觉而明确地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议题的,当是魏晋玄学。
与中国传统思想上其他概念术语一样,名教与自然这对范畴也具有模糊性与歧义性。
论魏晋名教自然论在《世说新语》中的投射作者:段华升来源:《美与时代·下》2019年第12期摘要:魏晋时代的崇奉礼教看似热烈,实则是不信礼教、破坏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认同礼教、相信礼教。
阮籍、嵇康、刘伶等人是魏晋易代之际名士中的代表人物,是《世说新语》中的典型人物。
他们看似荒诞不羁、破坏礼教,内心实则真正崇奉礼教。
以阮籍、嵇康、刘伶等人为例,探究《世说新语》中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教;自然论;阮籍;嵇康《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人物故事。
魏晋时期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世说新语》中名士们对玄学大多体现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倾向。
他们的言行或为纵欲享乐,或为惧祸避世、明哲保身,或为表现任性放达的名士风度,或为追求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
主要有饮酒、服药、清谈三种形式。
阮籍不拘礼法、刘伶嗜酒如命、嵇康服药求永生。
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现状用自己的方式大胆追求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也是本文所说的“越名教任自然”。
一、阮籍等人思想转变的原因阮籍、嵇康、刘伶等人毅然决然地弃儒入道,力斥礼教,鄙视礼法之士的种种行为并不是他们的初心。
其实,刘伶后世虽蔑视礼法、酗酒避世,但他骨子里还是崇尚“自然”、强调无为而治。
嵇、阮二人曾经对儒家的社会文明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热烈地推崇。
阮籍在少年时期把好学不倦、不慕荣贵、道德高尚的颜回和闵子骞作为效法的榜样。
在曹氏掌权的时代,三岁丧父的阮籍凭借曹氏父子与阮瑀的情义,生活得还算不错。
比阮籍小十四岁的嵇康不但为人正直、才华出众,而且相貌堂堂。
有人称赞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凭着这样的赞誉,他在士大夫中颇收声誉,是出了名的美男子。
在二十岁的时候,嵇康被沛王曹林看中,娶了当时的长乐亭公主,成为了宗室姻亲。
也就是说在正始(240—249)之前,阮籍、嵇康、刘伶等人不仅崇尚自然,而且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
他们也像所有想要报效国家的文人志士一样,都有着建功立业、报效王室的济世志向。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辩李明磊【摘要】摘要:魏晋时期,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性、非功利性的名教已经变得虚伪化、矫饰化和功利化。
一批具有儒学知识背景的魏晋名士援道入儒,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进行辨析。
王弼主张“化名教为自然”,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向秀、郭象则坚持“名教即自然”。
如果说阮籍、嵇康偏向于自然,裴頠偏向名教一端,那么,王弼、向秀、郭象则处于自然与名教之间。
与先秦儒家化自然为名教相对,魏晋名士化名教为自然,并希望最终能够弥合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紧张,实现二者的同一。
【期刊名称】林区教学【年(卷),期】2016(000)004【总页数】3【关键词】魏晋玄学;自然;名教;关系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一种哲学形态,它涉及自然与名教、有与无、本与末、言与意、体与用、天与人等多种辩题。
其中,自然与名教属于人道观问题。
所谓名教,即儒家道德规范、践行原则及评价标准,可引申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健康运行的一般儒家规范(它具有当然性);而自然则含义宽泛,它或指与人文相对的天然或本然状态,或指代与道合一的形而上学本体,或指自然而然。
一般而言,前者是原始儒家的经典议题,而后者则是先秦道家的主要议题。
先秦时期,二者是并行相悖、彼此悬隔和对立的。
魏晋时期,王弼、阮籍、嵇康、向秀和郭象等名士对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可能关系问题作了重点考察。
一、问题的缘起众所周知,原始儒家对人性、政治怀有超验的理性和理想追求。
至西汉董仲舒向汉武帝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逐渐异化出功利性的特征。
汉朝时期,儒学分化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注重对“五经”(《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礼记》)进行烦琐的训诂与发挥,而今文经学则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穿凿附会、随意曲解而演化为“谶纬之学”(把孔子的言论迷信化和神秘化)。
东汉末年,群雄蜂起,争霸天下。
统治者认定烦琐的古文经学、迷信化的今文经学乃至迂阔的原始儒学已经如同鸡肋,而功用性很强的学术(包括追求功利的法家之学和考核名实的“名法之学”)则成为他们趋之若鹜的对象。
从魏晋名士看“名教”与“自然”自古以来,每当社会发生较大的动荡或者战争频发的时代,都是百家争鸣、思想激荡的时代。
而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
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名教理论开始破产,“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
但是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他们更多的是追求入仕从政,追求“名教”。
因此,魏晋掀起了一股“名教”与“自然”的争辩之风。
《魏晋名士风流》是以简洁易懂地描写魏晋时期的社会变迁和名士的思想、生活来叙述魏晋的文化的一本书,借用其编辑的话:“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
魏晋名士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展现个性的可爱。
本书从不同方面勾勒出他们的精神风貌,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与众不同的价值观。
”书里分为三大篇:社会百态篇、生活情趣篇和思想灵魂篇。
书中有这么一段引言:“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魏晋名士的独特群体人格精神。
其主流价值取向的特征就是,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制;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
这些特征固然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全盘吸收和继承的,但它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中国古代士人曾经有过的骄傲,其参照和借鉴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我选择从魏晋的名士出发,以他们特殊的风流展示魏晋特殊的风度,以及这个时代的政治思想。
书中对魏晋的社会生活甚至服饰等方面有着比较独特的描述,但是本文里我打算注重于书中的第三篇——思想灵魂篇的玄学的“有无”与士人的“名教”“自然”。
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来自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解释玄学的涵义为“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之中有矛盾对立的两派:“名教”与“自然”。
略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摘要:名教与自然之辨,这是由魏晋玄学家用生命来践行的一个颇有争议的时代辨题,本文重点探讨名教与自然作为哲学范畴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发展脉络,意图理清魏晋时代的士人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的行为态度转变路径以及此玄学命题意义。
笔者认为魏晋时代的士人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索实为失败之举,只注玄远,不顾当下,实己脱离人之自我本然,一味地在自然之外追求自然实属画蛇添足。
论文关键词:名教,自然,玄学一、何谓名教名教何义?从词源上来看,名教一词的来源于“名”和“教”的合义。
名者何也?《说文解字》解释是:“名,自命也,从口从夕。
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由此可见,“名”在古代为夜色黑暗不能见到对方面目,而自报姓名的一种联系方式。
目的在于把自己的信息传递给未知对方,以做到相互知晓。
教者何也?《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教,上所施下效也,从攴从孝。
”可见,教具有政教、教化之意。
二者合而言之,名教应为施政教的一方与被政教一方之间互相传达信息,互通有无,以达到政通人和的一种教化方式。
《管子·山至数》认为:“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於天下”。
西汉大儒董仲舒更是主张“审察名号、教化万民”。
汉武帝进一步从符合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抑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的纲常名教作为品评百姓以及官职升迁的标准,名教逐步演化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
丘明之作,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众体,然未尽之。
”又在《后汉纪孝桓皇帝纪》里说:“春秋书齐晋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勋,所以囊括盛衰,弥纶名教也。
”由此可见,名教对于封建统治的盛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名教当以何为本?袁宏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
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
郑鲜之《滕羡仕宦议》言:“名教大极,忠孝而已。
可见,忠孝作为名教之本,其所产生的作用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