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儒学的关系
- 格式:doc
- 大小:47.00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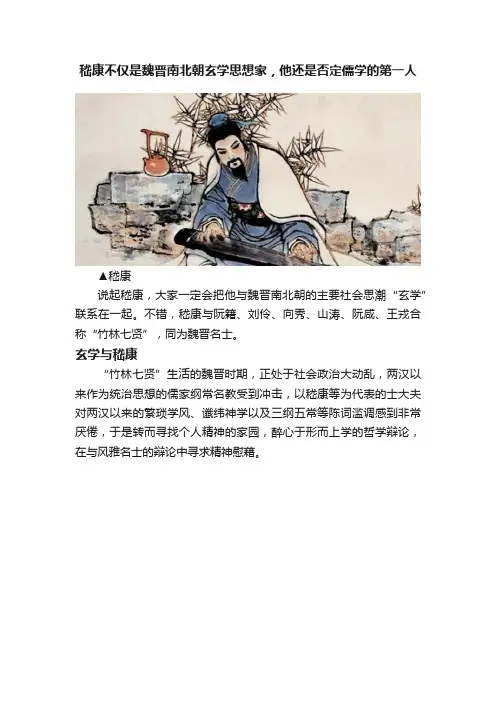
嵇康不仅是魏晋南北朝玄学思想家,他还是否定儒学的第一人▲嵇康说起嵇康,大家一定会把他与魏晋南北朝的主要社会思潮“玄学”联系在一起。
不错,嵇康与阮籍、刘伶、向秀、山涛、阮咸、王戎合称“竹林七贤”,同为魏晋名士。
玄学与嵇康“竹林七贤”生活的魏晋时期,正处于社会政治大动乱,两汉以来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纲常名教受到冲击,以嵇康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对两汉以来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以及三纲五常等陈词滥调感到非常厌倦,于是转而寻找个人精神的家园,醉心于形而上学的哲学辩论,在与风雅名士的辩论中寻求精神慰藉。
▲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经常聚集在一起,谈玄论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清谈的内容涉及生与死、有与无、动与静、名教和自然、圣人和常人、有情或无情、言能否尽意等哲学问题,谈论内容与老子《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玄之门”一样幽深微妙,故后人称之为“玄学”。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州)人。
好文论、赋诗歌、弹琴咏唱,好读老庄,倾向玄学,寄情山水,尚奇游侠,风度潇洒。
曾在太学中活动,评议时政,对司马家族诛杀异己、图谋篡位而又盛倡“名教”强烈不满,进行揭露、批判和抵制,最后为司马集团所不容,惨遭杀害,死时年仅四十岁。
嵇康不止于“谈玄论道”,他针对当时儒学“名教”教育,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批判教育思想,发人深省。
嵇康的教育批判思想▲赵孟頫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局部)嵇康在其著作《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和《释私论》等篇章中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批判当时传统的儒学教育和世俗教育。
一、大胆抨击名教所推崇的“圣人”偶像▲画像石中的尧舜禹“将如箕山之夫,颖水之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乎?”——嵇康《卜疑》“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对于传统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唐尧、虞舜和夏禹抨击一通,还常常要说一些非难成汤、周武王和轻视周公、孔子的话,足见其对儒家“圣人”的厌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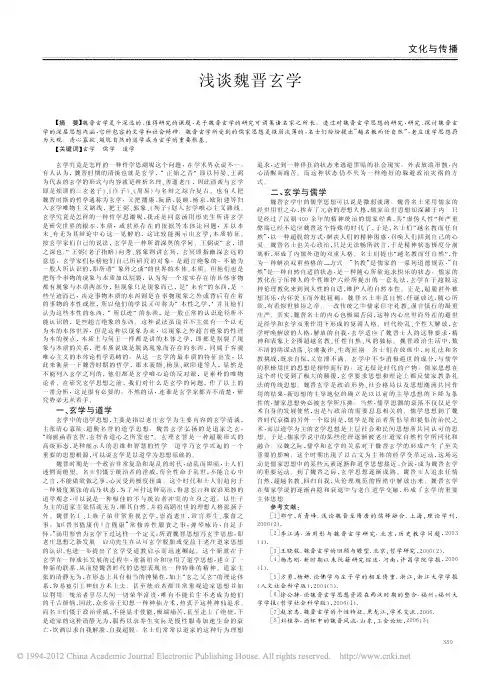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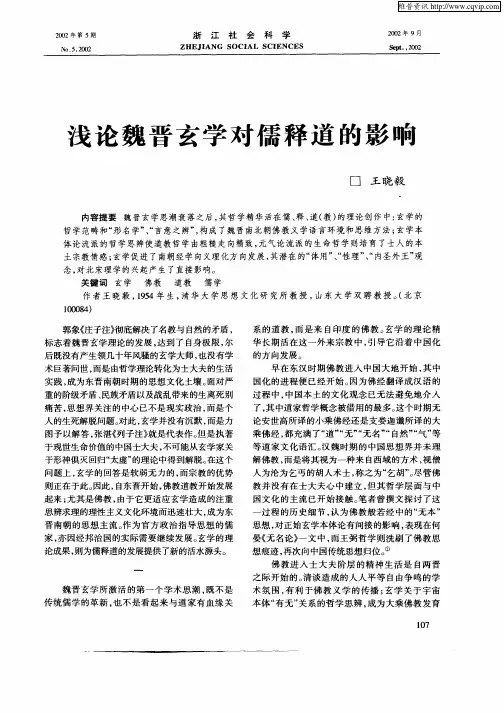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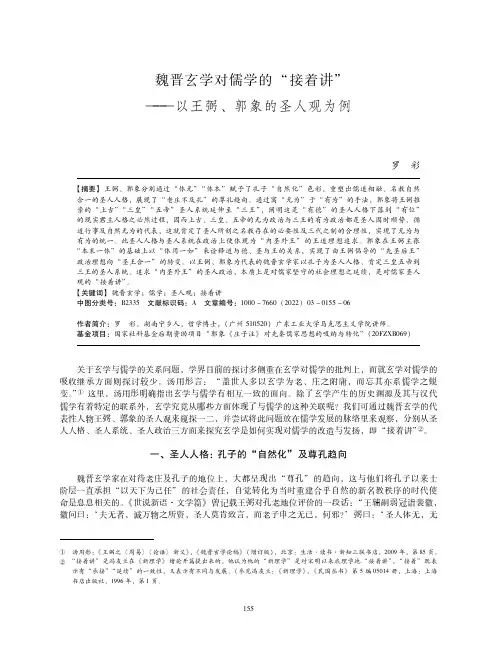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接着讲”———以王弼、郭象的圣人观为例罗 彩【摘要】王弼、郭象分别通过“体无”“体本”赋予了孔子“自然化”色彩,重塑出儒道相融、名教自然合一的圣人人格,展现了“老庄不及孔”的尊孔趋向。
通过寓“无为”于“有为”的手法,郭象将王弼推崇的“上古”“三皇”“五帝”圣人系统延伸至“三王”,阐明这是“有德”的圣人人格下落到“有位”的现实君主人格之必然过程,因而上古、三皇、五帝的无为政治与三王的有为政治都是圣人因时顺势、循道行事及自然无为的代表,这就肯定了圣人所创之名教存在的必要性及三代之制的合理性,实现了无为与有为的统一。
此圣人人格与圣人系统在政治上便体现为“内圣外王”的王道理想追求。
郭象在王弼主张“本末一体”的基础上以“体用一如”来诠释道与德、圣与王的关系,实现了由王弼倡导的“先圣后王”政治理想向“圣王合一”的转变。
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以孔子为圣人人格、肯定三皇五帝到三王的圣人系统、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政治,本质上是对儒家坚守的社会理想之延续,是对儒家圣人观的“接着讲”。
【关键词】魏晋玄学;儒学;圣人观;接着讲中图分类号:B2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2)03-0155-06作者简介:罗 彩,湖南宁乡人,哲学博士,(广州510520)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郭象《庄子注》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吸纳与转化”(20FZXB069)关于玄学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学界目前的探讨多侧重在玄学对儒学的批判上,而就玄学对儒学的吸收继承方面则探讨较少。
汤用彤言:“盖世人多以玄学为老、庄之附庸,而忘其亦系儒学之蜕变。
”①这里,汤用彤明确指出玄学与儒学有相互一致的面向。
除了玄学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汉代儒学有着特定的联系外,玄学究竟从哪些方面体现了与儒学的这种关联呢?我们可通过魏晋玄学的代表性人物王弼、郭象的圣人观来窥探一二,并尝试将此问题放在儒学发展的脉络里来观察,分别从圣人人格、圣人系统、圣人政治三方面来探究玄学是如何实现对儒学的改造与发扬,即“接着讲”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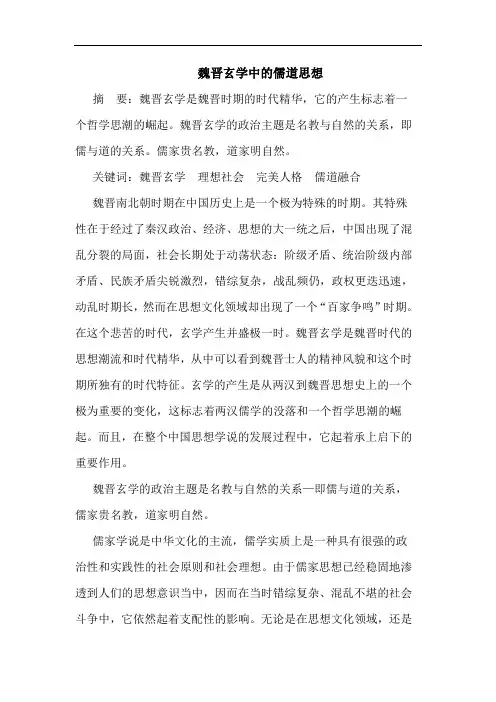
魏晋玄学中的儒道思想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时代精华,它的产生标志着一个哲学思潮的崛起。
魏晋玄学的政治主题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即儒与道的关系。
儒家贵名教,道家明自然。
关键词:魏晋玄学理想社会完美人格儒道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其特殊性在于经过了秦汉政治、经济、思想的大一统之后,中国出现了混乱分裂的局面,社会长期处于动荡状态: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激烈,错综复杂,战乱频仍,政权更迭迅速,动乱时期长,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时期。
在这个悲苦的时代,玄学产生并盛极一时。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代的思想潮流和时代精华,从中可以看到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和这个时期所独有的时代特征。
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这标志着两汉儒学的没落和一个哲学思潮的崛起。
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学说的发展过程中,它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魏晋玄学的政治主题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即儒与道的关系,儒家贵名教,道家明自然。
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学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实践性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
由于儒家思想已经稳固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因而在当时错综复杂、混乱不堪的社会斗争中,它依然起着支配性的影响。
无论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儒家的传统观念仍然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然而,随着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激化,传统的儒学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儒家思想伦理规范变得形式化和虚伪化。
这时,就需要道家思想来进行调节,社会思潮出现巨大转变,崇尚老、庄成为一时的风尚。
老庄哲学因而成为了玄学的源头活水,以道释儒,折中儒道是玄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及理论特色。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道家思想为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痛苦进行批判。
一、正始时期的儒道融合曹魏正始年间,是玄学的开创时期,核心人物是何晏和王弼。
作为正始玄学的领袖,何晏是忠实于曹魏政权的,但是由于从小被曹丕所憎恶,在曹丕、曹叡执政的黄初、太和年间得不到统治者的信任,受到排挤而无所事任,他高超的识见和政治理想都无法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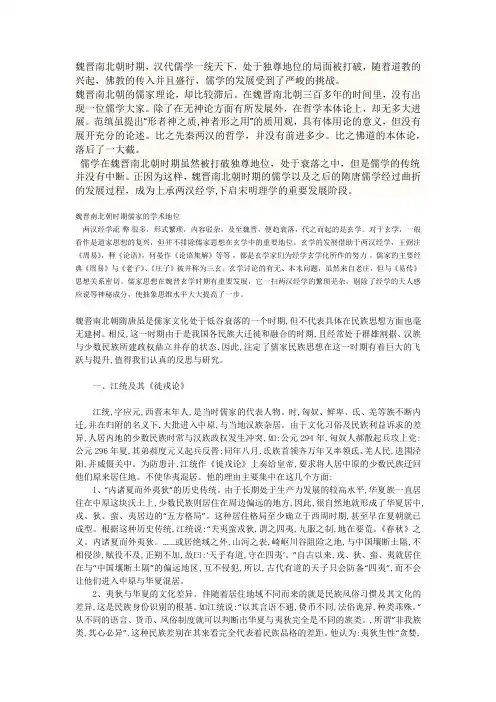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儒学一统天下,处于独尊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并且盛行,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魏晋南北朝的儒家理论,却比较滞后。
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一位儒学大家。
除了在无神论方面有所发展外,在哲学本体论上,却无多大进展。
范缜虽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质用观,具有体用论的意义,但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
比之先秦两汉的哲学,并没有前进多少。
比之佛道的本体论,落后了一大截。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被打破独尊地位,处于衰落之中,但是儒学的传统并没有中断。
正因为这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以及之后的隋唐儒学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成为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的学术地位两汉经学流弊很多,形式繁琐,内容驳杂,及至魏晋,便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玄学。
对于玄学,一般看作是道家思想的复兴,但并不排除儒家思想在玄学中的重要地位。
玄学的发展借助于两汉经学,王弼注《周易》,释《论语》,何晏作《论语集解》等等,都是玄学家们为经学玄学化所作的努力。
儒家的主要经典《周易》与《老子》、《庄子》被并称为三玄。
玄学讨论的有无、本末问题,虽然来自老庄,但与《易传》思想关系密切。
儒家思想在魏晋玄学时期有重要发展,它一扫两汉经学的繁琐芜杂,剔除了经学的天人感应说等神秘成分,使抽象思维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魏晋南北朝隋唐虽是儒家文化处于低谷衰落的一个时期,但不代表具体在民族思想方面也毫无建树。
相反,这一时期由于是我国各民族大迁徙和融合的时期,且经常处于群雄割据、汉族与少数民族所建政权鼎立并存的状态,因此,注定了儒家民族思想在这一时期有着巨大的飞跃与提升,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与研究。
一、江统及其《徙戎论》江统,字应元,西晋末年人,是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
时,匈奴、鲜卑、氐、羌等族不断内迁,并在归附的名义下,大批进入中原,与当地汉族杂居。
由于文化习俗及民族利益诉求的差异,人居内地的少数民族时常与汉族政权发生冲突,如: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起兵攻上党:公元296年夏,其弟郝度元又起兵反晋;同年八月,氐族首领齐万年又率领氐、羌人民,进围泾阳,并威慑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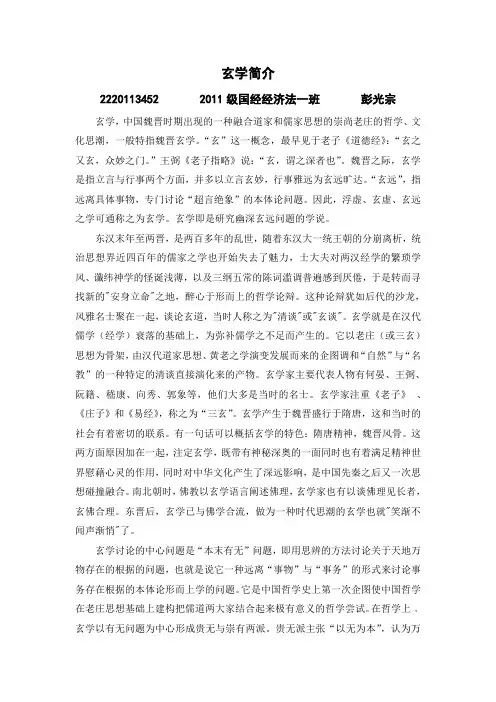
玄学简介2220113452 2011级国经经济法一班彭光宗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融合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崇尚老庄的哲学、文化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
“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魏晋之际,玄学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
“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
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
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玄学就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
它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清谈直接演化来的产物。
玄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他们大多是当时的名士。
玄学家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
玄学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这和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一句话可以概括玄学的特色:隋唐精神,魏晋风骨。
这两方面原因加在一起,注定玄学,既带有神秘深奥的一面同时也有着满足精神世界慰藉心灵的作用,同时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先秦之后又一次思想碰撞融合。
南北朝时,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玄学家也有以谈佛理见长者,玄佛合理。
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做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玄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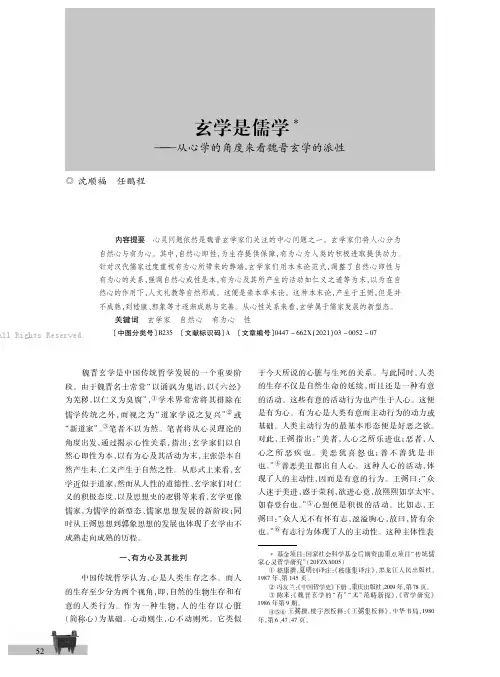
玄学是儒学———从心学的角度来看魏晋玄学的派性◎沈顺福 任鹏程内容提要 心灵问题依然是魏晋玄学家们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玄学家们将人心分为自然心与有为心。
其中,自然心即性,为生存提供保障,有为心为人类的积极进取提供动力。
针对汉代儒家过度重视有为心所带来的弊端,玄学家们用本末论范式,调整了自然心即性与有为心的关系,强调自然心或性是本,有为心及其所产生的活动如仁义之道等为末,以为在自然心的作用下,人文礼教等自然形成。
这便是崇本举末论。
这种本末论,产生于王弼,但是并不成熟,到嵇康、郭象等才逐渐成熟与完善。
从心性关系来看,玄学属于儒家发展的新型态。
关键词 玄学家 自然心 有为心 性〔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3-0052-07 魏晋玄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由于魏晋名士常常“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①学术界常常将其排除在儒学传统之外,而视之为“道家学说之复兴”②或“新道家”。
③笔者不以为然。
笔者将从心灵理论的角度出发,通过揭示心性关系,指出:玄学家们以自然心即性为本,以有为心及其活动为末,主张崇本自然产生末、仁义产生于自然之性。
从形式上来看,玄学近似于道家,然而从人性的道德性、玄学家们对仁义的积极态度,以及思想史的逻辑等来看,玄学更像儒家,为儒学的新型态、儒家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从王弼思想到郭象思想的发展也体现了玄学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历程。
一、有为心及其批判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心是人类生存之本。
而人的生存至少分为两个视角,即,自然的生物生存和有意的人类行为。
作为一种生物,人的生存以心脏(简称心)为基础。
心动则生,心不动则死。
它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心脏与生死的关系。
与此同时,人类的生存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延续,而且还是一种有意的活动。
这些有意的活动行为也产生于人心。
这便是有为心。
有为心是人类有意而主动行为的动力或基础。
人类主动行为的最基本形态便是好恶之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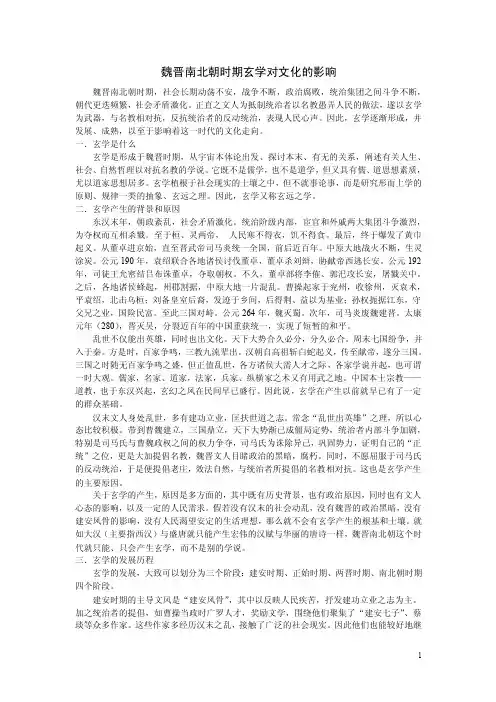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对文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战争不断,政治腐败,统治集团之间斗争不断,朝代更迭频繁,社会矛盾激化。
正直之文人为抵制统治者以名教愚弄人民的做法,遂以玄学为武器,与名教相对抗,反抗统治者的反动统治,表现人民心声。
因此,玄学逐渐形成,并发展、成熟,以至于影响着这一时代的文化走向。
一.玄学是什么玄学是形成于魏晋时期,从宇宙本体论出发、探讨本末、有无的关系,阐述有关人生、社会、自然哲理以对抗名教的学说。
它既不是儒学,也不是道学,但又具有儒、道思想素质,尤以道家思想居多。
玄学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但不就事论事,而是研究形而上学的原则、规律一类的抽象、玄远之理。
因此,玄学又称玄远之学。
二.玄学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东汉末年,朝政紊乱,社会矛盾激化。
统治阶级内部,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斗争激烈,为夺权而互相杀戮。
至于桓、灵两帝,人民寒不得衣,饥不得食。
最后,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
从董卓进京始,直至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全国,前后近百年。
中原大地战火不断,生灵涂炭。
公元190年,袁绍联合各地诸侯讨伐董卓,董卓杀刘辩,胁献帝西逃长安。
公元192年,司徒王允密结吕布诛董卓,夺取朝权。
不久,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长安,屠戮关中。
之后,各地诸侯蜂起,州郡割据,中原大地一片混乱。
曹操起家于兖州,收徐州,灭袁术,平袁绍,北击乌桓;刘备皇室后裔,发迹于乡间,后得荆、益以为基业;孙权扼据江东,守父兄之业,国险民富。
至此三国对峙。
公元264年,魏灭蜀。
次年,司马炎废魏建晋。
太康元年(280),晋灭吴,分裂近百年的中国重获统一,实现了短暂的和平。
乱世不仅能出英雄,同时也出文化。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
方是时,百家争鸣,三教九流辈出。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起义,传至献帝,遂分三国。
三国之时随无百家争鸣之盛,但正值乱世,各方诸侯大需人才之际,各家学说并起,也可谓一时大观。
儒家,名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之术又有用武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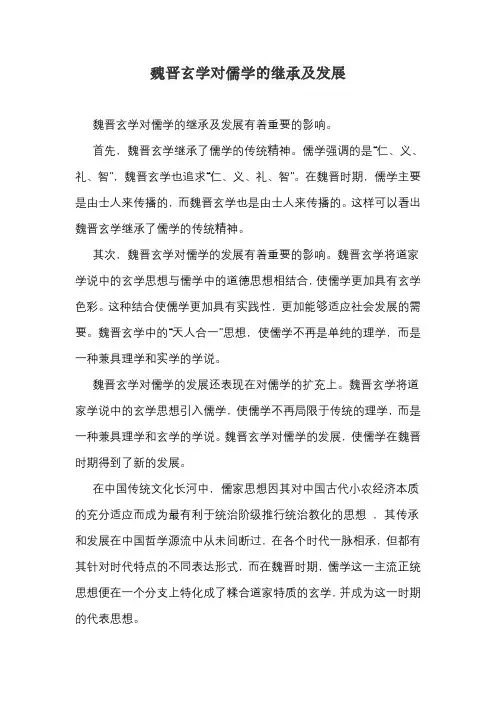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继承及发展魏晋玄学对儒学的继承及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魏晋玄学继承了儒学的传统精神。
儒学强调的是“仁、义、礼、智”,魏晋玄学也追求“仁、义、礼、智”。
在魏晋时期,儒学主要是由士人来传播的,而魏晋玄学也是由士人来传播的。
这样可以看出魏晋玄学继承了儒学的传统精神。
其次,魏晋玄学对儒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魏晋玄学将道家学说中的玄学思想与儒学中的道德思想相结合,使儒学更加具有玄学色彩。
这种结合使儒学更加具有实践性,更加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魏晋玄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使儒学不再是单纯的理学,而是一种兼具理学和实学的学说。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儒学的扩充上。
魏晋玄学将道家学说中的玄学思想引入儒学,使儒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理学,而是一种兼具理学和玄学的学说。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发展,使儒学在魏晋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儒家思想因其对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本质的充分适应而成为最有利于统治阶级推行统治教化的思想,其传承和发展在中国哲学源流中从未间断过,在各个时代一脉相承,但都有其针对时代特点的不同表达形式,而在魏晋时期,儒学这一主流正统思想便在一个分支上特化成了糅合道家特质的玄学,并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思想。
一、玄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魏晋玄学家的儒学背景从汉武帝始,儒学经董仲舒为适应统治阶级需要而改造后成为了官方哲学,并在教化、选官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充分实践,牢固确立了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但儒学在被统治阶级使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僵化,特别表现在名教思想上的僵化。
魏晋时期战乱频繁,统治者不断在名教的外衣下做出有悖伦常的事,传统儒家的价值观被当成了统治者掩饰自己对利益追求的工具。
这时出现的玄学家大多具有世家大族的家庭背景,在小农经济中属于地主阶级,为适应魏晋的门阀士族政治,在幼年时期必须接受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因此他们本身具备极高的儒学素养。
幼年时期的熏陶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玄学家的价值取向依然具有儒学内核,即作为士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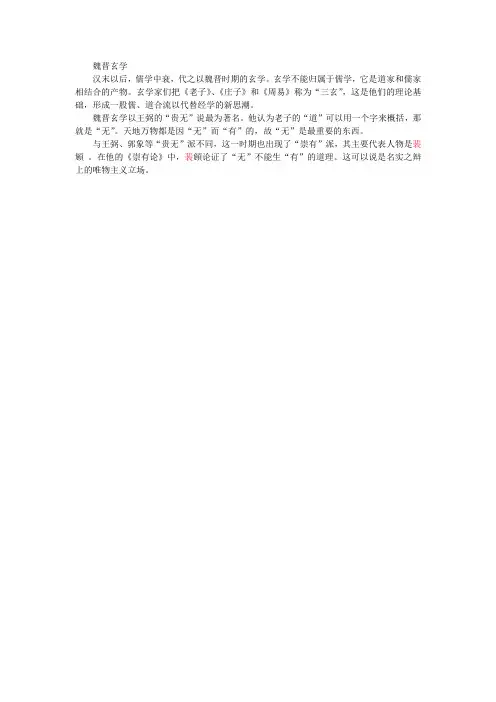
魏晋玄学
汉末以后,儒学中衰,代之以魏晋时期的玄学。
玄学不能归属于儒学,它是道家和儒家相结合的产物。
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这是他们的理论基础,形成一股儒、道合流以代替经学的新思潮。
魏晋玄学以王弼的“贵无”说最为著名。
他认为老子的“道”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无”。
天地万物都是因“无”而“有”的,故“无”是最重要的东西。
与王弼、郭象等“贵无”派不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崇有”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裴頠。
在他的《崇有论》中,裴頠论证了“无”不能生“有”的道理。
这可以说是名实之辩上的唯物主义立场。
浅论魏晋玄学与道、儒、佛三家的关系作者:陆晴晴来源:《速读·上旬》2015年第11期摘要:玄学作为一种高深的哲学思想在魏晋时期达到鼎盛,魏晋玄学在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同时受到了当时道、儒、佛三种主流思想的影响,对它们既有吸收,也有改变,从而趋于符合魏晋名士的心理状态与精神追求。
关键词:玄学;道;儒;佛;魏晋“玄学”一名源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这种深奥的哲学到了魏晋时期达到鼎盛。
魏晋玄学在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当时三大主流思想道、儒、佛家的影响,在与三家思想融合、偏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一、魏晋玄学与道学对于玄学和道学的界定经常混淆不清,从严格意义上讲玄学并不等于道学,玄学吸收了部分道学思想,并且玄学思想的形成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绚丽函着玄智,玄智者道心之所发也”,玄学提倡清心寡欲的道家理念。
庄子在《大宗师》中提出的道家理念是:“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他认为“道”是真实存在的。
何晏在《无名论》中说:“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
则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
”何晏把“无”抬高到与老庄提出的“道”同样的地位。
王弼在《老子注》第一章就注曰:“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
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
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
”老庄思想是“绝圣弃智”,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却认为“圣人体无”,可见魏晋玄学明显与道家思想不同了。
魏晋时期,战乱频仍,权力更替,统治腐朽。
士人们慑于统治者的淫威,为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心中常有郁结不得抒发之情。
面对这种时代的高压,他们唯有寄身自然,放浪形骸,远离政治围场,那么以老庄为主的道家思想无疑是最佳选择,恬淡无为,顺其自然,高蹈出世。
第七章琅琊王氏的思想演变(二)魏晋之际:由儒入玄魏晋之际,是琅琊王氏接受玄学影响时期。
当时,传统的儒学式微,儒、道融合的新哲学——魏晋玄学迅速兴起,风靡思想界。
这一时期的玄学思潮按时间顺序可划分为正始玄学(曹魏正始年间)、竹林玄学(魏末晋初)、元康玄学(西晋中后期),并出现了相应的士族名士群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元康名士。
值得注意的是,王祥从兄王雄的后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王戎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并且作为元老重臣,推动了元康玄学的兴起。
其从弟王衍、王澄,则是元康名士的代表人物,王衍还是“贵无”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当时,许多世家大族由儒入玄,一时间,“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
王戎、王衍、王澄由儒入玄,正式扭转了家族学风。
(一)名教自然“将无同”王雄官至幽州刺史,史载他“天性良固,果而有谋。
……怀柔有术,清慎持法。
……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显然是一个儒门弟子。
其子王浑、王义事迹均不详,王戎从崭露,角到名列竹林七贤,都与其父王浑的同僚阮籍有关。
《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阮籍与浑为友。
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
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
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
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
”王戎十五岁是正始九年(248)。
正始年问,何晏、王弼振起风,玄学清谈风靡上层知识界。
阮籍名高于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参加玄学清谈是毋庸置疑的。
观其对王浑所言,则可知王浑似未染玄风,以至“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这一“谈”字,在正始九年,无疑是玄学清谈。
清谈并不限制谈者的身份、年龄、资历,但却要求有严密清晰的逻辑推理能力。
王戎童年之时即神悟过人,又在盛极一时的论辩风气中长大成人,受其影响是必然的。
经阮籍介绍,王戎参加竹林之游,“善发谈端,赏其要会”,与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号“竹林七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和儒学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迭相专政,政治日趋腐败。
面对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
他们站在外戚、朝官一边反对当政的宦官。
宦官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残酷迫害反对派。
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开始不过问政治,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
东汉末年,曹操掌权,即以法治天下。
他在用人上提出唯才是举,曾下令:“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遇未而无知者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这种只问才能不问德行的思想,是直接与东汉以来儒家的名教相对抗的。
曹操杀了对他存大功的荀彧、崔琰、毛玠等人,也使一些人心惊胆战。
东汉末年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
政治上他们从过问政治、砥砺名教和积极的现世态度,转变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们接受了消沉的、对事不作反抗的,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
以老、庄、易为内容的玄学思想,开始抬头。
魏普时期洛阳的玄风及其东渡汉末三国,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化中,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融,东汉中后期人,是一名儒。
邓骘仰其名,召为舍人,马融不就,客居凉州武都汉阳。
遇羌人暴动,边境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
马融后悔未应邓骘之召,对他的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
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
今以曲俗飓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
遂往应邓骘之召,也就是这位大儒,为了保全生命,为大将军外戚梁冀诬害名臣李固,并作大将军《西第颂》。
政治上堕落的人,生活上无不堕落。
马融就是“居守眼器,多有侈饬,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
他以老庄哲学作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和灵魂的安慰。
他为《老子》作注,竭力捏合儒家和老庄。
论魏晋玄学向原始儒学的复归摘要:魏晋玄学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以人生价值为目的、构建形而上学理论依据特质鲜明的哲学。
从失去原始儒学精神已陷入危机的汉儒中解脱出来,重新思考人生价值意义,是玄学面临的时代而又超越时代的问题。
玄学借道家自然之论解析儒家伦理,为道德价值寻找内在依据,试图重新回到孔孟生活秩序源于内在德行自觉的心性论上。
而摆脱汉儒阴阳谶纬影响,超越繁琐训诂经学,把握儒家内在精神,则是从具体的道德之用上向原始儒学的复归。
关键词:玄学;自然本性;人生价值;原始儒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魏晋玄学也不离外,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以人生价值为目的、构建形而上理论依据特质鲜明的哲学。
魏晋之际社会时局不安,名士们通过形而上思辨的清谈方式,为人生价值、社会伦理体系寻找内在理论依据。
魏晋玄学固然受到社会时代影响,然也是对哲学永恒问题的思考,在理论建构中表现出向原始儒学部分复归。
一、汉代儒学的转变及后期危机“作为汉代思想特性的塑造者,董仲舒对于道德的探索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即制定出一套能够有效地维系国家长治久安的理论体系。
”[1]这就决定了董学并非是完全继承、恢复原始儒学或说是对人之根本问题的思考为己任,更多的是借儒学之用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目的。
如劳思光说:“儒学入汉代而丧失原有精神,遭受歪曲。
”[2]又说汉儒虽仍自命承孔子之学,但“其理论立场与先秦孔孟相去甚远”。
[3]事实上也是如此,以儒学为基础,并杂糅阴阳五行、墨、法等众多流派而建立的董氏“天人相应”之学成为汉代社会伦理的依据。
劳思光对此深恶痛绝,明确批评道:“董氏倡议罢黜百家,然究其实则董氏及当时儒生皆为阴阳五行观念所惑,不能承儒学,于是罢黜百家之结果,仅为伪儒学之得势。
”[4]思想理念的盛行自有时代的要求,虽不必追究董氏之过,然我们须明了汉儒已非孔孟原始儒学矣。
1、道德价值根源的外在化董氏所倡“天人相应”之学,认为“天”之规律及意志是价值的根源,以“存在”释“价值”的做法将德性标准排除在本性之外而寄于天道,孔孟儒学强调内在自觉德性的心性论转化为汉儒认为“天”是价值德行根源的宇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