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命神学看夏商周的社会文化变迁
- 格式:doc
- 大小:16.00 KB
- 文档页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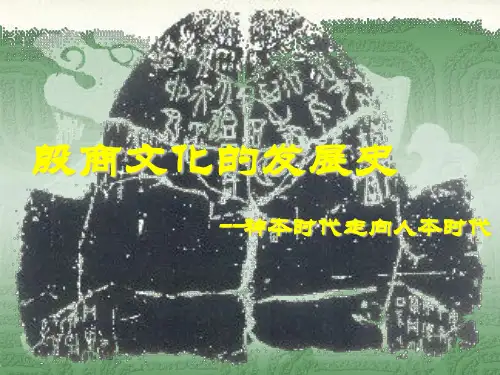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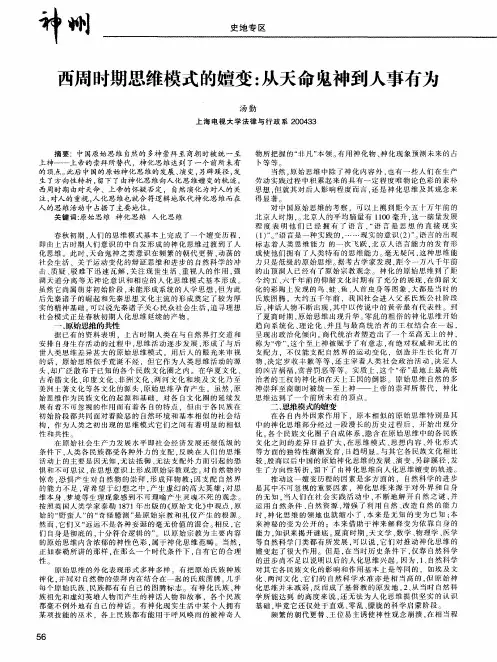

夏商时期人们开始逐步产生天命转移的思想
夏商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人们走出了原始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与此同时,人们也产生了关于“天命转移”的思想。
夏商时期,人民认为“天命转移”,它认为上天看重德行,对护国救民的统治者赐予了“气”,如果护国救民的统治者背叛了上天,他的“气”就会转移,转而赐予他的统治给君。
可以说,它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发展。
凡是能够及时处理人民疑问、安抚民心,具有善务修身之德的统治者,都能得到上天的赏识,而不能看到人民问题,不知从艰辛孝敬之父母,节护祖先家业者則会不堪考验,天地就会另辟蹊径,赐予另外一个人。
因此,“天命转移”的思想带给古代社会的是一种正义审判,他们不再只是追随血缘,而是
一个严禁腐败、官僚作风以及贪污受贿的新社会观念,这一观念也被用于后世的夏、商汤之争中,一直流传至今。
总之,“天命转移”的思想带来了中国古代社会一种全新的文化发展形式,根植于历史的观念,也成为了久远的传承,带给了我们今天严格的行政法治思维,也把社会的进步推动了一大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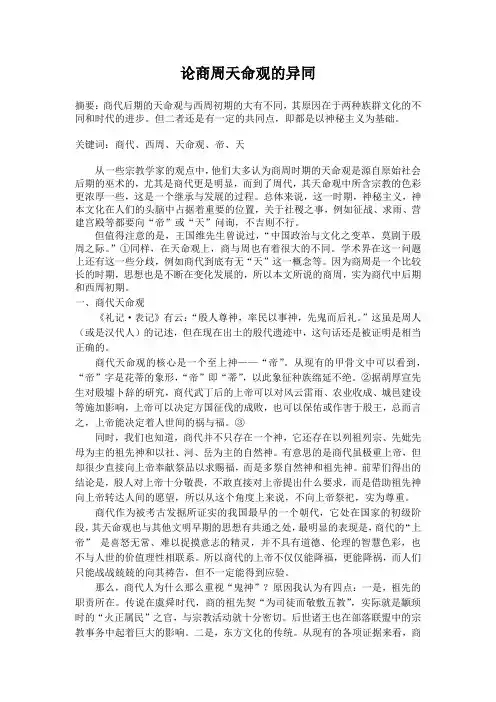
论商周天命观的异同摘要:商代后期的天命观与西周初期的大有不同,其原因在于两种族群文化的不同和时代的进步。
但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共同点,即都是以神秘主义为基础。
关键词:商代、西周、天命观、帝、天从一些宗教学家的观点中,他们大多认为商周时期的天命观是源自原始社会后期的巫术的,尤其是商代更是明显,而到了周代,其天命观中所含宗教的色彩更浓厚一些,这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神秘主义,神本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关于社稷之事,例如征战、求雨、营建宫殿等都要向“帝”或“天”问询,不吉则不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先生曾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①同样,在天命观上,商与周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还有这一些分歧,例如商代到底有无“天”这一概念等。
因为商周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思想也是不断在变化发展的,所以本文所说的商周,实为商代中后期和西周初期。
一、商代天命观《礼记·表记》有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这虽是周人(或是汉代人)的记述,但在现在出土的殷代遗迹中,这句话还是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
商代天命观的核心是一个至上神——“帝”。
从现有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帝”字是花蒂的象形,“帝”即“蒂”,以此象征种族绵延不绝。
②据胡厚宣先生对殷墟卜辞的研究,商代武丁后的上帝可以对风云雷雨、农业收成、城邑建设等施加影响,上帝可以决定方国征伐的成败,也可以保佑或作害于殷王,总而言之,上帝能决定着人世间的祸与福。
③同时,我们也知道,商代并不只存在一个神,它还存在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为主的祖先神和以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
有意思的是商代虽极重上帝,但却很少直接向上帝奉献祭品以求赐福,而是多祭自然神和祖先神。
前辈们得出的结论是,殷人对上帝十分敬畏,不敢直接对上帝提出什么要求,而是借助祖先神向上帝转达人间的愿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向上帝祭祀,实为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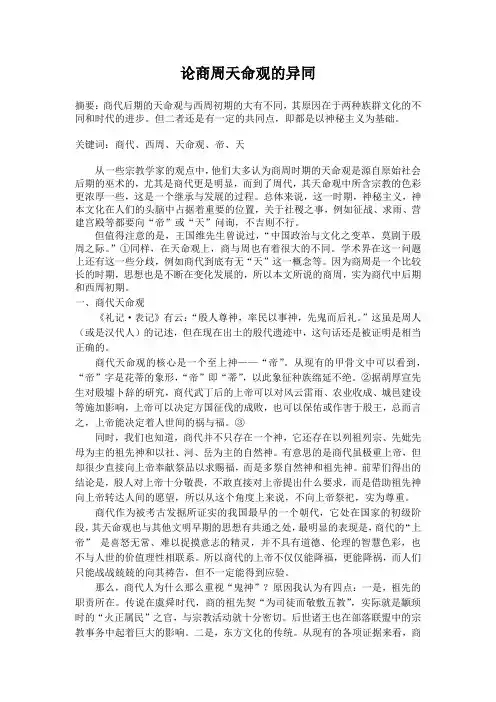
论商周天命观的异同摘要:商代后期的天命观与西周初期的大有不同,其原因在于两种族群文化的不同和时代的进步。
但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共同点,即都是以神秘主义为基础。
关键词:商代、西周、天命观、帝、天从一些宗教学家的观点中,他们大多认为商周时期的天命观是源自原始社会后期的巫术的,尤其是商代更是明显,而到了周代,其天命观中所含宗教的色彩更浓厚一些,这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神秘主义,神本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关于社稷之事,例如征战、求雨、营建宫殿等都要向“帝”或“天”问询,不吉则不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先生曾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①同样,在天命观上,商与周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还有这一些分歧,例如商代到底有无“天”这一概念等。
因为商周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思想也是不断在变化发展的,所以本文所说的商周,实为商代中后期和西周初期。
一、商代天命观《礼记·表记》有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这虽是周人(或是汉代人)的记述,但在现在出土的殷代遗迹中,这句话还是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
商代天命观的核心是一个至上神——“帝”。
从现有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帝”字是花蒂的象形,“帝”即“蒂”,以此象征种族绵延不绝。
②据胡厚宣先生对殷墟卜辞的研究,商代武丁后的上帝可以对风云雷雨、农业收成、城邑建设等施加影响,上帝可以决定方国征伐的成败,也可以保佑或作害于殷王,总而言之,上帝能决定着人世间的祸与福。
③同时,我们也知道,商代并不只存在一个神,它还存在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为主的祖先神和以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
有意思的是商代虽极重上帝,但却很少直接向上帝奉献祭品以求赐福,而是多祭自然神和祖先神。
前辈们得出的结论是,殷人对上帝十分敬畏,不敢直接对上帝提出什么要求,而是借助祖先神向上帝转达人间的愿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向上帝祭祀,实为尊重。

商周时期从神到人的阐述
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文明和政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它也被称为“天帝地尊”时代,这个时期的宗教信仰以祭祀神明为主。
起初的信仰以大自然神灵为中心,例如山神、河神、日神、月神等,重视对大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如表达出拜大地、纳谢四季万物之物的精神,以及守护新郎与新娘的婚嫁神灵、谋财神灵等等。
随着人类的社会文明的进步,其宗教信仰逐渐以人类化的神明为主,出现了很多以地位卓越、具有超越力量的神明,以表达人们对统治力和外来势力的尊敬和服从。
此外,为了庆祝特定的古代节目,如复活节,信仰也以特定神明为主,以象征人们对经典文化及祖先传统的尊重。
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每年定期举行的用以庆祝夏至、秋至两个节令(即夏节和秋节)期间,人们祭祀“伏羲氏”和“女娲氏”,以表达对文明的追求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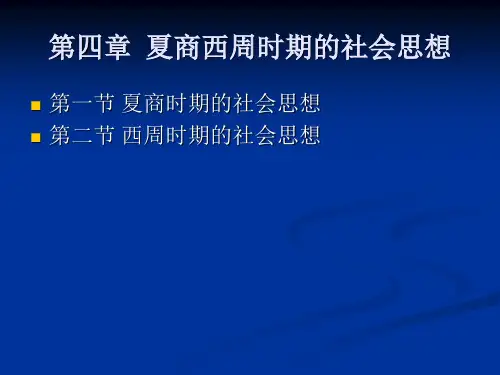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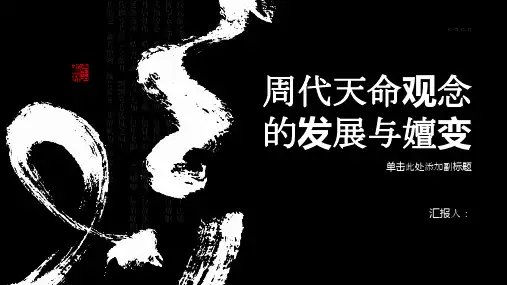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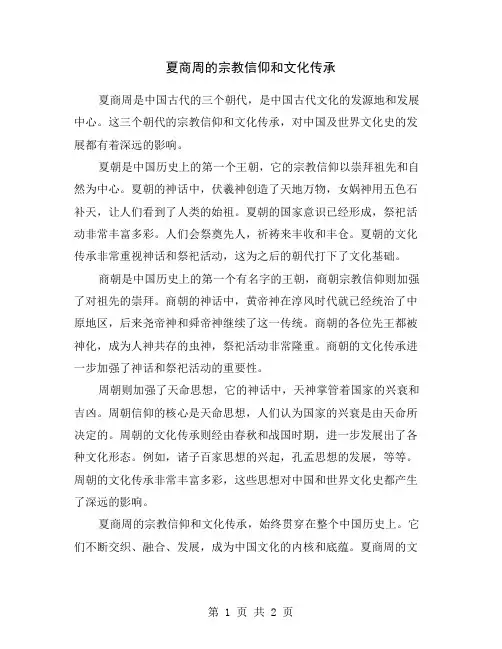
夏商周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的三个朝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和发展中心。
这三个朝代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对中国及世界文化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它的宗教信仰以崇拜祖先和自然为中心。
夏朝的神话中,伏羲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女娲神用五色石补天,让人们看到了人类的始祖。
夏朝的国家意识已经形成,祭祀活动非常丰富多彩。
人们会祭奠先人,祈祷来丰收和丰仓。
夏朝的文化传承非常重视神话和祭祀活动,这为之后的朝代打下了文化基础。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有名字的王朝,商朝宗教信仰则加强了对祖先的崇拜。
商朝的神话中,黄帝神在淳风时代就已经统治了中原地区,后来尧帝神和舜帝神继续了这一传统。
商朝的各位先王都被神化,成为人神共存的虫神,祭祀活动非常隆重。
商朝的文化传承进一步加强了神话和祭祀活动的重要性。
周朝则加强了天命思想,它的神话中,天神掌管着国家的兴衰和吉凶。
周朝信仰的核心是天命思想,人们认为国家的兴衰是由天命所决定的。
周朝的文化传承则经由春秋和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出了各种文化形态。
例如,诸子百家思想的兴起,孔孟思想的发展,等等。
周朝的文化传承非常丰富多彩,这些思想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商周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始终贯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它们不断交织、融合、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底蕴。
夏商周的文
化传承,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更是世界文化共享的文化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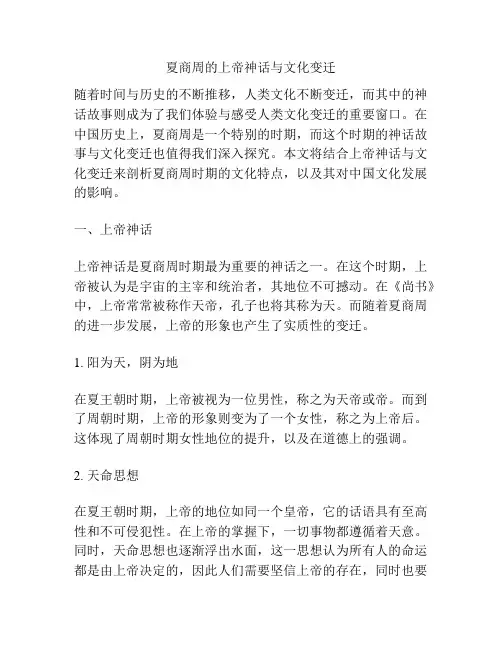
夏商周的上帝神话与文化变迁随着时间与历史的不断推移,人类文化不断变迁,而其中的神话故事则成为了我们体验与感受人类文化变迁的重要窗口。
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是一个特别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神话故事与文化变迁也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本文将结合上帝神话与文化变迁来剖析夏商周时期的文化特点,以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上帝神话上帝神话是夏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神话之一。
在这个时期,上帝被认为是宇宙的主宰和统治者,其地位不可撼动。
在《尚书》中,上帝常常被称作天帝,孔子也将其称为天。
而随着夏商周的进一步发展,上帝的形象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变迁。
1. 阳为天,阴为地在夏王朝时期,上帝被视为一位男性,称之为天帝或帝。
而到了周朝时期,上帝的形象则变为了一个女性,称之为上帝后。
这体现了周朝时期女性地位的提升,以及在道德上的强调。
2. 天命思想在夏王朝时期,上帝的地位如同一个皇帝,它的话语具有至高性和不可侵犯性。
在上帝的掌握下,一切事物都遵循着天意。
同时,天命思想也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思想认为所有人的命运都是由上帝决定的,因此人们需要坚信上帝的存在,同时也要尊重上帝的恩典。
3. 三皇五帝在夏商周时期,人们相信存在着三皇五帝,它们统治着古代中国。
三皇分别为女娲、神农与黄帝,其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时期。
而五帝则代表了古代中国的五大王朝,分别为夏、商、周、殷、周。
4. 周天子的崇拜随着周朝的建立,最早的夏商周神话也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性的神话。
西周的天子被认为是上帝的代表,其崇拜也成为了一种国家意识形态。
周天子通过上帝的授权,可以支配天下,并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5. 礼乐思想在夏商周时期,礼乐思想成为了一种强调文化秩序的道德体系。
在这种思想下,上帝成为了人们的心灵寄托,同时也被用来维护社会秩序。
文化中的一切庆典活动都需要与上帝相关联,升天堂和祭天成为了人们信仰和文化的重要标志。
二、文化变迁1. 夏王朝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王朝,在该时期,人们依然处在原始部落社会阶段,土著宗教和神话的影响非常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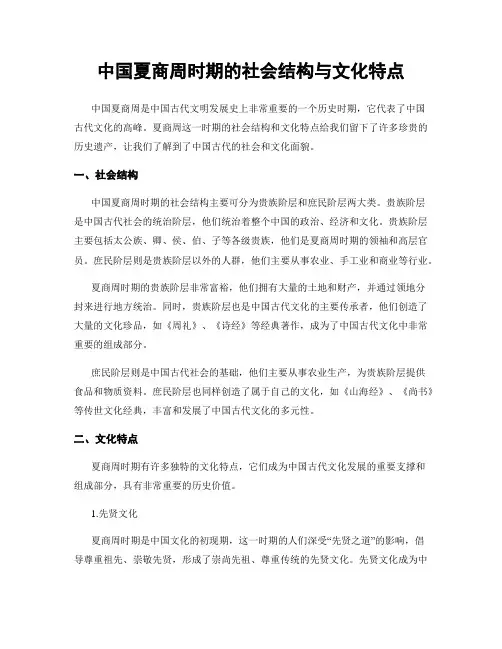
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点中国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
夏商周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产,让我们了解到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和文化面貌。
一、社会结构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主要可分为贵族阶层和庶民阶层两大类。
贵族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层,他们统治着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贵族阶层主要包括太公族、卿、侯、伯、子等各级贵族,他们是夏商周时期的领袖和高层官员。
庶民阶层则是贵族阶层以外的人群,他们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行业。
夏商周时期的贵族阶层非常富裕,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并通过领地分封来进行地方统治。
同时,贵族阶层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他们创造了大量的文化珍品,如《周礼》、《诗经》等经典著作,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庶民阶层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为贵族阶层提供食品和物质资料。
庶民阶层也同样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如《山海经》、《尚书》等传世文化经典,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性。
二、文化特点夏商周时期有许多独特的文化特点,它们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1.先贤文化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初现期,这一时期的人们深受“先贤之道”的影响,倡导尊重祖先、崇敬先贤,形成了崇尚先祖、尊重传统的先贤文化。
先贤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永恒的主题,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礼仪文化夏商周时期是中国礼仪文化始创期,这一时期的人们重视礼仪、注重规矩,形成了独特的礼仪文化。
礼仪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深深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历程。
3.易经文化夏商周时期也是中国易经文化的发源期,易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重要的一大经典,对中国思想文化具有重大影响。
易经文化强调“道法自然”、“顺天应人”的思想,对中国古代人们的社会观、宇宙观、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分支。
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作者:罗新慧来源:《历史研究》(京)2012年5期【内容提要】商周之际天命观念的变⾰,在中国传统⽂化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的跃动和觉醒,并⾮】周⼈天命观念的全部内容。
在翦商及建国过程中,周⼈基于现实需要⽽宣传天命。
周⼈与殷⼈的天命论并⾮迥然有别。
西周以降,周⼈的天命论绝⾮沿理性的轨道做直线式发展。
理性中夹杂⾮理性,觉醒与⾮觉醒相交织的状态,仍然是“精神觉醒”后周之上层思想领域内的⼤致状况。
词】殷周变⾰/德/天命观 【【关键】 对于商周之际天命观念的变⾰以及周⼈天命观在⽂化史上的意义,学者曾以“⼈道主义之黎明”,①“⼈⽂精神的跃动”②等加以描述、概括。
众多学者指出,周⼈“天命靡常”、“敬天保民”观念的提出,意味着周⼈抛弃殷⼈徒恃天命以为⽣的观念,转向寻求明德以为永命之基。
此⼀关键性转捩造成殷商命定之天向周⼈道德之天的转变,理性精神亦随之出现,继⽽得以发扬光⼤,从此成为传统⽂化的正统,声威远被。
周⼈天命观念的变⾰,在⽂化史上的确具划时代意义。
可是,如若考察周⼈天命观的完整意义,⽽不只注重于其中的理性因素,则可见周⼈的天命观显现出不为平常所注重的多样性来。
应当说,学者称之为周⼈天命观所表现的⼈⽂精神的跃动、⼈类精神的觉醒,是周⼈天命观中⾄为重要的内容,但是理性因素并不是周⼈天命观的全部。
并且,周⼈的天命观念并不是沿着理性的轨迹直线发展,相反周代历史发展中反复出现⾮理性因素。
这种理性与⾮理性相纠缠、觉醒之后仍有⾮觉醒的状态引⼈深思,“⼈类精神觉醒”之后的思想状况也值得进⼀步探究。
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多瞩⽬于周⼈天命观中的理性因素,⽽对天命蕴涵的其他意义以及天命观的发展变化关注不够。
本⽂结合出⼟⽂献与传世⽂献,考察殷周天命观的异同,揭⽰周⼈天命观的意义,缕析周⼈天命观念的变化,意在由此窥见周⼈天命观念的总体轮廓。
⼀、周初的天命论及其意义 周初天命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分析该时期天命观包含的因素,有益于了解周⼈天命论的完整意义以及此后周⼈天命观发展变化的线索。
从炎黄五帝到商周之变,阐述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发展脉络!中国古称“华夏”,也称“诸夏”、“诸华”,是古代史料记载中第一个朝代(夏朝)的自称,以此来区别与之敌对的四方蛮夷。
自夏朝以降,中原大地上经历了商朝、周朝,到了秦汉之后,方才逐渐形成中原大一统体系,并诞生了汉族概念,并以中华文明之名延续“华夏”衣钵。
人们将秦朝之前的历史时代称之为“先秦”。
那么,先秦时代的中国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呢?由于殷墟的发掘,对商朝的记载和佐证明显要强于前代,因此我们以商汤灭夏桀作为时间节点,分两部分来释析先秦社会发展变迁。
一、从五帝时期到夏后专权1、仰韶、龙山、华夏明代著名小说《西游记》的开篇便有一句曰:“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
说的是传说中国古代盘古开天辟地、三皇治理整顿世间、五帝定下人间社会伦理制度的故事。
历史上关于是否有盘古这个人或部落已经无从考究,但依据考古出土文物,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在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漫长年代中,中原大地曾出现了众多文明火种,我们依据今日地名,称之为“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
而这其中,仰韶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基本可以断定为夏文明的直系传承。
然而夏文明并不只有仰韶文化一个来源,地处黄土高原山侧地带的仰韶文化只是长江黄河流域众多文化发源地中的一个。
长江流域的大溪-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山东丘陵的大汶口文化,幽燕地区的红山文化等,均与仰韶文化频繁互动交流,最终进入了龙山文化阶段。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它涵盖了早期黄土高原上的仰韶文化和覆盖山东丘陵的大汶口文化,显示出此时的仰韶先民已经与居住在山东丘陵的东夷族群频繁联系,甚至很可能在此时就已经出现了东夷臣服仰韶夏人的情况。
只是这样的局面,遭到了南方河姆渡-良渚文化(长江下游)、大溪-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以及北方红山文化(幽燕地区)的冲击。
最终爆发了传说中的那两场传奇大战。
2、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龙山文化的出土遗址虽然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但基本分为原仰韶文化区域(推测为夏人)和原大汶口文化区域(推测为东夷人)。
商周时期天命观探微商周时期天命观探微摘要: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表现在天命观念上,它逐步实现了由殷商时期对神鬼观念的绝对崇拜向周朝时期突出人的地位的转变。
殷人完全慑服于、膜拜于一种超越的异己力量,称之为“帝”(即是天)。
在殷人的观念中,“帝”是自然风雨、人间祸福的主宰,在一定意义上,“帝”表现为一种“人格天”。
在殷周时期,对于“帝”(“人格天”)的绝对崇拜,仍然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
及至武王伐纣,周兴商灭,周人以一“小邦”(周人自称之)推翻商“泱泱大国”,仅仅依靠着天之垂怜是远远不够的,充分发挥民的力量,对于人的地位的重视,才是其能够克服万重艰难得以兴盛的主要原因。
正因如此,周人对于天不再是盲目的绝对崇拜,在一定意义上将天视为“形上天”,减少了殷商时期帝(即是天)所具有的人格色彩,这也是商周时期天命观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关键词:商周时期;神权;人;人格天;形上天;德中图分类号:B8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一、殷商时期对于神权的绝对崇拜自颛顼以大巫的身份改造原始宗教,在其影响下形成一种重视巫权和神权的混合文化即“旧中原文化”。
由于受到本族之风习以及旧中原文化的影响,殷人表现出一种对于鬼神的绝对信仰与崇拜(中国古代思想中“神”与“鬼”的观念意义相近,所以古代文献中常以“神鬼”并称)。
殷人重鬼,从殷墟甲骨卜辞的记事来看,殷人思想观念的主要特色表现为对某中超人的异己力量的依赖、恐惧而产生的崇拜,在一定层面上仍带有原始宗教性质。
殷人无事不卜,无日不卜,日夕均求接近鬼神,用频繁的占卜求知神帝和祖先对自己作为的态度,希望得到保佑,因而甘受鬼神的指导。
例如: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贞卯,帝弗其降祸。
――商承祚《殷契佚存》伐吾方帝受我又(佑)?――郭沫若《卜辞通纂》由此可知,“帝”最为殷民族的祖先神对于殷人的影响十分深远,殷人将其看作为世间一切的主宰。
作者: 余冬林
作者机构: 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九江332005
出版物刊名: 文教资料
页码: 52-53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34期
主题词: 神本;人本;文化;趋势
摘要:夏朝的文化渺渺茫茫,历史文献亦不足徵。
殷商时代,不仅已经把神秘力量神格化,而且已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神的系谱。
周灭商后,继承了殷商文化的一绪,同时也具有显著的西部特征。
周人完成了祖先神与至上神的二元化革命。
周人的伦理政治孕育了民本主义思潮的萌芽。
这种人本主义思潮的萌动,更鲜明具体地体现在周公制礼作乐上。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完成了从神本走向人本的过渡。
夏商到周朝文化的变迁周朝享国约800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
下面是有夏商到周朝文化的变迁,欢迎参阅。
夏商到周朝文化的变迁。
西周宗法制的综述宗法制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严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其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
这一制度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从而防止贵族间对于权位和财产的争夺。
在宗法制度下,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且世代均由嫡长子承继。
这个系统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又称宗主,为族人共尊。
宗子有祭祀祖先的权利。
若宗子有故而不能致祭,那么庶子才可代为祭祀。
和大宗相对应的是小宗。
在一般情况下,周天子以嫡长子继统,众庶子封为诸侯,历代的周天子为大宗,这些诸侯就是小宗。
诸侯亦以嫡长子继位,众庶子封为大夫,这些大夫为小宗,而诸侯则为其大宗。
大夫也以嫡长子继位,为大宗;众庶子为士,即小宗。
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和大夫实具有大宗与小宗双重身份。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宗和小宗的区别与贵族等级里的层层封建是完全合拍的。
如果说分封制从政治结构方面建立了贵族间的等级秩序,那么,宗法制则以注入了特定内容、贯彻了崭新原则的宗族传统观念使这个等级秩序得到稳固。
文献和彝铭记载中屡有“宗周”的记载,《诗经·公刘》说:“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从宗法系统看,周天子乃是地位最高的宗子。
周初,宗法制首先在周天子和诸侯间实施,以后逐渐及于中、小贵族,以至士与庶民之间,具有了普遍性质。
嫡庶的划分宗法制源于父权家长制家庭。
随着社会发展,漫长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取代,并最终确立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太古先民“知母不知父”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父权家长制家庭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并在诸妻中分别嫡庶。
据《独断》记载,三代的“一夫多妻制”情况是这样的:“天子娶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妇。
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部御女。
论夏商周三代的天命理论
侯玉臣
【期刊名称】《甘肃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5(000)004
【摘要】天命理论是夏商周三代奴隶制社会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理论.天命理论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代东方原始巫术文化的演变与发展.天命理论的形成是古代中国早期宗族社会在政治上的反映.天命理论的政治思想方针主要体现在以德治国的方针上,是古代东方宗教文化的集大成.
【总页数】4页(P196-199)
【作者】侯玉臣
【作者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21
【相关文献】
1.夏商周三代档案工作的特点
2.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刑罚与重刑主义研究
3."三重证据论古史一片赤诚为学人"r——评《夏商周三代纪年》
4.夏商周三代明堂的文献与史料研究
5.图说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之酒器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从天命神学看夏商周的社会文化变迁
--读晁错《夏商周的社会变迁》
夏商西周是中华民族较为早期的文化阶段,虽然文化并不如后世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那样繁荣,但文学与史学的萌芽都开始产生,并且带着浓郁的时代特征。
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表象中可以看出天命神学观的变化。
首先,引入一个神权法的概念:神权法思想是指在初民社会由于人们对自然认识水平有限,对很多事物无法认识、无法解释,而产生的一种对于天、神乃至某种动物的盲目崇拜用神来作为法作为一种评判事物是非的标准的思想。
夏商西周时期尚处于青铜时代,生产力并不发达,许多事情无法用科学解释,而天、神的观念正好可以“完美”地解释这些问题,于是人们对于天、神的崇拜无以复加,产生神权法的思想也就是必然的了。
就以夏商周的起源来说,其颇具神话色彩的传说中极力将帝王鼓吹为神之子,受天命而治人世,为其统治正名,强调天的至高无上性。
《史记•夏本纪》中称:“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而商人甚至宣称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孙,《诗经•商颂》的《长发》载:“有戎方将,帝立子生商。
”《玄鸟》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这样他们便从血缘上找到了充当上帝代理人的合法依据,并为垄断神权提供依据。
西周时期对政权的正名并没有一味沿袭夏商两代的消极神学论,而是将重点从天命逐渐转移到人世,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宣扬周朝德政,故而天命授之,王权依旧具有至高无上性。
从发掘的甲骨卜辞和历史文献来看,甲骨卜辞中记录最多的即对天象的占卜,以及在国有大事例如迁都征战时进行占卜,询问天的旨意,尤以殷商时期甲骨保存最多。
等到了周朝,由于筮法盛行,甲骨占卜逐渐失去了它显赫的地位,但仍为贵族所重视。
春秋时期,晋献公令从卜,卜人以“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可见龟卜即便在春秋时期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因汤武革命而使周人感到“天命靡常”,周人并不尽信于天,他们迷信的重要方式为蓍筮,是以人事来印证天意,这与周人浓重的历史意识有关,再次体现神意动摇的社会现实。
与此同时,商王朝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且仪式繁复,大多是以祭祀先祖为目的祈求风调雨顺,在这里可以看出,商人将祖先与天直接联系,反应了商人浓厚的宗教观念。
我认为夏商西周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是商周时期文学与史学的萌芽与发展,它标志着早期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夏朝尚未发现有文字记载,但是从孔子《论语》:“殷因于夏,其损益可知矣”中可以看出,夏商文化是具有继承性的,因此也不能忽视夏朝在文化方面的某些建树。
殷代早期的文学和史学萌芽受到神意迷信观念的极大影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积极因素才逐渐发展。
殷墟的甲骨卜辞中颇为注意记事的完整性,至商晚期,更偏重于记载重大事件,逐渐摆脱了神意对文化发展的桎梏。
周初人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典册文字在甲骨卜辞的基础上实现,不再是对神意进行祈求的记录,而是通过文章来阐明道理。
从典册文字中记言与记事的分开来看,可能已经产生专职记事的史官。
如果说殷商时期的文史学是从神事转移到人事的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西周时期的文学与史学更为重视人事的重要性,将历史的眼光集中于人,以青铜器上的彝铭为载体记录历史发展的全貌,其中以《多友鼎》为典型,记录了讨伐入侵的猃狁,开创了后世关于战争记载的先河。
此外,神意迷信的衰落与天命观的新发展也可体现于彝铭的另一功用。
青铜器在商朝主要作为礼器与祭器使用,是一种权利身份等级的象征,而彝铭则被赋予了历史教育的功能,为后世提供借鉴,教育周朝后代增强历史观念培养其德操,这与殷代将王朝兴衰寄予天命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
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断认识总结逐渐改变了对天命、对神意迷信的理解,逐渐挣脱对天的权威的畏惧与盲从,而这一认识的变化直接体现于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将记录对象从神事转移到人事,注重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基本确立文学史学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对后世有长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