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间性的成因
- 格式:docx
- 大小:22.97 KB
- 文档页数: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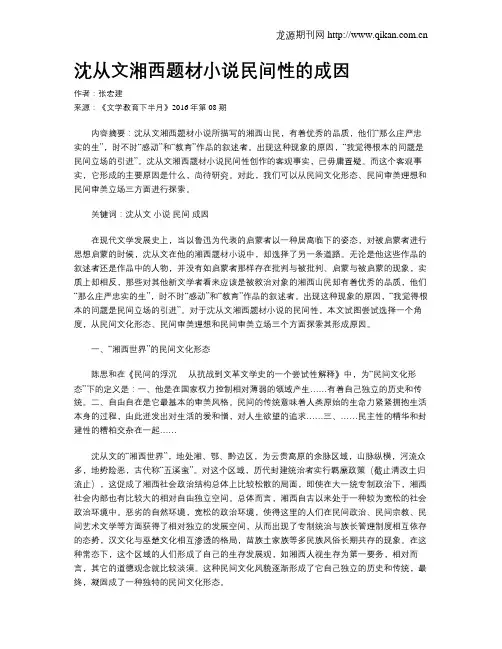
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间性的成因作者:张宏建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6年第08期内容摘要: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所描写的湘西山民,有着优秀的品质,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时不时“感动”和“教育”作品的叙述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民间立场的引进”。
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间性创作的客观事实,已毋庸置疑。
而这个客观事实,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尚待研究。
对此,我们可以从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审美理想和民间审美立场三方面进行探索。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民间成因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当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被启蒙者进行思想启蒙的时候,沈从文在他的湘西题材小说中,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无论是他这些作品的叙述者还是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如启蒙者那样存在批判与被批判、启蒙与被启蒙的现象,实质上却相反,那些对其他新文学者看来应该是被救治对象的湘西山民却有着优秀的品质,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时不时“感动”和“教育”作品的叙述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民间立场的引进”。
对于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间性,本文试图尝试选择一个角度,从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审美理想和民间审美立场三个方面探索其形成原因。
一、“湘西世界”的民间文化形态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中,为“民间文化形态”下的定义是:一、他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
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
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三、……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地处湘、鄂、黔边区,为云贵高原的余脉区域,山脉纵横,河流众多,地势险恶,古代称“五溪蛮”。
对这个区域,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羁縻政策(截止清改土归流止),这促成了湘西社会政治结构总体上比较松散的局面,即使在大一统专制政治下,湘西社会内部也有比较大的相对自由独立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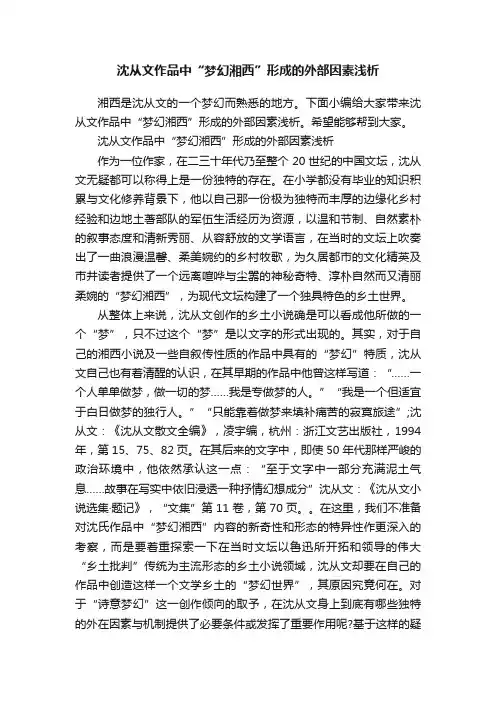
沈从文作品中“梦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浅析湘西是沈从文的一个梦幻而熟悉的地方。
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沈从文作品中“梦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浅析。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沈从文作品中“梦幻湘西”形成的外部因素浅析作为一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坛,沈从文无疑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份独特的存在。
在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知识积累与文化修养背景下,他以自己那一份极为独特而丰厚的边缘化乡村经验和边地土著部队的军伍生活经历为资源,以温和节制、自然素朴的叙事态度和清新秀丽、从容舒放的文学语言,在当时的文坛上吹奏出了一曲浪漫温馨、柔美婉约的乡村牧歌,为久居都市的文化精英及市井读者提供了一个远离喧哗与尘嚣的神秘奇特、淳朴自然而又清丽柔婉的“梦幻湘西”,为现代文坛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乡土世界。
从整体上来说,沈从文创作的乡土小说确是可以看成他所做的一个“梦”,只不过这个“梦”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
其实,对于自己的湘西小说及一些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中具有的“梦幻”特质,沈从文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他曾这样写道:“……一个人单单做梦,做一切的梦……我是专做梦的人。
”“我是一个但适宜于白日做梦的独行人。
”“只能靠着做梦来填补痛苦的寂寞旅途”;沈从文:《沈从文散文全编》,凌宇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5、75、82页。
在其后来的文字中,即使50年代那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中,他依然承认这一点:“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70页。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沈氏作品中“梦幻湘西”内容的新奇性和形态的特异性作更深入的考察,而是要着重探索一下在当时文坛以鲁迅所开拓和领导的伟大“乡土批判”传统为主流形态的乡土小说领域,沈从文却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这样一个文学乡土的“梦幻世界”,其原因究竟何在。
对于“诗意梦幻”这一创作倾向的取予,在沈从文身上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外在因素与机制提供了必要条件或发挥了重要作用呢?基于这样的疑问,本文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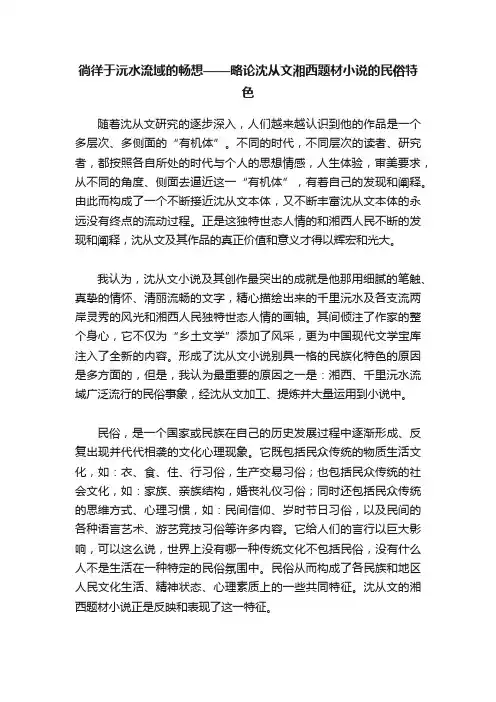
徜徉于沅水流域的畅想——略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俗特色随着沈从文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的作品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
不同的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逼近这一“有机体”,有着自己的发现和阐释。
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沈从文本体,又不断丰富沈从文本体的永远没有终点的流动过程。
正是这独特世态人情的和湘西人民不断的发现和阐释,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才得以辉宏和光大。
我认为,沈从文小说及其创作最突出的成就是他那用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怀、清丽流畅的文字,精心描绘出来的千里沅水及各支流两岸灵秀的风光和湘西人民独特世态人情的画轴。
其间倾注了作家的整个身心,它不仅为“乡土文学”添加了风采,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宝库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形成了沈从文小说别具一格的民族化特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湘西、千里沅水流域广泛流行的民俗事象,经沈从文加工、提炼并大量运用到小说中。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袭的文化心理现象。
它既包括民众传统的物质生活文化,如:衣、食、住、行习俗,生产交易习俗;也包括民众传统的社会文化,如:家族、亲族结构,婚丧礼仪习俗;同时还包括民众传统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如:民间信仰、岁时节日习俗,以及民间的各种语言艺术、游艺竞技习俗等许多内容。
它给人们的言行以巨大影响,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传统文化不包括民俗,没有什么人不是生活在一种特定的民俗氛围中。
民俗从而构成了各民族和地区人民文化生活、精神状态、心理素质上的一些共同特征。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正是反映和表现了这一特征。
一沈从文在一九三一年所写的<<甲辰闲话>>中,为自己的创作定下了一个总的目标,便是要为他的家乡—边陲极境的湘西,写出“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沈从文选集·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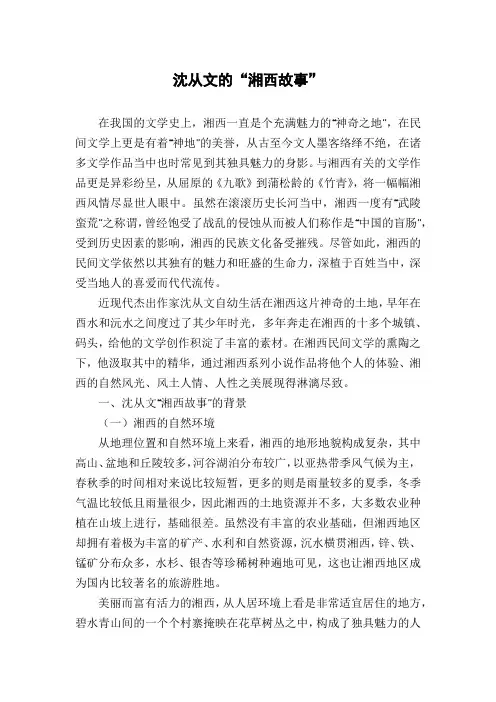
沈从文的“湘西故事”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湘西一直是个充满魅力的“神奇之地”,在民间文学上更是有着“神地”的美誉,从古至今文人墨客络绎不绝,在诸多文学作品当中也时常见到其独具魅力的身影。
与湘西有关的文学作品更是异彩纷呈,从屈原的《九歌》到蒲松龄的《竹青》,将一幅幅湘西风情尽显世人眼中。
虽然在滚滚历史长河当中,湘西一度有“武陵蛮荒”之称谓,曾经饱受了战乱的侵蚀从而被人们称作是“中国的盲肠”,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湘西的民族文化备受摧残。
尽管如此,湘西的民间文学依然以其独有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深植于百姓当中,深受当地人的喜爱而代代流传。
近现代杰出作家沈从文自幼生活在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早年在酉水和沅水之间度过了其少年时光,多年奔走在湘西的十多个城镇、码头,给他的文学创作积淀了丰富的素材。
在湘西民间文学的熏陶之下,他汲取其中的精华,通过湘西系列小说作品将他个人的体验、湘西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人性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沈从文“湘西故事”的背景(一)湘西的自然环境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上来看,湘西的地形地貌构成复杂,其中高山、盆地和丘陵较多,河谷湖泊分布较广,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春秋季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暂,更多的则是雨量较多的夏季,冬季气温比较低且雨量很少,因此湘西的土地资源并不多,大多数农业种植在山坡上进行,基础很差。
虽然没有丰富的农业基础,但湘西地区却拥有着极为丰富的矿产、水利和自然资源,沉水横贯湘西,锌、铁、锰矿分布众多,水杉、银杏等珍稀树种遍地可见,这也让湘西地区成为国内比较著名的旅游胜地。
美丽而富有活力的湘西,从人居环境上看是非常适宜居住的地方,碧水青山间的一个个村寨掩映在花草树丛之中,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间仙境。
一年四季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在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提到武陵山与雪峰山相映成趣,但这也成为了阻碍湘西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两座山脉的隔断下,湘西地区被分割成了许多丘陵和平原,且面积都很小,相互之间的交通成为多年来的一大难题,如果失去了水路交通,湘西将会是一个更加贫瘠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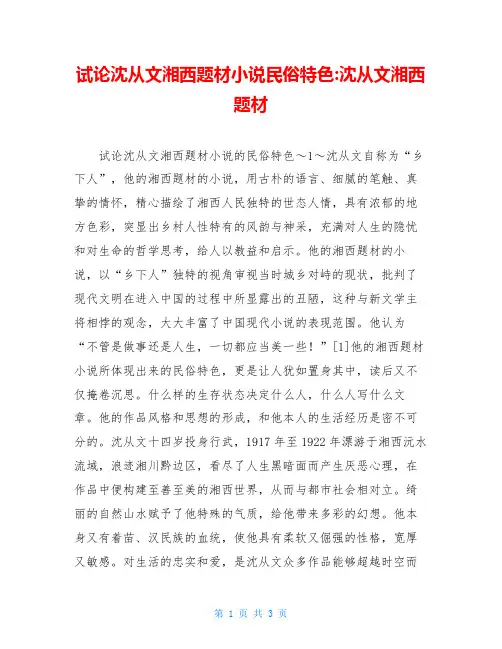
试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俗特色:沈从文湘西题材试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俗特色~1~沈从文自称为“乡下人”,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用古朴的语言、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怀,精心描绘了湘西人民独特的世态人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突显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充满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以教益和启示。
他的湘西题材的小说,以“乡下人”独特的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了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相悖的观念,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他认为“不管是做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1]他的湘西题材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民俗特色,更是让人犹如置身其中,读后又不仅掩卷沉思。
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决定什么人,什么人写什么文章。
他的作品风格和思想的形成,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沈从文十四岁投身行武,1917年至1922年漂游于湘西沅水流域,浪迹湘川黔边区,看尽了人生黑暗面而产生厌恶心理,在作品中便构建至善至美的湘西世界,从而与都市社会相对立。
绮丽的自然山水赋予了他特殊的气质,给他带来多彩的幻想。
他本身又有着苗、汉民族的血统,使他具有柔软又倔强的性格,宽厚又敏感。
对生活的忠实和爱,是沈从文众多作品能够超越时空而长久地像沅江里的活鱼一样,水淋淋欢蹦乱跳葆有充沛生命力的秘密。
民俗包括极其丰富的内容,它既有物质文化方面的内涵,又有精神方面的内涵。
物质文化方面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的习俗和生产交易的习俗上;精神文化方面则有更为广泛的内容,有民族传统的社会文化,如:婚丧礼仪习俗等;又有民众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如:节日习俗、语言艺术等。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小说主要就是表现了作家对民族意识和人物心态的深刻关注、再现了湘西农村形形色色的婚姻悲剧和描摹了湘西充满风情的环境和民俗美。
下面笔者就尝试用自己粗浅而又稚嫩的笔调,就这四个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充满民俗风情的生活环境提到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湘西生活环境,不得不说他笔下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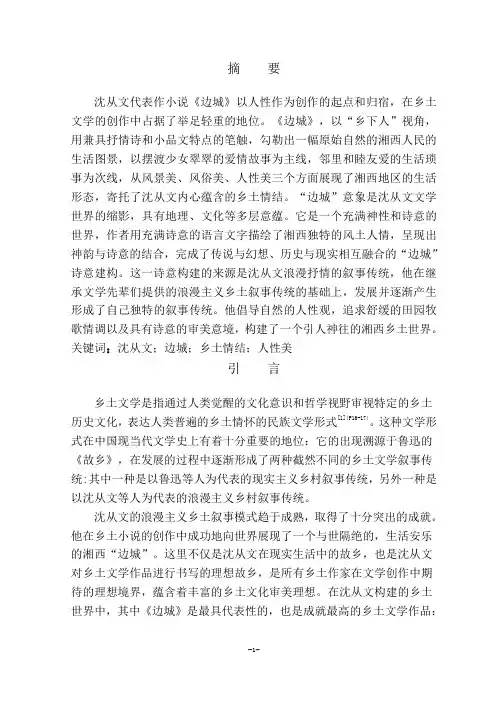
摘要沈从文代表作小说《边城》以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边城》,以“乡下人”视角,用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特点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原始自然的湘西人民的生活图景,以摆渡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邻里和睦友爱的生活琐事为次线,从风景美、风俗美、人性美三个方面展现了湘西地区的生活形态,寄托了沈从文内心蕴含的乡土情结。
“边城”意象是沈从文文学世界的缩影,具有地理、文化等多层意蕴。
它是一个充满神性和诗意的世界,作者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文字描绘了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呈现出神韵与诗意的结合,完成了传说与幻想、历史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边城”诗意建构。
这一诗意构建的来源是沈从文浪漫抒情的叙事传统,他在继承文学先辈们提供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渐产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传统。
他倡导自然的人性观,追求舒缓的田园牧歌情调以及具有诗意的审美意境,构建了一个引人神往的湘西乡土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乡土情结;人性美引言乡土文学是指通过人类觉醒的文化意识和哲学视野审视特定的乡土历史文化,表达人类普遍的乡土情怀的民族文学形式[1](P16-17)。
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其中一种是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村叙事传统,另外一种是以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乡村叙事传统。
沈从文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模式趋于成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
他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成功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安乐的湘西“边城”。
这里不仅是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乡,也是沈从文对乡土文学作品进行书写的理想故乡,是所有乡土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期待的理想境界,蕴含着丰富的乡土文化审美理想。
在沈从文构建的乡土世界中,其中《边城》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成就最高的乡土文学作品:它用简单的文字以及平实的语言再次向读者展现了在茶峒小镇中悠闲生活的村民,以及关于船女翠翠的亲情与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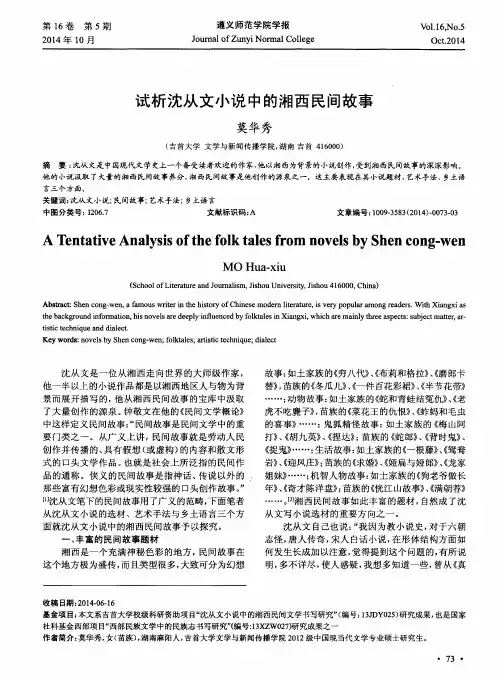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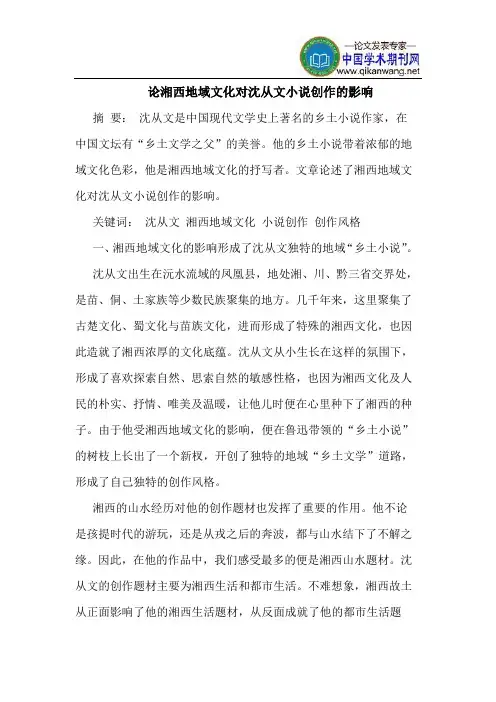
论湘西地域文化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摘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在中国文坛有“乡土文学之父”的美誉。
他的乡土小说带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他是湘西地域文化的抒写者。
文章论述了湘西地域文化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地域文化小说创作创作风格一、湘西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地域“乡土小说”。
沈从文出生在沅水流域的凤凰县,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
几千年来,这里聚集了古楚文化、蜀文化与苗族文化,进而形成了特殊的湘西文化,也因此造就了湘西浓厚的文化底蕴。
沈从文从小生长在这样的氛围下,形成了喜欢探索自然、思索自然的敏感性格,也因为湘西文化及人民的朴实、抒情、唯美及温暖,让他儿时便在心里种下了湘西的种子。
由于他受湘西地域文化的影响,便在鲁迅带领的“乡土小说”的树枝上长出了一个新杈,开创了独特的地域“乡土文学”道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湘西的山水经历对他的创作题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不论是孩提时代的游玩,还是从戎之后的奔波,都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感受最多的便是湘西山水题材。
沈从文的创作题材主要为湘西生活和都市生活。
不难想象,湘西故土从正面影响了他的湘西生活题材,从反面成就了他的都市生活题材。
家乡湘西及湘西的民俗成为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和支撑点,他从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中,提炼出饱含深刻寓意的意向母体,将民俗文化摄入作品并使之具体化、艺术化、形象化,从而使他的湘西地域小说具有丰厚的审美内涵。
二、自然、淳朴的民风民俗对沈从文创作的启发及影响。
湘西是一个静谧、和缓、永恒的世界,那里有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域和永远奔腾不息的浩荡沅水和沅水文化,有优美迷人的自然风光。
那里的人展示着最本真的生活态度及最本能的真善美。
“爱美”表现于妇女的装束方面给人一种简单、朴素、异常动人的印象,“热情”多表现于歌声中。
沈从文敏感而善于捕捉个人感受体验,他继承了湘西人激情、质朴、敏锐的特性,喜欢接触新事物,害怕沉溺于一成不变的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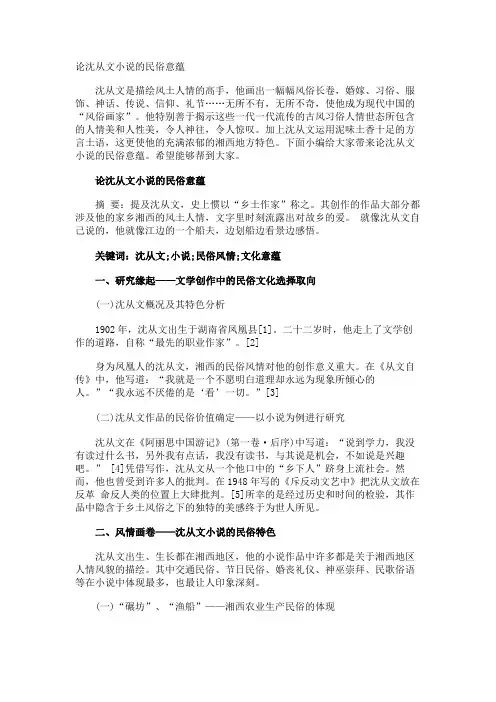
论沈从文小说的民俗意蕴沈从文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
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令人神往,令人惊叹。
加上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十足的方言土语,这更使他的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
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论沈从文小说的民俗意蕴。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论沈从文小说的民俗意蕴摘要:提及沈从文,史上惯以“乡土作家”称之。
其创作的作品大部分都涉及他的家乡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字里时刻流露出对故乡的爱。
就像沈从文自己说的,他就像江边的一个船夫,边划船边看景边感悟。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民俗风情;文化意蕴一、研究缘起——文学创作中的民俗文化选择取向(一)沈从文概况及其特色分析1902年,沈从文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1]。
二十二岁时,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自称“最先的职业作家”。
[2]身为凤凰人的沈从文,湘西的民俗风情对他的创作意义重大。
在《从文自传》中,他写道:“我就是一个不愿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
”“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
”[3](二)沈从文作品的民俗价值确定——以小说为例进行研究沈从文在《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一卷·后序)中写道:“说到学力,我没有读过什么书,另外我有点话,我没有读书,与其说是机会,不如说是兴趣吧。
” [4]凭借写作,沈从文从一个他口中的“乡下人”跻身上流社会。
然而,他也曾受到许多人的批判。
在1948年写的《斥反动文艺中》把沈从文放在反革命反人类的位置上大肆批判。
[5]所幸的是经过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其作品中隐含于乡土风俗之下的独特的美感终于为世人所见。
二、风情画卷——沈从文小说的民俗特色沈从文出生、生长都在湘西地区,他的小说作品中许多都是关于湘西地区人情风貌的描绘。
其中交通民俗、节日民俗、婚丧礼仪、神巫崇拜、民歌俗语等在小说中体现最多,也最让人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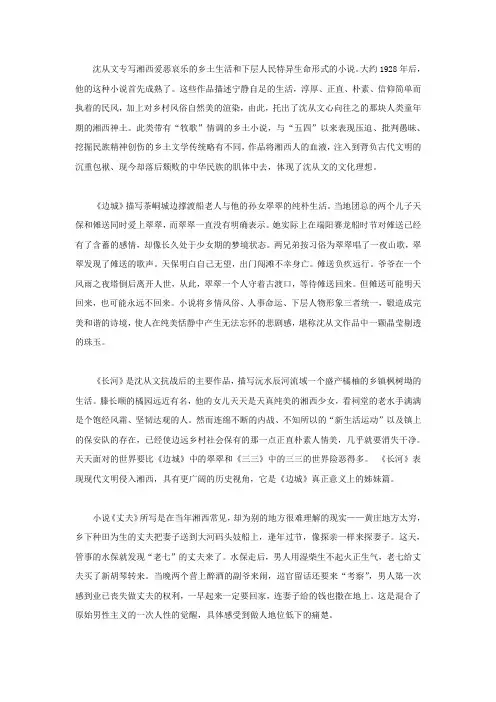
沈从文专写湘西爱恶哀乐的乡土生活和下层人民特异生命形式的小说。
大约1928年后,他的这种小说首先成熟了。
这些作品描述宁静自足的生活,淳厚、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着的民风,加上对乡村风俗自然美的渲染,由此,托出了沈从文心向往之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湘西神土。
此类带有“牧歌”情调的乡土小说,与“五四”以来表现压迫、批判愚昧、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略有不同,作品将湘西人的血液,注入到背负古代文明的沉重包袱、现今却落后颓败的中华民族的肌体中去,体现了沈从文的文化理想。
《边城》描写茶峒城边撑渡船老人与他的孙女翠翠的纯朴生活。
当地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翠翠,而翠翠一直没有明确表示。
她实际上在端阳赛龙船时节对傩送已经有了含蓄的感情,却像长久处于少女期的梦境状态。
两兄弟按习俗为翠翠唱了一夜山歌,翠翠发现了傩送的歌声。
天保明白自己无望,出门闯滩不幸身亡。
傩送负疚远行。
爷爷在一个风雨之夜塔倒后离开人世,从此,翠翠一个人守着古渡口,等待傩送回来。
但傩送可能明天回来,也可能永远不回来。
小说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统一,锻造成完美和谐的诗境,使人在纯美恬静中产生无法忘怀的悲剧感,堪称沈从文作品中一颗晶莹剔透的珠玉。
《长河》是沈从文抗战后的主要作品,描写沅水辰河流域一个盛产橘柚的乡镇枫树坳的生活。
滕长顺的橘园远近有名,他的女儿天天是天真纯美的湘西少女,看祠堂的老水手满满是个饱经风霜、坚韧达观的人。
然而连绵不断的内战、不知所以的“新生活运动”以及镇上的保安队的存在,已经使边远乡村社会保有的那一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就要消失干净。
天天面对的世界要比《边城》中的翠翠和《三三》中的三三的世界险恶得多。
《长河》表现现代文明侵入湘西,具有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它是《边城》真正意义上的姊妹篇。
小说《丈夫》所写是在当年湘西常见,却为别的地方很难理解的现实——黄庄地方太穷,乡下种田为生的丈夫把妻子送到大河码头妓船上,逢年过节,像探亲一样来探妻子。

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前创作原因试探赵江滨提要: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乡土小说和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田园乡土小说标示着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艺术倾向,但从审美角度审视,后者是对小说现实功利因素的超越和对艺术本性的回归。
文章在概括阐述两种乡土文学的基本社会背景及艺术特征之后,着重以沈从文早年生活和具体作品互训的方式,阐释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基本成因。
关键词: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生命意识。
AbstractThe enlightened regional novels and pastoral regional novels symbolize two artistic trends in contemporary regional literature,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Luxun and Shen Congwen respectively.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pastoral novels are transcension to utilitarian factors and regression of its artistic essentiality. After summarizing the fundament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kinds of regional novels, the text depicts the basic formation of pastoral style in Shen Congwen’s regional novels by mean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hen Congwen’s early life and his specific literary creations.Key words:regional novels pastoral style anima consciousness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叶,沈从文和废名(冯文炳)的乡土题材小说出现后,中国新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才可说真正获得了田园风格的存在形态。
沈从文的民间民俗文化09级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刘锐099038摘要:沈从文(1902年—1988年),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县人。
沈从文读过两年私塾,正规教育仅是小学,他是一个具有土家族血统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土家族文化传统的作家,他以湘西民间优秀文化精神及城市下层民众的优秀品德为参照观察“现代”文明,从而发展了自由主义的保守性,成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
他的作品大多都是对民间,民俗文化的描写,通过过一个故事的叙述来体现出自己深刻的思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沈从文眼里所看到的社会民间的生活形态。
关键词:沈从文民间文化湘西民俗文化说到沈从文我们就不得不说说他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
“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旨是指那种立足于传统文化,力图融合古今,也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倾向或思想派别。
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政治上可以很进步、很革命,甚至十分激进,但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却很谨慎。
沈从文自身是土家族人,出生于湘西,受到湘西文化的影响,其个人的文学作品风格也将这种文化融入其中。
尤其是受到当时历史客观环境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初的湘西自治运动,在使沈从文心中原有的湘西民族的自主自由精神自觉化的同时,也给了他以“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并从此构成了他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民族文化基础。
到北京后,一方面是北京的文化自由精神与丰厚传统文化的培育,使他有了“京派”风度;另一方面是自己生活的困苦,加上湘西人的固执,又使他形成了“乡下人”的精神气质。
正是这二者的结合,使他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使他成为“京派重镇”。
因此,沈从文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多的是侧重于在城市下层人民的体现。
沈从文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他将这种隔膜称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隔膜。
他与“城市”的隔膜,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悬殊和所谓文明教养的差异,最根本的,他与城市人在生活、经验、知识乃至价值观上,具有后天无法沟通的天壤之别。
引言纵观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界,沈从文无疑是很闪亮也很独特的。
作者用充满灵性与诗意的语言为世人勾画出一幅至纯至美的湘西民俗风情画。
湘西独特的地理位置,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朴实勤劳的人民的影响成就了沈从文特殊的个性气质,他自称为“乡下人”,“依恋于对‘乡下人’生活的体认和再现,从而使之成为湘西生活的自觉的叙述者。
”沈从文的小说和湘西民俗文化关系密切,湘西民俗是沈从文创作源泉。
他的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湘西特有的节目,奇异的地方风俗,神秘而古老的巫楚神话传说的描述,带有极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乡土风情,通过描写这些独特的湘西文化表达对自然的生命形式、原始人性的赞美和作家对民族意识及人物心态的深刻关注。
同时在这一系列的小说中,他以一种热忱和抨击的态度对民族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又多与民俗中的陋俗相连)“作了一种善意的记录”(《沈从文文集》十二卷P86 花城出版社),在他的追寻与探索中虽不无悲凉的气氛,伴随着严峻的民族危机感,同时也表现了“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
这也正是他的湘西小说中民俗特色的风格。
每每人们读后,犹如一杯醇酒,总是使你不断地去思索、回味。
本文试图通过对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中的几类突出民俗的探讨来展示湘西人民自然、健康的生命力,从而引起我们对湘西民俗传承的重视和自我发展的反思。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生动具体地描绘了湘西六类突出的民风民俗:婚恋民俗、巫楚文化、民居文化、丧葬民俗、节日民俗和湘西山歌,构成了一幅至纯至美的湘西民俗风情画。
一、婚恋民俗正如沈从文所言,湘西原是“被历史所遗忘”的角落。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后,湘西仍停留在原始或半原始状态,当然这里的风俗习惯也就仍然滞留在原始的落后状态,作为民俗现象之一的婚俗就不能不浸染上这历史的痕迹,因而影响到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
一方面婚俗中的陋俗导致了许许多多的婚姻悲剧。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始或半原始状态,湘西的婚俗里同样也有着自然淳朴的气息,也造就了许多天真烂漫的爱情佳话。
浅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摘要:沈从文对湘西生活的回忆性书写是他众多作品中较为典型的一部分,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乌托邦式的桃花源,而是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人间世界,那里人们的生活在战争与时代变迁的影响下显出颓败与堕落。
本文深刻剖析沈从文在不同时期乡土小说中对湘西世界的描写,并发掘沈从文作品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人与自然灵性相通的讴歌。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乡土小说一、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创作背景沈从文创作时期所处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我国社会的动荡时期。
沈从文在生活的都市中见惯了人情冷暖,他成了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乡下人”,故乡成了他精神上的净土,但几次回乡却发现物是人非,正如之前谈到对他一次又一次地重视记忆中的故乡,他看到社会变革冲击下湘西的变化与人们的堕落,他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索,并且将重建乡村世界与湘西自治的愿望倾注到他的作品中。
他不仅让我们读到自然与人给我们的启示,也企图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让我们正视我们所处的环境。
二、沈从文不同创作时期的湘西世界1.初期对湘西世界的描写:《从文自传》和《边城》从《从文自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少年时对家乡的记忆,如《我所生长的地方》中是这样写的“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都应当明白‘镇筸’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的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
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
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的向深山村庄走去,同农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一什之利。
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武术的神的侍奉者。
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皆有兵役……”(沈从文,1992)我们可以看到,湘西普通人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人们守法敬神,遵从古礼,甚至连兵卒都“纯善”如民。
不难看出沈从文记忆中的家乡人事有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是一种和谐尽然有序的状态。
同样沈从文的《边城》留给大家的印象相似,可却又有本质的不同,即沈从文笔下的茶峒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的现实世界,一条河打通了它与外界的联系,人们去附近的城镇赶集,庆祝节日,村民们同样按照古老的遗风生活,可这里不只有美好,仍然有苦难,这里的湘西世界似乎更加有魅力,因为这个地方是存在的,并不是桃花源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论影响沈从文创作的六个因素》篇一一、引言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其独特的文风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
沈从文的创作离不开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地域文化、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社会变迁和文学潮流等。
本文将从这六个方面来分析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影响。
二、地域文化因素沈从文生于湘西,长于湘西,湘西的地域文化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湘西的民俗风情、山水风光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沈从文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湘西的元素,如《边城》中的湘西山水、《长河》中的湘西人民等,都体现了湘西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时代背景因素沈从文生活在动荡的时代,他的作品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抗战时期,沈从文的创作主题多以反映人民疾苦、呼唤民族觉醒为主,如《边城》中的乡土情结和《长河》中的民族精神等。
因此,时代背景对沈从文的创作主题和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个人经历因素沈从文的生活经历也是其创作的重要源泉。
他曾有过边疆地区的游历,也有过乡村生活的体验,这些经历为他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此外,沈从文的个人情感经历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如他的爱情故事、家庭变迁等都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
五、家庭背景因素沈从文的家庭背景也是其创作的重要因素。
他的家庭环境及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父亲是当地的读书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理念和文风。
六、社会变迁与文学潮流因素沈从文生活在的社会大背景下,也见证了社会的巨大变迁。
社会变革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关注社会问题、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更是体现了这一点。
同时,文学潮流也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他吸收了现代文学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
七、结语综上所述,地域文化、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社会变迁以及文学潮流这六个因素都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00论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00——以《边城》为例00摘要00《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本文将试从《边城》看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人间社会和在其内心构建的精神世界。
00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湘西世界00目录00一、引言 (100)二、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 (100)三、沈从文的湘西民间社会 (300)四、沈从文的湘西精神世界 (500)五、结论 (700)参考文献 (800)一、引言00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
沈从文作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其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
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00小说《边城》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品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本文将试从小说《边城》分析沈从文的湘西自然世界,人间社会和在其内心构建的精神世界。
00沈从文研究从其创作伊始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可谓几经曲折变化。
从徐志摩、苏雪林、刘西渭的赞叹激赏到郭沫若、巴人、冯乃超等人的批判;从京派重镇、文学天才的肯定与褒扬,到建国后文学史上一个有代表性的反动文艺思想家的否定与批判;从海外研究的悄然兴起,到新时期以来国内研究的蓬勃发展。
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间性的成因内容摘要: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所描写的湘西山民,有着优秀的品质,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时不时“感动”和“教育”作品的叙述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民间立场的引进”。
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间性创作的客观事实,已毋庸置疑。
而这个客观事实,它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尚待研究。
对此,我们可以从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审美理想和民间审美立场三方面进行探索。
关键词:沈从文小说民间成因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当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者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被启蒙者进行思想启蒙的时候,沈从文在他的湘西题材小说中,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无论是他这些作品的叙述者还是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如启蒙者那样存在批判与被批判、启蒙与被启蒙的现象,实质上却相反,那些对其他新文学者看来应该是被救治对象的湘西山民却有着优秀的品质,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时不时“感动”和“教育”作品的叙述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民间立场的引进”。
对于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间性,本文试图尝试选择一个角度,从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审美理想和民间审美立场三个方面探索其形成原因。
一、“湘西世界”的民间文化形态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中,为“民间文化形态”下的定义是:一、他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
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
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三、……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地处湘、鄂、黔边区,为云贵高原的余脉区域,山脉纵横,河流众多,地势险恶,古代称“五溪蛮”。
对这个区域,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羁縻政策(截止清改土归流止),这促成了湘西社会政治结构总体上比较松散的局面,即使在大一统专制政治下,湘西社会内部也有比较大的相对自由独立空间。
总体而言,湘西自古以来处于一种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恶劣的自然环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这里的人们在民间政治、民间宗教、民间艺术文学等方面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从而出现了专制统治与族长管理制度相互依存的态势,汉文化与巫楚文化相互渗透的格局,苗族土家族等多民族风俗长期共存的现象。
在这种常态下,这个区域的人们形成了自己的生存发展观,如湘西人视生存为第一要务,相对而言,其它的道德观念就比较淡漠。
这种民间文化风貌逐渐形成了它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最终,凝固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形态。
沈从文选择湘西作为他小说创作的题材,势必受到这种湘西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
整个小说故事只有在这种文化形态下,才有某种“真实性”存在,否则,小说的情节就无法推进、展开,小说故事更无法承担起某种审美价值和作家的深远理想。
在小说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展开小说主人公故事前,用大量的文字描写故事的背景和环境,介绍“当地”的民间文化,如《丈夫》,开头述说农村妇女为了生存在河街码头做“生意”的常态,这使得丈夫和老七的故事具有了浓厚的民间性;《柏子》,全文不到4千字,开头却用了将近1100个字写河上水手们的雄强、自由自在、无拘无促的民间生活状态,也只有在这样的民间文化形态下,才能产生像柏子那样正直、大胆、朴素、善良等自然品性。
二、通过对民俗民谣写作,使整个小说形成一种无形的磁场,这个磁场制约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如《萧萧》,小说以“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开场,又以它为结束,用民俗喜庆反衬凸显悲痛,又以“随意唱着那自编的山歌”推进小说情节的开展;《月下小景》,小寨主傩佑与其钟情苗族女子的悲剧命运根源于民间文化的陋习恶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与第二个男子结婚。
”否则,“常常把女子用一扇小石磨捆在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到天坑里。
”三、通过对民间传说故事,或直接改写,或以此为依托,营造一种民间文化,展现边地山民的品性,如《媚金,豹子和那羊》,原先传说中不合理的部分使之合理化,豹子为何爽约,他不是因为贪睡,而是为了守约而爽约,这一情节的合理化,使得故事突出赞颂湘西边地山民守信的品格和真挚爱情的主题。
对民间文化,沈从文将它当作一种向民间文学接近、学习的过程,并且明确提出,对民间传说、故事要做到“人弃我取”。
可见,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民间性直接受其湘西民间文化形态制约。
除了上述三点外,沈从文小说中的风物、风俗描写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湖南湘西独特的地域性,使其有着独特的民间文化形态。
这种形态直接决定了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间性,而其民间的自由自在审美与原始愚昧并存,也在小说中有着具体的表现。
二、同哀同乐的民间审美理想“首先,民间的理想……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其次,还表现在历史整合过程中民间生活的自身逻辑性。
其三,……他们自觉把个人立场与民间立场很好地结合起来……”沈从文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说:“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了,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在离开湘西之前的20来年时间里,沈从文流窜于湘西特别是沅水流域的大街码头,对那里山民的喜怒哀乐十分熟悉,十分理解。
后来几次返回湘西,对湘西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他也非常清楚。
所以,他一直强调,我的作品旨在“替他所见的这个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社会组织,试作一种善意的记录”,来表现“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在小说里,沈从文甘愿把自己看作是他所努力描写的“湘西世界”民间中的一份子,感受着湘西山民“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并与他们同哀同乐。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叙写,正是建立在这种独特感受基础之上的。
因而,他的湘西题材小说所寄寓的理想,必定是有着丰富乡土情愫的民间审美理想。
在小说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作家深深理解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如柏子,注定一生在水上漂,收入微薄,随时有生命危险,“若说这生活还有使他们在另一时回味反省的机会,仍然是快乐的”,这快乐,来自于河街岸边那短暂的相会。
作家理解这些水手的快乐,就如理解他们的苦难一样,对此,就如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写道的那样,“我因为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汗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隐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二、在遵照民间生活自身逻辑的基础之上,作家流露出了与小说人物一样地担心、恐惧、焦虑和躁动,如《〈长河〉题记》,写道:“‘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长河》中,乡间人一面说“买橘子”不要钱,另一面又担心着要来的“新生活”,这时候,人们生活开始躁动不安起来,这躁动不安的心理正式对当权者的一种社会批判。
以三十年代中期沅水流域的农村生活为题材,一如既往地叹息农村社会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在都市文明冲击下无可奈何地瓦解和丧失。
三、自觉将个人立场与民间立场相结合,如《夫妇》,通过“捉奸”这个故事,将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展示了出来,在对如何处置这对新婚夫妇中,写出了乡民们自身的暴虐心理,展示了乡民们那种对城里人的崇敬、对村中“特权者”的敬畏,以及维护道德风尚的怪异方式,这才是民间的真实生活;又如《龙珠》,龙珠被赋予了人类一切美好的德行,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民族崇拜的偶像,由此也给他的爱情带来了苦恼,本族少女从不敢有非分之想,“做那荒唐艳丽的梦”。
除了上述之外,还表现在语言和文体上。
沈从文的语言“充满泥土气息”,他曾说“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
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文体上,作家文体的形成是“他对自己的情感记忆有了一种特别的把握”,“对对象的把握是和这对象本身一同产生的,你甚至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沈从文永远将自己视为“湘西世界”中的一份子。
这内在决定了他湘西题材小说审美理想的民间性,而他这种同哀同乐的民间审美理想,必将是他湘西题材小说具有民间性的重要原因。
三、自主选择的民间审美立场湘西世界渗入到了沈从文的灵魂深处,就如他常好以“乡下人”自居一样。
1923年,受“五四”余波影响,独自来到北京。
这时,沈从文已经过了20岁。
从一个人心理机制的形成发展来看,这时候,已基本发展完成,再说,沈从文这20年,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岁月。
出生在湘西一个显赫的军旅家庭;读书的时候,“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
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
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逃学这一年,造就我一生的性格与感情”;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颠连流荡于湘、川、黔、鄂四省边境地区,留下了有关沅水和它的五个支流、十多个县分的城镇及几百个大小水码头的人事安乐和风俗景物的深刻印象,看过兵士们割韭菜一样地杀人。
湘西世界,给了他灵性,铸就了他心性,也给了他日后对世间万物进行取舍的智慧。
他一再地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1923年来到大都市北京,当他用从湘西土地和人情中得来的知识和教养,关照打量和处理经营人事的时候,却处处犯困。
刚到北京,处处受困,没有饭吃,没有住处,遭遇了升学失败,求职碰壁,投稿受挫,处在社会最底层,遭受着绅士淑女们的鄙夷、羞辱目光;在身处都市、主流社会中,他发现“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有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有着“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另一面表面上做出绅士、俊才风度,思想深处却似人生为游戏。
在“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对立与互参”下,作家失望于现代物质文明浸染下都市人的人性异化,而,湘西的人事、山水幻化成为温馨的记忆,充满了温情。
如此,作家对自己家乡越发的深爱,试图用“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
于是,人性探索成了沈从文坚持艺术道路的思想中轴。
他说:“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