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出版研究
- 格式:doc
- 大小:27.50 KB
- 文档页数: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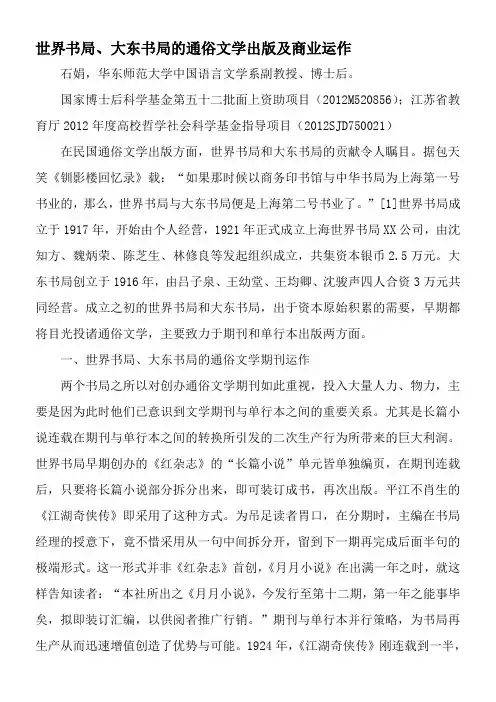
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及商业运作石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博士后。
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二批面上资助项目(2012M520856);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2012SJD750021)在民国通俗文学出版方面,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的贡献令人瞩目。
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载:“如果那时候以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为上海第一号书业的,那么,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便是上海第二号书业了。
”[1]世界书局成立于1917年,开始由个人经营,1921年正式成立上海世界书局XX公司,由沈知方、魏炳荣、陈芝生、林修良等发起组织成立,共集资本银币2.5万元。
大东书局创立于1916年,由吕子泉、王幼堂、王均卿、沈骏声四人合资3万元共同经营。
成立之初的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出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早期都将目光投诸通俗文学,主要致力于期刊和单行本出版两方面。
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期刊运作两个书局之所以对创办通俗文学期刊如此重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主要是因为此时他们已意识到文学期刊与单行本之间的重要关系。
尤其是长篇小说连载在期刊与单行本之间的转换所引发的二次生产行为所带来的巨大利润。
世界书局早期创办的《红杂志》的“长篇小说”单元皆单独编页,在期刊连载后,只要将长篇小说部分拆分出来,即可装订成书,再次出版。
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即采用了这种方式。
为吊足读者胃口,在分期时,主编在书局经理的授意下,竟不惜采用从一句中间拆分开,留到下一期再完成后面半句的极端形式。
这一形式并非《红杂志》首创,《月月小说》在出满一年之时,就这样告知读者:“本社所出之《月月小说》,今发行至第十二期,第一年之能事毕矣,拟即装订汇编,以供阅者推广行销。
”期刊与单行本并行策略,为书局再生产从而迅速增值创造了优势与可能。
1924年,《江湖奇侠传》刚连载到一半,世界书局就出版了《江湖奇侠传》1至4集单行本,未完成时即已大赚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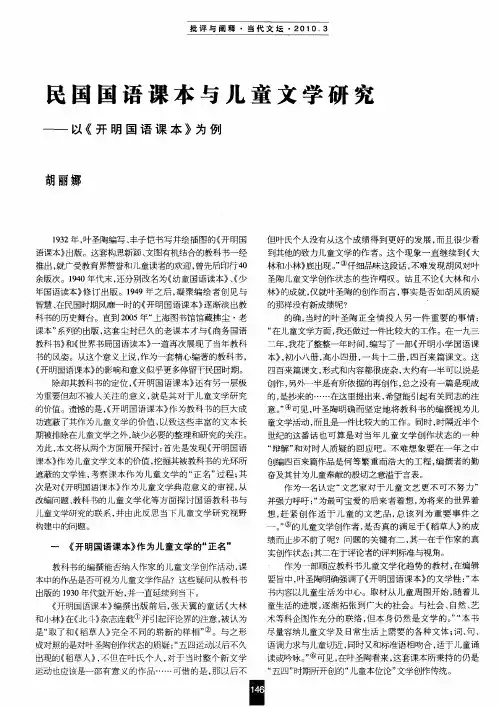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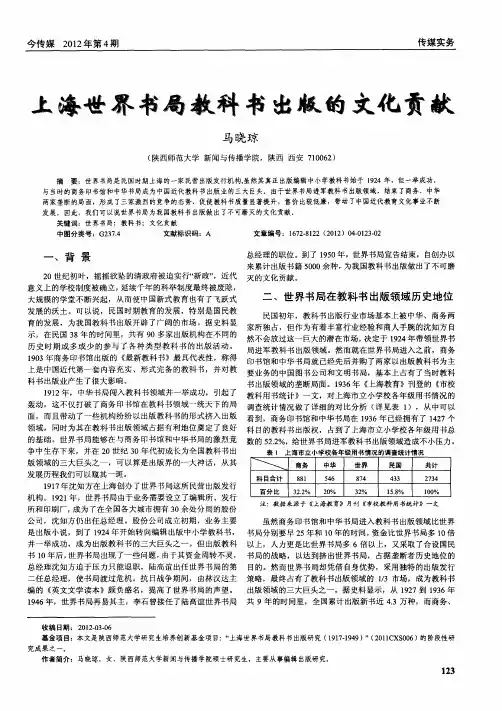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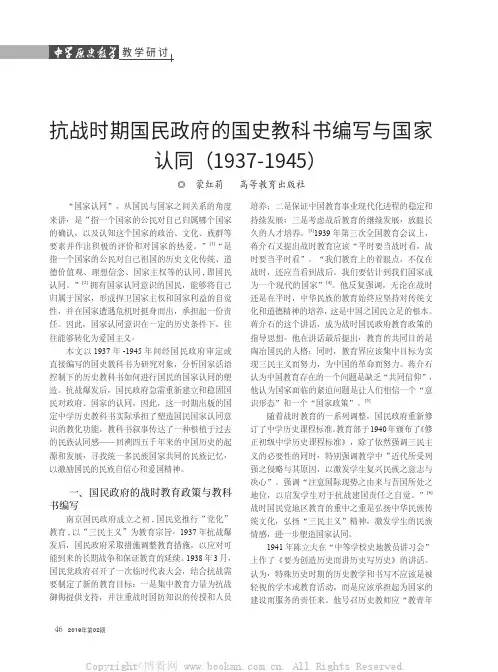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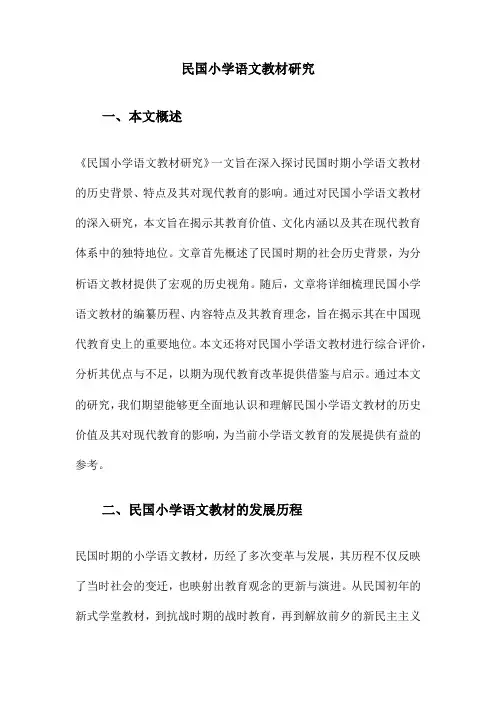
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一、本文概述《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研究》一文旨在深入探讨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材的历史背景、特点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通过对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其教育价值、文化内涵以及其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文章首先概述了民国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分析语文教材提供了宏观的历史视角。
随后,文章将详细梳理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编纂历程、内容特点及其教育理念,旨在揭示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文还将对民国小学语文教材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其优点与不足,以期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历史价值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为当前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历经了多次变革与发展,其历程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也映射出教育观念的更新与演进。
从民国初年的新式学堂教材,到抗战时期的战时教育,再到解放前夕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经历了从初创、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初创阶段,民国政府在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始着手编订新式学堂的教材。
这一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以传统经典为主要内容,同时融入了一些新式的知识元素,如自然科学、社会常识等。
这些教材在形式上也开始尝试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抗战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呈现出鲜明的战时特色。
教材内容强调民族精神、国家意识,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为主要目标。
同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教材也增加了一些与战争相关的知识,如防空、救护等。
解放前夕,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民国小学语文教材也迎来了其成熟阶段。
这一时期的教材,更加注重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学习规律,强调教材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教材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包括文学、历史、地理等多个领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知识素养。
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变革、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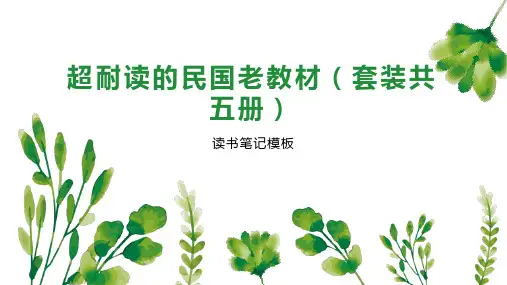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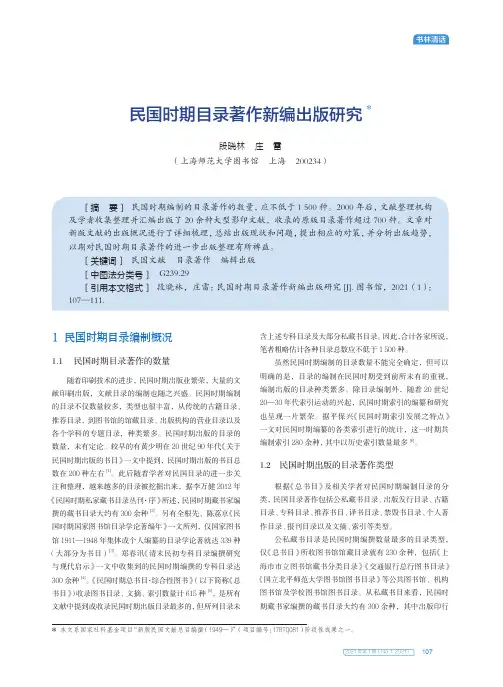
2021年第11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版民国文献总目编撰(1949—)”(项目编号:17BTQ081)阶段性成果之一。
民国时期目录著作新编出版研究*段晓林 庄 雷(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234)〔摘 要〕 民国时期编制的目录著作的数量,应不低于1 500种。
2000年后,文献整理机构及学者收集整理并汇编出版了20余种大型影印文献,收录的原版目录著作超过700种。
文章对新版文献的出版概况进行了详细梳理,总结出版现状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并分析出版趋势,以期对民国时期目录著作的进一步出版整理有所裨益。
〔关键词〕 民国文献 目录著作 编辑出版〔中图法分类号〕 G239.29〔引用本文格式〕 段晓林,庄雷:民国时期目录著作新编出版研究[J].图书馆,2021(1):107—111.1 民国时期目录编制概况1.1 民国时期目录著作的数量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民国时期出版业繁荣,大量的文献印刷出版,文献目录的编制也随之兴盛。
民国时期编制的目录不仅数量较多,类型也很丰富,从传统的古籍目录、推荐目录,到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出版机构的营业目录以及各个学科的专题目录,种类繁多。
民国时期出版的目录的数量,未有定论。
较早的有黄少明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民国时期出版的书目》一文中提到,民国时期出版的书目总数在200种左右[1]。
此后随着学者对民国目录的进一步关注和整理,越来越多的目录被挖掘出来,据李万健2012年《民国时期私家藏书目录丛刊·序》所述,民国时期藏书家编撰的藏书目录大约有300余种[2]。
另有全根先、陈荔京《民国时期国家图书馆目录学论著编年》一文所列,仅国家图书馆1911—1948年集体或个人编纂的目录学论著就达339种(大部分为书目)[3]。
郑春汛《清末民初专科目录编撰研究与现代启示》一文中收集到的民国时期编撰的专科目录达300余种[4]。
《民国时期总书目·综合性图书》(以下简称《总书目》)收录图书目录、文摘、索引数量计615种[5],是所有文献中提到或收录民国时期出版目录最多的,但所列目录未含上述专科目录及大部分私藏书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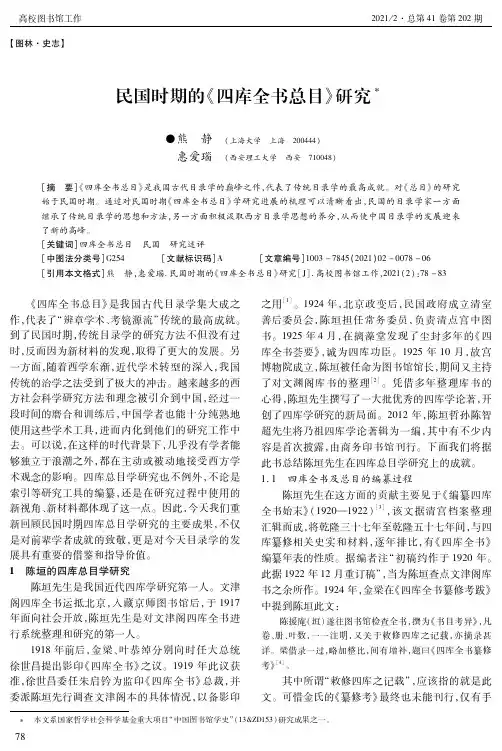
【图林·史志】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熊 静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惠爱瑙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 710048)[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巅峰之作,代表了传统目录学的最高成就。
对《总目》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
通过对民国时期《四库全书总目》学研究进展的梳理可以清晰看出,民国的目录学家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目录学的思想和方法,另一方面积极汲取西方目录学思想的养分,从而使中国目录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高峰。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民国 研究述评[中图法分类号]G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21)02-0078-06[引用本文格式]熊 静,惠爱瑙.民国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2):78-83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目录学集大成之作,代表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的最高成就。
到了民国时期,传统目录学的研究方法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因为新材料的发现,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西学东渐,近代学术转型的深入,我国传统的治学之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念被引介到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训练后,中国学者也能十分纯熟地使用这些学术工具,进而内化到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去。
可以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几乎没有学者能够独立于浪潮之外,都在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
四库总目学研究也不例外,不论是索引等研究工具的编纂,还是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新视角、新材料都体现了这一点。
因此,今天我们重新回顾民国时期四库总目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不仅是对前辈学者成就的致敬,更是对今天目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价值。
1 陈垣的四库总目学研究陈垣先生是我国近代四库学研究第一人。
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后,于1917年面向社会开放,陈垣先生是对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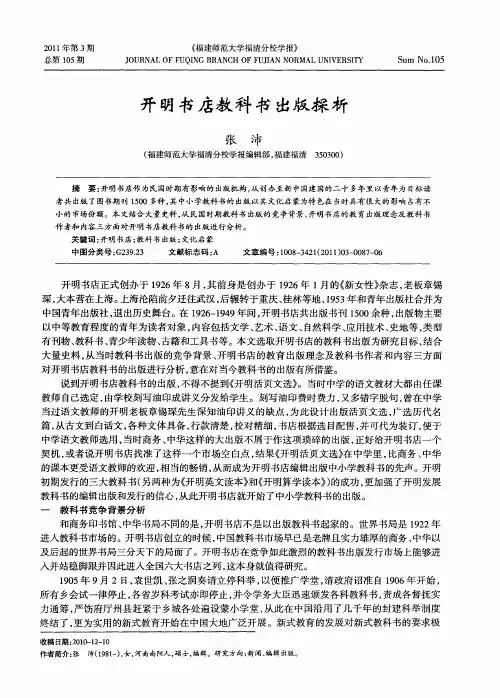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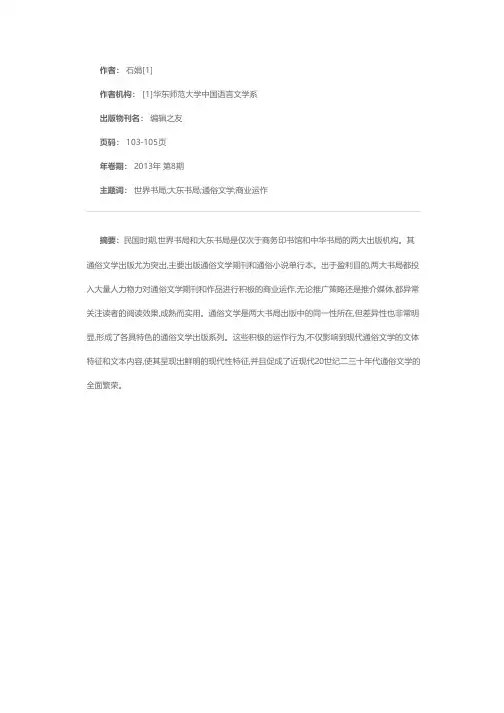
作者: 石娟[1]
作者机构: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出版物刊名: 编辑之友
页码: 103-105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8期
主题词: 世界书局;大东书局;通俗文学;商业运作
摘要:民国时期,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两大出版机构。
其通俗文学出版尤为突出,主要出版通俗文学期刊和通俗小说单行本。
出于盈利目的,两大书局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通俗文学期刊和作品进行积极的商业运作,无论推广策略还是推介媒体,都异常关注读者的阅读效果,成熟而实用。
通俗文学是两大书局出版中的同一性所在,但差异性也非常明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通俗文学出版系列。
这些积极的运作行为,不仅影响到现代通俗文学的文体特征和文本内容,使其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并且促成了近现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俗文学的全面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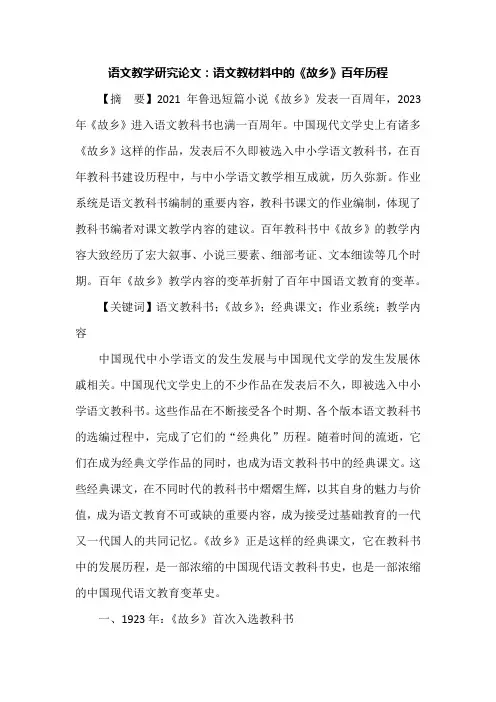
语文教学研究论文:语文教材料中的《故乡》百年历程【摘要】2021年鲁迅短篇小说《故乡》发表一百周年,2023年《故乡》进入语文教科书也满一百周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诸多《故乡》这样的作品,发表后不久即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在百年教科书建设历程中,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相互成就,历久弥新。
作业系统是语文教科书编制的重要内容,教科书课文的作业编制,体现了教科书编者对课文教学内容的建议。
百年教科书中《故乡》的教学内容大致经历了宏大叙事、小说三要素、细部考证、文本细读等几个时期。
百年《故乡》教学内容的变革折射了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变革。
【关键词】语文教科书;《故乡》;经典课文;作业系统;教学内容中国现代中小学语文的发生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休戚相关。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少作品在发表后不久,即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这些作品在不断接受各个时期、各个版本语文教科书的选编过程中,完成了它们的“经典化”历程。
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在成为经典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成为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课文。
这些经典课文,在不同时代的教科书中熠熠生辉,以其自身的魅力与价值,成为语文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成为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共同记忆。
《故乡》正是这样的经典课文,它在教科书中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语文教科书史,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变革史。
一、1923年:《故乡》首次入选教科书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为语文学科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语文教育内容的更新、教科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自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至国语统一运动,特别是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进入教科书从理念到选文作好了充分准备。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新文化运动的发难之作《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1]。
自此,《新青年》杂志就如何促进白话文学的发展,推进“文学革命”,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清末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特点探究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语文学科的独立。
从1904年到1949年,其间曾出版100多套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有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国文国语教科书,还有针对不同地区的《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中部国语》《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南部国语》《分部互用儿童教科书儿童北部国语》;有分内容编排的识字方面的《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说话方面的《复兴说话教科书》、作文方面的《作文教科书》;有根据性别编排的《女子国文教科书》。
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完成了从模仿西洋到自编独创,更是完成了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
教科书质量方面,单以1913年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而言,一经出版就大受欢迎,后来到1927年1月第一、三册分别是2686版和2306版,第六册在1912年3月就达61版。
时隔100多年,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印商务印书馆的《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的《国语读本》、开明书店的《开明国语课本》三本民国教科书,卖到告罄,受到时人追捧。
教科书的成功离不开背后的编辑,那么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团队到底有哪些特点?本文的探究不仅揭示民国教科书编者的特点,更对当今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队伍建设有一定启示作用。
一、编者人员:数量众多,精英辈出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者队伍庞大。
各大出版社集合了许多当时富有成就的大家进行教科书的编撰工作。
据统计,民国时期有许多中西贯通的学者加入了出版社编辑教科书,据对闫苹等编著的北师大图书馆馆藏78套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统计有:吴研因、胡贞惠、魏冰心、吕伯攸、薛天汉、戴洪恒、沈百英、朱文叔、叶绍钧、丰子恺、齐铁恨、丁觳音、赵欲仁、蒋息岑、施颂椒、林兰、陈伯吹、沈秉廉、赵景深、李小峰、陈鹤琴、梁士杰、陈剑恒、苏兆骧、王云五、于卫廉、刘瑞斌、赵玉笙、朱翊新、徐亚倩、王耀真、吴鼎、庄适、刘大绅、戴杰、许国英、范祥善、朱麟、任镕、武进、吕思勉、沈圻、顾颉刚、黎锦熙、陆费逵、易作霖、缪天绶、陈和祥、胡怀琛、王祖廉、黎锦晖、黎明、汪渤、何振武、戴克敦、庄俞、沈颐、郑朝汐、郭成爽、汪涛、樊炳清、范源廉、杨拮、刘传厚、金匮、顾倬。
作者: 张林[1]
作者机构: [1]信阳师范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出版物刊名: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48-52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8期
主题词: 民国时期;世界书局;“大学用书”
摘要:世界书局是民国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出版机构。
1932年,在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竞争日益激化和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逐渐兴起的背景下,世界书局开始进行大学教科书的编译,并出版一套"大学用书"。
该丛书以采选成书、公开征集和约定编著三种方式编辑,其主要来源包括书局之前出版的学术丛书、高校教师的课堂讲义、翻译的外国学术专著以及学者的编著等。
"大学用书"虽然是广义上的大学教材,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对近代高校学术研究和大学教科书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务国语教科书》之评析摘要: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在2005年初,出版发行了三套被历史掩埋近一个世纪的,适合于低年级的语文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开明国语课本》。
这三套民国老教材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算得上是最耀眼的三颗明珠。
1917年发行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十年间,发行量居然高达七八千万册,成为民国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初小语文教科书。
初版于1932年《开明国语课本》,发行期间,创下了印行40多个版次的记录。
《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也出版于上世纪的30年代,更被誉为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最早的白话教材之一。
本文聚焦于1917年初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聊聊笔者的所感所想。
《商务国语教科书》全套8册,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由当时教育部审定,供初等小学使用。
教科书设定依据的是1912年公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为日本学制,小学七年,前四年为国民学校,后三年为高等小学校。
编者庄俞认为:“只有我馆的《最新教科书》是依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各科俱有的,所以独步一时。
”商务教科书恰逢其时,严格按照学期制度来编著。
这种按学期制度编辑的方法,“实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纪录”。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05年重印时,在保留原书风貌的同时,依据今天人们的阅读习惯,删去部分不合时宜的内容。
重印后的《商务国语教科书》总共284篇。
第一册的前33课只有图片没有文字。
从34课开始,出现文字,通篇仅8字:“夜间早眠,日间早起。
”“教科书的取材内容源自儿童生活,并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
”第一册主要教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第二册主要教儿童识字及教授简短的句子,“从第三册开始出现简短的短文,前三册内容都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易于被儿童接受。
从第四册开始,文章渐长,渐渐引导儿童去了解我国的政治、历史、地理等知识,同时也编排了与儿童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本套教材的选文多故事性文章。
语言多用记叙和说明,兼有议论,也有犀利的议论文。
民国时期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出版研究
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不仅种类齐全,有一些教科书则成为经典之作,其《世界书局国语课本》更是至今还作为中小学教材重印发行。
则从传播学和编辑出版学的角度,采用一手文献资料,描述了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的发展面貌,对其出版物的内容进行归纳和分析,并解读其经典的教科书出版物,从而客观再现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的面貌,揭示了其教科书出版的现实意义。
标签:世界书局;教科书;编辑出版
民国时期,经济水平低未的社会民众一般知识水平也较低,封建思想的残留使得通俗文学作品仍是这些大众用于阅读消遣的书籍,进步文化还未能深入人心,一些除了通俗文学的其他出版物,未能在民众间广泛传播,而大多局限于精英层。
所以,一般出版物的量实则较少,而出版社赖以发展的则是教科书出版,尤其当商务印刷馆于1904年凭借一套《最新教科书》,奠定了在其出版业的元老地位之后。
教科书市场成为众多民营出版企业竞相争睹的一块田地。
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陆费违曾这么评价教科书在一家出版社中的地位,“教科书是书业中最大的业务,不出教科书,就算不得是大书局。
教科书印行数量的高低,往往影响到本公司股票市价的涨跌”[1]。
而世界书局较之中华书局和商务印刷馆是一家商业化的书局,依靠融资发展,其凭借商业化的敏锐嗅觉,一举攻下教科书市场,依靠教科书的出版崛起,从一家出版通俗文学作品的小书局一跃成为以大量出版中小学教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出版企业,成为民国时期的紧随中华和商务书馆后的第三大书局。
一、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的演变
近代教科书市场不同于其他出版物,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变换和政策的引导,由于当时政治形式波澜不定,而政府又迫切需要依靠教育来巩固其政权,所以教科书市场可谓“日新月异”。
而世界书局是一家商业化的出版企业,不仅在政府政策上聘请北大校长胡仁源作为教科书审定人,还高薪从中华和商务两大书局挖掘了包括范云六、沈思期、姜子贤在内的一些在教科书科目上专业且资深的编辑精英,直接组成世界书局的编辑发行团队,从而在政策上和内容上一步一步地打进教科书市场。
我们从世界书局这二十年左右的教科书出版的面貌就能够直观地看到其出版地位的演变。
首先,其出版的教材的范围和总类随着时代政策的发展而变化。
1924年,世界书局在摸索中探入教科书市场,在被商务和中华两大书局划分的教科书市场上,不仅在教科书的内容上精益求精,而且针对政府的审核制度想方设法打破了这一障碍,并使其成为了其出版教科书的机遇,随后多年在教科书市场上的大量投入,使得其在教科书市场慢慢有了一片天地。
至1930年,世界书局打破了教科书市场的多年两分的格局,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对教科书市场垄断,加剧了教科书市场的竞争,也使得近代中国的教科书从编辑、出版到发行有了一次演变,内容不断推陈出新,但价格日益低廉,从而使教师和学生有了更多样的教材选择,阅读到更精致的内容。
据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编的《上海教育》6月刊第十二期施种鹏所撰《市校教科用书统计》一文,对上海市立小学各年级用书的调查统计显示,当时,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在上海的市立小学中已经达到三分之一的占有率[2]。
从范围和总类来看,包括初高小学的教科书,其范围从新主义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国语科补充读物、史地科补充读物,到美术、
音乐、体育、缝纫用书。
其中新主义的教科书主要是由魏冰心编著国语政治类的课本,如小学前期三民主义课本、三民主义教学法、国语读本和社会读本等,江效唐编辑的卫生课本类,董文编著的地理課本类,戴消清编辑的习字课本类,杨逸业编辑的算术类等诸如此类。
中等学校用书的教科书包含初中、高中教科书,图书馆学、国技。
此外世界书局还大胆拓展教科书受众,针对当时对文化至少具有迫切需求的,但知识文化欠缺的民众出版了民众学校的用书,如“通俗的”[3]、“简化的”[3]民众课本,在广告中特别提及“教材渐进”[3]和“教法简捷”[3]的特点。
同时还出版了艺术类教科书,包含论述、图画、音乐、戏剧方面的教材等等。
由此可见,世界书局为出版新颖专业的教科书内容,聘请专家来进行编著,保证内容可行,为奠定教科书出版的三大书局之一的地位奠定基础。
世界书局在之后的六年内,依旧保持着这一传统,使得教科书内容有说服力。
到1936年,随着学制的改革和增加,教科书种类的增多,世界书局在此细分了教科书的种类,包括幼稚园用书,范围从教学、读本、故事,科目有国语、算术等。
小学校用书,包含科目有公民训练科、卫生科、体育科、国语科、常识科、社会科、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英语、职业等科类。
短期小学用书,其中包含课本、教学等在内。
民众学校用书,也包括课本、教学、尺牍在内,科目从常识、历史、地理、算术、珠算在内的学科。
初级中学用书、分为新课程标准世界初中教本,内含公民科、卫生科、国文科、英语、算学、历史、地理、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物理学在内的科目,当中每科的课本由不同的编者编著,于是以姓氏分别课本,如公民科中的徐氏初中公民、王氏初中公民等。
此外还包含高级中学用书、师范学校用书、商科职业学校用书、工科职业学校用书和大学用书在内的教科书。
这些各科目各种类的教科书都出自世界书局的各位编者手中,而世界书局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创新的传统也为其在教科书市场带来了长期的发展。
二、世界书局的典型教科书
教科书因为内容的时代性和研究的限制,现在翻看内容很多已经过了时,但还是有许多精心制作编辑的教科书,为后者不断改编提升,仍流传至今的或是具有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特质的,都属于世界书局出版的典型教科书。
这些典型教科书的存在,要归功于世界书局对出版教科书编者的重视。
其中有之后出版广为流传的《上下五千年的》林汉达,有传播三民主义到学校的魏冰心,还有在自己科目专注教科书编写的编者们。
1930年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的一次关于《标准英语读本》和《开明英文读本》的版权纠纷,让世界书局的英文编辑林达汉一度带上抄袭者的帽子。
林汉达受到刺激,立志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不久他远涉重洋去了美国,半工半读专注研究,不仅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还写成历史通俗读本《上下五千年》,畅销全国,启发教育了无数的中国读者。
所以客观地从林达汉的编辑生涯和为世界书局作出的贡献来说,这只能看作是一个污点。
林达汉为世界书局编著的许多英文读本,给世界书局添上了重要的一笔。
包括当时很有影响的英文读本,于1932年,编著了《活用英文法》,分上下两册,“原名为英文文法ABC,为学生自修用书……本书有头有绪、简而不漏、详而不杂,即初读英文者亦能一目了然”[4]。
同年,林达汉还编著了《高中英语标准读本》,是一本依据教育部颁布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编著的读本,是国内第一部高中英语读本,同时他还在同年编注了英文小说《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
除此之外,林汉达还为世界书局编著了经典的英文丛书,即“英文文学名著丛刊”等。
而林汉达主编的英文文学读本也成为世界书局
中期出版最多,影响也最大的书籍。
如《华文详注英文文学读本》、《世界近代英文名著集》两套,其中有金仲华注释的《安徒生童话选》、《漫琅兰斯科》等。
另有林汉达等主编的《英汉汉英两用辞典》、《世界标准英汉辞典》等工具书较为畅销,这些都为西方文学的传入起了中介作用。
朱联保谈及林汉达时回忆到:“1924年林汉达大学毕业后,在宁波四明中学教书,1928年暑期到上海,与大夏大学教授萧炳实共同拟编辑英文文学丛书的计划,建议世界书局出版……”[5]可见林汉达的编辑生涯早期在世界书局渡过,为世界书局留下许多经典英文文学或教科书,等等。
另一位教科书编者魏冰心,与林达汉专注编著英文书籍不同,主要于1930年左右编著世界书局的三民主义课本,主要编著的新主义教科书有中小学各级的《三民主义课本》、《三民主义课本教学法》、《国语读本》等,同时还参加了许多校对工作,把三民主义传播到学生中。
这些读本虽然现在没有了现实意义,但是能够从中了解三民主义和当时的历史。
魏冰心和薛天汉等学人还选取了民国时期的优秀作品集合而成为《世界书局国语课本》,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开创者的翘楚之作,亦是20世纪最富生命力的语文经典读本。
如今这套课本又被重印,仍然能够为今天的中学语文教育提供启发,极富现实意义。
“这套读本的字体选用颜体楷书,结体方正,笔力雄健,富于阳刚之美,即所谓颜筋。
读本一页一课,每课均有插图,采用中国传统写意技法,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一草一木,均寥寥几笔勾出,活泼灵动,意趣盎然,与课文的颜体楷书相互映衬,教人一翻开课本,便觉一股扑面而来的中国气韵”[6]。
此外,世界书局在这二十多年编写的教科书数不胜数,参与的编著者都如林达汉和魏冰心一样,在各自专业的科目领域贡献知识才能,为当时的中小学生提供教育资源。
参考文献:
[1]庞学栋.解放前教科书出版的竞争极其影响[J].出版发行研究,2003(1):89.
[2]王愁.近代商人出版家的成败:以沈知方和世界书局为中心的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23.
[3]刘洪权.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第五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2010:665.
[4]刘洪权.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第六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5]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C]//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237.
[6]民国小学国语课本堪为作文模范[N].新闻晚报,2011-12-28.。